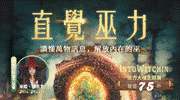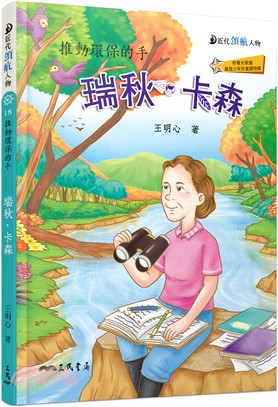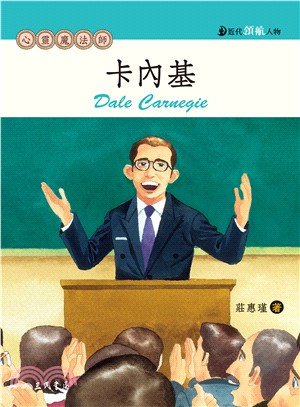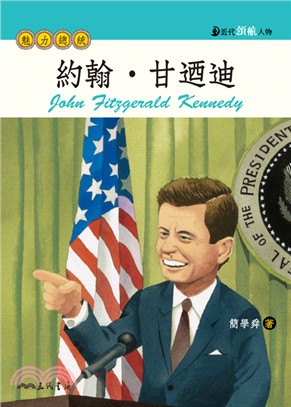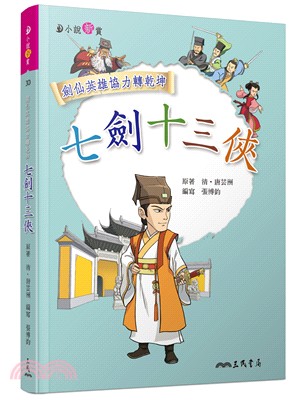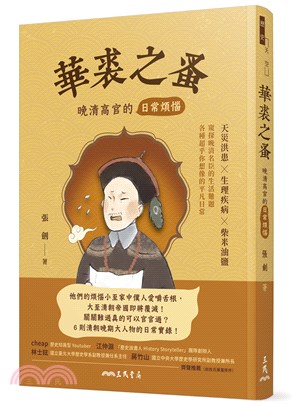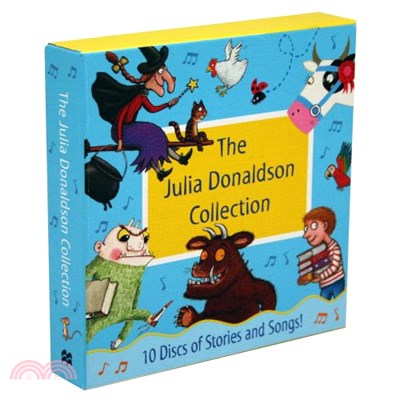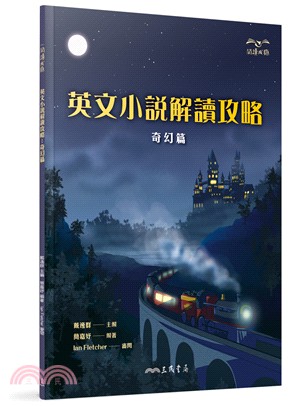浙東學術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ISBN13:9789863502357
替代書名:A Study on the Eastern Zhejiang Learnings: Knowledge, Morals and Social Dedication of Chinese Thoughts in 17th-18th Century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鄭吉雄
出版日:2017/06/03
裝訂/頁數:平裝/448頁
規格:21cm*14.8cm*2.5cm (高/寬/厚)
版次:初
適性閱讀分級:711【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浙東學術」在中國思想史中,究竟占有何種位置?
本書收錄作者多年來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討論了陳亮、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的文史之學,將他們的政論、史論、文獻學和史志之學綰合一起,試圖為南宋以降至清代中葉浙東地區學者學術思想勾勒出一條有意義的線索。浙東學術精神在於「史」,作者運用史學史的方法,也著重學術人的生平、治史方法等前後相承的發展,以傳統文獻學為基礎,同時強調歷史與觀念的互相釋證。心性之學、事功之學、歷史之學都是浙東學術的核心內容。心、事、史三個觀念放置一起,提醒了我們認知活動的主體性以及歷史知識和道德自覺之間的微妙關係。
作者簡介
現任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史講座教授。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荷蘭萊頓大學歐洲漢學講座,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訪問研究學人。教育部「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第一期子計畫主持人,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創辦人之一。曾訪問亞洲及歐美多所著名大學。研究領域包括《周易》、中國思想史、經典詮釋學、清代學術思想史、東亞儒學及文獻學等,著有《易圖象與易詮釋》、《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周易玄義詮解》等六種專書,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近世儒學文獻與思想》等十五種論文集,發表學術期刊論文六十餘篇。
序
緒言(摘錄)
本書主要研究清初至清中葉中國思想史的一條主線――浙東學者的學術思想,並沿此主線上溯至南宋探其淵源。本書所收錄的,部分是十多二十年前的研究成果,部分則是近幾年的新著。主題是浙東學術,以南宋為背景,側重清初至清中葉一段,從萬斯同受黃宗羲之教「獨尊史法」,講到章學誠兼文、史而通之以「義」的進路。由於浙東的精神在於「史」,我運用相應的近於「史學史」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著重學術人的生平、治史方法、歷史觀念等前後相承的發展研究,並且依循我在傳統漢學的訓練,以文獻學為基礎,同時強調思想史所著重的歷史與觀念互證的分析。我雜用上述的幾種方法,其實有方法論上的不得已,因為心性之學、事功之學、歷史之學都是浙東學術的核心內容。「心」、「事」、「史」三個觀念放置一起,提醒了我們認知活動的主觀性以及歷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之間的微妙關係。尤其歷史知識與道德自覺二者,是史家執筆寫史時,所無法迴避的重大課題。因為歷史考察的是人類的集體活動,作為人類的歷史家必將難以避免地將訓誨――不論訓誨的標準和內容是什麼――介入到史考、史纂等一連串的活動之中。史家對於史料,從解讀、比較、分析、重組,到下筆撰寫,內心的一把尺必然自覺或不自覺地不斷在作用著。如果像章學誠所說,「史」的精神是「切人事」,而不限於執筆寫史的話,那麼人類的德性根源以及自明此一根源(自明誠)的踐履之義是否獲得發揚,人文學知識能否契合於時代的脈動,可能也決定了人類集體命運是福是禍。上述所論,德性根源的問題可能不是專業史學家主要關懷,而史學方法也非哲學家所關心。有些問題到了專業學者的手上,專以某種方法切入,不免會得一而遺一。這就是我上文稱雜用幾種方法的原因。也許用廣義的「思想史」一詞來形容本書的性質比較適切──雖然我也常常用到文獻校勘(textual criticism)的方法。這是我將這部書的副題訂為「近代中國思想史中的知識、道德與現世關懷」的緣故。
我不得不承認,這部書採文史哲兼融的進路,在方法學上的混雜性(hybridity)其實是受到我的研究對象──浙東學者──的影響。他們大多身兼哲學家、經學家、史學家、詩人等多重身分(這也是中國傳統人文學的特色),在他們身上,「知識」與「道德」呈現出多樣的形態。他們也常強調二者之間存在一種複雜的關係,不可分割──「道德」的完成是大我(包含宇宙、國家、社會、家庭)的確立而不是小我的孤立──如此,德性最高的體現有賴於知識的擴充,而知識的擴充又必須有德性的自覺為輔,經書和史籍的研究,更開拓了人文知識的縱深。學者追慕的境界中,知識、道德即成為一種立體、活動、自由而具有創造性的狀態。這真是人文學者的理想。
清初至清中葉浙東學者以史學或史學精神為核心的學術規模,並不限於狹隘的歷史纂輯之學,而是強調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複雜而動態的關係,舉其要者有四:
其一在於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的融和,也就是道德與知識的整合;
其二在於經世的精神,從文史之學的變動性和當代性,推衍至文化意識在歷史研究與實踐中的弘揚;
其三強調史料鑑別與史筆文辭的平衡和結合,從「事信、言文」至於「文、史」之兼通而突顯「義」;
其四從著重易代之際故國遺民史事的整理,發展至對中國文化史、制度史、文獻史、地方志的全面反思與融貫。
上述是我試圖總括浙東學術的四項特點。浙東學術這一段發展,也印證著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發展與變遷,包括從清初慢慢從宋明理學蛻變的痕跡,朝代遞嬗經緯世宙的呼籲,發展到清中葉的專門漢學之中埋伏了整合其他學術研究(如先秦諸子研究),透顯出歷史文化的關懷。所以這部書和我另一部著作《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有一種承續的關係。本書第七章〈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恰好是這兩部書相緊扣的一個關節。在研究方法上我看重文獻的分析與解讀。這可能和我屬傳統中文系出身,長期接受漢學的訓練的緣故。「閱讀」是一種看似單純、實則複雜的精神活動。它是一個「理解」的過程,是讀者透過文字與千百年前的作者之間與世隔離、默默無語的交流。經過數十年交流,再透過文字的分析,我重新詮解了中國近世一批籍貫浙江的知識分子的經史之學,也為中國近世經典詮釋傳統(hermeneutic tradition)提出一個視界。
浙東學者研究《周易》的成果也很豐碩。讀者如需要參考浙東學者關於《周易》圖象之學方面的成果,可參我另一部書《易圖象與易詮釋》,這部書就不再重複了。《易》圖涉及儒道思想互動的問題,像黃宗羲的弟子之一仇兆鰲除了完成著名的《杜詩詳注》外,亦集注《參同契》,從事道教文獻的研究。關涉的課題隱然與浙東學者從儒家思想判別出道教思想的關心,有密切關係。浙東學者師弟子對道教信仰的涉獵、吸收與排斥,為中國東南沿海各種宗教思想活躍傳播的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從明清之際儒道對話再深入探討,將有利於我們更真切認識十七世紀中國民間宗教的活動。
本書各章多為舊著重寫而成,加入了我最新的研究,部分題目或亦已重訂。因此原發表在學術期刊的原文只能作參考。我生於香港,祖籍廣東省中山縣,並非浙東人。研究浙東學術,主要還是對於「明末清初」以及「經世」這兩個課題的興趣,完全談不上任何鄉邦文獻情結,更沒有預設一種對於研究對象一味吹捧的「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心態(我向來反對這種研究態度)。先師何佑森教授早歲研究學風的地理分布,其理論預設,就是認為任何人的生活,都必然與當地風土習尚存在若干內在聯繫。這可以說是鄉邦文獻廣泛的精神意義。任何一地域的文獻,都必然具有某些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但也必然同時具有某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universality)。這兩方面的精神意義,表面看是相反的,其實往往是並存的,都值得人文學者探索、了解和學習。我和浙東學者時空各異,「素昧平生」,但十九歲第一次讀到《文史通義‧書教》,深受感動,當時心神的激盪,至今記憶猶新。我一直很欣賞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切人事」三個字。「切人事」的觀念,和〈博約〉篇所講的「天性、至情」的「性情」之論,頗可互喻。「性情」植根於每個人最初源也是最深沉的內心世界,誰能真誠地抉發內心的這一點光輝,擴而充之,不論從事任何事業,不管其成就大小,都是一種「自我」的完成,都會蘊涵光采。這是人生最浪漫、最可貴之事。對於具有強烈的時代感的知識分子而言,「自我」之完成,又必然與時代息息相關。每個人的個性各不相同,時代環境又不斷變易,與日俱新,那麼知識分子也必然有不同的事功表現。學誠〈浙東學術〉所謂「面目迥殊,各有事事」即指此。我在〈浙東學術名義檢討〉一文中發揮了這個意思,作為浙東學術的概括描述。二○○六年湖北大學副校長周積明教授在《漢學研究通訊》發表了〈清代經世思潮研究述評〉一文,指出我的論斷「揭示了『經世』才是浙東學派的精神主脈,這一見解是關於浙東學派最新也最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積明教授的讚語我是當事人不能置一辭,只能說空谷足音,彌足珍貴,讀到一位老朋友的知音之言,心裡是很安慰的。不過一彈指頃,上距積明教授發言又已十年,韶光流逝之速,能不令人感嘆!
本書所收錄的十個篇章,既有有心栽花的成果,也有無心插柳的創獲,各篇章陸續寫成於二十年之中,雖非出於一時的嚴密構思,但因為個人精神的前後貫串,竟然也隱然形成一個整體關懷。
就像章學誠自稱自少至老某些觀點未嘗改變的經驗一樣,隨著歲月的飛逝,我對「浙東學術」的研究也有些從未更易過的觀點。當然,年齒漸長,人生體會愈多,對於讀書人如何在冷暖人間,踽踽找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領會也愈真切。懷抱這樣的心境閱讀學誠和其他明末清初的學者,我有了一種隔代知音之感。
從一九七九年我開始讀《文史通義》至今三十餘年,世界秩序急遽改換,知識體系也陷入了劇變。人文學的基礎研究中,靜態地去探討一個歷史的課題,往往已不再能喚起新一代年輕人的興趣。在「切人事」三字箴的警示下,作為學術界的資深耕耘者,我不能不重新反思這部書的意義。當然,從傳統史家看來,歷史的經驗有鑑戒的作用和價值,但治史而講鑑戒,好像在今天也已成為陳腔濫調。問題在於,人類集體行為是否不斷因循著某種模式,而使得過去衰敗的經驗能提供未來人類作為一種警示?而關鍵在於,人類社會尤其是最新二十年因為種種因素而有別於過往數千年。基因工程改變了生命的型態、資訊科技改變了社會的結構、航天技術縮短了世界的距離。歷史的陳跡,真的能供新一代文明人作為行為的鑑戒嗎?這恐怕有很大疑問。不過話說回來,「切人事」的精義在於,它預設了一個變動的、未知的世界。任何時代的學者,都應該要目光炯炯地觀察當代的特殊性,適切地調整學術的內容與方針,這才是「經世」的核心價值。
浙東學者治學的共同取向,從南宋開始,大多著意於文獻、經世、事功三者,金華文獻之傳,永嘉經制功利,永康事功之學,約可作為概括。他們既反對空談心性,亦不只求讀書明理,而是普遍重視歷史經驗,強調在文獻基礎上講求人文之學的實效,歸約為「經世事功」之旨,鮮少作虛浮的德性之談。這樣的取向,黃宗羲、萬氏兄弟、全祖望、章學誠在不同的向度發揚光大,朱舜水更將這種學風傳播到日本,對幕末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產生重大影響。而與宗羲、舜水年代相若的日本古學派學者,也有回歸經典、重視歷史、重視文獻的價值取向。出現在十七世紀東亞地域的這種學風,具有複雜的面向和意義,仍然值得二十一世紀初的我們探討。
〈浙東學術〉篇所述的浙東、浙西源流之說,上溯朱陸,區分博雅與專家,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余英時老師《論戴震與章學誠》、先師何佑森教授〈黃梨洲與浙東學術〉均有批評,後人接受此一譜系之說者並不多。但我試著從另一角度考察,發現章學誠與陸九淵的確存在著有趣的共同點,就是對於儒家尊經思想的抨擊。我們知道朱熹遍注群經,對儒家諸經都有精深的研究,而《象山年譜》淳熙二年條引朱亨道書記朱陸鵝湖之會: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九淵「堯舜之前何書可讀」的確是一個尖銳的質疑。儒家道統說所臚列的聖王,周武王以前尚未有經書,那麼儒家深心禮拜的「道」,雖說是經中之至理,經文之所載,但推溯其源,畢竟無法盡被經書所規範制約。我不知道陸九齡(「復齋」是九齡的別號)何以要止住這個有意思的問題。九淵之問,不啻從「道」這個具普世價值的觀念,去質疑「經」的權威性。而學誠〈浙東學術〉也說: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
據〈經解中〉,學誠觀念的「經」,實皆為「制度之經,時王之法」,故「六藝皆周公之政典」。然則推至周公以前,尚未有《六經》之時,當亦有「時王之法」可言,唯此「時王之法」見諸實踐而不見諸文字。正如〈經解上〉說: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為治為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
和九淵的理學觀點不同,學誠所持的是史學觀點。「經」既然取經綸、經紀、經世之義,那麼後儒尊經,而謂之「載道之書」,卻不知道「經」之所記本為聖王建立之制度,本於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需要而創造,都是切合人倫日用的實踐實跡。學誠特意從歷史的角度追溯「經」的歷史本質而批判後儒尊經的行為。陸九淵治理學,亦著重實踐,描述自身善於治心、治性情,而治史志之學、文獻之學的章學誠在〈博約〉篇中也自稱其治學源本「性情」,在〈浙東學術〉中又引陸九淵為浙東譜系之始,二人論學又都批判後儒尊經的思想,這都是異中之同。只不過,九淵歸宿於「心學」,學誠則提倡「經世之學」,則又有同中之異。這也是饒有趣味之處。
從我開始追隨先師何佑森教授研究浙東學術至今,倏忽三十載,佑森師已仙逝多年,我也從臺灣大學退休,轉返故鄉香港,轉服務於香港教育大學。邇來忙於校務,學殖荒落,深感愧恧,有負當年先師的期許。謹藉卷首,以誌涯略。佑森師病中為拙著題耑,是他畢生唯一一次為專書題字,倍邀光寵,謹此向遨遊於芴漠的先師,叩首深謝。
目次
緒言
第一章 浙東學術名義檢討
一、二十世紀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界定
二、關於「浙東學派」說的考慮與挑戰
三、章學誠觀念中「浙東學術」的主線
四、浙東學術與日本古學派──一個東亞儒學的視界
五、結語
第二章 陳亮的事功之學
一、陳亮事功之學的形成背景與學說重點
二、陳亮和朱熹關於事功之學的辯論
三、南宋浙東學者論陳亮的事功之學
四、清初浙東學者論陳亮的事功之學
五、結語
第三章 黃宗羲恢復證人講會與尊史思想
一、劉宗周「證人講會」的宗旨與創辦經過
二、黃宗羲「證人講會」的宗旨與恢復經過
三、黃宗羲晚年「尊史」的思想
四、結語
附錄:讀《留書》與《明夷待訪錄》隨劄
第四章 萬斯同的經世之學
一、制法
二、尊史
三、氣節
四、結語
第五章 論全祖望「去短集長之旨」
一、析「去短集長之旨」
二、去短集長與「成己成物」
三、去短集長與「多識亦聖人之教」
四、去短集長與「故國不可以遽剪」
五、結語
第六章 全祖望論毛奇齡
一、全祖望對毛奇齡的批評
二、毛奇齡操守上的三點問題
三、毛奇齡疏於「漢以後人」和「唐以後書」
四、毛奇齡的氣節問題
五、結語
第七章 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
一、撰寫動機與問題的提出
二、戴震「道」、「理」觀念的發展歷程
三、章學誠「道」觀念的發展歷程
四、結語
第八章 論章學誠的「道」──《文史通義‧原道》新釋
一、知音稀少的作品――〈原道〉
二、〈原道〉注釋
三、章學誠的「道」與經世思想
四、結語
第九章 章學誠「官師合一」說對清代科舉制度的批判
一、問題的提出
二、〈與史氏諸表侄論策對書〉所記章學誠的科舉經驗
三、學誠對科舉時文的評價
四、學誠「官師合一」的經世思想對科舉制度的批判
五、結語
第十章 釋「通」──論章學誠觀念中的「通儒」
一、釋「通」
二、章學誠觀念中的「通」
三、以方志學寄託史學及經世思想
四、史志、文獻學中的文化意識
五、經部與子、集關係的歷史源流
六、方志學的史學精神與近代詮釋
七、結語
第十一章 結論
引用書目
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七章 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因緣--「理」與「道」的新詮(摘錄)
二、 戴震「道」、「理」觀念的發展歷程
戴、章二人思想的進展與互動,余英時老師《論戴震與章學誠》言之最詳。戴震是如何在考據學家雲集的北京逐步追求他深心嚮往的義理?章學誠是如何在戴震經學考證言論的壓力下建構他的「六經皆史」觀念?能讀余老師大著者必不陌生。但學術界接受余老師觀點的,往往會著眼於「考據」與「義理」之間的一種緊張性;我則想借用余老師「內在理路」的提法,重新詮釋他的觀點。我認為戴震的「理」論和章學誠的「道」論之間,甚至可以說「考據」與「義理」之間,都存在一種潛藏於內部的密切關係。以下從戴震開始說明。
「道」和「理」是戴震所重視的兩大概念,大致而言,戴震早歲多提「道」,至晚年始轉而論「理」。其晚年定論,已以「理」取代「道」,而闡發於《孟子字義疏證》及〈與彭進士允初書〉。關於「理」的思想,拙著《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已有所申論,本章將避免重複,而集中討論戴震如何由「道」切入「理」。
戴震志於學甚早,但奠定學問基礎則始於見江永,事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時戴震二十歲,江永六十二歲。江永曾經集注朱熹與呂祖謙合著的《近思錄》,對宋明理學的概念與內涵相當熟悉。正如過去學者所注意到的,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戴震赴北京以前,顯然並沒有對程朱思想有任何不滿。這和他師承江永顯然有著絕對的關係。戴震雖然自稱「十七歲時,有志聞道」,但這顆求「道」的種子之所以在他的心中萌芽成長,興起了與宋明理學家相同的關懷,而有異於同時期的考據學者,也許與江永的教誨脫離不了關係。
早在戴震入京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時戴年方三十一,正在撰寫《毛詩補傳》,約於四年後復撰〈與是仲明論學書〉,已提出「經之至者道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
僕自少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睹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
〈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所提出的這些命題,雖然與他晚年寫定的作品,深淺不能相提並論;但從其中提問題的方式,已可窺見戴震學術觸角的敏銳,與心志的高遠。這明明表示他在而立之年,雖然雅奉經典字辭考訂之學(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但也注意到「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具有密切關係。戴震遲至一七六三年初才撰成《原善》,暢論「善」、「仁」、「道」、「常」等觀念,但從〈與是仲明論學書〉看來,早在一七五四年前後,他已注意到由「字詞」以通「道」,是一條不可迴避的路。也許有人認為戴震所謂「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乾嘉學者中也曾有類似的提法。但如果我們考慮戴震在一七五三年以後逐步撰著《原善》的過程與理論發展,我們就不能將戴震所講的「道」和其他考據學家所講的「六經載道」之「道」等量齊觀。「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兩句話出的一個重要意旨是:「語言訓詁」並不全然只是一種考據方法或技術,它同時也是一種通向真理的哲學方法。他接著又說明「語言」與各種專門知識,尤其是名物制度之間的關係,說: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行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
字詞的探討屬於語言學,恆星七政屬於天文學,誦《詩》須講求聲韻學,誦《禮》須知典章制度(宮室衣服)之學,誦《書》則須知地理學(地名沿革)。戴震強調上述的各種專門知識,彼此之間有不可分割的整體關係,是「未始相離」的。換言之,戴震很早就注意到經典的知識背後有一種一貫性和整體性,又共同貫串著一個最高的真理:「道」(經之至者道也)。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年初,戴震抵北京,見錢大昕、王昶、秦蕙田等學者,大昕亟稱其學精博,歎為「天下奇才」,戴氏始以名物訓詁之學為在京學者所推重。翌年,戴震完成《句股割圜記》,撰〈與方希原書〉: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
一七五七年東原游揚州,於都轉運使盧雅雨(字見曾)署中首晤惠棟,論學極相得。由於惠棟有著強烈尊漢反宋的立場,而戴震又在此數年之間逐步加重他的批判程朱的力度,學者咸認為惠棟實質上落實了戴震日後對宋儒的批判。余英時先生至謂:
惠、戴一七五七年揚州之會,彼此曾默默地訂下反宋盟約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自乾隆十八年癸酉至二十八年癸未(1753-1763)的十年之間,戴震先後撰寫〈尚書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諸篇論文,以及陸續完成之《經考》、《毛鄭詩考正》、《詩補傳》、《尚書義考》等著作。如果我們細讀這一批經學考據的著作,其實不難窺見戴震處處在發掘經典所載錄的典章制度背後的文化意識。在這十年之間,戴震並不是只做經典考據的工作,至遲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他又逐步撰寫《原善》,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時四十一歲)而完成《原善》初稿三章。換言之,戴震在一七五三至一七六三的十年之間,其實是同時執行「經學考證」以及「哲學思辯」兩項工作。難怪戴震在初成《原善》時極有自得之趣,自感「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甘味」了。一七六三年段玉裁始向戴震請業,即詳細讀了《原善》,後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說: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
從這段話看來,顯然段玉裁也注意到戴震同時進行的這兩項工作,彼此之間互相支持、互為表裡的關係。所謂「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指的正是利用經典考覈的理據,來疏通證明哲學的概念。自一七六三年以後,戴震仍然持續著這種一面繼續考證經典,一面疏通義理的工作。例如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戴震撰寫《杲溪詩經補注》時,就同時將《原善》三篇初稿發展為三卷本。其實在前一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戴震對於「理」概念的掌握已經成熟,對於「典章制度」實為「性命之理」的基礎的理念也大致釐清。他在該年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古今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這段話中值得我們注意的重點是:儒家學者必須運用「訓詁」的方法,研究經書中的「典章制度」,才能準確把握儒學中抽象的「理義」。這些話語,其實都明顯地向學術界公開宣示,他的經學考據以及《原善》一書,是息息相關、不可分割的—義理的梳解和訓詁的闡明,都無法脫離「典章制度」,因為這三者本來就是一整套學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戴震擴大《原善》初稿三章,為上中下三卷。《原善》卷首記此事說: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天人之道」屬於義理的穎悟,「經之大訓」則是考據的創獲。「治經之士,莫能綜貫」二語,關鍵就在「綜貫」這兩個字。戴震自忖他與其他「治經之士」不同之處,正在於「能綜貫」與「不能綜貫」。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戴震(時年四十七歲)在山西朱珪藩署中草創《緒言》一書,同年編成《汾州府志》,自認所持地理沿革的觀念為有獨得創獲。該年戴震曾作客於朱珪山西布政司使署,又撰寫〈古經解鉤沈序〉,再度申明他由語言訓詁,以闡明經典義理,通乎古聖賢之心志的理念: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戴震撰寫《杲溪詩經補注》,將他的《詩經》學從《詩補傳》再向前推進一步。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後十年(1767-1777)撰成了《中庸補注》,其中多次申明「道」不離乎「人倫日用」的觀點:
道不出人倫日用之常。
民非知之而能之也,由於先王之禮教而心志純一謹厚,無私慝佹肆之行,則亦能之。蓋生養教化盡於上,使民有恆心故也。
人倫日用之常,由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
人之為道若遠人,不可謂之道。
道之大目,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隨其身之為君、為臣、為父、為子,以及朋友。徵之踐行,身之修不修乃見。……人於人,情相同,恩相洽,故曰「仁者,人也」。事得其宜,則無失,故曰:「義者,宜也。」禮,則各止其分位是也。
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為昆弟、夫婦、朋友,概舉其事,皆行之不可廢者,故謂之達道。
在戴震自覺命途多舛的十餘年間,他仍然不斷地將他經學考證和義理疏通的工作,引申到「文化」的層面,擴大經典的意義,至於關懷人類大社群的生活與生命問題,並將這種關懷提升到哲學的層次。在這樣「精誠所致」的力量推動下,《緒言》終於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脫稿。至丙申年(1776)冬至翌年(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春,將《緒言》易名為《孟子字義疏證》。一七七七年,章學誠中舉人,同年戴震逝世。
從上文的論證,戴震畢生求「道」,無可置疑;而其晚年所定之《孟子字義疏證》竟將「理」字置於「道」字之前討論,內容則多至十五條,其中透露了何種不尋常訊息呢?「道」、「理」二概念,究竟哪一個才是戴震的晚年定論呢?錢穆先生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定「理」才是戴震晚年新的心得:
《疏證》之作,定在丙申,瑤田抄《緒言》之後,而即成於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與段懋堂書,正為「理」字義解,乃《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
《原善》先論「善」,再論「道」,始言「觀於其條理,可以知禮」。《孟子私淑錄》第一問問「性善」,第二問問「何謂天道」,至第十問始問「理之名起於條理歟」。《緒言》第一問亦「問道之名義」,第二問問「道」,第三問以後,始略及於「理氣」關係,第九問始問「理之名起於條理歟」。可見戴震撰寫《疏證》的前稿《原善》、《孟子私淑錄》及《緒言》義理著作時,「道」字位階的確遠較「理」字為更高。就這一點而言,錢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如果說「理」字義理,是戴震丁酉「最後新得」,則又與事實不符。因為用「分理」、「條理」之義來闡釋「理」字,實是戴氏與宋明理學家最大的歧異所在(說詳拙著《戴東原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於此不複述),而在《疏證》之前,《原善》、《孟子私淑錄》、《緒言》論「理」字均已闡發「分理」之義,顯見東原於「理」的匠心,早已獨運於先。無論如何,《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首論「理」十五條,卷中論「天道」四條及「性」九條,本末輕重,與前書大不相同,「理」字始轉居於首位,遠在「道」字之上,是無可懷疑的事實。由此推斷,東原於「理」字義證,早有蘊蓄,並非《疏證》之新得;唯《疏證》一書,始將「理」字置於「道」字之前,深致其義理,則是其晚年定論,可以確定。錢先生注意及此,可謂巨眼。戴震在丁酉去世前致書段玉裁時,復針對儒學「理」字,為他的詮解與宋儒的詮解劃了清楚的界線:
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宋儒之學,咸稱「道學」、「理學」,而戴震特於此二字別樹新義於宋儒,主要在於戴氏義理的方法,與宋儒大不相同。戴氏所謂「字義、制度、名物」是一體的,都指向「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目的。可見戴震對「知識」的定義,已超越了技術性之考證的層次,而進入一種綰合語言學方法、經典詮釋學以及經世思想為一體的境界。為了保證他所追尋的「理」概念具有最堅實的考證基礎,他埋首鑽研經籍,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各方面知識都不放過,整整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辛勤努力,他才沒有遺憾地完成鉅著《孟子字義疏證》,用字義考釋的方法,建構一個宏偉的義理世界。雖然學者認為戴震孟子學的發展軌跡不易掌握,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孟子學是在其經學考據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