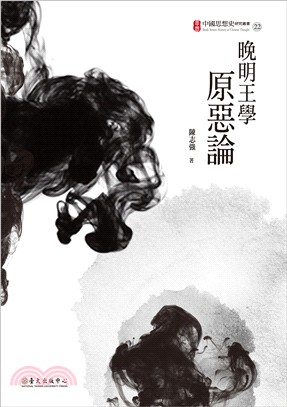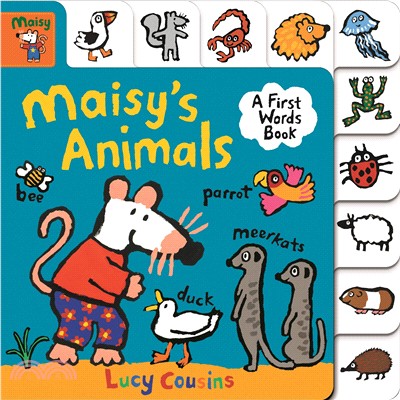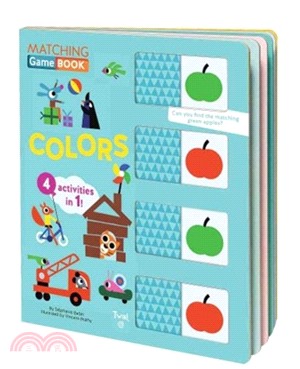晚明王學原惡論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
ISBN13:9789863503156
替代書名:On Evil: Thinking Through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of Late Ming Neo-Confucianism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陳志強
出版日:2018/10/26
裝訂/頁數:平裝/288頁
規格:21cm*14.8cm*1.7cm (高/寬/厚)
版次:初
適性閱讀分級:863【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人性非惡?惡從何來?如何去惡?
雖然理論上去「惡」與為「善」是修身的一體兩面,但歷史上「惡」的議題卻少見顯題與系統的論述。本書作為一部「即哲學史以為哲學」的學術專著,即旨於從哲學史角度清理晚明王學──自王陽明以降,下轄陽明後學,直到劉蕺山為止──的理論資源,繼而系統地開拓出一套關於「惡」的哲學理論。全書涉及的議題包括:(1)先秦與宋代儒者對過惡問題的開發;(2)王陽明對人性異化過程的分析;(3)王龍溪與羅近溪對意念歧出機制的揭示;(4)羅念菴對修道學者之過的診治;(5)劉蕺山對前賢惡論集大成的總結。期望本書的出版,可以推進學界對「惡」的問題的理解。
作者簡介
陳志強
香港人,1985年生。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2017-)。過往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2015-17)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2016-17)。2014-15年獲頒富布萊特(Fulbright)-研資局香港研究學者獎,赴美國波士頓大學擔任訪問學人。主要研究領域爲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史、比較哲學等,近年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學傳統中「惡」的理論。研究論文曾發表於《漢學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清華學報》、《東吳哲學學報》等學術期刊。
序
序二╱良知學籠罩下的惡的問題
楊儒賓(清華大學哲學所教授)
一
志強《晚明王學原惡論》此書是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晚明王學的惡的理論》大幅改寫而成,改寫的幅度不算小,據他自己的估計,大幅度的變動至少四分之一以上。至於各章各節,細部改動、增刪者也不少。一般改寫博士論文,以成專書者,都難免增刪改訂,志強此書亦不例外。志強此書改動較大者當是書名從「惡的理論」改成「原惡論」。「惡的理論」改成「原惡論」,就字面觀察,改訂不大。但對中國哲學傳統不陌生者,不難看出志強此書的用心。在中國哲學的術語中,「原」字往往意指探究本源之意,《淮南子》的〈原道〉、《文心雕龍》的〈原道〉、宗密的〈華嚴原人論〉、韓愈的〈原道〉〈原性〉、黃宗羲的〈原君〉〈原法〉諸篇莫不如是,這些帶著「原」字的篇章皆將其論文主旨提升到根源的層次,作徹底的反省。志強的《晚明王學原惡論》的「原」字內涵也不可能沒有這種徹底反思的原意。雖然志強行文一向沖淡自抑,但新書用了這個字,就不可能沒有中國傳統「原論」的涵義。
《晚明王學原惡論》此書上接原論傳統,近接唐君毅先生一系列《中國哲學原論》的專書而來,唐君毅先生的《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這些書是他的中國哲學史書寫的扛鼎之作,文字繁蕪,解義纏繞,其實不一定容易進入,但無疑都是20世紀中國哲學界的重要著作。志強出身中文大學,師承當代新儒家學者鄭宗義教授,其新書以「原惡」命名,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唐先生系列「原論」說的寫作。事實上,旁人如有這種聯想是合理的,志強寫此書,正是有意繼承唐先生的志趣而來。
在民國新儒家學者當中,甚至於放大範圍來看,在20世紀中國哲學家當中,唐君毅先生是少數對人的罪惡過錯有極深省察的學者。身為儒者,我們很難想像他會對惡罪沒有較清晰的認識。罪惡無定量,罪惡之存在依當事者的道德意識之敏感而定。理學家的反省意識特強,不要說巨惡了,即使是微過,反省至深的儒者的感受可能都會淵默而雷聲,深入骨髓。然而,民國儒家中,如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諸先生雖多有證體經驗,深入性海,但「惡罪」問題在他們的著作中,卻沒有明白顯現。唐君毅先生不同,唐先生對人的隱過、微過,有極深的省察,他的《人生之體驗續篇》深入個體微機隱念之地,析毫剖釐,一絲不容放過。他的領悟不要說放在當代中國,即使放在同時期的歐美哲人一同觀照,他對罪惡的體察之深仍是極特殊的。勞思光先生對唐君毅先生的道德意識之強,省察之深,甚有體會,譽揚也甚力。其譽揚洵屬如法如理,沒有踰越之處。據志強引唐先生的一位學生的證詞,唐先生生前原有意撰寫《中國哲學原論原惡篇》,後因考量立教的時機因素,乃作罷。
唐先生作罷的書,志強接著寫,此書的用意可知。在中國哲學悠久的「原論」傳統,以及在一代儒者唐君毅先生一系列《中國哲學原論XX篇》的籠罩下,志強此書到底該作何等定位?
二
《晚明王學原惡論》既然將「原惡」放在「王學」下定位,書外之意,當是「惡的問題」在陽明之後才有更深刻的省察,其為善去惡之工夫也當有前儒所未及者。
道德的惡的問題,可以說是理性的事實,是人生而為人不可避免的存在的性質。在人以外的動物世界中,動物有物競天擇,有血淋淋、黑漆漆的凶殘事件,但我們很難說動物的相殘有道德上的善惡,生物的存在依循非關道德意識的生物法則。但在人的世界中,不能沒有道德的善惡問題。孟子說:人皆有惻隱之心、善惡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他說四端之心,「人皆有之」,這不是推論的問題,而是當下呈現的的現量。四端之心牽涉到道德情感與道德知識的判斷諸多問題,但人在意念與行為上有道德的善與惡,孟子說:這是「固有之」,不用推敲。正因人的動機有善念,有惡念;人的行為有善舉,有惡舉,善惡之感乃是人的屬性不可去掉的質性,所以才有戰國時期人性善惡的大辯論。孟子的「性善」與荀子的「性惡」兩說更蔚然成為後世中土接納大乘佛教以及北宋理學抗衡佛道兩教的關鍵性理論。
善惡問題是老問題,對惡的問題窮究根源應該也不是在陽明之後才出現。很明顯地,當戰國儒家將善惡問題放到人性論的觀點下考量,已經是一種窮盡其源的提法。因為人性論意味著人的本質的問題,人性善惡或無善無惡或可善可惡,其意皆將善惡的問題和人的本質――也就是人的存在之依據連著考量。
然而,善惡的問題既然連著人性的問題一併考量,人性的問題深潛到何等境地,原則上,道德的善惡問題也會跟著深潛到同等的境地。儒家的人性論爭辯雖然在戰國時蔚為異彩,但由於其時儒者的關心不必集中在人的本質問題,各文化的發展總有偏重。到了東漢後,儒家人性論面對浩蕩而來的佛教義理,頓顯不足。佛教的核心教義在於人的解脫,佛教對於人的解脫雖各宗各派各有解說,但無礙於佛教的解脫預設著對於人的本質的反省深入到身心深層,以至超越三界之外的不可思議境界。在佛教的「惡」的反思中,「業力」、「無明」的概念遠非六道眾生所能盡,其悲智雙運、解行窮源的工夫也遠非前儒所能想像。善惡的問題隨著佛教帶來的人的本質的新的想像,其內涵頓顯深邃。
宋代理學興起,最大的思想刺激就是來自佛老的挑戰,如果我們借用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的說法,儒家在宋代復興的意義,就是要「立人極」。「極」字是理學的用語,更是周敦頤的用語,「極」字表極致,表標準,用朱子的說法,乃是表「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周敦頤「立人極」自然不能不追溯善惡的源頭到了極致,我們在〈太極圖說〉中,看到了「立人極」的目標,同樣在此文中,我們看到了周敦頤對於惡的起源一個經典的界定,他說:「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善惡的問題和人的氣質之性的問題和宇宙論的人的生成問題有關,應然與實然、倫理與自然在此有種詭譎的連結。周敦頤這種看待人性的觀點不能以「宇宙論中心」的觀點定之,至少「宇宙論中心」這個詞語如放在周敦頤體系上,其理論內涵需要重新界定,價值需要重新安頓。〈太極圖說〉所以成為理學的重要經典,正因它代表一種新的世界圖像與新的人的想像。
從宋代以後,論及道德的善惡問題,只要是儒家,其範圍就不可能只限於「人」的範圍,更恰當的說法,就不可能只是限於「有限人」的範圍。正是在宋代,一種貫穿有限、無限的人觀出現了。在宋代的理學體系中,一種界定人的有限、無限性的術語,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道心∕人心、德性之知∕見聞之知、先天之氣∕後天之氣的對分先後形成,這些兩兩對立的概念群組,彼此之間的分合如何解釋,程朱陸王容有差異,但人的本質中不能沒有這兩種性質的結合,用荒木見悟先生的用語,即是本來性與現實性的結合。隨著這種無限的人性論升起,善惡的問題也跟著水漲船高,它不可能只是人倫領域內的問題。理學家論善惡,當然不可能脫離人倫的領域,程伊川說:「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其說洵是無誤。但反過來說,也一樣成立,亦即禮樂、孝弟之盡其至,必定不能止於人倫界內,它一定有踰越人倫之外的內涵。
善惡問題到了宋儒手中,其精神非前儒所能到;宋儒工夫之細密,也遠非前儒所能及。程朱的格物窮理,「物物必格,事事窮至」,說細碎固可,但說其工夫藉著內外交治,以期成聖,可能更符合程朱的理念。張載有名的六有法「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其細密艱困比之清教徒或任何教派的苦行僧,恐有過之而無不及。張載、程伊川這種對治惡的工夫之所以如此細密,關鍵在於善惡的問題已被提升到「本體」的層次。
從善惡問題與本體的連結,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在宋代特別突顯出的為善去惡法門,此即「變化氣質」之說。「變化氣質」一語在當代社會的用法已淪為一種現世的公民修養,公民藉著符合公民社會的行為規範以規範自己,並達成個人性情的公共化。然而,宋儒的「變化氣質」不能脫離「氣質之性」的概念立論,「氣質之性」的概念則不能脫離「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形成」的脈絡立論。「在宇宙中的人」的「在」是潛存的「在」,但他的為人之本質總有相當程度是世界性的,他的氣質之性不能不是涉世的,涉自然的。但人既然身而為人,人總有道德定位作用的先驗之道德之心,此道德心帶有力之性質的道德之氣,所謂浩然之氣,這種心氣同流的主體使得任何的行動者可以從一氣同流的世界中興起,因而對現實有所匡正,有所為善去惡,所以需要「養氣」。「變化氣質」與「養氣」是同一套工夫的兩個面向,它們同依「體用論」的思維而立。
只有放在「體用論」的思維格式和「立人極」的倫理目標下,我們對宋儒如何思考惡,如何為善去惡,才可以找到理解的入口。宋儒的「善惡」概念都是意識語彙連接著自然語彙,我們僅舉一例以概其餘。周敦頤界定「性」為「剛柔善惡中而已」,「善惡」是道德語彙,「剛柔」是自然語彙,為善去惡的工夫乃是調和自然氣質,使之中和平正。也就是調和人的氣質之性中可善可惡的「剛善」、「柔善」,以達中和之說。宋儒的善惡問題總有宇宙問題,「立人極」總通向「證太極」。周敦頤之說是個典型的用法。
三
善惡問題在宋儒進入新的境界,周、張、二程、朱、陸諸儒所開出的理境遂得窮源至極,足以抗衡隋唐時期台、嚴、禪、密所開顯的本地風光。然而,千年來的儒學史顯示出的史實是善惡問題真正的精緻化,真正成為一代思潮的主流議題,並不是在宋代,而是在明代,尤其是在王陽明之後,才大顯於世。更明確地說,可斷代為王陽明與弟子王龍溪、錢德洪共同討論的《天泉證道記》形成之年,以至劉宗周於弘光二年絕食殉國為止的一百多年。王陽明良知學的出現是儒學史上的一大事件,這樁事件有幾個重要的歷史意義的斷點,他三十七歲的龍場驛之悟是一個關鍵性的事件,晚年的《天泉證道記》又是一樁重要事件。
理學的善惡問題之所以尖銳化,正是王陽明在遠征思田之前,和他的兩位大弟子討論良知善惡的問題才爆發出來。「良知至善」此義自孟子以下,當已懸為儒門共法,應該不會有爭議。但恰好在良知學發展到如日當空之際,王陽明最傑出的弟子王龍溪竟提出「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此說在陽明之後引發了一百多年的震撼作用,江右學派與東林學派諸君子的學術關懷,主軸之一可以說即是針對「無善無惡」之說的反動。即使直至明亡為止,劉宗周、黃宗羲師徒的學說的核心關懷之一也是如何回應王龍溪在天泉橋上的一席話。
本書的精采處正在於細緻地處理陽明之後,陽明後學如何面對惡的問題,它在16世紀出現有何意義?又是如何產生的?如何加以對治?志強從王陽明開始討論,接著討論王龍溪、羅近溪、羅念菴,最後殿之於劉宗周。在本書詳細的討論中,王學內部極精緻的析辨,也可以說概念之間如何正確地分辨,連帶地,工夫如何正確地下手,這些問題也就跟著出現。本書的探索很細,但我們或許可以掌握一條主線索,此即如何在兩種意義既相近也易於相混的概念之間,劃清界線。如王陽明在「知」與「意」之間,王龍溪在「乾知」與「識」之間,羅念菴在「良知」與「念」之間所作的劃分皆是。由於善惡問題的原始發生處就在人的生命本身,尤其見於意識的領域,意識語言本來即不易界定性質,加上陽明後學所用的語言高度集中在宋儒傳遞下來的基礎上,因此,不免有使用詞語相近或相同,其義卻迥然不同者,比如王陽明與劉宗周所用的「意」字,指涉即極不同。劉宗周作為明儒之殿軍,其操守之嚴,體證之深,遠邁前賢。他所用的語言如「氣」,如「獨」,其義卻多與前人不同,這些概念的分際如何澄清尤其值得留意。
志強此書集中處理陽明後學――也可以說是陽明學中「惡」的問題,焦點集中,此書可以繼新儒家前賢之志,發唐君毅先生未竟之意,應可無疑。本書析辨甚細,理路清晰,其勝義觀者自見,不待筆者嘮叨多語。但為什麼惡之原、惡之治這個道德實踐的關鍵問題到了陽明之後才特別突出?筆者或許可以提供一點進入的線索,這條線索不足以闡揚陽明後學善惡之說的精義,但或可作為支持志強此書的一個論點。
「本體」是理學核心概念,此義大概可以為治斯學者共許的說法。但如何理解「本體」?宋、明儒的偏重不同。我們觀宋儒使用「本體」,通常「體」、「用」兩字連用,本體以「體用」連用方式出現的意義,在於人的道德問題往往也是存有論的問題,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處理人的善惡問題,宋儒立其大。在陽明學的脈絡中,「本體」一詞卻常和「工夫」連結,體用論的問題變成本體―工夫的問題,明儒立其精。這種本體論的焦點的轉移不是矛盾的關係,也不必然如王夫之所批判的良知學是背叛儒門的問題。但焦點的轉移是那麼明顯,不可能沒有意義的,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性命之學的轉移。
在宋代,性命之學是和世界的誠明問題一併討論的,善惡問題繞著「氣質」的問題旋轉。陽明之後,儒學安身立命的問題和世界的誠明問題暫時脫鉤,學者的意識集中在主體的轉化、辨識、證成的問題上面,王學是徹底的心學。陽明後學不管是江右學派,不管是東林學派,不管是浙中學派,良知學的發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良知本身如何呈現,也就是工夫如何展開的問題。良知的絕對義所應允的主體與世界的終極連結的向度雖然也被觸及,但它的出現在實踐的過程中是次要的。即使陽明學強調良知在事上顯現,但格物是虛的,現象學意義下的客觀世界之於良知實踐乃是存有而不活動。道體也是虛的,陽明學真正的關心是心體,作為心體呈現原則的良知之作用流行才是實的,它是唯一的乾坤萬有基,陽明後學的善惡問題即是在良知學的架構下展現的。
目次
序一 讀《晚明王學原惡論》/鄭宗義
序二 良知學籠罩下的惡的問題/楊儒賓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主題與方向
二、研究進路的澄清
三、章節結構的安排
第二章 理論淵源——論先秦與宋代儒者的過惡思想
一、前言
二、先秦儒者過惡思想的簡述
(一)孔子
(二)孟子
(三)荀子
三、兩宋儒者過惡思想的簡述
(一)周濂溪
(二)張橫渠
(三)程明道
(四)陸象山
四、小結
第三章 「意」的墮落——王陽明論「惡」之起源
一、前言
二、陽明論「惡」的來源
三、陽明的去惡工夫及其「一滾」面向
四、「人性圓融說」在善惡問題上的理論意義
五、小結
第四章 「念」的歧出——浙中與泰州學者「惡」的理論研究
一、前言
二、「念」的歧出及「知識」與過惡的關係
三、當下自反的去惡工夫
四、小結
第五章 知見空言——羅念菴論「學者」之「過」
一、前言
二、「學者」知見空言之「過」
三、針對「學者」之「過」的去欲工夫
四、小結
第六章 集大成者——劉蕺山對「惡」的議題的總結
一、前言
二、陽明與蕺山過惡思想的理論關聯
三、《人譜》及其對「惡」的議題的總結
(一)〈人譜正篇〉
(二)〈人譜續篇二〉
(三)〈人譜續篇三〉
四、小結
總結
引用書目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緒論(摘錄)
一、研究主題與方向
人性非惡?惡從何來?如何去惡?—「惡」是一個貫通古今中外普遍的哲學問題。
眾所周知,「性善說」是孟子以至儒家哲學中一大重要理論。然而,無論古往今來與學界內外,都不乏一種流行的質疑:認為「性善說」過分樂觀地關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卻缺乏對人性醜惡面向的照察。早在先秦之世,儒門之內便有如荀子者質疑孟子的「性善說」。對於孟子「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的想法,荀子質疑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樸,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荀子.性惡》)荀子的意思是,從現實的一面看來,失喪純樸善良而犯下惡行往往是人生的常態;就著這一點而言,「性惡」比起「性善」似乎是對人性更為恰當的描述。時至今日,「性善說」同樣時常備受質疑。例如當代學者韋政通便嘗言:
儒家在道德思想中所表現的,對現實人生的種種罪惡,始終未能一刀切入,有較深刻的剖析。根本的原因就是因儒家觀察人生,自始所發現者在性善,而後就順著性善說一條鞭地講下來。……基督教的人生智慧因來自對人類原罪的認識,所以從原罪流出的一些概念,是負面的,非理性的,如:邪惡、貪婪、狠毒、兇殺、姦淫、偷盜、詭詐、仇恨、讒謗、怨尤、侮慢、狂傲、背約、妄證、說謊,基督教教義中,勸告世人的一些警句,無不是環繞這些概念說的。這一切所指控的事實,對資質醇厚,或善於自欺者來說,可能叫他們膽戰心驚,但這是充滿社會的事實,為儒家人生思想所不加措意的事實。
殷海光先生亦說:
儒家所謂「性善」之說,根本是戴起道德有色眼鏡來看「人性」所得到的說法。因為他們惟恐人性不善,所以說人性是善的。因為他們認為必須人性是善的道德才在人性上有根源,所以說性善。這完全是從需要出發而作的一種一廂情願的說法。
這些學者同樣認為儒家只關注人性之善,對人性中種種負面的、非理性的罪惡都未能予以正視。而即使是學界之外,對「性善論」抱有懷疑者亦不乏其人。例如填詞人林夕便引述了坊間一些說法曰:「孺子將溺於井,會有人幫忙;但時移地轉,有人給車撞倒了,途人反而走避,一地現鈔滿地金牛,路人有不忍之心爭相出手拾遺。你說那孟子,提倡什麼性本善,本性若皆善良,孟慈母何必要為子女教育問題,搬來搬去?」由此觀之,孟子「性善」的想法,無論古往今來與學界內外,都是極受爭議的議題。若然「性善」,世間何以有惡?
誠然,對於世間何以有「惡」的問題,儒學傳統不乏零星的討論。特別是儒學中所謂「氣性一路」,對「惡」的問題有著更為直接的論述。例如上面提到的荀子就認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好利、疾惡、耳目之欲、好聲色等是人性的自然傾向,單就此人性的自然傾向而言,往往會導致「犯分亂理,而歸於暴」的「惡」果。所謂「善」的成就,只能訴諸人依循「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的人為努力。在這意義上,荀子直接將「惡」撥入「性」中了解。後來兩漢學者,對「惡」的解釋也甚為直接。例如董仲舒就說:「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董仲舒將人之善惡與天之陽陰比配起來,將「仁」歸入「陽」的一面了解,而將「貪」、「情」、「欲」歸入「陰」的一面了解。在這理解下,人要去惡為善便只有「禁陰」—所謂「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是也。如是,董仲舒看來甚為直接將「惡」撥入「情」、「欲」中了解。即使是同時代的《論衡》亦提到:「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白虎通》亦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表面上,這些文字都反映了兩漢學者將「惡」放在「情」、「欲」中了解的風氣。是則至少在初步看來,一般「氣性一路」的學者直將「惡」放在「性」、「情」、「欲」中了解;姑不論解釋是否稱理,但至少他們對「惡」之來源的解釋,初看起來都甚為直接易明。
相較而言,孟子與心學學者對「惡」的解釋則更為迂迴隱晦。對於孟子而言,「心」指涉的惻隱之心、不忍人之心、乃至四端之心,是人踐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基礎,其自身自然不會產生「惡」。素謂孟子即「心」言「性」,其言人「性」之善乃從四端之「心」的落實而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就此而言,「性」與「心」理當一致,同樣不可能是「惡」的來源。孟子亦嘗言:「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孟子.告子上》)明言即便是飲食之「欲」,自其「無有失也」的狀態而言,其自身亦無所謂「惡」。是則在孟子哲學中,「惡」的出現並不能歸因人性自身的「心」、「性」、「欲」任何一部分。心學學者順乎孟子哲學的基本精神,固然亦不會將「惡」的出現訴諸於「心」與「性」。畢竟如明儒王守仁(陽明)所言:「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心」與「性」即是「理」,其自身斷不是「惡」。相較孟子哲學,心學學者更為推進之處,則在於他們在理論上將「心」的內部結構撐開,而進一步認為「心」內部的「意」、「知」、「物」、「情」、「念」、「欲」等環節,全都不是「惡」的來源。陽明便說:「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驟眼看來,「性」、「心」、「意」、「知」、「物」全皆是「理」不同層面的表現,就此而言都不是「惡」。陽明又言:「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情」本然地亦是「良知」自然之用,這裡沒有「善」「惡」之分。陽明高足王畿(龍溪)有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其最初無欲一念,所謂元也。⋯⋯元者始也,亨通、利遂、貞正皆本於最初一念,統天也。」直以為「念」的原初狀態無非是惻隱之心的表現,其作為「統天」者理論上亦當非「惡」。而劉宗周(蕺山)作為「廣義的王學者」(這一點將於下文再行交代),甚至更將「欲」往高看,而以之為生生之理的表現(「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是則「欲」之自身不僅不是「惡」,反而甚至可以是「善」的表現。由此觀之,對於孟學與心學學者而言,人「性」與「心」內部任何一個環節之自身—包括「意」、「知」、「物」、「情」、「念」、「欲」等概念—全都不能直接用以解釋「惡」的產生;是則相較於前面提到「氣性一路」的學者,心學學者如何解釋「惡」的出現,尤其是儒學理論中亟待澄清的難題。畢竟,「心」既然通於「性」與「理」而有善無惡,其所表現發動而成之「意」理當亦是有善無惡,「知」與「物」相應地亦當是有善無惡;既然「性」、「心」、「意」、「知」、「物」全皆有善無惡,那麼「惡」從何來?—這可謂是承接孟子「『性』既然是善,『惡』從何而來」這個問題而來的進階版本。又另一方面,陽明亦有言:「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這些將「惡」放在「意」念發動處理解的文字,表面上看來又似與上文謂「意」並非「惡」的想法對頭衝突。凡此種種心學學者對「惡」的解釋,不僅對於門外漢而言極為晦澀難明,即使對於專門的研究者而言同是難懂理處。例如西方學者倪德衛(David Nivison)質疑:
何以有惡?我認為王陽明沒有真正的答案。他只提供了一個命定論式的解釋:只有少數的人是「生而知之」,但大部分的人生來卻被嚴重「遮蔽」,並且必然經過長時間自我改善的過程才能重回正軌……王陽明並不真對惡的理論感興趣。他的問題是指引我們遠離於惡。
艾文賀(Philip J. Ivanhoe)亦說:
他(筆者按:王陽明)沒有提供解釋,而跟一眾佛學學者同樣相信解答這些問題並不重要。如佛學般,他關注治療遠多於理論。他嘗試為其理解的邪惡尋找療法,但他對惡的本質與根源卻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
至於中國學者陳來同樣指出:
惡的問題對儒家特別是心學總是一個困難。如果說惡是善的過與不及,則「過」或「不及」又緣何發生?「心之本體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得」,姑息、殘酷或可說仁之過與不及,而人的「私欲」如何歸屬呢?如果對於孝、弟而言,「心自然會知」,那麼私意私欲是否同樣是「自然會有」的呢?陽明說:「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才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人又為什麼會「自家著些意思」呢?良知既然是心之自然條理,為何不能規範「過」或「不及」呢?這些問題在陽明哲學中都未得真正解決。
王鵬甚至直以為陽明對「惡」的解釋陷於理論上的矛盾,他說:
陽明對惡之安頓之所以如此矛盾,有著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就陽明學內在的邏輯來講,因為心、性、理三者統而為一,所以惡不可能存在一個獨立的根源,它也就不是必然發生的。但同時,惡卻活生生的存在,而惡之不能必然發生與現實的存在之間的矛盾,對於陽明乃至整個心學來說總是無法克服的。
在王鵬的理解下,「惡」在陽明學中理論上不可能存在一個獨立的根源(不存在於「心」、「性」、「理」之上),然在現實上「惡」卻是活生生的存在,於此乃見陽明哲學在「惡」的問題上思想矛盾。如是,本書核心的問題意識,乃在通過晚明王學為中心,發明蘊含在心學傳統中「惡」的系統理論。期望彰明儒學傳統對「惡」的理解之後,能夠建立回應相關質疑的基礎。
事實上,單就理論而言,儒學的確較常論述「為善」的面向。但當知道,「去惡」與「為善」本來就是修德過程的一體兩面。如張灝便說:
儒家思想是以成德的需要為其基點,而對人性作正面的肯定。不可忽略的是,儒家這種人性論也有其兩面性。從正面看去,它肯定人性成德之可能,從反面看去,它肯定生命有成德的需要就蘊含著現實生命缺乏德性的意思,意味著現實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淨化、需要提升。沒有反面這層意思,儒家思想強調成德和修身之努力將完全失去意義。因此,在儒家傳統中,幽暗意識可以說是與成德意識同時存在,相為表裡的。
張灝所指的「幽暗意識」,意思是對於「人性中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有所正視和省悟。在基督教的語言中,所謂「黑暗勢力」可以指涉「邪惡、貪婪、狠毒、兇殺、姦淫、偷盜、詭詐、仇恨、讒謗、怨尤、侮慢、狂傲、背約、妄證、說謊」等罪惡。而由於在基督思想的系統中,人類的始祖偷吃了知善惡樹的果子,而世世代代的子孫都生而具有原罪,因此人性中的罪惡可謂是「與始俱來」。張灝尤具真知灼見的是,他注意到儒家傳統中「成德意識」與「幽暗意識」乃相依互存:「成德意識」乃是一種希望達到聖賢理想境界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是基於對現實生命是「昏暗的、是陷溺的,需要淨化、需要提升」的自覺。若人缺乏這種「幽暗意識」,對生命中種種罪惡、陷溺、墮落不以為然,則大概亦不會生起志於轉化生命的「成德意識」。因此,愈是對人性中「幽暗」的一面有真切的省悟,人愈會生起一種轉化生命的「成德」要求。在此理解下,張灝明言儒家思想並非一味地樂觀。
然而,雖謂儒學在理論上不能欠缺「幽暗意識」的一面,但這些想法在論述上卻始終沒有充分的開展。張灝復說:
兩者表現幽暗意識的方式和蘊含的強弱很有差異。基督教是作正面的透視與直接的彰顯,而儒家的主流,除了晚明一段時期外,大致而言是間接的映襯與側面的影射。
唯獨晚明劉蕺山的《人譜》,才可說是儒門直接論「惡」的經典:
《人譜》裡面所表現的罪惡感,簡直可以和其同時代西方清教徒的罪惡意識相提並論。宋明儒學發展到這一步,對幽暗意識,已不只是間接的映襯和側面的影射,而已變成正面的彰顯和直接的透視了。
這裡張灝明言,儒家主流對幽暗意識的論述只是一種「間接的映襯與側面的影射」,因而遂謂:「幽暗意識雖然存在,卻未能有充分的發揮」。唯有在「晚明一段時期」儒學對幽暗意識才有空前的討論。而宋明理學殿軍劉蕺山的《人譜》,即是當中的表表者。
如是,要廓清儒家思想對人性黑暗面的態度,晚明以降直到蕺山的《人譜》為終的一段思想資源,可謂是個中的關鍵。學界對蕺山的《人譜》已有不少討論,但大多集中在探討蕺山論「惡」的內部理論。相較而言,學界鮮有從哲學史發展的角度,考察蕺山與前賢在「惡」的議題上的理論關聯。欠缺這種哲學史向度的理解,或會使人誤以為蕺山論「惡」乃儒門獨樹一幟的孤例,並使人不能恰當定位《人譜》的價值與意義。本書撰寫的另一目的,即是從哲學史發展的角度,考察晚明一段時期—自陽明以降,下轄陽明後學,直到蕺山為終—「惡」的問題在理論上如何步步發展與轉進。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