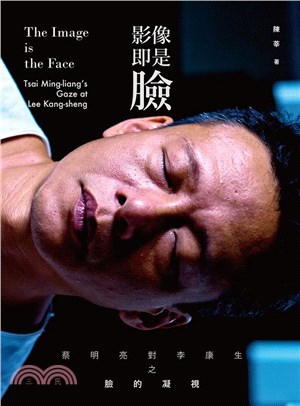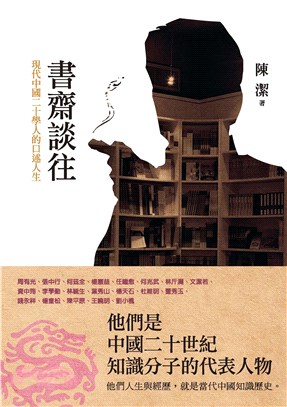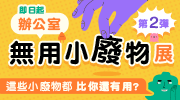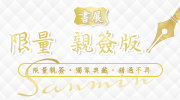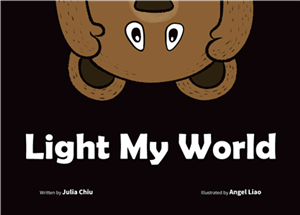影像即是臉:蔡明亮對李康生之臉的凝視
商品資訊
系列名:電影苑
ISBN13:9789574459070
替代書名:The image is the face: Tsai Ming-liang's gaze at Li Kang-sheng
出版社:書林
作者:陳莘
出版日:2021/01/06
裝訂/頁數:平裝/392頁
規格:23cm*17cm*1.9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1991年蔡明亮在台北遇見李康生
小康成為了蔡明亮電影永遠的主角
小康的臉對蔡明亮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沒有李康生的臉,蔡明亮的影像面貌是否還會如此獨特?
蔡明亮的存在是個獨特的現象。他是個異鄉人,來到台灣求學、定居、開始拍電影。他的電影只有一個主角、只有一張臉,看似限制了他,卻又矛盾地給了他自由及無限可能。藉由蔡明亮的課堂講稿、各階段的訪談、劇本、畫作、文字等等,《影像即是臉》記錄下蔡明亮尋找一張「影像之臉」的過程,也探問了「蔡明亮何以成為蔡明亮?」
這本書並不想要以蔡明亮的電影為單位去分析,或定義他的影像在哪種框架下象徵了什麼樣的意義,純粹只是從一個影迷與學習者的角度,由自身的困惑出發,試圖理解他的創作核心,再往下繼續尋找蔡明亮這個「人」的核心。
為什麼他的電影採取了那樣的表現方式?
為什麼永遠是李康生?
這傳達出蔡明亮的什麼?
藉由影像,在提出問題及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或也能對自身提問,找到解答。
本書特色
1. 從觀影者角度出發,真誠地向蔡明亮電影提問
2. 專章討論李康生在蔡明亮電影中的涵義
3. 從早期電影起,到後期影像作品、舞台劇與裝置展,以縱觀的方式討論
4. 結合藝術史、文學、影像理論、精神分析等面向的切入角度
作者簡介
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專長為藝術評論、策展實踐、中國藝術史、電影研究、精神分析。曾為關渡美術館、高雄美術館、鳳甲美術館等策展,並參與策畫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吳天章:別說再見」。曾獲得南贏文學現代詩優選、數位藝術評論獎、、台新文化基金會「新銳藝評獎」等,以及第十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類提名。企劃主編《ACT藝術觀點》63期、64期,並長期於《現代美術》期刊發表評論。著有《偽青春顯相館:吳天章》(2013)。
目次
序|我不想寫一本論文
前言|2013年,蔡明亮的一門課
壹 覆蓋在七紗下的臉
影像作者與演員共用的一張臉
達文西、王爾德、蔡明亮三人的聖約翰
畫外音 瞬間坍塌的敘事意外
貳 穿越迷界妄相的玄奘
「通俗煽情」對上「低限極簡」
玄奘即施洗約翰
畫外音 他人怎麼變成地獄
參 荒謬啊!愛情萬萬歲
無形的約定地——愛情空床
發生在《洞》裡頭的變形記
畫外音 怪誕、瑣細、傲慢的荒謬劇
肆 無法結痂的影像
抵賴之「癖」
這世界沒有道理
不反射思維的有機影像寶石
畫外音 從「題材」的開發轉為「情結」的描摹
伍 無法完成的作品
心靈照相式劇本
瘸子走過的乾涸黏液
畫外音 當「重複」成為一個鑑賞對象
陸 僭越在天邊的一朵雲
當誡令出現,「物」也閃現
穿透創傷結痂的方法——性交
模擬主體間性的鏡頭美學
畫外音 對不準的德勒茲影像論
柒 象徵界無可奈何的對象——小康
只畫一張椅子
為什麼是李康生的臉
沒有他人目光存在的「絕緣體」
遲緩絆住了欲望的幻化
畫外音 柏格森vs.佛洛伊德、德勒茲vs.拉岡
捌 蔡明亮的原始匱乏——自由與歸屬
「只有你」的原初場景
被東西南北鎖住的島嶼
畫外音 「緩慢」之外的暗物質影像
玖 朝向純影像的慢走長征
電影前那一刻的
追尋純影像——存在的觀相術
蔡明亮的聖狀反應
畫外音 這些思想家體現的拓撲思維
後記|是誰下了這盤棋?
參考書目
附錄1:蔡明亮導演作品編年
附錄2:蔡明亮各影像作品之合作演員
書摘/試閱
壹.覆蓋在七紗下的臉
拍攝《臉》的2006年,那年尚―皮耶.李奧(Jean-Pierre Léaud)六十二歲,導演楚浮去世二十二年。我們很難想像蔡明亮拍攝一部電影的初衷是如此簡單的理由,只為拍一張臉,他甚至形容其創作歷程宛如是「追尋這張臉」,慢慢地,他與這張臉的距離越來越近了。有天,他說出這個想望:
當時羅浮宮來找我的時候,問我想拍什麼,我毫不猶豫就回答了。而且是個奇怪的機緣,他們找我的時候,我正在參加楚浮20年的回顧展,在巴黎近郊的一個戲院。全部的人都一起看《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 1973)那部電影,「全部的人一起看」實在太奇怪了,這電影我那麼熟悉、那麼喜歡,而這些人都坐在我旁邊,到底哪個是真的。所以當天晚上在旅館,羅浮宮問我想拍什麼,我說我想拍尚―皮 耶.李奧的臉,這個念頭不是突然間冒出來的,它是生在那邊,所以 我說這電影的過程很像自畫像,尤其是《臉》。……其實我就是一直追尋這張臉孔,才來到《臉》這個影像,也等於是它把我帶進羅浮宮。
李奧飾演的法國導演楚浮(François Roland Truffaut)在《日以作夜》的片場中,反覆夢到同一個夢。一次又一次,年幼的他拿著拐杖,走在一條斜坡道上,不知要去哪,只覺得小孩在半夜裡,身著西裝,手拿拐杖相當怪異。漸漸的,來到最後一次的夢境,那根預備的拐杖才從電影院的鐵門縫隙伸了進去,把整幅《大國民》(Citizen Kane, 1940)劇照從裡頭拖了出來。一定要得逞的,不管幾次一定要得到手的,用夢的達成性達到妄想。對於蔡明亮來說,他也有一張臉要弄到手,無法善罷甘休、冒各種風險也要拖拉出來的這張臉,就是楚浮的演員——李奧的臉,錯失這張臉的遺憾可能會在夢裡糾纏一輩子,這是個不斷找上來的夢。 於是,這部在羅浮宮拍攝的影像就命名為《臉》(Visage),這名稱切題地描述著遠方的引力,這張臉是來自世界另一頭的注視。一張臉具有什麼魔力,從鏡子的發明與使用即可顯露,光線的完美反射需等到玻璃與金屬找到彼此,結合成正反兩面,我們才有機會「照見」自己。1450年,在義大利穆拉諾島(Murano)發現含有豐富氧化鉀和磁鐵的海草灰,可以燒製出一種極其清亮的水晶玻璃,工匠因為發現這祕密,被終生囚禁於小島上。五十七年後,另一位工匠發現將汞合金附著在玻璃的技法,人的臉終於無所遁形地映在鏡面了,我們很難相信十六世紀的人願意花八千英鎊去購買一面鏡子(在製鏡方法還是個商業機密時,一面鑲有精美銀框的威尼斯鏡售價幾乎是當時拉斐爾繪畫作品的三倍。在當局頒發給戴爾加洛兄弟〔Domenico d’Anzolo del Gallo〕二十年的專利之後,人們對穆拉諾鏡子所產生的熱情,讓瘋狂採購潮延續兩世紀之久)。
付出昂貴代價的買鏡人不是為了看到物理光線的反射,買鏡人購買的是——可以凝視一張臉的媒介,他們希望無時無刻都能獲得一張視像穩定的臉,這欲望等待了好幾世紀才由威尼斯人滿足了。散發出誘惑的是出現在鏡中的那張臉,所有鏡子的懸掛高度都是以照映臉的完整性為基準。為什麼鏡子會被用來映照一張臉?我們甚至可以說,是這張臉邀來鏡子的發明。這個我們喚為「臉」的地方到底有什麼特殊之處?它區別你與我的面容,是我們讀取一個人情緒的地方,也是會洩漏最多訊息的地方。它會說出我是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職業、生長在什麼環境等訊息,沒有人請它述說,它卻自行表露,且不知是什麼樣的力量在臉上刻出這些語言。它展示心靈,我們卻找不到背後有什麼連結管道,總之,它就是個顯形。人不能沒有鏡,人隨時需要從鏡子審核這張臉所給出的訊息。且浮現在這面鏡子上的臉不是別人——是自己,在鏡子前,人與自己的目光對視。
影像作者與演員共用的一張臉
發問只會對著一張臉問,而這組五官往往又會喚來濃厚的好奇,蔡明亮認識李奧這張臉的時間點是在大二時看到《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那張十五歲之臉,他追尋這張臉的日子好長,二十幾個年頭過去,這張臉與蔡明亮的電影事業有什麼關聯?他追的是演員李奧還是導演楚浮?拍攝這張臉的渴望是什麼?蔡明亮作品《臉》或許可解答一些疑惑。第一幕,巴黎的某間咖啡館,從窗外凝視桌上的一只咖啡杯,白色的,座位上沒有人,但有交談聲正打聽著某位離去的客人(李奧)。一會兒,穿著正式的小康臉色凝重地坐在杯子前,鏡頭外的助理還在追問客人的去向。小康(本片飾蔡導演)從地面拾起了一根白色羽毛,發楞許久。鏡頭轉到街上的電線,電線上沾黏著羽毛與大便,背景有咕嚕咕嚕的鴿子聲,空杯主人可能剛走過這兒。下一個鏡頭已是台北老家,小康母親在廚房砧板剁著一團絞肉。巴黎咖啡廳的那一幕,輕描淡寫的,從窗外看進去,看不出那杯子有什麼灼熱感。是課堂上聽蔡導演的講述,才知道望杯的心情如此忐忑:
那天我沒有趕上約定好的時間,抵達時只剩下一只空盪盪的杯子,靜 置桌上,心想……這樣也好。他已不是十五歲的尚―皮耶.李奧,是六十幾歲的李奧。我甚至不敢面對它,面對它要經過很大的決心,才能接受這殘酷的現實……。
等最後見著李奧本人時,他的確累了、老了,他有兩張臉,一張是十五歲,一張是六十幾歲,兩張臉重疊。
蔡明亮用記憶中熟悉的臉(從《四百擊》影像擷取出的安端〔Antoine〕),去核對現實中的臉——即將成為他演員的老臉。記憶中那張十五歲的臉,活成一個想像的樣子許久了,那是楚浮當時眼中所見的李奧,模樣機靈、防備的孩子,這臉停在某時間點,歷久彌新。等到這對相約人碰面時,眼前已是完全脫離影像的現實,蔡明亮在這張六十二歲的臉上尋了許久,最後這老臉才和劇中人安端重疊了。這種指認一張臉的過程,是文字根本無法敘述的,我們無法清楚告訴另一個人我在臉上看到什麼,什麼讓我確認那是我的父親、那是我的情人,臉就是臉,上面沒有隱喻或修辭。所以,一個導演刻意在影像中選用一張臉時,也意味著他要用「臉」來述說語言所不能及的東西,或不言而喻的東西。當我們讀取一張臉,不是憑藉知識,而是人生閱歷。一個人可以讀另一個人的臉(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比「讀」更貼近的動詞,但「讀」這個字無法顯示情感的瞬間傳導),只要盯著它,就瞬間意會了,不管是哪個國籍、性別、年齡,沒有人可以教會我們這件事,其他生物也無法互讀對方的臉。這是一張「人臉」特有的飽和度與溝通性。
臉上那個不言而喻的東西是什麼?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設法說出這個指認出他母親的憑藉,他說:
這不可名狀之物,即為氣質(l’air)。一張臉的氣質是不可分解的(一 旦我能分解,我便可證明或否絕,總之,我可懷疑,可偏離攝影。而 攝影的本性是完全明顯:明顯,即不願被分解的)。氣質不像側寫, 並不是概括的或智性的組成。⋯⋯氣質是個過渡的東西,由身體導向 靈魂——animula。氣質(我如此稱呼真相的表情,因沒有其他更好的 字眼)有如身分的固執附加物,天賦所得,毫不「自負」:氣質所以 能表現主體,因主體不自以為是。(巴特,1997:125-126)
臉同攝影,是一個完全「明顯」的物質,它的明證力已將自個兒全盤托出,屬於不願被分解的物質,臉無法進一步用運算來驗證。巴特進一步逼近臉的獨特性,指出這張臉的隆起是由完全不自知的氣質所形成,氣質是那層皮囊的主要支撐物,它是無能為力去更改的物質,也沒辦法分析出成分。一個導演選擇一個固定的演員,即選擇了一張影像創作的「臉」。對於這張臉的「面容」,他無能為力,導演必須認知到自己的無能為力,才算深刻的理解了氣質。如果夠透徹的話,他會進一步意識到影像作者與演員其實是「共用一張臉」。臉的先驗可質疑語言是否造假,因為臉的滿盈會讓語言變得言不由衷。意識到一張臉是什麼的作者,會慢慢地放棄會話的語言。為求這「真相的表情」,導演必須對自己的欲望下禁令,這張臉才會如其所是地存在,百分之百地由一張單純的「臉」去喚起另一個人的情感,因為,由身體導向靈魂的「氣質」會說出不受質疑的話。2012年的短片《無色》最後一幕,演繹的就是這真理,蔡明亮安排身著紅袈裟的玄奘走過摩肩擦踵的市集,穿過人聲鼎沸的人群,慢慢地,前方的路縮減為一條狹長淨白的通道,這個沒有任何一句對白的影像最終能說出什麼,只能完全託付給那張臉。紅僧在階梯的末端,走向一個窗口,最後被蔡明亮放入引號內強調的,只有臉,只有這張真相的表情,其他,別無所有。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