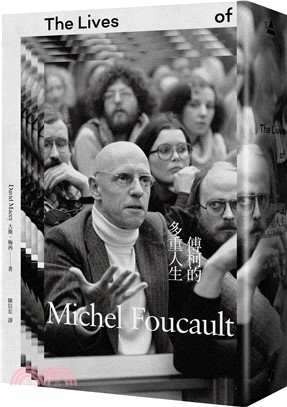傅柯的多重人生
商品資訊
系列名:David Macey
ISBN13:9786267236321
出版社:春山
作者:大衛.梅西
譯者:陳信宏
出版日:2023/08/15
裝訂/頁數:平裝/816頁
規格:21cm*14.8cm*4.5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83【十一年級】
商品簡介
最詳盡的傅柯傳記
當代最頂尖的傅柯專家艾登Stuart Elden專文補充新資訊
「這個時代光芒最閃耀的心靈。」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對傅柯人生的詳細評估以及職業生涯的概觀,仍是至今為止最傑出的著作。」
──史都華.艾登Stuart Elden
傅柯的著作與思考極具啟發性與開拓性,自一九六○年代以來不斷對人文及社會科學造成深刻衝擊,影響持續至今。相較於其他學術人,傅柯的一生顯得特別多采多姿,職業生涯的軌跡也異乎尋常,雖然經常想遠離法國的學術文化中心巴黎,最後卻獲選進入法國學術體制的最高殿堂法蘭西公學院,直到一九八四年因為愛滋併發症而驟然離世。
本書作者梅西對法國思想極為熟稔,他在艾希邦的首部傅柯傳記面世數年後展開另一個傅柯生平的研究、訪談與寫作計畫,不但獲得傅柯親友及艾希邦的幫助,更得到傅柯長期伴侶丹尼爾.德費的全力支持。梅西以英文寫作,對於並非出身自法國學術文化背景的讀者而言,其敘述顯得背景脈絡更加清晰,對各項細節的紀錄也更加詳盡,與艾希邦的傳記各有所長、互為補充。
梅西於二○一一年罹癌辭世,未能以陸續出土的資料重新修訂本書,然而這個二○一九年重出的新版特別邀請當代最頂尖的傅柯專家艾登(Stuart Elden)撰寫專文,根據三十年來的新資料與新研究全面審視梅西當年的成果,不但為讀者補充了最新進展與發現,更肯定這部傳記所達到的高度成就。
作者簡介
大衛.梅西 David Macey
英國傳記作家及翻譯家,專精二十世紀法國思想,他是倫敦大學學院法國文學博士,譯有近六十本法文著作,其中包括傅柯的法蘭西公學院講座《「必須保衛社會」》("Society Must Be Defended")。梅西長期為《激進哲學》(Radical Philosophy)雜誌供稿,著有《從知識脈絡解析拉岡》(Lacan in Contexts)、《傅柯的多重人生》、《批判理論辭典》(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及《法農傳記》(Frantz Fanon: A Biography)。《傅柯的多重人生》曾依出版社規劃需求而推出篇幅僅剩四分之一的精簡版《關鍵人物:傅柯》(Michel Foucault [Critical Lives])。
譯者簡介
陳信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獎項,目前為專職譯者。譯有《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反彈回升》、《貓哲學》等數十本書。
序
摘錄自〈引言〉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米歇爾.傅柯因為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所導致的併發症而去世,享年五十七歲。他的最後兩本著作才剛出版,並且在新聞媒體當中受到廣泛討論。在他去世之時,他無疑是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還達成了以《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這本書登上暢銷榜的不尋常成就,儘管這是一部深奧難懂的著作,而且他也說自己寫這本書的目標讀者是一小群專業人士。他成功跨越了把純學術界和廣泛文化圈隔開來的分界線。在將近十四年的時間裡,他一直任教於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這所法國學術界裡聲望最崇高的教育機構。他在美國備受讚揚,他的著作譯本也令他享譽國際,聲名遠播到巴西乃至日本。實際上,他的國際聲譽幾乎超越了他在法國的名望。在巴黎的書店裡,研究傅柯的著作有許多都是從英文翻譯而來,甚至可說大多數都是如此。
傅柯的人生有許多不同面向──身為學者、身為政治運動人士、身為小孩,以及身為男同性戀者。他的人生有非常公開的一面,也有極為私密的一面。在相當程度上,傅柯的人生也是法國的智識生活。法國智識生活的各項改變幾乎都反映在他的著作裡,各項發展也幾乎都受到他的影響。此外,他的傳記也必然是他那個時代的智識史。在一段大方得出人意料的頌詞當中,對於傅柯有過嚴厲批判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寫道:「在我這個世代針對我們這個時代提出診斷的哲學家當中,傅柯對於時代精神造成了最為長久的影響。」傅柯在學生時期目睹並且抗拒了沙特式存在主義的支配地位,而且他所屬的那個世代也發現或者重新發現了黑格爾、尼采與海德格。他師從阿圖塞(Louis Althusser)與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一九六○年代期間,他廣被視為結構主義「四人幫」的一員,另外三人則是拉岡、羅蘭.巴特與李維史陀。十年後,他又被歸為所謂的新哲學家,以倏然間揚棄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主義而著稱。在人生晚年,他又再度轉向,開始對斯多噶哲學進行平靜的沉思,並且探索一種可能的新倫理學。
傅柯一生的多重面向,令人難以對他的著作做出令人滿意的分期。在德雷弗斯(Hubert L. Dreyfus)與拉比諾(Paul Rabinow)那部深富影響力的傅柯研究著作當中,他們提出一套四階段的架構:一個海德格階段、一個考古學或者類結構主義階段、一個系譜學階段,以及最後的倫理學階段。這套架構不是完全不令人滿意,但壞處是把一個複雜的人生與一套複雜的著作化約至單純的哲學層面。這套架構不理會傅柯在政治方面的發展軌跡,也就是從法國共產黨黨員轉而進入一段政治沉寂的時期,接著是一段熱血沸騰並且極為好鬥的左派時期,然後再轉為對於人權的關注。此外,這套架構也沒有把傅柯職業生涯裡那段重要的文學階段納入考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傅柯在荷蘭的電視上和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之前,本來應該先播出一段介紹傅柯的短片,但他斷然拒絕提供一切傳記資訊,於是那部短片也就沒有拍成。然而,他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卻明白指出:「就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向來都希望自己的書是一部自傳當中的片段。我的書所探討的向來都是我自己的個人問題,包括在瘋狂、監獄以及性方面。」一年後,他又在佛蒙特以更強烈的語氣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個人傳記的一部分。」若說傅柯著作的歷史在相當程度上即是他的傳記,就某個層面上而言幾乎可說是不言而喻。也就是說,他的傳記是一項思想的故事,是一部書寫中的作品。在這類陳述當中,傅柯似乎暗示了作者與文本之間某種更深層的關係。在針對他最喜歡的一位作者所從事的討論當中,他說得稍微比較直白,甚至也可以被視為是為他自己的傳記提供了一項公式。他針對胡瑟勒(Raymond Roussel)這位小說家暨詩人指出:
身為作家的人,撰寫以及出版書籍並不只是在從事工作而已……他的主要作品終究是寫書過程中的自己。一名個人的私人生活、性偏好以及著作都互有關聯,不是因為他的著作翻譯了他的性生活,而是因為那部著作不只包含文本,也包含了整個人生。那部著作不僅只是那部著作,從事書寫的那名主體也是著作的一部分。
傅柯極少詳細談論自己的人生,尤其是他早年的人生。在一九八三年一場異常私密的訪談當中,他在結尾說道:
無論如何,我的私人生活一點都不有趣。如果有人認為不參照我人生中的某個部分,就沒辦法瞭解我的著作,那麼我願意考慮這個問題。﹝笑﹞我已經準備好在我同意的情況下回答這種問題。由於我的私人生活並不有趣,所以也就不值得保密。﹝笑﹞同理來說,可能也不值得張揚。
這種吊人胃口的語氣帶有一股強烈的自戀色彩,這點不需要受過精神分析訓練也看得出來;但這不是他一向的表現。更為典型的是他在《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一個著名段落裡所呈現出來的那種防衛性攻擊態度。一名想像中的對話者埋怨道:「你是不是又要說你從來都不是別人所指責的那種人?你已經在準備脫身的藉口,以便在下一本書從別的地方冒出來,而像現在這樣嘲笑我們:『沒有,沒有,我不在你們埋伏等待著我的地方,而是在那邊,笑著你們。』」傅柯回應指出:「我無疑不是唯一一個為了隱藏面貌而寫作的人。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叫我保持不變:那是état civil所遵循的倫理;那個機構管理我們的身分文件,但在寫作方面,那個機構也許會讓我們自由行事。」所謂的「état civil」,是法國相當於戶政總署的機構。在其他地方,傅柯稱之為「那個把個人存在轉變為一種制度的古怪機構」,並且將其中的公務員描述為「法律的原始型態」,因為他們「把每一個人的出生都轉變為一份檔案」。
﹝……﹞
傅柯拒絕陳述自己的身分或是回顧自己的歷史,有時也會以頗為風趣的方式表達。他曾對卡魯索(Paolo Caruso)說:「要我描述令我達到當前這些地位的行程會有點困難,而且我有很充分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自己還沒抵達目的地。」另一名訪問者責怪他從不交代自己的背景或童年,結果他的回應是:「我親愛的朋友,哲學家不是誕生而來……他們存在,就是這樣。」這類機智妙語不是一種油滑的表現,而是表達了根深柢固的信念。如同傅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向佛蒙特的一名自由撰稿作家所說的:
我不覺得有必要知道我究竟是誰。人生與工作最主要的吸引人之處就是成為你原本不是的人。你如果剛動筆寫一本書,就知道自己最後會寫出哪些內容,那麼你認為你還會有勇氣寫下那本書嗎?寫作與愛情關係都是如此,而人生也是一樣。這場遊戲之所以值得參與其中,原因就是我們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
「為了隱藏面貌而寫作」是他聲稱自己懷有的抱負,但他卻是個有許多面貌的人,而且他的人生也有許多深切區隔開來的不同面向。如果真有人能夠認識傅柯的所有不同面向,那麼這樣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傅柯去世之後,與他相伴超過二十年的丹尼爾.德費(Daniel Defert)才訝異地發現自己的伴侶向冰川街(rue de la Glacière)的道明會捐贈了大筆金錢,答謝他們在索爾舒爾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Saulchoir)對他的接待。傅柯也從不讓家人與朋友互相認識。他對於自己人生中的不同面向區隔得極為徹底,因而有些男性友人都真心誤以為自己在某一段時間是他「唯一的異性戀朋友」。以男性為主的許多人,都談及傅柯對於女性的深切厭惡;然而,在不同時期與他密切合作過的女性,包括凱特琳.馮畢羅(Catherine von Bülow)、艾蓮.西蘇(Hélène Cixous)與阿蕾特.法居(Arlette Farge),卻否認這項指控。
對於傅柯的主觀印象,實在是多樣得令人眼花撩亂。他有充滿誘惑力的一面,而且就像拉岡一樣,能夠讓他當下的對話者以為自己和他具有勝過別人的緊密關係。對於那些無心之間針對他的著作向他提問的人,他也有可能表現出刻薄而且凶暴輕蔑的態度。他接待賓客有可能非常大方,毫不吝惜自己的威士忌,儘管他本身很少喝。他的大方也有可能同時結合了怠慢客人的行為。一九七○年代晚期,一群年輕的德國「自治論者」來到他的公寓拜訪他,傅柯熱情接待他們,聆聽他們的發言,也和他們開玩笑,同時不斷撫摸他的貓。他為他們準備了餐點,然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表示自己不和他們一同進餐,因為他還有些關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牛奶配額的重要工作要做。受到傅柯邀請加入這場聚會的迪斯蒲(Laurent Dispot),這時候才頗不自在地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場的功能是為了扮演代理東道主的角色。許多人見到的傅柯,都是充滿魅力又熱情親切;但在一九六○年代初期的一場晚宴上,精神分析學家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見到的傅柯卻以近乎殘酷的諷刺話語駁斥另一名來賓的論點。同樣是精神分析學家的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在學生時期首度結識傅柯,他提出了一項近乎完美的折衷式評語,指稱傅柯為人「疏離而熱情」。有些人只認識身為法蘭西公學院教授的傅柯;有些人認識(或者聲稱自己認識)的,則是身穿黑色皮衣、上面裝飾著鏈子,會從他在沃吉哈赫街(rue de Vaugirard)的公寓溜出去找尋陌生人性交的傅柯。巴黎金滴區(Goutte d’Or)的外來移民人口認識的傅柯,則是一名為了對抗種族歧視而不惜遭受警察逮捕以及毆打的白人知識分子,儘管有些人以為他是沙特。
﹝……﹞
目次
致謝
引言:「我,米歇爾.傅柯……」
1. 保羅米歇爾
2. 狐狸、高師、共產黨
3. 穆斯特林根的嘉年華會
4. 北方
5. 瘋狂的歷史
6. 死亡與迷宮
7. 詞與物
8. 南方
9. 凡森大學
10. 「一個思想自由的地方」
11. 「不可容忍」
12. 激進教授
13. 痛苦檔案
14. 快感的運用
15. 異議分子
16. 死神之舞展開
17. 波蘭自由明亮而頑強的光輝
18. 未完成的人生
新版後記:死後的生命/史都華.艾登Stuart Elden
注釋
書目
其他參考著作
書摘/試閱
摘錄自〈6 死亡與迷宮〉
﹝……﹞
這時候,傅柯與德費已經在芳雷醫師街同居,決定共度終生。這項決定不表示雙方必須對彼此忠貞,但確實建立了一段延續至傅柯於一九八四年去世為止的關係。整體而言,這是一項頗為放鬆的夥伴關係,德費也指稱傅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相處。不過,他們確實遭遇了一些社交方面的困難以及一定程度的歧視。他們同居一事在他們的圈子裡不是祕密,但一九六三年的法國社會,尤其是法國學術界,對於同性伴侶的觀感並不是特別正面。
與丹尼爾.德費的關係對傅柯的人生造成重大變化,原因是這項關係導致他與巴特的疏遠。關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至少流傳有三個不同版本。索萊爾斯指稱巴特與傅柯爭風吃醋,其他人則是說巴特、傅柯與尚保羅.艾宏一起去丹吉爾(Tangier)度假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傅柯一再抱怨自己沒有收到德費的消息,而他終於收到一封信之後,對於巴特挖苦他的一句話反應非常激烈。根據德費的說法,是因為他占據了傅柯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工作的壓力,所以才造成傅柯與巴特疏遠,他也否認傅柯與巴特之間有過任何嚴重爭吵。到了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德費在準備教師資格考,傅柯已經開始撰寫《詞與物》。他們兩人經常忙到凌晨,所以傅柯只得放棄每週與巴特共進晚餐三次的習慣。他們的友情因此大幅降溫,但沒有突然中斷。直到一九七○年代初期,他們的友誼才終於因為政治上的歧見而畫下句點。
德費的出現也對傅柯的文本造成了輕微影響。《瘋狂史》的節略版在一九六四年推出之時,原本題獻給艾瑞克米歇爾.尼爾森的文字消失不見,而且也沒有再出現在後續的其他版本當中。這項新關係甚至抹除了先前這段友誼的痕跡。現在,德費成為傅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自此以後都是如此。他們兩人都有其他許多或多或少逢場作戲的性對象,傅柯身邊也經常環繞著一群仰慕他的年輕男子。傅柯從來不曾在他出版的作品當中公開提及德費,但倒是曾在一九八二年與德國電影導演雪洛特(Werner Schroeter)的對談裡描述了這項關係的重要性:
過去十八年來,我一直活在對一個人懷有熱情的狀態下。那道熱情也許在某個時刻展現為愛的型態。實際上,我們之間處於一種熱情的狀態,一種恆久的狀態……我完全投入於其中……我相信這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完全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止我回家找他,和他說話。123
他對德費的愛也許沒有立即造成他與巴特徹底斷絕關係,但確實導致傅柯無法實現過往的一項抱負。自從他離開漢堡之後,就一直著迷於前往日本的想法,甚至還有在那裡定居下來的念頭。這項著迷至少有一部分是一種觀點的表現,認為東方是西方理性的極限之一。如同他在《瘋狂史》的原始序言當中所寫的:
東方被視為起源,被夢想為產生懷舊之情與回歸之承諾的那個令人頭昏眼花的點……是起始的夜,西方形成於其中,但其中又有一條分界線。對於西方而言,東方就是西方所不是的一切,儘管西方必須到那裡找尋其原始的真理。這項分界在西方漫長演化過程中的歷史應該受到書寫,以其連續性與交換受到追溯,但也必須獲准以其悲劇性的莊嚴姿態出現。
前往日本的衝動來自於龐格提出的一項建議。一九六三年,東京的法國藝文協會(Institut Culturel Français)的主任職務出缺。由於傅柯在瑞典、波蘭與德國有豐富經驗,因此是充分合格的人選,他也對此相當熱衷,部分原因是他對於在克雷蒙費弘工作愈來愈感到不滿。他與葛侯迪的爭吵向來都是一件惱人的事情,傅柯也對自己在沒有什麼祕書人力可以支援的情況下必須負擔的行政工作感到厭煩。此外,他仍然不認為在大學教書是他真正的志業。日本看起來似乎是個相當吸引人的替代選項。
不過,他面對了兩項障礙。第一是傅柯的院長不願失去他,尤其是大學裡的應用心理學院只有他一個人有能力能夠加以重整。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日寫給教育部長的一封正式信件裡,那名院長寫道:
在當前的情況下,傅柯先生一旦離去,將導致我們的全體教職人員嚴重失衡。我們在下個學年不但無法找到替代他的人選,而且克雷蒙的哲學組正處於危急狀態……所以主任明年必定要在職……鑒於這些情況,我因此決定極力敦促傅柯先生婉拒他所收到的邀請。他已接受了我向他提出的論點,而我也對他這樣的無私表現深懷感激。
傅柯的無私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客套,而不是真正改變了心意。他不是一個會甘於接受學術權威過度操弄的人,所以很有可能是為了拖延時間而請這位院長寫信給部長。導致他無法離開的第二項障礙,當然就是他與丹尼爾.德費的感情。傅柯不願拋下自己的新伴侶,甚至提議德費和他一起到日本去,轉換跑道攻讀日本研究。德費對現代日本社會的發展毫無概念,因此認為自己去日本只能研究扇子與陶瓷,然而這樣的前景對他而言實在沒有什麼吸引力。除此之外,還有他的教師資格考;一旦去了東京,他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學業,也等於是放棄一切學術生涯的希望。最後,他做出了犧牲自己的資格考這項困難的決定。在此同時,法國外交部則要求傅柯必須立刻做出決定;總理龐畢度即將前往日本進行正式訪問,屆時法國藝文協會絕對不能沒有主任。先前曾以大學方面的阻礙為由搪塞外交部的傅柯,終於提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已經決定為了德費的資格考而犧牲到日本居住的樂趣。這一整齣誤會是在他們兩人沒有任何公開討論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結果。於是,德費暗中下定決心,他要寫出一部重大的智識著作來回報傅柯的犧牲。這個目標終究沒有實現,傅柯也從來不知道他的伴侶在心底藏有這項未能達成的抱負。
德費在一九六四年夏季成功通過教師資格考,接著就必須立即入伍服十八個月的兵役。由於他曾參與反戰運動,也曾擔任代表出席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反殖民委員會,因此對軍隊的觀感極為負面,也不願服役當兵。他不像傅柯那樣有個能夠對軍隊的醫療小組發揮影響力的父親,但卻有另外一個選項,而此一選項就顯示了教育在公然菁英主義的體制裡能夠為人帶來的好處。不久之前剛成立的公民合作部(Service civil de coopération)所訂立的條款,可讓符合資格的年輕男子到開發中國家服務以取代兵役(那些國家通常是法國的前殖民地,但不以此為限)。德費原本的計畫是要去越南,但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的東京灣事件與美軍在後續對北越展開的攻擊,導致這項計畫變得充滿危險,於是他改而接受突尼西亞的一項教職。因此,他就在斯法克斯(Sfax)這座位於加貝斯灣(Gulf of Gabès)的南部城市教導哲學而度過役期。傅柯經常前去探望他,他們兩人也在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的聖誕假期一同在突尼西亞四處旅遊。
﹝……﹞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