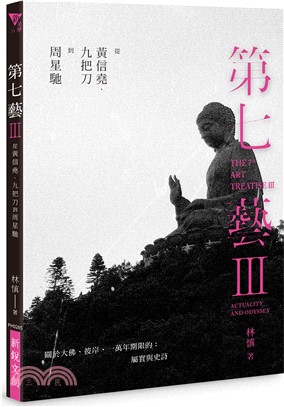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二十世紀下半葉,大都會與電影史邁進五光十色的迷幻年代。觀影四海皆見,林慎卻審視港台金獎電影,發展出具意象的原創文化主體論述──有別一般影評,此書和觀賞的對象一樣,自成可獨立看待的作品。
今冊以台灣和香港為雙主角。林慎以紀錄片與電影中間的缺口推論出「幻幕」的原創思想概念,去探索光影世界的虛實縫隙。以此為濾鏡觀之,一地電影的意義有待在地詮釋,而華語電影中的「彼岸」喻體亦變得實在。從周星馳的月光寶盒到九把刀的月老,「一萬年」之嘆透射出同月異彩。
古希臘七藝是現代人文基礎,而「電影」則是義大利理論作家Ricciotto Canudo所稱之「第七藝」。林慎自其第七部長篇作品《第七藝I》開始影論的書寫,藉由論理論影穿透迷霧,直視文化的靈光。
「《第七藝III》採後現代史學的懷疑主義,寓思於影。除了辨析電影銀幕上的虛實和導演的光影技藝,也展演了類狐狸型學者的駁雜多變。從《大佛普拉斯》到《月老》,再過渡到《大話西遊》,在夾議夾敘的文字鋪衍中,嗅聞觀影大眾嬉笑背後的情感結構和集體意識,既綴起港台幽微的關係紐帶,亦向相信愛情與永恆的青春韶華致意。」──林姵吟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院主任)
「林慎博士的《第七藝III》以跨學科的視野,結合哲學與電影,由香港到台灣,從九把刀到周星馳,貫穿東西、南北,不但為港台文化開闢了一條使跨界對話得以進行的渠道,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閱讀體驗。」──趙傑鋒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者)
----
劍橋博士級作家林慎的《第七藝》系列作相繼聚焦港台電影和社會文化,獲兩地的《金都》導演黃綺琳、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鄭政恆、影視教授劉永晧、《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作者陳光興教授、傳播學教授馮建三、港大中文學院主任林姵吟、電影研究者趙傑鋒博士等多個界別代表推薦,將陸續推出!
今冊以台灣和香港為雙主角。林慎以紀錄片與電影中間的缺口推論出「幻幕」的原創思想概念,去探索光影世界的虛實縫隙。以此為濾鏡觀之,一地電影的意義有待在地詮釋,而華語電影中的「彼岸」喻體亦變得實在。從周星馳的月光寶盒到九把刀的月老,「一萬年」之嘆透射出同月異彩。
古希臘七藝是現代人文基礎,而「電影」則是義大利理論作家Ricciotto Canudo所稱之「第七藝」。林慎自其第七部長篇作品《第七藝I》開始影論的書寫,藉由論理論影穿透迷霧,直視文化的靈光。
「《第七藝III》採後現代史學的懷疑主義,寓思於影。除了辨析電影銀幕上的虛實和導演的光影技藝,也展演了類狐狸型學者的駁雜多變。從《大佛普拉斯》到《月老》,再過渡到《大話西遊》,在夾議夾敘的文字鋪衍中,嗅聞觀影大眾嬉笑背後的情感結構和集體意識,既綴起港台幽微的關係紐帶,亦向相信愛情與永恆的青春韶華致意。」──林姵吟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院主任)
「林慎博士的《第七藝III》以跨學科的視野,結合哲學與電影,由香港到台灣,從九把刀到周星馳,貫穿東西、南北,不但為港台文化開闢了一條使跨界對話得以進行的渠道,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閱讀體驗。」──趙傑鋒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者)
----
劍橋博士級作家林慎的《第七藝》系列作相繼聚焦港台電影和社會文化,獲兩地的《金都》導演黃綺琳、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鄭政恆、影視教授劉永晧、《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作者陳光興教授、傳播學教授馮建三、港大中文學院主任林姵吟、電影研究者趙傑鋒博士等多個界別代表推薦,將陸續推出!
作者簡介
林慎是一名旅歐香港作家、理論犯罪學家、思想家、小說家。他生於香港,在劍橋大學法律學院博士畢業,歷任同校訪問學人、港大名譽研究員等。他的學說橫跨文史哲、社會學、美學等領域,提倡發展原生思想並提出「正統遊戲」、「偽真品」、「繁我」等原創概念,備受兩岸學院內外推薦。洪流中棄理從文,以著書立說為志業。
誠品、序言書室、博客來暢銷作家,著有《警國論》、《警教論》、《鑑藝論I》和《鑑藝論II》、影論《第七藝I》和《第七藝II》、小說《巴別人》、散文集《小離敍》。
聯絡:sanlam.secretarial@gmail.com
San Lam, PhD (Cambridge), is a contemporary thinker and best-selling author of Policier Treatises, Connoisseur Treatises, The 7th Art Treatises, and Babelians (novel). He looks at modern social ethos and introduces original ideas across sociolog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such as Legitimist Game and the Missensicals. Former HKU honorary fellow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誠品、序言書室、博客來暢銷作家,著有《警國論》、《警教論》、《鑑藝論I》和《鑑藝論II》、影論《第七藝I》和《第七藝II》、小說《巴別人》、散文集《小離敍》。
聯絡:sanlam.secretarial@gmail.com
San Lam, PhD (Cambridge), is a contemporary thinker and best-selling author of Policier Treatises, Connoisseur Treatises, The 7th Art Treatises, and Babelians (novel). He looks at modern social ethos and introduces original ideas across sociology,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such as Legitimist Game and the Missensicals. Former HKU honorary fellow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visiting scholar.
序
〈推薦語〉
「文化主體是近年來港、台人文社會研究的重要課題。《第七藝III》採後現代史學的懷疑主義,寓思於影。除了辨析電影銀幕上的虛實和導演的光影技藝,也展演了類狐狸型學者的駁雜多變。從《大佛普拉斯》到《月老》,再過渡到《大話西遊》,在夾議夾敘的文字鋪衍中,嗅聞觀影大眾嬉笑背後的情感結構和集體意識,既綴起港台幽微的關係紐帶,亦向相信愛情與永恆的青春韶華致意。」──林姵吟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院主任)
「林慎博士的《第七藝III》以跨學科的視野,結合哲學與電影,由香港到台灣,從九把刀到周星馳,貫穿東西、南北,不但為港台文化開闢了一條使跨界對話得以進行的渠道,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閱讀體驗。」──趙傑鋒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者)
〈前言〉
「在底片帶上有一幅此刻的影像也有過去和將來的諸多影像,但在螢幕上只有此刻的那一幅。
如果時間指的是改變的可能性,我們便不可以說『時間流逝』。它看上去就好比說,記憶是對於本來清晰地放在眼前的事物的一幅眩淡影像……舉例說『光學幻覺』,這用詞使人以為那是錯誤,即使根本沒有錯。」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
台灣深藏美麗島魂。上一冊以具象的「亞地靈」來描述這種難以說準、說清的精要,論及的《悲情城市》和《返校》都是十分沉重的電影。我從台灣學者陳光興的著作開始,以影論台,推展出帝國之眼的電影版本──索倫巨眼──和它的對應物,亦即前者推導出的湯姆.龐巴迪(Tom Bombadil)式猜想。我還特別探究了「詩與文清」,即《悲情城市》中梁朝偉一角和他的藝術家原型,也談到了《返校》這遊戲改編作的種種意涵。我不認為我的著作能夠完全說清楚這些佳作個中的奧妙,不過在瑕疵背後,至少不是毫無得著的。那也就是以電影來推展文化主體理論的思路。
台灣篇本來只是半頁大綱。寫著寫著,發現課題太大。也由於我不是本地人,對台灣的很多事物感到陌生又興奮,重頭考究起來,又都有新意。這注定是班門弄斧。港人跟台人同在華語世界,又隔了片海,說是絕對的他者或同者皆不盡然。這種「類同者」──姑且這樣說──的狀態或許有利拋磚引玉,帶來一點點新角度。今次討論的是比前著輕鬆一點的作品。輕鬆幽默不等如言之無物,細看之下更令人感到台灣這小島背負著不合比例的重量。希望諸君不吝指教。同時藉此機會感謝台灣出版社和編輯給予這系列得以連續免費出版的機會。跟這本書中論及的電影創作情況一樣,港台合作向來十分難得。
有關書名,再三考量下在英語名加上副題成為「The 7th Art Treatise III: Actuality and Odyssey」,對應的意思是《第七藝術論III:屬實與史詩》。至於中文書名用上人名,是因為華語讀者對這些電影人感到熟悉,我希望更多人因而接觸到這本嘗試加深文化內涵的讀物。除了接觸面,本也有寫作上的考量。讀過《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等經典,一直很希望有機會寫這種重量的著作。寫不到祈許之高度,至少門面上不要太失禮。
書名抽象,得體的代價是往往使人敬而遠之。我的第二本著作《警教論》(PT2)到最後階段有另一候選書名《警與教》。當時兼顧跟系列前作《警國論》的統一性才作罷,也避免過於抽象。繞了一個圈,終於有機會實現了。有趣的是,中英語名互有所指這做法在電影名字翻譯上十分常見。
概念上,「Actuality」是《第七藝I》原創「縱時性」(transience of actualities)的元件。而「Odyssey」乃古希臘荷馬所著的《奧德賽》,現在幾乎是傳說史詩的代名詞;劉鎮偉、周星馳的經典西遊系列英語名全用上西方世界熟悉的概念,月光寶盒變成「Pandora's Box」即潘朵拉的盒子,而電影名索性叫A Chinese Odyssey。除了呼應文本對象,我使用「屬實與史詩」上的另一重意思則分別見於這本書前半部分推論出屬實性,繼而在後半部分鑑讀兩大中國傳說人物史詩之旅的屬實之處。史詩寫傳說、傳奇人物的故事,而今冊就是從佛寫到月老再到孫悟空。我看這個書名頗能概括內容,也適合英語語境上的慣常用法。
在這一冊,我會承接上一冊的線索,調查台灣光影背後的文化主體,推論出「幻幕鏡」這原創概念。電影在華語中有電光影戲的語源意思,而西方亦有跟《聖經》相關的詞屏一說。我將會引伸這個概念,進行在地的知識建構,以此來看出虛構與屬實之間的分別。在討論了屬實性之後,佛教用語「彼岸」──一個象徵死亡與希望的圖騰──被抽取出來重點討論。此外亦會論及一些明顯虛構但屬實的後現代作品。此冊的主要文本為《大佛普拉斯》、《月老》和劉鎮偉、周星馳版本的《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編按:台灣片名為《齊天大聖東遊記》)和《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編按:台灣片名為《齊天大聖西遊記》)(下合稱《西遊》)。
現在就來撥開幻幕,揭開寶盒,開始第七藝術第三次光影之旅──
電影論.著台港。
「文化主體是近年來港、台人文社會研究的重要課題。《第七藝III》採後現代史學的懷疑主義,寓思於影。除了辨析電影銀幕上的虛實和導演的光影技藝,也展演了類狐狸型學者的駁雜多變。從《大佛普拉斯》到《月老》,再過渡到《大話西遊》,在夾議夾敘的文字鋪衍中,嗅聞觀影大眾嬉笑背後的情感結構和集體意識,既綴起港台幽微的關係紐帶,亦向相信愛情與永恆的青春韶華致意。」──林姵吟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院主任)
「林慎博士的《第七藝III》以跨學科的視野,結合哲學與電影,由香港到台灣,從九把刀到周星馳,貫穿東西、南北,不但為港台文化開闢了一條使跨界對話得以進行的渠道,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彩的閱讀體驗。」──趙傑鋒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者)
〈前言〉
「在底片帶上有一幅此刻的影像也有過去和將來的諸多影像,但在螢幕上只有此刻的那一幅。
如果時間指的是改變的可能性,我們便不可以說『時間流逝』。它看上去就好比說,記憶是對於本來清晰地放在眼前的事物的一幅眩淡影像……舉例說『光學幻覺』,這用詞使人以為那是錯誤,即使根本沒有錯。」
──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
台灣深藏美麗島魂。上一冊以具象的「亞地靈」來描述這種難以說準、說清的精要,論及的《悲情城市》和《返校》都是十分沉重的電影。我從台灣學者陳光興的著作開始,以影論台,推展出帝國之眼的電影版本──索倫巨眼──和它的對應物,亦即前者推導出的湯姆.龐巴迪(Tom Bombadil)式猜想。我還特別探究了「詩與文清」,即《悲情城市》中梁朝偉一角和他的藝術家原型,也談到了《返校》這遊戲改編作的種種意涵。我不認為我的著作能夠完全說清楚這些佳作個中的奧妙,不過在瑕疵背後,至少不是毫無得著的。那也就是以電影來推展文化主體理論的思路。
台灣篇本來只是半頁大綱。寫著寫著,發現課題太大。也由於我不是本地人,對台灣的很多事物感到陌生又興奮,重頭考究起來,又都有新意。這注定是班門弄斧。港人跟台人同在華語世界,又隔了片海,說是絕對的他者或同者皆不盡然。這種「類同者」──姑且這樣說──的狀態或許有利拋磚引玉,帶來一點點新角度。今次討論的是比前著輕鬆一點的作品。輕鬆幽默不等如言之無物,細看之下更令人感到台灣這小島背負著不合比例的重量。希望諸君不吝指教。同時藉此機會感謝台灣出版社和編輯給予這系列得以連續免費出版的機會。跟這本書中論及的電影創作情況一樣,港台合作向來十分難得。
有關書名,再三考量下在英語名加上副題成為「The 7th Art Treatise III: Actuality and Odyssey」,對應的意思是《第七藝術論III:屬實與史詩》。至於中文書名用上人名,是因為華語讀者對這些電影人感到熟悉,我希望更多人因而接觸到這本嘗試加深文化內涵的讀物。除了接觸面,本也有寫作上的考量。讀過《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等經典,一直很希望有機會寫這種重量的著作。寫不到祈許之高度,至少門面上不要太失禮。
書名抽象,得體的代價是往往使人敬而遠之。我的第二本著作《警教論》(PT2)到最後階段有另一候選書名《警與教》。當時兼顧跟系列前作《警國論》的統一性才作罷,也避免過於抽象。繞了一個圈,終於有機會實現了。有趣的是,中英語名互有所指這做法在電影名字翻譯上十分常見。
概念上,「Actuality」是《第七藝I》原創「縱時性」(transience of actualities)的元件。而「Odyssey」乃古希臘荷馬所著的《奧德賽》,現在幾乎是傳說史詩的代名詞;劉鎮偉、周星馳的經典西遊系列英語名全用上西方世界熟悉的概念,月光寶盒變成「Pandora's Box」即潘朵拉的盒子,而電影名索性叫A Chinese Odyssey。除了呼應文本對象,我使用「屬實與史詩」上的另一重意思則分別見於這本書前半部分推論出屬實性,繼而在後半部分鑑讀兩大中國傳說人物史詩之旅的屬實之處。史詩寫傳說、傳奇人物的故事,而今冊就是從佛寫到月老再到孫悟空。我看這個書名頗能概括內容,也適合英語語境上的慣常用法。
在這一冊,我會承接上一冊的線索,調查台灣光影背後的文化主體,推論出「幻幕鏡」這原創概念。電影在華語中有電光影戲的語源意思,而西方亦有跟《聖經》相關的詞屏一說。我將會引伸這個概念,進行在地的知識建構,以此來看出虛構與屬實之間的分別。在討論了屬實性之後,佛教用語「彼岸」──一個象徵死亡與希望的圖騰──被抽取出來重點討論。此外亦會論及一些明顯虛構但屬實的後現代作品。此冊的主要文本為《大佛普拉斯》、《月老》和劉鎮偉、周星馳版本的《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編按:台灣片名為《齊天大聖東遊記》)和《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編按:台灣片名為《齊天大聖西遊記》)(下合稱《西遊》)。
現在就來撥開幻幕,揭開寶盒,開始第七藝術第三次光影之旅──
電影論.著台港。
目次
推薦語/林姵吟、趙傑鋒
前 言
【第一章 幻幕鏡 GLAMOUR SCREEN】
第一節
上帝措詞
續《第七藝(I)、(II)》
第二節
透光門縫
《大佛普拉斯》黃信堯
【第二章 一萬年 GLANCE】
第三節(上)
彼岸執念
《月老》 九把刀電影/小說
第三節(下)
「日出西方」
關係式文化主體
【第三章 塵世間 GRIEVANCE】
第四節
不變承諾
繁我與新我
第五節
月老.月光
對讀《西遊記》劉鎮偉導、周星馳主演
後語
ABSTRACT(英文摘要)
參考文獻
前 言
【第一章 幻幕鏡 GLAMOUR SCREEN】
第一節
上帝措詞
續《第七藝(I)、(II)》
第二節
透光門縫
《大佛普拉斯》黃信堯
【第二章 一萬年 GLANCE】
第三節(上)
彼岸執念
《月老》 九把刀電影/小說
第三節(下)
「日出西方」
關係式文化主體
【第三章 塵世間 GRIEVANCE】
第四節
不變承諾
繁我與新我
第五節
月老.月光
對讀《西遊記》劉鎮偉導、周星馳主演
後語
ABSTRACT(英文摘要)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幻幕鏡 GLAMOUR SCREEN〉(節選)
例子一:大佛
伯克說的「具事實性」,或者王汎森說的包含敘述與評判的「雙元論證」,我認為都指向了一個了解電影的方向,也能回答較早前有關電影與紀錄片之別的問題。這種性質,姑且先併合成雙元事實性,是具有兩個基本面向的。一個是現實,我們看得到,感受得到,活在其中;另一個是經過濾鏡的東西,那也是具事實性的,卻又是有待詮釋的。我們甚至可以將維根斯坦的「可堪深邃思考性」(intelligibility)放在一起思考,所謂的「紀錄和詮釋」不是一種描述事實的狀態,更多是要放著一己主張才稱得上是詮釋。即使退一百步,少談詮釋,多談紀錄,根據早前羅志平扼要的說明,也是「取決於攝影師或剪輯師,最終則是製作人意志的展現」。
我想用一個例子更具體地說明此處的差異。導演黃信堯的作品,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下稱《大佛》)曾奪得台灣金馬獎的最佳新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原著」是黃信堯的短片作品),台北電影獎的百萬首獎和最佳劇情長片獎,更榮獲當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兩岸華語電影。黃信堯其實不是新導演,只是他拍紀錄片居多。最佳新導演獎項分類卻可看出紀錄片和電影的分類困難。
一般在資本市場的邏輯下,觀眾須首先掌握電影的基本性質,才能被吸引購票入場。如果不看預告片而單憑文字,如此一來有可能掉進只有伯克說的「科學家式」或維根斯坦的「語言」式陷阱。我想把這個明顯的標籤也塗抹掉。
舉例說,現在是有朋友邀請,你事先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麼電影,不過你聽說過黃信堯,知道他拍過很多紀錄片,亦有得過獎。你首先聽到的是一段台語獨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這部電影是由華文創和甜蜜生活聯合提供,由業界最專業的甜蜜生活來製作。﹝基於電影是如此籠統的說法,你不以為然。﹞我們邀請業界最難相處的葉女士和鍾先生來擔任監製。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啊。在電影的放映過程當中,我會三不五時﹝閩南語,指時常﹞出來講幾句話,宣傳一下個人的理念,順便解釋劇情。請大家慢慢看。就先不打擾。需要的時候我才再出來。
這種紀錄片旁白的方式不讓你感覺陌生,不管是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還是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影片,你接觸過很多次。接著你發現聽著獨白時的背景音樂,原來是接下來畫面中的樂手所奏的。一群人看來穿著不太整齊的制服,後面有一輛靈車。似乎是有人去世了。鏡頭是黑白的。你分不清這是不是紀錄片導演新片的劇情。他們在雜草中前行,旁邊有一個湖。畫面是淡定和寫實的。你清楚這不是那種充滿電腦特效或者《魔戒》一樣的一眼便知虛構的電影,也知道這不是仿真的歷史紀錄片。片中人繼續打著鼓,吹奏樂器,表現得不專業。你開始懷疑獨白所說的「業界最專業」是導演的玩笑。再接著你看著放滿雜物的小車在顛簸中前進的畫面。畫面沒有商業片常有的流線型拍攝手法,你不知道這是拍攝還是紀錄──還是兩者很多時候是同一回事(「film」除了電影也有紀錄片、底片的意思)。《大佛》中充滿這些生活小節的鏡頭,有在馬路的,有在垃圾場的、醫院的、爛地的,鏡頭就在一定距離中拍攝,沒有特別介入,也沒有渲染。
你斷不會突兀地說:「發生的事就像電影一樣。」
一直去到第五分鐘,你看到一尊大佛,它的頭被凌空吊著,背後有煙霧。你聯想起這有點像以往年代的武俠片,運功療傷或者進入異境的場面。大佛的頭部空間中鑽出了一個工人,他們正組裝大佛。你記得導演開場時諷刺監製是「業界最難相處」的人,你以為只是一個令觀眾入戲的玩笑,還以為自己聽錯。他第二次介入時說:
這個工廠大家都很關懷對方的老母。那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作者按:你想起一部戲謔如來佛祖的周星馳電影,「我只不過想研究一下人與人之間的一些微妙的感情」,見第五節。﹞菜脯白天的工作都是兼差的。正式的工作是在這當夜班警衛。他會順便在大家下班前把工廠打掃一下。
接著大佛被打響,產生了強烈聲音共鳴。自開場的送葬場面後就沒有過音樂,此時背後徐徐響起挑情一般的電吉他撥弦聲,然後在音樂襯托,你看到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正摸一位女士的屁股,一行數人走進工廠,有人問:「佛頭怎麼會這樣?」導演接著介紹劇情說:
在前面大小聲的,是工廠的老闆啟文。﹝作者按:你看到他的手摸竟然向女士的臀部中間,心想這太過分吧……﹞在後面摸屁股的,是高委員和他的助理瓦樂莉。雖然高委員的戲分不多,但是他奮鬥的過程值得我們來介紹……自從瓦樂莉來了之後,高委員的紅木桌就突然多了一片木板,主要是方便瓦樂莉辦公……
你開始肯定這電影的格調,充滿「幹話」。你開始聞到電影的性質。此影片充滿了對現實的描述,這種擁權且好色的政客形象幾乎是一種常見定型。說真正感受到戲劇性,可能要到你後來看著大佛藏屍,被震驚到的一刻為止。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電影中的虛實性。它是「拍出來」而不是用特技「畫出來」的,即使如此有時我們也未必能馬上意識到其事實性,到底是紀錄片的一種,還是電影的一種。
〈第二章 一萬年 GLANCE〉(節選)
解脫「彼岸執念」?
在台灣的形勢中,除了上節說的「現實彼岸」,還真有一個大家想移民去的「西方極樂世界」彼岸;在地圖中,它卻不在西方而在東方,正是橫跨了整個太平洋的美國。本來以為香港的中西夾縫已經算是奇特,但在權力更迭上,至少香港的西方古國離場,東方古國進場。縱處在切換期,但更迭是可辨識的。台灣發生的則是以往《亞細亞的孤兒》時代,台灣主體在中、日、自身中打轉。到了《月老》的時代,日本退場,仍有餘音,但具體的力量影響上,「外人」由日本變成了地理東方,文化西方的另一彼岸。
台灣的主體概念一部分由自己定奪,不須他人多言;另一方面作為島嶼──又或者說作為現今全球化下地緣結構的一員──它有以關係來界定的部分,也就是常說的國際形象或者國際關係定位。當中最顯著的力量就是設有太平洋艦隊的美國,也是二戰後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這方面的法律表現。當中2.2.2、2.2.3及2.2.6條目如下:
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美國在台協會1979)
美國一方面將台灣納入其保護傘內,另一方面其正式建交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勢有點複雜。對現時的探討尤其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超級大國尚且以這樣的形式來建立對台關係,其他國家只會更小心翼翼。台灣近年便持續有邦交國斷交的新聞,曾被形容為可能發生「雪崩式斷交」,不少民眾卻認為「沒差」、「無感」。(鏡媒體2017)2021年,尼加拉瓜成為蔡英文任內第八個斷交的國家,使邦交國數目跌至十四個。(聯合新聞網2021)2023年3月宏都拉斯與台灣斷交,邦交國數量跌至十三個。(BBC 2022)在這樣的現實政治困局下,確有聲音指出從「彼岸執念」中解脫方為上計。曾任職於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國防分析者的葛羅斯曼(Derek Grossman)表達了「與常識相悖的建議」:
台灣應考慮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從這場毫無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中解脫,進而將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深化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連結,藉此削弱中國對台灣的打壓……除了台灣在歐洲唯一的友邦梵蒂岡之外,其餘友邦多是又窮又小、地緣戰略價值極低的國家。(陳艾伶2021)
葛羅斯曼的說法不無道理,同時又帶著風險。不論是否要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要從目前這懸而未解的處境中解脫,確是有保持冷靜頭腦和破除執念的必要。美國這個西方彼岸早在1979年跟中方建交,雖說比英國、法國更晚,卻有國際上定調的影響,使台灣進入了八十年代以降的外交處境。上一冊援引了竹內好、陳光興等人的思想,我們知道在後殖民主義的格局,亞洲要脫離西方自立主體,其實有解開西方不在地的束縛以尋找在地資源的必要,不能不加思索地執著在台建立「另一個西方」。
台灣要解脫的西方彼岸,確是看起來「一片光明」,卻又相距「幾千、幾萬年」之遙。
歷史上美國對台灣彼岸的實際影響
美國在戰後世界的強大勢力也名副其實地阻止台灣「到達彼岸」。在六十年代時,中國大陸正經歷嚴重動盪,蔣經國曾言:「這是(國民政府)十八年以來,最重要的關頭,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林琮盛2013)計劃反攻,卻礙於海戰失利的近因,以及美國或因陷入越戰等國際形勢而不支持的遠因,胎死腹中:「因為國民政府此時已與美方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54年12月3日簽訂的國際條約),規定於台海上所進行的任何軍事行動都須先經過雙方的意見,一致了才能發動。而在當時美蘇兩強極端對峙的局勢下,反攻大陸非常有可能會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陳毅龍2019)
第三次大戰之說或有點偏離歷史實相,但陳毅龍有關中美條約的理解卻可以在其他更正式的文獻中找到答案,並且說明美方角色在台方計畫中的實然影響。國史館修纂處纂修葉惠芬指出:「在國際冷戰嚴峻情勢下,以彈丸之地的臺灣要完成登陸反攻準備,談何容易,反攻時程自然只得流於口號,一延再延。」蔣中正基於國際形勢無法妄進,一再要求修改計畫,可見其重視。而在計畫中,美國的角色不是輔助,而是必要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及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之後,國軍任何反攻行動都必須知會美國,甚至承諾不使用武力反攻的情況下制定的,如何突破美方限制,爭取其認同,甚至獲得援助,成為計畫必須考慮的重點。」(葉惠芬2016, p.149, 151)台灣前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限制其反攻意圖,後有中美建交後的《台灣關係法》,使台灣攻守都有美國的強大影子。
在正面反攻以外,蔣中正亦曾試圖說服美方利用韓戰和滇緬游擊隊進行反攻,並在日記中寄望「配合世界大勢,當待第三次大戰發動時反攻大陸」。(《蔣介石日記》,1953年5月3日,見於ibid, p.153)然而今時今日我們都知道事態的發展。尤幸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否則會生靈塗炭。蔣中正想等的時機,等到他離世還是等不到。
美夢初期多是空想。不過在美夢成真之前,這些極端的想法在責人之前首先責己,先便將台灣化成一個怨靈之地,也是遠至解禁初期的《悲情城市》至近年的《返校》一脈的白色恐怖歷史教訓。
念著彼岸,執著異己,在達陣之前天堂已經沉沒。
〈第三章 塵世間 GRIEVANCE〉(節選)
拍成《西遊》的九十年代背景
《西遊》上、下放映於1995年。當時香港社會正面對兩年後的主權移交,跟以往和接下來我們知道的將來一樣,香港「又一次」「史無前例」地面對移民潮。(後來我們都知道,香港的移民潮基本上是數年一次的常態。)社會各界憂慮移交後的生活會否受影響,香港主體性飽受衝擊。在這個有限的時間內,劉鎮偉反其道而行大講「一萬年」。一萬年固然是修辭技巧,但一萬年終歸也是一個時限,跟香港當初被割讓九十九年一樣,也有其終結之時;同時一萬年又是近在咫尺的限期前無法想像的極長時間。中方許諾的「五十年不變」,卡在中間,不長也不短。
但人算不及天算,不變在塵世間是否可能?
王家衛作為一萬年不變的創作者,設計了在《重慶森林》中傳呼機密碼為「愛你一萬年」。這個愛情密碼卻是無用功的。金城武不斷跟通話員檢查留言信箱,也是不會有回音的。愛你一萬年純粹是一個泡影。他的前女友已經不再愛他,他還是渴望有轉機,到便利店買下特定日期的鳳梨罐頭,跟自己玩一個遊戲。他希望至少記住所有,「如果一定要加一個日子的話,我希望它是一萬年。」這一萬年注定是空話。在論述王家衛作品中的「不變」主題時,我便有過以下觀察:
《花樣年華》面對的是含蓄的情感,包括被出賣的情緒和蠢蠢欲動的報復心,《2046》面對的卻多了一條不變的參考線。可是這世界有什麼是不會變的?又有誰能隨心所願地承諾不變便就不變?以不變,見萬變,來來回回地在回憶沼澤中掙扎。(AT1, p.32)
許心儀也有類似的觀察:「跳躍的時空使歷史失去意義,影響了主角建構回憶及建立身分,沒有與他人共同對過去的理解而失落與人的關係。混亂的身分逼使至尊寶保持距離地看待過去,疏離於社會,與他人的關係如同後現代文化下不帶點情感將自己與世界分離。沒有過去,只能消費歷史。觀眾也是消費了電影和原著故事的歷史。回歸現實,《月光寶盒》和《仙履奇緣》利用角色混離的身分和時空的拼湊比喻香港人身分認同,以悲慘的劇情回應香港政治前途……」(2017)極其重要的一點,也是對後現代作品甚或電影本身的批評,就是沒有出路:
《西遊記》似乎只講出了悲觀的預言,卻沒有提供仙路指引。(ibid)
如此一來,幻幕鏡下,悲苦喜樂一掃而空,虛無至極。要求一部電影改變人生,給人指出具體路線,本來也是過分的期望。不過至少在拋出矛盾後,總要有點整理和己見,否則盡是虛無。在《悲情城市》中我們可以探出亞地靈;在《返校》中有其怨念版本,以及不為己的犧牲精神,叫後人不要忘記;在《卧虎藏龍》會感受到新派武俠哲學和天地間的非具象亞地靈。在《西遊》至《月老》一類電影,即使它們的價值是明顯的,也是打動很多人的,有時表面看來卻還是難以說起「意義」這回事。在這種後現代詮釋中,任人如齊天大聖大翻筋斗,天花龍鳳,很多人還是說不出什麼要旨可言。這樣偏執地想下去,人很難在看後得到生命的動力,更別談什麼道德課堂。
影評人登徒在〈西遊記:時不我予,悔不當初〉(1995)一文指出《西遊》有胡鬧、場口連接、特技粗糙的問題,勝在飽含情感、水銀瀉地、「直叫觀者動容……餘音梟裊」,最後「像極了孫悟空一場思凡的噩夢」。跟另一位影評人李焯桃(1995)認為《西遊》是「Bad Timing的悲情神話」一樣,他認為其悲痛緣由實在是時間錯誤,而一萬年台詞是對王家衛《東邪西毒》之超越。「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一段至尊寶的愛的宣言:『曾經有段至真的感情……一萬年』,在總結《東》中各人心中隱而未宣的鬱結與遺憾之餘,更帶出了妄想[重新嚟過(編按:粵語,指「從頭再來過」)]與感懷(愛情期限一萬年),緊扣主題而感情濃度層層遞升。戲中僅兩次引用,便帶出一喜一悲的極端效果。」他沒有說出這類型電影的功用,唯指出香港也是一座悲情城市,而大限之說確是時代中的共同課題。
台灣沒有大限,人所共知的是其前途的不確定性。九把刀在承繼周星馳的優點時,無疑也會碰到短處。但在這奇獨的情況下,所謂「後現代」也好,香港大限所致也好,不確定性符合了台灣的基調。而在轉化「一萬年」這概念時,他繼承了情感上的飽滿,並不意圖尋找藥方,點到即止,只為觀眾逃離現實,珍惜眼前人。九把刀也不無意外地繼承了劉鎮偉和周星馳創作中的香港處境意識投射,在雖存異但接近的文化和地緣政治脈絡中,「不變」和「彼岸」等傳統的華語圈共有概念得以有在地發展和延伸,更偶有加深(包括畫龍點睛地起用馬志翔演出原著小說中不存在的一角)。
台灣那無底的不變與有涯的變數,使香港面對大限時的情緒得以再一次以另一種方式詮釋出來。香港與台灣相隔七百公里之遙,建橋相連,本就是一種「有用之用」。
(……)
例子一:大佛
伯克說的「具事實性」,或者王汎森說的包含敘述與評判的「雙元論證」,我認為都指向了一個了解電影的方向,也能回答較早前有關電影與紀錄片之別的問題。這種性質,姑且先併合成雙元事實性,是具有兩個基本面向的。一個是現實,我們看得到,感受得到,活在其中;另一個是經過濾鏡的東西,那也是具事實性的,卻又是有待詮釋的。我們甚至可以將維根斯坦的「可堪深邃思考性」(intelligibility)放在一起思考,所謂的「紀錄和詮釋」不是一種描述事實的狀態,更多是要放著一己主張才稱得上是詮釋。即使退一百步,少談詮釋,多談紀錄,根據早前羅志平扼要的說明,也是「取決於攝影師或剪輯師,最終則是製作人意志的展現」。
我想用一個例子更具體地說明此處的差異。導演黃信堯的作品,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下稱《大佛》)曾奪得台灣金馬獎的最佳新導演、最佳改編劇本(「原著」是黃信堯的短片作品),台北電影獎的百萬首獎和最佳劇情長片獎,更榮獲當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兩岸華語電影。黃信堯其實不是新導演,只是他拍紀錄片居多。最佳新導演獎項分類卻可看出紀錄片和電影的分類困難。
一般在資本市場的邏輯下,觀眾須首先掌握電影的基本性質,才能被吸引購票入場。如果不看預告片而單憑文字,如此一來有可能掉進只有伯克說的「科學家式」或維根斯坦的「語言」式陷阱。我想把這個明顯的標籤也塗抹掉。
舉例說,現在是有朋友邀請,你事先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什麼電影,不過你聽說過黃信堯,知道他拍過很多紀錄片,亦有得過獎。你首先聽到的是一段台語獨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這部電影是由華文創和甜蜜生活聯合提供,由業界最專業的甜蜜生活來製作。﹝基於電影是如此籠統的說法,你不以為然。﹞我們邀請業界最難相處的葉女士和鍾先生來擔任監製。我是始終如一的導演,阿堯啊。在電影的放映過程當中,我會三不五時﹝閩南語,指時常﹞出來講幾句話,宣傳一下個人的理念,順便解釋劇情。請大家慢慢看。就先不打擾。需要的時候我才再出來。
這種紀錄片旁白的方式不讓你感覺陌生,不管是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還是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影片,你接觸過很多次。接著你發現聽著獨白時的背景音樂,原來是接下來畫面中的樂手所奏的。一群人看來穿著不太整齊的制服,後面有一輛靈車。似乎是有人去世了。鏡頭是黑白的。你分不清這是不是紀錄片導演新片的劇情。他們在雜草中前行,旁邊有一個湖。畫面是淡定和寫實的。你清楚這不是那種充滿電腦特效或者《魔戒》一樣的一眼便知虛構的電影,也知道這不是仿真的歷史紀錄片。片中人繼續打著鼓,吹奏樂器,表現得不專業。你開始懷疑獨白所說的「業界最專業」是導演的玩笑。再接著你看著放滿雜物的小車在顛簸中前進的畫面。畫面沒有商業片常有的流線型拍攝手法,你不知道這是拍攝還是紀錄──還是兩者很多時候是同一回事(「film」除了電影也有紀錄片、底片的意思)。《大佛》中充滿這些生活小節的鏡頭,有在馬路的,有在垃圾場的、醫院的、爛地的,鏡頭就在一定距離中拍攝,沒有特別介入,也沒有渲染。
你斷不會突兀地說:「發生的事就像電影一樣。」
一直去到第五分鐘,你看到一尊大佛,它的頭被凌空吊著,背後有煙霧。你聯想起這有點像以往年代的武俠片,運功療傷或者進入異境的場面。大佛的頭部空間中鑽出了一個工人,他們正組裝大佛。你記得導演開場時諷刺監製是「業界最難相處」的人,你以為只是一個令觀眾入戲的玩笑,還以為自己聽錯。他第二次介入時說:
這個工廠大家都很關懷對方的老母。那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作者按:你想起一部戲謔如來佛祖的周星馳電影,「我只不過想研究一下人與人之間的一些微妙的感情」,見第五節。﹞菜脯白天的工作都是兼差的。正式的工作是在這當夜班警衛。他會順便在大家下班前把工廠打掃一下。
接著大佛被打響,產生了強烈聲音共鳴。自開場的送葬場面後就沒有過音樂,此時背後徐徐響起挑情一般的電吉他撥弦聲,然後在音樂襯托,你看到一個穿著西裝的男人正摸一位女士的屁股,一行數人走進工廠,有人問:「佛頭怎麼會這樣?」導演接著介紹劇情說:
在前面大小聲的,是工廠的老闆啟文。﹝作者按:你看到他的手摸竟然向女士的臀部中間,心想這太過分吧……﹞在後面摸屁股的,是高委員和他的助理瓦樂莉。雖然高委員的戲分不多,但是他奮鬥的過程值得我們來介紹……自從瓦樂莉來了之後,高委員的紅木桌就突然多了一片木板,主要是方便瓦樂莉辦公……
你開始肯定這電影的格調,充滿「幹話」。你開始聞到電影的性質。此影片充滿了對現實的描述,這種擁權且好色的政客形象幾乎是一種常見定型。說真正感受到戲劇性,可能要到你後來看著大佛藏屍,被震驚到的一刻為止。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電影中的虛實性。它是「拍出來」而不是用特技「畫出來」的,即使如此有時我們也未必能馬上意識到其事實性,到底是紀錄片的一種,還是電影的一種。
〈第二章 一萬年 GLANCE〉(節選)
解脫「彼岸執念」?
在台灣的形勢中,除了上節說的「現實彼岸」,還真有一個大家想移民去的「西方極樂世界」彼岸;在地圖中,它卻不在西方而在東方,正是橫跨了整個太平洋的美國。本來以為香港的中西夾縫已經算是奇特,但在權力更迭上,至少香港的西方古國離場,東方古國進場。縱處在切換期,但更迭是可辨識的。台灣發生的則是以往《亞細亞的孤兒》時代,台灣主體在中、日、自身中打轉。到了《月老》的時代,日本退場,仍有餘音,但具體的力量影響上,「外人」由日本變成了地理東方,文化西方的另一彼岸。
台灣的主體概念一部分由自己定奪,不須他人多言;另一方面作為島嶼──又或者說作為現今全球化下地緣結構的一員──它有以關係來界定的部分,也就是常說的國際形象或者國際關係定位。當中最顯著的力量就是設有太平洋艦隊的美國,也是二戰後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這方面的法律表現。當中2.2.2、2.2.3及2.2.6條目如下:
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而且是國際關切的事務;
表明美國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之舉,是基於臺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一期望……
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訴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壓手段,而危及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美國在台協會1979)
美國一方面將台灣納入其保護傘內,另一方面其正式建交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情勢有點複雜。對現時的探討尤其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超級大國尚且以這樣的形式來建立對台關係,其他國家只會更小心翼翼。台灣近年便持續有邦交國斷交的新聞,曾被形容為可能發生「雪崩式斷交」,不少民眾卻認為「沒差」、「無感」。(鏡媒體2017)2021年,尼加拉瓜成為蔡英文任內第八個斷交的國家,使邦交國數目跌至十四個。(聯合新聞網2021)2023年3月宏都拉斯與台灣斷交,邦交國數量跌至十三個。(BBC 2022)在這樣的現實政治困局下,確有聲音指出從「彼岸執念」中解脫方為上計。曾任職於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的國防分析者的葛羅斯曼(Derek Grossman)表達了「與常識相悖的建議」:
台灣應考慮主動斷絕與所有邦交國的外交關係,從這場毫無勝算的「邦交國爭奪戰」中解脫,進而將重心放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深化與中大型國家的非官方連結,藉此削弱中國對台灣的打壓……除了台灣在歐洲唯一的友邦梵蒂岡之外,其餘友邦多是又窮又小、地緣戰略價值極低的國家。(陳艾伶2021)
葛羅斯曼的說法不無道理,同時又帶著風險。不論是否要以這樣的方式進行,要從目前這懸而未解的處境中解脫,確是有保持冷靜頭腦和破除執念的必要。美國這個西方彼岸早在1979年跟中方建交,雖說比英國、法國更晚,卻有國際上定調的影響,使台灣進入了八十年代以降的外交處境。上一冊援引了竹內好、陳光興等人的思想,我們知道在後殖民主義的格局,亞洲要脫離西方自立主體,其實有解開西方不在地的束縛以尋找在地資源的必要,不能不加思索地執著在台建立「另一個西方」。
台灣要解脫的西方彼岸,確是看起來「一片光明」,卻又相距「幾千、幾萬年」之遙。
歷史上美國對台灣彼岸的實際影響
美國在戰後世界的強大勢力也名副其實地阻止台灣「到達彼岸」。在六十年代時,中國大陸正經歷嚴重動盪,蔣經國曾言:「這是(國民政府)十八年以來,最重要的關頭,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林琮盛2013)計劃反攻,卻礙於海戰失利的近因,以及美國或因陷入越戰等國際形勢而不支持的遠因,胎死腹中:「因為國民政府此時已與美方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與美國在1954年12月3日簽訂的國際條約),規定於台海上所進行的任何軍事行動都須先經過雙方的意見,一致了才能發動。而在當時美蘇兩強極端對峙的局勢下,反攻大陸非常有可能會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陳毅龍2019)
第三次大戰之說或有點偏離歷史實相,但陳毅龍有關中美條約的理解卻可以在其他更正式的文獻中找到答案,並且說明美方角色在台方計畫中的實然影響。國史館修纂處纂修葉惠芬指出:「在國際冷戰嚴峻情勢下,以彈丸之地的臺灣要完成登陸反攻準備,談何容易,反攻時程自然只得流於口號,一延再延。」蔣中正基於國際形勢無法妄進,一再要求修改計畫,可見其重視。而在計畫中,美國的角色不是輔助,而是必要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及中共發動八二三砲戰之後,國軍任何反攻行動都必須知會美國,甚至承諾不使用武力反攻的情況下制定的,如何突破美方限制,爭取其認同,甚至獲得援助,成為計畫必須考慮的重點。」(葉惠芬2016, p.149, 151)台灣前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限制其反攻意圖,後有中美建交後的《台灣關係法》,使台灣攻守都有美國的強大影子。
在正面反攻以外,蔣中正亦曾試圖說服美方利用韓戰和滇緬游擊隊進行反攻,並在日記中寄望「配合世界大勢,當待第三次大戰發動時反攻大陸」。(《蔣介石日記》,1953年5月3日,見於ibid, p.153)然而今時今日我們都知道事態的發展。尤幸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否則會生靈塗炭。蔣中正想等的時機,等到他離世還是等不到。
美夢初期多是空想。不過在美夢成真之前,這些極端的想法在責人之前首先責己,先便將台灣化成一個怨靈之地,也是遠至解禁初期的《悲情城市》至近年的《返校》一脈的白色恐怖歷史教訓。
念著彼岸,執著異己,在達陣之前天堂已經沉沒。
〈第三章 塵世間 GRIEVANCE〉(節選)
拍成《西遊》的九十年代背景
《西遊》上、下放映於1995年。當時香港社會正面對兩年後的主權移交,跟以往和接下來我們知道的將來一樣,香港「又一次」「史無前例」地面對移民潮。(後來我們都知道,香港的移民潮基本上是數年一次的常態。)社會各界憂慮移交後的生活會否受影響,香港主體性飽受衝擊。在這個有限的時間內,劉鎮偉反其道而行大講「一萬年」。一萬年固然是修辭技巧,但一萬年終歸也是一個時限,跟香港當初被割讓九十九年一樣,也有其終結之時;同時一萬年又是近在咫尺的限期前無法想像的極長時間。中方許諾的「五十年不變」,卡在中間,不長也不短。
但人算不及天算,不變在塵世間是否可能?
王家衛作為一萬年不變的創作者,設計了在《重慶森林》中傳呼機密碼為「愛你一萬年」。這個愛情密碼卻是無用功的。金城武不斷跟通話員檢查留言信箱,也是不會有回音的。愛你一萬年純粹是一個泡影。他的前女友已經不再愛他,他還是渴望有轉機,到便利店買下特定日期的鳳梨罐頭,跟自己玩一個遊戲。他希望至少記住所有,「如果一定要加一個日子的話,我希望它是一萬年。」這一萬年注定是空話。在論述王家衛作品中的「不變」主題時,我便有過以下觀察:
《花樣年華》面對的是含蓄的情感,包括被出賣的情緒和蠢蠢欲動的報復心,《2046》面對的卻多了一條不變的參考線。可是這世界有什麼是不會變的?又有誰能隨心所願地承諾不變便就不變?以不變,見萬變,來來回回地在回憶沼澤中掙扎。(AT1, p.32)
許心儀也有類似的觀察:「跳躍的時空使歷史失去意義,影響了主角建構回憶及建立身分,沒有與他人共同對過去的理解而失落與人的關係。混亂的身分逼使至尊寶保持距離地看待過去,疏離於社會,與他人的關係如同後現代文化下不帶點情感將自己與世界分離。沒有過去,只能消費歷史。觀眾也是消費了電影和原著故事的歷史。回歸現實,《月光寶盒》和《仙履奇緣》利用角色混離的身分和時空的拼湊比喻香港人身分認同,以悲慘的劇情回應香港政治前途……」(2017)極其重要的一點,也是對後現代作品甚或電影本身的批評,就是沒有出路:
《西遊記》似乎只講出了悲觀的預言,卻沒有提供仙路指引。(ibid)
如此一來,幻幕鏡下,悲苦喜樂一掃而空,虛無至極。要求一部電影改變人生,給人指出具體路線,本來也是過分的期望。不過至少在拋出矛盾後,總要有點整理和己見,否則盡是虛無。在《悲情城市》中我們可以探出亞地靈;在《返校》中有其怨念版本,以及不為己的犧牲精神,叫後人不要忘記;在《卧虎藏龍》會感受到新派武俠哲學和天地間的非具象亞地靈。在《西遊》至《月老》一類電影,即使它們的價值是明顯的,也是打動很多人的,有時表面看來卻還是難以說起「意義」這回事。在這種後現代詮釋中,任人如齊天大聖大翻筋斗,天花龍鳳,很多人還是說不出什麼要旨可言。這樣偏執地想下去,人很難在看後得到生命的動力,更別談什麼道德課堂。
影評人登徒在〈西遊記:時不我予,悔不當初〉(1995)一文指出《西遊》有胡鬧、場口連接、特技粗糙的問題,勝在飽含情感、水銀瀉地、「直叫觀者動容……餘音梟裊」,最後「像極了孫悟空一場思凡的噩夢」。跟另一位影評人李焯桃(1995)認為《西遊》是「Bad Timing的悲情神話」一樣,他認為其悲痛緣由實在是時間錯誤,而一萬年台詞是對王家衛《東邪西毒》之超越。「其中最精彩的莫過於一段至尊寶的愛的宣言:『曾經有段至真的感情……一萬年』,在總結《東》中各人心中隱而未宣的鬱結與遺憾之餘,更帶出了妄想[重新嚟過(編按:粵語,指「從頭再來過」)]與感懷(愛情期限一萬年),緊扣主題而感情濃度層層遞升。戲中僅兩次引用,便帶出一喜一悲的極端效果。」他沒有說出這類型電影的功用,唯指出香港也是一座悲情城市,而大限之說確是時代中的共同課題。
台灣沒有大限,人所共知的是其前途的不確定性。九把刀在承繼周星馳的優點時,無疑也會碰到短處。但在這奇獨的情況下,所謂「後現代」也好,香港大限所致也好,不確定性符合了台灣的基調。而在轉化「一萬年」這概念時,他繼承了情感上的飽滿,並不意圖尋找藥方,點到即止,只為觀眾逃離現實,珍惜眼前人。九把刀也不無意外地繼承了劉鎮偉和周星馳創作中的香港處境意識投射,在雖存異但接近的文化和地緣政治脈絡中,「不變」和「彼岸」等傳統的華語圈共有概念得以有在地發展和延伸,更偶有加深(包括畫龍點睛地起用馬志翔演出原著小說中不存在的一角)。
台灣那無底的不變與有涯的變數,使香港面對大限時的情緒得以再一次以另一種方式詮釋出來。香港與台灣相隔七百公里之遙,建橋相連,本就是一種「有用之用」。
(……)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