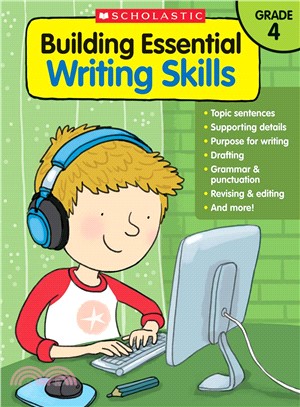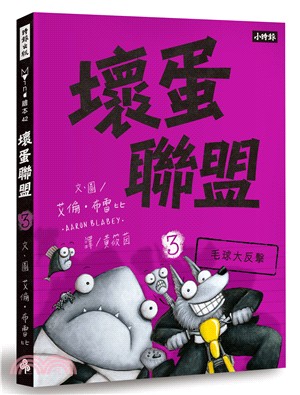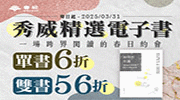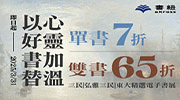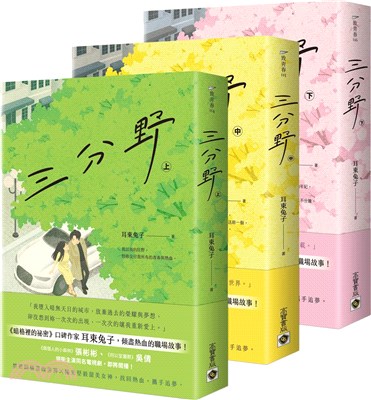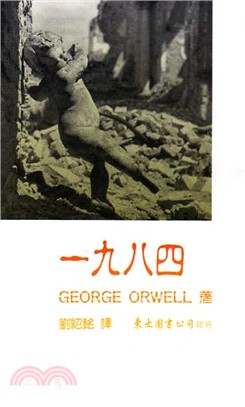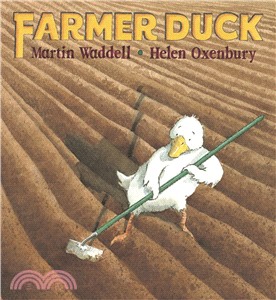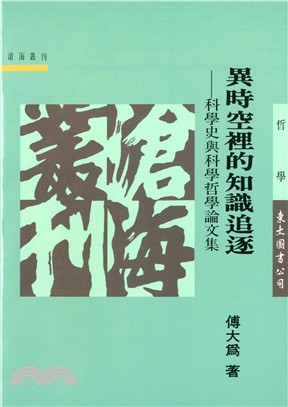歷史與人的命運(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書系
ISBN13:9787506359900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周政保
出版日:2011/09/28
裝訂/頁數:平裝/222頁
規格:26cm*19cm (高/寬)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歷史與人的命運》收錄了著名文學評論家周政保關于長篇小說的文學評述38篇。《歷史與人的命運》呈現的主要是作者對于小說的意義:作品與閱讀的全方位的精彩論述。作者解讀和評論了鐵凝的《大浴女》,賈平凹的《懷念狼》、《廢都》,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史鐵生的《務虛筆記》,阿萊的《塵埃落定》等耳熟能詳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中的精品,其真知灼見的論述,妙筆生花的文字,客觀形象的評說,引領著讀者走入了一個個別開生面的小說世界,又如博物館的解說員一般將這些精品佳作中的鮮亮之處一一娓娓道來,堪稱是文學評論的佳作。
作者簡介
周政保,江蘇常熟人,1965年赴新疆,曾供職于洛浦、積田、喀什等地。1972年被新疆大學中文系錄取;1980年又被該校研究生系錄取。1982年入伍,先後在烏魯木齊軍區等單位任創作員。1992年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曾出版過《小說與詩的藝術》、《泥濘的坦途》、《精神的出場》、《戰爭目光》、《非虛構敘述形態》、《蒼老的屋脊》、《自尊的獨語》、《周政寶報告文學評論集》等十幾部著作。《非虛構敘述形態》曾被評為第九屆解放軍文藝獎。在蘭州軍區工作期間,曾被授予二等功一次。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委員)。
名人/編輯推薦
《歷史與人的命運》編輯推薦:文學批評的繁榮與批評的質量,既受時代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又取決于批評家隊伍的集體力量和批評家個人的獨特思想與水平。在當代文學批評家隊伍里,有一批非常優秀的、能真誠和負責任地表達自己觀點,并能讓作家和讀者信服與敬佩的批評大家,他們的獨立思想與獨立人格,形成了他們的批評風格,取得了相當的研究成果,是我們當代文學史的寶貴財富。
目次
小說的意義:作品與閱讀
--兼涉長篇小說《狂欲》
與哈捷拉吉里村相關的小說想象
--評陸天明的《泥日》
《廢都》:廢都就是廢都
關于長篇小說《子民們》的評價與聯想
關于戰爭與愛情的故事
--龐天舒長篇小說《落日之戰》評述
荒誕的歷史玩笑
--張抗抗長篇小說《赤彤丹朱》讀記
《末日之門》印象
戰爭不是“游戲”
--朱秀海《穿越死亡》讀記
《馬橋詞典》的意義
口語傾訴的方式(或敘述就是一切)
--關于李銳的長篇小說《萬里無云》
《務虛筆記》讀記
陳染的煙霧
--讀《私人生活》小札
尋找“石頭油”的故事
--長篇小說《黑白》讀記
《木凸》的“木凸木凸木凸”
歷史或命運的無奈
--關于長篇小說《太陽回落地平線上》
《駝城》的“大盛魁掌柜”
“落不定的塵埃”暫且落定
--《塵埃落定》的意象化敘述方式
重讀張賢亮的《習慣死亡》
影子是重要的
--關于斯妤的長篇小說《豎琴的影子》
《高老莊》:超越敘述對象
《英雄無語》:“無語”的意義
《黃羊堡故事》:恍若隔世的歷史記憶
從茫然搖曳到絕望變態
--讀《搖曳的教堂》
誰能或怎樣才能摧毀那方“水土”
--我讀畢四海的《財富與人性》
《大浴女》:誰在塑造她們?
生命與歷史同行
--洪三泰的長篇小說《風流時代三部曲》
“懷念”的是“狼”么?
--讀長篇小說《懷念狼》
那一壟壟長滿大豆高粱的土地
--關于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
在愛情成為笑話之後
--讀池莉的長篇小說《小姐你早》
獨樹一幟的“第三條道路”
怎樣才算“好小說”
--或從長篇歷史題材小說《秦相李斯》說起
《大風起兮》:輝煌中的沉重
“撤退”及寫好“中國小說”
--談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
《痛失》的意義
于荒誕中見人生本相
--讀張煒的《能不憶蜀葵》
《白太陽》:愛情不僅僅是愛情
歷史變化與人的感情遭遇
--從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說起
鐵血軍人今猶在?
--評馬曉麗的長篇小說《楚河漢界》
歷史與人的命運
--查舜的長篇小說《青春絕版》
“標新立異”與表現力
--談李銳的《銀城故事》
--兼涉長篇小說《狂欲》
與哈捷拉吉里村相關的小說想象
--評陸天明的《泥日》
《廢都》:廢都就是廢都
關于長篇小說《子民們》的評價與聯想
關于戰爭與愛情的故事
--龐天舒長篇小說《落日之戰》評述
荒誕的歷史玩笑
--張抗抗長篇小說《赤彤丹朱》讀記
《末日之門》印象
戰爭不是“游戲”
--朱秀海《穿越死亡》讀記
《馬橋詞典》的意義
口語傾訴的方式(或敘述就是一切)
--關于李銳的長篇小說《萬里無云》
《務虛筆記》讀記
陳染的煙霧
--讀《私人生活》小札
尋找“石頭油”的故事
--長篇小說《黑白》讀記
《木凸》的“木凸木凸木凸”
歷史或命運的無奈
--關于長篇小說《太陽回落地平線上》
《駝城》的“大盛魁掌柜”
“落不定的塵埃”暫且落定
--《塵埃落定》的意象化敘述方式
重讀張賢亮的《習慣死亡》
影子是重要的
--關于斯妤的長篇小說《豎琴的影子》
《高老莊》:超越敘述對象
《英雄無語》:“無語”的意義
《黃羊堡故事》:恍若隔世的歷史記憶
從茫然搖曳到絕望變態
--讀《搖曳的教堂》
誰能或怎樣才能摧毀那方“水土”
--我讀畢四海的《財富與人性》
《大浴女》:誰在塑造她們?
生命與歷史同行
--洪三泰的長篇小說《風流時代三部曲》
“懷念”的是“狼”么?
--讀長篇小說《懷念狼》
那一壟壟長滿大豆高粱的土地
--關于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
在愛情成為笑話之後
--讀池莉的長篇小說《小姐你早》
獨樹一幟的“第三條道路”
怎樣才算“好小說”
--或從長篇歷史題材小說《秦相李斯》說起
《大風起兮》:輝煌中的沉重
“撤退”及寫好“中國小說”
--談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
《痛失》的意義
于荒誕中見人生本相
--讀張煒的《能不憶蜀葵》
《白太陽》:愛情不僅僅是愛情
歷史變化與人的感情遭遇
--從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說起
鐵血軍人今猶在?
--評馬曉麗的長篇小說《楚河漢界》
歷史與人的命運
--查舜的長篇小說《青春絕版》
“標新立異”與表現力
--談李銳的《銀城故事》
書摘/試閱
小說的意義:作品與閱讀
--兼涉長篇小說《狂欲》
我本想在這篇文章中使用“文本”這個概念,但無奈這個概念雖然時新而含意模糊--它在各種批評學理論中的理解及運用,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于是我就仍然使用“作品”這個概念:譬如,作為長篇小說,刊載于1989年《百花洲》第3期的《狂欲》就是一部“作品”。
按照常規思維的邏輯,小說的意義是經由作品而獲得實現的,或者說,小說的意義只能被體現于具體的小說作品之中。誠然,如果被稱為“作品”且堂堂皇皇地刊載于文學雜志,那一般來說,它總具備某種特定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具備某種特定的文學價值),但這里的重要問題是,一個作者依據他所操持的生活觀念與文學觀念而寫了一部“小說”,那應該由誰來認定它是一部“作品”呢?毫無疑問,應該由包括文學雜志編輯在內的讀者來認定。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作品”可能體現一部小說的意義,但這種可能性歸根結底還要通過社會閱讀來驗證。倘若換一種說法,那就是--小說的意義,必須在進入社會閱讀之後才可能實現;反之,任何小說都不可能產生意義。
不言而喻,社會閱讀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且不說閱讀某部作品時的特定心境,以及與這種心境相關的時代崇尚與歷史氛圍的差異性--譬如說讀短篇小說《班主任》、《李順達造屋》之類,即使是處在同一時代崇尚或歷史氛圍之中的讀者面對同一部作品,也可能因每個讀者的不同身份或不同文化修養而截獲不同的感受或不同的體驗或不同的判斷與印象……這是毫無辦法的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及人的藝術感覺的歷史發展時說:“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所以馬克思說:“只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也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我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
馬克思的精彩論述,實際上也在告訴我們--閱讀(或接受)之于作品意義的重要性,或者說,只有閱讀的過程才可能實現作品的意義--倘若讀者的感覺(或文學感受能力及其理解可能性)偏離了正常的審美軌道,那作品的意義也就可能被扭曲、被損害、被牽至遠離作者初衷的方向。甚至還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即明明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作品,但在一些人的閱讀印象之中,卻被認定為“毫無意義”。所以魯迅說革命家在《紅樓夢》中看到排滿,而道學家看到的則是淫穢,這盡管是一種嘲諷,但其中的意思倒是很逼真地道出了閱讀領域中的差別。
在我的觀念之中,作品的意義--或者說是一部小說的價值,完全是相對具體而生動的社會閱讀而言的。一部自以為很出色的小說,如果始終不進入社會的閱讀領域,那這部小說也就不可能產生意義--閱讀是小說之所以具有某種意義的土壤;而這塊“土壤”又絕非是一種抽象的假設:它是由一個個具體讀者組合而成的活生生的存在。
我在這里要涉及小說家張品成的一部作品,即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長篇小說《狂欲》--這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在去年下半年的《文藝報》上,專業評論家林為進曾作過比較公允的正面評價,而在今年年初的《百花洲》上,舒暢則撰文作了題為《欲壑中的迷失》的否定性的評價(無疑,這里的評價都是善意的同志式的各抒己見)。從這些很不相同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到,個體閱讀之于小說的意義、即對小說價值及其思情走向的判斷或認同,起著多么重要的作用!從這種不可避免的差別性之中,還可以發現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文學作品的閱讀,其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說穿了,即讀者應該怎樣閱讀作品(“應該”這個詞可能有點兒武斷,但從馬克思的關于藝術感覺的歷史發展觀點來說,“文學欣賞”畢竟具備某種內在的審美規律性,而其中的奧秘則與欣賞音樂或欣賞美術作品是一致的)。
一部文學作品在復雜的社會閱讀過程中必然地被“改寫”--這種發現于今天的接受美學領域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解了。譬如說,二十世紀的荷馬并不是中世紀的荷馬,而是我們的(或作為個體的“我的”)荷馬,而莎士比亞也決計不是莎士比亞時代的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已經成為我們的莎士比亞了!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讀者創造了不同的荷馬與莎士比亞,并從中找出不同的思情成份或藝術因素而從事不同的判斷與評價,這種現象之于作家作品,既是悲哀的,又是可喜的,因為這種閱讀過程中的無意識的“改寫”,也許可能違背或遠離作家作品的“初衷”,但也可能因種種“改寫”而使作品滋生相對恒久的藝術生命力--馬克思曾高度稱贊過古希臘藝術的永恒魅力,而這種永恒魅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則可以歸功于歷代欣賞者的“改寫”。當然,這種“改寫”肯定受制于歷史文化氛圍的牽引。所以,曾經寫過《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英國理論批評家特雷o伊格爾頓說:“任何作品的閱讀同時都是一種'改寫'。”又說:“沒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沒有任何一種關于這部作品的流行評價,可以被直截了當地傳給新的人群而在其過程中不發生改變,雖然這種改變是無意識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說被當作文學的事物是一個極不穩定的事件的原因之一。”(見伊格爾頓所著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依據這種比較可靠的觀點,那在不同讀者的不同閱讀過程中,就一部小說而產生某種感受與理解方面的分歧,也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文學接受現象了。不過,這里不包括那種“故意改寫”的情形,譬如康生對于小說《劉志丹》的“改寫”、姚文元對于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改寫”等等,因為他們的“改寫”所導致的“判斷”,早已超出了文學欣賞或文學批評的范圍,而屬于一種包藏卑劣政治用心的反動殺機的無恥運用。所以我所強調的,僅僅是那種自然而然的文學接受現象,那種正常的小說理解及審美感受方面的分歧,以及那種因分歧而導致的對于小說意義的不同判斷與不同評價。
但無論如何,當我們閱讀一部被稱為小說的文學作品的時候,首先應該意識到的是:你的對象是一種審美的精神產品--它不是被嚴格邏輯統治著的理論文章,也不是通訊報道之類的新聞文字,更不是政府部門的文件材料:它是小說,而小說的任何方面的社會效果都是經由小說方式的審美實現的;如果它是非審美的,或者說,它缺乏應該具備的審美作用,那諸如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啟迪作用之類的可能性,必然是一種空談或一種妄想。我以為這是文學世界的最起碼的常識。
張品成的《狂欲》到底是一部怎樣的長篇小說?它的意義究竟在哪里?而作為小說的意義,作品又是如何傳達的?在這里,我既不想全盤否定這部小說,也不想把這部小說說成很優秀或很杰出的作品--我只想說,這是一部有意義的小說:盡管作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某些思情藝術方面的缺憾,但作品所體現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探索不易,成功更難,因而不能因作品的一些性描寫而論定它的“迷失”。實際上,《狂欲》的總體題旨是比較自覺的,而性描寫大體上僅僅是一種傳達或表現的途徑(這方面的描寫是否顯得多余,或有點兒畫蛇添足的嫌疑,評論界還可以討論)。關于性描寫,文學界與非文學界早已發表過很多精彩的或不甚精彩的見解,或者說,就一般理論邏輯而言,應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即都以為文學創作并不排斥性描寫,關鍵是怎樣描寫與描寫的目的是什么。但一進入具體的創作與閱讀之後的把握,問題就顯得相當復雜與相當煩難了。對此,創作界與評論界都具有難言的深切之感。
我讀了《狂欲》之後,所留下的第一藝術印象是--這是一則結構不甚嚴密的長篇寓言,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具備一種隱隱約約的寓言傾向。如果僅僅從作品的背景、從作品的表層描寫、從這種描寫與生活原生面貌的接近程度、或者是從一般的“性”的與“欲”的角度來感受與理解,那就可能偏離作品所包孕的真正思情意圖與藝術探索目標--當然,如果出現這種閱讀情狀,那也不可把責任全部地推向小說之所以可能產生意義的社會閱讀,因為我在前面已經說到了,這部作品也存在著自身的缺憾。
我之所以說這部小說具備某種寓言傾向,那是因為這部小說--所描寫的雖然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蘇區農村生活,但作品真正企圖表現的,卻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農村文化現象,一種阻礙生存與繁衍的封建倫理觀念的虛偽與反人性實質(一方面是農民因沿襲傳統文化負面而滋生的愚昧落後,一方面則是與農民相敵對的反動階級的陰險殘忍)。無疑,這一切基本上是由以洪邁為代表的一族人的生存欲望、生理欲望、復仇欲望、宗族延續欲望的強烈沖撞與奔突中實現的,而在這種“狂欲”之中自然滲透了作者的社會變化剖析。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是那些丑陋的性描寫,也不可能是一種自然主義或純粹生理性的揭示與展覽。十分明顯,性描寫之于作品整體,不是一種津津樂道的“欣賞”,而是一種滴著血淚的控訴,一種蒸騰著苦澀氣息的批判--還應該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在嘲弄這些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而是在控訴與批判一種浸透了封建倫理道德與迷信的宗族文化。這種宗族文化作為小說描寫的縮影--盡管小說的故事不甚復雜,但它痛苦地體現了一種慘酷的不可避免的結局:它模糊(作為藝術描寫)而清晰(作為藝術表現及思情走向)地告訴讀者--革命的失敗、瘟疫的流行、敵對階級的猖狂殘酷,都不可能滅絕一個宗族的生存與延續(它們只可能摧殘這種生存與延續),而真正可能導致悲慘結局的,則是宗族內部早就存在著的封建文化傳統及其那種迷信所生成的愚昧落後:作為一種自戕因素,它在特定的環境中惡性膨脹而鑄造災難。
我覺得,這就是《狂欲》這則“長篇寓言”所隱含的意義--特別是,作品的描寫之于其中貫突的“狂欲”,所融入的批判態度是可感可觸的。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小說并沒有從根本上迷失自己的描寫與表現,以及這種描寫與表現所尋覓的整體思情走向。在這里,分歧最顯著的,大概是作品中所留下的那些情欲描寫、特別是那些男女交媾場面的比較細致的揭示,但就我的閱讀感覺而言,還不能輕率地認定這些描寫或揭示都是純粹的生理欲望的宣泄--全部這樣認定是不公允的,因為在小說中,無論是族長洪邁的動機,還是其中的那些男女主人公的種種“狂欲”的產生,都被打上了相應的體現某種社會文化色彩的烙印,當然,我也不能說這些“狂欲”的描寫場面,一點兒也不存在生理性欲望的宣泄成份,但叫人感到煩難的是:無論小說家還是評論家,都很不容易從中作出明明白白的區別--作為人類生存的具體內容,“性”的描寫之于小說,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眾所皆知的:但究竟怎樣描寫才富有意義、才具備文學的審美價值,這正是我們應該不斷探索的課題--盡管誰也拿不出盡善盡美的靈丹妙藥,但也不必發出莫名其妙的驚呼……如果以為《狂欲》的描寫具有所謂的“抹黑”嫌疑,那就有點兒冤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了。這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而是一部以農村文化現象作為描寫內容的富有寓言傾向的小說--這樣閱讀,對小說的意義也許可能產生一種比較可靠的感受與理解。我想,對于這部小說的肯定與否定,或肯定一部分與否定一部分,大概都可以作為個體閱讀的結果而存在,但重要的是一種整體性的、合乎小說藝術規律的判斷。
我的這篇短文是因《狂欲》而萌生的:我再一次感到了閱讀的重要:閱讀是第一性的、作品是第二性的,這種說法絕非毫無根據的妄論--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以可靠的方式閱讀小說,從而避免對于小說意義的高估或低估(或偏離)。不過,我在文章中涉及到了《狂欲》這部小說,所述也只是我的閱讀結果,至于可靠與否,則是另一回事,好在社會主義文學園地里所倡導的是“二為”前提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湊巧的是,這部小說所刊載的雜志就叫《百花洲》!
1990年3月
--兼涉長篇小說《狂欲》
我本想在這篇文章中使用“文本”這個概念,但無奈這個概念雖然時新而含意模糊--它在各種批評學理論中的理解及運用,差別實在是太大了。于是我就仍然使用“作品”這個概念:譬如,作為長篇小說,刊載于1989年《百花洲》第3期的《狂欲》就是一部“作品”。
按照常規思維的邏輯,小說的意義是經由作品而獲得實現的,或者說,小說的意義只能被體現于具體的小說作品之中。誠然,如果被稱為“作品”且堂堂皇皇地刊載于文學雜志,那一般來說,它總具備某種特定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具備某種特定的文學價值),但這里的重要問題是,一個作者依據他所操持的生活觀念與文學觀念而寫了一部“小說”,那應該由誰來認定它是一部“作品”呢?毫無疑問,應該由包括文學雜志編輯在內的讀者來認定。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作品”可能體現一部小說的意義,但這種可能性歸根結底還要通過社會閱讀來驗證。倘若換一種說法,那就是--小說的意義,必須在進入社會閱讀之後才可能實現;反之,任何小說都不可能產生意義。
不言而喻,社會閱讀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且不說閱讀某部作品時的特定心境,以及與這種心境相關的時代崇尚與歷史氛圍的差異性--譬如說讀短篇小說《班主任》、《李順達造屋》之類,即使是處在同一時代崇尚或歷史氛圍之中的讀者面對同一部作品,也可能因每個讀者的不同身份或不同文化修養而截獲不同的感受或不同的體驗或不同的判斷與印象……這是毫無辦法的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論及人的藝術感覺的歷史發展時說:“只有當對象對人說來成為人的對象或者說成為對象性的人的時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對象里面喪失自身。”“對象如何對他說來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所以馬克思說:“只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也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我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
馬克思的精彩論述,實際上也在告訴我們--閱讀(或接受)之于作品意義的重要性,或者說,只有閱讀的過程才可能實現作品的意義--倘若讀者的感覺(或文學感受能力及其理解可能性)偏離了正常的審美軌道,那作品的意義也就可能被扭曲、被損害、被牽至遠離作者初衷的方向。甚至還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即明明是一部很有價值的作品,但在一些人的閱讀印象之中,卻被認定為“毫無意義”。所以魯迅說革命家在《紅樓夢》中看到排滿,而道學家看到的則是淫穢,這盡管是一種嘲諷,但其中的意思倒是很逼真地道出了閱讀領域中的差別。
在我的觀念之中,作品的意義--或者說是一部小說的價值,完全是相對具體而生動的社會閱讀而言的。一部自以為很出色的小說,如果始終不進入社會的閱讀領域,那這部小說也就不可能產生意義--閱讀是小說之所以具有某種意義的土壤;而這塊“土壤”又絕非是一種抽象的假設:它是由一個個具體讀者組合而成的活生生的存在。
我在這里要涉及小說家張品成的一部作品,即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長篇小說《狂欲》--這是一部怎樣的作品呢?在去年下半年的《文藝報》上,專業評論家林為進曾作過比較公允的正面評價,而在今年年初的《百花洲》上,舒暢則撰文作了題為《欲壑中的迷失》的否定性的評價(無疑,這里的評價都是善意的同志式的各抒己見)。從這些很不相同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到,個體閱讀之于小說的意義、即對小說價值及其思情走向的判斷或認同,起著多么重要的作用!從這種不可避免的差別性之中,還可以發現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文學作品的閱讀,其本身就是一種藝術:說穿了,即讀者應該怎樣閱讀作品(“應該”這個詞可能有點兒武斷,但從馬克思的關于藝術感覺的歷史發展觀點來說,“文學欣賞”畢竟具備某種內在的審美規律性,而其中的奧秘則與欣賞音樂或欣賞美術作品是一致的)。
一部文學作品在復雜的社會閱讀過程中必然地被“改寫”--這種發現于今天的接受美學領域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見解了。譬如說,二十世紀的荷馬并不是中世紀的荷馬,而是我們的(或作為個體的“我的”)荷馬,而莎士比亞也決計不是莎士比亞時代的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已經成為我們的莎士比亞了!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讀者創造了不同的荷馬與莎士比亞,并從中找出不同的思情成份或藝術因素而從事不同的判斷與評價,這種現象之于作家作品,既是悲哀的,又是可喜的,因為這種閱讀過程中的無意識的“改寫”,也許可能違背或遠離作家作品的“初衷”,但也可能因種種“改寫”而使作品滋生相對恒久的藝術生命力--馬克思曾高度稱贊過古希臘藝術的永恒魅力,而這種永恒魅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則可以歸功于歷代欣賞者的“改寫”。當然,這種“改寫”肯定受制于歷史文化氛圍的牽引。所以,曾經寫過《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英國理論批評家特雷o伊格爾頓說:“任何作品的閱讀同時都是一種'改寫'。”又說:“沒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沒有任何一種關于這部作品的流行評價,可以被直截了當地傳給新的人群而在其過程中不發生改變,雖然這種改變是無意識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說被當作文學的事物是一個極不穩定的事件的原因之一。”(見伊格爾頓所著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依據這種比較可靠的觀點,那在不同讀者的不同閱讀過程中,就一部小說而產生某種感受與理解方面的分歧,也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文學接受現象了。不過,這里不包括那種“故意改寫”的情形,譬如康生對于小說《劉志丹》的“改寫”、姚文元對于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改寫”等等,因為他們的“改寫”所導致的“判斷”,早已超出了文學欣賞或文學批評的范圍,而屬于一種包藏卑劣政治用心的反動殺機的無恥運用。所以我所強調的,僅僅是那種自然而然的文學接受現象,那種正常的小說理解及審美感受方面的分歧,以及那種因分歧而導致的對于小說意義的不同判斷與不同評價。
但無論如何,當我們閱讀一部被稱為小說的文學作品的時候,首先應該意識到的是:你的對象是一種審美的精神產品--它不是被嚴格邏輯統治著的理論文章,也不是通訊報道之類的新聞文字,更不是政府部門的文件材料:它是小說,而小說的任何方面的社會效果都是經由小說方式的審美實現的;如果它是非審美的,或者說,它缺乏應該具備的審美作用,那諸如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啟迪作用之類的可能性,必然是一種空談或一種妄想。我以為這是文學世界的最起碼的常識。
張品成的《狂欲》到底是一部怎樣的長篇小說?它的意義究竟在哪里?而作為小說的意義,作品又是如何傳達的?在這里,我既不想全盤否定這部小說,也不想把這部小說說成很優秀或很杰出的作品--我只想說,這是一部有意義的小說:盡管作品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某些思情藝術方面的缺憾,但作品所體現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探索不易,成功更難,因而不能因作品的一些性描寫而論定它的“迷失”。實際上,《狂欲》的總體題旨是比較自覺的,而性描寫大體上僅僅是一種傳達或表現的途徑(這方面的描寫是否顯得多余,或有點兒畫蛇添足的嫌疑,評論界還可以討論)。關于性描寫,文學界與非文學界早已發表過很多精彩的或不甚精彩的見解,或者說,就一般理論邏輯而言,應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即都以為文學創作并不排斥性描寫,關鍵是怎樣描寫與描寫的目的是什么。但一進入具體的創作與閱讀之後的把握,問題就顯得相當復雜與相當煩難了。對此,創作界與評論界都具有難言的深切之感。
我讀了《狂欲》之後,所留下的第一藝術印象是--這是一則結構不甚嚴密的長篇寓言,也可以說,這部小說具備一種隱隱約約的寓言傾向。如果僅僅從作品的背景、從作品的表層描寫、從這種描寫與生活原生面貌的接近程度、或者是從一般的“性”的與“欲”的角度來感受與理解,那就可能偏離作品所包孕的真正思情意圖與藝術探索目標--當然,如果出現這種閱讀情狀,那也不可把責任全部地推向小說之所以可能產生意義的社會閱讀,因為我在前面已經說到了,這部作品也存在著自身的缺憾。
我之所以說這部小說具備某種寓言傾向,那是因為這部小說--所描寫的雖然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蘇區農村生活,但作品真正企圖表現的,卻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農村文化現象,一種阻礙生存與繁衍的封建倫理觀念的虛偽與反人性實質(一方面是農民因沿襲傳統文化負面而滋生的愚昧落後,一方面則是與農民相敵對的反動階級的陰險殘忍)。無疑,這一切基本上是由以洪邁為代表的一族人的生存欲望、生理欲望、復仇欲望、宗族延續欲望的強烈沖撞與奔突中實現的,而在這種“狂欲”之中自然滲透了作者的社會變化剖析。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是那些丑陋的性描寫,也不可能是一種自然主義或純粹生理性的揭示與展覽。十分明顯,性描寫之于作品整體,不是一種津津樂道的“欣賞”,而是一種滴著血淚的控訴,一種蒸騰著苦澀氣息的批判--還應該指出的是,作者不是在嘲弄這些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農民,而是在控訴與批判一種浸透了封建倫理道德與迷信的宗族文化。這種宗族文化作為小說描寫的縮影--盡管小說的故事不甚復雜,但它痛苦地體現了一種慘酷的不可避免的結局:它模糊(作為藝術描寫)而清晰(作為藝術表現及思情走向)地告訴讀者--革命的失敗、瘟疫的流行、敵對階級的猖狂殘酷,都不可能滅絕一個宗族的生存與延續(它們只可能摧殘這種生存與延續),而真正可能導致悲慘結局的,則是宗族內部早就存在著的封建文化傳統及其那種迷信所生成的愚昧落後:作為一種自戕因素,它在特定的環境中惡性膨脹而鑄造災難。
我覺得,這就是《狂欲》這則“長篇寓言”所隱含的意義--特別是,作品的描寫之于其中貫突的“狂欲”,所融入的批判態度是可感可觸的。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小說并沒有從根本上迷失自己的描寫與表現,以及這種描寫與表現所尋覓的整體思情走向。在這里,分歧最顯著的,大概是作品中所留下的那些情欲描寫、特別是那些男女交媾場面的比較細致的揭示,但就我的閱讀感覺而言,還不能輕率地認定這些描寫或揭示都是純粹的生理欲望的宣泄--全部這樣認定是不公允的,因為在小說中,無論是族長洪邁的動機,還是其中的那些男女主人公的種種“狂欲”的產生,都被打上了相應的體現某種社會文化色彩的烙印,當然,我也不能說這些“狂欲”的描寫場面,一點兒也不存在生理性欲望的宣泄成份,但叫人感到煩難的是:無論小說家還是評論家,都很不容易從中作出明明白白的區別--作為人類生存的具體內容,“性”的描寫之于小說,其存在的合理性是眾所皆知的:但究竟怎樣描寫才富有意義、才具備文學的審美價值,這正是我們應該不斷探索的課題--盡管誰也拿不出盡善盡美的靈丹妙藥,但也不必發出莫名其妙的驚呼……如果以為《狂欲》的描寫具有所謂的“抹黑”嫌疑,那就有點兒冤枉作者的一片苦心了。這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革命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而是一部以農村文化現象作為描寫內容的富有寓言傾向的小說--這樣閱讀,對小說的意義也許可能產生一種比較可靠的感受與理解。我想,對于這部小說的肯定與否定,或肯定一部分與否定一部分,大概都可以作為個體閱讀的結果而存在,但重要的是一種整體性的、合乎小說藝術規律的判斷。
我的這篇短文是因《狂欲》而萌生的:我再一次感到了閱讀的重要:閱讀是第一性的、作品是第二性的,這種說法絕非毫無根據的妄論--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以可靠的方式閱讀小說,從而避免對于小說意義的高估或低估(或偏離)。不過,我在文章中涉及到了《狂欲》這部小說,所述也只是我的閱讀結果,至于可靠與否,則是另一回事,好在社會主義文學園地里所倡導的是“二為”前提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湊巧的是,這部小說所刊載的雜志就叫《百花洲》!
1990年3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