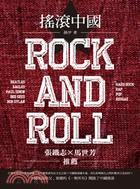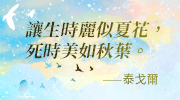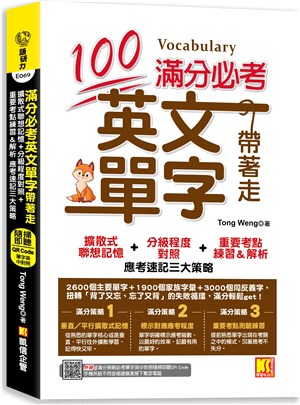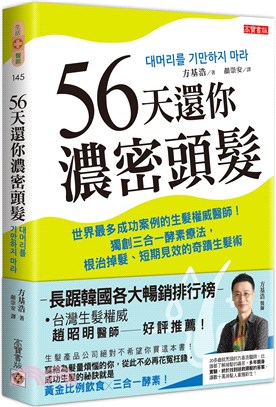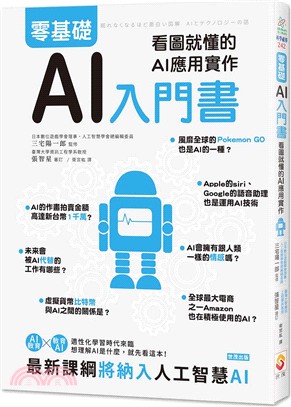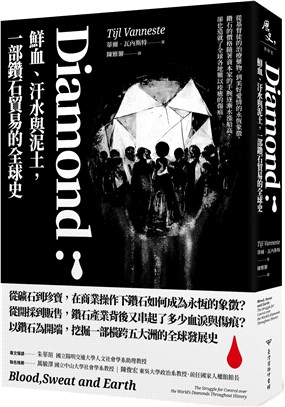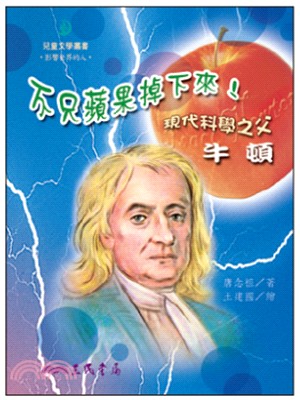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不可不看的理由
1.了解中國搖滾的入門書,是中國搖滾的簡史(1979-2010)
2.中國搖滾樂產生之前,華語世界只有西方搖滾樂。可說是,中國搖滾樂引領了華語搖滾之先,中國搖滾樂代表人物如崔健、唐朝、魔岩三傑,對於台灣音樂人、樂評人造成的影響不言可喻。
3.張鐵志(《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作者)、馬世芳(《再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作者)推薦
「這本帶點學術味的《搖滾中國》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搖滾的發展、社會意涵,以及後魔岩時期的轉型,為我們好好補了一門重要的課。」-張鐵志
中國搖滾樂是新時期以來重要的文化現象、精神現象與社會現象。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搖滾樂的發生、發展脈絡構成了新時期精神史、社會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個側面。本書通過對中國搖滾音樂人的具體創作及其與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的關聯的分析和梳理,來呈現中國搖滾樂精神歷程的變遷,並試圖藉此把握當代青年群體的主體狀態、精神構造方式、文化認同的變化,以及新時期的文化場域在數十年間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作者簡介
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並獲文學博士學位。2010年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工作至今。
名人/編輯推薦
補一堂中國搖滾的課
2008年五月我在北京。
五月十二號,發生汶川大地震;幾天後,在北京的星光現場舉辦一場搖滾義演包括眾多歌手如汪峰、艾敬,壓軸的是崔健。
那是我第一次看崔健演出。開場前的興奮與期待,不下於我去聽滾石或者狄倫;不只是因為他是一則華語搖滾的傳奇,不只是因為崔健在我二十歲的炙熱的青春是重要的聲音,也在於此前中國於我們來說根本是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存在:我們跟北京崔健的距離真的跟紐約狄倫阿伯差不多。
那晚演唱會結束後,在樂評人張曉舟的引介下,我們三人去吃宵夜,在北京的台菜店「鹿港小鎮」。我們談著音樂與政治,於我是一個如此的魔幻之夜。次年又在台北Legacy、在北京展覽館看了兩次崔健專場,依然震撼。
在那個五月的北京,我也和朋友受北京樂隊幸福大街女主唱吳虹飛之邀去她家喝酒。「在北京搖滾樂隊女主唱家喝酒」這件事,當時讓我感到莫名興奮,那畢竟是我和北京搖滾的初次邂逅。
那一回,我也認識了北京著名的自由薩克斯風手李鐵橋、當時還沒有如此大名的周雲蓬,和樂評人張曉舟。
那是一次開啟我的中國搖滾之旅的五月大門。
我們的確就是聽崔健、唐朝、魔岩三傑的一代。他們爆發的九零年代初,正好是我的大學時期,我的啟蒙時光。那也是新台語歌的時代:在聽了一個青春期的西洋搖滾後,我們終於有了華語的搖滾,終於可以跟著強烈的節奏高唱《夢回唐朝》、《一無所有》,或者《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
九零年代中期後,因為魔岩離開中國,我們幾乎斷絕了與中國搖滾的聯繫,只能偶爾買到台灣引進的蒼蠅樂隊,或者左小祖咒的《在地安門》台版等中國搖滾。
十年以後的2007年,我在北京鼓樓旁的一個小酒吧疆進酒,第一次看了中國音樂人的演出,那是一個許多人說好的盲人民謠歌手:周雲蓬。當時我們當然並不認識。我也在北京西邊的一個小的獨立白糖罐買了許多中國搖滾CD。然後是08年五月我在北京出版《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簡體版,開始重新認識並且連結起當代的中國搖滾。
我開始逐漸進入中國搖滾的場景,去看演出、音樂節,並且認真地補課,買中國樂評人的書、狂買當下或之前重要的搖滾專輯──只是,有些已然不存在的樂隊、有些傳奇的演出,是當時不在場的我得永遠錯過的,例如當年強悍瘋狂的舌頭、盤古、木推瓜,或者河酒吧時期的野孩子、周雲蓬,或者剛開始的迷笛音樂節。
我也和左小祖咒、周雲蓬、李鐵橋、小河、張瑋瑋、郭龍(以上四人曾同屬於一個樂隊叫美好藥店)、張佺(以上三人同屬「野孩子」)、萬曉利、吳虹飛、上海頂樓馬戲團的成員、廣州民謠樂隊五條人乃至萬能青年旅店成員,在深夜北京的胡同,在通縣、廣州、上海的小飯館中、在台北的快炒店或者「操場」喝酒,並和許多人成為感情深厚的哥們。我喜愛他們的熱情豪爽,喜歡聽他們談起那個在盛世之前、依然地下邊緣的北京,或者那些那個生活困頓但生猛無比的波希米亞時光。
至於少年時影響甚深的魔岩三傑,我也終於在摩登天空音樂節聽到如今有點臃腫的何勇嘶吼《垃圾場》、看張楚和一支金屬嘻哈樂隊合唱《姐姐》。(而後在我最愛的北京小酒館「江湖」見到張楚,並且有次在後海的胡同中與竇唯擦肩而過。)
少年時期深受中國搖滾影響的我,絕對不會想到我會帶著我的搖滾文字「反攻大陸」,聽到崔健親口說、看到何勇在微博上說喜歡我的書,並且有機會在中國擔任一些音樂獎項的評審。
這幾年,兩岸的搖滾交流也越來越多,重要的中國樂隊幾乎都一一來台,但我們對中國搖滾的歷史及其對中國青年文化的意義,了解依然相當單薄。這本帶點學術味的《搖滾中國》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搖滾的發展、社會意涵,以及後魔岩時期的轉型,為我們好好補了一門重要的課。
不過,本書仍然集中於兩千年前的歷史,而沒有針對當下。過去十年,搖滾樂越來越進入中國的青年文化,與此同時也更加地商業化、體制化,並且相比於九零年代後期,更失去想像力和爆發力。這個現象最明顯的就是過去兩三年搖滾音樂節在各地如蛋塔般湧現,其中許多都是地方政府和地產商支持的,其結果大多音樂節越來卻貧乏無趣。
但另一方面,雖然書中提到九零年代後期的搖滾如麥田守望者拒絕反思歷史與現實,而只是追求快樂,但也正是在這兩三年,由於中國社會矛盾加劇,中國搖滾也有重新「政治化」的趨勢,不論現在最有代表性的兩個主要音樂人左小祖咒和周雲蓬,或者這兩年最火的樂隊「萬能青年旅店」,都用音樂狠狠地撕裂社會的醜陋瘡疤,帶我們進入那個時代的黑暗迷宮。
這個主流化、商業化但也同時政治化的複雜現象,是當前中國搖滾最奇異的風景,並且正是中國的縮影:一方面我們看到中國崛起的光亮盛世,另一方面卻是社會矛盾的陰影不斷累積擴張。
最後,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這本書除了為我們補一門中國搖滾課,更大的刺激可能在於,我們是不是也該有這麼一本記錄與分析台灣搖滾史的書呢?
來動手吧……
音樂與文化評論人,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從Dylan到U2的抗議之聲》
張鐵志
目次
CHAPTER 1 緒論
1聲音的躍進
2在真空中書寫
3當我們談論搖滾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CHAPTER 2 搖滾來了!
1舶來的母語:西方搖滾樂對中國搖滾樂的影響
2混響的回聲:中國搖滾樂的登場與初期狀態
3當「西風」遇到「西北風」——中國搖滾樂與「尋根」思潮的關係
CHAPTER 3 像牛虻一樣飛——崔健
1踏上新長征路
2破殼而出
3對質時代
CHAPTER 4 孤獨的集體——「魔岩三傑」
1何勇:受傷的麒麟
2張楚:飛往內心之旅
3竇唯:浸漫的邊界
CHAPTER 5 新聲喧嘩——「後魔岩時期」的中國搖滾
1從魔岩到散沙——中國搖滾樂的分流
2青春的烏托邦——「北京新聲」一代的搖滾實踐
3市井之聲——子曰樂隊與二手玫瑰樂隊
4兩種表演者——蒼蠅樂隊與頂樓的馬戲團樂隊
結語
主要參考資料
附錄
附錄一 中國早期搖滾音樂人相關狀況
附錄二 八○年代在中國從事搖滾活動的外國音樂人相關狀況
後記
書摘/試閱
在對於中國搖滾樂的研究當中,對崔健的研究無疑佔據了最大的比重。有趣的是,崔健與知識份子/文人和樂評人對他的解讀之間一直存在著微妙的對峙,或者說,大部分研究著述對崔健的解讀,都與崔健自己在訪談中針對「搖滾」的「本質」和自己的具體創作所發表的觀點之間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錯位」。
比如,崔健一直反覆強調《一無所有》只是一首單純的情歌,但這首歌在之後卻經歷了一個被不斷經典化的過程,並被指認為「喊出了一個時代的感受,觸動了時代最敏感的一根神經」;崔健曾經將搖滾樂的本質和魅力來源概括為身體性和娛樂功能,但是在知識份子/文人眼中,他的音樂文本顯然屬於八十年代公共知識份子話語體系的一部分,承載著嚴肅的歷史反思和現實批判的任務,肩負著啟蒙大眾和為公眾代言的使命;崔健一直試圖淡化自己歌曲中的意識形態色彩,聲稱自己「不想跟任何人較勁」,但他的歌曲卻不斷被加以政治化的解讀,被視為一種「對立面的藝術」。
以上這些「錯位」的形成有著異常錯綜複雜的原因,其中肯定有研究者「誤讀」的成分(如美國學者Andrew F. Jones將《一無所有》中的「你」解讀為「壓抑的結構性力量」,就是明顯的「過度詮釋」),也存在崔健為了規避與官方話語發生直接衝突而選擇的表達策略的因素(如崔健曾否認《一塊紅布》中存在意識形態內涵),以及在對一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的差異造成的歧義(如崔健對何為「娛樂功能」有其非常獨特的理解)。在此,我無意去辨析在對於崔健的解讀中究竟有多少「誤讀」的成分,崔健的自我辯解中又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存在,我更為關心的其實是這種「錯位」和「誤讀」形成的原因。
關於搖滾樂的本質,崔健有一個著名的三「自」論斷:「我曾經把搖滾樂能夠給人的感覺概括為三個『自』,就是:自信——別丟掉自己;自然——別勉強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在崔健的闡釋中,無論是「自信」、「自然」還是「自由」,都是圍繞著「自己」展開的。換言之,對於崔健來說,搖滾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幫助他尋找、確立和面對自我。
關於崔健的「自我」,張新穎在《中國當代文化反抗的流變——從北島到崔健到王朔》一文中曾經通過對崔健與北島的對比分析指出:「在北島那裏,自我是一個明確的概念……而在崔健那裏,自我則是一個等待明確又不可能明確的概念,它是一個正在展開的動態過程,無法定論。反叛確立了北島的自我,崔健用它展開了自我。」在我看來,這個觀點中最具有啟發性的部分是「崔健用反叛展開自我」這一提法。關於「反叛」,崔健自己曾經這樣說過:「我覺得我的音樂非常簡單,它是反對一切讓人們丟失了自己的東西。
它可能是錢,可能是傳統觀念,可能是法律,可能是宗教,可能是政治,甚至可能是搖滾樂本身……有一天我可能會反對任何東西。可能會反對機會,因為人們看重機會;可能會反對毒品,因為有些人吸毒;可能會反對知識,因為有些人自命高深。也許我要的是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要反對什麼。
這就是搖滾樂,是我理解的搖滾樂。」將張新穎的分析與崔健的闡述相互印證,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於崔健來說,反抗不是目的——對此崔健在歌曲中曾有過多次「表白」:「不願與任何人作對」(《假行僧》),「不是天生愛較勁」(《時代的晚上》)——而是尋找和確立「自我」最重要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崔健的全部音樂創作確實可以被視為一種「對立面的藝術」,只不過這裏的「對立面」並不僅僅是主流意識形態和官方話語,而是隨著時代和藝術家自身的變化在不斷地發生變化。
按照這條線索,我將崔健迄今為止出版的五張個人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一九八九)、《解決》(一九九二)、《紅旗下的蛋》(一九九四)、《無能的力量》(一九九八),以及《給你一點顏色》(二○○五)劃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分析。第一個階段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與《解決》時期。這一時期,崔健的音樂文本所處理的主要是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從關於歷史和政治的宏大?事中贖回既往被壓抑、被「消聲」的主體,「自我」的確立是在對「革命歷史」的迷戀、質疑、反思和再?述的過程中實現的;「出走」的衝動是這一時期創作的一大主題,也是崔健找到的確立自我的正面途徑。
《紅旗下的蛋》可以被視為崔健創作的第二階段,也是崔健創作中一個「過渡性」和「轉折性」的階段。從《紅旗下的蛋》開始,崔健有意識地告別歷史,告別已經成為「崔健標誌」的文體和修辭手法——逆向的「政治抒情詩」與以個人方式對「紅色話語」的再?述。《無能的力量》和《給你一點顏色》可以被視為崔健創作的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與時代的對峙取代了與歷史的糾纏,成為了崔健的新姿態;「腐朽的魅力」取代了「一塊紅布」,成為了崔健反抗的新對象;而「飛不起來了」的崔健,用「看」代替了「走」,作為確立自我的新的手段。
《給你一點顏色》發行於二○○五年,與之前幾張專輯間隔的時間較長,從表面上來看也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如果說崔健以往作品中的「我」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找到崔健自己的影子,新專輯中的「我」已經化身為「城市船夫」、「網路處男」、按摩女郎、農民和小城文化青年等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以往崔健標誌性的、刻意含混不清的北京大院口音,也被唐山、河南、山東等各地方言口音所取代。但在我看來,這張專輯有著與前一張專輯一脈相承的問題意識:《無能的力量》中的「遺留問題」是如何準確地把握自身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給你一點顏色》依然承續了這一尚未被充分解決的問題,只是嘗試了另一種「突進」的方式,雖然這嘗試也許並不那麼成功。
1 踏上新長征路
聽說過 沒見過 兩萬五千里
有的說 沒的做 怎知不容易
埋著頭 向前走 尋找我自己
走過來 走過去 沒有根據地
——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在我看來,歌曲《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可以作為崔健這一時期創作主題的一個精准的概括: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既往作為自己這一代人主體建構最重要的資源的、關於革命的宏大?事,並在這個基礎上「尋找我自己」,重建起新的主體。在這裏我首先想通過對歌曲《南泥灣》的分析,探究關於文革的「紅色記憶」在崔健的主體建構中到底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南泥灣》 辨析「紅色搖滾」
既往的研究者往往傾向於將崔健演唱的《南泥灣》視為一種對「紅色話語」的戲仿、挑釁和顛覆。如有研究者認為:「崔健對《南泥灣》的重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集體強國夢的焦慮的浸潤下,將其被規定的所指置換成了抑制國家進步個人獨立的障礙,被急切地加以揚棄和背叛。以新的理想主義埋葬舊的理想主義的呼聲在《南泥灣》的搖滾樂聲中,得到激烈暢快的宣洩。」
持類似看法的還有加拿大學者胡可麗(Claire Huot),在她看來,崔健版本的《南泥灣》之所以被視為「有問題的」,不僅在於崔健將這首歌改寫成了一首搖滾歌曲,還在於原本樂觀的、歡快的黨的頌歌,變成了一首「聽起來好似葬歌的布魯斯歌曲」。然而在我看來,這樣的分析多少有些隔靴搔癢之感,下面我將通過對四首「紅色搖滾」歌曲的具體分析,結合崔健的自我闡述和創作背景,辨析《南泥灣》中對「紅色話語」的挪用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意識形態內涵。
「紅色搖滾」指的是以搖滾樂的編曲、配器和演唱方式,對已經成為「紅色經典」的革命歌曲的重新演繹。它是中國搖滾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其產生的較有影響力的作品包括:崔健的《南泥灣》、張楚的《社會主義好》、唐朝樂隊的《國際歌》,以及竇唯的《高級動物》(翻唱了《幸福在哪裡》的副歌部分)等。在我看來,上述對《南泥灣》的分析可能更適用於張楚和竇唯的個案。
張楚演唱的《社會主義好》收錄在一九九二年由北京電影學院音像出版社發行的《紅色搖滾》合輯中。在這首歌中,張楚採用了一種與他後來的作品中平靜、內斂的唱腔完全不同的,聲嘶力竭的、在情感上近乎歇斯底里的演唱方式。此外,在「社會主義好」、「人民地位高」這兩句歌詞中,張楚將之前放在「社會主義」、「人民地位」上的重音完全轉移到了「好」字和「高」字上,並將這兩個字原本上揚的、歡快的語調處理為下滑的、激憤的語調,造成了一種強烈的質疑和反諷效果。儘管對歌詞一字未易,但受眾依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中的聲音編碼進行解碼,「破譯」出其中挑釁性、抵抗性和顛覆性的情感資訊。
與此相似的還有竇唯的《高級動物》,在這首歌中,竇唯在羅列了「矛盾,虛偽,貪婪,欺騙,幻想,疑惑,簡單,善變」等四十八組二字形容詞,並做出「高級動物」的人性判斷之後,忽然近乎開玩笑般地植入了八十年代傳唱一時的歌曲《幸福在哪裡》的開篇「幸福在哪裡」的歌詞和旋律。儘管《幸福在哪裡》並非來自真正的「革命年代」,也非嚴格意義上的「紅色經典」,但它的原唱者的「身份」(殷秀梅,總政歌舞團歌唱演員)、誕生的場合(一九八四年春節聯歡晚會)都使它染上了一層濃厚的「官方」色彩。
而歌詞的內容與演唱風格,更使之與誕生於同時期的,由張振富和耿蓮鳳演唱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一樣,承擔著一種將「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詢喚為發展經濟時代新的建設主體的功能。在竇唯的演唱中,他用一種冷靜、疏離、近乎喃喃自語的唱腔取代了原唱字正腔圓、高亢清越的演唱風格,使之籠罩上了一層「黑夢」般的色彩。而竇唯在這裏將原歌的第一句歌詞放在了最後一句反覆吟唱的做法,更是通過對上下文關係的改變,使「幸福在哪裡」由原本用以引出意識形態教誨的設問句,變成了沒有答案的反問句,從而傳達出了一種迷惘、懷疑的顛覆性情感資訊。
一九九二年發行的唐朝樂隊的第一張專輯《夢回唐朝》中收錄了「搖滾版本」的《國際歌》,這首日後被追認為中國搖滾史上的經典之一的作品在當時曾引發了一場爭議。一九九三年《人民音樂》第三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國際歌》不容「搖滾」〉的文章,作者用頗為激烈的語氣對「四位長髮披肩者」將作為「英特納雄奈爾的不朽頌歌」的《國際歌》「套上重金屬色彩,披上搖滾外衣」的行為表示了不滿。接下來,作者錯誤百出地「杜撰」了一個作為「爵士樂的一種」,「活躍在酒吧、妓院」,「具有散漫、狂躁、頹唐、神經質的作派及樂隊形式,早在四十年代就走入低谷、陷入絕境」的西方搖滾樂歷史。
在作者看來,「它(《國際歌》)那嚴肅的革命內容,嚴謹、完美的形式特徵和莊嚴、雄偉的音樂表情,是相互統一的,是在革命的烈火中,在一百多年的傳唱實踐中固定下來的,不容作任何形式的改變」,而其對於「唐朝版」《國際歌》批評的主要依據則是「一切公正的朋友們都不難清楚地感受到,這種?喊之聲,這種宣洩之情,哪裡能和《國際歌》的內涵和情操同日而語,又怎麼能和革命先烈們高唱《國際歌》英勇就義的悲壯之情相提並論呢!」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數月,《人民音樂》上發表了一篇反批評文章《關於國際歌不容「搖滾」一文的意見》,《關》一文的作者首先指出了《國》一文在西方搖滾樂歷史方面的數處知識性硬傷,接著發表了對「唐朝版」《國際歌》的意見:「從個人的藝術觀點出發,我不贊成這種演釋,因為作品的體裁、內容和演唱形式三者之間的差異太大,故三者硬湊在一起就給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但作者以一種貌似客觀中立的姿態提出了「最聰明的做法應當是:幫助和引導青少年從喜愛搖滾音樂這一簡單的藝術形式,轉而欣賞層次較高的藝術作品」的「解決方案」。
無論是激烈的反對,還是「高姿態」的「寬容」,這兩篇文章在本質上是殊途同歸的——它們都試圖將《國際歌》與「搖滾」劃歸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異質的、互斥的音樂類型(「不可同日而語」、「硬湊」、「不倫不類」)。表面上看,唐朝樂隊的重新演繹對「原版」《國際歌》所做出的變更,以及以上兩篇批評文章的著眼點,都主要集中在歌曲的「形式」方面,但我認為無論是「改編」這一行為本身,還是圍繞它產生的論爭,其本質都是在爭奪闡釋「革命」的話語權。
「唐朝版」《國際歌》誕生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席捲中國的「毛澤東熱」的歷史語境之中。唐朝樂隊對《國際歌》的翻唱,在總體上有著和這場熱潮相一致的內驅力——為了回應八九十年代之交急劇商品化之後迅速拉大的貧富差距,填補在信仰和意識形態失落後許多人所經驗過的精神真空,通過復興革命黃金時代的理想主義信念建構出一種想像中的,「四海兄弟、天下大同」的虛擬社群感,其背後的指向其實是相當「革命」和「英特納雄奈爾」的。
這首歌之所以被視為一種「僭越」和「冒犯」,並不是因為它要顛覆歌曲原來所傳達的意識形態內涵,而是因為它要爭奪對於「革命」、「共產主義」等「神聖所指」的闡釋權和話語權,這一點可以非常清楚地從樂隊對歌曲在演唱方面的編排方式體現出來。原版《國際歌》採用了合唱的演唱形式,唐朝樂隊的版本一反搖滾樂「通行」的主唱演唱、樂隊伴奏的做法,在大體上延續了「合唱」這一形式,這樣做無疑是為了更加凸顯唯一的一句獨唱的內容。
依據這樣的演唱編排,當主唱丁武以其極具穿透力的嗓音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的時候,被非常清晰有力地傳達給聽眾的資訊是對「救世主」和「神仙皇帝」的懷疑與拒斥,以及要從經過「神仙皇帝」的改寫和架空,被蒙上一層正統(「嚴謹、完美的形式特徵和莊嚴、雄偉的音樂表情」)、權威(「不容作任何形式的改變」)色彩的,業已蛻變為「救世主」自我神話工具的歷史?事(「革命先烈們高唱《國際歌》英勇就義」)中「搶救」出其原初的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內涵,並「還原」其激進的、異端的美學特質的願望。
與以上三個個案相比,作為中國「紅色搖滾」開山之作的「崔健版」《南泥灣》所引發的風波簡直可以稱得上是「歪打正著」的「無心之失」。一九八七年崔健在首都體育館演唱了《南泥灣》,歌中頌揚的三五九旅的旅長王震憤然離席而去,不久崔健就接到其所在單位北京歌舞團「必須限期離職」的口頭通知。然而今天我們再來重聽這首歌曲時(收錄在一九九二年發行的專輯《解決》中),難免會對其當初引起的軒然大波感到不解。
事實上,「崔健版」的《南泥灣》可以說是整張專輯中最少「搖滾」色彩的一首歌——對比郭蘭英的原唱,崔健做出的主要改動有二:其一是通過在兩段歌詞之間加入間奏,放慢了整首歌的速度,其二是用與李谷一演唱《鄉戀》類似的「氣聲」唱法,以婉轉綿軟的風格代替了原唱「高、快、硬、響」的風格。我們很難在這兩處改動中找到任何「顛覆」和「戲仿」的味道,甚至可以說其與崔健所一向反對的「甜歌蜜曲」帶有一無二致的抒情風格,只不過是把抒情的對象由「戀人」變成了「革命歷史」,抒情的性質由男女之情變為了家國之情。
在與周國平的訪談中,崔健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小時候覺得特幸福。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特高興。老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自己沒挨過餓,沒吃過食堂……現在想起來還覺得特幸福,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一點兒都不誇張,玩兒,不光是覺得外國的小孩沒我們幸福,農村的小孩也沒我們幸福。我們都是院兒裏的,我爸是軍人,我媽是中央的,中央歌舞團嘛。」
崔健在這裏引用了姜文導演的,改編自王朔小說《動物兇猛》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標題來描述他的「紅色記憶」並不是一個偶然,可以從側面印證這一點的是,姜文在追溯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創作動因的時候曾經以與崔健上文的回憶如出一轍的方式描繪了自己的童年/少年記憶:「那時的天比現在藍,雲比現在白,陽光比現在暖。我覺得那時好像不下雨,沒有雨季。那時不管做了什麼事,現在回憶起來挺讓人留戀,挺美好。我就隨著這個心理去拍這個片子的。」
事實上,崔健、姜文和王朔的確分享著崔健口中的「院兒裏的」這樣一個共同的「紅色貴族血統」和童年/少年經驗,他們都是軍人家庭出身,在日漸衰敗的老北京「胡同族」的孩子們紛紛上山下鄉之時,作為北京「新貴」後代的他們卻在世外桃源般的「院兒裏」(部隊大院)度過了無憂無慮的青少年時光。這種經歷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他們對作為「紅色記憶」策源地的革命意識形態的態度——必定帶有或多或少的「敬意」和「認同」,或至少是曖昧的。
在訪談中崔健曾談及伏尼契的《牛虻》對自己的影響「我記得我小時候看《牛虻》就有這樣的高潮,愛不釋手,我喜歡當牛虻,臉上有塊疤什麼的都覺得酷,就那種感覺。」在「牛虻」身上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私人倫理與公共倫理之間相互衝突,又互為酵素的關係,一直是貫穿崔健之後創作的一個線索。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崔健就是「牛虻」:「革命者」中的「異端」,但本質上依然是一個革命者。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