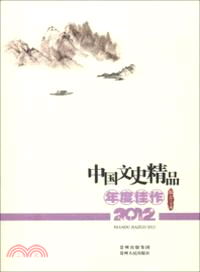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精選2012年全國各地報刊和網站中的一些好的文史精品佳作,內容涉及古今中外,講究思想、趣味、探秘。
作者簡介
耿立,原名石耿立,山東鄄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菏澤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出版過多部詩集、散文集和學術著作,是國內有影響的學者、散文家和詩人;山東省社科人文基地:水滸文化研究基地負責人。作品多次名列“中國散文排行榜”、“中國隨筆排行榜”、“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和“華人優秀散文排行榜”;曾獲第四屆冰心文學獎、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泰山文藝獎(文學創作獎)、“中山杯”華僑華人文學獎。
名人/編輯推薦
《中國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2)》是一部文史作品集,選編了2012年度最佳文史作品24篇,包括:諸榮會的《張之洞:文化“釘子戶”》、吳思的《德國人如何對待歷史》、范亦豪的《貓城斷想》、秦暉的《從俄國到中國》等。
序
去觸摸那些靈魂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多年了,我為友人朗誦詩歌《透明的夜》的時間地點已經渾然忘卻,在前幾日的聚會中,友人說還記得當年我朗誦這詩的言語腔調和夸張的舉止;在寫作《赳赳民國》序言時,腦子里驀然蹦出的就是:“走/到牛殺場,/去/喝牛肉湯……”
毫無來由,毫無端倪,真的是無端冒出的嗎?其實是艾青這詩歌營造的那氣氛正合我寫序時胸中的郁郁之氣。
我還完整地記得這詩,第一節只突兀的一行:透明的夜。如凡·高畫筆下的夜,纏繞旋轉而魅惑人,一下子籠罩了你的全身,你的前后左右,呼吸與發際,好似都是那夜,連腸道里都是那夜:酒徒的闊笑,狗的吠聲,醒的酒坊,野火一樣的燈,血的氣息,人的囂喧,泥色的語言,血染的手臂和頭顱,火一般的肌肉和里面的痛苦,憤怒和仇恨的力,夜的醒者、醉漢、流浪客、過路的盜、偷牛的賊……向沉睡的原野嘩然走去……這些濺射著火和血的鮮活的形象,動態和語言,是那么生猛鮮活,好像涌動的沸騰的血潑在雪野上,吱吱地冒泡。
這是我記憶的民國的群像,那么生機勃勃又滿是苦難的民國,那些民國的人物如黑鐵和礁石一樣深深鍥入黑沉沉的夜,如木刻的版畫,把這些靈魂突顯出來。
按一般的理解,民國的時間段只短短的三十八年,從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年。但在人們的心理時間上,這段民國的歷史好像很長。
這是皇權旁落專制蕭索的時代,這是民主和自由的種子落地的時代,這也是饑饉災荒連結、兵爨烽火四起的時代,這是異族比賽百人斬以中國人的血洗刀的時代。狄更斯《雙城記》的話,又一次擊中我: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這歷史像極了勃蘭兌斯在描述十九世紀歐洲的流亡作家時說的話:“這些人站在新世紀的曙光中……我感到他們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之夜,他們的臉色蒼白而嚴肅。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郁引人同情,他們不能不繼續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而且費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來”。“不得不懷著疑慮繼續生活”,是穿長衫把手指咬破的學生在1919年天安門廣場面對世界的基本方式,他們的血在熱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蛻變;而世界,那冰冷的歷史難道真的就是要用血而溫熱嗎?隨后就有劉和珍君的血再一次灑在歷史的廣場,人們說“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愿的學生之后,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處罰了兇手,并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我讀過《另一個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孫女張乃惠說: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并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請你們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開槍殺人,他何必這樣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卻不顧自己的痛苦,長跪不起。
魯迅曾說這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魯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對這樣的說法,我是懷疑的。段祺瑞孫女的說法是靠不住的,有的人已經考證段祺瑞根本根本就沒有出現在悼念大會上,更遑論什么“當眾長跪不起”了。
從這件事,我想到作為一個后來者應該怎樣對那些苦難歷史進行敘述和還原呢?在劫難過后,我們的民族和歷史應該以怎樣的姿態和苦難對視?為過往的歷史結賬?我們是該把苦難作為終點而輕易滑過放過,還是以苦難為起點?想苦難盡快結束,為苦難安放一個溫暖的詩意的尾巴,無疑是孱頭。應從苦難出發,在我們民族心靈里找出苦難的源頭;面對苦難,不是與苦難和解,而是最終消滅苦難,在我們民族的記憶里反芻苦難、舔舐苦難、咀嚼苦難;對苦難的制造者一個也不放過,拒絕合唱、拒絕趨附、拒絕屈從。用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從痛苦中產生對痛苦的愛,用痛苦的烈焰溫暖著他的時代和人世”,一個作家可以用愛擁抱歷史,但不要被愛燒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們不是記住仇恨,我們只是追尋那些痛苦的來路,我們拒絕遺忘。
各人進入歷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選擇了自己的方式進入民國,直面那些曾經過往的靈魂,不是風花雪月,只想揀拾那些骨頭,那些卡住歷史喉嚨的骨頭,那些讓對手如鯁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頭。
短短的民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是歷史為這個民族淬火的時代。文人星璨,猛將如云。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的汪精衛周作人胡蘭成等脊椎軟化的一族,更有張自忠趙登禹血涌于頂的慷慨悲歌之士。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的話,深得吾心:
“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裂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臟污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圣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未嘗騙來騙去,而至于絕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試溯舊史,輒至感慨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己。”
確是在民國的時代,那也是漢奸遍地梟雄遍地的時代,那也是我們民族毒瘤潰敗的時代。雖然我不是道德論者,一個腐朽的政權是不應該要求他的子民效命的,但生在這片土地的人,是應該愛這片文化的江山,有著我們祖塋和先民尸骨的土地。
但我又想愛國是應講究邏輯的,國家至上主義要求國家的子民為這個國家生為這個國家死。但這個國家怎樣愛自己的子民卻一直是遮蔽隱匿的,語焉不詳。愛國的前提是這個國家愛自己的子民,舍此,那愛國就變成了一個虛幻的騙局。
歷史是個巨大的黑洞,有時在夜深時分,我常常披衣而起,徘徊斗室,長嘯復長嘯。我常常咀嚼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從秦漢及至清末,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大轉型,由帝國轉為民國,用唐先生的話說便是: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我有時懷疑,對歷史洞徹的唐先生,真的能預測出歷史三峽有多長嗎?真有一雙高手在我們民族的背后撥弄么?歷史有時是詭異的,有時偶然才是必然。關注民國的那段歷史,是關注那些人,關注那些事件背后的人性的高度和人性的污濁。這是歷史三峽中最驚心動魄的時段,可以說是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但這段歷史曾一度被人們遺忘,甚至扭曲,我常想,這些民國的人與事消失了嗎?是否早已遁形于虛無?我知道,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茍活,為了眼前的殘羹冷炙,總是繞著走躲著走,盡量閃避,歷史成了一段古為今用的服從指令的弄虛作假,歷史成了假面舞會的俱樂部。歷史的臉皮已經偽飾得很厚,我們很難看到歷史臉蛋的本色。
但我深知,對某些人與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恥辱,為了歷史的尊嚴和寫作的尊嚴,總有人要寫。在某些苦難面前閉眼是可恥的,那是對精神最大的戕害,也是對人性最大的戕害。
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的人性?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我們應該有的良知?對待我們民族流過的血,所受過的苦難,我們是否有過心悸和反思,是否有過熱淚與痛哭?
面對著民國的那些豐沛的生命,我們只有對那些崇高的生命表達出敬意,對那些丑惡的靈魂表達出最大的鄙夷,我們才能獲得良心的安寧。歷史也有公平正義,讓該得到的評價得到,讓該開放的鮮花開放,正是那些亡靈所欣慰的。
其實無論社會如何走向,人性中,那些自然的本性,是我最關注的,雖然,人為的意識形態的文化的在異化著人,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說:“生命是自然賦予人類的,我們有著自然給予的腦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學反應,我們生命內容的90%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點屬于人為。”
但我認為,人為的部分中,也一樣有著合乎自然的東西,比如愛,比如對弱小者的同情與呵護,比如對丑惡的鞭撻和厭惡。
我常想一個人的文字是應該關乎心靈的,這也是合乎自然之道,這正如我讀到的《透明的夜》那樣的感覺: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走,我們走到民國去,去觸摸那些靈魂。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多年了,我為友人朗誦詩歌《透明的夜》的時間地點已經渾然忘卻,在前幾日的聚會中,友人說還記得當年我朗誦這詩的言語腔調和夸張的舉止;在寫作《赳赳民國》序言時,腦子里驀然蹦出的就是:“走/到牛殺場,/去/喝牛肉湯……”
毫無來由,毫無端倪,真的是無端冒出的嗎?其實是艾青這詩歌營造的那氣氛正合我寫序時胸中的郁郁之氣。
我還完整地記得這詩,第一節只突兀的一行:透明的夜。如凡·高畫筆下的夜,纏繞旋轉而魅惑人,一下子籠罩了你的全身,你的前后左右,呼吸與發際,好似都是那夜,連腸道里都是那夜:酒徒的闊笑,狗的吠聲,醒的酒坊,野火一樣的燈,血的氣息,人的囂喧,泥色的語言,血染的手臂和頭顱,火一般的肌肉和里面的痛苦,憤怒和仇恨的力,夜的醒者、醉漢、流浪客、過路的盜、偷牛的賊……向沉睡的原野嘩然走去……這些濺射著火和血的鮮活的形象,動態和語言,是那么生猛鮮活,好像涌動的沸騰的血潑在雪野上,吱吱地冒泡。
這是我記憶的民國的群像,那么生機勃勃又滿是苦難的民國,那些民國的人物如黑鐵和礁石一樣深深鍥入黑沉沉的夜,如木刻的版畫,把這些靈魂突顯出來。
按一般的理解,民國的時間段只短短的三十八年,從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年。但在人們的心理時間上,這段民國的歷史好像很長。
這是皇權旁落專制蕭索的時代,這是民主和自由的種子落地的時代,這也是饑饉災荒連結、兵爨烽火四起的時代,這是異族比賽百人斬以中國人的血洗刀的時代。狄更斯《雙城記》的話,又一次擊中我: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這歷史像極了勃蘭兌斯在描述十九世紀歐洲的流亡作家時說的話:“這些人站在新世紀的曙光中……我感到他們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之夜,他們的臉色蒼白而嚴肅。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郁引人同情,他們不能不繼續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而且費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來”。“不得不懷著疑慮繼續生活”,是穿長衫把手指咬破的學生在1919年天安門廣場面對世界的基本方式,他們的血在熱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蛻變;而世界,那冰冷的歷史難道真的就是要用血而溫熱嗎?隨后就有劉和珍君的血再一次灑在歷史的廣場,人們說“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愿的學生之后,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后又處罰了兇手,并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我讀過《另一個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孫女張乃惠說: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并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請你們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開槍殺人,他何必這樣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卻不顧自己的痛苦,長跪不起。
魯迅曾說這是民國最黑暗的一天,魯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對這樣的說法,我是懷疑的。段祺瑞孫女的說法是靠不住的,有的人已經考證段祺瑞根本根本就沒有出現在悼念大會上,更遑論什么“當眾長跪不起”了。
從這件事,我想到作為一個后來者應該怎樣對那些苦難歷史進行敘述和還原呢?在劫難過后,我們的民族和歷史應該以怎樣的姿態和苦難對視?為過往的歷史結賬?我們是該把苦難作為終點而輕易滑過放過,還是以苦難為起點?想苦難盡快結束,為苦難安放一個溫暖的詩意的尾巴,無疑是孱頭。應從苦難出發,在我們民族心靈里找出苦難的源頭;面對苦難,不是與苦難和解,而是最終消滅苦難,在我們民族的記憶里反芻苦難、舔舐苦難、咀嚼苦難;對苦難的制造者一個也不放過,拒絕合唱、拒絕趨附、拒絕屈從。用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給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傳記中的話來說就是“從痛苦中產生對痛苦的愛,用痛苦的烈焰溫暖著他的時代和人世”,一個作家可以用愛擁抱歷史,但不要被愛燒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們不是記住仇恨,我們只是追尋那些痛苦的來路,我們拒絕遺忘。
各人進入歷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選擇了自己的方式進入民國,直面那些曾經過往的靈魂,不是風花雪月,只想揀拾那些骨頭,那些卡住歷史喉嚨的骨頭,那些讓對手如鯁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頭。
短短的民國,是人才輩出的時代,是歷史為這個民族淬火的時代。文人星璨,猛將如云。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的汪精衛周作人胡蘭成等脊椎軟化的一族,更有張自忠趙登禹血涌于頂的慷慨悲歌之士。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的話,深得吾心:
“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裂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臟污染之外,一無可取。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圣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未嘗騙來騙去,而至于絕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試溯舊史,輒至感慨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己。”
確是在民國的時代,那也是漢奸遍地梟雄遍地的時代,那也是我們民族毒瘤潰敗的時代。雖然我不是道德論者,一個腐朽的政權是不應該要求他的子民效命的,但生在這片土地的人,是應該愛這片文化的江山,有著我們祖塋和先民尸骨的土地。
但我又想愛國是應講究邏輯的,國家至上主義要求國家的子民為這個國家生為這個國家死。但這個國家怎樣愛自己的子民卻一直是遮蔽隱匿的,語焉不詳。愛國的前提是這個國家愛自己的子民,舍此,那愛國就變成了一個虛幻的騙局。
歷史是個巨大的黑洞,有時在夜深時分,我常常披衣而起,徘徊斗室,長嘯復長嘯。我常常咀嚼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從秦漢及至清末,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大轉型,由帝國轉為民國,用唐先生的話說便是: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我有時懷疑,對歷史洞徹的唐先生,真的能預測出歷史三峽有多長嗎?真有一雙高手在我們民族的背后撥弄么?歷史有時是詭異的,有時偶然才是必然。關注民國的那段歷史,是關注那些人,關注那些事件背后的人性的高度和人性的污濁。這是歷史三峽中最驚心動魄的時段,可以說是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但這段歷史曾一度被人們遺忘,甚至扭曲,我常想,這些民國的人與事消失了嗎?是否早已遁形于虛無?我知道,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茍活,為了眼前的殘羹冷炙,總是繞著走躲著走,盡量閃避,歷史成了一段古為今用的服從指令的弄虛作假,歷史成了假面舞會的俱樂部。歷史的臉皮已經偽飾得很厚,我們很難看到歷史臉蛋的本色。
但我深知,對某些人與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恥辱,為了歷史的尊嚴和寫作的尊嚴,總有人要寫。在某些苦難面前閉眼是可恥的,那是對精神最大的戕害,也是對人性最大的戕害。
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的人性?誰能測度出歷史深處我們應該有的良知?對待我們民族流過的血,所受過的苦難,我們是否有過心悸和反思,是否有過熱淚與痛哭?
面對著民國的那些豐沛的生命,我們只有對那些崇高的生命表達出敬意,對那些丑惡的靈魂表達出最大的鄙夷,我們才能獲得良心的安寧。歷史也有公平正義,讓該得到的評價得到,讓該開放的鮮花開放,正是那些亡靈所欣慰的。
其實無論社會如何走向,人性中,那些自然的本性,是我最關注的,雖然,人為的意識形態的文化的在異化著人,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說:“生命是自然賦予人類的,我們有著自然給予的腦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學反應,我們生命內容的90%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點屬于人為。”
但我認為,人為的部分中,也一樣有著合乎自然的東西,比如愛,比如對弱小者的同情與呵護,比如對丑惡的鞭撻和厭惡。
我常想一個人的文字是應該關乎心靈的,這也是合乎自然之道,這正如我讀到的《透明的夜》那樣的感覺:
走
到牛殺場,去
喝牛肉湯……
走,我們走到民國去,去觸摸那些靈魂。
目次
去觸摸那些靈魂(代序)/耿立張之洞:文化“釘子戶”/諸榮會秋瑾:襟抱誰識?/耿立德國人如何對待歷史/吳思“餓鄉”:一個被忽略的讖語/蒼耳遺民,苦悶/李潔非張競生其人,張培忠其文/任啟發貓城斷想/范亦豪名將中的貴族(外四篇)/喬良事實比杜撰更離奇/哈米天安門城樓秘密翻建始末/陳徒手革命者托洛茨基之死/章魯生“不死鳥”張奚若/王開林蕭紅:文字與人生一起脫軌/王鶴追尋一個曠世悲劇/哈米徐凱倫“在三顆雞蛋上跳舞”的閻錫山/陳為人“總不能停止寫吧”/李木生從俄國到中國/秦暉西哈努克VS波爾布特:恩恩怨怨半世紀/張慧南懷瑾:亦儒非儒是佛非佛/彭蘇警惕科技迷信/田松沒有深夜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靜有關“知青”的記憶和思考/周大偉駐足國殤墓園/李雪晴浴血松山/李雪晴
書摘/試閱
毛澤東很年輕時曾參加過湖南新軍,在編于混成協(旅)五十標第一營左隊,在那兒他領得了生平第一支屬于自己的槍——一支“漢陽造”步槍,槍號8341。四十年后,中共中央成立警衛團,要毛澤東為之取番號,他情不自禁想起了那支編號為8341的步槍,就用那個槍號作了中央警衛團的番號,為此中央警衛團在1964年之后又被稱為“8341部隊”。雖幾經改變,仍回到這里——由此可想而知,那支“漢陽造”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幾年后,毛澤東先后兩次視察大冶鐵廠——對同一座工廠視察兩次,這對**來說并不多見——由此也可想而知,大冶鐵廠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毛澤東使用過的那支編號8341的步槍為漢陽兵工廠生產,工廠創始人是張之洞;毛澤東兩次視察的大冶鐵廠,其創始人也是張之洞。毛澤東有一次在回顧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時,曾滿懷深情地說,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不能忘記的,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由此更可想而知,張之洞在毛澤東心中的分量。
張之洞,一個生命幾乎與中國近代史等長的人物。
一般人對于他的了解恐怕就只在兩個方面:其一他是晚清的所謂“中興名臣”之一,后期“洋務派”代表人物;其二近代許多實業和大學都曾是他創辦的,如漢陽兵工廠、大冶鐵廠、盧漢鐵路、三江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
其實,張之洞的一生極其復雜,他的人生面目也是遠不止此兩者,他在歷史的許多時段所扮演的角色有時與我們所熟知的實業家形象很是不同,甚至恰恰相反。
近代實業家、晚清權臣的張之洞原本屬于朝中清流,且由此而發跡。這一點他與晚清另幾位所謂“中興名臣”、“洋務派”人物很不相同。
無論是曾國藩、胡林翼,還是李鴻章、左宗棠等世人眼中的“洋務派”,他們雖然也都有或高或低的科舉功名,但是他們最后崛起于晚清政壇,說穿了靠的還是他們鎮壓農民起義中取得的所謂“軍功”;而張之洞不同,他1863年考取“探花”,很快在朝中成為了清流領袖,然后下派任山西巡撫,后又擢升兩廣總督等,成了清廷真正的封疆大吏——這一切他并沒靠“軍功”。
對于清流,有一句現成話人們用來對其進行攻擊是最有殺傷力的:“清談誤國。”我想張之洞不可能不知道世上有這么一句話。但是成為一名清流似乎是他的人生必然,甚至是他的宿命。當然清流也不是誰想做就能做也做得了的,得有資格。
這資格首先便是其文化的優勢。張之洞祖籍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是唐朝名相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第39代孫,元代著名散曲作家張養浩第16代孫;出生時,其父張锳任貴州省興義知府,所以其少時在貴州興義府署度過。生長于書香門第、官宦之家的張之洞,從小接受的教育自然良好,而他本人也博聞強識,文才出眾,年方十一,即為貴州全省學童之冠,作《半山亭記》,名噪一時。此記全文,刻于安龍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歲在貴陽出版第一本詩文集。咸豐三年(1852),回直隸南皮應順天鄉試,名列榜首,成為解元。同治二年(1863)很順利考中進士第三,即成了探花,后歷任翰林院編修、教習、侍讀、侍講學士及內閣學士等職。如此科舉業績,自然讓張之洞充滿了一種文化優越感。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