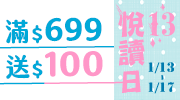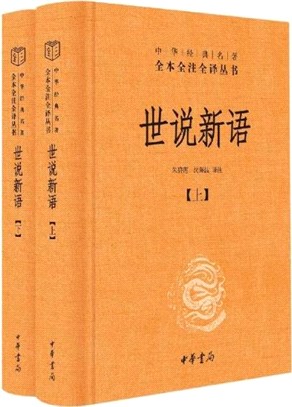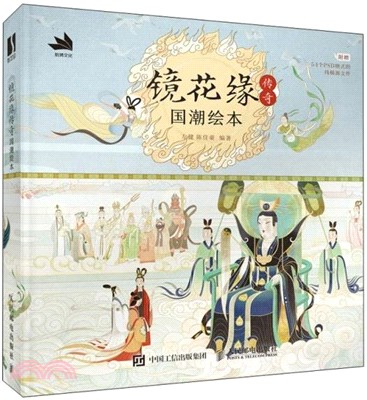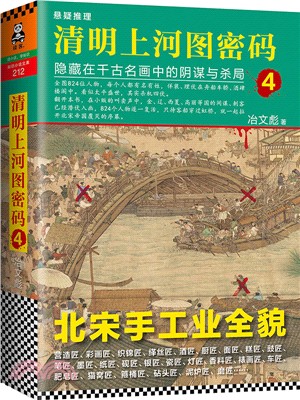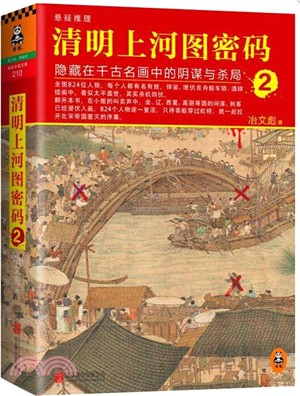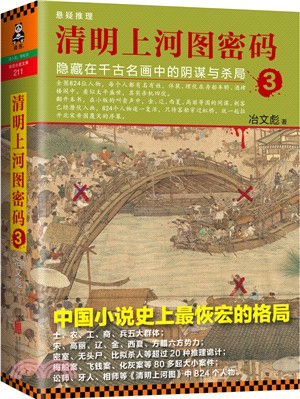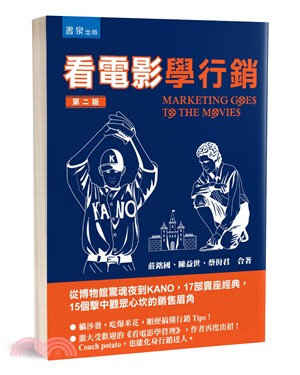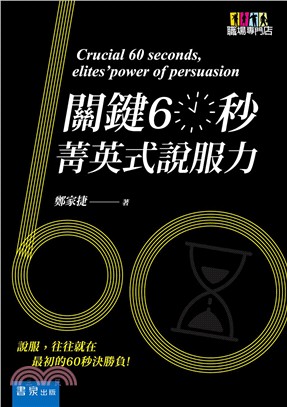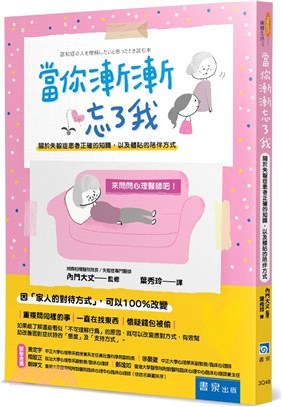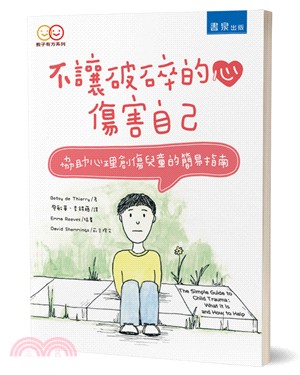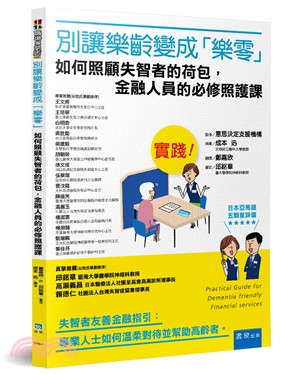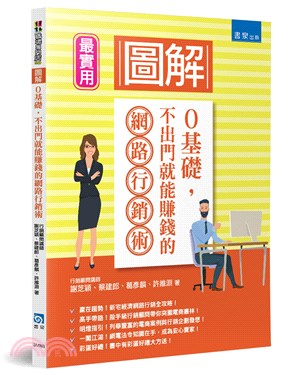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序言 《這世界總有我們的一塊地兒吧》黃佟佟
序言 《我眼中的麒淩》莊瓊花
《白衣》
她把手輕輕地放在上面,
這一刻她在思量,這一生她在思量——
翻開,還是不翻開。
《擦肩》
她哪裡會想到,她騙他,真的騙了一輩子。
該如何,讓他知道,她愛他。
卻原來,年華是一倏忽的事,生命是一倏忽的事,真的來不及。
再也來不及。
《不是相思,是紅豆杉》
“上次你問的那棵樹,女耗子精那棵,不是相思樹。”
“不是相思,是什麼呢?”
“紅豆杉,我當面更正了,這可是件重要的事兒。”
《隱身》
人世間,還有另外一種隱身,無須法術、口訣,停影液和定影液。
它的名字叫,卑微。
《纏》
長夜漫漫,等待一個永遠不會響的電話,
思念就象一炷無主孤魂,不知落在哪裡才好,
他一根草都不曾贈她,
惟有抱緊那套借來的運動衣,捕捉他的一絲氣息,算是憑據。
想人是硫酸蝕骨,她一夜夜銷減著……
她明白自己病得不輕,而這病似乎永遠都不會好了。
《醜妻》
她坐得遠,可是滿屋子都是這男人的氣息,
一浪浪地,潮水似的,暖而襲人,湧到她的周圍,
她不敢動,可是卻感覺自己模糊地幸福著,奇怪的幸福,可怕的幸福。
外面又下雨了嗎,不知道,
只聽到,簷畔有稀疏的滴水聲,每一聲都幾乎嚇她一跳。
《竟然》
他喜歡登珠峰,深海潛水,徒步穿越大漠,那樣的難度讓他著迷,
他愛的是不是她的難度?
她的難度,是火星撞地球,那曾是獨立的驕傲的星球,
旗鼓相當,互不相讓,誰也別想捕獲誰,
所以他征服,他攻克,他操控,難度讓人痛苦,又那麼讓人激奮。
只是現在,她的難度還能守住多少?
《半局》
他是個好男人,他有好男人的手,
好男人的手,勤勞、靈巧、細緻,
可以為他的愛人做出千百種好吃的點心,
而那手亦可以果決、有力、安全,
如那日他奔過來毫不猶豫地把她抱起。
然而她的生活是個半局——
……
下一步很近,又似乎山長水遠。
不能一起走,就總得在某個路口放手。
《輪回》
他知道這天會來,有許多例子演給他看,逃不過的,然而他寧願自己登時就死了,不,早前就早早地死了,也不願這樣被人拖著扯著廝打著,經過她的門。
滿樓道都是張望的臉和眼睛,賊是過街的老鼠。
只有她的門緊緊地閉著,像從沒有人在裡面住過。
《買春》(聯合報文學獎首獎作品)
他的手有著自行其是的專心,它們忙著,平刮、豎刮、斜刮角刮,督脈、膀胱經、夾脊穴、肩峰,有條不紊,輕車熟路,他簡直忍不住要讚歎這雙手,這雙老中醫的手,多麼從容自如,多麼冷靜靈巧。
她翻過身來,袒著胸,他的眼睛沒法不盯住那雙好乳,可是他的手絲毫不亂,任脈、天突穴、膻中穴,為什麼他的手只認得這些?以任脈為界,刮板向左沿著肋骨走向刮拭,輕輕地沒人事地經過那粒溫暖的朱砂色的乳頭,它們怎麼可以一絲抖顫和不安都沒有?
《青鳥》
如果幸福是一隻青鳥,我那只,也許和你那只長得不一樣。
《晚 鐘》
“我把生命中最好的時間用來愛你,
整整十年只做了這一件事,只為了這一件事。
你認為,這世界還有什麼人能取代你呢?
信東,你讓我留點力氣愛自己吧。”
《忘不了》
他哪裡是什麼記憶力超強的神童,什麼過耳不失,過目不忘,
他明明是想忘卻,卻永遠也忘不了。
忽然又一個想法攀上來,
他記得她,他重視她的繁枝細節,
是本能地記住,還是情不自禁地,忘不了?
這念頭一秒鐘就躥得巨大,象個奔跑的火球,熊熊地要吞滅她……
《未雨綢繆》
她默默地從裡屋拖出個箱子。
“你就要這幾件衣服?”他又驚又喜。
她不動聲色地把箱子推到他面前:
“這是你的。”
看著一臉愕然的他,她慢慢地說:
“我早有準備你會這樣,你會離開我,對不起,這套房子的房產證,寫的是我,一個人的名字。”
《孖姊》
蘇航還是搞不懂,他最愛的是誰。
雪亮給他歡樂,雪明給他力量,
哪種更重要,那要看人生在哪個時候,享齊人之福是做夢,
所以嘛,日子下去,
得到的這個成了蚊子血,失去的那個仍是朱砂痣,
咫尺的這個成了白米粒,天涯的那個還是明月光。
《舊恨》
思郎猛,行路也思睡也思,
行路思郎留半路,睡也思郎留半床,
舊恨不肯忘,恩情轉頭涼……
《白菜玫瑰》(林語堂文學獎獲獎作品)
“不用流眼淚哦,阿嬤給好多個中意你,好多好多。”
低頭看去,白色的瓷碟裡,盛滿一朵朵頭臉上仰的小白菜根,那些齊齊切剪的白菜根,你一定從未發現,從正面看,一層層晶瑩潔白的苞,瓣瓣曲折婉轉,好生生地擁簇著一點翠綠的芯,看上去,竟然是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
《老樣子》
他拉著她的手,靜靜地站著,身後有人擠碰著他,他動一下又站穩。
然後他忽然明白點了,張開手臂松松地抱了她一下,他懷裡熱乎乎地微鹹的汗味,讓她幾乎把持不住自己。
好像怕她厭煩,他匆匆結束了這場儀式,提高嗓門作出輕鬆狀,“你先來,我先走,那就這樣吧。”
她微笑著說,“好吧。”
沒說下次,誰都沒說。
書摘/試閱
01
春寒細雨,點滴的濕,點滴的冷。
從中大北門走到南門,也不過半個鐘頭,可是韓煦,她忽然笑了,仰著頭移開傘,細紛紛的雨絲,亮晶晶地沾了她的發和睫,“十年呵——”
路上極靜,假日,午後,又是雨天。
整片芳草樹蔭 ,整條紅磚小道,整個飄雨的天地,仿佛都是她的。
她的鞋子已經濕透了,但仍然走得不慌不忙,走得好安心。
背包裡的碩士研究生錄取通知,貼著背,連著心,暖而熨貼。
環境地理資源專業,誰都不懂她好好一個兒科醫師,竟突然間放棄了一切,在家裡閉門苦讀一年,選擇了這個專業。
這世上只有一個人會懂。
只是不知道,她還有沒有機會,讓他去懂
02
和畢盛的初次見面是在火車上。
那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從昆明開往廣州的普通列車,沒有空調,沒有水,硬座,兩天兩夜。
至今韓煦還記得那年的票價,七十二塊,因為那張車票,一直都藏著,小心地。
十七歲的韓煦是什麼模樣啊。
眼珠烏亮,睫毛忽閃,黑髮極短,身量極矮小。因為矮小所以拼了命去證明自己的膽識,和人賭獨自敢闖西南,背了個大包頭也不回地就去,去了一個月,口袋裡除了一張車票錢,就夠買兩包壓縮餅乾。
她自己用小剪子,把頭髮剪得零碎短促,使自己看起來像個男孩,私下裡的壯膽和避嫌,就算是吧,她知道自己還算俊俏。
果然,那天畢盛從背後走來,重重地按她的肩膀。
“小兄弟,咱們哥倆兒擠擠算了。”不等她答應,他就坐下來,一下子,他的臉,笑著的英氣勃勃的臉,就到了她的眼前,這麼近。
她的臉一下子紅了,而他的話還沒說完,“那兩個姐姐說,女人要和女人紮推坐,男人靠邊去!”
鄰座的兩個女生笑吟吟地看過來,一個道:“畢盛,你也不看清楚,你紮推的是兄弟啊,還是妹妹啊。”
畢盛大窘,又馬上站起來,紅著臉說對不起。
韓煦從沒見過男人害羞也會這麼好看,當然她的生活圈子男生極少,她讀衛校護理,二年級。
他還是坐在她身邊了。後來她猜,也許是有些不放心的意思吧。
他親切地問過她,“小妹妹,你家大人呢?”
韓煦儘量嚴肅地說,“就我一個大人出來的。”
他的女同學驚訝地說:“呵,你才多大啊,有十四歲嗎?”
這話令韓煦惱火,她氣自己穿著寬大的T恤,全無發育的行跡,她氣自己個子小又被人看小,氣那兩個女生的修長曲線,氣乎乎地大聲說,“我都十八歲了!”——氣得乾脆再添一歲。
“十八歲出門遠行,也頂厲害啊。”畢盛是這麼真誠地讚美。
但是他在她身邊坐下,兩天兩夜的時間,幫她擋住擁擠的人潮,提醒她什麼時候到站,給她看行李打開水,講笑話解悶兒。
韓煦第一次覺得,路上有個人照顧,可真好。
03
車近廣西的時候,天開始熱了。
這趟車沒空調,日頭烤得車廂似火,這時候畢盛就站著扇風,讓韓煦一個人坐得寬敞。
半夜韓煦靠著座背睡了,興許是太累,不知什麼時候,頭偏挨上了他的肩膀,不知睡了多久,不知挨了多久,只知道突然紮起的時候,見他醒坐著,動也不敢動的樣子,襯衫已經濕了大半。
他的兩個女同學熱得難受,就來埋怨畢盛。
“畢盛,要不是你做好事,我們早就坐空調臥鋪,舒舒服服地到廣州了!”
“畢盛,回去我們一定要把你的獎學金吃光才解恨!”
這時候他總是滿頭大汗地笑著,“好好,任吃任宰任罰!”
他們三個是中大的研究生,畢盛讀環境地理資源,那兩個女生讀旅遊地理經濟,結伴去路南縣考察地貌,畢盛帶隊。在一個彝族山寨裡,他把大部分的費用,還包括自己的手錶相機,都留給了那兩個剛剛失去父親的彝族小孩。
他原是個這麼善良的人,原是對每一個都這麼的好,對她也不例外。
可是怎麼這個想法,會令韓煦有點不高興了。
吃飯的時候,畢盛又遞過來一罐八寶粥,還是那句:“來,幫幫我,減輕負擔。”
“我不吃。”韓煦說。
“該餓了。”
“我不餓。”韓煦固執地,“我自己有東西吃。”
“那給點兒我嘗嘗好嗎?”
韓煦只好掏出那包皺巴巴的壓縮餅乾,她兩塊錢在車站買的,灰乎乎硬梆梆的幾塊。
畢盛拿了一塊,咬了一口,一嘴都是乾巴巴的粉末。
“哎,這個好吃,我跟你換了!”畢盛整包搶過來,像寶似的。
韓煦手裡捧著八寶粥,眼底潮熱卻作不得聲。
抬眼看他滿嘴是粉末鬍子,又忍不住天真地笑起來。
04
忘記那個小站的名字了。
慢車,每個小站都眷顧,人,一站站地蜂擁上來,又一站站地消散。
這麼熱的天,這麼慢的車,好像永遠到不了盡頭,有時又寧願它這麼慢下去。
那個小站,有孩子上來賣粽子,人站著擠著亂著。
懵懂中突然聽得一個女同學喊,“哎呀畢盛你的包——”
大家站起來,那個賣粽子的孩子已經泥鰍似的滑下車了。
“糟了我們的資料全在裡面!”畢盛想追,左突右閃,可人叢疊得密實,過道上擔子麻袋地根本擠不出去。
韓煦望向窗外,賣粽子的孩子在站台笑。
她生氣了,她一生氣就不知道哪來的力氣,一下子推上車窗,兩手抓住窗沿,騰地就躍出去了。
她敏捷落地,拔腿就追,身後畢盛喊她,喊她,她不管,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搶回來。
畢盛也想跳下去,可是車窗只能打開這麼多,他個子太大,塞了一半就卡住了,只能探著身子幹急。
這真是個厲害的小姑娘,他在這邊看著急著也激賞著。
她快得像一隻矯健的羚羊,追上對手,揪起衣領,一把扯過包,還不忘踢了人家一腳。,全然不顧四周呼喝著圍過來的混混。
火車慢慢地開了。
“快!快回來!”他拼命地喊著,聲音都啞了。
總算來得及抓住她的手臂,半拉半抱地把她弄上車,一把摟在懷裡,什麼聲音都在後面,只聽得登登登的心跳。
她耳根灼灼的熱,他臉上深深的紅。
依約的是他懷裡一浪浪潮暖的氣息,有點迷糊,有點醉。
那感覺至今依然如此真切,就像昨天,就像剛才。
“傻孩子,你不要命了。”他放開她。
她好像突然害羞了,什麼也不肯說。
兩個人默默地。
就這麼一路看窗外的風景。
看火車在深峻的山嶺中穿行,轟隆轟隆地,單調而安穩地響著。
轉彎處,嶺上的一朵白雲,,火車長長的車廂,倏地就鑽過去了。
她笑了,回過頭,原來他也在笑,兩個人馬上又不笑了。
05
很多時候,韓煦是裝睡的。
她半眯縫著眼,看畢盛的側面,心裡直想笑。看他的下巴,是怎樣在這兩天兩夜裡,密密地長了一茬鬍子根兒,看他本來乾淨的臉,又怎樣被這一把汗一把灰地污染。看他犯瞌睡時候頭一點一點的釣魚,還有他高高卷起的袖子,胳膊上結實生動的肌肉。
她更喜歡聽他們說話。
他們說中大的新網球場有多麼寬敞,嶺南學院的新圖書館多麼氣派,報告廳某位教授的講座有多麼精彩,誰獲得了英國大學的獎學金,誰的碩士論文上了學報。
還有許多她似懂非懂的名詞,什麼網上沖浪,什麼納米技術,什麼雅虎華爾街,什麼地表沉積與生態環境。
這個時候她就覺得他們很遙遠,很高大,很陌生。
大城市,名牌大學,研究生,光華閃閃。
而自己,不過是一個小城,一間小衛校的,一個中專生,將來一間小醫院的,一個小護士。
她仰頭看他,原來自己站的好低。
本來也是毫不相干的,各有各的生活。
可是這會兒她心裡莫名湧起的悲哀,竟愈發濃重、急切、蒼涼,她再看一眼談笑風生的畢盛,火車漸漸接近終點,就好像手裡抓不住的一把沙子,只能眼睜睜看著掌心漸漸虛空。
真是不甘心啊。
畢盛問她要地址了。他把自己的日記本翻開,最後一頁,潔白的一整頁,放在她手裡,很小心,很殷切。
下意識地,韓煦寫了家裡的地址。
“學校的呢?”
“哦——我們學習挺緊張的,老師不贊成通信。”
“對啊,你該正讀高中吧,正是學習緊張的時候。”
“哦,是啊是啊。”
“是重點高中吧?”
“哦,是啊,是重點,省重點高中,還是。”她這麼自然地撒了謊,她實在不忍心不撒謊,儘管隱隱地,她覺得自己必會後悔。
06
下車的時候,大家都疲憊之極,狼狽之極。
一路上風塵暑熱,現在畢盛和韓煦就像一大一小兩個黑人,只有眼睛還是亮晶晶的。
韓煦低著腦袋硬生生的說:“好了,現在我要轉車了,你也走你的吧。”
不妨畢盛拉過她的行李包:“什麼這麼重?”
“石頭,點蒼山上揀的石頭。”
“真厲害!”畢盛笑歎著,已經一手提了她的包大步走在前面。
韓煦無力抵抗,只能快步跟他走,乖乖地由他買票,由他送上長途客車,由他安排坐好,也由他在她手裡塞了麵包和水。
“將就點吃,我也只夠買這個了。”他帶著歉意地。
她的心上上下下,悲悲喜喜,卻不懂得說一句溫柔體己。
憋了很久出口卻橫橫地:“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必這麼照顧!”
畢盛笑了, “我知道你是個頂厲害頂厲害的小姑娘,”他停住,深深望她一眼,慢慢地說道,“但我還是喜歡照顧你。”
便不再說話,徑直下車揚手再見,大步走遠。
看來往的人流是怎樣把他遮蓋了啊,越來越遠,極目再極目,連一點衣服的顏色也望不見了。
韓煦移開眼,這才發現手裡的麵包,已經被自己揉碎了。
07
多麼瑣碎冗長的情節,韓煦笑著搖頭,可是十年溫故常新,她喜歡這麼細細的想起,細細地沉迷。
細雨漸收,她不再亂逛,下午約了導師見面,該回去換身衣服。
經過孫中山的青銅雕像,她的腳步慢了。
雕像下那一大片草地,眼下汪汪地亮濕著,茫茫地寂寞在煙水裡。
數碼相機在背囊裡,好想現在就照張相。
畢盛最喜歡這一大片草地,他說夏天的早上,絕早,高大的桉樹上小雀兒在叫,露水閃閃的,他就來這兒讀英語,晚飯後,夕陽在天,他的舍友會來這裡彈吉他,唱老狼的流浪歌手,總有飄著花裙子的女同學,遠遠地站著聆聽。
他寄過一張照片,坐在這片草地上,一個人微笑。那封信他說,真希望你能來中大,來看看,來玩玩,或者來讀書,怎麼都行,你來就好。
他的信很準時,每週一下午,一定到。
所以那段日子,每個週一下午的班會,韓煦總是心神不定,下課鈴一響,抓了書包就往家跑。
她家離衛校不遠,只坐三個站,可是很多時候,她不耐煩等那班車,就乾脆跑回去了。
她在風裡跑著,在斜陽裡跑著,繞過一棵棵開著花兒的紫荊樹,繞過水龍般的車和喇叭,穿過幽深的巷子,轉彎,再轉彎,她家,古舊的紅磚牆外,掛著一個生了繡的綠色郵箱,捏著小小的鑰匙,扭鎖,開箱,——果然他的信一定在裡面,靜靜地安詳地等她。
他永遠用白色的長長的信封,右下角印著“中山大學”,淡綠色的字,優雅而親切。
她把信小心地塞在書包隔層,愉快地舒口氣,這才慢慢地進屋,和婆婆打了招呼,洗米煮飯。
她能忍住不馬上看信,就好像一個小孩捨不得拆一塊糖,留一會兒再留一會兒,那快樂和期待就要漫溢,她捨不得一口飲盡,要一點點地啜品。
直到睡前,明明躺下了,信就貼在胸口,最近心的位置。
歎氣很久,輾轉很久,才爬起來扭亮檯燈,一點一點地撕開信封,一點一點地展開信紙,一個字一個字地看進眼裡。
其實,那些信從沒有什麼熱烈的字句,甚至曖昧的,都沒有。
多是一頁,有時兩頁,畢盛的信就像他的治學態度一樣嚴整有序。
第一段是問候,問她學習,身體,心情。第二段是介紹自己這一周的要事簡況,學校同學的一些趣事。最後一段比較活潑,會說到自己喜歡的一首歌,自己的夢想,極少極少的,會有一兩句像是想念的話,像寄那張相片時說的“怎麼都行,你來就好”。
欣喜中的一點悵然,韓煦希望裡面還有點什麼,可是又怕裡面還有點什麼。
08
回信最難寫的是,她的重點高中學習生活。
韓煦絕少撒謊,這次的謊讓她為難。突然的說出真相吧,畢盛會怎樣看她,少女的好強和虛榮,讓她遲疑著,遲疑著,而她最遲疑的是,害怕因此失去。
他,多麼多麼的好啊,即使自己不妄想什麼,難道保持著這種距離,這種聯繫,常常獲知一些他的消息氣息,也算過分嗎?
她含糊地原諒了自己。
為了讓信的內容充實,她真的買了一套高二的課本,似懂非懂地自學起來。
她頻繁地去一中找從前的同學雪芬,跟著人家自習,跟著人家打飯,在宿舍聽人家評論老師、男生和高考題。
再把別人的故事換個角色,在小檯燈下回信,寫著寫著,甚至有時候真的以為那就是自己。
畢盛從信中看到一個勤奮而優秀的重點高中學生韓煦,她的物理測驗考了全班第三名,作文被老師推薦給校報了,她週六日都要補課,她最喜歡的老師是數學老師,因為他能用最快的方法算出微積分。
果然,畢盛給予她很多的讚賞和鼓勵,他熱心地把自己的學習方法傾囊而授,學英語一定要背熟一些範文,寫議論文可以經常看看報紙的社論,《讀者》裡的一些小故事可以成為文章論據。
信,就這麼一來一往的。雖不熱烈頻密,但也不疏遠生分。這按時收發的溫情和關切,漸漸長成生命裡親密的習慣,長成無須宣揚的默契。
那時候,韓煦常常想,這樣就很好了,這樣就很滿足了。
他是她精神上的燈塔,遠遠地,淡淡地,一些光明。不管將來,不想以後,只要目前。
可是他終於講到將來。
寒假快到的時候,他的信寫到,“想好要讀的大學了嗎?需要我幫你出出主意嗎?你一直說對經濟感興趣,中大的嶺南學院有很棒的教授。”
韓煦的不安爬上心頭,那不安其實潛伏已久。
恰巧學校剛剛發下實習的安排,韓煦,即將以產科護士的身份,到一個縣城婦幼保健院實習兩個月。
09
這封信她一直沒回,也是因為忙著準備實習的事,也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回答。
畢盛的信又來了,這回他說,“我想去看看你,主要想帶一些複習參考書給你,16日下午,你在家等我就好,我能找到。”
這消息讓人既喜又悲。。
韓煦每日裡坐立不安地,一會兒哼著調子,一會兒又悶聲悶氣。
她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家裡只有一個七十歲的婆婆,婆婆不懂她怎麼了,一會兒洗窗簾,一會兒擦地,皺著眉頭又抿著嘴笑。
“明天有客人來!”韓煦對婆婆說。
婆婆哦了一聲。
“明天有個客人來,研究生,比大學生還厲害的。”吃飯的時候,韓煦又說。
婆婆又哦了一聲。
韓煦歎了口氣。
做夢都想見他,不是嗎?可是現在不行,她慌得很,在衣櫃的鏡子前照前照後,為什麼自己還是這樣矮小,她挺挺胸,還是那麼微弱的起伏。
她拉開衣櫃,她沒有好衣服見他,她穿什麼見他?
坐在桌子前面,把臉貼在鏡子前,為什麼鼻子上有一粒痘痘,雖然現在很小,但明天會長大長紅的,一定會的。
最擔心的,說什麼好呢?
寫信,她可以構思可以盤算可以修改,見面,她怕自己什麼也說不出來。
實質上,她怕她的重點高中生的身份,紙一樣的撐不住啊。
他僕僕風塵地來,坐了12個鐘頭班車的來,如果他失望——
可是她想見他,想見他,她趴在桌子上,煩亂透頂。
10
畢盛來了。
他的行李裝滿了參考書和腦黃金,那年最熱賣的補品,很重。
本來他想忍住,等韓煦考完了高考,再來。就像每一封信,他都刻意忍住的火熱和期盼,要耐心,要冷靜,要等。
可是浩如春水的思念可以一夜間就毀掉他苦心的築堤。
他小聲地對自己說,只是看看她,看完就走,好像這一眼可以支撐許多個日子的饑饉。
現在他終於來了,山城的陽光很好,街上的擾攘很好,幽深的巷子很好,指路的阿姨很好。
他敲門,老式的粵西的雙面木門,敲門聲篤篤,他的心也篤篤。
門很遲才開,是一位和善的婆婆,他記得韓煦在信裡曾經提到過的。
“婆婆好,我是廣州來的,阿煦的朋友。”
“我知道,你是客人。”婆婆說方言,畢盛最多能聽一半。
“阿煦在家嗎?”他向裡張望,好像那個敏捷的小姑娘隨時都會跳出來。
“無在屋啊,行出了。你跟我入來坐羅。”婆婆引路,斟茶,指指茶几上的一封信。
畢盛站起來接過茶,惦記著那信,手顫了顫,幾滴茶潑了衣服。
信說臨時參加一個全封閉的英語補習班,不能在家等他,非常抱歉等等。
近晚的陽光漸褪,畢盛感到有點涼。他還是笑著留下禮物,陪婆婆說了一會兒話,雖然,天知道他們是否能互相聽懂。
不肯留下用飯,怕麻煩老人,畢盛在車站買了個盒飯,匆匆趕夜車回去了。
夜晚是頗有一些涼意的,畢竟是冬。車窗外是黑黑的田野,一陣陣地,他心裡有一些難受,馬上又為她開脫,快高考了,當然是補習班比他重要,她還小呢,小女生,怎能要求她什麼,都是自己不好,衝動地要來,差點給她添麻煩。不能急,要耐心,要冷靜,要等,既然值得去等,既然決心去等。
可是,講完了道理,心還是有點疼。
11
一分一秒地捱到五點半,韓煦不行了,她感到心突突突地,要蹦出腔子。
她跑出學校,往家裡跑,不行,她得見他,行行好老天爺,我得見他。
她在風裡跑著,在斜陽裡跑著,繞過一棵棵開著花兒的紫荊樹,繞過水龍般的車和喇叭,穿過幽深的巷子,轉彎,再轉彎。
家門緊閉著,她側耳去聽,裡面靜悄悄的。她慌著掏出鑰匙開門,半推半撞地,客廳裡只有婆婆在吃水煙,只有婆婆,只有她。
“他呢?”她絕望地,聲音裡有哭的喊。
“客人走了,走了大半個鐘了,買昨好多禮。”婆婆笑眯眯地說。
韓煦的腿軟極了,扶著椅子,她捧緊抱緊那重重的禮物,好像僅剩的依傍。
一層層細心的包裝,高考參考書,厚厚的,新新的,還有腦黃金,紅桃K,還有太陽神喉頭菇,他想得真細,補腦補血補細胞的,這幾乎是那個年代所有最熱的保健品,他也是靠獎學金生活的,偶爾幫導師翻譯一點資料,一直想裝CALL機都捨不得。
“好靚仔的啊!”婆婆滿意地說,“好有心!”
韓煦又是愧悔又是心疼,坐了12小時的車,熱飯沒吃一口又回去,他餓不餓,他生氣嗎,他會原諒她嗎?
這一腔柔情悱惻跌宕,上下沖竄,如何按捺這長長的夜,長長的思念。
好像為了補償,好像為了順他歡喜,韓煦寫信給畢盛,好的,我就報考中大的嶺南學院吧,我一定努力考上,我一定要去中大,你等我。
寫完雙頰似火,卻又想像他看到這信的欣慰,想像他的高興,這激動使她暫時忘了,這謊拖得她越走越遠,回頭已難。或者她也顧不上了,像夏天撞向路燈的小飛蛾,只要那一瞬的光焰。
畢竟當時年紀小啊,不懂得,就算是假以愛的名義,可騙了還是騙了啊。
12
中大校道上的人多了起來,迎面的年輕父母,牽著個孩子,想是第一次來,指指這個,問問那個,快活的新鮮的趣味,韓煦笑著望他。
想起,當年她第一次來中大,終於,勇決地。
實習很苦,在婦產科,她給產婦插尿管、清潔下身,甚至她們便秘的時候,她要戴著透明的手套,給她們用開塞露。
輪值夜班的時候,天寒地凍,白褂子外面也只能松松披一件棉衣,寂靜子夜,倦極想打個盹,卻總有呼天嚎地的產婦慘叫著送來,她驚她怕她手忙腳亂,心時刻抽緊,跟在醫生和護士長的後面,搬這個拿那個,不小心就被罵個淋頭,連委屈地抽一下鼻子,都沒空。
偶爾回到家,連盼信的力氣也減了,看著畢盛的信裡越來越多的高考命題方向,模擬題和招生簡章,她更感到無比的遠,無比的漠然,無比的不相干,心裡遂抹了一把灰似的,卻掩不住汩汩的悲哀。
她的回信越來越短,心乏了,沒有力氣了,這強弩之末,這戲近尾聲。
他卻只當她全力備戰高考。
他知道她的成績在全級排名30名之內,他知道她的第一志願報了中大經濟管理,他知道她第三次模擬考試又連晉四名。
他心情很好,每一天早上的陽光,斑斑點點的金色射進窗子,他感到日子好像一朵徐徐綻開的花兒,一天舒展一點兒,就要完全地張揚地盛放。
韓煦卻出奇地冷靜,實習回來,已經沒課了,只是畢業的手續要奔走一下,她在家裡坐著,等著去一間縣醫院報道
高考的三天,喧嚷的酷暑和掙扎,她坐在窗子裡,聽路過的學生唏噓著題目的深淺。
她坐著,好像等待倒數的宣判。
七月十日,高考結束的第二天,畢盛的信又來了,那是他最後的一封信,只是當時,看起來無論如何,也不像是最後。
他說這個暑假他不回海豐老家了,一是跟導師去河南魯山做個礦山考察,一是等她的好消息,他相信她一定能考上,他有預感。
“我會一直在中大等你,在這裡等你。夏天的草地真漂亮,真想和你照張相,就在孫中山雕像下面的草地上可好?”
雖然我知道,你實在是個頂厲害的小姑娘,可我還是好想,一直在你身邊照顧你。”
夏天的蟬在窗外一大片咶噪,偶爾停下來,悄無聲息的午後,是誰在細細長長的哭?
13
其實他不知道,高考前她去了一次中大。
仲夏,黃昏,韓煦在北門下的車。
她從沒來過,不知道南門是正門,的士司機問她南門北門,她錯以為北和北京一樣該是正的。
中大以一場豪雨迎接她的初來乍到,夏天的雷陣雨,來的快走得疾,可是在毫無遮蔽的北門珠江岸邊,已經足以把她澆透。
她還沒看清自己今天有多漂亮,新買的涼鞋,跟細高細高,白底淡黃碎花上衣,蔚藍的長裙子,編得又緊又密烏黑發亮的辮子。
她今天是個多漂亮的女孩子,高挑,嬌俏,雅致又溫柔。
她費盡心思維護這漂亮,下了汽車在旅館裡精心裝扮,怕擠公共汽車髒了衣服,狠心打了三十多元的的士。
她濕淋淋地且跑且閃,雨鋪天蓋地,腳下一滑,折了一隻鞋跟。
索性站住,哪兒跑去,她反而癡笑了。
怎麼計算,算不過這場雨,就像怎麼計算,算不過這個命。
她就這麼濕淋淋地走在中大的校道上,光著腳,拎著鞋,偶爾有打著傘的人匆匆看她一眼
她無暇沮喪,更多的是茫然。
樹叢裡的路燈一盞盞亮起來。
研究生樓很好找,她到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
我這是幹什麼來了?
這一刻她還在問自己。
然而她總算來了,這就是中大,他的中大,她來了,走過了,看過了,完成了,她有點輕鬆。
衣服黏濕在身上,時而冷時而熱。她在研究生樓前的東湖邊兒坐下。
他近在咫尺了,樓裡一扇扇窗裡的燈,有一盞是他的。
她渾身一陣溫暖轉而又一陣淒酸。
校園暗暗的,但笑語聲是明亮的。向左,這條乾淨的路,載滿了紫荊樹,不是開花的季節,滿樹都是圓圓的葉子,他每天都踩的路,每天都踩,她想他走路的樣子。
在網球場,她扶著圍牆,他踩過的路,他扶過的牆。
在游泳館,她摸著欄杆,他也摸過的,他游過的水。
他踩過的中大的路,她也踩過了。
好了,這就行了。她想笑笑,卻打了個噴嚏。
身後有相擁快行的情侶,她卑微地急忙閃身,微弱燈下,那男生儒雅女生脫俗,笑聲明朗飛揚,她躲得更深了,躲在高深叢林裡,越見自己的虛弱矮小。
她險些忘記,她是粵西小縣的小護士,穿著廉價的軟底布鞋在彌漫消毒水的走廊上端著痰盂小跑——
這是他的中大,不是她的。
她心裡清清楚楚,無論如何,她不會去見他了。
轉身再看一眼那樓上的燈火,她踉蹌地離開。
朦朧中似乎有個聲音在無助哀切地喊,從今以後,也許再也見不著了啊。她加快步子,咬牙甩頭不去想。
小小身體的熱,暖不過衣裙的濕,她冷,很冷。
就這麼,誰想得到呢,火車上的初初相見,也竟是一生中的唯一。
14
她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早就寫好了。
她說他不必等下去,從頭到尾都是她的一場玩笑,希望他不要當真。她去不了中大,她不是重點高中的學生,她只是個衛校的小護士,沒辦法,當年成績不好,上不了重點,就想早點出來工作,現在好了,她有工作了,說不定很快就會嫁個醫生,她的師姐們都是這樣的。
她說謝謝你,實在是謝謝你。
對不起,實在是對不起。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八日,高考成績發佈那天,她去寄信。信封半倚在郵筒邊沿,她的手裡全是汗。
後邊的人催促了她的決心,她指間一松,信封倏地一下飄下去。
完了。
她失魂落魄地回家,飯也不吃就上床睡覺,睡了一天一夜。
如果這信太過殘忍,你可知道,每一刀都是先插在我的心上。
他再沒信來。
他果然不肯原諒她,自己又有什麼資格奢求他的原諒?
秋去冬來,春天的紫荊又開了一樹一樹。
他不再有任何消息,他終於放棄她。她徹底絕望。
一切都完了。
15
宋教授是她的導師,人很年輕,不過三十出頭。第一眼韓煦就想到,畢盛也和他仿佛年紀吧,日後也許可以從這裡打聽他的消息。
不等她問開課計劃,宋教授劈頭就問:“你是學醫出身的?”
韓煦忙答:“我知道基礎可能會薄弱些,但我肯花功夫的。”
“不是不是,我不懷疑你的能力和勤奮,要不怎會一年時間攻克了專業課?我只是好奇,你為什麼好好的醫生不幹了,跑來考這個專業?”
韓煦斟酌著,“也許——是因為喜歡吧。”
“我就更好奇了,這個專業挺偏的,有時還要下礦山鑽油田的,你一個女孩子,唔,二十七歲了,好像過了做夢的年紀啊,呵呵。”
“還是因為喜歡吧。”
“行啊,難得你這麼真誠的喜歡,我收你這個徒弟吧。”宋教授爽朗一笑,韓煦如釋重負。
其實,她很久不做夢了。
剛畢業那兩年,太苦了,行業欺生,她常常被排值夜班,搽著風油精提神,白天又睡不著,隨時被人喊去頂班。不服,人家冷冷答,你年輕又沒拍拖結婚的,不找你找誰啊,不願意啊,考醫學院當醫生去唄。
她就當真了,倒不完全為一口氣,只想過得好點兒。
第二年成人高考,還真給她考上了廣醫,去讀書,老老實實安安靜靜地坐在圖書館背解剖圖,偶爾看看窗外的紫荊樹,湛江也有紫荊樹,也開花,有紫有紅有香有蕊,但她總覺得,這花必不同中大的鮮豔熱烈。
偶爾她還會想,偶爾到成為一種習慣,一種頑疾,治不好的,也不去治。
直覺得他越來越遠,遠不可及,可是卻還清晰無比,鑿在石頭上似的。
大學讀完就做了兒科的醫生,工作不忙,小孩子無非感冒喉嚨發炎,不傷腦筋,接著很自然地,五官科的姚醫生開始約她出去,去得多了,淡淡地,也就開始談婚論嫁。
那天她是想著,要結婚了,也該把東西收拾一下,該扔的就扔掉吧。
老家的閣樓上,她扭亮那盞小燈泡,光沉沉的,她收拾衣服收拾鞋直到抽屜裡的小髮夾也清理好了,回頭,就剩下那口箱子了。
整整八年,她不敢碰,那箱子全是積塵。
掀開來,撲鼻的塵味兒,裡面是畢盛給她的一切物事,信、卡片、相片、書,還有那年他省吃儉用買的腦黃金,早已經變質了,巨人集團倒下了,史玉柱出來還債了,這麼多年過去了,她拿在手裡,癡癡看了一晚,不知是夢是醒。
時間有改變她的,她的身量也勻稱婀娜,她的面容更沉靜美麗,只是為什麼,就是忘不了,忘不了,時間一點也幫不了她啊。
16
沒人知道,她是如何一下子就清楚爽利了。
上三樓五官科找姚,病人多,她穿著白衣長褂靜靜倚著門。
看姚冷峻地忙著,這麼近卻這麼遠,這麼熟又這麼生,如果不用心,也許可以跟他過些平常的生活,可是——
姚起身走近她,“有事?”
她簡短地,“我不想結婚了。”
姚醫生素知韓煦的特立獨行,但也情急問道:“你看我證明都開了,這又是為什麼?”
“我想考研,考中大。”
“你想去中山醫進修是吧,可以啊,結了婚也可以啊。”
“不是中山醫,我要考環境地理資源專業,中大的。”
“你不是說真的吧,換專業可不是說換就換的。”
“對,所以我打算辭職,在家複習一年。”
“你一時衝動是吧,你想想清楚。”
韓煦低頭喃喃自語,“不想了,想了八年了。”
她突然很心急,年華是一倏忽的事,生命是一倏忽的事,只怕來不及。
她必須解決那個箱子,必須面對那些痛,否則她這輩子,都別想輕鬆的忘卻,都別想寧靜的活著。
她要明明白白證明,給他看,她能,她沒有撒謊,儘管已經晚點。
還有,最要緊的,她還不曾告訴他,她曾經愛,她一直愛。
怎麼能不讓他知道?
來得及嗎,你看,一眨眼地,青春就快剩個尾巴了。
宋教授給她開書目和課表,韓煦接過來看了一會兒,問,“宋教授,江肖明教授不上我們的課嗎?”
宋教授看她“咦,你知道江教授?”
“我以前在圖書館裡看過一本《環境地理學》,是他寫的。”
“那本書很舊了吧。”
“好像是一九九六年一月的。”
“那就是了,當年他還送我們一本呢,我那時還是他的研究生。”宋教授不由嗟歎起,“可惜那也是他最後一本書了。”
“哦?”
“九六年暑假,他帶了一個研究生去河南魯山,‘7.14’礦難你知道不?死了二十多個人,他們倆剛好也在下面——”
九六年,七月十四日,河南魯山,七月十四日,九六年。
韓煦飛快地計算著,手腳冰涼冰涼。
“那個研究生,也在裡面,不會吧,不會吧。”
“最可惜就是他了,那麼年輕,海豐人,長得很帥,很有才華,好像連戀愛都沒談過呢。”
韓煦頭腦昏昏沉沉地,心裡亂極躁極悲極。
“他的論文還得過獎,在年會上宣讀過,那,我找給你看看。”宋教授在書架上翻到一本論文集,指給她看,“這觀點,這思路,真是真是,哎,太可惜了。”
韓煦低下頭來,那個名字,那個名字,瞬間模糊了,啪地,一大顆眼淚掉下來,沒濕了,那兩個字。
畢盛。
17
又下雨了。
濕雲如夢,塵粉似的雨。韓煦腳馬不停蹄地走,心馬不停蹄地疼。
七月十一日,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
她突然狠狠地咬緊嘴唇。
也就是說,他走的時候,還沒有看到她的信,還不知道她是在騙他。
也就是說,他直到最後一刻,還相信她會考出好成績,九月裡就會在中大相見。
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機會看信,根本沒有機會生氣或者原諒。
他早就不在這裡了,他早就沒了,而這麼多年,她一無所知。
她哪裡會想到,她騙他,真的騙了一輩子。
該如何,讓他知道,她愛他。
卻原來,年華是一倏忽的事,生命是一倏忽的事,真的來不及
再也來不及。
雨下大了。
孫中山青銅雕像前,韓煦拿著相機央求一個打傘的女孩。
“請你,請你,幫我照張相。”
“可是下這麼大的雨。”
“幫我照張相吧,照張吧——”雨打濕了她的頭髮衣服,她臉上都是水,“照一張吧,很快的,很快的。”
女孩當她是個狂熱的旅遊者,只好夾著傘端起相機。
韓煦坐在那片草地上,微笑,雨水打濕那微笑,她不斷地眨眼,還是微笑。
雨越下越大,女孩看看鏡頭,再看看鏡頭。
只看到茫茫的雨,只看到茫茫的水。
相關商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