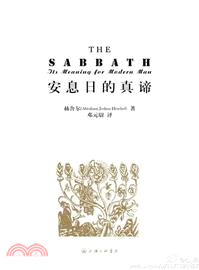安息日的真諦(簡體書)
商品資訊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安息日的真諦》是20世紀談安息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赫舍爾以優美、熱切、滿懷對上帝所造萬物的愛,所寫下的《安息日的真諦》一書,在出版之后,就被推崇為是猶太信仰的經典作品,幫助數以千計的讀者在現代生活追尋生命的意義。赫舍爾在這本簡短而深邃的小書里,默想第七日的意義,引入一個帶來巨大影響的觀念:一種不是呈現在空間中、而是呈現在時間中的“圣潔的建筑學”。他主張,猶太教是個時間的宗教,猶太教所揭橥之生命意義,無法在空間及充斥于空間的物質中獲得,只能在時間及彌漫于時間的永恒中領受,因此“安息日就是我們的大會堂”
作者簡介
赫舍爾(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72),波蘭出生的美國猶太拉比,二次大戰時在納粹德國失去母親與姊妹,流亡至美國后,在美國猶太神學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擔任神秘主義與倫理學教授。他集學者、作家、行動家與神學家等多種身份于一身,一生追尋真正的自由與信仰,也是作品廣受基督徒閱讀的猶太神學家之一,其中《先知》入選《今日基督教》二十世紀百大好書。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除本書外,還包括《覓人的上帝》、《人不是孤島》等。赫舍爾曾與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參與1965年的美國民權運動游行,他寫道:“當我在賽爾瑪游行,我的腳在祈禱。”(When I marched in Selma, my feet were praying.)
作者的最后一個安息日,與家人和許多朋友共享了一頓美好的晚餐,飯后有位來賓朗讀其年輕時寫的意第緒語詩篇。他那晚入睡后,便再也沒有醒來了。在猶太傳統里,一個人在睡夢中過世,被稱為“上帝之吻”;而在安息日過世,則是一個虔誠人配得的禮物。作者曾經寫道:“在敬畏神的人,死亡是項殊榮。”
作者的最后一個安息日,與家人和許多朋友共享了一頓美好的晚餐,飯后有位來賓朗讀其年輕時寫的意第緒語詩篇。他那晚入睡后,便再也沒有醒來了。在猶太傳統里,一個人在睡夢中過世,被稱為“上帝之吻”;而在安息日過世,則是一個虔誠人配得的禮物。作者曾經寫道:“在敬畏神的人,死亡是項殊榮。”
名人/編輯推薦
《安息日的真諦》告訴我們安息日的意義在于歡慶時間,而非空間。我們一周有六天生活在空間之物的宰制下;但到了安息日,我們試著讓自己與時間中的圣潔有所共鳴。在這日子,我們被呼召去分享那時間中的永恒事物,被呼召從創世的結果轉而關注創世的奧秘,從受造的世界轉而關注對世界的創造行動。
序
前言:時間的建筑學
科技文明就是人類對空間的征服。但這樣的征服,往往得犧牲一種基本的存在要素,這要素就是時間。處身科技文明中的我們,以時間換取空間;生活的主要目標即是在這空間世界里擴展自己的權力。然而,擁有得愈多,不表示愈真實地存在。我們在這空間世界所獲得的權力,在時間的疆界上戛然而止;惟有時間才是存在的核心。
控制這空間世界固然是我們人類擔負的一項任務,然而,如果我們在空間之域爭取權力的同時,卻失落了對時間之域的一切渴望,危機就此誕生。在時間之域中,生命的目標不是擁有,而是存在;不是占有,而是施予;不是控制,而是分享;不是征服,而是和諧共處。一旦對空間的控制、對空間之物的攫取,成為我們惟一的關注,生命就走上了岔路。
沒有任何事物比權力更為有用,但也沒有任何事物較權力更加可懼。過去,我們常常因為缺乏權力而受到剝削;如今,剝削我們的卻是權力所帶來的威脅。熱愛工作的確能帶來快樂,然而當我們在工作中貪得無饜,卻會跌入悲慘的境地。汲汲營營的心壺在利益之泉中破碎;世人若出賣自己,甘受物的奴役,便會成為這利益之泉中破碎的器皿。
科技文明根源于人心渴望征服與管理各種自然力量;工具的制作、紡織與耕作的技藝、房舍的建造、航海的技術──這一切都在人類的空間環境中不斷取得進展。時至今日,空間之物占據人們的心思意念,影響所及,包括眾人的一切活動,即便諸般宗教也經常受到如此的觀念所宰制。神祇居住在空間之中,廁身于特定所在,諸如群山、眾林、或樹或石,這些有神祇居住的地方特別被當作是圣所。神祇總與某一獨特的地點密不可分。“神圣”這個特質被視為與空間之物有所關聯,因此,首要的問題是:神在什么地方?人們狂熱擁護這個觀念,認為上帝就顯現在宇宙當中,結果卻因此認定上帝只顯現于空間之中、而非時間里面,顯現于自然、而非歷史,仿佛上帝只是物、不是靈。
甚至泛神論的哲學也是一種空間宗教:至高的存在被認為就是無限空間本身。“神即自然”,上帝的屬性就是向外延伸的空間,而不是時間。對斯賓諾莎(Spinoza)而言,時間僅止是一種偶然運動,一種思維模式。他并且打算以幾何學這種空間科學來建構哲學,這意味著他擁有的是一個空間取向的心智。
初民的心智很難不借助于想象力來理解一個觀念,而想象力正是馳騁于空間之域。諸神必定有其可見的形像,沒有形像的地方就沒有神靈。對圣像的崇敬,對圣山或圣所的崇敬,可不只是為多數宗教所固有,更是存在千代萬國的世人心中,不論他是虔誠的人、迷信的人,抑或反對宗教的人。所有人盡皆不斷向國旗、忠烈祠、為君王或民族英雄而立的紀念碑,宣誓他們的忠誠。無論何處,對忠烈祠的侮辱都被視為是種褻瀆,使得忠烈祠本身變得如此重要,世人反倒任其所紀念的事物遭到遺忘。紀念促成了遺忘,手段取消了目的。因為,空間之物任由世人擺布;縱然這些事物極其神圣而不能玷污,卻無法保證不為人所利用。為抓住神圣的特質,為使神靈永遠臨在,世人遂塑造神靈的形像。但是,一位可被塑形的神,一位可被局限的神,不過是人的影子罷了。
空間的光輝,與空間之物的華美,在在使我們著迷。物,是一種拖累人們心神、宰制我們全副心思的東西。我們的想象力傾向于將一切概念形像化;在每日生活中,我們首要關注于感官所向我們表明之物,關注于眼目所見、十指所觸之物。對我們來說,實在就是物性(thinghood),由占據空間一隅的物質所構成;就連上帝也被多數人設想為一種物。
我們惟物是瞻,所導致的后果就是我們看不見整個實在,以致我們無法認出:物只是物,物實際上只是材料。顯而易見的,當我們這樣來理解時間時,那無物性、非物質的時間,于我們而言就好像毫無實在可言。
的確,我們知道如何應付空間,但在面對時間時,非得使之臣服于空間之下,否則我們將手足無措。大部分人辛勤勞動,仿佛只是為著空間之物而作,至終,我們在被迫直視時間的面容時會驚駭不已,受困于對時間深植不移的恐懼中。我們遭受時間的譏笑,它就像是只老奸巨猾的怪物,張開熔爐般的大嘴,一口口吞噬人生的每一寸光陰,將之焚燒殆盡。于是,我們在時間面前退縮,逃到空間之物那兒尋求蔭蔽。我們將自己無力實踐的意圖寄望于空間之上;于是,財產象征了我們的壓抑,慶典象征了我們的挫敗。但空間之物無法防火,它們只會火上加油。難道,擁有財貨的喜悅,足以化解我們對時間的害怕?特別是這害怕終究會變成對那無以逃避之死亡的恐懼。被夸大的物,偽裝成幸福,實際上卻是對我們真實生命的威脅;倘若我們致力于空間之物,這更多是自尋煩惱,而不是得其祝佑。
世人不可能躲避時間問題。我們愈多思考,便愈了解到:我們無法藉由空間征服時間。我們只能在時間中掌管時間。
靈性生活的更高目標,不在于積存大量信息,而在于面對神圣時刻。比方說,在宗教經驗中,我們所領受的并不是物,而是一種屬靈的臨在。真正能在靈魂里留下痕跡的,并非行動所經過的場所,而是某個帶來洞察的時刻。這洞察的時刻是個機會,能帶領我們超越物理時間的限制。一旦我們無法感受到時間中這種永恒的榮美,靈性生活就開始腐化了。
我在此無意輕視空間世界。貶抑空間與空間之物的祝福,也就是貶抑創世大工,而那本為上帝眼中“看著是好的”。不可單單從時間的角度看世界;時間與空間彼此關聯,忽略任何一方都將使我們陷于半盲之境。我在此所要抗議的,乃是世人向空間無條件投降,甘為物之奴仆。我們絕不可忘記:并非物使時間有了意義,乃是時間使物有了意義。
和空間比起來,圣經談得更多的是時間;圣經在時間的維度中看待世界。圣經對世代與事件的關注,遠多于對列國與物事的關注;圣經更多關心歷史,而非地理。為理解圣經的教導,我們必須接受其前提,這前提就是:時間對生命的意義就算不比空間重要,也絕不遜色;時間有其自身的重要性與獨立性。
圣經希伯來文沒有“物”(thing)這字的同義字。后期希伯來文用以指“物”的“davar”,在圣經希伯來文中則意味了:“言語”、“字詞”、“信息”、“報導”、“音訊”、“勸告”、“要求”、“應許”、“決心”、“語句”、“主題”或“故事”、“言說”或“表述”、“職務”或“事務”、“行動”、“善行”、“事件”、“方式”或“方法”或“理由”或“原因”;但就是沒有“物”的意思。這只是因為圣經語言的貧乏嗎?還是說圣經的本意就是希望指出一種合乎中道的世界觀,提醒我們不可用物性來表達實在(reality;源于拉丁字 res,即“物”的意思)?
宗教史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就是農業節日轉變成紀念歷史事件的慶典。古人的節日與自然節氣緊密相連,他們在時序變遷中,歡慶在自然生活里所經歷到的事情;于是,節日的價值取決于自然帶來怎樣的物事而定。可是,在猶太教里,卻出現了變化:逾越節本是個春季節日,卻成為歡慶出埃及的日子;七七節本是在麥子收割的尾聲舉行的古老收割節(hag hakazir;出二十三 16,三十四 22),卻成為歡慶在西乃山賜下律法的日子;住棚節本是慶祝葡萄收成的古老節日(hag haasif;出二十三 16),卻成為紀念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時居住在棚里的日子(利二十三 42?43)。對以色列人來說,盡管自然界的循環與我們肉身生命的存活息息相關,但是歷史時間中的獨特事件,比自然循環中的反復歷程具有更多的屬靈意義。當其他民族的神祇關聯于處所或物事時,以色列的上帝卻是事件的上帝:祂是奴隸的救贖主,是律法書的啟示者,祂自己乃是顯現在歷史事件中,而非顯現在物事或處所中。于是,一種對于不具形體、無以思量者的信仰,就這樣誕生了。
猶太教是個時間的宗教,以時間的圣化為目標。對于那些空間取向的心智而言,時間是凝滯不變、反復循環、同質無異的,他們認為所有時刻都無甚分別,只是空殼,不具實質;圣經非但不是如此,反倒覺察到時間的多樣化特質:沒有兩個時刻是同樣的,每一時刻都是獨特的,是在當下那惟一的時刻,是獨一無二、全然寶貴的時刻。
猶太教教導我們,怎么與時間中的圣潔相連、與各種神圣的事件相連,學習如何在一整年的歲月之流里,把一個個浮現出來的美麗安息日視為圣殿,尊崇敬奉;換言之,安息日就是我們的大會堂。至于我們最重要的“至圣所”,就是贖罪日,這是一個無論羅馬人或德國人皆無法焚毀、即便背離了信仰亦無法遺忘的“地方”。據古代拉比所言,并不是因著我們守贖罪日,而是緣于這日子本身,緣于“這日子的本質”,人們在其中懺悔,才得以贖回吾人之罪孽。
我們可以將猶太教的禮儀刻畫為是關于時間之諸般意義形式的藝術,宛若是種時間的建筑學。對這禮儀的遵行,像是守安息日、月朔、各式節日、安息年與禧年,大多取決于一日中的特定時刻或一年中的特定時節而定。比方說,“喚禱”(the call to prayer)的儀式,即依循著黃昏、清晨、晌午的時序進行。猶太信仰的主題盡皆寄于時間之域。我們記得出埃及的那日,記得以色列民站在西乃山腳的那日;而我們對彌賽亞的盼望也是在期待一個日子,期待那諸日終結之日。
在一場精心構思的藝術表演中,最為重要的理念或角色不會隨便出場,而是像皇室典禮中的君王般,在某一特定時刻、以某種特定方式出場,來顯明其權柄與領袖地位。而在圣經里,字詞的使用同樣是極度講究的,尤其那些在圣經世界的廣闊意義體系中,如火柱般具備引路功能的字詞,更是如此。
最著名的圣經字詞之一,就是 qadosh(圣/圣潔)這個字;它比其他任何字詞都更能表達出上帝的奧秘和尊榮。那么,在世界歷史中,第一個被認為是圣潔事物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山嗎?還是一座祭壇?
首次出現 qadosh 此一著名字詞的,自然是創世記中創世故事的尾聲:“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圣日。”換言之,qadosh 這個字被用在時間上;這是一個具有何等深意的做法!事實上,我們在創世記載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節經文曾經指出,空間中的事物是可以被賦予圣潔性質的。
這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宗教思維正好相反。神秘主義者的心靈會期待,在天地獲得建立后,上帝會創造一個圣地──無論是圣山或是圣泉──隨之在其上建造一間圣所。然而,就圣經而言,天地建造完成后,最先出現的卻是那時間中的圣潔,也就是安息日。
在歷史的開端,世上只有一種圣潔,即時間中的圣潔;直到在西乃山上,上帝之言即將被道出時,才宣告了一種在人里面的圣潔:“你歸我為圣潔的民。”只有當百姓遭到試探去敬拜物,也就是敬拜那金牛犢后,上帝才吩咐設立會幕,那在空間中的圣潔。首先是時間的圣化,其次是人的圣化,最后是空間的圣化。時間由上帝使之為圣;空間,也就是會幕,則由摩西使之為圣。
雖然節日所紀念的事件都是發生于時間之中,但是這些節日所舉行的日期,仍舊依據著我們生活中的自然事物而定。比方說,逾越節和住棚節總在滿月之際慶祝;所有節慶都在某個月份中的某日來舉辦,而月份則反映了自然界中周期性發生的事情;猶太人的月份便是從朔月開始算起,直到另一輪新月再度出現在夜空中。相較之下,安息日全然與月份和月之盈缺無關,安息日的日期并不依憑于任何諸如月朔這類自然事件,而是依于創世的行動。因此,安息日究其本質乃是徹底獨立于我們的空間世界之外。
安息日的意義在于歡慶時間,而非空間。我們一周有六天生活在空間之物的宰制下;但到了安息日,我們試著讓自己與時間中的圣潔有所共鳴。在這日子,我們被呼召去分享那時間中的永恒事物,被呼召從創世的結果轉而關注創世的奧秘,從受造的世界轉而關注對世界的創造行動。
跋:圣化時間
外邦人將他們對上帝的意識投射為某個可見的形像,或將上帝與某種自然現象、某種空間之物連結起來。但在十誡里,世界的創造主顯明自己的方式,乃是透過一個歷史事件,透過一個時間中的事件,這事件就是祂將祂的百姓從埃及解救出來,并對他們宣告說:“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在地上曾經有過的最寶貴事物,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領受的兩塊石版,它們是無可比擬的無價之寶。摩西曾上到這山去領受它們,并待在那里四十晝夜,既不吃餅,也不喝水。上主交給他兩塊石版,在上面寫下十誡,這是在山上,上主從火中對以色列民所說的話語。但四十晝夜結束后,手里拿著兩塊法版的摩西下山之際,卻看到百姓圍著金牛犢跳舞,他便把手中的法版扔掉,在眾人眼前摔碎了。
“在埃及,每一個重要的宗教中心,都會根據“此乃創世之地”的說法來宣稱它的優越性。”相較之下,創世記則是說到創世之日,而非創世之地。
眾神話皆未提及創世的時間,圣經卻偏偏說到空間在時間中的受造。
人人都知道,大峽谷要比小溝渠更能引發敬畏之情;人人都知道,蟲子與老鷹有多么不同。但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對時間的差異具有同等的鑒別力?歷史學家蘭克(Ranke)宣稱,每個時代離上帝都同樣近。但猶太傳統則宣稱,在時間中有一種時代的階層,每個時代都不一樣。世人可以同等地在任何地點向上帝祈禱,但上帝卻不是同等地在任一時代向世人說話。比方說,在特定的時刻,先知預言之靈便離開了以色列。
對我們來說,時間只是個用來度量某個物理量的機制,而非我們棲居于其間的生活領域。我們的時間意識出自于對兩個事件的比較,發現其中一個事件比另一事件更晚發生;出自于我們聽到一段旋律,意會到一個音符接續著一個音符。對我們的時間意識而言,事件的先后之別是最基本的。
然而,時間僅止是在時間中各事件之間的關聯嗎?忽略與過去的關系,當下的時刻就沒有意義了嗎?再者,難道我們僅止是知道,對空間之物有所影響的時間中的事件嗎?如果沒有任何與這空間世界有關的事發生,難道時間就不存在了嗎?
若欲認出時間的終極意義,需要一種獨特的意識。我們全都生活于時間之中,是如此緊密地貼近它,以致我們反倒無法注意到它。空間世界圍繞著我們的存在,但這僅僅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則是時間。物只是海岸,真正航行的旅程是在時間之中。
存在從未藉由自身獲得闡明,存在只能透過時間方得以厘清。當我們閉上雙眼專注凝思,便能夠獲得毋須空間的時間,但我們絕無法擁有毋須時間的空間。在屬靈的眼光看來,空間乃是凍結的時間,所有的物都只是凝滯不動的事件。
我們可以從兩種觀點來覺察時間:一是空間的觀點,一是屬靈的觀點。從快速移動的火車車窗看出去,我們會有一種印象,就是我們自己仍靜止不動,移動的是窗外的風景。同樣的,當我們的靈魂被空間之物所運載,在凝視實在時,時間顯得是在不斷移動。然而,當我們學習去明白,乃是空間之物在不斷移動,我們便領會到,時間才是永不消逝的,事實本是空間世界在時間的無限擴展中滾動。如此,暫時性便可被定義為是空間對時間的關系。
實際上,所謂的空間,乃是一無邊界、連續而空虛的實體,它并不是實在的終極形式。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在時間中運行──從太初直到終末的日子──的空間世界。
對常人的心智來說,時間在本質上是短暫無常、稍縱即逝的。然而,真相是:當我們凝視空間之物時,時間從心頭倏忽而過。這是一個傳達給我們某種暫時感的空間世界。那超越空間、不依于空間的時間,乃是永存的;反而是這個空間世界愈趨朽壞。物在時間中朽壞,時間自身則不改變。我們不該說時間流逝,而應說空間流經時間。不是時間逝去,而是肉身在時間中逝去。暫時性是這空間世界的屬性,是空間之物的屬性。至于那超越空間的時間,卻超越了過去、現在、未來的劃分。
紀念碑注定要消逝,靈的日子卻永不過去。我們在出埃及記中讀到一段關于以色列民抵達西乃的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滿了三個月,在這日,就來到西乃的曠野。”(十九 1)這是一個令古代拉比感到困惑的表述:在這日?它本該說的是:在那日。這令人困惑的表述只有一種含義,就是賜下妥拉的那日從未過去;那日就是這日,就是每一日。無論我們何時研讀妥拉,對我們而言,它都“宛如是今天才賜給我們的”。出埃及的那日也具有同樣的含義:“每個世代的人,都必須把自己看成是彷佛曾親身走出埃及。”
一個偉大日子的價值,并不是以它在月歷上占據的空間來衡量。亞基巴拉比呼喊道:“所有的時間,都不若歌中之歌被賜給以色列的那日有價值,因為,所有的歌都是圣潔的,但歌中之歌乃是圣潔事物中最圣潔的。”
在靈的領域,一秒鐘與一世紀并無差異,一小時與一世代也沒有分別。族長猶大拉比(Rabbi Judah the Patriarch)發出吶喊:“有的人以一生的光陰獲致永恒,有的人卻在短短一小時中獲致永恒。”美好的一小時,或許有著彷如一生之久的價值;歸回上帝的那一瞬間,或可恢復那些遠離祂的失喪歲月。“在此世若有一小時的悔改與善行,勝過來世的全部生命。”
我們已說過,科技文明是人戰勝空間。可是,時間始終不為所動。我們可以征服空間上的距離,卻無法重拾過去,亦無法預知未來。人在空間之上,時間更在人之上。
時間是人所面臨最艱巨的挑戰。我們全都身在同一隊行伍中,走過時間的領地,永遠到不了終點,卻也無法獲得立足點。時間的實在遠非我們所能觸及。空間展露在我們的意志面前,我們可以隨自己高興來塑造和改變空間之物。然而,時間卻不是我們所能掌握。時間既切近又遠離我們,既內在于一切經驗,又超越一切經驗。時間獨獨屬乎上帝。
因此,時間乃是他性(otherness),一個遠非任何范疇所能含納的奧秘。時間和人的心智好像是兩個不相干的世界。可是,只有在時間中,才有眾生的團契和共性(togetherness)可言。
我們每個人都占據空間之一隅,彼此排斥地據有一方天地。我的肉身所占據的那一部分空間,是其他任何人所無法進駐的。然而,無人可占有時間。沒有任何時刻是我可以獨自占有的。這獨特的時刻固然隸屬于我,卻也隸屬于眾生。我們分享時間,卻占有空間。藉由爭奪空間的所有權,我是其他人的競爭者;藉由生活在時間的奧秘中,我是其他人的同代人。我們旅經時間,卻占據空間。我們很容易屈服在“空間世界乃為我而在、為人而在”的假象之下;但對時間,我們就不致產生這種假象。
神與物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原因在于,物是一種有別于存在整體、彼此分離的個別存在。看見一物,就是看見某種分別而孤立的事物。尤有甚者,物乃是、且可以是為人所擁有者。時間卻不允許任一瞬間可在其自身且為其自身地存在著。時間既非全體,亦非部分。時間不可分割,除非我們在心里分割。時間永遠超出我們的掌握。時間總是圣潔的。
永恒時間的偉大視野很容易被我們所忽略。根據出埃及記,摩西所看到的第一個異象是:“??從荊棘里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三 2)時間就像是永恒燃燒的荊棘。盡管每一時刻都必須消逝,以容讓下一時刻的到來,但時間本身卻并沒有被燒毀。
時間自身就有終極的價值,它甚至比滿布星辰的穹蒼更加莊嚴而令人生畏。時間以最古老的光華緩緩流逝,它所告訴我們的,遠比空間以其破碎物語所能說的多得多;時間乃是以個別存在為樂器,由此合奏出交響樂;時間釋放大地、使之成為現實。
時間是創世的歷程,空間之物是創世的結果。當我們注目于空間,可以得見創世的產物;當我們直觀于時間,則將聽聞創世的歷程。空間之物展現出一種虛假的獨立性。它們賣弄自己那虛假的、有限的持久性。這些被造之物將造物主隱藏起來。只有在時間的維度中,人才能遇見神,并開始意識到,每一個瞬間,都是創世行動,都是太初,都開啟嶄新的道路通往最終的實現。時間是上帝在空間世界中的臨在,也正是在時間中,我們才能夠覺察到萬物的合一。
我們所領受的教導是,創世并不是一個只發生過一次便一勞永逸的行動。使世界得以存在的行動,是個持續不斷的歷程。上帝創建世界,此一創建仍不斷在進行。只是因著上帝的臨在,才有當下的時刻。每一個瞬間都是創世的行動。一個時刻,并不是一個終點,而是太初的閃現,是太初的記號。時間是恒常的創新,是不斷創世的同義字。時間乃是上帝恩賜給空間世界的禮物。
一個沒有時間的世界,就是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一個在其自身并藉其自身而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更新,也不需要造物主。一個沒有時間的世界,就是一個與上帝隔絕的世界,只有物本身的世界,是未實現的實在。一個時間中的世界,則是一個通過上帝而向前進發的世界;是無限設計的實現;在這世界中的物,不是為自身,而是為上帝而存在。
為能見證世界創生的永恒旅程,就需在禮物中覺察贈禮者的同在,就需明白時間之根源乃是永恒,明白存在的秘密即是時間中的永恒。
我們無法透過對空間的征服、無法透過成就與名望,來解答時間的難題。我們只能藉由圣化時間來尋求答案。單從人來看,時間是晦澀難明的;對與神同行的人而言,時間則是喬裝了的永恒。
創造是上帝的語言,時間是上帝的詩歌,空間之物則是歌中的音符。每當我們圣化時間,便是與祂共同唱和。
生而為人的任務就是征服空間與圣化時間。
我們必須是為了圣化時間的緣故來征服空間。在周間,我們被呼召要借著與空間之物打交道來圣化時間。在安息日,我們被吩咐要在時間的中心同享圣潔。即使我們的靈命枯竭,即使我們緊繃的喉頭吐不出任何禱詞,安息日的安寧靜謐依然帶領我們通往無盡平安之境,并使我們開始意識到永恒的真義。在這世上,沒有任何觀念可以像安息日的觀念一樣,蘊涵如此豐富的屬靈能力。在千秋萬世之后,當許多我們所珍愛的理論僅存斷簡殘篇,那帷宇宙的錦繡依然發光如星。
永恒寓于一日。
科技文明就是人類對空間的征服。但這樣的征服,往往得犧牲一種基本的存在要素,這要素就是時間。處身科技文明中的我們,以時間換取空間;生活的主要目標即是在這空間世界里擴展自己的權力。然而,擁有得愈多,不表示愈真實地存在。我們在這空間世界所獲得的權力,在時間的疆界上戛然而止;惟有時間才是存在的核心。
控制這空間世界固然是我們人類擔負的一項任務,然而,如果我們在空間之域爭取權力的同時,卻失落了對時間之域的一切渴望,危機就此誕生。在時間之域中,生命的目標不是擁有,而是存在;不是占有,而是施予;不是控制,而是分享;不是征服,而是和諧共處。一旦對空間的控制、對空間之物的攫取,成為我們惟一的關注,生命就走上了岔路。
沒有任何事物比權力更為有用,但也沒有任何事物較權力更加可懼。過去,我們常常因為缺乏權力而受到剝削;如今,剝削我們的卻是權力所帶來的威脅。熱愛工作的確能帶來快樂,然而當我們在工作中貪得無饜,卻會跌入悲慘的境地。汲汲營營的心壺在利益之泉中破碎;世人若出賣自己,甘受物的奴役,便會成為這利益之泉中破碎的器皿。
科技文明根源于人心渴望征服與管理各種自然力量;工具的制作、紡織與耕作的技藝、房舍的建造、航海的技術──這一切都在人類的空間環境中不斷取得進展。時至今日,空間之物占據人們的心思意念,影響所及,包括眾人的一切活動,即便諸般宗教也經常受到如此的觀念所宰制。神祇居住在空間之中,廁身于特定所在,諸如群山、眾林、或樹或石,這些有神祇居住的地方特別被當作是圣所。神祇總與某一獨特的地點密不可分。“神圣”這個特質被視為與空間之物有所關聯,因此,首要的問題是:神在什么地方?人們狂熱擁護這個觀念,認為上帝就顯現在宇宙當中,結果卻因此認定上帝只顯現于空間之中、而非時間里面,顯現于自然、而非歷史,仿佛上帝只是物、不是靈。
甚至泛神論的哲學也是一種空間宗教:至高的存在被認為就是無限空間本身。“神即自然”,上帝的屬性就是向外延伸的空間,而不是時間。對斯賓諾莎(Spinoza)而言,時間僅止是一種偶然運動,一種思維模式。他并且打算以幾何學這種空間科學來建構哲學,這意味著他擁有的是一個空間取向的心智。
初民的心智很難不借助于想象力來理解一個觀念,而想象力正是馳騁于空間之域。諸神必定有其可見的形像,沒有形像的地方就沒有神靈。對圣像的崇敬,對圣山或圣所的崇敬,可不只是為多數宗教所固有,更是存在千代萬國的世人心中,不論他是虔誠的人、迷信的人,抑或反對宗教的人。所有人盡皆不斷向國旗、忠烈祠、為君王或民族英雄而立的紀念碑,宣誓他們的忠誠。無論何處,對忠烈祠的侮辱都被視為是種褻瀆,使得忠烈祠本身變得如此重要,世人反倒任其所紀念的事物遭到遺忘。紀念促成了遺忘,手段取消了目的。因為,空間之物任由世人擺布;縱然這些事物極其神圣而不能玷污,卻無法保證不為人所利用。為抓住神圣的特質,為使神靈永遠臨在,世人遂塑造神靈的形像。但是,一位可被塑形的神,一位可被局限的神,不過是人的影子罷了。
空間的光輝,與空間之物的華美,在在使我們著迷。物,是一種拖累人們心神、宰制我們全副心思的東西。我們的想象力傾向于將一切概念形像化;在每日生活中,我們首要關注于感官所向我們表明之物,關注于眼目所見、十指所觸之物。對我們來說,實在就是物性(thinghood),由占據空間一隅的物質所構成;就連上帝也被多數人設想為一種物。
我們惟物是瞻,所導致的后果就是我們看不見整個實在,以致我們無法認出:物只是物,物實際上只是材料。顯而易見的,當我們這樣來理解時間時,那無物性、非物質的時間,于我們而言就好像毫無實在可言。
的確,我們知道如何應付空間,但在面對時間時,非得使之臣服于空間之下,否則我們將手足無措。大部分人辛勤勞動,仿佛只是為著空間之物而作,至終,我們在被迫直視時間的面容時會驚駭不已,受困于對時間深植不移的恐懼中。我們遭受時間的譏笑,它就像是只老奸巨猾的怪物,張開熔爐般的大嘴,一口口吞噬人生的每一寸光陰,將之焚燒殆盡。于是,我們在時間面前退縮,逃到空間之物那兒尋求蔭蔽。我們將自己無力實踐的意圖寄望于空間之上;于是,財產象征了我們的壓抑,慶典象征了我們的挫敗。但空間之物無法防火,它們只會火上加油。難道,擁有財貨的喜悅,足以化解我們對時間的害怕?特別是這害怕終究會變成對那無以逃避之死亡的恐懼。被夸大的物,偽裝成幸福,實際上卻是對我們真實生命的威脅;倘若我們致力于空間之物,這更多是自尋煩惱,而不是得其祝佑。
世人不可能躲避時間問題。我們愈多思考,便愈了解到:我們無法藉由空間征服時間。我們只能在時間中掌管時間。
靈性生活的更高目標,不在于積存大量信息,而在于面對神圣時刻。比方說,在宗教經驗中,我們所領受的并不是物,而是一種屬靈的臨在。真正能在靈魂里留下痕跡的,并非行動所經過的場所,而是某個帶來洞察的時刻。這洞察的時刻是個機會,能帶領我們超越物理時間的限制。一旦我們無法感受到時間中這種永恒的榮美,靈性生活就開始腐化了。
我在此無意輕視空間世界。貶抑空間與空間之物的祝福,也就是貶抑創世大工,而那本為上帝眼中“看著是好的”。不可單單從時間的角度看世界;時間與空間彼此關聯,忽略任何一方都將使我們陷于半盲之境。我在此所要抗議的,乃是世人向空間無條件投降,甘為物之奴仆。我們絕不可忘記:并非物使時間有了意義,乃是時間使物有了意義。
和空間比起來,圣經談得更多的是時間;圣經在時間的維度中看待世界。圣經對世代與事件的關注,遠多于對列國與物事的關注;圣經更多關心歷史,而非地理。為理解圣經的教導,我們必須接受其前提,這前提就是:時間對生命的意義就算不比空間重要,也絕不遜色;時間有其自身的重要性與獨立性。
圣經希伯來文沒有“物”(thing)這字的同義字。后期希伯來文用以指“物”的“davar”,在圣經希伯來文中則意味了:“言語”、“字詞”、“信息”、“報導”、“音訊”、“勸告”、“要求”、“應許”、“決心”、“語句”、“主題”或“故事”、“言說”或“表述”、“職務”或“事務”、“行動”、“善行”、“事件”、“方式”或“方法”或“理由”或“原因”;但就是沒有“物”的意思。這只是因為圣經語言的貧乏嗎?還是說圣經的本意就是希望指出一種合乎中道的世界觀,提醒我們不可用物性來表達實在(reality;源于拉丁字 res,即“物”的意思)?
宗教史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就是農業節日轉變成紀念歷史事件的慶典。古人的節日與自然節氣緊密相連,他們在時序變遷中,歡慶在自然生活里所經歷到的事情;于是,節日的價值取決于自然帶來怎樣的物事而定。可是,在猶太教里,卻出現了變化:逾越節本是個春季節日,卻成為歡慶出埃及的日子;七七節本是在麥子收割的尾聲舉行的古老收割節(hag hakazir;出二十三 16,三十四 22),卻成為歡慶在西乃山賜下律法的日子;住棚節本是慶祝葡萄收成的古老節日(hag haasif;出二十三 16),卻成為紀念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時居住在棚里的日子(利二十三 42?43)。對以色列人來說,盡管自然界的循環與我們肉身生命的存活息息相關,但是歷史時間中的獨特事件,比自然循環中的反復歷程具有更多的屬靈意義。當其他民族的神祇關聯于處所或物事時,以色列的上帝卻是事件的上帝:祂是奴隸的救贖主,是律法書的啟示者,祂自己乃是顯現在歷史事件中,而非顯現在物事或處所中。于是,一種對于不具形體、無以思量者的信仰,就這樣誕生了。
猶太教是個時間的宗教,以時間的圣化為目標。對于那些空間取向的心智而言,時間是凝滯不變、反復循環、同質無異的,他們認為所有時刻都無甚分別,只是空殼,不具實質;圣經非但不是如此,反倒覺察到時間的多樣化特質:沒有兩個時刻是同樣的,每一時刻都是獨特的,是在當下那惟一的時刻,是獨一無二、全然寶貴的時刻。
猶太教教導我們,怎么與時間中的圣潔相連、與各種神圣的事件相連,學習如何在一整年的歲月之流里,把一個個浮現出來的美麗安息日視為圣殿,尊崇敬奉;換言之,安息日就是我們的大會堂。至于我們最重要的“至圣所”,就是贖罪日,這是一個無論羅馬人或德國人皆無法焚毀、即便背離了信仰亦無法遺忘的“地方”。據古代拉比所言,并不是因著我們守贖罪日,而是緣于這日子本身,緣于“這日子的本質”,人們在其中懺悔,才得以贖回吾人之罪孽。
我們可以將猶太教的禮儀刻畫為是關于時間之諸般意義形式的藝術,宛若是種時間的建筑學。對這禮儀的遵行,像是守安息日、月朔、各式節日、安息年與禧年,大多取決于一日中的特定時刻或一年中的特定時節而定。比方說,“喚禱”(the call to prayer)的儀式,即依循著黃昏、清晨、晌午的時序進行。猶太信仰的主題盡皆寄于時間之域。我們記得出埃及的那日,記得以色列民站在西乃山腳的那日;而我們對彌賽亞的盼望也是在期待一個日子,期待那諸日終結之日。
在一場精心構思的藝術表演中,最為重要的理念或角色不會隨便出場,而是像皇室典禮中的君王般,在某一特定時刻、以某種特定方式出場,來顯明其權柄與領袖地位。而在圣經里,字詞的使用同樣是極度講究的,尤其那些在圣經世界的廣闊意義體系中,如火柱般具備引路功能的字詞,更是如此。
最著名的圣經字詞之一,就是 qadosh(圣/圣潔)這個字;它比其他任何字詞都更能表達出上帝的奧秘和尊榮。那么,在世界歷史中,第一個被認為是圣潔事物的是什么呢?是一座山嗎?還是一座祭壇?
首次出現 qadosh 此一著名字詞的,自然是創世記中創世故事的尾聲:“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定為圣日。”換言之,qadosh 這個字被用在時間上;這是一個具有何等深意的做法!事實上,我們在創世記載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節經文曾經指出,空間中的事物是可以被賦予圣潔性質的。
這與我們習以為常的宗教思維正好相反。神秘主義者的心靈會期待,在天地獲得建立后,上帝會創造一個圣地──無論是圣山或是圣泉──隨之在其上建造一間圣所。然而,就圣經而言,天地建造完成后,最先出現的卻是那時間中的圣潔,也就是安息日。
在歷史的開端,世上只有一種圣潔,即時間中的圣潔;直到在西乃山上,上帝之言即將被道出時,才宣告了一種在人里面的圣潔:“你歸我為圣潔的民。”只有當百姓遭到試探去敬拜物,也就是敬拜那金牛犢后,上帝才吩咐設立會幕,那在空間中的圣潔。首先是時間的圣化,其次是人的圣化,最后是空間的圣化。時間由上帝使之為圣;空間,也就是會幕,則由摩西使之為圣。
雖然節日所紀念的事件都是發生于時間之中,但是這些節日所舉行的日期,仍舊依據著我們生活中的自然事物而定。比方說,逾越節和住棚節總在滿月之際慶祝;所有節慶都在某個月份中的某日來舉辦,而月份則反映了自然界中周期性發生的事情;猶太人的月份便是從朔月開始算起,直到另一輪新月再度出現在夜空中。相較之下,安息日全然與月份和月之盈缺無關,安息日的日期并不依憑于任何諸如月朔這類自然事件,而是依于創世的行動。因此,安息日究其本質乃是徹底獨立于我們的空間世界之外。
安息日的意義在于歡慶時間,而非空間。我們一周有六天生活在空間之物的宰制下;但到了安息日,我們試著讓自己與時間中的圣潔有所共鳴。在這日子,我們被呼召去分享那時間中的永恒事物,被呼召從創世的結果轉而關注創世的奧秘,從受造的世界轉而關注對世界的創造行動。
跋:圣化時間
外邦人將他們對上帝的意識投射為某個可見的形像,或將上帝與某種自然現象、某種空間之物連結起來。但在十誡里,世界的創造主顯明自己的方式,乃是透過一個歷史事件,透過一個時間中的事件,這事件就是祂將祂的百姓從埃及解救出來,并對他們宣告說:“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在地上曾經有過的最寶貴事物,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領受的兩塊石版,它們是無可比擬的無價之寶。摩西曾上到這山去領受它們,并待在那里四十晝夜,既不吃餅,也不喝水。上主交給他兩塊石版,在上面寫下十誡,這是在山上,上主從火中對以色列民所說的話語。但四十晝夜結束后,手里拿著兩塊法版的摩西下山之際,卻看到百姓圍著金牛犢跳舞,他便把手中的法版扔掉,在眾人眼前摔碎了。
“在埃及,每一個重要的宗教中心,都會根據“此乃創世之地”的說法來宣稱它的優越性。”相較之下,創世記則是說到創世之日,而非創世之地。
眾神話皆未提及創世的時間,圣經卻偏偏說到空間在時間中的受造。
人人都知道,大峽谷要比小溝渠更能引發敬畏之情;人人都知道,蟲子與老鷹有多么不同。但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對時間的差異具有同等的鑒別力?歷史學家蘭克(Ranke)宣稱,每個時代離上帝都同樣近。但猶太傳統則宣稱,在時間中有一種時代的階層,每個時代都不一樣。世人可以同等地在任何地點向上帝祈禱,但上帝卻不是同等地在任一時代向世人說話。比方說,在特定的時刻,先知預言之靈便離開了以色列。
對我們來說,時間只是個用來度量某個物理量的機制,而非我們棲居于其間的生活領域。我們的時間意識出自于對兩個事件的比較,發現其中一個事件比另一事件更晚發生;出自于我們聽到一段旋律,意會到一個音符接續著一個音符。對我們的時間意識而言,事件的先后之別是最基本的。
然而,時間僅止是在時間中各事件之間的關聯嗎?忽略與過去的關系,當下的時刻就沒有意義了嗎?再者,難道我們僅止是知道,對空間之物有所影響的時間中的事件嗎?如果沒有任何與這空間世界有關的事發生,難道時間就不存在了嗎?
若欲認出時間的終極意義,需要一種獨特的意識。我們全都生活于時間之中,是如此緊密地貼近它,以致我們反倒無法注意到它。空間世界圍繞著我們的存在,但這僅僅是生活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則是時間。物只是海岸,真正航行的旅程是在時間之中。
存在從未藉由自身獲得闡明,存在只能透過時間方得以厘清。當我們閉上雙眼專注凝思,便能夠獲得毋須空間的時間,但我們絕無法擁有毋須時間的空間。在屬靈的眼光看來,空間乃是凍結的時間,所有的物都只是凝滯不動的事件。
我們可以從兩種觀點來覺察時間:一是空間的觀點,一是屬靈的觀點。從快速移動的火車車窗看出去,我們會有一種印象,就是我們自己仍靜止不動,移動的是窗外的風景。同樣的,當我們的靈魂被空間之物所運載,在凝視實在時,時間顯得是在不斷移動。然而,當我們學習去明白,乃是空間之物在不斷移動,我們便領會到,時間才是永不消逝的,事實本是空間世界在時間的無限擴展中滾動。如此,暫時性便可被定義為是空間對時間的關系。
實際上,所謂的空間,乃是一無邊界、連續而空虛的實體,它并不是實在的終極形式。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在時間中運行──從太初直到終末的日子──的空間世界。
對常人的心智來說,時間在本質上是短暫無常、稍縱即逝的。然而,真相是:當我們凝視空間之物時,時間從心頭倏忽而過。這是一個傳達給我們某種暫時感的空間世界。那超越空間、不依于空間的時間,乃是永存的;反而是這個空間世界愈趨朽壞。物在時間中朽壞,時間自身則不改變。我們不該說時間流逝,而應說空間流經時間。不是時間逝去,而是肉身在時間中逝去。暫時性是這空間世界的屬性,是空間之物的屬性。至于那超越空間的時間,卻超越了過去、現在、未來的劃分。
紀念碑注定要消逝,靈的日子卻永不過去。我們在出埃及記中讀到一段關于以色列民抵達西乃的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滿了三個月,在這日,就來到西乃的曠野。”(十九 1)這是一個令古代拉比感到困惑的表述:在這日?它本該說的是:在那日。這令人困惑的表述只有一種含義,就是賜下妥拉的那日從未過去;那日就是這日,就是每一日。無論我們何時研讀妥拉,對我們而言,它都“宛如是今天才賜給我們的”。出埃及的那日也具有同樣的含義:“每個世代的人,都必須把自己看成是彷佛曾親身走出埃及。”
一個偉大日子的價值,并不是以它在月歷上占據的空間來衡量。亞基巴拉比呼喊道:“所有的時間,都不若歌中之歌被賜給以色列的那日有價值,因為,所有的歌都是圣潔的,但歌中之歌乃是圣潔事物中最圣潔的。”
在靈的領域,一秒鐘與一世紀并無差異,一小時與一世代也沒有分別。族長猶大拉比(Rabbi Judah the Patriarch)發出吶喊:“有的人以一生的光陰獲致永恒,有的人卻在短短一小時中獲致永恒。”美好的一小時,或許有著彷如一生之久的價值;歸回上帝的那一瞬間,或可恢復那些遠離祂的失喪歲月。“在此世若有一小時的悔改與善行,勝過來世的全部生命。”
我們已說過,科技文明是人戰勝空間。可是,時間始終不為所動。我們可以征服空間上的距離,卻無法重拾過去,亦無法預知未來。人在空間之上,時間更在人之上。
時間是人所面臨最艱巨的挑戰。我們全都身在同一隊行伍中,走過時間的領地,永遠到不了終點,卻也無法獲得立足點。時間的實在遠非我們所能觸及。空間展露在我們的意志面前,我們可以隨自己高興來塑造和改變空間之物。然而,時間卻不是我們所能掌握。時間既切近又遠離我們,既內在于一切經驗,又超越一切經驗。時間獨獨屬乎上帝。
因此,時間乃是他性(otherness),一個遠非任何范疇所能含納的奧秘。時間和人的心智好像是兩個不相干的世界。可是,只有在時間中,才有眾生的團契和共性(togetherness)可言。
我們每個人都占據空間之一隅,彼此排斥地據有一方天地。我的肉身所占據的那一部分空間,是其他任何人所無法進駐的。然而,無人可占有時間。沒有任何時刻是我可以獨自占有的。這獨特的時刻固然隸屬于我,卻也隸屬于眾生。我們分享時間,卻占有空間。藉由爭奪空間的所有權,我是其他人的競爭者;藉由生活在時間的奧秘中,我是其他人的同代人。我們旅經時間,卻占據空間。我們很容易屈服在“空間世界乃為我而在、為人而在”的假象之下;但對時間,我們就不致產生這種假象。
神與物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原因在于,物是一種有別于存在整體、彼此分離的個別存在。看見一物,就是看見某種分別而孤立的事物。尤有甚者,物乃是、且可以是為人所擁有者。時間卻不允許任一瞬間可在其自身且為其自身地存在著。時間既非全體,亦非部分。時間不可分割,除非我們在心里分割。時間永遠超出我們的掌握。時間總是圣潔的。
永恒時間的偉大視野很容易被我們所忽略。根據出埃及記,摩西所看到的第一個異象是:“??從荊棘里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三 2)時間就像是永恒燃燒的荊棘。盡管每一時刻都必須消逝,以容讓下一時刻的到來,但時間本身卻并沒有被燒毀。
時間自身就有終極的價值,它甚至比滿布星辰的穹蒼更加莊嚴而令人生畏。時間以最古老的光華緩緩流逝,它所告訴我們的,遠比空間以其破碎物語所能說的多得多;時間乃是以個別存在為樂器,由此合奏出交響樂;時間釋放大地、使之成為現實。
時間是創世的歷程,空間之物是創世的結果。當我們注目于空間,可以得見創世的產物;當我們直觀于時間,則將聽聞創世的歷程。空間之物展現出一種虛假的獨立性。它們賣弄自己那虛假的、有限的持久性。這些被造之物將造物主隱藏起來。只有在時間的維度中,人才能遇見神,并開始意識到,每一個瞬間,都是創世行動,都是太初,都開啟嶄新的道路通往最終的實現。時間是上帝在空間世界中的臨在,也正是在時間中,我們才能夠覺察到萬物的合一。
我們所領受的教導是,創世并不是一個只發生過一次便一勞永逸的行動。使世界得以存在的行動,是個持續不斷的歷程。上帝創建世界,此一創建仍不斷在進行。只是因著上帝的臨在,才有當下的時刻。每一個瞬間都是創世的行動。一個時刻,并不是一個終點,而是太初的閃現,是太初的記號。時間是恒常的創新,是不斷創世的同義字。時間乃是上帝恩賜給空間世界的禮物。
一個沒有時間的世界,就是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一個在其自身并藉其自身而存在的世界,不可能更新,也不需要造物主。一個沒有時間的世界,就是一個與上帝隔絕的世界,只有物本身的世界,是未實現的實在。一個時間中的世界,則是一個通過上帝而向前進發的世界;是無限設計的實現;在這世界中的物,不是為自身,而是為上帝而存在。
為能見證世界創生的永恒旅程,就需在禮物中覺察贈禮者的同在,就需明白時間之根源乃是永恒,明白存在的秘密即是時間中的永恒。
我們無法透過對空間的征服、無法透過成就與名望,來解答時間的難題。我們只能藉由圣化時間來尋求答案。單從人來看,時間是晦澀難明的;對與神同行的人而言,時間則是喬裝了的永恒。
創造是上帝的語言,時間是上帝的詩歌,空間之物則是歌中的音符。每當我們圣化時間,便是與祂共同唱和。
生而為人的任務就是征服空間與圣化時間。
我們必須是為了圣化時間的緣故來征服空間。在周間,我們被呼召要借著與空間之物打交道來圣化時間。在安息日,我們被吩咐要在時間的中心同享圣潔。即使我們的靈命枯竭,即使我們緊繃的喉頭吐不出任何禱詞,安息日的安寧靜謐依然帶領我們通往無盡平安之境,并使我們開始意識到永恒的真義。在這世上,沒有任何觀念可以像安息日的觀念一樣,蘊涵如此豐富的屬靈能力。在千秋萬世之后,當許多我們所珍愛的理論僅存斷簡殘篇,那帷宇宙的錦繡依然發光如星。
永恒寓于一日。
目次
前言:時間的建筑學
第一章時間的殿堂
第二章超越文明
第三章空間的光輝
第四章惟獨天國,別無一物?
第五章“你是惟一”
第六章日子的同在
第七章永恒寓于一日
第八章直觀永恒
第九章時間中的圣潔
第十章務要貪婪
跋:圣化時間
附錄:父親的安息日(蘇珊娜·赫舍爾)
第一章時間的殿堂
第二章超越文明
第三章空間的光輝
第四章惟獨天國,別無一物?
第五章“你是惟一”
第六章日子的同在
第七章永恒寓于一日
第八章直觀永恒
第九章時間中的圣潔
第十章務要貪婪
跋:圣化時間
附錄:父親的安息日(蘇珊娜·赫舍爾)
書摘/試閱
我們家就如每一個敬虔的猶太家庭,禮拜五晚上是一周的高峰時刻。母親和我會點亮安息日燭臺,瞬時間我感覺自己的心境、甚至包括自己的身體,都得到了轉化。在點亮餐廳的燭光后,我們會走進客廳,那里有幾扇向西的窗戶,可以看到哈德遜河(HudsonRiver),我們就在那兒贊嘆頃刻來到的落日之美。
那份隨著我們點起燭光而到來的平安感受,多少也與禮拜五的緊張忙亂有關。父親常說,迎接一個圣潔日子的預備工作,與這日子本身一樣重要。整個早上,母親忙碌地采買食品,到了下午,當她作菜時,緊張的氣氛便逐漸升高。父親會在日落前一或二小時,從他的辦公室回來,好預備他自己。而當這一整周的工作時刻即將結束之際,我的父母都在廚房里,瘋狂地要想起他們可能忘記預備的事項──水煮開了嗎?遮爐片(blech)蓋住火爐了嗎?烤箱啟動了嗎?
霎時,時間到了──這是日落前二十分鐘。當我們點亮燭光、祝禱安息日之到來時,無論在廚房還有什么事沒能完成,盡皆拋諸身后。父親如此寫道:“安息日之來到,像是一種撫慰,抹去恐懼、哀傷與黯淡的記憶。”
父親很少在禮拜五晚上到會堂去,他喜歡在家里禱告,而我們的晚餐通常是安靜、緩慢而放松的。我的父母并未參與很多社交活動,但大約每隔兩個月,他們會邀請一些朋友或同事來參加安息日晚宴。菜單千篇一律:我們的哈拉面包(challah)譯1是在當地的面包鋪買的,母親會煮雞湯、烤小母雞、準備色拉和青菜。至于餐后甜點,父親會削一顆金冠蘋果,試著不要削斷蘋果皮,我們大家就共享這顆蘋果。母親對廚藝并不熱衷,父親也總是吃得很清淡,因此,這些食物并不會令我們感到興奮。盡管如此,在每一次用餐前,父親總會舉起他的叉子,看著我說道:“媽咪是位好廚師。”
在我們的安息日晚宴上,有一個不常見的規矩:
父親從他的姊夫、一位克比基尼徹拉拜(KopycznitzerRebbe)那兒得到一份禮物,是兩個長形鑲銀的香料盒,里面放著番石榴枝和尤加利葉。雖然通常是在安息日結束時的祝禱禮,才會祝福并聞它們的馨香之氣,但我們會在舉行祝酒禱辭之前便祝福與聞香氣,這是一個哈西德派譯的習慣,這習慣在拉比文獻中的依據可參考我父親在本書的討論。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優惠價:87
146
海外經銷商無庫存,到貨日平均30天至4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