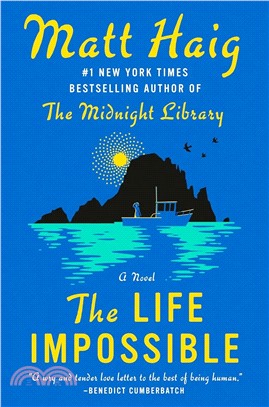商品簡介
陳忠實編著的《白墻無字》內容介紹:自進入社會開始工作直到今天,不覺間競有五十個年頭了,無論換過多少單位的辦公室.或是鄉下和城里的住宅,還有現在的工作點的房子里,除了幾樣簡單的辦公和生活用具,四面墻壁從來都不曾掛一方紙頁想來似乎還不是有意為之,純粹屬于一種無意識的習性驅使下的習慣。想做的事和宗教認可的行為準則,努力去做努力追尋就可以了,萬一實現不了或發生錯誤,宗教總結自我反省,也可以避免吹牛和言行不一的尷尬……我的墻壁一九空白著。
作者簡介
陳忠實,1942年生于西安灞橋區。自1965年發表散文處女作以來,迄今進行文學創作近半個世紀,其間,有多篇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獲獎。1993年,他厚積薄發,以雄奇史詩般的長篇小說《白鹿原》斬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奠定了文壇地位,創造了長篇小說的藝術高峰。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目次
散文 僅說一種本能的情感驅使 我讀《創業史》 熱情率性與悄沒聲息 我經歷的狼 大智慧者的人生選擇 十九屆世界杯足球賽點評(十三篇) 毛烏素沙漠的月亮 我經歷的鬼
書摘/試閱
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三十一年前的1979年的2月下旬,因“文革”而癱瘓了十余年的陜西作家協會(當時為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我有幸作為代表參加。會議結束的那天下午,一位陌生人敲門并走進我的房子,開口便自報家門:我是《陜西日報》文藝部的編輯呂震岳。我自然虔誠恭敬迎接。老呂頭發脫得稀疏,臉上突兀著一副高而又直的鼻梁,說話嗓門很響亮。他沒有一句客套和寒暄的話,開口便約稿,并再三強調副刊版面最大的容載量是七千字。說完急匆匆走掉了。
我在這年春天剛剛開始新時期的文學創作,興致正盛,接連寫了三四個短篇,都送給幾家文學雜志了。盡管記著老呂的約稿,卻無奈這幾篇小說都在萬字上下,報紙版面難以容納。到五月初,收到老呂一封短信,催問約稿事。我頓然覺得有負老呂了,當即決定把正在構思的一個短篇小說確定給他寫出來,關鍵還是七千字的極限。我便從兩條途徑探路,一是結構,要集中要緊湊;二是語言,必須簡潔凝練,才可能縮短篇幅,經兩三構思,較為順利寫成《信任》。尚不足七千字,甚為慶幸。這篇小說托一位正好要去陜報的作家朋友丁樹榮捎給老呂,我便帶著被褥騎著自行車到西安北郊農村參加夏收勞動去了。
大約半月后,我從下鄉的農村回到西安郊區文化館,才知道《信任》已發表多日,從送走稿件到見諸報紙剛好一周時間,這是我的習作發表得最快的一次。又過了幾天收到老呂來信,說《信任》見報后反響很大,不斷有讀者打電話和寫信說看法,約我到報社去看讀者來信。第二天我趕到陜報,老呂很興奮,嗓門更響亮,把一摞讀者來信交給我。我讀著那些多為贊賞《信任》的或長或短的信,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欣慰。那些寫信的人,是全省各地從事各種職業的男人和女人,我更感覺到心理上的踏實。
此時《人民文學》一位編輯到陜西組稿,我很敬重又很崇拜的王汶石向她推薦了《信任》,當即在7月號《人民文學》轉載(各種文學選刊尚未創刊)。這事我隨后才得知,更敬重王汶石老師了。
1980年春節剛過,接到北京一位編輯來信,告知《信任》獲得第二屆全國短篇小說獎,這又是太過重大的喜訊。這屆評獎是由讀者投票推選,可以判斷不單陜西讀者喜歡《信任》。這一年《陜西日報·秦嶺副刊》搞農村題材征文評獎,老呂寫信約我應征。我很用心寫了《第一刀》,發表后不久,老呂又電話告我去編輯部看讀者來信。我看著那些評說習作的熱情洋溢的信,鼓舞和欣慰是最好的享受了。老呂摘編發表了三位讀者來信。這是我最早寫農村體制改革的一個短篇小說,由此發端,三年后寫成十二萬字的中篇小說《初夏》。
十年后的1990年初秋某日,我從鄉下回到省作家協會開會,《陜西日報》副刊部年青編輯田長山和另外三位先生趕來,說陜報要宣傳一位長期深入渭北的農業科技工作者李立科,要我采訪寫作報告文學,且鄭重說明,是陜報總編輯騫國政點名欽定的。我當時正融入《白鹿原》的寫作過程,孤守原下一隅,目無暇顧,當即推辭。然架不住幾位編輯詞懇意切的煽火,尤其說到是省委決定要宣傳這位默默地為農民干實事的科學家,我不敢執意推辭了,只得把手頭正寫的《白》暫且放下,便接受下來,僅提出一個要求,讓田長山和我聯手完成這一寫作使命。
一個由農業科技記者、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共七八人組成的采訪組來到合陽縣。我平生唯一一次被授名為特約記者。我們見到了李立科。我們和李立科坐下長談。主要是傾聽李立科說他在合陽十幾年的科技普及和推廣,自然免不了發問。我們到幾個鄉鎮和幾個村莊,訪問那些接受新技術并且獲得顯著效益的干部和農民,更多地感知到干部和農民對李立科的贊頌乃至感恩的真摯情感。我們跟著李立科來到田間地頭,親眼看到實施他的新技術和未用新技術的麥田里差異明顯的麥苗,起碼對我也是一次科技知識的普及。記得我們采訪到號稱合陽的西北利亞的一個鄉鎮,那位樸實而又務實的鄉黨委書記說到李立科,似乎有講不完的故事,言語里深沉的情感味兒是那樣自然的、由衷的。這個號稱西北利亞的鄉鎮,年降雨量很少,李立科的新技術正好解決了缺水保墑使麥子增產的矛盾,他說他這個書記也好當了。我至今依舊不能忘懷的是,接受我們采訪的李立科不久前剛剛做過面部頜骨癌癥手術,說話困難;許多接受采訪的男女鄉民,說著說著便泣不成聲……我在那一刻,真實地理解了作為一個人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那些男女鄉民的眼淚,無疑是對一個堪稱偉大生命的禮贊。
回到西安不久,我和田長山寫成了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于一個人的記憶》。全篇約一萬五千字,《陜西日報》全文刊發。
隔日,陜西省委和陜西省政府聯合作出向李立科學習的決定,在《陜西日報》頭版刊登。一個長期扎根渭北高原為民興利造福卻默默無聞的農業科學家李立科,突顯在人們眼前,影響著也提升著人們的審美和價值判斷。我也完成了一次心靈洗禮。
1992年春天,在寫完《白鹿原》等待編輯審稿意見的頗為忐忑的情境里,我一個人仍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徒增吟誦古典詩詞的興致。初夏時節,一個始料不及的好事發生了,《渭北高原,關于一個人的記憶》被評為1990~1991年度全國報告文學獎。這是中國作協的獎項,《渭》文是由誰家推薦參評,我竟然不知,所以說是意料不及的好事。
三十多年過去,我頗多感慨,在我文學寫作的生涯中,有幸獲得三項國家文學獎,而其中兩項(短篇小說獎和報告文學獎)的作品,都是在《陜西日報》發表的,而且是編輯熱誠邀約促成的創作。且不論理性的意義,也不說道德的操守,單就純粹本能的情感驅使,恰是《陜西日報》這方平臺,讓我獲得了文學創作探索過程中的重要突破……許多年來,凡有《陜西日報》召喚,需我配合,我都不敢馬虎,多是那種本能的情感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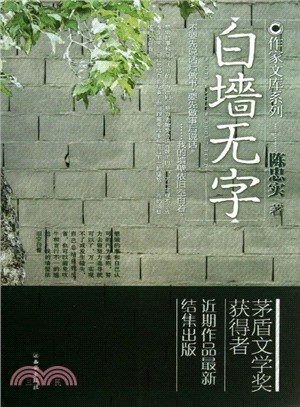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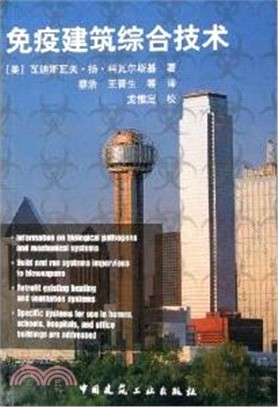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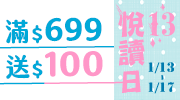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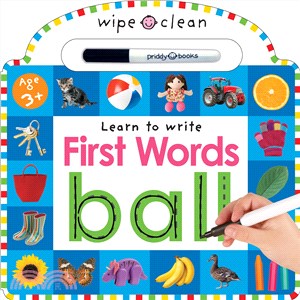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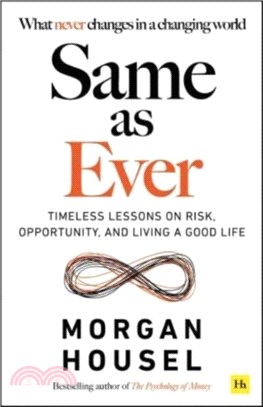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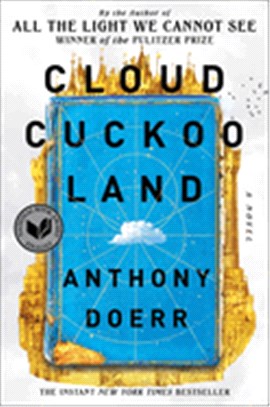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