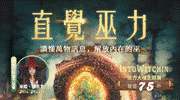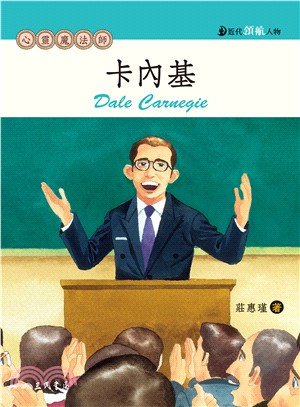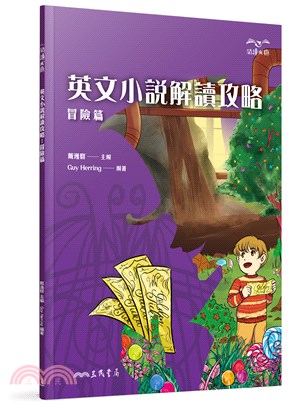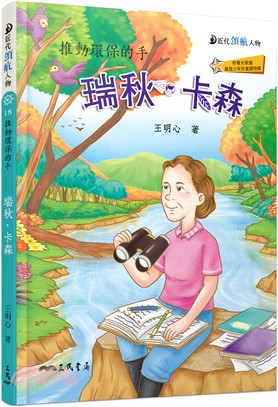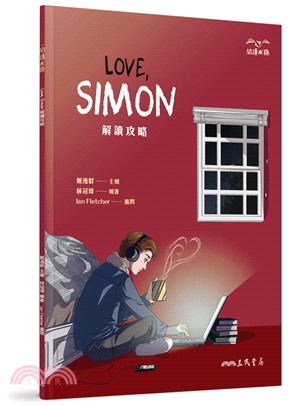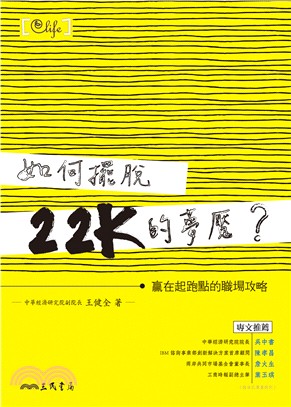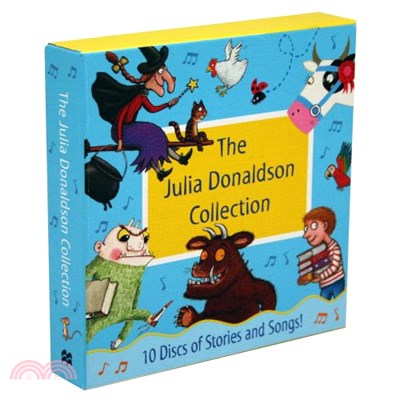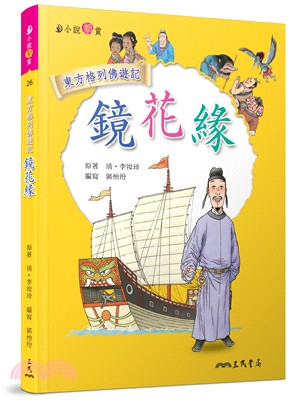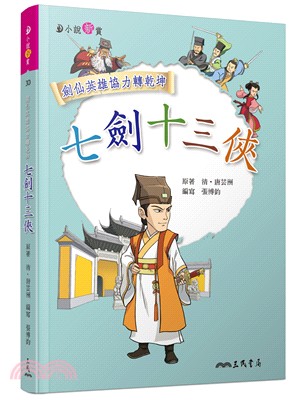匆促的記者―公民新聞、媒體與社會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公民新聞,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與操作,更是網絡與個人傳播設備普及後一個方興未艾的現象。公民記者的出現,代表專業記者在報導和評論公共事務上已脫離人民的期待。
不管是民主或集權國家,跟傳統新聞記者一樣,公民記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別。公民,而為記者,這是另類新聞的建構,對建制新聞的一種不滿和挑戰。
「匆促的記者」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著重公民記者「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專業記者「唯利是圖」的急就章。兩者的互動牽涉公民社會與主流新聞媒體的為與不為,關係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生活經驗的取捨。
由於歷史因素、結構和環境使然,中港台的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論是追求利潤的異化,或依附權勢的腐化,主流新聞媒體的墮落都有脈絡可尋,公民新聞的理念和實踐也因此有相當差異的走向,反映出整體需求與個人機會安排的分野。
這是第一本比較中港台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專著。透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匆促的記者」嘗試在名詞和行動之間,檢視公民新聞的促因、守門人和新聞界限、公民社會的擴張、微博與新聞自由、獨立媒體和財團壟斷、公民記者和國家機器、與新聞何去何從等問題。
不管是民主或集權國家,跟傳統新聞記者一樣,公民記者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方面,都不可或缺,只是角色及功能有別。公民,而為記者,這是另類新聞的建構,對建制新聞的一種不滿和挑戰。
「匆促的記者」有雙重含義,一方面著重公民記者「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另一方面批判專業記者「唯利是圖」的急就章。兩者的互動牽涉公民社會與主流新聞媒體的為與不為,關係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和生活經驗的取捨。
由於歷史因素、結構和環境使然,中港台的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呈現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論是追求利潤的異化,或依附權勢的腐化,主流新聞媒體的墮落都有脈絡可尋,公民新聞的理念和實踐也因此有相當差異的走向,反映出整體需求與個人機會安排的分野。
這是第一本比較中港台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的專著。透過理論探討和實證分析,「匆促的記者」嘗試在名詞和行動之間,檢視公民新聞的促因、守門人和新聞界限、公民社會的擴張、微博與新聞自由、獨立媒體和財團壟斷、公民記者和國家機器、與新聞何去何從等問題。
作者簡介
張讚國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冒牌記者?公民記者的理論與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聞的促因:商業媒體的墮落
第三章
新聞無界限:消失的守門人
第四章
公民社會的擴張:人人都是記者
第五章
中國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獨立媒體:夾縫中的聲音
第七章
台灣公民記者:愛拼才會贏
第八章
結論:新聞與公民記者何去何從
第一章
冒牌記者?公民記者的理論與操作
第二章
公民新聞的促因:商業媒體的墮落
第三章
新聞無界限:消失的守門人
第四章
公民社會的擴張:人人都是記者
第五章
中國微博:以小博大的精神
第六章
香港獨立媒體:夾縫中的聲音
第七章
台灣公民記者:愛拼才會贏
第八章
結論:新聞與公民記者何去何從
書摘/試閱
匆促的記者:由名詞到行動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
這期間,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病情,於2003年3月15日將最早在廣東被看成是怪病的傳染病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任何簡稱的根本作用,不過在方便溝通,避免冗長的文字減低傳播的效率。
SARS的英文縮寫卻讓香港特區政府(SAR)頗為難堪(《南華早報》雜誌,2013年3月31日,頁27),在官方發佈的英文新聞稿中堅持稱為atypical pneumonia, 中文是「非典型性肺炎」或「非典」,音譯為「沙士」。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阿Q罷了,不管如何稱呼,SARS的致命力不會因用字不同而有所差別,就像在國名冠上「人民」兩字的國家,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從官方到民間,由海內到海外,中國掩飾SARS疫情的動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安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地方官僚無能顢頇、醫療預警系統的腐敗、草菅人命、建立政府威信或保護國家形象等,不一而足。美國《時代》雜誌2003年5月5日以「SARS的真相」為題的封面報導,只是其中一個對中國的嚴厲指控。
剛開始時,北京政權信誓旦旦,堅持一切都在衛生機構的控制之下,還多少瞞天過海,讓各國信以為真。最終引起其他國家重視SARS的新聞報導,不是出自中國或香港的媒體,而是美國的《時代》雜誌和其他媒體。
10年後,根據Fionnuala McHugh在《南華早報》(2013年3月31日,頁27)雜誌的報導,SARS似乎是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海外媒體所預期報導的故事,它們幾乎指望帶有新聞價值的死亡事件會跨過中國邊境;SARS是香港真正移交的時刻。
當時,海外媒體的消息來源是北京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一個在中國醫療體系邊緣的公民。2003年4月初,他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把SARS在北京的嚴重情況,先傳給國內兩個媒體集團,但未獲回應(《南華早報》,2013年4月13日,頁A6),他只好對外發佈。
儘管事態嚴重,面對這種敏感事件,國內的新聞媒體顯然另有顧慮,美國的《時代》週刊和其他媒體卻報導了蔣彥永的訪問。北京官方罔顧生命,一手遮天的蠻橫舉止,令世界各國政府不滿,輿論譁然。紙終究包不住火,中國政府被迫承認疫情,並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職務。
從2002年底到2003年4月初,在整個SARS疫情於中國流傳過程中,蔣彥永不僅盡到了醫生應有的職責,當北京官方對他的警告和質問視若無睹時,特別是新聞媒體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而噤若寒蟬,他也扮演了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雖然他未必有此念頭。其實,公民記者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還未受到重視。
以存在論和知識論的角度探討,SARS的不幸事件包含概念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以及它們各自所可能帶來對外在環境的理解或誤解,與對應的操作方法。
具體說,由發生到結束,SARS牽涉兩個並行的過程:其一,疾病本身的流傳—它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北京官方的蓄意隱瞞,這是客觀的存在;其二,疾病的新聞報導—它不能獨立於SARS之外,無中生有,既必須有客觀依據,又不免主觀干擾,如個人先入為主的看法,包括政府官員和記者。
這兩個過程的進展時而平行,像鐵路的兩條軌道,時而交叉,如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者是事件或物體與概念的脫鉤,後者則是現實和視覺或想像的接觸,它們所引起的效應,不論是正面或負面,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或解決辦法。
如果SARS是個怪病,它的起因和治療範圍就難以明確界定。因為不確定,它的後果便不易掌握,對北京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也相對提高。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做法就算事出有因,頂多是鴕鳥心態,無助防範疫情的擴大,反而火上加油。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診斷,雖然照樣無法阻止病毒「殺死」病人,或危害人間,一個名詞的準確運用至少縮小了醫治的門徑。所謂對症下藥,症是認知,下藥是操作,或許這是在疾病流傳後期,其他國家較少有人死亡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北京官方的刻意欺瞞不免助長中國、香港和台灣在疫情爆發後許多生命的無謂喪失。名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全在一念之間,禁止某個名詞的討論或流通,如SARS,也就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對應之道。
名詞與行動
當然,名詞或稱呼的存在與否,無損事件或行動的發生。蔣彥永的電子郵件除了透露真相,更傳達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曾經當過醫生,醫學經驗、知識和見解卻不被官方與媒體重視和接受;他不是記者,卻做了類似新聞報導的工作,以消息來源,受到了國外主流媒體的關注。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在中國的國家機器與主流媒體之外,即使是邊緣的個人對社會中心也會產生相當的作用。無論是天災或人禍,SARS是個不幸悲劇,牽扯出事件、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錯綜複雜問題,它們多少都和定義有關。
SARS是天災,還是人禍?它們的分野何在?
事件如何成為新聞?一人哭,或天下哭,何時才算事態嚴重?
媒體是人民的耳目,或是上情下達的工具?人命大,還是國家顏面緊要?
公民社會以個人為主,還是以集體為重?集體是個人的總和?誰來代表?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決條件是界定每個關鍵名詞。定義是抽象的,行動則很具體,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必然關係?如是,抽象的定義怎麼精確轉化成具體的行動?如果不是,相同的行動是否可用不同的名詞來描述?
同樣的道理,在公民記者和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多角關係中,一個基本的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既然是新聞報導,為什平常通用的「記者」一詞不足以表達,還得另創新詞?
記者就是記者,公民記者到底是記者這個概念的擴張或限定?
由知識社會學的視野看,一個概念或術語的出現,與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不會冒然而生。這些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極其錯綜(Mannheim, 1936),其中能動性(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互為促因及後果,對概念的產生與形成,特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字義表面看,公民記者是個很簡單的名詞,它不過是在眾所周知的「記者」稱呼上附加「公民」兩字。也就是說,公民記者有別於一般記者。如果要吹毛求疵,跟白馬非馬的爭論一樣,公民記者與記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相提並論。說白馬非馬,當然是詭辯,經不起仔細推敲。
深一層看,公民記者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包含兩個現代社會的重要觀念:公民與記者。分開來談,公民或記者的定義及其社會效用牽涉廣泛,觸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公民社會的存在、公民的權利及義務、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人民當家做主與知的權利,以及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等。
不論中外,有關公民或記者這兩個概念的討論和爭辯,再加上它們彼此間的互動結果,大多圍繞在這些衍生出來的問題。每一個子題都可以單獨成書,更多的是成千上萬的學術論文或報紙雜誌的文章。
即使書籍浩瀚,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多年,到目前,沒有人可以大言不慚的說,公民或記者的定義早已塵埃落定,它們的效應也一清二楚,毫無疑慮。
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如果不是一知半解,便是視野狹窄,甚至是專斷,容不下其他另類或替代觀點。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北韓和古巴,把新聞媒體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全置於國家領導之下(其實是共產黨的指揮系統),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都有新聞記者的行業,他們的形成卻往往無關公民的社會角色。
就算在民主、自由國家,公民與記者的角色與功能也非一成不變。由於封建與民主的歷史鬥爭、社會變遷、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宰制、新聞與權勢及財團掛鉤、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公民社會的擴張和個人獨立自主意識的抬頭等主要因素,公民與記者的意義和實際操作不斷被反覆檢驗。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因此是流動的,隨時空而異。
公民記者既然是公民與記者兩個概念的合併,以總體永遠大於個別單元的合計看,在抽象角度上,公民記者概念的出現絕非偶然,公民新聞更不是無風起浪,那些以公民記者自居的人也非渾水摸魚或無理取鬧,總有理論與操作的基礎。
以通俗話來說,所謂的公民記者,在一般人眼中,很可能就是冒牌記者或山寨記者,反正不是真的記者。至少這個名詞初聽之下,許多人會產生不少在傳播研究文獻中常探討的疑問:
公民記者是新聞記者,還是社會行動者?亦或兩者兼具?
公民記者到底所為何事?
社會上既然有專業記者,為什還出現公民記者?
誰來決定公民記者的身份?
當一個公民記者是否有些特定的要求或規定?
數據網絡的興起與個人通訊工具的普及,跟公民新聞有什關聯?
專業記者受僱於新聞媒體,公民記者替誰做事?
相對於專業的新聞工作,公民記者應該是業餘了?
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都經過編輯部審核,在事實與評論上,力求客觀和平衡,公民記者由誰把關?
專業記者面對外來壓力時,尤其是來自國家機器與利益團體的威脅利誘,所屬的媒體組織通常可以提供法律辯護和財力支持的機制,公民記者會不會為五斗米折腰?
有關受眾隱私及其他職業道德問題,主流媒體有一套可循的內外專業規範,執行起來大致對記者的舉止有相當約束作用,公民記者向誰負責?
公民新聞對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到底效應如何?
這些問題看似容易,由於牽涉經濟、政治、科技、傳播、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層面,回答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恐怕一時不會有明確的答案,更可能會言人人殊。
一方面,公民記者出現的時間還很短暫,大致是2000年代初期的事,幾乎沒有歷史或成規可言;公民記者的社會角色和傳播效用仍然混沌不清,在新聞報導上的定位與功能,也有待時間的考驗和釐清。
另一方面,公民記者的操作大多圍繞個別突發或危機事件,事過境遷後,很少系統化。任何缺乏持續性的社會操作或組織安排,要形成某種制度,從而挑戰、改變甚至取代現有的制度,不僅會後繼無力,也難以蔚為風潮。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記者是意識的覺醒與某種獨立的宣稱,亦即普通人以公民的姿態在新聞領域取得新定位,而非毫無個人特性的廣大受之一,更不是傳統媒體用以營利的基本單位。如果新聞是社會檔案,公民新聞就不是附件,而是主文,由成千上萬的獨立公民共同主筆。
從新聞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記載中起,記者在社會所扮演與應擔當的角色,就一直是新聞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難題,更何況新興的公民記者。本書不可能,更無意,在這方面強作仲裁。
嚴格說,「公民記者」也許是網絡擴散後的流行概念,公民新聞的操作其實不算新奇,大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建制的主流報導做法,在觀念與實際操作上,打破墨守成規,跟早期的前衛派(avant-garde)作家的風格有點類似。
在1920年代,捷克的共產黨新聞記者Egon Erwin Kisch站在獨特的角度或立場,推出一系列的寫實與社會批判報導文學,以「匆促的記者」(Reporter in a Rush)聞名。後來,這些前衛派的左派報導文學經由電影院在西方流傳,逐漸演變為新聞紀錄片和攝影新聞的濫觴(Hobsbawm, 1994,頁192)。
目前的公民記者自然與共產黨或左派無關,在報導題材上也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的社會動盪大異其趣。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無所不在,至少不是當年的傳播環境可以比擬,全球化也壓縮了時空,打破國界與心理的樊籬。
由於大部分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對現實事件的看法有所差別,縱然具有某種前瞻性的視野,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偏重短暫的效應,而非長期影響,與前衛派「匆促的記者」沒有兩樣。
公民記者並非來去匆匆,以「匆促的記者」稱呼當今的公民記者,不意味對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任何貶義,頂多突顯他們在新聞報導過程中稍縱即逝的作用,以及堅持社會使命的一種「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光從名詞看,他們先是公民,然後是記者(何雪瑩,《明報》,2010年11月7日,頁P3)。
在追求時效、速食文化產物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包括意見的自由市場,「匆促的記者」用來描述目前主流新聞記者的操作行為,也很貼切。為了與網絡媒體競爭,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傳統的媒體已經放棄了嚴謹查證、深入調查的專業化守則,急就章的設法在所謂的「第一時間」內,搶先報導或評論,置真相和真理於不顧。
從傳統新聞到公民新聞,這其間的轉化過程是意識的覺醒,某種心靈特質的呈現。也許,《詩經》「王風」集一首名為「黍離」的詩中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為公民記者的寫照:「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相關課題,不在提出一言九鼎的論斷,而在提供知識的蒙與批判性的見解。透過相關理論架構與比較研究設計,檢視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實際例子,分析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之間的三角關係及互動,並探討公民記者在公民社會中何去何從。
一個公民記者再如何神通廣大,知識和能力總是有限,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論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一旦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投入新聞報導的工作,他們的力量總和無疑將遠大於單獨個人的努力,新聞觸角與涵蓋面也將滲透社會各階層,深化公民社會的基礎。沒有公民的參與,公民社會將難以成形,更遑論操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只是一個小起步,一種概論的嘗試,談不上面面俱到。更多的書仍有待關心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如何在中國、香港和台灣落地生根的人來動筆,在歷史長河逆游。
公民記者,顧名思義,指的是從事新聞報導工作的公民。
這個定義簡潔明瞭,但定義本身不能解釋為什一個名詞(公民記者)與其所指涉的行動(新聞報導)會出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特別是網絡時代。公民記者這個名詞被普遍使用,大約是在2000年代初期。
不論是普通用語或專門術語,一個名詞的產生與使用,往往脫不了特定的時空背景,總有歷史的軌道和複雜的當時社會因素使然。過去的經驗與現在的情境交互牽扯、修訂和塑造,名詞及現實就有理論的原則和操作實證的基礎關係。
舉例說,2003年肆虐香港和其他地方的一個急性流行性傳染病毒,最早爆發在2002年11月16日中國廣東省。由於致命的起因不明,民間認為是種難以解釋的「怪病」,鄉里市井遂流傳毫無科學依據的預防偏方,如以醋熏對抗病毒,以訛傳訛。
既然怪病無以名之,未知的事務便代表某種異象,穿鑿附會之下,人為災難或天譴的流言四起,人心惶惶。中國官方以謠言惑眾,混淆視聽,封鎖了新聞媒體與網路對疫情的報導和討論。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初,有關疫情癥狀的任何名詞因而並未見諸中國的新聞報導,但病毒繼續流竄。
2003年2月21日,病原由一個廣州訪客帶入香港,再傳染到其他地方,尤其是擴散到世界許多華人聚居的城市。在幾個月內,病毒橫掃,受感染的人數激增,重者死亡,輕者住院,弄得危機四伏。
最後,全球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受波及,造成774人死亡,8,096人住院,其中以中國(348人)、香港(299人)、台灣(47人)、加拿大(38人)和新加坡(32人)最為慘重,包括前三地區的17位醫護人員殉職。中國於2003年6月15日遏止病毒的擴散,全世界的最後一個病例(2003年7月13日)則出現在美國(《南華早報》,2013年3月2日,頁A16)。
這期間,世界衛生組織根據病情,於2003年3月15日將最早在廣東被看成是怪病的傳染病正式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任何簡稱的根本作用,不過在方便溝通,避免冗長的文字減低傳播的效率。
SARS的英文縮寫卻讓香港特區政府(SAR)頗為難堪(《南華早報》雜誌,2013年3月31日,頁27),在官方發佈的英文新聞稿中堅持稱為atypical pneumonia, 中文是「非典型性肺炎」或「非典」,音譯為「沙士」。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其實是阿Q罷了,不管如何稱呼,SARS的致命力不會因用字不同而有所差別,就像在國名冠上「人民」兩字的國家,幾乎都不是民主國家。
從官方到民間,由海內到海外,中國掩飾SARS疫情的動機有不同的解釋,例如安定民心、維持社會秩序、地方官僚無能顢頇、醫療預警系統的腐敗、草菅人命、建立政府威信或保護國家形象等,不一而足。美國《時代》雜誌2003年5月5日以「SARS的真相」為題的封面報導,只是其中一個對中國的嚴厲指控。
剛開始時,北京政權信誓旦旦,堅持一切都在衛生機構的控制之下,還多少瞞天過海,讓各國信以為真。最終引起其他國家重視SARS的新聞報導,不是出自中國或香港的媒體,而是美國的《時代》雜誌和其他媒體。
10年後,根據Fionnuala McHugh在《南華早報》(2013年3月31日,頁27)雜誌的報導,SARS似乎是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時,海外媒體所預期報導的故事,它們幾乎指望帶有新聞價值的死亡事件會跨過中國邊境;SARS是香港真正移交的時刻。
當時,海外媒體的消息來源是北京解放軍301醫院的退休醫生蔣彥永,一個在中國醫療體系邊緣的公民。2003年4月初,他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把SARS在北京的嚴重情況,先傳給國內兩個媒體集團,但未獲回應(《南華早報》,2013年4月13日,頁A6),他只好對外發佈。
儘管事態嚴重,面對這種敏感事件,國內的新聞媒體顯然另有顧慮,美國的《時代》週刊和其他媒體卻報導了蔣彥永的訪問。北京官方罔顧生命,一手遮天的蠻橫舉止,令世界各國政府不滿,輿論譁然。紙終究包不住火,中國政府被迫承認疫情,並免去衛生部長張文康的職務。
從2002年底到2003年4月初,在整個SARS疫情於中國流傳過程中,蔣彥永不僅盡到了醫生應有的職責,當北京官方對他的警告和質問視若無睹時,特別是新聞媒體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而噤若寒蟬,他也扮演了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雖然他未必有此念頭。其實,公民記者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還未受到重視。
以存在論和知識論的角度探討,SARS的不幸事件包含概念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以及它們各自所可能帶來對外在環境的理解或誤解,與對應的操作方法。
具體說,由發生到結束,SARS牽涉兩個並行的過程:其一,疾病本身的流傳—它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如北京官方的蓄意隱瞞,這是客觀的存在;其二,疾病的新聞報導—它不能獨立於SARS之外,無中生有,既必須有客觀依據,又不免主觀干擾,如個人先入為主的看法,包括政府官員和記者。
這兩個過程的進展時而平行,像鐵路的兩條軌道,時而交叉,如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者是事件或物體與概念的脫鉤,後者則是現實和視覺或想像的接觸,它們所引起的效應,不論是正面或負面,都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或解決辦法。
如果SARS是個怪病,它的起因和治療範圍就難以明確界定。因為不確定,它的後果便不易掌握,對北京政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可能帶來的威脅也相對提高。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做法就算事出有因,頂多是鴕鳥心態,無助防範疫情的擴大,反而火上加油。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診斷,雖然照樣無法阻止病毒「殺死」病人,或危害人間,一個名詞的準確運用至少縮小了醫治的門徑。所謂對症下藥,症是認知,下藥是操作,或許這是在疾病流傳後期,其他國家較少有人死亡的原因。
在某種程度上說,北京官方的刻意欺瞞不免助長中國、香港和台灣在疫情爆發後許多生命的無謂喪失。名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全在一念之間,禁止某個名詞的討論或流通,如SARS,也就限制了所有可能的對應之道。
名詞與行動
當然,名詞或稱呼的存在與否,無損事件或行動的發生。蔣彥永的電子郵件除了透露真相,更傳達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曾經當過醫生,醫學經驗、知識和見解卻不被官方與媒體重視和接受;他不是記者,卻做了類似新聞報導的工作,以消息來源,受到了國外主流媒體的關注。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在中國的國家機器與主流媒體之外,即使是邊緣的個人對社會中心也會產生相當的作用。無論是天災或人禍,SARS是個不幸悲劇,牽扯出事件、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錯綜複雜問題,它們多少都和定義有關。
SARS是天災,還是人禍?它們的分野何在?
事件如何成為新聞?一人哭,或天下哭,何時才算事態嚴重?
媒體是人民的耳目,或是上情下達的工具?人命大,還是國家顏面緊要?
公民社會以個人為主,還是以集體為重?集體是個人的總和?誰來代表?
要回答這些問題,先決條件是界定每個關鍵名詞。定義是抽象的,行動則很具體,兩者之間是否有一對一的必然關係?如是,抽象的定義怎麼精確轉化成具體的行動?如果不是,相同的行動是否可用不同的名詞來描述?
同樣的道理,在公民記者和新聞、媒體與公民社會的多角關係中,一個基本的問題就值得深入探討:既然是新聞報導,為什平常通用的「記者」一詞不足以表達,還得另創新詞?
記者就是記者,公民記者到底是記者這個概念的擴張或限定?
由知識社會學的視野看,一個概念或術語的出現,與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息息相關,不會冒然而生。這些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極其錯綜(Mannheim, 1936),其中能動性(agency)和結構(structure)的互為促因及後果,對概念的產生與形成,特別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字義表面看,公民記者是個很簡單的名詞,它不過是在眾所周知的「記者」稱呼上附加「公民」兩字。也就是說,公民記者有別於一般記者。如果要吹毛求疵,跟白馬非馬的爭論一樣,公民記者與記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相提並論。說白馬非馬,當然是詭辯,經不起仔細推敲。
深一層看,公民記者這個概念相當複雜,包含兩個現代社會的重要觀念:公民與記者。分開來談,公民或記者的定義及其社會效用牽涉廣泛,觸及民族/國家的興起、公民社會的存在、公民的權利及義務、民主機制和言論自由的保障、人民當家做主與知的權利,以及媒體獨立和新聞自由等。
不論中外,有關公民或記者這兩個概念的討論和爭辯,再加上它們彼此間的互動結果,大多圍繞在這些衍生出來的問題。每一個子題都可以單獨成書,更多的是成千上萬的學術論文或報紙雜誌的文章。
即使書籍浩瀚,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多年,到目前,沒有人可以大言不慚的說,公民或記者的定義早已塵埃落定,它們的效應也一清二楚,毫無疑慮。
採取這種立場的人,如果不是一知半解,便是視野狹窄,甚至是專斷,容不下其他另類或替代觀點。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北韓和古巴,把新聞媒體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全置於國家領導之下(其實是共產黨的指揮系統),便是很好的例子。這些國家都有新聞記者的行業,他們的形成卻往往無關公民的社會角色。
就算在民主、自由國家,公民與記者的角色與功能也非一成不變。由於封建與民主的歷史鬥爭、社會變遷、資本主義商業化的宰制、新聞與權勢及財團掛鉤、資訊與傳播科技的突飛猛進、公民社會的擴張和個人獨立自主意識的抬頭等主要因素,公民與記者的意義和實際操作不斷被反覆檢驗。這兩個概念的內涵因此是流動的,隨時空而異。
公民記者既然是公民與記者兩個概念的合併,以總體永遠大於個別單元的合計看,在抽象角度上,公民記者概念的出現絕非偶然,公民新聞更不是無風起浪,那些以公民記者自居的人也非渾水摸魚或無理取鬧,總有理論與操作的基礎。
以通俗話來說,所謂的公民記者,在一般人眼中,很可能就是冒牌記者或山寨記者,反正不是真的記者。至少這個名詞初聽之下,許多人會產生不少在傳播研究文獻中常探討的疑問:
公民記者是新聞記者,還是社會行動者?亦或兩者兼具?
公民記者到底所為何事?
社會上既然有專業記者,為什還出現公民記者?
誰來決定公民記者的身份?
當一個公民記者是否有些特定的要求或規定?
數據網絡的興起與個人通訊工具的普及,跟公民新聞有什關聯?
專業記者受僱於新聞媒體,公民記者替誰做事?
相對於專業的新聞工作,公民記者應該是業餘了?
傳統媒體的新聞報導都經過編輯部審核,在事實與評論上,力求客觀和平衡,公民記者由誰把關?
專業記者面對外來壓力時,尤其是來自國家機器與利益團體的威脅利誘,所屬的媒體組織通常可以提供法律辯護和財力支持的機制,公民記者會不會為五斗米折腰?
有關受眾隱私及其他職業道德問題,主流媒體有一套可循的內外專業規範,執行起來大致對記者的舉止有相當約束作用,公民記者向誰負責?
公民新聞對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到底效應如何?
這些問題看似容易,由於牽涉經濟、政治、科技、傳播、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層面,回答起來,卻是千頭萬緒,恐怕一時不會有明確的答案,更可能會言人人殊。
一方面,公民記者出現的時間還很短暫,大致是2000年代初期的事,幾乎沒有歷史或成規可言;公民記者的社會角色和傳播效用仍然混沌不清,在新聞報導上的定位與功能,也有待時間的考驗和釐清。
另一方面,公民記者的操作大多圍繞個別突發或危機事件,事過境遷後,很少系統化。任何缺乏持續性的社會操作或組織安排,要形成某種制度,從而挑戰、改變甚至取代現有的制度,不僅會後繼無力,也難以蔚為風潮。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公民記者是意識的覺醒與某種獨立的宣稱,亦即普通人以公民的姿態在新聞領域取得新定位,而非毫無個人特性的廣大受之一,更不是傳統媒體用以營利的基本單位。如果新聞是社會檔案,公民新聞就不是附件,而是主文,由成千上萬的獨立公民共同主筆。
從新聞這個概念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記載中起,記者在社會所扮演與應擔當的角色,就一直是新聞界和學術界爭論不休的難題,更何況新興的公民記者。本書不可能,更無意,在這方面強作仲裁。
嚴格說,「公民記者」也許是網絡擴散後的流行概念,公民新聞的操作其實不算新奇,大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建制的主流報導做法,在觀念與實際操作上,打破墨守成規,跟早期的前衛派(avant-garde)作家的風格有點類似。
在1920年代,捷克的共產黨新聞記者Egon Erwin Kisch站在獨特的角度或立場,推出一系列的寫實與社會批判報導文學,以「匆促的記者」(Reporter in a Rush)聞名。後來,這些前衛派的左派報導文學經由電影院在西方流傳,逐漸演變為新聞紀錄片和攝影新聞的濫觴(Hobsbawm, 1994,頁192)。
目前的公民記者自然與共產黨或左派無關,在報導題材上也與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間的社會動盪大異其趣。網絡與社交媒體的無所不在,至少不是當年的傳播環境可以比擬,全球化也壓縮了時空,打破國界與心理的樊籬。
由於大部分公民記者與傳統記者對現實事件的看法有所差別,縱然具有某種前瞻性的視野,除了少數例外,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偏重短暫的效應,而非長期影響,與前衛派「匆促的記者」沒有兩樣。
公民記者並非來去匆匆,以「匆促的記者」稱呼當今的公民記者,不意味對他們的工作能力有任何貶義,頂多突顯他們在新聞報導過程中稍縱即逝的作用,以及堅持社會使命的一種「捨我其誰」的急迫感。光從名詞看,他們先是公民,然後是記者(何雪瑩,《明報》,2010年11月7日,頁P3)。
在追求時效、速食文化產物充斥市場的情況下,包括意見的自由市場,「匆促的記者」用來描述目前主流新聞記者的操作行為,也很貼切。為了與網絡媒體競爭,獲取更大的經濟效益,傳統的媒體已經放棄了嚴謹查證、深入調查的專業化守則,急就章的設法在所謂的「第一時間」內,搶先報導或評論,置真相和真理於不顧。
從傳統新聞到公民新聞,這其間的轉化過程是意識的覺醒,某種心靈特質的呈現。也許,《詩經》「王風」集一首名為「黍離」的詩中一句話,可以用來作為公民記者的寫照:「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本書的主要目的,就相關課題,不在提出一言九鼎的論斷,而在提供知識的蒙與批判性的見解。透過相關理論架構與比較研究設計,檢視中國、香港與台灣的實際例子,分析公民新聞、媒體和社會之間的三角關係及互動,並探討公民記者在公民社會中何去何從。
一個公民記者再如何神通廣大,知識和能力總是有限,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論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一旦成千上萬的普通人投入新聞報導的工作,他們的力量總和無疑將遠大於單獨個人的努力,新聞觸角與涵蓋面也將滲透社會各階層,深化公民社會的基礎。沒有公民的參與,公民社會將難以成形,更遑論操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書只是一個小起步,一種概論的嘗試,談不上面面俱到。更多的書仍有待關心公民社會與民主體制如何在中國、香港和台灣落地生根的人來動筆,在歷史長河逆游。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