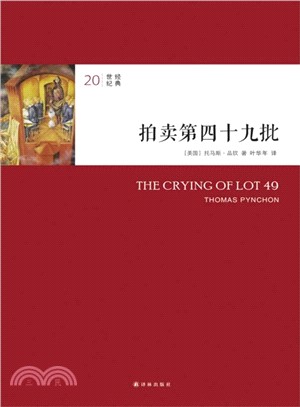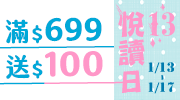人民幣定價:20 元
定價
:NT$ 120 元優惠價
:87 折 104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在品欽已有的長篇小說中,《拍賣第四十九批》是最易讀,又能全面反映其獨特創作風格的一部。
主人公奧迪帕發現前男友的遺產中有大量郵票,這郵票似乎暗示了某種秘密。為此她四處尋訪調查,慢慢地她不知自己是真的有所發現,還是陷入了幻覺之中。莫非一切不過是死者為她設下的一個龐大的惡作劇?所有可能的知情者都在她接近時離奇消失。郵票最終進行拍賣,據說會有一個從未露面的人前來競拍。她坐在拍賣廳裡,等待那個神秘人物的到來……
主人公奧迪帕發現前男友的遺產中有大量郵票,這郵票似乎暗示了某種秘密。為此她四處尋訪調查,慢慢地她不知自己是真的有所發現,還是陷入了幻覺之中。莫非一切不過是死者為她設下的一個龐大的惡作劇?所有可能的知情者都在她接近時離奇消失。郵票最終進行拍賣,據說會有一個從未露面的人前來競拍。她坐在拍賣廳裡,等待那個神秘人物的到來……
作者簡介
湯瑪斯•品欽(1937— )
美國當代傳奇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以神秘的荒誕文學與當代科學的交叉結合為特色,包含豐富的意旨、風格和主題,涉及歷史、自然科學和數學等不同領域。他曾獲美國全國圖書獎,但拒絕領獎。
他對自己的個人生活諱莫如深,成名後深居簡出,早年的照片和檔案也離奇消失,使外界對他的私生活同對他的作品一樣充滿好奇與無奈。
美國當代傳奇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以神秘的荒誕文學與當代科學的交叉結合為特色,包含豐富的意旨、風格和主題,涉及歷史、自然科學和數學等不同領域。他曾獲美國全國圖書獎,但拒絕領獎。
他對自己的個人生活諱莫如深,成名後深居簡出,早年的照片和檔案也離奇消失,使外界對他的私生活同對他的作品一樣充滿好奇與無奈。
名人/編輯推薦
編輯推薦
湯瑪斯•品欽是當代美國文學怪傑,身世隱秘,行文譎詭。《拍賣第四十九批》是品欽諸多小說中最有故事性、最易讀的一部,被品欽愛好者們稱為“最佳的認識品欽的書”。
媒體評論
本書獲美國藝術文學院羅森塔爾基金獎,入選美國《時代》週刊百部英語小說佳作。
《拍賣第四十九批》發生在這個亦悲亦喜的宇宙中,伴著偏執狂的鬧劇和令人心碎的形而上的獨白,讓人一眼認出這就是品欽的王國。它也是一部偵探小說嗎?沒錯,只要你別忘記它所偵探的是藏于一切萬有之中的那個秘密。——《時代》週刊
荒誕、雙關和諷刺的噴發。——《紐約時報》
散文大師的手筆……品欽錯綜複雜的符號體系一如喬伊絲的《尤利西斯》。——《芝加哥論壇報》
書摘/試閱
一個夏日的下午,奧迪帕?馬斯太太參加了一個特百惠家用塑膠製品推銷聚會後回到家。該聚會的女主人也許在熱融乾酪中放入了太多的櫻桃白蘭地,使她竟沒發現她,奧迪帕,已被指定為一個名叫皮爾斯?英弗拉裡蒂的加利福尼亞州房地產巨頭的遺囑執行人,或如她所認為的是遺囑女執行人,而那巨頭在他業餘消遣中曾虧損了二百萬美元,但依舊擁有數量眾多的纏結不清的資產,足以使它的全部清理工作不只是一件名譽性的事情。奧迪帕站在起居室裡,在電視機顯像管綠瑩瑩、冷冰冰的眼睛的盯視下,口中念叨著上帝,試圖感覺到自己已醉得無法可醉。然而這不管用。她想起了在馬薩特蘭的一個旅館的房間,砰的一聲,門似乎被永久性地關上,驚醒了大廳下麵的兩百隻鳥;想起太陽在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所在的斜坡後升起,但在斜坡上的人卻無一看見,因為那斜坡朝向西方;想起巴托克樂隊協奏曲第四樂章裡的一段冷冰冰的、憂鬱的曲調;想起皮爾斯放在床頭上方架子上的一尊塗白的傑伊?古爾德胸像,那架子非常狹窄,以至她總是惴惴不安,唯恐那胸像有朝一日會倒下來掉在他們身上。在夢境中她曾想弄明白,他是否就是那樣被家中唯一的那尊雕像砸死的?然而那卻只使她笑了起來,大聲地無助地笑:你病重了,奧迪帕,她對自己說,或者是對房間說,它能聽懂。
那封信來自洛杉磯的瓦珀、威斯特富爾、庫比契克和麥克明格斯律師事務所,由一個名叫梅茨格的人簽署。信中說,皮爾斯在春天死去了,而他們現在才發現那份遺囑。梅茨格將是遺囑的共同執行人,並在任何可能相關的訴訟中擔任特別法律顧問。奧迪帕也在一份一年前的遺囑附錄中被指定為遺囑執行人。她努力回想那段時間是否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在下午餘下的時間中,在她去“松林中的基尼烈”商業區的那家市場購買義大利乳清乾酪和聆聽米尤紮克音樂(今天她穿過掛著珠簾的入口處時正聽到韋恩堡18世紀樂團由博伊德?比弗擔任獨奏的維瓦爾第卡祖笛協奏曲的集注版錄音的第四小節)的路上,然後在她在陽光下採集芳草園裡的墨角蘭與羅勒草,閱讀最新一期的《科學美國》中的書評,在義大利式鹵汁麵條上添加層層調料,給麵包抹上蒜泥,撕碎生菜葉,最後開啟烘箱,同時趕在她丈夫溫德爾(“馬喬”)?馬斯下班回來前調製好黃昏時飲用的檸檬威士卡雞尾酒的過程中,她驚訝著,納悶著,磨磨蹭蹭地往回穿過厚厚一副紙牌那麼多的日子,那些日子似乎(她難道不是率先承認這一點?)或多或少是雷同的,或者似乎像魔術師的一副紙牌,所有的紙牌都微妙地指向同一方向,任何特出的紙牌都逃不過訓練有素的眼睛。她一直回憶到亨特利和布林克利的事的一半時才想起去年有一天淩晨三點左右有過這個長途電話,她將永遠無法得知它來自何處(除非現在他留下了日記),說話者先以濃重的斯拉夫腔調開始,說他是特蘭西瓦尼亞領館的二秘,在尋找一隻逃亡的蝙蝠;接著調節為滑稽的黑人腔;隨後是懷有敵意的墨西哥裔花衣少年流氓腔的方言,滿口“他媽的”和“雞奸”的詞語;然後是一個蓋世太保軍官的尖叫聲問她在德國有無親戚;最後是他的拉蒙特?克蘭斯頓藍調樂團的腔調,他用這腔調一路講到馬薩特蘭。“皮爾斯,行啦,”她終於插上了嘴,“我想我們有——”
“但是,馬戈,”他認真地說,“我剛從韋斯頓長官那兒回來,在遊樂宮裡的那個老頭被殺害奎肯布希教授的同一把獵槍殺死了。”或類似的話。
“天哪。”她說。馬喬已翻過身來看著她。
“你何不把他的電話掛了。”馬喬明智地建議道。
“我聽到了。”皮爾斯說。“我想現在該是溫德爾?馬斯接受來自影子密探的小小拜訪的時候了。”接著是寂靜,完全的徹底的寂靜。所以這就是她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拉蒙特?克蘭斯頓。那根電話線可以指向任何方向,有任何長度。在那次通話之後的幾個月裡,電話線意義不明的寧靜變換成被復活的回憶:對他的臉、身體、他給予她的東西、她偶爾裝作沒聽見他說的事情的回憶。這回憶取代了他,把他置於被遺忘的邊緣。那幽靈一年後才來拜訪。但現在有了梅茨格的信。那麼去年皮爾斯打電話給她是不是要告訴她關於這份遺囑附錄的事?或者他是後來才作出那決定,多少是因為她的惱火和馬喬的冷淡?她感到被暴露,被愚弄,被羞辱。她在一生中從未執行過遺囑,不知道從何入手,不知道該如何告知在洛杉磯的律師事務所她不知從何入手。
“馬喬,寶貝。”她哭泣道,幾乎是束手無策。
馬喬?馬斯回到家,急衝衝地穿過紗門。“今天又是一個失敗。”他開始說。
“讓我告訴你。”她也開口說了。但是先讓馬喬說吧。
他是廣播電臺的流行音樂欄目主持人,在沿半島更遠些的地方工作。他時時感到職業上的良心危機。“伊迪,我對它們一點也不相信。”他通常都能擺脫出來的。“我在努力,但我確實做不到。”他情緒低落,也許遠低於她的影響所能到達的地步,於是那些時刻常常使她近乎驚恐。然而也許是看到她將要情緒失控才使他的情緒又恢復如常的。
“你太敏感了。”是的,還有那麼多別的話她也該說,然而出口的卻是這一句。但不管怎樣,這句話並沒錯。有幾年時間他是一個舊汽車推銷員,所以他對現在那份職業的意義有高度的認識,以至他的工作時間對於他是一種強烈的折磨。每天早晨馬喬三次順著鬚根,三次逆著鬚根刮他的上唇,以除去胡髭留下的任何微乎其微的痕跡,哪怕新刀片總是讓他出血,他依舊堅持不懈;他購買全天然肩的套服,然後去找裁縫把翻領改得異乎尋常的狹窄;他在頭髮上只用清水,像傑克?萊蒙那樣梳頭,把頭髮甩得更開。看見木屑,甚至削鉛筆的刨花,他都會畏縮,他們這些人用它來為壞掉的變速器靜音,這是眾所周知的。而且雖然他節食,他仍然做不到像奧迪帕那樣用蜂蜜給自己的咖啡添加甜味,因為它如同所有其他黏乎乎的東西一樣令他悲傷,使他過於辛酸地回想起常常與馬達潤滑油相混合以欺騙性地滲入活塞與汽缸之間的空隙的那種東西。有一天晚上他退出了一個聚會,因為有人似乎惡毒地在他能聽見的地方用了“奶油泡芙”這個詞。那個男人是個匈牙利難民,糕點師,多嘴多舌者,但這就是你的馬喬:臉皮很薄。
然而至少他曾相信過汽車。也許過分相信了:他怎麼能不信呢,見到比他貧窮的人,黑人,墨西哥人,趕馬車的人,每週七天天天有一隊人帶來看那最令人憎惡的折價舊汽車:他們自己、他們家庭和他們整個像模像樣的生活必備的帶有發動機的金屬延伸物,它們赤裸裸地擺在那兒,讓任何人,讓像他自己那樣的陌生人看,車身歪斜,底盤生銹,擋泥板重新油漆後顏色深淺差那麼一點就足以讓車子——如果不是馬喬本人——掉價,車內令人絕望地散發著孩子的、超市中烈酒的、兩代或三代吸煙者的或只是灰塵的氣味——而在這些汽車被徹底清理後,你還不得不查看這些人生活的實際殘剩物,而沒有辦法說清什麼東西被真正拒絕了(當他認為能獲得的東西是那麼少時,人們出於恐懼對大部分能得到的都只得接受並保存),什麼東西是純粹(也許是悲慘地)丟失了:剪下的五或十美分的購物優惠券,商家贈券,宣傳市場特價品的粉紅色傳單,香煙,軟齒塑膠梳,招聘廣告,從電話簿裡撕下的黃頁,舊內衣或已過時的早期服裝的,用來擦去你自己呼在擋風玻璃內壁上的水汽以讓你能看見如電影、女人或你垂涎的車和可能只是為了訓練的需要而讓你把車駛向路邊的員警的碎布片,像一盆“絕望”沙拉一樣,覆蓋著灰燼、濃縮的廢液、塵埃、身體的排泄物——看到這一切他就會噁心,但他不得不看。假若這裡很乾脆是個廢舊車堆積場,很可能他能挺過去,把它當成一份職業:可是導致汽車毀壞的暴力不常見,對他來說遠遠不足以造成奇跡,因為直至我們自己的最後時刻來臨,每一個死亡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周複一周無休無止的舊汽車銷售儀式從來沒有達到過暴力或流血的程度,因而它太不切實可信,不能使易受影響的馬喬長期接受它。即使與那永無變化的灰色疾病的充分接觸以某種方式使他有了些免疫力,他仍然無法接受每一個車主每一個幽靈魚貫而入,只是為了把一個有凹痕的、功能障礙的他自己的車型換成另一個同樣沒有前途的、他人生活的汽車投影。仿佛這樣做是最自然不過的。對於馬喬來說這是可怖的事。無休無止的、錯綜複雜的亂倫。
奧迪帕無法理解他怎麼現在仍能變得那麼苦惱沮喪。在他與她結婚時,他已經在KCUF電臺工作了兩年,在蒼白的、喧鬧的幹道上的那個命運已遠遠丟在他身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朝鮮戰爭被老一代的丈夫們遠遠地丟在腦後一樣。也許,願上帝可憐她,他應該參加過戰爭,這樣他可能會先要遺忘樹林中的日本佬,虎牌坦克中的德國佬,在黑夜中拿著號角的外國佬,而不是任何與令他驚恐的長達五年的命運有關的事。五年。當他們大汗淋漓地或哭叫著噩夢的話語醒過來時,你安慰他們,抱住他們,他們安靜下來了,有一天他們忘了它:她知道那種情況。然而馬喬何時會忘記?她猜想流行音樂欄目主持人這個職位(他是通過他的密友,KCUF廣播電臺廣告部經理得到這份工作的,那經理每星期拜訪一次“命運”,而那“命運”是個贊助人)是一種途徑,它讓排行榜上的前兩百名,甚至從機器裡嘰嘰喳喳出來的新聞拷貝——所有有關少年欲望的欺騙性的夢——成為他與那種命運之間的緩衝器。
他太相信命運了,他根本不相信電臺。然而看到他此時在暮光中的起居室裡,像一隻在上升氣流裡的大鳥朝表面有水珠凝結的調酒壺裡的酒滑翔而去,從他巨大的渦環中心向外微笑時,你會以為一切都是完全平靜的,金燦燦的,晴朗的。
直到他開口說話。“今天芬奇叫我進去,”他對她傾訴起來,“想談談我的形象問題,他不喜歡我的形象。”芬奇是節目部主任,馬喬的死對頭。“他說我現在太不正經了。我應該是一個年輕的父親,一個大哥哥。這些少女打電話來提出請求,在芬奇聽來,我說的每一個詞裡都顫動著不加掩飾的淫欲。所以現在我得把所有的電話交談錄下來,芬奇將親自刪去他認為是冒犯性的話語,這意味著我的一切交談對話都將終止。這是審查制度,我告訴他,‘密探’,我咕噥一聲,然後我逃離了。”他和芬奇可能每星期都要來一次這樣的例行公事。
她讓他看梅茨格的來信。馬喬對她與皮爾斯的事全都知道:他們在馬喬與她結婚前一年結束了關係。他讀了那封信,眨了一陣眼睛後靦腆地縮回去了。
“我該怎麼辦?”她說。
那封信來自洛杉磯的瓦珀、威斯特富爾、庫比契克和麥克明格斯律師事務所,由一個名叫梅茨格的人簽署。信中說,皮爾斯在春天死去了,而他們現在才發現那份遺囑。梅茨格將是遺囑的共同執行人,並在任何可能相關的訴訟中擔任特別法律顧問。奧迪帕也在一份一年前的遺囑附錄中被指定為遺囑執行人。她努力回想那段時間是否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在下午餘下的時間中,在她去“松林中的基尼烈”商業區的那家市場購買義大利乳清乾酪和聆聽米尤紮克音樂(今天她穿過掛著珠簾的入口處時正聽到韋恩堡18世紀樂團由博伊德?比弗擔任獨奏的維瓦爾第卡祖笛協奏曲的集注版錄音的第四小節)的路上,然後在她在陽光下採集芳草園裡的墨角蘭與羅勒草,閱讀最新一期的《科學美國》中的書評,在義大利式鹵汁麵條上添加層層調料,給麵包抹上蒜泥,撕碎生菜葉,最後開啟烘箱,同時趕在她丈夫溫德爾(“馬喬”)?馬斯下班回來前調製好黃昏時飲用的檸檬威士卡雞尾酒的過程中,她驚訝著,納悶著,磨磨蹭蹭地往回穿過厚厚一副紙牌那麼多的日子,那些日子似乎(她難道不是率先承認這一點?)或多或少是雷同的,或者似乎像魔術師的一副紙牌,所有的紙牌都微妙地指向同一方向,任何特出的紙牌都逃不過訓練有素的眼睛。她一直回憶到亨特利和布林克利的事的一半時才想起去年有一天淩晨三點左右有過這個長途電話,她將永遠無法得知它來自何處(除非現在他留下了日記),說話者先以濃重的斯拉夫腔調開始,說他是特蘭西瓦尼亞領館的二秘,在尋找一隻逃亡的蝙蝠;接著調節為滑稽的黑人腔;隨後是懷有敵意的墨西哥裔花衣少年流氓腔的方言,滿口“他媽的”和“雞奸”的詞語;然後是一個蓋世太保軍官的尖叫聲問她在德國有無親戚;最後是他的拉蒙特?克蘭斯頓藍調樂團的腔調,他用這腔調一路講到馬薩特蘭。“皮爾斯,行啦,”她終於插上了嘴,“我想我們有——”
“但是,馬戈,”他認真地說,“我剛從韋斯頓長官那兒回來,在遊樂宮裡的那個老頭被殺害奎肯布希教授的同一把獵槍殺死了。”或類似的話。
“天哪。”她說。馬喬已翻過身來看著她。
“你何不把他的電話掛了。”馬喬明智地建議道。
“我聽到了。”皮爾斯說。“我想現在該是溫德爾?馬斯接受來自影子密探的小小拜訪的時候了。”接著是寂靜,完全的徹底的寂靜。所以這就是她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拉蒙特?克蘭斯頓。那根電話線可以指向任何方向,有任何長度。在那次通話之後的幾個月裡,電話線意義不明的寧靜變換成被復活的回憶:對他的臉、身體、他給予她的東西、她偶爾裝作沒聽見他說的事情的回憶。這回憶取代了他,把他置於被遺忘的邊緣。那幽靈一年後才來拜訪。但現在有了梅茨格的信。那麼去年皮爾斯打電話給她是不是要告訴她關於這份遺囑附錄的事?或者他是後來才作出那決定,多少是因為她的惱火和馬喬的冷淡?她感到被暴露,被愚弄,被羞辱。她在一生中從未執行過遺囑,不知道從何入手,不知道該如何告知在洛杉磯的律師事務所她不知從何入手。
“馬喬,寶貝。”她哭泣道,幾乎是束手無策。
馬喬?馬斯回到家,急衝衝地穿過紗門。“今天又是一個失敗。”他開始說。
“讓我告訴你。”她也開口說了。但是先讓馬喬說吧。
他是廣播電臺的流行音樂欄目主持人,在沿半島更遠些的地方工作。他時時感到職業上的良心危機。“伊迪,我對它們一點也不相信。”他通常都能擺脫出來的。“我在努力,但我確實做不到。”他情緒低落,也許遠低於她的影響所能到達的地步,於是那些時刻常常使她近乎驚恐。然而也許是看到她將要情緒失控才使他的情緒又恢復如常的。
“你太敏感了。”是的,還有那麼多別的話她也該說,然而出口的卻是這一句。但不管怎樣,這句話並沒錯。有幾年時間他是一個舊汽車推銷員,所以他對現在那份職業的意義有高度的認識,以至他的工作時間對於他是一種強烈的折磨。每天早晨馬喬三次順著鬚根,三次逆著鬚根刮他的上唇,以除去胡髭留下的任何微乎其微的痕跡,哪怕新刀片總是讓他出血,他依舊堅持不懈;他購買全天然肩的套服,然後去找裁縫把翻領改得異乎尋常的狹窄;他在頭髮上只用清水,像傑克?萊蒙那樣梳頭,把頭髮甩得更開。看見木屑,甚至削鉛筆的刨花,他都會畏縮,他們這些人用它來為壞掉的變速器靜音,這是眾所周知的。而且雖然他節食,他仍然做不到像奧迪帕那樣用蜂蜜給自己的咖啡添加甜味,因為它如同所有其他黏乎乎的東西一樣令他悲傷,使他過於辛酸地回想起常常與馬達潤滑油相混合以欺騙性地滲入活塞與汽缸之間的空隙的那種東西。有一天晚上他退出了一個聚會,因為有人似乎惡毒地在他能聽見的地方用了“奶油泡芙”這個詞。那個男人是個匈牙利難民,糕點師,多嘴多舌者,但這就是你的馬喬:臉皮很薄。
然而至少他曾相信過汽車。也許過分相信了:他怎麼能不信呢,見到比他貧窮的人,黑人,墨西哥人,趕馬車的人,每週七天天天有一隊人帶來看那最令人憎惡的折價舊汽車:他們自己、他們家庭和他們整個像模像樣的生活必備的帶有發動機的金屬延伸物,它們赤裸裸地擺在那兒,讓任何人,讓像他自己那樣的陌生人看,車身歪斜,底盤生銹,擋泥板重新油漆後顏色深淺差那麼一點就足以讓車子——如果不是馬喬本人——掉價,車內令人絕望地散發著孩子的、超市中烈酒的、兩代或三代吸煙者的或只是灰塵的氣味——而在這些汽車被徹底清理後,你還不得不查看這些人生活的實際殘剩物,而沒有辦法說清什麼東西被真正拒絕了(當他認為能獲得的東西是那麼少時,人們出於恐懼對大部分能得到的都只得接受並保存),什麼東西是純粹(也許是悲慘地)丟失了:剪下的五或十美分的購物優惠券,商家贈券,宣傳市場特價品的粉紅色傳單,香煙,軟齒塑膠梳,招聘廣告,從電話簿裡撕下的黃頁,舊內衣或已過時的早期服裝的,用來擦去你自己呼在擋風玻璃內壁上的水汽以讓你能看見如電影、女人或你垂涎的車和可能只是為了訓練的需要而讓你把車駛向路邊的員警的碎布片,像一盆“絕望”沙拉一樣,覆蓋著灰燼、濃縮的廢液、塵埃、身體的排泄物——看到這一切他就會噁心,但他不得不看。假若這裡很乾脆是個廢舊車堆積場,很可能他能挺過去,把它當成一份職業:可是導致汽車毀壞的暴力不常見,對他來說遠遠不足以造成奇跡,因為直至我們自己的最後時刻來臨,每一個死亡都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周複一周無休無止的舊汽車銷售儀式從來沒有達到過暴力或流血的程度,因而它太不切實可信,不能使易受影響的馬喬長期接受它。即使與那永無變化的灰色疾病的充分接觸以某種方式使他有了些免疫力,他仍然無法接受每一個車主每一個幽靈魚貫而入,只是為了把一個有凹痕的、功能障礙的他自己的車型換成另一個同樣沒有前途的、他人生活的汽車投影。仿佛這樣做是最自然不過的。對於馬喬來說這是可怖的事。無休無止的、錯綜複雜的亂倫。
奧迪帕無法理解他怎麼現在仍能變得那麼苦惱沮喪。在他與她結婚時,他已經在KCUF電臺工作了兩年,在蒼白的、喧鬧的幹道上的那個命運已遠遠丟在他身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朝鮮戰爭被老一代的丈夫們遠遠地丟在腦後一樣。也許,願上帝可憐她,他應該參加過戰爭,這樣他可能會先要遺忘樹林中的日本佬,虎牌坦克中的德國佬,在黑夜中拿著號角的外國佬,而不是任何與令他驚恐的長達五年的命運有關的事。五年。當他們大汗淋漓地或哭叫著噩夢的話語醒過來時,你安慰他們,抱住他們,他們安靜下來了,有一天他們忘了它:她知道那種情況。然而馬喬何時會忘記?她猜想流行音樂欄目主持人這個職位(他是通過他的密友,KCUF廣播電臺廣告部經理得到這份工作的,那經理每星期拜訪一次“命運”,而那“命運”是個贊助人)是一種途徑,它讓排行榜上的前兩百名,甚至從機器裡嘰嘰喳喳出來的新聞拷貝——所有有關少年欲望的欺騙性的夢——成為他與那種命運之間的緩衝器。
他太相信命運了,他根本不相信電臺。然而看到他此時在暮光中的起居室裡,像一隻在上升氣流裡的大鳥朝表面有水珠凝結的調酒壺裡的酒滑翔而去,從他巨大的渦環中心向外微笑時,你會以為一切都是完全平靜的,金燦燦的,晴朗的。
直到他開口說話。“今天芬奇叫我進去,”他對她傾訴起來,“想談談我的形象問題,他不喜歡我的形象。”芬奇是節目部主任,馬喬的死對頭。“他說我現在太不正經了。我應該是一個年輕的父親,一個大哥哥。這些少女打電話來提出請求,在芬奇聽來,我說的每一個詞裡都顫動著不加掩飾的淫欲。所以現在我得把所有的電話交談錄下來,芬奇將親自刪去他認為是冒犯性的話語,這意味著我的一切交談對話都將終止。這是審查制度,我告訴他,‘密探’,我咕噥一聲,然後我逃離了。”他和芬奇可能每星期都要來一次這樣的例行公事。
她讓他看梅茨格的來信。馬喬對她與皮爾斯的事全都知道:他們在馬喬與她結婚前一年結束了關係。他讀了那封信,眨了一陣眼睛後靦腆地縮回去了。
“我該怎麼辦?”她說。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