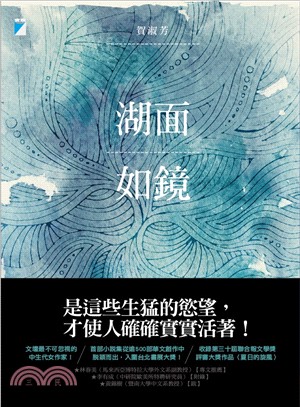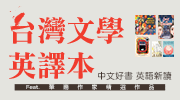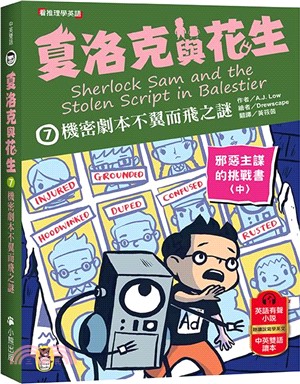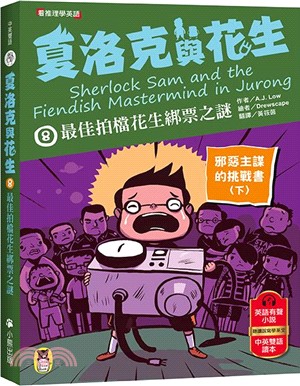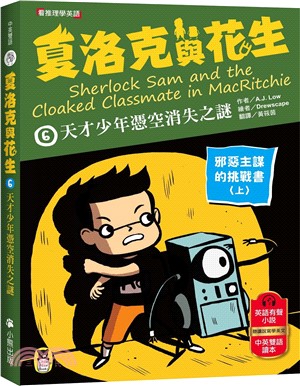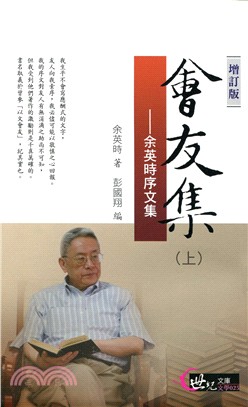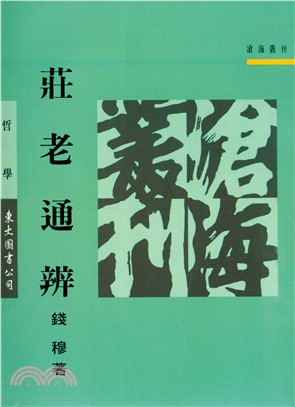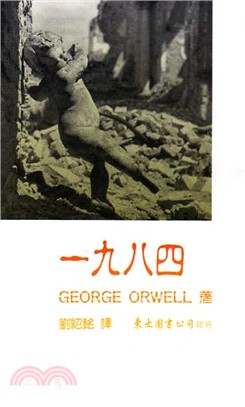湖面如鏡
商品資訊
定價
:NT$ 290 元優惠價
:90 折 261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我要在一個遠遠的地方像孩子那樣重新出世。
自己生下我自己。
是這些生猛的慾望,才使人確確實實活著!
文壇最不可忽視的中生代女作家!
首部小說集從逾500部華文創作中脫穎而出,入圍台北書展大獎!
收錄第三十屆聯合報文學獎評審大獎作品〈夏日的旋風〉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專文推薦】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附錄】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跋】
她的文字濃烈深沉,每篇都是殘暴的詩;
而她筆下,命運是巨大的羅網,人們前仆後繼。
這裡有最強悍柔軟的女性,幽微難辨的慾望,有扭曲失速的吶喊,亦有苦吟。
是遠嫁台灣的外籍新娘,孤注一擲地緊擁住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也是驟失愛貓的妻,漸日形銷骨立,穿過牆與牆的縫隙而去;是被校方打壓言論自由的大學女講師;是為了心愛的牧師,募款建造教堂的妓女;也是被迫信教,精神崩潰之後,終日裸著身子夢遊的女精神病患。女人,女人,在小說裡,她們喧囂也沉默,互相指認出自己的身世。
九篇短篇,深深淺淺地疊出當代女人的身影。女人總在出走,又禁不住回眸,在凝視與凝視間轉換形貌,在索求中,嘗到活著的愛與苦。賀淑芳鍛造文字一如煉金,看似句點,卻隱藏著叩問,總在世俗的庸常中,一遍又一遍逼視出個人存在的困境,而她對社會議題的犀利思考與高度的自我指涉,也讓《湖面如鏡》除了文學與美學上的獨特韻味之外,還具備了批判性,是近年來獨樹一格的女作家代表人物。
自己生下我自己。
是這些生猛的慾望,才使人確確實實活著!
文壇最不可忽視的中生代女作家!
首部小說集從逾500部華文創作中脫穎而出,入圍台北書展大獎!
收錄第三十屆聯合報文學獎評審大獎作品〈夏日的旋風〉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專文推薦】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附錄】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跋】
她的文字濃烈深沉,每篇都是殘暴的詩;
而她筆下,命運是巨大的羅網,人們前仆後繼。
這裡有最強悍柔軟的女性,幽微難辨的慾望,有扭曲失速的吶喊,亦有苦吟。
是遠嫁台灣的外籍新娘,孤注一擲地緊擁住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孩子;也是驟失愛貓的妻,漸日形銷骨立,穿過牆與牆的縫隙而去;是被校方打壓言論自由的大學女講師;是為了心愛的牧師,募款建造教堂的妓女;也是被迫信教,精神崩潰之後,終日裸著身子夢遊的女精神病患。女人,女人,在小說裡,她們喧囂也沉默,互相指認出自己的身世。
九篇短篇,深深淺淺地疊出當代女人的身影。女人總在出走,又禁不住回眸,在凝視與凝視間轉換形貌,在索求中,嘗到活著的愛與苦。賀淑芳鍛造文字一如煉金,看似句點,卻隱藏著叩問,總在世俗的庸常中,一遍又一遍逼視出個人存在的困境,而她對社會議題的犀利思考與高度的自我指涉,也讓《湖面如鏡》除了文學與美學上的獨特韻味之外,還具備了批判性,是近年來獨樹一格的女作家代表人物。
作者簡介
賀淑芳
一九七○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州。曾任工程師和報章副刊專題記者。二○○八年政大中文所碩士畢業。曾獲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等。曾於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執教,目前就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博士班。著有短篇小說集《迷宮毯子》。
一九七○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州。曾任工程師和報章副刊專題記者。二○○八年政大中文所碩士畢業。曾獲中國時報文學評審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等。曾於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執教,目前就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博士班。著有短篇小說集《迷宮毯子》。
目次
目錄:
【推薦序】幽禁無所──序賀淑芳《湖面如鏡》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自序】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01 夏天的旋風
02 天空劇場
03 箱子
04 牆
05 湖面如鏡
06 Aminah
07 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
08 十月
09 小鎮三月
【跋】在語言裡重生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附錄】緘默寂靜的聲音,震耳欲聾的抗議──賀淑芳的議題小說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
【推薦序】幽禁無所──序賀淑芳《湖面如鏡》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自序】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01 夏天的旋風
02 天空劇場
03 箱子
04 牆
05 湖面如鏡
06 Aminah
07 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
08 十月
09 小鎮三月
【跋】在語言裡重生 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附錄】緘默寂靜的聲音,震耳欲聾的抗議──賀淑芳的議題小說 李有成(中研院歐美所特聘研究員)
書摘/試閱
【推薦序】
幽禁無所──序賀淑芳《湖面如鏡》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賀淑芳的小說有一種孤獨的氛圍,濃烈而龐大,像久蓄陰雨而不預告何時發作的肥大烏雲,低低的壓在其虛構世界的天空。
「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這是〈夏天的旋風〉裡,母親給女兒的「金科玉律」。和許多人一樣,她以為伴侶、子女可以消除個人生活中的孤獨。這是美麗的想望,卻可能也是虛妄的。女兒結婚了,卻終究擠不進那歡樂的倫常關係,彷如家裡的局外人。即使在人擠人的遊樂場依然是孤伶伶的一個人。另一個母親(也許竟也是同一個?)在另一篇小說〈箱子〉裡,一天夜半醒轉,悲從中來,「不斷在心裡重複地說,我不要一個人,命再長也無甚樂趣。」她的哀哭沒有回音,卻足夠令人觸動。其他小說人物,比如隔壁家的安娣、大學的女講師、剪頭髮的印尼女人與圍坐她店裡一群不剪頭髮的客人、「信仰之家」的女孩們,無論已婚未婚、年輕年老,幾乎無一人能倖免於孤獨的籠罩。
孤獨,源於幽禁。〈牆〉中由牆砌出的由後院到廚房的有限空間,或許是這些小說中最具象的一個幽禁所在。隔壁的安娣就活動於其中,從養貓到養魚,外界——包括丈夫——與她完全隔離。牆如果是一個禁閉的象徵,那麼,牆的拆除卻未必是自由的隱喻(何況安娣家原本還有前門可以任她進出)。安娣在她家後院那面牆拆掉之後,也隨之神祕失蹤。年幼的敘述者相信,她是被豬籠草吞掉了。
幽禁之所,不在有牆無牆。它處處皆是。身在其中的人,有些可以選擇走出去,有些不可能出逃,有些沒想過出逃。
〈湖面如鏡〉中被指「態度不當地對待可蘭經」的女講師,屬於第一類。她涉入言論的禁區,引來排山倒海的責備與抨擊,於是不獲院方續聘。而她並不以為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勇氣可嘉,另一方面恐怕亦與另有退路不無關係:她還可以「申請出國,就找個什麼計畫出去」 。通過離開職場,她或許可以走出思想與言論自由被「非常非常地敏感」(院長使人發噱而又毛骨悚然的用語)的圈限的學術界。然而這並非人人輕易可做的抉擇。那個被指「在班上頌揚同性戀」的女講師,最後不是還孤獨地被困於湖面如鏡的漆黑混沌中嗎?
阿米娜故事系列中的主角阿米娜,以及「信仰之家」的其他女孩們,被置放於不是她們所選擇的宗教身分裡。國家體制以崇高的理由,確保她們安守於其身分之中。種種訴求宣告無效之後,阿米娜開始夢遊了。她褪下衣物,赤裸遊走,將應該遮蔽的,盡皆展露給夜色。夢遊,是她出逃的方式。然而,當早禱聲悠揚的響起,阿米娜還是回來了。她不得不回來,回到「信仰之家」,回到她的頭巾與長袍之中。在醒著的世界裡,她是跑不掉的。
賀淑芳小說中更多的,可能還是一群沒想過出逃的人。她們在〈箱子〉、〈天空劇場〉、〈牆〉、〈小鎮三月〉等篇中比比皆是。她們重複過著一樣的日子,百無聊賴,而渾然不知。她們生活中值得講述的,「總是別人的故事」。而對於自己的痛苦,則缺乏感知。比如〈小鎮三月〉述及的四姐,對右腳僵化「好像渾不在意、連痛苦都從腦子裡割切了那般歡悅地笑著」。她們被禁閉於對生活的無所感知裡。這種生活,賀淑芳在一篇散文中精確的稱之為「無意識的生活」。
幽禁,無須有形,無須有所。因而孤獨,甚至無力。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自序】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這本集子裡,有些稿件積存超過十年。寫〈牆〉時我尚在八打靈的《南洋商報》當記者。下班後在租來的房裡打稿。那是一棟座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從陽臺到廚房布滿灰塵,到處灰溜溜的。住宅區的聲海傾洩灌入,寂靜無垠龐大。
最初寫小說時根本沒抱希望。事實上,能不能繼續寫作、出書,皆有賴於各種現實條件支撐。在以為逃離它時,它仍像皮膚那樣緊貼著。
〈牆〉是我離開工廠後寫的第一個短篇。過了三十歲後,轉行,撿回寫作。彷彿跨過一道隘口。這以後陸續有些小說刊登在《南洋商報》張永修編的南洋文藝版。兩大報館(當時還是分開的兩家)辦事處相距不遠,當中棲身、流動的作家不少,下班後偶聚交談。吉隆坡聚集的人文圈子很小。寫作人與社運分子、報人多有往來,或許因為友人裡頭頗多熱心社運,那些翻騰的話語,如滾圈的砂子般盤旋複述,刺激了許多想法。
最初構想的故事多從公共議題切入。經過語言框裁,現實與虛構彼此宛如「延續的公園」。小說不是真實生活的記錄,但是卻和瞬逝的生活共存。尚在不久以前,我曾跟朋友說,嚮往文學裡最美的風景。但正如博爾赫斯的動物寓言〈Á Bao A Qu〉所喻,這至美的風景竟似不可描述,彷彿它必須是語言留白處。據說此名源自馬來語Abang Aku,故事採自馬來半島的神話。神靈自星空殞落掉在一處無以名之的所在。設若它圓滿返天,這故事就終結了。然而這生與死、創與癒彷彿永不結束。它沉默。成為橫亙遠處的風景。寫作與語言的關係是如此。就像你不會想為任何淺薄的關係多花一分力氣,能使你同時迷醉與探索的必是深切的情感與欲望。寫作就是在跟這樣的欲望親密:宛如在這道無可彌合的裂口深處,有翅膀伸觸彼岸。彼岸非是此世不可。或許無甚深奧,瑣碎熙攘,卻仍想若不斷地寫,也可能開出蓓蕾。
如今大家常說大家的生活都過得差不多一樣了。日常生活像在窄巷裡往返。窄巷分岔,或許也是小說穿接相遇的阡陌。在阡陌的岔口,遇見別人時也遇見陌生的自己。
這本集子裡,有些小說跟此時此地馬來西亞的政治有關,有些則更關心自己跟現實側身觀看的意識(無論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些則產自一個意念,譬如想要反駁一些流於二元對立簡化的觀點。有些是家人的故事,有些是聽來的他人的故事。虛構混合著事實,而事實總比小說所能想及的更加荒謬。公共議題搬進小說之後,是否還能在書寫中延續指控、或為受委屈者發聲?或對被書寫者負有一定的倫理責任?
每次書寫這些故事,「他人」就成為一面折射「我」的鏡子,無論「他人」強或弱。只要一個人執筆寫作,多少就握有權力。我的故事到底要怎麼說,才對他/她公平呢。要如何才能把她/他的主動與欲望還給他/她,而又不至於干擾故事。有時你以為是在結構中受害的人,她/他卻可能把自己看成具有選擇權的人。正是這一點,才能使一個人在最艱窘的環境中依然保有希望和自尊。也許這本集子在這方面仍然不是很成功,但盡可能靠近。在寫這些小說時,我試圖把一些自己和他人(母親、鄰居、朋友)的經歷與語言縫編成故事,咀嚼此地的滋味與形狀。雖然或許不免咀嚼得變形了。
小說的聲音可會飄過空谷?也許。沙灘上的足跡,以及雨天路上的濡濕腳印,也不知哪個比較短暫。如果小說的生命不長,那就寫給這不長。雖然經常感到好像有個等著要說的東西會隨時沉沒。如果把馬華文學消失的可能性懸置起來,小說對當前的思索也許可以使「此刻」拉遠。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的霸權問題,與之抵抗的口號並不新穎(譬如愛國),但其中族群觀點與角力狀況在半個世紀後卻有細微的差異。語言改變個體的力量確實龐大,既然我剛好在這裡,就盡量注視這張網,這裡頭滾動的偏見、聲音與感受,多少像觸角一樣伸進了小說裡。即便小說捕獲的只是剩餘──那些在歷史與社會語境中未能占一席地位的零碎、卑微與微不足道,那些對歷史和過去的奇怪說法,或許是值得打撈的碎片。
雖然大部分小說寫的總是他人的故事,但他人的想法與感情往往只是一種局限的知道。只能靠著想像來填補,或渡入自己的情感與思索。因為這層渡入與變形,「現實」切換在另一條水平線上走。彷彿這一現實的界面是個傾側的倒影。〈箱子〉和〈夏天的旋風〉是留台期間所作。〈天空劇場〉是剛離台歸鄉之初,和母親同住老家時寫。〈湖面如鏡〉寫時人還在金寶教書──這篇小說得感謝友人黃婉湄跟我分享她在國內大學的親身經歷,也有部分細節取自新聞報導。二○一二年八月開始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報到。餘下的四篇小說,包括以改教的阿米娜為人物的兩篇小說(回教的議題小說因受黃錦樹提醒而重拾再寫),即〈Aminah〉與〈風吹過黃梨葉與雞蛋花〉,最初只是要寫一系列改教議題的故事,經過考察之後,就變得集中在阿米娜及其朋友身上,從二○一二年初開始動筆,每天反覆修改,至少完成三個版本。〈Aminah〉也曾擬題〈有關阿米娜的二三事〉,那一整年幾乎一直重寫阿米娜/(洪/張)美蘭。我希望她不那麼悲慘,張美蘭是從洪美蘭蛻變出來,在此僅選最早與最後的兩個版本把她們一起留下。前兩個版本曾投港台一些文學雜誌,但不獲刊登,當時也寄給幾個朋友看。二○一二年底時也抽出一小段作為「驚花」圖文詩展(此活動由吉隆坡幾個作家朋友劉藝婉、梁靖芬、尼雅、陳頭頭以及我五個人共同主催)。〈小鎮三月〉及〈十月〉,也是近期在金寶與新加坡兩地往返中寫成。〈十月〉從找資料到寫完費時超過半年,南洋理工大學的圖書館資料幫了大忙。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在講故事,從工廠裡的工程師到記者編輯皆然。生活裡的故事無可終止,因應生存而不斷複述與變異。總有編造故事,超越平庸生活的欲望。有這些欲望與需要,使我感到自己確確實實活著 ── 我母親、祖母和姑姑們也大概如此,她們說的話像是給石磨碾過的麵粉,也許對歷史無感,但總有瑣碎的日常史;儘管故事來到時總是已在中間。之前之後,那一大片錯綜複雜的疑問,難以望盡如大霧;而細節碎片漫溢如汪洋。或許寫作無可避免得是載浮載沉,或為浮木或為船桅。倘若是無法登岸之茫途,那麼至少這無岸之河上,小說容許魚群泅過,魚回返卵、草飛回泥中、灰燼夢見火──哪怕這邊域的寫作,終將消逝、遺忘在歷史大霧中。
或許其實也不會那麼悲慘。畢竟寫作的航程屬於未知。
我仍然期盼小說有批判性。但如果小說能夠有批判力,應該同時也能與迂迴的沉默並行。讓叢叢問題如同疏密各異的時間,在小說體內迴成疊疊花瓣。
初稿於三月下旬,最後修訂於六月底
新加坡
【內文試閱】〈夏天的旋風〉
(第三十屆聯合報文學獎評審大獎作品)
蘇琴對遊樂場的印象,總是脫離不了旋轉的摩天輪。但這樣的印象有點過時了。當摩天輪美妙地暫停一分鐘,她乘坐的觀覽箱正巧停在最高點。週日午後,陽光刺眼,遊樂場裡光暈漫射,從那個巨大鋼骨圈的籠子裡往下望,地面上的嘉年華會有若一場無法正視的、旋轉不止的漩渦,七彩繽紛地飛旋底下、波濤起伏,讓人看了頭暈目眩。她覺得身體各個部分像是隨時會散開,像紙張一樣穿過鐵花被風斂走。雖然這不是雲霄飛車或狂飆飛碟,但依然有某種恐怖感從頭頂那裡冷冷澆下,彷彿她被虛空縛在一座深淵之上,至於穹頂那裡到底有什麼,怎樣也無法扭頭去看清楚。
「今天,會有點,改變,我,我們,一定。」
錄下這句話之後,就沒有下文了。錄音卡帶的輪子繼續轉動,喀啦喀啦,像一顆骷髏頭在滾動,喀啦喀啦,空空的眼睛追著外面旋轉的世界。雖然想再說什麼,但蘇琴所能給予的只有空白,無法再變成聲音。這不是世上任何人所認識的蘇琴。當她被剩下一個人時,當她想到自己將會被拋棄或者應該要採取主動時,她就會想,不如給自己講個故事。但她發現要對著麥克風說些什麼話,簡直就是荒謬離譜。試試吐出一個音:哦 ──。
錄下自己的聲音,播放。直到她從耳機裡聽見自己的聲音為止,在那之前,她從來不知道別人抗拒她的原因。聲音侷促不安,如一條蛇藏在裡頭,吐著遊絲般的氣息卡在語句之間。
她嘗試模仿另一種腔調,但依然有某種頑固的音質,如鱗片般沾在每句話尾端。試試說「我 ──」拉長,聽著它慢慢地變形成O ──。電池將近耗完之際,那拉長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某種不知名的動物藏在洞穴裡鳴叫。在什麼也沒錄到的地方,錄音機就只是沙沙地響。
在飄泊的頭十年,她一直懷著樂觀的期望。她畢業後飛到新加坡工作,數年後,和一個男人飛到臺北結婚。當時她相信,假如妳不冒險,事情就會永遠膠著,什麼好事也不會發生。但只要妳夠謹慎,小心翼翼端著手中的托盤,那些美妙的東西就不會打碎。
她踩著一雙橘黃色的拖鞋走進遊樂場。像太陽一樣的黃色,可以踩出信心洋溢的第一步,一切將重新開始。忘掉過去,讓衝突就只是過去的衝突。誤會,就只是有待驅散的陰影而已。雖然這幾天她一直覺得有一種將萬物化為塵土的時鐘音律,在體內滴答踱步,尤其是晚上睡覺之前,風在十二樓的高處呼嘯而過。從高樓往下望,夜間的臺北晶光燦爍,像一張面具等著她飛撲下去抓進手心。但與此同時,也有另一把聲音會撫平那些囈語般此起彼落的囂音。那股聲音極之強韌,猶如將人從泥沼裡拉出來的救生纜,從看不到盡頭的高處,遙遙垂下提醒她:妳還沒有 ──。哦。我還沒有什麼?呵,我有好多東西都「還沒有」!假如妳眼睜睜看著救生纜在掌心裡消失,什麼都抓不到,身體卻不受控制地繼續往下沉──那又能怎樣?
經過兩年來的冷戰之後,所有過去掩藏在檯面下的東西都被掀出來。但今天,她決定了這不會是一次單純的出遊,未來將不會再含糊地混過去。她將做下一個重要的決定,通過一個重要的測驗。
看著已漸鬆弛的軀體,對那身泳衣略感不安,她從背包裡抽出一件恤衫套上,才推門出去,回到喧囂鼎沸的空氣裡。嘩嘩的水聲沖刷巨大的鋼骨,五彩的陽光在水花裡疊纍著擴大,在夏日的水蒸氣裡,叫笑聲到處膨脹。濕漉漉的人群相互推搡著朝前走。他們嘻笑著,水從眼簾往下滴,幾乎什麼都看不清楚。
她沒下水,頭頂著草帽,燦爛的陽光灑滿遊樂場裡的芸芸眾生。蘇琴在這裡跟著她等待的人。那是每日聽見的口音,浮懸在她的腳步前面。那種彼此之間聽起來自在無比、彼此接納、而且無須轉換的腔調。這一行人正踩過細沙衝進水裡,嗯,她的眼睛看見了他們,那個丈夫,和一雙兒女。他們毫無原因的狂喜,奔向人工浪池。她不由自主地涉水滑過去。在水裡,蘇琴和一大群她不認識的人套在顏色各異的橡皮圈裡,共同屏息等待下一場高浪襲來的快意。浮在水裡的身體很輕,不足以傾覆;這是大家一起合作假裝沒頂的虛假恐懼。這是好的,蘇琴想,要在這人山人海的池裡溺斃,比被壓死還難。
蘇琴發現那個丈夫(或父親)半浮半蹲在兩個孩子之間,一雙張開的手臂顯得尤其雪白,左右兩手各自緊抓著一雙兒女的救生圈。三個人被這雙強壯的手臂串連在一起,有如被一條隱形的鎖鍊套住,誰也不會被浪沖開。波浪過去以後,他們呼哈呼哈地笑著,紛紛咳出嗆進鼻咽裡的水,這時他會暫時鬆手來擦一把臉。然後他們同時皺眉,那種笑起來眼睛往兩旁斜落的表情,是那麼相似。
蘇琴決定玩一個不出聲的遊戲,不說話,閉上嘴巴。她決定悄悄空出這個位子,一個母親缺席的歡樂場面。
「好不好玩?」點頭。
「上不上去?」搖頭。
男人緊攬著他們,緊張兮兮地囑咐孩子一定要抓牢橡皮圈的邊緣,孩子被逗得很樂。他的前額髮際已見稀少,但肩膀寬闊,看起來很可靠。
現在蘇琴記得她的母親。她把許多特殊的優點和缺陷都遺傳給她。母親也曾經緊摟著她,嘴巴湊近她的耳朵,溫熱的氣息吹過頸項,就像她準備用一口氣吹活這個冥頑不靈的泥人:「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
無法控制,蘇琴在水中冒出眼淚。
這就是母親想盡辦法要告訴她的話,她重複了那麼多次,以至於蘇琴覺得那就是她母親自己的金科玉律,似乎那就是她母親此生最想說的。
有一些話卡在肚子裡,蘇琴從來就無法把那些真正想說的話吐出來。沒有適當的機會,那些話在心裡研磨了好幾年。有時候她懷疑,這些話可能根本沒有說出來的價值,甚至也可能不是她真正想講的,到底哪一句才是必須說出來的話呢,她想自己也許沒有辦法知道。也許死前的那一刻就會懂,也許在說出來的剎那,也就完成了。但假如到頭來一直都不懂,那又怎樣呢?
遊樂場最好的事,或許就在於它是一場無須多言的狂歡大會。但你卻可以從激烈的遊戲中證明自己。強烈地笑、尖叫,或者失色地跑,提著橡皮圈,從一個地方奔向另一個地方,從高處滑向低處,或者從低處衝向高聳的頂點。夏天的陽光燙燒肌膚,蘇琴發現遊樂場有一張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過的臉孔。當然每個地方都會有特別的表情,就像在車廂或電梯裡都有各自專屬的臉孔那樣。遊樂場的臉,是屬於痙攣的臉,因為強烈的歡樂而痙攣。這種歡樂和死亡相似,像太陽一樣從體內放射,慢慢地燒著體內的每一根纖維,令你不得不渾身滾燙地到處亂跑。
厭倦了人工浪,那個小女兒踩過細沙,小步地奔跑。現在他們又要跑到另一個地方去。在樂園裡歡快地移動,他們不會相信,一家人不過只有數年時光暫時相聚。現在,想像自己是個隱形的母親,被家人忽略的存在,蘇琴沉默地跟隨在後,從後面看著三人的影子在陽光下跳動。
他們被帶到一座大城堡前面,小孩在那裡反覆不斷地爬上滑梯、梯級,沿著密封的滑道衝到水池裡。反覆滾落,又反覆爬上頂端,等著自己被突如其來的海浪沖刷,讓圍觀的父母觀看,他們是何等聰明而敏捷,可以禁得起無數次的考驗或打擊。
他們跑到沙灘上玩排球。在另一個地方,他們三人共乘一艘橡皮艇,在一個膨脹橢圓的大碗裡尖叫環繞。十多分鐘以後,蘇琴看到他們被排出到一條小河裡,筋疲力竭地癱倒在橡皮艇上。
「我們是否要回去了?」
「不要、不要,我們還沒有玩那個、那個!」
「天啊,」那個父親看了那列正緩緩爬上斜坡、旋即疾速俯衝的列車,人們幾乎是光禿禿地把自己暴露在高速颳過的空氣裡。「我可以說不嗎?」
「妳能坐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她舉起攝錄機對著他們,變換焦距,把他的臉拉近、放大,然後再推遠、變小。她想要從那張臉看出來,那裡頭究竟是有懇求,抑或僅是敷衍的意味。但她只看到一張異常疲憊的臉,一股已經失去活力、幾乎平坦、沒有溫度的視線,僵硬地對著鏡頭。她希望那是出於這些過度激烈的遊戲,而不是因為過去幾年消逝了的時光。在攝錄螢幕的影像裡,他們並排站著,背後的七彩氣球、卡通、鋼骨與那些塑膠玩意,稠密地包圍著他們,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剩下。
現在他們正在一條長龍裡排隊,一瞬間就即將登上那輛飛車。蘇琴和他們站得很靠近,假如有別人在一旁看他們,也會自然地認為蘇琴和他們是一家人。他伸出手,看似想碰她的肩膀,但最後卻是落在女兒細軟的頭髮上,他把她抱起來,嘴唇在她額頭上一親。同時擺了個鬼臉,讓太陽眼鏡低低地滑落到鼻尖上頭。小女孩沒被逗笑,她蹙眉看他。背後連綿的說話聲像膨脹的海綿一樣親密地貼過來,但沒有任何歡樂會滲透進來。
上空不時傳來一陣陣震耳欲聾的俯衝歡呼聲,當它在頭頂上掠過的時候,蘇琴覺得頭皮發麻,就像有一把利刃在頭頂上劃過那樣。她知道是什麼東西神使鬼差地使她點頭,因為那陣颳過公寓的風,像漩渦一樣會把她吞沒,吸到深谷底下。
一定要坐上去,她模糊地想。就算只能暫時麻痺也好。
她注意著前面這個男孩的動作,他安靜地吹著泡泡。她猜想他其實很緊張,但他掩飾得很好,她沒有看見他顫抖。他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他的眼睛非常平靜地盯著眼前一根水草末端冒出來的七彩泡泡。泡泡昇到空中,變大,上昇,變得更大,越來越高,然後破掉。就像嘉年華會忽然停頓了似的。
她聽見後面有個女孩對媽媽說:我要去小便。她媽媽毫不猶疑就帶她離開,兩個人再也沒有回來過。
妳應該想辦法和他說說話。說著話的時候,人們就會忘記時間過得多麼慢。妳知道自己無法這麼做,因為只要一開口說話,眼淚就會失控掉下來。
她想,她是在作夢。在夢中,任何不可能的交談都可以進行。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會發生。
「妳好嗎?」男孩忽然轉過頭來問她。
「好,」她轉頭對他微笑。「當然好。」
沉默的遊戲結束了。現在,他們總算先開腔。不管她的口音如何,他們必須要開口對她說話。她伸手摸摸他的頭髮,他沒有抗拒,雖然他到現在還不肯叫她,因為不知應該如何稱呼她:阿姨、阿嬸?
「妳可以不坐,」他說,「假如妳害怕。」
「我不害怕。」
「我媽會害怕,她上次也在出口那裡等我們。」
聽著這話,她不是不驚異的,那個女人,每次都像她這樣嗎?還是她代替了她的位置,變得像她?
「我沒有那麼害怕。」
「如果這火車掉下來 ──」
她安慰他。雖然她一點也不瞭解那種地獄般的狂歡,這整片拆掉後就將只剩沙漠的城堡,此刻正激騰地叫嚷。但她願意說服別人相信那些她希望自己相信的。
「再過一百年都不會掉下來。」
她永遠不會再坐第二次。那種翻轉過來的感覺,整個人被懸掛倒過來,就像垃圾桶被翻過來猛力搖晃,要把裡頭的東西全部倒光似的。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被緊緊地吸附在座位上,可是裡頭又有什麼東西要往外飛,就像是有一部分的靈魂要被風斂走。
她無法制止地與其他人一起高聲尖叫,不知喊出「哇」還是「呀」,也無法聽出別人在喊什麼。有一種共振的歡樂像痛苦一樣強烈地盤據了她,如膨脹的海綿般擠壓著她的心臟。
也許她陷入了夢境,也許她曾經昏死過去。一朵白茫茫的雲霧,從鼻子底端昇上來,逐漸擴張,膨脹,直至它完全蓋住她的眼睛。有一瞬間她什麼也看不到,再也看不到那片疾速飛逝的模糊風景。只見到一種光滑的、濃稠的、純淨的白色。那真是一種噁心的空白。它那麼黏膩,分明是什麼都沒有,卻又什麼都容不下,凝滯不動地蹲坐在她頭上,壓著她的臉。無法掙扎,彷彿她已經死了,變成一具無法動彈的屍體,被一團封在蠟裡的奶白物質包裹起來。到這地步她僅能狂喊,憤慨地抽光肺葉裡的空氣,直到有個東西慢慢地沿著咽喉爬上來,她感覺到自己開始嘔吐。
這片覆罩著她眼鼻的空白顏色逐漸變輕、縮小、遠離她的臉,沒有重量、它甚至看來帶著光滑的弧形感。她清楚地看見一顆巨大的、白色的O,從張開的嘴巴裡冒了出來。
兩顆,三顆。她沒辦法數。它們全都冉冉地飄上湛藍無垠的天空。
她想,沒有人看見,她嘔了一連串氣球出來。白色的氣球。
坐在前方的父親自然不會看見。身旁的男孩不曉得究竟是睜開還是閉著眼,在全程中他一直尖叫。嗯,他的確是什麼都沒看見,他在過後對她說:「妳沒有嘔吐。」
男孩迷惑地看著她。她可以讀出藏在他心裡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看吧,妳果然跟我們不一樣。
在他們一起衝出來的剎那,父子三人都立刻張開紙袋,各自往袋子裡大吐特吐。蘇琴記得今天上午,他們在餐廳裡點了漢堡、焗飯、火腿雞排、薯片、冰可樂。當時她根本不想勸阻他們。
他們都低著頭,以類似的抽搐感和節奏,嘔出腸胃裡的雜食所化成的液態。無論是揉著胸口的動作,還是呼氣之後的虛軟模樣,他們看起來都是如此相似,她掏出紙巾給他們,白色的紙巾。她接過那三個裝滿嘔吐物的紙袋時,並非是不噁心的。
不只是因為眼前的孩子都是另一個女人生下的緣故,即使是她自己生下的孩子,也可能會長得更像父親,或更像自己。他們都會成為他的孩子,或者也會成為她的孩子,如果她盡力爭取,如果。如果她到死的時候還愛著他們。他們也許會無可避免地說著和她明顯不同的口音,或者也會逐漸地、一點一滴地愛回她。
但每個人都會離開她。在她死的時候,必然是一個人,孤伶伶地死去。
這個下午真漫長,她覺得自己熬了很久。在遊樂場的另一邊,他們經過一種不停在旋轉的心形大杯子。
「還要玩嗎?」
小孩失措地看她。
蘇琴先走進去,她坐在裡頭等候。她抬起眼睛注視著三父子,她等候著他們的下一步。那個丈夫(那個父親)走過來了,他坐在她旁邊,握緊她的手。
「妳怎麼啦?」他說。「大家都很累了。」
她不理他。她轉頭朝向還呆站在杯子外面的那兩個孩子叫喊:「快點上來,快點。遊樂場要關門囉!」
孩子們立刻爬上來,男的靠向他父親。女孩起初猶疑著不知該坐哪裡。她伸手用力一拉,把女孩拉過來,讓女孩的耳朵貼近自己的心臟。
起初杯子的速度很慢,就像一首悠揚的樂曲。隨後,音樂越來越激昂,杯子就轉得越來越快。蘇琴覺得自己就像被一根看不見的湯匙,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拌攪。他們的鎮靜和防備快速被融化,每個人的嘴巴似乎都被塞進了另一張嘴巴,從那裡吐出了尖銳的叫聲,不屬於任何口音或腔調,共同的叫聲縈繞在遊樂場的上空。
正如蘇琴所想像的那樣。在杯子停下來的時候,他們四個人就像一般正常的家人那樣,緊緊地黏在一起,像四塊融化的方糖。
幽禁無所──序賀淑芳《湖面如鏡》
林春美(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賀淑芳的小說有一種孤獨的氛圍,濃烈而龐大,像久蓄陰雨而不預告何時發作的肥大烏雲,低低的壓在其虛構世界的天空。
「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這是〈夏天的旋風〉裡,母親給女兒的「金科玉律」。和許多人一樣,她以為伴侶、子女可以消除個人生活中的孤獨。這是美麗的想望,卻可能也是虛妄的。女兒結婚了,卻終究擠不進那歡樂的倫常關係,彷如家裡的局外人。即使在人擠人的遊樂場依然是孤伶伶的一個人。另一個母親(也許竟也是同一個?)在另一篇小說〈箱子〉裡,一天夜半醒轉,悲從中來,「不斷在心裡重複地說,我不要一個人,命再長也無甚樂趣。」她的哀哭沒有回音,卻足夠令人觸動。其他小說人物,比如隔壁家的安娣、大學的女講師、剪頭髮的印尼女人與圍坐她店裡一群不剪頭髮的客人、「信仰之家」的女孩們,無論已婚未婚、年輕年老,幾乎無一人能倖免於孤獨的籠罩。
孤獨,源於幽禁。〈牆〉中由牆砌出的由後院到廚房的有限空間,或許是這些小說中最具象的一個幽禁所在。隔壁的安娣就活動於其中,從養貓到養魚,外界——包括丈夫——與她完全隔離。牆如果是一個禁閉的象徵,那麼,牆的拆除卻未必是自由的隱喻(何況安娣家原本還有前門可以任她進出)。安娣在她家後院那面牆拆掉之後,也隨之神祕失蹤。年幼的敘述者相信,她是被豬籠草吞掉了。
幽禁之所,不在有牆無牆。它處處皆是。身在其中的人,有些可以選擇走出去,有些不可能出逃,有些沒想過出逃。
〈湖面如鏡〉中被指「態度不當地對待可蘭經」的女講師,屬於第一類。她涉入言論的禁區,引來排山倒海的責備與抨擊,於是不獲院方續聘。而她並不以為懼。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勇氣可嘉,另一方面恐怕亦與另有退路不無關係:她還可以「申請出國,就找個什麼計畫出去」 。通過離開職場,她或許可以走出思想與言論自由被「非常非常地敏感」(院長使人發噱而又毛骨悚然的用語)的圈限的學術界。然而這並非人人輕易可做的抉擇。那個被指「在班上頌揚同性戀」的女講師,最後不是還孤獨地被困於湖面如鏡的漆黑混沌中嗎?
阿米娜故事系列中的主角阿米娜,以及「信仰之家」的其他女孩們,被置放於不是她們所選擇的宗教身分裡。國家體制以崇高的理由,確保她們安守於其身分之中。種種訴求宣告無效之後,阿米娜開始夢遊了。她褪下衣物,赤裸遊走,將應該遮蔽的,盡皆展露給夜色。夢遊,是她出逃的方式。然而,當早禱聲悠揚的響起,阿米娜還是回來了。她不得不回來,回到「信仰之家」,回到她的頭巾與長袍之中。在醒著的世界裡,她是跑不掉的。
賀淑芳小說中更多的,可能還是一群沒想過出逃的人。她們在〈箱子〉、〈天空劇場〉、〈牆〉、〈小鎮三月〉等篇中比比皆是。她們重複過著一樣的日子,百無聊賴,而渾然不知。她們生活中值得講述的,「總是別人的故事」。而對於自己的痛苦,則缺乏感知。比如〈小鎮三月〉述及的四姐,對右腳僵化「好像渾不在意、連痛苦都從腦子裡割切了那般歡悅地笑著」。她們被禁閉於對生活的無所感知裡。這種生活,賀淑芳在一篇散文中精確的稱之為「無意識的生活」。
幽禁,無須有形,無須有所。因而孤獨,甚至無力。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自序】關於繁花萬鏡,以及卑微零碎的
這本集子裡,有些稿件積存超過十年。寫〈牆〉時我尚在八打靈的《南洋商報》當記者。下班後在租來的房裡打稿。那是一棟座落在三岔路口的房子,從陽臺到廚房布滿灰塵,到處灰溜溜的。住宅區的聲海傾洩灌入,寂靜無垠龐大。
最初寫小說時根本沒抱希望。事實上,能不能繼續寫作、出書,皆有賴於各種現實條件支撐。在以為逃離它時,它仍像皮膚那樣緊貼著。
〈牆〉是我離開工廠後寫的第一個短篇。過了三十歲後,轉行,撿回寫作。彷彿跨過一道隘口。這以後陸續有些小說刊登在《南洋商報》張永修編的南洋文藝版。兩大報館(當時還是分開的兩家)辦事處相距不遠,當中棲身、流動的作家不少,下班後偶聚交談。吉隆坡聚集的人文圈子很小。寫作人與社運分子、報人多有往來,或許因為友人裡頭頗多熱心社運,那些翻騰的話語,如滾圈的砂子般盤旋複述,刺激了許多想法。
最初構想的故事多從公共議題切入。經過語言框裁,現實與虛構彼此宛如「延續的公園」。小說不是真實生活的記錄,但是卻和瞬逝的生活共存。尚在不久以前,我曾跟朋友說,嚮往文學裡最美的風景。但正如博爾赫斯的動物寓言〈Á Bao A Qu〉所喻,這至美的風景竟似不可描述,彷彿它必須是語言留白處。據說此名源自馬來語Abang Aku,故事採自馬來半島的神話。神靈自星空殞落掉在一處無以名之的所在。設若它圓滿返天,這故事就終結了。然而這生與死、創與癒彷彿永不結束。它沉默。成為橫亙遠處的風景。寫作與語言的關係是如此。就像你不會想為任何淺薄的關係多花一分力氣,能使你同時迷醉與探索的必是深切的情感與欲望。寫作就是在跟這樣的欲望親密:宛如在這道無可彌合的裂口深處,有翅膀伸觸彼岸。彼岸非是此世不可。或許無甚深奧,瑣碎熙攘,卻仍想若不斷地寫,也可能開出蓓蕾。
如今大家常說大家的生活都過得差不多一樣了。日常生活像在窄巷裡往返。窄巷分岔,或許也是小說穿接相遇的阡陌。在阡陌的岔口,遇見別人時也遇見陌生的自己。
這本集子裡,有些小說跟此時此地馬來西亞的政治有關,有些則更關心自己跟現實側身觀看的意識(無論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有些則產自一個意念,譬如想要反駁一些流於二元對立簡化的觀點。有些是家人的故事,有些是聽來的他人的故事。虛構混合著事實,而事實總比小說所能想及的更加荒謬。公共議題搬進小說之後,是否還能在書寫中延續指控、或為受委屈者發聲?或對被書寫者負有一定的倫理責任?
每次書寫這些故事,「他人」就成為一面折射「我」的鏡子,無論「他人」強或弱。只要一個人執筆寫作,多少就握有權力。我的故事到底要怎麼說,才對他/她公平呢。要如何才能把她/他的主動與欲望還給他/她,而又不至於干擾故事。有時你以為是在結構中受害的人,她/他卻可能把自己看成具有選擇權的人。正是這一點,才能使一個人在最艱窘的環境中依然保有希望和自尊。也許這本集子在這方面仍然不是很成功,但盡可能靠近。在寫這些小說時,我試圖把一些自己和他人(母親、鄰居、朋友)的經歷與語言縫編成故事,咀嚼此地的滋味與形狀。雖然或許不免咀嚼得變形了。
小說的聲音可會飄過空谷?也許。沙灘上的足跡,以及雨天路上的濡濕腳印,也不知哪個比較短暫。如果小說的生命不長,那就寫給這不長。雖然經常感到好像有個等著要說的東西會隨時沉沒。如果把馬華文學消失的可能性懸置起來,小說對當前的思索也許可以使「此刻」拉遠。馬來西亞建國以來的霸權問題,與之抵抗的口號並不新穎(譬如愛國),但其中族群觀點與角力狀況在半個世紀後卻有細微的差異。語言改變個體的力量確實龐大,既然我剛好在這裡,就盡量注視這張網,這裡頭滾動的偏見、聲音與感受,多少像觸角一樣伸進了小說裡。即便小說捕獲的只是剩餘──那些在歷史與社會語境中未能占一席地位的零碎、卑微與微不足道,那些對歷史和過去的奇怪說法,或許是值得打撈的碎片。
雖然大部分小說寫的總是他人的故事,但他人的想法與感情往往只是一種局限的知道。只能靠著想像來填補,或渡入自己的情感與思索。因為這層渡入與變形,「現實」切換在另一條水平線上走。彷彿這一現實的界面是個傾側的倒影。〈箱子〉和〈夏天的旋風〉是留台期間所作。〈天空劇場〉是剛離台歸鄉之初,和母親同住老家時寫。〈湖面如鏡〉寫時人還在金寶教書──這篇小說得感謝友人黃婉湄跟我分享她在國內大學的親身經歷,也有部分細節取自新聞報導。二○一二年八月開始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報到。餘下的四篇小說,包括以改教的阿米娜為人物的兩篇小說(回教的議題小說因受黃錦樹提醒而重拾再寫),即〈Aminah〉與〈風吹過黃梨葉與雞蛋花〉,最初只是要寫一系列改教議題的故事,經過考察之後,就變得集中在阿米娜及其朋友身上,從二○一二年初開始動筆,每天反覆修改,至少完成三個版本。〈Aminah〉也曾擬題〈有關阿米娜的二三事〉,那一整年幾乎一直重寫阿米娜/(洪/張)美蘭。我希望她不那麼悲慘,張美蘭是從洪美蘭蛻變出來,在此僅選最早與最後的兩個版本把她們一起留下。前兩個版本曾投港台一些文學雜誌,但不獲刊登,當時也寄給幾個朋友看。二○一二年底時也抽出一小段作為「驚花」圖文詩展(此活動由吉隆坡幾個作家朋友劉藝婉、梁靖芬、尼雅、陳頭頭以及我五個人共同主催)。〈小鎮三月〉及〈十月〉,也是近期在金寶與新加坡兩地往返中寫成。〈十月〉從找資料到寫完費時超過半年,南洋理工大學的圖書館資料幫了大忙。
我覺得各行各業都在講故事,從工廠裡的工程師到記者編輯皆然。生活裡的故事無可終止,因應生存而不斷複述與變異。總有編造故事,超越平庸生活的欲望。有這些欲望與需要,使我感到自己確確實實活著 ── 我母親、祖母和姑姑們也大概如此,她們說的話像是給石磨碾過的麵粉,也許對歷史無感,但總有瑣碎的日常史;儘管故事來到時總是已在中間。之前之後,那一大片錯綜複雜的疑問,難以望盡如大霧;而細節碎片漫溢如汪洋。或許寫作無可避免得是載浮載沉,或為浮木或為船桅。倘若是無法登岸之茫途,那麼至少這無岸之河上,小說容許魚群泅過,魚回返卵、草飛回泥中、灰燼夢見火──哪怕這邊域的寫作,終將消逝、遺忘在歷史大霧中。
或許其實也不會那麼悲慘。畢竟寫作的航程屬於未知。
我仍然期盼小說有批判性。但如果小說能夠有批判力,應該同時也能與迂迴的沉默並行。讓叢叢問題如同疏密各異的時間,在小說體內迴成疊疊花瓣。
初稿於三月下旬,最後修訂於六月底
新加坡
【內文試閱】〈夏天的旋風〉
(第三十屆聯合報文學獎評審大獎作品)
蘇琴對遊樂場的印象,總是脫離不了旋轉的摩天輪。但這樣的印象有點過時了。當摩天輪美妙地暫停一分鐘,她乘坐的觀覽箱正巧停在最高點。週日午後,陽光刺眼,遊樂場裡光暈漫射,從那個巨大鋼骨圈的籠子裡往下望,地面上的嘉年華會有若一場無法正視的、旋轉不止的漩渦,七彩繽紛地飛旋底下、波濤起伏,讓人看了頭暈目眩。她覺得身體各個部分像是隨時會散開,像紙張一樣穿過鐵花被風斂走。雖然這不是雲霄飛車或狂飆飛碟,但依然有某種恐怖感從頭頂那裡冷冷澆下,彷彿她被虛空縛在一座深淵之上,至於穹頂那裡到底有什麼,怎樣也無法扭頭去看清楚。
「今天,會有點,改變,我,我們,一定。」
錄下這句話之後,就沒有下文了。錄音卡帶的輪子繼續轉動,喀啦喀啦,像一顆骷髏頭在滾動,喀啦喀啦,空空的眼睛追著外面旋轉的世界。雖然想再說什麼,但蘇琴所能給予的只有空白,無法再變成聲音。這不是世上任何人所認識的蘇琴。當她被剩下一個人時,當她想到自己將會被拋棄或者應該要採取主動時,她就會想,不如給自己講個故事。但她發現要對著麥克風說些什麼話,簡直就是荒謬離譜。試試吐出一個音:哦 ──。
錄下自己的聲音,播放。直到她從耳機裡聽見自己的聲音為止,在那之前,她從來不知道別人抗拒她的原因。聲音侷促不安,如一條蛇藏在裡頭,吐著遊絲般的氣息卡在語句之間。
她嘗試模仿另一種腔調,但依然有某種頑固的音質,如鱗片般沾在每句話尾端。試試說「我 ──」拉長,聽著它慢慢地變形成O ──。電池將近耗完之際,那拉長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某種不知名的動物藏在洞穴裡鳴叫。在什麼也沒錄到的地方,錄音機就只是沙沙地響。
在飄泊的頭十年,她一直懷著樂觀的期望。她畢業後飛到新加坡工作,數年後,和一個男人飛到臺北結婚。當時她相信,假如妳不冒險,事情就會永遠膠著,什麼好事也不會發生。但只要妳夠謹慎,小心翼翼端著手中的托盤,那些美妙的東西就不會打碎。
她踩著一雙橘黃色的拖鞋走進遊樂場。像太陽一樣的黃色,可以踩出信心洋溢的第一步,一切將重新開始。忘掉過去,讓衝突就只是過去的衝突。誤會,就只是有待驅散的陰影而已。雖然這幾天她一直覺得有一種將萬物化為塵土的時鐘音律,在體內滴答踱步,尤其是晚上睡覺之前,風在十二樓的高處呼嘯而過。從高樓往下望,夜間的臺北晶光燦爍,像一張面具等著她飛撲下去抓進手心。但與此同時,也有另一把聲音會撫平那些囈語般此起彼落的囂音。那股聲音極之強韌,猶如將人從泥沼裡拉出來的救生纜,從看不到盡頭的高處,遙遙垂下提醒她:妳還沒有 ──。哦。我還沒有什麼?呵,我有好多東西都「還沒有」!假如妳眼睜睜看著救生纜在掌心裡消失,什麼都抓不到,身體卻不受控制地繼續往下沉──那又能怎樣?
經過兩年來的冷戰之後,所有過去掩藏在檯面下的東西都被掀出來。但今天,她決定了這不會是一次單純的出遊,未來將不會再含糊地混過去。她將做下一個重要的決定,通過一個重要的測驗。
看著已漸鬆弛的軀體,對那身泳衣略感不安,她從背包裡抽出一件恤衫套上,才推門出去,回到喧囂鼎沸的空氣裡。嘩嘩的水聲沖刷巨大的鋼骨,五彩的陽光在水花裡疊纍著擴大,在夏日的水蒸氣裡,叫笑聲到處膨脹。濕漉漉的人群相互推搡著朝前走。他們嘻笑著,水從眼簾往下滴,幾乎什麼都看不清楚。
她沒下水,頭頂著草帽,燦爛的陽光灑滿遊樂場裡的芸芸眾生。蘇琴在這裡跟著她等待的人。那是每日聽見的口音,浮懸在她的腳步前面。那種彼此之間聽起來自在無比、彼此接納、而且無須轉換的腔調。這一行人正踩過細沙衝進水裡,嗯,她的眼睛看見了他們,那個丈夫,和一雙兒女。他們毫無原因的狂喜,奔向人工浪池。她不由自主地涉水滑過去。在水裡,蘇琴和一大群她不認識的人套在顏色各異的橡皮圈裡,共同屏息等待下一場高浪襲來的快意。浮在水裡的身體很輕,不足以傾覆;這是大家一起合作假裝沒頂的虛假恐懼。這是好的,蘇琴想,要在這人山人海的池裡溺斃,比被壓死還難。
蘇琴發現那個丈夫(或父親)半浮半蹲在兩個孩子之間,一雙張開的手臂顯得尤其雪白,左右兩手各自緊抓著一雙兒女的救生圈。三個人被這雙強壯的手臂串連在一起,有如被一條隱形的鎖鍊套住,誰也不會被浪沖開。波浪過去以後,他們呼哈呼哈地笑著,紛紛咳出嗆進鼻咽裡的水,這時他會暫時鬆手來擦一把臉。然後他們同時皺眉,那種笑起來眼睛往兩旁斜落的表情,是那麼相似。
蘇琴決定玩一個不出聲的遊戲,不說話,閉上嘴巴。她決定悄悄空出這個位子,一個母親缺席的歡樂場面。
「好不好玩?」點頭。
「上不上去?」搖頭。
男人緊攬著他們,緊張兮兮地囑咐孩子一定要抓牢橡皮圈的邊緣,孩子被逗得很樂。他的前額髮際已見稀少,但肩膀寬闊,看起來很可靠。
現在蘇琴記得她的母親。她把許多特殊的優點和缺陷都遺傳給她。母親也曾經緊摟著她,嘴巴湊近她的耳朵,溫熱的氣息吹過頸項,就像她準備用一口氣吹活這個冥頑不靈的泥人:「不管妳去哪裡,妳聽著,妳的未來,就是要結婚,生個孩子。不讓自己老的時候,孤伶伶一個人。」
無法控制,蘇琴在水中冒出眼淚。
這就是母親想盡辦法要告訴她的話,她重複了那麼多次,以至於蘇琴覺得那就是她母親自己的金科玉律,似乎那就是她母親此生最想說的。
有一些話卡在肚子裡,蘇琴從來就無法把那些真正想說的話吐出來。沒有適當的機會,那些話在心裡研磨了好幾年。有時候她懷疑,這些話可能根本沒有說出來的價值,甚至也可能不是她真正想講的,到底哪一句才是必須說出來的話呢,她想自己也許沒有辦法知道。也許死前的那一刻就會懂,也許在說出來的剎那,也就完成了。但假如到頭來一直都不懂,那又怎樣呢?
遊樂場最好的事,或許就在於它是一場無須多言的狂歡大會。但你卻可以從激烈的遊戲中證明自己。強烈地笑、尖叫,或者失色地跑,提著橡皮圈,從一個地方奔向另一個地方,從高處滑向低處,或者從低處衝向高聳的頂點。夏天的陽光燙燒肌膚,蘇琴發現遊樂場有一張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出現過的臉孔。當然每個地方都會有特別的表情,就像在車廂或電梯裡都有各自專屬的臉孔那樣。遊樂場的臉,是屬於痙攣的臉,因為強烈的歡樂而痙攣。這種歡樂和死亡相似,像太陽一樣從體內放射,慢慢地燒著體內的每一根纖維,令你不得不渾身滾燙地到處亂跑。
厭倦了人工浪,那個小女兒踩過細沙,小步地奔跑。現在他們又要跑到另一個地方去。在樂園裡歡快地移動,他們不會相信,一家人不過只有數年時光暫時相聚。現在,想像自己是個隱形的母親,被家人忽略的存在,蘇琴沉默地跟隨在後,從後面看著三人的影子在陽光下跳動。
他們被帶到一座大城堡前面,小孩在那裡反覆不斷地爬上滑梯、梯級,沿著密封的滑道衝到水池裡。反覆滾落,又反覆爬上頂端,等著自己被突如其來的海浪沖刷,讓圍觀的父母觀看,他們是何等聰明而敏捷,可以禁得起無數次的考驗或打擊。
他們跑到沙灘上玩排球。在另一個地方,他們三人共乘一艘橡皮艇,在一個膨脹橢圓的大碗裡尖叫環繞。十多分鐘以後,蘇琴看到他們被排出到一條小河裡,筋疲力竭地癱倒在橡皮艇上。
「我們是否要回去了?」
「不要、不要,我們還沒有玩那個、那個!」
「天啊,」那個父親看了那列正緩緩爬上斜坡、旋即疾速俯衝的列車,人們幾乎是光禿禿地把自己暴露在高速颳過的空氣裡。「我可以說不嗎?」
「妳能坐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她舉起攝錄機對著他們,變換焦距,把他的臉拉近、放大,然後再推遠、變小。她想要從那張臉看出來,那裡頭究竟是有懇求,抑或僅是敷衍的意味。但她只看到一張異常疲憊的臉,一股已經失去活力、幾乎平坦、沒有溫度的視線,僵硬地對著鏡頭。她希望那是出於這些過度激烈的遊戲,而不是因為過去幾年消逝了的時光。在攝錄螢幕的影像裡,他們並排站著,背後的七彩氣球、卡通、鋼骨與那些塑膠玩意,稠密地包圍著他們,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剩下。
現在他們正在一條長龍裡排隊,一瞬間就即將登上那輛飛車。蘇琴和他們站得很靠近,假如有別人在一旁看他們,也會自然地認為蘇琴和他們是一家人。他伸出手,看似想碰她的肩膀,但最後卻是落在女兒細軟的頭髮上,他把她抱起來,嘴唇在她額頭上一親。同時擺了個鬼臉,讓太陽眼鏡低低地滑落到鼻尖上頭。小女孩沒被逗笑,她蹙眉看他。背後連綿的說話聲像膨脹的海綿一樣親密地貼過來,但沒有任何歡樂會滲透進來。
上空不時傳來一陣陣震耳欲聾的俯衝歡呼聲,當它在頭頂上掠過的時候,蘇琴覺得頭皮發麻,就像有一把利刃在頭頂上劃過那樣。她知道是什麼東西神使鬼差地使她點頭,因為那陣颳過公寓的風,像漩渦一樣會把她吞沒,吸到深谷底下。
一定要坐上去,她模糊地想。就算只能暫時麻痺也好。
她注意著前面這個男孩的動作,他安靜地吹著泡泡。她猜想他其實很緊張,但他掩飾得很好,她沒有看見他顫抖。他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他的眼睛非常平靜地盯著眼前一根水草末端冒出來的七彩泡泡。泡泡昇到空中,變大,上昇,變得更大,越來越高,然後破掉。就像嘉年華會忽然停頓了似的。
她聽見後面有個女孩對媽媽說:我要去小便。她媽媽毫不猶疑就帶她離開,兩個人再也沒有回來過。
妳應該想辦法和他說說話。說著話的時候,人們就會忘記時間過得多麼慢。妳知道自己無法這麼做,因為只要一開口說話,眼淚就會失控掉下來。
她想,她是在作夢。在夢中,任何不可能的交談都可以進行。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會發生。
「妳好嗎?」男孩忽然轉過頭來問她。
「好,」她轉頭對他微笑。「當然好。」
沉默的遊戲結束了。現在,他們總算先開腔。不管她的口音如何,他們必須要開口對她說話。她伸手摸摸他的頭髮,他沒有抗拒,雖然他到現在還不肯叫她,因為不知應該如何稱呼她:阿姨、阿嬸?
「妳可以不坐,」他說,「假如妳害怕。」
「我不害怕。」
「我媽會害怕,她上次也在出口那裡等我們。」
聽著這話,她不是不驚異的,那個女人,每次都像她這樣嗎?還是她代替了她的位置,變得像她?
「我沒有那麼害怕。」
「如果這火車掉下來 ──」
她安慰他。雖然她一點也不瞭解那種地獄般的狂歡,這整片拆掉後就將只剩沙漠的城堡,此刻正激騰地叫嚷。但她願意說服別人相信那些她希望自己相信的。
「再過一百年都不會掉下來。」
她永遠不會再坐第二次。那種翻轉過來的感覺,整個人被懸掛倒過來,就像垃圾桶被翻過來猛力搖晃,要把裡頭的東西全部倒光似的。她覺得自己的身體被緊緊地吸附在座位上,可是裡頭又有什麼東西要往外飛,就像是有一部分的靈魂要被風斂走。
她無法制止地與其他人一起高聲尖叫,不知喊出「哇」還是「呀」,也無法聽出別人在喊什麼。有一種共振的歡樂像痛苦一樣強烈地盤據了她,如膨脹的海綿般擠壓著她的心臟。
也許她陷入了夢境,也許她曾經昏死過去。一朵白茫茫的雲霧,從鼻子底端昇上來,逐漸擴張,膨脹,直至它完全蓋住她的眼睛。有一瞬間她什麼也看不到,再也看不到那片疾速飛逝的模糊風景。只見到一種光滑的、濃稠的、純淨的白色。那真是一種噁心的空白。它那麼黏膩,分明是什麼都沒有,卻又什麼都容不下,凝滯不動地蹲坐在她頭上,壓著她的臉。無法掙扎,彷彿她已經死了,變成一具無法動彈的屍體,被一團封在蠟裡的奶白物質包裹起來。到這地步她僅能狂喊,憤慨地抽光肺葉裡的空氣,直到有個東西慢慢地沿著咽喉爬上來,她感覺到自己開始嘔吐。
這片覆罩著她眼鼻的空白顏色逐漸變輕、縮小、遠離她的臉,沒有重量、它甚至看來帶著光滑的弧形感。她清楚地看見一顆巨大的、白色的O,從張開的嘴巴裡冒了出來。
兩顆,三顆。她沒辦法數。它們全都冉冉地飄上湛藍無垠的天空。
她想,沒有人看見,她嘔了一連串氣球出來。白色的氣球。
坐在前方的父親自然不會看見。身旁的男孩不曉得究竟是睜開還是閉著眼,在全程中他一直尖叫。嗯,他的確是什麼都沒看見,他在過後對她說:「妳沒有嘔吐。」
男孩迷惑地看著她。她可以讀出藏在他心裡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看吧,妳果然跟我們不一樣。
在他們一起衝出來的剎那,父子三人都立刻張開紙袋,各自往袋子裡大吐特吐。蘇琴記得今天上午,他們在餐廳裡點了漢堡、焗飯、火腿雞排、薯片、冰可樂。當時她根本不想勸阻他們。
他們都低著頭,以類似的抽搐感和節奏,嘔出腸胃裡的雜食所化成的液態。無論是揉著胸口的動作,還是呼氣之後的虛軟模樣,他們看起來都是如此相似,她掏出紙巾給他們,白色的紙巾。她接過那三個裝滿嘔吐物的紙袋時,並非是不噁心的。
不只是因為眼前的孩子都是另一個女人生下的緣故,即使是她自己生下的孩子,也可能會長得更像父親,或更像自己。他們都會成為他的孩子,或者也會成為她的孩子,如果她盡力爭取,如果。如果她到死的時候還愛著他們。他們也許會無可避免地說著和她明顯不同的口音,或者也會逐漸地、一點一滴地愛回她。
但每個人都會離開她。在她死的時候,必然是一個人,孤伶伶地死去。
這個下午真漫長,她覺得自己熬了很久。在遊樂場的另一邊,他們經過一種不停在旋轉的心形大杯子。
「還要玩嗎?」
小孩失措地看她。
蘇琴先走進去,她坐在裡頭等候。她抬起眼睛注視著三父子,她等候著他們的下一步。那個丈夫(那個父親)走過來了,他坐在她旁邊,握緊她的手。
「妳怎麼啦?」他說。「大家都很累了。」
她不理他。她轉頭朝向還呆站在杯子外面的那兩個孩子叫喊:「快點上來,快點。遊樂場要關門囉!」
孩子們立刻爬上來,男的靠向他父親。女孩起初猶疑著不知該坐哪裡。她伸手用力一拉,把女孩拉過來,讓女孩的耳朵貼近自己的心臟。
起初杯子的速度很慢,就像一首悠揚的樂曲。隨後,音樂越來越激昂,杯子就轉得越來越快。蘇琴覺得自己就像被一根看不見的湯匙,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拌攪。他們的鎮靜和防備快速被融化,每個人的嘴巴似乎都被塞進了另一張嘴巴,從那裡吐出了尖銳的叫聲,不屬於任何口音或腔調,共同的叫聲縈繞在遊樂場的上空。
正如蘇琴所想像的那樣。在杯子停下來的時候,他們四個人就像一般正常的家人那樣,緊緊地黏在一起,像四塊融化的方糖。
主題書展
更多
相關商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