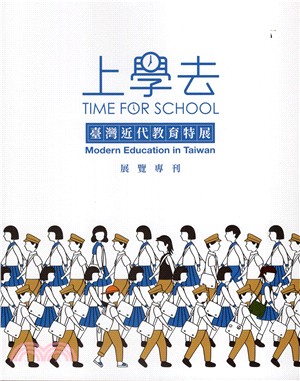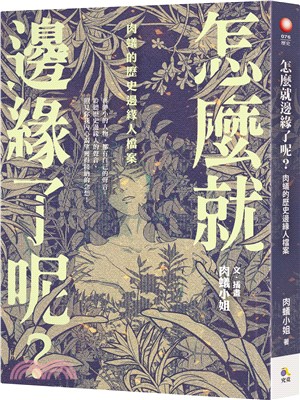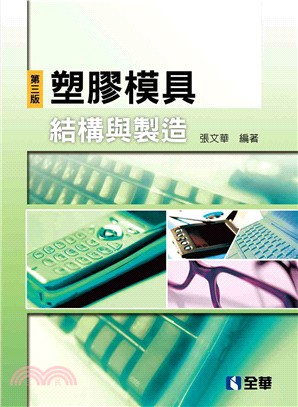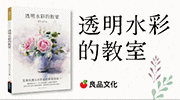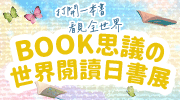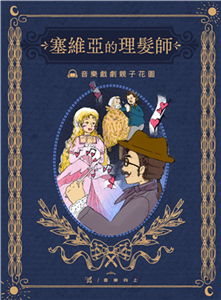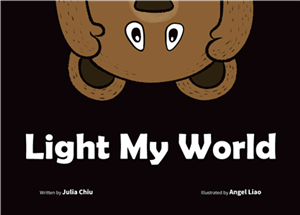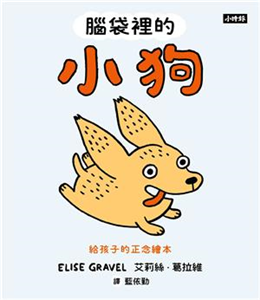翻譯研究新視野(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比較文學名家經典文庫.
ISBN13:9787533463755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謝天振
出版日:2015/01/01
裝訂/頁數:精裝/280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翻譯研究新視野》一書是我國譯介學奠基人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備受注目,人文學科出現了“翻譯轉向”。作為可以滋生很多悖論與理念的領域,翻譯研究涵蓋理解、詮釋、道德、思維和語言的關係以及語際轉換過程中的忠實與叛逆,等等。在本書中,作者以廣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文化洞察,深入探討了上述命題,深化了人們對翻譯的性質與意義以及譯者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的認識和理解
作者簡介
謝天振: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教授、比較文學暨翻譯學博士生導師、國際知名比較文學家與翻譯理論家、中國比較文學譯介學創始人、中國翻譯學學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翻譯學學科建設最有力的宣導者和批評者之一。兼任《中國比較文學》主編、《東方翻譯》執行主編、《中國翻譯》編委、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暨翻譯研究會會長、中國翻譯協會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翻譯委員會委員。
名人/編輯推薦
叢書宣傳語
集結經典
講述一個學科成長的歷程
真正的書寫者,一生也許只為一部書而存在,那是他或她的經典。
那部書將銘刻書寫者獨有的精神姿態,襟懷、學養、持守與求索,那是他或她與此在與永恒的對話。
本著這樣的初衷,我們開始搜求中國比較文學界碩儒時彥們的“那部書”。而這里奉獻的就是我們第一次的收獲。十一位學人,十一部心血結晶,涵蓋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中日古代文學、英國文學與中國文化、俄羅斯文學及其文化、中西比較詩學、女性主義詩學及其在中國的影響、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西方神學詮釋學、儒家經典與詮釋學、翻譯研究等領域,折射出一個學科三十年的恢弘歷程。
時光永是流逝,我們將與真正的書寫者一同尋覓天壤間的那部大書。
目次
國內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認識上的誤區(代前言)
第一章 當代國際譯學研究的最新趨勢
第一節 西方翻譯研究史的回顧與反思
第二節 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三大突破和兩大轉向
第三節 俄羅斯、東歐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
第二章 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第一節 翻譯研究:比較文學立場
第二節 文學翻譯:一種跨文化的創造性叛逆
第三節 翻譯:文化意象的失落與歪曲
第四節 誤譯:不同文化的誤解與誤釋
第三章 翻譯文學新概念
第一節 翻譯文學:爭取承認的文學
書摘/試閱
(代前言·節選)
謝天振
最近一二十年來,我國的翻譯研究取得了較大進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國的翻譯研究中翻譯研究的理論意識已經覺醒,這不僅反映在近年來發表在《中國翻譯》和《外國語》等雜志和有關學報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國內出版界近年來推出的好幾套頗具規模的翻譯研究叢書上。其中,湖北教育出版社最近接連推出的兩套頗具規模的翻譯研究叢書――“中華翻譯研究叢書”和“外國翻譯理論研究叢書”[1]以及一套全面展示翻譯家的創作風采的《巴別塔文叢》[2]。前兩套叢書不僅對近幾十年來英美法蘇的翻譯理論進展作了相當詳盡的評介,而且還進一步推出了國內學者自身對翻譯理論的思考。而后一套叢書,即《巴別塔文叢》,則把翻譯家譯作以外的文章匯編成集,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集中展示了翻譯家作為創作者的一面。此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青島出版社等近年來也不斷有新的譯學理論著述推出。這表明,我國學術界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支譯學研究隊伍,譯學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氣候。
然而,與此同時,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是,盡管上述譯學進展在學術界引起學者們的欣喜,但這種進展相當長時期以來還只是局限在一個并不很大的學者圈子內,并沒有在我國的翻譯界(遑論整個學術界)引起較為普遍和熱烈的反應。比較多的翻譯界人士對近年來我國譯學研究上所取得的進展取一種比較冷漠的態度,在他們看來,譯學研究,或者說得更具體些,翻譯的理論研究,與他們沒有什么關系。長期以來,我國的翻譯界有一種風氣,認為翻譯研究都是空談,能夠拿出好的譯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國翻譯界有不少翻譯家頗以自己幾十年來能夠譯出不少好的譯作、卻并不深入翻譯研究或不懂翻譯理論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為榮,而對那些寫了不少翻譯研究的文章卻沒有多少出色譯作的譯者,言談之間就頗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風氣所及,甚至連一些相當受人尊敬的翻譯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翻譯家就這樣說過:“翻譯重在實踐,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為苦。文藝理論家不大能兼作詩人或小說家,翻譯工作也不例外: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譯東西卻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為戒。”[3]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況,我覺得這與我國翻譯界在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的認識上存在的三個誤區有關。
第一個誤區是把對“怎么譯”的研究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的全部。
應該說,這樣的認識誤區并不局限于中國翻譯界,它在中外翻譯界都有相當的普遍性。事實上,回顧中外兩千余年的翻譯史,我們一直都把圍繞著“怎么譯”的討論誤認為是翻譯研究、甚至是翻譯理論的全部。從西方翻譯史上最初的“直譯”“意譯”之爭,到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到前蘇聯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關譯論;從我國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依實出華”“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來的“信達雅”“神似”“化境”說,等等,幾乎都是圍繞著“怎么譯”這三個字展開的。但是,如果我們冷靜想一想的話,我們當能發現,實際上“怎么譯”的問題,對西方來說,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已經基本解決了,對我們中國而言,至遲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決。目前大量存在的關于“怎么譯”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大多是個人翻譯實踐的體會和經驗總結,它們也許能提供一些新的翻譯實例和個案,但很少也很難再有理論層面上的創新和突破。因此,時至今日,如果我們仍然一昧停留在“怎么譯”問題的討論上,我們的翻譯研究、尤其是譯學研究恐怕就難以取得大的、實質性的進展。前些年,已故王佐良教授曾在一次專題翻譯討論會上說過這樣一番話:“嚴復的歷史功績不可沒。‘信、達、雅’是很好的經驗總結,說法精練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但時至今日,仍然津津于這三字,則只能說明我們后人的停頓不前。”[4]王教授這番話的用意,我想決不是要否定嚴復“信、達、雅”三字的歷史功績,而是希望我們后人能在翻譯研究上有所突破。
同樣,不無必要說明一下的是,我們提出不要一昧停留在“怎么譯”問題的討論上,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要或反對研究“怎么譯”的問題。其實,“怎么譯”的問題今后仍然會繼續討論下去的,而且仍將在我們的翻譯研究中占據相當大的比例,這與翻譯這門學科的技術性和操作性比較突出這一特點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呼吁不要一昧停留在“怎么譯”的問題上,主要著眼于學術層面,是希望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研究者們能看到這個問題所包含的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方面是翻譯家們對翻譯技巧的研究和探討,這是翻譯家們的翻譯實踐的體會和經驗總結,其中有些經驗也已經提升到理論層面,有相當的價值,從而構成了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內容則是一些已經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只不過是更換了一些新的實例而已,缺少學術價值,像這樣的內容也許放到外語教學的范疇里,去對初譯者、對外語學習者談,更為合適。因為對這些人來說,“怎么譯”的問題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因此仍然是一個新鮮的、有意義的問題。而對譯學界來說,也許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跳出狹隘的單純的語言轉換層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從廣闊的文化層面上去審視翻譯,去研究翻譯,這樣對中國譯學理論的建設也許會更有意義。
我國翻譯界在對翻譯研究和翻譯理論的認識上存在的第二個誤區是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片面強調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以為凡是理論,就應該對指導實踐有用,所謂“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所謂“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指導人們的行動”。否則,就被譏之為“脫離實際”,是無用的“空頭理論”。對理論的這種實用主義認識,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的各行各業,當然也包括翻譯界,都已經被普遍接受,并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于是,當我們一談到理論,人們第一個反應就是:你這個理論對我的實踐有用嗎?在翻譯界,人們的反應就是:你搞的翻譯理論對提高我的翻譯水平有用嗎?有人就說:“譯家不可能因為掌握了現有的任何一套翻譯理論或遵循了以上任何一套翻譯原則,其翻譯水準就會有某種質的飛躍。……如今我國譯林之中的后起之秀,可謂人才濟濟,無論他們用什么翻譯理論武裝自己,無論他們對翻譯的過程、層次有多透徹的認識,無論他們對翻譯美學原理如何精通,無論他們能把讀者分成多少個層次從而使其翻譯更加有的放矢,也無論他們能用理論界最近發明的三種機制、四種轉換模式把翻譯中的原文信息傳遞得如何有效,他們的譯作會比傅雷的高明多少呢?霍克思(David Hawks)與閔福德(John Minford),雖然是西方人士(后者還曾是筆者所在學系的翻譯講座教授),從來就不信什么等值、等效論,他們憑著深厚的語言功底和堅強的毅力,也‘批閱十載’,完成了《紅樓夢》的翻譯。在眾多的英文版《紅樓夢》中,他們的譯作出類拔萃,在英美文學翻譯界堪稱一絕。霍克思在他寫的翻譯后記一書中也沒有提到任何時髦的翻譯理論,但東西方翻譯界和翻譯理論界仍然為其譯作而折服。由此可見,翻譯理論與譯作的質量并沒有必然的關系。”[5]還有一位自稱“在二十世紀出版了五十多部中英法互譯作品的譯者”也聲稱:“從實踐上講,西方的‘純理論’對我完全無用。”[6]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我國翻譯界對譯學理論的認識也往往強調“來自個人的翻譯實踐”。在相當多人的潛意識中,總認為只有自身翻譯實踐過硬的人才有資格談翻譯理論,否則就免開尊口。其實,隨著學科的深入發展和分工日益精細,文藝理論家不能兼作詩人、小說家,就象詩人、小說家不能兼作文藝理論家一樣(個別人兼于一身的當然也有,但那屬特例),是很正常的現象。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原不必苛求。同理,翻譯實踐水平很高明的翻譯家未必能談出系統的翻譯理論來,反之,談翻譯理論頭頭是道的翻譯理論家卻未必有很高的翻譯實踐水平,同樣不足為怪。我們有些翻譯家,對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希望自己既能“寫翻譯理論頭頭是道,非常中肯”,又能“譯東西高明”,這當然令人欽佩。以此標準律已,精神可嘉,無可非議,但若以此標準求諸他人,甚至求諸所有談論或研究翻譯的人,那就顯得有點苛求,甚至不合情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文學創作界,從來沒有聽說有哪位作家對文學批評家或理論家說,“我不懂什么文藝理論,我不是照樣寫出不錯的小說來了嗎?”更沒有哪位學者或大學教師對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含譏帶諷地說:“我們的文藝學科的建設不是靠你們這些空頭理論文章,而是靠我們的作家的創作。”在語言學界,也從不曾聽說有人對語言學家興師問罪:“我從來不讀你們的語言學著作,我說話不照樣也很好。你們這種語言學理論對我有何用?”創作了眾多不朽世界經典著作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文學大師,他們其實也沒有提到過他們的創作受惠于何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但這是否就可以成為我們否定丹納、否定別、車、杜或任何其他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理由呢?任何一門學科,如果只有實踐而沒有理論的提升和總結,它能確立和發展起來嗎?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在我國翻譯界的某些人眼中竟然成了謬論,這只能說是中國譯學的悲哀。我國古代文論家袁枚就說過:“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后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7]由此可見,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在某一方面有所特長的話,很可能就會在另一方面有所缺失。譬如,有些人抽象思維比較發達,談起翻譯理論來自然就會“頭頭是道”,而有些人則形象思維比較發達,語言文字修養比較出色,于是文學翻譯的水平就比較高。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應該相互寬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岐視。這樣,我們的翻譯事業才會發達。
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后果:首先是局限了翻譯理論的范圍,把翻譯理論僅僅理解為對“怎么譯”的探討,也即僅僅局限在應用性理論上。
翻譯理論、尤其是傳統的翻譯理論,確實有很大一部分內容一直局限在探討“怎么譯”的問題上,也即所謂的應用性理論上。但是,即使如此,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也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怎么譯”以外的一些問題,如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國語言學家Wilhelm von Humboldt (洪堡)對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就有過相當精辟的闡述:他一方面指出各種語言在精神實質上是獨一無二的,在結構上也是獨特的,而且這些結構上的特殊性無法抹殺,因而翻譯原則上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任何語言中,甚至不十分為我們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語言中,任何東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強的、最弱的東西,都能加以表達。”[8]再如Walter Benjamin(沃爾特·本雅明)還在1923年就已經指出,“翻譯不可能與原作相等,因為原作通過翻譯已經起了變化”。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既然翻譯是自成一體的文學樣式,那么譯者的工作就應該被看作詩人(按:實泛指一切文學創作者)工作的一個獨立的、不同的部分。”[9] Benjamin的話深刻地揭示了文學翻譯的本質,并給了文學翻譯一個十分確切的定位。這些話至今仍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
對翻譯理論的實用主義態度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把理論的功能簡單化了,使人們以為似乎理論只具有指導實踐的功能。其實,理論,包括我們所說的翻譯理論,除了有指導實踐的功能以外,它還有幫助我們認識實踐的功能。辭海中“理論”詞條在“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指導人們的行動。”前面還有這么一段話:“(理論是)概念、原理的體系,是系統化了的理性認識。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并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性的正確反映。”這就點出了理論的認識功能,即幫助人們理性地認識客觀事物,包括人們的實踐。這就象語言學理論一樣,語言學理論的研究雖然不能直接提高人們的說話和演講水平,但卻能深化人們對語言的認識。
這里我們也許還可舉一個譯學研究以外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我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中曾經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國譯界的某些人看來,恐怕也難逃“空頭理論文章”的“惡謚”,因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沒有管理過一個企業、鄉鎮、城市,也沒有管理過整個國家的經歷,更遑論有何“業績”。套用到翻譯界來的話,也即此人既沒有翻譯的實踐,翻譯水平也乏善可陳。但眾所周知,盡管這篇文章沒有具體闡述如何管理廠礦企業,如何治理城市國家,但正是這篇文章改變了我們對向來深信不疑的“兩個凡是”的盲從,從而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理論的認識作用及其巨大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翻譯理論在某種程度上也與之相仿。譬如George Steiner(斯坦納)在《通天塔》一書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譯”的觀點,認為“每當我們讀或聽一段過去的話,無論是《圣經》里的‘列維傳’,還是去年出版的暢銷書,我們都是在進行翻譯。讀者、演員、編輯都是過去的語言的翻譯者。……總之,文學藝術的存在,一個社會的歷史真實感,有賴于沒完沒了的同一語言內部的翻譯,盡管我們往往并不意識到我們是在進行翻譯。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我們的文明,就因為我們學會了翻譯過去的東西。”[10]這樣的觀點不僅擴大了、同時也深化了我們對翻譯的認識。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