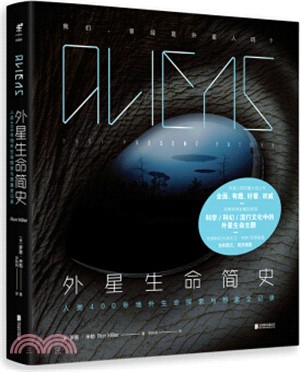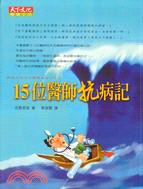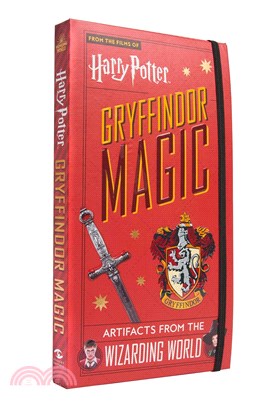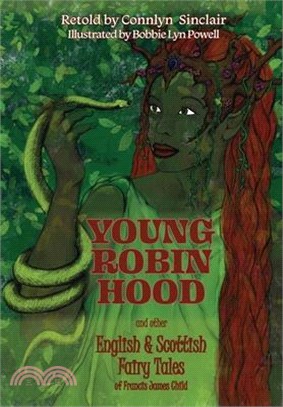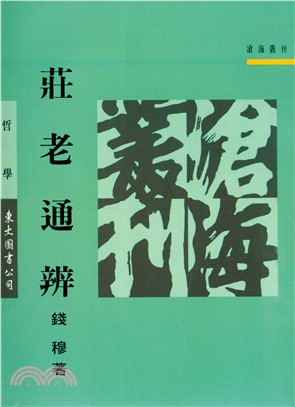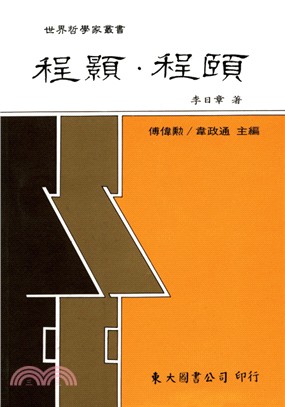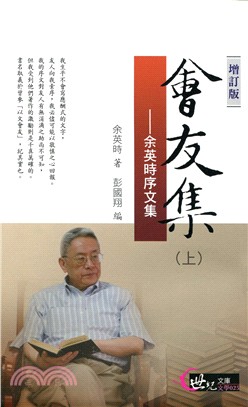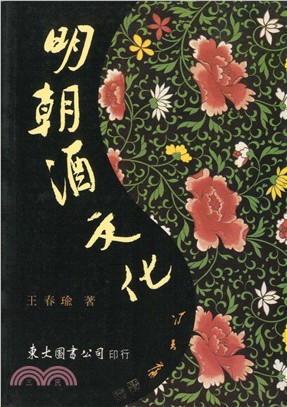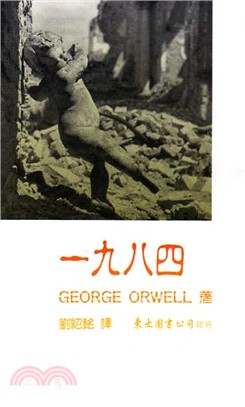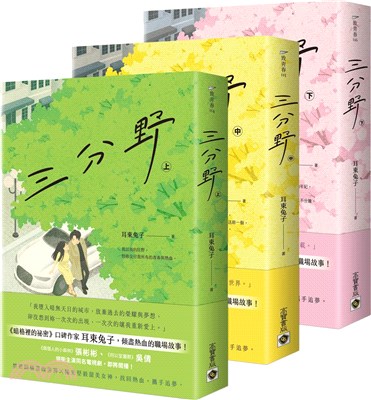夢的隕落
商品資訊
定價
:NT$ 250 元優惠價
:90 折 225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6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特色
● 邵氏臺灣名導潘壘的小說著作!
● 從潘壘親身經歷的愛情中改寫而成的淒美故事。
● 全書不只塑造了一個深具緬甸風情的女孩,也塑造了在時代悲劇下一再失落的癡情男子。
內容簡介
潘十五年來心心念念的,是當年在中緬邊境作戰時,認識的緬甸少女瑪愛耶。即使戰後被共軍擄獲,承受了將近十四年的勞改監禁,想見少女的慾望支持著他,撐過了那段非人生活。
他趁機逃了出來。輾轉流落香港後,一存夠了錢,他就不顧一切奔向緬甸邁加,想要回到瑪愛耶居住的村落,找到那嬌小甜美的愛人,牽起她的手,永遠陪在她身邊。
這樣的想望焦灼著他,但世界仍然在戰爭的陰影下,中緬印之間的戰火在地下隱隱交鋒,踏上了久違的國度,命運依然嘲弄著他……
潘壘運用自身在東南亞流連的經歷,成功塑造了一段真摯執著的愛情故事;同時亦成功地將緬甸邊境鄉村的純樸與風情,透過這個故事渲染而出,體驗那帶著熱帶異國風情的美好感動。
追逐著過去,主角夢想著再次見到愛人的美好的畫面,但這終究是夢,隔了十五年的夢。遲來的追尋,等到的,也只有令人惆悵的隕落。
作者簡介
潘壘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生於越南海防市。一九四九年來台,獨資創辦台灣光復後第一本文學雜誌──《寶島文藝》月刊。一九五二年起,全心投入小說創作,出版了《紅河三部曲》、《魔鬼樹》、《歸魂》、《狹谷》、《安平港》等二十三本暢銷著作,為台灣五○年代的文壇巨擘。其中多本著作被改編為電影登上大銀幕;長篇巨著《魔鬼樹》更在一九七二年被華視改編為連續劇,紅極一時。
一九六○年代進入「中影製片部」編導組,自此投身電影界編寫劇本。一九六三年受邀進入香港「邵氏」,是邵氏四大文藝導演之一,更被譽為保守年代最勇於創新的作家導演。七○至八○年代已編導過四十三部電影,合作過的演員有唐寶雲、鄭佩佩、王羽、李烈、柯俊雄、張美瑤、龍君兒、胡燕妮、胡茵夢等港台兩地知名巨星演員。
一九六二年以《一萬四千個證人》獲得第一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同年再以《颱風》一片代表台灣參加「亞洲影展」,揚威海外;一九六四年以《情人石》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入圍肯定。其他電影代表作還有《金色年代》、《蘭嶼之歌》、《毒玫瑰》、《落花時節》、《新不了情》、《紫貝殼》、《天下第一劍》等片。
二○一四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了《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訴說這位縱橫文壇、馳騁影壇的傳奇人物!
潘壘身為作家兼導演,其創作的小說或電影,不論在哪個年代都堪稱跨時代的經典之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生於越南海防市。一九四九年來台,獨資創辦台灣光復後第一本文學雜誌──《寶島文藝》月刊。一九五二年起,全心投入小說創作,出版了《紅河三部曲》、《魔鬼樹》、《歸魂》、《狹谷》、《安平港》等二十三本暢銷著作,為台灣五○年代的文壇巨擘。其中多本著作被改編為電影登上大銀幕;長篇巨著《魔鬼樹》更在一九七二年被華視改編為連續劇,紅極一時。
一九六○年代進入「中影製片部」編導組,自此投身電影界編寫劇本。一九六三年受邀進入香港「邵氏」,是邵氏四大文藝導演之一,更被譽為保守年代最勇於創新的作家導演。七○至八○年代已編導過四十三部電影,合作過的演員有唐寶雲、鄭佩佩、王羽、李烈、柯俊雄、張美瑤、龍君兒、胡燕妮、胡茵夢等港台兩地知名巨星演員。
一九六二年以《一萬四千個證人》獲得第一屆金馬獎優等劇情片;同年再以《颱風》一片代表台灣參加「亞洲影展」,揚威海外;一九六四年以《情人石》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並獲入圍肯定。其他電影代表作還有《金色年代》、《蘭嶼之歌》、《毒玫瑰》、《落花時節》、《新不了情》、《紫貝殼》、《天下第一劍》等片。
二○一四年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出版了《不枉此生──潘壘回憶錄》(左桂芳編著),訴說這位縱橫文壇、馳騁影壇的傳奇人物!
潘壘身為作家兼導演,其創作的小說或電影,不論在哪個年代都堪稱跨時代的經典之作!
目次
總序 無擾為靜,單純最美/宋政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書摘/試閱
一
又是春天了。
在香港,春天給我的感覺是很微弱的。這也許是由於這十多年苦難的生活,逐漸增長的年歲,使我對人生變得冷漠的緣故;可是,當我想起了瑪愛耶,我才醒悟,這一段冗長而悲慘的地獄生涯,反而使我對她的愛更執著。年歲的增長,竟將我的熱情和戀慕,濾得像深谷的清流一樣,澄淨而甘淳。但,春天,我的春天永遠是感傷的,因為我離開瑪愛耶的時候,正是多愁的早春。
計算起來,已經整整十五個年頭了,而我從未忘記過她。時間,加濃了我對她的思念,使我的記憶愈加清晰──她那嬌小的、顯得略微有點瘦弱的身體,一身緬甸少女素靜的裝束,頭頂的小髮髻,迷惘而含愁的眼睛,那令我心碎的微笑;我只要閉起眼睛,幾乎還能異常清晰地看見,那飄在小小的耳朶後面的短髮,以及嘴角因微笑而顯露出的細細的皺紋……。
我時常這樣想:假如那天晚上她並沒有隨著村人來參加我們的晚會,或者她並沒有獨自到我的帳篷裡來,而且,如果那天晚上我並沒有喝酒的話,那麼,我可能是恨她的。雖然我知道那種恨是出於強烈的愛,但,至少這個悲劇便不會發生了。
這就是命運!它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它使我在一種迷亂的激情中得到了瑪愛耶,但隨即又迫使我們離開,永遠失去了她。
其實,假如我能像其他的人一樣,把初戀視為生命的點綴的話,那麼一切都改變了!可是我不能,分離之後,我愈來愈感覺到我是多麼需要她,即使是十五年後的今天,我這種慾望仍然是那麼強烈;為了要再見到她,我忍受著飢餓和恥辱,掙扎著活下去!
每當我因現實的挫折而感到絕望的時候,我似乎便可以聽到她的聲音──發自一個遙遠的地方而非常清晰的聲音:
「你不會再回來了!你不會再回來了!」
那天晚上,當劉錚他們從營地趕到村子裡來,告訴我部隊在明天清晨出發的消息之後,我便問過自己:我還會回來嗎?
說實話,當時我有點惘然。在戰爭期間,要一個間接負有作戰任務的士兵──一個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去回答這一個問題,毋寧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記得,當時瑪愛耶從屋子裡走出來,疑惑不安地望著劉錚。於是,我低聲對劉錚說:
「你先回去吧,我馬上就來!」
劉錚走了之後,瑪愛耶突然驚惶地捉往我的手,我感覺到她的手冰冷。
「是什麼事?」她低促地用緬甸話問我。當她快樂或者是生氣的時候,不管我聽不聽得懂,她總是和我說緬甸話的。
我能告訴什麼呢?我只默默地凝望著她。屋子裡的燈光,從後面落在她的身上──一個夢樣的輪廓。半晌,她嘶啞地問:「你們要走了?」那聲音好像並不是由她發出的,有點顫抖。
為了避開她的眼睛,我緊緊地抱著她。「瑪愛耶!」我深情地喊著她的名字:「瑪愛耶!」
她開始痛心地哭泣起來了。她的哭聲使我感到紛亂,於是,我努力找些我能說而她易於了解的字句勸慰道:
「瑪愛耶!你聽我說,現在是打仗,我是兵,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捧起她的臉,繼續說:「等到把日本人打走了,我會回來的!」
她淒苦無助地搖著頭。「你不會再回來了!」她重複地唸著:「你不會再回來了!」
「妳為什麼不相信我呢?」我搖撼著她說。
「我相信!我相信!」她含糊地喊道:「可是,什麼時候你才能夠回來呢?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絕對不會想到,這次分別竟然使我無法再回到她的身邊去。
後來,中印公路終於打通了,中國駐印軍隨即回國援救國內的危局,而戰爭就在那年的秋天結束了。那個時候,我們的部隊駐屯在廣州,當時我們的那份狂喜和激動是可以想見的,我們每個人都在計劃著復員之後的事情,幸福似乎已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但,我卻沒有想到回家,雖然我離開越南(從祖父那一代開始,我們僑居在海防)已經有六年多了。當時我只有一個意念:脫下軍服,便立刻到緬甸去,我要娶瑪愛耶,然後把她帶回國,再繼續讀完我的醫科。我認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我的,而且從離開她的那天開始,我已經儲蓄了一筆數目不算少的旅費,同時以結婚這個理由,我還可以向家中要一點錢。
可是,當我們朝夕盼望著復員令,開始對軍隊生活感到憎惡和厭倦的時候,危機已經在人們對和平的迷醉與歡狂時偷偷地醞釀著,在陰謀者的策動下,一個可詛咒的新的戰爭終於在北方和政府所忽略的角落裡爆發了,我們隨即被空運到東北去增援……
悲劇就這樣形成了。
經過兩個月的苦戰,我們的部隊終於被持有俄式槍械的共軍所擊潰,惶亂中我曾經和一些同伴逃亡,我們化了裝,晝宿夜行,挨盡了艱苦,但不幸在最後的一段路程裡,我們被一支土共部隊俘獲了。從此,在十三年另七個月的時間裡,我們過著中古世紀奴隸式的非人生活。
如同是一個永不甦醒的噩夢,想到它就會使我渾身顫抖。直到去年的初夏,我抓住了一個偶然的(只有一個經過長期囚禁的人,才會相信一切逃亡的計劃都是沒有希望的)機緣,逃過了邊界。當我的腳踏著溫暖的泥土,呼吸到芬芳的自由的空氣時,我才能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我才意識到,我已經是一個疲乏、消沉、帶點神經質的中年人!唯一不變的,只有我對瑪愛耶的愛心──它是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如同瑪愛耶的形象,在我那被相思的濃情所包裡的心靈裡,她仍然是一個嬌小的楚楚可憐的女孩子。
在香港街頭流浪的第三天,我竟於無意間(因為是他先發現我的)遇見醫學院時期教藥物學的老教授,經過短短的談話,他帶我到他在九龍開設的診所裡去。
最初的三個月裡,我是他的病人,然後便變成了他的助手。他是個孤獨的人,我記得在學校裡時他並不怎樣喜歡我,原因是我的功課並不好;其實,做醫生並不是我的志願,我從小便以為自己將來會為一個畫家,或者像父親一樣,是一個生活在海上的人。但,理想、抱負、那些美麗的憧憬和幻夢,都離我而去了。尤其是當我明白越南的老家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土地已經割讓給越共時,我連最後的一點點熱情都消失掉了。我曾經為這件事悲傷了很久,我不知道家中的人是否已經撤到南越去,是否安然無恙;總之,我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老教授曾經勸慰我,一邊託人替我在西貢打聽家人的消息。等到孱弱的身體和疲憊的心靈漸漸恢復過來之後,我要去見瑪愛耶的慾望亦漸漸加強了,但這是一個秘密,我從沒有向老教授透露過,我一方面是害怕他會恥笑我的癡心,同時我不願意讓任何人分享我回憶瑪愛耶時心中所升起的快樂。
做一個內科醫生的助手,工作是相當輕鬆的。老教授堅持著要給一份薪金,我只好依從他,不過,我把它全部積存在他那裡。整整十個月,除了到旅行社去打聽消息,我幾乎沒有離開過診所。
當應診的規定時間過了之後,我便把自己留在診所後面的小房間裡,研讀老教授為我指定的功課,同時為一份綜合雜誌翻譯一些短篇文稿。
直至有一天,當老教授看完最後一個病人,正要準備離開診所時,我用一種微微有點激動的聲音叫住他:
「嚴教授,我有一件事……」
他回過身來,睜睜地望著我。他那孕滿憐愛的目光使我變得有點拘束。
「我們坐下來談吧!」他把帽子掛回衣架上,然後溫和地向我說。
坐下之後,看見我始終沒有開口,於是他問:「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我緩緩地抬起頭:「我……我要走了!」
「走!到那裡去?」他詫異起來。
「緬甸!」我簡短地回答。
「哦!你已經和家裡連絡上了!」
我搖搖頭,露出一絲苦笑。「去看另外一個人。」我低聲說:「一個緬甸女孩子!」
他的眼睛漸漸瞇起來,眼鏡的玻璃片上又映出發光的百葉窗,像是整理了一下思緒,他說:「你告訴過我的,你以前在緬甸打過仗。」
「十五年前。」我補充道。
「你們一直有聯絡嗎?」
「沒有!」
他頓了一下,一絲深摯的微笑開始從他那滿佈皺紋的嘴角流露了出來。
「你認為有這個必要嗎?」他探詢地問道。從他的語氣裡,我聽到另外一種意義。但我平靜地說:
「在大陸上,我沒有死,而且還逃出來,大概就是為了要見她吧!」
「那很好!」他向我轉過身來,按著我的手說:「你應該去看她!要不然你會追悔一生的!」
我忽然敏感地想到,他始終過著獨身生活的原因──但他已經繼續說話了:
「你存在我這裡的錢不夠的。」
「我還有一些稿費。」
他點點頭,回復原來的姿勢。「你已經打聽過了?」
「嗯,」我回答:「我幾乎每半個月就打聽一次,大後天就有一條船……」
「你要坐船去?」他打斷了我的話。
「坐船比較省錢,而且經過越南的時候,我就等於回過一次家了!」
「其他的手續呢?」
我愧疚地把我已經偷偷地辦妥了出境護照和簽證這回事告訴他,同時,也述明了今後的計劃。他非但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反而極力鼓勵我。最後,他還摯切地說:「你馬上就去訂船票吧!我會盡我的能力幫助你的!」
又是春天了。
在香港,春天給我的感覺是很微弱的。這也許是由於這十多年苦難的生活,逐漸增長的年歲,使我對人生變得冷漠的緣故;可是,當我想起了瑪愛耶,我才醒悟,這一段冗長而悲慘的地獄生涯,反而使我對她的愛更執著。年歲的增長,竟將我的熱情和戀慕,濾得像深谷的清流一樣,澄淨而甘淳。但,春天,我的春天永遠是感傷的,因為我離開瑪愛耶的時候,正是多愁的早春。
計算起來,已經整整十五個年頭了,而我從未忘記過她。時間,加濃了我對她的思念,使我的記憶愈加清晰──她那嬌小的、顯得略微有點瘦弱的身體,一身緬甸少女素靜的裝束,頭頂的小髮髻,迷惘而含愁的眼睛,那令我心碎的微笑;我只要閉起眼睛,幾乎還能異常清晰地看見,那飄在小小的耳朶後面的短髮,以及嘴角因微笑而顯露出的細細的皺紋……。
我時常這樣想:假如那天晚上她並沒有隨著村人來參加我們的晚會,或者她並沒有獨自到我的帳篷裡來,而且,如果那天晚上我並沒有喝酒的話,那麼,我可能是恨她的。雖然我知道那種恨是出於強烈的愛,但,至少這個悲劇便不會發生了。
這就是命運!它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它使我在一種迷亂的激情中得到了瑪愛耶,但隨即又迫使我們離開,永遠失去了她。
其實,假如我能像其他的人一樣,把初戀視為生命的點綴的話,那麼一切都改變了!可是我不能,分離之後,我愈來愈感覺到我是多麼需要她,即使是十五年後的今天,我這種慾望仍然是那麼強烈;為了要再見到她,我忍受著飢餓和恥辱,掙扎著活下去!
每當我因現實的挫折而感到絕望的時候,我似乎便可以聽到她的聲音──發自一個遙遠的地方而非常清晰的聲音:
「你不會再回來了!你不會再回來了!」
那天晚上,當劉錚他們從營地趕到村子裡來,告訴我部隊在明天清晨出發的消息之後,我便問過自己:我還會回來嗎?
說實話,當時我有點惘然。在戰爭期間,要一個間接負有作戰任務的士兵──一個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去回答這一個問題,毋寧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記得,當時瑪愛耶從屋子裡走出來,疑惑不安地望著劉錚。於是,我低聲對劉錚說:
「你先回去吧,我馬上就來!」
劉錚走了之後,瑪愛耶突然驚惶地捉往我的手,我感覺到她的手冰冷。
「是什麼事?」她低促地用緬甸話問我。當她快樂或者是生氣的時候,不管我聽不聽得懂,她總是和我說緬甸話的。
我能告訴什麼呢?我只默默地凝望著她。屋子裡的燈光,從後面落在她的身上──一個夢樣的輪廓。半晌,她嘶啞地問:「你們要走了?」那聲音好像並不是由她發出的,有點顫抖。
為了避開她的眼睛,我緊緊地抱著她。「瑪愛耶!」我深情地喊著她的名字:「瑪愛耶!」
她開始痛心地哭泣起來了。她的哭聲使我感到紛亂,於是,我努力找些我能說而她易於了解的字句勸慰道:
「瑪愛耶!你聽我說,現在是打仗,我是兵,這是沒有辦法的!」我捧起她的臉,繼續說:「等到把日本人打走了,我會回來的!」
她淒苦無助地搖著頭。「你不會再回來了!」她重複地唸著:「你不會再回來了!」
「妳為什麼不相信我呢?」我搖撼著她說。
「我相信!我相信!」她含糊地喊道:「可是,什麼時候你才能夠回來呢?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絕對不會想到,這次分別竟然使我無法再回到她的身邊去。
後來,中印公路終於打通了,中國駐印軍隨即回國援救國內的危局,而戰爭就在那年的秋天結束了。那個時候,我們的部隊駐屯在廣州,當時我們的那份狂喜和激動是可以想見的,我們每個人都在計劃著復員之後的事情,幸福似乎已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但,我卻沒有想到回家,雖然我離開越南(從祖父那一代開始,我們僑居在海防)已經有六年多了。當時我只有一個意念:脫下軍服,便立刻到緬甸去,我要娶瑪愛耶,然後把她帶回國,再繼續讀完我的醫科。我認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我的,而且從離開她的那天開始,我已經儲蓄了一筆數目不算少的旅費,同時以結婚這個理由,我還可以向家中要一點錢。
可是,當我們朝夕盼望著復員令,開始對軍隊生活感到憎惡和厭倦的時候,危機已經在人們對和平的迷醉與歡狂時偷偷地醞釀著,在陰謀者的策動下,一個可詛咒的新的戰爭終於在北方和政府所忽略的角落裡爆發了,我們隨即被空運到東北去增援……
悲劇就這樣形成了。
經過兩個月的苦戰,我們的部隊終於被持有俄式槍械的共軍所擊潰,惶亂中我曾經和一些同伴逃亡,我們化了裝,晝宿夜行,挨盡了艱苦,但不幸在最後的一段路程裡,我們被一支土共部隊俘獲了。從此,在十三年另七個月的時間裡,我們過著中古世紀奴隸式的非人生活。
如同是一個永不甦醒的噩夢,想到它就會使我渾身顫抖。直到去年的初夏,我抓住了一個偶然的(只有一個經過長期囚禁的人,才會相信一切逃亡的計劃都是沒有希望的)機緣,逃過了邊界。當我的腳踏著溫暖的泥土,呼吸到芬芳的自由的空氣時,我才能清清楚楚地看見自己,我才意識到,我已經是一個疲乏、消沉、帶點神經質的中年人!唯一不變的,只有我對瑪愛耶的愛心──它是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如同瑪愛耶的形象,在我那被相思的濃情所包裡的心靈裡,她仍然是一個嬌小的楚楚可憐的女孩子。
在香港街頭流浪的第三天,我竟於無意間(因為是他先發現我的)遇見醫學院時期教藥物學的老教授,經過短短的談話,他帶我到他在九龍開設的診所裡去。
最初的三個月裡,我是他的病人,然後便變成了他的助手。他是個孤獨的人,我記得在學校裡時他並不怎樣喜歡我,原因是我的功課並不好;其實,做醫生並不是我的志願,我從小便以為自己將來會為一個畫家,或者像父親一樣,是一個生活在海上的人。但,理想、抱負、那些美麗的憧憬和幻夢,都離我而去了。尤其是當我明白越南的老家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的土地已經割讓給越共時,我連最後的一點點熱情都消失掉了。我曾經為這件事悲傷了很久,我不知道家中的人是否已經撤到南越去,是否安然無恙;總之,我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
老教授曾經勸慰我,一邊託人替我在西貢打聽家人的消息。等到孱弱的身體和疲憊的心靈漸漸恢復過來之後,我要去見瑪愛耶的慾望亦漸漸加強了,但這是一個秘密,我從沒有向老教授透露過,我一方面是害怕他會恥笑我的癡心,同時我不願意讓任何人分享我回憶瑪愛耶時心中所升起的快樂。
做一個內科醫生的助手,工作是相當輕鬆的。老教授堅持著要給一份薪金,我只好依從他,不過,我把它全部積存在他那裡。整整十個月,除了到旅行社去打聽消息,我幾乎沒有離開過診所。
當應診的規定時間過了之後,我便把自己留在診所後面的小房間裡,研讀老教授為我指定的功課,同時為一份綜合雜誌翻譯一些短篇文稿。
直至有一天,當老教授看完最後一個病人,正要準備離開診所時,我用一種微微有點激動的聲音叫住他:
「嚴教授,我有一件事……」
他回過身來,睜睜地望著我。他那孕滿憐愛的目光使我變得有點拘束。
「我們坐下來談吧!」他把帽子掛回衣架上,然後溫和地向我說。
坐下之後,看見我始終沒有開口,於是他問:「你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我緩緩地抬起頭:「我……我要走了!」
「走!到那裡去?」他詫異起來。
「緬甸!」我簡短地回答。
「哦!你已經和家裡連絡上了!」
我搖搖頭,露出一絲苦笑。「去看另外一個人。」我低聲說:「一個緬甸女孩子!」
他的眼睛漸漸瞇起來,眼鏡的玻璃片上又映出發光的百葉窗,像是整理了一下思緒,他說:「你告訴過我的,你以前在緬甸打過仗。」
「十五年前。」我補充道。
「你們一直有聯絡嗎?」
「沒有!」
他頓了一下,一絲深摯的微笑開始從他那滿佈皺紋的嘴角流露了出來。
「你認為有這個必要嗎?」他探詢地問道。從他的語氣裡,我聽到另外一種意義。但我平靜地說:
「在大陸上,我沒有死,而且還逃出來,大概就是為了要見她吧!」
「那很好!」他向我轉過身來,按著我的手說:「你應該去看她!要不然你會追悔一生的!」
我忽然敏感地想到,他始終過著獨身生活的原因──但他已經繼續說話了:
「你存在我這裡的錢不夠的。」
「我還有一些稿費。」
他點點頭,回復原來的姿勢。「你已經打聽過了?」
「嗯,」我回答:「我幾乎每半個月就打聽一次,大後天就有一條船……」
「你要坐船去?」他打斷了我的話。
「坐船比較省錢,而且經過越南的時候,我就等於回過一次家了!」
「其他的手續呢?」
我愧疚地把我已經偷偷地辦妥了出境護照和簽證這回事告訴他,同時,也述明了今後的計劃。他非但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反而極力鼓勵我。最後,他還摯切地說:「你馬上就去訂船票吧!我會盡我的能力幫助你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