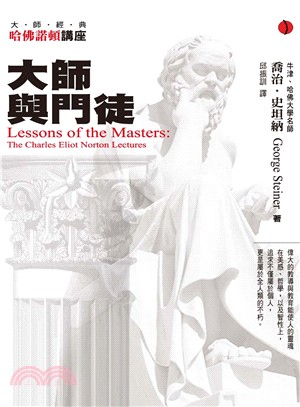大師與門徒:哈佛諾頓講座
商品資訊
系列名:大學堂叢書
ISBN13:9789863600374
替代書名:Lessons of the Masters : 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出版社:立緒文化
作者:喬治.史坦納
譯者:邱振訓
出版日:2015/05/13
裝訂/頁數:平裝/256頁
規格:20.5cm*15cm*1.6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牛津、哈佛大學名師 喬治.史坦納 George Steiner
談大師們與門徒的動人故事
偉大的教導與教育能使人的靈魂在美感、哲學,以及智性上,
追求不僅屬於個人,更是屬於全人類的不朽。
本書為喬治.史坦納教授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系列講題,以六篇在講座中對於教學方式與典故的內容為藍本,闡述師生間的衝突與遭遇,對各種教育形式中無數的情結、權力、信任與激情進行深刻的反思。
喬治.史坦納深研西方古典哲學與文學,為當代西方人文學名師,在其教學生涯中曾巡迴世界各名校講座,足跡遍及劍橋、牛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紐約、日內瓦大學……
史坦納在本書中列舉了眾多人物典範,包括蘇格拉底與柏拉圖、耶穌和他的門徒、維吉爾與但丁、浮士德與華格納、孔子與許多佛教高僧、胡塞爾與海德格及鄂蘭、莎士比亞與波洛涅斯、布洛德與卡夫卡、歌德與叔本華及尼采、赫曼.赫塞與尼克特、弗洛依德、亨利.詹姆斯、川端康成、理查.費曼、波柏與阿格西、韋伯等等。
他對傳統與師生關係的討論另闢蹊徑,反覆環繞著三大主題進行論述︰老師剝削學生信賴感與獨立性的權力;老師相對受學生顛覆與背叛的威脅;還有師生之間相互的信賴與關愛,指導與學習。
※本書原書名為《哈佛諾頓講座之大師與門徒》
談大師們與門徒的動人故事
偉大的教導與教育能使人的靈魂在美感、哲學,以及智性上,
追求不僅屬於個人,更是屬於全人類的不朽。
本書為喬治.史坦納教授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系列講題,以六篇在講座中對於教學方式與典故的內容為藍本,闡述師生間的衝突與遭遇,對各種教育形式中無數的情結、權力、信任與激情進行深刻的反思。
喬治.史坦納深研西方古典哲學與文學,為當代西方人文學名師,在其教學生涯中曾巡迴世界各名校講座,足跡遍及劍橋、牛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紐約、日內瓦大學……
史坦納在本書中列舉了眾多人物典範,包括蘇格拉底與柏拉圖、耶穌和他的門徒、維吉爾與但丁、浮士德與華格納、孔子與許多佛教高僧、胡塞爾與海德格及鄂蘭、莎士比亞與波洛涅斯、布洛德與卡夫卡、歌德與叔本華及尼采、赫曼.赫塞與尼克特、弗洛依德、亨利.詹姆斯、川端康成、理查.費曼、波柏與阿格西、韋伯等等。
他對傳統與師生關係的討論另闢蹊徑,反覆環繞著三大主題進行論述︰老師剝削學生信賴感與獨立性的權力;老師相對受學生顛覆與背叛的威脅;還有師生之間相互的信賴與關愛,指導與學習。
※本書原書名為《哈佛諾頓講座之大師與門徒》
作者簡介
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
1929年生,牛津大學博士,歷任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日內瓦大學及牛津大學比較文學教授,2001年起任哈佛大學諾頓講座教授,為當代重要文學評論家,其著作多年來深獲好評,其《巴別塔之後︰語言翻譯面面觀》(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與《藍鬍子城堡︰對文化再定義之討論》(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均已成為經典著作。
1929年生,牛津大學博士,歷任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日內瓦大學及牛津大學比較文學教授,2001年起任哈佛大學諾頓講座教授,為當代重要文學評論家,其著作多年來深獲好評,其《巴別塔之後︰語言翻譯面面觀》(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與《藍鬍子城堡︰對文化再定義之討論》(In Bluebeard’s Castle: Some Notes Toward the Redefinition of Culture)均已成為經典著作。
目次
全書目錄
導論
1 源遠流長
2 火雨
3 萬世師表
4 思想大師
5 大師在美國
6 不老的智慧
結語
謝辭
導論
1 源遠流長
2 火雨
3 萬世師表
4 思想大師
5 大師在美國
6 不老的智慧
結語
謝辭
書摘/試閱
導論
半世紀以來,我在各國各種不同高等教育體系中任教,深覺自己愈來愈無法確定這份「教職」的正當性與真相究竟為何。我用引號是為了突顯出這個辭在宗教與思想背景上的複雜根源。「教職」是個字義模糊的辭彙,它跨越了從因循而無味的餬口謀生到崇高的神聖使命之間的諸多差距;它包含的類型眾多,下自誤人子弟的冬烘先生,上至循循善誘的百代宗師。我們深浸在近乎無以數計的教學型態裡──諸如基礎教育、技術指導、科學、人文、道德,還有哲學──卻很少回頭省思所謂的傳道授業解惑,用一個較精確而實際的方式來說,這份奧祕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是什麼使得一個人能夠教導另一個人,這份權威又來自何處?其次,那些受教者回應的主要次序又是什麼?這問題不只困擾了奧古斯丁,而且至今仍是自由主義氣氛中的痛腳。
我們可以簡化出三種主要的情境或關係結構。有些師者在心理上「毀」人不倦(destroyed their disciples)(少數時候在肉體上也會如此);他們會敗壞學生的精神,摧殘學生的希望,戕害學生的信賴感與獨立性;在這靈性的世界裡仍有吸血鬼存在。相對地,有些學生、徒弟與學徒也會推翻、背叛甚至毀滅他們的業師;這齣戲碼同樣包含了心靈與肉體的層面。一當選校長,洋洋得意的華格納也會一腳踢開他那瀕死的恩師浮士德。第三類關係則是一種交流,一種互信互慕之情,一種愛(就像「最後的晚餐」中「愛的門徒」那樣)。透過彼此互動、同化的過程,師徒間能夠教學相長。深刻的對談也會產生最深厚的情誼,而這同時也會包含清晰的洞見與愛的不理性;看看亞西比德(Alcibiades)與蘇格拉底(Socrates),埃羅伊茲(Hèloïse)與阿貝拉(Abelard),還有鄂蘭(Arendt)與海德格(Heidegger)這些例子吧!有些學生甚至會覺得老師逝世後將難以獨活。
儘管有無數種組合與差異的可能,這每一種關係模式在宗教、哲學、文學、社會學以及科學等各領域中卻是屢見不鮮。由於舉世皆然,使得我們無法對這題材進行全面性的探究;因此後續的各章節只能提供幾乎是刻意汰選後最精要的簡介。
我們面臨的癥結在於這些問題源自於歷史情境,而且反覆出現,猶如時間的巨斧來回擺動所鑿出的斧痕。究竟傳授(tradendere)是什麼意思,又是什麼使誰對誰的傳授得以正當化?「已經傳授的東西」(traditio)與希臘文中「現在所傳授的東西」(paradidomena)之間的關係總是曖昧難明。「傳襲」(tradition)一詞仍保留了「反叛」(treason)與「傳遞」(traduction)的部分語義,這或許並非意外。而這些感受與企圖,在「翻譯」(translatio)的概念中不斷發生共鳴。教學,就其基本意義而言,是不是一種翻譯?是不是一種讓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賦予忠實與轉讓這些卓越德性的文字實作?我們可以看到這問題有許多不同的答案。
真正的教學一直被認為是模仿著對海德格所說存有能揭示與封閉內在真理(aletheia)的超越舉動,或者說得更精確些,是模仿著一種神聖的舉動。一般世俗的入門或進階學習,都是宗教與教會教育的翻版,而其原本在解讀哲學與神話時,是透過了口語上的交流。老師就是個聆聽者與傳信者,讓他所啟發、教導的對象能夠掌握到他所啟示的「理、道」(Logos),那個「太初之道」。事實上,這就是猶太經師「托拉」(Torah)、《可蘭經》講師,以及《新約聖經》講師的真正模樣。只是這種典範透過一種類比──而這類比又帶來了許多的困惑──延伸到對世俗知識、對智慧(sapientia)及科學(Wissenschaft)的分享、傳授與典籍編纂。我們在神聖經典及其注釋的大師身上所看到的典型與實踐,也延伸到了世俗領域之中。因此,在任何教育史上,都可以看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阿吉巴(Akiba)、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身影。
相對地,也有人說真正能禁得起檢驗的教學,要透過老師的示範。老師展示給學生看他對授課內容的掌握、他操作化學實驗的能力(所以實驗室總是一堆「操作者」)、他解決黑板上數學算式的能耐,以及在畫室中描繪石膏像或人體模特兒的能力。示範性的教學是種表演,而且可以是一場無聲的表演。或許,教學確實也該是如此。老師的手指導了學生怎麼彈鋼琴。有效的教學是外顯的,是一種表演。這種令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深感興趣的「展露」深植於字源學中:拉丁文中的「dicere」是「表現」的意思,後來又指「透過言說表示」;中世紀英文中的「token」與「techen」則含有「展現」的意思(老師是否終究是個藝人呢?)。在德文中,表示「指出」這意思的「deuten」,和表示「意味著」的「bedeuten」有密不可分的關連。這一連串的字辭意義關係,讓維根斯坦否定了在哲學裡有任何真正只透過文字指導的可能。尤其關於道德,只有透過大師的真實生活,才能夠顯出其證明。光是蘇格拉底和諸聖先賢他們自身的存在,就是種教導。
這些說法都可能過於理想。傅柯(Foucault)的觀點儘管相當簡化,卻相當中肯。教學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公開或隱然展現。老師擁有心理、社會、身體的權力;能夠對學生賞罰黜陟。老師的權威來自於制度或個人魅力,或是兩者都有;而這是靠著威脅或承諾來加以維繫。知識本身,從教育系統與制度的定義及傳授來看,就是權力的形式。在這種意義下來說,即使是最極端的教導形態,也都是保守而充滿了穩定的理想價值〔在法文中,「終身教職」(tenure)指的就是穩定(stabilization)〕。今日「反文化」與新世紀的種種論爭,以及其根源 ──在宗教上言必稱典和自由講述的爭論──都使得正式的知識與科學研究成了剝削策略與階級統治。誰對誰教了些什麼,又有些什麼樣的政治目的?我們會發現,這種作為暴力的教導結構,會升高到迸發出性愛激情,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課堂》(La Leçon)對此做了極辛辣的嘲諷。
不經反省地過活,就是對教導的拒絕,對教學的否定。老師找不到學生,找不到能夠繼承他的學說道統的人。摩西(Moses)毀了第一份石版,也就是上帝親手銘寫的那份訓誡。尼采(Nietzsche)在苦於需要回應時,卻缺乏適當的學生。這就是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的悲劇。
或者,也可能是老師所傳授的學說與信條(doxa),被認為過於危險。這些學說被埋藏在某個神祕的地方,希望久久不被人所發現;或是更戲劇性地,隨著大師逝世而長眠地底。在鍊金術的歷史與猶太教神祕教義喀巴拉(Kabbalistic)的傳說中,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更常見的,是只有少數揀選過的親信弟子才能夠接受大師真正的精要;一般大眾只能聽聞較為鬆散模糊的版本罷了。這種祕傳與外教的區別,產生出了李奧.史陀(Leo Strauss)對柏拉圖(Plato)的解讀。今日的生物遺傳學與粒子物理學中,能見到類似的情形嗎?是否還有對人類、對社會過於危險而無法進行測試,或是無法出版的假說及發現呢?軍事機密,或許其實是種複雜而隱密的兩難的表面偽裝而已。
有些情況下,透過意外、透過自我欺騙〔費瑪(Fermat)已經解決了他的定理嗎?〕,或是透過歷史活動,這些學問也會隨之消散。有多少口傳的智慧與科學(例如植物學與醫學療法)已經永遠不可復得?從亞歷山卓(Alexandria)到薩拉耶弗(Sarajevo),又有多少經書典冊已經盡付祝融?阿爾比教派(Albigensian)的書卷,如今只徒留懷疑。尤其在人文學科中,這些「真理」、這些極富深意的隱喻與洞見,都極可能已經失傳,再不可復得了〔這正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喜劇的看法〕。如今,除了攝影一途,我們已經無法重製凡.艾克(Van Eyck)的筆觸與色調了。據說,我們也無法重現帕格尼尼(Paganini)所拒絕教授的那三拍延長音(fermata)。英國巨石群和復活島上的巨大石像,又是用了什麼方法使它們矗立當地?
很明顯地,教學的技藝與活動,是種辯證過程,儘管辯證一詞已被廣泛濫用了,大師從學生身上學習,也由於這種相互關係而調整;就理想來說,乃成為一種交換的歷程。施成為得,就像在愛這迷團中一樣。保羅.瑟蘭(Paul Celan)說得好:「我在成為你的時候,才更是我自己。」當師傅發現學生不堪造就或是背叛師訓時,會將學生逐出師門;而當學生認為自己已超越了師傅,就必須要拋棄師傅才能成為自己(維根斯坦甚至會叫他要這麼做)。勝過師傅,以及在心理分析所說的伊底帕斯(Oedipus)式的忤逆,會造成揮之不去的悲痛;在《神曲.煉獄篇》(Purgatorio)中但丁對維吉爾(Virgil)的告別,或是川端康成的《名人》(Master of Go),都是明證。或者,也可能帶來復仇的快慰,無論是在小說裡〔華格納(Wagner)贏過了浮士德(Faust)〕,或是在現實中〔海德格不僅勝出,更打垮了胡塞爾(Husserl)〕。
而我,現在要針對在哲學、文學與音樂上的一些實例來進行考察。
半世紀以來,我在各國各種不同高等教育體系中任教,深覺自己愈來愈無法確定這份「教職」的正當性與真相究竟為何。我用引號是為了突顯出這個辭在宗教與思想背景上的複雜根源。「教職」是個字義模糊的辭彙,它跨越了從因循而無味的餬口謀生到崇高的神聖使命之間的諸多差距;它包含的類型眾多,下自誤人子弟的冬烘先生,上至循循善誘的百代宗師。我們深浸在近乎無以數計的教學型態裡──諸如基礎教育、技術指導、科學、人文、道德,還有哲學──卻很少回頭省思所謂的傳道授業解惑,用一個較精確而實際的方式來說,這份奧祕究竟是怎麼回事。究竟是什麼使得一個人能夠教導另一個人,這份權威又來自何處?其次,那些受教者回應的主要次序又是什麼?這問題不只困擾了奧古斯丁,而且至今仍是自由主義氣氛中的痛腳。
我們可以簡化出三種主要的情境或關係結構。有些師者在心理上「毀」人不倦(destroyed their disciples)(少數時候在肉體上也會如此);他們會敗壞學生的精神,摧殘學生的希望,戕害學生的信賴感與獨立性;在這靈性的世界裡仍有吸血鬼存在。相對地,有些學生、徒弟與學徒也會推翻、背叛甚至毀滅他們的業師;這齣戲碼同樣包含了心靈與肉體的層面。一當選校長,洋洋得意的華格納也會一腳踢開他那瀕死的恩師浮士德。第三類關係則是一種交流,一種互信互慕之情,一種愛(就像「最後的晚餐」中「愛的門徒」那樣)。透過彼此互動、同化的過程,師徒間能夠教學相長。深刻的對談也會產生最深厚的情誼,而這同時也會包含清晰的洞見與愛的不理性;看看亞西比德(Alcibiades)與蘇格拉底(Socrates),埃羅伊茲(Hèloïse)與阿貝拉(Abelard),還有鄂蘭(Arendt)與海德格(Heidegger)這些例子吧!有些學生甚至會覺得老師逝世後將難以獨活。
儘管有無數種組合與差異的可能,這每一種關係模式在宗教、哲學、文學、社會學以及科學等各領域中卻是屢見不鮮。由於舉世皆然,使得我們無法對這題材進行全面性的探究;因此後續的各章節只能提供幾乎是刻意汰選後最精要的簡介。
我們面臨的癥結在於這些問題源自於歷史情境,而且反覆出現,猶如時間的巨斧來回擺動所鑿出的斧痕。究竟傳授(tradendere)是什麼意思,又是什麼使誰對誰的傳授得以正當化?「已經傳授的東西」(traditio)與希臘文中「現在所傳授的東西」(paradidomena)之間的關係總是曖昧難明。「傳襲」(tradition)一詞仍保留了「反叛」(treason)與「傳遞」(traduction)的部分語義,這或許並非意外。而這些感受與企圖,在「翻譯」(translatio)的概念中不斷發生共鳴。教學,就其基本意義而言,是不是一種翻譯?是不是一種讓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賦予忠實與轉讓這些卓越德性的文字實作?我們可以看到這問題有許多不同的答案。
真正的教學一直被認為是模仿著對海德格所說存有能揭示與封閉內在真理(aletheia)的超越舉動,或者說得更精確些,是模仿著一種神聖的舉動。一般世俗的入門或進階學習,都是宗教與教會教育的翻版,而其原本在解讀哲學與神話時,是透過了口語上的交流。老師就是個聆聽者與傳信者,讓他所啟發、教導的對象能夠掌握到他所啟示的「理、道」(Logos),那個「太初之道」。事實上,這就是猶太經師「托拉」(Torah)、《可蘭經》講師,以及《新約聖經》講師的真正模樣。只是這種典範透過一種類比──而這類比又帶來了許多的困惑──延伸到對世俗知識、對智慧(sapientia)及科學(Wissenschaft)的分享、傳授與典籍編纂。我們在神聖經典及其注釋的大師身上所看到的典型與實踐,也延伸到了世俗領域之中。因此,在任何教育史上,都可以看到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阿吉巴(Akiba)、和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身影。
相對地,也有人說真正能禁得起檢驗的教學,要透過老師的示範。老師展示給學生看他對授課內容的掌握、他操作化學實驗的能力(所以實驗室總是一堆「操作者」)、他解決黑板上數學算式的能耐,以及在畫室中描繪石膏像或人體模特兒的能力。示範性的教學是種表演,而且可以是一場無聲的表演。或許,教學確實也該是如此。老師的手指導了學生怎麼彈鋼琴。有效的教學是外顯的,是一種表演。這種令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深感興趣的「展露」深植於字源學中:拉丁文中的「dicere」是「表現」的意思,後來又指「透過言說表示」;中世紀英文中的「token」與「techen」則含有「展現」的意思(老師是否終究是個藝人呢?)。在德文中,表示「指出」這意思的「deuten」,和表示「意味著」的「bedeuten」有密不可分的關連。這一連串的字辭意義關係,讓維根斯坦否定了在哲學裡有任何真正只透過文字指導的可能。尤其關於道德,只有透過大師的真實生活,才能夠顯出其證明。光是蘇格拉底和諸聖先賢他們自身的存在,就是種教導。
這些說法都可能過於理想。傅柯(Foucault)的觀點儘管相當簡化,卻相當中肯。教學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公開或隱然展現。老師擁有心理、社會、身體的權力;能夠對學生賞罰黜陟。老師的權威來自於制度或個人魅力,或是兩者都有;而這是靠著威脅或承諾來加以維繫。知識本身,從教育系統與制度的定義及傳授來看,就是權力的形式。在這種意義下來說,即使是最極端的教導形態,也都是保守而充滿了穩定的理想價值〔在法文中,「終身教職」(tenure)指的就是穩定(stabilization)〕。今日「反文化」與新世紀的種種論爭,以及其根源 ──在宗教上言必稱典和自由講述的爭論──都使得正式的知識與科學研究成了剝削策略與階級統治。誰對誰教了些什麼,又有些什麼樣的政治目的?我們會發現,這種作為暴力的教導結構,會升高到迸發出性愛激情,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課堂》(La Leçon)對此做了極辛辣的嘲諷。
不經反省地過活,就是對教導的拒絕,對教學的否定。老師找不到學生,找不到能夠繼承他的學說道統的人。摩西(Moses)毀了第一份石版,也就是上帝親手銘寫的那份訓誡。尼采(Nietzsche)在苦於需要回應時,卻缺乏適當的學生。這就是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的悲劇。
或者,也可能是老師所傳授的學說與信條(doxa),被認為過於危險。這些學說被埋藏在某個神祕的地方,希望久久不被人所發現;或是更戲劇性地,隨著大師逝世而長眠地底。在鍊金術的歷史與猶太教神祕教義喀巴拉(Kabbalistic)的傳說中,這類例子不勝枚舉。更常見的,是只有少數揀選過的親信弟子才能夠接受大師真正的精要;一般大眾只能聽聞較為鬆散模糊的版本罷了。這種祕傳與外教的區別,產生出了李奧.史陀(Leo Strauss)對柏拉圖(Plato)的解讀。今日的生物遺傳學與粒子物理學中,能見到類似的情形嗎?是否還有對人類、對社會過於危險而無法進行測試,或是無法出版的假說及發現呢?軍事機密,或許其實是種複雜而隱密的兩難的表面偽裝而已。
有些情況下,透過意外、透過自我欺騙〔費瑪(Fermat)已經解決了他的定理嗎?〕,或是透過歷史活動,這些學問也會隨之消散。有多少口傳的智慧與科學(例如植物學與醫學療法)已經永遠不可復得?從亞歷山卓(Alexandria)到薩拉耶弗(Sarajevo),又有多少經書典冊已經盡付祝融?阿爾比教派(Albigensian)的書卷,如今只徒留懷疑。尤其在人文學科中,這些「真理」、這些極富深意的隱喻與洞見,都極可能已經失傳,再不可復得了〔這正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喜劇的看法〕。如今,除了攝影一途,我們已經無法重製凡.艾克(Van Eyck)的筆觸與色調了。據說,我們也無法重現帕格尼尼(Paganini)所拒絕教授的那三拍延長音(fermata)。英國巨石群和復活島上的巨大石像,又是用了什麼方法使它們矗立當地?
很明顯地,教學的技藝與活動,是種辯證過程,儘管辯證一詞已被廣泛濫用了,大師從學生身上學習,也由於這種相互關係而調整;就理想來說,乃成為一種交換的歷程。施成為得,就像在愛這迷團中一樣。保羅.瑟蘭(Paul Celan)說得好:「我在成為你的時候,才更是我自己。」當師傅發現學生不堪造就或是背叛師訓時,會將學生逐出師門;而當學生認為自己已超越了師傅,就必須要拋棄師傅才能成為自己(維根斯坦甚至會叫他要這麼做)。勝過師傅,以及在心理分析所說的伊底帕斯(Oedipus)式的忤逆,會造成揮之不去的悲痛;在《神曲.煉獄篇》(Purgatorio)中但丁對維吉爾(Virgil)的告別,或是川端康成的《名人》(Master of Go),都是明證。或者,也可能帶來復仇的快慰,無論是在小說裡〔華格納(Wagner)贏過了浮士德(Faust)〕,或是在現實中〔海德格不僅勝出,更打垮了胡塞爾(Husserl)〕。
而我,現在要針對在哲學、文學與音樂上的一些實例來進行考察。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