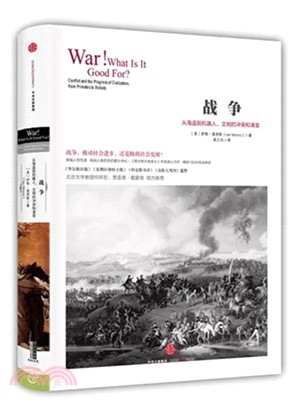商品簡介
這本書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地理學、進化生物學,以及科技和軍事知識,講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卻又引人入勝的戰爭故事,歷數從海盜到機器人的15000年的爭鬥和暴力,從原始社會到古代文明,再到“美利堅帝國”。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時代,人們生活在爭鬥不休的小社會中,有1/10甚至1/5的可能會死於暴力。與之相反,在20世紀,儘管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等大小戰亂,每100個人卻只有不到1個人死於暴力。這都是因為戰爭,也只有戰爭打造出的利維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權國家,才能夠確保穩定,從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富庶。
這本書對15 000年人類戰爭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來的半個世紀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時期。如果我們可以渡過這一階段,那麼自古以來一直存在的終結戰爭的夢想或許就可以實現。但莫里斯認為,要想知道戰爭接下來要把我們帶向何方,必須先明瞭戰爭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本書無疑將永遠改變我們看待戰爭的方式,並改變我們在未來應對衝突的選擇。對於那些認為戰爭是普世災難的人來說,這本書將改變他們看待歷史的角度;而對於每一個參與戰爭與和平的事業,或是在任何一方面會影響人類命運走向的人,都應當讀這本書。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戰爭,推動社會進步,還是阻礙社會發展?
穿越人性荒漠 挑戰人類歷史的**悖論
《西方將主宰多久》作者潛心力作,橫跨15000年戰爭史
序
我很高興伊恩•莫里斯的又一本簡體中文譯著《戰爭》出版,在此之前他已有《西方將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在中國出版,且都引起了相當廣泛的關注。一如既往,這本書也有許多引人入勝的材料和激發我們思想的觀點,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觀點,也是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作者認為,從長程的觀點看,戰爭是好的,常常是建設性的,他並力圖展示為什麼說戰爭是好的理由和資料。
這一“長程”的觀點是很“長”的,莫里斯強調他看戰爭不只是從近代500 年的觀點,也不是從人類有文字史以來5 000 年的觀點,而是他在前兩本書中也採取了的、人類近15 000 年來的歷史觀點,而且主要是從客觀結果來看。他認為,人類經過1 萬多年的進化,終於擺脫了部落與個人之間頻繁的互相殘殺,人類的暴力死亡率即便在激烈動盪的20 世紀,也比在石器時代下降了90%。而戰爭在這一過程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可以從史料清晰得知,人類幾千年來的戰爭,雖然有建設性的和反建設性的,但總體趨勢是建設性的。
而戰爭之所以在總體上起了這種好的作用,莫里斯認為,是因為通過戰爭,人類創造出了更龐大、組織更完善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減少了社會成員死於暴力的風險。政府的統治者採取措施,維持和平,雖然不一定出於心中的善意,但即便在不經意間,這樣的舉措也達成了創造更大、更和平的社會這一目標。戰爭創造出更大規模的社會,這一社會由更強有力的政府統治,而這樣的政府用強制力確保了和平,並為繁榮奠定了基礎。簡單地說就是,“戰爭塑造國家,國家締造和平”。戰爭創造出強大的國家—利維坦,而利維坦讓人們更安全、更富有。戰爭雖然在有些條件下可以走向建設性的反面,讓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會倒退回更小、更窮困、更暴力的社會,但從長期的總體趨勢來看,戰爭使人類更安全、更富庶。我們不難看到,作者還是在肯定生命和反對暴力的基礎上讚揚戰爭的。他說戰爭是好的,恰恰是因為他認為戰爭從長遠來說可能比和平還更有效地保障了生命。戰爭促進了大的政治社會的建構,而一種大的政治社會往往能夠更有效地維護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換言之,少數大戰代替了頻繁的小戰,一次短暫的劇痛代替了持久的小痛,“坐寇”代替了“流寇”,而前者比後者反而更能保護人們。作者並不美化國家及其統治者的“善意”,但十分強調國家的“善果”,強調國家相對無政府狀態的優越性,甚至也強調大國相對小國的優越性。
的確,在莫里斯那裡有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他對無政府狀態的後果極其擔心。他引愛比克泰德的話讚揚“羅馬統治下的和平”說羅馬“為我們帶來了偉大的和平,不再有戰爭、打鬥、巨寇或是海盜;從日出到日落,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隨意出行”。同此,他也讚揚曾經的英國乃至今天的美國作為“世界員警”在維護世界秩序與和平方面的作用。他最後的一個觀點是:戰爭正在自我終結。他將21 世紀上半葉和20 世紀上半葉進行比較,認為未來的40 年將是最危險的40 年,正像德國曾經挑戰英國的霸權,而事實上卻是美國取代了英國的霸權一樣,現在也有對美國霸權的挑戰。而有些奇特,甚至有點兒反現實主義的是,莫里斯最後把希望寄託在一種矽基生物的技術發展上,說傳統的人的碳基智慧和電子技術的矽基智慧將合併為一個全球意識,其思維能力將讓歷史上出現過的一切相形見絀。他認為這種“技術統治的世界”如果及時地取代“美國統治下的世界”,世界就會有希望。萬事萬物的電腦化進程發展得越快,我們就越有可能在“世界員警”衰微而引發新的鋼鐵風暴之前實現從“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到“技術統治下的和平”的轉變。但是,將希望寄託在一種技術成就上,期望政治的問題通過目前看來還相當渺茫的科技奇點得到解決,這是否也是一種比較奇特的樂觀期望?
莫里斯為戰爭辯護的主要理由是:戰爭造就了強大的國家,創造了大規模的、組織完善的政治社會。但我們或許可以質疑說:第一,國家,包括強大的國家是不是只是由戰爭造就的?還有沒有其他的、同等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原因?第二,即便我們承認國家,尤其是強大國家主要是戰爭推動造成的,那是不是也並非是戰爭直接造成的,而是經過了人們對戰爭的反省,接受戰爭的教訓而採取了防範戰爭的措施和建設維護持久和平的制度,包括推廣反戰的意識與觀念,如此才造就了強大且長治久安的國家?這也就引出了第三點質疑,即國家,包括強大的國家也有多種形態,而我們究竟要哪種強大的國家?是要短期強大的國家,還是要可持續的強大國家?而可持續的強大國家是不是恰恰要優先考慮全民的安全與福祉,而不是把戰爭放到首位?而現代意義上可持續的強大國家是否恰恰要通過反戰、維權、法治和憲政建設?人類是否應當主要是通過“數人頭”而非“殺人頭”取得進步和發展?第四,在今天的核武器時代,戰爭是否還能推動造就強大的國家?大國、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是更有可能造成其同歸於盡甚至人類的滅亡?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很難贊同一種在戰爭與國家之間的單因論和直接論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上萬年來人類社會暴力事件的減少,但即便這一減少的趨勢的確存在,它也不是直線型的,不是單一因素促成的;而在戰爭因素對這一趨勢的影響方面,看來也更多的是因為反省和吸取戰爭的教訓而出現的制度與觀念的努力起了作用,而不是戰爭直接起了作用。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當我們在事後談論一場戰爭或一系列戰爭所帶來的客觀上的好結果的時候,我們是否也將這作為日後事先選擇戰爭的理由(自然只能是一種結果論的理由)?事後評價和事先選擇是有區別的,而莫里斯似乎沒有清晰地意識到這種區別。比如他談到戰爭是地獄,但又說從長期來看,其他選擇可能更糟糕。他甚至直接批評邱吉爾的話“吵吵總比打打好”說,在古代歷史的記載中,很難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例證,表明人們自願組成一個更大的社會,而不是被實際或潛在的暴力迫使就範。那麼,這種對戰爭的事後評價會不會變成一種對戰爭的直接訴求?對只是某一些戰爭所帶來的建設性後果的分析,會不會變成對一般的戰爭的普遍肯定?而如果變成這種普遍肯定的話,這種普遍肯定顯然就容易變成一種選擇戰爭的支持理由,或至少是催化這種態度:發生戰爭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或許還更好。因而不畏懼激化走向戰爭的因素,甚至不畏懼發動戰爭,從而真的帶來了大難。
我們從道德的角度判斷戰爭,可以主要從三個方面觀察:第一是戰爭本身作為行為與活動的性質,即戰爭的本性;第二是發動戰爭者乃至介入戰爭的各方的意圖和動機,即所要達到的目標;第三是戰爭實際上促成的結果,這一結果可能會接近某一方的目標,但由於合力的作用,它絕不會完全滿足任何一方的願望,而且,由於戰爭其暴力相搏的本性,它一定要帶來大量生命財產的損失。即便有長期的好的結果,也還是一定有戰爭中所付出的生命財產的代價。而且正如作者所承認的,還有一種完全是反建設性、純粹破壞性的戰爭,不僅造成社會停滯,而且造成社會倒退很多年。
戰爭有哪裡好?除了作者所說到的,其實還可以補充一些。當然,這還是只能主要是指戰爭的客觀結果。除了一場大的統一戰爭結束了連年的、相持不下的混戰,終於帶來了強大的國家與它統治下的地區和平,甚至推進了世界和平。戰爭還可能推動科技的發展。由於雙方在戰爭中集中了人力物力,極力想戰勝對方,從而帶來了技術的突破,這種突破的成果常常可以從軍用領域向民用領域轉移,我們實際看到的許多科技發明最初都是在戰時出現的。近代以來,戰爭還可能推動了社會平等,包括階級、階層和兩性的平等,緩解了階級衝突,或者鬆動了意識形態的禁錮,有時富人和窮人、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乃至男人和女人來到了同一戰壕,站到了同一戰線。戰爭甚至還引發了一些不無好處的革命,一些和平時期不易解決的沉屙終於得到瞭解決。戰爭還可能刺激了經濟,長遠來說帶來了人們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還有像核武器的威懾遏制了核大國之間的戰爭等。戰爭對精神和道德也不無起到錘煉作用,面對生死和平時很難戰勝的困難,戰時卻通過極大地調動人的精神和道德潛力而戰勝了這些困難。但我想,我們無論如何還是要重申:這只是戰爭一個方面的結果,還有另一方面的、更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大量生命財產的損失、家破人亡,對經濟的直接摧殘甚至毀滅性的打擊,多少年都很難恢復過來,還有廣泛和持久的心靈創傷和道德傷害,為下一場戰爭醞釀的持久的敵意和復仇心等。而問題還在於,前述的種種戰爭好處,在核武器時代一旦戰爭爆發,可能都要化為青煙。
以上是從戰爭的結果方面分析,如果從戰爭的意圖方面觀察呢?一場戰爭必定涉及不只一方,而且,發動戰爭一方的意圖是主導性的,這種意圖是否有好的呢?對此可能要有極嚴格的限制,有人甚至否認今天有任何“發動正義戰爭”的可能性。不過,莫里斯看來也沒有從這方為戰爭辯護,相反,他充分認識到人們發動戰爭的自利乃至邪惡意圖。
最後從戰爭的屬性來說,我們一定不要忘記,戰爭的第一本性就是人類的相搏,就是成建制的、大規模的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廝殺。戰爭不僅本身就是殘酷,還助長殘酷,它容易把殘忍的習慣從戰場帶到非戰場,從戰時帶到戰後。戰爭無論如何都不是人之為人的驕傲。而且,我們不僅要持一種人類的觀點,還要持一種個人的觀點,因為生命實際是在一個個具體的個人那裡真實存在的,我們因此也就不僅要持一種長期的觀點,還要持一種短期的觀點。這是由戰爭的本性決定的。某一場戰爭可能會帶來長遠的好的結果,但我們是否還要念及和哀悼這場戰爭中死去的人們呢?他們死去就是死去了,那就是他們全部生命的結束。而沒有這場戰爭,他們本來是可以不死的。世界上也沒有誰能夠活15 000 年,大多數人的壽命也就是50~100 年。所以,我們總是要優先考慮儘量減少戰爭,包括減少戰爭中的傷亡;我們還要儘量優先考慮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和平談判和相互妥協的方式解決衝突。
我與莫里斯教授曾在2014 年11 月中旬中信書院舉辦的前沿論壇中見過面。當時對這本書的觀點,我當面提出過一些疑問,莫里斯教授解釋說,他的意思其實是:戰爭並不是全無是處,在歷史上並不是沒有一點兒好處。如果是這樣,他的立論應當是建立在比較不易受批評和攻擊的立場上,但細看全書,似乎在有些地方又表達得過於強勢。我希望我的批評沒有太誤解他的意思,或者可視作一種對贊許戰爭的一般觀點的批評。我推薦人們讀這本書,因為它能夠提供一個我們澄清自己的反戰理由的機會,或者看清自己隱蔽的好戰“理由”的“緣故”。戰爭總是引人注目的,這不僅是因為戰爭中有各種偶然因素、劇烈衝突、戲劇性變化、勝者與敗者、英雄與梟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戰爭是攸關千百萬人生死的事情。研究戰爭的文獻卷帙浩繁,但這本《戰爭》將以其獨特的觀點與方法,成為其中一部新穎的傑作。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對戰爭的長程觀察
我很高興伊恩‧莫里斯的又一本簡體中文譯著《戰爭》出版,在此之前他已有《西方將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在中國出版,且都引起了相當廣泛的關注。一如既往,這本書也有許多引人入勝的材料和激發我們思想的觀點,而其中最具挑戰性的觀點,也是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作者認為,從長程的觀點看,戰爭是好的,常常是建設性的,他並力圖展示為什麼說戰爭是好的理由和資料。
這一“長程”的觀點是很“長”的,莫里斯強調他看戰爭不只是從近代500 年的觀點,也不是從人類有文字史以來5 000 年的觀點,而是他在前兩本書中也採取了的、人類近15 000 年來的歷史觀點,而且主要是從客觀結果來看。他認為,人類經過1 萬多年的進化,終於擺脫了部落與個人之間頻繁的互相殘殺,人類的暴力死亡率即便在激烈動盪的20 世紀,也比在石器時代下降了90%。而戰爭在這一過程中起了莫大的作用。可以從史料清晰得知,人類幾千年來的戰爭,雖然有建設性的和反建設性的,但總體趨勢是建設性的。
目次
目錄
推薦序對戰爭的長程觀察 // VII
前言 送葬人之友 // XIII
為我們時代的和平 // XVII
戰爭締造國家,國家實現和平 // XXIV
戰爭豬 // XXVIII
進攻計畫 // XXXIII
第一章不毛之地?古羅馬的戰爭與和平
世界邊緣的戰鬥 // 003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 007
坐寇 // 017
我們能不能都安然相處 // 020
我們就是怪獸 // 025
怎樣才能變成羅馬 // 035
第二章將怪獸放入囚籠:建設性的戰爭
並非西方式的戰爭 // 039
為什麼一些帝國比另一些更幸運 // 041
囚籠 // 048
利維坦遇到紅桃皇后 // 053
同一個充滿矛盾的假設 // 058
烈火戰車 // 064
推動一切的囚籠效應 // 070
擴張,再擴張 // 078
第三章蠻族的反擊:反建設性的戰爭(1~1415年)
帝國的極限 // 083
帝國跨上戰馬 // 086
建設性與反建設性的血腥迴圈 // 094
帝國的墳墓 // 101
僵屍帝國 // 106
沒有出路 // 109
把世界裝入“囚籠” // 113
自然試驗 // 118
幸運的少數人 // 125
第四章 500年戰爭:歐洲(幾乎)征服世界(1415~1914年)
將成為國王的人 // 129
為什麼歐洲人的火器最優良 // 131
回報 // 139
訓練啊,寶貝兒,訓練 // 146
對世界開戰 // 152
“看不見的拳” // 159
戰爭與永久的和平 // 167
日不落 // 172
不列顛統治下的和平 // 181
第五章鋼鐵風暴:爭奪歐洲的戰爭(1914年至20世紀80年代)
有序世界重歸混沌 // 193
未知的未知 // 195
風暴來臨 // 202
沒有勝利者的和平 // 211
“世界員警”之死 // 214
暴風驟雨 // 218
學著愛上原子彈 // 225
一路走向彼得羅夫的時刻 // 231
第六章赤牙血爪:貢貝黑猩猩為何走向戰爭
殺手人猿與嬉皮黑猩猩 // 241
死亡博弈 // 246
我的朋友們幫了一點兒忙 // 250
人猿星球 // 253
裸猿 // 256
2.7 磅的魔法 // 262
和平主義者的困境 // 268
超越彼得羅夫 // 273
第七章地球最後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堅帝國(1989年~?)
從這兒到不了那兒 // 281
金星與火星 // 288
美國的布林戰爭 // 293
不可避免的類比 // 300
打破鎖鏈 // 306
書摘/試閱
戰爭與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個新的力量出現,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間,戰爭變成了人民參與的事業。”
在親歷了這一切的克勞塞維茨看來,這才是 18世紀末的真正遺產。1787年,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以“我們人民”作為其憲法草案的開篇詞,並非是隨意為之的:正是武裝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餉的職業軍人或是雇傭兵在獨立戰爭中站出來反對英國人。美國的革命者們缺少資金和組織,無力為軍隊支付薪餉,只能靠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徵召軍隊,並且率領他們圍著死板而緩慢的職業軍隊繞圈子。在開放的市場和政治之外,開放的秩序現在又帶來了有人民的力量參與其中的開放的戰爭。一場新的軍事革命開始了。
起初,人們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儘管他們本應想到。許多歐洲觀察家們堅持認為,美國獨立戰爭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們認為,戰爭中的美國人根本不是一股團結一致的力量,而僅僅是一盤散沙:如果不是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以及馮•施托伊本—一位來自德意志的軍官,他將大陸軍訓練得更接近於職業軍隊—參與進來,美國人很可能會輸掉這場戰爭。
即便在歐洲人意識到美國人進行了一場新穎的人民戰爭之後,他們也對此不以為意。他們認為,獨立戰爭後的美國軍隊簡直微不足道。一直到1791年,以寡敵眾的邁阿密印第安人還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殲滅了一支美國軍隊。印第安人殺死了 600名白人士兵,並且把土塞進他們的嘴裡,以滿足他們對土地的貪婪。很多歐洲人認為,如果這就是人民戰爭的結果,那麼不要也罷。
美國獨立戰爭真正給歐洲人留下印象的,並非他們進行戰爭的方式,而是這個新興的共和國發佈的關於超越戰爭的聲明。就連比大多數美國人都更稱得上知兵的喬治•華盛頓也對法國記者說“是讓騎士精神和瘋狂的英雄主義精神終結的時代了”,因為“商業為人們帶來的好處將取代戰爭和征服……就像《聖經》中所說,‘列國再也不學習戰事’”。
在 18世紀 90年代中期,歐洲的文學沙龍中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就是有關世界和平的提議,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國人的啟迪。不過,最具影響力的還要屬伊曼努爾•康得(Immanuel Kant)的小冊子《永久和平論》(Perpetual Peace)。康得或許是歐洲最為著名的哲學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廣受爭論的專著而聞名[就連其他的哲學家起初也覺得他長達800頁的《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澀難懂],也以其嚴謹的生活方式而著稱(他餐後都會大笑:並非因為他喜歡笑,而是這樣有助於消化)。不過,《永久和平論》既不龐雜,也不嚴厲,康得甚至在其開篇還開了個小玩笑:他說,這篇文章的題目取自“荷蘭一家旅店標識上的諷刺文字,那標識上畫了一處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得指出永久的和平在當前就有實現的可能。他認為,原因在於開放的共和國比封閉的君主國更善於經營商業。“如果進行戰爭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國裡那樣,那麼“公民們很可能會對進行這樣不高明的賭博持謹慎態度”。而一旦共和國棄絕了戰爭,那麼每個國家“都可能,也應當為其自身的安全考慮而要求其他國家一起加入一個類似于公民組織的組織之中,因為在這樣的組織中,每一個國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證。如此就形成了國家聯盟”。這樣一來,就再也不會有戰爭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論》仍然頗具影響力,經常在大學的課堂上被要求閱讀(有時候同《薩摩亞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問世的 1795年,其中的一些觀點就已經很顯然是錯誤的。共和主義非但沒有帶來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歐洲推入了戰爭之中。
事情的誘因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為了削弱英國,而給予美國革命者異常慷慨的軍事援助,這簡直是整18世紀最具諷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為此大量舉債,到了 1789年,他已經無法支付借款產生的利息了。他試圖增稅,結果引發了納稅人的反感,這種反感很快演變成了暴力行為。革命者逮捕了國王和他的妻子瑪麗•安托瓦內特,並在不久後將他們送上了斷頭臺。前前後後在斷頭臺上送命的法國人還有16 592人。
惶恐的歐洲大國組成了一個強大的同盟,以圖恢復局勢。1793年,法國革命者們突然感到恐懼,於是發動了一場威力超乎克勞塞維茨想像的人民戰爭。“整個國家都投入其中,”克勞塞維茨說道,“只要是有用的資源,都被投入戰爭之中;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戰爭的發生。”100萬法國人就此加入了戰爭。
康得認為,共和國的公民們對進行戰爭這種不高明的賭博會持謹慎態度。在這點上他可能說得不錯,但一旦公民們決定發動戰爭,他們就會帶著一種在職業軍人身上鮮見的暴力的狂熱參加戰爭。在美國獨立戰爭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羅來納兩州進行的大戰之外,罕有什麼激烈的大戰。而在法國革命戰爭中,人們卻帶著一種狂熱的正義感投入其中,並把矛頭直指戰爭中的敵人。一位法國軍官在1794年寫給他姐妹的信中寫道:“我們帶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願兵親手殺死了3名婦女。這無疑是暴行,但為了共和國的安全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在那一年,革命軍把25萬鄉下人當作反革命分子殺掉了。他們嫌槍決和斷頭臺處決的效率太低,乾脆把平民綁在一起丟進河裡。“盧瓦爾河變成了一條革命的河流,”指揮官揶揄道,“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我將這些惡魔從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過,當革命者面對訓練有素的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軍隊時,他們遇到了麻煩;在美國革命者最初面對英軍和效忠英國的黑森雇傭軍的時候,他們也曾遭遇同樣的窘境。法國的人民軍隊人數眾多,紀律渙散,指揮乏力,特別是在他們將那些反動軍官都斬首或驅逐出境之後。拯救法軍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隊,因為炮兵部隊保留了那些非貴族出身、在革命爆發前就在軍中服役的軍官們。1796年,這些炮兵軍官中的一個—個頭矮小、喜歡爭吵、來自外省的拿破崙•波拿巴—找到了將人民軍隊變為勝利之師的方法。
革命者們聲稱:“我們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戰術,只需要火、鐵和愛國精神。”而拿破崙的天才之處在於他將口號變成了現實。拿破崙的部隊拋棄了經常拖住職業軍隊後腿的補給線,轉而在所經之處購買或是搶奪他們需要的資源。 17世紀以來,就再也沒有人這樣做過了,因為軍隊的規模已經太大,無法在行軍沿途經過的農場中弄到足夠的物資。但拿破崙將自己的部隊分解成兵團和建制更小的師,讓他們分別沿一條路線獨自行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每一個兵團或師也可以獨立作戰,但拿破崙的勝利秘訣是,各支部隊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敵人的地點,從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戰。
在戰場上,拿破崙採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無法像傳統的職業軍人那樣完美地運用複雜的線性戰術,因此他也不要求他們做到這點。相反,成群的散兵會狙擊敵人整齊的佇列,而大群的法國步兵則在密集槍炮的掩護下排著參差的佇列前進。一旦接近敵軍,法軍陣列就會分散為混亂的戰線,對敵軍進行齊射,用人數的優勢彌補準確度的不足;法軍也可能會繼續前進,舉著固定好的刺刀沖入敵陣。敵人的職業軍隊也經常會在法軍的衝鋒下丟下火槍逃走。
就在康得寫作《永久和平論》的時期,法國人的人民戰爭的目標正在不經意地由保衛革命果實演變成了擴大革命成果。 1796年,拿破崙席捲了義大利北部; 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 1800年 12月,法軍打到了距離維也納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得去世後三年,拿破崙佔領了康得的家鄉柯尼斯堡。
歐洲的人民戰爭的方式與美國的截然不同。在英國人於1781年於約克鎮投降後,美國人便鑄劍為犁。將軍們都回到了自家的農場,而傑弗遜和他的同道中人則頑固地抗拒著中央集權、稅收、國債、常備軍以及利維坦常用的其他工具。
對一些美國人來說,這意味著他們與那些腐朽的歐洲人截然不同。而實際上,美國在遇到危險時(比如在 18世紀末,當美國人擔心法國人可能入侵時)也回到了利維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國與歐洲的真正區別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區別。在1781年之後,美國的存在幾乎不會面臨任何威脅。因此,美國人可以只維持很弱小的軍事力量,甚至開始討論他們究竟是否需要一個利維坦。與此相反,歐洲國家的周遭都是虎視眈眈的鄰國。一點點兒的劣勢可能就會導致致命的後果,為了生存,共和國也必須像君主國一樣拼命戰鬥。
在美洲和歐洲,愛國熱忱的勃發都是開放秩序興起的一部分。不過,拿破崙發現,人民戰爭並非必須伴隨著共和制度,從而使歐洲的人民戰爭與美國的人民戰爭進一步分道揚鑣。 1799年一場靜悄悄的政變讓拿破崙成了法國實際上的君主。1804年,拿破崙公開加冕稱帝。自此,法國大軍的戰爭目標就變成了舊式的帝國擴張。喬治•華盛頓相信,商業讓戰爭變得不再必要,而拿破崙卻不這麼認為。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