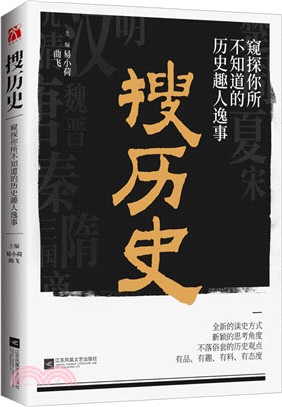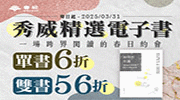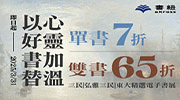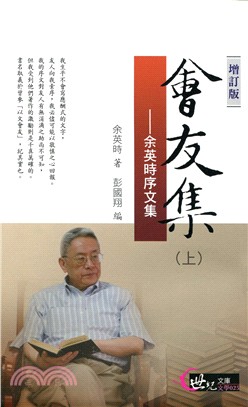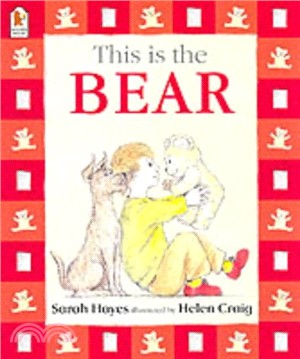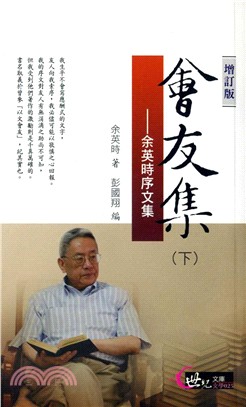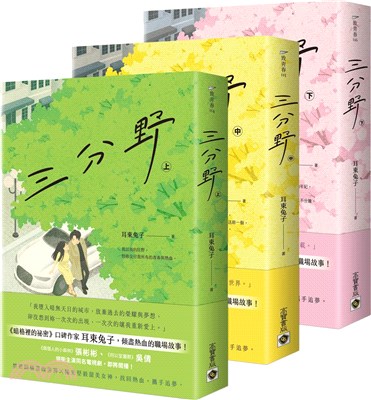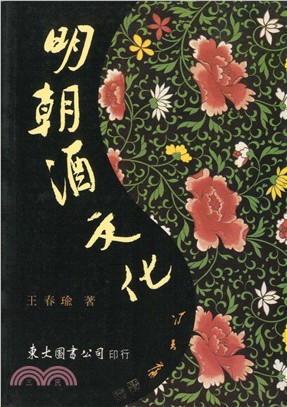左手的繆思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本書簡介
「詩文雙璧」的余光中,以右手,向詩的繆思不斷燃香,左手也在案頭筆耕散文。他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簫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於字裡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當思想與文字相遇,每如撒鹽於燭,會噴出七色的火花。
余光中在台灣文學的豐盛耕耘及重要性,放眼現代文壇,少見能出其右者,《左手的繆思》更成為他散文的代名詞。陳芳明說:「他筆下揮灑成形的恢宏氣象,既是個人豐饒生命的投影,也是當代歷史魂魄的縮影。」他學貫中西,以文為論,有豐富的知識,將夾敘夾議的文章,寫得說理透徹、深入淺出;有璀璨的文采,評述一代文學家或藝術家,均能點出其神魂氣魄,比喻鮮活、精采易讀。
他揮灑詩人的感性,「感情用事」的篇章讀來灑脫浪漫。〈記佛洛斯特〉中一張與美國詩壇巨擘的泛黃合照,紀念東西方兩大詩人交會時互換的光亮。當他初聞佛洛斯特「挾有十九世紀風沙」的聲音,竟熱淚盈眶,盡顯對文學大師的孺慕之情,猶如今日文青仰望余光中這顆恆星。
他具備學者的理性,認為寫文應有知性作為感性的脊梁。他用暢達的文筆與清明的分析,評論艾略特、安格爾,介紹梵谷、畢卡索,綜論各種畫風流派,深究個人生命史的演變,讓我們深深體會到:學理與藝術性竟能完美交融。看詩人論詩分外好看,作者本身詩藝超群,評價影響二十世紀的大詩人時,更能引領我們一窺創作門道的虛實。
第一篇短文〈猛虎與薔薇〉,暗示他知性與感性兼備的文風,既如猛虎般陽剛,也有薔薇的陰柔。以他在本書揭露的散文美學,來檢視他歷年的文集,無一不符合標準,彷彿實現了遙遠的時空承諾,也預見了未來的創作成就。
本書特色
★ 余光中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繆思》初版於1963年,書名成為台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典故。
★ 余光中用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雖自謙散文是副產,但書中收錄了知性與感性兼具、令人讚嘆的美文。
作者簡介
一生從事詩、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寫作的四度空間,詩風與文風的多變、多產、多樣,盱衡同輩晚輩,幾乎少有匹敵者。從舊世紀到新世紀,對現代文學影響既深且遠,遍及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曾在美國教書四年,並在臺、港各大學擔任外文系或中文系教授暨文學院院長,曾獲香港中文大學及臺灣政治大學之榮譽博士。先後榮獲「南京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國立中山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之貢獻獎、第三十四屆行政院文化獎、第十三屆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等。現為國立中山大學榮休教授。
著有詩集《白玉苦瓜》、《藕神》、《太陽點名》等;散文集《逍遙遊》、《聽聽那冷雨》、《青銅一夢》、《粉絲與知音》等;評論集《藍墨水的下游》、《舉杯向天笑》等;翻譯《理想丈夫》、《溫夫人的扇子》、《不要緊的女人》、《老人和大海》、《梵谷傳》、《濟慈名著譯述》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二)、《秋之頌》等,合計七十種以上。
序
自序
《左手的繆思》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初版雖在民國五十二年,其中作品的寫作時間,從四十一年到五十二年,先後卻有十一年之差。在那初征的十一年裏,詩集卻出了四本之多,足見我創作之始,確是以詩為主,散文只能算是旁敲側擊。
當時用「左手的繆思」為書名,朋友們都覺得相當新鮮,也有讀者表示不解。其實我用「左手」這意象,只是表示副產,並寓自謙之意。成語有「旁門左道」之說,臺語有「正手」(右)「倒手」(左)之分。在英文裏,「左手的」(left-handed)更有「彆扭」與「笨拙」之意。然則「左手的繆思」,簡直暗示「文章是自己的差」,真有幾分自貶的味道了。雖然早在十七世紀,米爾頓已經說過他的散文只是左手塗鴨,但在十六年前,不學如我,尚未發現此說。 集中最早的一篇少作,是〈猛虎與薔薇〉。那年我剛臺大畢業,散文雖也寫過多篇,「美文」卻是初試。當時為什麼沒有繼續寫下去,現在卻已感到惘然。等到再用散文來抒情,寫出〈石城之行〉和〈記佛洛斯特〉一類的作品來時,已經是〈猛虎與薔薇〉之後的六、七年了。 〈猛虎與薔薇〉在中央副刊發表時,作者已經二十四歲了,無論如何,都難說是「早熟」。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在這年齡所寫的作品,往往勝我許多。但在另一方面,今日的青年散文作家,一開筆便走純感性的路子,變成一種新的風花雪月,忽略了結構和知性,發表了十數篇之後,反來覆去,便難以為繼了。缺乏知性做脊椎的感性,只是一堆現象,很容易落入濫感。不少早熟的青年散文作家,開筆驚人,但到了某一層次,沒有知性的推力,更難上攀一分,實在可惜。
本集收文十八篇,就比例而言,仍以詩、畫的論評份量為重。從十多年的這一頭回顧,這些長評短論,有些還站得住腳,有些就顯得淺薄或誇大了。相對而言,幾篇抒情之作似乎較耐時間的考驗。當時之理,未必盡為今日所認可,但當時之情,卻近於人之常情,真個是「理短情長」了。而鏡破片片,每一片中都是一我,也難以指認誰真誰幻了。
余光中 六十八年八月於中文大學
目次
目錄
自序
記佛洛斯特
艾略特的時代
舞與舞者
莎翁非馬羅
中國的良心——胡適
美國詩壇頑童康明思
死亡,你不要驕傲
繆思的偵探
簡介四位詩人
梵谷——現代藝術的殉道者
畢卡索——現代藝術的魔術師
現代繪畫的欣賞
樸素的五月
石城之行
塔阿爾湖
重遊馬尼拉
書齋‧書災
猛虎和薔薇
後記
書摘/試閱
艾略特曾說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證之以我在愛奧華成的經驗,頗不以為然。在我,一九五九年四月是幸運的:繼四月三日在芝加哥聽到鋼琴家魯多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奏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之後,我在四月十三日復會見了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
佛洛斯特曾經來過愛奧華城,但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梁實秋先生留美時,也曾在波士頓近郊一小鎮上聽過佛洛斯特自誦其講求那更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物換星移,此老依然健在,所謂「紅葉落盡,更見楓樹之修挺」;美國二十世紀新詩運動第一代的名家,如今僅存他和桑德堡二人,而他仍長桑德堡三歲,可謂英美詩壇之元老。這位在英國成名,在美國曾獲四度普利澤詩獎的大詩人,正如鍾鼎文兄希梅尼斯時所寫的,已經進入「漸遠於人,漸近於神」的無限好時期,然而美國的青年們仍是那麼尊敬且熱愛他,目他為一個寓偉大於平凡的慈祥長者,他們舉眼向他,向他求信仰與安全感,智慧與幽默。當他出現在大音樂廳的講壇上,「炫數千年輕之美目以時間之銀白時」,掌聲之潮歷四五分鐘而不退。羅西尼說他生平流過三次淚,一次是當他初聞帕格尼尼拉琴時。而當我初聞佛洛斯特那種挾有十九世紀之風沙的聲音時,我的眼睛竟也濕了。我似乎聽見歷史的騷響。
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半,我去「詩創作」班上課,發現平時只坐二三十人的教室裏已擠滿了外班侵入的聽眾約五六十人。我被逼至一角,適當講座之斜背面。二時五十分「詩創作」教授安格爾(Paul Engle)陪著佛洛斯特進來。銀髮的老人一出現,百多隻眸子立刻增加了反光,笑容是甚為流行了。他始終站著,不肯坐下,一面以雙手撐著桌緣,一面回答著同學們的許多問題。我的位置只容我看見他微駝的背影,半側的臉,和滿頭的白髮。常見於異國詩集和《時代週刊》的一個名字,忽然變戊了血肉之軀,我的異樣之感是可以想像的。此時聽眾之一開始發問:
「佛洛斯特先生,你曾經讀過針對你的批評嗎?你對那些文字有什麼感想?」
「我從來不讀那種東西。每當有朋友告訴我說:某人發表了一篇評你的文章,我就問他,那批評家是否站在我這一邊,如果是的,那就行了。當朋友說,是的,不過頗有保留,不無含蓄;我就說:讓他去含蓄好了。」
聽眾笑了。又有人問他在班上該如何講詩,他轉身一瞥詩人兼教授的安格爾,說:
「保羅和我都是幹這一行的,誰曉得該怎麼教呢?教莎士比亞?那不難——也不容易,你得把莎士比亞的原文翻譯成英文。」
大家都笑起來。安格爾在他背後做了一個鬼臉。一同學忽然問他〈指令〉(Directive)一詩題目之用意。他搖頭,說他從不解釋自己的作品,而且:
「如果我把原意說穿了,和批評家的解釋頗有出入時,那多令人難為情啊!解釋已經作古的詩人的作品,是保險得多了。」 等笑聲退潮時,又有人請他發表對於全集與選集的意見。
「《英詩金庫》(Golden Treasury)固然很好,但有人懷疑是丁尼生的自選集(笑聲)。有人大嚷選集有害,宜讀全集。全集嗎?讀白朗寧的全集嗎?噁!」
接著他又為一位同學解釋詩的定義,說「詩是經翻譯後便喪失其美感的一種東西」,又說「詩是許多矛盾經組織後成為有意思的一種東西」,不久他又補充一句:「當然這些只是零碎的解釋,因為詩是無法可下定義的。」他認為「有餘不盡」(ulteriority)是他寫詩追求的目標——那便是說,在水面上我們只能看見一座冰山的一小部份,藏在水面下的究竟多大永遠是一個謎。他又說:「我完全知道自己任何一首詩的意義,但如果有人能自圓其說地作不同解釋時,我是無所謂的。有一次一位作家為了要引用我的詩句,問我是否應該求得我的出版商的同意。我說,『不必了吧,我們何不冒險試一次呢?』」
本年度佛洛斯特被任命為國會圖書館的英詩顧問。一位同學問他就任以來有何感想。他答稱,正式的公事只有四次,其一是艾森豪總統曾經向他請教有關祈求永久和平的一篇禱告詞。 「這種文字總是非常虛偽的,」他說。「人生來就註定要不安,騷動,而且衝突。這種衝突普遍存在於生命的各種狀態,包括政治和宗教。有一次我對總統說,既然羅斯福夫人,路透先生,及我所有受過教育的朋友們都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那我們何不參加幫忙,助其發展,且渡過這一階段?社會主義是無法長存的。」
如是問答了約一小時,「詩創作」一課即算結束。安格爾教授遂將班上三位東方同學——菲律賓詩人桑多斯(Bienvenido Santos),日本女詩人長田好枝(Yoshie Osada)及筆者——介紹給佛洛斯特。他和我們合照一像後,就被安格爾教授送回旅舍休息。
匆匆去藝術系上過兩小時的「現代藝術」,即應邀去安格爾教授家中。他的客廳裏早已坐(或立)滿了自愛奧華州首府德莫因趕來的各報記者及書評家等。晚餐既畢,大家浩浩蕩蕩開車去本校的大音樂廳,聽佛洛斯特的演說。還不到八點,可容二千多人的大廳已經坐滿了附近百哩內趕來的聽眾和本校同學。來遲的只好擁擠著,倚壁而立。八點整,佛洛斯特在安格爾的陪伴下步上了大講臺,歡迎的掌聲突然爆發,搖撼著複瓣的大吊燈。安格爾作了簡單的介紹後,即將一架小型的麥克風掛在佛洛斯特的胸前,然後下臺。老詩人撫著麥克風說: 「這樣子倒有點像柯立基詩中身懸信天翁的古舟子了。」
聽眾皆笑了,他們愛這位白髮蕭騷而不失赤子之心的詩人,正如愛一位縱容他們的老祖父。他們聽他朗誦自己的詩,從晚近的到早期的,一如在檢閱八十年的往事。在兩詩之間,佛洛斯特的回憶往往脫韁而逸;他追念亡友湯默斯(Edward Thomas),懷想大西洋對岸的故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感慨很深。他以蒼老但仍樸實有勁,且帶濃厚的新英格蘭鄉土味的語音朗誦〈不遠也不深〉,〈雪晚林畔〉,〈一叢花〉,〈修牆〉,〈僱工之死〉,〈窗前樹〉,〈分工〉,〈認識了夜〉及許多雙行體的小品。到底年紀老了,有好幾處他自己也念錯了;例如〈不遠也不深〉的第二行,他便將書上印的look誤為face了。將誦〈一叢花〉時,他說當初他應該加上一個小標題——「何以他留它在此」。關於〈僱工之死〉,他說那長工不是他的僕人,而是他的朋友,同事。他說他特別偏愛雙行體(couplet),因為它語簡意長;這種詩句往往在火車上或午夜散步之際閃現於他心中。有一次他在自己電視節目將完時忽想起了兩行:
呵上帝,饒恕我開你的小玩笑,
則我也將你開的大玩笑忘掉。
還有一次他寫了四行,
馬克斯和恩格爾:
這兩個騙人的難兄難弟,
打的算盤是如此的經濟,
把人類調得如此的整齊,
結果是一點酵也發不起。
直到九點半,佛洛斯特才在掌聲中結束了他寓莊於諧的演說。我隨記者及書評家們回到安格爾寓所,參加歡迎佛洛斯特的雞尾酒會。來自東方的我,對於這種游牧式的交際,向來最感頭痛,但為了仰慕已久的大詩人,只好等下去。十點一刻,佛洛斯特出現於客廳,和歡迎者一一握手交談。終於輪到我;老詩人聽安格爾介紹我來自中國,很高興,且微笑說:
「你認識喬治葉嗎?」
「你是指葉公超大使嗎?」我說。
「是啊,他是我的學生呢。他是一個好學生。」
「我有一位老師在三十年前留美時聽過你的朗誦。在國內時他曾經幾次向我提起。」
「是嗎?那是在哪兒?」
「在波士頓。」
「啊!臺灣的詩現狀如何?」
「人才很多,軍中尤盛,只是缺少鼓勵。重要的詩社有藍星,現代,創世紀三種。你的詩譯成中文的不少呢。」
於是我即將自己譯的「請進」,「火與冰」,「不遠也不深」,「雪塵」四首給他看。他瞇著眼打量了那些文字一番,笑說:
「嗯,什麼時候我倒要找一個懂中文的朋友把你的譯文翻回去,看能不能還原,有多大出入。」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能譯一點詩的人誰沒有先讀過你的詩呢?」
接著他問我回國後是否教英國文學;當我說是的時,他問我是否將授英詩。我作了肯定的答覆。他莞爾說:
「也教我的詩嗎?」
「也教,如果你將來不就自己的作品發表和我相異的解釋的話。」
記起剛才下午他調侃批評家們的話,也笑了。談話告一段落,我立刻請他在兩本新書的「現代叢書」版的《佛洛斯特詩集》之扉頁上為我簽名。他欣然坐下,抽出他那老式的禿頭派克鋼筆,依著我的意思,簽了一本給夏菁,一本給我。給我的一本是如此:「給余光中,羅貝特‧佛洛斯特贈,並祝福自由中國,一九五九於愛奧華城。」夏菁是我的詩友中最敬愛佛洛斯特的一位,這本經原作者題字的詩集將是我所能給他的最佳禮物了。 然後我即立在他背後,請長田好枝為我們合照一像。俯視他的滿頭銀髮,有一種皎白的可愛的光輝,我忽生奇想,想用旁邊几上的剪刀偷剪幾縷下來,回國時贈藍星的詩人們各一根,但一時人多眼雜,苦無機會下手。不久老詩人即站了起來,和其他來賓交談去了。十一點半,安格爾即送他回去休息。
林中是迷人,昏黑而深邃,
但是我還要赴許多約會,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佛洛斯特曾說他是一個天生的雲遊者;當他在音樂廳朗誦「雪夜林畔」到此段時,我忽然悟出其中有一種死的象徵,而頓時感到鼻酸。希望他在安睡以前還有幾百哩,甚至於幾千哩的長途可以奔馳。
艾略特的時代
「選擇一首好詩並揚棄一首劣詩,這種能力是批評的起點,最嚴格的考驗便是看一個人能否選擇一首好的『新詩』,能否對於新的環境作適當的反應。」這是美國大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在他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詩與批評之用途」中的一句話。處於當前自由中國新文學的環境,我們尤其欣賞、重視這意見。對於批評家最嚴格的考驗便是看他能不能選擇一首好詩,尤其是好的新詩。選擇一首好的舊詩並不太難,因為我們對於古代的作者已經有了透視的距離,秋毫和輿薪之間的比例我們已經瞭然,當時作者間的互相品評,與乎後之學者的長期淘汰,可以作我們的參考;也並不太容易,因為我們對於傳統每有過份的崇拜,對於習俗缺乏自覺的分析。 反叛傳統,但同時並不忽視傳統,是艾略特對於詩的一貫態度。做一個大批評冢他必須了解傳統,熟悉受他批評的對象;而做一個大詩人,他必須披荊斬棘,另闢天地的抱負與能力。艾略特對於現代文學的貢獻,在創作和批評兩者的影響,可以比擬十九世紀初的柯立基,而猶過之。一九四八年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頒予艾略特,即為獎勵這種開風氣之先的精神。 艾略特於一八八八年九月廿六日生於美國米蘇里州的聖路易城。他的祖先原居新英格蘭,出了不少大學校長和牧師,據說最早的先人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湯默士‧艾略特勳爵(Sir Thomas Elyot, 1499-1545)——當時有名的散文家,曾任英國駐西班牙大使。父親是聖路易的商人。艾略特在聖路易讀完中學,便去東部進哈佛大學。一九○九年他獲得文學士學位,一年後,又取到文學碩士學位,遂橫渡大西洋,在巴黎大學研究一年,旋又回到哈佛,以三年時間撰寫博士論文。一九一四年,他去英國,在海給特學校教書,其後復在洛依茲銀行工作,一面開始編輯《標準季刊》(Criterion Quarterly)。他的處女詩集《普魯夫洛克》(Prufrock)出版於一九一七年;第一本批評文集《聖林》(The Sacred Wood)出版於一九二○年;兩年後,艾略特發表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荒地》(The Waste Land),遂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中崇高的地位。此後他的聲譽扶搖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歸化為英國人,且宣佈自己「以宗教言,為一英國天主教徒,以政治言,為一保皇黨員,以文學言,為一古典主義者。」他在文學上的榮譽極多,其中包括劍橋大學與哈佛大學的講座,牛津與劍橋的榮譽研究員,以及歐洲與美國十四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一九四八年,他更榮獲英國的O.M.勳章(Order of Merit)與諾貝爾文學獎。 艾略特是二十世紀對於英美,甚至是全世界,詩壇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他不是一位多產的作者。在創作方面,自一九○九年以迄一九五○年,他的總產量是七十首詩和三本詩劇。在批評方面,他的文集已經超過十五卷。艾略特的題材和視界是狹窄的,他的風格變化不多。他的天才是集中的,不像畢卡索那種波賽遁(Poseidon)式的善變,也不像克利那種流星雨式的揮霍靈感。《普魯夫洛克》出版於他廿九歲那年,其中最重要的一首作品〈普魯夫洛克的戀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創作日期更早在他的大學時代。其後陸續出版的的集子有《一九二○詩集》,《荒地》,《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精靈詩集》(Ariel Poems),《未完成的詩》(Unfinished Poems),《四個四重奏》(Four Ouartets)等。《空洞的人》是他哲學觀念的分水嶺,在這以後,艾略特自懷疑歸於信仰,自歷史的社會觀轉為宗教的社會觀,自混亂的現象復返依有秩序的原則。他在〈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寫道:
我們所謂的開端常是結尾,
而結尾常常只是開一個端。
結尾是我們出發的起點。
然而影響現代文學至鉅的不是艾略特後期這種帶有濃厚宗教氣氛的作品,而是早期那種以對比為主要表現手法的詩。籠罩著艾略特早期作品的一種含有甚重的「時間之鄉愁」的歷史感。在現代的世界裏,我們找不到光榮、偉大、安全、以及完整;在「過去」的面前,「現在」是自卑的,醜惡的,破碎的,彷徨的。艾略特的境界正如歷史的通衢與個人的小巷交叉的十字路,渺小而無意義的個人徘徊其中,困惑於大街的紛擾與小巷的陰鬱,目眩於紅綠燈的交替。這種知識份子的幻滅與壓抑感因外界的波動與內心的混亂之交互感應而更形複雜,遠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興衰之感所能包羅。作一個較好的譬喻,我們可以說,讀艾略特早期的詩,有如俯窺一株水仙花反映在投過石子之水面的破碎的倒影。
每天早晨你都能看見我,在公園裡
讀著漫畫和體育版的新聞。
特別令我注意的常是
一個英國的伯爵夫人淪為女伶。
一個希臘人被謀殺於波蘭舞中。
另一個銀行的騙局已破案。
我卻是毫不動容,
我始終沒有心亂,
除非當街頭的鋼琴,單調且慵困地
重覆一首濫調的平凡的歌,
而風信子的氣息自花園對面飄來,
使我想起別人也要求過的東西。
這些觀念是對還是錯?
這種忠於現代生活之偶然性與瑣碎性的恍惚迷離的意象,對於頓足搥胸的浪漫主義是一種反抗。起首的兩行就「暗示」這位以第一人稱「我」出現的人物之卑瑣與無聊。第三行至第五行反映出一個沒有落的世界——英國貴族的式微,希臘傳統的蕩然,以及現代道德的混亂——然而這一些並不足以亂「我」的心。接著是單調的琴音,風信子的氣息,對於他人秘密的情慾之一瞬間的同情,結果還是面臨困惑。事實上,現代生活就是由這些粉然雜陳的支雜破碎的「現象」拼湊而成;美是不太美的,抱歉得很。美本身在二十世紀便是值得懷疑的東西。艾略特堅持,一位詩人應該能透視美與醜,且看到無聊、可怖、與光榮的各方面。在他的詩中,美與醜,光榮的過去和平凡的現在,慷慨的外表和怯懦的內心,恆是並列而相成的。現代主義在美與真之間,寧取後者。現代的大作家,無論是艾略特或奧登,漢明威或福克納,皆寧可把令人不悅的真實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不願捏造一些粉飾的美,做作的雅,偽裝的天真。 較之艾略特的「哲學」,更重要的是他的富於暗示的技巧。他從法國詩人拉福爾格(Jules Laforgue),藍波、魏爾崙,與柯比艾爾(Tristan Corbie)悟出暗示勝於坦陳的原理,乃發揚光大,使之接近超現實主義,而展現出一個現實與幻想交融的世界。他將直述與婉說,情慾與機智,事實與徵象溶為一爐。在他的詩中,一種不可捉摸的音樂起伏於莊嚴與庸俗之間;情緒形態之傳達代替了固定情感的刺激感應。在現實的灰色霧後,隱約可見歷史的堂皇遠景。這種交疊的表現法在電影中早有了很好的運用。
「波士頓晚郵」的讀者們
搖擺於風中,如一田成熟的玉米。
當黃昏在街上朦朧地甦醒,
喚醒一些人生命的慾望,
且為另一些人帶來「波士頓晚郵」,
我跨上石級,按響門鈴,疲倦地
轉過身去,像轉身向羅希福可點頭說再見,
假使街道是時間,而他在街的盡頭,
而我說,「海麗雅特表姐,波士頓晚郵來了。」
羅希福可(La Rochefoucauld)是十七世紀法國的散文家,以明暢簡潔,幽默見稱。歷史的斯芬克獅恆蹲守在人類的去路上。「波斯頓晚郵」是切身的現實,羅希福可是渺茫的往昔;然而現實與往昔畢竟是如此的不可分。一迴首而見羅希福可的幢幢巨影;這種突如其來的一驚一疑正是現代詩的特色,而這種超現實主義的表現法令我們想起了達利(Salvador Dali)的「伏爾泰的幻象」。 艾略特的影響遍及於大西洋兩岸。年輕的詩人們拒絕接受他那種戴了古典主義之假面具的浪漫主義,他的退入英國天主教,以及他那種掩蓋不了死亡願望的悲觀主義,可是他們卻贊美,並學習,他的暗示能力。在英國,奧登,史班德與路易斯公開承認他的啟示;在美國,他感召了艾肯,麥克里希,格瑞格里,及其他作家。和佛洛斯特不同的是:佛洛斯特是民族性的,艾略特是國際性的,佛洛斯特是現代詩中獨來獨往的人物,而艾略特是開風氣的大師,他把英詩從二十世紀貧血和虛偽的治朝詩人(Georgian Poets)的陷阱中救了出來。 在英美的批評界,艾略特的地位亦很崇高。他對於伊麗莎白時代的劇本,十七世紀的玄學派,法國的象徵詩人等有很深邃的研究。他重新予拜倫的長詩以較高的評價,而將米爾頓自古典書架的第一欄搬到第二欄。儘管晚期的論調因趨向保守而令批評界驚訝,他的論文仍是非常發人深省的。在學問的豐富,思想的精妙,態度的冷靜與乎文字的清晰各方面,很少學者能與他匹敵。以下讓我們翻譯艾略特論傳統的一段文字,以結束對這位開風氣的大師的簡介: 「陶醉於懷古的傷感中,是毫無益處的。第一,即使在最優秀的活的傳統之中,也恆有優劣因素的混合,和許多有待批判的成份;其次,傳統也不僅是感情方面的事。同樣地,如果不加以充份批判的研究,我們也無法很有把握地固執幾個教條式的觀念,因為在某一時代認為是健康的信仰,如果它不是少數的基本因素之一,到了另一個時代就可能變為一個危險的偏見。同樣地,我們也不應該株守傳統,以保持我們對於比較不受歡迎的人們的優越地位。」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