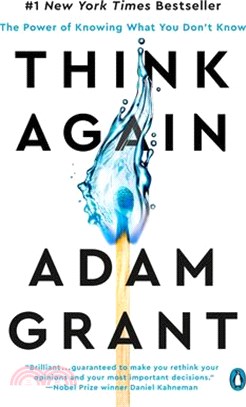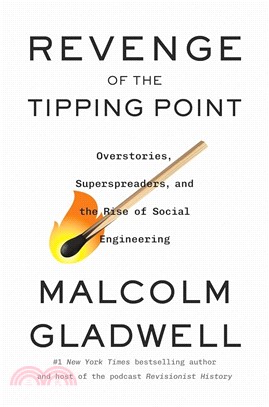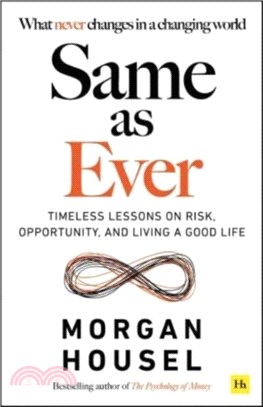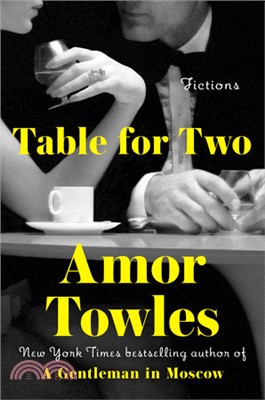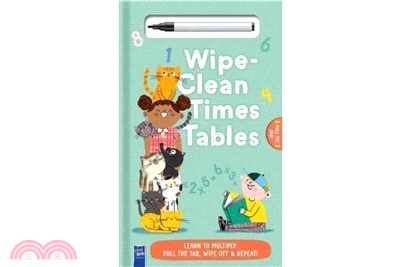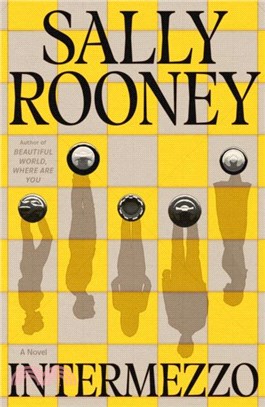流浪者系列02:繼任者
商品資訊
系列名:幻想藏書閣
ISBN13:9789869272896
替代書名:The Successor
出版社:奇幻基地
作者: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
譯者:吳淑華
出版日:2016/07/07
裝訂/頁數:平裝/448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勒胥聖魂回歸,他的一切一夕改變,他拿到了先知咒符,卻開始黃金鏽蝕、眾叛親離,黑暗讓他無路可走、別無選擇、成為「外來者」的僕人……
金色的東西在陌生老人的手掌裡閃爍著。
老人玻璃般透亮的眼底掠過一抹陰影,無睫毛、厚皮的眼瞼眨了一下:
「你的家庭依舊帶著印記,梭爾。這是命運。」
舊城每到歡騰節依習俗要在廣場上砍下罪犯的頭顱,多年後改由街頭藝人用戲劇表演斬首來娛樂群眾。許多流浪劇團來到城內只為賺取大批賞金。
衛兵隊上校伊葛‧梭爾、大學院長朵莉亞的兒子路偃爾,在繼任了傑出英雄和知名學者的貴族後裔身分壓力下成長,習慣安靜不被注意。而命運安排了喜劇演員唐塔莉與他相遇……
一次戲劇演出之後,讓伊葛想起了懦弱之咒,從此不知所蹤,整個家族陷入愁雲慘霧。路偃爾為踏上尋父之旅而加入了唐塔莉的流浪劇團。
勒胥修會的聖魂依然作祟——塔樓的「勒胥密令」、黑荒疫的散播、流匪之亂、孩童之死、伊葛和朵莉亞隱藏多年的祕密——在兩人的旅途中一一被揭開……
當再一次先知咒符的黃金沾上銹蝕,一個陌生人站在門邊時,他是選擇要打開門讓第三元力進來毀滅世界還是選擇死亡?
「心理系」奇幻大師夫妻檔——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文筆獨特優美,人物描寫細膩,筆法與英語系作家完全不同,特殊的敘事腔調,以及帶有俄羅斯童話色彩的奇幻氛圍,有如魔法版《罪與罰》在語言形式和人物內心的探究上,均承繼了優良的俄國文學傳統。
作者簡介
賽爾基&瑪麗娜.狄亞錢科Sergey and Marina Dyachenko
這對烏克蘭夫妻檔作家賽爾基和瑪麗娜.狄亞錢科文壇佳偶,其小說和短篇作品已獲得眾多文學獎座的肯定,並榮獲2005年歐洲Eurocon最佳科幻小說作者大獎,目前兩人定居於基輔。發表於 1997 年的奇幻小說《傷痕者The Scar》,是狄亞錢科夫婦「流浪者系列」(Wanderers Series)四部曲的第一集,與前傳《守門者The Gate-Keeper》幾乎拿遍俄國所有的奇幻文學大獎,也奠定了他們「心理系」奇幻大師的地位。
序
序
小男孩坐在滿佈灰塵的箱子上。窗簾遮蓋著窗,有如柱子覆蓋上厚重的灰塵一般。當陽光灑下,灰白色的蝶蛾倉皇地四處飛散。
窗外傳來鐵片的叮噹聲和馬蹄踏地的聲響。屋外有人喊著「敵人」、「戰爭」;屋內,這裡是父母親曾待過的地方。他們如同這些頂著天花板的光柱,堅毅地護衛著這個家......
他很怕這個老人。老人既陌生又無法理解;因為他,親人的行為舉止都跟以往不同。父母親並未把注意力放在兒子身上,老人彷彿像是小男孩頭頂上的烏雲。他們也怕這老人,但為何要交給他這東西?
小男孩哭後,擦拭眼淚。這東西...... 這迷人的東西。難道不能再擁有它了嗎?媽媽從珠寶盒裡拿出這個東西,允許他可以用手指摸一下當作獎賞。這樣開心的時刻難道也不會再有了嗎?看呀看的,視線跟著天花板上的光影游移著......
他們說了甚麼有關鏽斑的事,但也沒看見甚麼鏽斑,還有關於戰爭的事。小男孩想像整片的戰茅森林,細長的旗幟有如分叉的蛇信一般...... 眾多的紅衣騎士,飄散著令人愉悅的火藥味...... 他的父親戰勝了所有的人。
但為何老人只是沉默地點著頭呢?!
小男孩用眼淚沾濕的手指在箱子上畫了一張可怕的鬼臉。以前當他畫鬼臉時就會被罵,而現在他特別高興。他露出了歪斜、下垂的嘴角,皺著眉頭,心理想著:嗯,就給他吧...... 就讓他......
於是金色的東西在陌生人的手掌裡閃爍著,在那老人修長的手掌裡。此刻小男孩忍不住號啕大哭,急忙地從自己躲藏的地方跑了出來,想要奪走玩具。他不相信這一次他不可以任性妄為。
「路偃爾!」
母親臉頰泛紅,父親嚴厲斥責,而男孩也對自己激動的行為感到後悔。因為老人用審視、銳利的眼光逼視著他許久。還有一件奇怪的事:男孩的小短褲是如何變成乾的?
老人玻璃般透亮的眼底掠過一抹陰影;無睫毛、厚皮的眼瞼眨了一下。男孩蜷縮了起來,老人把目光轉向他的母親,說道:
「您為他取了一個紀念羅偃的名字?」
窗外傳來軍靴鐵片叮噹作響的聲音,有人大聲吶喊著重要的決策和命令。老人嘆了口氣道:
「當一塊石頭從高處掉落...... 總是期待它可以掉入坑裡。也不會發生雪崩。我們總是如此期待。」
男孩哽咽著,用握成拳狀的手擦拭著眼睛。他躲在父親外套袖子後面,因此沒看見父母親詫異地互使眼色。
老人陰鬱地冷笑,說道:
「你的家庭依舊帶著印記,梭爾。這是命運。」
母親驚嚇地瞪大雙眼;父親沉默地托著臉頰,彷彿受著牙痛之苦...... 老人點頭說道:
「不過...... 沒什麼,我胡謅的。你們忘了我說的話吧。」
當老人身後的門一關上,在失落感中頓時多了份輕鬆。
他的手陷在那溫熱的手掌裡。你將會有許多其他的玩具。別難過了,我親愛的小太陽。
第一章
1
我們終究趕上了!幸運的是城門在我們一進入後便砰地一聲關上了。原本城門可能會在我們抵達前就關上,弗拉巴斯特還因此怒斥,咒罵了一整路。我們會遲到了是因為輪軸壞掉了,而輪軸會壞掉是因為昏昏欲睡的穆哈沒有看見路上的坑漥;穆哈會昏昏欲睡是因為弗拉巴斯特叫我們通宵達旦地排演...... 這樣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跑一趟鐵鋪。弗拉巴斯特嘶啞地和鐵匠議價,他吐了一口口水之後,還是付了錢,然後又打了穆哈好幾下。
由於時間已近夜晚,當然沒人還有力氣高興我們在城門關閉之前抵達了這件事。這裡早就開始了慶祝活動,街上人潮洶湧,明天也會是如此...... 我們沒有人會抬起頭看著掛在高聳於屋頂上那金色的風信旗,只有穆哈例外,他不時張開小嘴驚奇地看著城裡的新事物。
主廣場看來已經全被機靈參賽者的馬車和帳棚佔滿了,在激烈的搶奪下我們佔到了角落的位置,十分勉強地停放了三輛我們的四輪貨車。我們的左邊是四處漂泊的馬戲團,疲憊的熊在室外的獸籠裡沮喪地咆哮著;右邊駐紮了木偶戲團的演員,他們打開箱子,裡面有大型木偶的木製雙腳,看來有點可怕地直立著;對面則搭建著我們熟識同行的帳篷,他們是沿海地區的雜技演員。有幾次我們在一些市集裡和他們偶遇,那時候他們可是搶走了我們為數眾多的錢幣;而南面所有的通道都搭建了舞台。弗拉巴斯特變得陰鬱了起來,我繞到另一頭好偷偷噗哧地笑:哈-哈,莫非老頭以為我們在這兒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團體?顯然在歡騰節期間從任何地方前來的人,即使是最遙遠的地方都可以任意在此駐留,但先決條件只有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但也非常奇怪的條件。節目的第一幕必須要有砍頭的表演,任何人或形式都可以。市紳們的品味實在怪異,哪怕拿個滑稽的木偶上絞刑台,把頭吊在法院前做為裝飾,這樣也行。
慶祝活動在黎明時分便開始了。
我們甚至有點瘋狂,畢竟我們是漂泊的表演者,而非一群無依無靠的鄉下孤兒,我們的人生都在節慶或嘉年華會場合表演。這是一個富裕之城,居民富有且自滿。穿著鑲金邊制服的僕人站在鑲金四輪轎式馬車踏板上,驕傲至極,小販扛著奢華、稀有的貴重物品很吃力地站著;城市居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在小提琴和鈴鼓的伴奏下在廣場那兒翩然起舞,甚至連流浪狗似乎都有人照料,而且都有股高傲之氣。
流浪歌手相互拋擲著高溫的火把,走鋼索的演員在叮噹作響的高空架上跳舞,他們騰空而下,完美地落在觀眾圍成的圓圈裡。在繩索架上,某個穿深黑針織緊身衣的人看起來像蜘蛛,又像蒼蠅的 (順道一提,穆哈從攤子上拿了某個東西對著弗拉巴斯特自誇,弗拉巴斯特就是那個一直揪著他耳朵在紅白衛兵群眾中鑽來鑽去的人。)
接下來輪到我們了。
第一幕劇是木偶搏鬥–只是用來表演砍頭給人看的,木偶表演不過是齣極短、毫無意義的滑稽劇碼。頭從主角身上飛了出去,有如軟木塞從香檳酒瓶飛離一般。看起來像是挨餓的消瘦女孩拿著帽子繞著人群來回走動,但打賞的人很少,看樣子觀眾是不喜歡這個表演。
一旁的熊發出吼叫聲;身材魁武、穿著肉色針織緊身衣的盜賊扭轉著小夥子那顆如橡皮般的小腦袋瓜子,最後假裝把他的頭擰開了。在此關鍵時刻小夥子被折成一半,那一瞬間我膽顫心驚,誰知道這些雜耍演員......
小夥子鞠躬謝幕,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熊看起來像隻老狗,不情願地用後腳站立繞了一圈,遞出的帽子很快地就裝滿了錢幣。
南方人讓我們先上台演出,握了握弗拉巴斯特的手,說道:「開始吧。」
為了歡騰節我們準備了個遊戲,叫做「膽大的歐拉勒與不幸的玫瑰」。想當然耳,不是我扮演不幸的玫瑰,而是蓋茲娜。她必須要對她心愛的歐拉勒說出大量獨白,接著要為他的去世而哭泣,因為劇中套著肥厚外套的劊子手砍下了男主角的頭顱。劇本是弗拉巴斯特寫的,但我怎麼也不敢去問他:為什麼要特別去折磨高尚的歐拉勒呢?
扮演歐拉勒的人是巴瑞安;他吃力地擔任著我們劇團裡所有情人的角色,但這不應該是他該扮演的角色,他已經老了不太合適......。弗拉巴斯特面帶陰鬱地答應讓他盡快改演優雅父親的角色,但試問,又有誰同情劇中劇的蓋茲娜呢?穆哈是目前演出情人角色的人選,可是他僅僅十五歲,他只到蓋茲娜的肩膀......
我透過布幕看過美麗的玫瑰,她戲服的下襬及鬆開的頭髮神靈活現地攤開在舞台木板上,對著觀眾控訴著為何給了歐拉勒這種殘忍狠毒的結局。美女蓋茲娜老是用豐滿的胸部、細緻潔淨又瑰麗的臉孔,還有那陶瓷娃娃似的湛藍雙眸獲得觀眾的垂青,那時她搬出演員的看家本領,激昂的喊叫聲,伴隨著令人憐惜的啜泣,撼動了群眾。其實也不需要太多,只要為劇中愛人之死,成功地擠出兩、三滴淚水就可以了。
正因為現在蓋茲娜睫毛上閃爍著這兩滴珠淚,觀眾沉靜了下來。
在後台彷彿可以聽見劊子手沉重的步伐-弗拉巴斯特穿上自己那件肥厚外套,故意盡可能地將頓足聲放大。高尚的歐拉勒頭放在斷頭台上;劊子手擺弄著帶有缺口的巨大斧頭好嚇唬美麗的玫瑰,而後他揚起手許久,當他的武器落下時巴瑞安的首級也伴隨著落下。
按照弗拉巴斯特的構想,斷頭臺有小簾子遮住-因此觀眾只能看見處決者的肩膀以及劊子手揮刀砍人的動作。然後某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從布幕的缺口中遞出被砍下的首級。
哎呀,這算甚麼頭顱!弗拉巴斯特持久熱情地用制型紙塑造出這顆頭顱。這顆頭十分像巴瑞安,只是整顆顏色為紅藍色,脖子帶有血水痕和黑色鋸痕;真可怕,這才不是顆頭顱。當劊子手弗拉巴斯特扯下那塊鋪著在托盤物品上的方巾,抓著頭顱上頭髮的墊圈展示給觀眾看,女士中的某人有可能因此噗通一聲栽倒暈過去。弗拉巴斯特可是對自己這個點子非常引以為傲呢。
總之,弗拉巴斯特抬手揚起斧頭,而我準備將放有可憐歐拉勒頭顱的托盤遞給他;沒想到一瞬間呈現在我腦海、落在我身上的道具,像是為了貪婪牧女準備的惡作劇。
一顆大白菜球莖。
我的天。,哎呀,為什麼我做了這種事?!
好像誰抓住了我,把可怕的紙頭顱放到一旁,我穩妥地把白菜球莖放在托盤上並在上頭擺上頭巾。美麗的玫瑰用手掩面痛哭失聲;觀眾前巴瑞安可見的身體抽蓄幾下後安靜了下來。
劊子手於斷頭台前彎腰致敬-而我看見了弗拉巴斯特伸長了的手。已經來不及用甚麼將它換掉;我把托盤遞給了他。
這一分鐘是怎麼過的啊!?我被炸成了有兩個同樣強烈感覺的兩半-來自弗拉巴斯特鞭刑的恐懼和渴望看到現在舞台所發生的......。不,第二種感覺看似比較強烈。我緊貼著布幕顫抖。
美麗的玫瑰痛哭著。劊子手將托盤展示給她看,嚴肅地看向觀眾......然後撤下方巾。
我的天。
這廣場是如此安靜無聲,看來,他們是不明白今日自己所看見的素材。緊接著安靜無聲之後突然爆發一陣大笑,而許多風信旗上習以為常的市鴿因此騰空飛起。
沒有人看的見弗拉巴斯特的面孔-它被劊子手的紅色面具蓋住。這點我承認我早就考量到了。
美麗的玫瑰把自己漂亮的櫻唇張到了極致,體型不大的烏鴉都可能自由地飛進飛出。在她的臉上凍結著如此真切又無比氣惱的訝異,身為一個平凡演員的蓋茲娜這輩子是絕對不可能演得出來的。很多人因哈哈大笑而長嚎;對手警覺的面孔從所有帳篷和簡易的小戲台探了出來,心想:這些吹毛求疵老練的市民們市發生了甚麼事?
而此時弗拉巴斯特能做的事只有急忙抓起白菜球莖的部分,並滿是激烈地將其穿到頭上。
......好不容易退到了幕後,蓋茲娜揪住我的頭髮:
「這是妳幹的?妳幹的?妳幹的?!」
弗拉巴斯特緩緩費勁地脫下劊子手的斗篷;他的臉看起來完全毫無畏懼般。
「弗拉團長,這是她做的!唐塔莉毀了我的舞台生涯!她毀了我們的劇目!她........」.
「安靜,蓋茲娜」,弗拉巴斯特不太高興地說道。
容光煥發的穆哈現身了-整個盤裡都是賞錢,錢幣堆得像座小山,而且他們不時微微發亮。
「冷靜下來,蓋茲娜」,弗拉巴斯特說著,「我准她的。」
輪到我托著下巴。
「是嗎?」,巴瑞安冷靜地重問了一次。「正如我所見,我很喜歡......」
沒料到會這般......觀眾愛極了,是吧,穆哈?
蓋茲娜滿臉通紅,嗤地一聲後走開了。我開始同情她了,大概不該開這個玩笑。蓋茲娜她太嚴肅了..現在她將會氣上許久。
「我們走吧」,弗拉巴斯特對我說道。
當我們放下馬車的簾子,他重重地揪住我的耳朵,而且用力扭轉。
可憐的穆哈,如此搞了一整天!我的雙眼因疼痛而一片灰暗,當我再度看見弗拉巴斯特,看起來像是我眼淚婆娑地看他。
「妳想,有准許妳這麼幹嗎?」,我的折磨者問道並又再度拉扯我的耳朵,我尖叫一聲隨即跳開。
「儘管再試試看」,他從齒縫中回應著。「再試一次看看......扒了妳的皮。」
「觀眾可是很喜歡啊!」,我啜泣起來,吞聲飲泣。
「賞錢更多了......」。
他走向我–我住了嘴,把背縮進防水布幕裡去。
他抓住我的另一隻耳–我瞇起眼睛,他扯著它,彷彿沉思般;而後放開說道:
「妳再變花樣看看,我就把妳賣到馬戲團。」
他走了,而我想了一下:就這麼容易脫身了。這可是可能會招來鞭打的......
不過,弗拉巴斯特假若沒有面具遮住他驚嚇瞪大的雙眸,他是怎麼都不可能饒恕我這些出乎常軌的舉動。
2
「鼩鼱」小酒館主人天生就不愛說話。
小酒館老闆記性很好;他知道今天他的客人看上了哪支酒,不過,這裡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要知道,客人可是城裡響噹噹又尊貴的人物......
小酒館主人明白在這天客人不想引人注目;一早這張桌子就留給了他,屏風把酒店裡歡慶的人潮給隔絕開了。
這位城裡的名人已經一連數年來此並坐在這張單人桌,得以從容不迫地啜飲著自己極其講究的飲品。
老闆多年來觀察這獨特的儀式,清楚地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麼。
當貴賓的酒杯大約空了一半,門旁就會出現一位又高又瘦弱的身影;在門框前的某個陌生人點了下頭,否則他不會走過去,只用冷漠的目光環視整個酒館。陌生人是一個有著如同裏海鷗鯉那般晶瑩目光的枯瘦老頭;不停對酒館老闆點頭,他每次都由隔牆後方往桌子那頭逕直走去,酒店老闆了解陌生人需要的是哪種酒–老頭的品味跟和他共同進餐的人口味不一樣。
酒館老闆可以立誓,這兩個人從未開口對話過。城內貴客沉默地喝完自己的半杯酒;老頭稍稍抿了一口自己的酒,便起身離開了。客人坐在桌旁替自己又點了一杯酒及道地的下酒菜;假設之前他看起來是愉悅又緊張的,那麼老闆現在捕捉到他眼底的放鬆–卻同時有些失落。慷慨地付了帳,令人尊敬的城市人離開酒店時不停地對酒館主人點頭告別。
「鼳鼱」主人非常明白,這般不可磨滅的印象要是向鄰居提及這些事件,年復一年重複,–總是在歡騰節這日,老闆預料消息靈通的長舌婦會很欣喜–但他天生沉默寡言,也可能是因為某件不可思議的事件使得聰穎的老闆保持沉默。
3
就在那個時候節慶照常進行。
我們的南方對手們獻給可敬的觀眾一部巨大且排長講究的短篇文藝作品,開演前貼了公告好讓所有人可看到《勒胥修會的故事》。
在我們舞台前的群眾逐漸倒戈轉向對面的舞台–我們也湊熱鬧地往外瞧。「故事」從巨大破布製木偶砍頭橋段開始–這顆頭,說句不好聽的,就是用鈕釦接在襯衣領子上。之後就成了勒胥神聖的模樣–高蹺上魁武的小伙子,到眉毛處都被灰斗篷遮蓋住。按作者的設計斗篷的邊緣被蠕蟲蛀壞,這樣可以讓觀眾聯想到潮濕的墓地,而非一個蟲蛾攀附其上的大箱子,下擺處綴上些許肥滋滋的蚯蚓–我的天!,這鮮明、精力充沛的景象,似乎就像是在釣魚場一樣.........
觀眾在此時被嚇到了。孩童們因恐懼驚聲大叫,神聖的鬼魂像五月的貓般嚎叫起來,–我敢保證,觀眾受了這幕影響!假設勒胥的聖魂就同真正看到一樣,那到底他從哪來的這群追隨者。
我驚訝到來不及思考,勒胥修會的信徒就出現在舞台上了!全部有四人,因為南方人的劇團很大;從前面他們看起來像戴了兜帽的稻草人,而從後面看每個人被畫上骨架,這個別具寓意地用以闡述,其實勒胥成員們散播著死亡。觀眾們開始鼓掌,據說,市民中充滿荒疫的目擊者,十九年前這場荒疫讓附近地區半數以上的居民們死亡;根據傳聞,這場荒疫是被勒胥信徒叫喚出來的......
當時我很幸運地尚未出世;我那消瘦又蒼白的母親喜歡提及我們家族是如何強大、富裕又有名。荒疫幾天內吞噬了他們:我的祖父和祖母,甚至叔伯、嬸嬸們,堂兄弟姊妹分配到一個巨大的墓地,他們的房子被火焚毀,而財產被趁火打劫了。整個家族只有我母親和她弟弟從毀滅中逃過一劫;剩下的龐大家產在十年間逐漸減少,我的童年在偌大空蕩的房間度過,裡面全是具貴族血統、稀有的狗兒,散亂的書本全雜亂無章......
母親過世後小叔叔把我監禁在孤兒院。在孤兒院開始我被稱叫作弗拉巴斯特。
......弗拉巴斯特在我耳邊大聲地吸著氣,看來南方人懂得如何獲得青睞,而我們必須好好地準備,好吸引愚蠢的看官們到我們這邊來。
《勒胥修會的故事》獲得空前的迴響,雙頰緋紅的小妞扮演正義代表,在卸下的艙門處靈活地戰勝了勒胥兄弟,在那他們還痛苦地呻吟並抱怨著。觀眾瘋狂了般鼓掌,弗拉巴斯特做了個不滿意的表情並當穆哈也準備拍手時朝他發出噓聲。
半小時候我們依舊尚未開演,因為就在隔壁展開了鼓手們的對決。雙方在耳朵上掛了自己的樂器,還有地上擺了尺寸像水井木架般大的巨鼓。轟隆聲停了下來,塞住耳朵;眾人時而輕聲鼓掌並吹口哨和音,可憐人們拼命使勁讓他們的鼓發出怒吼狂嚎,誰也無法壓過對方。終於,巨鼓的主人跳躍到鼓上,用腳使盡全力往死裡打,腳掌彷彿像燃燒起來而跳動,他獲得了如雷般的掌聲,隨即劈啪一一聲後消失在巨鼓裡面。在聲響中決戰結束了。
我們表演的時刻來臨了,讓《公主與獨角獸》的劇目演出讓觀眾來評論。
我欣賞這齣創作,弗拉巴斯特跟某位流浪作家以高價買下它;作品內容描述公主(蓋茲娜)愛上了貧窮青年(巴瑞安),但邪惡巫師突然將她的愛人變成了獨角獸。說真的,本人認為,假設巫師是如此這般的邪惡,就不要讓他變成高尚的獨角獸,他可以變成其他東西,汙水桶或是有洞的皮鞋......真的,等等試試修改內容,把主角變成垃圾桶......
方慶扮演巫師,我們永遠的惡棍,除他沒人懂得怎麼橫眉豎目、嫌惡地撇嘴及惡毒咒罵;看在公平分上這麼說吧,除了這些外他甚麼都不會。我們的方慶是個善良又愚笨的人。他就幹些繁重的活。
巴瑞安和蓋茲娜演唱二部合唱,蓋茲娜有著高亢、銀鈴般的聲音,因它失去理智的不只有市集的商賈,甚至也有大人物......說正格的,沒有「莊嚴的愛情」蓋茲娜可是不願意與人接吻的,我的印象中這樣的愛情大概有六或七次吧。
表演不好不壞地進行了;接近終場時看倌們開始感到不耐。微調變換舞台的情境,穆哈用力敲打銅盆,弗拉巴斯特揮動金屬錫片,而巴瑞安在煙霧團中抽畜(是我在台架下點燃潮濕的麥秸束)。不過沒有任何幫助,在我們舞台前的觀眾看得出越來越少。
南方人齜牙咧嘴地笑著。該想辦法挽救局面回來。
穆哈拿著盤子很快地跑向觀眾,賞錢比一半還少,那邊已經開演喜劇《戴綠帽的丈夫》了。又有一些市民加入我們的觀眾行列–在這裡我看見了金髮先生。
真是不可思議。他高出觀眾一整顆頭–像是小球在浪潮上。來自四周的人都盯著他的那雙每到不可思議的眼眸直看,像是日光下閃閃發光的兩塊冰。他已不再年輕,不過要稱他是老人家也是讓人難以啟齒的。我的人生中從未遇過如此多的尊貴之人;他就像是栩栩如生的雕像,像是偉大將領的青銅像。現在這尊紀念雕像看向我們這方,看得出來這沉思者是要走還是要留下來。
金髮先生,您別走啊!!
我差一點就等到了,目前弗拉巴斯特帶著辦事員配飾,結束自己的獨白,他據說是位冷酷的先生,而他的太太則是美德之光。
當我帶著假胸部及翹臀急忙跑出舞台時,他剛好說完最後一句台詞。我像是豌豆粒從調皮鬼的煙袋跳了出去;對我來說這個廣場上現在只存在一位觀眾而已。
哎呀,我扮演一個感到絕望的太太,如此有美德,如此善良,或許,善良的男士允許我和“閨密”倆一起做著繡工?
“閨密”穿著細高跟鞋搖搖擺擺地從側慕走出來。在燈光下有個餐桌大小的紡織架;當我輕柔哼曲的時候:「哎呀,我的好姊妹,多麼複雜的針黹,多麼漂亮的圖案」,從“閨密”身上帽子、鞋子、面紗、洋裝、內衣持續地消失........
穆哈只剩下一件褲子。在他們面前凸出一根粗大的紅蘿蔔;設計橋段的人互相交換眼色,我們用織布架上拉緊的床單把「丈夫」和觀眾圍開來。
這一幕可以演個沒完沒了。
額頭彼此靠在一起,我和穆哈發出呻吟和叫春聲,喘息的思吟聲響起,物品東倒西歪;我不斷地從織布架伸出光裸的大腿,穆哈則規律地用自己那乾癟的屁股擠壓在拉上的布簾上。我們極盡所能地表現激情;穆哈的黑眼珠燃燒地更熾熱了,汗滴流至他的上唇,我懷疑那一刻他無須紅蘿蔔也可以做得來......
弗拉巴斯特那段時間則配著獨白,他發出的聲音是如此直率、真誠而自信,觀眾因此發自內心大笑到站都站不穩。
弗拉巴斯特高舉雙手歌誦般地說道:
道德啊!噢,荒淫!不幸!
腐惡勢力無處不興.......
我將解放受縛之犬,
而那邪淫之眼絕非
天作美眷得以視見。
在他背後緩緩地拉開小窗簾;觀眾前看不見的巴瑞安躲藏在「丈夫」身後,觀眾吃驚的是首先弗拉巴斯特頭頂上露出尖銳的頂點,之後第一根小樹叉,最後是巨大多棻的犄角!
觀眾突然爆出一陣狂笑,險些沒讓肚皮破掉。犄角越長越高,停佇一會兒之後,最終在弗拉巴斯特的後腦勺形成特殊的模樣。
弗拉巴斯特舉起手指說:
要否去見親愛的一眼?
我家老婆巧織女紅,
與社會良婦皆相同;
似雪白鴿偎在純潔懷抱中。
若小鳥依人,如絨兔柔情。
這兔子完全要了觀眾的命。
「快去!」,某個人從群眾裡叫了出來,「快去看看,你這個笨蛋只注意自己的兔子!!」
弗拉巴斯特懷疑的緊閉雙唇並盤算自己的狀況:
「工作......工作讓我連一分鐘都無法分心......」
樹冠下他的面孔充滿令人敬畏、動容的嚴肅,甚至我看了這幕二十次,也沒忍住噗哧一笑。不置可否弗拉巴斯特是個恣意妄為的人、是個霸王、是個吝嗇鬼,但他也是個卓越不凡的演員。
就是如此卓越不凡,因此可以向他請求任何事情......
弗拉做了結尾,我從紡織架織布的小洞終於看見了我的金髮先生。
老天,他並沒哈哈大笑。他像個配種的種馬粗魯地大笑。臉孔上褪去了貴族般的蒼白,開始像蕃茄一樣泛紅。他哈哈大笑,看著弗拉巴斯特和他的犄角;我是多麼渴望跑去前頭並對著整個廣場大聲喊叫:是我,是我想出了這個花招!你們全部笑成一團都是我想出的點子,是我!是我!是我!
當然,我哪都沒現身。穆哈穿著歪斜胸衣和好不容易穿上的外衣緩慢地用匍匐而行的方式走出織布架;「丈夫」疑惑地以為我們依舊不停地做著繡工。觀眾們鼓起掌來。
我們接連三次鞠躬謝幕。
此時我屈著膝做出不合時宜的請安禮,我面向群眾驚恐地四處張望:搞丟他了,搞丟他了!!
過了一會兒他出現在舞台下方。我彷彿被滾水燙傷一般;弗拉巴斯特和穆哈早就隱退至幕後,當我的金髮先生還未用手把我攙扶起來時,我就像是一個上了發條的娃娃不停地謝幕著。
一枚沉甸甸的金幣意外地落到我手中。他挪動著那完美雙唇,面對著我,就正對著我!而我卻聽不見任何一個字。
神蹟十分短暫,瞬間弗拉巴斯特毫無憐憫的手捉住我的衣襬把我拉走了......
整整半天我都帶著這枚金幣;決定把它視作我此生的護身符。然而,隔天恢復正常,羅曼蒂克的激情念頭消褪了,金幣護身符先變成了一小撮銀幣,之後又變成了帽子、洋裝的腰部繫帶及同夥夥伴們食堂慶祝用的蝴蝶結。
書摘/試閱
序
小男孩坐在滿佈灰塵的箱子上。窗簾遮蓋著窗,有如柱子覆蓋上厚重的灰塵一般。當陽光灑下,灰白色的蝶蛾倉皇地四處飛散。
窗外傳來鐵片的叮噹聲和馬蹄踏地的聲響。屋外有人喊著「敵人」、「戰爭」;屋內,這裡是父母親曾待過的地方。他們如同這些頂著天花板的光柱,堅毅地護衛著這個家......
他很怕這個老人。老人既陌生又無法理解;因為他,親人的行為舉止都跟以往不同。父母親並未把注意力放在兒子身上,老人彷彿像是小男孩頭頂上的烏雲。他們也怕這老人,但為何要交給他這東西?
小男孩哭後,擦拭眼淚。這東西...... 這迷人的東西。難道不能再擁有它了嗎?媽媽從珠寶盒裡拿出這個東西,允許他可以用手指摸一下當作獎賞。這樣開心的時刻難道也不會再有了嗎?看呀看的,視線跟著天花板上的光影游移著......
他們說了甚麼有關鏽斑的事,但也沒看見甚麼鏽斑,還有關於戰爭的事。小男孩想像整片的戰茅森林,細長的旗幟有如分叉的蛇信一般...... 眾多的紅衣騎士,飄散著令人愉悅的火藥味...... 他的父親戰勝了所有的人。
但為何老人只是沉默地點著頭呢?!
小男孩用眼淚沾濕的手指在箱子上畫了一張可怕的鬼臉。以前當他畫鬼臉時就會被罵,而現在他特別高興。他露出了歪斜、下垂的嘴角,皺著眉頭,心理想著:嗯,就給他吧...... 就讓他......
於是金色的東西在陌生人的手掌裡閃爍著,在那老人修長的手掌裡。此刻小男孩忍不住號啕大哭,急忙地從自己躲藏的地方跑了出來,想要奪走玩具。他不相信這一次他不可以任性妄為。
「路偃爾!」
母親臉頰泛紅,父親嚴厲斥責,而男孩也對自己激動的行為感到後悔。因為老人用審視、銳利的眼光逼視著他許久。還有一件奇怪的事:男孩的小短褲是如何變成乾的?
老人玻璃般透亮的眼底掠過一抹陰影;無睫毛、厚皮的眼瞼眨了一下。男孩蜷縮了起來,老人把目光轉向他的母親,說道:
「您為他取了一個紀念羅偃的名字?」
窗外傳來軍靴鐵片叮噹作響的聲音,有人大聲吶喊著重要的決策和命令。老人嘆了口氣道:
「當一塊石頭從高處掉落...... 總是期待它可以掉入坑裡。也不會發生雪崩。我們總是如此期待。」
男孩哽咽著,用握成拳狀的手擦拭著眼睛。他躲在父親外套袖子後面,因此沒看見父母親詫異地互使眼色。
老人陰鬱地冷笑,說道:
「你的家庭依舊帶著印記,梭爾。這是命運。」
母親驚嚇地瞪大雙眼;父親沉默地托著臉頰,彷彿受著牙痛之苦...... 老人點頭說道:
「不過...... 沒什麼,我胡謅的。你們忘了我說的話吧。」
當老人身後的門一關上,在失落感中頓時多了份輕鬆。
他的手陷在那溫熱的手掌裡。你將會有許多其他的玩具。別難過了,我親愛的小太陽。
第一章
1
我們終究趕上了!幸運的是城門在我們一進入後便砰地一聲關上了。原本城門可能會在我們抵達前就關上,弗拉巴斯特還因此怒斥,咒罵了一整路。我們會遲到了是因為輪軸壞掉了,而輪軸會壞掉是因為昏昏欲睡的穆哈沒有看見路上的坑漥;穆哈會昏昏欲睡是因為弗拉巴斯特叫我們通宵達旦地排演...... 這樣的結果就是我們必須跑一趟鐵鋪。弗拉巴斯特嘶啞地和鐵匠議價,他吐了一口口水之後,還是付了錢,然後又打了穆哈好幾下。
由於時間已近夜晚,當然沒人還有力氣高興我們在城門關閉之前抵達了這件事。這裡早就開始了慶祝活動,街上人潮洶湧,明天也會是如此...... 我們沒有人會抬起頭看著掛在高聳於屋頂上那金色的風信旗,只有穆哈例外,他不時張開小嘴驚奇地看著城裡的新事物。
主廣場看來已經全被機靈參賽者的馬車和帳棚佔滿了,在激烈的搶奪下我們佔到了角落的位置,十分勉強地停放了三輛我們的四輪貨車。我們的左邊是四處漂泊的馬戲團,疲憊的熊在室外的獸籠裡沮喪地咆哮著;右邊駐紮了木偶戲團的演員,他們打開箱子,裡面有大型木偶的木製雙腳,看來有點可怕地直立著;對面則搭建著我們熟識同行的帳篷,他們是沿海地區的雜技演員。有幾次我們在一些市集裡和他們偶遇,那時候他們可是搶走了我們為數眾多的錢幣;而南面所有的通道都搭建了舞台。弗拉巴斯特變得陰鬱了起來,我繞到另一頭好偷偷噗哧地笑:哈-哈,莫非老頭以為我們在這兒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團體?顯然在歡騰節期間從任何地方前來的人,即使是最遙遠的地方都可以任意在此駐留,但先決條件只有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但也非常奇怪的條件。節目的第一幕必須要有砍頭的表演,任何人或形式都可以。市紳們的品味實在怪異,哪怕拿個滑稽的木偶上絞刑台,把頭吊在法院前做為裝飾,這樣也行。
慶祝活動在黎明時分便開始了。
我們甚至有點瘋狂,畢竟我們是漂泊的表演者,而非一群無依無靠的鄉下孤兒,我們的人生都在節慶或嘉年華會場合表演。這是一個富裕之城,居民富有且自滿。穿著鑲金邊制服的僕人站在鑲金四輪轎式馬車踏板上,驕傲至極,小販扛著奢華、稀有的貴重物品很吃力地站著;城市居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在小提琴和鈴鼓的伴奏下在廣場那兒翩然起舞,甚至連流浪狗似乎都有人照料,而且都有股高傲之氣。
流浪歌手相互拋擲著高溫的火把,走鋼索的演員在叮噹作響的高空架上跳舞,他們騰空而下,完美地落在觀眾圍成的圓圈裡。在繩索架上,某個穿深黑針織緊身衣的人看起來像蜘蛛,又像蒼蠅的 (順道一提,穆哈從攤子上拿了某個東西對著弗拉巴斯特自誇,弗拉巴斯特就是那個一直揪著他耳朵在紅白衛兵群眾中鑽來鑽去的人。)
接下來輪到我們了。
第一幕劇是木偶搏鬥–只是用來表演砍頭給人看的,木偶表演不過是齣極短、毫無意義的滑稽劇碼。頭從主角身上飛了出去,有如軟木塞從香檳酒瓶飛離一般。看起來像是挨餓的消瘦女孩拿著帽子繞著人群來回走動,但打賞的人很少,看樣子觀眾是不喜歡這個表演。
一旁的熊發出吼叫聲;身材魁武、穿著肉色針織緊身衣的盜賊扭轉著小夥子那顆如橡皮般的小腦袋瓜子,最後假裝把他的頭擰開了。在此關鍵時刻小夥子被折成一半,那一瞬間我膽顫心驚,誰知道這些雜耍演員......
小夥子鞠躬謝幕,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熊看起來像隻老狗,不情願地用後腳站立繞了一圈,遞出的帽子很快地就裝滿了錢幣。
南方人讓我們先上台演出,握了握弗拉斯巴特的手,說道:「開始吧。」
為了歡騰節我們準備了個遊戲,叫做「膽大的歐拉勒與不幸的玫瑰」。想當然耳,不是我扮演不幸的玫瑰,而是蓋茲娜。她必須要對她心愛的歐拉勒說出大量獨白,接著要為他的去世而哭泣,因為劇中套著肥厚外套的劊子手砍下了男主角的頭顱。劇本是弗拉巴斯特寫的,但我怎麼也不敢去問他:為什麼要特別去折磨高尚的歐拉勒呢?
扮演歐拉勒的人是巴瑞安;他吃力地擔任著我們劇團裡所有情人的角色,但這不應該是他該扮演的角色,他已經老了不太合適......。弗拉斯巴特面帶陰鬱地答應讓他盡快改演優雅父親的角色,但試問,又有誰同情劇中劇的蓋茲娜呢?穆哈是目前演出情人角色的人選,可是他僅僅十五歲,他只到蓋茲娜的肩膀......
我透過布幕看過美麗的玫瑰,她戲服的下襬及鬆開的頭髮神靈活現地攤開在舞台木板上,對著觀眾控訴著為何給了歐拉勒這種殘忍狠毒的結局。美女蓋茲娜老是用豐滿的胸部、細緻潔淨又瑰麗的臉孔,還有那陶瓷娃娃似的湛藍雙眸獲得觀眾的垂青,那時她搬出演員的看家本領,激昂的喊叫聲,伴隨著令人憐惜的啜泣,撼動了群眾。其實也不需要太多,只要為劇中愛人之死,成功地擠出兩、三滴淚水就可以了。
正因為現在蓋茲娜睫毛上閃爍著這兩滴珠淚,觀眾沉靜了下來。
在後台彷彿可以聽見劊子手沉重的步伐-弗拉斯巴特穿上自己那件肥厚外套,故意盡可能地將頓足聲放大。高尚的歐拉勒頭放在斷頭台上;劊子手擺弄著帶有缺口的巨大斧頭好嚇唬美麗的玫瑰,而後他揚起手許久,當他的武器落下時巴瑞安的首級也伴隨著落下。
按照弗拉斯巴特的構想,斷頭臺有小簾子遮住-因此觀眾只能看見處決者的肩膀以及劊子手揮刀砍人的動作。然後某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從布幕的缺口中遞出被砍下的首級。
哎呀,這算甚麼頭顱!弗拉斯巴特持久熱情地用制型紙塑造出這顆頭顱。這顆頭十分像巴瑞安,只是整顆顏色為紅藍色,脖子帶有血水痕和黑色鋸痕;真可怕,這才不是顆頭顱。當劊子手弗拉斯巴特扯下那塊鋪著在托盤物品上的方巾,抓著頭顱上頭髮的墊圈展示給觀眾看,女士中的某人有可能因此噗通一聲栽倒暈過去。弗拉斯巴特可是對自己這個點子非常引以為傲呢。
總之,弗拉斯巴特抬手揚起斧頭,而我準備將放有可憐歐拉勒頭顱的托盤遞給他;沒想到一瞬間呈現在我腦海、落在我身上的道具,像是為了貪婪牧女準備的惡作劇。
一顆大白菜球莖。
我的天。,哎呀,為什麼我做了這種事?!
好像誰抓住了我,把可怕的紙頭顱放到一旁,我穩妥地把白菜球莖放在托盤上並在上頭擺上頭巾。美麗的玫瑰用手掩面痛哭失聲;觀眾前巴瑞安可見的身體抽蓄幾下後安靜了下來。
劊子手於斷頭台前彎腰致敬-而我看見了弗拉斯巴特伸長了的手。已經來不及用甚麼將它換掉;我把托盤遞給了他。
這一分鐘是怎麼過的啊!?我被炸成了有兩個同樣強烈感覺的兩半-來自弗拉斯巴特鞭刑的恐懼和渴望看到現在舞台所發生的......。不,第二種感覺看似比較強烈。我緊貼著布幕顫抖。
美麗的玫瑰痛哭著。劊子手將托盤展示給她看,嚴肅地看向觀眾......然後撤下方巾。
我的天。
這廣場是如此安靜無聲,看來,他們是不明白今日自己所看見的素材。緊接著安靜無聲之後突然爆發一陣大笑,而許多風信旗上習以為常的市鴿因此騰空飛起。
沒有人看的見弗拉斯巴特的面孔-它被劊子手的紅色面具蓋住。這點我承認我早就考量到了。
美麗的玫瑰把自己漂亮的櫻唇張到了極致,體型不大的烏鴉都可能自由地飛進飛出。在她的臉上凍結著如此真切又無比氣惱的訝異,身為一個平凡演員的蓋茲娜這輩子是絕對不可能演得出來的。很多人因哈哈大笑而長嚎;對手警覺的面孔從所有帳篷和簡易的小戲台探了出來,心想:這些吹毛求疵老練的市民們市發生了甚麼事?
而此時弗拉斯巴特能做的事只有急忙抓起白菜球莖的部分,並滿是激烈地將其穿到頭上。
......好不容易退到了幕後,蓋茲娜揪住我的頭髮:
「這是妳幹的?妳幹的?妳幹的?!」
弗拉巴斯特緩緩費勁地脫下劊子手的斗篷;他的臉看起來完全毫無畏懼般。
「弗拉團長,這是她做的!唐塔莉毀了我的舞台生涯!她毀了我們的劇目!她........」.
「安靜,蓋茲娜」,弗拉斯巴特不太高興地說道。
容光煥發的穆哈現身了-整個盤裡都是賞錢,錢幣堆得像座小山,而且他們不時微微發亮。
「冷靜下來,蓋茲娜」,弗拉斯巴特說著,「我准她的。」
輪到我托著下巴。
「是嗎?」,巴瑞安冷靜地重問了一次。「正如我所見,我很喜歡......」
沒料到會這般......觀眾愛極了,是吧,穆哈?
蓋茲娜滿臉通紅,嗤地一聲後走開了。我開始同情她了,大概不該開這個玩笑。蓋茲娜她太嚴肅了..現在她將會氣上許久。
「我們走吧」,弗拉斯巴特對我說道。
當我們放下馬車的簾子,他重重地揪住我的耳朵,而且用力扭轉。
可憐的穆哈,如此搞了一整天!我的雙眼因疼痛而一片灰暗,當我再度看見弗拉斯巴特,看起來像是我眼淚婆娑地看他。
「妳想,有准許妳這麼幹嗎?」,我的折磨者問道並又再度拉扯我的耳朵,我尖叫一聲隨即跳開。
「儘管再試試看」,他從齒縫中回應著。「再試一次看看......扒了妳的皮。」
「觀眾可是很喜歡啊!」,我啜泣起來,吞聲飲泣。
「賞錢更多了......」。
他走向我–我住了嘴,把背縮進防水布幕裡去。
他抓住我的另一隻耳–我瞇起眼睛,他扯著它,彷彿沉思般;而後放開說道:
「妳再變花樣看看,我就把妳賣到馬戲團。」
他走了,而我想了一下:就這麼容易脫身了。這可是可能會招來鞭打的......
不過,弗拉斯巴特假若沒有面具遮住他驚嚇瞪大的雙眸,他是怎麼都不可能饒恕我這些出乎常軌的舉動。
2
「鼩鼱」小酒館主人天生就不愛說話。
小酒館老闆記性很好;他知道今天他的客人看上了哪支酒,不過,這裡與眾不同之處在於,要知道,客人可是城裡響噹噹又尊貴的人物......
小酒館主人明白在這天客人不想引人注目;一早這張桌子就留給了他,屏風把酒店裡歡慶的人潮給隔絕開了。
這位城裡的名人已經一連數年來此並坐在這張單人桌,得以從容不迫地啜飲著自己極其講究的飲品。
老闆多年來觀察這獨特的儀式,清楚地知道下一步他要做什麼。
當貴賓的酒杯大約空了一半,門旁就會出現一位又高又瘦弱的身影;在門框前的某個陌生人點了下頭,否則他不會走過去,只用冷漠的目光環視整個酒館。陌生人是一個有著如同裏海鷗鯉那般晶瑩目光的枯瘦老頭;不停對酒館老闆點頭,他每次都由隔牆後方往桌子那頭逕直走去,酒店老闆了解陌生人需要的是哪種酒–老頭的品味跟和他共同進餐的人口味不一樣。
酒館老闆可以立誓,這兩個人從未開口對話過。城內貴客沉默地喝完自己的半杯酒;老頭稍稍抿了一口自己的酒,便起身離開了。客人坐在桌旁替自己又點了一杯酒及道地的下酒菜;假設之前他看起來是愉悅又緊張的,那麼老闆現在捕捉到他眼底的放鬆–卻同時有些失落。慷慨地付了帳,令人尊敬的城市人離開酒店時不停地對酒館主人點頭告別。
「鼳鼱」主人非常明白,這般不可磨滅的印象要是向鄰居提及這些事件,年復一年重複,–總是在歡騰節這日,老闆預料消息靈通的長舌婦會很欣喜–但他天生沉默寡言,也可能是因為某件不可思議的事件使得聰穎的老闆保持沉默。
3
就在那個時候節慶照常進行。
我們的南方對手們獻給可敬的觀眾一部巨大且排長講究的短篇文藝作品,開演前貼了公告好讓所有人可看到《勒胥修會的故事》。
在我們舞台前的群眾逐漸倒戈轉向對面的舞台–我們也湊熱鬧地往外瞧。「故事」從巨大破布製木偶砍頭橋段開始–這顆頭,說句不好聽的,就是用鈕釦接在襯衣領子上。之後就成了勒胥神聖的模樣–高蹺上魁武的小伙子,到眉毛處都被灰斗篷遮蓋住。按作者的設計斗篷的邊緣被蠕蟲蛀壞,這樣可以讓觀眾聯想到潮濕的墓地,而非一個蟲蛾攀附其上的大箱子,下擺處綴上些許肥滋滋的蚯蚓–我的天!,這鮮明、精力充沛的景象,似乎就像是在釣魚場一樣.........
觀眾在此時被嚇到了。孩童們因恐懼驚聲大叫,神聖的鬼魂像五月的貓般嚎叫起來,–我敢保證,觀眾受了這幕影響!假設勒胥的聖魂就同真正看到一樣,那到底他從哪來的這群追隨者。
我驚訝到來不及思考,勒胥修會的信徒就出現在舞台上了!全部有四人,因為南方人的劇團很大;從前面他們看起來像戴了兜帽的稻草人,而從後面看每個人被畫上骨架,這個別具寓意地用以闡述,其實勒胥成員們散播著死亡。觀眾們開始鼓掌,據說,市民中充滿荒疫的目擊者,十九年前這場荒疫讓附近地區半數以上的居民們死亡;根據傳聞,這場荒疫是被勒胥信徒叫喚出來的......
當時我很幸運地尚未出世;我那消瘦又蒼白的母親喜歡提及我們家族是如何強大、富裕又有名。荒疫幾天內吞噬了他們:我的祖父和祖母,甚至叔伯、嬸嬸們,堂兄弟姊妹分配到一個巨大的墓地,他們的房子被火焚毀,而財產被趁火打劫了。整個家族只有我母親和她弟弟從毀滅中逃過一劫;剩下的龐大家產在十年間逐漸減少,我的童年在偌大空蕩的房間度過,裡面全是具貴族血統、稀有的狗兒,散亂的書本全雜亂無章......
母親過世後小叔叔把我監禁在孤兒院。在孤兒院開始我被稱叫作弗拉斯巴特。
......弗拉斯巴特在我耳邊大聲地吸著氣,看來南方人懂得如何獲得青睞,而我們必須好好地準備,好吸引愚蠢的看官們到我們這邊來。
《勒胥修會的故事》獲得空前的迴響,雙頰緋紅的小妞扮演正義代表,在卸下的艙門處靈活地戰勝了勒胥兄弟,在那他們還痛苦地呻吟並抱怨著。觀眾瘋狂了般鼓掌,弗拉斯巴特做了個不滿意的表情並當穆哈也準備拍手時朝他發出噓聲。
半小時候我們依舊尚未開演,因為就在隔壁展開了鼓手們的對決。雙方在耳朵上掛了自己的樂器,還有地上擺了尺寸像水井木架般大的巨鼓。轟隆聲停了下來,塞住耳朵;眾人時而輕聲鼓掌並吹口哨和音,可憐人們拼命使勁讓他們的鼓發出怒吼狂嚎,誰也無法壓過對方。終於,巨鼓的主人跳躍到鼓上,用腳使盡全力往死裡打,腳掌彷彿像燃燒起來而跳動,他獲得了如雷般的掌聲,隨即劈啪一一聲後消失在巨鼓裡面。在聲響中決戰結束了。
我們表演的時刻來臨了,讓《公主與獨角獸》的劇目演出讓觀眾來評論。
我欣賞這齣創作,弗拉斯巴特跟某位流浪作家以高價買下它;作品內容描述公主(蓋茲娜)愛上了貧窮青年(巴瑞安),但邪惡巫師突然將她的愛人變成了獨角獸。說真的,本人認為,假設巫師是如此這般的邪惡,就不要讓他變成高尚的獨角獸,他可以變成其他東西,汙水桶或是有洞的皮鞋......真的,等等試試修改內容,把主角變成垃圾桶......
方慶扮演巫師,我們永遠的惡棍,除他沒人懂得怎麼橫眉豎目、嫌惡地撇嘴及惡毒咒罵;看在公平分上這麼說吧,除了這些外他甚麼都不會。我們的方慶是個善良又愚笨的人。他就幹些繁重的活。
巴瑞安和蓋茲娜演唱二部合唱,蓋茲娜有著高亢、銀鈴般的聲音,因它失去理智的不只有市集的商賈,甚至也有大人物......說正格的,沒有「莊嚴的愛情」蓋茲娜可是不願意與人接吻的,我的印象中這樣的愛情大概有六或七次吧。
表演不好不壞地進行了;接近終場時看倌們開始感到不耐。微調變換舞台的情境,穆哈用力敲打銅盆,弗拉巴斯特揮動金屬錫片,而巴瑞安在煙霧團中抽畜(是我在台架下點燃潮濕的麥秸束)。不過沒有任何幫助,在我們舞台前的觀眾看得出越來越少。
南方人齜牙咧嘴地笑著。該想辦法挽救局面回來。
穆哈拿著盤子很快地跑向觀眾,賞錢比一半還少,那邊已經開演喜劇《戴綠帽的丈夫》了。又有一些市民加入我們的觀眾行列–在這裡我看見了金髮先生。
真是不可思議。他高出觀眾一整顆頭–像是小球在浪潮上。來自四周的人都盯著他的那雙每到不可思議的眼眸直看,像是日光下閃閃發光的兩塊冰。他已不再年輕,不過要稱他是老人家也是讓人難以啟齒的。我的人生中從未遇過如此多的尊貴之人;他就像是栩栩如生的雕像,像是偉大將領的青銅像。現在這尊紀念雕像看向我們這方,看得出來這沉思者是要走還是要留下來。
金髮先生,您別走啊!!
我差一點就等到了,目前弗拉斯巴特帶著辦事員配飾,結束自己的獨白,他據說是位冷酷的先生,而他的太太則是美德之光。
當我帶著假胸部及翹臀急忙跑出舞台時,他剛好說完最後一句台詞。我像是豌豆粒從調皮鬼的煙袋跳了出去;對我來說這個廣場上現在只存在一位觀眾而已。
哎呀,我扮演一個感到絕望的太太,如此有美德,如此善良,或許,善良的男士允許我和“閨密”倆一起做著繡工?
“閨密”穿著細高跟鞋搖搖擺擺地從側慕走出來。在燈光下有個餐桌大小的紡織架;當我輕柔哼曲的時候:「哎呀,我的好姊妹,多麼複雜的針黹,多麼漂亮的圖案」,從“閨密”身上帽子、鞋子、面紗、洋裝、內衣持續地消失........
穆哈只剩下一件褲子。在他們面前凸出一根粗大的紅蘿蔔;設計橋段的人互相交換眼色,我們用織布架上拉緊的床單把「丈夫」和觀眾圍開來。
這一幕可以演個沒完沒了。
額頭彼此靠在一起,我和穆哈發出呻吟和叫春聲,喘息的思吟聲響起,物品東倒西歪;我不斷地從織布架伸出光裸的大腿,穆哈則規律地用自己那乾癟的屁股擠壓在拉上的布簾上。我們極盡所能地表現激情;穆哈的黑眼珠燃燒地更熾熱了,汗滴流至他的上唇,我懷疑那一刻他無須紅蘿蔔也可以做得來......
弗拉斯巴特那段時間則配著獨白,他發出的聲音是如此直率、真誠而自信,觀眾因此發自內心大笑到站都站不穩。
弗拉斯巴特高舉雙手歌誦般地說道:
道德啊!噢,荒淫!不幸!
腐惡勢力無處不興.......
我將解放受縛之犬,
而那邪淫之眼絕非
天作美眷得以視見。
在他背後緩緩地拉開小窗簾;觀眾前看不見的巴瑞安躲藏在「丈夫」身後,觀眾吃驚的是首先弗拉斯巴特頭頂上露出尖銳的頂點,之後第一根小樹叉,最後是巨大多棻的犄角!
觀眾突然爆出一陣狂笑,險些沒讓肚皮破掉。犄角越長越高,停佇一會兒之後,最終在弗拉斯巴特的後腦勺形成特殊的模樣。
弗拉斯巴特舉起手指說:
要否去見親愛的一眼?
我家老婆巧織女紅,
與社會良婦皆相同;
似雪白鴿偎在純潔懷抱中。
若小鳥依人,如絨兔柔情。
這兔子完全要了觀眾的命。
「快去!」,某個人從群眾裡叫了出來,「快去看看,你這個笨蛋只注意自己的兔子!!」
弗拉巴斯特懷疑的緊閉雙唇並盤算自己的狀況:
「工作......工作讓我連一分鐘都無法分心......」
樹冠下他的面孔充滿令人敬畏、動容的嚴肅,甚至我看了這幕二十次,也沒忍住噗哧一笑。不置可否弗拉斯巴特是個恣意妄為的人、是個霸王、是個吝嗇鬼,但他也是個卓越不凡的演員。
就是如此卓越不凡,因此可以向他請求任何事情......
弗拉做了結尾,我從紡織架織布的小洞終於看見了我的金髮先生。
老天,他並沒哈哈大笑。他像個配種的種馬粗魯地大笑。臉孔上褪去了貴族般的蒼白,開始像蕃茄一樣泛紅。他哈哈大笑,看著弗拉斯巴特和他的犄角;我是多麼渴望跑去前頭並對著整個廣場大聲喊叫:是我,是我想出了這個花招!你們全部笑成一團都是我想出的點子,是我!是我!是我!
當然,我哪都沒現身。穆哈穿著歪斜胸衣和好不容易穿上的外衣緩慢地用匍匐而行的方式走出織布架;「丈夫」疑惑地以為我們依舊不停地做著繡工。觀眾們鼓起掌來。
我們接連三次鞠躬謝幕。
此時我屈著膝做出不合時宜的請安禮,我面向群眾驚恐地四處張望:搞丟他了,搞丟他了!!
過了一會兒他出現在舞台下方。我彷彿被滾水燙傷一般;弗拉斯巴特和穆哈早就隱退至幕後,當我的金髮先生還未用手把我攙扶起來時,我就像是一個上了發條的娃娃不停地謝幕著。
一枚沉甸甸的金幣意外地落到我手中。他挪動著那完美雙唇,面對著我,就正對著我!而我卻聽不見任何一個字。
神蹟十分短暫,瞬間弗拉斯巴特毫無憐憫的手捉住我的衣襬把我拉走了......
整整半天我都帶著這枚金幣;決定把它視作我此生的護身符。然而,隔天恢復正常,羅曼蒂克的激情念頭消褪了,金幣護身符先變成了一小撮銀幣,之後又變成了帽子、洋裝的腰部繫帶及同夥夥伴們食堂慶祝用的蝴蝶結。
得獎作品
◎2005年歐洲科幻大會年度最佳作家
EFSF’s (European Science Fiction Society)Best Writers of Europe in Eurocon 2005.
(2003年為《夜巡者》作者謝爾蓋‧盧基揚年科Sergey Lukyanenko獲得同獎項)
◎本系列前傳《守門者The Gate-Keeper》獲得1994年俄國「水晶桌獎」最佳處女作。
◎《傷痕者The Scar》獲1997年「石中劍獎」最佳科幻小說肯定!
《傷痕者The Scar》在俄國賣座超過100萬冊!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