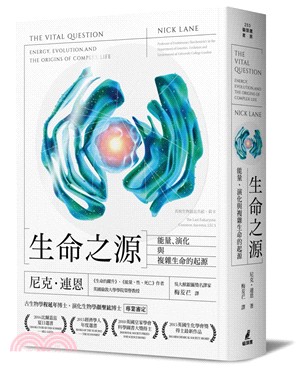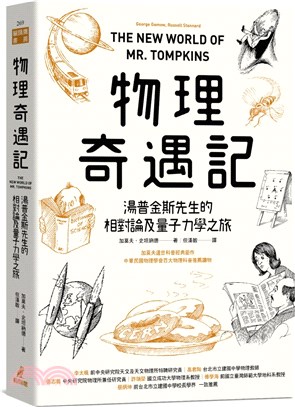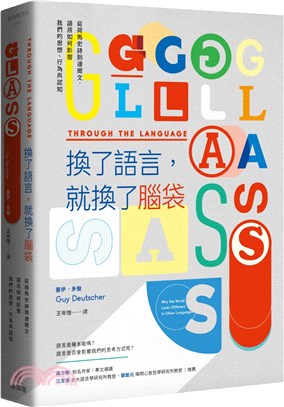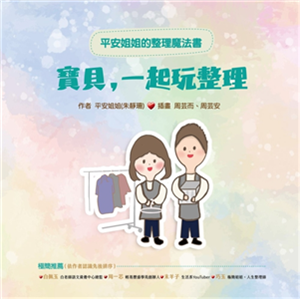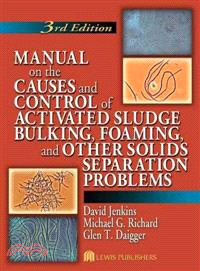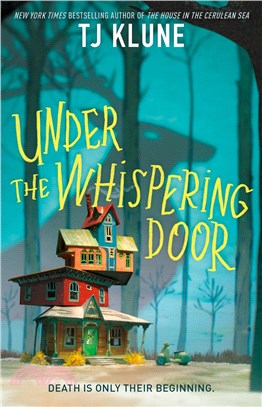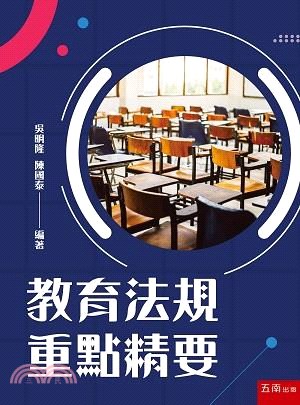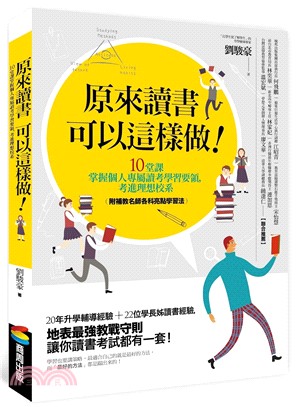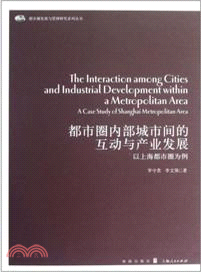生命之源:能量、演化與複雜生命的起源
商品資訊
系列名:貓頭鷹書房
ISBN13:9789862623107
替代書名:The Vital Question:Energy, 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lex Life
出版社:貓頭鷹
作者:尼克‧連恩
譯者:梅苃芢
出版日:2016/10/08
裝訂/頁數:平裝/528頁
規格:21cm*14.8cm*3.3cm (高/寬/厚)
重量:625克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617【九年級】
商品簡介
「假若,連恩教授所建構的思維體系是正確的話,
它將有如哥白尼革命一般的重要,甚或更為驚世!」
──程延年
繼《生命的躍升》、《能量、性、死亡》後,
生化學大師尼克‧連恩(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榮譽教授)又一力作
窮盡一生對生命如何發展而成的大哉問
什麼是生命?
什麼是「活著」?
複雜生命又是如何演化而來?
◎程延年博士古生物學專業審定
◎顏聖紘博士演化生物學專業審定
◎清大生科黃貞祥助理教授專文推薦
◎吳大猷銀籤獎名譯家梅苃芢最新譯作
◎2016比爾蓋茲夏日選書
◎2015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2010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大獎、2015年英國生化學會獎得主最新作品
從幾萬英呎的高空到深不見底的深海海溝,我們的地球到處都充斥著生命。然而,生物學的核心卻是一個亙古難解的問題:複雜生命哪裡來?或者,換句話說,生命最初又是如何開始的。大師級生化學家尼克連恩則在本書中針對此問題提出解答。
第一個原始生命誕生之後,長達二十五億年的時光,這些單細胞生物基本上並無多大改變,仍維持原核型態。然而,在這生命演化的四十億年時光裡,僅僅一次,生命出現了跳躍性的成長,發展出前所未見的複雜性。在這之後所有的複雜多細胞生物,從香菇到人類,不僅出現令人費解、不同於原始細菌的生物特徵,如有性生殖、細胞凋零等,更甚,若是在顯微鏡下檢視這兩者的細胞,除了香菇有細胞壁之外,其他真核細胞的特徵皆一應俱全,無法輕易分辨兩者。為什麼只有真核細胞可以有這麼多樣的演化?以及,為什麼這樣激烈的演化是如何、又為何發生的呢?
尼克連恩認為答案在於「能量」: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代謝與存活皆需要耗費相當高能的能量。連恩以進化論為基礎,結合了前沿研究當中能量轉換與細胞生物學的關係,從中討論生命的起源到多細胞生物的出現,並提供一個嚴謹的論證,同時加深我們對於「活著」與「死亡」在生物意義上的見解。
既嚴謹又豐富,本書對生命起源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解答,這個解答也可以幫助我們思索,在地球上出現的生命形式,到底是一個偶然,還是宇宙定律下的必然?
古生物學專業審定│程延年
演化生物學專業審定│顏聖紘
推薦序│黃貞祥
專業推薦(按姓氏筆畫序)
王弘毅/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李家維/《科學人》雜誌總編輯
林大利/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
林仲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林勇欣/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副教授
邵廣昭/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講座教授、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孫維新/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徐堉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高文媛/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濟民/國立臺灣博物館 館長
彭鏡毅/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前研究員兼博物館主任
各界好評
「尼克連恩藉由縝密的科學推論提供了生命的一覽圖。他的寫作清晰,如同簡潔有力的散文,然而其中卻滿盈著科學的深度,讀者將會被其生物學的驚人觀點給深深滿足」──《紐約時報》
「如果我是一個有錢的男人,我會買下所有的刷次,然後贈送給要念生物學的每一位大學新生。」──Franklin Harold 《Microbe》雜誌總編輯
「他是一個原創的研究者與思想家,也是一名充滿熱情和理想的教育者。他的理論如此高明,範圍驚人,且深具挑戰性……若此理論正確,尼克連恩將如同哥白尼同等重要。」──英國《衛報》
「一個生命形成的新理論。」──英國《金融時報》
「比起其他的書,此書有著最令人信服的生命起源的過程推論……連恩從一個細胞獲得能量的角度出發,到為什麼有「有性生殖」和「老去」,以深入了解生命這個問題的各種層面。」──《The Economist Intelligent Life》
「改變生物學觀點的書……應該要有更多人知道這個觀點。」──比爾蓋茲
「近年來,對於生命的演化史最深且最有啟發性的作品。」──《經濟學人》
作者簡介
連恩為演化生化學家,目前為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榮譽教授。他的研究主題為演化生化學及生物能量學,聚焦於生命的起源與複雜細胞的演化。除此之外,他也是倫敦大學學院粒線體研究學會的創始成員,並領導生命起源的研究計畫。連恩出版過三本叫好又叫座的科普書,至今已被翻譯為二十多國語言。2010年,他以《生命的躍升》獲得科普書最高榮譽──英國皇家學會科學圖書大獎,而他的另一本著作《能量、性、死亡》則入圍上述大獎的決選名單,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報》年度年輕科學作家的候選名單,同時也被《經濟學人》提名為年度好書。連恩對於生化學和演化生物學的貢獻在2015年更獲得英國生化學會獎肯定。連恩現定居於倫敦,關於更多他的資訊,請造訪他的個人網站:www.nick-lane.net
目次
第一部分:問題
第一章 什麼是生命?
第二章 什麼是活著?
第二部分:生命的起源
第三章 生命最初的能源
第四章 細胞的起源
第三部分:複雜性
第五章 複雜細胞的誕生
第六章 性、死亡的起源
第四部份:預測
第七章 力量與榮耀
總結:來自深海
書摘/試閱
序論 為何生命會是這樣地存在?
在生物學的核心議題,有一個黑洞。直白地說吧,我們其實不知道,為什麼生命,是以今日這樣的形態,存於世上。今天地球上所有的複雜生命,都來自一個共同的祖先;那是一顆從簡單細菌祖先所演變出來的細胞;在整整四十億年的時光中,只有過這麼一次偶然的機緣。這只是某個瘋狂的意外?抑或是大自然其實還做過其他複雜生命的演化實驗,但全都以失敗告終?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所有生命的共祖,已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細胞了。它有著跟你的細胞差不多一樣的複雜性,而且它把這個複雜性,不只傳給了你跟我的細胞,還傳給了其他所有後代,從樹木到蜜蜂都是。你可以在顯微鏡下面,試著分辨自己的細胞跟香菇的細胞。你會發現,它們長得幾乎一模一樣。但是我們長得一點也不像香菇呀,那為什麼我們的細胞卻如此相似呢?而這,不只是外形相似的問題。所有複雜生物的細胞,都共享著數種非常精巧、令人咋舌的特徵,諸如有性生殖、細胞自殺以及老化。然而這些特徵,在細菌身上,卻完全沒有可以相比擬的行為。關於「為什麼這些獨一無二的特徵,會全部聚集在我們那個祖先細胞身上?」或是「為什麼這些特徵,並沒有在細菌身上,獨自演化出來?」這些問題,學界並沒有統一的答案。如果說,這些特徵,都是透過天擇所篩選出來,而天擇的原則,就是每一代都略有差異,而且每代都比上一代更優秀一點,那麼為什麼類似的特徵,卻沒有在其他的機緣下,在各種不同的細菌族群中演化出來呢?
這些問題,其實凸顯出了,生命的演化在地球上,所遵循的是一條極為獨特的軌跡。生命在地球誕生約五億年之後出現,大概是四十億年以前,但是之後它的複雜程度,就卡在細菌等級,卡了超過二十億年,這已經差不多是我們地球年齡的一半了呢。細菌的外形,在這整整四十億年裡面,都跟剛開始出現時一樣簡單(但是它們的生化反應,可一點也不簡單)。相反的,所有外形複雜的生物,包括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動物、真菌、海藻,以及我們稱為「原生生物」的單細胞生物,像是變形蟲之流,全部都是從約十五到二十億年前,同一個祖先所繁衍出來的。這個祖先,很明顯是個「現代化」的細胞,它有極為精巧的內部結構、前所未見的分子機動性;這些,全部都是由許多複雜的奈米機器所驅動,而這些奈米機器,是由數千個基因所製造。這些基因,大部分都不曾在細菌身上見過。然而,在細菌跟這個細胞祖先之間,沒有殘存的演化中間形態;沒有所謂的「失落的環節」,可以用來解釋這些複雜的特徵,是如何以及為何出現。在形態簡單的細菌,跟歎為觀止的各種複雜生物中間,是一片難以解釋的空白鴻溝。這是演化學上的
黑洞。
我們每年都要花上幾十億美金,做生醫研究,極力尋求諸如「為何我們會生病」這種複雜問題的答案。對於基因跟蛋白質如何互動、調控它們的分子路徑為何?它們又是如何互相影響?我們不但所知甚多,而且非常詳細。我們也建立了精巧的數學模型、設計了電腦模擬程式,去驗證我們的預測。但是,我們卻不知道這些細節,如何演化出來!如果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細胞如此運作,那我們如何能夠期望自己了解疾病呢?就像如果我們不知道一個社會的歷史變遷,就不可能理解這個社會一般;如果我們不知道細胞如何演化出來,就不可能理解它的運作原理。而這還不只為了實用的理由而重要,這也是關乎於人類的問題,關於為何我們會出現的問題。到底是哪些科學定律,規範了宇宙、恆星、太陽、地球,以及生命的誕生呢?同樣的定律,是否也統御了宇宙其他地方的生命?外星人的生命形態,跟我們的一樣嗎?這些形而上的問題,也正是我們何以為人的核心問題。在我們發現了細胞約三百五十年以後,我們卻仍然不知道,為何地球上的生命是如此運作。
或許你沒注意到我們其實不知道答案,不過這不是你的錯。今天教科書跟期刊上提供了各種資訊,但是絕大多數,都不是在研究這類「童稚的」問題。而網路上,又充斥著各種雜亂無章的論據,其中還混入程度不一的胡言亂語,讓我們暈頭轉向。不過,不知道答案的原因,不僅僅只是因為資訊過多的緣故,事實上,只有很少的生物學家稍微意識到,在他們的研究的主題中心,有個大黑洞。大部分的科學家,都忙於研究其他的問題。他們研究的材料,絕大多數都是較大型生物,或是幾種特定的動物或植物;相較之下,只有很少數的人在研究微生物,而只有更少的人,才在研究細胞的早期演化。這其中還要擔心創生論者與「智能設計論者」的攪局:承認我們其實無法回答所有問題,很可能會幫否定論者,也就是那些全盤否認我們對於演化論,有任何扎實知識的人,開了一扇大門。事實上,我們對演化論的知識,當然非常扎實,而且我們知道非常多。關於生命起源以及早期細胞的演化,所做的假設,除了必須要能解釋一籮筐的現象、要局限於現有知識的框架下,同時還要能預測意料之外、但是可以透過實證來驗證的交互作用。我們對於天擇所知甚詳,對於某些會改變基因體的隨機意外,也了解不少。這些現象都跟細胞的演化相吻合。但是,也正是這些現象,造成我們的疑問:為什麼生命的演化,是循著這樣一條軌跡呢?
科學家都是充滿好奇之人,如果這個問題是如此明顯的話,它應該會家喻戶曉才對。然而事實上,它其實一點也不顯眼。眾多爭相出頭的解答,往往僅局限於圈內人流傳而已,更糟的是,它們還常讓問題顯得更加隱晦。另一個問題是,這些解謎的線索,需要來自各個不同領域,從生物化學、地質學、譜系發生學、生態學、化學以及宇宙學等等。沒幾個人,能敢自稱是所有領域的專家。尤有甚者,今日我們正處於基因組革命(genomic revolution)的潮流中,科學家已經掃描出數千段完整的基因體序列,全部伸展開來的話,大概有幾百萬到幾十億個字母之多,而且常常帶著跟遠古時代完全相反的訊息。要解讀這些訊息,需要非常嚴謹的邏輯能力,同時要熟稔資訊學跟統計學,如果還懂一點生物學,則更有加分之效。所有的論證,常常像是走在五里霧中一般;每次我們打開一個缺口,眼前所展開的,就是一幅更超現實的景象。過去曾讓我們感到滿足的論點,瞬間消失殆盡。眼前所面對的,是一幅全新的圖像,既真實,又棘手。不過從研究者的觀點來看,能找到新穎且重要的新問題,可是極其興奮的一件事呢!現在,生物學界最大的問題尚待解答,而本書,就是我試著去解答它的起點。
細菌如何跟複雜的生命產生連結?關於這個問題,要追溯回到一六七○年代,荷蘭的顯微鏡學家雷文霍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發現微生物的那個時代。他在顯微鏡下面所展示的活潑「小動物們」,剛開始少有人信,不過很快地,就被另外一位天才虎克(Robert Hooke)所證實。雷文霍克那時也觀察到了細菌,並在他一六七七年所發表的著名論文裡寫道:「在我的視野下面,它們是難以置信的小,小到這樣的程度,讓我覺得即使有一百個這種小東西,一個接著一個排起來,也不會超過一粒沙的寬度;假使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一百萬個這種小生物在一起,大概勉強跟一粒沙的體積一樣大吧。」。以前很多人懷疑過,雷文霍克真的可以用他那台簡陋的單眼顯微鏡,看到細菌嗎?不過現在這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他發現兩件事,第一,他發現細菌無處不在─不僅僅只是在自己的牙齒上,也在雨水中、在海水中。第二,根據微生物各種引人注意的行為,以及「小腳」構造(纖毛),雷文霍克直覺地將「非常非常小的動物」(細菌),跟「大怪獸」(也就是細小的原生生物)兩者區分開來。他甚至注意到了有些較大的細胞,體內帶有許許多多的「小泡」,他把這些小泡拿來跟細菌相比,當然,那時候他用的不是「細菌」這個名稱。在這些小泡之中,雷文霍克應該已經觀察到了細胞核,也就是所有複雜細胞體內的基因儲存所。不過除此之外,這些結果就這樣被靜靜地擱置了好幾世紀之久。在雷文霍克發表他的結果五十年之後,著名的分類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也僅僅只是把所有的微生物,全部歸類到「蠕蟲門」(phylum Vermes)下面的「變形蟲屬」(genus Chaos)而已。十九世紀時,與達爾文同時代的德國科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演化學家,曾再次將細菌與其他微生物區分開來,將它們之間巨大的差異正式化。不過從概念上來說,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太大的進展。
生物化學知識上的統合,是這個問題的轉捩點。細菌在代謝反應上面所展現的多才多藝,讓它們非常難以被分門別類。它們幾乎可以生長在任何一種環境下,從水泥、電池酸液到玻璃表面都可以。如果這各種各樣的維生方式,沒有什麼共通點,那我們要怎麼將細菌歸類呢?而如果無法分門別類,又怎麼有辦法了解它們呢?幸好,就像化學周期表統合了化學一般,生物化學也為細胞演化,帶來了可循的規則。另外一個荷蘭科學家克萊佛(Albert Kluyver)曾經指出,所有生命雖然看似複雜多樣,其實都是根基於類似的生物化學反應過程。呼吸反應、發酵反應以及光合作用,外表差異極大,但其實都有一樣的基礎;而這種概念上的完整性,正好見證了所有的生命,都是源自一個共同祖先。會發生在細菌身上的,也會發生在大象身上。因此,如果從生物化學的等級來看,那細菌跟複雜生命的界線,就幾乎不存在。細菌誠然比複雜生命要多才多藝,但是維繫牠們生存的基本反應,是非常相似的。克萊佛的學生凡尼爾(Cornelis van Niel)跟史坦尼爾(Roger Stanier),或許是對細菌與複雜生命之間的差異,描述得最透徹的人了:他們說,細菌是最小的功能單位。意思是說,從功能的角度來說,細菌就像原子,不可再被分割。比如很多細菌,都能行跟我們一樣的呼吸作用,但是它們必須要用完整的個體來處理,而無法像人類的細胞一樣,裡面有一小部分構造,專門用來處理呼吸作用。隨著細菌長大,它們會分裂成兩半,但是它們的功能卻不會分成兩半。
接著,有三場最關鍵的革命,顛覆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建立起來對生命的看法。第一場,是由美國微生物學家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所挑起的,在一九六七年那個有嬉皮革命而著名的「愛之夏」。馬古利斯認為,複雜的細胞,並非遵循「標準」的天擇規則演化出來,而是經由一種狂亂的合作方式所產生:細菌彼此合作之緊密,讓一個細菌甚至進入另一個體內。一般所謂「共生」,指的是兩個或多個物種之間,長期的互動,通常都是彼此交換代謝物質,或是互相服務。在細菌的例子裡,這些被交換的物質,是生命之源,是代謝所需的受質,也是支持細胞活下去的動力。馬古利斯用了內共生作用(endosymbiosis)來描述這現象:它跟共生一樣是交換,但是這種交換是如此親密,以至於某些合作夥伴,乾脆直接住在宿主細胞體內;就像聖經裡面說的:「商人乾脆直接在聖殿裡面做起生意了。」其實這種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回二十世紀早期,而它的遭遇,讓人聯想起古老的板塊理論。板塊理論指出,非洲跟南美洲兩塊大陸,「看起來」很像是曾經連在一起,然後被拉開來;但是這個天真的論點,長久以來都被斥為無稽。細胞也是一樣,有些複雜細胞體內的構造,看起來就像是細菌,而且似乎也會獨立生長跟分裂。或許,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它們本來就是細菌。
也如同板塊理論一般,這些想法,都遙遙領先它們的時代太多。一直要到了一九六○年代,分子生物學的時代興起後,才有可能提供強而有力地實例證明。馬古利斯提出了細胞內兩個特化的構造為例:第一個是線粒體,也就是呼吸作用的基地,在這裡,食物會和氧氣燃燒,轉換成生命所需要的能量;另一個例子則是葉綠體,也就是植物體內的光合作用引擎,可以將太陽能轉換成化學能。這兩個「胞器」(意思是細胞的微小器官),仍然保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基因體,帶有一小撮基因,可以轉譯出幾十個參與呼吸作用或是光合作用的蛋白質。這些基因的序列,洩漏了它們的身世:很明顯地,線粒體跟葉綠體,都是從細菌變來的。注意,我是說「變來的」,因為它們已經不再是細菌,也沒有任何獨立性了,大部分維持它們生活所需的基因(至少需要一千五百個基因左右),都已經跑到細胞核,也就是細胞的基因控制中心裡了。
關於線粒體跟葉綠體,馬古利斯是對的。到了一九八○年代,已經沒什麼人再質疑這項論點。不過馬古利斯的野心遠大於此。她認為,複雜的細胞,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真核細胞(eukaryotic cell,這個字源自希臘文,意思是「有真正的核」),其實就是共生作用的拼貼作品。對她而言,細胞的其他部分,特別是纖毛(也就是雷文霍克稱之為「小腳」的構造),也都是從細菌演變來的(她認為纖毛來自螺旋體)。她的理論後來漸漸合併了各家論點,最後馬古利斯將其正名為「連續內共生學說」。她認為,不只細胞是細菌的合作成果,其實整個世界,都是細菌們互相合作的網絡,也就是所謂的「蓋婭」;這是她跟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一起提出來的先進想法。雖然「蓋婭」這個概念,在除去了洛夫洛克原本非常目的論的內容之後,最近幾年轉化成比較正式的面貌,也就是所謂的「地球系統科學」(earth systems science)重生,也較被大眾接受。但是另外一個概念,關於複雜的「真核細胞」,是由細菌拼裝而成,則只有很少的證據支持。事實上,大部分細胞裡面的構造,看起來都不像是來自細菌,同時,基因上面也沒什麼證據支持這種看法。因此,馬古利斯說對了一半,但是對另一些部分,則幾乎是錯定了。不過她的奮鬥精神、堅強的女性特質、不畏與達爾文主義者互爭鋒頭,以及傾向去相信一些帶有目的性的理論,混在一起,注定了她在二○一一年,因為中風而英年早逝後,留下頗具爭議的形象。對某些人來說,她是女性主義的英雄,在另一些人眼中,她卻像個失控的大砲。不幸地,這些都讓人忽略了她的科學成就。
第二場革命,是一場「譜系發生學」的革命,這是一門探尋我們祖先基因的學問。早在一九五八年,克里克(Francis H. C. Crick)就已經預測了這場革命會出現。他用一貫冷靜的文筆寫道:「生物學家應該體認到,很快地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研究主題,或許可以稱作『蛋白質分類學』(protein taxonomy)─我們可以研究各種生物的蛋白質胺基酸序列,然後比較各物種之間的差異。這些序列,可能代表了生物表徵裡最細微的部分,同時可能有大量的演化資訊隱藏於其中。」結果,它真的實現了。現代的生物學,幾乎就是在研究蛋白質跟基因序列裡面隱藏的資訊。現在,我們已經不再直接比對胺基酸序列,而是比對DNA裡面的字母順序(因為DNA負責轉譯出蛋白質),這樣做的敏感性更高。不過儘管如克里克般有遠見,在當時也沒有人能想像到,我們會從基因裡面,挖掘出怎樣的祕密。
這次傷痕累累的革命先鋒,是微生物學家渥易斯(Carl R. Woese)。他大約從一九六○年代開始,就默默地著手進行研究,但一直要到約十年之後才獲得成果。渥易斯選擇了一個基因,做為各物種之間比較的標準。當然啦,這個基因,必須是所有生物都擁有,而且在大家身上,它還必須做著一模一樣的工作才行。同時這項工作,必須是非常重要而基本,基本到如果有一絲絲功能上的改變,都會導致細胞被天擇淘汰。如果大部分的變動都被淘汰了,那剩下的,就是改變很少的基因─也可以說這是從亙古以來,改變極為緩慢的基因。如果說,我們想要比對各物種之間,幾十億年以來基因所累積的差異,然後藉此畫出一棵、可以一直追溯到物種誕生之初的生命樹,那麼變異緩慢這點,就絕對必要。而這也正是渥易斯宏遠的野心所在。為了要符合這一切的要求,渥易斯回頭把重心放在一個所有細胞都有、而且是最基本的工作上,那就是製造蛋白質這件事。
細胞的蛋白質,是由一種叫做「核糖體」的超小奈米機器所製造;所有的細胞,都有這種優秀的機器。在進入資訊時代後的生物學裡,最具代表性的東西,大概除了那圖騰般的雙螺旋DNA以外,就屬核糖體了。從各種尺度上來講,它的構造都正好體現了一種,人類智慧難以想像的矛盾。細胞已經很小了,小到在人類歷史大部分的時間裡,完全沒有人知道它們的存在。但是從數量級上來看,核糖體更是小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光是你的一顆肝細胞裡,就可以塞下一千三百萬個核糖體。不過,核糖體不是只有體積小讓人難以理解,若從原子的尺度來看,它們還是複雜到難以想像的超級機器。它們由許多次單元組合而成,是一台會移動的機器;而它們工作起來精確的程度,遠遠勝過自動化工廠的生產線。這一點也不誇張:核糖體的工作,有如讀著一條發報機的紙帶,每條紙帶上,都寫好了製造一條蛋白質所需的密碼。核糖體一邊精確地依序翻譯它們,一個字接著一個字地,同時一邊把所有所需的蛋白質零件(胺基酸),連成一串長鏈,組裝出一條蛋白質;而每個胺基酸的順序,都根據紙帶上的密碼順序。核糖體工作的出錯率,大概是每一萬個字會錯一個,這數字,遠低於世上任何高精度工業的製造程序。而它們工作的速率,大概是每一秒鐘可以串起十個胺基酸,一條由數百個胺基酸接起來的蛋白質,只要不到一分鐘就可以做出來。渥易斯選擇了核糖體的一個次單元,或者說這台機器的一個零件,去比較在不同物種之間,從大腸菌、酵母菌,到人類體內,這個零件的基因序列,有什麼不同。
這個比較的結果非常驚人,完全顛覆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渥易斯可以清楚的區分細菌與複雜的真核生物,這部分沒有問題。在這一棵根據物種基因相似程度所畫出來的樹上,細菌跟真核生物這兩大家族,分開在不同枝幹上;而各家族內的不同生物,也可以區分開來。這部分結果唯一讓人意外的是,動物、植物與真菌,這三群讓大部分生物學家,耗費畢生心力研究的對象,竟然是如此親近。而真正讓人跌破眼鏡的結果,則是他分出了另外一群新的生物「域」(domain)。我們其實已經認識這些單細胞生物很久了,但是過去一直都把它們當成細菌,因為它們看起來,真的就跟細菌一模一樣:一樣的小、一樣的缺乏值得注意的內部構造。但是它們的核糖體,卻像《愛麗絲夢遊仙境》裡面那隻微笑的貓一樣,洩漏了看似不存在、卻留在那裡的祕密。新分出來的這群生物,或許一樣沒有真核生物的複雜性,但是它們的基因跟蛋白質,卻跟細菌的完全不同。現在這群單細胞生物,我們稱為古菌(archaea),因為原本科學家直覺地認為,它們可能比細菌還古老,不過這種看法可能有誤。新的觀點認為,它們兩者應該一樣古老。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從基因跟它們的生化反應來看,古菌跟細菌之間的鴻溝,跟細菌與真核生物(我們)之間的差異,一樣巨大。根據渥易斯那棵著名的「三域」生命樹,古菌與真核生物反而是「姐妹群」,兩者分家比較晚。
從某些方面來看,古菌與真核生物,確實有很多地方很像,特別是它們處理資訊的方式(也就是說它們讀取基因的資訊,然後轉譯成蛋白質的方式)。古菌有少許跟真核生物很相似的複雜機器,而這少數相似之處,就是真核細胞複雜化的種子。渥易斯並不認同細菌與真核生物之間,是因為在形態上有巨大鴻溝而不同;相反地,他主張將生物分成三個地位相等的域,每一域在演化上,都各自發展出一片天,沒有哪一域可以算是其他域的祖先。渥易斯最強調的,就是拒絕使用老舊的「原核生物」(prokaryote)這個名詞。「原核」這兩個字,是「在有細胞核以前」的意思,古菌跟細菌都符合原核生物的定義。渥易斯反對的理由,是因為他認為,並沒有任何基因上的證據,支持古菌與細菌的出現,早於真核生物。相反的,渥易斯認為這三域生物,都可以直接回溯到最古老的年代,它們共享一個祖先,但不知何故分道揚鑣。在他晚年,渥易斯對於演化最早期階段的看法,卻變得神祕難解。他認為我們對生命,需要有一個更全面、更整體的看法。這是很諷刺的一件事,因為由渥易斯自己所寫下的革命史,本身卻是根據非常化約的、單一基因的分析。渥易斯所掀起的革命,當然是貨真價實的;而細菌、古菌跟真核生物,也毫無疑問分屬於完全不同的族群。但是他的整體論主張,也就是必須把所有生物的所有基因體,都納入分析,正帶領了我們進入第三場細胞革命,而這場革命,又顛覆了渥易斯自己的結果。
這第三場革命正方興未艾,它的推論其實有點微妙,但是影響層面卻非常廣。這場革命的起因,正是根基於前兩場革命,它的問題是:前兩場革命之間的關聯是什麼?要知道,渥易斯的生命樹所描繪的,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基本的基因,在三個生物域中分歧的情況。而馬古利斯則完全相反;她主張的,是不同物種的基因,會透過內共生作用互相取得、融合,然後合而為一。如果要畫成樹狀圖的話,會是一棵融合的樹,而不是分岔的枝幹,這跟渥易斯的主張完全相反。他們不可能都對!但是其實他們也都沒有全錯。在科學裡面常常就是這樣,事實總是介於兩者之間。不過,你可別以為這是兩者妥協後的成果。其實,這次的答案,與其說是另類,不如說讓人振奮。
我們現在知道,線粒體跟葉綠體確實是從細菌,透過內共生作用演化而來。但是細胞的其他部分,則很可能是透過傳統的方式演化出來。問題是,這些事件在何時發生?葉綠體只存在於藻類跟植物體內,因此最可能是由藻類跟植物的共祖獲得,這應該發生在比較晚的時間點。相反地,所有真核生物都有線粒體,所以線粒體的取得,應該比較早(這裡有一些背景故事,我們將在第一章詳談)。但是有多早呢?或者換個方式問,哪一種細胞,可以獲得線粒體?教科書上面的標準答案常常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細胞,像變形蟲一般,是一個掠食者,可以改變形狀、匍匐前進,可以透過一種叫做「吞噬作用」的動作,吞掉其他細胞。換言之,可以吞掉線粒體的細胞,應該是一個即將完備、相當資深的真核生物細胞了。不過我們現在知道這是錯的。過去幾年,針對更多較具代表性的物種,大量分析它們的基因之後,科學家得到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那就是:獲得線粒體的宿主細胞,應該是個古菌,是一個來自古菌域的細菌!所有的古菌,都是原核生物。根據這個定義,它們沒有細胞核、沒有性生活,也沒有任何複雜細胞的行為特徵,當然也沒有吞噬作用。根據形態學對「複雜」的定義來看,這顆宿主細胞可說是一無所有。但是,不知道怎麼著,有天它得到了一個細菌,然後細菌變成了線粒體。而只有從那時候開始,它才漸漸演化出其他複雜的特徵。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關於「所有複雜的生命,均來自同一個祖先」這件事,很可能取決於它有沒有獲得線粒體,是這件事引發了複雜生命。
這個激進的觀點:「複雜的生命,源於一個古菌宿主,與一個變成線粒體的細菌之間的內共生作用。」早在一九九八年,就由一位擁有過人直覺的演化生物學家,馬丁(William F. Martin)預測過了。馬丁是一位思想奔放的人,他的猜測,是根基於我們觀察到,真核生物的基因,呈現了一種驚人的拼貼式排列法,這其中大部分都是他本人發現的。舉個生化反應的例子好了,比如發酵作用:古菌會進行一種發酵反應,而細菌的發酵反應則很不一樣,控制這兩種發酵作用的基因,非常不一樣。但是真核生物呢,則是從古菌那裡拿一點基因,再從細菌那裡拿一點基因,然後把兩者編在一起,形成另一套配合緊密的發酵反應步驟。這種錯綜複雜的基因混合現象,不只出現在發酵反應上,幾乎所有複雜細胞的生化反應皆如此,這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為什麼宿主細胞,要從內共生者那裡,拿來這麼多基因?又為什麼它要把這些基因,緊緊鑲嵌到自己的基因裡面,把原本就有的基因換掉呢?對這些問題,馬丁想得非常透徹。他跟謬勒(Miklós Müller)一起提出了一個答案,稱之為「氫氣假說」(hydrogen hypothesis)。他們認為這個宿主細胞是一個古菌,而古菌可以靠兩種簡單氣體為生,一個是氫氣,另一個是二氧化碳。這個內共生者(也就是未來的線粒體),則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細菌(就細菌來說,這很正常),它可以提供宿主細胞生長所需要的氫氣。當我們一步一步靠著推理,慢慢揭開兩種細菌之間相處的詳細情形後,才知道為何一個原本靠著簡單氣體,就可以過活的細菌,後來會變成一個到處搜刮有機物(食物),來供養內共生者的細菌。不過,這不是這裡的重點。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馬丁的預測,複雜的生命,興起於兩個細胞間的單一共生事件。他預測「宿主細胞」就是一個古菌,缺乏真核細胞的複雜構造。馬丁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較簡單的、中間型的、缺少線粒體的真核細胞;取得線粒體,跟複雜生命的誕生,是一體兩面,是同一件事情。同時馬丁認為,所有複雜細胞的精巧特徵,包括細胞核、性行為,以及吞噬作用,都是在經過了這個獨特的內共生事件,在取得線粒體以後,才會演化出來。他的預測,是演化史上最棒的洞見之一,值得廣為傳播。很可惜的,如果這理論,不是因為跟「連續內共生學說」混淆在一起的話(但是兩者預測出的結果,完全不同),它應該會更有名。馬丁理論中的各項具體預測,在最近二十年裡,都已經透過基因研究,被細細檢視過。這理論,就像是個紀念碑一樣,見證了生化推理的威力。如果諾貝爾獎有生物學獎項的話,應該沒有人比馬丁更有資格拿。
然而,繞了一圈,我們又回到了原點。我們已經知道了非常多事情,但是,卻仍然不知道為何生命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形式。我們知道複雜的細胞,在這四十億年的演化史中,只有一次機會,透過一次古菌跟細菌之間的內共生作用誕生(見圖1)。我們也知道,複雜細胞的種種特徵,都出現在這次融合之後;但是我們仍不知道,為什麼這些獨特的特徵,會出現在真核生物身上,卻從不出現在細菌,或是古菌身上?我們依然不明瞭是哪些力量,限制了細菌跟古菌?為什麼它們的形態一直是如此簡單?儘管它們能執行的生化反應,已經遠遠不同於以往;儘管它們的基因,已經變化甚多;儘管它們如此多才多藝,可以從氣體跟岩石中活出生命?我們現在所有的,是一個非常前衛的理論架構,可以讓我們在追尋答案時遵循。
我相信答案的線索,就藏在那古怪的生物能量產生機制裡面。這個奇怪的機制,在細胞身上施加了一種非常普遍、卻甚少被察覺的限制。基本上,所有的生命,都是靠著「質子流」在維持生命(質子,是一顆帶正電的氫原子。譯注:一顆質子跟一顆電子結合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個氫原子)。它有點像是電力,不過要把電子代換成質子,所以可以稱為質子力(proticity)。當我們透過呼吸作用燃燒食物後,所產生的能量,都會用來把質子運輸過一張膜,讓這張膜的一側像水庫一樣,充滿質子。當這些質子穿過膜流回另一側時,它們的作用方式,就像是水庫大壩的水流一樣,會推動水力發電廠的渦輪發電。這種在膜的兩側,製造出質子的濃度梯度,來幫細胞發電的方式,完全出乎我們意料。這個理論最早在一九六一年被提出,在隨後的三十年間,由二十世紀一位最有創意的科學家,米契爾(Peter D. Mitchell)逐漸發展完成;它被稱為是在生物學史上「自達爾文以降,最反直覺的想法了」。它也是生物界中,唯一可以跟物理界的愛因斯坦、海森堡(Werner K. Heisenberg)、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等人的理論齊名的想法。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從蛋白質的層級,知道質子梯度作用的詳細情形。我們也知道,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使用一樣的質子梯度:質子發電,內建在所有生命之中,如同普世通用的遺傳密碼一樣。但是,我們對於這種反直覺的能量生成方式,如何演化出來,卻一無所知。所以,我認為在今日生物學核心裡,有兩大未解的問題:一個是為何生命用這種令人費解的方式演化出來;另一個則是,為何細胞用這樣獨特的方式發電。
我相信,這兩個問題,其實緊密相關,互相纏繞著彼此,而本書正試圖去回答它們。我想要說服你們一件事,那就是:能量才是演化的核心。只有當我們把能量的觀點帶進來,去思考這些問題,才有可能了解生命的本質。我想告訴你們,生命跟能量兩者的關係,可以一直追溯回到太古之初─只有在一個生生不息的星球上、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中,才有可能產生所有生命所需最根本的機能。我也想帶你們去看,生命的起源,是由能量的流動所驅使,而質子梯度,就是演化出細胞的關鍵;如何使用它,則限制了細菌與古菌的結構。我會解釋給你們聽,這樣的限制,如何主宰往後細胞的演化,讓細菌跟古菌,永遠只能維持簡單的外形,儘管它們的生化反應能力,早已變化多端。我也想證明,是一場稀有的事件,一次內共生事件,讓一個細菌跑到一個古菌體內,才突破了這層限制,讓極度複雜的細胞,可以演化出來。我想告訴你們,一個細胞,親密地生存在另一個細胞體內這種情況,絕非易事,因此形態複雜的生命體,總共只誕生過一次。我還希望能夠多說服你們一些,像是這種親密的共生關係,基本上已經可以去預測複雜生命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包括了細胞核、有性生殖、兩種性別,甚至將永生不朽的生殖細胞,與終歸一死的體細胞區分開來;而最後這個特徵,正是「有限生命」與「命中注定死亡」現象的起源。我最後要說服你們的就是,從能量的觀點去思考,有助於讓我們預測自己生命的樣子,特別是演化中最深遠的「交易」:用疾病伴隨著老死,去交換充滿生殖力與適應力的青春。我認為,如果能洞悉這一切,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改善自身的健康,或至少多了解一些。
若你是科學邏輯支持者,那你大可皺眉質疑我的論點,在生物學界裡,這算是行之有年的優良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達爾文自己:他稱自己的《物種起源》是「一帖漫長的論證」。時至今日,想要細細陳述這千絲萬縷的科學世界中,各項證據如何彼此關聯;或是想要提出一個假說,有條理地解釋萬物之形,用一本書,恐怕仍然是最好的辦法。免疫學家梅達瓦(Peter B. Medawar)曾經這樣形容科學假說:就是憑想像力,躍入未知中。一旦縱身躍入,假說就變成了「企圖用讓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去講一個故事」。符合科學原理的假說,必須是要能夠被檢驗的預測。在科學裡面,恐怕沒有一種侮辱,比稱呼一個假說是「連錯的資格都沒有」要更嚴重了(譯注:這句話傳說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包立,在評論一項糟糕的科學理論時的用語),也就是說,無法被反證。因此,在本書中,我將要展示一個,可以把能量與演化聯結在一起的假說,說一個前後連貫的故事。我會極盡所能的,把它講得高潮迭起又老嫗能解;同時內容足夠詳細到可以被反證。這個故事,一部分是根據我自己的研究(你們可以在後面的延伸閱讀裡面找到原始論文),其他則是根據別人的研究。我有許多研究,都是跟在德國杜塞爾多夫的馬丁一起進行,他對「正確」的敏銳度,總是讓人驚訝。此外我也跟波明安可夫斯基(Andrew Pomiankowski)合作。他是一位具有數學頭腦的演化遺傳學家,也是我在倫敦大學學院最好的同事之一。同時,還有幾位能力卓越的博士班學生一起參與。這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經驗,而我們才在這段旅程的起點而已呢!
我已經試著讓本書的內容精簡,專注於重點,刪除了許多有趣但離題的故事。這本書,是一次論證,可以隨時依需要而詳細或精簡。它有許多隱喻性以及趣味十足(我希望是)的細節,對於想將一本以生物化學為基礎的書本,講到對一般讀者而言,也活靈活現,這可是相當重要的呢。畢竟我們之中只有很少數人,能夠輕易地看穿那顯微世界裡,如外星球般的各種巨大分子彼此交互作用,但那些才是貨真價實的生命。然而重點還是科學本身,這也是我寫作的風格。直言不諱的方式雖然老套,卻是美德,它讓文章簡潔,而且直指核心。假設我要提到鏟子,卻每幾頁就提醒你:所謂鏟子就是一種挖土的工具,用來埋葬人;你一定馬上就會大感不快。雖然線粒體可能沒鏟子那麼好懂,但是如果我每次都寫:「所有大而複雜的細胞,比如人類的,都有一種迷你發電廠;它是很久以前,由本來獨立生活的細菌所變成,今天則可以提供我們的細胞生存所需的能量」,那未免也太冗長了;我會說「所有真核生物,都有線粒體」,後面這句子,明顯要強而有力多了。當你習慣了少數幾個專有名詞後,你會發現它們可以在簡潔中,傳達豐富的意義;而且在這個例子裡,問題立刻浮現:線粒體是怎麼來的?如此我們馬上就來到未知的邊緣,同時也是科學中最有趣的事。我會儘量避開不必要的術語,偶爾再稍微解釋一次,除此之外,我希望你們可以慢慢熟悉重複出現的術語。為了安全起見,我還在書末加入主要術語的名詞解釋表。我重複檢查了幾次,希望本書可以對任何有興趣的人來說,都淺顯易懂。
而我真心希望你們會覺得有趣!我們即將要面對的新世界,是如此令人興奮;這世界包含了新的構想、可能性,以及即將讓我們了解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都是我們陌生的。我要為這個新而未開發的世界,描繪輪廓;像是展望一幅從生命源頭,一直延伸到我們的生與死的遠景。多虧了跨越生物膜兩側的質子梯度,以及與它有關的幾個簡單想法,將如此大規模的尺度聯結在一起。對我來說,從達爾文以降,生物界中最好的幾本書,都是論證集。這本書也將遵循這個傳統。我將論證,是能量規範了地球上生命的演化;同樣的力量,也應適用於宇宙其他任何一處。而合成能量與演化這兩個原則,將讓生物學變得比較容易預測,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何生命是如此運作;不只是在地球上,同時也在宇宙其他可能有生命的地方。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