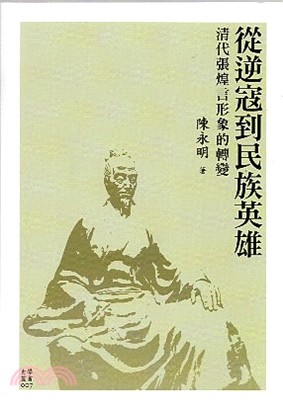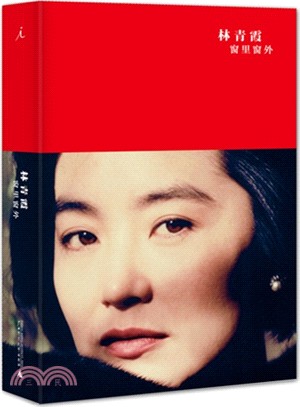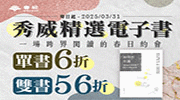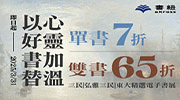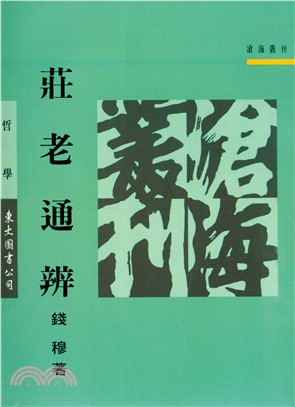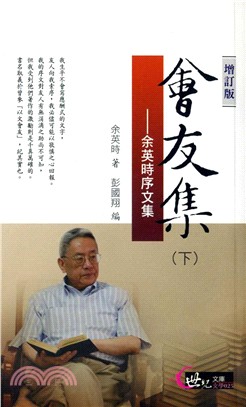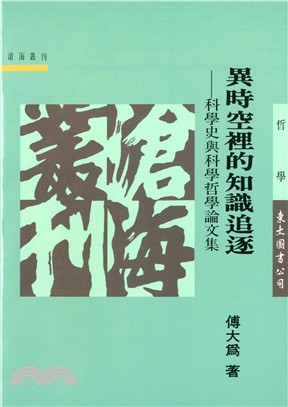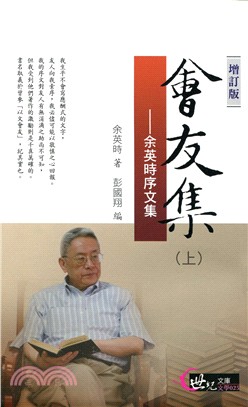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
商品資訊
系列名:史學叢書
ISBN13:9789863502487
替代書名:From Rebel to National Hero: The Images of Zhang Huangyan in Qing Dynasty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作者:陳永明
出版日:2017/09/12
裝訂/頁數:平裝/280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版次:1
適性閱讀分級:903【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張煌言,曾與鄭成功合作反清,一起北征、攻打南京。兵敗後,鄭成功遠走臺灣;張煌言則選擇以死明志,被清廷處決於杭州。張煌言從容就義的氣節及其抗清事蹟,並未隨著時間而消逝,反而在民間傳頌不絕,後世學者形容他是「南明抗清的最後一人」、「一代完人」。
然而,細究清代的兩個半世紀,張煌言的歷史形象並不一致,有著多次轉變的過程:從南明的「志士」、清初的「逆寇」,進而成為「儒家忠臣」,再到清朝後期的「革命先驅」,最終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延續至今。本書在論述此過程的同時,也探究「社會記憶」和「歷史書寫」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並分析形象轉變的社會變遷、群體認同等內在因素。特別是清中葉以降的急劇社會變遷,是如何左右人們的歷史記憶;張煌言的抗清事蹟、歷史地位,又是如何被一次又一次的重構和書寫。
作者簡介
陳永明
香港大學文學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文學碩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國歷史文化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中國史學史、南明史及清史。著有《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2011),及〈清入關後的滿化文化政策──以服飾和語言為中心的考察〉(2016)、〈政治抑壓下的集體記憶: 清初張煌言事蹟的傳播〉(2016)、〈乾隆《貳臣傳》立傳原則平議〉(2013)、〈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2010)等論文近四十篇。
序
序
張煌言是南明史上少數頗具偶像魅力的歷史人物。自他身故後,其悲壯的抗清事蹟,不但沒有隨著時光逐漸遭人遺忘,反因當事人遺著的傳世和士人的謳歌而在民間廣為傳播,並一再為史家所書寫。綜觀有清一代,這位歷史人物既是浙江一帶老百姓共同擁有的社會記憶,同時也是南明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其聲名之隆,即使在清亡後仍歷久不衰。張氏雖謂曾「抗清十九年」,惟考諸史實,他真正獨當一面在抗清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時間,大約只有短短的五年(1654-1659),後世論者卻每將他與奠定臺灣抗清基地、被清人視為心腹大患的鄭成功相提並論。箇中原因,頗有值得細心玩味之處;與此相涉的社會記憶和歷史書寫等問題,亦有深入探討的價值。
「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本屬兩個不同範疇的事。一般而言,前者乃係社會群體對特定人、事的集體回憶,當中往往帶有濃厚的情感因素和主觀判斷,很多時候,真相與想像之間更糾纏不清。反之,後者則為史家依從嚴格學術規範,對人類往事的重構和敘述,其間雖自擬定課題、篩選資料以至撰寫策略,處處均不無主事者的「一家之見」,但若是嚴謹的史學著作,原則上仍必須接受證據的制約,力求筆下做到「言必有據」,決不天馬行空,又或任憑己意而「游談無根」。因此,過往有不少人會認為兩者判若鴻溝,不應混作一談。然而,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事實上一直存在著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互動關係,並非完全毫不相干。
大抵上,社會對某人某事的集體記憶,在特定的環境下,每每會成為史家所關注的課題,而經史家書寫的人和事,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強化和延續了大眾對該人該事的記憶。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尤為明顯,特別是在社會經歷急劇變遷的時期。此因中國人向來重視「以史為鑑」,強調史學的「經世」價值。長久以來,每當星移物換、社稷為虛之際,寫史便成了史家用以扶危定傾,藉此振衰起敝的重要道德使命。至於統治者和野心家挪用歷史,以求達到政治目的之做法,更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若從這方面來看,不難發覺社會記憶或歷史書寫,均牽涉到社會話語權的博弈。參與其事者,或多或少都希望藉此重新界定他們身處世界中的常識和真理,從而重塑和規範他們眼前所見的失衡社會秩序。觀乎張煌言的歷史形象,在清代兩個半世紀中,由「抗清志士」、「儒家忠臣」、「革命先驅」到「民族英雄」的更替,無疑正是這種博弈下的結果。當中所折射出的,不單是論者在政治立場上的改轅易轍,更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在世界觀上的根本改變 ―― 由「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固是政治立場上由「華夷之辨」到「滿漢一體」的一百八十度轉變;而由「儒家忠臣」到「革命先驅」,則是思想理念上從服膺傳統「君權神授」,到倡議現代「主權在民」的知識型(épistème)過渡。同樣地,張氏「民族英雄」形象的出現,也標誌著中國人在國際問題上,已揚棄了舊有的天朝模型,轉而擁抱舶來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借用法國思想家傅柯的話說,這些變動不啻是一種思想上的「斷裂」(rupture)。
也許,於族群認同問題紛擾不休的當下,重新反思我們的歷史記憶,似亦不無裨益。
綜觀入清以來,涉及張煌言的文字,不時散見於史著、文集之中,而近代有關張氏的研究亦為數不少。因應本書匿名審查人的建議,書末特意加入一篇附錄 ―― 〈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介紹自清初至今有關張氏詩文的輯存,以及後世張傳的書寫情況,俾便讀者可以清楚掌握作所欲闡述不同時期的歷史書寫。
目次
序
導論
第一章ˉ百折不回的抗清事蹟
家世及早年經歷
加入抗清行列
從漂泊到北伐
從歸隱至遇害
第二章ˉ臨難毋苟免的忠君信念
堅持拼死抵抗的少數派
綱常為本的抗清理念
寧死不屈的忠君志節
忠君與孝親的兩難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
西湖墓穴中的「王先生」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清初史著中的儒家忠臣
全祖望的定調
從逆寇到忠臣
第四章ˉ褒忠文化中的勝朝孤忠
清室的旌表
「一代完人」形象的確立
表忠史學中的張煌言
歷史記憶的文化環境
第五章ˉ革命話語中的民族英雄
清末張氏遺著的流傳
革命風潮與張傳的重寫
民族英雄地位的確立
結論
徵引文獻
附錄ˉ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
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三章ˉ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摘錄)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大抵上,時至清代,「國亡寫史」已成中國的史學傳統,而對於明朝遺民而言,這無疑是他們可以報效故國的最後工作。不少曾經親身參與抗清運動的志士,在事敗歸隱山林之後,經常以國史為念,並且擔心自己與同儕的救國事蹟最終會因史冊失載而湮沒於後世。對於黃氏等遺民史家來說,為故國寫史,為勝朝忠臣立傳,固是無可推諉的「後死之責」,而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緬懷過去,同時更具有彰顯人間正氣的現實意義。黃宗羲替張煌言所寫的墓誌銘,開宗明義便道出這一點: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常人藐為說鈴,聖賢指為血路也。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為,即非從容矣。
這番話,反映了他對士人職責的認識。在黃宗羲心目中,「扶危定傾」是人臣不可推卸的責任,只要一日「吾身未死」、「吾力未盡」,便不容苟且塞責。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則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面前,其考量的重點便不在成敗得失,而應在於「義之所在」。換言之,他們不應因為本身的努力或可能徒勞無功,而放棄作為「四民之首」所應盡的使命和責任。職是之故,儘管環境惡劣,末代忠臣的努力在別人眼中有如「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不但實際效果成疑,還會換來世人的訕笑,被譏評為不識大體;惟在道德責任的驅使下,他們卻仍然堅持不懈,務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黃宗羲對張煌言至死不屈的肯定,旨在道出:明末忠臣所體現的,正是儒家傳統強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從容」道德精神。
黃宗羲對明遺民姜埰(升菴,1607-1673)於明亡後堅持客死異鄉的評論,或可以作為補充。姜氏原為山東萊陽人,崇禎四年(1631)進士,明亡前因言獲罪,貶戍宣州。據黃氏記述:
甲申(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
譜載,姜埰在謫戍宣州衛途中,不幸遭逢國變而流落江南,後雖得南京政府赦罪,但念及並未獲得先帝寬宥之旨,有生之年都不敢違背出戍之令,堅持不應私自回鄉,臨終前更一再囑咐子女,要把他葬在宣州,以示其不忘先帝之志。黃氏對姜氏看似近乎迂腐的作法,評價如下:
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而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劫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劫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 ……。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是之謂「義至」。
從黃宗羲對姜埰因無朝廷「放赦之文」而不敢「營歸田之計」的稱許,可見他認為人臣的職責必須貫徹始終,力求做到「仁盡義至」。在他看來,仁人志士這種發自內心的自我要求,並不會因為外在環境的改變而須臾或忘。這正好解釋何以他對張煌言「從容」之舉推崇備至。黃宗羲在張氏墓誌的結語中,特意將墓主與宋末忠臣文天祥作一比較,指出張氏的成就比諸後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喙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為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1646)航海、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虛喝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為益難矣。
黃宗羲在其《行朝錄》的序言中曾自言,他之所以著力於勝朝舊事,無非欲藉助史傳,使後世「知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盪為冷風野馬,尚有此等人物」。由此足見,黃氏為張氏寫誌立傳,目的便是要表彰死者值得敬佩的「從容就義」道德勇氣,使之得以流芳百世。正如另一同時的遺民林時對(1615-1705)所說:「孤臣軼事憑遺老,寫向琅函萬古傳。」這種動機,可以說幾乎是所有明遺民撰寫南明史的主要原因之一。類似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明遺民高宇泰(1618-1678)為明季死難忠臣所作的《雪交亭正氣錄》,其用意便在於使「人心繇而不泯」,讓忠臣的行誼「得憐且愧者十百於億萬人之中」。又如查繼佐《國壽錄》之命名,實寓有「其人雖死,而其事不朽」之深意。借用侯方域(1618-1655)所言,抗清者「功不成,節乃見」,彰顯「故明養士三百年」之報,可以說是明遺民為明、清易代死節者立文字的共識。
更重要的是,從明遺民的角度出發,他們為勝朝寫史,還可以用來表白自己堅貞不屈的志節,特別是為殉節忠臣所立的文字,它不但是對死者的崇敬,同時也對自己遺民身分表示肯定。在大多數清初明遺民的心目中,那些在易代之際殺身成仁的同儕,其節操與自己於明亡後堅拒不出的志節是一致和相通的,兩者之間並無高下之分。用黃宗羲的話說,「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他以宋史為例,指出:
宋之亡也,文(天祥)、陸(秀夫)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
儘管遺民與殉國者生死殊途,但是他們為故國所作的犧牲,卻同樣教人肅然起敬。因此,對於死難者的追思和表彰,也同時意味著對生存者的肯定和勉勵。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黃宗羲替張煌言寫墓誌銘,亦可以理解成是他對本身道德抉擇的一種自我認同(self-identity)。作者視張氏為明忠臣的典範,並通過對其為故國獻身殉節的回憶,確認自己的遺民身分和責任,由此使自己更加堅信「盡忠守節」是每個前朝遺民必須堅守的基本道德原則。而一如為國捐軀,遺民志節也是儒家道德的最高表現,亦即黃氏口中所說的「天地之元氣」。職是之故,黃宗羲筆下的張煌言,不啻是作者源於忠臣情結的自我投射和自我期許。這也是當時整個明遺民群體,通過對敘述明季忠臣事蹟所建構的集體記憶。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