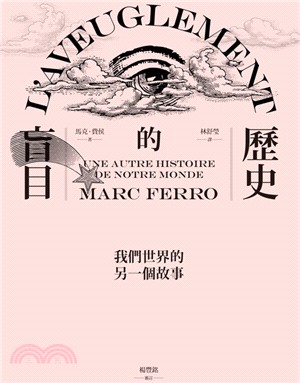商品簡介
人們通常比較相信幻象,更甚於已經建立起來的真相――馬克.費侯
全球知名的歷史學者 年鑑學派大師馬克.費侯代表鉅作 撼世登場
費侯深入過去,只為說明當代的盲目,同時找回重要的共鳴。「社會的過去是一個取之不盡的仇恨寶庫……。」他語帶深意地表示。――《世界報》(Le Monde)
歷史學者企圖揪出盲目歷史的源頭,呼籲重視歷史的清明與智慧。――《程序》(LA PROCURE)
人類的命運,從來息息相關
陳弱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 強力推薦
楊豐銘/中研院民族所博士後研究員 審訂
《歷史的盲目》是當代法國學者馬克.費候的新著。書名的意思是有關「盲目」的歷史。馬克.費候主要研究二十世紀前期的歷史,特別專精於俄羅斯/蘇聯史以及電影史。這本書所說的「盲目」有很多種,包括:未能預見重大的潮流與事件、對現象的誤讀、忽視危機、拒絕承認發生的事、以多重標準評判事物。由於作者是現代歐洲史學者,書中談的幾乎都是對二十世紀和當代歐洲造成嚴重衝擊的事情,但其中不少的影響也是世界性的。某種程度上,這本書是負面的歷史,充滿不好、違反人道的場景:衝突、戰爭、災難、暴政、屠殺、經濟危機等等。重點是,人們沒有預見這些事,或者雖然看到但不以為意。看這本書,會覺得二十世紀以來雖然是人類技術和經濟空前發達的時代,也是危機重重的時代。這的確是我們時代的重要特徵。這本書所想傳達的訊息應該是,設法創造清醒的狀態,不要一再受到突襲。――陳弱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位法國年鑑學派的資深重要史家,過去我們台灣對他的印象以擅長處理電影與歷史的課題居多,偶爾還有一些認識是專長在俄國革命、一戰史、二戰史、法國史及殖民史,好像就沒了。其實他著作等身,我們引介進來的只是一小部分,好在現在又多了一個選擇。透過《歷史的盲目》,作者振聾發聵地指出,人們對於當代現勢,其實一直無法從過去經驗記取教訓。有各種盲目造成這些行為,像是輕蔑、輕信、盲目樂觀及不願承認。從伊斯蘭革命、共產政體垮台到阿拉伯之春,這些事件似乎都未曾被預期到,這在在顯示我們毫無歷史意識及拒絕接受事實;或者是加入歷史卻不接受歷史。其中有句「人們通常比較相信幻象,更甚於已經建立起來的真相」,根本一語道破現今國際現勢的窘況。――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耄耋之年的年鑑學派老將馬克‧費侯推出這本鉅著,縱筆所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新殖民主義、猶太大屠殺、伊斯蘭激進主義一路寫到911之後的恐攻事件及其餘波。就地理空間論,費侯要打破盲目的探照燈則遍及法國、德國、美國、俄國、中國和阿拉伯世界。費侯告訴我們人類之所以盲目是「自以為是」的結果,許多自以為是的政策造就後來無可挽回的悲劇。費侯結合事件史和長時段的手法,為我們展演了上個世紀的歷史鉅變以及關於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種故事。――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
為什麼我們在面對現實時,這麼盲目?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主義的崛起,猶太人的滅絕,五月風暴、共產主義垮台、2001年911恐怖攻擊、經濟危機,或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崛起:這個世紀這麼多的插曲,顛覆了世界的秩序,也出其不意地讓我們措手不及。
在我們從來沒有被知會的時候,在專家們一片混亂的時候,在如今幾乎即時可用的分析要素增加的時候,人們沒有預測到的無情狀況,不斷出現。
在整個國家、政治領袖或單純的市民都不知道、不能夠或不想要突然看到事實的真相的關鍵時刻,所有人都被不同形式的盲目折磨著:缺乏判斷力或理解能力、否認、盲從、錯覺或學說的影響。也因為在面對悲劇與大變動時缺乏勇氣而盲目。
但我們什麼都可以預見嗎?面對歷史的轉折,有可能想像出處、反應或了解嗎?帶著嚴謹與熱情,大歷史學家馬克.費侯要來探討這些問題,解開我們這個世界的盲目的原因,辨認幾個識見卓越者的英明睿智。完全未曾發表過的調查,將為我們的思考帶來啟發,讓我們的識見更卓越。
評論
馬克.費侯在《歷史的盲目》一書中偶爾會提出一些困擾的問題,而他也堅定地以教學手法回答這些問題,沒有敷衍、沒有廢話,讓本書更值得一讀。他主張,「身為歷史學者,就是要思考並反問自己一些問題,勇於對官方說法提出質疑;要教導國民了解問題,教他們思考問題……」,而他的書就符合這個目標。
――《政治與議會評論》(REVUE POLITIQUE & PARLEMENTAIRE)
《歷史的盲目》讓人覺得好像是馬克.費侯長久的寫作生涯中,曾經討論過的不同主題的掃描,橫跨作者自己看過及經歷過的某些證據時刻,給人包羅萬象的感覺。―― Un compte rendu de Jean-Guillaume Lanuque
作者簡介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 (EHESS) 研究部主任,法國史學雜誌《年鑑》(Les Annales) 的主編之一,將電影作為文獻和媒介進行歷史研究的先鋒。著有《俄國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917)、《第一次世界大戰》(La Grande Guerre)、《電影與歷史》(De Cinéma et Histoire)、《貝當》(un Pétain) 、《殖民史》(L’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 《世紀之謎︰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LA VÉRITÉ SUR LA TRAGÉDIE DES ROMANOV)。他也曾參與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的許多歷史節目的製作,著述三十多種,翻譯二十多種語言,世界風行。
關於譯者
林舒瑩
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畢業,比利時法語魯汶大學大眾傳播系及歐洲研究所碩士,現專職翻譯,譯有《我還活著――潛水鐘之愛》、《第一口啤酒的滋味》、《高老頭》、《小氣財神葛蘭岱》、《我還不想睡》、《我不想去上學》、《世紀之謎︰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我為何成為美國公民》等書。
序
盲目與歷史感
2015年1月,在針對《查理週刊》雜誌社、一家猶太商店與一些警察的恐怖攻擊事件後,歐洲輿論突然出現難得的團結,顯示某種覺醒正在我們的社會中發生。突尼斯巴爾杜博物館槍擊事件更確認了這個情況。長久以來閉著的眼睛似乎睜開了,面對我們的歷史,不再有各種形式的盲目,無論是昨日的歷史,抑或今天的歷史。如何才能了解它其實一直不斷地在湧現呢?我們有一大群專家、學者、政治人物,準備和我們分享他們對於我們生活環境中的任何變化所做的預兆分析。問題當然不只侷限在最近的事件當中。亞蘭.居貝(AlainJuppé)承認,他曾完全被2010年出其不意的突尼西亞革命給騙了。歐巴馬也承認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埃及的事件,不過關於這個事件,十六家按理應該向他說明的新聞社,居然都不知道要警告他。然後,伊斯蘭國就突然出現了……
然而,還有其他的翻轉以更深沉的方式,搖撼我們對於歷史感的信念,例如:四分之一世紀以前,這個歷史感還在想像資本主義在蘇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未來?歷史往往當下便抓住其當事人的錯,此一形式的盲目,前例不勝枚舉。在此有必要回顧提醒一下,這些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情況嗎?
2007年:隨著次級房貸危機而來的金融危機。
2001年:世貿中心恐怖攻擊。
2000年:當大家在期待日本時,中國突然成為經濟超級大國。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的共產主義結束。
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
1968年:由年輕人發起的法國五月文化革命。
1962年:法國人自阿爾及利亞撤離。
1942-1945年: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
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
1929年:經濟大蕭條。
1914-1918年:一場人們以為會很短卻持續四年的戰爭(一次世界大戰)。
在這些未曾預料到的集體盲目以外,還要再加上屬於個人的或純屬對於情勢的誤判,例如美國人排除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可能性的誤判,或史達林拒絕相信間諜理查.索爾日提供給他的希特勒下次進攻蘇聯的日期之誤判。
這些頻頻出現且如此驚人的盲目類型,卻沒有什麼規律可言。其他危機或現象都能夠被社會、被它的觀察者、被它的領袖預料到。「不要搞錯敵人,他在南方,不在東方」,就在2015年1月的恐怖攻擊,及1月11日的覺悟及自由警報的大日子之前,我們寫下了這段話。
十九世紀,由於預感到「歐洲病夫」鄂圖曼帝國即將殞落,及民族性的起飛將造成它的分裂,西方的總理公署紛紛加以利用。因為類似的理由,許多積極的參與者也預料到奧匈帝國的崩落。未來的推測,在看起來似乎無法避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清楚地顯現出來。然而,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從此將缺乏可以證明一場戰爭的真正且具體可見的利益,因為列強已將世界瓜分殆盡,往後的戰爭將只會帶來毀滅與革命。俄羅斯、德國與匈牙利,就曾經有過戰爭與三次革命。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像一次無法避免的失敗出現了。去殖民化很快就像一個抑扼不住的程序蔓延開來,無論它是否存有一些足以去抗爭的反抗力量。然而,許多阿爾及利亞法國移民卻沒有意識到,FLN(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部隊在阿爾及爾行軍當天所策動的力量。對此,我們要如何防止以色列的領袖與殖民者有天也掉入類似的盲目之中,帶來悲劇不安的結果呢?
在其他族群當中,為什麼匯集偶爾具預言性的相對遠見與類似的盲目於一體呢?這就是本調查核心的問題之一。出乎意料或沒被注意到的事件之開展,和一些不同屬性與廣度的現象及情勢結合。我們可以只考慮評估他們的可預見性程度嗎?當然,在過去,有一些無法預見的事件,如來自歐洲的航海者與美洲人相遇。至於那些我們編列造冊的人,假如可以肯定有些人會像遭受雷殛一般的打擊—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或2001年的世貿中心恐怖攻擊—那麼其他人則根深蒂固於一段或長或短的歷史的過去當中。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可以察覺它的突然出現,卻不見得能夠想像到它的出處。這就是猶太種族滅絕的情況,也就是說歷史的可預見性是沒有芮氏評級表的。
但是,假如現在是未預料到的,那不就是過去被誤解了嗎?在面對未料到的新局勢這個第二個形式的盲目以外,可以再加上在面對人們不想看、不想知道的事情時的各種拒絕圖像。從德國人拒看納粹受害者的屍體開始,一直到其對所做行為的犯罪性質之否認。其他的盲目形象諸如:軍隊的盲從、各國對於其歷史故事的信仰、憤恨不滿、空論派的精神等等。
研究面對歷史時盲目的原因,這個問題在啟蒙時期之前,在西方是完全沒有被提起的。社會的變化已經不再被歸因於天意,而除了證券交易商與保險人員以外,人們也不再那麼地在過去的分析去尋找未來的道路,因為他們認為從此以後要靠科學與理性去找到它。這是認同進展的歷史感給人的想像。在西方世界裡,法國大革命就代表這個歷史感知中的第一個變化。然而,代表這個變化的最重要角色—中產階級—卻無論在它的發展過程中或之後,在被認為是它孕育的完美社會中,都無法用技能或才華取代繼承(也無法以財富的等級取代血統的等級)。因為工業革命而發展的社會思想,於是將歷史進展中的再生功能與主使者角色歸於工人階級。
在這個計畫之下,再標榜一個有文化、有技能、博學而非商業的社會。因此,為了替思想者以被剝削者的名義取得的權力辯護,那麼為革命計畫提供一個科學的輪廓就變得必要了。在十九世紀,一如科學,政治社會也「向前進」,從專制主義朝向自由主義,再從自由主義朝向民主主義,知識與「正確」的想法之傳播必然要確保進展的勝利,並透過普選,確保機構的民主化及之後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歷史感。因此,造就了利用歷史的原動力—階級鬥爭,來結束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形式的時代。整體的運動似乎不可逆轉。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猛然打斷了這個程序。很多被認為與歷史的發展程序相同的革命運動,突然都失去了它的很多組成。失去了它的武器:反戰的總罷工被共產國際否決,因為罷工只在一些「先進的」國家進行,這其實比較有利於君主專制政體。但革命運動也失去了它的論據:社會主義已肯定經濟利益的決定性力量,而愛國的熱情則表現出它的力量。當吹動第一聲號角,並且根據義大利自由黨創黨人克羅采(BenedettoCroce)的口號,出現「假如社會主義是一個理想,那麼保衛家園也是一種天性」時,它也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最後,它也失去了它的希望。出發上戰場,讓人忘了革命的概念。勝利也是。對於歷史感的分析,難道已失去所有依據?它並不全然贊成一個單一的意念,但也並不因此不贊成一個意義或一個方向的概念。三年後,專制政權的失敗、貧困、鎮壓與仇恨,讓俄羅斯爆發革命。它把一切都帶走了:沙皇制度、領導階級、體制。它會擴展到整個歐洲嗎?歷史又恢復正常了嗎?
以這個歷史觀點來看的另一個衝擊,是法西斯主義以及德國納粹主義完全無預警地突然出現。德國,這個科學的祖國,人們等的是由它來接大革命計畫的班。創傷的廣度前所未有。它標示了馬克思理論的不恰當,一如非理性戰勝科學精神。第三個衝擊—讓人失去對承襲自進展與理性的歷史感之真相的信仰—是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隨之而來的蘇維埃系統的垮台。
然而,當人們呼喊這些難以置信的事件象徵「歷史的終結」時,他們不也表現出一種信仰的行為?確實,我們並不想聽到:「伊斯蘭的機會到了。」但這不也是一種信仰的行為,在啟蒙時代,這個肯定的意思是說,因為理性,社會從此將變成自己命運的主宰……在1930年代的背景裡,保羅.瓦勒希(PaulValéry)反而看到歐洲衰退的徵兆與殖民化的結束。然而,他沒有考慮到該時期世界局勢顯而易見的那一面,也就是美國與蘇聯強權的突然出現。他也沒有考慮到殖民地造反的預示徵兆—東非、印度、印度支那。他沒有提到殖民化成本或相關的問題。他的觀察始於前面的時期,也就是歷史的理性行為應該戰勝一切的時期:
歐洲建立了科學,科學改變了生活,也讓擁有它的那些人的能力變多了。但是,透過它自身的本質,它基本上是可以傳播的;它必然導致一些通用的方法與祕訣。它提供給一些人的方法,所有其他人也可以得到。這不是一切。這些方法增加產量,而不只是數量。在傳統的商業目標以外,再加上欲望與需要透過傳染或模仿所產生的許多新的目標。人民很快就要求獲得他們必須獲得的知識,以便成為創新事物的愛好者與購買者。在這些創新事物之中,武器是最新近的……。因此,三個世紀以來,造就歐洲之優勢的人為不平等的武力,有快速消失的傾向。而建立在原始統計數字上的不平等則有重新出現的傾向……。
也就是說,中國人、印度人、非洲人的數目都在增加,歐洲人的數目卻停滯不前……
在整個歷史當中,沒有什麼比將歐洲政治與經濟的競爭力和歐洲科學的統一與聯盟進行比較、結合與對質更愚蠢的了。……抗爭,不過是在西方範圍內的長距離運輸,﹝並且﹞不可避免地造成歐洲回到它的面積所指定給它的次等地位,而它的精神工作與內部交易已把鬥爭從這個地位抽離出來。歐洲已然沒有自己的想法的政治。
「沒有什麼比……更蠢」……或者,今天「沒有什麼比」慶祝中國製造第一百架空中巴士或賣掉這些不知道它的目的為何的尖端武器的香檳酒會「更蠢」……愚蠢,還是盲目?
這個關於從二十世紀到2015年的盲目的調查,有助於解釋要澄清一個非常隱晦不明的一般情況有多困難,以至於這幾十年來,人們開始懷疑進步的概念嗎?不再掌握歷史的社會,就像馬勒霍(Malraux)曾經預言過的,再也不知道誰會相信宗教的興起?但所有人都無法相信,只是無法相信,卻又感覺到在低沉的深處,有一股還只是一盤散沙的怒氣。正如歷史學者羅桑瓦隆(PierreRosanvallon)所說的,民主政體只有在西方才受到監督,除非人們以納粹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主義的方式,對它的原則與合法性提出異議。假如社會主義自蘇聯政體垮台以來失去了它的一部份武器,假如全自由黨人在公海上划這樣一條愚人船,民主國家與共和國就應該一起更新其軍火庫的資源—我們稱之為翻轉歷史的東西的另一面。這裡,我們試著將過去幾個盲目的源頭去掉,如此有助於識別我們周遭的盲目嗎?
鑑於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未曾發表的,無論情勢是否可預見,我們都必須找出一個途徑才能回答。第一個方法,也就是「短歷史」之法,就放在自大戰結束以來依序出現的盲目圖像與表現之上。未預料到的、已完成的、被激起的事件。第一個?1918年11月11日,由德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這個矛盾的歡騰景象:他們以為已經贏得戰爭,殊不知這是因為戰敗了,他們簽署停戰協定。這是「群眾的誤解」。此外,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幻覺助長戰勝者的陣營。然而,假如歷史不會重演,那麼某些行為是可以讓它被相信。群眾的誤解還發生在1938年。達拉迪(Daladier)自慕尼黑會議歸來時,法國人的這個歡騰景象:他們相信和平被救回來了。
此外,在這第一個方法中,我們也將提到這些反駁,假設有的話。我們也會提到一些平行的情況。我們也會探討盲目的其他表現方式。
「管理,即是預測,」我們很樂意和孔德(AugusteComte)看法一致。然而,預測的能力,或者說預言的能力,只能基於分析的能力。
在第二個方法中,也就是和前者交叉的「長歷史」之法,如果我們可以利用這和過去一樣久遠的最後一個表達方式,我們將尋找盲目的根源,就像保羅.瓦勒希在這裡所進行的。因此,我們認為有在基督教國家或伊斯蘭地區培養政治精神的學說的作者與信奉者,對於他們運用這些學說的能力都很盲目,無論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伊斯蘭主義……事與願違的結果還是歷史的濫用,一些指揮社會所承擔的行為的大原則,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嘲笑,如人權、慈善、國家主權。在一些已經能夠顯現出某些盲目的來源之中,社會的過去必然在列。由此,我們也聽到國家、黨、教會的長篇傳奇、個人與家庭的回憶錄(雙重遺產),以及謠言、種族主義、排外的陳腔濫調與神話。在這些理論的與實用的因素的交會處,資訊有沒有加入歷史的可理解性之中呢?使用的是什麼語言呢?加入掃除這些盲目及其根源行列的學者、作家與藝術家,都將面對這個結論。除了文學以外,電影與社會科學也把他們的卓越識見的部份帶到歷史的智慧裏頭。
台灣版序 ⊙尉任之 譯
《歷史的盲目》出版不到一年,國際現勢再次證明人們沒能從過去的經驗汲取教訓。這個文本致力於拆解盲目的不同形式,和盲目所滋生出來的種種行為。
這本書指認的第一個形態的盲目是「輕蔑」,也就是我們對一個事件所下的錯誤詮釋。在二十世紀我們第一個可以察覺的案例,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人歡騰地誤以為打了勝仗。
近一年來最令人擔憂的輕蔑是西方世界對土耳其艾爾段(Erdogan)政府的信任,咸信他這幾年建立了一種以基督教民主為範本—這裡當然是伊斯蘭—的實踐。事實上這是一種伊斯蘭式的獨裁,重拾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泛突厥的夢想,隱藏著建立一個邊界從「地中海到中國海」,將俄羅斯和中國突厥斯坦(中亞和新疆)都納入版圖的大國霸權的企圖心。
第二種我們可以指認的盲目型態是「輕信」,特別是那些一九一九年後那些朝聖者們的輕信,他們為蘇聯的第一批建設成果欣喜若狂,卻對同時進行著的拘捕和契卡(la Tcheka)—政治警察—剝奪一切政治自由的行為視若無睹。「輕信」,也是今天這些受社群網站上傳播的誓語愚弄而前往敘利亞跟伊斯蘭國並肩作戰的人士,直到他們被拘捕、凌虐,像懺悔者一樣回到原來的國家:突尼西亞、法國、比利時等等。
另一種盲目的形態是經濟學者與投資客「盲目的樂觀」,對中國,甚至印度這些超級強國的崛起絲毫不察,循環的概念不再是經濟學必然的法則,而「積極的態度」也不再有相同的用途,至少在相對的穩定性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
「否認」,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和日本人面對他們史無前例的罪行和殘忍時自願的盲目。
尤有甚者,日本人堅持否認「慰安婦」的用途,甚至在戰敗後,把她們「當作禮物」送給美軍。
「否認」是盲目相當出名也可能是最實用的一種型態,人們用來面對他們自己的種族歧視。非常清楚地,在面對黑人領袖時美國無所不在的白人至上主義,南非則是凌駕一切的黑人至上主義,我們甚至無法想像它的領導者曾經擔任過曼德拉的副手⋯⋯歐盟不願見到它所肩負的理念在因恐懼難民潮而逐漸抬頭的民粹主義下崩解,不論這些難民來自何處,他們都是「全球的不幸者」,但除了德國以外,其他國家都只以美麗的修辭來予以搪塞。
至於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崛起,人們則拒絕認清,一方面它源自西方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孕育它的主要國家像沙烏地阿拉伯、伊朗、阿富汗事實上並沒有被西方殖民過,它們所感受到是對曾在世界閃耀的伊斯蘭的羞辱。
目次
序 盲目與歷史感
第一章 意外事件,這些組成歷史的星雲:中國的覺醒、五月風暴與蓋達組織
第二章 群眾的誤解
第三章 激進的盲從
第四章 盲目的樂觀
第五章 空談理論的精神:納粹主義升高
第六章 透視戰爭(1939-1941)
第七章 猶太人,盲目的受害者(及其他隱形的犧牲者)
第八章 不承認,對照形式:德國與蘇聯
第九章 人們有感受到大原則的偏離嗎?
第十章 交叉與合併的盲目:阿爾及利亞的悲劇
第十一章 這些助長盲目的歷史觀點
第十二章 面對蘇聯解體的費解
第十三章 面對歷史的個人
第十四章 過去及其傳承
第十五章 「資訊自由」的責任
第十六章 電影、螢幕或現實的口譯者
結論
參考書目――出版社
書摘/試閱
第一章意外事件,這些組成歷史的星雲:中國的覺醒、五月風暴與蓋達組織
最近的三個事件與形勢讓許多社會與政府驚愕不已。這三起發生在最近五十年內的重要事件,因為無法預料,而讓人無從評斷:正當人們期待日本的經濟復甦時,中國經濟強權卻大舉入侵;「五月風暴」的年輕人運動;以及蓋達組織的出現,接著是前所未有的 2001 年紐約世貿中心恐怖攻擊事件。很明顯的,這些事件沒有什麼好比較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它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已經被認定為「無法預料」。因此,把不可比較的拿來做比較,是某種歷史實驗,正如研究古希臘的學者馬歇爾.德蒂安(Marcel Detienne)所建議去做的。
對三個互相沒有任何關係的歷史狀況做如此「違反常理的對照」,其實可以讓我們瞭解到某些本質不同的星雲(nébuleuse)—經濟的、文化的、政治宗教的—已經可以組成歷史的動機,即使當代大國的領袖們並不是這樣看。事實上,領袖們對於世界的理解是從某些機構或組織開始的,而這些星雲卻是建構在所有這些機構或組織的渠道之外。確切地說是因為這些事件按理說沒有任何共同點,除了沒被人預料到的以外,隨著我們「實驗」的抽絲剝繭,它們之間被證實存在的相似點,以一種驚人的方式,一一浮現,這是在面對歷史時的前幾個盲目的論據之一。隨著被調整過、被變造過、被加工過,有時甚至變得難以辨認的歷史的流逝,我們在一些本質上非常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發現了它們。在這些論據當中,至少有二個必須馬上說明。
一方面,我們發現連結在某種「星雲」之中的某些角色之間的非官方「關係」,長期以來在某些由有地位、有特權的聯盟、機構或組織所組成的「社會」眼中,總是被視而不見。社會對於不符合制式社會形式的一切,都覺得不對。另一方面,這些前所未見的力量浮現之初的做法,和通常在我們看不到異類做法時所表現的做法是不一樣的。那麼誰能夠評判它們值不值得或有沒有能力進入歷史呢?
意料之外:中國商店的經濟力
二十世紀初或甚至之後,有誰能夠想像中國經濟的飛躍竟是從它的商店或小企業迸發?經濟學家兼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不行,就連那些把經濟的進步和生產合理化結合起來的人也不行。我援引他的一句話:「商店把城市堵死了,商店聚集也無法冒出一個傲慢的資本主義,甚或民主政治的中產階級。」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強權一直覬覦「中國市場」,企圖瓜分中國,以便在中國建立漢學家伊夫,謝佛利(Yves Chevrier)所謂的「共管式」的統治。
在 1911 年推翻帝制的中國革命之後,中國變成共和國,中國市場夢消失了很久,更因為 1949 年的共產革命,這個夢甚至可能永遠消失了。從這天開始,當人們談到中國,馬上就會聯想到它所代表的,與蘇聯有關的政治風險。1951 年開始的韓戰證實了這個想法。假如我們看戰後的美國作品—例如權威的漢學家鮑大可(Doak Barnett)的作品—就會發現中國市場的神話消失了。然而,「在這些年期間及其後,」歷史學家兼漢學家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沿海城市的織造技術因金屬框架工藝的引進而改良,從而帶來了進步,然而在它們處於世界相對較落伍的系統方面,卻顯得是可以被忽略的。」織造之後,是為電子、視聽設備,尤其是平板、玩具等等的組裝與代工。中國的小玩意馬上遍佈世界各個階層,甚至包括送給歐巴馬總統表示敬意的兒茶樹盒子:薄荷 made in USA,盒子 made in China。從此以後,翻轉是很驚人的。1975 年,中國僅佔國際貿易的0.7%,2007 年,已佔全球出口的 9%,進口的 7%。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佔了很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
如果這個挑戰在歐美好像前所未見,那是因為他們的領袖和專家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共產黨與台灣的政治關係上,甚至香港的地位上。他們沒有衡量這三個主體的華人之間非靜態的地下關係的重要性,此外還有散居各地的中國人:印尼、泰國、新加坡等等,約有三千五百萬人口。各種經濟網路就這樣以一種緩慢的任務分擔的傾向建立起來;不一定要經過正式協定才能具體化,因為這樣的協定可能會更緊繃,尤其是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南韓之間。分工合作避開了西方。在這個互補的背景當中,台灣的華人可以獲取西方的科技,香港的華人扮演走向外國市場平台的角色,同時也帶來他們的金融經驗,而中國大陸則提供廉價的勞動力。這個人才薈萃的重要性,在北京政府打造出一些向香港與台灣的華人開放的「經濟特區」時,就顯現出來了,並且在外國資金大舉湧入之前,就已經到位。因此,中國便成為設備組裝零件輸出國,換取原料,而在西方的「中國市場」夢中,機制已經被翻轉了。最初,一個沒有中央領航,也沒有方向的星雲商店,就這樣造就了一個不走傳統發展路線的突飛猛進,也跌破一些外交家與專家的眼鏡。
五月風暴:反對既定秩序的年輕人
在法國,1968 年「五月風暴」(Mai 68)的爆發,完全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一開始是學生運動,反抗的對象是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部長。數週前他才宣佈「他最感驕傲的是他對國家教育的作為。」戴高樂並不瞭解這個事件的主張:「他們到底要什麼?」被搞得惱火的他問。低估了示威力道的他,依舊照著他很久以前就排好的官方行程前往羅馬尼亞。當他回到法國時,眼見國家被罷工癱瘓了,許多車子被燒起來,便直率地說了一句:「改革,可以!政治混亂,休想!」於是,事後,人們回想起來,才發現這些事件發生前有幾個預兆。早在 1967 年,國際境遇主義在史特拉斯堡的宣傳小冊子中便揭露了某個正在大眾化的社會團體的身分,說這個團體無法在社會中扮演和他能力相符的角色。這指的正是學生。他們因為受到局部措施的影響,例如大學宿舍禁止性關係、高等教育入學篩選計畫等等,而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情緒。1968 年,年輕人的「政治訴求」首次以行動的方式出現,意圖取回屬於他們這個年紀、這個世代的權力。他們的抗議不是出於一個簡單的動機,或只是再度表達他們對父母的不滿,就像之前共產黨、基督教或納粹的年輕人所做的那樣。這群學生過著文化類似的生活,被公認是新類型的消費者,但他們有屬於他們自己的道德觀,一種在兩部「賣座」的美國電影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特殊觀點: 拉茲洛. 貝納迪克(LászlóBenedek)導演,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飛車黨》與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導演,詹姆士.狄恩主演的《養子不教誰之過》。在法國,新浪潮電影揭露了不可言明的社會關係,尤其是克羅德. 夏布羅爾(Claude Chabrol)、高達(Jean-Luc Godard)和他們特立獨行的名演員,碧姬.芭杜或揚波.貝蒙。1968 年文化部想改動法國電影資料館,也就是存放這些膠卷的聖殿, 同時想解雇一手創立它的亨利. 朗格盧瓦(Henri Langlois),終於在 1968 年 2 月引發了一場盛大的示威遊行—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負責這項決定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勒霍(André Malraux)被喝倒采,才建議戴高樂將軍要照顧年輕人—他吃了苦頭才知道必須如此⋯⋯
這些年輕的示威者也譴責引發越戰、造成蘇聯鎮壓布拉格的美國人。傳統的政治劃分界線已然不見。同樣消失不見的還有對政治或工會領袖的尊重,以及,更普遍的,對於菁英分子的尊敬。權力原則再次受到質疑,無論在校園或家庭裡都受到嘲笑。最初幾場示威的特點是輕鬆與揶揄。最初的口號是「要做愛,不要戰爭」,「禁止去禁止」,而第一個口令是把花及小女孩的微笑獻給維持秩序的人。接著,暴力遊行之初的加強鎮壓造成騷動,汽車燃燒的圖片也凸顯出集體的意識。在它的結構中,運動有被一大堆行動委員會與各種政治形式的獨立小團體煽動的原創性,除了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l’Union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以外。在這些運動之中,「三二二運動」(Mouvement du 22 mars)由頗具領袖魅力的丹尼爾.龔邦迪(Daniel Cohn-Bendit)策動,他的身上集結了來自社會主義革命組織或野蠻行為,這些舊托洛茨基派分裂分子,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想法,馬庫色認為:在後工業化社會中,學生建立起了可自由抗議的唯一力量。完全被事件嚇到的工會組織與共產黨,尤其是在暴亂之夜後,對這個「小中產階級」的運動顯得有些敵意。喬治.馬歇(George Marchais)就曾在《人道報》(L’Humanité)中寫下:「丹尼爾.龔邦迪『這個無政府主義
的德國人』。」但他卻在第二時間決定附和抗議浪潮。欠缺牽制運動力量的他們,可以在此找到加強壓制現場的足夠力量。瞭解到鎮壓對於抗爭運動有某種擴散作用的黨與工會﹝其子也出現在遊行隊伍當中的州長莫里斯.葛里(MauricGrimaud)所領導的鎮壓,沒有出現太多暴力﹞,也對逐漸升高的運動感到震驚,示威者以佔領工廠,然後是某些象徵地標,如奧德翁劇場(Odéon)與法國廣播電視台(ORTF)的方式,來回應政府的政策。接著是全國性大罷工。
因此,法國的學生運動並沒有引起一種和美國社會平行的社會群體—嬉皮,也沒有產生一個像在德國產生的政黨—不久之後的綠黨,而是具有驅動作用,將文化革命變成社會運動,接著演變成政治危機。1968 年 5 月 20 日,有四到六百萬人罷工。事件自此不再由學生行動委員會主導,總理喬治.龐畢度和工會進行了幾場協商,簽訂葛內爾(Grenelle)合約。左翼政治人物—尤其是密特朗與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試著恢復運動,取回權力。然而,戴高樂總統既沒有事先通知,甚至也沒有告知龐畢度,就秘密前往巴登—巴登法軍駐地。他在 5 月30 日回到巴黎,隨即宣佈解散國會,這就是戴高樂派對待國會的作法。疲倦的輿論,在大選中敲響了勝利之鐘。「68」事件的政治人物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了。此後十多年都不曾再見到他們。作家貝納.法蘭克(Bernard Frank)的一句玩笑話,給了這些事件一個方向,反倒是一些領袖們被這些事件蒙蔽了眼睛:「1968 年的『五月風暴』難道不是 1940 年 6 月的翻版?『工作、家庭、祖國』口號的翻版?沒錯,的確是,但不僅這些:還有的,請自己去瞭解⋯⋯Be yourself,做你自己⋯⋯」
在這些「良好意圖」背後,還有一個隱匿的、來自下層的,讓菁英分子放棄卓越的想法,進行某種文化革命的意志,一種由少數或惡質的大學畢業生擔任紅衛兵並從中獲益的革命。這是傳承,從 1968 年 5 月迸發出來的各種星雲中冒出來的產物,傳承給不同的命運,基本上其網路在各大學之間—巴黎第十大學、巴黎索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大學及柏林大學—仍然虛擬。這些意外事件並沒有導致任何政治上的實質變化,在法國,它們甚至造成了一個危機,並且在一年後,造成戴高樂總統在他自己主導的公民投票中失敗而辭職。但是五月風暴的影響深遠,四十多年後,它的痕跡還在:它是由這些星雲所勾畫出來的渴望與價值的直接延伸。那麼這些未曾發表過的概念,就不是因為政黨、政府與工會了。領袖們如何才能意識到不是源自他們,不會為了合法或有效而回到當時堅持的任何分析當中,以及似乎和製造國家力量的著名原則不相容的東西?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