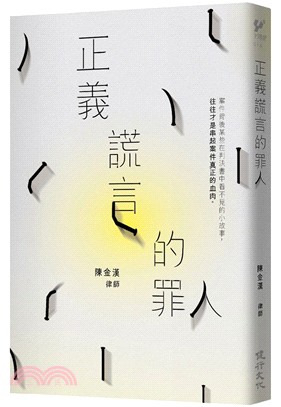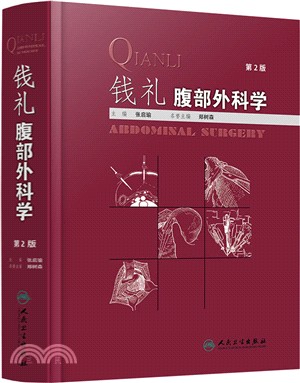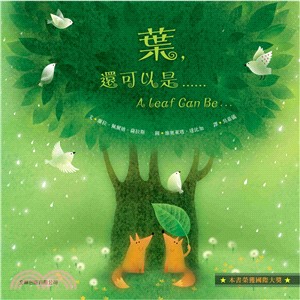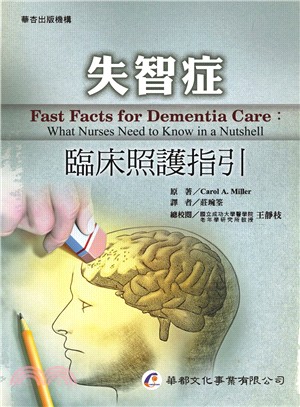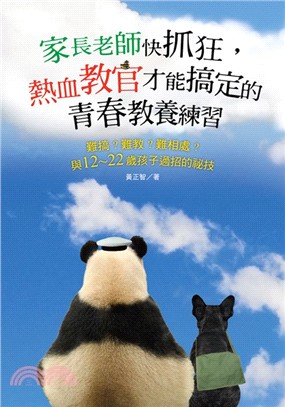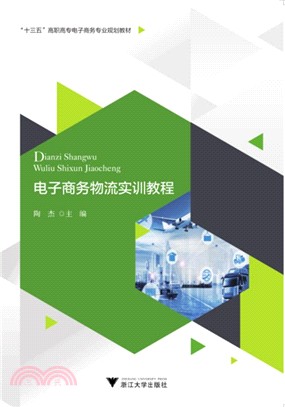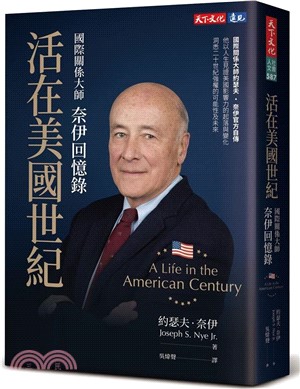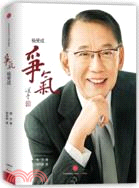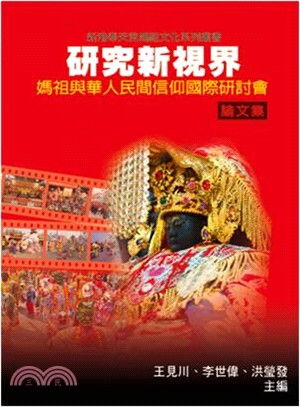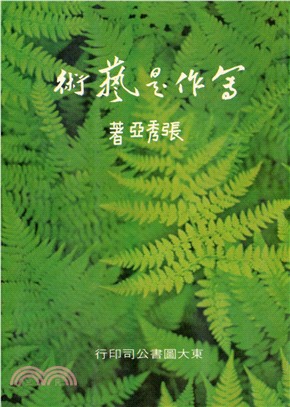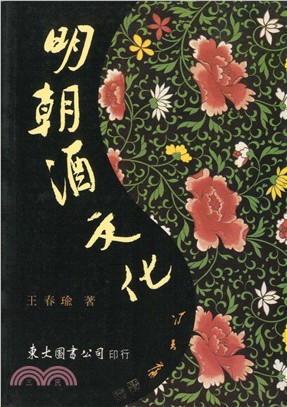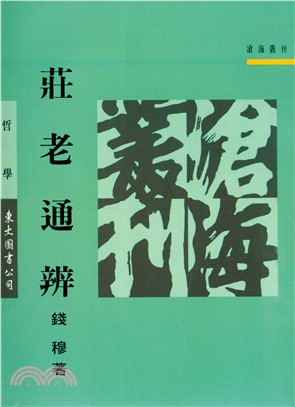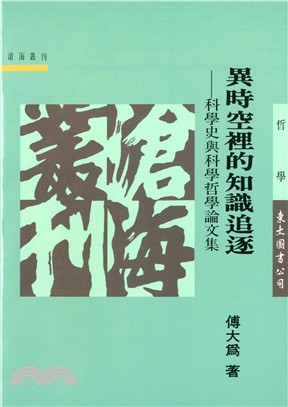正義謊言的罪人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謊言包裹下所贏得的也只是一份扭曲的正義……
十六個真實的案例故事背後,拼湊出來的是一個怎樣的人生!誰是真正的受害者?如何定罪?又有誰能真正代表正義?
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則殘酷冰冷的故事。但除了邪魅血腥的法律事實外,案件背後某些在判決書中看不見的小故事,往往才是串起案件真正的血肉。
本書是作者執業二十多年的反思與自白。
從數百件刑案中著手整理資料,回憶和重建案情,逐案回溯當年每個案件在腦海中的印記,包括被害人、被告、證人和家屬,甚至檢察官和承審法官。有些被害人只是記憶裡的一顆頭顱、一具殘屍或一堆白骨。有被告至今仍蹲在苦牢,有人早已槍決,有人沉冤已雪,也有的還逍遙法外,繼續他們貽害人間的歲月。較特別的是,有兩位檢察官後來也變成了被告,其中一位尚在服刑中。
救人不代表正義,殺人不代表罪惡?從炙熱到冰冷的極境邊緣,往往都膠著解不開的愛恨情仇。
多篇故事反應了作者心中的道德量尺與現實真相的彼此拉扯。有毫不掩飾的描述,很多時候,不少律師是用踐踏正義的方式來成就自己的偉大。更袒露新手律師面對生命中第一件案件時,捫心自問:一個缺乏道德勇氣的人又將如何成為一個好律師?甚或感嘆:為了一份工作,每個人到底該支付多少人生的世故?
身為資深律師的作者的確是說故事的能手,不少事件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直指人心,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本書特色
★喜歡《罪行》、《罪咎》以及《正義》,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思索人性善惡的讀者,
看完本書將對人生與法律有更深刻透徹的感悟!
★用筆溫潤解剖過往的人與事,所解剖的不只是案情和法律,而是深層的人性。
★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直指人心,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
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作者簡介
一九六三年中秋節生,雲林台西蚊港人。東吳大學法律系畢,執業律師。著有短篇小說《關於十四》、散文《兩滴刺青――母親與我》。
名人/編輯推薦
據他所言,書中事件皆有所本。……每句話、每個轉折,也會因過度專注而觸動神經。一
路仔細讀來,對於活生生人性與冷冰冰法律所產生的衝擊,有更深更沉的感受與體悟。
――侯榮惠(一位半退休的廣告人)
面對整個司法系統,作者在高牆與雞蛋間猶豫著。經過二十多年的磨歷,沒有以卵擊牆的
壯烈,卻也進化成屢屢與牆來回碰撞的回力球;以機智與些許世故衝擊再反彈,用輕快的
撞擊聲嘲笑著體制與現實。 ――黃齊睿(文壇新星)
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直指人心!(推薦序)
律師,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頭銜!在其銳利眼神與犀利言辭的背後,實難以得知包藏著究竟是一顆怎樣的心?
與金漢是在朋友餐會中相識,總是在言不及義中互動,總是在杯觥交錯中觀察。雖曾禮貌性互留聯絡方式,私下也未有過片言隻語的交流。直到他送我第一本著作……
訊息承載過多的封面顯得有些雜亂,但是「兩滴刺青」的書名,卻別具認知不協調的吸引力。清楚記得,收到書的第二天恰逢週日,就在一路不忍讀又不捨停的閱讀糾結中,看畢全書已是深夜時分。幼年的失怙困頓,並未坍塌他的人生路途;母親的悲憫情懷,更深遠影響他的受想行識。原來在炯炯眼神與咄咄言辭的背後,竟潛藏著一顆溫良而善感的心。
第二天清晨,趁著思緒尚未平復,寫下寥寥數語閱後心情,發出彼此第一則簡訊。下班前接到他的電話,寒暄數語之後,問起我對哪一篇特別有感,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令我數度掩卷低迴不已的「紅蘿蔔燉飯」那篇。語畢,心中突然升起「莫非這人在試探我,是否只是禮貌性的隨意翻、信口謅?」的念頭,旋即對此小人之心自感慚赧。而後,律師形象淡出,友誼於焉淡入。
大約兩年之後,再次收到他的第二本著作《關於十四》。一口氣閱罷之後,懷著友直之心,直言其中某些情節交代的斧鑿痕,他大肚能容不以為忤,甚至因而有了進一步的「以書會友」交情,彼此若看到不錯的新書,就多買一本送對方。
個人行事龜毛朋友週知,於是有幸成為金漢第三本著作的第一位讀者――校對。據他所言,書中事件皆有所本。由於在校對過程中每個字、每個標點,皆不會放過,因此每句話、每個轉折,也會因過度專注而觸動神經。一路仔細讀來,對於活生生人性與冷冰冰法律所產生的衝擊,有更深更沉的感受與體悟。
自身長期從事做作的消費文案工作,欠缺資格亦難以置喙金漢的文字底蘊。但對自詡資深推理小說控的我而言,金漢不愧是說故事的能手,其中有不少事件透過峰迴路轉的鋪陳敘事,頗得社會派推理的況味。直指人心的貪嗔痴慢疑,在法律面前無所遁形之後,往往不是一時的快意恩仇,而是無止境的唏噓喟嘆。
期望金漢能在繁忙工作中持續創作不輟,一如他私淑的德國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透過真實事件與思辨過程,讓讀者對人生與法律有更深刻透徹的感悟!
侯榮惠(一位半退休的廣告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推薦序)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用安那•卡列尼娜的這兩句話來形容這本書再適合不過了。
這本書是好友金漢律師執業二十多年面對種種不幸的反思與自白。反思的問題很宏大,大到懷疑法律真的等於正義?在〈真假正義〉一篇中,作者毫不掩飾的寫道:很多時候,很多律師是用踐踏正義來成就自己的偉大。
而在〈三季人〉一篇中,新手律師面對生命中第一件案件,追問自己:一個缺乏道德勇氣的人又將如何成為一個好律師?最後還問道:為了一份工作,每個人到底該支付多少人生的世故?
如果把這些問題問李敖大師,他告訴你:妓女不需要靠性慾來接客,律師不應該靠正義打官司。您會怎麼說呢?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法律之下,難有高尚,而律師常常是那個通行證的製造者。
多篇故事皆反應了作者心中的道德量尺與現實真相彼此拉扯,面對整個司法系統,作者在高牆與雞蛋間猶豫著。經過二十多年的磨礪,沒有以卵擊牆的壯烈,卻也進化成屢屢與牆來回碰撞的回力球;以機智與些許世故衝擊再反彈,用輕快的撞擊聲嘲笑著體制與現實。
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莫曾說:理性是激情的奴隸,除了侍奉和服從激情,不能假裝還有別的差事。當律師用法律包裹的外衣侍奉著被告激情後產生的惡之子,這句話看起來格外諷刺。
看完書我想問:和法律打交道的人啊,要有怎樣的心量,才能被迫接受成為不幸與犯罪的吸塵器呢?
我猜作者可能會說:寸土寸金的都市,新台幣能買到律師的心理空間、而權力可以買到法官的。
至於錢買不到的東西,用靈魂交換也行。在〈誰聰明〉一篇中,你會驚訝的發現舞台上演技拙劣的過氣演員,只要願意將靈魂賣給浮士德,完全可以蛻變成生活中的影后!許多選擇或許是特定時空背景下無奈的產物,切莫追問人性究竟是光明還是黑暗,只能說人性從來都是幽明之間的,處在灰色地帶,所以別輕易考驗人性。
全書讀完,或許很多人會生出跟我一樣的疑惑:大律師,您真雞婆!
諸多內容作者毫不掩藏身為律師的犀利與尖銳,句句珠璣。而在看似口尖舌快的背後,作者始終褪不去儒家文化下薰陶出的「良知」。法律給予的訓練是法理情,而傳統文化基因給予我們的,更多的是情理法。過猶不及,作者在〈謊言〉與〈回家〉裡展現的是中庸。
用謊言安慰一個擔心孩子的癌末母親,用喋喋不休勸慰堅決離婚的丈夫。我猜事務所應該是沒有合夥人的,否則……
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在《品格之路》一書中提出了兩種美德:簡歷美德與悼詞美德。這是個人人都在追求簡歷美德的時代,物質與慾望翻騰,金錢共權力翩舞。恭喜出書,這是簡歷美德嗎?不,我更傾向看做這是一位資深法律人長情的告白。
黃齊睿(文壇新星)
序
二○一三年六月間,蒙好友東方廣告公司侯總經理贈予《罪行》、《罪咎》和《誰無罪》三本書,是德國知名刑案大律師——費南迪•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的大作,給我內心帶來無比的衝撞與震撼。
感謝侯兄賜予我這個良知的洗滌與人性的啟迪。
也感謝侯兄榮惠和羅兄建發百忙中撥冗為本書細心校對和指正。
我從電腦檔案中列出所有辦過的刑事案件。這二十幾年來,我所辦過的刑案總共不會超過兩百件,且盡是些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車禍傷害等之類的芝麻小案,重大案件,寥寥可數。
我用很多的時間整理資料,花了更多的時間去回憶和重建案情,逐案的回憶著當年每個案件在我腦海中所印記的每一張臉譜,包括被害人、被告、證人和家屬,甚至於是檢察官和承審法官。
有些被害人只是記憶裡的一顆頭顱、一具殘屍或一堆白骨。有被告至今還蹲在苦牢,有人早已槍決,有人沉冤已雪,也有的還逍遙法外,繼續他們貽害人間的歲月。較特別的是,有兩位檢察官後來也變成了被告,其中一位尚在服刑中。
歷歷往昔,事杳人非。如過場黑白電影般,一幕又一幕。
刑案,在審判過程中,首重事實真相的發現。每一個案件都是一則殘酷冰冷的故事。但除了邪魅血腥的法律事實外,案件背後某些在判決書中看不見的小故事,往往才是串起案件真正的血肉。
相較於民案,刑案更能透徹人性與晦暗。
殺與被殺,害與被害,從炙熱到冰冷的極境邊緣,往往都轇輵著解不開的愛恨情仇。當情緒情感找不到出口時,悲劇就來了,案件就發生了。
感謝那些我所辦過刑案中的人與事,感謝那一片曾經不光采的黑暗,讓我更體悟人性光明存在的可貴。
如果法律能為自己說話,它們第一個埋怨的人就是律師。
這是哈利•法克斯的一句名言。
我深信不疑。
律師沒有說謊的權利。
這點,每個律師都清楚,但卻沒有律師做得到,不論蓄意或無心。法庭上,除被告外,律師往往是說謊最多的一位。
很多專辦刑案的大律師都忠誠地服膺著一條圭臬:「律師唯一的天職,就是竭盡所能的為被告辯護,別無其他。」
「竭盡所能」,就是問題之所在。
律師,是除了檢察官和法官之外,聽到最多謊言的人,但也可能是被告之外,說謊最多的人。然,辯護和說謊,本屬二事。每一案件,都是先事實而後法律。謊言下的偽事實,又如何能得到真誠的法律?在法庭上,我們都將謊言包裝成是「據當事人所稱……」,這種說法,往往只是律師為了平衡自己心中的那份罪惡感而已。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把竭盡所能的說謊當成是盡力的辯護。
我常想,如果受刑人關進監獄後應有教化功能,那麼,先期的訴訟程序,就更應具備某種教化功能。因為,被告入獄前學不會的又如何強求能在監獄中學會?訴訟過程中能宥恕的又何必到服刑中才寬恕。
辯護律師應有半個法官的角色,對被告要有某種程度的教化之功。相同的,檢察官也應有半個辯護人的責任,對被告有利之處,檢察官要有某種程度的注意和提點。這在刑事訴訟法有明文,但卻少有人做到。很多律師往往是被當事人的高酬勞所教化,一味的附和當事人,附和金錢和謊言。很多檢察官也往往在不覺中被自己的高權位所教化,每每將被告視為不赦的罪人,利用恐懼氛圍辦案,對權握的案件和被告欠缺適度的友善。
金錢吞噬律師,權位吞噬了檢察官和法官。
如果你不認同,那你的身分可能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或是一隻鴕鳥。
我也常想,為何上過法院的人都不會信賴司法?
態度和器度,適足以說明一切。檢察官、法官和律師的態度都包括在內。
律師,不該是讓謊言淹沒法庭的那個人。
檢察官,不該是讓權力恐懼氛圍淹漫偵查庭的那個人。
法官,也不該是讓權力傲慢充斥法庭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知道,法律如果推不開特權的門,那它也就跨不進人民的心。
很遺憾,現今的社會,往往是反讓特權輕易的敲開敲碎法律的巧門。如果立法、執法者又兼為法律敗壞者,那法律又有何存在的意義?如果大家都可以習以為常的淡看特權的司法關說,那又如何怪罪法律走不進人民的心呢?
二十幾年來,我所辦過的案件,都早已摺進了歲月的櫥窗裡。
年輕時,總以為自己風骨凜然,洞觀世事,是正義的化身,竭盡舌辯之能,在法曹內爭勝爭贏。而今回首,可笑又可悲。某些時候某些案件,扭曲人性所爭得的只是醜惡的勝利,謊言包裹下所贏得的也只是一份扭曲的正義。
法律,本是謙卑的。是律師、檢察官和法官讓法律顯得高高在上。
我深明,法律絕無法救贖已發生過的一切遺憾。律師、法官也不可能實踐百分之百的正義。只希望能早早捨棄那曾經的江湖濁氣和詭辯之舌,再次的用筆溫潤的去解剖,解剖一些過往的人與事,不只是案情和法律,而是深層的人性。
書摘/試閱
空號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
老師叫鐵飯碗,但在早年也被慣稱為「窮教員」。
全天下都一樣,會念書的孩子永遠是窮人家裡的一盞燈,但也是負擔。
民國七十五年,我花了一整年的薪水,偕我太太飛到紐約大學參加我兒子醫學博士的畢業典禮。那天,做父母的我們,再一次感到無比的榮耀。
我兒子專研免疫醫學,年紀輕輕就榮任國際免疫學會聯盟(IUIS)主席,是相當知名的免疫醫學博士,享譽國際。
我兒子很孝順,打從他開始工作後,每月匯給我們夫妻倆五萬元生活費,至今二十五年了,從未間斷。
多年來,我們戶頭裡的錢多到不知該如何花,心裡卻空虛得不知該怎麼填補。
我媳婦,聽說,聽說也是個醫生,不知道是否就是畢業典禮那天介紹給我們認識的那一位?聽說她父母是台灣早期移民美國的地產大亨。當時因為雙方在台親友都不多,所以並沒回台舉辦婚禮宴客。聽說我兩個孫子都上高中了,也聽說各方面的成績都跟他們父母一樣的優秀。
這些都是我聽我兒子說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不知道是生活中的哪個環節出了差錯,為什麼所有關於為人父母該知道的一切,我們都只能是聽說?
現在,這一切已不重要了。
──
一九九八年間,我兒子應邀回台參加台灣國際免疫醫學年會,年會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日子。我兒子和我們約好,會在前一天回家和我們一起晚餐。我太太幾天前就開始張羅,我們一連好幾天都興奮得睡不著,每天從早到晚,我們都一起拚命努力的回憶和討論著,兒子小時候最喜歡哪些菜餚。在討論中,我們夫妻還多次為了兒子最喜歡的到底是雞肉飯還是滷肉飯,面紅耳赤地爭執了好幾回,各自堅持,互不相讓。
當晚的餐桌上有滷肉飯、南瓜炒新竹米粉、清蒸白鯧魚、乾扁四季豆、酸筍片炒三鮮、香菇炒銀芽和何首烏烏骨雞湯。
黃昏時刻,五點、六點、七點、八點,我們在興奮中苦等了四個小時,一直不見人影。
最後,我們只等到了一通電話。
他說因為班機延誤,他會從機場直接到君悅飯店,參加台灣醫界朋友為他舉辦的歡迎酒會。
這一餐,足足等了十一年,圓形的餐桌上,我們竟等不到一個小團圓。
第二天,我們夫妻在十點前就趕到會議中心門口等我兒子。
十二點會議結束後,他在一群人恭維簇擁下走出大門。一見到我們,他快步趨前彎腰來和我們握手:「爸媽,真對不起!大老遠的,不是叫你們不必來嗎,這次的行程很滿也很緊,沒空和你們多聊。今天的會議很成功,大家等我一起聚餐,都是官商政要和醫學界前輩,不好推辭,真的非常抱歉。餐後我又得直接趕班機飛往日本,參加明天一早的另一個會議,你們多保重,有空再聯絡,我一定會很快抽空再回來。」
他用雙手摸摸我和他母親早已皺褶的臉皮,他的手依然帶點嬰兒肥,十分柔軟細緻,和當年孩提時代沒兩樣。但在我們都還來不及開口前,他已轉身消失在那群西裝革履的上流人群中了。
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這無傷的慟,如果不是痛徹心扉,我也不會記得這麼多,記得這麼清楚。
很遺憾,我必須承認,我很討厭我兒子趨前彎腰和我們握手的模樣,作態的客套,毫無溫度的涼薄,那不是記憶中的兒子。我們不是來開會,我們只是單純的想來看看我們十多年未見的兒子,想來跟他簡單聊聊而已。
這是我兒子第一次讓我感到心痛,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和我兒子面對面說話,雖然我們都還來不及說到半句話。
那一天,真的很受傷。
回家的公車上,我們一路的沉默,一直並肩的正襟危坐,讀著一本陌生的哀傷,好像整個世界都已和我們毫不相干的分離了。
突然間,我太太側身用力的緊抱著我,咧嘴放聲哭倒在我懷裡,在一對女學生讓位給我們的博愛座上。
我沒說半句話,輕輕地拍著她的背。
瞬間,我的視線,模糊了。
──
我太太向來體弱多病,家族有嚴重的糖尿病史,手腳多處新舊傷口難癒。
七年前,她左腳因蜂窩性組織炎而截去兩趾,從此走路不平衡,經常會跌倒。
我申請了一個外傭看護幫忙照料。但人久病就多疑,沒多久,我太太懷疑我與外傭有不正常的曖昧關係,行為開始乖張無理。
她規定外傭和我不能同時離開她的視線,規定我不能早出或晚歸,還經常無端的搜檢外傭的房間和皮包,誣賴外傭偷錢偷東西,手腳不乾淨,還會以「賤人」「不要臉」等不堪的字眼謾罵外傭。她甚至習慣性地摜摔東西發洩情緒,有時還故意把客廳和浴室弄髒弄亂,再命外傭好好地整理。我屢次勸阻,結果只是惹得變本加厲。
好幾次,我冷眼竊看到,她竟為自己能帶給外傭那樣無辜的折磨而感覺到寬慰的神情。
我很確定,她病了,身心都已病得不輕。
雖然我經常事後再三地向外傭道歉,也暗自塞錢為她們加薪,但外傭還是無法忍受而逃跑了。前後不到一年,她趕走了三個外傭,最後一個向勞工局檢舉僱主不當凌虐成案,結局是我們暫時無法再申請。
──
三個多月前,我太太因糖尿病引發眼角膜嚴重剝離,兩眼視力急速的惡化,住院一星期。她要求我聯絡兒子,希望在她全盲之前,有機會能再親眼見到兒子一面。
這是一個病母無可厚非的薄願。我極力安撫,告訴她兒子很快就回來了。
其時,那支我們和我兒子唯一可以連結的電話,早就不通了,他沒主動再來電,我也無處可尋。
住院期間,天天看著那麼多白袍身影在病房裡忙碌的穿梭,每個醫生每一句貼心的問候,都讓我感到無比的心痛。
多麼希望,希望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那資優絕倫的孩子。
出院前一天,主治醫生告訴我,我太太的視力確定完全無法回復了。
沒太多驚訝,因為我早有心理準備。
深夜,我茫然地獨坐在醫院的家屬休息室,闔眼整理我茫亂的心緒,一再試圖重複地說服自己,是否該下定一個決心了?我害怕,茫然無助……
我在疲困中不自覺地睡著了。
醒來,已是凌晨時分。
慘白冰冷的燈影把醫院的長廊映照得像殯儀館。
突然,我看見我兒子出現在我眼前。
這時候怎麼會……?我心中興奮驚疑地輕揉雙眼,不知自己是否在做夢。定神後才發現,是斜立在書報攤上的醫學雜誌封面照:嘉惠無數病患的免疫學巨擘――魯銘城醫師。
這是二十五年來我們父子二度重逢。沒想到,竟是以這種方式再見面。
回病房途中,無名地,我開始悲傷。
──
案發前兩天,我太太再次的大吵大鬧,說她一定要和兒子講話、一定要兒子回來,否則她就不想活了。
我要她安靜,逼不得已,我把幾個月前電話已變空號的殘酷實情告訴她,也牽著她的手指把電話號碼輸入,再把右下角的重撥鍵指給她。
她一連撥了兩天,每次聽到空號的回應,她就立刻歇斯底里地抓狂,一邊聲嘶力竭的對著話筒哭喊:「你不是我兒子,你不是我兒子,你走開,……趕快叫我兒子來接,……叫我兒子來接 ……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一邊用話筒不斷用力敲打沙發、桌椅和她自己的頭,直到全身力氣放盡為止。
第二天下午,我在廚房釘掛勾,她已在客廳將自己敲得頭破血流,奄奄一息的癱躺在沙發上。她不再撥打電話,不再嘶叫哭喊。
我沒將她送醫,心想,該是時候了。
於是,我下定了這一生最大的決心:決定把我們人生所殘剩的歲月送給我那救人無數的兒子。
接下來發生的事,你應該都清楚了。
律師,謝謝你陪我回憶,謝謝你聆聽完我的故事。
你說,誰是兇手!
──
在律見魯先生的第二個星期後,我接到檢方開庭通知,庭期訂在三星期後。
我馬上遞出聲請狀,陳述被告因不忍臥病在床的髮妻長期遭受病魔糾纏之苦,一心念於想為妻子減免痛不欲生的殘命,一時失慮而殺妻,請求檢方向亞東醫院調取被告妻張季薇歷次在該院就診的詳細病歷,以資為證,並請求准予將被告無保飭回或交保。
經過五個星期八次的律見後,我已將魯先生的故事整理完畢。
開庭時,我庭呈一份給檢察官,並趁被告尚未押解到庭前,將我最後一次律見時,發現被告似有輕生念頭的情況告訴檢察官,當庭向檢察官請求撤回交保的聲請。
檢察官相當年輕,絕對不滿三十,一副十分聰明洞觀的態勢。
他刻意放慢講話速度來掩飾他的年紀,很客氣的回答我:「大律師,你想太多了吧,真要輕生的話,還需要選地點嗎?我們已依你的聲請向亞東醫院調到所有的病歷,交保與否。本署會參考大律師的意見,依法處理。」
檢察官隨意翻了一下我庭呈厚厚的手稿,順手丟在一旁,不耐而輕浮。
「大律師,內容這麼多,這是論文還是答辯狀?」
「都是。」
我簡單而肯定的回答。
檢察官聽到後,突然停頓下來,瞟了我一眼。
在法庭內,檢察官或法官越是樣板的稱呼和毫無遮掩的客套,那代表他心中早已自有定見,不論是否為偏執之見,爭執是最愚蠢而危險的行為。
我沒多說,但我的確不喜歡他在聰明中夾雜著一股傲慢的態度。
結果,花不到十分鐘庭訊,魯先生被無保飭回。
我想,我又在檢察官面前自作聰明的放了一個大屁。
──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魯老先生的電話。
現在媒體很糟糕,每天每小時都是重複報導一些扒糞新聞,台灣人也喜歡,他們還有能力可以讓內容更精彩。反正現在景氣差,整個社會也都是靠著挖掘別人的八卦生活,不是嗎?
他說得很清淡,語氣像和尚。
他再次感謝我聆聽完他的故事,並提出他的最後一個條件。要求我當天就把他口述的文稿快遞給平面媒體和電視台。
第三天,里長打電話告訴我,魯老先生已在自宅中上吊身亡。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