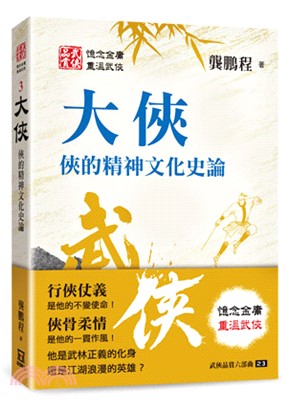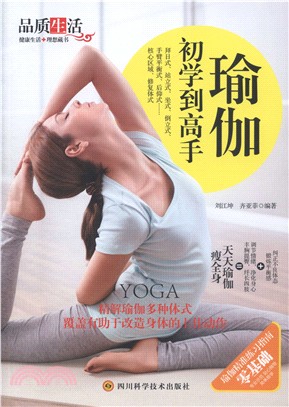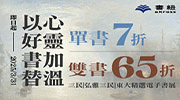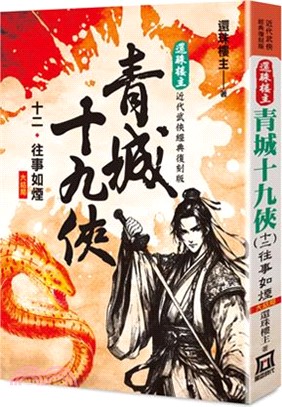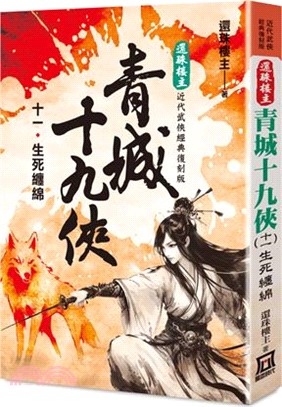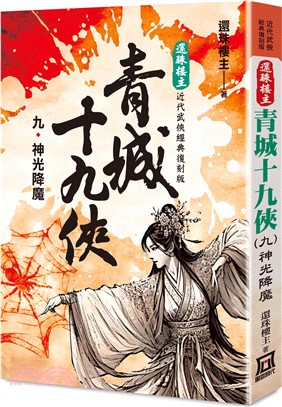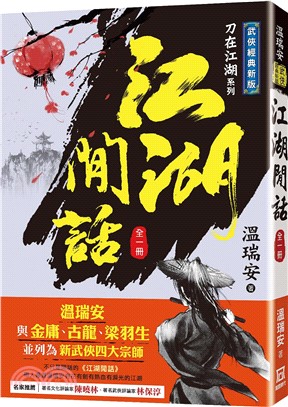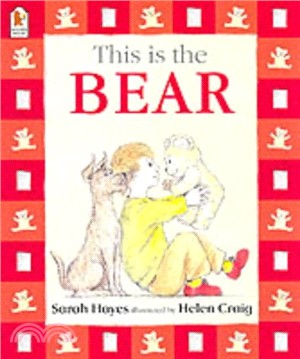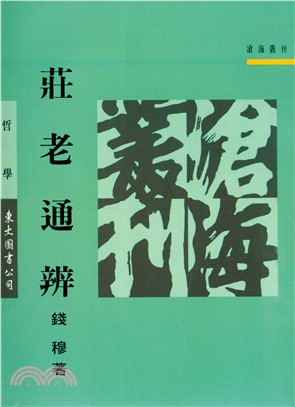商品簡介
武俠品賞六部曲1:論劍之譜(上)武俠五大家品賞
武俠品賞六部曲2:論劍之譜(下)武俠五大家品賞
武俠品賞六部曲3:大俠――俠的精神文化史論
武俠品賞六部曲4:武藝──俠的武術功法叢談
武俠品賞六部曲5:修訂金庸(上)金庸小說新版評析
武俠品賞六部曲6:修訂金庸(下)金庸小說新版評析
※兩岸知名武俠評論家龔鵬程、陳墨聯手出擊!
※集結武俠小說五大名家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臥龍生共襄盛舉!
※俠氣、俠骨、俠情、俠義、俠行,俠的定義為何?真正的「俠」又該是何種風貌?
※兼具學術與文學價值,挑戰傳統對「大俠」的看法,更深入對「大俠」的研究!?
※藉由深入淺出的敘述,讓你更了解什麼是「大俠」、「大俠」的精神又在何處
英雄快意江湖,
浪子千山獨行;
揭開歷史布幔,
找尋俠客精神!
我寫《大俠》,就是想要解說中國的俠與俠義傳統之流變,我是從小嗜讀武俠小說的人,對俠,有特殊的感情與嚮往。這時,我成了一個武俠的論述者、研究者與推廣者,說劍談龍,再度滿足一下我對武俠的感情,呼喚一些我少年時的記憶。這些記憶,是極為複雜的,因此我的論說恐怕也還會繼續下去。論說能否博得喝采與共鳴,則不重要。因為,俠客的心境,永遠是孤獨的。
俠,經常被理解為歷史上一種急公好義、紓解人間不平的人物,長久以來,對於俠,我們總有一種難言的讚嘆之情。他們那種堅持信念、不畏強梁的勇氣,義之所在、雖死不辭的壯烈,以及那種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孤寂與放浪,也在在顯示了與眾不同的情操,扣人心弦。就這樣,正義的英雄走入了人世、走入江湖。然而,究竟活生生存在於歷史中的俠,是不是真如我們所嚮往的那樣,是個正義的浪漫英雄?本書即是想打破俠之浪漫想像,暫時關閉幻想和憧憬之門,揭開歷史的布幔,看看俠客的真面貌,並說明俠的神話式嚮往究竟是怎麼形成的。
作者簡介
目次
一、複雜的俠客形象
二、漢代的遊俠
三、唐代的劍俠
四、俠與文士的一種關係
五、清代的俠義小說
六、晚明晚清文化景觀再探
七、近代知識分子的生命型態
八、鴛鴦蝴蝶與武俠小說
九、武俠小說的現代化轉型
十、人在江湖
十一、劍本無情
十二、殺人或自殺
十三、三少爺的劍
十四、且爭雄於帝疆
十五、方紅葉之江湖閒話
十六、金庸小說上的俠
十七、青春少年時
書摘/試閱
俠客行
我的籍貫上寫的是「江西省,吉安縣」,即古「廬陵」。自古號為文章節義之鄉,是宋朝文天祥、歐陽修出生處,也是禪宗祖師青原行思的法脈發祥之地。
但文風傳承,到了我父祖輩,顯然已雜有許多武獷豪俠之氣。因為鄉居樸鄙,為了爭資源、鬥閒氣,村子間經常械鬥,教打習武之風甚盛。而村子裡頭,雖皆同為一公之子孫,卻也免不了會有些衝突與競爭。所以角力鬥狠,也頗為常見。這些事,我當然不曉得,都是小時候聽父親講古時聽來的。
後來在所寫《花甲憶舊集》裡記載了不少他曾向我們講述的片段。據他說,他當時在吉安縣寶善鄉七姑嶺集福市擔任保長時,曾經會過一些江湖道上的人:
不論江湖、教師及各方賭友,來到七姑嶺一定會來看我。無論何方朋友來找我,先在茶館喝茶,茶賬早有人先付了。他們出了事,我會出面擺平,決無問題。他們也少不了一個我這樣的人。我絕不會到公賭場去拿一毛分。不要非份之錢,鬼也會怕。現在想來也真是的,吃自己的飯,管別人的事。但在那時候,我這個性,就無法忍住。
這時來了一位李老師傅,名叫李子玉,真有兩手,他的點穴與打脾功夫到了家。他下手,可以準時死亡。如果一百天,絕過不了一○一天,這是一點不假。父子二人,兒子叫李金生,比我年輕四歲,是父傳子的功夫。李師應原在景德鎮鄱陽一帶把水口,又是青幫老頭。後來因戰爭回到吉安,由一位石工從安福縣帶到他家,就在他們楊家教這玩意。與教學別的功夫不一樣,大概以一週為出師,專授點穴。
有一天,我們幾人到值夏市去玩,順便到楊家去拜訪這位李師傅。
說來話長,那時延喜在學,我們家共有七人。正好那天延喜他們要出師,我問他們功夫如何,他們也說不上,因為李師傅名氣很大,他們也不敢多問。只有延喜他受不了,嘴巴忍不住,向金生說,他沒有學到,要向金生討教兩手。我們坐在一旁,希望看看他的招式。金生答應他,要延喜先上。
延喜從小有點根底,也拜過不少名師。延喜一出手,金生雙手架開。上前一馬,右手輕輕一招,延喜跌到近丈遠,起也起不來,嚇得其他人大為吃驚。金生對大家說明,是打的中央大脾,要用什麼手法去推治。
那時延喜十分痛苦,滿口白水吐出來。我們在一旁看到很著急,只是靜觀其變,看他怎樣動手。那時我對他父子毫無認識。他把延喜反背起來,人往下一駝,再把延喜放在凳子上,用推拿功夫,五分鐘恢復正常。他後來對我說明了打中央脾的道理。這又叫「五里還陽」。
他的意思和道理是這樣的:出手輕重,三十分鐘後會慢慢回醒過來。那個時代沒有鐘錶,以走五里路為準,完全以防身、自衛,不傷道德。
我記得李師傅對我解釋,這「五里還陽」的道理很有意義。老式的中國,交通不便,做小本生意,單行獨跑。有時跑幾十里或百餘里之地方,沒有人煙。這些地方,也是盜匪出沒之所。當然做大買賣的商人是不會從此經過。所生存的也只有些小盜。到時萬一遇上了,就正好用打「五里還陽」的手法對付他。等我們跑了五里路遠時,他回醒了,想追上來也追不上了。這就是所謂道德。
我後來還是拜了他為師。這實在不是出於我的本意,這完全是因李老無論如何要收我為徒。這是他的利益,好在這一地帶開碼頭,這是後來的事。
正好延喜恢復正常後,有一位隔壁村的人,名叫毛大標,是個種田人,粗裡粗氣。那時他在值夏一位蕭仁和的教頭處學符法功夫,又叫寄打功夫,是用刀斬不入之神打。他們表演時確實如此,其中密道就不得而知。
此人奉他師傅命令來到楊家,找李師傅,一進祠堂門就叫:「李師傅,不准在這裡教拳」。李問他卻是為何。
他說:「你是騙人的,根本沒有這門功夫。」
李當然無法容忍,答應他說:「你就來考驗一下如何?」他也就走過來,叫李下手。
那時,李叫他一聲:「老弟,這不是開玩笑,是要命的。我年齡那麼大,出外面混了一輩子,出外靠朋友,你是不是受人指使來的?」
毛大標那裡懂得這些,通著李下手。我在一旁又不便插嘴。
我看李師傅只用二指在他脖子上一點,他的頭往右一側。他一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走了。我看好像很難過的樣子。
幾天後,李派人去問過他,但他不很認輸。從此毛大標好像感冒一樣,一天天病情加重。到了一月以後,值夏市也無法去了。後來李師傅叫他徒弟來找我。問我毛家有不有親朋。
他對我說,毛大標只有七十天的壽命,要我轉告他家。如果「毛」來請罪賠禮,他會給他藥吃,治好。我也請過族兄立益去告訴他。但大標就是死也不服這口氣,向他低頭。
世界上就有這樣的人。結果,從他到楊家算起,正好七十天,真是難以相信,但是有事實證明。從此我對他這一手,感到驚人。可惜大標成了冤死鬼。
從此李也聲名大振。後來,他們在別處教技,來到值市一帶,也必定會來找我。此後我們接近的時間也比較多。他兒子金生對我都是哥前哥後,我們十分親近。我總是勸他父子,千萬不可亂授徒弟,以免造成許多不幸。
他金生倒很聽我的話,他每次到了七姑嶺住在我店裡,而且我們同睡暢聊,我也從不問他的功夫,他有時拖我起床,要教授我幾下真功夫,我也拒絕。我不願意學他的功夫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年輕時脾氣不好,容易衝動,萬一一時失手,損德。我不傷人,人不害我。
我現在後悔的是,沒有學到他的藥方。本來他徒弟根力,把他這本傳家藥書偷到了。根力不識字,就拿給我,要我幫助他抄下來,我卻沒有理他,真是太可惜了。後來李家父子要捉他處死,就為的這本藥寶。如果捉到了,定會以他們幫規欺師滅祖論罪處死,誰也保不了。
有一次,金生來集福市看我,正碰上根力在我店中,好在他眼快,一看到金生,轉腳往後門就跑,金生也眼快,也就往後門進去。根力在七姑嶺太久了,轉幾個彎,不見人影。金生轉回來,好生氣的樣子。我勸他:「算了吧!又何必一定要捉他,他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他才坐下來告訴我,他說:「他不跟我父親也沒有關係,他偷走了我們的藥典,對我們來說,這有多麼重要。如果這藥書落到敵對手中,那還得了。這事要你幫忙,要他把藥書放在你這裡,我念他跟了我們幾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會放過他。但要他處處小心,不要給我父親碰上。如果被我父親捉到了,絕不會放過他。」
卻原來為這藥書要捉他,我那裡會知道?後來我才說根力也不對,我要他把藥書一定要還他們。
後來根力在七姑嶺也傳了幾個徒弟,整天跟我跑跑腿。
回想這些也很好玩。有一天,我考驗他。我問他,你拿什麼東西去教人家,小心出洋相。他也常常在我面前握握手,試看我的底子。
那一天,我心血來潮,跟他較量幾下,真沒有想到,我一出手,他就跌倒了。他站起來問我是不是金生教我的。我才相信,李家父子沒有傳他的功夫。
後來,不久祖亮農場發生一件偷魚的事。這場風波鬧開了。他農場有好幾位工人,是龔家人。一名叫立原的人,他半夜起來上廁所,聽到前面有網魚聲音,他跑去一看,是他們段家人,四、五人正在掛網,魚又不少。
立原說:「你們偷魚。」段家人說:「魚是泰和某村抓來的,絕不是你們農場的。」立原當然不相信,就跑過去要把他們的魚網拿過來,有話明天再說。對方不肯。雙方拉拉扯扯。
就在這時候,對方下了立原的毒手,名叫「五百錢」。這門功夫雖是普通,但要真正準點到家,實在還不容易。那時候正在抗戰中期,難民又多,所以五花八門的東西特別多。道理是找錢吃飯,有些當然也是騙錢,花招百出,但還算在軌道上跑,不像今天臺灣的社會,亂殺亂來,沒有江湖規矩。
但當時立原毫不知情。對方下手之後,幾人回段家去了。下手人叫段世洪,是他太太教他的。他太太又是從一鳳陽婆處得來的。聽說他太太是鳳陽人,內情不詳。
第二天早晨,立原回家報告祖亮。那時祖亮在中正大學,不在家,由祖亮老婆在家管理。這女人很聰明,通情達理,是南昌人。
明剛趕緊來找我,要我幫忙處理,立原把情形告訴了我。我一見立原,雙眼紅得硃砂一樣。我問他:「你是不是眼珠痛?」
他說:「沒有哇。」
我發現他情形不對,再拿他的手一看,我才問他:「是不是對方打了你?」他說沒有。
我一時明白了,一定是你們拉拉扯扯之時,對方下了你的手。因為他功夫沒有到家,並不十分高明,所以一看便知。我告訴他趕回農場去。我即帶了一夥年輕人到段家去,找他們的保長交涉。
後來他們村莊上也來了好幾位仕紳,我就把情形說給他們聽,不料他們不很接受,反而說,又是我大村莊欺侮他們。我一時向他們說不清楚,我告訴他們人命關天,我也暫時不跟你們理論,最好你們派幾個人去農場,一看便知。我要去吉安請醫師來,一切問題等我回來再來解決。我就叫帶去的青年人,叫他們現在去段家附近,見耕牛就牽,目前不管那麼多。
我轉身就回去把情形告訴明剛。我說立原傷勢十分嚴重。我現在要去吉安請李師傅來,我就趕緊包了一條船下吉安去了。
我到吉安直往荊泰壽糕餅店去。因該店老板也是李師傅的徒弟。說到「荊泰壽」,是吉安唯一有名的糕餅店。只要是吉安所管的地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我到荊泰壽,一問,正好他老師傅出來了,我即前去把事情告訴他,地也就即刻答應同我回去。
閒話少說。我去租了二匹馬趕回家來。我也沒有在家停留,即刻往農場去。我們到了農場,段家有不少人在那裡等候。他們看到立原情況,也十分著急。
他們段家這個下手的人段世洪,跑得不知去向,我也無閒跟他們說什麼。帶李師傅到樓上去看立原傷勢。那時我叫他那段保長上樓來證明,人命關天,並不是我們以大吃小。他才道歉說,實在想不到,他世洪會出這毒手,真是畜牲。我說現在我們不必說這些,說地無用,只要立原不死,一切問題都好解決。
那時李師傅拿出一顆藥丸,只有花生米大,用一半,再用冷開水送下。他叫我吩咐點一支香,大概香燒到二寸時,立原說要上廁所,幾個人扶他上廁所。這一瀉,瀉下了有一臉盆多的黑血,真是嚇死人。再過幾分鐘,再上廁所去了一次,立原即恢復正常,以後吃了二帖水藥,真是藥到病除。
高明。病人好了,就好解決。一切藥費由段家負責。不過我幫了李師傅很大的忙。當時他告訴我,他的藥丸要賣五百元法幣一粒。結果我要段家給一千元一粒,又謝了他二千元,所以李師傅對我這個朋友十分親切。
這一糾紛就這樣結束了。等段家付完錢,我也把耕牛歸還他們。所以他父子並不拿我當徒弟看待,完全以知己、好友相待。後來別人不相信我沒有學到他的功夫,我再三聲明,別人也不相信。就這樣,後來一般江湖朋友來到集福市,一定來拜訪我。
這時,有一位劉師傅,是一個大力士,手上的真功夫,那還了得。我記得在羅家墟之時,劉某在泰和一帶教打。有一天在我們茶館喝茶,當場表演一手,滿桌茶點,少說也有幾十斤,他一隻手拿一隻腳,離地尺多再放到原地,滿桌茶水一點不盪桌上。
後來他到七姑嶺來找我,求我化解他與李師傅一件誤會。他把詳情告訴我,我當時給他一個滿口答應,此事包在我的身上。後來我給他們雙方化解了一場誤會。如果不是我,李家父子就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他。那位大力士劉師傅也害怕他。他們是跑江湖,靠朋友混飯吃,遇上我這樣的一位朋友,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有利的。對我來說嘛,朋友不怕多,冤家只怕一個,人總會遇到困難之時,那曉得什麼時候要人呢?
那年正月十五日,是我們家元宵節,十分熱鬧。沒想到這一天大不吉利。我大嫂患女人病,十分嚴重,下部流血不止。像她十八、九歲守寡,又沒有生過孩子,竟會發生這種嚴重的病。所以一時大家手足無措,心無主張。
真是人有旦夕禍福,鄉下地方又無良醫。這一夥女人只知道去拜神求佛,我看情形不對,毫不考慮包一小船下吉安去求醫。
我到吉安,直往我姐姐店裡去,一進門,我就對我姐夫說:大嫂病情十分危險,我來請醫生。我把病情詳細說了一遍,他趕緊出門去,要我在店中等他。
他店中正好有一位朱姓國術師。我在年底時跟他喝過一次酒,算是一面之交的酒友。我這人對江湖道上的人有好感,我喜歡他們的義氣。他聽我說,我姊夫要出去請醫生,他一把拉住我姊夫,問他:「那裡去請?請誰?我就是!別人的事,我可以不管,舅舅的事,我不能不管。」就這樣,我們租了三匹馬,急忙趕回來。
回到家,天已黑了。我在路上半信半疑,此人會不會醫病?又是個半醉的人,也只好盡人事而聽天命。
我未到家門,遠遠聽見哭聲,我想,恐怕沒有了希望。我一人先衝進房去,果然大嫂不能言語了,像死人一樣,我不知如何是好。那朱師傅也跟在我後面。他用手一摸,笑說:「快弄酒來吃。」捉了一隻公雞,他把公雞頭放在房門檻上用刀一斬,血流在地上,劃了一張符,貼在房門上,在祖宗前點香拜拜。他就說:「我們喝酒。」
真是個酒鬼。我沒有辦法,只好聽他的,陪他吃幾杯。他只是連說好酒好酒。我實在忍不住,說:「朱師傅,請你先去看好不好?」他才把酒杯放下,進房去動手。
這些女人只知哭哭啼啼,硬說沒有用了。老朱叫我伯母拿一條長毛巾給他,他用雙手在病人胸部慢慢往下掃。我嫂嫂的眼珠也就慢慢打開來了,前後不到三分鐘。他把長毛巾在肚部緊緊一綁,就這麼幾下,人全部清醒過來,說話像好人一樣。即開了一藥單,吃了兩帖水藥,就這樣完全好了。這不是神醫嗎?
這下把我大嫂的病醫好了,他的醫運也來了。所以說一個人做人做事,處處都是學問。人曉得什麼時候要人?我只跟他喝了一次酒,人家對我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我也萬萬沒有想到,在這無形中遇上一位救命的朋友。後來我對他的報答,也是他一生中未曾料到。所以說,幫別人的忙,就是幫自己的忙。
後來我幫他賺的錢,難以計算。他是個迷迷糊糊的酒鬼,衣衫破爛不堪。兩年後,在吉安買了店,開了一家木器店,黃金首飾用不盡。衣住食行,行有一匹駿馬。
當然一是他的醫道;二是他的運氣。自從醫好我大嫂開始,一傳十十傳百,遠近數十里前來求請者不知多少。後來我家也成了他的家。每天有人來請他吃飯,有他一定有我。我不去,他也就不會去。當然我又不能不去,我真不去,人家一定生我的氣。
鄉下人比較重情,一個人運氣來了,擋也擋不住。這個病人只要他去了,病一定會好,沒有出過一點差錯。說來真是神奇萬分。死人他也可救活。
有一天,我們二人在七姑嶺新善村茶社喝茶,我村來了一位婦人,哭哭啼啼來找朱師傅,說她丈夫前後不到幾分鐘死了。她實在不甘願,要我請朱先生去看一看。站在我旁邊一位我村婦人叫九姑的,她用手拉我的衣服,輕輕說:「人都死了,她哥哥去值夏買棺木去了。」要我們不必去,如果去了,怕會損害朱師傅的名譽。
但我又怎麼好說呢?老朱聽她說完之後,起身拉我說:「我們去看看。」我只好跟他走。叫這位婦人先趕回去,說我們馬上就來,並叫她準備一斤多燒酒。我又以為他酒蟲來了。
我二人一路回去,我看他在路旁採了一大把草,我也沒注意是什麼草。趕到病家,我一看,人真的死了,但我沒有做聲。老朱上前用手一摸,就在身上拿出來一大包銀針。
他拿了一支有三、四寸長的針,在病人身上各穴道下手。少也有五十針以上,前面打了,又翻身後面。針打完後,用面盆把燒酒倒下去,再點火燒燒酒。再又把這些草放進去,再拿出來,在病人身上亂擦一通。前面擦了往後面又擦。手續做完之後,老朱叫他老婆點一支香。告訴她:「香燒了一半,他有動靜再來叫我,我在保長家喝茶」。說完,我們去了。
我們回到家,坐了不久,他老婆跑來叫朱師傅,說他會說話,請他趕快去。老朱叫她趕快回去,怕他跌下來就麻煩了,我們馬上就來。幾分鐘後,我二人再去他家,一進門,見他坐在門板上向我們點頭。老朱翻他眼珠看了一下,就開了一張藥單,告訴他吃兩帖就可以,我們就回來了。
就這幾下,死人還陽。這位神醫,自然名揚鄉里。說實在話,確實救了不少病人。他的幾手我內心很欽佩。後來他的發展傳到泰和境內。
人嘛,福到心靈,一點也沒錯。後來發了財,說話也有條有理,不是從前那樣酒話連篇。
小時候聽父親講說的族中軼事,當然還不止於此。我們小孩子對這些奇情俠舉,是深深著迷的。父親也曾為了逗我玩,教了我一套「打四門」的基本工夫。可是點穴打脾的本領,父親也終究沒能學會,卻令我神往不已。
待我開始上學後,父親就開始後悔他以前跟我講太多江湖武打的事了。因為我啥事也不做,整天迷戀著武俠小說及連環圖畫,在那裡頭覓仙蹤、養俠氣。父親每天都要趁著麵攤子上生意稍稍得空時,出來捉我回去。
我經常在租書攤子裡看得正入神,忽一耳光打來,或腦門上拍搭一巴掌,然後被揪著耳朵,提拎回家。回去後,母親就痛打我一頓。她那時身強體健,打起孩子來頗見精神。通常總要打斷一兩塊竹條或木板。並罰我跪。有時跪地、有時跪焦炭,還要端個板凳或一臉盆水。待打罵完畢,讓我去做功課,他們去忙生意時,我就一溜煙又鑽出去找武俠小說和連環圖畫看了。
這就像演戲一樣,幾乎日日如此。左鄰右舍漸漸見怪不怪,任我哀號慘哭,也懶得再來管我了。而我則因沉溺太甚,功課亦日益荒疏,考初中時,便差點考不上學校,勉強矇上當時剛設立的臺中市立第七中學。
然積習並未因受到了教訓有所改變。我仍舊愛看武俠作品,且在行為上越來越傾向模仿那種生活樣態了。
每天清晨我絕早便去學校。因學校尚在開闢建設階段,遍地都是土石磚竹木板,我很容易地就在校園中找到一處僻靜之所,搭了個寨子,浮為水泊,號召了一群徒友,組織成一個小幫派。每天在學校裡打打鬧鬧,有時則溜到校外野地的河溝及竹林中去撒野。
或許這仍與小孩子們扮家家酒類似,只是好玩而已。代表了我對武俠世界的嚮往,離真正練武行俠之事,尚甚遙遠。直到初二去逛一書展,偷到一冊李英昂先生所編《廿四腿擊法》之後,情況才開始改變。
李先生這本書很薄、很簡要,但對我的啟發極大。不唯教我以技擊之法,實亦教我以技擊之道。因為它專講腿法。為何專門講腿擊呢?它開宗明義便分析道:「手是兩扇門,全憑腳打人」,說腿的氣力較大,攻擊距離也較遠,故剋敵致勝,須用腿攻。這跟我們小孩子打架時的經驗和習慣,實在太不相同了。令我初讀時極為驚異,彷彿入一新國度。
試看他所介紹的技法,都覺得若不可思議而又似乎頗有道理。試著依書中所述,練習拔筋、劈腿、起腳,既學到了技術,也增益了不少知識。許多姿勢招式,初看時覺得根本不可能做到,是因不懂得如何借力、如何走步、如何用勁、如何平衡重心。彎下腰,手指也只能碰到膝蓋,腰腿又不夠柔軟,怎能做得來書本上的動作?所以這就需要勤練,仔細揣摩做工夫。在不斷體會中修正,而且也須不斷進修以了解更多趨避進擊之道。
這才從對武俠的浪漫迷戀逐漸轉入實際武技的探索,開始去收集市面上所有能買得著的刀經拳譜、談武論藝之書,回來鑽研。
這時我便發現,武俠小說中所描述的各種武功、人物及事蹟,不完全真實,卻也未盡為虛構。金鐘罩、鐵布衫、硃砂掌、一指禪、三才劍、六合刀,一一皆有其法式與原理,亦各有其傳承、信仰及故事。
這些東西所構成的「武林」,則是在武俠文學之外,另一個神祕、有趣且極其複雜的世界。而各派宗師,各基於其技擊理念與開悟之機緣,創立一套套拳法,其中必有獨到之處。然亦有所謂的「罩門」,那是練不到的所在,亦即其武學觀念及技法構成中的盲點。
每門武術都有這樣的盲點,就像西洋拳的拳擊手從來不懂得腳也是武器;在跆拳道裡,則手也只彷彿是漂亮的擺飾。習慣腰馬沉穩的拳路者,對騰挪跳躍者即殊不以為然;大開大闔、長橋大馬的家數,也瞧不起小巧工夫。反之亦然。思考其間之是非,比較其技擊之術法與觀念,洞察其特識與盲點,實在令人感到興味盎然。何況,諸派之掌故歷史、恩怨情仇,讀來也確乎有趣。
當時有同學張哲文、房國彥與我一道切磋。每天我們在學校工地或校外河川沙洲上打磚頭、劈石子、浸藥酒來泡洗雙手,用細砂子來插練。練到鐵砂掌略有成效,劈空掌則未能成功。
拳套方面,我由彈腿練起,以北派長拳為主,兼習螳螂、劈掛等象形拳種。其實,只要找得著拳譜,我大概都會練一練。故各派拳法,幾乎均有涉獵,雖未必能精,基本的道理尚稱熟悉。
我有一種偏見,認為凡拳術能傳得下來,必有書本子可以依循,所以訪書重於求師,只須找著拳譜即不難據譜修練。這當然是受了武俠小說的騙,然而事實上僅憑口耳相傳,恐怕也確實不免於訛誤失傳,因此流傳拳種,大約都有圖籍可以參考是不錯的。
但據書修習,有兩個困難,一是本身對拳理須有相當之理解,否則難以體會。因拳術玄奧,時有非文字所能盡意之處,欲因言求意、得魚忘荃,須恃讀者之善悟。其次則是中國的拳書,類似中國的藝術,如琴譜字帖,看起來只有一個個音或一個個字。這一音到那一音,這個字到下個字,乃至這一筆到下一畫之間,速度與力量各如何,並無記載。這並非忘了記,而是不必記也不能記,快慢徐疾及其間用力輕重,全憑使筆撚弦者自己去體會,並且由自己表現出來。故此均非客觀性的譜,乃是要讀者使用者「主體涉入」去參與之的知識。
相關商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