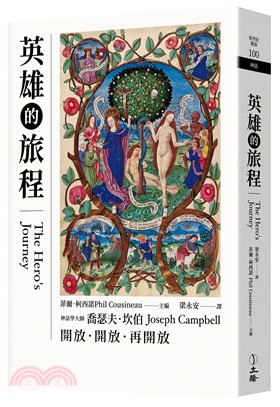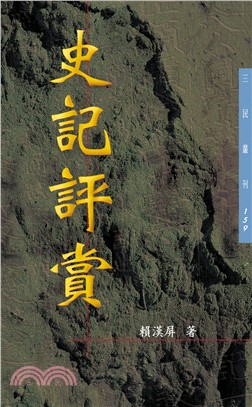英雄的旅程
商品資訊
系列名:新世紀叢書
ISBN13:9789863601531
替代書名:The Hero’s Journey
出版社:立緒文化
作者:菲爾‧柯西諾
譯者:梁永安
出版日:2020/04/06
裝訂/頁數:平裝/472頁
規格:21cm*14.8cm*2.8cm (高/寬/厚)
重量:677克
版次:3
商品簡介
.坎伯的神話之旅:我們需要神話來為自己的一生提供指引,需要神話以便接觸永恆,需要神話才能瞭解人生的奧秘之道,才能發現自己的本來面貌。
.追隨內心直覺的喜悅,由神話中體驗生命的智慧,追尋開放、開放、再開放的生活。
神話是人類心靈的歷史――坎伯的神話之旅
本書充滿機鋒與智慧,是由一群心理學、人類學、文學、電影製作人等,共同訪問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之對話,訪問者都是在美國當代該領域中的精英,其中還有一位是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坎伯從他所研究的神話中體驗生命的智慧,他鼓勵人要過一種開放,開放,再開放的生活,去挖掘心靈的各個面向,與不同的層次。
坎伯認為人的一生所經歷的是一種英雄之旅,但什麼是英雄呢?
坎伯重新定義英雄,他說,嬰兒從一出生就是英雄,因為他經歷了一次艱難的冒險。在戰場死亡的戰士與生產死亡的母親,所去的天堂是一樣的,因為生產也是一種英雄行為,在那過程裡,她把自己交給另一個生命。我們生活中也常常會有一些英雄行為,例如一個人為他的家庭、團體、後代――所做的奉獻等等都是。
此外還有各種英雄的定義如:「決心成為自己,是一種英雄氣概」、「要遵循內在的喜悅」、「追求生命的經驗」、「尋找內在的啟悟」、「對苦難的體驗」等。
坎伯發揚了美國當代神話學的研究,同時把神話帶到現代人的生活裡。例如大導演史丹利.庫伯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喬治.盧卡斯的「星際大戰三部曲」即引用坎伯的神話觀念拍攝完成。
「神話是人類心靈的歷史」。在一個我們已經失去與神話聯繫的時代,坎伯所代表的,是一個路標的角色。
作者簡介
詩人、編劇、探險旅遊導遊,得過多項文學、影片獎,著有Deadliness,編有The Soul of the Word、Soul: an Archaeology(中文版由立緒出版,書名為《靈魂筆記》)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前言/史都華.布朗(Stuart L. Brown,本書電影版執行製作)
激情這東西讓大部分精神科醫師都忐忑不安。「你對喬瑟夫.坎伯的崇拜,似乎是你渴望一個彌撒亞的移情作用。」一個朋友得知我想為坎伯拍一部紀錄片的時候說這樣說,他是個著名的心理分析醫師。我一直希望可以把坎伯的精彩思想用影像記錄下來,在電影院和電視上放映,留為永遠的紀念。我的這個夢想,終於落實為片長一小時的「英雄的旅程」,在一九八七年首映。這部電影,也是各位手上這本書內容之所本。
大部分美國中西部的長老派教徒,對於任何的狂熱都懷有戒心(運動和宗教方面的狂熱除外),我年邁的雙親自不例外。如果我能夠把我的「坎伯熱」轉移為對教會的支持或對自己醫療事業和經濟保障的促進,他們肯定會開心得多。
由於不聽師長父母之言是不明智和無禮的,所以在與坎伯漫長而密切的交往歲月,我都努力克制,不把他當成一個崇拜的對象,而我也顯然做到了這一點,因為證之於一些我要好和尊敬的朋友的觀感,我並未淪為一個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人,而是仍然有著獨立的思考和感受能力。
然而,回顧多年來與坎伯的相處,我的感受卻很像是愛――不單是對他的愛,也是對其他受過他感染的人的愛。看到他們從坎伯那裡獲得的喜樂與成長,是我會花十年以上的努力去為坎伯拍一部紀錄片的一大動力。我相信,我拍的這部紀錄片,將可以讓更多的人從他那裡獲得啟明。當然,我會有這個信念,是從親身經驗而起的。
***
他們認為成群結隊地前進是不體面的。所以,他們每個都會從一個自己選擇的地點進入森林,一個最黑和沒有路的地點。如果有路,就一定是別人走過的路,意味著你不是在冒險。――坎伯
***
一九七二年,也就是我三十九歲一年,我利用教授休假的機會要完成一個有關謀殺的研究。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裡那段期間,我發現最早期有談到暴力的文獻,都是神話性質的,而讓我驚訝的是,見於古代神話裡的家庭暴力模式,竟和美國當代的家庭暴力模式出奇的相似。於是我開始讀坎伯四大冊的《神的面具》(Masks of God)。讀完以後,我才瞭解到,坎伯對於人類的象徵、心理學、靈性和藝術遺產,具有驚人的融會能力,這種能力,是自達爾文以降任何試圖瞭解人的生物模式的科學家必備的。另外,在閱讀這幾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到,自己受到滋養的,並不僅止於知性的方面。讀完它們以後,我感到我對自己和對世界的觀感都迥異於從前。我變得能安頓於自己與世界之中。因此,我很自然會想知道更多坎伯的見解,而且也跟很多其他讀過他的書的人一樣,對坎伯其人感到好奇。讀他的書讀得愈多,我就愈有一種衝動,要把他廣博的知識與融會世界神話的能力引介給學術界以外的廣大聽眾認識。
由於我不是個製作電視節目專家,所以就找來已故的史帕林(Greg Sparlin)當拍檔。然而,起初坎伯拒絕了我們把他的作品搬上電視的構想,因為他認為,最適合表現他思想的媒體是文字。我們花了很多次的努力才說服他。不過,當他一旦作出了投入的承諾,我就很有把握,我們的影片將可以讓別人恰如其分領略到坎伯的學術深度與活力,並因此經驗到自己靈魂的深化。雖然當時相信我這個信念的人寥寥無幾,但我一點也不以為意。
就像很多原創性的計畫一樣,我開了很多次錯誤的頭,拍攝的計畫一直牛步不前。到了一九八一年年終,我愈來愈為坎伯的健康擔心,因為僅僅六個月內,他就得了兩次嚴重的肺炎。雖然他看來康復情況良好,而且健談如昔,但有醫師背景的我還是不能不憂心忡忡。坎伯已經年近八十,但卻仍然沒有有關他這個人和他的作品的足夠影像記錄。沒有錯,他是已經出版了很多本很上乘的作品,但我仍然強烈感覺到有把他的思想拍成電影的必要,因為正如坎伯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後來所說的,坎伯身上具有一種自然流露的「生命力」,可以誘導聽眾起而行去投入自己的靈性探索之旅。由於感到時間緊迫,我把努力提高了一倍。
「英雄的旅程」的正式拍攝工作始於一九八二年,地點是加州大瑟爾(Big Sur)的愛斯蘭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在製作人弗里(Bill Free)的幫助下,我找來一些背景大異其趣的人跟坎伯進行談話︰從坎伯的詩人老友布萊(Robert Bly)到諾貝爾獎得主吉耶曼(Roger Guillemin),不一而足,甚至還有一個以前從未聽過坎伯名字的年輕女士。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認為背景不同的對話者將可引發更多不同的話題。我的期望是,眾多的話題,加上導演肯納德(David Kennard)的技巧,加上愛斯蘭研究所的優美環境,再加上坎伯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與生命活力,能讓整部紀錄片更形豐富。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取材自在愛斯蘭研究所拍攝到的對話。
大約四五個月後,當我們開始剪接底片的時候,我發現有一把聲音在我心裡喋喋不休。這是我很不習慣的事,那怕它要對我說的是「追隨你內心直覺的喜悅」(fellow your bliss)。我心裡的聲音反覆不停對我說:「把坎伯下一次的全國演講系列拍成錄影帶吧,因為這將是他最後一次了。」令人難過的是,被它言中了。
有些人是在輕鬆、不那麼正式的環境裡表現得最好的。因此,在我們第一次進行剪接的時候,用了很多在這種場合所拍到的底片。然而,愈到後來,我們愈發現,坎伯表現得最好的,是那些他能夠自己挑選話題的場合,是那些他能夠使用他歷幾十年琢磨到最完美的材料的場合。
在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五年初,我和一個攝影小組追隨著坎伯旅行全國各地,拍攝他最後一次的全國講學之旅。我們在新墨西哥的陶斯(Taos)拍了他的「心靈與象徵」講演,在聖大菲(Santa Fe)拍了「神話在時間裡的轉化」,在紐約她太太主持的「大開眼界」劇院(Open Eye Theater)拍了「永恆的哲學:印度教與佛教」,在三藩市的美術宮劇院拍了「西方之道:亞瑟王傳說」和「聖杯的追尋」,在三藩市的加州歷史學會拍了「當代的神話:詹姆斯.坎伯哀思與湯馬斯.曼」。就這樣,我們得到了長達五十小時的母帶,而坎伯最有力的一些講演的影像記錄,也可以永遠留存下去。自此,我沒有再聽到聲音在我心裡喋喋。
坎伯進行全國性講學期間,每當一場講演或研討會結束,總會有人跑來問我們:「這個坎伯是什麼來歷?他是怎樣會成為現在這個人的?」總之,凡聽過他講演的,莫不流露出對其人其觀念的好奇和著迷。他們提出的問題,啟發了我們對這部電影以及各位手上這本書以最後的形式的。
在我看來,「英雄的旅程」全片的最高潮是坎伯在一九八五年接受全國藝術俱樂部頒贈文學獎章的部份。因為片長所限,我們只能收入頒獎典禮上喬治.盧卡斯、理查.亞當斯(Richard Adams)和希爾曼(James Hillman)等人所致的讚辭,而且只是節錄,尤其讓我難過的,是坎伯所發表受獎詞的部份,我們必須全部割愛。不過,這種遺珠之陷卻因為這本書的出版而獲得部份補償,因為是書可以讓那個不同凡響的盛會以更接近完整的形式呈現出來,也可以把很多其他因為片長之限不得不割愛的材料包含進來。
坎伯一向認為,他的觀念要比他本人來得重要,所以,在拍攝他的電影和編輯此書期間,我們都努力去做到我們相信他會期望的:讓他的觀念以異乎尋常的清晰,道出他是個有創思的人。
一九八七年,電影版的「英雄的旅程」分別在東岸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西岸的導演協會首映。西岸首映會後的座談會,是坎伯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講話。雖然他愛開玩笑說,自己已跡近是個「死人」(The Death),但在座談會上,他仍然不遺餘力把他最新的思想心得和合成帶給聽眾。座談會結束時,我看著他接受人生最後一次的熱烈鼓掌,只覺得心中一陣極大的酸楚。他在四個月之後過世。
重看過「英雄的旅程」的對話抄本和剪餘片以後,我情商影片的副製作人柯西諾(Phil Cousineau)想辦法把它們轉化為書本的形式。柯西諾拍片期間在各方面所作的重大貢獻以及他與坎伯夫婦愈來愈深入的交誼,都讓我印象深刻,而我也知道,坎伯夫婦不但欣賞他神話知識上的寬度,也欣賞他智慧上的深度。
一九八八年,「英雄的旅程」和由坎伯與記者莫比爾(Bill Moyer)的對談所拍成的「坎伯與神話的力量」(Joseph Campbell and the Power of Myth,共六集;編按:「坎伯與神話的力量」的文字版本〔The Power of Myth〕已由立緒文化出版,中譯書名為《神話的力量》),先後在公共廣播網(PBS)作全國性的播映,結果引發了極端熱烈與廣泛的迴響。在我看來,這種潮湧般的返響印證了一件事情:坎伯所說的話,會觸動我們每一個人。
目次
〈引言〉◎菲爾.柯西諾
〈導讀〉喬瑟夫.坎伯的神話研究◎李子寧
〈談話者簡介〉
1 冒險的召喚
2 試煉之路
3 靈視的追尋
4 與女神相會
5 恩賜
6 借助魔法逃走
7 跨越歸來的門檻
8 兩個世界的大師
跋:老虎與山羊
〈坎伯年表〉
書摘/試閱
引言╱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本書主編)
坎伯在神話海洋裡的漫長奧德賽之旅,既是一種學術性的探求,也是一種靈性的探求。透過大量的閱讀、寫作、遊歷,以及跟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男女的會遇,坎伯發現全世界的神話遺產展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並印證了一個他始自學生時代就堅信的信念:自然的核心具有根本的統一性的。
「真理只有一個,聖者以各種名字稱呼它。」印度古經典《吠陀》裡的這句話,屢屢受坎伯的徵引,作為其觀點的註腳。綜合歷史中的不變真理,成為了他生命中的燃點;透過神話來會通科學與宗教、心靈與身體、東方與西方,則成了他職志中的職志。
在《千面英雄》的序言裡,坎伯說:「我希望我這個透過比較來闡明神話相似性的工作,會可能有助於目前也許並不太絕望的統一世界的事業。不是以基督教會或某個政治大國的名義統一,而是在人類相互理解的意義上的統一。」
坎伯用於研究神話、宗教與文學的比較性歷史方法,與傳統學者大異其趣之處,在於後者強調的相異處,而他強調的則是相似處。他深深相信,不同文化千差萬別的神話內容與意象裡,存在著相通的主題與原型。另外,他也相信,透過重新詮釋神話中一些本初性(primordial)的意象――如「英雄」、「死亡與復活」、「童女成孕」、「應許之地」等――將可以揭露人類心靈的共同根源,甚至可以讓我們明白,靈魂是怎樣看待自己的。
「神話是『神的面具』,透過它,人可以讓自己跟存在的驚奇連接起來。」坎伯這樣說過。他相信,我們在辨認出這些意象的超時間性(timelessness)時所感受到的震撼,乃是一個證明,證明所有的人類生命,都是從同一個深邃的靈性根基湧現出來的。
就像愛因斯坦致力為外在世界的各種能量建立一個「統一場論」一樣,坎伯也致力於為各種我們內在的能量鍛鑄一個統一的理論。他認為,所謂的「神」,不過都是這些人類內在能量的擬人化。而物理學家所稱為的「實在的肌理」(fabric of reality),在坎伯那裡則被稱為「寶石的網絡」(the net of gems)。「寶石的網絡」這個隱喻,源出於印度人的宇宙論,而它也是對坎伯把神話、宗教、科學與藝術編織在一起的努力的一個妙喻。他認為這些不同領域裡的老師,致力的是同一件事情,認為在人類的精神史的全程裡,有同一個系統的原型衝動(archetyal impulses)――「同一首宏偉莊嚴的歌」。
坎伯是個破格的學者、老師與作家,而他所走的道路,和他在萬千神話裡發現的「左手道路」(left-hand paths)隱然相似,不管那是《由誰奧義書》(Kena Upanishad)裡所說的「一條鋒利得像剃刀邊沿的橋樑」,還是佛教所說的「中道」,又還是聖杯傳說中那個「沒有路或徑」的黑森林。他依循著直覺,在傳統學術界的殿堂之外另闢徯徑,沿著自己的學術的「道」(Tao),走入一種對神話的靈性與心理學性的觀照,擁抱一種諸聖徒與薩滿巫師所可以直接體驗的超越真實(trancendent reality)。這種被神祕主義者稱為宇宙意識(cosmic consciousness)的直接知覺,說成是與眾神的親身會遇也不為過。那是一種具有療力的靈視(vision),可以從表面的混亂裡看到秩序,可以在黑暗的核心抓住肯定生命的美(life-affirming Beauty)。如果誠如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說:「從不停的流逝中搶奪永恆,乃是人類存在(human existence)的一大詐術。」那麼,像坎伯這樣能夠經驗永恆的人,就合該被稱為我們的騙子手,我們的靈性嚮導了。
坎伯走的,是一條非正統的學術路線,而這一點――正如他喜歡開玩笑說的――讓他失去了一些來自同儕學者的榮寵。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事實上,他對自己的獨豎一幟和「半弔子」是極為自傲的。他曾經形容他老師印度學家吉謨(Heinrich Zimmer)「樂在自己研究之中」,這個形容,也顯然適用於他本人。他高度的生命與學術熱情先是感染了他在莎拉.勞倫斯學院的學生,稍後又贏得數以十計的藝術家的傾心。他把思想轉化為探險,把知識轉化為智慧,並向他的讀者和聽眾揭示出神話對人的切身相關性。對這些讀者聽眾而言,坎伯絕不是個研究細瑣題材而又大肆吹噓的人,而毋寧是法國人優雅地稱之為的animateur,也就是一個有著神授魅力的老師;他不只能把極其複雜的學問以活潑的方式介紹給一般聽眾,還可以喚起納巴可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的frisson〔戰慄〕――人因認識到自身生命的真理所引起的戰慄。單單是他的這份禮物,就讓他成為我們時代最受愛戴的老師之一。
雖然教了五十多年書和寫過二十多本著作,但坎伯卻認為,他的貢獻不過是給了別人一把「打開繆思領域的鑰匙」。繆思的領域雖然是無影無形的,但卻是靈感與想像力的源頭,可以指導我們怎樣形塑我們的生命。就此而言,坎伯可以說是個現代的秘義傳授者(mystagogue),是個帶領我們穿透一些奧祕文本的嚮導,它們包括了《貝奧武甫》(Beowulf)、《吉爾伽米什》(Gilgamesh),《西藏渡亡書》(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亞瑟王傳奇,印第安人神話,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的聖典,以致於像喬哀思、湯馬斯.曼、畢卡索等現代神話締造者的作品。在用現代語言迻譯這些莊嚴的敘事與意象的時候,他教會我們「如何閱讀神話」:把它們視為象徵,視為隱喻,用讀詩的方式去讀它們,用靈魂去讀它們。
然而,坎伯除了有解讀「隱喻變形」(matephorphosis)的天分以外,也擁有把經典個性化(personalized)的能力,在他以前,擁有這種能力的學者寥寥無幾。透過嚴格的學術方法和一種沿自赫耳墨斯(Hermes)的詮釋―創發(hermeneutics-inventive)藝術,坎伯為古老的神話注入了新的生命――而就像卡繆(Albert Camus)所說的,這是每一代的人都必須去做的。在其亞瑟王傳奇的研討課的最後,他曾經撂了一個挑戰︰到底我們是準備去追尋聖杯還是荒原?也就是,你是準備去追求靈魂的創意性探險,還只是追求經濟上有保障的生活?是準備去活在神話裡面,還只是打算讓神話活在你裡面?
隨者一位出神狂喜(ecstatic)的學者的再現,很多早已在科學的理性主義時代銷聲匿跡的思想家的思想,得以再次綻放出光芒。坎伯喜歡提醒他的聽眾︰「〔令人難忘的〕不是追尋過程的痛苦,而是獲得啟悟時的狂喜。」有時還會補充一句:「生命不是個待解的難題,而是個待生活的奧祕。」
但這是如何可能的呢?想要獲得這種境界,我們唯一能夠做的,是不是只是等待一個偶然的會遇呢?而在這個解神話化(demythologized)的時代,我們又要怎樣才能扭轉逃離神話的趨勢?難道不再有任何神聖的東西了嗎?我們要怎樣把贗品從崇高裡分離出來呢?
對於現代人要怎樣在已經除魅化(dis-enchantment)的環境中生活,坎伯有一個他專屬的回答︰找出你生命中的真正激情,並追隨它,在沒有道路的地方覓路前進。用他自己的語言來說,就是「追隨你內心直覺的喜悅」。當你明確無疑地體驗的「阿哈!」的感覺,你就知道你是馳騁在奧祕上面。
坎伯不止歇地追隨他內心直覺的喜閱,致力要找出神話、傳說、童話、民間故事、文學與詩這些夢般世界背後隱藏著的和諧。他的尋覓,讓人聯想起詩人葉慈(John Keats)對莎士比亞的形容︰「環繞著人類的靈魂航行」(circumnavigation of the soul) 。如果說弗洛依德和榮格透過對深層心理學的研究,把那個被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棄如敝屣的靈魂觀念拯救回來的話,那麼,坎伯連同埃利亞代(Mircea Eliade)和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等一票宗教史家或人類學家所作的泛文化探索,則是復興我們已經奄奄一息的神話,讓它們在靈魂的故事和意象裡,獲得重新的安頓。不管是合起來看還是分開來看,他們都是像榮格所建議的那樣,透過重新編織古代神話的故事網絡(story-web),「夢想著讓神話繼續向前進」。
坎伯的探索無可避免地把他帶進了永恆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的領域。永恆哲學的雄偉基調泛見於古代印度和中國的聖哲,蘇菲派與基督教的神祕主義者,以至於像惠特曼(Walt Whiteman)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這樣的詩人或哲學家,而這個基調要述說的,是人類靈魂的最深深處,乃是神聖實在(divine reality)的一面鏡子︰Tat tvat svi〔你就是它〕。上帝的國就在我們裡面,此時此地。如果我們能夠直悟作為自我最本質的奧祕向度,就會乍然明白,我們是與自然的終極力量渾然一體,我們自己就是轉化之旅的最後祕密。所以坎伯才會說︰「你就是你一直尋尋覓覓想知道的奧祕。」
坎伯相信,這種靈性的觀照,不但是超越時間的,也是超越地域的。不管是對薩滿巫師與古代聖者的智慧教誨,還是對當代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創造性直覺能力,他都懷有同樣高度的尊崇。因此,就像許多的永恆哲學家那樣,坎伯對那些認為只有少數人才是上帝選民的主張,是不予苟同,甚至嗤之以鼻的。他認為,神啟並不是少數人可以壟斷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他堅持:「每一個民族都是上帝的選民。」每一個神明都是一個隱喻、一個面具,它所指向的,乃是作為奧祕的終極根基,是宇宙的超越能量的本源,也是每一個人自身的奧祕本源。
幾十年來,有無數懷著最大熱誠的人想從坎伯那裡知道人生終極意義為何的答案,但坎伯最後卻意識到:「當人們告訴你他們在尋覓生命的意義時,他們事實上是在尋覓對生命的深邃體驗。」
做為一個關心生命的形而上向度的神話學家,作為一個關注現象背後的真實(things-beyond- appearences)的醫生,他奉獻了一生之力,去繪製出那張靈魂自身的旅程的地圖。他所畫出的地圖,是一張內在世界或深度世界的地圖,而它所顯示的那個寶貴地域,是微弱的心所無法通過的,而只能靠一顆堅強的心去穿過。坎伯這樣的推論說︰如果神話就像夢那樣,是源出於心靈的最深處的話,它理當也可以把我們帶回到心靈的最深處。出來的路就是返回的路。那是一種要超越所有信仰與成規的已知邊界的移動,一種對真正攸關重要的事情的尋覓,一條通向真正個體性的道路,一番回歸原初經驗(original experience)的途程,一個鍛造意識自身的範式(paradigm)――一言以蔽之,就是英雄的旅程:
英雄從日常生活的世界出發,冒種種危險,進入一個超自然的神奇領域;他在那兒跟各種奇幻的力量遭遇,並且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祕之地 冒險歸來,帶回能夠造福他同類的力量。
「單一神話」(monomyth)是坎伯信念的核心,也就是說,他相信一切的神話都是同一個神話的展現。他的這個觀念,就像中世紀的動物寓言集裡的獅身鷹首獸(gryphon)一樣,不是一下子就迸出來的,而是一點一點逐漸成形的,是坎伯對他景仰的大師的關鍵觀念進行創造性綜合的結果。這些大師包括了喬哀思、湯馬斯.曼、吉謨、安德希爾(Evelyn Underhill)、庫馬拉斯瓦米(Ananda K. Coomaraswamy)和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後者曾在一段深具影響力的文字裡說過:「決心成為自己乃是一種英雄氣概(will to be oneself is heroism)。」
這個單一神話,事實上是一個元神話(metamyth),是一個對人類靈性史的統一性的哲學解讀,是故事(story)背後的大故事(Story)。借用日本古代禪宗公案的話來說,這是由單一隻神話手掌所拍出的掌聲,它講述的是普遍性的自我轉化的探求。英雄的旅程是關於探求自我深度的勇氣的,是一個創造性的重生的意象,是我們內在的永恆循環,是一個離奇的發現︰發現追尋者所追尋的奧祕就是追尋者自身。英雄的旅程是把兩個相隔遙遠的觀念綁在一起的象徵,一個是古人對靈性的探求,一個是今人對自我認同的探求。正如坎伯所說的,這兩種探求「事實上是一樣的,它們的形狀雖然千變萬化,但我們總可以在它們裡面找到那個驚人的、恆常不變的故事。」
坎伯的人生涵蓋了從野牛比爾(Buffalo Bill)到電影「星際大戰」的漫長歲月,而作品則涵蓋了從希臘神祇阿波羅到阿波羅太空船的紛紜主題。所以,他的故事,不折不扣是個有一千張臉的故事。而布朗矢志要把這個故事拍攝下來,則可以說是一個靈視(vision)的追尋。
有好幾年的時間,坎伯都不願意接受我們為他留下影像記錄的建議,擔心這會流於一種名人崇拜。他反覆說:「〔說話者〕不是我,而是神話。」而對於讀者望穿秋水所期待於他去寫的自傳,他則說:「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在避開這種玩意兒。」在荷馬史詩中,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曾經告訴庫克洛普斯(Cyclops),自己是「誰也不是」(No Man)。這是個坎伯津津樂道的故事,然而,「誰也不是」這個意象,很可能就像聖杯的追尋和《芬尼根守靈記》(Finnegans Wake)的夢境系列一樣,是坎伯自我意象的一個重要部份。除接受過幾次深度的訪談以外,他一向的信條,可以用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一句話來表達:「真正的藝術來自匿名的自我。」
一旦拍攝小組決定了除了在愛斯藍研究拍攝到的那些內容以外,還需要在坎伯檀香山的家裡拍攝一些輔助性的內容時,我就被選派為代表,告訴他,我們這樣做的用意何在。我告訴他,為了讓紀錄片能夠有一個戲劇性的架構和變得更有力,我們認為有必要把他的學習歷程包含在影片裡。例如,我們想知道,他是怎樣發現成為他作品的橫樑的那些主題的?他是什麼時候首次認識到,凱爾特人的曙光神話(twilight myths)與喬哀思的夜世界小說(nightworld novels)是位於同一條連續線的上面的?
一直要等到拍攝的工作全部完成、我們在剪接室裡埋首剪接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英雄的旅程」這個主題真的就像阿里阿德涅的線團(Ariadne’s thread)一樣,可以把我們帶出龐大底片的迷宮。就像大多數的對話和訪談一樣,坎伯的對話和訪談也是錯綜複雜的。他所談論到的範圍,從《奧義書》到康德,從諾思替教派的福音書(Gnostic Gospels)到黑麋鹿(Black Elk),天南地北,範圍極其遼闊。不過,坎伯穿過他自己的迷宮的那條蜿蜒的路徑、他的作品與他的生活的相關性,此時卻成為了我們剪接的「線團」,而他一些略嫌晦澀的議論,也可以從中得到照明。一次又一次,聆聽坎伯回顧自己的過去時,我們都會想起叔本華說過的一句話:善於生活的人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就像是在讀一本寫得很好的小說。例如,坎伯在敘述自己和一些朋友(克利希那穆爾提〔Jiddu Krishnamurti〕、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里克茨〔Ed Ricketts〕、瓦特〔Alan Watt〕等,又特別是他的太太珍.厄爾曼〔Jean Erdman〕)初識的情景時,他的敘述就更像是一個光芒的閃現或小說裡強有力的一章,而不僅止是一則軼聞。在坎伯晚年,很多藝術家都紛紛表示自己曾受過他的巨大影響,而他對於自己的人生故事能有這樣一個尾曲,顯然懷有很深的感激。
一九八七年二月,布朗歷八年辛勤所拍成的愛的結晶「英雄的旅程:喬瑟夫.坎伯的世界」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首映,七個月後,坎伯在檀香山家中安然辭世,享年八十三歲。在布朗當初夢想透過電影把坎伯推介給世人的時候,對神話有興趣的人寥寥無幾,不過,在至影片最後拍成播映的大約十年之間,公眾對神話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此時,坎伯的名氣,早已從他的前學生和忠實讀者之間,延燒到了大眾文化的領域。諸如製片家喬治.盧卡斯和喬治.米勒、雕刻家諾古基(Isamu Noguchi)、搖滾歌星大衛.伯恩(David Byrne)和「感恩死者」(Grateful Dead)樂團、教士、詩人、心理學家,甚至喜劇演員,都公開表示他們對坎伯的景仰和承認從他那裡受益匪淺。
第二年夏天,「英雄的旅程」與坎伯接受記者莫比爾訪談所拍成的「神話的力量」先後在公共廣播網播出。而隨之而來的「坎伯熱」,大出每個人的意料之外。事前,又有誰相信,美國大眾會樂於在電視上看一個學者和一個記者談宗教談七小時呢?然而,坎伯的錄音帶和著作在接下來的熱賣,卻證明事實恰恰相反。而以坎伯為主題的討論會,也如雨後春筍般在學校的教室、心理治療師的辦公室、教堂的地下室、禪學中心和好萊塢的劇情討論室裡舉行起來。
坎伯的這種吸引力,遠遠不是人們對被浪漫化了的卡默洛特(Camelots)和特洛伊的興趣可以解釋的。事實上,美國人是受到了一個激情洋溢的說故事人的催眠。更可況,這個說故事人曾經是一個強有力的運動家和音樂家,後來則搖身變成為尊嚴獨具的哲學家和作家,並且把普遍的人文主義(universal humanism)與世俗的靈性主義(secular spirituality)作出了激動人心的融合。在他的作品裡,你可以找到一把打開藝術、音樂和宗教世界的大門的萬能鑰匙。更重要的是,他指出:「神話是關於你該如何生活的。」
在一個懷疑主義和焦慮情緒瀰漫的時代,竟然有人登高一呼,呼籲我們找出「那能激發和活化我們心靈」的力量,自然會讓人感到振奮。事實上,大眾在坎伯身上看到的,是葉慈所說的「老鷹的心靈」(the old eagle’s mind),是一個智慧深沈的老頭兒,是一片永遠年輕的土地上最罕有的原型。
坎伯對神話重要性的疾呼,復興了冬眠已久的對靈性與美學生命的文化討論。一九八六年冬天,一個讓人難忘的會議在三藩市舉行,名稱是「從儀式到狂喜」,它的主角包括了坎伯、精神醫師佩里(John Perry)和「感恩死者」樂團。當「感恩死者」的加西亞(Jerry Garcia)在台上向坎伯承認古代的神祕狂歡儀式與搖滾音樂會之間有相似之處時,台下歡聲雷動,震徹屋宇。「他們不明白自己說些什麼,我們也不明白我們說些什麼,但我想我們說的是同一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能在一夜之間明白神話,但那個嚮往「共同語言」的舊夢,卻一下子間復興了起來。
(全文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