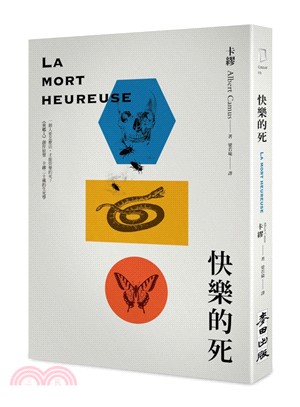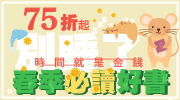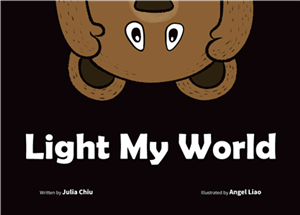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愛麗絲‧米勒的悲劇
商品資訊
系列名:Psychotherapy
ISBN13:9789863571780
替代書名:Das wahre 'Drama des begabten Kindes': Die Tragödie Alice Millers
出版社:心靈工坊文化
作者:馬丁‧米勒
譯者:林硯芬
出版日:2020/04/20
裝訂/頁數:平裝/240頁
規格:21cm*14.8cm*1cm (高/寬/厚)
重量:299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最有勇氣的家族書寫,最具建設性的理論實踐──兒童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之子直面傷痕累累的母子關係,明辨母親學說的價值與侷限,終止創傷惡果代代蔓延。
「我作夢也想不到要寫一本關於我母親的書,她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到無法描寫的人……」
身為舉世聞名的兒童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的獨子,馬丁.米勒與母親的關係卻疏離而緊繃,他甚至為此瀕臨崩潰。母親過世後,馬丁終於鼓起勇氣,藉著書寫本書重新認識母親這個人,才終於同理雙方的處境,也明辨了愛麗絲.米勒理論的價值及侷限。
愛麗絲.米勒以《幸福童年的祕密》等經典著作建立起兒童捍衛者的聲名,但她自己卻從未處理童年創傷,內心壓抑的憤怒塑造出極端、激烈的性格,兒子馬丁則成了最直接與長期的受害者。這應驗了愛麗絲.米勒自己的主張:父母的創傷會蔓延到子女身上。
「母親待我猶如敵人,真讓我覺得自己像隻怪物,而她想除掉牠……」
傷痕累累的馬丁透過訪查回溯,揭開母親絕口不提的早年經歷:在僵化保守的猶太家庭成長、經歷殘酷的納粹屠殺;他同時看見母子間因戰爭創傷而扭曲的情感互動,理解母親為何無法按她創造的知識對待兒子。這個歷程為馬丁自身的情緒找到出路,也讓同為心理治療師的他,親身體會到回溯家族歷史在創傷修復上的價值。
「當愛麗絲‧米勒的兒子並不好……即便如此,我的母親仍是個偉大的童年研究者。」
本書可說是馬丁在母親的立論基礎上,親身實踐了更具建設性的做法,不僅為米勒全球的舊雨新知分享了發人省思、勇氣十足的生命故事,也為心理治療貢獻了精彩絕倫的案例。
感動推薦──
丁興祥/輔仁大學心理系退休教授
王浩威/作家、心理治療師
林蔚昀/作家、波蘭文學譯者
周仁宇/兒童精神科醫師、精神分析師
蘇絢慧/諮商心理師、心理叢書作家
(依姓氏筆畫排列)
作者簡介
1950年生於瑞士蘇黎世,早年曾為小學老師,現為執業心理治療師。他是兒童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之子。儘管是個擁有數十年經驗的治療師,但母親極端的性格與強大的輿論影響力,於公於私都為他帶來巨大壓力,甚至到了自己承受心理創傷,多次接受治療無果的程度。2010年母親過世後,在出版商鼓勵下勇敢回溯母親生命史,寫成本書,也為自己糾結的人生帶來釋懷。現居瑞士。
林硯芬,資深德文譯者,譯有《夏娃的覺醒:擁抱童年,找回真實自我》、《身體不說謊:再揭幸福童年的祕密》、《滿足:與其追尋幸福,不如學習如何知足》、《神祕靛熱》等。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一個悲傷痛苦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蘇絢慧/諮商心理師、作家
很多人也許都有一個想像:如果自己有一個享譽盛名的心理治療師母親,她對待孩子必然溫柔、敏銳、耐心,極富同理心,如此一來,自己會有一個幸福的童年、美滿的家庭,不用歷經任何苦痛、掙扎、缺憾和衝突,可以安穩成長,成為想要實現的自己。
說到這點,還有誰像本書的作者馬丁‧米勒一樣,有個舉世聞名的兒童心理學家母親──愛麗絲‧米勒?她所出版的《幸福童年的祕密》幫助也療癒了許多童年受創的人,讓他們明白童年的傷痛不是他們的錯,而是來自無能給愛的父母和代代相傳的家庭不幸。
儘管馬丁‧米勒後來也成為一位心理治療師,擁有數十年治療經驗,但母親極端的性格與強大的輿論影響力,不論在生活或是專業方面都為他帶來巨大壓力,母子關係充滿衝突、掙扎和糾結。即使尋求心理治療多次,都很難化解那一份深層的矛盾和痛苦。
沒有人有幸福的童年。即使愛麗絲‧米勒極力想從自己母親帶給她的失落和傷痛中解脫,努力投入寫作和繪畫來療癒自己,並以心理治療來解救自己,好讓自己和母親不同,不那麼冷漠而具毀滅性,但她仍無可避免地因為無愛的童年而進入了一段無愛的假性親密關係,加上深怕自己的兒子馬丁‧米勒會像他丈夫一樣,而對孩子進行指控和控制。同時,她也因為自己幼年遭受許多暴力傷害,以致面對兒子遭遇父親不當的肢體暴力時決定迴避,無法挺身保護孩子。
這種種情感的深層糾結和矛盾、切割和疏離,無疑讓馬丁‧米勒經歷長期的自我衝突和壓抑。他感覺母親把他看成怪物,並且極力要去除他內在的怪物特性。身為心理分析專家的母親對他所給出的心理評論,讓馬丁感到極度憤怒和錯亂。
那些成長過程以及和母親相處的經驗一直不曾為外人所知,直到在愛麗絲‧米勒過世後,馬丁‧米勒終於在旁人的支持及鼓勵下,透過回溯母親的一生,真正理解屬於母親生命的種種真實。
馬丁‧米勒並不想以本書來作為名人孩子向世人抱怨父母的訴狀,而是透過研究、訪談,重新了解歷史軌跡,認識他因沒有機會離開「兒子」的位置而未能好好了解的「愛麗絲‧米勒」。在這一段重新回看母親生命,包括她的童年以及所經歷的戰爭之歷程後,母親的輪廓總算漸漸清晰,包括她生理和心理層面的創傷及影響。
六年前,我有幸為《幸福童年的祕密》寫推薦序,如今再能推薦《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愛麗絲‧米勒的悲劇》,我感到一份特別的情感在心中流動。閱讀了這一本既沉重又開展的親子和解之書,相信每一位讀者都會從中體悟到屬於自己的領會和獲得,我特別建議想從童年傷痛中療傷的人閱讀。
而我則有兩點很深的感觸:
第一點是,我們沒有幸福完美的童年,並不只在於我們未能擁有完美的父母,也在於我們未能身處理想的時代。沒有一個世代是完美的,戰爭時代留下了許多「戰爭的孩童」,他們歷經匱乏、貧窮、殺戮、暴力和許多的自我分裂,在還未能意識清楚自己身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時,就已長大並為人父母。他們甚至有許多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經歷了什麼創傷。即便戰後的現代,看似物資富足無匱乏且局勢和平,但只要活在社會情境中,看不見的心理壓力和存在焦慮仍無時無刻影響著成為父母的人,也影響著正在成長的我們。沒有人可以迴避、否認這些影響。
第二點,任何想要療癒童年或家庭傷痛的人,若只知控訴和抱怨,療癒恐怕終其一生都難以發生。最重要的療癒因子,在於我們的心理移動,不再只是死守在「孩子」的位置來解讀和體會一切。雖然創傷知情是非常重要的治療過程,我們不能否認和迴避在我們身上發生過的真實,但療癒能否完成,關鍵在於我們能否鬆動心中對某些記憶和遭遇的觀點,以一個更大的社會視角理解時代對人們身心及行為無可迴避的衝擊及影響,如此才能將身而為人的脆弱及限制歸還給自己及父母,從一個更具深度、廣度的距離重新理解家庭中的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究竟是怎樣地有限卻又盡力的在找尋各自的解脫。
只有回到對人的認識以及對人性深刻的理解,或許我們才有一點點契機領悟到一些對人的慈悲及憐憫下的寬容和饒恕,包括至親和自己。
序
前言
母親過世幾週後,我有個接受新聞雜誌《明鏡週刊》訪問的機會,以下便是我與訪問者艾兒可‧許密特(Elke Schmitter)及菲利浦‧歐姆克(Philipp Oehmke)的對話,這段對談一直糾纏著我直到寫了本書為止:
明鏡週刊:您說您的母親終身致力於找尋方法,揭開他人的創傷,但自己卻不知該如何與兒子談論自己的創傷?
馬丁‧米勒:我試過無數次與她對談,就像您現在和我這樣,但卻踢到了鐵板,所以關於您題問,我無法進一步給您其他解釋,我不只是她的兒子,我也是心理治療師,也就是一個讀過傳記並深入分析的人,但是我並未滲透入其中,大家總有一天會接受這點的,這層阻礙也讓我在過去的三十年來無法接近我母親,我必須承認。
明鏡週刊:您母親創造了一份獨一無二的作品,此作品裡說到:精神分析無助於精神創傷,但有另一個解除童年壓抑與重獲新生的獨特方法──我將試著向你們展示之。我們現在認為,在我們彼此對談了十分鐘後,您母親隻字未提她作品中任何一個自己人生歷程裡的重點,她無法將自己的方法使用在自己人生最巨大的創傷上。
馬丁‧米勒:即使她在她的著作中正確地看到了那麼多的事物。我的悲哀是,我這個戰後世代所生的小孩沒辦法與我的父母建立起一段情感關係。
明鏡週刊:請您幫助我們:關係喪失不正是您母親所譴責的、父母的殘酷與畸形的原因嗎?
當時的我作夢也想不到要寫一本關於我母親的書,她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到無法描寫的人。直到二0一0年的秋天,我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向一位美國出版業者介紹了她的作品,我才開始認真思考這件事。那位出版商認為,對我以及我母親的讀者來說,寫一本有關她的書將會大大有益。這段話縈繞在我心頭,引起我非常矛盾的感受,起初我感受到一股強烈的拒絕,認為寫一本書的念頭極為荒謬,然而即便情感上出現了劇烈的抗拒,此念頭卻揮之不去,我勉為其難地決定接下這個困難的計畫。
第一個問題是──我對我母親所知甚少,愛麗絲‧米勒──我在這本關於我母親的書裡,將常常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把她的人生歷程都封鎖了起來,將她的私人生活變成了一個被守護得嚴嚴實實的祕密,尤其是戰爭那幾年,她特別守口如瓶。誠如眾人所知,我母親是二戰時期在華沙存活下來的猶太人,但實際上她幾乎不曾提及那段日子,最多只是委婉地帶過或使用很有距離感的說詞描述之,就連對我她也鮮少提起,直到我四十一歲才獲知一二。我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所有與猶太人有關的,以及所有與波蘭有關的事物,都與我隔離得遠遠的,我既沒學過父母的母語波蘭文,也沒人教我任何猶太文化,我宛如文化工藝品般地長大,被當成瑞士人來養育,瑞士對我父母來說基本上是個很陌生的國家。我體現了所謂的倖存後的新開始,就像倖存者身上常可見的那樣。這是其一。
也就是說,我對這些實情所知甚少,但我卻對我那從未被議題化的母親痛苦領會甚多,這是現在的我在做了寫這本書所需的調查研究之後所了解到的事。從有關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研究,我們得知這些孩子都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關注,他們必須代替在那段苦難時期所或缺的情感對象,因此孩子們成了父母的依靠與存在基礎。人們稱這種過程,也就是親子關係的反轉,為:親職化,即因創傷侵擾而感到痛苦的父母透過自己的孩子去追回情感上的支撐,就像我母親在她的第一本著作《幸福童年的祕密》裡強調的:孩子擁有一種非凡的天賦,他們能出色地領會父母的需求,即便父母未曾吐露。他們完全了解父母所期待的是什麼,並且表現出相應的行為反應,這也是我曾經做過的事。
我與母親的關係──我如今終於了解了──有著那種扭曲關係的所有特點,包括轉遞被壓抑的迫害創傷,也就是說,我母親和我以某種精神官能症的方式而非常接近彼此,我們由於一種從屬的親近而擁有緊密的連繫。透過這種方式,我在情感上成為了我母親大屠殺經歷的一部分──而我當然一無所知,無論是小時候還是長大後。我成了見證者,是的,是戰爭創傷的一部分,卻渾然不知當初究竟發生過什麼。我成了一段苦痛史的參與者,儘管或者正是因為我對這段過去並不了解。我可以說是經歷了母親受到的納粹迫害,也就是這種盲目迫害的後果。
德國作家暨時事評論家亨里克・布羅德(Henryk Broder,1946年生)在一九八二年鄂爾文・萊瑟(Erwin Leiser)的電影《劫後餘生》(Leben nach dem Überleben)裡是這麼描述大屠殺倖存者所生之子的命運:「我一直覺得自己彷彿被束縛在一個我所不知道的、看不到的,但卻使我深受重負的驚恐座標系裡,我無法與之對抗。」我又在這幾句話中看到了自己。
我記得以前我們去蘇黎士拜訪親戚時,我在他們家裡看到了一些我不認識的東西,餐櫃上的木頭人偶有種神奇魅力吸引了我,那是正統猶太教男性塑像,旁邊還有一座光明節燭台。然而我卻完全不敢去詢問所有這些東西的意義,那未曾說出的禁問完全發揮了作用,即使長大成人,我還是一再地面對母親的恐懼,她很害怕被別人知道她的私事,直到她過世為止,她都小心謹慎地留心著不要讓任何私事公諸於世。
直到先前提過的《明鏡週刊》訪問以及美國出版業者的建議,我對母親的這種絕對服從才開始不斷動搖。
即便滿腹罪惡感,我還是認為,相較於進一步向母親的讀者隱瞞她人生經歷究竟正確與否的問題,對我來說,我自己究竟敢不敢探究自己的故事、是否有勇氣去揭露我的人生根源,反而才是更重要的。
我當然讀過我母親的著作,在《拆除沉默之牆》(Abbruch der Schweigemauer, 1990)裡,愛麗絲‧米勒建議所有讀者揭開自己的真相、自己的故事,並解除壓抑。我現在認為,即便我長年讓自己做心理治療,而且也擁有幾十年心理治療師的工作經驗,針對這樣的案例,要去克服的不只一座沉默之牆,還有一座巨大的罪惡感之牆。
在這樣的情感狀態下,我開始著手撰寫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有許多早已被遺忘的記憶浮現而出,而且我真的認為自己能描繪出母親的人生。直到和我的編輯艾娃瑪莉亞‧波勒(Evamaria Bohle)討論時,我才意識到自己陷入了角色混淆之中,我主要是以我的情感體驗來刻畫母親,母親傳遞給我的價值觀瀰漫在「事實」當中。
我再一次從頭開始,拜訪了時代的見證者,我母親仍在世的親戚──她在美國的表親伊蘭卡(Irenka)與阿菈(Ala),我開啟了一個奇妙、有趣且至今都未知的世界,那是我母親在戰前成長的世界,這個世界被二戰與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殘暴地摧毀了。如今我相信,愛麗絲‧米勒之所以無法成為我的慈母,其原因就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那段迫害歲月緊緊包裹住的創傷之中。我現在非常驚訝,母親在其著作《教育為始》(Am Anfang war Erziehung, 1980)裡那麼客觀地描述希特勒的童年,是如何做到的。最讓我感到荒謬的,是在大眾的感受以及對我母親這本書的批評當中,一再出現低估了希特勒所作所為的譴責聲。人們再無法以更好的方式隱藏、壓抑自己的過去。
(未完)
目次
【推薦序2】幸福童年裡暗藏的悲劇/周仁宇
【推薦序3】推倒沉默之牆,勇敢說出自己的童年往事/丁興祥
關於愛麗絲‧米勒
母親的來信,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前言
拆除沉默之牆,複雜而大膽的行徑
2.結局:愛麗絲‧米勒沒有墳墓
3.遺傳的個體:猶太女性
我母親所說的是:童年的傷痛
我發現的是:愛麗西亞‧恩拉德與她的家庭,一九三九年之前
真實的自己與主觀的世界
4.被否認的創傷:存活下來的
我母親所說的是:「我必須殺了我自己」
我發現的是:愛麗絲‧洛斯托夫斯卡存活於華沙,一九三九~一九四五
以假的自己存活下來
5.勉強的愛:妻子
壓抑住的恨:我父母的婚姻
愛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6.選擇疏離:移民
瑞士的新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八五
嚮往之地普羅旺斯,一九八五~二0一0
藏身處傳來的虛擬訊息:網路
新開始的不可能
7.找到的自由:童年研究者
作為精神分析師的母親,一九五三~一九七八
通往自由的道路
寫作之幸:《幸福童年的祕密》
人生主題的變體:愛麗絲‧米勒與父母的戰爭
8.遺傳的苦痛:母親
沉默的見證者: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一九五0~一九七二
康拉德‧施德特巴赫的信徒:受迫害的兒子,一九八三~一九九四
母親的來信,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把兒子當成迫害者:戰爭創傷的力量
尾聲:二00九~二0一0
9.接受檢驗的知識:治療師
自《幸福童年的祕密》以來的時代變遷
知曉自己的人生經歷
心智化:愛麗絲‧米勒方法的理論
知情見證者‧治療師與當事人的關係
《幸福童年的祕密》還有什麼沒說的?
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二0一0年四月九日
10.從摧毀沉默之牆開始:後記/奧利維‧舒柏
謝辭
延伸閱讀
書摘/試閱
8.遺傳的苦痛:母親
沉默的見證者: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1950-1972
每當我被問及兒時記憶時,總有一個場景不斷浮現,雖不怎麼聳動,也未反映出任何我所承受過的各種暴力經過,不過它的氣氛卻讓我歷歷在目,以致我曾一度將它理解為我在家中角色的關鍵答案。
當時的我大約八歲,我父母兼差為某間出版社訂正手稿樣本,我還記得他們是如何高度專注地坐在餐桌旁。我看著他們,不說話,持續好幾個鐘頭,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並不真的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但很清楚自己不能發出聲音,絕對的寂靜掌控著一切,某種程度上,這種寂靜從一開始就包圍著父母與我。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們之間通常用波蘭文,而我卻只學過(瑞士)德語,這讓我更加被孤立。父母親從沒想過要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去反思他們對我的態度,他們讓我成為了自己家庭之內的局外人,身為孩子,我無法理解他們的這種行為,當然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在自己的家裡會這樣被排擠。後來我才了解,身背重負的父母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宿命投射在孩子身上,也很震驚地發現,我在父母的家中竟是個外國人,就像我父母在瑞士也是外國人一樣。我成了自己家中的陌生人,而且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兩人則忙著遺忘戰爭以及重新獲得安全感,孩子的需求基本上只是次要之事。
我成了父母的沉默觀察者,這種巨大的沉默幾十年來包圍著所有我身上發生之事:蔑視、情感干預、對身為人的我漠不關心,且即便我已成人亦然。這樣的狀況在我家內部造成了一種複雜的交互作用,我基於觀察者的角色,被迫敏銳觀察周遭,發展出一種X光視角,掃描幾乎所有的動作與話語,希望務必明白自己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向我解釋發生了什麼,因此我必須獨自透過觀察去推斷實際情況,這種方法潛藏著誤解的危險。我可以說是很幸運的,沒有變成神經病,而是發展出一種極大的才能,對人們行為的理解相當敏銳,很容易便能解讀並了解人與人之間非語言式的溝通。身為心理治療師,這種能力一再幫助我去找到並理解複雜的心理因果關係。
在我成年之後,我母親對我最嚴重的干涉是在九0年代,我和第一任妻子離婚而陷入了嚴重困局時,我聽從她,讓一位康拉德‧施德特巴赫(Konrad Stettbacher)的學生為我做了原始療法(Primal Therapy),當時她仍是極力推崇施德特巴赫的。我能揭穿他是個騙子,這也要歸功於我沉默觀察者的能力,我之後還會再回來談這個部分。
如今我當然知道,那些由於戰爭、迫害、逃亡、移民、經濟危機而背負著極為沉重負擔的父母們,要他們用同理心去感受自己孩子的世界是很費力的。即便如此,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去看我經歷過的事,對我來說還是很困難,以治療師的身分我辦得到,但是以兒子的身分即使過了幾十年,我還是很痛苦。世界知名的兒童研究者愛麗絲‧米勒,沒有人像她那樣為孩子爭取自我心理發展權利、對抗家暴的父母,但身為她的兒子,我的處境卻是更加困難。
不過話說從頭:我在一九五0年四月來到這個世上,當時我父母都正忙著撰寫他們的博士論文。愛麗絲‧米勒在我成年後曾對我形容過生產與產後的幾個月對她來說有多受傷,以下是我從回憶中記錄下來的:
當陣痛終於開始時,我去了蘇黎士州立醫院,我對生產非常的恐懼,產台上的我驚慌失措,心中又浮現出從前的恐懼感,我覺得自己完全被交到了別人的手上,就在這個時候,陣痛突然又停止了。三天後我才再次能夠開始嘗試把你生下來,而這幾天我就在蘇黎士山上四處散步,拒絕當媽媽的巨大罪惡感與恐懼讓我很痛苦,我覺得我是完全孤立地面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人給我支持,就連你父親也沒有。終於陣痛又開始了,而你健康地來到這個世界,這次的生產過程雖然沒什麼狀況,但是你出生後沒多久,又出現了新的難題:我覺得自己完全無法照顧好你這個無助的孩子,而你也讓我當母親的第一步過得不輕鬆,你從一開始就拒絕被哺乳,我對此感到很傷心,我非常失望,因為我自己的孩子拒絕了我與我的母愛,我必須把母奶擠出來,而你只用非常小的瓶子喝奶。
對我母親來說,我,也就是一個小嬰兒,「控制」了她所有時間,需要她全心全意的關注,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透過我的生理需求「強迫」她該如何過生活。這是她非常難以接受的,無論如何都無法勝任,因為對她來說,接受某人的規定是最恐怖的事。我不記得我母親給予過我任何自主權,我的自主權始終是被禁止的,她後來對此承認,且一再說她對此有很深的罪惡感。我母親每次向我解釋為何她在我出生之後不久就立刻把我交給一位熟人照顧時,總是很官方地提出下面這種說詞:「因為你父親和我在忙博士論文,而且家裡空間太小了,無法同時再養一個孩子,所以我們必須把你送走。」根據我的調查,以及撰寫本書時獲得的概觀視角,我現在已不再認為她這種說法令人信服,我拒絕喝母奶這件事深深傷了她的心,我認為我與母親之間這種早期的關係經歷是我們這麼多年來關係一直不太融洽的原因之一,我之後會再提出幾個事件來證明此論點。
那位熟人也不太會照顧新生兒,我應該在她那裡待了有兩週左右,不斷地哭鬧尖叫,而且身體狀況很糟糕,直到阿菈姑婆把我接走為止,伊蘭卡說:「如果我們沒去接你的話,你可能已經死了。」我在阿菈、布尼歐還有當時十八歲的伊蘭卡家中度過了我人生最初的一年半的時光,我的父母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
接下來的一個重要的轉折事件是我妹妹尤莉卡在一九五六年的出生,正如之前提到的,她一出生就是個唐氏症患者,她的出生與我父親對我母親隱瞞自己妹妹患有此症的這件事,讓我父母的婚姻更是雪上加霜,這個孩子其實本應拯救我父母分崩離析的婚姻,但卻使兩人隔閡越來越深。我們兩個孩子都被送走,尤莉卡一年後就回到我父母身邊,而我則在一間位在哈爾賓塞奧(Halbinsel Au)的育幼院裡待了兩年。我被告知,是為了治癒尿床問題而必須這麼做。在那段時間裡我基本上和家人沒有聯繫,我完全忘了自己有個妹妹,不過即便如此,我對於待在「愛麗絲阿姨」──我們如此稱呼育幼院院長──身邊的日子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回憶,只有上學這件事成了災難。沒有人為我做上學的相關準備,我無法應付學校,覺得自己很失敗、無法成功,尤其是學校要求的課業,學校自此一直都是個難題,而有關我那不理想的成績的討論,則是我父親鄙視我時最喜歡說的話題。
我被接回家就像我被送進育幼院一樣突然,當時我八歲,我父母搬了家,在我離開兩年後,所有一切都是又新又陌生的。大客廳的天花板上懸吊著一張鞦韆,有個表情很怪異的小女孩坐在上面──我的妹妹。我不想要她,而期待我持續體諒的父母,其態度非但沒阻止我的這種想法,反而更挑起了我的這種念頭。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的主要關係人一直都是女傭或保母,我與她們在家裡組成了一個家庭,我和她們說德語,而我父母彼此之間卻講說波蘭文,不過他們常常會轉換,因為我母親很難接受兒子與保母在情感上比與她還要親近。
我父親殘忍、暴力卻迷人、有魅力,和他一起活動,如健行或滑雪,常常由於我累到生病而告終。他可能想把我變成一個「真漢子」。他可以好到為我煮我最喜歡的食物,然後又全部回到原點。我很愛他──就像一個孩子愛著他的父親那樣──但是我對他也有一種無法言喻的畏懼,因為他的情緒與攻擊一直都是捉摸不定的。我究竟有多怕他,這件事直到好幾年後,透過一次心理治療我才明白。他曾用不同的方式折磨我──不論是心理或生理。我那位與他進行著某種形式長期抗戰的母親讓他隨心所欲地這樣做,她在那個時期完全消失在她的精神分析世界裡,常常若非不在家,就是正忙碌著。
一九六0年,我們從拉珀斯維爾搬到了蘇黎士,我母親隨即在我們家隔壁設立了診療室,大家都必須一直保持安靜,隨時小心,她總是很累,不然就是正在路上。靠近她是不可能的,她自己才有權力決定何時有興趣靠近你。我沒印象父母會對我的事感興趣,情感方面我只能交給自己。
我十七歲才進入一間天主教寄宿學校就讀,在那裡度過了我最後的中學生涯,而我母親則很誇張地拼命用電話和我聯絡。我是自己想要去寄宿學校的,我覺得在那裡比在家自由多了,雖然學校管得很嚴,不過還是比家裡壓抑、具攻擊性又累人的氣氛舒服許多。無論如何,我和母親之間產生了一種怪異的電話關係,她每天總會在用餐時間打電話來,我的同學們吃飯時,我會被叫去接電話,而且每個星期天至少得花一個小時和她通電話。我不記得自己是曾否反抗這種巨大的困擾,一方面我也不敢,另一方面則是我終於感受到被重視、被看到了。
高中畢業後我想繼續唸大學,但父母都不相信我有能力,我接受了小學老師的培訓然後自立了,童年成了過去。
(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