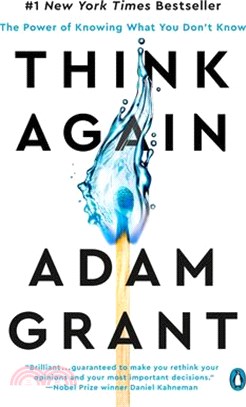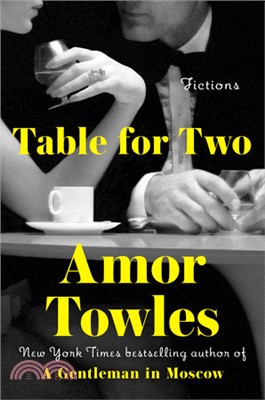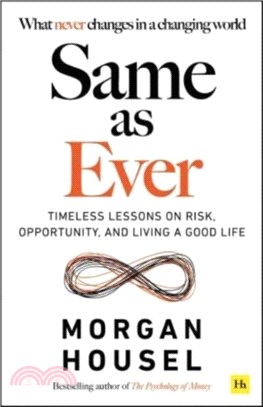庫存:2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13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思想史大師林毓生的成名之作
以胡適、陳獨秀與魯迅三位思想家為案例,
將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上溯至五四時期,
解釋現代中國何以出現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將文化遺產全盤否定。
林毓生在書中提出著名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一說:
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如果要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
就必須徹底改變人們的價值和精神、文化與信仰,
現代中國的政治危機,因此也成了一場思想與意識的危機!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起源和性質所做的研究。這種反傳統主義如此激烈,要求徹底摧毀過去的一切,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一種空前的歷史現象。
在社會與歷史發生根本變遷的時期,經常出現反傳統的衝動。新規範、價值的理解與支配,使得許多傳統上視為理所當然的準則和慣例,變得格格不入和難以容忍,人們因此常會要求將它們摧毀。
傳統的「摧毀」具有許多種類,反傳統主義的類型亦見繁多。人們可以抨擊所覺察出的傳統中有害的部分,而不必然要全盤地譴責過去。如果某一傳統內的轉變潛力是巨大的,那麼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該傳統的某些符號和價值,還可經由重塑和轉化,提供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還可以在變遷的過程中保留文化認同的意義。
林毓生表示,當建設出可實施運行的現代社會時,從傳統汲取出的文化成分,可以扮演著促進更勝於損害的角色功能。因此,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
以胡適、陳獨秀與魯迅三位思想家為案例,
將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上溯至五四時期,
解釋現代中國何以出現激烈的反傳統主義,將文化遺產全盤否定。
林毓生在書中提出著名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一說:
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如果要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
就必須徹底改變人們的價值和精神、文化與信仰,
現代中國的政治危機,因此也成了一場思想與意識的危機!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起源和性質所做的研究。這種反傳統主義如此激烈,要求徹底摧毀過去的一切,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一種空前的歷史現象。
在社會與歷史發生根本變遷的時期,經常出現反傳統的衝動。新規範、價值的理解與支配,使得許多傳統上視為理所當然的準則和慣例,變得格格不入和難以容忍,人們因此常會要求將它們摧毀。
傳統的「摧毀」具有許多種類,反傳統主義的類型亦見繁多。人們可以抨擊所覺察出的傳統中有害的部分,而不必然要全盤地譴責過去。如果某一傳統內的轉變潛力是巨大的,那麼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該傳統的某些符號和價值,還可經由重塑和轉化,提供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還可以在變遷的過程中保留文化認同的意義。
林毓生表示,當建設出可實施運行的現代社會時,從傳統汲取出的文化成分,可以扮演著促進更勝於損害的角色功能。因此,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
作者簡介
林毓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序
著者弁言
由於種種機緣,《中國意識的危機》最早是以英文撰寫而成,自1979年英文版在美問世後,先後出現過兩個中譯本。多少年來,筆者始終以一個關懷現代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前途,認同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的心情來討論各項有關的問題,因此這次拙著能夠再次「返回」,與中文和華文世界讀者切磋,內心快慰何似!
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兩種語言的對譯,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中譯英固屬不易,英反中,更是難上加難―尤其當中文是著者的母語時。這次拙著中譯本告成,得眾友生大力襄助,其中楊貞德、丘慧芬費心聯絡,嚴搏非約總其成,在此一併致謝。
翻譯分工如下:〈前言〉郭亞珮譯;第一章〈緒論〉王遠義譯;第二章〈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一)〉正文楊芳燕譯,注釋郭亞珮譯;第三章〈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二)〉第一、二節楊芳燕譯,第三節傅可暢譯;第四章〈陳獨秀之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楊貞德譯;第五章〈胡適的偽改革主義〉楊貞德譯;第六章〈魯迅意識的複雜性〉劉慧娟譯;第七章〈結論〉劉唐芬譯。
前言
班傑明‧史華慈
在19世紀的西方,中國經常被認為是凍結了的傳統主義的最佳典範。到了20世紀中葉,對許多人來說,中國已經變為革命之地――一個與自己過去的文化社會秩序全面而徹底地斷絕了的社會。若是我們反思一下,中國何以是不變傳統的最佳象徵,我們就會感知到,這個看法,跟下列觀感緊密相連:中國設法維繫了一個把社會、文化和政治整合在一起的秩序,這個秩序中的統治階級,致力於體現政治跟精神兩方面的權威。傳統的不斷延續,幾乎是它無所不包的整體的一個功能。共產黨人興起奪權後,我們清楚體會到他們領導層的意識形態是外來的。而且這個意識形態明白地要求與過去的「封建」社會和文化整體革命性地斷絕。
我們必須附加一項說明。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學習者,在共產黨人還沒勝利之前,就深深地了解到,一些頂尖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大程度上已是林毓生教授所說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信仰者。扼要地說,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有兩項假設:第一,過去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秩序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第二,這個整體必須被棄絕。與林教授一樣,大多數學習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人都對「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支配力感到震驚。他們也深刻地了解,在五四之後的幾十年間,多數在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持續堅守這一態度。他們因此常把共產黨領導人視為五四運動的孩子。
現在,非常清楚地,不論反傳統的傾向有多麼真實而強烈,也不論過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的整合在現實裡是多麼真實,與整體主義式的傳統整體斷裂,這一整齊的辯證性影像,作為一個對於現代中國的複雜歷史的總體描述,是高度不足的。過去幾十年裡的許多筆墨都花費在大幅地修正這一與過去整體斷裂的鮮明影像上。傳統文化的複雜性與其中多樣的分枝已經卓有成效地被探索。現代中國的生活在各層面上與過去的文化之間無意識或無聲息的延續,也被徹底地檢驗了。面對這個相當合理的、矯正性的修正主義,我必須指出,林教授這部細緻而思慮縝密的作品,絕非企圖重新主張原來的想像。他絕非號稱傳統中國在現實裡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由不可分割的各部分所組成的整體。他也絕非企圖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事實上標誌著一個與傳統中國文化――不論它是好是壞――的整體斷裂。其實,他的分析的中心觀點是:深植於中國某些文化傾向的某些態度深度地塑造了反傳統主義者的觀點。
他所申明的是,儘管傳統中國文化有它非凡的多元性,儘管它內部也有相互衝突的不同趨勢,但是文化是整合為一體的概念,社會和文化的所有面向都能以某種方式由政治秩序來控制的概念,以及還有有意識的想法可以決定性地轉化人類生活的概念,在傳統文化裡形成了一個有力而普遍的觀念綜合體。他繼而強調,這些文化習性甚至以許多細緻的方式形塑了那些最堅決反對傳統的人。
我不應在這裡重複林教授精細而微妙的論點。在它的許多的價值之中,我只想指出,它在過度的「修正主義」可能會模糊了問題的焦點時,把我們的注意力再次集中於「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這一20世紀中國的異常現象。林教授對這些修正再清楚不過了。這些修正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他所描述的態度在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扮演了深刻的角色。因此,儘管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過去的文化遺產的態度裡察覺到種種的矛盾情緒和複雜心理,至少在目前它仍然堅守根本棄絕這一官方信條。當然,根據它對馬克思歷史哲學的一元化進化式的詮釋,它能將中國的不良過往算成世上所有高等文明的不良過往的一部分。它已經能夠無保留地讚許過去的物質成就,也能夠對過去的高等和通俗文化的各面向持或多或少的正面態度。但是,它的依據始終是否定了這些文化面向的當下價值的外來的觀念系統。不管人們對馬列主義參考框架強加的限制感到多麼惱怒,也不管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仍繼續被他們的過去所左右,官方意識形態裡「整體主義」的面向並未消失。
當我們將中國的現代思想和政治經驗跟一些其他的非西方文化區域――像是印度和伊斯蘭教世界――的思想和政治經驗進行對比時,林教授所強調的主題的重要性就變得更清楚。當然,就好像現代中國也有著名的「新傳統主義」思想家一樣,那些領域裡也有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並且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我們也知道,在印度和伊斯蘭教世界裡,許多知識分子對印度教跟伊斯蘭教的信奉經常是淺薄和不可靠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些社會裡,知識分子經常慣於辨識像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印度教與民主之間的兼容性,而非兩者之間的尖銳的對立性。在那裡,還沒有任何國家起來允諾對大眾的傳統信仰實行正面攻擊。林教授的分析告訴我們,不管其他因素有什麼影響,對那些文化來說,舊的政治秩序的崩潰並沒有像在中國一樣有著整體主義式的牽連。他的分析更提示了,那些社會裡的知識精英也許不像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他所說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的播送者〕那樣,認為有力量實現他們對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造。
十分難能可貴的是,林教授並沒有簡單地用抽象論理式的命題來表達他的論點。他反而選擇了更困難的途徑:他通過觀察三個中國最著名的「五四」人物――陳獨秀、胡適和魯迅――來證明他的論點。這三個人相互之間有極大的不同,他們的內心世界複雜而充滿矛盾。但林教授相信,儘管他們這麼不同,他們之間卻有一些他所關心的共通的基本傾向。除了他的論點的說服力,他對這三個人物的分析也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他們的新視角。此外,他的論點引導他對中國文化遺產本身提出深刻而有效的質疑。對於理解現代中國,以及思考現代世界裡最困難的一些問題,這本書都做出了思想性和提示性的貢獻。
由於種種機緣,《中國意識的危機》最早是以英文撰寫而成,自1979年英文版在美問世後,先後出現過兩個中譯本。多少年來,筆者始終以一個關懷現代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前途,認同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的心情來討論各項有關的問題,因此這次拙著能夠再次「返回」,與中文和華文世界讀者切磋,內心快慰何似!
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兩種語言的對譯,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中譯英固屬不易,英反中,更是難上加難―尤其當中文是著者的母語時。這次拙著中譯本告成,得眾友生大力襄助,其中楊貞德、丘慧芬費心聯絡,嚴搏非約總其成,在此一併致謝。
翻譯分工如下:〈前言〉郭亞珮譯;第一章〈緒論〉王遠義譯;第二章〈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一)〉正文楊芳燕譯,注釋郭亞珮譯;第三章〈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二)〉第一、二節楊芳燕譯,第三節傅可暢譯;第四章〈陳獨秀之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楊貞德譯;第五章〈胡適的偽改革主義〉楊貞德譯;第六章〈魯迅意識的複雜性〉劉慧娟譯;第七章〈結論〉劉唐芬譯。
前言
班傑明‧史華慈
在19世紀的西方,中國經常被認為是凍結了的傳統主義的最佳典範。到了20世紀中葉,對許多人來說,中國已經變為革命之地――一個與自己過去的文化社會秩序全面而徹底地斷絕了的社會。若是我們反思一下,中國何以是不變傳統的最佳象徵,我們就會感知到,這個看法,跟下列觀感緊密相連:中國設法維繫了一個把社會、文化和政治整合在一起的秩序,這個秩序中的統治階級,致力於體現政治跟精神兩方面的權威。傳統的不斷延續,幾乎是它無所不包的整體的一個功能。共產黨人興起奪權後,我們清楚體會到他們領導層的意識形態是外來的。而且這個意識形態明白地要求與過去的「封建」社會和文化整體革命性地斷絕。
我們必須附加一項說明。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學習者,在共產黨人還沒勝利之前,就深深地了解到,一些頂尖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大程度上已是林毓生教授所說的「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信仰者。扼要地說,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有兩項假設:第一,過去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秩序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第二,這個整體必須被棄絕。與林教授一樣,大多數學習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人都對「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支配力感到震驚。他們也深刻地了解,在五四之後的幾十年間,多數在中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持續堅守這一態度。他們因此常把共產黨領導人視為五四運動的孩子。
現在,非常清楚地,不論反傳統的傾向有多麼真實而強烈,也不論過去的政治文化秩序的整合在現實裡是多麼真實,與整體主義式的傳統整體斷裂,這一整齊的辯證性影像,作為一個對於現代中國的複雜歷史的總體描述,是高度不足的。過去幾十年裡的許多筆墨都花費在大幅地修正這一與過去整體斷裂的鮮明影像上。傳統文化的複雜性與其中多樣的分枝已經卓有成效地被探索。現代中國的生活在各層面上與過去的文化之間無意識或無聲息的延續,也被徹底地檢驗了。面對這個相當合理的、矯正性的修正主義,我必須指出,林教授這部細緻而思慮縝密的作品,絕非企圖重新主張原來的想像。他絕非號稱傳統中國在現實裡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由不可分割的各部分所組成的整體。他也絕非企圖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事實上標誌著一個與傳統中國文化――不論它是好是壞――的整體斷裂。其實,他的分析的中心觀點是:深植於中國某些文化傾向的某些態度深度地塑造了反傳統主義者的觀點。
他所申明的是,儘管傳統中國文化有它非凡的多元性,儘管它內部也有相互衝突的不同趨勢,但是文化是整合為一體的概念,社會和文化的所有面向都能以某種方式由政治秩序來控制的概念,以及還有有意識的想法可以決定性地轉化人類生活的概念,在傳統文化裡形成了一個有力而普遍的觀念綜合體。他繼而強調,這些文化習性甚至以許多細緻的方式形塑了那些最堅決反對傳統的人。
我不應在這裡重複林教授精細而微妙的論點。在它的許多的價值之中,我只想指出,它在過度的「修正主義」可能會模糊了問題的焦點時,把我們的注意力再次集中於「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這一20世紀中國的異常現象。林教授對這些修正再清楚不過了。這些修正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他所描述的態度在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扮演了深刻的角色。因此,儘管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過去的文化遺產的態度裡察覺到種種的矛盾情緒和複雜心理,至少在目前它仍然堅守根本棄絕這一官方信條。當然,根據它對馬克思歷史哲學的一元化進化式的詮釋,它能將中國的不良過往算成世上所有高等文明的不良過往的一部分。它已經能夠無保留地讚許過去的物質成就,也能夠對過去的高等和通俗文化的各面向持或多或少的正面態度。但是,它的依據始終是否定了這些文化面向的當下價值的外來的觀念系統。不管人們對馬列主義參考框架強加的限制感到多麼惱怒,也不管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仍繼續被他們的過去所左右,官方意識形態裡「整體主義」的面向並未消失。
當我們將中國的現代思想和政治經驗跟一些其他的非西方文化區域――像是印度和伊斯蘭教世界――的思想和政治經驗進行對比時,林教授所強調的主題的重要性就變得更清楚。當然,就好像現代中國也有著名的「新傳統主義」思想家一樣,那些領域裡也有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並且未來可能會越來越多。我們也知道,在印度和伊斯蘭教世界裡,許多知識分子對印度教跟伊斯蘭教的信奉經常是淺薄和不可靠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些社會裡,知識分子經常慣於辨識像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印度教與民主之間的兼容性,而非兩者之間的尖銳的對立性。在那裡,還沒有任何國家起來允諾對大眾的傳統信仰實行正面攻擊。林教授的分析告訴我們,不管其他因素有什麼影響,對那些文化來說,舊的政治秩序的崩潰並沒有像在中國一樣有著整體主義式的牽連。他的分析更提示了,那些社會裡的知識精英也許不像中國的優秀知識分子〔他所說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的播送者〕那樣,認為有力量實現他們對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造。
十分難能可貴的是,林教授並沒有簡單地用抽象論理式的命題來表達他的論點。他反而選擇了更困難的途徑:他通過觀察三個中國最著名的「五四」人物――陳獨秀、胡適和魯迅――來證明他的論點。這三個人相互之間有極大的不同,他們的內心世界複雜而充滿矛盾。但林教授相信,儘管他們這麼不同,他們之間卻有一些他所關心的共通的基本傾向。除了他的論點的說服力,他對這三個人物的分析也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他們的新視角。此外,他的論點引導他對中國文化遺產本身提出深刻而有效的質疑。對於理解現代中國,以及思考現代世界裡最困難的一些問題,這本書都做出了思想性和提示性的貢獻。
目次
感謝的話
著者弁言
前言 班傑明.史華慈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一)
第三章 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二)
第四章 陳獨秀之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
第五章 胡適的偽改革主義
第六章 魯迅意識的複雜性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 我研究魯迅的緣起 林毓生 口述;嚴搏非 整理
附錄二 魯迅的「個人主義」
附錄三 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政治觀的困境 陳忠信 譯;林毓生 校訂
著者弁言
前言 班傑明.史華慈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一)
第三章 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之根源(二)
第四章 陳獨秀之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
第五章 胡適的偽改革主義
第六章 魯迅意識的複雜性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 我研究魯迅的緣起 林毓生 口述;嚴搏非 整理
附錄二 魯迅的「個人主義」
附錄三 魯迅思想的特質及其政治觀的困境 陳忠信 譯;林毓生 校訂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緒論
20世紀中國思想史最顯著的、特有的面貌之一,乃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持續和極度的全盤化否定的態度。雖然共產主義革命在改造國家和社會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新秩序與傳統歷史文化遺產間的關係,仍然懸而未決,曖昧不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並不對老中國的傳統採取純屬民族主義式的頌揚,相反地,他們更傾向於根除這些傳統,因為他們不僅視傳統為對當前的威脅,也將其視作實現社會主義未來願景的藩籬。
這種當代文化矛盾的直接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之交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起源的特殊性質,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運動時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識傾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又重新響起了五四時期盛極一時的「文化革命」口號,特別是在1966-1976年間最富戲劇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中,而這個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採取一種嫉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而且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產生,都基於一種共同的內在設想:如果要進行意義深遠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們的價值和精神整體地改變。實現這樣的轉變,便進一步預設著有必要激烈徹底地拒斥中國仍存於今天的過去的舊傳統。
文化革命的思想,在毛澤東的革命心態中長期居於顯著的地位,而且已成為後期毛澤東革命理論的基本成分。我們不能只從政治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文化革命」的意圖,或者只把它視為政治和社會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功能。當然,權力鬥爭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上曾經層出不窮,但它們並不構成產生「文化革命」必然的內在邏輯。而政治與社會革命既非必須依靠「文化革命」才能進行,也不必然會引起「文化革命」。
進一步地說,毛澤東極度強調的「文化革命」,並非來自馬列主義的傳統。無論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如何以唯意志論的解釋來強調人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以及在革命過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些「主觀的」因素終究是被「客觀的」社會經濟的現實所制約的。對照之下,毛澤東則把進行革命和塑造歷史現實(historical reality)的決定性作用,歸諸人的意識。源自這一信念,遂帶來毛澤東主義者將「文化革命」的問題視為首要關切之務。列寧也頗有唯意志論的一面,特別是在強調知識精英應將其優越的「意識」施加在群眾的「自發性」之上時尤為如此。但是,列寧主義者重視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與毛澤東主義者在「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意識因素,僅僅有一種表面的相似性。列寧與毛澤東都曾論述過文化與教育促使落後民族進入社會主義的關鍵性功能;他們也都相信無產階級的意識,不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發地產生。然而,列寧主義者對於此一意識的範圍和聚焦的觀點,反映了專家政治的傾向(technocratic proclivity),此種傾向與毛澤東主義者所強調的要旨,並不相同。雖然他們兩方都認為教育甚為重要,但是列寧主義者所強調的是組織教育、專家教育和政治教育,至於毛澤東主義者所強調的教育(雖然不排斥上述的那些類型),則是向群眾灌輸恰如其分且必要之社會與道德的思想和價值,俾以轉變群眾的心智和精神。
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堅持和強調――伴隨著極力主張作為「文化革命」先決條件的對舊文化的徹底拒斥――事實上是作為馬列主義變體的毛澤東思想的最顯著特徵之一,反映了其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前提的質的分離。雖然探究毛思想中「文化革命」概念的複雜根源,並非本書的主旨,但值得提出的是:根據五四時期知識群體的激進思想來研究毛澤東思想,將可獲致豐富的成果,因為這種激進思想對毛澤東在求學時期的知性生活曾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鑒於文化反傳統主義(cultural iconoclasm)是一股貫穿直至70年代的強大的潮流―這股潮流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現在他對「文化革命」必要性的極度重視―所以,充分理解五四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意義,無論如何地強調都不為過。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激進五四運動,在後傳統中國歷史上(in post-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是個轉折點。就這個反傳統主義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它在現代世界史上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反叛運動顯現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意識中文化認同的深刻危機;它也是後來文化和知識發展的預兆。以後數十年中,文化反傳統主義的各種表現,都是以五四時期的反傳統主義為出發點的;的確,甚至後來出現的許多保守思想和意識形態,在不同程度上,也表現出五四時代反傳統主義對它們的影響。
基本上,本書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起源和性質的研究。這種反傳統主義如此激烈,以至於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稱作全盤化的(totalistic)。就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和文化變遷而言,這種反傳統主義要求徹底摧毀過去的一切,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種空前的歷史現象。誠然,在社會與歷史發生根本變遷的時期,反傳統的衝動經常地出現。新規範、價值的理解與支配,使得許多傳統上視為理所當然的準則和慣例變得格格不入和難以容忍,人們因此常會要求將它們摧毀。但是,傳統的「摧毀」具有許多種類,反傳統主義的類型亦見繁多。人們可以抨擊所覺察出的傳統中有害的部分,而不必然要全盤地(in toto)譴責過去。根除某一傳統中不合時宜或有害的成分,通常不一定含有完全否定文化遺產的意思。如果某一傳統內的轉變潛力是巨大的,那麼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該傳統的某些符號和價值,還可經由重塑和轉化,提供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還可以在變遷的過程中保留文化認同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在建設出可實施運行的現代社會時,從傳統汲取出的文化成分,可以扮演著促進更勝於損害的角色功能。因此,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雖然有些時候,某些個人或群體相信過去的一切既無用處也無價值,但在其他社會的歷史中,卻從未出現過像中國五四時期那樣的持續如此之久、歷史影響如此深遠的全盤化反傳統主義。因此,研究五四時期在中國產生的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根源和性質,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項頗具挑戰的工作。如果要了解當前的中國歷史,充分考慮這一特殊的歷史經驗也是極為重要的。
為了闡明五四時期反傳統運動中知識分子思想的多樣性,在力求避免對這些反傳統主義者的研究中的膚淺與重複,本書同時對五四時期知識界三位最著名的領導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反傳統意識的根源和性質,採取比較的方式來研究。這三位人物在五四早期都具有相同的反傳統主義傾向,同時他們也參與了《新青年》雜誌所發起的反傳統運動。然而他們三人的反傳統思想的特質有許多深切不同之處,正如他們性格上與政治傾向上有顯著差異。我希望通過對這三人思想的比較來闡明五四反傳統主義中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在分析陳獨秀、胡適和魯迅這三人的思想發展與他們的主要觀念的工作中,我將不受通常把1915-1927年作為五四時期這種頗為武斷的、機械的時間劃分所限。以這三人為先驅的反傳統運動,在五四時代早期(1915-1919)和中期(1919-1923)達到了高峰;但在此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中,魯迅所發表的著作,仍然持續顯現出全盤化反傳統主義的衝動。胡適在五四時期雖曾參與全面抨擊中國傳統的活動,但直到1934年才清楚地解釋他的論點。然而,他嗣後的反傳統著作,根本上沒有脫離早期全盤化反傳統思想的根本主題;儘管他的這些著作在時間上已邁過了五四時期,但我仍將它們列入討論分析之中。
因為本書的目的不是撰寫一部知識分子的總體傳記,所以我僅提供相關的、為數有限的傳記性資料。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陳獨秀、胡適和魯迅所普遍關懷的問題和反傳統思想上。我之所以選擇他們作為研究對象,部分原因是他們三人係大家公認的五四領袖人物,部分原因是他們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方面有顯著的差異。陳獨秀終究蛻變成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領導人;他被公認具有強烈的道德熱情;富有戰鬥氣質和大無畏的個人主義精神。他堅強有餘而精細不足,因而對社會和文化問題所涉及的精微而曲折的含義或複雜情況,顯現不十分關心。胡適則不然,他是杜威式的自由主義者,後來轉變成一位對國民黨具有矛盾心理的支持者。他圓通自滿,溫文儒雅,偶爾虛榮自負。胡適心思機敏,文字文風表達出一種淺顯的明暢,但他從未能涉入較難層次的社會、文化問題,也未曾能深刻地探索他所關懷的問題。對照之下,魯迅則是一位非凡而繁複的人物,具有一顆機智、敏銳、精緻而富有創造力的心靈。他以冷嘲的幽默與辛辣的諷刺著稱。外表上他疏遠、冷漠,內心中則悲憤、沉鬱;但他有一種誠摯的關懷和道德的熱情,這使他得以用異乎尋常的雄辯來表達中國文化危機的極度痛苦。魯迅晚年在政治上非常同情共產黨人,但迴避形式上的黨紀束縛和堅硬的意識形態信諾。
我們將看到,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傾向方面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反傳統主義的特質。但他們共同得出了一個相同的基本結論:以全盤拒斥中國的過去為要求的思想和文化革命,正是現代社會和政治變遷的基本前提。因此,「理解五四反傳統主義的全盤化性質」這一問題,是無法從心理學的、政治學的或社會學的概括來加以解釋的。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必須根據20世紀中國社會和思想的變化及其連續性――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辯證脈絡之中――進行考察;這種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正是我們首先應予以探討的。
20世紀中國思想史最顯著的、特有的面貌之一,乃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進行持續和極度的全盤化否定的態度。雖然共產主義革命在改造國家和社會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新秩序與傳統歷史文化遺產間的關係,仍然懸而未決,曖昧不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並不對老中國的傳統採取純屬民族主義式的頌揚,相反地,他們更傾向於根除這些傳統,因為他們不僅視傳統為對當前的威脅,也將其視作實現社會主義未來願景的藩籬。
這種當代文化矛盾的直接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之交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起源的特殊性質,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運動時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識傾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中,又重新響起了五四時期盛極一時的「文化革命」口號,特別是在1966-1976年間最富戲劇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中,而這個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採取一種嫉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而且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產生,都基於一種共同的內在設想:如果要進行意義深遠的政治和社會變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們的價值和精神整體地改變。實現這樣的轉變,便進一步預設著有必要激烈徹底地拒斥中國仍存於今天的過去的舊傳統。
文化革命的思想,在毛澤東的革命心態中長期居於顯著的地位,而且已成為後期毛澤東革命理論的基本成分。我們不能只從政治權力鬥爭的角度來理解毛澤東「文化革命」的意圖,或者只把它視為政治和社會革命過程中的一種功能。當然,權力鬥爭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上曾經層出不窮,但它們並不構成產生「文化革命」必然的內在邏輯。而政治與社會革命既非必須依靠「文化革命」才能進行,也不必然會引起「文化革命」。
進一步地說,毛澤東極度強調的「文化革命」,並非來自馬列主義的傳統。無論原本的馬克思主義如何以唯意志論的解釋來強調人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以及在革命過程中改造人性的重要性,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些「主觀的」因素終究是被「客觀的」社會經濟的現實所制約的。對照之下,毛澤東則把進行革命和塑造歷史現實(historical reality)的決定性作用,歸諸人的意識。源自這一信念,遂帶來毛澤東主義者將「文化革命」的問題視為首要關切之務。列寧也頗有唯意志論的一面,特別是在強調知識精英應將其優越的「意識」施加在群眾的「自發性」之上時尤為如此。但是,列寧主義者重視的意識在歷史上的作用,與毛澤東主義者在「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意識因素,僅僅有一種表面的相似性。列寧與毛澤東都曾論述過文化與教育促使落後民族進入社會主義的關鍵性功能;他們也都相信無產階級的意識,不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自發地產生。然而,列寧主義者對於此一意識的範圍和聚焦的觀點,反映了專家政治的傾向(technocratic proclivity),此種傾向與毛澤東主義者所強調的要旨,並不相同。雖然他們兩方都認為教育甚為重要,但是列寧主義者所強調的是組織教育、專家教育和政治教育,至於毛澤東主義者所強調的教育(雖然不排斥上述的那些類型),則是向群眾灌輸恰如其分且必要之社會與道德的思想和價值,俾以轉變群眾的心智和精神。
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堅持和強調――伴隨著極力主張作為「文化革命」先決條件的對舊文化的徹底拒斥――事實上是作為馬列主義變體的毛澤東思想的最顯著特徵之一,反映了其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前提的質的分離。雖然探究毛思想中「文化革命」概念的複雜根源,並非本書的主旨,但值得提出的是:根據五四時期知識群體的激進思想來研究毛澤東思想,將可獲致豐富的成果,因為這種激進思想對毛澤東在求學時期的知性生活曾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鑒於文化反傳統主義(cultural iconoclasm)是一股貫穿直至70年代的強大的潮流―這股潮流在毛澤東思想中表現在他對「文化革命」必要性的極度重視―所以,充分理解五四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意義,無論如何地強調都不為過。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激進五四運動,在後傳統中國歷史上(in post-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是個轉折點。就這個反傳統主義的深度和廣度而言,它在現代世界史上很可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反叛運動顯現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意識中文化認同的深刻危機;它也是後來文化和知識發展的預兆。以後數十年中,文化反傳統主義的各種表現,都是以五四時期的反傳統主義為出發點的;的確,甚至後來出現的許多保守思想和意識形態,在不同程度上,也表現出五四時代反傳統主義對它們的影響。
基本上,本書是對五四時期反傳統主義的起源和性質的研究。這種反傳統主義如此激烈,以至於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稱作全盤化的(totalistic)。就我們所了解的社會和文化變遷而言,這種反傳統主義要求徹底摧毀過去的一切,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種空前的歷史現象。誠然,在社會與歷史發生根本變遷的時期,反傳統的衝動經常地出現。新規範、價值的理解與支配,使得許多傳統上視為理所當然的準則和慣例變得格格不入和難以容忍,人們因此常會要求將它們摧毀。但是,傳統的「摧毀」具有許多種類,反傳統主義的類型亦見繁多。人們可以抨擊所覺察出的傳統中有害的部分,而不必然要全盤地(in toto)譴責過去。根除某一傳統中不合時宜或有害的成分,通常不一定含有完全否定文化遺產的意思。如果某一傳統內的轉變潛力是巨大的,那麼在有利的歷史條件下,該傳統的某些符號和價值,還可經由重塑和轉化,提供有利於變遷的「種子」,同時還可以在變遷的過程中保留文化認同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在建設出可實施運行的現代社會時,從傳統汲取出的文化成分,可以扮演著促進更勝於損害的角色功能。因此,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並不必然根生於現代化過程之中或力爭現代性之際。雖然有些時候,某些個人或群體相信過去的一切既無用處也無價值,但在其他社會的歷史中,卻從未出現過像中國五四時期那樣的持續如此之久、歷史影響如此深遠的全盤化反傳統主義。因此,研究五四時期在中國產生的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根源和性質,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項頗具挑戰的工作。如果要了解當前的中國歷史,充分考慮這一特殊的歷史經驗也是極為重要的。
為了闡明五四時期反傳統運動中知識分子思想的多樣性,在力求避免對這些反傳統主義者的研究中的膚淺與重複,本書同時對五四時期知識界三位最著名的領導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的反傳統意識的根源和性質,採取比較的方式來研究。這三位人物在五四早期都具有相同的反傳統主義傾向,同時他們也參與了《新青年》雜誌所發起的反傳統運動。然而他們三人的反傳統思想的特質有許多深切不同之處,正如他們性格上與政治傾向上有顯著差異。我希望通過對這三人思想的比較來闡明五四反傳統主義中的統一性與多樣性。
在分析陳獨秀、胡適和魯迅這三人的思想發展與他們的主要觀念的工作中,我將不受通常把1915-1927年作為五四時期這種頗為武斷的、機械的時間劃分所限。以這三人為先驅的反傳統運動,在五四時代早期(1915-1919)和中期(1919-1923)達到了高峰;但在此以後相當長的時間中,魯迅所發表的著作,仍然持續顯現出全盤化反傳統主義的衝動。胡適在五四時期雖曾參與全面抨擊中國傳統的活動,但直到1934年才清楚地解釋他的論點。然而,他嗣後的反傳統著作,根本上沒有脫離早期全盤化反傳統思想的根本主題;儘管他的這些著作在時間上已邁過了五四時期,但我仍將它們列入討論分析之中。
因為本書的目的不是撰寫一部知識分子的總體傳記,所以我僅提供相關的、為數有限的傳記性資料。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陳獨秀、胡適和魯迅所普遍關懷的問題和反傳統思想上。我之所以選擇他們作為研究對象,部分原因是他們三人係大家公認的五四領袖人物,部分原因是他們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方面有顯著的差異。陳獨秀終究蛻變成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並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領導人;他被公認具有強烈的道德熱情;富有戰鬥氣質和大無畏的個人主義精神。他堅強有餘而精細不足,因而對社會和文化問題所涉及的精微而曲折的含義或複雜情況,顯現不十分關心。胡適則不然,他是杜威式的自由主義者,後來轉變成一位對國民黨具有矛盾心理的支持者。他圓通自滿,溫文儒雅,偶爾虛榮自負。胡適心思機敏,文字文風表達出一種淺顯的明暢,但他從未能涉入較難層次的社會、文化問題,也未曾能深刻地探索他所關懷的問題。對照之下,魯迅則是一位非凡而繁複的人物,具有一顆機智、敏銳、精緻而富有創造力的心靈。他以冷嘲的幽默與辛辣的諷刺著稱。外表上他疏遠、冷漠,內心中則悲憤、沉鬱;但他有一種誠摯的關懷和道德的熱情,這使他得以用異乎尋常的雄辯來表達中國文化危機的極度痛苦。魯迅晚年在政治上非常同情共產黨人,但迴避形式上的黨紀束縛和堅硬的意識形態信諾。
我們將看到,這三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傾向方面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反傳統主義的特質。但他們共同得出了一個相同的基本結論:以全盤拒斥中國的過去為要求的思想和文化革命,正是現代社會和政治變遷的基本前提。因此,「理解五四反傳統主義的全盤化性質」這一問題,是無法從心理學的、政治學的或社會學的概括來加以解釋的。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必須根據20世紀中國社會和思想的變化及其連續性――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辯證脈絡之中――進行考察;這種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正是我們首先應予以探討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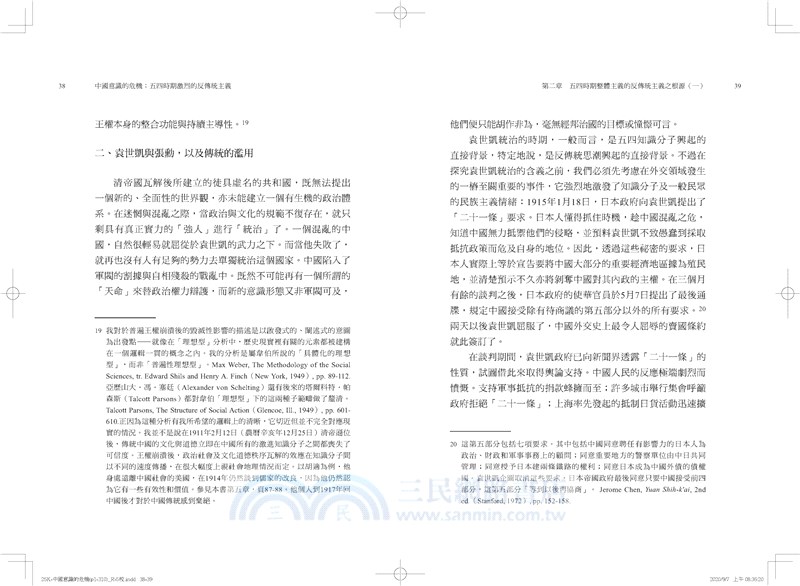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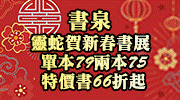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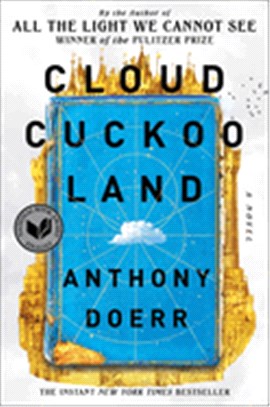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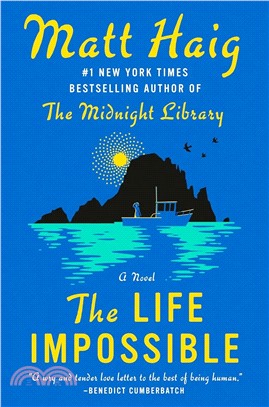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