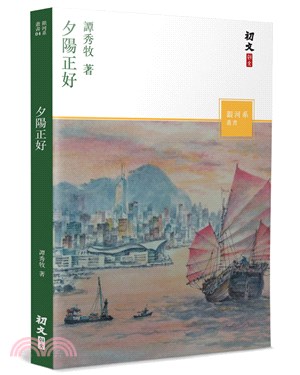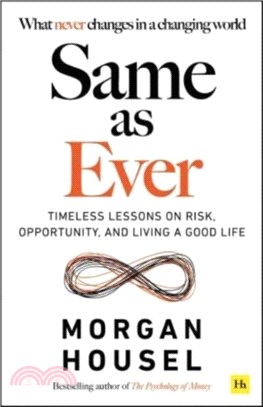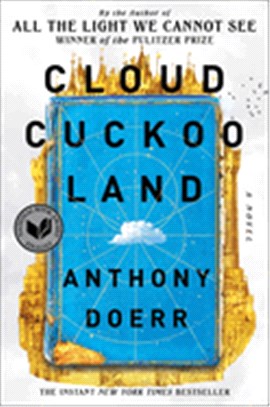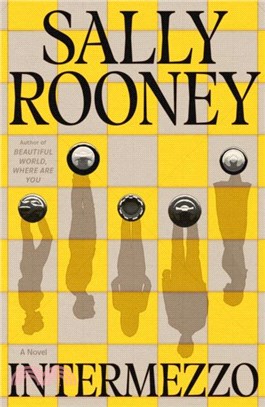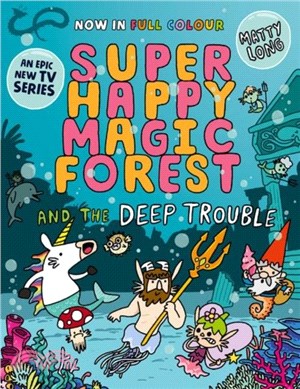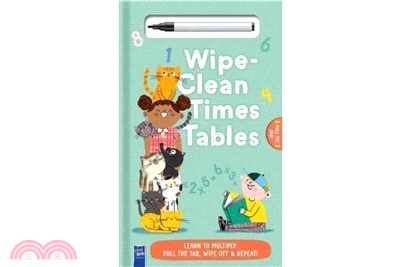夕陽正好
商品資訊
定價
:NT$ 270 元優惠價
:90 折 243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7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收錄作家譚秀牧五十多年來的短篇小說創作。書中大部份的小說曾刊登於不同的書刊雜誌,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
收錄的作品按作者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收錄創作均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
書中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收錄的作品按作者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收錄創作均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
書中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作者簡介
譚秀牧
原籍廣東省開平縣。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生。一九四七年移居香港。
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一九五六年起,先後曾擔任出版社及報紙編輯多年。一九六一年主編《南洋文藝》月刊。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三年任華僑日報文化版編輯,以及《香港年鑑》主編。
已出版作品有小說集《明朗的早晨》、《寂寞的山村》、《阿嬌和她的同伴》,長篇小說《金色的旅程》、《譚秀牧散文/小說選集》。另外著有《兒童畫教學》。
原籍廣東省開平縣。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生。一九四七年移居香港。
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寫作。一九五六年起,先後曾擔任出版社及報紙編輯多年。一九六一年主編《南洋文藝》月刊。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三年任華僑日報文化版編輯,以及《香港年鑑》主編。
已出版作品有小說集《明朗的早晨》、《寂寞的山村》、《阿嬌和她的同伴》,長篇小說《金色的旅程》、《譚秀牧散文/小說選集》。另外著有《兒童畫教學》。
序
捱出來的故事
本書選錄譚秀牧多年來的小說創作,大部份都曾收錄於不同的單行本,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收錄的作品大致按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長篇創作只好割愛,内容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從時間的跨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差不多經歷五十年,如此長期堅持實屬難得。這些作品,作者坦言都是趁工餘時間,在深夜,一點一滴的「捱」出來。而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從人物折射歷史
譚秀牧善於捕捉當時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片段,經過綜合、提煉、虛構,塑造一個又一個在窮苦生活下默默耕耘的人物。例如寫於五十年代的兩篇短篇〈夜工〉與〈母女倆〉均是以當年普遍的童工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創造出冒認成年去工廠上夜班的金華以及幫補家計到街市擺攤叫賣臭丸的小蘭。〈同情〉則寫因母親賣菜「阻街」被警察抓去,被逼一個人「揹著一個破舊的麻包,右手拿著鐵鉤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一邊走,一邊往四下裏窺望;發現路旁有垃圾堆,就走近前去用鐵鉤撥弄幾下,彎下腰去,看看有可換錢的破爛的東西沒有」的小牛。以上三篇的主角都是孩子,在故事裏,他們面對或大或小的挫折,但仍然堅忍地活下去。
至於〈艇家之子〉,雖然都是孩子,但作者則將重心轉移至側面描寫一個艇家之子,母親早逝,在父親的教導下,如何早熟。小小年紀的孩子已經熟練划船、游泳這些海上生活的技能,而當敍事者想將打破了的杯子丟進海裏的時候,他立即如此反應:
「給我,給我,不要丟掉!」
我以為他留下來,準備賣給收買爛玻璃的人,便毫不猶疑的給他。他接了,輕捷地跳上岸,爬過那塊高大的岩石,走到山邊去。我望著他,真有些疑惑不解。
一會兒,他回到艇上來了,望望他的手,卻空著。
「你拿到哪兒去啦!」我詫異地問。他指一指荆棘叢生的山坡,映眨著小眼說:
「丟了。」
「丟在海裏,不是很便當嗎?」 「我們常在這裏捉魚,它會割傷我們的腳哩!」他拉一拉幾乎跌下來的褲子,揩了把鼻涕說。
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原來他指的「我們」,不只是他父親,而是這個漁村裏所有的漁民;同時也包括了在這附近捉小魚的泳客們。這麼一想,我馬上疚愧起來了。
「我」的愚昧舉措反襯孩子對海的愛護、對處理垃圾後果的睿智。如果說在那個艱苦的五十年代,前述三篇的孩子是「勇」的例子,則〈艇家之子〉的主角就是既「勇」且「智」的代表了。
〈樓上人家〉寫那對被遺漏在家的子女,每晚吵鬧至深夜,弄得樓下的羅生羅太睡不得安寧,羅太經過明查暗訪之後發現他們本性不壞,不過是因沒有家人照料,缺乏關懷與愛護,才會「玩超人之類的粗野遊戲」。雖然這家孩子的父母有些與別不同,但在香港確實有不少家庭也因父母外出工作,導致子女獨留在家,而不少因此而生的安全問題至今亦時有所聞。
從際遇反映社會
雖然譚秀牧的小說沒有炫目的技巧,亮麗的形式,但是卻善於製造或大或小的衝突與挫折,讓讀者體會身處其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如何在逆境中應對。〈夜工〉的金華上夜班卻突然患上感冒,在這個時候,領班看見他工作遲緩的樣子,被「領班高舉起來的拳頭,已隨著叫罵聲而閃電似的朝金華的腿上使勁打下去了。」金華的工友們都紛紛予以同情關懷,例如陳發就把他拉起來,責問打人的領班,護送金華回家,更好心以謊言:「工友們因為他年紀最小,便叫他早些回來休息。你讓他好好休息兩天再算吧!明天是糧期了,明早你拿他的工咭到廠裏來出糧好啦!」安慰金華的母親,減輕她的不安與疑慮。〈惡人禮讚〉更以幽默反諷的筆法,敍述「惡人」高洛在面對大廈的惡狗、住客的惡鄰居、街外來的惡匪徒,如何以棋高一著的「惡行」克服難關,最後更獲政府頒發好市民獎。閲畢本篇,更讓人發覺原來要做一個「好人」,倒要像高洛那樣夠「惡」才行,字裏行間充滿令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至於〈同道中人〉,透過「我」這個敍述者,刻劃福哥的形象。福哥是一個捉蟋蟀的專家,他對捉蟋蟀熱點的地理環境與人情風貌都非常熟悉:
「還要走多遠?」我問。
……
「本來,去雞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為甚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卻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為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雞冠山雖然近,但是容易被人誤會為盜墓賊,於是這次捉蟋蟀就另找地點。稍後,到了目的地,「我」捉蟋蟀是:「我開始試著,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為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甚麼地方去了。」笨拙異常;至於福哥:「彎著腰,腳步輕得恍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著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強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著觸鬚,茫然地打著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身手輕快敏捷,兩人表現的巨大差別就進一步烘托出福哥手藝的精湛。而福哥更通曉蟋蟀的習性: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著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為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蜂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這種知識,不可能單純從書本上學習而來,而是福哥透過多年捉蟋蟀經歷多番險境的經驗之談。
從幽默諷刺現實
〈惡人禮讚〉以幽默的筆法描繪一個「惡人」如何「以惡治惡」,從而突出平日我們這些「好人」如何受到社會的不公對待,卻敢怒不敢言。高洛的出現,正正是做了我們日常生活想做卻不敢做的言行,反抗社會的一切不義。〈火辣辣的夏夜〉以之前喜歡打尖插隊的牛頸榮遇上剛剛出獄的崩耳才作為故事的主綫,故事從外形、語言、行為三方面詳細描繪了崩耳才的形象:
外形:「說話的人約廿七、八歲。瘦削身材,方臉,左邊的耳朵缺了半片。他穿著長袖波恤,衫腳捲到肚皮上。」
語言:「老友,你拿不拿到後面去?」、「老友,放開我的手!」、「面子是你自己掉的,怨得誰?」、「我才坐了兩年花廳,絕不介意多坐幾年!」
行為:「崩耳才一手支著臉頰,另一隻手捏著香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他瞟牛頸榮一眼,接著,快速地把手掌一轉,反過來把牛頸榮的手一搭,一撥;牛頸榮像觸了電,他的手給彈到櫃枱邊,撞在圍板上。」
崩耳才冷酷,坐過牢,說話簡單直接,身手功夫更遠在牛頸榮之上,是真正的「有料之人」。至於牛頸榮僅僅是外貌比較攝人,卻沒有真材實料,過招片刻就已經高下立見。因此,故事描述牛頸榮在不知道崩耳才底細之前,還咄咄逼人,要找人算賬,自然就讓讀者啼笑皆非!
而譚氏這種營造幽默的藝術形式,更普遍見於他的極短篇創作。例如〈夕陽正好〉裏,潘伯退休之後,無所事事,卻被子女輪番勸說:
素蘭想起有位同學,在鄰邨的社區中心任職。對爸爸提議:「阿爸,隔鄰邨社區中心有個明光耆老小組,時常有節目,如老人旅行、老人象棋賽、耆英健康舞……不如我替你拿張表格,申請入會,參加活動吧……。」
這時,漢良忽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阿爸,街坊會禮拜六,舉辦新春敬老百歲宴,吃齋又有抽獎,我買兩張餐券,你與阿媽……」
身體仍然健壯,卻被家人以為已經風燭殘年,不斷「老人」前、「老人」後,潘伯自然覺得討厭,難怪他要再重出江湖,另找新工,開始新生活了。
至於〈劫匪奇遇記〉以異性同名的偶然事故,最終導致劫匪被捕;〈誘惑〉以王愛琴自由自在吃乳鴿勸喻朋友不要盲目迷信崇拜表裏不一的偶像;〈聖誕奇遇拆良緣〉以新郎巧遇内地來港的表嫂一番話,捅破一樁騙人的「良緣」,原來大家眼中單身的老好人一早在内地已經結婚生子,卻還厚顔在香港結識異性重婚;〈巨獎的誘惑〉以爸爸投入十萬資金買六合彩,但僅僅換來彩金十萬零一百元,說明靠博彩發達的虛妄……以上都可見作者在各個極短篇的精巧構思。
結語:香港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
在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引入外國多種多樣的文學思潮與理論,此起彼伏。當中,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更曾成為不少香港作家實驗的寫作綱領。不過,在前衛寫作之外,同時期的香港仍有不少以傳統現實主義筆法筆耕的作家。譚秀牧的作品透視社會階層之深之廣,與同時代的作家比較,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看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傳統小說出色的形象、對話、動作描寫之外,更有獨特的幽默感,日後研究者如要重寫香港小說史,譚秀牧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
黎漢傑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本書選錄譚秀牧多年來的小說創作,大部份都曾收錄於不同的單行本,僅本書最後兩篇:〈沒有休止符的哀歌〉與〈阿爸風生水起記〉未曾結集,原刊於千禧年出版的《鑪峰文藝》。收錄的作品大致按寫作與公開發表日期順序編列,限於篇幅,長篇創作只好割愛,内容以短篇為主,輔以字數比較精簡的中篇。從時間的跨度來看,作者的創作差不多經歷五十年,如此長期堅持實屬難得。這些作品,作者坦言都是趁工餘時間,在深夜,一點一滴的「捱」出來。而小說所構造的世界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底下階層的人物,他們在愛情、工作、生活等方面,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糾紛、掙扎,讀者可以從中看到在血與汗之下,一幕幕捱出來的故事。
從人物折射歷史
譚秀牧善於捕捉當時當地低下階層的生活片段,經過綜合、提煉、虛構,塑造一個又一個在窮苦生活下默默耕耘的人物。例如寫於五十年代的兩篇短篇〈夜工〉與〈母女倆〉均是以當年普遍的童工問題作為寫作的題材,創造出冒認成年去工廠上夜班的金華以及幫補家計到街市擺攤叫賣臭丸的小蘭。〈同情〉則寫因母親賣菜「阻街」被警察抓去,被逼一個人「揹著一個破舊的麻包,右手拿著鐵鉤子,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著。一邊走,一邊往四下裏窺望;發現路旁有垃圾堆,就走近前去用鐵鉤撥弄幾下,彎下腰去,看看有可換錢的破爛的東西沒有」的小牛。以上三篇的主角都是孩子,在故事裏,他們面對或大或小的挫折,但仍然堅忍地活下去。
至於〈艇家之子〉,雖然都是孩子,但作者則將重心轉移至側面描寫一個艇家之子,母親早逝,在父親的教導下,如何早熟。小小年紀的孩子已經熟練划船、游泳這些海上生活的技能,而當敍事者想將打破了的杯子丟進海裏的時候,他立即如此反應:
「給我,給我,不要丟掉!」
我以為他留下來,準備賣給收買爛玻璃的人,便毫不猶疑的給他。他接了,輕捷地跳上岸,爬過那塊高大的岩石,走到山邊去。我望著他,真有些疑惑不解。
一會兒,他回到艇上來了,望望他的手,卻空著。
「你拿到哪兒去啦!」我詫異地問。他指一指荆棘叢生的山坡,映眨著小眼說:
「丟了。」
「丟在海裏,不是很便當嗎?」 「我們常在這裏捉魚,它會割傷我們的腳哩!」他拉一拉幾乎跌下來的褲子,揩了把鼻涕說。
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過來,原來他指的「我們」,不只是他父親,而是這個漁村裏所有的漁民;同時也包括了在這附近捉小魚的泳客們。這麼一想,我馬上疚愧起來了。
「我」的愚昧舉措反襯孩子對海的愛護、對處理垃圾後果的睿智。如果說在那個艱苦的五十年代,前述三篇的孩子是「勇」的例子,則〈艇家之子〉的主角就是既「勇」且「智」的代表了。
〈樓上人家〉寫那對被遺漏在家的子女,每晚吵鬧至深夜,弄得樓下的羅生羅太睡不得安寧,羅太經過明查暗訪之後發現他們本性不壞,不過是因沒有家人照料,缺乏關懷與愛護,才會「玩超人之類的粗野遊戲」。雖然這家孩子的父母有些與別不同,但在香港確實有不少家庭也因父母外出工作,導致子女獨留在家,而不少因此而生的安全問題至今亦時有所聞。
從際遇反映社會
雖然譚秀牧的小說沒有炫目的技巧,亮麗的形式,但是卻善於製造或大或小的衝突與挫折,讓讀者體會身處其中的主角以及他們的夥伴們如何在逆境中應對。〈夜工〉的金華上夜班卻突然患上感冒,在這個時候,領班看見他工作遲緩的樣子,被「領班高舉起來的拳頭,已隨著叫罵聲而閃電似的朝金華的腿上使勁打下去了。」金華的工友們都紛紛予以同情關懷,例如陳發就把他拉起來,責問打人的領班,護送金華回家,更好心以謊言:「工友們因為他年紀最小,便叫他早些回來休息。你讓他好好休息兩天再算吧!明天是糧期了,明早你拿他的工咭到廠裏來出糧好啦!」安慰金華的母親,減輕她的不安與疑慮。〈惡人禮讚〉更以幽默反諷的筆法,敍述「惡人」高洛在面對大廈的惡狗、住客的惡鄰居、街外來的惡匪徒,如何以棋高一著的「惡行」克服難關,最後更獲政府頒發好市民獎。閲畢本篇,更讓人發覺原來要做一個「好人」,倒要像高洛那樣夠「惡」才行,字裏行間充滿令人無奈的黑色幽默。
至於〈同道中人〉,透過「我」這個敍述者,刻劃福哥的形象。福哥是一個捉蟋蟀的專家,他對捉蟋蟀熱點的地理環境與人情風貌都非常熟悉:
「還要走多遠?」我問。
……
「本來,去雞冠山,半個鐘頭就可到達了。」福哥說,煙火在嘴角閃亮一下。「不過,今晚,我們不要到那邊去了,――」
「為甚麼?你前幾天不是說,那裏的蟋蟀多,又夠狠的麼?」
「今天早上,聽捉草蜢的王伯說,那裏近月來,時常有盜墳賊打劫陰司路,所以鄉民和當局都巡得緊。」福哥的聲音有些沙滯,但卻夠響亮。他燃起一根香煙,然後說「為免誤會,還是避開好些。你或許不知道,給鄉下佬碰到了,把你打個半死,才再講道理!」
雞冠山雖然近,但是容易被人誤會為盜墓賊,於是這次捉蟋蟀就另找地點。稍後,到了目的地,「我」捉蟋蟀是:「我開始試著,前後左右都是吱咧咧,牠們似在大合唱,無法從混成一片的音響中分別出其個體的所在。只好自以為是地,不停開亮電筒尋找,偶然發現一隻,但牠那麼精靈地,兩三下子就不知跳到甚麼地方去了。」笨拙異常;至於福哥:「彎著腰,腳步輕得恍似駕風而行,毫無聲息。一邊細聽著蟀鳴。聽準了聲音,知道了蟀兒的所在,突然開亮電筒照射;蟀兒給突如其來的強光弄得頭昏目眩,舞動著觸鬚,茫然地打著轉,福哥拱起手指的手掌像輕巧的罩子,蓋下去,就把牠捉住了。」身手輕快敏捷,兩人表現的巨大差別就進一步烘托出福哥手藝的精湛。而福哥更通曉蟋蟀的習性:
「福哥,剛才蟋蟀忽然不叫,究竟將有甚麼事情發生?」想起剛才的情景,不禁帶著餘悸問道。
「這是動物界的自衛現象,」福哥解釋道:「蟋蟀多的地方,蛇必多;因為蟋蟀是蛇的點心。凡是蟋蟀忽然停止鳴叫,必是蛇已出來活動;蜂兒聞到氣味,鑽回土洞去躲避,於是便沒了聲音了。」
這種知識,不可能單純從書本上學習而來,而是福哥透過多年捉蟋蟀經歷多番險境的經驗之談。
從幽默諷刺現實
〈惡人禮讚〉以幽默的筆法描繪一個「惡人」如何「以惡治惡」,從而突出平日我們這些「好人」如何受到社會的不公對待,卻敢怒不敢言。高洛的出現,正正是做了我們日常生活想做卻不敢做的言行,反抗社會的一切不義。〈火辣辣的夏夜〉以之前喜歡打尖插隊的牛頸榮遇上剛剛出獄的崩耳才作為故事的主綫,故事從外形、語言、行為三方面詳細描繪了崩耳才的形象:
外形:「說話的人約廿七、八歲。瘦削身材,方臉,左邊的耳朵缺了半片。他穿著長袖波恤,衫腳捲到肚皮上。」
語言:「老友,你拿不拿到後面去?」、「老友,放開我的手!」、「面子是你自己掉的,怨得誰?」、「我才坐了兩年花廳,絕不介意多坐幾年!」
行為:「崩耳才一手支著臉頰,另一隻手捏著香煙,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他瞟牛頸榮一眼,接著,快速地把手掌一轉,反過來把牛頸榮的手一搭,一撥;牛頸榮像觸了電,他的手給彈到櫃枱邊,撞在圍板上。」
崩耳才冷酷,坐過牢,說話簡單直接,身手功夫更遠在牛頸榮之上,是真正的「有料之人」。至於牛頸榮僅僅是外貌比較攝人,卻沒有真材實料,過招片刻就已經高下立見。因此,故事描述牛頸榮在不知道崩耳才底細之前,還咄咄逼人,要找人算賬,自然就讓讀者啼笑皆非!
而譚氏這種營造幽默的藝術形式,更普遍見於他的極短篇創作。例如〈夕陽正好〉裏,潘伯退休之後,無所事事,卻被子女輪番勸說:
素蘭想起有位同學,在鄰邨的社區中心任職。對爸爸提議:「阿爸,隔鄰邨社區中心有個明光耆老小組,時常有節目,如老人旅行、老人象棋賽、耆英健康舞……不如我替你拿張表格,申請入會,參加活動吧……。」
這時,漢良忽然想起一件事,插嘴道:「阿爸,街坊會禮拜六,舉辦新春敬老百歲宴,吃齋又有抽獎,我買兩張餐券,你與阿媽……」
身體仍然健壯,卻被家人以為已經風燭殘年,不斷「老人」前、「老人」後,潘伯自然覺得討厭,難怪他要再重出江湖,另找新工,開始新生活了。
至於〈劫匪奇遇記〉以異性同名的偶然事故,最終導致劫匪被捕;〈誘惑〉以王愛琴自由自在吃乳鴿勸喻朋友不要盲目迷信崇拜表裏不一的偶像;〈聖誕奇遇拆良緣〉以新郎巧遇内地來港的表嫂一番話,捅破一樁騙人的「良緣」,原來大家眼中單身的老好人一早在内地已經結婚生子,卻還厚顔在香港結識異性重婚;〈巨獎的誘惑〉以爸爸投入十萬資金買六合彩,但僅僅換來彩金十萬零一百元,說明靠博彩發達的虛妄……以上都可見作者在各個極短篇的精巧構思。
結語:香港的現實主義小說寫作
在六十年代以還,香港引入外國多種多樣的文學思潮與理論,此起彼伏。當中,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更曾成為不少香港作家實驗的寫作綱領。不過,在前衛寫作之外,同時期的香港仍有不少以傳統現實主義筆法筆耕的作家。譚秀牧的作品透視社會階層之深之廣,與同時代的作家比較,均有過之而無不及。觀看他的作品,除了繼承傳統小說出色的形象、對話、動作描寫之外,更有獨特的幽默感,日後研究者如要重寫香港小說史,譚秀牧必然是一個不能繞過的名字。
黎漢傑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目次
目錄
捱出來的故事 黎漢傑
同情
夜工
阿嬌和她的同伴
寂寞的山村
樓上人家
阿誠的畫家夢
謀殺進行曲
搭枱客
惡人禮讚
同道中人
豆皮婆試劍
火辣辣的夏夜
夕陽正好
怪茶客
劫匪奇遇記
誘惑
等待占美
聖誕奇遇拆良緣
巨獎的誘惑
本色
神遊世界
没有休止符的哀歌
阿爸風生水起記
後記
捱出來的故事 黎漢傑
同情
夜工
阿嬌和她的同伴
寂寞的山村
樓上人家
阿誠的畫家夢
謀殺進行曲
搭枱客
惡人禮讚
同道中人
豆皮婆試劍
火辣辣的夏夜
夕陽正好
怪茶客
劫匪奇遇記
誘惑
等待占美
聖誕奇遇拆良緣
巨獎的誘惑
本色
神遊世界
没有休止符的哀歌
阿爸風生水起記
後記
書摘/試閱
夜工
還有幾分鐘,便是午夜十二時了。
工友們都到外面吃東西去了。寂靜的廠房很熱;中央的燒審裏的炭火仍是很熾烈。金華搬了張矮櫈子,走到遠離燒窰的天井裏,挨著潮濕的牆坐下,馬上便發出鼾聲來。
肚子裏的咕嚕咕嚕的聲響,怎麼也不能把他吵醒;下午三點鐘吃的兩個隔夜麵包,早已消化掉了。但這時候,爭取時間小睡一會,對於他來說,真比爭取吃飽肚子來得要緊。
他今年才十四歲,本不應該做通宵的夜班工作的;假如廠方曉得他還不滿十六歲,也許不讓他幹。但是,夜班比日班多五角錢,而且還有五角錢的宵夜費――這一塊錢,對他的誘惑真大,於是他便假說自己有十六歲了。他雖是小小年紀,但誰也不懷疑他不能當夜班。他一來這裏,便是當夜班的,而且已幹了十多天了;雖然消瘦了一半,可是他跟大人一樣,從開工到收工,一直未出過亂子。
他的父親幾個月前才死去。母親進了醫院生小弟弟,明天才能回家。在母親不在家的幾天中,他經過一夜辛苦工作後,回到家裏還得照顧比他小一半的弟弟。今天弟弟病倒了,他照顧了他一整天,竟沒有睡過。辛苦了一整夜,而得不到休息,接著又要捱夜工了;對於他,這真是很殘酷的折磨。好容易,才捱過去了半夜,他非常希望這半小時的休息,能給他軟癱得難於支撑下去的身體,注進足夠的氣力,好能支持他幹完這天工作。所以,他很快便熟睡了。
當他睡得正酣的時候,卻被人叫醒了。他瞪眼一看,原來是何維。
「快些吃吧,就快夠鐘了。」他笑咪咪地把一根油條塞到金華的手裏。
「嗯,怎麼好要你請吃呢?」他一望見油條,飢餓的饞涎馬上湧滿口腔。他一邊說,一邊摸出一個角子來,「我把錢還給你吧。」
何維把他拿著角子的手推回去。他便大口的嚼著油條。何維看著,也覺得其中的香味,因而爽朗地笑了。
他比金華大三歲。他們同一天來這搪瓷廠工作,幹的都是洗花模之類的雜工,他們很快成了朋友
「放工回去,你就見著媽媽啦――還有小寶寶呢。」他拿來了一杯開水,遞給金華,跟著在他旁邊下來。
「是呀!」想起媽媽和小寶寶,他馬上樂開了,滿是灰塵烏黑的臉上,堆起了笑容。「她說,不是今晚回來,就是明天早上哈!」
「多謝你呀!」他把最後一口油條吞下,一口氣的灌下那杯開水,抹抹鼻唇,感激地望著何維說。
「嗯,這也用得著道謝麼?」
工友們都陸續回來了。十多個噴花壺子,又開始嘶絲地合唱起來。
金華回到他工作的那個角落裏。身旁三四個烘烘的爐子,像一道火燄織成的牆;他竭力坐開去,但還感到那煎熬人的熱力,像非榨乾他的血汗不可似的熨著他。熨的太難受時,他就用小手掌在面前的盆裏,兜一些混濁的水灑在向著爐子的那邊身上,藉以涼涼熱得快要焦的皮膚;但不一會,那點兒水便給熨乾了;不乾的是流個不住的汗水。
剛才睡那一會兒所產生的氣力,很快便消失了。他手中握著的鮑魚刷,慢慢變得沉重起來,就像拿著一塊鐵似的。旁邊待洗的花模迅速的積壓起來,外面,噴花工友要等一會兒,才有乾淨的花模噴花;那些等得不耐煩的,便鼓噪地叫喊起來:
「喂!洗花模的,睡了啦?」
聽到吆喝聲,他勉強振作一下。他極力想擦得快些,但花模上的積粉,卻似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先前擦兩下便擦掉了,現在擦幾下還是擦不掉。而且,他的眼皮沉重了許多,不停的垂壓下來;他想竭力不讓它合攏,但只是眉毛稍為動一下,眼皮簡直不聽指揮。像用紅絲裹起來的眼珠,看的東西也一開二,左右上下的晃個不停。
「金華,用冷水抹一抹面吧,」何維把花模送進來時,搖他幾下,「洗一洗面,就會精神起來囉!你看,」他指一指牆上的鐘,想用時間的觀念來刺激他振作起來,「還有四個鐘頭就放工了。」
「是呀,就快放工了。」他機械地點點頭。
接著,他站起來,連續打著阿欠。走到貯水池邊,臼了一盆子水,唏哩嘩啦的往頭上淋下來,果然精神一些。
但這不是由充足的精神產生出來的氣力,終於還是不能持久的。不一會兒,他又頭昏腦脹起來了。他又走到水池旁邊,淋了一大盆水,然而他的神經像麻木了似的,再也振作不起來了,同時,他覺得,肚子裏好像有一把炭火在煎熬著他的血,全身每個細胞都覺到熱剌剌。腰骨和四肢都酸痛得很,每動一 下,都像蟲子在裏面咬一口那樣難受。浸在盆子裏的手遲鈍了,他雖覺得已用全部氣力洗擦著,然而盆子裏的水,卻像一泓死水,連一點兒漣漪也激不起來。
「金華,快些,外面的模子已經用完了!」何維進來取花模,看見他像一段木頭似的,禁不住著急起來。
「啊啊,是!」他被這驀地裏響起來的聲音嚇了一跳,愴惶地扳一扳腰。 何維瞪著眼睛看看,金華那微張著,彷彿不能合攏的嘴唇乾得就要爆裂,
而且紅得像火燒;把手掌在他的額角上按一按,就像摸在剛才燒過的花模上似的熨手,他不禁吃一驚。望一望壁鐘――真見鬼,怎麼才是四點鐘呢。
「嗯,你得好好休息幾天才是!」他悄聲地說,一邊把手伸進盆裏,從金華的手中拿過刷子,「我跟你換一換,你去疊盆子吧,那沒有這麼辛苦的。」
金華勉強站起來,揉著眼睛走到噴花間去了。
在一個角落裏,排放在鐵網上待燒窰的盆子,一網一網的疊放得像小山那麼高,他要趕快的把那些盆子安置在近著燒窰的空地上,騰出鐵網作别樣用。
坐著工作得太疲倦,來回地走動一下,對他確是起些鬆地的作用,他果然覺得比洗花模輕鬆得多。
鐵網上的小盆子,已被他逐一的移放到地上了。地上,小盆子愈疊愈高,他要用櫈子墊腳,才夠高往上放。這麼一來,爬上爬下的取盆子,使他微小得可憐的氣力,消耗得特别快。他又感到手腳麻木不聽指揮了。幸好,有個一直在門外搬東西的,跟他年紀相仿的名叫阿忠的小工,回到噴花間來,總算給他幫了不少忙;站在櫈子上,不用爬下來拿盆子了。
他愈來愈覺到,身體內處處都像在冒出火燄,血似乎沸透了,喉嚨乾渴的要命,灌滿了一肚子開水,還是止不住渴。他的眼睛發酸得出了淚水,闔起來了。
還有幾分鐘,便是午夜十二時了。
工友們都到外面吃東西去了。寂靜的廠房很熱;中央的燒審裏的炭火仍是很熾烈。金華搬了張矮櫈子,走到遠離燒窰的天井裏,挨著潮濕的牆坐下,馬上便發出鼾聲來。
肚子裏的咕嚕咕嚕的聲響,怎麼也不能把他吵醒;下午三點鐘吃的兩個隔夜麵包,早已消化掉了。但這時候,爭取時間小睡一會,對於他來說,真比爭取吃飽肚子來得要緊。
他今年才十四歲,本不應該做通宵的夜班工作的;假如廠方曉得他還不滿十六歲,也許不讓他幹。但是,夜班比日班多五角錢,而且還有五角錢的宵夜費――這一塊錢,對他的誘惑真大,於是他便假說自己有十六歲了。他雖是小小年紀,但誰也不懷疑他不能當夜班。他一來這裏,便是當夜班的,而且已幹了十多天了;雖然消瘦了一半,可是他跟大人一樣,從開工到收工,一直未出過亂子。
他的父親幾個月前才死去。母親進了醫院生小弟弟,明天才能回家。在母親不在家的幾天中,他經過一夜辛苦工作後,回到家裏還得照顧比他小一半的弟弟。今天弟弟病倒了,他照顧了他一整天,竟沒有睡過。辛苦了一整夜,而得不到休息,接著又要捱夜工了;對於他,這真是很殘酷的折磨。好容易,才捱過去了半夜,他非常希望這半小時的休息,能給他軟癱得難於支撑下去的身體,注進足夠的氣力,好能支持他幹完這天工作。所以,他很快便熟睡了。
當他睡得正酣的時候,卻被人叫醒了。他瞪眼一看,原來是何維。
「快些吃吧,就快夠鐘了。」他笑咪咪地把一根油條塞到金華的手裏。
「嗯,怎麼好要你請吃呢?」他一望見油條,飢餓的饞涎馬上湧滿口腔。他一邊說,一邊摸出一個角子來,「我把錢還給你吧。」
何維把他拿著角子的手推回去。他便大口的嚼著油條。何維看著,也覺得其中的香味,因而爽朗地笑了。
他比金華大三歲。他們同一天來這搪瓷廠工作,幹的都是洗花模之類的雜工,他們很快成了朋友
「放工回去,你就見著媽媽啦――還有小寶寶呢。」他拿來了一杯開水,遞給金華,跟著在他旁邊下來。
「是呀!」想起媽媽和小寶寶,他馬上樂開了,滿是灰塵烏黑的臉上,堆起了笑容。「她說,不是今晚回來,就是明天早上哈!」
「多謝你呀!」他把最後一口油條吞下,一口氣的灌下那杯開水,抹抹鼻唇,感激地望著何維說。
「嗯,這也用得著道謝麼?」
工友們都陸續回來了。十多個噴花壺子,又開始嘶絲地合唱起來。
金華回到他工作的那個角落裏。身旁三四個烘烘的爐子,像一道火燄織成的牆;他竭力坐開去,但還感到那煎熬人的熱力,像非榨乾他的血汗不可似的熨著他。熨的太難受時,他就用小手掌在面前的盆裏,兜一些混濁的水灑在向著爐子的那邊身上,藉以涼涼熱得快要焦的皮膚;但不一會,那點兒水便給熨乾了;不乾的是流個不住的汗水。
剛才睡那一會兒所產生的氣力,很快便消失了。他手中握著的鮑魚刷,慢慢變得沉重起來,就像拿著一塊鐵似的。旁邊待洗的花模迅速的積壓起來,外面,噴花工友要等一會兒,才有乾淨的花模噴花;那些等得不耐煩的,便鼓噪地叫喊起來:
「喂!洗花模的,睡了啦?」
聽到吆喝聲,他勉強振作一下。他極力想擦得快些,但花模上的積粉,卻似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先前擦兩下便擦掉了,現在擦幾下還是擦不掉。而且,他的眼皮沉重了許多,不停的垂壓下來;他想竭力不讓它合攏,但只是眉毛稍為動一下,眼皮簡直不聽指揮。像用紅絲裹起來的眼珠,看的東西也一開二,左右上下的晃個不停。
「金華,用冷水抹一抹面吧,」何維把花模送進來時,搖他幾下,「洗一洗面,就會精神起來囉!你看,」他指一指牆上的鐘,想用時間的觀念來刺激他振作起來,「還有四個鐘頭就放工了。」
「是呀,就快放工了。」他機械地點點頭。
接著,他站起來,連續打著阿欠。走到貯水池邊,臼了一盆子水,唏哩嘩啦的往頭上淋下來,果然精神一些。
但這不是由充足的精神產生出來的氣力,終於還是不能持久的。不一會兒,他又頭昏腦脹起來了。他又走到水池旁邊,淋了一大盆水,然而他的神經像麻木了似的,再也振作不起來了,同時,他覺得,肚子裏好像有一把炭火在煎熬著他的血,全身每個細胞都覺到熱剌剌。腰骨和四肢都酸痛得很,每動一 下,都像蟲子在裏面咬一口那樣難受。浸在盆子裏的手遲鈍了,他雖覺得已用全部氣力洗擦著,然而盆子裏的水,卻像一泓死水,連一點兒漣漪也激不起來。
「金華,快些,外面的模子已經用完了!」何維進來取花模,看見他像一段木頭似的,禁不住著急起來。
「啊啊,是!」他被這驀地裏響起來的聲音嚇了一跳,愴惶地扳一扳腰。 何維瞪著眼睛看看,金華那微張著,彷彿不能合攏的嘴唇乾得就要爆裂,
而且紅得像火燒;把手掌在他的額角上按一按,就像摸在剛才燒過的花模上似的熨手,他不禁吃一驚。望一望壁鐘――真見鬼,怎麼才是四點鐘呢。
「嗯,你得好好休息幾天才是!」他悄聲地說,一邊把手伸進盆裏,從金華的手中拿過刷子,「我跟你換一換,你去疊盆子吧,那沒有這麼辛苦的。」
金華勉強站起來,揉著眼睛走到噴花間去了。
在一個角落裏,排放在鐵網上待燒窰的盆子,一網一網的疊放得像小山那麼高,他要趕快的把那些盆子安置在近著燒窰的空地上,騰出鐵網作别樣用。
坐著工作得太疲倦,來回地走動一下,對他確是起些鬆地的作用,他果然覺得比洗花模輕鬆得多。
鐵網上的小盆子,已被他逐一的移放到地上了。地上,小盆子愈疊愈高,他要用櫈子墊腳,才夠高往上放。這麼一來,爬上爬下的取盆子,使他微小得可憐的氣力,消耗得特别快。他又感到手腳麻木不聽指揮了。幸好,有個一直在門外搬東西的,跟他年紀相仿的名叫阿忠的小工,回到噴花間來,總算給他幫了不少忙;站在櫈子上,不用爬下來拿盆子了。
他愈來愈覺到,身體內處處都像在冒出火燄,血似乎沸透了,喉嚨乾渴的要命,灌滿了一肚子開水,還是止不住渴。他的眼睛發酸得出了淚水,闔起來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