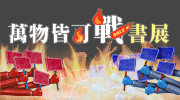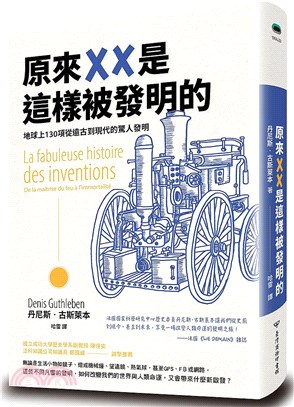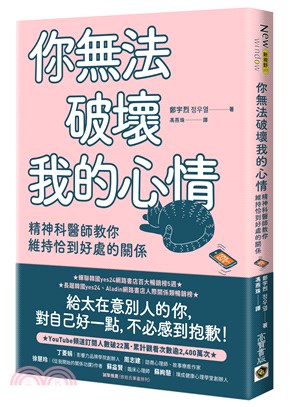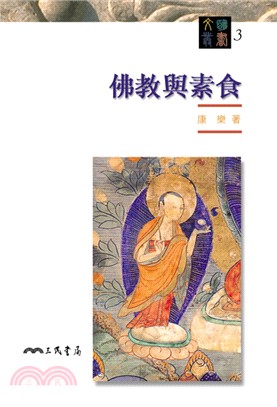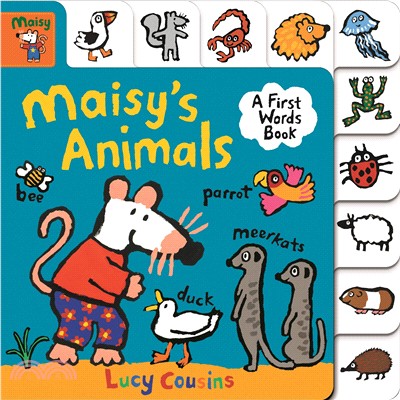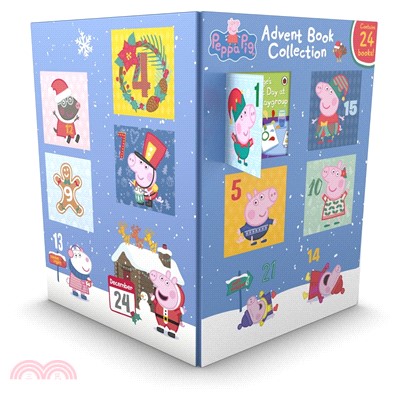人民幣定價:50 元
定價
:NT$ 300 元優惠價
:87 折 261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建黨偉業(套裝全2冊)》是一幅二十世紀早期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色彩斑斕的歷史長卷。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學的態度、磅?的氣勢和翔實的史料,全面展示了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8年井岡山會師這十年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所涌現的一大批杰出的風云人物,形象地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發展壯大的曲折歷程,生動地刻畫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黨的創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輝形象,著力描寫他們在追求真理、尋找救國之路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和人格力量。
作者簡介
黃亞洲,浙江杭州籍。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影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雜文學會聯誼會組委會名譽主任,浙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浙江省作家協會黨委書記兼主席。出版長篇小說、散文集、詩集等文學專著二十余部。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中國魯迅文學獎、金雞獎、金鷹獎、華表獎、飛天獎、百合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并在法蘭克福、開羅、芝加哥獲有關國際電影節獎。
目次
第一章 在水龍沖洗血跡的時候,不妨直接行動 第二章 告訴兒子:監獄是研究室 第三章 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第四章 驅張團入京,小騾車出城 第五章 1920年的夏天,陽光如此逼人 第六章 中國的天平,現在向上海傾斜 第七章 建黨偉業:一棟樓與一條船 第八章 這個馬林不是馬,比牛還牛 第九章 毛澤東劉少奇踩水車:必須同時兩條腿 第十章 黨首們在另一面黨旗下宣誓 第十一章 難啊,去歐洲才找到了中國共產黨 第十二章 交鋒廣州,黨內如此硝煙彌漫 第十三章 黃埔學員出槍操練,湖南農民押人游街 第十四章 駛進謎團的中山艦 第十五章 北伐軍在上海一頭撞上四一二 第十六章 反抗,全國的槍和矛都在滴血 第十七章 可以脫他的鞋,但取不了他的頭 第十八章 中國革命現在走進了山里 作品研討會紀要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在水龍沖洗血跡的時候,不妨直接行動 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陳獨秀便多夢了。夢多而雜,伴鼾,有一次還罕見地淌了口水,藍花枕巾糊了一塊,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 支撐著陳獨秀夢境的那些圓木很堅壯,黝黑而粗糲,像他的個頭,以至于相隔近百年,他的夢境還沒有坍塌,而被今人洞察。 圓木交叉著,頂端懸一口鐘。鐘什么形狀,記不清了,他只感覺到是銅質的,音色如劍,有穿透力,龍華寺的法印和尚兩年前對他說:爾命如鐘。他一直弄不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鐘還是時鐘。若說梵鐘,他是不信的。他一直指佛國為虛妄之境,三寶雖則莊嚴但俱不足為信。若說是時鐘,那就是一種流水的概念或者是歷史的概念,大而無當的東西。 陳獨秀當時并未細問,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細剖。第二年陳獨秀就受蔡元培之邀離滬北上,再也不去龍華踏青,當然也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學之後三個月就圓寂了。 而他在一九一九年暮春的那些詭譎的夢境里,確乎是聽見鐘聲的,一口小銅鐘像是上岸的魚一樣不停地翻著肚皮,亂蹦亂顛。那是一種驚心動魄的聲音。 夢里的天空是法蘭西的天空。暗顏色。準確地說不是天空而是屋穹,一個大廳,其經緯點應是巴黎。 巴黎的凡爾賽宮華貴而壓抑。由于夢境的緣故,陳獨秀看不清大廳的邊沿。一扇門他是看見的。他沒經過那扇橡木門就發覺自己已置身于大廳吊燈的昏黃色之中了。他伸出手指,觸到了那扇門,他覺得這兩扇門堅硬得不成道理。 門邊站著的那兩個戴圓形高帽的拉門人,他也看見了。他們長著與他一樣的褐黃色的眼珠,胸前一排排的紐扣像黃金一樣閃光。他還順著兩位拉門人的褐黃色的目光,看見了會議桌周遭的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這一圈人大多穿著黑色的燕尾服,一把把大剪刀掛在屁股上。他們走起路來,剪刀就無聲地工作,把空氣剪成碎片。會議廳里的空氣一下子都叫這些剪子主宰了,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 在聽到銅鈴之前陳獨秀先聽著剪子們的發言。發言很兇,殘忍而又文質彬彬。但是這些出自槍管的殘酷的聲音很快就被一個女人的呼喚所取代了。 “當家的,醒醒,你醒醒!”他聽出來了,這是君曼的聲音。 接著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 已經日上三竿,瓦楞上和院子里滿是陽光。高君曼要陳獨秀喝點大米粥,要給他擦個身子,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 高君曼告訴他,昨天夜里學生尋上門來不少,說要拉起一個行動小組,響應陳先生對中國的“直接改造”,想聽聽先生的意見。 陳獨秀一時沒有聽清夫人的話。空氣沉悶而潮濕。太陽亮晃晃地停在他的額角上。他有點氣喘。 陳獨秀在這些令整個中國知識界都驚悸不安的日子里,不僅多夢,而且得了熱傷風,熱得厲害,每天早晨的衫子都是濕淋淋的。 陳獨秀在喝了一大碗熱粥後,眼皮子打架,繼續回床上做他的夢。他累,不想說話。 高君曼說:“刮痧不頂用了,該給你拔拔火罐子。” 陳獨秀沒有聽見高君曼說的,而是繼續聽見了剪子們的話。那些烏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閃著兩條細細的白色的光。 有一把剪子從會議桌旁邊站起來,用嚓嚓嚓的聲音說:“我大英帝國的海軍當時均集中于地中海,東部不免空虛。再說,德軍又對我施行潛艇戰略,我們不能不請日本相助。我也知道,我們當時所允酬謝日本之價,未免昂貴,但是,既然有契約在前,總不能成為一頁廢紙吧?而今戰勝了德國,日本以實力援助戰事,實功不可沒。而中國,雖為戰勝國,畢竟,未對此次戰爭出一兵一卒。所以,現在,對中國山東膠州問題,本總理與美國總統和法國總理的意見相同,認為還是應該讓日本國繼承德國之權利。” 響了幾下掌聲,陳獨秀聽見了。美國人和法國人都拍了掌。掌聲里呆呆坐著五個中國人,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長陸征祥、駐美公使顧維鈞,也有南方軍政府的代表王正延。呆呆的中國人聽見掌聲,臉色一齊漲紅,如龍華寺的那些羅漢。 有個中國人拍了一下桌子,拍得不重。陳獨秀從夢里看過去,認識那人就是上海嘉定人氏顧維鈞。他聽見顧維鈞在喊叫。 “中國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戰勝國?中國有十四萬華工參加了這次世界之戰,試問,哪個戰場哪個角落沒有我們中國人?” “是穿軍裝的中國人嗎?手里有槍嗎?”有人說。 然後是笑聲。大廳的回音使這些笑聲聽起來很厚實。 陳獨秀又看見一位剪子從哄笑聲中站起來。 “請允許我把草擬的《凡爾賽條約》的第156條念一下:德國將按照1898年3月6日與中國所訂條約及關于山東省之其他文件,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及特權,其中以關于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予日本。諸位,聽清楚了嗎?” 陳獨秀接著聽見了上牙床與下牙床咬出的吱吱的聲音,他聽出來了,這一聲音發自于中國的陸總長之嘴,有如夜鼠磨牙。 那剪子還在嚓嚓嚓響:“本條款還有如下內容:所有在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權利,其所包含支路,連同無論何種附屬財產、車站、工場,固定及行動機件、礦產,開礦所用之設備及材料,并一切附隨之權利及特權,均為日本獲得,并繼續為其所有。” 另一位黑剪子又念:“第158條,德國應將關于膠州領土內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他各項檔案、登記冊、地圖、證券及各種文件,無論存放何處,自本條約實行起三個月內移交日本。諸位同意否?” 陳獨秀怒喊一聲“放屁”!他覺得他此時不能不喊,但他用足了氣力而聲帶卻如棉絮一樣沒有共振。他的話,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沒有聽見。 那洋人又說:“請陸征祥閣下到桌前來驗看一下條款內容。” 陸征祥呆坐不動。 陳獨秀靠在橡木大門上,覺得腿腳有些麻木。他很喪氣。這時候他又聽見了兩個高鼻子拉門人的對話。 一個說:“就我記憶所及,中國人自從他們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後,就沒有站起來過。” 另一個說:“就我記憶所及,他們中國人,自從他們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後,就沒有發出聲音過。” 陳獨秀以頭觸門。他此時悲憤已極。他覺得整個大門都被他撞坍了,他自己也頭痛如裂。 “當家的,”又是高君曼的聲音,“你怎么了?撞床檔上了!” 陳獨秀說:“鐘,打鐘!”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陡地睜圓。 “那是座鐘,都三點了!” “那是巴黎的鐘!”陳獨秀兩眼如鈴,鈴上遍布血絲。“鐘很響,君曼,我聽出來了,那是用中國人的骨頭敲的,是骨頭,腿骨!” 妻子扶他坐正,說:“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蘆,買吧?” 陳獨秀瞪著鼻子前面的空氣說:“堂堂堂,堂堂堂,你難道就沒聽見鐘聲?國內的南北和會,分贓!黨派分贓!世界的巴黎和會,也是分贓,列強分贓!我這人怎么就這么該死?我怎么會說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君曼,我得的是眼病吧?眼睛瞎了!北大學生跑到美國使館門口喊威爾遜大總統萬歲,不就是我唆使的么?” “小心涼。披上褂子。” “現在才聽見鐘聲!什么公理戰勝,強權失敗,其實他威爾遜的十四條,沒一條是給中國人想的!堂堂堂,堂堂堂,你聽見沒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中國人還能不從被窩里爬起來么?” “汗那么多。” “我的汗都是從淚腺里流出來的!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陳獨秀!我是陳獨傻!” “喝口茶,當家的,喝口茶。” “把自來水筆給我拿過來。《每周評論》要出第二十期,我要敲鐘了!要拿威爾遜的腿骨來敲鐘,這條洋狗!” “躺下吧!當家的,手都打抖,怎么握筆?” “君曼,你是不是我老婆?!” 陳獨秀說出這句咬牙切齒的話的時候,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臉蛋伸進門里嘻嘻笑起來,兩口參差不齊的小白牙像兩棒沒有長全的玉米。 毛澤東無夢。 毛澤東一向睡眠很好。近三個月天天冷水晨浴,使得他的夜眠更沉。無夢的毛澤東一天到晚聽見鈴聲。他的圓口黑布鞋總是踩著鈴聲的有力的節奏走過草坪,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 手握小銅鈴的老校工驚異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昨夜毛先生寢室又麇集一幫長衫人物,湊著油燈談西洋談巴黎,直至雞鳴。毛先生送客關門的時候,他也披衣起身,看看學校大門拴緊沒有。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熬夜就是熬命。但是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帳鉤一松鼾聲便起,清晨出門井水洗身之時,眼圈子從來沒見青的。老校工搖著銅鈴想,教歷史的先生與教其他科目的先生畢竟不一樣,若是一樣了,中國的歷史也就沒這么精彩了。 長沙修業小學四年級的孩子一見二十六歲的歷史教員出現在門口,就刷刷地起立,齊喊:“先生好!” 喊畢,齊嶄嶄坐下,一陣風。 毛澤東把粉筆盒往講桌上一放,看著大家,忽然高聲說:“同學們,起立!” 孩子們遲遲疑疑起立。動作遲緩者都懷疑自己聽錯了,怎么又起立,剛才不是喊過“先生好”了么! “諸位同學,今天先生講的課,是八國聯軍侵略中華。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國,就是欺侮我們中國人站不起來,腰桿不直。今天先生來講這段歷史,聽課者還能坐得住嗎?所以這堂課,先生愿意看見你們站著,你們愿意站著嗎?” “愿意!”滿教室轟轟響。 有個男孩子雄赳赳說:“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嗎?” “凳子,是給屁股坐的,但是這堂課,凳子可以給鞋底子踩!” 大約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站上了凳子,這么一站,中國的男人便偉岸了許多。 毛澤東說:“個頭是高了,可是還有不少腰桿子沒挺直!” 話音未落,腰桿子都全挺直了。 毛澤東環視教室,說:“像中國人了!” 他于是夾起半截白粉筆,在黑板上寫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個字,剛寫畢,便聽得遠處傳來七八聲槍響,不知道是在處決還是在嚇唬。長沙城一年四季老聞槍聲,也是見怪不怪了。“堂堂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張敬堯兄弟總是喜歡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準星前頭,他們開槍就像啪啪啪扇男人耳光或者啪啪啪打女人屁股,日日夜夜隨意得很,而這種暴政,又何異于黑板上的那八個字。 毛澤東轉過身,面對一屋子聳得像寶塔一樣的孩子們,心里尋思:今天晚上新民學會開會的時候,要自覺地把巴黎的火藥味同長沙的火藥味融在一起研究。 他嘴里說出的話卻是:“同學們,先生今天不講八國聯軍了,講什么呢?講講巴黎和會。這兩樁事情,其實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強盜之舉。所以,同學們,你們不要坐下,你們依舊給我站著。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凈了,你們都盯著先生看!若見先生講得憤怒了,你們也可以跟先生一樣,用腳跺凳子、跺磚地,因為你們今天長得跟先生一樣高了,你們的跺腳會很有力。先生告訴你們,地球是圓的,長沙一跺腳,巴黎的街道也會顫抖起來!” 陳獨秀後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紅色的痧痕,是李大釗刮出來的。碎瓷碗片在李大釗手中柔潤如玉,這使高君曼折服。陳獨秀趴在床上,一縷陽光在他的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層油膜。他說:“痛,痛。” 李大釗說:“那是寒氣出膚之痛,忍著。” 陳獨秀說:“蔡先生後來怎么講的,守常,說下去。” 他是指蔡元培校長幾個鐘頭前在西齋飯廳的一席話。李大釗匆匆趕到箭桿胡同,就是來告訴陳獨秀這番慷慨之言的。他知道陳獨秀這些日子相當關注蔡校長的想法。一校之長在國家緊急之時的動靜往往能成為火星子,點燃某一根導火索。 “我一點不怪蔡先生。”陳獨秀喘著氣說,“湯爾和這個人,先是薦我上任,現在又轟我下臺,蔡先生也是迫于無奈罷了。” 陳獨秀被免文科學長已有二十幾天了。對于此事,他真的一點不怪蔡校長。頑固派對《新青年》圍剿日甚,當校長的身處夾縫,采進兩步退一步之策,也屬情理之中。 “你輕一點,”陳獨秀的聲音悶在肥厚的枕頭里,“守常,說下去。” 高君曼先是擠擠眼,後來又直接拉李大釗到門外,小聲說:“李先生,我已經知道怎么刮了,李先生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仲甫的急脾性,您是有數的。” 陳獨秀在屋里聽見個大概,急得拍床:“君曼你?唆什么,快讓李先生進來!” 李大釗對高君曼說:“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給仲甫說兩三句話,抵得上兩三百道手上功夫哩!” 這是公元1919年5月2日黃昏,汗淋淋的陳獨秀趴在自家的藍花兒枕頭上,瞪大牛眼,聽著蔡元培校長的悲憤之言。 這些語言在經過轉述之後,依然滾燙如淚,能炙痛人心。 蔡元培校長當時是說給參加《國民雜志社》例行社務會議的十余名各校學生聽的。他說話的時候十根手指都在顫抖,以至于不能不握緊兩只拳頭。 “同學們,”他路過飯廳的時候,突然就沖進來,面對這十余名各校學生,神色悲愴。“失敗了!我們失敗了!晴天霹靂啊,我昨日一個晚上沒有睡著啊,政府已經接到中國代表團來電,關于索還膠州租借的對日外交,失敗了,徹底失敗了!” 學生們一齊站了起來。 頭發梳得光溜溜的這位北大校長語音哽咽:“同學們!政府的外交部長陸征祥,快頂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脅之下,已經想把我們的山東獻出去了!他已經電請政府同意在和約上簽字了!同學們,同學們,你們都應該知道,膠州亡了,就是山東亡了!山東亡了,國家就不成其國家了!此時此刻,一個大學校長說這些話,心里悲憤啊!” 蔡元培說到這里,一個踉蹌,穿灰長衫的學生許德衍趕緊一把攙住他。蔡元培站正了又說:“昨日,我同外交委員會的汪委員長幾個人,一齊給陸征祥外長打了一個十一字的電報!” 許德衍馬上說:“同學們,電報稿在這里,我念一下,蔡校長的電報確是十一個字: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聽清楚了:不必生還!如果他陸征祥敢賣山東,他什么時候敢回來就什么時候打死他!” “不必生還!”學生們揮拳擊桌,“打死他!” 蔡元培說:“同學們呀,同學們!你們能想象得出,我們的政府會這般的軟弱,這般的無能嗎?他們一片又一片地向列強割我們國家的地,用割地的錢購來一批又一批的槍炮,再用槍炮鎮壓一省又一省的民眾!你們是知道的,他們的槍口是對著百姓的,他們沒有一桿槍口敢對著西方列強,敢對著小日本!同學們,你們都是國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說的話,如今只有靠你們來說了!我作為校長,本來是千不該萬不該呼吁你們離開書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國難當頭之時,我只能痛心地請求你們大家放下書本,共圖救亡大計了!你們可以寫文章,可以打電報,可以向民眾呼喚,喚起全國輿論,以阻止政府簽約!同學們,山東在你們手里,中國在你們手里,你們要起來啊!” 好幾個學生代表突然號啕失聲。 “我愿意以血喚起民眾!”一個年輕學生兩眼通紅,突然像兔子一樣蹦起來,他的名字叫劉仁靜,“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總統府大門口!” 蔡元培說:“同學們,我呼吁你們行動起來,不是要你們做出過于激烈的行為!你們千萬不要同刺刀對抗!熱血是你們身上最寶貴的東西,你們一定不要白白灑掉!只有你們保護好了自己,你們才有力量呼喊正義與良知!……你怎么了?” 蔡元培突然看見一個穿青布長衫的學生在咬自己的手指頭,咬狠了,鮮血滿手。 那青年哭著,在自己攤開的筆記本上,寫下淋淋漓漓兩個字:“血拼!” 蔡元培後來知道那個叫夏秀峰的學生還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他當時只感覺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來的淚珠兒,不經意之間,已經變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兒了。中國現代史後來證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對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他在成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後,北大就成為中國的一粒火星。 這兩天,高君曼很有點火氣。 現在,她兩手叉腰,又沖院子說:“干嗎呀?再怎么著,也得湊個時辰呀!” 進北京兩年一個月,高君曼說話也溜了,半腔京片子。 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湊著玻璃窗看院子。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擠滿了長衫和眼鏡。 干燥的五月三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眼鏡後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這個夜晚是非常時刻,空氣中有導火索燃燒的吱吱之聲。在這樣的時刻,學生們不能不黑壓壓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桿胡同九號。中國思想界巨人的聲音,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 就在幾個鐘頭之前,《國民雜志》社的社務會議作出一項決定,決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學全體同學,于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三院禮堂舉行學生大會,并邀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校代表一起參加,討論應急行動步驟。 但是高君曼像個門神。 從門隙中透出的燈光打在高君曼的挺拔的鼻梁上,她鼻梁上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樣閃著黑色的光。 “我知道,全知道,”高君曼盡量壓著聲音說,“我知道青島要亡了,我知道山東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這會兒陳先生病重,這會兒他燙得像塊炭,同學們,他要這么勞累下去,他也得亡!” “中國遭禍了,節骨眼上了,我們要聽陳先生的聲音!”一個名叫鄧中夏學生這樣說。 又有同學說:“師母,陳先生是我們的旗幟!” “他受風寒了,知道不?”高君曼說,“風大,旗幟不能老插著,知道不?你們今天晚上把這面旗幟收起來,抽屜里放一放,行不?” 學生們沒有動彈的,只見黑壓壓的沉默的一片。這年頭,年輕人特別頑固。 高君曼氣恨恨掩上門,這時候就聽屋里的陳獨秀在說:你良心壞了。 “你胡說什么?”高君曼臉上掛不住了,她三步兩步就跳進了屋。她看見丈夫乖乖地趴著,光背脊上粘連著三只小小的火罐。 “我要出去!”陳獨秀低聲吼,像頭受傷的獅子,“君曼你今天良心壞了。” “你自己想想,你今兒腿腳硬不硬?你額頭燙不燙?你能下床嗎?”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陳獨秀軟綿綿的聲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顧出門。 “你們的先生今天是病人,”高君曼仍然這樣對頑固的學生們說,試圖以情動人。“病人啥都不圖就圖個安靜,你們今兒饒了他好不好?你們要真關心你們的先生,能不能幫我走一走藥渣兒,帶帶先生的病?” 年輕的長衫們沉默。 高君曼端過一只藥罐子,抓起藥渣,沖著學生一把把地抖。學生們沉默地從兩邊讓開。藥渣如同失去了光澤的星星,粘連成一條模模糊糊的黑色銀河,從臺階上一直蜿蜒到大門口。 學生們魚貫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藥渣發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藥渣的聲音還沒有結束的時候,隨著一聲大喝,房門開了。 陳獨秀出了門,在門口昂首而站。屋內燈光漏出來,把他的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顫顫地粘連在他的後背脊上。 “我知道你們為什么而來!”陳獨秀把著急的妻子推到身後,“你們是為巴黎而來!我告訴你們,同學們,實際上,中國的外交不會斷送于巴黎,而只會斷送于沉默!” 陳獨秀說到這里就把手舞起來,背脊上的小火罐隨之顫動。 “你們要喊!諸位同學,你們要喊!陳先生今天喊不動了,而你們,你們要喊!” 學生們齊聲說:“知道了,陳先生!” “後天,也就是五月四號,”陳獨秀揮動拳頭,“請大家看《每周評論》第二十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話!” “空話!空話!”學生們喊。 高君曼想扶陳獨秀進房,陳獨秀又一把推開了她。?當一聲,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現在,到了直接解決的時候了!我一條喉嚨,只能在紙上喊,而你們,你們喉嚨多,你們要一齊喊,喊出聲來!你們要喊得巴黎每一道街路都打擺子!中國不能沒有聲音!你們就是聲帶!中國只有你們是聲帶了!” “我們會喊的,陳先生!”長衫們齊刷刷喊,許多眼鏡後面淚光閃耀。 蔡元培聽見了聲音。聲音使他心境復雜。 若是北大學子面對砧板和刀鋒沒有聲音,他是著急的。他的“并包兼蓄”的辦學方針以及聘任陳獨秀之類的大膽之舉,說到底,就是為了拓寬學子的聲帶。但是學生一旦熱血上了臉,那就很可能不僅僅是涉及聲帶了。作為大學校長,他又不能不控制火候。 五月四日午後,操場上不斷傳來口號,一陣狠似一陣。那是巖漿在運行,而且離突破口不遠了。蔡元培聽得出來。 “還我青島!保我主權!”“取消二十一條!”“國民判決國賊!”“誅賣國賊曹、章、陸!” 蔡元培左腳那只已經裂了一條細口子的黑皮鞋,在校長辦公室的褪色地板上發出的咯咯的聲響,像母雞下蛋後的聲音。蔡元培忽然發現自己此時的心態也是母雞的心態,他很怕身子底下的軟和和的雞蛋碎裂,畢竟是學子啊,手無寸鐵! 他繞著寫字桌,一步步走得很慢,似乎是怕驚醒什么。其實他明白,他怕驚醒的是自己心里的一個念頭,這個念頭是一道命令,命令他瘋狂地跑下樓,在最後的一剎那,把學校的大鐵門鎖上。 他知道學生們要上街游行,地點很可能是天安門,甚至使館區。他也知道政府聽不得吶喊,政府對付學生自有一套包括刺刀在內的策應預案。 電話鈴響起來。教育總長打來的,聲音急促。 “學生是不是集合了?” “有可能。” “什么有可能,孑民兄,我電話里都聽見學生的口號了,打雷一樣。” “天要打雷,總長阻得住嗎?” “阻不住也要阻,孑民兄,使學生勿生事端,是你我職責所在。”教育總長傅增湘聲音頓時高了好幾度。 “學生一腔愛國熱情,怎么能叫事端呢?”蔡元培的倔脾氣上來了。 “我告訴你一條消息,”傅增湘放低聲音,“政府剛剛開完緊急會議,軍隊和警察都開始吹哨子了。” 蔡元培心里一緊。 “昨日夜間,北京大學千名學生聚會,大總統當夜就獲知了。” 蔡元培仍然不吱聲。窗戶之外,悶雷似的口號越見激烈。 他又聽傅增湘在電話里說:“聚會地點就在法科禮堂,京城十三所中等以上學校均有代表參加,場面如此張揚,孑民兄你不會一無所聞吧?” 蔡元培當然知道昨夜發生于法科禮堂的那場風暴。他雖未身處風暴中心,但那種嘯叫聲他是聽到的。雞叫三遍時他還獨處書房,瞪著窗外的夜空。他很為他的學生驕傲,他知道這場風暴是屬于整個民族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屈辱,終于選擇了一個直接的爆發點,這爆發點沒選擇其他地方,恰恰選擇了他治下的一群學生的嘴巴。 “同學們!同學們!同學們!”他不知道跳到臺上這樣喊的學生姓甚名誰,有人當夜就來激動地告訴他,這位戴眼鏡的是文科的學生。“外交危急!國事危急!民族危急!我們要以死抗爭!要血,我們有血!要命,我們有命!我們堅決不準政府簽署賣國和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我們要上街游行!我們要喚醒國人!在這民族淪亡時刻,我們北大的莘莘學子若再保持沉默,若不奮起抗爭,我們也就像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一樣,也是民族的罪人!” 有人還告訴他,一位姓謝的學生,大約是法科的,當場就裂斷衣襟,嚙破中指,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 還有一個學生,叫劉仁靜的,惟十八歲,卻更是熱血灌頂,當場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閃,說要割頸,要以死激勵國人抗爭,四五個學生拼命抱住他,才奪下了那把菜刀。 會上發言的學生有許德衍,有張國燾,有丁肇青,然後再是大會臨時主席、法科學生廖書侖。這位臨時主席慷慨激昂宣布:“同學們,大會作出如下決定:第一,聯合各界,一致抗爭!第二,立即通電巴黎專使,堅決不在和約上簽字!第三,通電全國各省市,定五月七日為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游行示威活動!第四,定于五月四日,也就是明天,北京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蔡元培之所以徹夜未眠,獨坐雞鳴,就是他在腦海里一遍一遍地演映著這場風暴。風暴將他的心情卷得很復雜。他知道這場風暴未來的去向可能是天安門,并且會狠狠撞上那道堅固的具有皇家顏色的天安門城墻。 “此次聚會通過兩個宣言,大總統也知道了。”傅增湘電話里又說,“警察總監吳炳湘在學生中布置耳目不少,孑民兄這你也該是明白的。你知道宣言的事嗎?” 這兩個宣言的手抄件,此刻就擺在校長室的寫字桌上。一個是文言的,詞章厚重激烈,許德衍起草。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黯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之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儕我于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日亡青島耳,是亡山東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拱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沖,實南北之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于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隸牛馬之痛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另一個是白話的,氣勢更如火山噴涌,羅家倫起草。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宣言,當然可以,”教育總長電話里的聲氣又大起來,“然而聚眾鬧事,甚至于去外交使團所在地滋事,便是大險招啊,若真個招致鮮血涂地,則于學生,于教育界,于國家,都不是好事啊,孑民兄,你也是當過教育總長的,我剛才在緊急會議上挨了警察總監吳炳湘一頓訓,又挨了警備司令段芝貴一頓訓,錢總理也翻了我好幾個白眼,我是感到了壓力的,壓力很大啊。此事你一定要幫幫忙,既是幫我,也是幫你自己啊!你我官位不保事小,學生鮮血橫流事大啊!” 這最後一句話,很有些求告之意。蔡元培當過教育總長,知道總長是個不好當的差使,但是從傅增湘這句話中,他也明顯地聽出了某種虛偽,傅增湘還是看重總長這個位子的。然而,話雖虛偽,“鮮血”二字,卻如兩下重錘,重重砸在蔡元培的心坎上。 他一夜難眠,就是怕這兩個字。真的,這兩個字,只能涌動在他的學生的心頭,而不能流淌在他的學生的臉上。 蔡元培想一想,還是對電話這樣答復:“總長先生,元培愿如實稟告,如今國難當頭,北大學生無法安坐于教室之中,拳拳愛國之心,殊屬難得,元培實在不忍心攔阻學生!” 蔡元培停頓了一下。從隱隱約約的口號聲分析,學生游行隊伍已集合完畢。 “對政府的干預,元培當然也有擔心。”蔡元培繼續大聲說,“作為校長,元培又何嘗不想千方百計保護學生?我不忍看到學生流血,更不忍看到學生犧牲,可是也不能出于此種擔心,而悶住我們學生的救國呼聲!” 說畢,電話啪地擱上。 蔡元培的嘴唇和電話線抖得一樣厲害。 片刻之後,他拔腿沖出了校長室。 蔡元培跑到學校大門口的時候,氣喘得幾乎站不住。管門的老校工說:“校長,喝口水?” 蔡元培手一指,說:“拉上。” 老校工立馬明白了校長的意思。管門的其實早就為“開關”二字忐忑不安了。 銹跡斑斑的鐵門嘰嘰嘎嘎響,兩個校工一齊推。 “快點!快點!”校長說。 口號聲越來越清晰,蔡元培知道學生隊伍已經起步了。 鐵門拉緊,老門衛雙手捧出一把看起來很怕人的大鎖:“蔡校長,在下還有大鎖一把。” “鎖!鎖上!”校長說。 老門衛合起雙掌,蹲個馬步,以一種夸張的身姿,吧嗒一聲合了鎖。 蔡元培聽著鎖響,心里踏實了一些。 口號聲如海濤般轟響,游行隊伍已經臨近大門了。放眼望去,隊伍花花白白一片,真如涌動的海浪。因為許多旗幟都是撕破了白床單做成的,取其意為賣國賊曹章陸出喪,這也是昨日法科禮堂大會的倡議之一。 “取下!”蔡元培忽然手指大鎖,“快取下!” 老門衛愣住了,聽不懂校長的意思。 “取下鎖,聽明白么?取下這把鎖!” 老門衛聽明白了,馬上取出長柄銅鑰匙,慌慌忙忙開啟了大鎖。 三個門衛一齊動手,推開大鐵門。 蔡元培頓腳說:“誰叫你們開門了?” 眾人又一齊呆住。蔡元培說:“鎖,拿掉!門,關上!” 鐵門復又嘰嘰嘎嘎拉攏。 浩浩蕩蕩的學生游行隊伍現在逼近了大門,白色旗號此起彼落,吼聲如潮。 “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民賊不容存,誅夷曹、章、陸!” 大鐵門。黑色柵欄。隊伍被迫停下。 蔡元培緊張地瞪著隊伍,他覺得自己快要倒下了。 走在頭里的許德衍一聲喝“開門”,游行總指揮傅斯年便把手像刀一樣一劈,幾個學生就沖了上去,協力一撥拉,緊閉的大鐵門立即洞開。 游行隊伍涌出大門,如洪流出閘,奔騰浩蕩。 蔡元培避在門衛房內,表情呆然地聽著轟然涌動的腳步聲和口號聲。 “校長做得很好。”有人在他背後字正腔圓地說。 蔡元培回頭,見是李大釗。 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身著黑色長衫,其目光透過圓圓的眼鏡,格外深沉。他就這么深沉地久久地瞧著自己的校長。 “門是將關未關,鎖是將鎖未鎖。”李大釗說,“若天下之領導者均以此種立場對待民意,則天下有救了。” 蔡元培心里復雜,不吱聲。 李大釗又說:“北大為有蔡校長而自傲。” 蔡元培嘆一聲,說:“唯守常知我最深。” 他看窗外。 窗外巨濤滾滾,一波一波,呼嘯出校。 午後已過一時,新華門內總統府的宴廳里,還是酒香撲鼻,未有散席之意。 大總統徐世昌興致很高。他今天宴請剛由日本歸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應邀作陪者是國務總理錢能訓、交通總長曹汝霖、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徐世昌這樣想,眼下外交乏力,民眾怨憤,時局艱危,若是幾位重臣再不撫慰一番,則是幾乎沒有人再說政府好話了。 他再一次端起酒杯,側臉,懇懇切切對章宗祥說:“爾出使日本,多有操勞,不僅大大改善中日關系,還為本政府謀取了新貸款之允諾,殊為不易。” 他沒有注意到一名衛士現在出現于宴廳門口,并且神色慌忙,那衛士耳語站在門口的一位侍衛官說:“隊伍三千,已經到了天安門!” 侍衛官說:“知道了。” 衛士問:“要不要稟報總統?” 侍衛官搖頭:“不必。” 徐世昌繼續興致很高,他眼望眾人,說:“望諸位務以國家為重,勿聽流言,照常供職,共濟艱難!來來,舉杯!” 他還是沒有注意到衛士又來向侍衛官耳報:“學生要去東交民巷滋事!教育部次長在天安門當場勸阻,學生說,我們今天的行動,教育部管不了!” 侍衛官說:“步軍統領李長泰不是去了嗎?警察總監吳炳湘不是也去了嗎?” 衛士說:“他們也阻止了,可是學生人多,一喊打倒賣國賊,便堵不住!” 侍衛官無法,便向徐世昌走去,徐世昌的臉立即就僵硬了,他的花白胡子抖了起來。 終于,他重重放下酒杯,對總理錢能訓說:“打電話給吳總監,令其妥速解散學生,不許去東交民巷!” 曹汝霖臉色一變,幫腔說:“總統說得對,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 錢能訓斜眼盯著曹汝霖,說:“學生群情激憤,難以控制,若是東交民巷去不了,會不會殃及其他,恐宜早作預謀。” 曹汝霖心頭一驚,又一慌,心是想:這個錢能訓,不僅能訓,且能猜,把我多日的擔心給點破了。 他趕緊站起來,說總統慢用諸位慢用,我還是先回家吧。 曹汝霖回家了,“殃及其他”是他最擔心的。他現在急速回家,這時候他還不知道,他的一連串的慌忙的動作,都像一只專門撲火的飛蛾。 從“火燒趙家樓”現場倉皇奔逃的瞿秋白,一路氣急吁吁。他捂著胸口,覺得自己的心一直在往喉嚨口跳。 在胡同拐彎處,他差點沒撞在楊昌濟和楊開慧父女身上。 人沒有撞上,眼鏡卻由于腳步的驟止而掉落在地。瞿秋白慌忙撿起眼鏡,對姑娘說:“對不起,警察追我,能不能讓我也攙扶一下令尊大人?” 還沒等楊開慧表態,病體虛弱的楊昌濟便一把挽上了瞿秋白。他發現這位學生的手心都是汗,且很冷。教授關注著時局,這位學生為何氣急吁吁,他心里早已明白了七八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