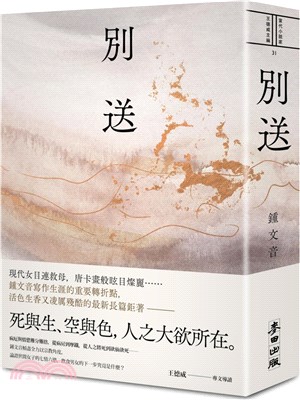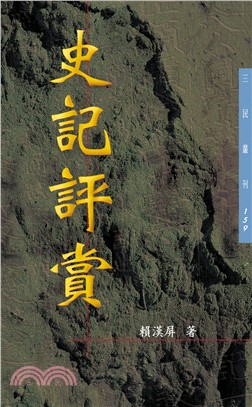別送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現代女目連救母,唐卡畫般眩目燦麗……
鍾文音寫作生涯的重要轉折點,
活色生香又凌厲殘酷的最新長篇鉅著——
死與生、空與色,人之大欲所在。
國藝會長篇小說專案獎助!
王德威專文導讀
在愛苦之海之涯,人如何孤身而立?
走回一個人,要跋涉多少長途,要跌倒多少岐路?
鍾文音這回把前半生關注的「母」題,壯闊成一座令人目眩神迷的榮枯盛景,
彷彿滿山髑髏,都是她的過去色身。
她火力全開,燒盡血淚。以此送別,從此別送。
//
病厄與情慾難分難捨,從病房到摩鐵,從人之將死到欲仙欲死……
鍾文音傾盡全力以宗教角度,論證世間女子的七情六慾,飲食男女的下一步究竟是什麼?
鍾文音讓文字成為另外一種秘戲圖,陰森幽麗,卻也觸目心驚。
如何分別她的愛,是這次書寫的大關鍵。
小說中遭逢家變後的女子踏上遠行之路,去到西藏,從而觸發新的緣法。愛染輪迴,中陰救度,俗骨凡胎,方死方生。在高原凜冽的空氣中,一個台灣女子出入寺院和市廛、荒野和葬場。她尋尋覓覓,能獲得什麼啟悟?抑或是,她的度亡之旅只是又一次「受想行識」的遭遇,一場因色見空的輪迴?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禪宗著名的偈語撲面而來。鍾文音創作近三十年,她的紅塵男女故事有如風飛沙起,四散飄移。藉著《別送》,她有意面向宇宙星塵,讓那未知與不可知在筆下爆裂湧現,從而證成須彌盡在芥子之中。而如果塵埃也只是虛構,她的文字因緣是別是送,污染還是不污染,何能一語斷定?塵埃落而不定,鍾文音「有情」又「無情」的敘事完而不了,文學與佛學的對話仍在持續。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
徘徊煙花與佛家的半僧半人半獸,
眼淚起點是她的煙花,眼淚盡頭也是她的佛家。
《別送》是島嶼平原與高原交會的故事,也是與甲木薩(文成公主)、母親、李雁兒三個女人命運相關而交織的故事。李雁兒的人生旅程,從最初就是母親,到了現在,母親這個議題也還無法拋掉,因為等待最終的告別來到。啟動別後,探訪死後的世界,她認為這才算是她和母親緣分的最後一哩路。
當年少守寡、性格暴烈的母親病倒,李雁兒開始按下告別的開關,一併引爆出她的自我凝視。母逝之後,前往西藏潛修佛法,終結母親臥榻纏綿成繭寶寶的哀傷時光與病子懺罪之路。這個重新觀看自我與世界的方式,也是她要前進母親心靈的冒險新經歷。當抵達高原為母親畫天梯與畫唐卡,許多過去的點滴衝撞當下,過往的佛學人生受到現實的考驗與回應。
//
生死纏綿、氣勢磅礡的《別送》,帶著漩渦式的敘述,漩渦不斷地環繞著故里與他鄉,島嶼與高原,生與死,愛與欲,漩渦打轉如金屬陀螺,以此對應生命的輪迴,去而復返的意念與騷動。李雁兒伏地的雙膝蹲低,將雙手滑向土地的膜拜儀式,反覆去回,猶如不斷複誦經文,遙祭一次次地回到她生命的過去現場:嘉南平原、孤單童年、亡父、寡母、戀人們、高原……,像一場穢土地獄到淨土天堂之旅。
李雁兒環繞生死寫就關於許多修行者,如何從欲望的切離與和死神對決的逃脫;關於完全拋棄塵俗退隱山林的旅程;關於神話的歷程故事,這些未竟的未完成,多年以來已萎縮成母親,母親的生死難關內化成她的恐懼核心,幾乎就是她多年來關注的一切的凝結。
《別送》共分成「離開之謎」、「抵達之謎」、「留下之謎」三卷,在母親臨終之前與之後,來到西藏回望,母親最後的島嶼生活,表面彷彿她是等待母親的重生,事實是她超度的是自己的習氣與沾染的愛慾。
送別,成了別送,因為無法送難以別。
千里,送別。這回,別送。
作者簡介
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習畫。專職寫作,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
一個人周遊列國多年,曾參與台灣東華、愛荷華、聖塔菲、柏林、香港浸會大學等之國際作家駐校計畫。
曾獲中時、聯合、吳三連等國內重要文學獎。已出版多部旅記、散文、短篇與長篇小說。2011年出版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2020最新短篇小說集《溝》。
近年長居島內,筆耕「異鄉人」小說系列,此系列已出版2018《想你到大海》、《別送》。
目次
請不要盛夏走
【離開之謎】
一 受難經
ཨོཾ 等待離開的人
二 愛染經
མ 青春烈焰
ཎི 萎敗的密室
三 神經
པ 個人的神曲
四 七夢經
དྨེ 起霧時間
ཧཱུྃ 贖回的記憶
【抵達之謎】
五 遊步經
ཨོཾ 虧欠的旅程
ཨ 中陰轉運站
བྷི 塵埃落定
ར 夢中天梯
ཧཱུྂ 病僧
ཁེ 毒姑娘
【留下之謎】
六 髑髏經
ར 顛倒女人
ཨོཾ 神操
མ 死神埋下的時間記號
ཎི 只為一無所有
七 度亡經
པ 無常院
དྨེ 藏訣歌
八 心經
ཧཱུྃ 罪之華
回望○
書摘/試閱
保險員阿芳來到家裡的時候,看到她的母親,立即明白為何她會在生命的這個時間渡口想要買殘照險了。害怕沒有陽光的長照漫漫,只好先買如夕陽殘照之險。
生平的第一張保單,保單所羅列的身體可以補助的傷害部分,看起來像是一連串的身體精密儀器下被解構的物質,無言存在卻四處疼痛尖鳴著,看著保單彷彿聽見獅子吼口中常說的業力警報器。
身體比起所有的萬用字典或商業術語都要來得繁複,如一座宇宙,厚厚一本關於身體名稱搭配著各式各樣如星空銀河的手術,如顯微鏡下抹片細胞分裂的繁花異景。分流術、分離術、切除術、切開術、切斷術、造廔術、造口術、截除術、植入術、復位術、移植術、吻合術、造袋術、縫合術、整形術、修補術、重建術、剖解術、擴張術、閉鎖術、減壓術、穿刺放液術、迴路成形術,切割重塑修補擬造,有要擴張有要閉鎖的,人的身體不再是整體,而是節節支解成可供換算的保額積分點數。
身體如何是存在之詩?這些身體的字詞,滿滿印在保險單上,就像千佛萬佛,佛的各種名號猶如倒映著人心的渴望。無逃走神經切除術,無逃走?該逃走卻沒逃走的神經是什麼?失去痛反應的神經是因為逃走而不痛了嗎?
阿芳聽著笑說反正別生病,這些字眼都與我們無關。那買保險幹嘛?她又問。阿芳說,買來防萬一啊,萬一是千金難買早知道,果然是保險員如金玉良言的話術。母親是活生生的例子,她要防萬一這倒是千真萬確,母親什麼保險也沒有,連勞保都被母親怕太老會領不到而早早結清。保險不能保命,但或可保危險時的經濟救助。阿芳送她一枝原子筆,上面印著手機電話,像摩鐵旅館床櫃旁附贈的筆。阿芳就像所有的保險業者對保險有著奇異的執迷,深信可買未來的安心。她簽下保單,將首筆款項交到阿芳手上,完成此生此世對身體必要承諾似的慎重。
我的姊姊是利用保險獲得理賠的,姊姊留給小孩和丈夫一筆錢,她透過完美的一場精心設計,終結了自己,阿芳邊數著錢邊對她說。她驚訝至極,瞬間有種錯覺阿芳是在暗示她如走投無路可以臨淵一跳似的。正想問細節時,阿芳的手機響起,下一個客戶臨時改時間要阿芳火速前往。我知道妳很好奇如何精心完美設計,其實說穿了就是讓保險公司抓不到把柄。姊姊把車開向斷壁懸崖,看起來像是一場意外,但我到現場就知道是姊姊刻意的。她聽了覺得奇特,那麼精工於人心的保險公司難道不知道?因為沒有人比我了解我的姊姊。阿芳留下神祕微笑離去,那張神祕的臉,彷彿讓她看見阿芳的姊姊,決定一場精心設計的完美死亡過程,從出發到按下死亡倒數計時器,這阿芳姊姊是如何辦到的?為何自己沒辦法為母親設計一趟完美的死亡旅程?她吃著阿芳帶來的新竹米粉,目眶噙著熱湯的濕氣,夾起第一口如霜降的米粉時,淚滴了下來。明白和死神的交易,必須藝高膽大且心細異常,她代母親和死神交手多回,死神卻毫無提前到來的跡象。阿芳轉身,她突然明白死神不和執著的人交易,因為執著者如鐵球,瞬間就沉入苦海;只有空鐵缽的人,才能乘著水隨潮流而行。
她和母親都在等著將鐵球磨成空鐵缽,倒盡這一切。
3
隨著復健無望,母親不再需要按摩師,母親需要的是度亡師。
到處都有按摩師,度亡師卻難尋,度亡師要有經驗,但度亡師的經驗如何經驗?那個控告父母將他生出來前沒有經過他同意的新聞聽得她直嘆世間無奇不有,新聞奇花異草下的浮生亂世某種程度也讓她安頓,知道原來她的生活仍是可喜至尚未被崩壞。那個被質問的父母說,我去哪裡徵求你出生的同意書?必須有勞神鬼辦案,問問度亡師。
按摩師則不用問,按摩師的手一摸,彷彿探視器,視障者的眼睛全長在手上。
最初母親歷經整年推拿按摩的舒筋整骨經絡舒通與針灸電療,甚至去嘗試蜂針治療,她想要喚醒母親死去的神經,但當她看著蜜蜂的頭部被反覆擠壓而露出防衛性的尾部螯刺時,她心裡開始後悔,接著蜜蜂的毒針像針炙經穴的針器具扎進母親的皮膚,伴隨母親的尖叫聲與淚流不止,她看著母親手上虎口跳動著白色的球囊,中醫師邊說著球囊裡面就是蜂毒,正在一張一縮的推動毒液進入體內。母親的淚水瞬間真是鑽心,她忙跟醫師說不治療了,失語母親才停止流眼淚。
母親的運動神經沒被喚醒,卻加強了痛覺神經。她夢見亂竄撲騰的蜜蜂倒鉤拉出自己的心臟、腸子時嚇醒,起來開燈,跪著念經,邊懺悔邊迴向給白日因母親而死去的一隻隻蜜蜂,兩三隻蜜蜂就讓她投降,母親怕痛,她是看母親痛而痛。外力種種只徒增母親劇痛,而身體仍是故障。
其實真正需要按摩的是女兒,她的腰肩舊傷,按摩師彷彿是通靈師算命仙,一摸就成精地知曉身體的疾病史與傷心史。捏、掐、頂、戳、彈、擠,她的身體是刀俎下的骨肉。故障的右手關節,逐漸冰凍卡住,骨肉沾黏,骨肉不分。長年支撐她身體的骨架脊椎也幾節反錯扭絞。按摩師有如摸壁鬼吸血鬼,不是吸吮她的皮就是用擒拿術鎖住各個穴道關節。回顧這歷程,所經歷的江湖奇人異士,各種奇怪曖昧的空間,散著中藥補血補氣的蔘薑枸杞味道。她買過各種療程與儀器。試過原始痛點棒、蒸腳機、氣血機、電療、針療、氣壓衣、高壓氧機、遠紅外線艙。她去了各種奇異的國術館與養生館,那些月入百萬的師傅,談笑風生或評論時事的瞬間就把她的骨頭折了幾下,才上午號碼到她已三十幾號。她和那些骨頭彎掉的人並坐在藍色塑膠椅子上,像是垮掉的故障人列隊等著秒殺送修。
那間靠近車站的一間地下室,生意好到要抽牌的國術館,就一個師傅和兩個助理,拿著木製鐵鎚敲打著她,兩個助理架起她,把她的手拉起再硬推,就像卡榫歸位。當晚讓她痛到覺得手像是被對折過的劇痛,三分鐘六百元,接著拿了一包很像羊屎的黑色藥丸給她,她還在套鞋子,下一號已躺上床。她想要問自己究竟是怎麼回事,師傅早已不理只管忙著下一位。某一回她又聽到有奇人奇術可以治療骨頭疼,診所滿滿像是朝香團,上午來到時號碼竟已一百多號。醫師手裡拿著像釘槍的電動器具,往人的身體像牆壁般釘著,整間診所像是股東發放產品大會。每個空間都有人,坐的位子更是有人起來就立馬有人搶入。長得像釘槍的脈衝光像衝鋒槍地釘著,感覺只是鬆開肌肉,對她的沾黏似乎無用。至於其他常見的泰式按摩腳底按摩復健科電動鐵床拉腰或拉頸椎,針炙、電針、拔罐、埋針,早已如喝水般的普通。
那些為縮小骨盆縮小腰縮小臉縮小腿而來的美眉們和因受傷而來的人,一眼就可判讀分別,美眉們總盯著手機瞧,疼痛不關她們的事。不若她和等待受刑的人總盯著床上的身體瞧,想從別人的疼痛現場暗示自己疼痛並不可怕的幻覺,聽著別人的哀號也舒緩了孤單與疼痛。
那個林森北路按摩雙人組,妻子負責抓腳,丈夫按摩全身。說是獨門獨派祖傳功夫,氣功了得,按摩時會灌注一股真氣,鬆解所有的氣血堵塞。氣血堵塞則病灶生,氣血一通百病癒。那時她和還沒倒下的母親走在中山北路,楓香樹影秋光日暖,母女兩人走在起風的下午,秋陽從枝葉中篩漏光影,那時她好想和母親一直散步下去,那是她印象中少數幾個和母親悠閒同行的美好時刻,沒有碎語沒有怨語,靜靜走著,朝目標踱去。
母親那天穿著一件暗紫色輕薄型毛衣,毛衣靠近肩頸繡著彩翼蝴蝶,蝶翼上綴滿小水晶,秋陽下閃爍燦爛流光。她沒意識到母親當時的身形是傾斜的,走路歪向一邊,一直撞到她的右背膀,於是她換走到母親的另一邊,但又覺得母親靠馬路走很危險,於是又走回原來那一邊,母親繼續每隔幾步就撞著她的右臂。(後來她回想起來心裡充滿歉意,如果當時牽著母親的手走就可以免去這樣的左邊右邊皆不得的窘境,但她們不習慣碰觸,那會像炭般地火燙。她無知於彼時神遺下的記號,給予她母親走路傾斜的疾病暗示。)那日的秋陽樹影成了回憶川流的岸上風景,錯身的台北都會女性的亮麗和她們母女的暗色調形成對比,彎曲傾斜的母親時不時就轉頭對她說著妳怎麼不穿漂亮一點?穿靚亮一點?妳看看別的女生。她聽了笑著沒回話,她一輩子沒穿過窄裙套裝高跟鞋,她不屬於這樣的打扮,但母親總是非常期待女兒打扮很流行時尚(許久之後她才明白隱身在集體流行洪流裡是如此輕盈,走在路上和所有的集體陌生人如雨融海,毫無邊界),打扮這件事深深影響著母女的感情,她當年經常莽撞回話,言語如手榴彈,把彼此的心炸成碎片。
按摩店位在最熱鬧的色情酒店與旅館充斥的七條通鄰近的窄巷,拉著行李入駐日租屋的旅客川流在機車陣中。老舊的大廈電梯上下時就像喘氣的老人,出入的多半是住套房的金絲貓仔,夜晚在鄰近七條通上夜班的女子和她們這樣的母女打照面,眼皮浮腫,散發貓羶味。攢食查某,母親低聲說著,口氣沒有鄙視,倒像是跟女兒解說這世界充滿五色人的口吻。
那回母親被雙人按摩組按得哀哀叫,按摩男師傅笑說妳是肉在痛,還是錢在痛?捨不得花錢。都痛,都痛,痛死了,她的母親又哀哀叫地回答。後來母親不願去,她幫母親付錢也不去,母親說真是太痛。母親曾偷偷問她,那個按摩老公有偷吃妳豆腐嗎?她笑說沒有,怕媽媽擔心。起初因為覺得被按了真的身體有轉好,但日久卻因為再也無法忍受那語言的暗示侵入與手的調情偷渡。男師傅有回說,我這手法對女生身體特別好,因為我的陽氣灌到妳的陰體上,又悄悄邊按邊說妳要身體好,要觀想和我做那件事,這樣妳就可以獲得滋潤。她笑著假裝沒聽到,身體卻抗拒地搖著,男師傅感覺到了竟說沒想到妳這麼保守。那次她忍住按摩整個結束,換衣服時,她就決定再也不來,心靈忍受著騷擾,身體也不會好到哪了。
男師傅說他小時候看見過阿公打坐的身體浮起來,當時躲在神桌下,不敢喊阿公,怕一喊阿公就從空中掉下來。她想這阿公沒有教孫子在按摩時千萬不要逾越或若有似無地碰觸女生私處?自此她不再讓任何男性按摩。滿街暗巷懸掛著養生會館、日式中式泰式按摩、經絡推拿、腳底按摩民俗療法、雙乳壓油壓指壓、芳療紓壓,走進去彷彿動輒要刷上萬元被扒一層皮才能離開的店家總是讓她害怕,想起之前傻傻走進去以為一堂九百元,按摩一半卻不斷兜售好幾萬療程的擾人,幾乎是快速穿上衣服匆匆套上鞋子狼狽地離開。心志不堅時,刷上兩三萬元也是曾有過的事,買課程之後要預約按摩時間往往困難如買明星演唱會的票。
她曾陪母親跑過一些奇怪推拿店,推門進去時感覺就像遇見老派揚州老師傅,男人多半精瘦細膚,女人一身硬頸硬骨,帶著江湖氣。後來她才理解母親不再去七條通那間按摩店是因為母親不喜歡給男人按摩﹐母親守寡多年,對不管各種年齡層的男生總是心懷抗拒。抗拒就按不好,就跟她後來抗拒語言的騷擾一樣,即使手藝再好都無法承受。母親喜歡給台灣老阿姨按摩,因為聊天可以轉移疼痛,其次是大陸女人,偶爾才接受泰國女人。母親也不選太瘦或太胖的,太瘦如南洋曬傷的那種烏溜溜女孩讓母親沒安全,但又嫌那種胖女孩爬上按摩床在脊柱腰椎踩踏時會心慌慌。在那黑暗的密室裡,她有時會陪著母親,手握著母親,陪伴母親勞頓的身體如舟子般地翻船漏水,被拗折反剪倒扣時發出的尖叫哀號。
那是她和母親以身體交換親密的一段苦時光。
身體軌道因年久失修而散碎漂浮的零件得以在短時間裡被拼圖,女人們彷彿像太空機械的手臂馴服著骨與肉。最可怕的是推拿師傅為了知道哪邊氣血不通,朝背部的針灸或用十幾個玻璃盞吸住血肉的拔罐,大約類似被水蛭或食人魚的囓齒咬進血肉的痛,讓母親汗流浹背,咬牙切齒。最後一著是母親被推拿師傅用膝蓋將其臀部頂了起來,把母親嚇得像是背後有個看不見的魔抓住她似地放聲尖叫。母親起身之後,發誓再也不來。
她自己一個人去體驗時,以為母親先前經歷的這些已是疼痛之最了,哪裡知道師傅竟說她的身體用針灸沒效,要用小圓針才行。小圓針是一種針刀,立面如圓刀,切進肉與肉的筋脈,她被切二十六刀,一刀竟索價五百元。她癱軟離開那間中醫診所時,首次有解離之感,靈魂與身體的解離,走回停車場,連車的方向盤都無法握,手腳分離斷裂感的窒痛一波波襲來。
母親後來在小診所醫生的鼓吹下,朝腰間最痛的點打消炎針解決,就像母親年輕時連治療蛀牙都嫌浪費時間,竟致直接拔掉,老年一口牙也沒有,拔掉牙的老虎,除了語言繼續吐出火焰,其餘只要她轉身就再也傷不了她。她想連大象都因不想被拔去象牙而開始演化成無牙之象,人類演化過程,為何無法除去疼痛?
4
深海般的車站地下層,人潮來往的美食地下街,角落擺著一整排椅子,背後站著身穿白色制服的盲人,等著路過的人停下繳上百元伸出頸肩給一雙陌生的手按摩捏掐,那些把頭擱在椅子上的人穿著染上一日疲憊風霜的白色襯衫,期望百元十分鐘可以獲致短暫的舒服幻覺。她每每經過時覺得這些人像是表演的列隊者,重複的疲憊川流在一座大型車站的地下道,暗無天日的地下道連結著管線似的通路。沒生意時,盲人像是靜默的雕像,帶著墨鏡如深海的魚群,也像街頭表演者。巔峰時間,他們又像是開武林大會的對決者,進行著快手練拳的反覆動作,朝每個肩頸趴伏者下各種按捏掐的重手。流動的人群與靜止的盲眼按摩師並置,恍然一邊是深海洋流,一方是失去光反應的魚群,快速與慢速的極端運轉中,突然有流動的洋流轉向靜默的盲眼深海時,盲眼按摩師瞬間以觸鬚探觸身體,通道裡任何的聲紋,都逃不過聽覺敏銳如雷達的盲眼按摩師。
她看見一個沒有戴上墨鏡的盲眼人以濁白眼珠望著她,她知道那是錯覺,那盲眼人什麼也沒看到。但她突然瞬間如魚被鉤挫殤之感,那濁白眼珠竟像極了母親。她想起聽見母親哭泣的那個清晨,她起身拍著母親,用手揮舞在母親眼前時,母親的眼睛沒有反應,母親應該是發現四周一片昏暗時大哭了。母親那張像是未完成的雕像容顏,混濁的瞳孔裡窩藏著一潭深水,她躲進去避開夏日過度曝光的刺目之光,在地窖般的千古黑暗中尋覓一絲母親的光。不可逆轉的失明,一旦失去就永遠失去的殘酷,她多麼想給母親一丁點的視力,一點微火。她要媽媽別怕,女兒的光還在。
在靜謐的甬道密室裡,一整排如剛砌下大理石的那種待形塑的臉龐,隱沒在森林藤蔓纏繞黑穴裡的青苔,穿著白色制服的盲眼師傅們聽見推門有人走動的聲音紛紛豎起兩張耳膜。她停在這個有著像母親濁灰白眼珠子的人面前,盲眼洪流裡唯一不戴墨鏡的裸臉者。她指名要讓這個人按摩,遞給推拿店老闆百元,坐下後,將頭靠在鋪著不織布的洞口,臉面朝下。她發現洞口的地上擱置著一盆小小的多肉葉仙人掌,讓無聊望著地面的人可以把眼光停在仙人掌上,或許也是轉移疼痛的方法。她聽見身後這個眼白混濁阿姨按下碼表的聲音。妳肩膀很硬,阿姨聲線粗啞。按摩話術都差不多,不外很硬很彎很錯位很沾黏。濁灰白眼阿姨將指勁摁進她的頭頸痠麻穴位,放鬆後扭動著她的頸部。喀嚓一聲,骨頭錯位瞬間回正。碼表響起,時間到了。按摩的疼痛與舒服結束,鈔票奉上,身體繼續傾斜,沾黏,冰凍,無法旋轉。十分鐘像是快速奔馳而過的飛船,眼白混濁的阿姨問要不要延長啊?她抬起頭,臉上還沾著不織布,扯下不織布遞給阿姨,她搖頭笑著說了聲謝謝。下一個號碼很快就遞補上來,像是百元剪髮。所有服務身體的事情都轉變成固定模式與精簡的計費時間。她用不疼痛左手抓抓右肩,感覺還是硬梆梆,身體仍像是走動一只肥肥企鵝的時間之海,等待傾倒沉積的心靈垃圾。在車站巨大的停車之海,她找到自己的小舟,等待取車繳費時,她看見大學時同在佛學社的老同學,一個很久不見的所謂同修,但同修早已不同修。
好久不見,她打招呼著。那同修卻有點不想跟她多說話的感覺,只淡淡說,慚愧了。她頓時知道他的意思是這段時間沒來,退步而慚愧了。她正要回說我也很久沒去時,他卻急忙轉身下樓。她本想安慰他每個人都有不同時期各陷落於世俗的狀態,或短或長,或者永遠不再來者也是極多。且那些突然不來的人往往最初都是最精進的學生,他們期望高,一旦失望也就迅速退場,學佛場有時也如股票交易場,來時像火燒,走時像灰燼。心靈需要復健期,有些人進入漫長亂投醫的狀態有時竟至綿延一生,最終只是成了一輛心靈拼裝車。心靈史就像按摩史,每個人都各有偏方進入身體的歧路花園。
5
繞著母親色身轉的是汗水,熱天裡臥床者的色身總濕透了床枕;到了冬日,手腳轉僵硬,縮成剪刀手,觸摸如冰塊。起初固定來家裡的陌生人有居家護理師、針灸師,還有一位幫母親從醫院按摩到家裡的盲眼人。盲眼人每回來總像一個明眼人地說著她的房子陳設,說著她掛的神像是誰,說著她母親的手掌紋路圖,盲眼人解讀其中的密碼謎團,說著她的母親很捨不得走。
盲眼人一直想幫母親復健手腳,但卻沒有辦法防堵不斷在吃掉母親身體的病菌, 菌去復返,臥床者的大敵,色身準備投降。於是很多的角色即將落幕,隨著母親啟動最後一場告別的來臨。採買工拍背工沐浴工打掃工朗讀工陪病工,隨著母親即將離宴人世而將告別的分裂自我。當這些疲憊都成了身後事時,她知道日後將常想念起這些因為母親才擁有的奇特身分。
最後一個來見母親當時還能張開一絲目光且手腳尚能微動的陌生人是居家復健師,長照方案的一點點福利。那個個子不高老是帶著微笑的復健師是母親唯一出院後見到陌生者會微笑的人,但那回她來,似乎知道這將是最後一次來幫她的母親做復健了,彷彿心裡回響著這是最後一次的回音,以後不再見面了,於是復健師所有的聲音與動作都被放慢,很仔細地按著揉著。她怕母親躺久不動變成剪刀手剪刀腳,還請另一位自費的盲眼按摩師來家裡,這盲眼按摩師很願意到府服務,即使她知道媽媽不喜歡給男生按摩,但她想盲眼人什麼都看不到,色身應可跨越那條難堪的界線吧。母親沒有復健希望,逐漸地針灸師復健師護理師都退位了,最後只剩下盲眼按摩師還願意撐起母親的病體。家裡沒有人走動,又恢復深海般的死寂。
這盲眼按摩師身體頗壯,看起來像是可以爬一百零八層刀梯的乩身靈體,在神明出巡的陣頭之前,吞火球刀刺背的人。他說起自己是三十幾歲才眼睛瞎掉的,是一個眼睛光明時到處遊玩的匪類人,所以什麼樣的身體極品也都玩過。她聽了自己就更不給這個男盲眼師按摩,對男按摩師的戒心依在。雖然這盲眼師暗示過很多次可以按完她的母親之後換按她,母女合起來且只收一千元。她笑著沒有接話,且因聽過盲眼師曾跟母親附耳說阿嬤把汝查某囝嫁乎我好否?雖是玩笑話,但不知為何她覺得這玩笑話聽起來比真話還真。也許連盲眼師都感覺到這屋子的空蕩蕩,一間沒有男人氣息的屋子,盲眼師故而探視地說鬧著。
盲眼按摩師幫她母親按摩,她在旁邊看著,說是看著倒更像是盯著盲眼按摩師手腳乾不乾淨似的,那盲眼按摩師也總打破沉默地邊按摩邊和她說著話。
妳的書很多,每一本都有看完嗎?你怎麼知道?她覺得奇特。我聞到很多紙的味道,他說的時候,正把母親按得哀爸叫母。母親的眼睛翳灰,瞳孔因痛溢著淚光,眼裡求饒地帶著怒氣。彷彿說著我再活能有幾年,為什麼妳非得這樣讓我受苦?她退到床的後邊,不敢靠近母親。妳看這麼多書,但仍然常感到灰心無力?盲眼按摩師又說著。沒等她回話就又說著妳的唐卡最好去裱起來,藏式唐卡佛像裱在卷軸上容易受潮,最好改成壓克力框。連客廳牆上掛著唐卡他都知道,她想著這人根本沒盲。你又聞到味道了?你聞到我經常焚香這不難,因為空氣到處都是香塵殘存的氣味。但要知道我掛的是唐卡,這就很難的,我可能擺的是立體佛像也可能是玻璃框的佛像,但知道我掛的是比較少見的西藏唐卡,除非你觸摸,不然不會知道。
其實我是猜的,因為妳燒的香是藏香,一般會燒藏香的多半懸掛唐卡。當然也可能是裱立體框而不是卷軸,只是憑直覺,覺得妳會喜歡卷軸,比較古典。
又何以知道我比較喜歡古典?
妳的傢俱偏木質氣味,且是老木頭的香味,這種人大概都滿古典的。盲眼按摩師忽然低語說著唐卡上的佛像是準提佛母,妳修持得很好。她聽了驚詫,盲眼按摩師怎麼如此精確地知道上面掛的是準提佛母像。就是要猜也會猜觀音菩薩或阿彌陀佛,很多明眼人看過她懸掛的佛像還無法分辨是千手千眼觀音或是準提佛母。盲眼師還說這張唐卡將準提佛母十八臂各臂或結印或持劍或捻數珠或舉金剛杵等物,十八樣寶物,繪得栩栩如生。
她聽到盲眼師在按摩時邊念念有詞,念咒似地念著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縱然不斷酒肉妻子,只要依法修持。無不成就。準提佛母,簡直對世人太寬容。她聽到末句不斷酒肉與妻子時笑了,世人生活照舊如常,慾望如常,卻希望自己的福報是強大升級版,裝載著抵達淨土的各種超載具功能。
她聽著盲眼按摩師倒背如流的佛言佛語,一時竟喃喃自語地說著希望母親不要再延壽了,這苦吃太久了。
盲眼師聽到了笑著往門外走時說母親延不延壽不是看妳,也不是看佛。
她覺得這盲眼師根本不是盲眼人,倒像是有著二十七雙眼睛的千手千眼觀音。
那你猜猜我長什麼樣子?她笑說。
那我得摸妳才知道,盲眼按摩師笑回。
她聽了忙轉話題,你按摩我母親全身,那你說我媽媽長什麼樣子?
妳媽媽身型偏中胖,腿漂亮,個性不是屬於秀氣的人,頗大氣呢,可惜妳媽媽脾氣很急,煩惱很多,摸起來總是手腳冰冷,頭部卻熱脹。
她聽得猛稱是,覺得這盲眼按摩師根本像是一個卜命的摸骨師。
妳要我幫妳按摩嗎?盲眼按摩師又問。
不用謝謝,她快速回著。
盲眼按摩師聽她忙說不用也心知肚明地微笑著。
他笑著嘆口氣,彷彿是可惜啊可惜啊。妳長得滿好看的,尤其有一雙閃著星子般的美麗如湖水的眼睛。她聽了突然有種感動,在這樣如荒原般的房子有陌生人傳來溫度,即使是曖昧的語詞竟也是可喜。
他每回剛進到屋子,常要她形容住家的河邊風景給他聽。
有一回她沒說窗外風景,倒說了手機收到不斷轉傳的勵志故事。有一個盲人在街上乞討,盲人在板子上寫說我看不見,我是盲人,我看不見,請你們幫助我。有個女生看到他板子上寫的文字, 就上去幫他改了文字:我看不見你們所看見的,所以請你們幫助我。改了意思完全就不一樣,不是看不見,只是看不見你們所看見的。
你看見很多我們看不見的東西,她邊說邊遞給盲眼按摩師七百元,他來家裡按摩母親一次的費用。他接過,不用摸就知道的數字。盲眼按摩師潛入這座寂靜如深海的空間,每周一回,甚至母親因敗血症住院時這盲眼按摩師也沒間斷地去醫院病房探望母親,但也是那個時候,她跟盲眼按摩師說母親出院後就不需再按摩了,因為敗血症把母親最後的眼睛餘光也吞噬一空了,我想讓母親就安安靜靜地過完餘生,且每回按摩其實我媽媽都很抗拒,媽媽很怕痛。
盲眼按摩師聽了點頭,然後他用手摸了摸她母親,彷彿在道別。接著杵在她面前良久,無語,彷彿那看不見的眼睛窩藏著一團火。
盲眼按摩師拄著拐杖離開病房,拐杖聲敲擊著地磚,蒼白的鎢絲燈下身影孤寂,他背後好像長出眼睛似的,突然轉身朝著還杵在大門口望向他的她揮手道別。
又一個轉身自此不再相見的人,最後一個撤退母親這場不斷拉長戰線的人。所有的醫病關係,走到盡頭時,不說再見。
這最靠近母親身體的一師也撤退了,度亡師還遠在天邊。最後的訪客離開,她又回到習慣的寂靜空氣。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