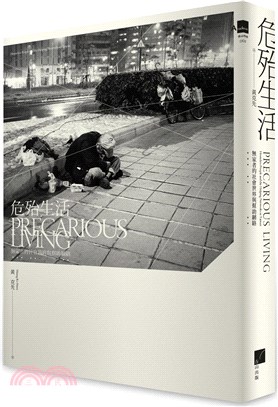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
商品資訊
系列名:春山學術
ISBN13:9786269500369
替代書名:Precarious Living: Homeless People and the Helping Networks in Taiwan
出版社:春山
作者:黃克先
出版日:2021/11/16
裝訂/頁數:平裝/408頁
規格:21cm*14.8cm*2.5cm (高/寬/厚)
重量:496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找到掩蓋在表象下的底層秩序,看見無家者間豐而危殆的互助網絡
臺灣無家者現場的都市民族誌
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一群芝加哥大學社會學者抱持著「把褲子弄髒」的實作精神,深入城市中被認為失序的地域進行參與觀察,發現舊有社群雖逐漸凋敝,但新的連帶卻不斷形成,各鄰里基於不同族裔、職業或社交次文化,發展出大都會的多元樣貌。
這種「在表面失序的邊緣人群中,發現不為主流所知的生活世界」 ,後來一直存在於社會學的傳統中。過去被認為如動物般活著的邊緣者,他們在內部擁有自成一格的次文化及社會秩序,互動也展現了特定規範與價值;而在種種「偏差」、「失序」行為的背後,其實也隱藏著人們所共有的愛、渴望、尊嚴、互助精神及意志。
基於這樣的學科訓練,讓作者黃克先認為在無家者孤離的表象下存在著真實的生活連結;他們棲宿之地看似髒亂,卻是這個綿密且立體的社會世界運行的空間。
本書以在艋舺公園從事的民族誌為素材、從連帶分析的角度切入,呈現無家者在工作、休閒、親密關係、社交上,如何運用豐富且多樣的連帶,滿足精神與物質上的需求。但是,因為不確定性高的露宿環境、不穩定的經濟生活、社會汙名及歧視、制度性支持的缺乏,使得無家者之間這些豐富的連帶較一般人更顯脆弱。同時,圍繞著他們的幫助網絡,包括宗教、國家與「善心人士」,雖然提供物資與服務以供急難所需,但在互動中也傷害他們的尊嚴並扭轉其自我認同。最終,不穩定且帶著貶義的連帶,連同窘迫的物質生活與絕望的存在感受,讓無家者的生活更形危殆。
本書呈現無家者的生命歷程與社會生活實況,更交織了一位研究者的反身性思考,除了描繪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也點出善意提供協助的一方應有的反思,同時試圖提出面對臺灣無家可居問題的政策建議與行動方案。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呂秉怡(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副召集人)
阿潑(文字工作者)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林迪真(荷蘭籍宣教士)
林瑋嬪(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施逸翔(臺灣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孫大川(前監察院副院長、「貧窮人的臺北」發起人)
張獻忠(芒草心協會創辦人)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
鄭麗珍(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趙彥寧(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
謝國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作者簡介
黃克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議題涵蓋無家者、華人社會的宗教發展、政教關係、基督宗教,研究專長包括宗教社會學、都市底層研究、質性方法、微觀社會學。曾發表於多篇期刊論文於《臺灣社會學》、《臺灣社會學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Social Compass。曾翻譯社會學名著包括《人行道》(與劉思潔合譯)、《泰利的街角》、《真實烏托邦》、《自由之夏》等。
序
導論 走近╱進看不見的世界
孤離的獸般存在?
「人是社會的動物」這句話我們總會掛在嘴邊,順手拈來解釋人間百態,無家者卻是人中特例。這個社會普遍認為無家者不存在人際連帶(interpersonal ties,後文簡稱為連帶)。此共識不只存在於大眾媒體、學術文獻上,實際接觸過無家者的社工或志工,甚至包括無家者自己都這麼說。少了人性中的這一塊,無家者在他人眼中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二○一六年初夏的某日清早,我跟著芒草心同仁及志工,來到了土城看守所,迎接一位協會服務過的阿漢出監,當初入獄是因為出借身分給他人公司報稅。
阿漢講話幽默風趣,為人豪爽,個性溫和,接觸過他的人很容易被他吸引。我們拿著「歡迎阿漢回來(阿漢兩字上還撒金粉)」的布條,看著一個個出監的人走出,一旁的社工聊到阿漢為何會入監,主要因為缺錢、人又單純,才鋌而走險當人頭,最後出事了卻被當防火牆,仲介和背後的老闆卻都沒事。「但為何像阿漢這樣的人特別容易受害?」我心裡想著。
阿漢出來後抽了兩根菸,在我們陪同下回到住處外熟識的小攤一同洗塵,吃豬腳麵線脫脫霉氣。席間一位因芒草心活動而認識阿漢並持續幫助他的男性,知道我是想做無家者研究的學者,便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他平時做著專業白領的工作,休假時會到艋舺公園坐著觀察這些人,也幫助阿漢好一段時間,會發現「為什麼阿漢這樣流浪十幾年交不到一個朋友?大家平常一天到晚都坐下來喝酒稱兄道弟,但骨子裡想的都是偷到對方的錢及利用對方,一轉頭就開始很生氣地罵對方。」這樣的說法,讓我想起另一位在芒草心服務的社工,不久前他騎車送我回家,評論起服務的前無家者狀態總是起起伏伏,即使找到不錯的工作也難以翻身,他認為缺乏社會支持是重要因素。我也看到另一位長期投身無家者服務的社工,以「遊民最缺的不是錢 而是真實的生活關係」投書,反省:「我們提供了所有我們看見遊民缺乏的資源,包含餐食、居住、醫療、就業,但是就是少了一項:『真實的生活關係』。」 所謂的貧窮問題,不單純是因為物質匱乏,而是被公權力認定為社會關係的匱乏,這不管在東方或西方皆是如此。
無家者,不管在大眾媒體鏡頭下或書寫中、將之視為都市之瘤或犯罪淵藪的人們心中、認為他們是無辜受害者的一線工作者眼裡,他們的存在是原子化的,身形是孤離的。提起無家者這個字眼,腦中會浮現的多是一個人落魄倒臥路旁,或是蜷曲著身子瑟縮在角落的身影。這群人在身處的環境中,無力採取行動或開展關係;即使真的有行動或關係,也只是表面或虛假的。他們能做的,只有被動受人處置、取締、驅趕、同情、協助或供給。這種對無家者的理解,也出現在針對無家者做過的學術研究中,它們雖破除了一般媒體或社會大眾對於無家者汙名化的想像,標示出了他們是特定結構之下的受害弱勢群體,他們的存在或被視為是待修正的社會問題,或被當成展現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規訓權力的工具,是社會重重排除下的犧牲品。
如此一來,無力建立社會關係的無家者,似乎不會也不該是社會學研究的題目。「如果社會學能教大家就這麼一件事……就是:我們總是在一個比我們自身更廣大一點的世界參與著社會生活。」是我教授社會學導論第一堂必定提及的一句話。 但是,無家者不是林中樹,卻像荒漠裡的一根孤木,在人來人往的都市叢林裡孤單立著;他們無法參與社會,只能被動授予。
離開阿漢的住處,我來到了他以前睡過但如今在導覽時喜歡諷為「動物園」的艋舺公園,坐在柱旁。阿漢是這麼語帶嘲諷,又讓人聽來有些心酸地說:「裡頭的人醉生夢死,都是動物,都是畜牲,哪裡有人?沒有。」但也直說自己以前就是這樣,「睡在那裡,那一格裡。」這個號稱全臺使用率最高的公共空間熙來攘往的人們,有從捷運站出來要前往龍山寺參觀的外國觀光客,有拿著紙討論我不瞭解的數字的白髮老人家,另一頭則是一群群聚集下棋及在旁觀棋不語的人們,還有眼前其他柱旁與我相對而坐的無家者,彷彿石化般,一動也不動地默然坐著。他們沒有歷史,沒有社交,缺乏關係,只是食色性也的獸般存在,身處一片沒有秩序的野性叢林裡,等待著救贖或正在沉淪,唯一的渴望是吞噬別人或等著被吞噬。
但,真的是這樣嗎?(未完)
目次
導論 走近╱進看不見的世界
第一部 無家者的社會世界
第一章:無家者的勞動:喧囂的工作樂園
第二章:如何走向無家:與原(生)家庭的距離
第三章:打造新家庭:伴侶關係及擬家關係
第四章:公園作為社群:互助與較勁並行的道德經濟
【插曲之一】有生命的連帶
第二部 無家者的幫助網絡
第五章:與宗教的相遇:理想信者的形塑
第六章:與社福體制相遇:主流價值的鞏固
第七章:與「善心人士」相遇:幫助他人的象徵政治
【插曲之二】一同走在回「家」的路上
結論 危殆生活
Just about Anything Looks Better?
【附錄一】政策建議與行動方案
【附錄二】研究方法與限制
【附錄三】關於無家者的讀物或影視作品
謝辭
注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第四章 公園作為社群:互助與較勁並行的道德經濟
K哥幾個月前來到公園露宿,住了兩個月遇見住附近願意接濟他的朋友,就搬去同住,但他仍愛待在公園直到深夜才回去。主因是菸癮很重、口袋常常連買菸錢都沒有的他,待在公園不怕沒菸抽,但待在朋友家卻常會面臨菸不小心抽完,又找不到或不好意思屢屢向朋友借的困境。他曾好幾次半夜從借宿的朋友家醒來發現沒菸抽,又步行十分鐘回到公園來跟人借菸。有天,K哥的菸又抽光了,他走到公園住民阿嬌姨前面,問她有沒有菸。阿嬌姨號稱公園有求必應的「媽祖婆」,只見身上沒有菸的她起身比了個五,示意稍等個五分鐘。她優雅緩慢地朝公園東側長廊前去,我以為她是去東北角的7-11,但過一會兒她卻自西側回來,面帶微笑且瀟灑地「變」出一整包菸給K哥。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這不是一包在附近便利商店買來完整密封的菸,而是用萬寶路的菸盒拼裝近十種不同廠牌的菸,原來,阿嬌姨繞著公園走,見認識的人就開口:「有菸嗎,分一兩支。」這樣的資源或服務的互通有無,在公園時時可見。有時是便當、餅乾、素菜、飲料,有時則是看顧行李、跑腿買檳榔、修理手機,或是傾聽對方訴苦。
一般外界總認為公園是都市失序的危險地帶,其間的無家者是原子化、獸般的存在,亟需外界施加柔性的善心救助或硬性的強力管制。但從阿嬌姨行腳繞圈變出的這包拼裝菸,則以物質形式具現了在這樣的空間中,看似分離的無家者們,彼此之間乃由看不見的連帶串接而成為一個社群。在其中待久了便會發現,公園裡的住民由於物質生活條件不佳,許多生活所需物品、必要資訊或協助,都必須藉由互助、交換取得,所以無家者之間建立連帶十分快速。
我幾次目睹一位公園新成員,才來沒兩天便融入這裡的生活,與其他人聊天時像認識很久一樣。而所謂「新」成員,很多其實都是長年流浪或位居底層生活的熟面孔,他們或因工作關係遷移或種種人際因素而暫離公園,或曾與其他公園住民在過往職場或各種扶貧場合、機構 中照過面。儘管他們並非持續且長期待在公園裡,但也深知艋舺公園聚集了許多相互熟識且能幫助自己的底層人士,並存在著豐沛的幫助網絡,因此偶爾會來此處走走,有人就此長住下來。
乍看之下,這個公園的界線不甚清楚,似乎常有新舊面孔來來去去,裡頭的人顧自己都來不及了,怎會有餘力顧及別人,遑論形成一個互助社群。然而,公園雖不是那種基於相同血緣、地緣或功能而形成界限清楚、成員固定、互動頻繁且關係緊密的共同體,但確確實實透過日常共同進行的交換實作與持續的互動,逐漸形成人際間的連帶所疊成的社會性群體。
席地吃喝與媠氣
席地 聚集喝酒並搭配食物,是公園無家者最常見的社交活動,在每天下午五點起會陸續見到有人開喝。公園附近的教會,牧師在講臺上常喜歡在講道時聊到為何淪為無家的道德觀察。有位牧師說:「萬華朋友百分之九十都是被酒捆綁住,酒一喝,誰也不認識誰……你們要捨棄喝酒!酒,帶來是非。你們能不能戒?」一位熟悉公園生態的無家者,也私下告訴我公園是個大染缸「讓人沉淪」,最大的原因就是養成了群聚喝酒的「壞習慣」。服務遊民的社工也常視酒癮為阻礙其達成個案工作目標的重要因素,近年來也特別在遊民社會工作訓練中,聘請醫院精神科醫師教授「藥酒癮戒治」工作坊。然而,這種將席地喝酒活動問題化,把它視為妨礙脫貧、脫遊的因素,看不到它背後隱含著一種人際間的情感交流與社交秩序,過程中參與者投射並實現他們特定的價值與想望。以下討論並非為無家者飲酒的行為提供正當化的理由,但確實想強調,我們不應視無家者的飲酒行為為單純的個人選擇,以此證成「他們的貧窮處境是自作自受」的道德批判。
第二章提過的小學即逃家的金毛,是我在公園認識的年輕住民之一,年約四十的他以前做過工、當過清潔隊員,如今靠出陣頭、做金屬回收維生。他十年前在臺北流浪時曾在大樓當保全,某天在捷運站內偶遇也獨身在大都會討生活的小學同學小苓,當時小苓在萬華跟著這裡的角頭生活,金毛便隨著小苓來此依靠同一位大哥,兩人並結婚共同生活。他們經濟狀況不好,有時睡網咖、有時睡公園、有時睡其他兄弟家,近半年來夫妻都有工作,便在附近租房子,平常仍在公園逗留。只是,最近幾週我鮮少看到金毛,在三月初的一個夜晚,見到他才知道,他在避風頭。金毛說:「公園不是說來就來的,公園仇人多的是……」他說之前離開,是因為有個醉漢嗆他:「你現在都靠勢(khò-sè,意指依仗、依恃)你老婆啦」,被說吃軟飯的金毛不開心,便叫兩個壯碩的朋友來「請」那個人「去喝茶」,對方放話在公園再見到他就要報仇。
既然如此,今天為何冒險來公園,不怕被盯上嗎?金毛才說,小苓犯了小條的罪被判勞動服務,但懶惰未服役而被抓進去關了。身為親人的他只能一週探視一次。金毛無奈地說:「本來每天都可以握的手,現在握不到了,怪怪的。」金毛從口袋掏出一封寫得密密麻麻的信,是今天收到小苓寫給他的,他簡述內容說:「老公你不要太難過,沒有人說話,你就去找一些人說,你可以去喝酒,但不要喝太多,喝完了,心要開,話講出來就不會太悶,去公園找人聊聊吧。」平時會勸金毛不要喝酒惹事的小苓,因為察覺先生沒有她的陪伴,整天關在幾坪大的雅房內,怕他之前的憂鬱症又回來,於是要他來公園。
晚上,金毛跟著幾個老人、附近住戶及大哥席地喝開,看著他有說有笑,跟剛才到公園時「悶悶的樣子」判若兩人。趁著上廁所,金毛經過我身旁,我說你看起來好很多了,他回應:「你人啊,就是要心開開,才能講話。你一顆頭在那裡想,晚上睡不著在想,想了十天,那些話都是廢話,你要喝了酒,心開開,話才敢講出來,好受一點,不然光是想、悶在心裡會鬱卒,沒有用。今天也是喝了酒才能講這麼多。」雖然有屋可住,但斗室狹窄又沒有親人,關在房內心裡總悶悶的,反倒是來公園跟朋友露天席地吃喝才變得心開,後者更像是個家。其實,不少有房子的經濟弱勢者,之所以愛來艋舺公園下棋、簽牌,而非待在自己的斗室裡,也是這個原因。
這種席地聚集的集會,常以下述的動態過程進行:十二月底一個黃昏,武雄一如往常在下午四點多下工,搭捷運回到公園時,正好撞見等待明天清晨出陣頭的阿義,他們相約一個去廣州街買下酒菜—滷雞腳,這也是武雄的最愛,另一個則去附近的雜貨店拿回兩小瓶高梁,在公園西南側的石階上相聚,然後開始邊喝邊聊。隨著夜色漸深,一旁陸續有無家者經過,他們會叫住路過的人一起進來喝一杯,於是阿國、慶仔、阿禿、小黑都加入行列,喝光了兩瓶高梁,於是就叫後來加入的人再去拿酒,吃光了小菜,後加入的人就主動或被使喚去夜市再帶回點東西。有些人因為最近多賺了些工錢,會買回較昂貴的菜(如生魚片或鵝肉)或酒(如威士忌),這時就會引發一陣驚呼及讚嘆,「喔~小黑現在不小了,要叫黑老大了。」阿義這麼讚許帶回好菜的小黑。但相反的,倘若扭扭捏捏或買回來的酒、菜不如預期,那就會被挖苦(例如,「米酒頭?我們有喝這麼差嗎?」)。就這麼一直輪下去,每個人都有參與、貢獻,而相互的評價也在一次次的貢獻中建立。因此,這不只是一種等價交換的經濟行為,而是建立團體連帶及個人聲譽的道德行動。
有些人的「有格」是被稱許的,意指在這類社交行為中表現得宜、不發酒瘋,出錢也出得「媠氣」(suí-khuì,意指與他人互動的舉止,讓人激賞、讚許),自己吃喝開心的同時也顧及群體的情緒。做事人雖然崇尚「不牽靠自己」的勞動邏輯,但也會參與席地吃喝的過程,看看對方是否是占人便宜或說話不算話的人,藉此評估是可以共事的伙伴,而非拖累自己的「普攏拱的」(phû-lōng-kòng)。 因此,遇到粗工公司的老闆或叫工仔在缺工時,也會主動推薦在吃喝中確認過的可靠「酒肉朋友」。反之,這些做事的無家者在工作過程中,發現某些同儕會偷工減料、偷懶甚至占同事或老闆便宜,也會恥於在下工後與不乾淨的他們吃喝,與那種盤剝工人的老闆及𨑨迌人一樣,這些人都被稱為會「偷吃步」(thau-tsia̍ h-pōo)的「鬼」。
在席地吃喝裡,也常有𨑨迌人一起盤撋,但他們同樣常在過程裡想動腦筋占別人便宜、不出錢,這種行為叫作「喝阿斯巴拉的」、「喝王八蛋」、「吃王八蛋」的。大家雖然不會直接在酒攤中撕破臉,但隔天再遇見,多少會聽到當面諷刺的酸言酸語,像大家在黃昏時會問候下班了嗎?吃喝王八蛋的慣犯會被私下諷刺:「平常跟著人家喝、跟人要菸,吃王八蛋的,幹嘛要做工。去工作的都是白癡。我想想人家不做工也是對啊……」在公園的名聲臭了,之後也沒人會願意與他一起休閒,這種人際網絡上的受損,也可能連帶影響工作機會,畢竟有不少工作都是靠同儕之間報訊,或依其口碑跟老闆推薦的。
另外,在席地吃喝中還有些人是被「看無」(khuànn-bô,在此指讓人看不起),不是因為他們像𨑨迌人一樣吃喝王八蛋,而是因為他們不會這一套「媠氣」地輪流付錢吃喝的藝術,而只會努力賺錢守財,不懂得盤撋的人情事故。彭仔就是這樣的人。矮小又不善言辭的他非常勤於工作。公園的人說他「很厲害。他白天去做工,晚上都會去茶室賣香腸,平時也去工地做……他是很努力,你不要看他這樣」。但他的人緣很差,我常看到做事人聚在一起消遣他,說「彭仔很『破格』(phuà-keh,指一個人是帶來霉運的掃把星,常壞了大家的興致或計畫),跟他到哪,衰到哪」、「不會做(事頭)又愛接」,或嘲弄他的身材跟不識字。有次下午四點多,見他穿著工地服來回在公園走動,在遠處環顧四周找人卻沒人願意搭理他,我就聽見同樣做完工回來休息的阿勇在旁說:「我們做完工都只想趕快換掉(衣服),比較快活……他就是來展(tián,即炫耀)(有工作)的啦。」隨即對他大喊道:「你走開啦……公園不歡迎你啦,走啦。」
後來我也問老江湖的做事人老鄭,大家為何要這樣為難彭仔。他就說,彭仔「太厲害,太會算……會賺不會花」,「公園就是有一種人,只有錢,沒有人情,沒有人情世故。這種人有奶便是娘。」接著說,有時不管做工或舉牌,都是需要「盤撋……這款眉角(mê-kak,或做鋩角,指做事中細微但關鍵的訣竅)也是要顧,以後工作才好說」。對老鄭來說,武雄是公園「有格」做事人的典範。這種有格也展現在平時喝酒吃飯時的「媠氣」、「不計較(錢)」。雖然做事人在表面上的論述十分崇尚「不牽」與個人主義成功觀,但在實作上仍在社交裡區辨怎麼樣才像個懂得在集體休閒活動裡表現「媠氣」的體面之人,而不是守財奴或是鬼。
在席地吃喝活動中的酒菜等物質,承載著特定階層所賦予的意義,象徵著帶來或吃喝這些物質的人的格調、氣概、尊嚴,從吃喝中的互動也反映了群體倫理。 無家者席地吃喝,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負責任、縱情放蕩、拒絕正派生活,也不能將此實作簡化為他們身陷貧窮困境的關鍵因素,而無視真正使他們難以脫貧的結構性力量,例如整體產業狀態、社會中階級再製的機制與國家政策走向。(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