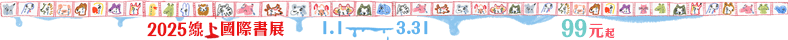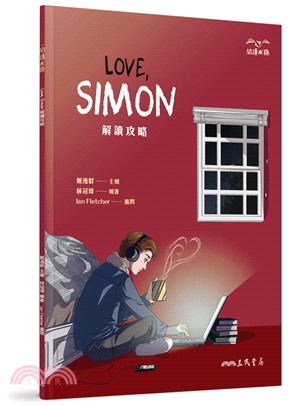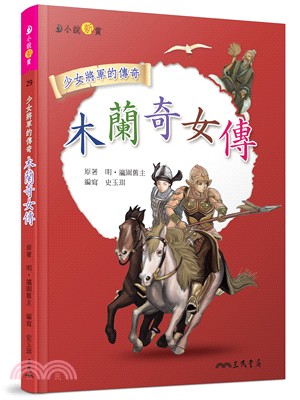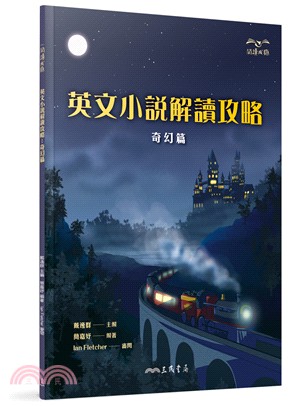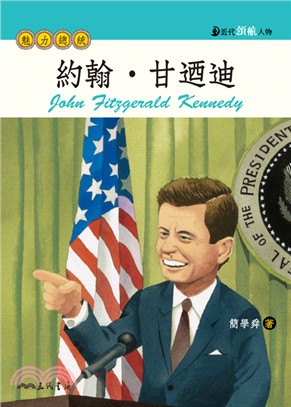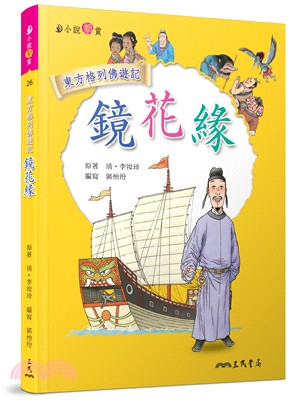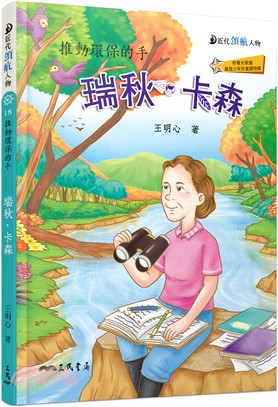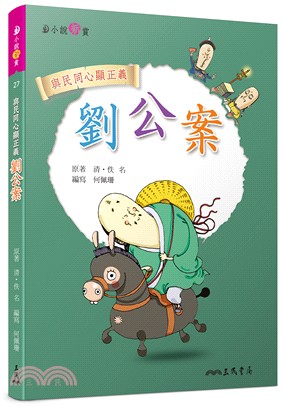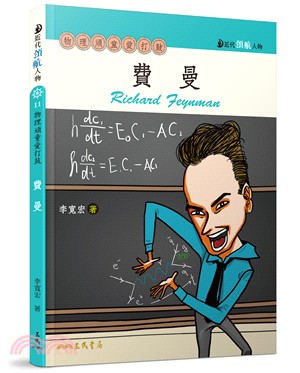讀陸賈《新語》
陸賈楚人,《新語》文體,上承荀卿,下開淮南,頗尚辭藻。荀屈同為賦宗,蓋荀卿曾南遊楚,而染其文風耳。《莊子‧外篇》如〈天道〉、〈天運〉,亦近此體。賈誼以下至董仲舒,為北方文體。西漢文章,至賈董而始變。
《新語‧道基》篇開首,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此即《中庸》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也。下文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一節,極似《易大傳》。然則《易大傳》殆先《新語》,成於秦儒,會通儒道,亦楚風也。據是疑開首傳曰,亦指《易傳》。惟今《易傳》無其文。豈《易傳》自《新語》後,尚續有增刪,始成今之定本乎?
〈術事〉篇開端,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此等亦極近《中庸》,皆自荀卿法後王之論來。其過激則為韓非。司馬遷〈六國年表序〉亦承此旨。而賈董則近法先王,此亦晚周至漢初學術界一分野也。
〈術事〉篇又云: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書孔子為仲尼,其風亦盛於晚周,如《中庸》、《孝經》皆其證。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雖亦偶有其例,要之至晚周始成風習。漢儒率多稱孔子,此亦證《新語》當屬漢初。
〈輔政〉篇、〈無為〉篇皆參雜以老子之說。《老子》書起於晚周,《易傳》、《中庸》皆承儒義而參以道家言,《新語》亦爾,此乃當時學術大趨也。
〈無為〉篇云: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又曰: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道德連用本《老子》,中和連用本《中庸》,尚寬之說亦本《中庸》,《語》、《孟》以至〈易繫傳〉皆言剛,不尚寬。
〈辨惑〉篇記孔子夾谷之會,辭語與《穀梁》大相近,然則《穀梁》亦遠起先秦矣。雖至漢中葉後遞有增潤,始成今本,不可謂其絕無師承也。
〈慎微〉篇亦會通《老子》、《中庸》以陳義。其曰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以道德合之於權勢,不僅《老子》有此義,即《中庸》亦有之。《孟子》言孝,舉舜,而《中庸》言孝必據周公。舜之孝行尚在草莽,周公則正籍權勢以大顯其道德者。篇末引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亦證《孝經》遠起漢前。
〈辨惑〉篇又云: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棄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又曰: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又曰:隱之則為道,布之則為文。其所描述,知其時實多入深山求神仙之事,與當孔子時沮溺荷篠之徒,大異其趣。《莊子‧寓言》,始有此等意想,殆自晚周而始盛。秦皇海上方士雖無驗,然楚漢之際,天下大亂,此等風氣仍持續,即張子房亦解穀欲從赤松子遊。然就《新語》以避世與隱居分別,則儒道合流,並不包括神仙在內。隱之為道,布之為文,顯羼有道家義。
〈資質〉篇深歎質美才良者伏隱而不能通達,不為世用,是乃惜隱,非高隱也。此顯是會通儒道義而有此。
〈至德〉篇屢引春秋事,是必三《傳》多有行於時者。篇末故春秋穀三字下有缺文,是殆引《春秋穀梁傳》也。
〈懷慮〉篇云:據土子民,治國治眾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此《大學》所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厥後董仲舒亦言,明明求仁義,如恐不及者,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如恐不及者,小人之事。此皆封建采邑之制既壞,貴族崩潰,工商生產事業新興以後,為晚周以迄漢中葉一種共有之思想也。
〈懷慮〉篇又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眾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此一節,可見當時智識界一種流行風氣,殆是混合陰陽五行災異變怪之說於縱橫捭闔權謀術數之用,蒯通自稱與安期生遊,即此流也。此後淮南賓客亦多此類。至董仲舒言災異,乃以會通之於經術,此乃中央政權大定之後,與漢初撥亂之世不同矣。至以經藝連文,則稱六經為六藝,已始於其時矣。
〈懷慮〉篇又云:戰士不耕,朝士不商,前一語與韓非耕戰之議異,下一語開漢制仕宦者不得經商之先聲。
〈本行〉篇盛倡儒道,然其語多近《荀子》與《大學》,並旁采《老子》,亦徵其語實出漢初,與武帝時人意想不同。
〈本行〉篇又云: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觀下一語,知孔子定六經,其說遠有所自。殆起荀卿以下,或出秦博士,而賈承其說。觀上一語,則儒道陰陽合流之跡已顯。
〈明誡〉篇有云: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此義遠承《荀子‧天論》。
〈明誡〉篇又云: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此一節與仲舒以下言陰陽災變者無大異趣,然與上引〈懷慮〉篇所云有不同。蓋雖兼采陰陽家言,而固以儒術為主,此乃漢代儒術所以與方術縱橫之士之有其不同所在也。
〈明誡〉篇又曰:聖人察物,無所遺失。○○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可知自董仲舒治《春秋》,通之陰陽,下迄劉向治《穀梁》而志五行,其風遠自漢初,有其端緒矣。
〈思務〉篇有云: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蟲夏藏。熒惑亂宿,眾星失行。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此等語即陳平所謂宰相之職在助天子理陰陽之旨也。陳平陸賈同時,宜其所言之相通矣。
丁酉歲暮,赴臺北講學,行篋匆匆,僅攜陸賈《新語》一冊。旅邸客散,偶加披玩,漫誌所得。〈懷慮〉以下,則返港後新春所補成。戊戌人日錢穆識。
此稿成於民國四十七年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
—(中國名人小傳試作之一)
中國民族,是一個具有悠長歷史的民族。論中國文化之貢獻,史學成就,可算最偉大,最超越,為世界其他民族所不逮。孔子是中國大聖人,同時亦是中國第一個史學家,他距今已在二千五百年之前。西漢司馬遷,可說是中國古代第二個偉大的史學家,距今亦快到二千一百年。孔子《春秋》和司馬遷《史記》,同是中國古代私人著史最偉大的書。
遠在西周,中國人早懂得歷史記載之重要,常由政府特置史官來專管這工作。那些史官是專業的,同時也是世襲的。司馬氏一家,世代相承,便當著史官的職位,聯綿不輟。到遷父親司馬談,是西漢的太史令,正值武帝時。在春秋時,司馬氏一家,由周遷晉,又分散到衛與趙。另一支由晉轉到秦,住居今陝西韓城縣附近之龍門。遷便屬這一支,他誕生在龍門。
當時的史官,屬於九卿之太常。太常掌宗廟祭祀,這是一宗教性的官。史官附屬於太常,這是中國古代學術隸屬於宗教之下的遺蛻可尋之一例。因此史官必然要熟習天文與曆法。同時司馬談並研究《易經》與道家言。因這兩派學說在當時,都和研究天文發生了連帶的關係。
司馬談是一位博涉的學者,他有一篇有名的〈論六家要旨〉,保留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可見司馬談博通戰國以來各學派,不是一位偏狹的歷史家。他的思想態度偏傾於道家,但他究是一位史學傳統家庭中的人,因此他依然注重古典籍與舊文獻,不像一般道家不看重歷史。
司馬遷出生在景帝時,那時漢初一輩老儒,像叔孫通、伏勝、陸賈、張蒼、賈誼、晁錯諸人都死了。漢文帝本好刑名家言。他的政治作風亦偏近於黃老。他夫人竇氏,更是黃老的信徒。景帝尤不喜儒家言。時有博士轅固生,因議論儒道兩家長短,得罪了竇太后,命他下虎圈刺豕。這很像西方羅馬的習俗。
但司馬遷十歲時,他父親便教他學古文字,治古經籍。因此他的學問,不致囿限在戰國以下新興百家言的圈套中。他將來綜貫古今,融會新舊,成為一理想的高標準的史學家,在他幼年期的教育中,已奠定了基礎。這一層,在《史記》裏,他屢次鄭重地提及。
他幼年的家庭生活,還保持著半耕半牧古代中國北方醇樸的鄉村味。他二十歲開始作遠遊。〈自序〉說: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這是何等有意義的一次遊歷呀!中國到漢時,文化綿延,已達兩三千年了。全中國的地面上,到處都染上了先民故事的傳說和遺跡。到那時,中國民族已和他們的自然天地深深地融凝為一了。西北一角,周漢故都,是司馬遷家鄉。這一次,他從西北遠遊到東南,沿著長江下游,經過太湖鄱陽洞庭三水庫,逾淮歷濟,再溯黃河回西去。這竟是讀了一大部活歷史。遠的如虞舜大禹的傳說,近的如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種種具體遺存的業績,他都親身接觸了。這在一青年天才的心裏,必然會留下許多甚深甚大的刺激和影響,是不言可知了。
這一次回去,他當了漢廷一侍衛,當時官名稱郎中。照漢制,當時高級官吏,例得推薦他們子弟,進皇宮充侍衛。他父親的官階,還不夠享受此殊榮。但武帝是極愛文學與天才的,想來那位剛過三十年齡的漢武帝,早聽到這一位剛過二十年齡的充滿著天才的有希望的新進青年的名字了。我們可想像,司馬遷一進入宮廷,必然會蒙受到武帝的賞識。
在當時,他大概開始認識了孔子十三代後人孔安國。安國也在皇宮為侍中,安國的哥哥孔臧,是當時的太常卿,又是司馬談的親上司。司馬遷因此得從安國那裏見到了孔家所獨傳的歷史寶典《古文尚書》了。他將來作《史記》,關於古代方面,根據的〈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重要的史料,有許多在當時為一般學者所不曉的古文學新說。
大概他在同時前後,又認識了當時最卓越的經學大儒董仲舒。仲舒是一位博通五經的經學大師,尤其對孔子《春秋》,他根據《公羊》家言,有一套精深博大的闡述。將來司馬遷的史學及其創作《史記》的精神和義法,據他自述,是獲之於仲舒之啟示。
他當皇宮侍衛十多年,大概是他學問的成立期。後來有一年,他奉朝廷使命,深入中國的西南角。〈自序〉說: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這一段行程,從四川岷江直到今雲南西部大理,即當時的昆明。大概和將來諸葛孔明南征,走著相同的道路。這又補讀了活的中國史之另一面。但不幸,他這一次回來,遭逢著家庭慘變。
當時漢武帝正向東方巡狩,登泰山,行封禪禮。這是中國古史上傳說皇帝統治太平祭祀天地的一番大典禮。但武帝惑於方士言,希望由封禪獲得登天成神仙,因此當時一輩考究古禮來定封禪儀式的儒生們,武帝嫌其不與方士意見相洽而全體排擯了。司馬談是傾向道家的,但他並不喜歡晚周以來附會道家妄言長生不死的方士。因此他在討論封禪儀式時,態度接近於儒生。照例,他是太史令,封禪大祭典,在職掌上,他必該參預的。但武帝也把他遺棄了。留在洛陽,不許他隨隊去東方。司馬談一氣病倒了。他兒子奉使歸來,在病榻邊拜見他父親。
〈自序〉說:
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其父,下同),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
接著是他父親的一番遺命,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後世中衰,絕於余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遷俯首流淚,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看了這一段敘述,可想司馬談是一位忠誠骾直而極負氣憤的人。他很想跟隨皇帝去泰山,但不肯阿從皇帝意旨。沒有去得成,便一氣而病了,還希望他兒子在他死後把此事的是非曲折明白告訴後世人。司馬遷性格,很富他父親遺傳。他父親臨終這一番遺囑,遂立定了他創寫《史記》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