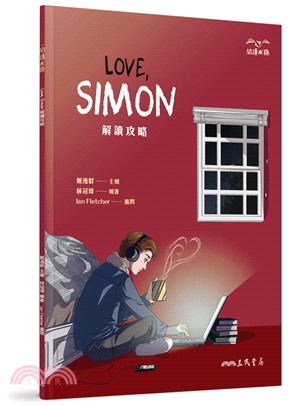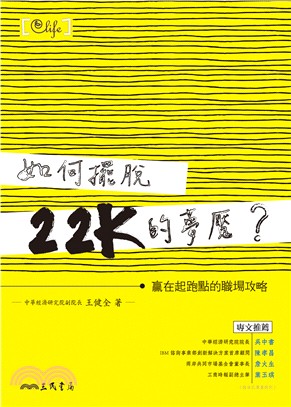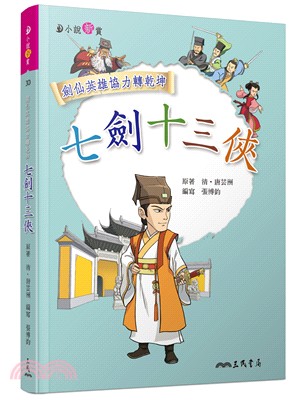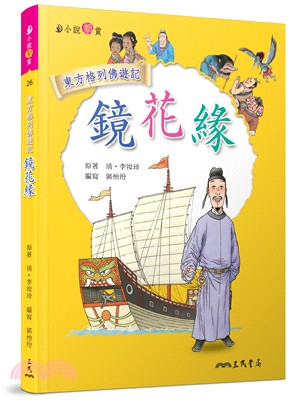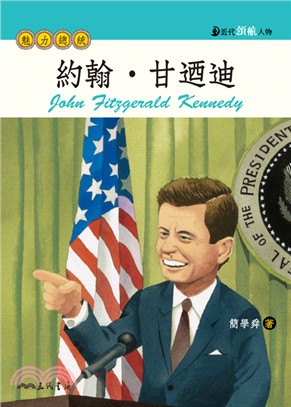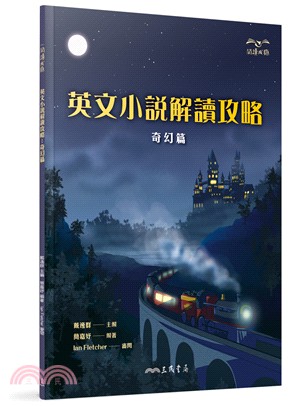商品簡介
世界級舞團「舞蹈空間」與日本、香港、西班牙頂尖編舞家、奧斯卡音樂大師合作軌跡珍貴全紀錄!
表演藝術界人才濟濟,但要成功整合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優秀藝術人才,始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場膾炙人口的「國際共製」演出背後,都是主事者專業、耐心、手腕的極致體現,更需要永不放棄、止於至善的決心!
表演藝術在台灣,至今仍是小市場的文創手工藝品,但「舞蹈空間」舞團創辦人平珩卻早已從「國際共製」中看到未來,藉由與世界各地的藝術總監、製作人、編舞家、音樂家和舞者合作,不僅可以誘發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創作動能,更可以透過一部部「超規格」的作品,讓世界在舞台上看見台灣。
別出心裁的《時境》,用150公斤的扁豆,演繹時間的軌跡;《沉睡的巨獸》以130個大紙箱,堆疊出社會與政治、生存與人性;《反反反》運用2公尺長的碳纖方框,聚焦壓迫與弱勢;《媒體入侵》用7米高的巨大氣球,搭配聲光投影,詮釋「液態」的世界……
「國際共製」是藝術家跨越顛峰的墊腳石,也是屬於藝術行政工作者一堂永遠不會結束的課。不管你站在台上,坐在台下,還是隱身幕後,「舞蹈空間」的故事都將會為你提供最寶貴的經驗。而能夠打破國籍、語言隔閡的,從來都是人與人之間,那一分為夢想獻身的赤誠!
作者簡介
大學念的是英文系,22歲以前很喜歡跳舞,一心只想做舞者。赴美留學後,赫然發現原來過度樂觀的人,並不適合吹毛求疵的表演生涯,於是四年間邊走邊看,盡情吸取紐約花花世界中無盡的藝術創意。
返台後,一頭栽入從沒想過的藝術行政工作,在無太多前例可循的情況下邊做邊想,為有才的藝術家們作嫁,誠心誠意、親力親為成全大家的構想。因為是心甘情願,所以從不叫苦,還把各種挑戰當成吃補,每回總是睜大眼睛開心去發現可以學到的招數。
一路走來,和56位編舞家、171位舞者、168位設計者們合作發表了84部新作;辦過7屆皇冠迷你藝術節、16屆皇冠藝術節、7屆小亞細亞戲劇/舞蹈網絡,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學近30年,擔任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4年、常務理事12年,也曾任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規劃形形色色藝文相關活動不下3000場。
雖獲中興文藝獎、國家文藝獎、台北文化獎、北藝大名譽教授肯定,但她認定這些都是得自所有合作藝術家們的無限創意。因此,她想要用力分享,除了走進劇場觀賞演出外,表演藝術還有什麼潛藏的普世價值。書寫或許不是舞蹈人的專長,但她依舊奮力一搏,只因為相信藝術的創意和與人不斷溝通的本質,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弦外之音」。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舞蹈既然是人類的母語,何來種族與國界?
台中歌劇院首任藝術總監、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王文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的國際戲劇協會(ITI),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以「國際舞蹈日」讚頌舞蹈藝術的特殊價值;他們每年邀請一位舞蹈家致上獻詞(message),直至今日,約計四十篇的藝術禮讚,每次翻閱,似乎都提醒著我們,舞蹈是劇場藝術中真誠實踐的先驅,說不了謊的身體,先一步定義了舞蹈藝術的本質:心靈與情感的誠實映照。
這也是為什麼,舞蹈家追求肢體的自由與變化時,極少重複自己;而做為觀眾的我們,每次被引發的共鳴振幅,往往巨大深長且無力阻擋。
即便編舞家運用的是人類平等擁有的四肢與軀幹,每一個非凡而觸動人心的作品,依然有能力訴說出不同的故事與思想。從伊莎朵拉.鄧肯近百年前舞出紅色生命力時,舞蹈家就用行動進行示範:舞蹈作為世界共通語言,在人類跨越族群與國界的永恆平等信念上,舞蹈藝術早就實踐著了。
一九九三年的國際舞蹈日獻詞中,曾以作品《May B》風靡台灣與全球的法國編舞家瑪姬.瑪漢點出了舞蹈在精神上的神聖:「我一直相信『藝術』——尤其是舞蹈藝術——可以拉近不同國家人民間的距離、是溝通與相互了解的工具,而這個神聖的語言讓所有交流都變可能……我希望全世界開始使用舞蹈跟孩子溝通,它讓心靈與身體靠近、是我們想再度開始互相關心時最急需的工具。」
獲獎無數的比利時Rosas舞團創辦人安娜.泰瑞莎.姬爾美可(Anne Teresa De Keersmaeker)在二○一一年說:「舞蹈讚頌人之所以為人的每一個部分……我們用盡所有的感官去表達快樂、悲傷……以及許多重要的人生時刻,身體記憶著所有可能的人類經驗……我視舞蹈為思考工具,它揭露我們看不見、說不出的事。舞蹈串聯人、天與地……它沒有起始、沒有終了。」
兩年後,林懷民老師在巴黎拉維萊特劇院(la Villette)宣讀二○一三年如詩的文字:「《詩大序》把舞蹈的起源闡述得非常好:『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舞蹈的訊息望似模糊,卻充分表露一個人的心境,甚至族群的性格與特質……舞蹈只存在於那一剎那。如此易逝,如此珍貴,彷彿是生命的隱喻。在這個數位時代,動態的圖像成千上萬。個個炫目迷人。但它們無法取代舞蹈,因為圖像不會呼吸。」
舞蹈,是舞蹈家的母語;他們編舞,就是在訴說;而他們透過舞作所傳達的詩意,便是你我的悲喜。這樣的舞蹈世界觀,在平老師身上,也早已根深蒂固。
記得是上個世紀末,平老師給了我一個機會,要我去美國費城參加一個舞蹈座談;因為她臨時無法成行,我在電話上覺得責無旁貸應該要幫這個忙,但是心裡忐忑不安,怕砸了平老師以及台灣的招牌。我抓著電話筒,一直想要問出平老師的武功秘笈,她都是怎麼分析舞蹈的? 編舞家都在想什麼? 舞蹈空間是怎麼會進行這麼多國際拓展? 費城的舞評都說了些什麼?
平老師一貫輕鬆的語氣拋出了一句話:「舞蹈就是每天的生活唄,我們做什麼,老外也一樣做什麼。」然後說得掛電話了,要去教課。我像看到向來溫煦的平老師,邊走邊回頭微笑著揮手,然後進入舞蹈系排練教室,歡喜地跟著舞者一起呼吸去了。
而在多年後的今天,讀完這本書,我才發現,這些成就的累積,不是台灣舞蹈界的常態,而是平老師不知不覺中實踐了生活與舞蹈合一的信念——她就跟這些大師一樣,除非必要場合,嘴上是不會一直闡述這些道理的,他們自然而然就將堅信的價值觀用行動展現出來,就是像在生活中煮開水、洗碗筷一樣不需要立定志向就能實踐,實踐著攜手全球一起跳舞,因為相信「舞蹈既然是人類共通的母語,何來種族與國界?」。
沒有大張旗鼓宣示,舞蹈空間就常常「用舞蹈來跟孩子溝通」,她讓孩子有機會真正從身體進入心裡,享受純真表達的美好;本書中所提到的日本東京鷹,就是延伸那肢體語言暢快淋漓的爽朗表現——孩子的淘氣與青年的肢體活力,兩者完美地結合著。
平老師頻繁的國際串聯,雖然在台灣少見,但原來也只是舞蹈人的正常表現:當視野習慣關注人類的整體需求時,國界或人種都不會是障礙,反而到處是攜手合作的開端。而書中所提舞蹈空間舞團與瑪芮娜的合作,就是一個走進我們「看不到、說不出」的深刻作品——雖然,平老師只是用她慣常的平靜娓娓道來。
是正視舞蹈藝術的時刻了。讀完這本書,我們會發現,沒有舞蹈空間,台灣的舞蹈風景會平淡無奇;而舞蹈空間過去三十年來的累積,也不是一項理所當然,而是平珩老師做為舞蹈人的自發性表現。如果我們問她,怎麼做了這麼多事情? 也是跟舞者一樣的意志力造就而成的嗎? 我相信,她應該還是會微笑聳肩、輕描淡寫一句:就很正常呀,很多事可以做。
三毛說:「作家,就是寫字的人。」而舞蹈空間,就是那個為舞蹈創造更多空間可能的人。
【推薦序】
這不是一條理所當然的道路,卻是一段動人的歷史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劇劇顧問/耿一偉
經常有人問我關於策展的秘訣,我都說:「就是把偶然作成必然。」他們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但相信大家讀完《一堂永遠不會結束的課》後,就會知道,這才是節目製作的王道。在偶然中能見到必然的能力 ,其實是一種審美判斷,也就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所提到的反思判斷力,是一種從特殊發現普遍的能力。
在國際共製蔚為風潮的今日,從文化部、國藝會、藝文場館到藝術節都投入鼓勵國際共製的行列。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平老師才是台灣最早推動國際共製的關鍵人物,而她手中的資源,就是皇冠小劇場與舞蹈空間舞團。不過,平老師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她做國際共製,完全是以民間私人機構的角色在推動,這與國家機構有著充足資金、不計成本地為場館品牌或文化外交的目標努力不同。平老師推動國際共製,只有一個單純的動機,就是對舞蹈的愛。有了這份愛,會讓她願意拿出自己所有的時間與資源,投入推動國際間的舞蹈合作。
美國舞蹈學者潘妮洛普.漢斯泰(Penelope Hanstein)認為藝術領導者,具有四種特質,首先是寬廣的覺察力,能專注在當下,細心觀察世界。第二是轉換觀點,能夠突破既有框架來看問題。第三是發現新興的模式,嘗試在事情尚未明朗之前,捕捉全貌。第四是容忍含混,有時事態不明甚至充滿矛盾,也是必要的過程,要有抗壓力,願意跟問題相處。我們可以在這本書中,見到平老師如何展現這四種特質,感受到她是如何用她的微笑,心臟很大顆地面對國際共製的結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種偶然、意外與變動。
在寫這篇文章的前一週,恰好平老師邀我去錄她的podcast節目《舞空A》,她在節目中提到每次在舉辦「小亞細亞|亞洲小劇場網絡」期間,許多國外團隊都驚艷於皇冠小劇場旁邊的自助餐,即使台灣能提供的日支費是最少的,但平老師與她的團隊招呼這些藝術家的熱情,卻讓這些外國友人留下深刻記憶。支持國際共製的基礎,是一種好客。而好客是如此勞心勞力,無法用利益權衡的角度,去說服人們是否應該要好客,因為根本划不來。好客的人之所以好客,只因他們喜愛做這件事,好客本身就讓人感到開心。就跟跳舞一樣,腳傷就是勳章。
皇冠小劇場於一九八四年創立之後,成為台灣小劇場運動的重要基地,各種生猛的實驗演出,都在這裡獲得支持,讓演出時坐在這裡的一百對眼睛,得以閃閃發光,呼吸急促。一個藝文空間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空間很大,而是這裡的人心都很大。
即使皇冠小劇場不再,這些演出不再,也沒有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些國際共製創造什麼票房還是產業,但最終卻有了平老師這本書,讓故事留了下來,串成一段動人的歷史。
【推薦序】
結伴同遊
2010-2019香港西九文化區行政總監、現任香港藝術學院院長/茹國烈
看平珩老師的新書,才發覺「小亞細亞」原來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看她娓娓道來,也勾起我的一些回憶。
「小亞細亞」其實是兩個活躍於亞洲的文化交流網絡,戲劇網絡與舞蹈網絡各辦了七年,兩個網絡交疊之處,就是都有平珩老師和我做為港台兩地的發起人。
一九九七年起,我們先開始了「小亞細亞戲劇網絡」。由三個城市發起,香港(藝術中心)、台北(皇冠劇場)和東京(小愛麗絲劇場)。其後陸續加入上海戲劇學院、北京青年藝術劇院和韓國釜山大學,參與的演出除了來自這些城市,也有來自深圳、大阪、名古屋、京都、雪梨和新加坡。
這是一個以場地為單位的網絡,我們在亞洲找不同城市的劇場做為伙伴,這些劇場抱有同樣的信念,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雙邊交流」,我們相信文化交流的本質是增加了解而非購買節目,所以每個場地每年需要向其他成員推薦及介紹要送出的節目,同時又須選擇要邀請的節目,透過討論過程,大家能夠認識彼此更多。
再者,我們也相信「小就是美」,小劇場演出因為較為輕便,而能巡迴不同城市,增進交流。小劇場演出帶有的實驗性,更能看到那個城市表演的新創意和將來的領軍人物。
而「長期合作」更是我們秉持的態度,相信文化是一個細水長流的過程,文化交流需要長期而且定點去做,所以這個網絡在每個城市找一個劇場做為伙伴,維持長期的合作。
在這三個信念之下,我們訂立出一個交流指引,讓交流可以長期順暢地進行,不需每次逐項再談,為節目策劃中爭取寶貴的時間和自由。小亞細亞戲劇網絡交流指引包含:不設藝術總監,各城市每年互相推薦節目,自由選擇;每年訂於七月至九月演出,方便串聯演出;每項演出基本巡演人員為八人,演出費各地一致;每城市逗留一星期,每城市至多演出四場,並可有一場教育活動;而影響活動成敗最大的經費問題,則採平均分攤方式合作─當地食宿、交通、場地、宣傳均由邀請方負責,國際和城際交通由演出方負責。
就憑這些信念、共識和一班很好的伙伴,「小亞細亞」成長得很快。從一九九七到二○○三年,七年之內,成員由三個增加到六個城市,參與劇團共二十五個,來自十一個亞洲城市,共兩百多場演出。
到一九九九年,我又和平珩老師用另一種形式,發起「小亞細亞舞蹈網絡」,由四個城市發起:香港、台北、東京、墨爾本。每年每個城市推薦一個二十分鐘左右的獨舞短篇,四段獨舞串起來,就是約九十分鐘的一晚節目。這演出就在四個星期內,巡迴四個城市演出。現在回頭看來,這也是一種跨城市的共製節目模式。
這個交流模式有趣的是,四位原本互不認識的舞者,需要在一起生活和演出共度四週,有些舞者因此成為好友,也衍生出很多合作交流的可能性。有一年,四位舞者自發把四支舞連起來;更有一年,我們把四位舞者早一個星期聚在一起,四個人合作編出了一套新舞作。
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玩的交流模式,也很受到歡迎,在二○○一年,首爾加入成為第五個城市。那年我們有五位舞者,巡迴了六個城市(墨爾本、台北、香港、東京、大阪和首爾)。「小亞細亞舞蹈」的限制是不能無限擴大,五個城市,巡迴五個星期已經是極限,再擴大就變得太複雜,巡迴太長也令人疲累。它只能是「小就是美」。
既然這兩個交流模式是這麼成功,為什麼小亞細亞戲劇網絡和舞蹈網絡卻分別在二○○三和二○○五運作七年後完結了?
首先是資助疲勞,這兩個網絡能夠維持,是需要各成員在自己的城市找資金。大部分城市的藝術資助都是僧多粥少,大部分資助機構都傾向支持一些新的項目。「小亞細亞」連續舉辦五六年後,已有些城市找不到資助了。第二是人才疲勞,有些城市在五六年之後想停一停,把資源用來要做其他新的計畫,而且亦找不到適合的戲劇節目和推薦舞者。
香港和台北是兩個網絡的核心推手,在二○○三和二○○四年曾經嘗試一個新構思:《小亞細亞創作者會議》,聚集不同城市,不同界別的創作人,集中一段時間做工作坊,期望能催生一個亞洲共製的新作品,在首爾做了一次試演,然後因為種種原因,就沒有繼續了。
現在回想,「小亞細亞」沒有走得更長更遠,實在很可惜。九年來的經營,累積了不少經驗和人脈網絡,實際推展了很多高質素的藝術交流,是一個很好的品牌。我有時幻想,如果有穩定持續的資金,或者得到官方的參與,「小亞細亞」或許可以變成一個常設的亞洲藝術交流平台,一直延續到今天。
但又想想,「小亞細亞」的本質是完全由民間操作,由各城市共同分擔資源、共同創想,如果改變成政府主導,或者轉由單一城市為主導者,整個事情的精神和面貌應該都會很不一樣。
跨地合作,其實是要天時地利人和的結合,時機不對,勉強不來。在小亞細亞網絡合作的一班朋友,到現在還不時聯絡,談起二十多年前曾經在「小亞細亞」文化交流的旗幟下,在亞洲各地結伴同遊,仍然興致勃勃,恍如昨天。
文化交流,就是結伴同遊,不是嗎?
序
自序
好不容易放眼天下
一九八○年赴美進修時,透過台灣友人介紹,在紐約大學藝術學院上課的第一天,便和同樣在該院讀電影的李安約見,兩人生分地在學院附近的印度餐館共進簡餐,當時沒聊太多,只記得暗自嘀咕這五元美金的飯錢真不便宜,接下來的三年就再也沒一塊兒去過任何餐廳吃飯了。
之後,每隔一陣子大夥聚會時,都會興致盎然地聽李安講故事:一下是他如何與室友、也是老朋友的王獻箎輪流下廚,光聽到菜名就足以讓大家口水直流;一會兒又聽他描述另一位原本個性極其溫和的亞洲室友,某天如何突然兇狠狠地拿刀與他們相向對峙;或者,他好不容易擁有了一台破車,沒想到因為車上一點零錢引起頑童覬覦被砸破車窗,只得沮喪地開著沒窗的車子去伊利諾州找老婆討秀秀,再帶著老婆特別準備的一大盒滷味邊吃邊開回紐約。每個故事從他嘴裡講出來的同時,都讓我們看到生動的畫面,也忍不住跟著他又悲又喜。
為了李安電影所的畢業製作,我們卯足了勁大力幫忙,以全是研究生的超優班底在紐約街頭搶鏡頭。當時在念表演、現在是優劇場總監的劉若瑀還跨刀擔任女主角;就連久未出江湖、我們的二房東張致泉,也禁不住他一臉「無辜」的懇求,撩下去為他的影片配樂出馬演奏。那幾年,在這麼「平淡」的學習氛圍下,大多數人一畢業便想著啟程回家,唯獨李安說要留下來「進軍好萊塢」!大家聽了莫不面面相覷,全想著他大概是瘋了,台灣人怎麼可能打進好萊塢?!美國只是汲取養分的所在,壓根兒沒人想過要留下來「爭名」!
當然,懷抱國際「大夢想」的李安,後續成就已是眾人皆知,而從未存有「奢望」的我,在回台工作至今近四十年間,也因緣際會走上與國際接軌之路。或許是因為表演藝術在台灣,至今仍是不夠具有市場規模經濟的文創手工藝品,柴米油鹽的繁瑣難免磨人志氣,但與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手,的確讓我這種「沒膽識」的人,摸索出一條從未預見之途。
與「老外」交手,如同江湖武林高手對決,天下之大,需要做足準備,但也處處無法預料。當年或許是以「無招」應對,而今回看已然歸納出一些「絕招」,重點不在輸贏,而是拿捏分寸站穩立場,看到所得、忘記所失。雖然未能生出李安「大氣魄」的壯麗山河,在細水長流的披荊斬棘間,倒也遇見了一些特別的景致,篩出「長智慧」的樂趣。
序曲
什麼是國際共製?
台灣劇場主辦節目大多是以國外邀演與國內新製作為主。國外節目除要負擔演出費外,還需支付高額的旅運及團隊落地住宿等接待費用,所以一般都會邀演已完成的作品,在可見菜色中找出適合本地觀眾的口味。但近二十年來,國外機制健全的劇場,逐漸開放越來越多的「共同製作」,品味相近的劇場可以結伴「押寶」,一起投資大家看好的製作,經費規模擴大可提供更理想的製作條件,尋找更具突破性的藝術家合作,或是以更充裕時間來發展創新方向。
參與共製的劇院,共同擁有節目首輪演出權,確保這個新製節目的演出場次,而不是在首演一年半載後,才能排入其他劇場演出。新製節目被擔保的演出量越大,人事及製作成本自然降低,而且可保證是由首演最強卡司擔綱。當然分攤經費還是次要目的,搶先成為能識千里馬的「伯樂」,才是業界最讓人快意之事!
這種合作模式在出版界是常態,出版社通常可依通路的預估來訂定初版的印刷量,電影界先賣版權的行銷手法大家更不陌生,但表演藝術演出製作不具所謂市場機制,幾乎無法用票房來打平製作費用,一般邀演國際節目主要是為「開視野」而無法盈利,如果還要再多負擔一些共製成本,豈不注定「雪上加霜」?
為什麼要國際共製?
國際共製絕對不是有錢大爺就能呼風喚雨的,江湖上行走,總會先經過一番禮尚往來的「暖身」,掂過彼此斤兩後,才可能有進一步的合作。以國家兩廳院為例,國外節目來訪,看的不是劇場外觀有多華麗,而是從舞台技術人員裝台水準、節目承辦人對團隊起居接待等各項安排細節來感受,要什麼給什麼還不夠,「超前部署」才能顯現專業。而台灣觀眾「識貨」又熱忱的回饋,往往是更能讓外國團隊印象深刻的利器。在有「地利、人和」條件下,慢慢累積出來的「天時」才會發生。畢竟大家想要的是旗鼓相當、心照不宣的好伙伴,如果參與共製的劇場,無法提供相對水準的演出配合,委屈了大家看好的「寶貝」,那可就是罪過! 所以這種共製的邀約,一定是要在相當程度的理解與信任基礎下才能產生。
近年,台灣參與國際共製的案例逐步增加,我們因此有機會經由共製而與世界知名劇場共列。像兩廳院二○一二年與法國卡菲舞團合作的《有機體》,由該團北非裔、街舞出身編舞家穆哈.莫蘇奇(Mourad Merzouki)將五位台灣現代舞者和卡菲的街舞舞者編織成舞,搭配古又文的服裝設計,在沒有預期之下,巡演全球近百場,讓兩廳院到處插旗。
二○一三年兩廳院與新加坡濱海劇院共製梅田宏明的《形式暫留》、二○一四年應瑞士洛桑劇院之邀,與索恩河沙隆國家表演藝術空間(Espace des Arts scène National de Chalon sur Saone)、日內瓦偶劇團(Puppet Theater Geneva)法國蒙貝利亞爾MA劇院(MA Scène Nationale-Montbéliard)共製戲偶大師楊輝的《牛仔褲》等案例,都宣示了兩廳院不是只會「買節目」,也有參與國際表演藝術大家庭的意願與實力,增加了兩廳院在國際的能見度。台灣的國家交響樂團在二○一五年,與歐洲的阿姆斯特丹皇家大會堂管弦樂團、皇家利物浦愛樂、美國的聖路易斯交響樂團及澳洲的塔斯馬尼亞交響樂團共同委託作曲家譚盾創作《狼圖騰》,也展現出參與全球樂壇的企圖心。
所以,國際共製費用雖會增加節目的負擔,但可以因此了解國際市場押寶的重點,也能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並永遠在此作品上留下「分了一杯羹」的紀錄。況且主要製作劇場因為是首輪的「首演」,往往是出資最多的一方,其他共製單位相對分配比例較小,如果再將其視為行銷未來及下一次實質合作的「投資」,那CP值就更高了。
也許是不像大劇場要承擔沉重的資金分配與回收壓力,我個人所屬的小劇場及小團,在「國際共製」尚未普遍之時,早已不知不覺走上國際合作之路,而未抱太多期待地一路走來,竟也是收穫滿滿,藉由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相識到相交,誘發我持續在工作上充滿動能地精進,這其中有三個最重要的體悟:
一、知己知彼,相互學習
我們要交到好朋友,最不能有目的性的「功利」念頭,相識總要從了解身家開始,先互通學習背景、專長、興趣,是交手的基本,再慢慢發掘出進一步深入交談的主題。能開心聊天的對象,就可能是「一呼即應」的合作伙伴。只是「麻吉」固然還不足以成就計畫,對手的做事方法、工作視野、圈內其他人的評價都是重要的觀察指標。如果你始終都是那位唯一的領頭羊,只有獨自一人瞻前顧後,勞心勞力終究不能長久,大夥合作能有時走前鋒、有時樂跟隨地相互競合,才會是「過癮」的旅程。
二、平起平坐,才能合作
合作的本質就像理想的婚姻,務必要能門當戶對,這不是指財力對比,而是處事文化的相當。不拘小節的人一定比較能夠欣賞和自己同樣不拘小節的朋友,「臭味相投」才能「平起平坐」,也唯有平起平坐論事,沒有過多的猜疑與算計,合作才不容易橫生枝節。
三、不是文化落差,各有所別而已
無論身處何處,即使同在亞洲,地緣之別造就的文化特色各有所長,有人凡事據理力爭,有人非常客氣,國際共製間最有趣之事,便是在這文化差異中探出分寸,有時不明說並不表示完全同意,即使言無不盡時都還可能會有弦外之音,認清各人各地的行事風格,對「症」下藥,才能讓事情圓滿。
從事藝術行政四十年間,憑藉以上這些小小心得,倒也發展出五種案例,每個個案合作期程短則四、五年,長則超過二十年,所幸這悠悠歲月並非不堪回首,反而因此拼出一個由時間、空間與知識共組的立體圖像,希望這畫面可以打動更多人了解廣交、深交「國際朋友」的重要。
目次
目錄
推薦序
舞蹈既然是人類的母語,何來種族與國界?/王文儀
這不是一條理所當然的道路,卻是一段動人的歷史/耿一偉
結伴同遊/茹國烈
自序
好不容易放眼天下
序曲
什麼是國際共製?
為什麼要國際共製?
一切從小亞細亞網絡交流開始
第一章 長長久久,演化再生──當舞蹈空間遇上瑪芮娜
一眼相中她
情定《橄欖樹》
以《時境》打天下
敲醒《沉睡的巨獸》
《反反反》?為何不!
《媒體入侵》的神奇之旅
第二章 心意相通,無往不利──與日本的不解之緣
相濡以沫的朋友們
天作之合──島崎徹
我舞蹈.我厲害──《徹舞流》
無遠弗屆的《舞力》
一場「東京鷹」的遠距戀
拚命喝杯《月球水》
十年一劍為《月球水2.0》搞笑
第三章 客隨主變,兵來將擋──向大部頭製作學習
製作人眼中的《風云》
《迴》──好個春秋大夢
該隨誰起舞?
舞台下的暗流
少即是多?
如夢幻泡影──攜手香港「進念.二十面體」
從「非法」開始的夢幻組合
凌駕在技術之上的技術
尾聲 一堂永遠不會結束的課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