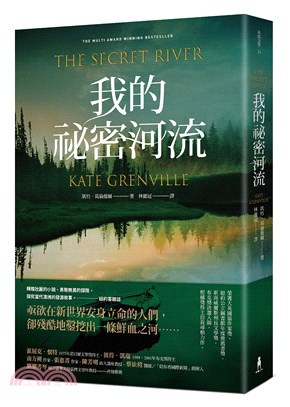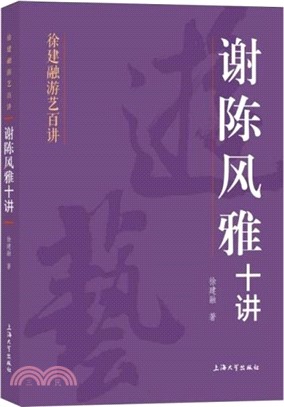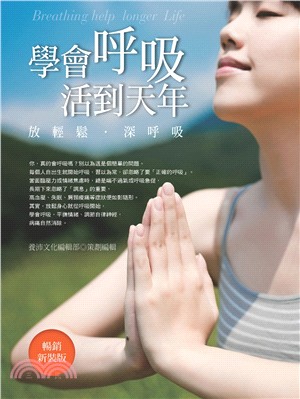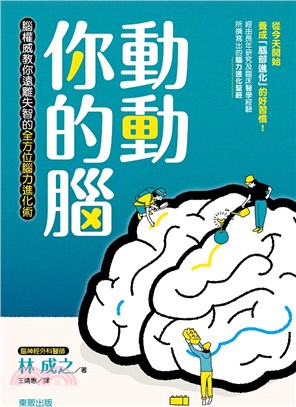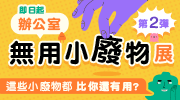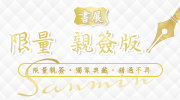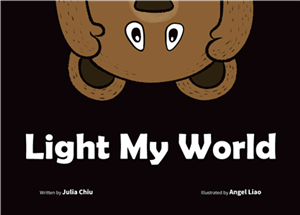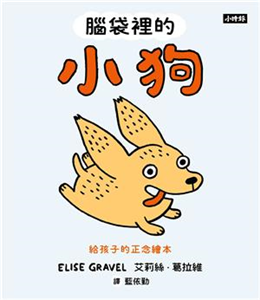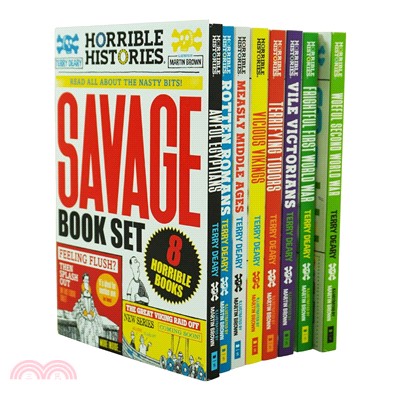我的祕密河流(經典新裝版)
商品資訊
系列名:木馬文學
ISBN13:9786263141506
替代書名:The Secret River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凱特‧葛倫薇爾
譯者:林麗冠
出版日:2022/04/13
裝訂/頁數:平裝/336頁
規格:21cm*14.8cm*2.1cm (高/寬/厚)
版次:2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大英國協作家獎、紐約公立圖書館年度推薦書獎、新南威爾斯州長文學獎
澳洲圖書產業獎、澳洲書商選書獎、布克獎決選入圍
亟欲在新世界安身立命的人們,卻殘酷地鑿挖出一條鮮血之河……
柑橘獎得主最重要、最深刻的自我尋根力作
「輝煌壯麗的小說、勇敢無畏的探險,
探究當代澳洲的發源故事。」── 紐約客雜誌
一八○六年九月的一個早晨,「亞歷山大號」在雪梨海灘下錨,重罪犯們從陰暗的船艙上到陽光直晒的甲板,威廉.索恩希爾用手遮臉,感覺眼淚熱辣辣地流下臉龐──逃過絞刑死劫、配發至地球的盡頭,這個男子即將展開新的人生。
索恩希爾原本是倫敦泰晤士河上的船夫,整日勞苦卻不能養活妻小,一家子擁有的只是破舊的衣裳,以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所加給他們的無窮磨難。每個人都在鋌而走險,結局卻各不相同,索恩希爾為謀溫飽而犯罪,不幸被捕後在妻子奔走、貴人伸手之下豁免死罪,換來流放邊疆的命運。到了豔陽藍天、陌生無依的雪梨,他才發現不堪如自己者竟能得到無法在倫敦奢望的一片荒地,可以自力耕種照養全家,他的生命首次出現歸屬感,也首次掌握了生生不息的土地,播下希望的種子。
可是索恩希爾並不知道,「他的」這塊應許之地早有一群人居住其上,這些人在森林裡行蹤飄忽,而雙方的相會猶如海洋遇上河流,彼此激烈地傾注混攪──他們心裡的無知轉變成恐懼,而恐懼正是災難的源頭。夾雜在白人墾荒者和原住民之間的索恩希爾,正面臨著自己人生當中最困難的抉擇……
澳洲圖書產業獎、澳洲書商選書獎、布克獎決選入圍
亟欲在新世界安身立命的人們,卻殘酷地鑿挖出一條鮮血之河……
柑橘獎得主最重要、最深刻的自我尋根力作
「輝煌壯麗的小說、勇敢無畏的探險,
探究當代澳洲的發源故事。」── 紐約客雜誌
一八○六年九月的一個早晨,「亞歷山大號」在雪梨海灘下錨,重罪犯們從陰暗的船艙上到陽光直晒的甲板,威廉.索恩希爾用手遮臉,感覺眼淚熱辣辣地流下臉龐──逃過絞刑死劫、配發至地球的盡頭,這個男子即將展開新的人生。
索恩希爾原本是倫敦泰晤士河上的船夫,整日勞苦卻不能養活妻小,一家子擁有的只是破舊的衣裳,以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所加給他們的無窮磨難。每個人都在鋌而走險,結局卻各不相同,索恩希爾為謀溫飽而犯罪,不幸被捕後在妻子奔走、貴人伸手之下豁免死罪,換來流放邊疆的命運。到了豔陽藍天、陌生無依的雪梨,他才發現不堪如自己者竟能得到無法在倫敦奢望的一片荒地,可以自力耕種照養全家,他的生命首次出現歸屬感,也首次掌握了生生不息的土地,播下希望的種子。
可是索恩希爾並不知道,「他的」這塊應許之地早有一群人居住其上,這些人在森林裡行蹤飄忽,而雙方的相會猶如海洋遇上河流,彼此激烈地傾注混攪──他們心裡的無知轉變成恐懼,而恐懼正是災難的源頭。夾雜在白人墾荒者和原住民之間的索恩希爾,正面臨著自己人生當中最困難的抉擇……
作者簡介
凱特.葛倫薇爾 Kate Grenville
一九五○年生於雪梨,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創意寫作碩士,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創意藝術博士。
葛倫薇爾曾經擔任電影剪接及製作,在英國、法國工作多年,後來師事現代小說大家蘇肯尼克(R. Sukenick)等人研習寫作。一九八四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有鬍子的女士》,迄今已完成十餘部短篇、長篇小說以及非小說作品,翻譯成德、荷、義、葡、中等語文出版,其中兩部長篇小說曾改拍成電影上映。
她的寫作與國族歷史緊密相關,文句優美感人,以音樂般的字句傳達流暢的故事。她曾在英國、澳洲兩地研究英國以澳洲為罪犯流放地的歷史,並為了紀念她祖母家族篳路藍縷、開闢疆域的事蹟,而把自己的姓氏由原本的「吉伊」改為「葛倫薇爾」。小說《我的祕密河流》當中,也有相當部分取材自她祖先的親身遭遇。
《我的祕密河流》是葛倫薇爾最重要的作品,推出後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廣受好評,先後獲得大英國協作家獎、紐約公立圖書館年度推薦書獎、新南威爾斯州長文學獎、澳洲書商選書獎等,並入圍布克獎決選、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初選。二○一三年曾改編成舞台劇演出,二○一五年改拍成兩集迷你影集。
葛倫薇爾於二○一七年獲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頒予終身成就獎,二○一八年獲頒澳大利亞勳章,以表揚她的卓越貢獻。現與兒女同住在雪梨。
一九五○年生於雪梨,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創意寫作碩士,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創意藝術博士。
葛倫薇爾曾經擔任電影剪接及製作,在英國、法國工作多年,後來師事現代小說大家蘇肯尼克(R. Sukenick)等人研習寫作。一九八四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有鬍子的女士》,迄今已完成十餘部短篇、長篇小說以及非小說作品,翻譯成德、荷、義、葡、中等語文出版,其中兩部長篇小說曾改拍成電影上映。
她的寫作與國族歷史緊密相關,文句優美感人,以音樂般的字句傳達流暢的故事。她曾在英國、澳洲兩地研究英國以澳洲為罪犯流放地的歷史,並為了紀念她祖母家族篳路藍縷、開闢疆域的事蹟,而把自己的姓氏由原本的「吉伊」改為「葛倫薇爾」。小說《我的祕密河流》當中,也有相當部分取材自她祖先的親身遭遇。
《我的祕密河流》是葛倫薇爾最重要的作品,推出後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廣受好評,先後獲得大英國協作家獎、紐約公立圖書館年度推薦書獎、新南威爾斯州長文學獎、澳洲書商選書獎等,並入圍布克獎決選、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初選。二○一三年曾改編成舞台劇演出,二○一五年改拍成兩集迷你影集。
葛倫薇爾於二○一七年獲澳大利亞藝術理事會頒予終身成就獎,二○一八年獲頒澳大利亞勳章,以表揚她的卓越貢獻。現與兒女同住在雪梨。
名人/編輯推薦
得獎紀錄:
2006年大英國協作家獎
2006年大英國協作家獎(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區)最佳圖書
2006年新南威爾斯州長文學獎
2006年澳洲書商選書獎
2006年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澳洲圖書、年度澳洲文學小說
2006年紐約公立圖書館年度推薦書獎
入圍榮耀:
2005年柯林.羅德瑞克獎
2006年布克獎
2006年麥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
2006年昆士蘭州長文學獎
2006年維多利亞州長文學獎
2007年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各界好評推薦:
派屈克.懷特(197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彼得.凱瑞(1988、2001年布克獎得主)
南方朔(作家)
張惠菁(作家)
陳芳明(政大講座教授)
蔡依橙(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劉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一部獨特的小說……一次壯闊的自我探索旅程……只有文學大師才能以看似不費吹灰之力的力道掌握如此廣闊的故事,並且精煉到完美的境界。」 ── 週日獨立報
「這是一本人人都該閱讀的小說。」── 愛爾蘭時報
「本書是作者葛倫薇爾贏得柑橘獎之後,再一次展現她優異的寫作風格。」── 週日泰晤士報
「一部輝煌壯麗的小說……一次勇敢無畏的探險,探究當代澳洲的發源故事。」── 紐約客雜誌
「節奏漂亮、情感豐富,又使讀者的情緒跟著波動……這不是普通的歷史故事,而是真正有溫柔、有同情的小說。」── 泰晤士報
「文化碰撞的傑出故事……殖民主義的詳盡描寫,叫人不寒而慄。」── 衛報
2006年大英國協作家獎
2006年大英國協作家獎(東南亞與南太平洋區)最佳圖書
2006年新南威爾斯州長文學獎
2006年澳洲書商選書獎
2006年澳洲圖書產業獎:年度澳洲圖書、年度澳洲文學小說
2006年紐約公立圖書館年度推薦書獎
入圍榮耀:
2005年柯林.羅德瑞克獎
2006年布克獎
2006年麥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
2006年昆士蘭州長文學獎
2006年維多利亞州長文學獎
2007年國際都柏林文學獎
各界好評推薦:
派屈克.懷特(197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彼得.凱瑞(1988、2001年布克獎得主)
南方朔(作家)
張惠菁(作家)
陳芳明(政大講座教授)
蔡依橙(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劉柳書琴(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教授)
「一部獨特的小說……一次壯闊的自我探索旅程……只有文學大師才能以看似不費吹灰之力的力道掌握如此廣闊的故事,並且精煉到完美的境界。」 ── 週日獨立報
「這是一本人人都該閱讀的小說。」── 愛爾蘭時報
「本書是作者葛倫薇爾贏得柑橘獎之後,再一次展現她優異的寫作風格。」── 週日泰晤士報
「一部輝煌壯麗的小說……一次勇敢無畏的探險,探究當代澳洲的發源故事。」── 紐約客雜誌
「節奏漂亮、情感豐富,又使讀者的情緒跟著波動……這不是普通的歷史故事,而是真正有溫柔、有同情的小說。」── 泰晤士報
「文化碰撞的傑出故事……殖民主義的詳盡描寫,叫人不寒而慄。」── 衛報
序
中文版序
十八世紀中期以前,澳洲大陸一直只是想像中的存在。一七七〇年,探險家詹姆士.庫克船長的艦隊抵達澳洲沿海;幾年後,英國政府便決定以此地作為囚犯的流放所。接下來的五十年,一批又一批的囚犯接連抵達這塊新大陸。
我往上推九代的一位老祖先索羅門.衛斯曼,就在那時來到澳洲。他原先在倫敦泰晤士河做船夫,偷了一批木材而被定罪,一八〇六年到達雪梨,過了幾年就獲得赦免,成了定居當地的開拓者,並累積了不少財富。
這故事是我母親說的,她說衛斯曼祖先是因為「取得」了雪梨附近霍克斯布里河域的土地,才能在澳洲發達起來。我一直很相信母親說的,直到十年前,我才意識到,這故事還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大約在六萬年前,澳洲原住民早已在此定居,在嚴酷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下,他們靠打獵和採集維生,繁衍不息。而一切在英國人抵達後卻變了樣,衛斯曼祖先就是當時被流放澳洲的英國人。
我瞭解到,衛斯曼祖先的土地不是「取得」的,而是從原住民手中「搶奪」來的。在學校裡讀到的澳洲歷史鮮少提及原住民,進一步研究後,促使我正視這段悲傷的過往。我才知道,原來在這個邊疆地區,原住民和白人之間的關係,套用一位著名的澳洲人類學家的話, 是「一條祕密的鮮血之河」。
因此我深切覺得,必須進一步瞭解衛斯曼祖父的事情,寫下殖民者的故事,不是為了作價值論斷,也並非要譴責誰,我的出發點在於體諒。我想衛斯曼不會是天使或惡魔的極端,他只是一個平凡人,為了自己和家庭討生活的平凡人。
為了勾勒出十九世紀前期邊疆地區的生活樣貌,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不僅查閱當代的文獻,更實際走訪那片荒叢之地。我去了衛斯曼祖父的故居附近,像他一樣乘船上溯霍克斯布里河;嘗試他們家以前吃的食物,還親手用油脂做了一個陽春的燈,因為他們都是這樣照明的。我想盡辦法要體驗樹皮屋裡的生活,只因他們以前就住在這種地方,離最近的小鎮要好幾天路程。我還去了倫敦,在那裡明白到,衛斯曼祖父不幸誕生在社會的最底層,注定生活在極度匱乏之中,日復一日挨餓受凍,一輩子都是艱難萬分。
構思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逐漸把老祖父的故事轉換成另一個主人翁:威廉.索恩希爾。索恩希爾是一個極度善感的人,心思細膩,但他身處的世界,卻是不容許任何一絲的軟弱。
初抵澳洲,他便身陷從未想像過的生命處境。在他以前熟知的那個世界,索恩希爾絕不敢希冀三餐溫飽以外的事物;然而,在這片新大陸,像他這出身的人,竟也能「取得」一片土地,據地為主。要擁有一塊地看似容易,在索恩希爾的文化裡,所有權標記就代表了領地,而這片土地尚未有人畫界。這裡沒有圍籬,沒有道路,更沒有堅固的住所。原住民四處遷徙,不帶太多行囊,而每個部落謹守各自的領域,毋須畫地為界。
過了好久好久,索恩希爾才逐漸意識到,出沒在「他的」領土週遭的這些黑影,不僅已先他一步在此落腳,更會誓死保禦領地,於是索恩希爾面臨了無法取捨的抉擇。
進一步構思書的走向,我發覺他的妻子莎莉幾乎和索恩希爾佔有相同的份量,隨著故事進展,索恩希爾踏上通往某種「領悟」的旅途;而莎莉也有自己的旅程,終點是另一種不同的領悟。
書名「我的祕密河流」有很多層意義,就字面上來看,指的是霍克斯布里河。它也是「祕密的血河」,流過澳洲殖民史的水域。對我個人來說,這條祕密的河,是我自己的旅程,身為早期殖民者的後代,這是一趟認識過往的路途。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凱特.葛倫薇爾
十八世紀中期以前,澳洲大陸一直只是想像中的存在。一七七〇年,探險家詹姆士.庫克船長的艦隊抵達澳洲沿海;幾年後,英國政府便決定以此地作為囚犯的流放所。接下來的五十年,一批又一批的囚犯接連抵達這塊新大陸。
我往上推九代的一位老祖先索羅門.衛斯曼,就在那時來到澳洲。他原先在倫敦泰晤士河做船夫,偷了一批木材而被定罪,一八〇六年到達雪梨,過了幾年就獲得赦免,成了定居當地的開拓者,並累積了不少財富。
這故事是我母親說的,她說衛斯曼祖先是因為「取得」了雪梨附近霍克斯布里河域的土地,才能在澳洲發達起來。我一直很相信母親說的,直到十年前,我才意識到,這故事還有我不知道的一面。
大約在六萬年前,澳洲原住民早已在此定居,在嚴酷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下,他們靠打獵和採集維生,繁衍不息。而一切在英國人抵達後卻變了樣,衛斯曼祖先就是當時被流放澳洲的英國人。
我瞭解到,衛斯曼祖先的土地不是「取得」的,而是從原住民手中「搶奪」來的。在學校裡讀到的澳洲歷史鮮少提及原住民,進一步研究後,促使我正視這段悲傷的過往。我才知道,原來在這個邊疆地區,原住民和白人之間的關係,套用一位著名的澳洲人類學家的話, 是「一條祕密的鮮血之河」。
因此我深切覺得,必須進一步瞭解衛斯曼祖父的事情,寫下殖民者的故事,不是為了作價值論斷,也並非要譴責誰,我的出發點在於體諒。我想衛斯曼不會是天使或惡魔的極端,他只是一個平凡人,為了自己和家庭討生活的平凡人。
為了勾勒出十九世紀前期邊疆地區的生活樣貌,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不僅查閱當代的文獻,更實際走訪那片荒叢之地。我去了衛斯曼祖父的故居附近,像他一樣乘船上溯霍克斯布里河;嘗試他們家以前吃的食物,還親手用油脂做了一個陽春的燈,因為他們都是這樣照明的。我想盡辦法要體驗樹皮屋裡的生活,只因他們以前就住在這種地方,離最近的小鎮要好幾天路程。我還去了倫敦,在那裡明白到,衛斯曼祖父不幸誕生在社會的最底層,注定生活在極度匱乏之中,日復一日挨餓受凍,一輩子都是艱難萬分。
構思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逐漸把老祖父的故事轉換成另一個主人翁:威廉.索恩希爾。索恩希爾是一個極度善感的人,心思細膩,但他身處的世界,卻是不容許任何一絲的軟弱。
初抵澳洲,他便身陷從未想像過的生命處境。在他以前熟知的那個世界,索恩希爾絕不敢希冀三餐溫飽以外的事物;然而,在這片新大陸,像他這出身的人,竟也能「取得」一片土地,據地為主。要擁有一塊地看似容易,在索恩希爾的文化裡,所有權標記就代表了領地,而這片土地尚未有人畫界。這裡沒有圍籬,沒有道路,更沒有堅固的住所。原住民四處遷徙,不帶太多行囊,而每個部落謹守各自的領域,毋須畫地為界。
過了好久好久,索恩希爾才逐漸意識到,出沒在「他的」領土週遭的這些黑影,不僅已先他一步在此落腳,更會誓死保禦領地,於是索恩希爾面臨了無法取捨的抉擇。
進一步構思書的走向,我發覺他的妻子莎莉幾乎和索恩希爾佔有相同的份量,隨著故事進展,索恩希爾踏上通往某種「領悟」的旅途;而莎莉也有自己的旅程,終點是另一種不同的領悟。
書名「我的祕密河流」有很多層意義,就字面上來看,指的是霍克斯布里河。它也是「祕密的血河」,流過澳洲殖民史的水域。對我個人來說,這條祕密的河,是我自己的旅程,身為早期殖民者的後代,這是一趟認識過往的路途。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我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凱特.葛倫薇爾
目次
中文版序
陌生人
第一部 倫敦
第二部 雪梨
第三部 森林中的空地
第四部 百畝良田
第五部 劃清界線
第六部 祕密的河流
索恩希爾的宮殿
陌生人
第一部 倫敦
第二部 雪梨
第三部 森林中的空地
第四部 百畝良田
第五部 劃清界線
第六部 祕密的河流
索恩希爾的宮殿
書摘/試閱
第二部 雪梨
這個雪梨城是一個又糟又亂的地方,老經驗的人稱它為「營地」。一八〇六年的時候,它仍然保留原始風貌,是一個還不太成熟的暫居地。
二十年前,附近是一個複雜的大水域,雪梨只是附近數百個小海灣之一。一七八八年一月一個炎熱的下午,白色的大鳥從海岸的樹上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英國皇家海軍的一位船長將船開進這個海域,並且選擇停泊在一個擁有淡水溪流和狹長海灘的海灣。他步出船,下令將英國國旗升起,並且宣佈此地是「信念捍衛者」英國國王喬治三世領土的延伸。現在它的名字是雪梨海灣,作用只有一個:收容那些被英國法庭判刑的罪犯。
九月的一個早晨,「亞歷山大號」在雪梨海灣下錨,索恩希爾花了一些時間才看清他四周的地方。重罪犯們被帶到甲板上,但是因為被拘留在暗處太久,天空灑下的光線彷彿在侵襲他們的臉龐,強烈的光點從水面反射,閃閃發光。他用手遮臉,從指間瞇著眼看,感覺到眼淚熱辣辣地流下臉龐,便眨著眼睛將淚撇開。他暫時看清楚周遭的事物,包括「亞歷山大號」停泊的明亮水域,以及有一部分像腳掌般伸進海中、上面覆滿森林的起伏地形。沿著海岸附近有幾排短小而厚實的金色建築物,它們的窗戶呈現金色的光滑表面,它們在一道道光線裡游移,變得模糊。
他的耳鳴嚴重,他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太陽,那熾熱穿透了他薄薄的衣服,現在雖然在陸地上,他又開始暈船,覺得腳下的土地好像在膨脹,陽光從水面上發出的邪惡閃光重擊著他的頭骨。
走到碼頭木板上剛好病到不知不覺,算是一種解脫。
就在他被陽光曬得痛苦萬分時,有個女人出現,叫著他的名字,並且從人群中擠向他。「小威!」她喊著:「在這裡,小威!」他轉身看去。「我太太,」他想著:「是我太太莎莉。」但她就好像只是他太太的一張照片;分開這麼久,他不敢相信她的本尊就在眼前。
當一個蓄著黑色濃鬍的男人用一根棍子推她回去時,時間剛好夠他打量她身邊緊靠著她大腿的男孩,以及她臂彎裡襁褓中的嬰兒。「還沒輪到妳,妳這娼婦。」他叫嚷著,用他張開的大手打她的頭。之後她就隱沒在一堆臉孔之中,只見他們張嘴叫喊的喉嚨,在陽光下像是一個個漆黑的洞。「索恩希爾!威廉.索恩希爾!」在一片吵雜聲中他聽到有人叫他。「我就是索恩希爾。」他回答,自己的聲音又沙啞又小聲。那個大鬍子男人抓著他的手臂,在異常清晰的陽光照耀下,索恩希爾看到他嘴巴四周的鬍子全是麵包屑。那個人看了一下手中的名單,然後大喊:「威廉.索恩希爾指派給索恩希爾太太負責管束!」他叫得太用力了,以致於他鬍子上的麵包屑紛紛掉落。
莎莉走上前去。「我是索恩希爾太太,」她在嘈雜聲中喊道。索恩希爾被強光和噪音所震懾,但他清楚聽到她的聲音。「他不是指派給我負責管束,他是我丈夫。」那個人投以嘲諷的眼光。「他或許是妳丈夫,但現在妳是主人了,寶貝,」他說:「指派給妳管束,寶貝,那就悉聽尊便,妳想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男孩抓著莎莉的裙子角,盯著他父親看,大大的眼睛滿是恐懼。這是威利,現在五歲了,變得更高更瘦。對一個這麼小的小孩來說,九個月的旅程就像一輩子那麼長。索恩希爾看得出,他的小孩並不認得眼前這個彎下身子靠近他的陌生人。
新生兒是在七月「亞歷山大號」停泊在開普敦時出生的,莎莉運氣很好,她開始陣痛的時候,船正好在港口,生完之後,他們讓他去看她,但時間很短。「是男孩,小威,」她低聲說。「要取名理查嗎?紀念我父親?」然後她蒼白的嘴唇就再也說不出話來了,只有她那隻按著他的手繼續對他訴說著事情。過了片刻,他們將他帶回男子區,雖然他有時可以聽到艙壁以外的嬰兒聲,卻從不知道哪個嬰兒可能是他孩子的聲音。
現在他不需要拼命找出他孩子的聲音來源了。嬰兒的哭聲大到令他震耳欲聾。
「小威,」她一邊笑著說,一邊伸手拉他的手。「小威,是我們,記得嗎?」他看到他記憶中的彎曲牙齒,以及她微笑時眼睛瞇起來的樣子。他嘗試要跟著微笑,「莎莉,」他想說下去,卻說不出話,那兩個字變成像啜泣般讓人窒息的喘氣。
國王陛下的政府核發給囚犯威廉.索恩希爾的觀護人索恩希爾太太一個星期的食物、幾條毯子,以及一間在碼頭後面山坡上的小屋。那是國王陛下覺得必須提供的物資範圍,目的是要讓奴僕威廉.索恩希爾替他主人,亦即他的妻子做任何需要可能做的事。他在各方面都是奴隸,必須聽命於主人行事。因此,重罪犯仍然是囚犯,但是主人要善盡管理之責。就一個家庭而言,這表示全家要能夠自力更生,不再仰賴政府的資助。
這項巧妙的設計,實現了國王陛下的仁慈,讓許多人免受絞刑。
從當天下午開始,索恩希爾一家就得靠自己過活了。
指派給他們落腳的山丘陡峭嶔崎,滿是石板,上面已經住了不少人,就像蛋糕上爬滿螞蟻一樣。有些人住在小屋裡,但是大部分人在靠近山坡的突出岩石下搭蓋了住處,有些人利用牆壁掛起帆布,其他人則是搬來一些大樹枝抵著出口。相形之下,索恩希爾的抺灰籬笆牆小屋就顯得很大,即使除了泥牆和泥地之外,裡頭什麼奢華的東西也沒有。
他們三人站在門口往裡面看,沒有一個人想趕快進去。小威利把拇指伸進嘴裡,目光遲鈍地望著,避免接觸到索恩希爾的眼光。「至少不是洞穴,」莎莉最後說道。他可以從她略嫌高亢的聲音中聽出她竭力克制。「不用擔心,」他讓自己說出這些話。男孩轉過去抬頭看他,然後把臉、拇指等統統埋進她
的裙子。「非常舒適。」對他而言,他的話聽起來和一個人在管筒裡說話一樣空洞。
太陽沉落到山脊後面,潮濕的空氣開始往山下移動。有一男一女從另一個洞穴沿著山坡走到索恩希爾家,那個男人留了一臉纏結的鬍鬚,但一點頭髮也沒有,而那個女人有一個沒牙的癟嘴,穿的裙子破爛不堪。兩人的臉孔都黑黑髒髒的,而且都喝了酒,走起路搖搖晃晃。那男人拿了一根悶燒的棍子,而那女人拿了一個茶壺。「嘿!」那女人說:「送你們這個,別客氣。」
索恩希爾以為那是在開玩笑,因為茶壺的底部是木頭做的,於是當著那女人的面笑了起來。但是她並沒有跟著笑。「挖個洞,」她說。這時她突然打了個嗝,整個胸部抽動了一下,所以中斷說話。「在它周圍升個火。」打嗝的力道使得她必須閉上眼睛。「棒得很,」她大喊。她直接走到索恩希爾跟前,把一隻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因此聞到她身上的蘭姆酒味和骯髒味。「真他媽的棒極了!」
那個男人酩酊大醉,連眼珠子都在眼睛裡頭轉個不停。他用雷鳴般的大嗓門叫嚷,好像索恩希爾一家人遠在半哩外似的:「夥伴,看看那些沒用的野蠻人。」然後發出充滿蘭姆酒味的一陣大笑。接著他態度轉趨認真,屈膝盯著威利看。「他們特別喜歡像你孩子這種美味可口的食物。」他俯身用硬梆梆的手指捏著威利圓胖的臉頰,把威利弄得大哭,還在打嗝的女人便把那男人拖開。
他們將一點醃豬肉插到木棍上用火烤,並且用一片片樹皮當作盤子來盛裝。沒有小杯子,他們就直接從壺嘴喝那女人帶給他們的茶。麵包在他們手上碎開,但是他們把麵包屑從地上撿起來吃掉,一邊嚼一邊覺得泥粒在他們的齒間嘎吱作響。
索恩希爾家最晚吃飽的人,是咂咂作聲吸著莎莉母奶的小嬰兒。
時值黃昏,他們坐在小屋外的地上,往下看著這個初來乍到的地方。從山坡這裡往下看,流放地向平原擴展,是個新開發的小地方。其中有一些充滿車輪痕跡的街道,兩邊的溪流都流進海濱,但是在更遠之外,像動物奔跑足跡般的便道將建築物連接起來,石頭和樹木間的扭結,就像樹木本身一樣。往下靠海邊的是碼頭及沿著海岸用磚塊和石頭砌成的一些大型建築。但是離海邊較遠的地方,建築物零星分散成一間間用樹皮或塗料搭成的小屋,與其說是屋子,不如說是將泥巴和木棍黏在一,用木柴籬笆圍住的簡陋場地。豬隻在河流旁邊的灰泥巴裡打滾;一個只用一塊破布遮住腰身的赤裸小孩,站著看一群小狗抓咬帶著一群小雞的母雞;一個男人挖掘歪斜籬笆後面的一塊地。
每件東西看起來都奇怪地互不相干,這裡的地被分割成幾個方塊,散置在這片地廣物稀的土地上,就像英國領土的碎片。
更遠之外是綿延幾哩的粗獷森林。這片森林的灰色比綠色多,四面八方圍繞著山脈和山谷,像布料紋路般一致,低窪地區之間則是水塘。
索恩希爾以前從未到過其他地方,他曾經想像全世界就跟倫敦一樣,相差只是幾隻鸚鵡和幾棵棕櫚樹而已。空氣、水、泥土和岩石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這個地方和他以前所看過的地方完全不同。
在他過去的歲月裡,這個海灣早就存在,隨著地形發展出它的外觀。他曾經在倫敦的黑暗和塵土之中,做牛做馬地低頭工作,在那同時,眼前這棵自行更替葉片的樹木正悄悄呼吸,悄悄生長。一季季的太陽和高溫,一季季的風和雨,都是自然更迭,他完全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早在他來此之前,這個地方就一直存在。在他離開以後,這個地方會繼續颯颯作響、繼續呼吸,並且堅持本我,而土地會隨著自己本來的生命軌跡,繼續推擠。
索恩希爾往下可以看到「亞歷山大號」。隨著令人作嘔的搖晃,他記得那張吊床、他頭頂上橫樑的結,以及不論他睡醒或沉睡時都張著看他的一隻眼睛。
夜復一夜躺在那裡,他一直想著莎莉,直到對她的回憶變得了無新意為止。但是現在她的臀部緊貼著他的臀部,她的大腿與他的大腿靠攏。要不是為了威利,他就不必躡手躡腳,蜷縮著讓自己的體積變小,而且如果不是顧忌威利,他就能夠轉身看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在他們擁抱時感受她緊緊相依所傳來的溫暖。
在他們後面的山丘上,有隻鳥一再發出「啊,啊,啊」的哀鳴,但是除了這點以外,現在整個世界已經不再有悲傷的事情。
要離開火堆走進陰鬱的小屋,並不容易。索恩希爾拿著火把帶路先走進去,但是火把一下子就熄滅了,餘煙還將他們燻得差點窒息,所以他把火把丟到外面。他們靠著觸覺把毯子鋪好,然後把嬰兒放在上面。他寬慰地嘆了一口氣,好像腳下踩著的是羽毛鋪蓋一樣,立即就睡著了。
一開始威利不肯躺在嬰兒旁邊,雖然他已經筋疲力盡,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聲音高亢易怒。索恩希爾原本希望他和莎莉能夠回到火堆旁邊聊天,彌補他們生命中分離九個月的缺口。莎莉睡在毯子的最外緣,索恩希爾躺在泥地上,聽著威利漸漸靜下來睡著。
最後他發現莎莉靠著他移近。「他睡著了,小威,」她輕聲說:「可憐的小傢伙。」
除了腿靠著腿之外,他們一直到現在才觸摸彼此。他覺得有點害羞:莎莉一路上獨自航行,隱身在艙壁的另一端,誰知道她的情況怎樣?
他覺得她可能心有同感。她的肩膀貼著他的肩膀,她的腿和他的腿靠攏並排,但卻帶著羞怯,就好像是碰巧如此。他可以感受到她的溫暖,她的肉體和肌膚。他感覺到她的雙手往上移到他的胸膛,再移到他的臉,努力想要回憶她所知道的丈夫。
「感謝您,韓歇爾太太,感謝您拒絕這項特權。」她喊道,試著要低聲耳語,但卻笑著衝口說出,在那一刻,舊日的她,那個發現可憐的蘇珊娜.伍德很滑稽的厚臉皮女孩,他的莎莉,又回來了。他把一隻手放在她大腿上,身體轉向她,以便在黑暗中能仍隱約看著那張他深愛的臉。他知道她正在微笑。
「另外也要感謝索恩希爾太太,」他說。「我也得感謝她,寶貝。」她和他十指緊緊交纏,他聽到她正在哭,但是也在笑,可以說是悲喜交集。「小威,」她低語,想要說點什麼,但是他們雙手的接觸代表心中的千言萬語。
第二天早上,索恩希爾懷疑他在黑暗中遇到黑人是否只是一個夢。白天時回想起他和黑人的對話――「走開!走開!」――這種記憶讓人很難置信。
人們很容易先從熟悉的部分理解。這一小塊英國領地在森林內延伸。雪梨這地方看似陌生,但是在某些方面(而且是索恩希爾一家認為很重要的方面)它都是泰晤士河的翻版。在這裡想要生存,除了依靠它與英國連繫起來的船隻之外,別無他法。政府當局原本希望這裡最後能自行生產農作物和羊群,但是流放地仍舊不斷向英國本土求助,派遣運送民生必需品的船隻。在碼頭和這些載滿麵粉、豌豆、釘子、帽子、白蘭地和蘭姆酒的船隻之間,船夫的小船前前後後川流不息,就和泰晤士河的情況一樣。
索恩希爾一生都當船夫,在泰晤士河或是在雪梨灣的水面上做這件事,差異並不大。
他為許多主人工作,但主要是為亞歷山大.金恩先生幹活兒,在金恩先生的石砌倉庫中,有一間是索恩希爾第一天就看到的。金恩是個整潔的人,一對小耳朵伏貼著頭,下巴的酒窩深到可以丟進一隻靴子。他個性開朗,喜歡逗人高興,索恩希爾總是很感激,如果知道笑話是金恩先生開的,他的笑聲會更由衷。
金恩先生涉足多項領域,但是與索恩希爾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是一種桶子,這種桶子裝著某種在澳洲很珍貴的液體,金恩先生請人用船從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印度群島運進來。金恩先生會在早上過來,在太陽下站在碼頭上,手上拿著清單,在貨物送往海關的途中。仔細地清點桶數;有多少牙買加甜酒,多少法國白蘭地和錫蘭琴酒。他付錢不囉嗦,而且面帶微笑,因為他知道沒有出現在清單的其他酒桶,在晚上會有人替他看守。那是索恩希爾的工作:將那些酒桶從船上暗中運到流放地附近的海灣,運到那裡,就可以避開海關緊抓不放的手。
「你會分到一杯羹,索恩希爾,」金恩帶著沉著的微笑告訴他,那是屬於成功商人的微笑。「你會發現酒比法定貨幣還好。」索恩希爾並不擔心分不到一杯羹,他說:「您可以信任我,金恩先生。」他們握了手,就這麼講定了。
金恩先生是個快樂的人,不會擔心桶箍底下小小的裂口,以及索恩希爾口袋裡的螺絲錐。他不會苦惱,因為他不知道,當他安然地躺在羽毛床鋪裡時,索恩希爾正摸黑忙碌工作。
早上和下午,被鏈在一起的囚犯在劈柴搭建的營房裡拖著腳走來走去,腳鐐還發出叮噹響聲,由於囚營裡的吊床靠得太密,囚犯們往往成為彼此夢境的一部分。
如果莎莉沒有擔任他的觀護人,索恩希爾就會被分派到其中一個囚營,或者會被指派給某個移民,這個移民因此可以一年換取一次食物和一套工作服,而且可以隨意指揮他轄下的囚犯。有些人運氣好,碰到比較好心的主人,這種主人會讓囚犯不愁吃穿,一年過後還會讓他們申請假釋許可證。但是對許多主人而言,有人免費替他做事,這種吸引力實在令人難以抗拒,所以一年刑期還沒結束,主人們就會先確定奴僕被控某項輕罪或是其他罪行,免得他們取得假釋許可證。
假釋許可證是新南威爾斯的特產,這裡一年裡有三季沒種麥穀也沒放牧,利用土地生產糧食是當務之急。政府當局瞭解,這個地方要能夠自給自足,必須靠的是自由工人,而不能靠被迫服刑的罪犯。要讓那些人有足夠的自由,可以憑自己付出的勞力得到好處,但又不致於太過自由而擺脫囚犯的身分,假釋許可證是一個方法。
來這裡一年半之後,囚犯可以申請假釋許可證,口袋裡擺一張這樣的證件,就可以和任何普通人一樣自由行動。他可以隨意選擇雇主出賣勞力,或是佔用一塊地自行工作,唯一的限制是他不能離開這個殖民地。對於本來應該上絞刑台的人而言,這項限制似乎是很輕微的束縛。
但是接下來的一年,也就是在可以申請假釋許可證之前,索恩希爾的主人就莎莉,這一點變成他們之間談笑的話題。每天晚上,他們先鋪好一層蕨類植物,然後再鋪上一塊帆布作為床墊,他會轉身面對她。「女士,我最好稱呼你索恩希爾太太,」他一邊說,一邊緊抱著她,在海上的那幾個月,他已經在想像中觸摸過她的肉體,現在他的雙手做再多次這個動作也不厭倦。「是的,索恩希爾太太,好的,索恩希爾太太,隨時聽您吩咐,索恩希爾太太。」這個地方有許多事情讓人摸不清頭緒,但是他最清楚的仍然是她肉體的觸感。莎莉靠得更近,帆布底下的蕨類植物也跟著移動,就像和他們同床共枕、一刻也靜不下來的動物。「咦,索恩希爾,」她低語:「我的好男人,讓我想想看,你要怎麼伺候我?」
這個地方靠蘭姆酒運作,就像馬匹靠燕麥運作。蘭姆酒是交易的貨幣,錢幣則是幾乎用不上。此外,蘭姆酒可撫慰人心,在這塊殖民地上的每個人,都可能因為喝了酒而像飛上月亮一樣。
只要在流放區走動,就一定會走到開放式酒棚,這種建築只不過是用幾根打進土裡的樹枝所撐起的樹皮屋頂,再加上用枝條做成的櫃檯。在這個地方隨時都可以買到蘭姆酒。有人攤開四肢躺在翻轉過來的酒桶上,頭靠在櫃檯上,早已不醒人事,手裡仍然緊緊抓住酒杯,連指關節都呈現白色;在櫃檯後面,臉龐瘦削的人面無表情地看著他們的世界。
靠著金恩先生知情而分一杯羹,以及金恩先生不知情的蘭姆酒,索恩希爾一家人很快就搬進河邊的另一間小屋。這間屋子主要是泥土蓋的,比第一間大,還有石頭壁爐和樹皮煙囪。雨通常會透過屋頂以及樹皮滲進來,但是他們互相提醒,這個房子比當年向巴特勒租來的房間好太多了,尤其是在通風方面。
他們把屋子隔成兩個房間,中間用一塊掛在椽上的帆布隔開,其中一間用來開設酒棚。她證明了自己經營客棧的能力,一邊運用微笑的魅力讓客人樂開懷,一邊倒著金恩先生的牙買加好酒,威利在外面的泥巴路上跑來跑去,小查理則是安靜地躺在搖籃裡。
每個週末,莎莉會清點所得,包括索恩希爾在水上工作的酬勞和她自己賣酒的收入,然後把錢藏在床墊下的一個盒子裡。之後他們哄孩子們在角落睡覺,索恩希爾將大酒桶裝滿酒,再為他們自己倒一大杯金恩先生的上等法國白蘭地――這種酒和總督在山上豪宅裡享用的酒一模一樣――然後在床墊上開始放鬆飲酒,把雙腳放在堆成一堆的硬幣盒上。
那些輕聲絮語的時光充滿了樂趣,他們互相傾訴未來的願景。勤奮節儉的人很快就可以達成目標,這種例子在這裡俯拾皆是。曾經是亞歷山大號指揮官的沙克林船長就是其中一例,在倫敦,沙克林不過是眾多容貌粗陋、腳趾外露的船長之一,但是他在此地落腳,現在已經是這裡穿著銀鈕釦背心、神氣活現的人物。他變豐潤了,生活優渥使得他容光煥發,鬍子刮得乾淨到透出青色的微光。
即使是重罪犯出身的人,也可以透過制度――從指派做奴僕、申請假釋許可證到取得特赦――在幾年內打拼出頭天。他看到這種人站在碼頭上,不可一世地打量別人:這些人比他好不到哪裡去,卻因為擁有自由而賺進大把鈔票,現在可以大大方方直視任何人。
索恩希爾夫婦告訴自己,不久之後,他們會存夠錢回到倫敦。只要他們確定能夠擁有永久產權,他們就可以在波若市場天鵝巷裡買一間很棒的小房子,屆時,河邊碼頭會繫著一艘和上等蘋果一樣好的擺渡船,還會有一個既優秀又強壯的學徒負責划船,他們則是悠閒地待在溫馨客廳裡的壁爐旁,舒適的扶手椅讓他們筋骨放鬆,而女僕會來添加煤炭。「我覺得,小威!」莎莉捲起身子貼著他耳語說:「我可以聞到她剛端給我們的烤馬芬鬆餅上的奶油香!」
乾脆擁有兩艘船好了,還有幾個學徒。
「其中一艘載著印度的渦紋圖案披巾,」莎莉低語:「還有,我再也不必自己洗衣服了。」
索恩希爾可以想像自己悠閒地享用一碟小鯡魚和一杯上等好酒,看起來就像有很多黃金存在銀行裡。他飯後抽著菸斗到河邊散步時,小老百姓會向他問候。「您好,索恩希爾先生!日安,索恩希爾先生!」做窮人時經常練習當富人的樣子,所以他知道以後他會成為和善的有錢人。
一點運氣,再加上大量的勤奮,有了這些,就沒有任何事可以攔阻他們。
這個雪梨城是一個又糟又亂的地方,老經驗的人稱它為「營地」。一八〇六年的時候,它仍然保留原始風貌,是一個還不太成熟的暫居地。
二十年前,附近是一個複雜的大水域,雪梨只是附近數百個小海灣之一。一七八八年一月一個炎熱的下午,白色的大鳥從海岸的樹上發出尖銳刺耳的叫聲,英國皇家海軍的一位船長將船開進這個海域,並且選擇停泊在一個擁有淡水溪流和狹長海灘的海灣。他步出船,下令將英國國旗升起,並且宣佈此地是「信念捍衛者」英國國王喬治三世領土的延伸。現在它的名字是雪梨海灣,作用只有一個:收容那些被英國法庭判刑的罪犯。
九月的一個早晨,「亞歷山大號」在雪梨海灣下錨,索恩希爾花了一些時間才看清他四周的地方。重罪犯們被帶到甲板上,但是因為被拘留在暗處太久,天空灑下的光線彷彿在侵襲他們的臉龐,強烈的光點從水面反射,閃閃發光。他用手遮臉,從指間瞇著眼看,感覺到眼淚熱辣辣地流下臉龐,便眨著眼睛將淚撇開。他暫時看清楚周遭的事物,包括「亞歷山大號」停泊的明亮水域,以及有一部分像腳掌般伸進海中、上面覆滿森林的起伏地形。沿著海岸附近有幾排短小而厚實的金色建築物,它們的窗戶呈現金色的光滑表面,它們在一道道光線裡游移,變得模糊。
他的耳鳴嚴重,他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太陽,那熾熱穿透了他薄薄的衣服,現在雖然在陸地上,他又開始暈船,覺得腳下的土地好像在膨脹,陽光從水面上發出的邪惡閃光重擊著他的頭骨。
走到碼頭木板上剛好病到不知不覺,算是一種解脫。
就在他被陽光曬得痛苦萬分時,有個女人出現,叫著他的名字,並且從人群中擠向他。「小威!」她喊著:「在這裡,小威!」他轉身看去。「我太太,」他想著:「是我太太莎莉。」但她就好像只是他太太的一張照片;分開這麼久,他不敢相信她的本尊就在眼前。
當一個蓄著黑色濃鬍的男人用一根棍子推她回去時,時間剛好夠他打量她身邊緊靠著她大腿的男孩,以及她臂彎裡襁褓中的嬰兒。「還沒輪到妳,妳這娼婦。」他叫嚷著,用他張開的大手打她的頭。之後她就隱沒在一堆臉孔之中,只見他們張嘴叫喊的喉嚨,在陽光下像是一個個漆黑的洞。「索恩希爾!威廉.索恩希爾!」在一片吵雜聲中他聽到有人叫他。「我就是索恩希爾。」他回答,自己的聲音又沙啞又小聲。那個大鬍子男人抓著他的手臂,在異常清晰的陽光照耀下,索恩希爾看到他嘴巴四周的鬍子全是麵包屑。那個人看了一下手中的名單,然後大喊:「威廉.索恩希爾指派給索恩希爾太太負責管束!」他叫得太用力了,以致於他鬍子上的麵包屑紛紛掉落。
莎莉走上前去。「我是索恩希爾太太,」她在嘈雜聲中喊道。索恩希爾被強光和噪音所震懾,但他清楚聽到她的聲音。「他不是指派給我負責管束,他是我丈夫。」那個人投以嘲諷的眼光。「他或許是妳丈夫,但現在妳是主人了,寶貝,」他說:「指派給妳管束,寶貝,那就悉聽尊便,妳想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男孩抓著莎莉的裙子角,盯著他父親看,大大的眼睛滿是恐懼。這是威利,現在五歲了,變得更高更瘦。對一個這麼小的小孩來說,九個月的旅程就像一輩子那麼長。索恩希爾看得出,他的小孩並不認得眼前這個彎下身子靠近他的陌生人。
新生兒是在七月「亞歷山大號」停泊在開普敦時出生的,莎莉運氣很好,她開始陣痛的時候,船正好在港口,生完之後,他們讓他去看她,但時間很短。「是男孩,小威,」她低聲說。「要取名理查嗎?紀念我父親?」然後她蒼白的嘴唇就再也說不出話來了,只有她那隻按著他的手繼續對他訴說著事情。過了片刻,他們將他帶回男子區,雖然他有時可以聽到艙壁以外的嬰兒聲,卻從不知道哪個嬰兒可能是他孩子的聲音。
現在他不需要拼命找出他孩子的聲音來源了。嬰兒的哭聲大到令他震耳欲聾。
「小威,」她一邊笑著說,一邊伸手拉他的手。「小威,是我們,記得嗎?」他看到他記憶中的彎曲牙齒,以及她微笑時眼睛瞇起來的樣子。他嘗試要跟著微笑,「莎莉,」他想說下去,卻說不出話,那兩個字變成像啜泣般讓人窒息的喘氣。
國王陛下的政府核發給囚犯威廉.索恩希爾的觀護人索恩希爾太太一個星期的食物、幾條毯子,以及一間在碼頭後面山坡上的小屋。那是國王陛下覺得必須提供的物資範圍,目的是要讓奴僕威廉.索恩希爾替他主人,亦即他的妻子做任何需要可能做的事。他在各方面都是奴隸,必須聽命於主人行事。因此,重罪犯仍然是囚犯,但是主人要善盡管理之責。就一個家庭而言,這表示全家要能夠自力更生,不再仰賴政府的資助。
這項巧妙的設計,實現了國王陛下的仁慈,讓許多人免受絞刑。
從當天下午開始,索恩希爾一家就得靠自己過活了。
指派給他們落腳的山丘陡峭嶔崎,滿是石板,上面已經住了不少人,就像蛋糕上爬滿螞蟻一樣。有些人住在小屋裡,但是大部分人在靠近山坡的突出岩石下搭蓋了住處,有些人利用牆壁掛起帆布,其他人則是搬來一些大樹枝抵著出口。相形之下,索恩希爾的抺灰籬笆牆小屋就顯得很大,即使除了泥牆和泥地之外,裡頭什麼奢華的東西也沒有。
他們三人站在門口往裡面看,沒有一個人想趕快進去。小威利把拇指伸進嘴裡,目光遲鈍地望著,避免接觸到索恩希爾的眼光。「至少不是洞穴,」莎莉最後說道。他可以從她略嫌高亢的聲音中聽出她竭力克制。「不用擔心,」他讓自己說出這些話。男孩轉過去抬頭看他,然後把臉、拇指等統統埋進她
的裙子。「非常舒適。」對他而言,他的話聽起來和一個人在管筒裡說話一樣空洞。
太陽沉落到山脊後面,潮濕的空氣開始往山下移動。有一男一女從另一個洞穴沿著山坡走到索恩希爾家,那個男人留了一臉纏結的鬍鬚,但一點頭髮也沒有,而那個女人有一個沒牙的癟嘴,穿的裙子破爛不堪。兩人的臉孔都黑黑髒髒的,而且都喝了酒,走起路搖搖晃晃。那男人拿了一根悶燒的棍子,而那女人拿了一個茶壺。「嘿!」那女人說:「送你們這個,別客氣。」
索恩希爾以為那是在開玩笑,因為茶壺的底部是木頭做的,於是當著那女人的面笑了起來。但是她並沒有跟著笑。「挖個洞,」她說。這時她突然打了個嗝,整個胸部抽動了一下,所以中斷說話。「在它周圍升個火。」打嗝的力道使得她必須閉上眼睛。「棒得很,」她大喊。她直接走到索恩希爾跟前,把一隻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因此聞到她身上的蘭姆酒味和骯髒味。「真他媽的棒極了!」
那個男人酩酊大醉,連眼珠子都在眼睛裡頭轉個不停。他用雷鳴般的大嗓門叫嚷,好像索恩希爾一家人遠在半哩外似的:「夥伴,看看那些沒用的野蠻人。」然後發出充滿蘭姆酒味的一陣大笑。接著他態度轉趨認真,屈膝盯著威利看。「他們特別喜歡像你孩子這種美味可口的食物。」他俯身用硬梆梆的手指捏著威利圓胖的臉頰,把威利弄得大哭,還在打嗝的女人便把那男人拖開。
他們將一點醃豬肉插到木棍上用火烤,並且用一片片樹皮當作盤子來盛裝。沒有小杯子,他們就直接從壺嘴喝那女人帶給他們的茶。麵包在他們手上碎開,但是他們把麵包屑從地上撿起來吃掉,一邊嚼一邊覺得泥粒在他們的齒間嘎吱作響。
索恩希爾家最晚吃飽的人,是咂咂作聲吸著莎莉母奶的小嬰兒。
時值黃昏,他們坐在小屋外的地上,往下看著這個初來乍到的地方。從山坡這裡往下看,流放地向平原擴展,是個新開發的小地方。其中有一些充滿車輪痕跡的街道,兩邊的溪流都流進海濱,但是在更遠之外,像動物奔跑足跡般的便道將建築物連接起來,石頭和樹木間的扭結,就像樹木本身一樣。往下靠海邊的是碼頭及沿著海岸用磚塊和石頭砌成的一些大型建築。但是離海邊較遠的地方,建築物零星分散成一間間用樹皮或塗料搭成的小屋,與其說是屋子,不如說是將泥巴和木棍黏在一,用木柴籬笆圍住的簡陋場地。豬隻在河流旁邊的灰泥巴裡打滾;一個只用一塊破布遮住腰身的赤裸小孩,站著看一群小狗抓咬帶著一群小雞的母雞;一個男人挖掘歪斜籬笆後面的一塊地。
每件東西看起來都奇怪地互不相干,這裡的地被分割成幾個方塊,散置在這片地廣物稀的土地上,就像英國領土的碎片。
更遠之外是綿延幾哩的粗獷森林。這片森林的灰色比綠色多,四面八方圍繞著山脈和山谷,像布料紋路般一致,低窪地區之間則是水塘。
索恩希爾以前從未到過其他地方,他曾經想像全世界就跟倫敦一樣,相差只是幾隻鸚鵡和幾棵棕櫚樹而已。空氣、水、泥土和岩石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這個地方和他以前所看過的地方完全不同。
在他過去的歲月裡,這個海灣早就存在,隨著地形發展出它的外觀。他曾經在倫敦的黑暗和塵土之中,做牛做馬地低頭工作,在那同時,眼前這棵自行更替葉片的樹木正悄悄呼吸,悄悄生長。一季季的太陽和高溫,一季季的風和雨,都是自然更迭,他完全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早在他來此之前,這個地方就一直存在。在他離開以後,這個地方會繼續颯颯作響、繼續呼吸,並且堅持本我,而土地會隨著自己本來的生命軌跡,繼續推擠。
索恩希爾往下可以看到「亞歷山大號」。隨著令人作嘔的搖晃,他記得那張吊床、他頭頂上橫樑的結,以及不論他睡醒或沉睡時都張著看他的一隻眼睛。
夜復一夜躺在那裡,他一直想著莎莉,直到對她的回憶變得了無新意為止。但是現在她的臀部緊貼著他的臀部,她的大腿與他的大腿靠攏。要不是為了威利,他就不必躡手躡腳,蜷縮著讓自己的體積變小,而且如果不是顧忌威利,他就能夠轉身看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在他們擁抱時感受她緊緊相依所傳來的溫暖。
在他們後面的山丘上,有隻鳥一再發出「啊,啊,啊」的哀鳴,但是除了這點以外,現在整個世界已經不再有悲傷的事情。
要離開火堆走進陰鬱的小屋,並不容易。索恩希爾拿著火把帶路先走進去,但是火把一下子就熄滅了,餘煙還將他們燻得差點窒息,所以他把火把丟到外面。他們靠著觸覺把毯子鋪好,然後把嬰兒放在上面。他寬慰地嘆了一口氣,好像腳下踩著的是羽毛鋪蓋一樣,立即就睡著了。
一開始威利不肯躺在嬰兒旁邊,雖然他已經筋疲力盡,眼淚幾乎奪眶而出,聲音高亢易怒。索恩希爾原本希望他和莎莉能夠回到火堆旁邊聊天,彌補他們生命中分離九個月的缺口。莎莉睡在毯子的最外緣,索恩希爾躺在泥地上,聽著威利漸漸靜下來睡著。
最後他發現莎莉靠著他移近。「他睡著了,小威,」她輕聲說:「可憐的小傢伙。」
除了腿靠著腿之外,他們一直到現在才觸摸彼此。他覺得有點害羞:莎莉一路上獨自航行,隱身在艙壁的另一端,誰知道她的情況怎樣?
他覺得她可能心有同感。她的肩膀貼著他的肩膀,她的腿和他的腿靠攏並排,但卻帶著羞怯,就好像是碰巧如此。他可以感受到她的溫暖,她的肉體和肌膚。他感覺到她的雙手往上移到他的胸膛,再移到他的臉,努力想要回憶她所知道的丈夫。
「感謝您,韓歇爾太太,感謝您拒絕這項特權。」她喊道,試著要低聲耳語,但卻笑著衝口說出,在那一刻,舊日的她,那個發現可憐的蘇珊娜.伍德很滑稽的厚臉皮女孩,他的莎莉,又回來了。他把一隻手放在她大腿上,身體轉向她,以便在黑暗中能仍隱約看著那張他深愛的臉。他知道她正在微笑。
「另外也要感謝索恩希爾太太,」他說。「我也得感謝她,寶貝。」她和他十指緊緊交纏,他聽到她正在哭,但是也在笑,可以說是悲喜交集。「小威,」她低語,想要說點什麼,但是他們雙手的接觸代表心中的千言萬語。
第二天早上,索恩希爾懷疑他在黑暗中遇到黑人是否只是一個夢。白天時回想起他和黑人的對話――「走開!走開!」――這種記憶讓人很難置信。
人們很容易先從熟悉的部分理解。這一小塊英國領地在森林內延伸。雪梨這地方看似陌生,但是在某些方面(而且是索恩希爾一家認為很重要的方面)它都是泰晤士河的翻版。在這裡想要生存,除了依靠它與英國連繫起來的船隻之外,別無他法。政府當局原本希望這裡最後能自行生產農作物和羊群,但是流放地仍舊不斷向英國本土求助,派遣運送民生必需品的船隻。在碼頭和這些載滿麵粉、豌豆、釘子、帽子、白蘭地和蘭姆酒的船隻之間,船夫的小船前前後後川流不息,就和泰晤士河的情況一樣。
索恩希爾一生都當船夫,在泰晤士河或是在雪梨灣的水面上做這件事,差異並不大。
他為許多主人工作,但主要是為亞歷山大.金恩先生幹活兒,在金恩先生的石砌倉庫中,有一間是索恩希爾第一天就看到的。金恩是個整潔的人,一對小耳朵伏貼著頭,下巴的酒窩深到可以丟進一隻靴子。他個性開朗,喜歡逗人高興,索恩希爾總是很感激,如果知道笑話是金恩先生開的,他的笑聲會更由衷。
金恩先生涉足多項領域,但是與索恩希爾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是一種桶子,這種桶子裝著某種在澳洲很珍貴的液體,金恩先生請人用船從馬德拉斯、加爾各答、印度群島運進來。金恩先生會在早上過來,在太陽下站在碼頭上,手上拿著清單,在貨物送往海關的途中。仔細地清點桶數;有多少牙買加甜酒,多少法國白蘭地和錫蘭琴酒。他付錢不囉嗦,而且面帶微笑,因為他知道沒有出現在清單的其他酒桶,在晚上會有人替他看守。那是索恩希爾的工作:將那些酒桶從船上暗中運到流放地附近的海灣,運到那裡,就可以避開海關緊抓不放的手。
「你會分到一杯羹,索恩希爾,」金恩帶著沉著的微笑告訴他,那是屬於成功商人的微笑。「你會發現酒比法定貨幣還好。」索恩希爾並不擔心分不到一杯羹,他說:「您可以信任我,金恩先生。」他們握了手,就這麼講定了。
金恩先生是個快樂的人,不會擔心桶箍底下小小的裂口,以及索恩希爾口袋裡的螺絲錐。他不會苦惱,因為他不知道,當他安然地躺在羽毛床鋪裡時,索恩希爾正摸黑忙碌工作。
早上和下午,被鏈在一起的囚犯在劈柴搭建的營房裡拖著腳走來走去,腳鐐還發出叮噹響聲,由於囚營裡的吊床靠得太密,囚犯們往往成為彼此夢境的一部分。
如果莎莉沒有擔任他的觀護人,索恩希爾就會被分派到其中一個囚營,或者會被指派給某個移民,這個移民因此可以一年換取一次食物和一套工作服,而且可以隨意指揮他轄下的囚犯。有些人運氣好,碰到比較好心的主人,這種主人會讓囚犯不愁吃穿,一年過後還會讓他們申請假釋許可證。但是對許多主人而言,有人免費替他做事,這種吸引力實在令人難以抗拒,所以一年刑期還沒結束,主人們就會先確定奴僕被控某項輕罪或是其他罪行,免得他們取得假釋許可證。
假釋許可證是新南威爾斯的特產,這裡一年裡有三季沒種麥穀也沒放牧,利用土地生產糧食是當務之急。政府當局瞭解,這個地方要能夠自給自足,必須靠的是自由工人,而不能靠被迫服刑的罪犯。要讓那些人有足夠的自由,可以憑自己付出的勞力得到好處,但又不致於太過自由而擺脫囚犯的身分,假釋許可證是一個方法。
來這裡一年半之後,囚犯可以申請假釋許可證,口袋裡擺一張這樣的證件,就可以和任何普通人一樣自由行動。他可以隨意選擇雇主出賣勞力,或是佔用一塊地自行工作,唯一的限制是他不能離開這個殖民地。對於本來應該上絞刑台的人而言,這項限制似乎是很輕微的束縛。
但是接下來的一年,也就是在可以申請假釋許可證之前,索恩希爾的主人就莎莉,這一點變成他們之間談笑的話題。每天晚上,他們先鋪好一層蕨類植物,然後再鋪上一塊帆布作為床墊,他會轉身面對她。「女士,我最好稱呼你索恩希爾太太,」他一邊說,一邊緊抱著她,在海上的那幾個月,他已經在想像中觸摸過她的肉體,現在他的雙手做再多次這個動作也不厭倦。「是的,索恩希爾太太,好的,索恩希爾太太,隨時聽您吩咐,索恩希爾太太。」這個地方有許多事情讓人摸不清頭緒,但是他最清楚的仍然是她肉體的觸感。莎莉靠得更近,帆布底下的蕨類植物也跟著移動,就像和他們同床共枕、一刻也靜不下來的動物。「咦,索恩希爾,」她低語:「我的好男人,讓我想想看,你要怎麼伺候我?」
這個地方靠蘭姆酒運作,就像馬匹靠燕麥運作。蘭姆酒是交易的貨幣,錢幣則是幾乎用不上。此外,蘭姆酒可撫慰人心,在這塊殖民地上的每個人,都可能因為喝了酒而像飛上月亮一樣。
只要在流放區走動,就一定會走到開放式酒棚,這種建築只不過是用幾根打進土裡的樹枝所撐起的樹皮屋頂,再加上用枝條做成的櫃檯。在這個地方隨時都可以買到蘭姆酒。有人攤開四肢躺在翻轉過來的酒桶上,頭靠在櫃檯上,早已不醒人事,手裡仍然緊緊抓住酒杯,連指關節都呈現白色;在櫃檯後面,臉龐瘦削的人面無表情地看著他們的世界。
靠著金恩先生知情而分一杯羹,以及金恩先生不知情的蘭姆酒,索恩希爾一家人很快就搬進河邊的另一間小屋。這間屋子主要是泥土蓋的,比第一間大,還有石頭壁爐和樹皮煙囪。雨通常會透過屋頂以及樹皮滲進來,但是他們互相提醒,這個房子比當年向巴特勒租來的房間好太多了,尤其是在通風方面。
他們把屋子隔成兩個房間,中間用一塊掛在椽上的帆布隔開,其中一間用來開設酒棚。她證明了自己經營客棧的能力,一邊運用微笑的魅力讓客人樂開懷,一邊倒著金恩先生的牙買加好酒,威利在外面的泥巴路上跑來跑去,小查理則是安靜地躺在搖籃裡。
每個週末,莎莉會清點所得,包括索恩希爾在水上工作的酬勞和她自己賣酒的收入,然後把錢藏在床墊下的一個盒子裡。之後他們哄孩子們在角落睡覺,索恩希爾將大酒桶裝滿酒,再為他們自己倒一大杯金恩先生的上等法國白蘭地――這種酒和總督在山上豪宅裡享用的酒一模一樣――然後在床墊上開始放鬆飲酒,把雙腳放在堆成一堆的硬幣盒上。
那些輕聲絮語的時光充滿了樂趣,他們互相傾訴未來的願景。勤奮節儉的人很快就可以達成目標,這種例子在這裡俯拾皆是。曾經是亞歷山大號指揮官的沙克林船長就是其中一例,在倫敦,沙克林不過是眾多容貌粗陋、腳趾外露的船長之一,但是他在此地落腳,現在已經是這裡穿著銀鈕釦背心、神氣活現的人物。他變豐潤了,生活優渥使得他容光煥發,鬍子刮得乾淨到透出青色的微光。
即使是重罪犯出身的人,也可以透過制度――從指派做奴僕、申請假釋許可證到取得特赦――在幾年內打拼出頭天。他看到這種人站在碼頭上,不可一世地打量別人:這些人比他好不到哪裡去,卻因為擁有自由而賺進大把鈔票,現在可以大大方方直視任何人。
索恩希爾夫婦告訴自己,不久之後,他們會存夠錢回到倫敦。只要他們確定能夠擁有永久產權,他們就可以在波若市場天鵝巷裡買一間很棒的小房子,屆時,河邊碼頭會繫著一艘和上等蘋果一樣好的擺渡船,還會有一個既優秀又強壯的學徒負責划船,他們則是悠閒地待在溫馨客廳裡的壁爐旁,舒適的扶手椅讓他們筋骨放鬆,而女僕會來添加煤炭。「我覺得,小威!」莎莉捲起身子貼著他耳語說:「我可以聞到她剛端給我們的烤馬芬鬆餅上的奶油香!」
乾脆擁有兩艘船好了,還有幾個學徒。
「其中一艘載著印度的渦紋圖案披巾,」莎莉低語:「還有,我再也不必自己洗衣服了。」
索恩希爾可以想像自己悠閒地享用一碟小鯡魚和一杯上等好酒,看起來就像有很多黃金存在銀行裡。他飯後抽著菸斗到河邊散步時,小老百姓會向他問候。「您好,索恩希爾先生!日安,索恩希爾先生!」做窮人時經常練習當富人的樣子,所以他知道以後他會成為和善的有錢人。
一點運氣,再加上大量的勤奮,有了這些,就沒有任何事可以攔阻他們。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