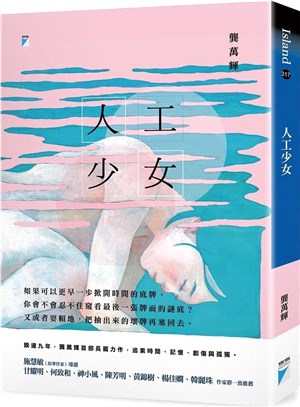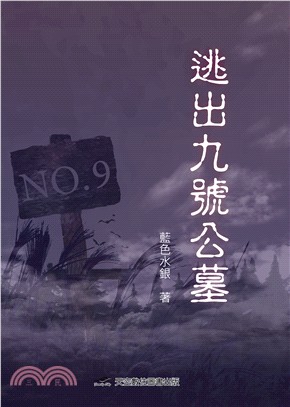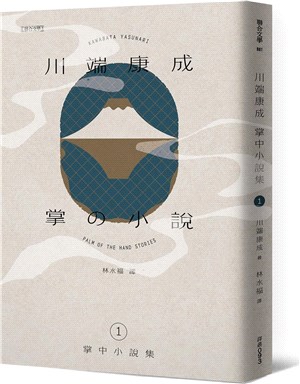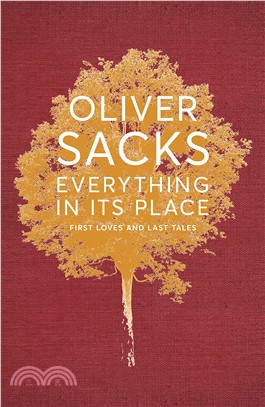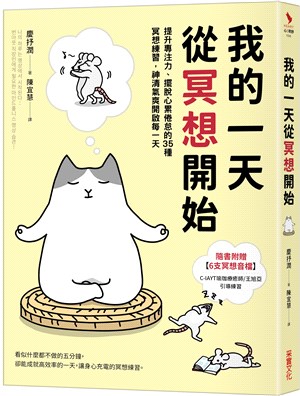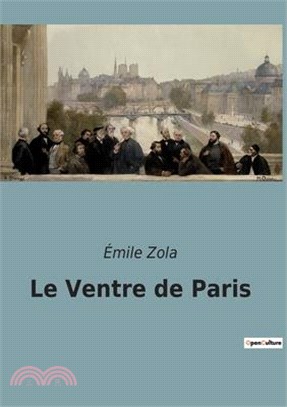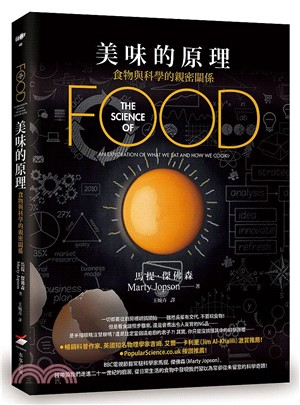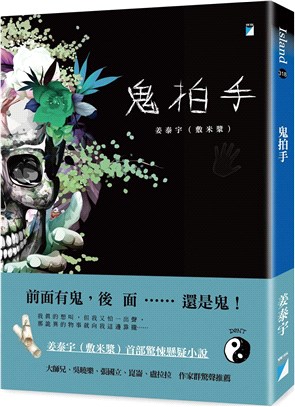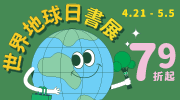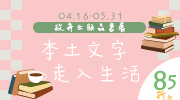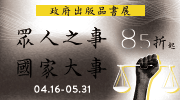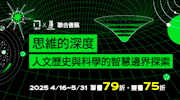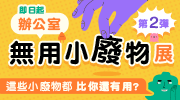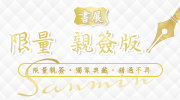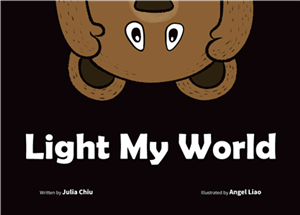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睽違九年,龔萬輝首部長篇力作,本書獲國藝會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內容簡介
睽違九年,龔萬輝首部長篇力作,
追索時間、記憶、創傷與孤獨。
▍如果可以更早一步掀開時間的底牌,
▍你會不會忍不住窺看最後一張牌面的謎底?
▍又或者耍賴地,把抽出來的壞牌再塞回去。
這是一個誕生的故事,也將是一個逃亡的故事。
誕生和毀滅,其實離得很近。
人工女兒莉莉卡誕生之時,這座城市已經因為一場瘟疫而毀滅。父親「我」帶著女兒走進昔日文明的廢墟之中,展開一場個人記憶、創傷和文明的追尋之旅。
他們打開了一扇扇房門,隨意回轉時間,每一個房間都是時間的容器,盛裝一段私人記憶。父親教女兒辨識人類遺留下來的記憶和碎片,而至失落的文明,一一指認時間的遊戲裡,分屬個人、妻子,甚至同代人的記憶與創傷。
故事中亦搓揉了瘟疫來襲的災難想像,假想繁華的熱帶城市重新變成雨林,描繪人類繭居於房內的末日意象,一個人面對孤獨的時光、蛹化的成長,以及人造的浮華與虛無。
睽違九年,龔萬輝以個人首部長篇小說探討時間、記憶與孤獨,故事中的旅程亦將成為疫病下讀者開啟個人時間、記憶的一把金鑰──如果可以選擇,你會打開哪一扇門?
// 莉莉卡,任何把時光留住的方法都是虛妄的。
一如我們走進一個個房間,卻一再地錯失。
早已經沒有人留在那裡。
房間裡也已經不是原本的樣子了。 //
★名人推薦
施慧敏(馬華作家)導讀
甘耀明、何致和、神小風、陳芳明、黃錦樹、楊佳嫻、韓麗珠 作家群一致推薦
「太沉重的傷害,只有詩意和魔幻可以救贖。龔萬輝打破理性世界中的時間,抵禦了殘酷的客觀現實;也透過虛實交界的隙縫,那些無可訴說、無可解決的創傷,不是掩藏而以另一種光怪陸離的形式得以被看見、被理解,開啟了不同以往看待傷痛的路徑。」──施慧敏(馬華作家)
本書獲國藝會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內容簡介
睽違九年,龔萬輝首部長篇力作,
追索時間、記憶、創傷與孤獨。
▍如果可以更早一步掀開時間的底牌,
▍你會不會忍不住窺看最後一張牌面的謎底?
▍又或者耍賴地,把抽出來的壞牌再塞回去。
這是一個誕生的故事,也將是一個逃亡的故事。
誕生和毀滅,其實離得很近。
人工女兒莉莉卡誕生之時,這座城市已經因為一場瘟疫而毀滅。父親「我」帶著女兒走進昔日文明的廢墟之中,展開一場個人記憶、創傷和文明的追尋之旅。
他們打開了一扇扇房門,隨意回轉時間,每一個房間都是時間的容器,盛裝一段私人記憶。父親教女兒辨識人類遺留下來的記憶和碎片,而至失落的文明,一一指認時間的遊戲裡,分屬個人、妻子,甚至同代人的記憶與創傷。
故事中亦搓揉了瘟疫來襲的災難想像,假想繁華的熱帶城市重新變成雨林,描繪人類繭居於房內的末日意象,一個人面對孤獨的時光、蛹化的成長,以及人造的浮華與虛無。
睽違九年,龔萬輝以個人首部長篇小說探討時間、記憶與孤獨,故事中的旅程亦將成為疫病下讀者開啟個人時間、記憶的一把金鑰──如果可以選擇,你會打開哪一扇門?
// 莉莉卡,任何把時光留住的方法都是虛妄的。
一如我們走進一個個房間,卻一再地錯失。
早已經沒有人留在那裡。
房間裡也已經不是原本的樣子了。 //
★名人推薦
施慧敏(馬華作家)導讀
甘耀明、何致和、神小風、陳芳明、黃錦樹、楊佳嫻、韓麗珠 作家群一致推薦
「太沉重的傷害,只有詩意和魔幻可以救贖。龔萬輝打破理性世界中的時間,抵禦了殘酷的客觀現實;也透過虛實交界的隙縫,那些無可訴說、無可解決的創傷,不是掩藏而以另一種光怪陸離的形式得以被看見、被理解,開啟了不同以往看待傷痛的路徑。」──施慧敏(馬華作家)
本書獲國藝會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龔萬輝
一九七六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曾就讀於吉隆坡美術學院和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目前從事文字和繪畫創作。曾獲台灣聯合報文學獎、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海鷗文學獎、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等。曾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訪問作家。著有小說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間》、散文集《清晨校車》和圖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輕》。
龔萬輝
一九七六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曾就讀於吉隆坡美術學院和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目前從事文字和繪畫創作。曾獲台灣聯合報文學獎、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海鷗文學獎、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等。曾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IWW)訪問作家。著有小說集《卵生年代》、《隔壁的房間》、散文集《清晨校車》和圖文集《如光如影》、《比寂寞更輕》。
序
【導讀‧節錄】虛構的真實 ◎施慧敏(馬華作家)
「這個世界或許早已一遍一遍地毀滅過了」,小說裡的人們帶著愛的毀損和各自的傷疤走在人生的旅途,關係斷裂(棄與被棄)導致的生命不可復原的剝落感和遺失感,就是貓切掉的尾巴、惠子缺了一枚的拼圖,鑿出的一方小小空洞。那個空洞,更是星野進入的假人模特兒胯下的幽深小孔,他以為的唯一出口,等到鑽身出來,早已成了被遺忘在廢墟裡的鬼魂。只有鬼魂不受時間限制,永遠存在,一直到遙遠的未來。這些怪誕的情節,某種程度而言,正是小說意義的黑洞──傷害是沒有時間性的無限後遺。所以夏美背上那一座扭曲變形的時鐘(《永恆的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彰顯了人與時間無休止的關係,它不是長度的數量概念,而是強度的心理概念。如此,記憶才會變成廢墟。
當廢墟變成遺址,後人如何考古,終有錯讀和擅自增添的想像,畢竟我們只是旁觀他人的苦痛。於此,小說裡的超驗別有深意,如果傷痛是不忍見的,或者,如果直面傷痛的時候想要擁抱傷痛,應當如何呢?
柏拉圖說過一個故事,有人看到一具屍體,好奇想探個究竟,卻又噁心,非常掙扎。因此,亞理斯多德借力使力,進一步說明模仿的好處,就是可用來迴避令人膽顫心驚的畫面。我斷章取義視為創作者的溫柔,這也是萬輝寫作的方式,太沉重的傷害,只有詩意和魔幻可以救贖。文中一旦觸及殘暴的死亡,如地道裡的馬共嬰兒成了一群野豬崽子、惠子溺水時看見的巨鰭長頸獸、慢慢融掉的父親、像蟲類一樣吐絲纏繞自己消失的直樹、蛾群從哥哥的傷口湧現出來……他就會透過一個幻視或妄想的徵狀(作者所描寫的主觀現實,即使是變形的超現實),打破理性世界中的時間,抵禦了殘酷的客觀現實;也透過這種虛實交界的隙縫,那些無可訴說、無可解決的創傷,不是掩藏,而以另一種光怪陸離的形式得以被看見、被理解,開啟了不同以往看待傷痛的路徑。
那麼,究竟作者說了什麼創傷?小說的背景是在瘟疫肆虐的時期,外在的現實與小說裡的禁制,隔離與封鎖幾乎完全切合。因此,對於人的處境、人我的關係、與世界的連結,更是反覆表達一種「玻璃」阻隔的無語狀態。
在城市漸漸廢棄之時,「我」為何要帶著人造女兒跨越空間的門檻,穿梭在時間的界線上?讀者如何在錯序的敘事中通往書寫的核心?顯然「少女」不僅僅是莉莉卡,同時也是惠子、夏美、阿櫻表姐、小艾,甚至於直樹。少女天真美好,畫裡的維納斯「如一顆晶瑩而無瑕的珍珠」、「裸露在微風之中的身體接近一種永恆」,可故事裡的少女們卻都是社會的畸零人,有隱痛,有挫傷的身體,遭受疾病、家暴、霸凌、性侵、展演、背叛,以及流失孩子。
她們要不被相機、針孔攝像頭、社會眼光、父權價值監督的凝視,要不乾脆在直播間把自己當成景觀。如傅柯所言,用不著武器,她們會在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變成自身的監視者。母親談起阿櫻表姐刻意壓低聲量、故意不答或要「我」住嘴;直樹被其他男生惡意作弄,「他遮掩下身困在那裡,我別開臉去」,顯然羞恥存在於注視之中,並且一直是恥感文化的內涵,人們服膺或無能反抗社會規訓,因此以畏縮和忽視的方式來應對其中的焦慮。
當老師指定惠子當人像模特兒,同學們圍繞她作畫,是更具體的觀看之眼,擁有權力的人最隱蔽,完全被剝奪權力的人卻有最大的能見度;這是少女們生命的癥結,最後只能把自己藏得更深,寧可與時間隔閡、斷裂,餘留空白。受創的女兒們也有一個受創的父親,阿魯老人、惠子的父親、甚至「我」都是被拒之門外的人。「女兒」與「父親」受苦的原因是相通的,都來自於人類共同的生存狀態和價值序列。
此外,傷害也源於政治和國家的暴力,直樹的伯父和老三古身為馬共的一分子,漫長年月的內耗與虛妄,在時差中成了荒謬的存在,成了被時代和歷史遺棄的人。瘟疫猖狂,小說以城市的應對措施──「受困的人們用麥克筆寫了求救的大字貼在玻璃窗上──H,E,L,P、疲倦、惶恐的眼睛、無助而徒然地揮手」做為阿櫻表姐被性侵的隱喻;為了防堵瘟疫死灰復燃,少年默使用老三古從森林帶出來的長槍,清掃無人看管的動物;捷運站測體溫的關卡,黑衣人環伺在側,何嘗沒有影射之意?「政府之眼」無所不在的「凝視」,確保了「管理」的法可以執行,但小說經由防疫制度來揭示背後的權力/暴力機制。
龐大世界的災難,說到底就是人生實難,因而坍塌成「我」心裡的廢墟。而「少女」如作者所言,是時間壓輾之後倖存下來的事物,是「我」糾結斑斑的傷害和愛的年月裡,對世界懷抱的僅存善意。即使「我」慶幸「人造女兒」沒有活在我的時代,實際上,她的存在已經證明了「我」從來沒有真正絕望過,所以那些詩意的文字才能化身為廢墟裡攀爬瘋長、蓬勃繁殖的動植物。尤其,一隻在月光下斑紋躍動、從斷橋縱身入海的馬來虎,它野性、帥氣地游到對岸去。《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說:「有老虎的故事,是一個比較好的故事」,因此,一定有更多同代人比我看懂時間背面的寓意,更領會到虛構裡的真實。
【後記】看不見的女兒,以及看不見的父親
曾經有一段漫長的時間,像電視上不斷重播的影片,我和W總是並肩而坐,在那間明亮的診所裡等待叫號。那白色的場景,硬邦邦的塑膠椅上,坐著互不認識,卻似乎都漂浮在相同情境之中的人們──給公司請了半天假,仍穿著上班套裝打開筆電的女人;化了妝而抱著名牌包包的少婦,或者一對臃胖的中年夫妻,無語而相依地打起瞌睡……似乎在那裡,每個人都等候了太長的時間,而常常掛著一種被磨蝕的,空洞、抽離的表情。我總是擅自把那幕情境想像成科幻劇某些常見的場景,那巨大廢車場一樣的地方,棄置著那些瑕疵處處的機器人,戰損的、斷手缺腳的報廢品──
那些候診的人皆是不孕者。失去延續基因能力的人類,仍苦求各種人工的技法,奢望製造出一個生命。
不知為什麼,在我身處的年代,那樣的人真是太多了。
我總是在診所裡排號而至整個上午的時間都虛擲而逝。終於輪到我的時候,卻又因為坐得太久而整個人虛虛浮浮的,任由護士引領到那個隱蔽而狹小的房間裡──呃,是的,你必須一個人待在裡面,把尚留著體溫的白濁液體灌進塑膠小罐子裡,從一扇小暗窗,傳遞到另一頭看不見全景的實驗室裡。
如今回想起來,那些小房間並排而像時鐘旅館的排列方式,而且隔音其實並不好,我會聽見護士在門外閒聊午飯要吃什麼,或者隔壁房間的另一個人扭開水喉洗手的聲音。而我獨自被留在那個房間裡面,坐在幽暗燈光底下,看著小電視機播放著消音的歐美A片(呃,為了讓你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總是在那幽暗的時刻,我會想起少年時候的自己,也曾經如此孤單地,把自己反鎖在跟弟弟共用的睡房,企圖把整個世界鎖在門外;或是一個人蹲在學校汙髒的廁所隔間裡,盯著牆上莫名其妙五爪劃過的褐色屎痕,無望而貪戀地,重複相同的動作──
那隨即就嘩啦啦跟著馬桶水一齊沖掉的,或者在衛生紙上乾涸成鼻涕化石那樣的,無效的時光。
一如房間裡那扇小暗窗的後面,科幻電影般的實驗室裡,冒著冰霧的低溫冰箱塞滿了一排一排試管,裡頭皆是陷入了永凍休眠的人類之卵。它們在某個時刻停止了細胞分裂,停留在初生萌發的一刻──那似乎是人類以執念發明出來的,將時間按停的其中一種方法。我亦忍不住想像那些看不見的細胞核之中,皆攜帶著螺旋狀的一句密語,如書頁裡夾著一張留言字條,等待有人把它揭曉。
但我始終沒有成為一個父親。
多年以前曾經在小說中任意搬弄的情節,一對年輕的夫妻陷入無限寂靜的時光,如今卻像是該死的預言。那些小說情節彷彿穿透了一層看不見的薄膜而滲透到現實中來。現實中的我,後來站在簡陋的醫院病床邊,目睹醫生用鉗型鋏從W之膣中夾出了血淋淋之肉塊,那未及成形即夭折的人類胎兒。或許從那一刻開始,我和W都覺得無法再這樣繼續了。不想再重來,那些按表操課的步驟,永遠不能理解的縮寫英文名詞,以及那月曆上畫滿的圈圈叉叉……那一段孵夢的旅程,經歷了好幾年,就這樣結束了。
這段虛無之旅程,我知道W其實承受的傷痛,遠遠比我多了太多。
但有時候我仍會獨自想像,比如在臉書上看見同輩朋友們晒娃的照片,或者無意間在跳轉電視台的時候看到的那些電視劇或電影──請回答1988、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記,或蘇菲亞.柯波拉的Somewhere……那樣的時候,我會偷偷想像,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的話,我將如何向她描述我身處的,這個紊亂又燦爛的世界?會由我教她認字,握筆寫下自己的姓名嗎?或者,我會將我所知道的一切知識和技藝,一點一點地告訴她?
但有什麼總是在這裡就斷裂了。
一如我沉默的父親,曾經在多年以前,下班的午後,仍穿著汗臭的襯衫而興致勃勃地要教我打乒乓球。我的記憶裡此刻仍可以聽見乒乓球彈跳的聲音。想起那時的父親,應該就是我現在的歲數吧。而我在那情境中還是少年。我們各據著乒乓桌的兩端,握著球拍,互相扣擊著那刁鑽的白色小球,發出一種節奏重複而清脆的聲響。但那時的我,其實並不耐煩那永無止境的基礎練習,只期盼打球的時間早一點過去。而我的父親,卻總帶著一種想掩飾起來,但似乎是當時的我所不能理解的疲憊感。
我始終沒有從父親身上繼承乒乓球的各種技巧。更多珍貴的經驗,已經隨著時光而恍恍失傳。如果我真的擁有一個女兒的話,我可以告訴她什麼而不令她覺得無聊而厭煩呢?然而我努力從少年記憶中考古挖掘出來的,似乎也只能是日本動畫片、古老的電腦遊戲,和那些褪色消失的老街之景。那些曾經任我虛擲的時間此刻皆如玻璃碎片,如河上之光閃閃爍爍。
那些時間留下的細節瑣碎而無用,不曾看懂它們在未來所指涉的意義。一如一座城市地圖縮影般的電路板,或者大學時的藝用解剖學課本,必須一一死背皮膚之下的肌束和骨頭的名字,卻無從明白生命運轉的方式。
後來我才明白,我以為我在小說裡虛構出了一個女兒,或許,其實我只是貪戀於扮演著想像的父親──可以任意切換著不同角色的,複數的父親。
我也曾經想過,若在科幻故事那樣的平行時空裡,一切皆如預想那樣,真的有一個女兒在過去的一刻哇哇誕生,那我會不會如同那些忙著生兒育女的朋友們,成日被淹沒在把屎把尿、餵奶、換尿片,長期嚴重睡眠不足的恍惚之中,而終於決定放棄繼續寫完這耗費時日而漫漫無期,且似乎也換不了多少實質回報的小說。
所以這本小說的完成,其實有點像是鋼之煉金術士的等價交換──以看不見的女兒,換取了一個情節零散的故事。
如你知道,後來瘟疫來襲。末日隱喻的現實的各種細節,因為身陷其中,而顯得太過切身和巨大,也不免就這樣滲進了小說裡──城裡之人傾巢而出搶購糧食和衛生紙,然而明亮又現代感的購物商場卻又在下一刻就空無一人。每個人在隔離時期禁鎖於房間裡,凝視著孤獨,側耳傾聽隔壁房間的聲音。以及漫長無邊的孤單時刻,面對巨大災難的各種想像和恐懼……
我在瘟疫失控的國度,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變成無比合理的事。如吐絲作繭之蟲類,我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裡寫字,一天卻只能以一千多字的進度匍匐而行。每每是日光傾斜而知當下的時刻,望出窗外,是對面的另一扇窗,相隔很近。窗子裡是一家印度人,有時他們為了通風,會把窗子打開一道縫,我就會聽見和筆下的小說情節格格不入的印度歌曲。那一陣子,不知為什麼,在浮躁而寂靜的城市頂上,天空常常出現異常絢麗的夕陽和雲彩。
我有時不禁會想像眼前這一切,因為一場疾病而毀滅的模樣。
那些原本深藏在不同房間裡暗湧的故事,會不會像草地的石塊被突然掀開一樣,那些人類的貪婪、幻夢、敗德和美好,皆如突然裸露在日光底的蟲蟻,倉皇逃散,或者隱匿在更深的夢境皺褶之中。也許到最後,像傾斜的積木而無人可以扶持,這座城市就這樣無聲而絢爛地倒下了。我這時才有些不可告人的僥倖──親愛的,妳無須目睹我身處的這個世界,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小說是虛構的,因瘟疫而不斷攀升的死亡數字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而孤獨必須是真實的。我在這段漫長的寫作過程,一直想像著我牽著一個看不見的女兒,可能已經是十二、三歲的少女模樣,會開始和我賭氣、抵抗,而我們兩人身處這座頹壞的無人之城亦如夢遊一樣。我開著一輛爛車,依著和所有人相反方向的路線,開展了我們的公路旅行……
或許我原來想寫的其實是一篇關於逃亡的故事,趕在一切消亡之前。
又或許,我只是在重複一段早已演練過的路程而已。
我記得父親過世之後,我曾經在一場夢中跟隨著他,回到他出生的鄉下。我對那處地方其實仍有著童年印象。那是一幢非常老舊的店屋,是我阿公留下的雜貨店。那裡恆常停留幽暗的光度,而且充滿著各種乾貨混雜起來的氣味。小時候,我對那雜貨店裡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我會偷偷把整隻手臂埋進米袋裡而引來大人責罵。但那時的老店已是遲暮了。我長大之後就不曾再回去那裡。而現實之中,那間雜貨店在多年後的一天,被熊熊烈火吞噬,彼時已經沒有人住在裡面了。
夢中的我坐在父親的車上,從車窗看去那童年記憶的原址,如今卻只剩下被火熏成黑色的梁柱。木造的門窗、樓梯皆只剩下炭條。原本幽暗的店鋪,因為屋頂都沒了而充滿陽光──那裡真的什麼都沒有了。父親停下了車。我跟在父親的身後,踩進那座廢墟之中。
在那荒蕪的情景裡,父親叨叨絮絮地告訴了我很多他留在這裡的往事。似乎是眼前的一切已皆然頹敗,而必須以更多的故事去充塞那空洞的現實。但我發現,在那處處破綻之中,比故事更早一步占據了全景的,卻是各種不同的荒草和蕨類。那些綠色的植物,在人類離棄的時間裡,它們無聲而堅毅地在這裡發芽、扎根,從零星的枝葉慢慢衍生出更多的枝葉,終於慢慢地把整個流失意義的空間占據成一座叢林。
我站在那失去了原有形狀的廢墟裡,不明白父親載著我回到這裡的原因。突然聽見細微而尖銳的叫聲,草叢的綠葉顫動,走出了幾隻蹣跚學步的幼貓。那些小貓各自擁有不同的毛色,眼睛都是灰色的。牠們似乎不曾見過人類,好奇而無懼,對著我和父親嗷叫,小小的肚子起伏如風箱。
父親蹲了下來,說:「看起來都還不到一個月大呢。」
那群貓崽似乎無有父母,好像本來就是從那座棄置的廢墟中孕育出來的。牠們彼此打鬧著,追撲著草叢之間閃現的小灰蝶。我在那框破敗又生氣盎然的情景之中,彷彿站在過去和未來的交界。回頭看父親,父親卻往更深處走去了。他的背影漸漸隱沒在草叢之中,像一枚枯黃的落葉,融進了一整片斑駁、深邃的綠色裡。
「這個世界或許早已一遍一遍地毀滅過了」,小說裡的人們帶著愛的毀損和各自的傷疤走在人生的旅途,關係斷裂(棄與被棄)導致的生命不可復原的剝落感和遺失感,就是貓切掉的尾巴、惠子缺了一枚的拼圖,鑿出的一方小小空洞。那個空洞,更是星野進入的假人模特兒胯下的幽深小孔,他以為的唯一出口,等到鑽身出來,早已成了被遺忘在廢墟裡的鬼魂。只有鬼魂不受時間限制,永遠存在,一直到遙遠的未來。這些怪誕的情節,某種程度而言,正是小說意義的黑洞──傷害是沒有時間性的無限後遺。所以夏美背上那一座扭曲變形的時鐘(《永恆的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彰顯了人與時間無休止的關係,它不是長度的數量概念,而是強度的心理概念。如此,記憶才會變成廢墟。
當廢墟變成遺址,後人如何考古,終有錯讀和擅自增添的想像,畢竟我們只是旁觀他人的苦痛。於此,小說裡的超驗別有深意,如果傷痛是不忍見的,或者,如果直面傷痛的時候想要擁抱傷痛,應當如何呢?
柏拉圖說過一個故事,有人看到一具屍體,好奇想探個究竟,卻又噁心,非常掙扎。因此,亞理斯多德借力使力,進一步說明模仿的好處,就是可用來迴避令人膽顫心驚的畫面。我斷章取義視為創作者的溫柔,這也是萬輝寫作的方式,太沉重的傷害,只有詩意和魔幻可以救贖。文中一旦觸及殘暴的死亡,如地道裡的馬共嬰兒成了一群野豬崽子、惠子溺水時看見的巨鰭長頸獸、慢慢融掉的父親、像蟲類一樣吐絲纏繞自己消失的直樹、蛾群從哥哥的傷口湧現出來……他就會透過一個幻視或妄想的徵狀(作者所描寫的主觀現實,即使是變形的超現實),打破理性世界中的時間,抵禦了殘酷的客觀現實;也透過這種虛實交界的隙縫,那些無可訴說、無可解決的創傷,不是掩藏,而以另一種光怪陸離的形式得以被看見、被理解,開啟了不同以往看待傷痛的路徑。
那麼,究竟作者說了什麼創傷?小說的背景是在瘟疫肆虐的時期,外在的現實與小說裡的禁制,隔離與封鎖幾乎完全切合。因此,對於人的處境、人我的關係、與世界的連結,更是反覆表達一種「玻璃」阻隔的無語狀態。
在城市漸漸廢棄之時,「我」為何要帶著人造女兒跨越空間的門檻,穿梭在時間的界線上?讀者如何在錯序的敘事中通往書寫的核心?顯然「少女」不僅僅是莉莉卡,同時也是惠子、夏美、阿櫻表姐、小艾,甚至於直樹。少女天真美好,畫裡的維納斯「如一顆晶瑩而無瑕的珍珠」、「裸露在微風之中的身體接近一種永恆」,可故事裡的少女們卻都是社會的畸零人,有隱痛,有挫傷的身體,遭受疾病、家暴、霸凌、性侵、展演、背叛,以及流失孩子。
她們要不被相機、針孔攝像頭、社會眼光、父權價值監督的凝視,要不乾脆在直播間把自己當成景觀。如傅柯所言,用不著武器,她們會在凝視的重壓之下變得卑微,變成自身的監視者。母親談起阿櫻表姐刻意壓低聲量、故意不答或要「我」住嘴;直樹被其他男生惡意作弄,「他遮掩下身困在那裡,我別開臉去」,顯然羞恥存在於注視之中,並且一直是恥感文化的內涵,人們服膺或無能反抗社會規訓,因此以畏縮和忽視的方式來應對其中的焦慮。
當老師指定惠子當人像模特兒,同學們圍繞她作畫,是更具體的觀看之眼,擁有權力的人最隱蔽,完全被剝奪權力的人卻有最大的能見度;這是少女們生命的癥結,最後只能把自己藏得更深,寧可與時間隔閡、斷裂,餘留空白。受創的女兒們也有一個受創的父親,阿魯老人、惠子的父親、甚至「我」都是被拒之門外的人。「女兒」與「父親」受苦的原因是相通的,都來自於人類共同的生存狀態和價值序列。
此外,傷害也源於政治和國家的暴力,直樹的伯父和老三古身為馬共的一分子,漫長年月的內耗與虛妄,在時差中成了荒謬的存在,成了被時代和歷史遺棄的人。瘟疫猖狂,小說以城市的應對措施──「受困的人們用麥克筆寫了求救的大字貼在玻璃窗上──H,E,L,P、疲倦、惶恐的眼睛、無助而徒然地揮手」做為阿櫻表姐被性侵的隱喻;為了防堵瘟疫死灰復燃,少年默使用老三古從森林帶出來的長槍,清掃無人看管的動物;捷運站測體溫的關卡,黑衣人環伺在側,何嘗沒有影射之意?「政府之眼」無所不在的「凝視」,確保了「管理」的法可以執行,但小說經由防疫制度來揭示背後的權力/暴力機制。
龐大世界的災難,說到底就是人生實難,因而坍塌成「我」心裡的廢墟。而「少女」如作者所言,是時間壓輾之後倖存下來的事物,是「我」糾結斑斑的傷害和愛的年月裡,對世界懷抱的僅存善意。即使「我」慶幸「人造女兒」沒有活在我的時代,實際上,她的存在已經證明了「我」從來沒有真正絕望過,所以那些詩意的文字才能化身為廢墟裡攀爬瘋長、蓬勃繁殖的動植物。尤其,一隻在月光下斑紋躍動、從斷橋縱身入海的馬來虎,它野性、帥氣地游到對岸去。《少年Pi的奇幻漂流》裡說:「有老虎的故事,是一個比較好的故事」,因此,一定有更多同代人比我看懂時間背面的寓意,更領會到虛構裡的真實。
【後記】看不見的女兒,以及看不見的父親
曾經有一段漫長的時間,像電視上不斷重播的影片,我和W總是並肩而坐,在那間明亮的診所裡等待叫號。那白色的場景,硬邦邦的塑膠椅上,坐著互不認識,卻似乎都漂浮在相同情境之中的人們──給公司請了半天假,仍穿著上班套裝打開筆電的女人;化了妝而抱著名牌包包的少婦,或者一對臃胖的中年夫妻,無語而相依地打起瞌睡……似乎在那裡,每個人都等候了太長的時間,而常常掛著一種被磨蝕的,空洞、抽離的表情。我總是擅自把那幕情境想像成科幻劇某些常見的場景,那巨大廢車場一樣的地方,棄置著那些瑕疵處處的機器人,戰損的、斷手缺腳的報廢品──
那些候診的人皆是不孕者。失去延續基因能力的人類,仍苦求各種人工的技法,奢望製造出一個生命。
不知為什麼,在我身處的年代,那樣的人真是太多了。
我總是在診所裡排號而至整個上午的時間都虛擲而逝。終於輪到我的時候,卻又因為坐得太久而整個人虛虛浮浮的,任由護士引領到那個隱蔽而狹小的房間裡──呃,是的,你必須一個人待在裡面,把尚留著體溫的白濁液體灌進塑膠小罐子裡,從一扇小暗窗,傳遞到另一頭看不見全景的實驗室裡。
如今回想起來,那些小房間並排而像時鐘旅館的排列方式,而且隔音其實並不好,我會聽見護士在門外閒聊午飯要吃什麼,或者隔壁房間的另一個人扭開水喉洗手的聲音。而我獨自被留在那個房間裡面,坐在幽暗燈光底下,看著小電視機播放著消音的歐美A片(呃,為了讓你比較容易進入狀況?)。總是在那幽暗的時刻,我會想起少年時候的自己,也曾經如此孤單地,把自己反鎖在跟弟弟共用的睡房,企圖把整個世界鎖在門外;或是一個人蹲在學校汙髒的廁所隔間裡,盯著牆上莫名其妙五爪劃過的褐色屎痕,無望而貪戀地,重複相同的動作──
那隨即就嘩啦啦跟著馬桶水一齊沖掉的,或者在衛生紙上乾涸成鼻涕化石那樣的,無效的時光。
一如房間裡那扇小暗窗的後面,科幻電影般的實驗室裡,冒著冰霧的低溫冰箱塞滿了一排一排試管,裡頭皆是陷入了永凍休眠的人類之卵。它們在某個時刻停止了細胞分裂,停留在初生萌發的一刻──那似乎是人類以執念發明出來的,將時間按停的其中一種方法。我亦忍不住想像那些看不見的細胞核之中,皆攜帶著螺旋狀的一句密語,如書頁裡夾著一張留言字條,等待有人把它揭曉。
但我始終沒有成為一個父親。
多年以前曾經在小說中任意搬弄的情節,一對年輕的夫妻陷入無限寂靜的時光,如今卻像是該死的預言。那些小說情節彷彿穿透了一層看不見的薄膜而滲透到現實中來。現實中的我,後來站在簡陋的醫院病床邊,目睹醫生用鉗型鋏從W之膣中夾出了血淋淋之肉塊,那未及成形即夭折的人類胎兒。或許從那一刻開始,我和W都覺得無法再這樣繼續了。不想再重來,那些按表操課的步驟,永遠不能理解的縮寫英文名詞,以及那月曆上畫滿的圈圈叉叉……那一段孵夢的旅程,經歷了好幾年,就這樣結束了。
這段虛無之旅程,我知道W其實承受的傷痛,遠遠比我多了太多。
但有時候我仍會獨自想像,比如在臉書上看見同輩朋友們晒娃的照片,或者無意間在跳轉電視台的時候看到的那些電視劇或電影──請回答1988、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記,或蘇菲亞.柯波拉的Somewhere……那樣的時候,我會偷偷想像,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的話,我將如何向她描述我身處的,這個紊亂又燦爛的世界?會由我教她認字,握筆寫下自己的姓名嗎?或者,我會將我所知道的一切知識和技藝,一點一點地告訴她?
但有什麼總是在這裡就斷裂了。
一如我沉默的父親,曾經在多年以前,下班的午後,仍穿著汗臭的襯衫而興致勃勃地要教我打乒乓球。我的記憶裡此刻仍可以聽見乒乓球彈跳的聲音。想起那時的父親,應該就是我現在的歲數吧。而我在那情境中還是少年。我們各據著乒乓桌的兩端,握著球拍,互相扣擊著那刁鑽的白色小球,發出一種節奏重複而清脆的聲響。但那時的我,其實並不耐煩那永無止境的基礎練習,只期盼打球的時間早一點過去。而我的父親,卻總帶著一種想掩飾起來,但似乎是當時的我所不能理解的疲憊感。
我始終沒有從父親身上繼承乒乓球的各種技巧。更多珍貴的經驗,已經隨著時光而恍恍失傳。如果我真的擁有一個女兒的話,我可以告訴她什麼而不令她覺得無聊而厭煩呢?然而我努力從少年記憶中考古挖掘出來的,似乎也只能是日本動畫片、古老的電腦遊戲,和那些褪色消失的老街之景。那些曾經任我虛擲的時間此刻皆如玻璃碎片,如河上之光閃閃爍爍。
那些時間留下的細節瑣碎而無用,不曾看懂它們在未來所指涉的意義。一如一座城市地圖縮影般的電路板,或者大學時的藝用解剖學課本,必須一一死背皮膚之下的肌束和骨頭的名字,卻無從明白生命運轉的方式。
後來我才明白,我以為我在小說裡虛構出了一個女兒,或許,其實我只是貪戀於扮演著想像的父親──可以任意切換著不同角色的,複數的父親。
我也曾經想過,若在科幻故事那樣的平行時空裡,一切皆如預想那樣,真的有一個女兒在過去的一刻哇哇誕生,那我會不會如同那些忙著生兒育女的朋友們,成日被淹沒在把屎把尿、餵奶、換尿片,長期嚴重睡眠不足的恍惚之中,而終於決定放棄繼續寫完這耗費時日而漫漫無期,且似乎也換不了多少實質回報的小說。
所以這本小說的完成,其實有點像是鋼之煉金術士的等價交換──以看不見的女兒,換取了一個情節零散的故事。
如你知道,後來瘟疫來襲。末日隱喻的現實的各種細節,因為身陷其中,而顯得太過切身和巨大,也不免就這樣滲進了小說裡──城裡之人傾巢而出搶購糧食和衛生紙,然而明亮又現代感的購物商場卻又在下一刻就空無一人。每個人在隔離時期禁鎖於房間裡,凝視著孤獨,側耳傾聽隔壁房間的聲音。以及漫長無邊的孤單時刻,面對巨大災難的各種想像和恐懼……
我在瘟疫失控的國度,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變成無比合理的事。如吐絲作繭之蟲類,我每天在固定的時間裡寫字,一天卻只能以一千多字的進度匍匐而行。每每是日光傾斜而知當下的時刻,望出窗外,是對面的另一扇窗,相隔很近。窗子裡是一家印度人,有時他們為了通風,會把窗子打開一道縫,我就會聽見和筆下的小說情節格格不入的印度歌曲。那一陣子,不知為什麼,在浮躁而寂靜的城市頂上,天空常常出現異常絢麗的夕陽和雲彩。
我有時不禁會想像眼前這一切,因為一場疾病而毀滅的模樣。
那些原本深藏在不同房間裡暗湧的故事,會不會像草地的石塊被突然掀開一樣,那些人類的貪婪、幻夢、敗德和美好,皆如突然裸露在日光底的蟲蟻,倉皇逃散,或者隱匿在更深的夢境皺褶之中。也許到最後,像傾斜的積木而無人可以扶持,這座城市就這樣無聲而絢爛地倒下了。我這時才有些不可告人的僥倖──親愛的,妳無須目睹我身處的這個世界,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小說是虛構的,因瘟疫而不斷攀升的死亡數字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而孤獨必須是真實的。我在這段漫長的寫作過程,一直想像著我牽著一個看不見的女兒,可能已經是十二、三歲的少女模樣,會開始和我賭氣、抵抗,而我們兩人身處這座頹壞的無人之城亦如夢遊一樣。我開著一輛爛車,依著和所有人相反方向的路線,開展了我們的公路旅行……
或許我原來想寫的其實是一篇關於逃亡的故事,趕在一切消亡之前。
又或許,我只是在重複一段早已演練過的路程而已。
我記得父親過世之後,我曾經在一場夢中跟隨著他,回到他出生的鄉下。我對那處地方其實仍有著童年印象。那是一幢非常老舊的店屋,是我阿公留下的雜貨店。那裡恆常停留幽暗的光度,而且充滿著各種乾貨混雜起來的氣味。小時候,我對那雜貨店裡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我會偷偷把整隻手臂埋進米袋裡而引來大人責罵。但那時的老店已是遲暮了。我長大之後就不曾再回去那裡。而現實之中,那間雜貨店在多年後的一天,被熊熊烈火吞噬,彼時已經沒有人住在裡面了。
夢中的我坐在父親的車上,從車窗看去那童年記憶的原址,如今卻只剩下被火熏成黑色的梁柱。木造的門窗、樓梯皆只剩下炭條。原本幽暗的店鋪,因為屋頂都沒了而充滿陽光──那裡真的什麼都沒有了。父親停下了車。我跟在父親的身後,踩進那座廢墟之中。
在那荒蕪的情景裡,父親叨叨絮絮地告訴了我很多他留在這裡的往事。似乎是眼前的一切已皆然頹敗,而必須以更多的故事去充塞那空洞的現實。但我發現,在那處處破綻之中,比故事更早一步占據了全景的,卻是各種不同的荒草和蕨類。那些綠色的植物,在人類離棄的時間裡,它們無聲而堅毅地在這裡發芽、扎根,從零星的枝葉慢慢衍生出更多的枝葉,終於慢慢地把整個流失意義的空間占據成一座叢林。
我站在那失去了原有形狀的廢墟裡,不明白父親載著我回到這裡的原因。突然聽見細微而尖銳的叫聲,草叢的綠葉顫動,走出了幾隻蹣跚學步的幼貓。那些小貓各自擁有不同的毛色,眼睛都是灰色的。牠們似乎不曾見過人類,好奇而無懼,對著我和父親嗷叫,小小的肚子起伏如風箱。
父親蹲了下來,說:「看起來都還不到一個月大呢。」
那群貓崽似乎無有父母,好像本來就是從那座棄置的廢墟中孕育出來的。牠們彼此打鬧著,追撲著草叢之間閃現的小灰蝶。我在那框破敗又生氣盎然的情景之中,彷彿站在過去和未來的交界。回頭看父親,父親卻往更深處走去了。他的背影漸漸隱沒在草叢之中,像一枚枯黃的落葉,融進了一整片斑駁、深邃的綠色裡。
目次
目錄
【出版緣起】「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的第二部作品 ◎林曼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序章˙一趟旅程
第一個房間˙黑色的房間
第二個房間˙換取的孩子
第三個房間˙貓語術
第四個房間˙阿櫻表姐
第五個房間˙模擬城市的暫停時間
第六個房間˙浴缸裡的維納斯
第七個房間˙夏美的時鐘
第八個房間˙地下突擊隊
第九個房間˙諸神黃昏
第十個房間˙暗房的光
第十一個房間˙寶可夢老人
第十二個房間˙房間的雨林
【後記】看不見的女兒,以及看不見的父親
【導讀】虛構的真實 ◎施慧敏(馬華作家)
【出版緣起】「馬華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的第二部作品 ◎林曼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序章˙一趟旅程
第一個房間˙黑色的房間
第二個房間˙換取的孩子
第三個房間˙貓語術
第四個房間˙阿櫻表姐
第五個房間˙模擬城市的暫停時間
第六個房間˙浴缸裡的維納斯
第七個房間˙夏美的時鐘
第八個房間˙地下突擊隊
第九個房間˙諸神黃昏
第十個房間˙暗房的光
第十一個房間˙寶可夢老人
第十二個房間˙房間的雨林
【後記】看不見的女兒,以及看不見的父親
【導讀】虛構的真實 ◎施慧敏(馬華作家)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序章˙一趟旅程(節錄)
我記得,那天早晨特別明亮。
我從一場夢中醒來,恍恍忘記了所有細節。睜開眼,床邊的窗子已經亮了,還可以聽見鳥類在遠處的叫聲。今天的早晨,似乎和昨天沒有什麼不同。街上開始有車子駛過的聲音,陽光從窗簾透了進來,伸出手,可以把手影倒映在牆上。我從枕頭底下摸出我的電子雞,那其實只是一個蛋圓形的塑膠電子玩具,小小的黑白螢幕裡,有一隻像素粗糙的小雞伏著睡覺。我必須等牠醒來,然後再餵牠一點吃的。
房間的門這時喀噠一聲被打開了,父親從門口探進頭來,我趕緊把手縮回被子,閉著眼睛假裝還在睡,父親似乎看了一會,又輕輕把門關上了。
鬧鐘還沒響,但父親似乎很早就起床了。我可以從門底縫間,看見父親在客廳裡走來走去的影子。然後窄窄的影子停留在我的房間門口,站了許久。父親終於又打開了房門,走到我的床邊,伸手把我搖醒。
「快起床。」父親說:「不然就趕不及了。」
明明未到上學的時間,但父親卻說,今天不必去學校了。快點換衣服,跟爸爸出門。我心底歡呼,只要可以不去學校都算是好事。隨隨便便刷了牙,換著衣褲,聽見父親掏出鑰匙打開了大門。我急急忙忙跟了出去,套了拖鞋才想起什麼,說等一下,又跑回房間,把枕頭下的電子雞收進了褲袋。匆匆瞄了一眼,小雞仍然躺在那蛋圓形的容器裡面,不曾被任何躁動驚醒。
父親的車子已經老舊了,那是一台白色的Nissan Sunny,扭開了引擎,像是喚醒沉睡的巨獸,發出巨大咆哮。車裡的收音機正播放一首流行歌曲,冷氣口呼呼作響,掩蓋了音樂的細節,讓一切聽起來都含含糊糊的。車子行駛著,我坐在父親旁邊,看著風景從眼前趨近而逝。望後鏡上掛著一串佛珠,和一個戴著竹蜻蜓的小叮噹。小叮噹是我掛上去的,原本是麥當勞兒童餐的贈品,我隨手掛在車上,竟然就一直掛著了。那玩偶的一身藍色已經被陽光晒到泛白。隨著車子行進,佛珠和小叮噹一路晃蕩。望後鏡裡有一雙父親的眼睛,直直望著前方。細細的皺紋纏繞著父親的眼睛,像是網住了一隻魚。父親一貫靜默不語。
車子開進了加油站,父親搖下玻璃窗,向加油的工人說了什麼,那個印度工人熟練地把油缸的蓋子打開,把油嘴伸進車子裡。父親下車到櫃檯還錢,讓我在車裡等他。趁父親不在,我把電子雞從口袋掏出來。小雞已經醒了,在螢幕裡來回踱步。我必須一直守著牠,如果放著不理,小雞會拉出一堆大便。如果忘記餵食,小雞就會靜默而孤獨地死去。那死亡是真實的。死亡是不可推翻的。螢幕上會出現一個小小的十字架,代表小雞已死,而你不管怎樣都無法把牠喚醒了。
許久父親才從加油站的販賣店裡出來。他捧著一大堆東西,把鼓鼓的塑膠袋丟到後車廂。我看了看,袋子裡有三支大瓶裝的礦泉水,一整條吐司,以及雜七雜八的罐頭、餅乾、啤酒和快熟麵,還有父親開長途車的時候,用來提神的喉糖。我曾經趁父親不注意,偷吃過一顆,被那極辣的薄荷味嗆出眼淚。
我看著這些東西,彷彿要去野餐或露營那樣,心想我們應該是要去很遠的地方。父親調整了一下望後鏡,踩了油門,車子噴出一陣暢快的黑煙,慢慢離開了我們的城鎮,開上了縣道。
當時的我恍恍未知,那其實是一次逃亡的旅程。
許多年後,親愛的莉莉卡,我總是一再想起,當時和父親一起在車裡,不斷在曲曲折折的公路上前進的那些光景。窗外的風景往後流逝,漸漸地看不見那些店屋和電線桿。車子背離了繁華的市鎮,穿過橡膠林和油棕園,路邊不時閃現一兩座馬來人的高腳屋,運氣好的話,可以看見那些放養的黃牛或山羊,在路邊低頭吃草。車子經過牠們的時候,牠們會抬起頭來看著我們,眼睛清澈而明亮,彷彿我們闖入了牠們浮泡的夢境。我總是趴在窗鏡前,想再看清楚一點,車子卻已經把風景拋遠了。
有時車廂冷氣不冷,父親會把車窗絞下,讓路上的風灌進來,把我和父親的頭髮都吹亂。有時父親也會停下,拿出一台富士牌的傻瓜相機,對著眼前的空景按下快門。我不知道父親到底在拍些什麼,但拍照的父親讓我有一種其實我們正在假日旅途中的錯覺。
車子在路上開了許久,父親把車子停在路邊,讓老舊的引擎冷卻一下。公路旁有一座巨大的電訊塔,紅白色的鐵條交錯,高高地伸向天空。天空飄著幾朵白色的雲,我必須用手遮住耀眼的陽光,才能看見塔的頂尖。父親下了車,走到電訊塔後面的草叢裡。我跟在他的身後,看著父親站立的背影。父親背對著整條公路,不顧其他經過的車子,扯開褲帶,拉下了拉鍊,就往草叢深處小便。
我在父親身後,隱約以為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了父親伸出雞雞的影子。但其實我只看見父親胯間的水滴映著光,伴隨綿長的滋滋通通的撒尿聲。我覺得非常丟臉,總覺得路上疾駛而過的人們都在看著我們。在豔陽底下,父親仍然站在那裡似乎永遠都尿不完……
莉莉卡,請容我不斷向妳複述這些瑣碎的細節。
我們必須把這些細節都串起來,尋找回當年的那條路線,在摺痕破損的地圖上指認出我曾經到過的地方。莉莉卡,我必須帶著妳,依著這條無人知曉的逃亡路徑,離開這座被瘟疫漸漸侵蝕的城市。這座城市已經再不需要神的存在。然而我卻一直想不起來那趟旅程,我和父親最後抵達的目的之地。我只記得那些路上不斷重複的油棕園、椰子樹、馬來高腳屋,以及路經石子小路,跨過了那些不同名字的河溪。
我們離開了一座城鎮,又進入一座城鎮,那之間的路途幾乎都一模一樣,以致我不斷懷疑我們其實只是一直在鬼打牆,困鎖在一段重複回轉的片段,怎麼都走不到下一個場景。
或許那更像是困在一個行走的鐘裡,以為過了十二就是十三,但不知怎麼地又回到了一的起點。
像父親曾經告訴過我的,我們的家族總是莫名其妙捲進時代的那些大遷徙之中。他小時候跟隨整村人遺棄了原本的老家,為了隔絕馬共而被英殖民政府強行集中在擁擠不已的「新村」裡。以為只是短暫生活,過幾天就可以回來住處,或許是大家為了搬遷忙成一團而終究忘記了,竟沒有人想過要把一隻名叫「多多」的老狗一起帶走。而幾個月後,終於領到英政府發下來的通行證,家人回到那無人的屋子看看,原有的木板隙縫竟鑽出了攀緣的植物。推開了門,看見門口一堆白骨和未及腐化的褐色毛髮,而木板門上皆是一道一道狗爪劃出來的凌亂交錯的爪痕……
又或者更早,父親尚未出生的年代,我的祖父其實只是被同鄉人哄騙,從遙遠的北方隻身渡海而來,抵達這座其實沒有傳說中那麼美好的南洋半島,而無法預想自己終將一生困頓於此,再也回不去出生之故土。
有時候,父親會在行進的旅程裡,或者我們停下來休息的那些破爛小旅館裡,告訴我這些失去了細節,而裡頭的人物皆面目模糊的關於逃亡和遷徙的故事。但總有太多破碎不已的情節,看不見一個時間的全貌。我們似乎只是站在那故事尚未完結的省略號上,從一個一個間隔的小圓點,跳到下一個圓點……
像那些我們短暫停留過的房間。那些房間都像是在時間河流突起的石頭。
我總會想起這些。九歲那時候,跟隨著父親身影的流浪時光。我們似乎總是在旅行。父親開著車,在半島南端不同的城鎮之間遊蕩,住進不同的小旅館裡。那之中有一種稍稍脫離了現實的虛浮感(或許是因為大家此刻都在學校裡而只有我不必去上課),以及像是偷來的時間,那麼不可告人。但不知為什麼,只是小學生的我,卻都是坐在父親旁邊的助手座。那輛車子就像是父親和我的容器。車上總是兩個人,非常奇怪,那是母親恆常缺席的印象。
這麼多年過去,我已經想不起我和父親到底去過了什麼地方,那些地名、路名皆不復記憶,但卻依稀記得那些我們住過的旅館房間。
那一律是小鎮上的老舊旅館,並不是現今那種燈光明亮而陳設現代感的星級旅店,或近年流行起來的那種個性獨特的民宿。那比較像是時差的結界,一切的事物皆已不合時宜。那種廉價的小旅館,都有一種陳設相仿的格局和氣味。灰濛濛的玻璃百葉窗、牆頭上幾何圖案的通氣孔、塞子用破布纏著的熱水壺,以及起了毛球、摸起來粗粗糙糙的涼被……而守住櫃檯的皆是穿著背心的禿頭男子,或者打瞌睡的老阿姨。往後我在王家衛的電影裡,看見梁朝偉和張曼玉,窒在小房間裡暗渡彼此情慾,突然覺得好熟悉,而憂傷地想起我也曾經置身在那樣光度幽暗的房間裡。
我記得和電影一樣,總要穿過一道小門,走上鋪滿了小方塊磁磚的樓梯,到二樓才會看見房間。而樓梯口總會有陌生的女人,不知從哪裡鑽身出來,要向父親招徠。她們皆是頹萎老去的女人,用厚重的眼影和口紅仍掩蓋不住衰老的痕跡,只有紋眉留下兩條灰灰藍藍的色彩,不曾因為歲月而褪色,如今卻顯得非常突兀。然而不知為什麼,她們現身而對父親注目許久,但只要一看到父親身後的我,她們就會黯然退卻,退到剛才她們原本隱身的隙縫之中。
每一次,父親在進入旅館的房間之前,一定都會先在門上敲兩下,才打開門。這樣恍若儀式的動作,彷彿是為了提前告知原本在房間裡的什麼,我們擅闖於此的歉意。我長大之後,不知不覺延續了這個習慣。有一次我帶著年輕的妻,為了慶祝某年的情人節而特地去訂了一晚的昂貴飯店,當我們微醺踉蹌,說著笑話來到預定的房間門口,少女妻看著我預先敲門而一臉不解:「你不覺得這樣很怪嗎?」
但那些房間本來就是借來的,時間的容器,莉莉卡。
(全文未完)
序章˙一趟旅程(節錄)
我記得,那天早晨特別明亮。
我從一場夢中醒來,恍恍忘記了所有細節。睜開眼,床邊的窗子已經亮了,還可以聽見鳥類在遠處的叫聲。今天的早晨,似乎和昨天沒有什麼不同。街上開始有車子駛過的聲音,陽光從窗簾透了進來,伸出手,可以把手影倒映在牆上。我從枕頭底下摸出我的電子雞,那其實只是一個蛋圓形的塑膠電子玩具,小小的黑白螢幕裡,有一隻像素粗糙的小雞伏著睡覺。我必須等牠醒來,然後再餵牠一點吃的。
房間的門這時喀噠一聲被打開了,父親從門口探進頭來,我趕緊把手縮回被子,閉著眼睛假裝還在睡,父親似乎看了一會,又輕輕把門關上了。
鬧鐘還沒響,但父親似乎很早就起床了。我可以從門底縫間,看見父親在客廳裡走來走去的影子。然後窄窄的影子停留在我的房間門口,站了許久。父親終於又打開了房門,走到我的床邊,伸手把我搖醒。
「快起床。」父親說:「不然就趕不及了。」
明明未到上學的時間,但父親卻說,今天不必去學校了。快點換衣服,跟爸爸出門。我心底歡呼,只要可以不去學校都算是好事。隨隨便便刷了牙,換著衣褲,聽見父親掏出鑰匙打開了大門。我急急忙忙跟了出去,套了拖鞋才想起什麼,說等一下,又跑回房間,把枕頭下的電子雞收進了褲袋。匆匆瞄了一眼,小雞仍然躺在那蛋圓形的容器裡面,不曾被任何躁動驚醒。
父親的車子已經老舊了,那是一台白色的Nissan Sunny,扭開了引擎,像是喚醒沉睡的巨獸,發出巨大咆哮。車裡的收音機正播放一首流行歌曲,冷氣口呼呼作響,掩蓋了音樂的細節,讓一切聽起來都含含糊糊的。車子行駛著,我坐在父親旁邊,看著風景從眼前趨近而逝。望後鏡上掛著一串佛珠,和一個戴著竹蜻蜓的小叮噹。小叮噹是我掛上去的,原本是麥當勞兒童餐的贈品,我隨手掛在車上,竟然就一直掛著了。那玩偶的一身藍色已經被陽光晒到泛白。隨著車子行進,佛珠和小叮噹一路晃蕩。望後鏡裡有一雙父親的眼睛,直直望著前方。細細的皺紋纏繞著父親的眼睛,像是網住了一隻魚。父親一貫靜默不語。
車子開進了加油站,父親搖下玻璃窗,向加油的工人說了什麼,那個印度工人熟練地把油缸的蓋子打開,把油嘴伸進車子裡。父親下車到櫃檯還錢,讓我在車裡等他。趁父親不在,我把電子雞從口袋掏出來。小雞已經醒了,在螢幕裡來回踱步。我必須一直守著牠,如果放著不理,小雞會拉出一堆大便。如果忘記餵食,小雞就會靜默而孤獨地死去。那死亡是真實的。死亡是不可推翻的。螢幕上會出現一個小小的十字架,代表小雞已死,而你不管怎樣都無法把牠喚醒了。
許久父親才從加油站的販賣店裡出來。他捧著一大堆東西,把鼓鼓的塑膠袋丟到後車廂。我看了看,袋子裡有三支大瓶裝的礦泉水,一整條吐司,以及雜七雜八的罐頭、餅乾、啤酒和快熟麵,還有父親開長途車的時候,用來提神的喉糖。我曾經趁父親不注意,偷吃過一顆,被那極辣的薄荷味嗆出眼淚。
我看著這些東西,彷彿要去野餐或露營那樣,心想我們應該是要去很遠的地方。父親調整了一下望後鏡,踩了油門,車子噴出一陣暢快的黑煙,慢慢離開了我們的城鎮,開上了縣道。
當時的我恍恍未知,那其實是一次逃亡的旅程。
許多年後,親愛的莉莉卡,我總是一再想起,當時和父親一起在車裡,不斷在曲曲折折的公路上前進的那些光景。窗外的風景往後流逝,漸漸地看不見那些店屋和電線桿。車子背離了繁華的市鎮,穿過橡膠林和油棕園,路邊不時閃現一兩座馬來人的高腳屋,運氣好的話,可以看見那些放養的黃牛或山羊,在路邊低頭吃草。車子經過牠們的時候,牠們會抬起頭來看著我們,眼睛清澈而明亮,彷彿我們闖入了牠們浮泡的夢境。我總是趴在窗鏡前,想再看清楚一點,車子卻已經把風景拋遠了。
有時車廂冷氣不冷,父親會把車窗絞下,讓路上的風灌進來,把我和父親的頭髮都吹亂。有時父親也會停下,拿出一台富士牌的傻瓜相機,對著眼前的空景按下快門。我不知道父親到底在拍些什麼,但拍照的父親讓我有一種其實我們正在假日旅途中的錯覺。
車子在路上開了許久,父親把車子停在路邊,讓老舊的引擎冷卻一下。公路旁有一座巨大的電訊塔,紅白色的鐵條交錯,高高地伸向天空。天空飄著幾朵白色的雲,我必須用手遮住耀眼的陽光,才能看見塔的頂尖。父親下了車,走到電訊塔後面的草叢裡。我跟在他的身後,看著父親站立的背影。父親背對著整條公路,不顧其他經過的車子,扯開褲帶,拉下了拉鍊,就往草叢深處小便。
我在父親身後,隱約以為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了父親伸出雞雞的影子。但其實我只看見父親胯間的水滴映著光,伴隨綿長的滋滋通通的撒尿聲。我覺得非常丟臉,總覺得路上疾駛而過的人們都在看著我們。在豔陽底下,父親仍然站在那裡似乎永遠都尿不完……
莉莉卡,請容我不斷向妳複述這些瑣碎的細節。
我們必須把這些細節都串起來,尋找回當年的那條路線,在摺痕破損的地圖上指認出我曾經到過的地方。莉莉卡,我必須帶著妳,依著這條無人知曉的逃亡路徑,離開這座被瘟疫漸漸侵蝕的城市。這座城市已經再不需要神的存在。然而我卻一直想不起來那趟旅程,我和父親最後抵達的目的之地。我只記得那些路上不斷重複的油棕園、椰子樹、馬來高腳屋,以及路經石子小路,跨過了那些不同名字的河溪。
我們離開了一座城鎮,又進入一座城鎮,那之間的路途幾乎都一模一樣,以致我不斷懷疑我們其實只是一直在鬼打牆,困鎖在一段重複回轉的片段,怎麼都走不到下一個場景。
或許那更像是困在一個行走的鐘裡,以為過了十二就是十三,但不知怎麼地又回到了一的起點。
像父親曾經告訴過我的,我們的家族總是莫名其妙捲進時代的那些大遷徙之中。他小時候跟隨整村人遺棄了原本的老家,為了隔絕馬共而被英殖民政府強行集中在擁擠不已的「新村」裡。以為只是短暫生活,過幾天就可以回來住處,或許是大家為了搬遷忙成一團而終究忘記了,竟沒有人想過要把一隻名叫「多多」的老狗一起帶走。而幾個月後,終於領到英政府發下來的通行證,家人回到那無人的屋子看看,原有的木板隙縫竟鑽出了攀緣的植物。推開了門,看見門口一堆白骨和未及腐化的褐色毛髮,而木板門上皆是一道一道狗爪劃出來的凌亂交錯的爪痕……
又或者更早,父親尚未出生的年代,我的祖父其實只是被同鄉人哄騙,從遙遠的北方隻身渡海而來,抵達這座其實沒有傳說中那麼美好的南洋半島,而無法預想自己終將一生困頓於此,再也回不去出生之故土。
有時候,父親會在行進的旅程裡,或者我們停下來休息的那些破爛小旅館裡,告訴我這些失去了細節,而裡頭的人物皆面目模糊的關於逃亡和遷徙的故事。但總有太多破碎不已的情節,看不見一個時間的全貌。我們似乎只是站在那故事尚未完結的省略號上,從一個一個間隔的小圓點,跳到下一個圓點……
像那些我們短暫停留過的房間。那些房間都像是在時間河流突起的石頭。
我總會想起這些。九歲那時候,跟隨著父親身影的流浪時光。我們似乎總是在旅行。父親開著車,在半島南端不同的城鎮之間遊蕩,住進不同的小旅館裡。那之中有一種稍稍脫離了現實的虛浮感(或許是因為大家此刻都在學校裡而只有我不必去上課),以及像是偷來的時間,那麼不可告人。但不知為什麼,只是小學生的我,卻都是坐在父親旁邊的助手座。那輛車子就像是父親和我的容器。車上總是兩個人,非常奇怪,那是母親恆常缺席的印象。
這麼多年過去,我已經想不起我和父親到底去過了什麼地方,那些地名、路名皆不復記憶,但卻依稀記得那些我們住過的旅館房間。
那一律是小鎮上的老舊旅館,並不是現今那種燈光明亮而陳設現代感的星級旅店,或近年流行起來的那種個性獨特的民宿。那比較像是時差的結界,一切的事物皆已不合時宜。那種廉價的小旅館,都有一種陳設相仿的格局和氣味。灰濛濛的玻璃百葉窗、牆頭上幾何圖案的通氣孔、塞子用破布纏著的熱水壺,以及起了毛球、摸起來粗粗糙糙的涼被……而守住櫃檯的皆是穿著背心的禿頭男子,或者打瞌睡的老阿姨。往後我在王家衛的電影裡,看見梁朝偉和張曼玉,窒在小房間裡暗渡彼此情慾,突然覺得好熟悉,而憂傷地想起我也曾經置身在那樣光度幽暗的房間裡。
我記得和電影一樣,總要穿過一道小門,走上鋪滿了小方塊磁磚的樓梯,到二樓才會看見房間。而樓梯口總會有陌生的女人,不知從哪裡鑽身出來,要向父親招徠。她們皆是頹萎老去的女人,用厚重的眼影和口紅仍掩蓋不住衰老的痕跡,只有紋眉留下兩條灰灰藍藍的色彩,不曾因為歲月而褪色,如今卻顯得非常突兀。然而不知為什麼,她們現身而對父親注目許久,但只要一看到父親身後的我,她們就會黯然退卻,退到剛才她們原本隱身的隙縫之中。
每一次,父親在進入旅館的房間之前,一定都會先在門上敲兩下,才打開門。這樣恍若儀式的動作,彷彿是為了提前告知原本在房間裡的什麼,我們擅闖於此的歉意。我長大之後,不知不覺延續了這個習慣。有一次我帶著年輕的妻,為了慶祝某年的情人節而特地去訂了一晚的昂貴飯店,當我們微醺踉蹌,說著笑話來到預定的房間門口,少女妻看著我預先敲門而一臉不解:「你不覺得這樣很怪嗎?」
但那些房間本來就是借來的,時間的容器,莉莉卡。
(全文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