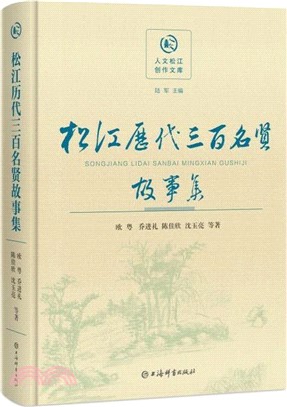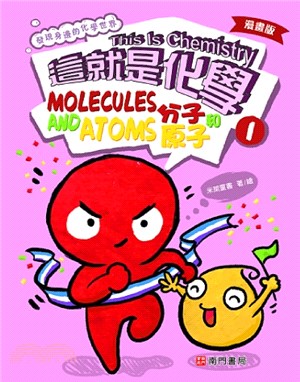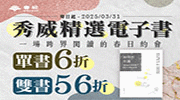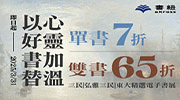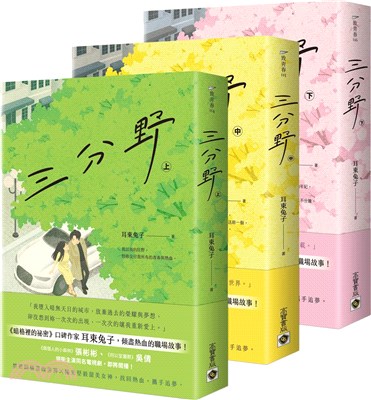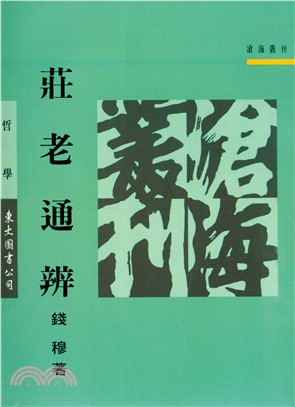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降,香港除了有葉靈鳳、曹聚仁、劉以鬯等既參加過新文學運動,同時對新文學文獻也大感興趣的老一輩作家,又湧現出一批從事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新文學愛好者。他們中的佼佼者有方寬烈、杜漸、黃俊東、盧瑋鑾、許定銘等位,無言先生也在他們之中,而且是他們之中最年長的。
陳無言一九七七年開始在《星島日報.星辰》、《明報》等刊物發表文章,一生所寫文章未曾結集,《文苑拾遺錄》為作者生前所擬文集書名,本書收錄了陳無言書話文章及散文。
陳無言一九七七年開始在《星島日報.星辰》、《明報》等刊物發表文章,一生所寫文章未曾結集,《文苑拾遺錄》為作者生前所擬文集書名,本書收錄了陳無言書話文章及散文。
作者簡介
陳無言
本名陳莊生,福建漳州龍溪人,筆名陳野火、書丁。福建漳州龍溪人,生於一九一三年四月,歿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一九七七年開始在《星島日報.星辰》、《明報》等刊物發表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傳記與書話文章。生前喜歡收集舊書與古錢幣,一生所寫文章未曾結集。
本名陳莊生,福建漳州龍溪人,筆名陳野火、書丁。福建漳州龍溪人,生於一九一三年四月,歿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一九七七年開始在《星島日報.星辰》、《明報》等刊物發表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家傳記與書話文章。生前喜歡收集舊書與古錢幣,一生所寫文章未曾結集。
序
我所知道的陳無言先生
陳子善
在我記憶中,最早知道陳無言先生的大名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其時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香港昭明出版社推出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本,之後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重印),翌年,香港友聯出版社推出劉紹銘先生主持翻譯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兩部文學史著作先後進入內地,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帶來不小的震動,至少我個人讀過之後產生了重新審視已有的內地現代文學史著作的想法。如果我沒有記錯,我是先讀到《中國新文學史》,再讀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的〈跋〉中感謝了無言先生:
在本書撰寫中,陳無言先生不惜時間、金錢,蒐羅賜贈資料……均在此永志不忘。
雖然只有短短二十餘字,但無言先生在司馬長風一長串感謝名單中榮列首位,可見他對司馬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幫助很大。這是我首次知道無言先生的大名,而且對無言先生產生了好奇心。
不久,我因研究郁達夫,有機會與郁達夫的友人,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鄭子瑜先生取得聯繫。一九八四年,專攻中國修辭學的子瑜先生應邀訪問內地修辭學研究的重鎮――上海復旦大學,約我見面,交談甚歡。正是這次談話,不但促成了周作人的《知堂雜詩抄》在內地出版,也促成了我結識無言先生。我向子瑜先生打聽陳無言其人,他回答道:太巧了,我們熟識。你研究新文學,他也對新文學入迷,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很熟悉,我介紹你們認識,對你一定有幫助。這真令我喜出望外。
後來,我才知道,子瑜先生和無言先生都祖籍福建漳州,既是同鄉,也是中學同學,友情甚篤。於是,經過子瑜先生牽線搭橋,我與無言先生聯繫上了,魚雁不斷。無言先生長我三十五歲,是我的師長輩,但他十分客氣,一直稱我這個小輩「子善先生」,無論是寫信稱呼還是寄贈書刊題字,都是如此,始終不變。
可以想見,我們通信的中心話題就是新文學,交流資訊,討論問題,互通有無。當時我需要港臺出版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刊,他都及時尋覓寄贈,而他需要一些三四十年代內地出版的新文學書籍,我也在上海為他搜羅寄去。當然,他提供給我的大大超過我提供給他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和《赤地之戀》等張愛玲著作的香港初版本是他寄贈的,梁實秋在臺灣出版的許多著譯版本也是他寄贈的,我成為《香港文學》作者之前的每期《香港文學》月刊仍是他寄贈的。特別是極為少見,可能是孤本的葉靈鳳散文集《忘憂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香港西南圖書印刷公司初版),他也並不秘不示人,而是全書影印,裝訂成冊寄贈,我後來將《忘憂草》全書編入《葉靈鳳隨筆合集》第一卷,書名就定為《忘憂草》(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文匯出版社初版),從而使此書終於與內地讀者見面。可惜無言先生已經去世,未及親見。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首次赴港參加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那天下午,也是無言先生好友的方寬烈先生親自到深圳接我,一併經羅湖過關渡海,直奔港島北角敦煌酒樓,無言先生早已等候在那裡,為我接風洗塵。那是一個頗為愉快的晚上,兩位香港文史前輩與我這樣一個上海小朋友盡興暢敘。研討會結束後,香港文壇友人又為我舉行一次難得的午宴,高伯雨、方寬烈、黃俊東、盧瑋鑾、蘇賡哲、楊玉峰等位都參加了,無言先生自然也在座。飯後,無言先生不顧行走不便,執意與寬烈先生一起帶我去神州、實用等舊書店訪書,在神州和實用都留下了合影。第二天,香港另一位富於傳奇性的作家林真先生賞飯,無言先生又與寬烈先生、俊東先生一起參加了。此後,我只要有機會到港,一定與無言先生和寬烈先生等歡聚,還登門觀賞過無言先生的珍貴藏書。當年與無言先生的這些親切交往,我至今歷歷在目。
無言先生在世時,我們見面話題太多,竟忘了向他請教經歷,尤其是他何以會對新文學那麼充滿興趣,樂此不疲。他一九九六年仙去,三年之後寬烈先生寫了〈專研三十年代文壇佚史的陳無言〉一文,後又見告若干史實,我因此得以擇要寫入紀念小文〈無言先生〉中,現再作補充和修訂如下:
陳無言,一九一三年生,福建漳州龍溪人,本名莊生,筆名陳野火、書丁等。一九三二年畢業於龍溪縣立高級中學。此後先後執教於龍溪的小學和中學,期間曾參加中學同學許鐵如(即後來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的彭沖)主持的「薌潮劇社」,參與劇本的編寫,這大概是他迷上新文學之始。一九三七年起先後擔任漳州《中華日報》、《商音日報》的編輯。不久因侵華日軍逼近漳州,他遠走香港,入正大參茸行任職。一九四〇年,作家楊騷到港,因同鄉關係借住陳無言處一個多月。差不多同時,他又結識了主編香港《大公報.文藝》的女作家楊剛。與楊騷和楊剛的接觸,大概促使他進一步迷戀新文學,在此之前,他已在用心搜集「原版新文學書籍,以及三十年代出版的雜誌」了。一九四一年以後,陳無言轉而經商,奔走於浙閩粵各地,並且成了家。一說在此期間他又進武漢大學文學院深造。抗戰勝利後,陳無言重回香港正大參茸行,任文牘和司帳多年。離開商界後,他又擔任過家庭教師,並為《明報》、《新晚報》等多家香港報刊撰文以維持生計。同時他也一直保持自己的愛好,繼續出沒於香港多家大小舊書店,致力於獵取新文學絕版書刊,逐漸成為香港屈指可數的新文學書刊收藏家。
無言先生這樣一份履歷,當然一點也不顯赫,但他對新文學的一腔熱情卻是完全出自內心,一以貫之。而且他不僅精心收藏,在蒐書過程中,每有心得,也動筆撰文,與讀者分享,日積月累,數量已相當可觀。無言先生逝世後,我每次到港與寬烈先生見面,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無言先生一生留下不少文字,但生前未能出書,實在是莫大的遺憾。如何彌補呢,我們是否應該為他編選一本以作紀念?寬烈先生手中保存了一些剪報,後來寄給我,希望我在內地謀求出版,然而,我幾經努力未果。再後來,我建議寬烈先生在香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不料當時規定出版資助必須作者本人提出申請,但無言先生早已謝世,無法自己申請了,這事又一次擱淺。直到寬烈先生也與世長辭,這事仍無進展,真是好事多磨啊。而今,在無言先生逝世整整廿六年之後,經陳可鵬兄和黎漢傑兄的共同努力,《文苑拾遺錄:陳無言書話集》終於編竣,即將問世了,豈不令我深感欣慰?
《文苑拾遺錄》一書清楚地顯示,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年間,無言先生在《星島日報》、《明報》副刊和《明報月刊》上發表了近四十餘篇長短文字,寫得這麼多,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料。他介紹和評論的現代作家之多之廣,更是令我吃驚,其中有許地山、劉延陵、梁宗岱、梁遇春、夏丏尊、羅家倫、羅皚嵐、羅念生、羅黑芷、盛成、彭家煌、彭芳草、楊騷、王世穎、徐蔚南、傅彥長、胡春冰、袁昌英、顧仲彝、吳天、楊剛、冼玉清、何家槐、李長之、張天翼、徐訏、柳木下、周楞伽、馬國亮、卜少夫、齊同、呂劍等位,甚至還有當代作家流沙河。其中約半數以上,大概直至今日內地現代文學研究界仍乏人問津,由此可知無言先生眼光之獨到。他對現代文學史上的邊緣作家和失蹤者一直有極為濃厚的興趣,記得他曾開過一個擬訪書的作家名單給我,除了上面他已寫過的好幾位之外,還有高語罕、敬隱漁、白薇、常風、張若谷、伍蠡甫、盧夢殊、李白鳳、李白英、林憾廬、孫席珍等,從中應可進一步窺見無言先生的新文學史觀。正如他自己在〈從《魯迅全集》人名注釋出錯談到被當作一人的兩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一文的前言中所表示的:
筆者一向有個心願,就是介紹被人忽略甚至遺忘的新文學作家。雖然他們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們總算在文學園地出過一點力,不應該被歧視以至湮沒無聞。
筆者明知介紹名字陌生的作家,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吃力」是沒有名氣的作家資料不容易搜集,「不討好」是寫出來也未必有人欣賞。雖然如此,但筆者為了興趣關係,總捨不得放棄。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工作頗有意義也好,有人認為是傻人做傻事也好,筆者絕不計較。而且,即便是寫許地山、張天翼等讀者已經比較熟悉的作家,他也力圖從新的角度切入,特別注重這些作家與香港的關聯,寫許地山就寫他在香港時所作的《貓乘》,寫張天翼就突出他在香港留下的文字,寫胡春冰就強調他在香港的戲劇活動,寫柳木下就寫到他在香港的寫詩經歷,而這些正是內地讀者和研究者所知寥寥乃至完全不知的。
應該承認,無言先生這些文章中,我特別看重他對與楊騷、楊剛、吳天、柳木下等作家交往的回憶,因為這是他的獨家秘辛,而且他很慎重,只是照實寫出,不隨便發揮。他一九三九年在香港陪同吳天拜訪了許地山、葉靈鳳、戴望舒等名作家和木刻家陳煙橋,但他只在〈記劇作家吳天〉一文中提了一筆,並未展開,很是可惜。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詩人楊騷在香港的時候〉中提供的楊騷一九四〇年回憶的「魯林失和」的第一手史料,極為重要,太重要了,故有必要照錄如下:
魯迅寫罵人的文章雖然十分潑辣,但當面對朋友發脾氣卻很少見。只有一次,我親眼看見魯迅與林語堂發生衝突。兩人本來是好朋友,不料因小小誤會而爭吵起來,幾乎鬧得無法收場。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在北四川路一間酒樓,請魯迅和許廣平吃晚飯。被邀作陪的有林語堂夫婦、章衣萍、吳曙天、郁達夫、川島這幾位。那天我恰巧去探望魯迅,因此也作了陪客。席間李小峰提起這一次版稅事,得到迅師諒解,實在非常感激。不過,始終認為有人從中挑撥,這個人是誰,不必說出名字,相信大家早已明白。魯迅聽了這番話雖不出聲,但面色已陰沉下來。大概林語堂沒有留意,反而附和李小峰。說友松與小峰不但是同業,而且都是周先生的學生,實在不應該挑撥離間。這時魯迅忽然站起身來,滿面怒容並大聲說:這件事我一定要向大家聲明。我向北新追討版稅,是我自己的主意,完全與友松無關。林先生既指明是友松挑撥是非,就請他拿出證據來。林語堂料不到魯迅有此一著,愈想解釋愈變成爭吵。於是兩人各執一詞,都不肯讓步。後來郁達夫恐怕事情愈鬧愈糟,一面勸魯迅坐下,一面拖著林語堂往外跑,林太太自然也跟著走,當晚的宴會也就不歡而散。
陳子善
在我記憶中,最早知道陳無言先生的大名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其時中國內地剛剛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香港昭明出版社推出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三卷本,之後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重印),翌年,香港友聯出版社推出劉紹銘先生主持翻譯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這兩部文學史著作先後進入內地,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帶來不小的震動,至少我個人讀過之後產生了重新審視已有的內地現代文學史著作的想法。如果我沒有記錯,我是先讀到《中國新文學史》,再讀到《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的〈跋〉中感謝了無言先生:
在本書撰寫中,陳無言先生不惜時間、金錢,蒐羅賜贈資料……均在此永志不忘。
雖然只有短短二十餘字,但無言先生在司馬長風一長串感謝名單中榮列首位,可見他對司馬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的幫助很大。這是我首次知道無言先生的大名,而且對無言先生產生了好奇心。
不久,我因研究郁達夫,有機會與郁達夫的友人,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的鄭子瑜先生取得聯繫。一九八四年,專攻中國修辭學的子瑜先生應邀訪問內地修辭學研究的重鎮――上海復旦大學,約我見面,交談甚歡。正是這次談話,不但促成了周作人的《知堂雜詩抄》在內地出版,也促成了我結識無言先生。我向子瑜先生打聽陳無言其人,他回答道:太巧了,我們熟識。你研究新文學,他也對新文學入迷,對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很熟悉,我介紹你們認識,對你一定有幫助。這真令我喜出望外。
後來,我才知道,子瑜先生和無言先生都祖籍福建漳州,既是同鄉,也是中學同學,友情甚篤。於是,經過子瑜先生牽線搭橋,我與無言先生聯繫上了,魚雁不斷。無言先生長我三十五歲,是我的師長輩,但他十分客氣,一直稱我這個小輩「子善先生」,無論是寫信稱呼還是寄贈書刊題字,都是如此,始終不變。
可以想見,我們通信的中心話題就是新文學,交流資訊,討論問題,互通有無。當時我需要港臺出版的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書刊,他都及時尋覓寄贈,而他需要一些三四十年代內地出版的新文學書籍,我也在上海為他搜羅寄去。當然,他提供給我的大大超過我提供給他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和《赤地之戀》等張愛玲著作的香港初版本是他寄贈的,梁實秋在臺灣出版的許多著譯版本也是他寄贈的,我成為《香港文學》作者之前的每期《香港文學》月刊仍是他寄贈的。特別是極為少見,可能是孤本的葉靈鳳散文集《忘憂草》(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香港西南圖書印刷公司初版),他也並不秘不示人,而是全書影印,裝訂成冊寄贈,我後來將《忘憂草》全書編入《葉靈鳳隨筆合集》第一卷,書名就定為《忘憂草》(一九九八年八月上海文匯出版社初版),從而使此書終於與內地讀者見面。可惜無言先生已經去世,未及親見。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首次赴港參加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辦的中國當代文學研討會。那天下午,也是無言先生好友的方寬烈先生親自到深圳接我,一併經羅湖過關渡海,直奔港島北角敦煌酒樓,無言先生早已等候在那裡,為我接風洗塵。那是一個頗為愉快的晚上,兩位香港文史前輩與我這樣一個上海小朋友盡興暢敘。研討會結束後,香港文壇友人又為我舉行一次難得的午宴,高伯雨、方寬烈、黃俊東、盧瑋鑾、蘇賡哲、楊玉峰等位都參加了,無言先生自然也在座。飯後,無言先生不顧行走不便,執意與寬烈先生一起帶我去神州、實用等舊書店訪書,在神州和實用都留下了合影。第二天,香港另一位富於傳奇性的作家林真先生賞飯,無言先生又與寬烈先生、俊東先生一起參加了。此後,我只要有機會到港,一定與無言先生和寬烈先生等歡聚,還登門觀賞過無言先生的珍貴藏書。當年與無言先生的這些親切交往,我至今歷歷在目。
無言先生在世時,我們見面話題太多,竟忘了向他請教經歷,尤其是他何以會對新文學那麼充滿興趣,樂此不疲。他一九九六年仙去,三年之後寬烈先生寫了〈專研三十年代文壇佚史的陳無言〉一文,後又見告若干史實,我因此得以擇要寫入紀念小文〈無言先生〉中,現再作補充和修訂如下:
陳無言,一九一三年生,福建漳州龍溪人,本名莊生,筆名陳野火、書丁等。一九三二年畢業於龍溪縣立高級中學。此後先後執教於龍溪的小學和中學,期間曾參加中學同學許鐵如(即後來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的彭沖)主持的「薌潮劇社」,參與劇本的編寫,這大概是他迷上新文學之始。一九三七年起先後擔任漳州《中華日報》、《商音日報》的編輯。不久因侵華日軍逼近漳州,他遠走香港,入正大參茸行任職。一九四〇年,作家楊騷到港,因同鄉關係借住陳無言處一個多月。差不多同時,他又結識了主編香港《大公報.文藝》的女作家楊剛。與楊騷和楊剛的接觸,大概促使他進一步迷戀新文學,在此之前,他已在用心搜集「原版新文學書籍,以及三十年代出版的雜誌」了。一九四一年以後,陳無言轉而經商,奔走於浙閩粵各地,並且成了家。一說在此期間他又進武漢大學文學院深造。抗戰勝利後,陳無言重回香港正大參茸行,任文牘和司帳多年。離開商界後,他又擔任過家庭教師,並為《明報》、《新晚報》等多家香港報刊撰文以維持生計。同時他也一直保持自己的愛好,繼續出沒於香港多家大小舊書店,致力於獵取新文學絕版書刊,逐漸成為香港屈指可數的新文學書刊收藏家。
無言先生這樣一份履歷,當然一點也不顯赫,但他對新文學的一腔熱情卻是完全出自內心,一以貫之。而且他不僅精心收藏,在蒐書過程中,每有心得,也動筆撰文,與讀者分享,日積月累,數量已相當可觀。無言先生逝世後,我每次到港與寬烈先生見面,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就是,無言先生一生留下不少文字,但生前未能出書,實在是莫大的遺憾。如何彌補呢,我們是否應該為他編選一本以作紀念?寬烈先生手中保存了一些剪報,後來寄給我,希望我在內地謀求出版,然而,我幾經努力未果。再後來,我建議寬烈先生在香港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不料當時規定出版資助必須作者本人提出申請,但無言先生早已謝世,無法自己申請了,這事又一次擱淺。直到寬烈先生也與世長辭,這事仍無進展,真是好事多磨啊。而今,在無言先生逝世整整廿六年之後,經陳可鵬兄和黎漢傑兄的共同努力,《文苑拾遺錄:陳無言書話集》終於編竣,即將問世了,豈不令我深感欣慰?
《文苑拾遺錄》一書清楚地顯示,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年間,無言先生在《星島日報》、《明報》副刊和《明報月刊》上發表了近四十餘篇長短文字,寫得這麼多,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料。他介紹和評論的現代作家之多之廣,更是令我吃驚,其中有許地山、劉延陵、梁宗岱、梁遇春、夏丏尊、羅家倫、羅皚嵐、羅念生、羅黑芷、盛成、彭家煌、彭芳草、楊騷、王世穎、徐蔚南、傅彥長、胡春冰、袁昌英、顧仲彝、吳天、楊剛、冼玉清、何家槐、李長之、張天翼、徐訏、柳木下、周楞伽、馬國亮、卜少夫、齊同、呂劍等位,甚至還有當代作家流沙河。其中約半數以上,大概直至今日內地現代文學研究界仍乏人問津,由此可知無言先生眼光之獨到。他對現代文學史上的邊緣作家和失蹤者一直有極為濃厚的興趣,記得他曾開過一個擬訪書的作家名單給我,除了上面他已寫過的好幾位之外,還有高語罕、敬隱漁、白薇、常風、張若谷、伍蠡甫、盧夢殊、李白鳳、李白英、林憾廬、孫席珍等,從中應可進一步窺見無言先生的新文學史觀。正如他自己在〈從《魯迅全集》人名注釋出錯談到被當作一人的兩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一文的前言中所表示的:
筆者一向有個心願,就是介紹被人忽略甚至遺忘的新文學作家。雖然他們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們總算在文學園地出過一點力,不應該被歧視以至湮沒無聞。
筆者明知介紹名字陌生的作家,是一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吃力」是沒有名氣的作家資料不容易搜集,「不討好」是寫出來也未必有人欣賞。雖然如此,但筆者為了興趣關係,總捨不得放棄。不管有人認為這種工作頗有意義也好,有人認為是傻人做傻事也好,筆者絕不計較。而且,即便是寫許地山、張天翼等讀者已經比較熟悉的作家,他也力圖從新的角度切入,特別注重這些作家與香港的關聯,寫許地山就寫他在香港時所作的《貓乘》,寫張天翼就突出他在香港留下的文字,寫胡春冰就強調他在香港的戲劇活動,寫柳木下就寫到他在香港的寫詩經歷,而這些正是內地讀者和研究者所知寥寥乃至完全不知的。
應該承認,無言先生這些文章中,我特別看重他對與楊騷、楊剛、吳天、柳木下等作家交往的回憶,因為這是他的獨家秘辛,而且他很慎重,只是照實寫出,不隨便發揮。他一九三九年在香港陪同吳天拜訪了許地山、葉靈鳳、戴望舒等名作家和木刻家陳煙橋,但他只在〈記劇作家吳天〉一文中提了一筆,並未展開,很是可惜。值得慶幸的是,他在〈詩人楊騷在香港的時候〉中提供的楊騷一九四〇年回憶的「魯林失和」的第一手史料,極為重要,太重要了,故有必要照錄如下:
魯迅寫罵人的文章雖然十分潑辣,但當面對朋友發脾氣卻很少見。只有一次,我親眼看見魯迅與林語堂發生衝突。兩人本來是好朋友,不料因小小誤會而爭吵起來,幾乎鬧得無法收場。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二九年八月底,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在北四川路一間酒樓,請魯迅和許廣平吃晚飯。被邀作陪的有林語堂夫婦、章衣萍、吳曙天、郁達夫、川島這幾位。那天我恰巧去探望魯迅,因此也作了陪客。席間李小峰提起這一次版稅事,得到迅師諒解,實在非常感激。不過,始終認為有人從中挑撥,這個人是誰,不必說出名字,相信大家早已明白。魯迅聽了這番話雖不出聲,但面色已陰沉下來。大概林語堂沒有留意,反而附和李小峰。說友松與小峰不但是同業,而且都是周先生的學生,實在不應該挑撥離間。這時魯迅忽然站起身來,滿面怒容並大聲說:這件事我一定要向大家聲明。我向北新追討版稅,是我自己的主意,完全與友松無關。林先生既指明是友松挑撥是非,就請他拿出證據來。林語堂料不到魯迅有此一著,愈想解釋愈變成爭吵。於是兩人各執一詞,都不肯讓步。後來郁達夫恐怕事情愈鬧愈糟,一面勸魯迅坐下,一面拖著林語堂往外跑,林太太自然也跟著走,當晚的宴會也就不歡而散。
目次
我所知道的陳無言先生/陳子善
淺談前輩書話家陳無言/黃晚鳳
多才短命的梁遇春
魯迅日記所提及之林惠元
悼念戲劇家胡春冰
詩人楊騷在香港的時候
介紹一本絕版好書――《無梯樓雜筆》
專寫短篇小說的孫席珍
楊昌溪的《文人趣事》
麗尼的散文詩與譯品
「現代派」作家徐霞村
從《作家筆名錄》出錯談到羅皚南與羅念生
詩人劉延陵與小說家羅黑芷
編《文藝》版出身的女作家楊剛
兩度誤傳死訊 談詩人梁宗岱
廣東才女冼玉清
第一位編寫劇本的女作家袁昌英
逝世十三週年紀念――談戲劇家顧仲彝
《草木篇》作者另一部少見的作品──流沙河的短篇小說集:《窗》
神秘詩人柳木下及其《海天集》
羅家倫及其詩集《疾風》
小說家何家愧與《貓》
《龍山夢痕》的兩位作者王世頴與徐蔚南
談許地山《貓》
夏丏尊及其《平屋雜文》
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閱後
譯有十五種文字的一本書――《我的母親》著者盛成
李長之的《詩經試譯》 把詩經譯成現代口語
談三本新文學參考書
駱賓基短篇小說選 作者要再提筆創作
記劇作家吳天
名作家徐訏的一生
老作家張天翼
東北作家齊同――高滔
《藝術三家言》著者之一傅彥長
《羽書》之作家――散文家吳伯蕭逝世
失去了聽覺的作家――周楞伽
詩人梁宗岱逝世 晚年時研究醫藥而放棄文學工作
散文《一劍集》 此係詩人之第一本散文集
從《魯迅全集》人名註釋出錯談到被當作一人的兩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
一九八四年來港定居 馬國亮自學成才
附錄 喜得舊書一批/許定銘
附錄 書癡陳無言/黃仲鳴
編後記/黎漢傑
淺談前輩書話家陳無言/黃晚鳳
多才短命的梁遇春
魯迅日記所提及之林惠元
悼念戲劇家胡春冰
詩人楊騷在香港的時候
介紹一本絕版好書――《無梯樓雜筆》
專寫短篇小說的孫席珍
楊昌溪的《文人趣事》
麗尼的散文詩與譯品
「現代派」作家徐霞村
從《作家筆名錄》出錯談到羅皚南與羅念生
詩人劉延陵與小說家羅黑芷
編《文藝》版出身的女作家楊剛
兩度誤傳死訊 談詩人梁宗岱
廣東才女冼玉清
第一位編寫劇本的女作家袁昌英
逝世十三週年紀念――談戲劇家顧仲彝
《草木篇》作者另一部少見的作品──流沙河的短篇小說集:《窗》
神秘詩人柳木下及其《海天集》
羅家倫及其詩集《疾風》
小說家何家愧與《貓》
《龍山夢痕》的兩位作者王世頴與徐蔚南
談許地山《貓》
夏丏尊及其《平屋雜文》
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閱後
譯有十五種文字的一本書――《我的母親》著者盛成
李長之的《詩經試譯》 把詩經譯成現代口語
談三本新文學參考書
駱賓基短篇小說選 作者要再提筆創作
記劇作家吳天
名作家徐訏的一生
老作家張天翼
東北作家齊同――高滔
《藝術三家言》著者之一傅彥長
《羽書》之作家――散文家吳伯蕭逝世
失去了聽覺的作家――周楞伽
詩人梁宗岱逝世 晚年時研究醫藥而放棄文學工作
散文《一劍集》 此係詩人之第一本散文集
從《魯迅全集》人名註釋出錯談到被當作一人的兩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
一九八四年來港定居 馬國亮自學成才
附錄 喜得舊書一批/許定銘
附錄 書癡陳無言/黃仲鳴
編後記/黎漢傑
書摘/試閱
魯迅日記所提及之林惠元
魯迅日記中所提及的人物,大約有數百人之多。大部分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作家、翻譯家、版畫家、以及書刊編輯等。但也有一部分是不見經傳的人物,例如林惠元(別號若狂)的名字就比較陌生了。
因為林惠元只是一個尚未成名的作家及翻譯家,他寫過散文,也寫過介紹外國作家的文章,分別發表於語絲、中學生、青年界等刊物。不過這些文章並沒有結集出版,所以知者不多。後來他專心致力於翻譯工作,花了不少時間譯完一部《英國文學史》,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據說這部書是根據F. S. Delmer原著:English Literature(From Beowulf To Bernard Shaw)全譯的。可惜出版後銷路不如理想,令他心灰意冷;終於悄然離開上海,返回他的家鄉漳州。
為了了解林惠元在上海時與魯迅及其他作家來往的情形,現在先將幾段日記摘抄出來(由筆者略加說明)然後再介紹他的身世。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下午。小峯(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峯),予塵(原名章廷謙,筆名川島,《語絲》負責人之一)來。雨。楊維銓(詩人,筆名楊騷)、林若狂來。晚邀諸客及三弟,廣平同往中有天夜餐。」
九月廿七日:
「晚。玉堂、和清(即《宇宙風》編輯林憾廬)、若狂、維銓同來,夜邀諸人至中有天晚餐。」
十月一日:
「晴。上午得林若狂信并稿。」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晚。林若狂持白薇稿來。」
三月十日:
「夜。楊維銓,林若狂來。」
三月十七日:
「晚應小峯招飲。同席為語堂、若狂、石民(詩人,翻譯家)、達夫、映霞、維銓、馥泉(翻譯家汪馥泉,曾與陳望道等創辦大江書舖,一度接替施蟄存主編《現代月刊》)等。」
四月十一日:
「下午。林惠元來,不見,留函而去。」
四月十三日:
「覆林惠元信。」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九日:
「上午。林惠元、白薇來,未見。」
三月三十日:
「上午。白薇及林惠元來。」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林惠元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經常去探訪魯迅;也知道林惠元認識不少作家,比較有交情的是楊騷與白薇。
林惠元本身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但提起他兩個親人,相信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原來林憾廬、林語堂都是他的叔父。惠元的父親林孟温是長兄,憾廬排行第三,語堂排名第六。惠元在兄弟中也是大哥。二弟惠泉(早逝)、三弟惠潛(現在南洋經商)、四弟惠川(抗戰期間病逝)、五弟惠瀛(現在星加坡教書)。
惠元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初間到漳州的。後來擔任民眾教育館館長,館址設在漳州中山公園內。當時筆者剛好高中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因與惠川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也就認識了惠元。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經常穿著一套並不時髦的西裝。是一個性格爽朗,熱情而健談的老實人。後來筆者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以及世界名著譯本,都是惠元所提供的。
記得有一次跟惠元閒談,話題扯到作家生活方面。惠元感慨地說:「一般人以為做了作家就可以名利兼得,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不過,這只是看到美好的一面。但暗澹的一面,是外界的人無法看到的。就以我本身所經歷的事為例吧:我曾經花了一年的心血,譯了一部《英國文學史》,請六叔替我校閱,並請他寫一篇序文推薦這部書。可是等了幾個月還沒有消息,惟有追問六叔。他的答覆是沒有時間看稿,所以也沒有辦法寫序。當時我負氣取回原稿,親自跟書店接洽。據他們的看法這是冷門書,又沒有名家作序,恐怕難有銷路。結果沒有一家肯印這部書。當時我很窮沒有能力自費出版,只好以低價賣給北新李小峯。後來書雖然出版了,但是銷路不好。我受了這一次打擊,以後再也提不起譯書的興趣了。這種情形雖然只是我個人的遭遇,相信也是一般未成名作家的遭遇。」
一九三二年四月間。漳州政府接受海外僑領的建議,調派十九路軍入閩。由蔡廷鍇主軍,蔣光鼐主政。漳州則由一團軍隊駐守,團長李金波兼城防司令。
林惠元除了本職(民眾教育館館長)之外,後來兼任抗日委員會主席。這個機構是縣政府委派人員與當地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組成的,(會址也在中山公園內)主要的任務是宣傳反日及抵制日貨。本來有不少商人向廈門日本洋行採購布匹和藥品,運來漳州出售,據說利潤相當好。自從抗日會成立,林惠元主張用勸諭、警告、標封拍賣(只能收回成本)的辦法,結果收效極大。販賣日貨商人因為無利可圖,也就改營國產及英美貨品了。
當時有一個商人簡孟嘗存有大批日本藥品,經抗日會屢次勸諭與警告,他始終不肯合作,日貨還是一批批從廈門運到漳州來。後來經惠元暗中調查,發現簡孟嘗是有後台老闆的。原來李團長就是簡的姐夫,生意是兩個人合作經營的。但惠元並沒有被權勢所嚇倒,於是召集各委員開會討論,結果議決採取行動。一方面標封存貨,一方面把簡孟嘗遊街儆戒,並在他胸前掛了一塊紙牌,上面寫著:「奸商簡孟嘗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李團長知道這件事是惠元出的主意,認為非把他剷除不可。於是派了幾個車隊到抗日會,正式拘捕惠元押往團部,連同另一名犯人立即綁赴刑場槍斃。行刑後在街張貼告示,宣佈林惠元勾結悍匪王俊,在北鄉一帶打家劫舍,證據確鑿,應即執行槍決。筆者記得惠元遇害時大概是三十歲左右、而且尚未結婚。
後來惠川告訴筆者,關於惠元被害的前因後果以及詳細情形,早由他父親寫信給六叔(當時語堂在上海),據六叔回信說,這件事已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的名義,並由宋慶齡領銜:發電報給蔡廷鍇,請他徹查這宗案件。但據筆者所知,那封電報並沒有發生作用,因為當時蔡廷鍇正醖釀閩變,哪有功夫理會這種小事兒呢?
惠元遇害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死者已矣!不過,有一個問題一直在筆者腦海中盤旋:
「一個反日工作者,他沒有死在敵人手上,反而死於抗日軍隊的槍下。這究竟是幽默?還是諷刺呢?」
《星島日報.星辰版》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
魯迅日記中所提及的人物,大約有數百人之多。大部分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作家、翻譯家、版畫家、以及書刊編輯等。但也有一部分是不見經傳的人物,例如林惠元(別號若狂)的名字就比較陌生了。
因為林惠元只是一個尚未成名的作家及翻譯家,他寫過散文,也寫過介紹外國作家的文章,分別發表於語絲、中學生、青年界等刊物。不過這些文章並沒有結集出版,所以知者不多。後來他專心致力於翻譯工作,花了不少時間譯完一部《英國文學史》,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據說這部書是根據F. S. Delmer原著:English Literature(From Beowulf To Bernard Shaw)全譯的。可惜出版後銷路不如理想,令他心灰意冷;終於悄然離開上海,返回他的家鄉漳州。
為了了解林惠元在上海時與魯迅及其他作家來往的情形,現在先將幾段日記摘抄出來(由筆者略加說明)然後再介紹他的身世。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
「下午。小峯(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峯),予塵(原名章廷謙,筆名川島,《語絲》負責人之一)來。雨。楊維銓(詩人,筆名楊騷)、林若狂來。晚邀諸客及三弟,廣平同往中有天夜餐。」
九月廿七日:
「晚。玉堂、和清(即《宇宙風》編輯林憾廬)、若狂、維銓同來,夜邀諸人至中有天晚餐。」
十月一日:
「晴。上午得林若狂信并稿。」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晚。林若狂持白薇稿來。」
三月十日:
「夜。楊維銓,林若狂來。」
三月十七日:
「晚應小峯招飲。同席為語堂、若狂、石民(詩人,翻譯家)、達夫、映霞、維銓、馥泉(翻譯家汪馥泉,曾與陳望道等創辦大江書舖,一度接替施蟄存主編《現代月刊》)等。」
四月十一日:
「下午。林惠元來,不見,留函而去。」
四月十三日:
「覆林惠元信。」
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九日:
「上午。林惠元、白薇來,未見。」
三月三十日:
「上午。白薇及林惠元來。」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林惠元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經常去探訪魯迅;也知道林惠元認識不少作家,比較有交情的是楊騷與白薇。
林惠元本身雖然沒有什麼名氣,但提起他兩個親人,相信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原來林憾廬、林語堂都是他的叔父。惠元的父親林孟温是長兄,憾廬排行第三,語堂排名第六。惠元在兄弟中也是大哥。二弟惠泉(早逝)、三弟惠潛(現在南洋經商)、四弟惠川(抗戰期間病逝)、五弟惠瀛(現在星加坡教書)。
惠元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初間到漳州的。後來擔任民眾教育館館長,館址設在漳州中山公園內。當時筆者剛好高中畢業,還沒有找到工作。因與惠川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也就認識了惠元。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經常穿著一套並不時髦的西裝。是一個性格爽朗,熱情而健談的老實人。後來筆者讀了不少新文學作品,以及世界名著譯本,都是惠元所提供的。
記得有一次跟惠元閒談,話題扯到作家生活方面。惠元感慨地說:「一般人以為做了作家就可以名利兼得,生活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不過,這只是看到美好的一面。但暗澹的一面,是外界的人無法看到的。就以我本身所經歷的事為例吧:我曾經花了一年的心血,譯了一部《英國文學史》,請六叔替我校閱,並請他寫一篇序文推薦這部書。可是等了幾個月還沒有消息,惟有追問六叔。他的答覆是沒有時間看稿,所以也沒有辦法寫序。當時我負氣取回原稿,親自跟書店接洽。據他們的看法這是冷門書,又沒有名家作序,恐怕難有銷路。結果沒有一家肯印這部書。當時我很窮沒有能力自費出版,只好以低價賣給北新李小峯。後來書雖然出版了,但是銷路不好。我受了這一次打擊,以後再也提不起譯書的興趣了。這種情形雖然只是我個人的遭遇,相信也是一般未成名作家的遭遇。」
一九三二年四月間。漳州政府接受海外僑領的建議,調派十九路軍入閩。由蔡廷鍇主軍,蔣光鼐主政。漳州則由一團軍隊駐守,團長李金波兼城防司令。
林惠元除了本職(民眾教育館館長)之外,後來兼任抗日委員會主席。這個機構是縣政府委派人員與當地各界知名人士聯合組成的,(會址也在中山公園內)主要的任務是宣傳反日及抵制日貨。本來有不少商人向廈門日本洋行採購布匹和藥品,運來漳州出售,據說利潤相當好。自從抗日會成立,林惠元主張用勸諭、警告、標封拍賣(只能收回成本)的辦法,結果收效極大。販賣日貨商人因為無利可圖,也就改營國產及英美貨品了。
當時有一個商人簡孟嘗存有大批日本藥品,經抗日會屢次勸諭與警告,他始終不肯合作,日貨還是一批批從廈門運到漳州來。後來經惠元暗中調查,發現簡孟嘗是有後台老闆的。原來李團長就是簡的姐夫,生意是兩個人合作經營的。但惠元並沒有被權勢所嚇倒,於是召集各委員開會討論,結果議決採取行動。一方面標封存貨,一方面把簡孟嘗遊街儆戒,並在他胸前掛了一塊紙牌,上面寫著:「奸商簡孟嘗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李團長知道這件事是惠元出的主意,認為非把他剷除不可。於是派了幾個車隊到抗日會,正式拘捕惠元押往團部,連同另一名犯人立即綁赴刑場槍斃。行刑後在街張貼告示,宣佈林惠元勾結悍匪王俊,在北鄉一帶打家劫舍,證據確鑿,應即執行槍決。筆者記得惠元遇害時大概是三十歲左右、而且尚未結婚。
後來惠川告訴筆者,關於惠元被害的前因後果以及詳細情形,早由他父親寫信給六叔(當時語堂在上海),據六叔回信說,這件事已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的名義,並由宋慶齡領銜:發電報給蔡廷鍇,請他徹查這宗案件。但據筆者所知,那封電報並沒有發生作用,因為當時蔡廷鍇正醖釀閩變,哪有功夫理會這種小事兒呢?
惠元遇害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死者已矣!不過,有一個問題一直在筆者腦海中盤旋:
「一個反日工作者,他沒有死在敵人手上,反而死於抗日軍隊的槍下。這究竟是幽默?還是諷刺呢?」
《星島日報.星辰版》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