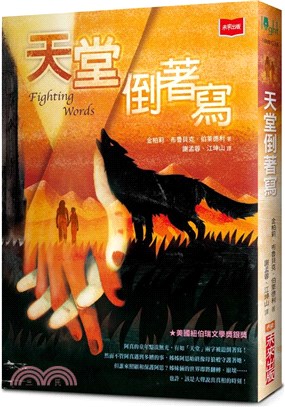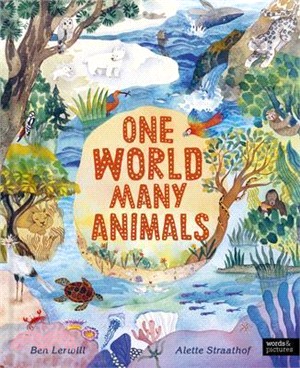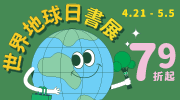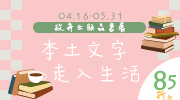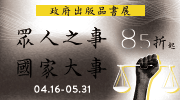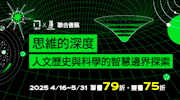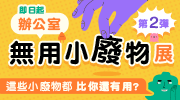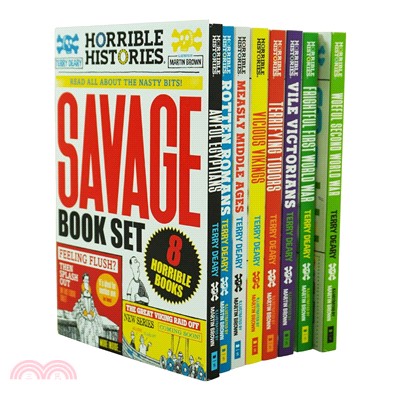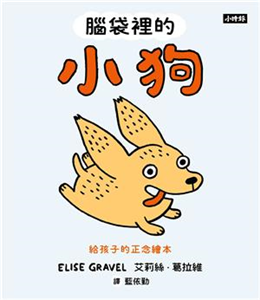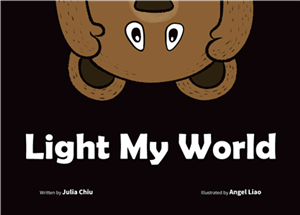天堂倒著寫
商品資訊
系列名:小說館
ISBN13:9786263551565
替代書名:Fighting Words
出版社:未來出版
作者:金柏莉.布魯貝克.伯萊德利
譯者:謝孟蓉;江坤山
出版日:2023/04/14
裝訂/頁數:平裝/296頁
規格:21cm*15cm*2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
勇敢的捍衛自己,大聲的說出真相,
整個世界都會傾聽你、幫助你!
強而有力、動人心弦的青少年議題小說,透過十歲主角溫暖、真誠、幽默中透著辛酸的語調,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深受啟發並明白──如何在身陷困境時勇於發聲、為自己挺身而出,重建親情、友誼,以及自己的人生!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號角書獎 ★美國柯克斯書評獎決選好書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年度好書 ★美國《號角》雜誌年度好書
★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好書 ★美國《書單》年度好書
★美國《柯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美國圖書館協會推薦好書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年度好書 ★美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年度好書
★美國書評網站BookPage年度好書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飛越戰火的女孩》作者最新力作!
王加恩(臺北市教育局學輔中心督導‧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臺北馬偕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輔大臨床心理所臨床助理教授)
林滿秋(金鼎獎青少年小說家‧臺北書展大獎得主)
感動推薦
張子樟(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專文導賞
一本讓人沒有一口氣看完會無法好好入眠的好書!提醒我們面對極其痛苦的生命創傷時,彼此相愛是最大的良藥!作者將她自身的經歷轉化為既深刻又生動的文字,讓讀者與主角一同感受到創傷所帶來的恐懼,經驗了他人的幫助與專業的醫治,以及得以找回勇氣與夢想的希望!如果你或是你身邊的人正面對著生命中巨大的傷痛,翻開此書,你會知道自己絕不孤單!也鼓勵你勇敢尋求學校輔導室或心理專業的幫助!!
──王加恩
(臺北市教育局學輔中心督導‧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
臺北馬偕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輔大臨床心理所臨床助理教授)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飛越戰火的女孩》作者
再度獲獎最新力作!
最終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壓迫和殘酷,而是好人對此沉默。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阿真的童年黯淡無光,有如「天堂」兩字被迫倒著寫!然而不管阿真遇到多糟的事,姊姊阿思總會待在她身邊:當她們的媽媽入監服刑,阿真有阿思當靠山;當媽媽的男友克利頓收留她們時,阿真有阿思陪伴;當姊妹倆不得不逃離克利頓家時,阿真有阿思可以倚靠。阿思從六歲開始照顧同母異父的妹妹阿真,她是阿真的母狼,是阿真的守護者。但誰來保護阿思呢?從阿思試圖傷害自己的那一刻起,阿真的世界徹底翻轉、崩壞……也許,該是大聲說出真相的時刻!
一本強而有力、動人心弦的青少年議題小說,透過主角溫暖、真誠、幽默中透著辛酸的語調,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深受啟發,同時深切明白本書作者最想傳達的──身陷困境或受到傷害時,要勇於發聲、為自己挺身而出;一有機會,一定要尋求幫助。無論人生中的某件事讓你感覺多麼糟糕,這些糟糕的感覺都是暫時的。我們總是可以痊癒,我們總是可以好起來,重建並贏回親情、友誼,以及自己的人生!
勇敢的捍衛自己,大聲的說出真相,
整個世界都會傾聽你、幫助你!
強而有力、動人心弦的青少年議題小說,透過十歲主角溫暖、真誠、幽默中透著辛酸的語調,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深受啟發並明白──如何在身陷困境時勇於發聲、為自己挺身而出,重建親情、友誼,以及自己的人生!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號角書獎 ★美國柯克斯書評獎決選好書
★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年度好書 ★美國《號角》雜誌年度好書
★美國《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好書 ★美國《書單》年度好書
★美國《柯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美國圖書館協會推薦好書
★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年度好書 ★美國芝加哥公共圖書館年度好書
★美國書評網站BookPage年度好書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飛越戰火的女孩》作者最新力作!
王加恩(臺北市教育局學輔中心督導‧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臺北馬偕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輔大臨床心理所臨床助理教授)
林滿秋(金鼎獎青少年小說家‧臺北書展大獎得主)
感動推薦
張子樟(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專文導賞
一本讓人沒有一口氣看完會無法好好入眠的好書!提醒我們面對極其痛苦的生命創傷時,彼此相愛是最大的良藥!作者將她自身的經歷轉化為既深刻又生動的文字,讓讀者與主角一同感受到創傷所帶來的恐懼,經驗了他人的幫助與專業的醫治,以及得以找回勇氣與夢想的希望!如果你或是你身邊的人正面對著生命中巨大的傷痛,翻開此書,你會知道自己絕不孤單!也鼓勵你勇敢尋求學校輔導室或心理專業的幫助!!
──王加恩
(臺北市教育局學輔中心督導‧臺灣大學心理學博士
臺北馬偕醫院資深臨床心理師‧輔大臨床心理所臨床助理教授)
★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飛越戰火的女孩》作者
再度獲獎最新力作!
最終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壓迫和殘酷,而是好人對此沉默。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阿真的童年黯淡無光,有如「天堂」兩字被迫倒著寫!然而不管阿真遇到多糟的事,姊姊阿思總會待在她身邊:當她們的媽媽入監服刑,阿真有阿思當靠山;當媽媽的男友克利頓收留她們時,阿真有阿思陪伴;當姊妹倆不得不逃離克利頓家時,阿真有阿思可以倚靠。阿思從六歲開始照顧同母異父的妹妹阿真,她是阿真的母狼,是阿真的守護者。但誰來保護阿思呢?從阿思試圖傷害自己的那一刻起,阿真的世界徹底翻轉、崩壞……也許,該是大聲說出真相的時刻!
一本強而有力、動人心弦的青少年議題小說,透過主角溫暖、真誠、幽默中透著辛酸的語調,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深受啟發,同時深切明白本書作者最想傳達的──身陷困境或受到傷害時,要勇於發聲、為自己挺身而出;一有機會,一定要尋求幫助。無論人生中的某件事讓你感覺多麼糟糕,這些糟糕的感覺都是暫時的。我們總是可以痊癒,我們總是可以好起來,重建並贏回親情、友誼,以及自己的人生!
作者簡介
金柏莉.布魯貝克.伯萊德利(Kimberly Brubaker Bradley)/文
美國《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著有多本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品,獲獎無數。
《天堂倒著寫》是她新近創作的青少年小說,與舊作《飛越戰火的女孩》同樣榮獲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由於童年經歷,她希望藉由這部得獎新作,幫助更多讀者勇於為自己發聲、克服創傷並痊癒(一定可以的)!就像美國黃石國家公園那十四匹狼一樣的改變荒蕪野地,重拾美好且豐饒的人生。
目前跟丈夫、愛狗住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自家農場上,貓、馬成群,日日勤於筆耕。
作者個人網站:kimberlybrubakerbradley.com
美國《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著有多本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品,獲獎無數。
《天堂倒著寫》是她新近創作的青少年小說,與舊作《飛越戰火的女孩》同樣榮獲美國紐伯瑞文學獎銀獎。由於童年經歷,她希望藉由這部得獎新作,幫助更多讀者勇於為自己發聲、克服創傷並痊癒(一定可以的)!就像美國黃石國家公園那十四匹狼一樣的改變荒蕪野地,重拾美好且豐饒的人生。
目前跟丈夫、愛狗住在美國田納西州的自家農場上,貓、馬成群,日日勤於筆耕。
作者個人網站:kimberlybrubakerbradley.com
序
【導讀】
勇敢、大聲的說出來!
張子樟(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這是一本優秀的青少年小說,涵蓋了性侵害、寄養、無家可歸、吸毒成癮和其他沉重的現實問題。
就寫作技巧層面而言,作者選擇使用第一人稱書寫,手法相當高明,因為讀者可以很快融入故事情節,進而深信主角所說的一切,認同她、同情她、理解她。
主角阿真的個性從一開始就顯得突出。她的言行讓人想起《吉莉的選擇》(Great Gilly Hopkins)中的吉莉,個性雖不盡相同,但同樣立刻吸引讀者。因為同情她,讀者才會融入她的世界,並且關心她要如何解除困境。
阿真一出生,當時六歲的姊姊阿思就被迫瞬間長大,猶如成年人般一肩扛起照顧阿真的責任。隨著時間推移,原本讓阿真信任、依賴的姊姊阿思卻似乎深受某種創傷所苦,來到寄養家庭後,甚至頻繁做噩夢、容易陷入沮喪。
原來多年來阿思身心深受侵害,卻不敢舉報。她擔心自己在法庭上不得不坐在罪犯面前作證,而對方的律師則會想盡辦法讓她聽起來像在撒謊。對她來說,說出真相並不容易。
某天晚上阿思試圖自殺,阿真這才意識到──她其實不知道姊姊究竟經歷了什麼;但她知道自己和姊姊都必須獲得幫助,並學會大聲疾呼,即使她們不確定周遭的世界是否想傾聽她們要說的話。
書中另一位要角是照顧阿真和阿思的「寄養媽媽」蘭欣。她心直口快但心地善良,為這對姊妹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令人難以置信。作者把她的個性設定得有稜有角、頑固卻堅定,也因此她與兩個女孩的個性相配且互補。她們需要她,她也需要她們。她與當局爭鬥,以確保姊妹倆能夠得到適當的心理評估和諮商,因為她知道並理解她們所遭受的創傷。
這本書的情節鋪陳流暢易讀,透過阿真的語調,整體敘述生動活潑,字裡行間充滿了愛和勇氣。對於讀慣中產階級孩子快樂故事的讀者而言,這個故事本身有能力讓他們產生同理心,並理解書中角色所面對的困境。雖然有些部分會讓讀者感到不快,然而對青少年讀者來說,書中所帶出的議題非常值得討論與注意,尤其是關於「尊重他人是否同意」以及「身體自主權」。
作者的書寫令人讚揚、尊重和欽佩。她勇敢的在〈後記〉中道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創作並與世界分享這個涉及未成年性侵害、性騷擾、不當觸碰、身體自主權等話題的故事。
作者更想藉由這部作品傳達的是──經歷過這類創傷的孩子皆可以治癒,他們從來都不孤單。這種事發生在不少孩子身上,但全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人們開始更常談論性騷擾這類議題,說不定許多可能的加害者由於害怕被追究責任和揭露罪行,這些事情就會較少發生。
《天堂倒著寫》除了明確的以「性侵害」為主題,作者還特地藉由故事情節安排,大聲疾呼:一些常見但看似無害的騷擾言行,仍然有害,且會讓人受創。
故事中,十歲的阿真能感受到被他人不適當的觸碰是可怕且不對的,但由於資訊匱乏,她不知道像這樣的騷擾舉止會遭到懲罰;後來在心理治療師的引導下,她漸漸懂得使用適當的應對方式來武裝、保護自己,也理解了「同意」的概念,更學會把話大聲說出來的重要性。例如:針對男同學崔偉的騷擾和霸凌,阿真的自我捍衛與集結受害同學合力反撲的經驗,就證明了直言不諱和大聲說出實情的力量。
成年人有責任正確的教育兒童,讓他們充滿自信,並要求他們在糟糕或不恰當的事情發生時,必須主動、勇敢的說出來,而不是讓孩子們自行面對和處理他們還沒準備好的一切。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優點之一──強調「大聲疾呼」的力量。
例如:阿真為了畫家譜一事,對老師說出一個不該出口的「雪」字,因而被叫到校長室報到。她告訴校長,如果她沒有說出這個字眼,就不會被叫來解釋自己的導師有多麼麻木不仁,以及她因此有多麼無助。「看吧,大嘴巴有用。 」
我們必須教導孩子們面對不公正時,應該勇敢的說出來。雖然阿真從不羞於說出自己的想法,卻被教導要對某些問題保持沉默:「我學到了有些事情幾乎沒辦法聊,因為是沒有人想知道的事。」這令人想起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最終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壓迫和殘酷,而是好人對此沉默。」
事實上,解決性侵害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涉及兒童時。這本書以率真但優雅的急需方式做到了這點。孩子們需要知道──他們在泥淖中掙扎時並不孤單;大嘴巴是必要的,總會有人伸出援手。
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契可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在他的名篇〈大學生〉寫著:「……無論是在哪個年代,照樣有過……這樣的愚昧,這樣的哀傷……這樣的壓抑。所有這些可怕的災難,從前有過,現在還有,將來也會有,因此再過幾千年之後,生活也不會得到改善……」遭遇困境時,人們如果消極些,也許就認了,因為這是世界永恆的循環,抗爭的聲音與爭取平等的力量永遠存在,卻遲早會被掩沒。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由於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生活在暗黑角落的弱勢孩子也有機會上學,任何事情再也無法掩蓋,包括這本書裡提到的所有不公不義的事。我們深信,隨著時代的進步,正義的力量終將出現。
【後記】
後 記
我想要你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它發生在我身上。
第二件事是我能夠痊癒。這需要時間、努力,但我辦到了。人一定可以痊癒的。
我小時候遭到性侵。這件事很痛苦、糟糕,而且在很多方面以難熬的方式影響我的人生。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跟任何人說。當我開始能夠談這件事,其他人也開始跟我說他們的故事。人數還不少。我了解到很多人受性騷擾影響。多數人覺得難以啟齒,但要克服它所造成的傷害,能夠談是第一步。
最後,我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我寫了這本書,希望它能幫助讀者找到自己的話語。
為什麼會難以啟齒?我想那是因為遭到侵犯的孩子被迫要處理大人的事情,而且是在他們作好準備之前好幾年。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沒有力量,而且驚恐莫名。他們心想一定是自己有什麼問題││不知為何,但發生的事一定是他們的錯(從來就不是)。
有些家庭面臨成癮與精神疾病等難題,讓一切更加惡化。當成年人無法好好照顧孩童,孩童(像是阿思)本身就必須表現得像是成年人,擔負起他們還沒準備好要處理的責任。當你還沒度過孩童期卻必須當個成年人,那是一件困難且有害的事情。
表面上看起來健康的家庭也可能一團糟。光是觀察某個人,不一定就能判斷他們是不是過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一開始先相信。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們受到傷害了,或是他們需要協助,相信他們。說:「真的很抱歉。」說:「這不是你的錯。」說:「你說出來很勇敢。我以你為傲。」
如果你是那個受到傷害的人,請先相信那不是你的錯。也請相信那是錯的、有害的,你應該獲得幫助。努力去找到自己的話語。
一有機會,就為你自己或信任你的朋友尋求幫助。如果可以的話,告訴你的爸媽,或是任何你能信任的成年人。如果那個人沒有幫助你,改向跟其他人說。教師、警察、醫師都有義務通報;換句話說,當有人跟他們提到性侵,他們就必須提出正式的報告。告訴任何一位你能信任的成年人,不斷跟他們說,直到他們幫助你。
本書中,阿真學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同意」。其實,「同意」這個概念很好理解:沒有你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對你的身體做任何事││而允許是指說「好」,而不只是沒有說「不」。有時我們不習慣徵求同意,不習慣在朋友一臉哀傷時說:「嘿,你想要一個擁抱嗎?」習慣徵求別人同意是好事。請多練習。當別人跟你說「不」的時候,一定要聽。
事實上,孩子不能同意某些成年人的事情。他們的年紀還太小。在某些情況下,孩子願不願意表示同意根本無關緊要││他們就是不能。在這些情況下,要怪罪的永遠不是孩童,而是成年人。
無論人生中的某件事讓你感覺多麼糟糕,你要知道這些糟糕的感覺都是暫時的。我們總是可以痊癒,我們總是可以好起來。我保證。
在臺灣,如果你想要找如何獲得幫助或是幫助某個人的更多資訊,可以打直撥「113」專線,這是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二十四小時保護專線。以下的網址也可以找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聯絡資訊: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04-6634-105.html。
最後,如果你曾想過要傷害自己,拜託,千萬不要。很多地方能幫助你。你隨時可以免費直撥「1925」 (依舊愛我),這是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安心專線。除了各縣市社區心理諮商服務: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558-69568-107.html,這個網頁也列出包括「生命線」、「張老師」等許多全國諮詢和救援服務專線: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327-8715-107.html。
最後的最後,當一隻狼。照顧自己的狼群。然後戰鬥。
如果你想深入思考本書所涵蓋的主題,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和朋友一起討論的問題。
1. 為什麼阿真說阿思的超能力是讓自己隱形?阿思隱形有什麼好處?如果人們真的看到她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2. 阿真周遭的人真的看到她了嗎?她沒有隱形,但是她擅長戴上面具,躲在後面。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會如何幫助或傷害她?
3. 戴奉老師對阿真有什麼看法?校長(潘妮博士)呢?蘭欣呢?哪個人看到了最真實的阿真?
4. 阿真如何學會展現自己?是什麼幫助她找到自己的話語?是什麼幫助她持續戰鬥?
5. 阿真對阿思的愛如何讓故事出現轉折?阿思對阿真的愛又如何讓故事發生變化?愛我們的人如何讓我們變得誠實和堅強?
6. 書中最驚悚的時刻是阿思傷害自己的時候。在她所能做的事情當中,為什麼這是最糟糕的?為什麼阿思不答應阿真她永遠不會再這樣做?她能做出那樣的承諾嗎?
7. 為什麼阿真的故事這麼難以啟齒?是什麼讓她有足夠的勇氣說出來?
勇敢、大聲的說出來!
張子樟(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這是一本優秀的青少年小說,涵蓋了性侵害、寄養、無家可歸、吸毒成癮和其他沉重的現實問題。
就寫作技巧層面而言,作者選擇使用第一人稱書寫,手法相當高明,因為讀者可以很快融入故事情節,進而深信主角所說的一切,認同她、同情她、理解她。
主角阿真的個性從一開始就顯得突出。她的言行讓人想起《吉莉的選擇》(Great Gilly Hopkins)中的吉莉,個性雖不盡相同,但同樣立刻吸引讀者。因為同情她,讀者才會融入她的世界,並且關心她要如何解除困境。
阿真一出生,當時六歲的姊姊阿思就被迫瞬間長大,猶如成年人般一肩扛起照顧阿真的責任。隨著時間推移,原本讓阿真信任、依賴的姊姊阿思卻似乎深受某種創傷所苦,來到寄養家庭後,甚至頻繁做噩夢、容易陷入沮喪。
原來多年來阿思身心深受侵害,卻不敢舉報。她擔心自己在法庭上不得不坐在罪犯面前作證,而對方的律師則會想盡辦法讓她聽起來像在撒謊。對她來說,說出真相並不容易。
某天晚上阿思試圖自殺,阿真這才意識到──她其實不知道姊姊究竟經歷了什麼;但她知道自己和姊姊都必須獲得幫助,並學會大聲疾呼,即使她們不確定周遭的世界是否想傾聽她們要說的話。
書中另一位要角是照顧阿真和阿思的「寄養媽媽」蘭欣。她心直口快但心地善良,為這對姊妹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令人難以置信。作者把她的個性設定得有稜有角、頑固卻堅定,也因此她與兩個女孩的個性相配且互補。她們需要她,她也需要她們。她與當局爭鬥,以確保姊妹倆能夠得到適當的心理評估和諮商,因為她知道並理解她們所遭受的創傷。
這本書的情節鋪陳流暢易讀,透過阿真的語調,整體敘述生動活潑,字裡行間充滿了愛和勇氣。對於讀慣中產階級孩子快樂故事的讀者而言,這個故事本身有能力讓他們產生同理心,並理解書中角色所面對的困境。雖然有些部分會讓讀者感到不快,然而對青少年讀者來說,書中所帶出的議題非常值得討論與注意,尤其是關於「尊重他人是否同意」以及「身體自主權」。
作者的書寫令人讚揚、尊重和欽佩。她勇敢的在〈後記〉中道出自己也曾是受害者,創作並與世界分享這個涉及未成年性侵害、性騷擾、不當觸碰、身體自主權等話題的故事。
作者更想藉由這部作品傳達的是──經歷過這類創傷的孩子皆可以治癒,他們從來都不孤單。這種事發生在不少孩子身上,但全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人們開始更常談論性騷擾這類議題,說不定許多可能的加害者由於害怕被追究責任和揭露罪行,這些事情就會較少發生。
《天堂倒著寫》除了明確的以「性侵害」為主題,作者還特地藉由故事情節安排,大聲疾呼:一些常見但看似無害的騷擾言行,仍然有害,且會讓人受創。
故事中,十歲的阿真能感受到被他人不適當的觸碰是可怕且不對的,但由於資訊匱乏,她不知道像這樣的騷擾舉止會遭到懲罰;後來在心理治療師的引導下,她漸漸懂得使用適當的應對方式來武裝、保護自己,也理解了「同意」的概念,更學會把話大聲說出來的重要性。例如:針對男同學崔偉的騷擾和霸凌,阿真的自我捍衛與集結受害同學合力反撲的經驗,就證明了直言不諱和大聲說出實情的力量。
成年人有責任正確的教育兒童,讓他們充滿自信,並要求他們在糟糕或不恰當的事情發生時,必須主動、勇敢的說出來,而不是讓孩子們自行面對和處理他們還沒準備好的一切。這也是本書最重要的優點之一──強調「大聲疾呼」的力量。
例如:阿真為了畫家譜一事,對老師說出一個不該出口的「雪」字,因而被叫到校長室報到。她告訴校長,如果她沒有說出這個字眼,就不會被叫來解釋自己的導師有多麼麻木不仁,以及她因此有多麼無助。「看吧,大嘴巴有用。 」
我們必須教導孩子們面對不公正時,應該勇敢的說出來。雖然阿真從不羞於說出自己的想法,卻被教導要對某些問題保持沉默:「我學到了有些事情幾乎沒辦法聊,因為是沒有人想知道的事。」這令人想起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最終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壓迫和殘酷,而是好人對此沉默。」
事實上,解決性侵害問題並不容易,特別是涉及兒童時。這本書以率真但優雅的急需方式做到了這點。孩子們需要知道──他們在泥淖中掙扎時並不孤單;大嘴巴是必要的,總會有人伸出援手。
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契可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在他的名篇〈大學生〉寫著:「……無論是在哪個年代,照樣有過……這樣的愚昧,這樣的哀傷……這樣的壓抑。所有這些可怕的災難,從前有過,現在還有,將來也會有,因此再過幾千年之後,生活也不會得到改善……」遭遇困境時,人們如果消極些,也許就認了,因為這是世界永恆的循環,抗爭的聲音與爭取平等的力量永遠存在,卻遲早會被掩沒。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由於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生活在暗黑角落的弱勢孩子也有機會上學,任何事情再也無法掩蓋,包括這本書裡提到的所有不公不義的事。我們深信,隨著時代的進步,正義的力量終將出現。
【後記】
後 記
我想要你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它發生在我身上。
第二件事是我能夠痊癒。這需要時間、努力,但我辦到了。人一定可以痊癒的。
我小時候遭到性侵。這件事很痛苦、糟糕,而且在很多方面以難熬的方式影響我的人生。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跟任何人說。當我開始能夠談這件事,其他人也開始跟我說他們的故事。人數還不少。我了解到很多人受性騷擾影響。多數人覺得難以啟齒,但要克服它所造成的傷害,能夠談是第一步。
最後,我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我寫了這本書,希望它能幫助讀者找到自己的話語。
為什麼會難以啟齒?我想那是因為遭到侵犯的孩子被迫要處理大人的事情,而且是在他們作好準備之前好幾年。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沒有力量,而且驚恐莫名。他們心想一定是自己有什麼問題││不知為何,但發生的事一定是他們的錯(從來就不是)。
有些家庭面臨成癮與精神疾病等難題,讓一切更加惡化。當成年人無法好好照顧孩童,孩童(像是阿思)本身就必須表現得像是成年人,擔負起他們還沒準備好要處理的責任。當你還沒度過孩童期卻必須當個成年人,那是一件困難且有害的事情。
表面上看起來健康的家庭也可能一團糟。光是觀察某個人,不一定就能判斷他們是不是過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該怎麼辦?一開始先相信。如果有人告訴你他們受到傷害了,或是他們需要協助,相信他們。說:「真的很抱歉。」說:「這不是你的錯。」說:「你說出來很勇敢。我以你為傲。」
如果你是那個受到傷害的人,請先相信那不是你的錯。也請相信那是錯的、有害的,你應該獲得幫助。努力去找到自己的話語。
一有機會,就為你自己或信任你的朋友尋求幫助。如果可以的話,告訴你的爸媽,或是任何你能信任的成年人。如果那個人沒有幫助你,改向跟其他人說。教師、警察、醫師都有義務通報;換句話說,當有人跟他們提到性侵,他們就必須提出正式的報告。告訴任何一位你能信任的成年人,不斷跟他們說,直到他們幫助你。
本書中,阿真學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同意」。其實,「同意」這個概念很好理解:沒有你的允許,任何人都不能對你的身體做任何事││而允許是指說「好」,而不只是沒有說「不」。有時我們不習慣徵求同意,不習慣在朋友一臉哀傷時說:「嘿,你想要一個擁抱嗎?」習慣徵求別人同意是好事。請多練習。當別人跟你說「不」的時候,一定要聽。
事實上,孩子不能同意某些成年人的事情。他們的年紀還太小。在某些情況下,孩子願不願意表示同意根本無關緊要││他們就是不能。在這些情況下,要怪罪的永遠不是孩童,而是成年人。
無論人生中的某件事讓你感覺多麼糟糕,你要知道這些糟糕的感覺都是暫時的。我們總是可以痊癒,我們總是可以好起來。我保證。
在臺灣,如果你想要找如何獲得幫助或是幫助某個人的更多資訊,可以打直撥「113」專線,這是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二十四小時保護專線。以下的網址也可以找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聯絡資訊:https://dep.mohw.gov.tw/DOPS/cp-1204-6634-105.html。
最後,如果你曾想過要傷害自己,拜託,千萬不要。很多地方能幫助你。你隨時可以免費直撥「1925」 (依舊愛我),這是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安心專線。除了各縣市社區心理諮商服務: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558-69568-107.html,這個網頁也列出包括「生命線」、「張老師」等許多全國諮詢和救援服務專線: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327-8715-107.html。
最後的最後,當一隻狼。照顧自己的狼群。然後戰鬥。
如果你想深入思考本書所涵蓋的主題,以下是一些你可以和朋友一起討論的問題。
1. 為什麼阿真說阿思的超能力是讓自己隱形?阿思隱形有什麼好處?如果人們真的看到她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2. 阿真周遭的人真的看到她了嗎?她沒有隱形,但是她擅長戴上面具,躲在後面。這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會如何幫助或傷害她?
3. 戴奉老師對阿真有什麼看法?校長(潘妮博士)呢?蘭欣呢?哪個人看到了最真實的阿真?
4. 阿真如何學會展現自己?是什麼幫助她找到自己的話語?是什麼幫助她持續戰鬥?
5. 阿真對阿思的愛如何讓故事出現轉折?阿思對阿真的愛又如何讓故事發生變化?愛我們的人如何讓我們變得誠實和堅強?
6. 書中最驚悚的時刻是阿思傷害自己的時候。在她所能做的事情當中,為什麼這是最糟糕的?為什麼阿思不答應阿真她永遠不會再這樣做?她能做出那樣的承諾嗎?
7. 為什麼阿真的故事這麼難以啟齒?是什麼讓她有足夠的勇氣說出來?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1
我剛刺的刺青上面用OK繃遮著,OK繃卻在下課時間脫落了。戴奉老師從我旁邊經過,那時我正把厚外套掛在我們四年級教室的掛勾上,她倒抽了一口氣。
她說:「阿真,那是刺青嗎?」
我舉起手腕給她看。「這個圖案是個符號。」
「我知道,」戴奉老師說:「那是真的嗎?」
真到不能再真了,現在還會痛,而且旁邊的皮膚還紅紅腫腫的。「是。」我說。
她搖搖頭,嘴裡唸唸有詞。我不是她偏愛的學生。我可能是她最不偏愛的學生。
我不在乎。我愛、愛、愛死了我的符號刺青。
我今年十歲。我會把全部的故事告訴你們,有些部分很難說,所以會留到晚一點再說,先從輕鬆的說起。
我姓羅柏,中間名是堂天,名字是真鮮甜,我叫真鮮甜.堂天.羅柏。對,我知道,既然有這種名字,為什麼不乾脆用中間名就好?我從來沒告訴過任何人我的名字是真鮮甜,可是它就寫在我的學生紀錄卡上,通常在上學的第一天,老師都會想也不想就唸出來。
最近我經歷了很多上學第一天。
如果可以趕在老師大聲說出真鮮甜之前先開口,我會說:「大家都叫我阿真。」其實,不管怎樣我都會開口(請叫我阿真,不要叫我真鮮甜,謝謝),但是最好沒有人聽過真鮮甜,這樣我會比較輕鬆。
有一次有個男生舔我,想嚐嚐我是不是真的鮮甜。我就踢了他的――阿思說我不可以寫粗話,除非我不想要別人讀我的故事。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是滿口粗話,只是寫文章的時候不寫而已。總之,我就不偏不倚的踢了他的牛仔褲拉鍊(就這樣描述好了),結果有事的人是我。每次都是女生有事,通常是我。
阿思才不管那些,她說,阿真,你要捍衛自己,不管誰對你機車,都不要忍氣吞聲。
我可以在文章裡面寫機車嗎?
總之,她沒說機車,她說了更髒的詞。
我還是重寫吧,阿思說如果我想說髒話,可以說雪,或雪花,或雪白。
我不偏不倚的踢了他的雪。
不管誰對你機車,都不要忍氣吞聲。
嗯,這一招有用。
好,回到我的部分。真鮮甜.堂天.羅柏。堂天當然是天堂倒著寫,通常我班上至少有一個女生叫堂天,我們這裡真的很多人取這個名字,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覺得聽起來很蠢。把天堂倒過來寫?我媽媽到底在想什麼?
說不定她什麼都沒想。事實就是如此。我媽媽現在關在監獄裡。她被宣告停止親權了,這是最近才發生的,以前都沒人想管這件事,不過等到她出獄時,我都大到可以投票的年紀了。
我對她沒有印象,只記得一個很小的片段,像是電影場景一樣。阿思說她當媽媽的能力跟倉鼠差不多,倉鼠有時會吃掉自己的寶寶。照顧我的人一向是阿思,現在也幾乎是。
阿思是我姊,她十六歲。
我現在寫的還是比較輕鬆的部分,看你相不相信吧。
阿思的全名是阿思.格蕾絲.羅柏。阿思不是暱稱,她沒有更正式的名字,雖然聽起來應該有。至於羅柏――羅柏是媽媽的姓,我們不知道爸爸是誰,只知道我和阿思大概不同爸爸,而且兩個爸爸都不是克利頓,真是感謝上帝。阿思發誓真的不是,我相信她。
寫故事時可以寫到上帝的名諱嗎?但我剛才不是隨口亂喊上帝,我是真的感謝祂,不論天上的神是哪一位,謝謝祂沒讓克利頓當我的親生爸爸。
阿思以前有一張媽媽的照片,是她受審時拍的。她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長著幾顆爛瘡,吸冰毒吸出滿嘴黑牙,淺白色長直髮油膩膩的;阿思說她的頭髮漂白過,不過那又怎樣,反正看得出來沒有質感,像細繩一樣垂著。阿思的頭髮又軟又亮,沒染黑時是深棕色,是媽媽頭髮的升級版,而且她的眼睛也像媽媽。我的頭髮有彈性,老是纏在一起。我的眼睛顏色比阿思和媽媽的淺。
阿思的膚色像脫脂牛奶的白,非常淺,肚皮白得幾乎發青。她出門一碰到陽光就晒成鮮紅色。我的膚色比較偏棕色,而且從來不需要擦防晒乳。總之,雖然我跟阿思對爸爸一無所知,但我們猜想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這樣很好,對吧?因為如果同一個男的待了那麼久都沒走,能生得出我和阿思,那麼他就應該一直留下來,幫我們解決那一堆麻煩,除非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雪人。阿思認為(我也認為),媽媽大概從來沒告訴過我爸爸或她爸爸有了小孩的事,所以我們也不能怪他們沒有留在我們身邊。說不定他們是好男人,各方面都很棒,除了跟我們的媽媽來往之外。我媽一直是個闖禍精。
我和阿思早就放棄媽媽了,不放棄不行。不只是因為她被關,還有因為她一進監獄就得了所謂的精神分裂,是冰毒害的;她瘋得很嚴重,而且是永久的。甚至就算我們走進媽媽的牢房,她也不可能認得出我們。但我們也去不了就是了,她被關在堪薩斯州,我們現在沒有錢、沒有車。她不會寫信或打電話給我們,因為她不能寫也不能打,她也講不出什麼有條理的話。再說,她也絕對不會有這個念頭,她已經徹底忘記我們了。我覺得她很可憐,真的可憐,但我改變不了什麼。
我這個人口無遮攔。這是好事,非常好,我說件事,你就知道為什麼了。上個星期在學校(是我帶著新刺青上學的前一、兩天),戴奉老師叫我們畫家譜,她先示範給我們看:畫出像樹枝的線條,母親、父親、祖父母、阿姨、姑姑、叔叔、伯伯、堂表兄弟姊妹。
我的家譜一定是畫到媽媽就沒了,鐵牢裡的媽媽,旁邊突出一枝阿思。我才不要畫那種圖,更何況我懷疑戴奉老師已經打算好了,要把大家的作品貼在教室外面的布告欄給全校看。
戴奉老師就是不懂。不知道她怎會到現在還這樣,我還以為她已經開始懂一些了。
我沒畫家譜,但畫了一匹母狼。我愈來愈會畫狼了,我把牠的眼睛畫得黑黑、柔柔的,嘴巴張大,露出尖牙。我向堂天借了銀色的筆來畫狼毛。
戴奉老師經過我旁邊時說:「阿真,你在做什麼?我出的題目不是這個。」
我說:「這匹狼就是我的家譜。」我對她擺臭臉。戴奉老師不知道我所有的事,但她知道的也不少,更何況最近發生了那麼多事。如果她停下來想一想,就算只想一下也好,我敢說她可能就猜得到我為什麼不想畫家譜。她沒有,她抿了抿嘴,然後說:「我叫你做我出的題目。」
我說:「你的題目是雪。」
我說了雪,於是給自己找了麻煩。
我早就知道會有麻煩,所以我才說的。我被罰去校長室報到。我和校長現在算是朋友了,校長是潘妮博士(潘妮是她的姓,我問過了。)
潘妮博士說:「阿真,這次又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我才不要畫那個題目。我畫不出我的家譜,而且我的家族又不關別人的事。」我說。
「哦。」潘妮博士這樣說。接著她問我畫了什麼來代替,然後同意畫一匹狼看來是合理的折衷方案。她說她會和戴奉老師談一談。
我說:「露易莎也不想畫她的家譜,堂天也是。」堂天的爸爸幾年前離家出走了;至於露易莎,我不知道她的故事,但老師宣布要我們做什麼時,我看到她的眼神變得空洞。「戴奉老師還是沒聽進去,除非等到哪一天她不得不聽。」
潘妮博士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她在對誰歎氣。她說:「阿真,我會找她談。」
我說:「她應該要更細心觀察才對。」我才十歲,就注意到露易莎的眼神和堂天縮起肩膀的模樣,戴奉老師是老師吔。
蘭欣說,你可以信任某些人,不能信任所有的人。我想我永遠不會信任戴奉老師。
潘妮博士說:「阿真,如果你戒掉雪這一類的用詞,對你也許會有幫助。」
我說;「大概不會。」我不是故意頂嘴,又說:「我說了雪,結果我來了這裡,把事情解釋給你聽。如果我沒說雪,我就得說出不想畫家譜的原因,全班都會聽到我的事,然後我在遊戲場就會被大家捉弄。」
潘妮博士猶豫了。她看著我,我感覺看了很久,然後她才說:「謝謝你解釋給我聽。」她建議我在她辦公室那張舒服的椅子上待到下課,她有一櫃的書讓我看。我不怎麼喜歡看書,不過那裡有一本講恐龍便便的書很有趣。
不知道潘妮博士對戴奉老師說了什麼,但我不用畫家譜了,戴奉老師也沒有貼任何一張家譜在走廊上。
看吧,大嘴巴有用。下一次我打算把大嘴巴的功力用在把克利頓送進牢裡,而且關上很久、很久。
我現在說的,還是故事比較輕鬆的部分。
2
我和阿思跟蘭欣一起住,她是我們的寄養媽媽。他們一向用這個詞,寄養媽媽,可是蘭欣沒有一點慈母的樣子。她甚至沒有冰毒可以當藉口。
「歡迎你們。」社工第一次帶我們去她家時,她這樣說。那是一、兩個月前,八月下旬的事了,當時天氣還很熱,距離我們離開克利頓家一個星期。感覺像一年前的事,一輩子以前。但其實沒有。
蘭欣的房子是雙拼住宅的其中一半,可以這樣說吧。有個迷你庭院和狹窄的客廳,裡面不髒亂,味道也還可以。「這間是你們的房間。」蘭欣說:「阿真,我通常不接像你這麼小的女孩,但你們兩個是姊妹這一點我喜歡,可能不會那麼常吵架。」
那時我和阿思從來沒吵過架。
臥室很不錯,上下鋪都鋪好了床單、枕頭和毯子,一人一個木頭抽屜櫃。
「呵,」阿思說:「沒多少空間。」她拿走我手上的超市塑膠袋,扔進第一個抽屜櫃最上層,把自己的塑膠袋扔進第二個的最上層。
我們所有的家當就是這些。我們離開克利頓家時很匆忙。
我們在逃命。
「比提供緊急安置的那個巫婆好。」我說的是頭幾天收留我們的那個女人。蘭欣家的房間比那個巫婆家的小,可是感覺比較親切,人也是。
阿思嗤之以鼻。「話先別說得太早。」
我們回到客廳時,蘭欣說:「他們沒讓你們回去拿衣服嗎?課本、玩具之類的?」
「克利頓把我們的東西燒掉了,」阿思說:「警察說的。」
我們從婷亞姊姊家看到了煙。克利頓把我們所有的東西丟進後院的枯枝葉堆,潑上汽油,再點燃火柴。警察說克利頓想銷毀我們跟他一起住的證據。
蘭欣轉身向還在翻文件的社工說:「她們有服裝零用金嗎?」
社工查了查筆記,說我們有。
於是,社工一離開,蘭欣就把我們塞進她的老破車裡,載我們去Old Navy門市。衣服隨便我挑,有兩百美金的額度可以買。阿思有兩百五十元,因為她年紀比較大。
「別忘了買內衣褲,」蘭欣在路上說:「襪子、睡衣之類的,因為等到你們的寄養費入帳之前,我不會再幫你們買任何東西喔。」她停頓了一下,又說:「你們需要學校用品嗎?書包、筆記本、鉛筆?」
我快速搖頭。我才不要把自己的兩百元用在那上面。
阿思說:「克利頓毀了我的筆電。那是學校借給我在這個學年用的。」
蘭欣歎了一口氣。「這我得想辦法解決。」她說:「明天早上我把阿真安頓好之後,會去你的高中一趟。我在監理所上班,幸好監理所十點才開門。阿思,你有駕照嗎?」
阿思點點頭。她在學校上過駕駛課,通過了考試。她的手指沿著副駕駛座的窗戶劃。「留在克利頓家了。」她說。
「我可以幫你申請補發,」蘭欣說:「這我們也會解決。你開我的車之前一定要先買保險,你是優良駕駛嗎?」
阿思說:「目前為止還是。」
一夕之間失去所有家當的感覺真奇怪,一方面,我很高興能得到全新的東西,而且還是Old Navy品牌,那麼時髦的店。我大多數的衣服都來自愛心舊衣中心,有時婷亞姊姊會把她不要的給我,但她自己的衣服通常也是從愛心舊衣中心拿來的,所以其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不過我本來有一件真的很喜歡的紫色套頭衫,還有一、兩件還不錯的T恤。
我伸手到前座抓住阿思的手臂。「嘿,」我說:「上學第一天,我從頭到腳穿的都會是新的吔。」一定很棒,好像我是那種有正常媽媽的孩子,媽媽有工作之類的。
我要去新學校,不是我去了一輩子的那一所,也不是這幾天去的緊急安置學校。全新的,從頭來過。
「很好啊。」阿思的語氣聽起來不是真心誠意。她也會穿新衣服,但去的是老地方。我們鎮上有好幾所小學,但只有一所國中、一所高中。
我們走進Old Navy,各自抓了一部推車。阿思陪我走到女童區。「先買內褲。」她說。她拿出一包七件裝的低腰內褲,看了看尺寸,然後丟進我的推車。
「喂!」我說:「讓我自己選!」她拿了白色,我想要彩色的。
「好,」阿思說:「你拿自己要的。一套睡衣、兩條牛仔褲,至少三件上衣。要試穿,不要太合身,你還會繼續長大。」
我試穿了牛仔褲,找到幾條喜歡的。全新的。我從特價區拿了幾件T恤。兩百元是一大筆錢,可是Old Navy很貴。接著我看見一件桃紅色連帽T,上面有紫色亮片的OLD NAVY字樣。這件衣服沒有特價,而且八月的天氣也還用不著穿連帽T,可是我一年到頭都愛穿,讓那些布料圍著脖子,只要把帽子戴起來,別人就看不見我,我卻可以看見別人。更何況我有兩百元哩。我把連帽T丟進推車裡。
我沿著鞋子展售架一雙一雙挑。我討厭腳上這雙鞋,但是Old Navy的鞋子不多。我找到一雙合腳的果凍鞋,只要六塊錢,最起碼從來沒有人穿過。
「阿真!」我聽到阿思從店的另一頭叫我,「過來這邊,快點!」
我匆匆忙忙過去,阿思站在店中央,旁邊有張堆滿鞋的檯子。
不是隨便的鞋,是紫色絨布高筒運動鞋。
紫色。
絨布。
高筒運動鞋。
「噢。」我說。我從來沒看過這麼想擁有的鞋。
「買。」阿思說。她咧著嘴笑開了。
「你也買。」我說。
「免了,」她對我搖搖手,笑著說:「看看你的推車和我的差了多少。」
她的推車裡有牛仔褲、黑色內褲、黑色襪子、黑色T恤和運動內衣。還有黑色眼線和睫毛膏。如果有黑色口紅,阿思一定也會買。她喜歡黑色。我可不喜歡。
紫色絨布高筒鞋要三十元,比亮片連帽T還貴。我把鞋放在推車的最上層,還摸了摸它們。只摸一次而已。我,明天,第一天上學:新牛仔褲、亮片連帽T、紫色絨布高筒鞋。我這輩子第一次,即將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算過總金額了,知道錢夠用;可是我忘了還有營業稅,田納西州的營業稅很高。結果我這一車東西要兩百二十一元。
我想過把襪子放回去,還有那幾件便宜的T恤,但是扣掉的錢沒多少。
我可以買果凍鞋。
阿思把高筒鞋從收銀臺拿走,放進她自己的推車裡。「我來買。」她說。
「真的嗎?」
她把一件運動內衣放回去,還有一件上衣。「你有洗衣機嗎?」她問蘭欣。
蘭欣點頭。
阿思說:「那我就沒問題了。」她伸出一隻手摟著我,「我得照顧我妹妹呀,反正哪有人兩件內衣還不夠穿的?」
我永遠都有阿思當靠山。阿思什麼事情都能解決。
我在店裡就把絨布高筒鞋穿到腳上。本來要把我的臭鞋丟進垃圾筒的,阿思卻叫我留著,你永遠不知道哪天會需要一雙備用的鞋。我們回到蘭欣家,蘭欣訂了披薩當晚餐。外送到家。義式臘腸和香腸都加。她幫我們各開一罐汽水,阿思幫我們的每一件新衣服剪吊牌,我坐在那裡盯著蘭欣看。
她真的是我見過最醜的女人之一。她長得像五官全部混在一起、下巴肉一坨又一坨的那種小狗。而且她臉上還有圓圓的小腫塊凸起來。不是青春痘喔,是青春痘大小的東西,好像下面連著莖一樣,直接從皮膚表面長出來,整張臉都是,還有脖子。我開始數,數到第三十六個時,她瞪了我一眼。
「不要看了。」她說:「這個叫贅瘤,不是癌,不會傳染,扯了會痛。」
我說:「如果它們孵化呢?」
她說:「如果它們孵化了,就會變成小怪物,趁你睡覺時攻擊你,讓你癢到海枯石爛。所以你最好希望它們不會孵化。」
披薩送來之後,蘭欣把披薩啪一聲扔在桌上,然後分了紙盤給我們。「我收寄養兒童是為了錢。」她說。
我不介意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先弄清楚我們的處境很好。
「我只收女孩。」她說:「大部分年紀都夠大了,生活可以自理。可以的話一次兩個人。」她在她的盤子邊緣按熄香菸,「我以前有個室友,不過那個經驗很雪,要應付那種該分攤的錢從來都湊不出來的人。我就想,給我由政府負責付錢的室友吧,那樣我就輕鬆多了。結果通常是這樣沒錯。」她又點了一根菸,「你們要打官司?提告?」
阿思點點頭。她靠過去,不聲不響的從蘭欣那包菸中抽了一根出來。蘭欣啪一聲打了她的手。「不行,」她說:「你未成年。我不會助長青少年犯罪。還有,相信我,你會寧可從來沒起過頭。我就是。好了,衣服已經有了,學校筆電的事我們也會處理,現在你們還需要什麼?」
「手機。」阿思說。克利頓把她的砸爛了。而且那一支還滿新的,手機錢克利頓都還沒付完。
蘭欣搖搖頭。「不關我的事。你想要,就去打工。」
「阿真才十歲,」阿思說:「她不能打工。」
蘭欣聳聳肩。「她才十歲,不需要手機。你也不需要。我家客廳有市內電話,用那個打。」
「你在開玩笑嗎?」阿思一臉惱怒。
我說:「阿思需要手機,我們真的需要一支。」
蘭欣和阿思看著我,蘭欣說:「不要擔心,你在這裡很安全。」
阿思笑出聲音。「嗯,最好是。」
我們把紙盤丟進垃圾筒,還有披薩盒。晚餐就這樣結束。蘭欣打開電視,窩進躺椅裡。我和阿思坐到沙發上。
「你今天有沒有遇到婷亞姊姊?」我問阿思。
她哼了一聲。「沒。不要問了。」
「你一定會遇到,」我說:「除非她生病。」婷亞姊姊和阿思同年級。
「沒有。」阿思說。
婷亞姊姊的媽媽堅持打電話跟警察說我們的事。我並不想領情,但至少人家報了警。「婷亞姊姊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向蘭欣說明:「她……就像我的另一個姊姊。」我轉向阿思,「那不是她的錯。」
阿思一下子站起來。「該睡了。」
「阿思,」我說:「現在才――」
她抓住我的手臂。「睡覺。」
「你們房裡有一個鬧鐘。」蘭欣說:「你們幾點起床才來得及上學,自己看著辦。阿真,明天我會載你去學校,之後你就要自己搭校車。」
我穿上全新的睡衣。我從沒擁有過新的睡衣,這一套摸起來皺皺的。「去刷牙。」阿思說。
我對她翻白眼。我一向都會刷牙。
她說:「把你那些打結的頭髮梳開。」
我說:「你不是我的老大。」這句話是我們姊妹之間的玩笑話,她當然是我的老大。
我走出浴室,牙齒也刷了,頭髮能梳開的我也盡力梳了,阿思已經蓋好毯子躺在上鋪。我爬上去,窩到她身邊說:「現在睡覺實在太早了。」
「對你又沒壞處。」阿思說。她伸出右手,張開五指,我伸出我的左手小妞妞抵住她的大拇哥,再來換成我的大拇哥抵住她的小妞妞。我們的兩隻手一起一步一步走向空中,小妞妞對大拇哥、小妞妞對大拇哥,愈爬愈高,爬到上不去了為止。以前阿思教我邊做邊唱〈小小蜘蛛爬水管〉,但我們很早以前就省略了唱歌的部分。等到我的手伸到極限之後,我們就會再一步一步爬下來。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阿思唱著:「我愛你。」
我跟著唱。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
我愛你。
早上的時候我愛你,下午也一樣。晚上的時候我愛你,天上有月亮。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
我愛你。
婷亞姊姊的媽媽以前那輛車子裡有個東西叫做錄音機,把小小的塑膠卡帶(這個東西叫做錄音帶)塞進裡面,就可以播音樂。婷亞姊姊的媽媽不知道從哪裡拿到一捲錄音帶,裡面都是這種呆呆傻傻的兒歌,而且因為她只有這一捲錄音帶,所以隨時隨地都在播。婷亞姊姊的媽媽不常開車載我們,即使如此,在那輛車再也跑不動之前,我們還是把每一首歌都背起來了,阿思、婷亞姊姊,還有我。在我的記憶中,阿思幾乎都唱〈嘶奇哪嘛淋嘰〉當我的搖籃曲。
現在外面天還沒暗,但是阿思已經拉上窗帘,房間裡都是暗影。我把頭窩在姊姊的肩膀上。這張床我不習慣,新睡衣穿起來刺刺的,但阿思是一直沒變的阿思。
在蘭欣家的第一夜,我們手牽著手睡著了。
(摘錄自《天堂倒著寫》)
1
我剛刺的刺青上面用OK繃遮著,OK繃卻在下課時間脫落了。戴奉老師從我旁邊經過,那時我正把厚外套掛在我們四年級教室的掛勾上,她倒抽了一口氣。
她說:「阿真,那是刺青嗎?」
我舉起手腕給她看。「這個圖案是個符號。」
「我知道,」戴奉老師說:「那是真的嗎?」
真到不能再真了,現在還會痛,而且旁邊的皮膚還紅紅腫腫的。「是。」我說。
她搖搖頭,嘴裡唸唸有詞。我不是她偏愛的學生。我可能是她最不偏愛的學生。
我不在乎。我愛、愛、愛死了我的符號刺青。
我今年十歲。我會把全部的故事告訴你們,有些部分很難說,所以會留到晚一點再說,先從輕鬆的說起。
我姓羅柏,中間名是堂天,名字是真鮮甜,我叫真鮮甜.堂天.羅柏。對,我知道,既然有這種名字,為什麼不乾脆用中間名就好?我從來沒告訴過任何人我的名字是真鮮甜,可是它就寫在我的學生紀錄卡上,通常在上學的第一天,老師都會想也不想就唸出來。
最近我經歷了很多上學第一天。
如果可以趕在老師大聲說出真鮮甜之前先開口,我會說:「大家都叫我阿真。」其實,不管怎樣我都會開口(請叫我阿真,不要叫我真鮮甜,謝謝),但是最好沒有人聽過真鮮甜,這樣我會比較輕鬆。
有一次有個男生舔我,想嚐嚐我是不是真的鮮甜。我就踢了他的――阿思說我不可以寫粗話,除非我不想要別人讀我的故事。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是滿口粗話,只是寫文章的時候不寫而已。總之,我就不偏不倚的踢了他的牛仔褲拉鍊(就這樣描述好了),結果有事的人是我。每次都是女生有事,通常是我。
阿思才不管那些,她說,阿真,你要捍衛自己,不管誰對你機車,都不要忍氣吞聲。
我可以在文章裡面寫機車嗎?
總之,她沒說機車,她說了更髒的詞。
我還是重寫吧,阿思說如果我想說髒話,可以說雪,或雪花,或雪白。
我不偏不倚的踢了他的雪。
不管誰對你機車,都不要忍氣吞聲。
嗯,這一招有用。
好,回到我的部分。真鮮甜.堂天.羅柏。堂天當然是天堂倒著寫,通常我班上至少有一個女生叫堂天,我們這裡真的很多人取這個名字,不知道為什麼,但我覺得聽起來很蠢。把天堂倒過來寫?我媽媽到底在想什麼?
說不定她什麼都沒想。事實就是如此。我媽媽現在關在監獄裡。她被宣告停止親權了,這是最近才發生的,以前都沒人想管這件事,不過等到她出獄時,我都大到可以投票的年紀了。
我對她沒有印象,只記得一個很小的片段,像是電影場景一樣。阿思說她當媽媽的能力跟倉鼠差不多,倉鼠有時會吃掉自己的寶寶。照顧我的人一向是阿思,現在也幾乎是。
阿思是我姊,她十六歲。
我現在寫的還是比較輕鬆的部分,看你相不相信吧。
阿思的全名是阿思.格蕾絲.羅柏。阿思不是暱稱,她沒有更正式的名字,雖然聽起來應該有。至於羅柏――羅柏是媽媽的姓,我們不知道爸爸是誰,只知道我和阿思大概不同爸爸,而且兩個爸爸都不是克利頓,真是感謝上帝。阿思發誓真的不是,我相信她。
寫故事時可以寫到上帝的名諱嗎?但我剛才不是隨口亂喊上帝,我是真的感謝祂,不論天上的神是哪一位,謝謝祂沒讓克利頓當我的親生爸爸。
阿思以前有一張媽媽的照片,是她受審時拍的。她蒼白的臉上毫無血色,長著幾顆爛瘡,吸冰毒吸出滿嘴黑牙,淺白色長直髮油膩膩的;阿思說她的頭髮漂白過,不過那又怎樣,反正看得出來沒有質感,像細繩一樣垂著。阿思的頭髮又軟又亮,沒染黑時是深棕色,是媽媽頭髮的升級版,而且她的眼睛也像媽媽。我的頭髮有彈性,老是纏在一起。我的眼睛顏色比阿思和媽媽的淺。
阿思的膚色像脫脂牛奶的白,非常淺,肚皮白得幾乎發青。她出門一碰到陽光就晒成鮮紅色。我的膚色比較偏棕色,而且從來不需要擦防晒乳。總之,雖然我跟阿思對爸爸一無所知,但我們猜想應該不是同一個人。
這樣很好,對吧?因為如果同一個男的待了那麼久都沒走,能生得出我和阿思,那麼他就應該一直留下來,幫我們解決那一堆麻煩,除非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雪人。阿思認為(我也認為),媽媽大概從來沒告訴過我爸爸或她爸爸有了小孩的事,所以我們也不能怪他們沒有留在我們身邊。說不定他們是好男人,各方面都很棒,除了跟我們的媽媽來往之外。我媽一直是個闖禍精。
我和阿思早就放棄媽媽了,不放棄不行。不只是因為她被關,還有因為她一進監獄就得了所謂的精神分裂,是冰毒害的;她瘋得很嚴重,而且是永久的。甚至就算我們走進媽媽的牢房,她也不可能認得出我們。但我們也去不了就是了,她被關在堪薩斯州,我們現在沒有錢、沒有車。她不會寫信或打電話給我們,因為她不能寫也不能打,她也講不出什麼有條理的話。再說,她也絕對不會有這個念頭,她已經徹底忘記我們了。我覺得她很可憐,真的可憐,但我改變不了什麼。
我這個人口無遮攔。這是好事,非常好,我說件事,你就知道為什麼了。上個星期在學校(是我帶著新刺青上學的前一、兩天),戴奉老師叫我們畫家譜,她先示範給我們看:畫出像樹枝的線條,母親、父親、祖父母、阿姨、姑姑、叔叔、伯伯、堂表兄弟姊妹。
我的家譜一定是畫到媽媽就沒了,鐵牢裡的媽媽,旁邊突出一枝阿思。我才不要畫那種圖,更何況我懷疑戴奉老師已經打算好了,要把大家的作品貼在教室外面的布告欄給全校看。
戴奉老師就是不懂。不知道她怎會到現在還這樣,我還以為她已經開始懂一些了。
我沒畫家譜,但畫了一匹母狼。我愈來愈會畫狼了,我把牠的眼睛畫得黑黑、柔柔的,嘴巴張大,露出尖牙。我向堂天借了銀色的筆來畫狼毛。
戴奉老師經過我旁邊時說:「阿真,你在做什麼?我出的題目不是這個。」
我說:「這匹狼就是我的家譜。」我對她擺臭臉。戴奉老師不知道我所有的事,但她知道的也不少,更何況最近發生了那麼多事。如果她停下來想一想,就算只想一下也好,我敢說她可能就猜得到我為什麼不想畫家譜。她沒有,她抿了抿嘴,然後說:「我叫你做我出的題目。」
我說:「你的題目是雪。」
我說了雪,於是給自己找了麻煩。
我早就知道會有麻煩,所以我才說的。我被罰去校長室報到。我和校長現在算是朋友了,校長是潘妮博士(潘妮是她的姓,我問過了。)
潘妮博士說:「阿真,這次又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我才不要畫那個題目。我畫不出我的家譜,而且我的家族又不關別人的事。」我說。
「哦。」潘妮博士這樣說。接著她問我畫了什麼來代替,然後同意畫一匹狼看來是合理的折衷方案。她說她會和戴奉老師談一談。
我說:「露易莎也不想畫她的家譜,堂天也是。」堂天的爸爸幾年前離家出走了;至於露易莎,我不知道她的故事,但老師宣布要我們做什麼時,我看到她的眼神變得空洞。「戴奉老師還是沒聽進去,除非等到哪一天她不得不聽。」
潘妮博士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她在對誰歎氣。她說:「阿真,我會找她談。」
我說:「她應該要更細心觀察才對。」我才十歲,就注意到露易莎的眼神和堂天縮起肩膀的模樣,戴奉老師是老師吔。
蘭欣說,你可以信任某些人,不能信任所有的人。我想我永遠不會信任戴奉老師。
潘妮博士說:「阿真,如果你戒掉雪這一類的用詞,對你也許會有幫助。」
我說;「大概不會。」我不是故意頂嘴,又說:「我說了雪,結果我來了這裡,把事情解釋給你聽。如果我沒說雪,我就得說出不想畫家譜的原因,全班都會聽到我的事,然後我在遊戲場就會被大家捉弄。」
潘妮博士猶豫了。她看著我,我感覺看了很久,然後她才說:「謝謝你解釋給我聽。」她建議我在她辦公室那張舒服的椅子上待到下課,她有一櫃的書讓我看。我不怎麼喜歡看書,不過那裡有一本講恐龍便便的書很有趣。
不知道潘妮博士對戴奉老師說了什麼,但我不用畫家譜了,戴奉老師也沒有貼任何一張家譜在走廊上。
看吧,大嘴巴有用。下一次我打算把大嘴巴的功力用在把克利頓送進牢裡,而且關上很久、很久。
我現在說的,還是故事比較輕鬆的部分。
2
我和阿思跟蘭欣一起住,她是我們的寄養媽媽。他們一向用這個詞,寄養媽媽,可是蘭欣沒有一點慈母的樣子。她甚至沒有冰毒可以當藉口。
「歡迎你們。」社工第一次帶我們去她家時,她這樣說。那是一、兩個月前,八月下旬的事了,當時天氣還很熱,距離我們離開克利頓家一個星期。感覺像一年前的事,一輩子以前。但其實沒有。
蘭欣的房子是雙拼住宅的其中一半,可以這樣說吧。有個迷你庭院和狹窄的客廳,裡面不髒亂,味道也還可以。「這間是你們的房間。」蘭欣說:「阿真,我通常不接像你這麼小的女孩,但你們兩個是姊妹這一點我喜歡,可能不會那麼常吵架。」
那時我和阿思從來沒吵過架。
臥室很不錯,上下鋪都鋪好了床單、枕頭和毯子,一人一個木頭抽屜櫃。
「呵,」阿思說:「沒多少空間。」她拿走我手上的超市塑膠袋,扔進第一個抽屜櫃最上層,把自己的塑膠袋扔進第二個的最上層。
我們所有的家當就是這些。我們離開克利頓家時很匆忙。
我們在逃命。
「比提供緊急安置的那個巫婆好。」我說的是頭幾天收留我們的那個女人。蘭欣家的房間比那個巫婆家的小,可是感覺比較親切,人也是。
阿思嗤之以鼻。「話先別說得太早。」
我們回到客廳時,蘭欣說:「他們沒讓你們回去拿衣服嗎?課本、玩具之類的?」
「克利頓把我們的東西燒掉了,」阿思說:「警察說的。」
我們從婷亞姊姊家看到了煙。克利頓把我們所有的東西丟進後院的枯枝葉堆,潑上汽油,再點燃火柴。警察說克利頓想銷毀我們跟他一起住的證據。
蘭欣轉身向還在翻文件的社工說:「她們有服裝零用金嗎?」
社工查了查筆記,說我們有。
於是,社工一離開,蘭欣就把我們塞進她的老破車裡,載我們去Old Navy門市。衣服隨便我挑,有兩百美金的額度可以買。阿思有兩百五十元,因為她年紀比較大。
「別忘了買內衣褲,」蘭欣在路上說:「襪子、睡衣之類的,因為等到你們的寄養費入帳之前,我不會再幫你們買任何東西喔。」她停頓了一下,又說:「你們需要學校用品嗎?書包、筆記本、鉛筆?」
我快速搖頭。我才不要把自己的兩百元用在那上面。
阿思說:「克利頓毀了我的筆電。那是學校借給我在這個學年用的。」
蘭欣歎了一口氣。「這我得想辦法解決。」她說:「明天早上我把阿真安頓好之後,會去你的高中一趟。我在監理所上班,幸好監理所十點才開門。阿思,你有駕照嗎?」
阿思點點頭。她在學校上過駕駛課,通過了考試。她的手指沿著副駕駛座的窗戶劃。「留在克利頓家了。」她說。
「我可以幫你申請補發,」蘭欣說:「這我們也會解決。你開我的車之前一定要先買保險,你是優良駕駛嗎?」
阿思說:「目前為止還是。」
一夕之間失去所有家當的感覺真奇怪,一方面,我很高興能得到全新的東西,而且還是Old Navy品牌,那麼時髦的店。我大多數的衣服都來自愛心舊衣中心,有時婷亞姊姊會把她不要的給我,但她自己的衣服通常也是從愛心舊衣中心拿來的,所以其實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不過我本來有一件真的很喜歡的紫色套頭衫,還有一、兩件還不錯的T恤。
我伸手到前座抓住阿思的手臂。「嘿,」我說:「上學第一天,我從頭到腳穿的都會是新的吔。」一定很棒,好像我是那種有正常媽媽的孩子,媽媽有工作之類的。
我要去新學校,不是我去了一輩子的那一所,也不是這幾天去的緊急安置學校。全新的,從頭來過。
「很好啊。」阿思的語氣聽起來不是真心誠意。她也會穿新衣服,但去的是老地方。我們鎮上有好幾所小學,但只有一所國中、一所高中。
我們走進Old Navy,各自抓了一部推車。阿思陪我走到女童區。「先買內褲。」她說。她拿出一包七件裝的低腰內褲,看了看尺寸,然後丟進我的推車。
「喂!」我說:「讓我自己選!」她拿了白色,我想要彩色的。
「好,」阿思說:「你拿自己要的。一套睡衣、兩條牛仔褲,至少三件上衣。要試穿,不要太合身,你還會繼續長大。」
我試穿了牛仔褲,找到幾條喜歡的。全新的。我從特價區拿了幾件T恤。兩百元是一大筆錢,可是Old Navy很貴。接著我看見一件桃紅色連帽T,上面有紫色亮片的OLD NAVY字樣。這件衣服沒有特價,而且八月的天氣也還用不著穿連帽T,可是我一年到頭都愛穿,讓那些布料圍著脖子,只要把帽子戴起來,別人就看不見我,我卻可以看見別人。更何況我有兩百元哩。我把連帽T丟進推車裡。
我沿著鞋子展售架一雙一雙挑。我討厭腳上這雙鞋,但是Old Navy的鞋子不多。我找到一雙合腳的果凍鞋,只要六塊錢,最起碼從來沒有人穿過。
「阿真!」我聽到阿思從店的另一頭叫我,「過來這邊,快點!」
我匆匆忙忙過去,阿思站在店中央,旁邊有張堆滿鞋的檯子。
不是隨便的鞋,是紫色絨布高筒運動鞋。
紫色。
絨布。
高筒運動鞋。
「噢。」我說。我從來沒看過這麼想擁有的鞋。
「買。」阿思說。她咧著嘴笑開了。
「你也買。」我說。
「免了,」她對我搖搖手,笑著說:「看看你的推車和我的差了多少。」
她的推車裡有牛仔褲、黑色內褲、黑色襪子、黑色T恤和運動內衣。還有黑色眼線和睫毛膏。如果有黑色口紅,阿思一定也會買。她喜歡黑色。我可不喜歡。
紫色絨布高筒鞋要三十元,比亮片連帽T還貴。我把鞋放在推車的最上層,還摸了摸它們。只摸一次而已。我,明天,第一天上學:新牛仔褲、亮片連帽T、紫色絨布高筒鞋。我這輩子第一次,即將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算過總金額了,知道錢夠用;可是我忘了還有營業稅,田納西州的營業稅很高。結果我這一車東西要兩百二十一元。
我想過把襪子放回去,還有那幾件便宜的T恤,但是扣掉的錢沒多少。
我可以買果凍鞋。
阿思把高筒鞋從收銀臺拿走,放進她自己的推車裡。「我來買。」她說。
「真的嗎?」
她把一件運動內衣放回去,還有一件上衣。「你有洗衣機嗎?」她問蘭欣。
蘭欣點頭。
阿思說:「那我就沒問題了。」她伸出一隻手摟著我,「我得照顧我妹妹呀,反正哪有人兩件內衣還不夠穿的?」
我永遠都有阿思當靠山。阿思什麼事情都能解決。
我在店裡就把絨布高筒鞋穿到腳上。本來要把我的臭鞋丟進垃圾筒的,阿思卻叫我留著,你永遠不知道哪天會需要一雙備用的鞋。我們回到蘭欣家,蘭欣訂了披薩當晚餐。外送到家。義式臘腸和香腸都加。她幫我們各開一罐汽水,阿思幫我們的每一件新衣服剪吊牌,我坐在那裡盯著蘭欣看。
她真的是我見過最醜的女人之一。她長得像五官全部混在一起、下巴肉一坨又一坨的那種小狗。而且她臉上還有圓圓的小腫塊凸起來。不是青春痘喔,是青春痘大小的東西,好像下面連著莖一樣,直接從皮膚表面長出來,整張臉都是,還有脖子。我開始數,數到第三十六個時,她瞪了我一眼。
「不要看了。」她說:「這個叫贅瘤,不是癌,不會傳染,扯了會痛。」
我說:「如果它們孵化呢?」
她說:「如果它們孵化了,就會變成小怪物,趁你睡覺時攻擊你,讓你癢到海枯石爛。所以你最好希望它們不會孵化。」
披薩送來之後,蘭欣把披薩啪一聲扔在桌上,然後分了紙盤給我們。「我收寄養兒童是為了錢。」她說。
我不介意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先弄清楚我們的處境很好。
「我只收女孩。」她說:「大部分年紀都夠大了,生活可以自理。可以的話一次兩個人。」她在她的盤子邊緣按熄香菸,「我以前有個室友,不過那個經驗很雪,要應付那種該分攤的錢從來都湊不出來的人。我就想,給我由政府負責付錢的室友吧,那樣我就輕鬆多了。結果通常是這樣沒錯。」她又點了一根菸,「你們要打官司?提告?」
阿思點點頭。她靠過去,不聲不響的從蘭欣那包菸中抽了一根出來。蘭欣啪一聲打了她的手。「不行,」她說:「你未成年。我不會助長青少年犯罪。還有,相信我,你會寧可從來沒起過頭。我就是。好了,衣服已經有了,學校筆電的事我們也會處理,現在你們還需要什麼?」
「手機。」阿思說。克利頓把她的砸爛了。而且那一支還滿新的,手機錢克利頓都還沒付完。
蘭欣搖搖頭。「不關我的事。你想要,就去打工。」
「阿真才十歲,」阿思說:「她不能打工。」
蘭欣聳聳肩。「她才十歲,不需要手機。你也不需要。我家客廳有市內電話,用那個打。」
「你在開玩笑嗎?」阿思一臉惱怒。
我說:「阿思需要手機,我們真的需要一支。」
蘭欣和阿思看著我,蘭欣說:「不要擔心,你在這裡很安全。」
阿思笑出聲音。「嗯,最好是。」
我們把紙盤丟進垃圾筒,還有披薩盒。晚餐就這樣結束。蘭欣打開電視,窩進躺椅裡。我和阿思坐到沙發上。
「你今天有沒有遇到婷亞姊姊?」我問阿思。
她哼了一聲。「沒。不要問了。」
「你一定會遇到,」我說:「除非她生病。」婷亞姊姊和阿思同年級。
「沒有。」阿思說。
婷亞姊姊的媽媽堅持打電話跟警察說我們的事。我並不想領情,但至少人家報了警。「婷亞姊姊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我向蘭欣說明:「她……就像我的另一個姊姊。」我轉向阿思,「那不是她的錯。」
阿思一下子站起來。「該睡了。」
「阿思,」我說:「現在才――」
她抓住我的手臂。「睡覺。」
「你們房裡有一個鬧鐘。」蘭欣說:「你們幾點起床才來得及上學,自己看著辦。阿真,明天我會載你去學校,之後你就要自己搭校車。」
我穿上全新的睡衣。我從沒擁有過新的睡衣,這一套摸起來皺皺的。「去刷牙。」阿思說。
我對她翻白眼。我一向都會刷牙。
她說:「把你那些打結的頭髮梳開。」
我說:「你不是我的老大。」這句話是我們姊妹之間的玩笑話,她當然是我的老大。
我走出浴室,牙齒也刷了,頭髮能梳開的我也盡力梳了,阿思已經蓋好毯子躺在上鋪。我爬上去,窩到她身邊說:「現在睡覺實在太早了。」
「對你又沒壞處。」阿思說。她伸出右手,張開五指,我伸出我的左手小妞妞抵住她的大拇哥,再來換成我的大拇哥抵住她的小妞妞。我們的兩隻手一起一步一步走向空中,小妞妞對大拇哥、小妞妞對大拇哥,愈爬愈高,爬到上不去了為止。以前阿思教我邊做邊唱〈小小蜘蛛爬水管〉,但我們很早以前就省略了唱歌的部分。等到我的手伸到極限之後,我們就會再一步一步爬下來。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阿思唱著:「我愛你。」
我跟著唱。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
我愛你。
早上的時候我愛你,下午也一樣。晚上的時候我愛你,天上有月亮。
嘶奇哪―嘛―淋―嘰―叮―嘰―叮,嘶奇哪―嘛―淋―嘰―嘟。
我愛你。
婷亞姊姊的媽媽以前那輛車子裡有個東西叫做錄音機,把小小的塑膠卡帶(這個東西叫做錄音帶)塞進裡面,就可以播音樂。婷亞姊姊的媽媽不知道從哪裡拿到一捲錄音帶,裡面都是這種呆呆傻傻的兒歌,而且因為她只有這一捲錄音帶,所以隨時隨地都在播。婷亞姊姊的媽媽不常開車載我們,即使如此,在那輛車再也跑不動之前,我們還是把每一首歌都背起來了,阿思、婷亞姊姊,還有我。在我的記憶中,阿思幾乎都唱〈嘶奇哪嘛淋嘰〉當我的搖籃曲。
現在外面天還沒暗,但是阿思已經拉上窗帘,房間裡都是暗影。我把頭窩在姊姊的肩膀上。這張床我不習慣,新睡衣穿起來刺刺的,但阿思是一直沒變的阿思。
在蘭欣家的第一夜,我們手牽著手睡著了。
(摘錄自《天堂倒著寫》)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