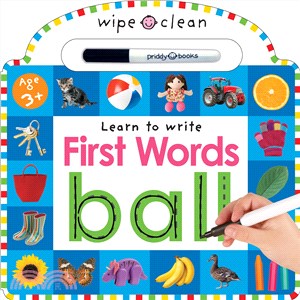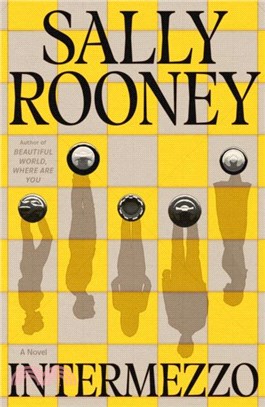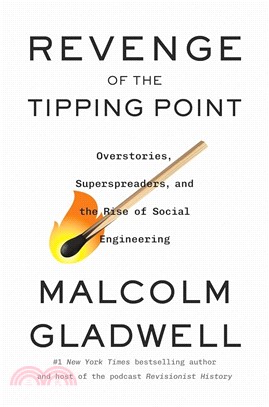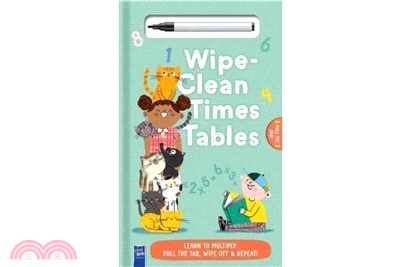革命前的寧靜:激進想法的起源,往往在意料之外
商品資訊
系列名:黑盒子
ISBN13:9786267263006
替代書名:The Quiet Before: On the Unexpected Origins of Radical Ideas
出版社:黑體
作者:蓋爾.貝克曼
譯者:劉議方
出版日:2023/06/07
裝訂/頁數:平裝/368頁
規格:21cm*14.8cm*2.4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臉書和推特又如何限制人們的想像力?
本書帶你穿越時空,回到11個歷史現場
探索種種激進想法,透過不同媒介迸發的時刻。
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革命,究竟是轟轟烈烈的,還是緩慢孕育的?美國資深媒體編輯蓋爾.貝克曼試圖告訴你,推動革命的想法,其實更常是在安靜私密的空間中交流成形的。革命先驅們在狹小隱蔽的角落竊竊私語、構築理想,並慎重討論如何實現他們的目標。而人們為求變革所運用的媒介科技,往往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本書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考察人們如何用各種不同的媒介交流互動、一點一滴地醞釀革命。從17世紀推動科學革命的信件往返,到1830年代的英國工人爭取投票權的請願書,再到百年後非洲的黃金海岸反抗殖民者的報紙,1990年代讓女性發出憤怒之聲的小誌,乃至新冠疫情大流行時,流行病學家和醫師在無能政府的陰影下,利用通訊軟體來自救。
在本書描繪的11個歷史現場中,都揭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從去殖民化到女性主義──皆是在相對封閉的關係網中形成的,這個私密的人際空間令某一個群體能孕育出之後廣泛傳播的概念和思想。然而,本書也敲醒警鐘:當下由社群媒體主導的世界,正令這樣的空間加速消逝,也導致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等運動未能發揮其潛力而功虧一簣。
本書如同一場精彩的媒介與社會運動辯證之旅,除了讓我們重新思考過往媒介所蘊含的核心價值,也為社會變革的出路指明了方向。
※本書聚焦11個歷史場景,在此先睹為快:
‧1635年,法國的天文學家佩雷斯克用成千上萬封「信件」召集分散各地的人們觀測月食,成功測量經度並重繪了世界地圖。
‧1839年,英國的憲章運動領導人歐康納募集了百萬名工人連署的「請願書」,為工人普選權的實現打下基礎。
‧1913年,義大利的未來主義者提出一份又一份充滿想像力的前衛「宣言」,激發藝術家米娜.洛伊也寫下《女性主義宣言》。
‧1935年,在非洲的英屬黃金海岸,由當地人創辦的《西非時報》和《非洲早報》,吹響了非洲民眾反抗殖民統治的號角。
‧1968年,蘇聯的異議分子娜塔莉亞.戈巴涅夫斯卡亞藉由秘密傳遞地下刊物「薩秘茲達」,記錄極權的暴行並散播人權的種子。
‧1992年,美國的年輕女孩們透過拼貼自製「小誌」,向主流社會和男性主宰的龐克音樂界發出桀驁不馴的「暴女」之聲。
‧1985年,一群舊金山的科技宅在網路上創造了史上第一個虛擬社群「WELL」,探測了線上交流的尺度和可能。
‧2011年,不滿獨裁統治者的埃及人在「臉書」上動員集結,點燃阿拉伯之春的怒火,卻在推翻政權後陷入臉書打造的困境。
‧2017年,白人至上主義者齊聚在線上平台「Discord」的封閉聊天室中,密謀一場示威遊行,夢想將極右翼思想帶入美國社會。
‧2020年,因政府無能應對新冠病毒,流行病學家和醫師利用「電子郵件」、「WhatsApp」和「推特」建立的群組,共商正確的防疫對策。
‧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者反思「社群媒體」為運動帶來的利弊,並投身於組織社區民眾、將政治訴求帶入體制內的變革中。
作者簡介
《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的資深編輯,曾任《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作者與編輯,著有《當他們找上我們時,我們將離開》(When They Come for Us, We’ll Be Gone),該書榮獲國家猶太圖書獎(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及薩米.羅爾猶太文學獎(Sami Rohr Prize),並被《紐約客》和《華盛頓郵報》評為年度最佳圖書。貝克曼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媒體研究博士學位,並為諸多媒體刊物撰稿,包括《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華爾街日報》。目前他與妻子及兩個女兒居於布魯克林。
譯者簡介
劉議方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後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取得學位。目前為自由譯者。譯有《在家不要談政治》、《開啟多重宇宙的自動書寫法》。
名人/編輯推薦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羅冠聰∣前香港立法會議員
熱烈推薦
張鐵志∣VERSE創辦人暨總編輯
黃哲斌∣天下雜誌編輯顧問
瞿筱葳∣g0v零時政府共同發起人
魏玓∣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依姓氏筆劃排列)
序
推薦序
革命要回到日常對話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一個國家的進步通常不會來自執政者的恩澤,也未必是因為反對黨的監督,而在於社會運動是否發達。參與社會運動者通常是被體制忽視的受壓迫者,或是對未來有遠大理想的先知,更可能是搖旗吶喊的熱血鄉民,社會運動者的主張未必全然都對或合乎時宜,但至少點出制度的可能不足,讓社會有思考與討論的機會。
隨著網際網路興起、社群媒體普及,在人手一機的時代,社會運動似乎變得更為容易。1994年墨西哥薩帕塔(Zapatistas)游擊隊透過網路傳播獲得全球輿論聲援,成了數位時代第一個資訊游擊戰運動,而1999年西雅圖的「反全球化」運動,以及近年來的埃及革命、阿拉伯之春、美國占領華爾街、台灣反服貿、香港反送中等,網際網路在其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將網路傳播稱為「大眾自主傳播」(mass self- communication)的時代,公民可以在網路發布訊息, 自主發展橫向溝通,分享自己的痛苦、恐懼、夢想、希望,連結彼此,克服孤獨絕望的無力感,從中找到行動目標,形成有歸屬感的社會連帶對抗權勢集團。對向來資源貧乏的社會運動行動者來說,網路可以快速推廣理念,召喚公眾行動,網路民主游擊戰也在全球蔓延開來。
不過,也許有人會問,社會運動真的改變社會了嗎?網路讓社會改革變得更好?
社會的改變本來就是慢的,強調速度的網路社會運動也很難帶來社會的立即改變,更何況,改變社會的行動不單要在網路發生,也更需要落實在實體生活中。
網路號召的行動來得快也去得快,就像人們的憤怒快速被激起,也可能因為找到出口快速消散,即使成功地推翻權力者,但有時也只是統治階層換人做做看。頭人換了、政權交替,政治體制、民心思維與社會文化並沒有隨之改變。
這並不是說,網路無法成為革命的節點或是社運發動機,而是得進一步思考,即使透過網路拉倒了政權,如何讓「改變」在日常生活裡實踐?
以選舉幕僚為故事背景的台劇《天選之人—造浪者》頗受好評,劇中「三十歲以前不是左派沒有良心,三十歲以後還是左派沒有腦袋」的台詞也引起不少討論,如果你曾是懷抱改革理想的憤青或許對此並不陌生,句中的「左派」有時會置換成「社會主義」,意味著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如果有理想的人沒有認清/識現實,恐怕是沒見識也沒腦袋。
「理想」與「現實」本來存在落差,但「理想」卻是改變社會世界、推向進步的動力,重點是「理想」有沒有回應/到「現實」社會?有沒有把「左派價值」融入到日常生活?
草根運動組織行動者阿林斯基(Saul Alinsky)在《叛道》(Rules for Radicals)書中提到他心中理想社會──平等、正義、和平、合作、平等充分的教育機會、充分且有益的就業、健康,以及創造出讓人們得以依循那些讓生命有意義的價值而活的環境。
雖然這是對生活的美好想像,也是許多人投入改革行動的初心,不過,這些理想未必會因為某個政權被推翻或政黨輪替就會立即實踐,有時甚至有可能越來越糟。因為即使是實施了民主制度也不代表一切變得美好,不是每個群體的聲音都會被聽見,仍然充滿著性別、種族、年齡、階級等種種壓迫,以及各式各樣的「微歧視」。
革命是容易的,民主是困難的,革命之後未必會帶來民主,理想的民主生活是需要先將人視為主體,平等尊重不同的意見,相互理解,透過共同討論才有可能共同完成。例如,如何使社會成員在家庭、學校、社區生活中就能學習互為主體、彼此尊重,同理溝通、尋求共識,而非傻傻或無奈地聽命於家長、教師、理事長權威,而忘了每個人都是有思想的獨立個體,但現實上這些價值也往往只是號召革命的口號,很少在日常生活或社會行動中真正實踐。然而,這更是社會改革者在革命初始就得有的認知,如同阿林斯基所說的:「作為一個組織者,我從世界真實所在之處著手,而非從我希望世界成為的樣子起步。」
這並不是說你要像政客一樣討好選民,而是進入群眾、走入社區,透過不斷地討論及對話,了解生活的現實與需求,從人民的角度思考問題,讓「理想」連結到人們日常生活進而產生思想與力量,才有機會實踐真正的政治與文化革命。
換句話說,社會行動不只是宣傳,更重要的是社會溝通,而溝通就不能只是夸言高深且難以落實的理想,是要在群眾的經驗範圍裡進行溝通,尊重對方的價值觀,因為人們需要一座橋樑,協助他們從自身的經驗跨越到新的道路上。
我們必須承認,翻轉式的社會改革是緩慢的,這樣的溝通也是緩慢的,就如同蓋爾.貝克曼(Gal Beckerman)在《革命前的寧靜:激進想法的起源,往往在意料之外》書中開宗明義說的:「改變──那種顛覆社會規範並根除正統觀念的改變──起初發生得很慢」。他還指出:「孕育一個激進的新觀念的過程十分獨特,而且具備某些條件:狹小的空間、大量的熱度、充滿激情的竊竊私語,以及能為一個共同明確的目標而爭論、努力的一定程度的自由」。
這就是社會溝通,但也是難以落實的艱難理想,一方面我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瞬間發生戲劇性的革命轉變,同時又要求受壓迫的人充滿耐心與人溝通,而社群媒體近期發展,讓人越來越沒耐心,溝通更為困難。
網路的確帶來對話,也讓社會運動有了新的力量與可能,但也因為演算法與自我選擇而形成密不通風、難容異議的同溫層,不僅讓社會大眾各據戰場,相互對立,更成了假新聞擴散的溫床,甚至是民主國家也以捍衛民主之名強化網路的管制。另一方面,權力者越來越熟悉網路的操作,或者是乘著網路風向而起,懂得如何靈活地操控網路,透過製作假訊息獲取利益。
網路是史上速度最快、擴散最廣的傳播媒介,但即使帶來了社會的變革、政權的更替,從近年來的許多地區的「革命」經驗來看,往往在一陣短暫騷動後,又回到既有的政治體制,原有的權力架構未有太大的改變,網路成為革命先鋒的期待,似乎只是短暫的曙光,其原有最不受宰制、互動性最強、自由度最高的特性,也因為僵固的政治文化與權力結構越趨黯淡。
不同的媒介會帶來不同的互動模式與思考方式,也會形成不同的社會關係與行動力量,《革命前的寧靜》回顧了世界各國近期的「革命」歷史,探討在行動之前的媒介使用與社會影響,也反思不同媒介所造成的行動侷限與問題。
網路如水,既能載舟,亦能覆舟。要提醒的是,不論你想用什麼方式改變社會,或者用什麼手段推翻政權,都要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互為主體、相互理解,共同行動,才有真正改變的可能。
目次
推薦序 革命在發生前,就已開始/羅冠聰
序曲
第一章 耐心:1635年,普羅旺斯艾克斯
第二章 凝聚:1839年,曼徹斯特
第三章 想像:1913年,佛羅倫斯
第四章 辯論:1935年,阿克拉
第五章 專注:1968年,莫斯科
第六章 掌控:1992年,華盛頓州
插曲 網路空間
第七章 廣場:2011年,開羅
第八章 火炬:2017年,夏洛特維爾市
第九章 病毒:2020年,紐約市
第十章 名字:2020年,明尼阿波利斯市
尾聲 桌子
致謝
註釋
書摘/試閱
序曲
改變──那種顛覆社會規範並根除正統觀念的改變──起初發生得很慢。人們不是直接就砍掉國王的頭,而是先會花上數年甚至數十年講他的八卦,想像他光著身子、滑稽的樣子,將他從神祇降為會犯錯的凡人(從此有顆頭可被砍掉)。各式各樣的革命皆是如此。先是奴隸制存在,然後有一小群人開始憂慮起他們染上另一群人所擁有的道德敗壞,並仔細忖度有什麼事可做。他們的談話將他們變成了一個有目的的團體,這個目的就是廢除奴隸制,而隨著彼此的討論越來越熱烈,最後化為行動,進而促成思想的改變,最終寫進法律。
我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人群集結上街的那一刻──腎上腺素、催淚瓦斯、震耳欲聾的口號,騎馬的警察追趕著孤身一人的抗議者,或一個男人挺身面對一輛坦克車。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共有現實(shared reality)的某塊實心磚第一次裂開的那一瞬間,當下通常是一群人在交談。更具體地說(且讓我重新詮釋一個被矽谷變為無意義行話的詞語),這些人正在「孕育」(incubating)。孕育一個激進的新觀念的過程十分獨特,而且具備某些條件:狹小的空間、大量的熱度、充滿激情的竊竊私語,以及能為一個共同明確的目標而爭論、努力的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區組織者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叛道》(Rules for Radicals)已成為社運人士們的聖經。他在書中寫道,成功的革命遵循著一部劇本的三幕式結構。「第一幕介紹人物及劇情;第二幕,劇情和人物會有所進展,力圖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而最後一幕,則是善與惡戲劇化的衝突及其化解之道。」阿林斯基站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的高處上,觀察到一整代革命者的問題在於他們「缺乏耐心」。他們衝到第三幕,渴望善戰勝惡的「啟示」。但實際上這並不是捷徑,而是「為對抗而對抗──爆發,然後回到黑暗。」
「孕育」正是在前兩幕中發生。阿林斯基知道,如果沒有前兩幕中想法憑空迸發、計劃、辯論和說服的過程,可能你會有一場精彩的抗議活動,令人目瞪口呆,但一無所獲。
現今,這樣子的「孕育」會在哪裡發生?會不會是在社群媒體上?在一個爆紅的主題標籤(hashtag)仍被視為具顛覆性潛力的網站上,像是推特和臉書?
我們在個人生活中已經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社群平台既帶來了好處,也帶來壞處。這些平台上的交流皆極度活躍。它們作為社交的場合,就如一場喧鬧的雞尾酒會,你會在不同的對話間跳來跳去,花幾分鐘看某人的瘋狂故事或有趣的笑話,但在晚上結束時筋疲力盡。首先,這些空間是為了盈利而建的,我們對此不再天真無知。創辦這些平台的公司扮演著我們對話的主持人,使某種類型的對話享有特權,並限制了其他類型對話的潛力,這是設計使然。儘管我們仍然將這些工具視為一種聯繫方式,但我們知道──此時此刻在直覺上知道──什麼樣的表達方式會吸引別人按「讚」,按下豎起的大拇指按鈕。那些「讚」源自參與感所激起的多巴胺回饋,因此,我們需要產出能引發強烈情緒的內容(就是「引發」這個詞):憤怒、悲傷、厭惡。
如果社群媒體使我們變得容易分心,將我們拖入永無止息、一串接著一串的照片與華而不實的評論中,那麼應該不難理解其對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s)的影響。從二○一○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起義,到本世紀末的#MeToo運動,在社群媒體上進行的運動(movements)也將自己塑造成能適應這些社群擴音機的形式──為了吸引注意力及滿足情感而高聲喧嚷,進行資訊轟炸,但這樣的形式下,資訊往往轉瞬即逝。我們的數位對話常常讓人感覺好像是透過擴音器進行的──一種沒有任何真正親密感的表演。我們發起的各種運動,那些激進變革的熔爐,現在具有同樣的特質。
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後的幾週期間,我發現自己幾乎每個週末都在參加抗議活動。在那段日子裡,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想做點什麼,將川普獲勝的震驚──甚至還沒有怒火全開,只是震驚──傾注到某種公民行動中。我從不喜歡參加示威活動,但我與我的妻子和女兒們走上了街頭。(她們製作了自己的抗議牌,在牌子上以帶著流痕的紅色油漆寫著:「愛使美國偉大,而非仇恨。」)和其他人一起遊行穿越曼哈頓中城,感覺真好。但我也想到,在一個憤世嫉俗或清醒的時刻,我周圍的每個人都沒完沒了地在他們的照相手機前擺姿勢。我也這樣做了,而當然這些照片是要分享到網路上的。在最初的幾週之後,我沒有再參加任何抗議活動,但我女兒的照片和她們的抗議牌仍然留存於臉書上。我經歷了阿林斯基所說的革命第三幕。
儘管社群媒體為各種運動提供了一股力量,使其能以驚人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規模組織動員──讓每個人在幾個小時內到達時代廣場或曼哈頓中城──這股力量卻也阻礙了這些運動的發展。正如社會學家齊納普.圖菲其(Zeynep Tufekci)在她的著作《推特與催淚瓦斯》(Twitter and Teargas)中所敘述,此矛盾的狀況在於,社群媒體這台擴音機能為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們帶來「注意力全面集中的一刻」,「但這些人幾乎或完全沒有一起面對挑戰的共同經歷。」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跳過:一番爭論後,才敲定意識型態及組織結構的艱辛,還有確立強烈的身分認同以及設定目標的過程。由此形成的各種運動,它們的深度與堅實度正如那個舉起拳頭的表情符號一般。
「孕育」──因為推特或臉書上真的沒有空間──最終迷失了。
倒不是說「孕育」不能在網路上發生。在某種程度上,川普的當選,證實了另類右派(alt-right)已成功醞釀了屬於白人至上主義和厭女思想的地下世界。因為他們的觀點對主流來說太惡毒了,所以他們創造了自我封閉的宇宙,或者被迫進入其中。首先是保留了早期網路上舊式的、有著激烈聊天室構造的網站,像是Reddit;然後是4chan或8chan等論壇;或是在更鮮為人知的平台上,例如Gab。他們不斷地跳入更深的洞,在洞裡他們可以互相慫恿,懷抱陰謀論,爭論哪種方式可以最有效地將他們的觀點帶給更廣大的群眾,分享迷因(memes)看看效果,並爭奪領導地位。在那裡孕育滋長的許多故事情節──關於跨國入侵、控制財富和媒體的邪惡勢力、對於女性主義削弱男性力量的不滿──最終會透過川普總統的嘴,進入美國的文化。
當某些想法太過有害,以至於我們將其排拒到視線之外,然後擔憂這些想法可能如何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發酵時,便會產生這種迫不得已的「孕育」。我們已經在暗網(Dark Web)上的兒童色情內容和ISIS的招募成果中看到了這一點──現在我們想到封閉空間時,腦海中浮現的就是這類例子。這實在很可惜,因為當我們只將這些隱蔽的角落與極具破壞性、令人憎惡的東西聯想在一起時,會忽略了這些隱蔽之地的價值,尤其那是對於具備「利社會」(pro-social)力量之人而言的價值,而他們迫切需要這樣的地方。
想想「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大家都認為這是過去十年中極為成功的運動之一。在二○一三年,一開始它只是個主題標籤,隨後這場運動經歷起起落落──在數起警察暴力的殘酷事件(並且經常被拍下影片)之後,二○二○年人們對這場運動的關注度在激烈的氛圍中達到了巔峰。
社群媒體使社運人士得以向一大群觀眾引介並加強一套陳述──一套極其清楚的陳述,即「應該認真看待黑人的生命」。一個媒體能帶來這樣的病毒式傳播,也能設定議題,再怎麼強調其潛力都不為過。它使之前我們的集體故事中被遺落的部分變得不可忽視。在二○二○年的那個夏天,社群媒體掀起一波正面的狂潮。在社群媒體的帶領下,人們集體示威,在草坪插上寫著「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戶外告示牌,思辨並談論種族議題。一些過往似乎不容質疑的象徵符號,例如邦聯旗幟的星星與橫條,幾乎頃刻間便轉而被更多的美國人棄之敝屣。然後那個夏天結束了。
先是陳述,然後是緩慢地聚集力量。「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參與人士們也開始意識到,社群媒體如何阻礙了後者。他們能在哪裡想出共同的目標?他們能在哪裡制定戰略,並從情感轉向意識型態(在這場運動中,即是將改革延伸為革命的意識型態)?他們能在哪裡發展以贏得政策上的勝利,在哪裡成立組織並選出富有同情心的立法者,在哪裡透過抗議活動達成特定的、地方性的,甚至是不穩定的目標?他們能在哪裡聚集,以執行更艱鉅的任務:重新配置、安排那些支撐著被拆除的美國國旗所象徵的底層體系?
我第一次接觸到「孕育」,是在我研究蘇聯的異議人士時。就像另類右派人士──但他們當然非常不同──為了互相交流溝通,那些蘇聯異議人士被迫創造出更私密的空間:他們的國家完全控制了出版的管道,甚至登記了每一台打字機,如此一來,某個字母是誰打出來的,都能追查到。他們的解決手段是秘密出版「薩祕茲達」(Samizdat) 。透過在洋蔥紙上寫文章(有時最多同時打出十或十五張),從一人手中傳到另一人手中,薩祕茲達成為了這些異議人士建構並堅持其反對極權國家的方式。他們寫下了所目睹的事情,編纂侵害人權及公民權事件的清單。他們寫了關於「應該做什麼」的文章,然後又寫其他文章反駁那些論點。他們也透過這種方式翻譯並傳播西方世界的著作。異議人士的關係網圍繞著薩祕茲達而形成,並且變得牢固。生產薩祕茲達是危險的──被抓到的話,經常可能會被流放到東邊某個遙遠的地方──但這只會增加那些異議人士的忠誠度。
那些異議人士所處的壓抑環境禁止辯論及自由思考(freethinking),然而,他們用薩祕茲達建造了一個暗影下的公民社會以進行這些活動,此情形持續了幾十年。當蘇聯最終因無法維持其經濟體系而突然解體時,另一個可替換的公民權概念已經存在、被孕育了出來,並傳達了一套很快便成為規範的價值觀。〔至少直到二十一世紀,隨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掌權而出現新的威權主義為止〕因為有薩祕茲達與它在表面下不斷醞釀的理想,在國家崩潰時,蘇聯領導人們很難讓人民挨餓或用坦克碾過他們──異議人士的願景就在那裡,被保存下來,無法輕易被粉碎。
在檔案存放室裡,每當我觸碰那些幾乎半透明的紙,感受它們的脆弱,凝視著印在上面就事論事的黑色文字時,我都會為薩祕茲達的功效所震懾。它需要注意力的集中。創造薩祕茲達所涉及的高風險,意味著你必須細細思量你想說什麼。它還允許交流對話。那些紙頁本身包含了多個聲音,多次來回的對話,全都在他們更遠大計畫的疆域內。薩祕茲達為異議人士打造了一個秘密世界。任何人都無法進入其中,除非有人交給他們一份薩祕茲達。這給了他們自由,他們可以犯錯、嘗試新概念,以及幻想一套更人道的新社會秩序。他們掌控了那些頁面。沒有其他人規定薩祕茲達的形式或限制其內容。如果有人想要散播一首關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具煽動性的詩,或是一篇關於資本主義可能帶來好處的文章,他們只需要找到紙張和打字機(通常是在黑市上),他們的關係網就會接收並傳播他們的貢獻。
我們用來對話的媒介,會塑造我們可以進行的對話類型,甚至設下我們思維的界限。這是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深刻見解:從口述文化到書寫文化再到電子文化(electronic culture)的變遷,為人類處理現實的方式帶來了轉變,而此轉變改變了人類。一九八○年代,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接下麥克魯漢的接力棒,在其著作《娛樂至死》(Amuse Ourselves to Death)中將怒火轉向電視,他認為電視對公共論述產生了不利影響。他的說法是「電視的形式會排除其內容」──換句話說,媒介是一個容器,能容納某些類型的思想,卻會屏除其他類型的。對他來說,印刷品一直以來相當有助於理性的爭論,但電視的視覺即時性卻排斥這件事。我們只能猜測,若他還在世,對於抖音之類的媒介會有何感想。
而說到社群媒體,它把什麼排除在外,又把什麼高高舉起了?若以這個問題來探討這個現今似乎無處不在的溝通交流模式,很明顯地,社群媒體並不是很適合讓各種激進的想法留存下來,慢慢地連貫在一起,而且風險很高。儘管當矽谷的社群媒體巨頭們說,這些平台的存在是為了「改變世界」時,我們仍不免懷疑,但我們已經不再考慮任何其他能改變世界的方式了。這些平台占據了主導地位。我們錯誤地認為,這些平台相當於十八世紀的咖啡館(那裡確實孕育了由咖啡因和報紙推動的民主),但社群媒體並不利於變革過程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它們只會讓想法爆發,然後返回黑暗。
然而,革命的歷史很長,並且充滿了其他可能性。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薩祕茲達及所有其他以書寫進行交流、使對立的主張及身分認同得以形成的共有方式──如何看待至少從發明活字印刷時就存在,直到美國線上(AOL)聊天室出現,這之間的漫漫地下文字長流?那麼,信件、請願書、宣言(manifesto)、小報和雜誌呢?那些由偉大的男男女女們所撰寫的鴻篇巨著,遮蔽了這些地下發聲渠道。但它們就在網路時代之前,在我們種種模糊記憶的另一端,依然存在於那裡,而且暫時可見,並提供了另一種方法,讓我們了解到一個媒介將人們團結起來意味著什麼。(未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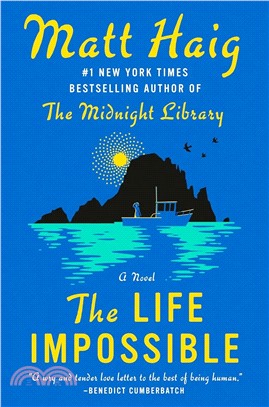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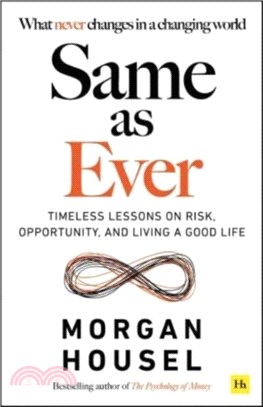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