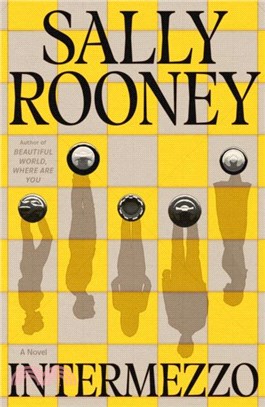水中家庭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令人崩潰的理工男的半生?!
世界給予我規則,我努力學習,突然有一天,規則打敗我、嘲笑我!
冷專業背後,家庭裡甜蜜辛酸、溺水的日常
白樵、朱宥勳、寺尾哲也、吳佳駿、林楷倫、高翊峰、班與唐、廖淑芳、蔡欣純
齊聲推薦
「海上巨大的風力發電支柱塔、平台船、雪山隧道挖掘時源源不絕滲出的水——《水中家庭》所描繪的一切堅固事物都帶有漂浮的性質。在仿若暈船的無止境晃動和眩暈之中,小說靜靜疊合出人心深藏的真相。」 ──寺尾哲也
這是一本難得以道路、水、電與公用建設架構出的小說,逸脫職業小說,轉指如同城市底下電網、水網及路網維持人們(或說社會)的內心。看似複雜卻是純粹的故事展演,真實虛幻,《水中家庭》是佈滿作者誠意的娛樂幻術。
──林楷倫(作家)
一本環套式解構之書。作者先解構自身,跳脫原孤絕,隱喻性高的文字,在《水中家庭》改以清澈至湖底有光的白描,好行第二層解構。簡潔風格代謝推進的,是延續上世紀卡夫卡的公務員形象:後工業網路時代,由更繁複的發包、監造、利潤利息、混凝土坍度輸電網路交流量造出的,關於「秩序」的龐大骨幹。第三層為人際關係:兄弟,夫婦,親族同事與其輻射出的各自家族型態的拉岡鏡像式折射與對照(亦解構了數世紀積累的男性神話)。現代生活的水,為凝狀之水,窒礙混濁,是讓人逐漸動彈不得的水泥固化進程,陳泓名消融一切的最終步驟,是莫里斯・布朗肖於《文學空間》裡提及的讀者獨特的透明目光。被觀看後,被解放,如是滅與生。
──白樵(作家)
敘事的本質是生命的延伸,而《水中家庭》的本質,似乎是水平面下一切阻力的延伸。
──吳佳駿(小說家)
配啤酒、鹽酥雞一口氣讀完《水中家庭》,深刻地感覺到這是送給公職小螺絲釘們最溫柔的小說。
以前在公家機關碰過的前輩、承包商老闆,總愛開難笑的笑話、抱怨政客、抱怨法規⋯⋯,但他們手握城市的未來藍圖,滿是工程規劃設計案、施工圖等。然而藍圖的願景再美,對小螺絲釘來說,不過是盡力讓事情正常運作而已,別被告上法院即可。
我無法想像自己的人生也變那個樣子,所以佩服陳泓名能將他們的痛苦寫下來。若感到痛苦,那就翻開《水中家庭》吧。或許能看見海面上巨大的風機,安靜卻依舊轉動著,沒有失常與正常。 ──班與唐(小說家)
「回顧今生,差點陷入沒有規則的地獄的時候,我認為有三個。第一個是母親離開的時候,第二個是父親的葬禮,第三個是三十二歲的現在。」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信仰機能的工程師阿名,努力像機器人一樣工作,卻看著認知的世界慢慢走向崩塌:差點在山裡淹死的父親、以船為家而關係疏離的弟弟、名字裡面有水的自己、以及電話裡恐嚇要煮了小孩的妻子。
主角阿名大學時,曾在雪山隧道內施工的父親突然承認自己早已退休,家中失去經濟支援,為了撐起自己的前途,他開始了遠離親人與獨自面對壓力的人生。畢業後就職彰化水務局,經過同事鼓勵,轉換跑道至臺灣電力公司梧棲區,負責離岸風電業務。
從為金錢所困,到結婚、生子、離婚,耗盡半生直至發現自己原來一無是處。發現了越多規則,就被越多規則擊敗。這是個不停道別的故事。政府的雪山隧道的施工奪走了父親的生之意志,疫情規則奪走了見母親最後一面的機會,故事中的阿名半輩子奉獻給公共工程,也獻給孤單的父親,用粗糙的手代替溫暖的話。
回頭想想,公共工程耗費如此巨大的金錢,耗盡了數十萬人的青春,我們卻視其當然,難道這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嗎?風機在海中央旋轉,如此巨大。小說一邊回應著時代的工程難題:離岸風電、大埔案、核能公投、疫情時期,一邊以冷靜的的文字,白描了理工科男生冷專業的背後,家庭裡甜蜜辛酸、溺水的日常。
作者簡介
小說、散文寫作。成大水利系、獨立書店「楫文社」負責人,現居墳墓山旁與捷運水泥基樁下。獲臺北文學獎、鍾肇政文學獎、新北文學獎;獲國藝會與文化部創作補助:臺電工程史、離岸風電、公共工程、澎湖家族史;出版小說集《湖骨》、《水中家庭》。
目次
名家推薦
父親的葬禮
2016
2017
2019
2020
尾聲
後記
致謝
書摘/試閱
三十二歲之前,組成我的人生大部分元素,就是「聽音樂並且不停工作與讀書」,這三件事佔據了大部分的時間。等待固定的節奏,落後但緩慢追回,調控整個工程進度,有時候感覺美,大部分的時候都只是向前,想說什麼,但是看見自己鏡子前的外貌,以及對別人的談吐,就知道我裡面其實什麼也沒有。
很抱歉,因為能言善道的人太多了,沒人想知道我聽什麼音樂,實際上,聽音樂就跟吃飯一樣,有些人把一口飯吃得頭頭是道,但我不行,因為音樂只是我找回固定節奏的一種方式。
咆哮、還是抱怨,都只是一種裝飾。這是我從三十幾年來,聽音樂得到的小小的感想。好像我有什麼獨到的觀察一樣,其實並沒有,三十幾年來,我專心至一,才理解這種微不足道的事情,雖然理解的當下很滿足,但也感到失落,對,就只是小小的失落。我再也不會講跟音樂有關的事情了,音樂與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唯一的關聯就是,它是規律的。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便明白,規律是一種神聖的價值。
七歲時,我不得不中斷父親與母親的漫長爭吵,因為上圍棋課的時間到了。
車陣中,父親的眼神疲累,車內唱片的音樂重複,下手歌播放前,音樂便已經在腦中響起。下車時,父親仍然記得提醒我:下車小心。
在圍棋課,我們不能第一步就下在中間,這是很重要的價值。無關乎勝負,勝負也許沒那麼規律,但是不能下在中間,有關為什麼圍棋發展正麼久,三四百年來,以前的棋士用盡智慧理解出最有效率地圍地方法,如果你們繼續下中間,不照著定石走,那麼學了也是白學。老師這樣跟我們講的時候,我想,我的同儕們,應該沒有一個人懂,他們只想要趕快下棋,因為這樣才能擺脫課程。
唯獨我不想。
我想要繼續聽老師的課,不想下課回家。
當時,聽了這句話之後,我仍要求爸媽繼續讓我上圍棋課,直到小學畢業,就是為了聽老師繼續講類似這樣的規律。我想,如果一點一滴,逐漸理解所有的規則,那我應該會變成一個很棒的人,或者,接近完美的人。當然,我知道教條彼此都可能產生矛盾,但只要先記住,一定也有它的意義。就像學習講話一樣。
當我回到家後,首先聽到這些話。
「你從來都不把我、我、我、放在眼裡。」母親說出「我」這個詞的時候,用雙手用力刺著自己的胸口。「你瞧不起人啊?」
「是不是誰都入不了你的眼啊?」母親踢翻了椅子,父親的身子又縮得更靠牆了。
我心中知道答案:沒有啊,媽媽,爸他不是這樣的。
然而,從我去上圍棋課,到凌晨媽媽離開後,他都說不出一句話。
早上醒來時,家裡只剩下父親了。他用粗到不行的手指,抹了抹昨晚的淚痕,並且問起:「昨、昨天上課,老師教了什麼啊?」
陽光在父親的頭髮上。
我和父親說:「我會打劫了。」
父親問:「打劫?」
我說:「用那邊救這邊,圍棋的方法。」
鐵門打開,鑰匙撞擊門鎖,父親的臉明顯僵住了。我絕對看過這個場景數萬次了,連我都冒出冷汗,那是母親回來的訊號。前年,我插入他們的爭吵,徹夜之後,他們抱著我哭;前三個月,我再次插入他們的爭吵,徹夜之後,母親對我說,你們陳家聯合起來對付我;前幾天,我站在旁邊看,徹夜之後,父親沒睡的眼睛,愣愣地看著窗外的晨光。
我問父親,為什麼不和媽媽講道理,而不管我當時如何發問、如何反駁、如何解析,父親都只說:我只是想和你媽媽走到最後,走到幸福。啊──,完全不能明白,完全不能,為什麼他可以忍受呢?為什麼他總是要這樣忍受不合理的事情呢?難道,被蒙在鼓裡的是我嗎?有一陣子我很氣他,覺得他是廢人、覺得他活該、覺得他死好,這就是他選的。
「看我,你看我。」母親對著父親吼著。
父親抬頭。
「你眼裡根本沒有我嘛,你根本就再放空嘛!」母親說。
我吞了吞口水,想著:父親,你幸福嗎。接著,在母親即將踹開父親正在跪坐的椅子前,我走到他們旁邊,說:「我要上圍棋課了。」母親悻悻然地走進主臥室,摔著她的化妝品,玻璃破碎、水花飛濺、我走在父親的前面,領著他坐上車。
父親雙脣顫動,手握著方向盤,而我主動按了收音機的按鈕,匡噹噹噹,吉他聲非常地吵,我又主動把聲音調小,嗶嗶嗶。此刻,內心有種沉甸甸的感覺,看著窗外,小學生們走在電線桿與電箱的縫隙,成群結隊,突然間,我覺得,這樣非常幸福。這樣幸福的感覺,一直伴隨到我長大,都是這樣認為的。並沒有比別人還悲慘的童年、也沒有什麼遺憾,男人有許多隱忍的事情,這也不算什麼,這樣子長大,本來就很幸福了。
比同班的人都還又認真學圍棋,又會拖著老師到最後一刻,直到爸爸說:再不回去,媽媽煮的菜都要冷了喔。直到母親離開了家裡,和父親離婚,我才漸漸減少去圍棋課,同時,我也逐漸忘記母親的模樣,但心裡也不曾在乎,而弟弟因為短暫和母親住在一起過,因此比我記得的多一點。我們從未聊過這個人,除非父親主動提起。
我很慶幸這些規則我都還記得,閒來無事的時候,仍然可以用手機下一盤棋。儘管在AI時代中,舊定石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但是對上段數比較低的對手,我偶爾還可以自己給自己激勵兩句。啊哈,我贏了。
我認為我的心智堪稱如此堅固,應該是有個喜愛在飯後跟我們說教的父親。我們家沒有電視,聽父親說話,就是唯一的娛樂。不用擔心,我們並不是被逼著聽,我與弟弟,阿清,都喜歡聽著父親每一句話,直到如今父親走了之後,在他的喪禮時,想起來父親說,要記住你們老媽,要去找她,她其實很孤單。突然又被父親這樣的蠻不講理的方式,體會了父親的真意。事實上,我認為我們都是很愛父親的,真的,活到三十幾歲,恨的東西沒有變少,但也沒有太大的恨,阻礙我活下去,我認為這都得感謝父親。
回顧今生,差點陷入沒有規則的地獄的時候,我認為有三個。
第一個是母親離開的時候,第二個是父親的葬禮,第三個是三十二歲的現在。
第一個故事我不是很想要講,那時候我很小了,對於母親的記憶不多,相反的,被離家的母親丟回家的弟弟,應該對母親比較多的認識吧,所以,對於母親的離開,我只記得當時我相當地恐慌,原因跟理由全都忘記了,那就只是一種純然地,孩提時期,對於死亡的突然認知。母親的離開,為什麼與死亡緊緊相連呢?這我也弄不明白,只是大學時期,那個愛心理分析,榮格還是佛洛伊德的課修了高分的女友,常常跟我說,這很重要。
當時二十二歲的我。
大學時期的我,把女友的話記著,放心裡。有時候想到母親,就會拿起來用一下,想到母親沒關係,這很重要。大部分的時候,想到女友那了然於胸的表情,我也常是分離出另一個我,看著我自己,突然這樣也了然於胸了。這是下圍棋時的習慣,在大學時期都學著去註冊圍棋網的會員,每個月瘋著去報名棋院賽,網路上比賽比較多,一個下午下來,還可以下到五六盤。下完棋就去接女友下課,吃晚餐,隨意聊了天之後,晚上繼續研究棋譜。
父親也幻想學會下棋,時常跟我說:我學一下子也可以,有什麼難的。但是父親的工作在兩千零六年之後,卻又更忙了。通車的兩年之後,在兩千零八年的年底,那時候我在大二的暑假,父親開車要去宜蘭的路上,突然說不想要走雪山隧道。
我問為什麼,父親才說,他怕水,經過雪隧那幾批工班後,他都怕自己被淹死。
在山裡面被淹死。
在長長北宜公路的路程中,三小時到南方澳漁港吃飯的路上,父親說他其實早就失業了,他只是偶爾接接模板工、抽水車點工的工作,但他也很慶幸他失業了,因為他再也無法忍受出碴、湧水或著小規模坍塌的撤離訓練。一九九一年剛進工地時,他所有人都徒手工作,拿著手提式鑽機,向岩面設置炸藥,撤離,並且進行全斷面開炸,落碴用鐵牛車運出來,一次在山洞裏面工作十小時。父親說,自己的肺應該有問題,因為吸進了不夠多的空氣,又吸入了粉塵。這期間,父親與母親結婚,生下了我,又因為父親太少回家,母親帶著弟弟離開。
一九九三年,我四歲,父親二十六歲,父親抽開始抽水,每天都有水,無盡的水,抽了三年的水,抽到第三年,終於把全斷面挖掘機拆除,改採用鑽炸法開挖,也就是他結婚之前,在擁有我、擁有弟弟、擁有已經離開的妻子之前,早在人類會挖掘山洞時,就會採用的工法,非常古老,沒有和進步。因為太多水了,連全斷面開挖機都無法推進,只能採用以前的方法。隧道鑚掘機(TBM)在十九世紀被發明,在建造英法海底隧道時,聲名大噪。三年後,引進臺灣進行技術轉移,但是響亮的名聲鐘就被雪山隧道脆弱的岩脈所摧毀。
「技術轉移?」我在快要暈車前問。
「陌生人到你家施工,總得拿走什麼回去吧,你看通馬桶師傅通馬桶,下次可以自己試看看。」他說。
「具體要怎麼做才能轉移?」我無視父親的廢話。。
「外國人做東線,我們自己做西線,一邊做一邊學。」
「聽起來很好,各取所需。」
「但也最後這台才用了六年,有個屁用。」
「至少有些理由吧。」我說,記得那時候還在讀大學土木系,「這麼大的工程,億來億去,各式各樣的教授或是技師,為了這六年,應該也是評估後才決定吧,不然那些規劃報告書是空白的嗎?」
「不可能,那些都是給官員酬庸。」父親說,「你還太年輕。」
我忍住翻白眼的慾望,很奇怪的是,我總覺得跟父親聊天,才會引起我的某些很不滿的情緒。平常的時候,就連身邊的女友都稱讚過我說,就是因為看我沒什麼情緒,感覺交往起來,不會太黏或是太累,才最終選擇了我。但是和父親說話時,父親那種硬下結論的時候,我每次都無法適應。不過,弟弟阿清總是提醒我,誰都也會硬下結論,打屁喇賽而已,別那麼難聊。
父親終於坦承,他早就已經結束坪林的工作,那些什麼後續的路面維護、抽砂工程,都是父親為了掩飾而說出來的話。我很同情父親,他為何要說謊呢?我們又並不在乎,他究竟有沒有工作,儘管我未曾懷疑過他說過的任何話,原因都是作為土木業的一員,他算是現地的大前輩,摸過的水泥比我們看過的水還要多。父親講箍筋該如何綁、業主如何省料,我也都會記在心中。原本以為,父親說了這些,我自己似乎會感到不滿,但事實上,什麼也都沒有消失,反而多了點同情心,竟然會為了這種事情瞞了我們這麼久,父親依然完整地存在那裡,我依然尊敬他,阿清依舊會與他抽菸,那他是為了什麼而努力呢?其實根本不需要做這些啊。
放下了某些重擔,感覺他的影子,變得更薄一些,他說,接下來就靠你們了,我老了。二零一零年,父親失去了所有活力,那時他四十四歲,他說著這些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感受到什麼,單純認定是到跑累了、走累了,只是在操場邊喝杯水休息一下。那趟去宜蘭的旅程,他都相當地開心,純粹享受著閒逛、拍照的樂趣,甚至還去百貨買了雙快一萬元的登山鞋。
他拍著阿清的肩膀,走到我面前。
身上還有菸味,含糊地說:我要退休了。接著伸展筋骨,彷彿把棒子交給我後,就退到旁邊的草皮開始喘氣。
而我自己,也開始著手各種畢業的事情,畢業也是某種清算,而且要花費許多錢。大大小小算下來,清償學貸後,我算了算,必須再多接打工了,並且確實減少紀念性的飲食。而我認為,我的女友也很聰明,她離開了我,因為我並沒有多餘的心力陪伴她,反而得由她扶持我,她說:感情就像是樹,如果樹已經夠大了,那麼它可以發揮支撐、妥適保護的作用,但如果它尚未長大,那麼它便需要各式各樣的關懷,陽光、充足的水以及合適的溫度與濕度,若是缺乏任何一種,那麼樹就長不大,就會永永遠遠地缺乏下去。我覺得十分合理,便答應了和平分開,當然,那使我掉淚很多次,只是如今,我已經感受不到任何意義,才能用這樣冷淡的方式說明。
我問她:「我──妳、妳可以和我說,我的問題在哪?」
她說:「不,不是的,問題不是問題本身,我看到的是你。」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我問,「還是有什麼能讓我學習的心理理論?」
「不知道是否有那種東西,但我想,那也不適用我們。」她說。
我歪頭想著,沒有嗎?嘗試去定義一個永遠無法定義的事物,並且產生分歧,這不就是學派的本質嗎?白天上課的時候,我也想著這個問題,晚上打工時,我騎著車,經過了長長的線道,彎入市區的巷弄裡面,鑽過停滿了機車的路,靠著鐵門停下來了。打工前,我總會提早二十分鐘抵達,看著老闆給的褐色公事包裡面的資料,坐在機車上陷入長考。
那時候的思考就像是做夢,夢裡面,我們會自殺,會掉下懸崖,會失去道德,會和不是女友的人做愛。我無邊無際的想任何事情,甚至計算父親死後,會留下那些財產,檢視父親的身體,思考著糖尿病與心瓣膜脫落,四十五歲的他,可以保哪種壽險而不會花太多錢,他抽菸,又有多久能活?可以早點去死嗎?我會想如果阿清,但是想到他餐飲科畢業,又想著要如何巧妙地斷絕關係,千萬不要要我養他。
我是長子,現在父親不幹了,於是輪到我了。
打卡機發出機械聲,上面顯示一排時間,一切瞻妄都會在打卡的時候停止。所有的疑問都會停止,不,這樣講錯了,只剩下一個疑問,那就是我到底怎麼了?這不是一個探詢式的提問,它沒辦法只是放在心裡。
我認為,這個提問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會帶來擾亂,擾亂就會失序,而失序會帶來更多擾亂、有機、擴展。畢業前夕,我又修了隧道工程的課,以及畢業所需要的學分,但是隧道工程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期中考也沒有考古題可以依循。
事務所的工作,再加上平常學業的難題,導致我累到在走廊間吐了出來,為了掩飾,我還趕緊去廁所拿拖把,才把剩下的穢物嘔在馬桶。
我看著馬桶的空洞,上面漂浮著廚餘殘渣。喔,原來這也是隧道淹水了嗎?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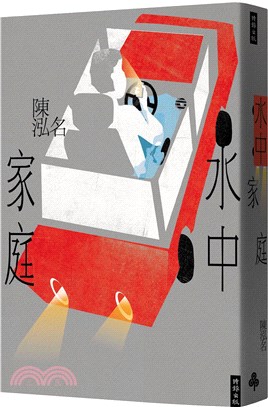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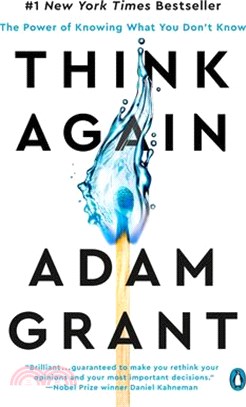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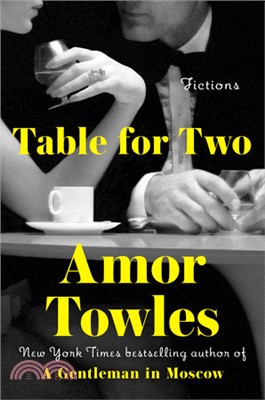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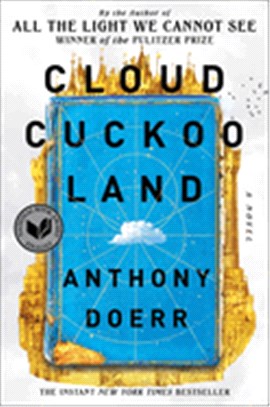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