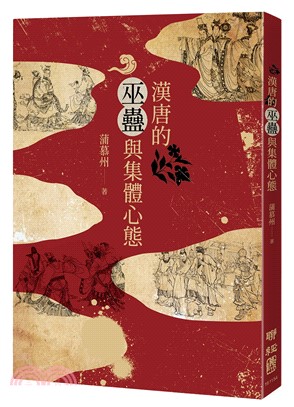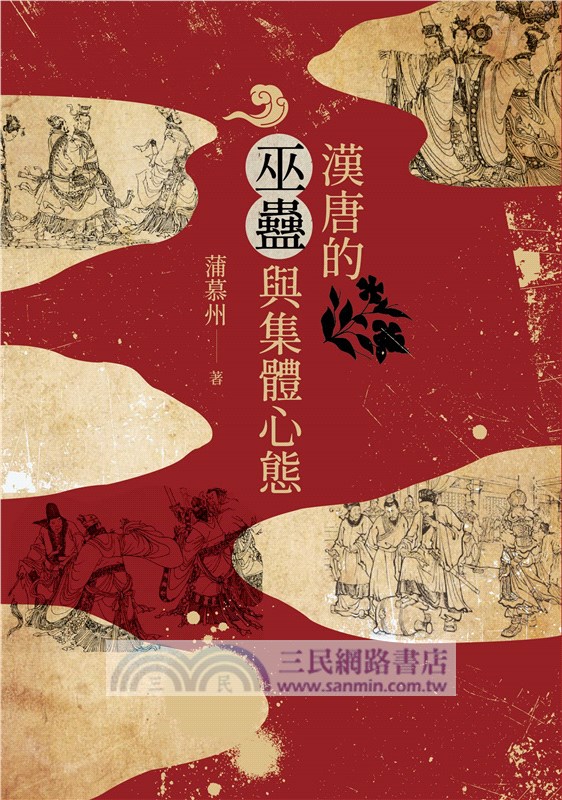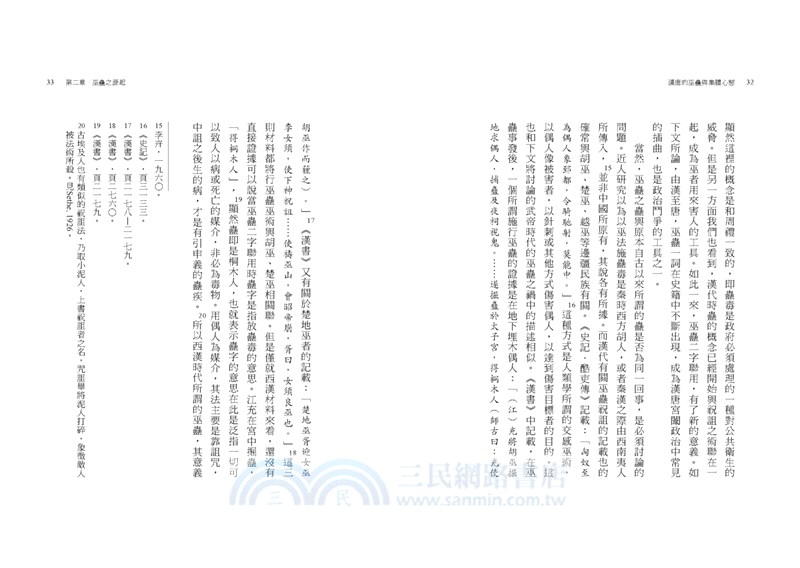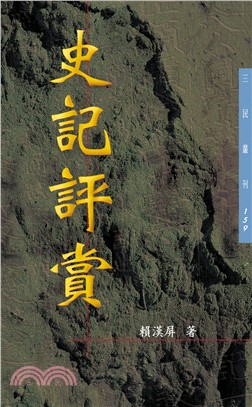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漢武帝晚年發生巫蠱之禍,數千人喪命、太子自殺。
後世典冊經常提及此事的慘烈,
巫蠱之術也成為往後數百年宮廷鬥爭的新工具,
對內廷政治、社會記憶以及宗教心態均造成一定的影響。
《漢唐的巫蠱與集體心態》由跨學科的角度出發,闡釋這個跨越宗教、政治、
大眾心態等等因素的主題,並且對中外巫術之異同提出比較與考量。
史籍記載了許多發生在宮廷之間的巫蠱事件,大多牽涉到皇親國戚及政府官員,其中又以漢唐之間最為頻繁。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法律和宗教環境滋養或鼓勵了巫蠱的信仰和行為?這些事件延續如此之久,對於我們了解宗教和社會的發展有何意義?當時的宗教心態是什麼?同時,官方史籍的記載和私人記載、方志、醫藥文獻,以及宗教文獻如佛經道藏中的記載有何異同?本書一一剖析,並探討相互的牽扯與關聯。
作者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退休)。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埃及學博士。專長是古代埃及史、中國古代宗教社會史以及比較古代史。曾在中央研究院及美國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葛林耐學院等地工作教學,是少數能夠從事埃及學及漢學研究的學者,近來亦致力於比較古代史的研究。專書有:《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尼羅河畔的文采 ;古埃及文選》、《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法老的國度》、Wine and Wine Offering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Daily Life in Ancient China; Ghosts and Religious Life in Early China 等。
序
序
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更多的了解人類社會,過去的人做了什麼,如何做的,又為什麼做,有些什麼結果和影響。這些問題的解答,最後都關係到對人性的了解。由於研究者能掌握和利用的資料基本上只是極少數的片段,我們必須要承認,許多時候,研究的結論不是定論,而是在各種條件支持下所達到的比較合理的陳述或解釋。這一般性的原則或者了解,要落實到實際的例子上,會有哪些問題?問題仍然是人,是一個個的研究者,和一個個的讀者,他們的個人人格、氣質、興趣、知識、經歷,以及對於歷史研究方法的了解。
歷史研究的過程大致可以用以下的幾個層次來描述:
一、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可稱為歷史。
二、發生過的事,有些有留下痕跡。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如果有些痕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可稱為史料。史料不等於歷史,但人們可以藉著研讀史料來推測某些歷史事實。
三、單獨的歷史事實不構成歷史真相,但是一連串的歷史事實有可能構成對歷史真相的了解。研究者在各種史料中選擇一些材料,來構成對某個歷史事件或者時段的描述,一般可以稱為歷史寫作。寫作的結果,可稱為歷史知識。歷史知識是史家解釋史料或排比個別歷史事實而得到的結果。
四、歷史事實不等於歷史知識,歷史知識是對歷史真相的描述,它有可能接近一部分的歷史真相,但不是無條件等於歷史真相。
五、歷史知識是被動存在的,讀者對歷史知識的利用,是主動的,是會造成後果的。也就是說,歷史寫作的發生作用,是作者和讀者共同造成的。
歷史寫作的題目是如何決定的?什麼值得寫?什麼不值得寫?這是研究者個人必須釐清的。客觀的說,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但由於人是有記憶的動物,記憶造成人的自我認同,人也靠記憶(加上理性)形成個人價值觀,而社會集體記憶則形成文化認同,這使得了解過去發生過的事變得重要。在人與人之間,承認共同的記憶,是形成社群的基本條件。如果各人對於曾經發生過的事有不同的記憶,那麼就必須設法達到一個共識,否則無法共同生活。顯然,如果有人認為他的記憶比別人正確,同時,他又可以設法讓別人同意他的記憶,那麼一種共同的群體記憶就逐漸的形成。但人要如何讓別人同意他的記憶是正確的,是真正曾經發生過的事?這就牽涉到人類社會的一些現實,也就是記憶權威的建立造成了共同的歷史記憶。可想而知,這樣的歷史記憶,不等於真正發生過的事情。因為這是用一種記憶壓過了或者取代了另外一種記憶。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作用,就是或者強化某種歷史記憶,或者改變某種歷史記憶。當然很多時候歷史研究也在發掘或者形成新的歷史記憶。同時,即使是有相同的記憶,各人對於那記憶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如何解讀,則是進一步的問題。
所以歷史研究是一種兼有主觀和客觀兩種因素的活動。材料的被發現可以是一種客觀的活動,但是如何利用這些材料來重建對於過去曾經發生的事件的描述,就是主觀的活動。
因此,什麼樣的題目值得做,是要看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取向。沒有任何題目是值得或者不值得做的,關鍵在於研究者所提出他以為值得做的理由,是否具有說服力。當然這是假設研究者是獨立進行研究,而不是由其他人或機構指定題目。但有沒有說服力是兩方面的事情:論者的文化社會背景,以及接受者的文化社會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某種說法如果具有說服力,常常不一定完全是說法的內容有理,而是誰在說。新的說法代替了舊的說法,不一定代表新的說法在內容上比舊的說法更有解釋力或者合理性。是的,要看是誰在說,是誰在聽。
從事歷史寫作的人,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他人接受,而不是被拋棄。即使一時不被接受,仍然有機會在將來被接受。這是說,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是根據可靠的材料,以及盡可能理性的態度和邏輯的推論而完成的。當然,研究的結果最後必須受到同行的檢驗。至少在一段時間一個地區之內,同行的檢驗可以保障研究者的作品不是個人的幻想或扭曲事實的結果,或者用錯資料,了解資料不足,等等問題。至於整個研究社群是否會受到政治或社會因素的干涉或者影響,以至於整體社群都處於一種(在另一種立場看來)偏見之中,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麼歷史寫作的目的是什麼?這可能沒有什麼單一的答案。因為每個作者都會有自己的選擇,自己的理由和目的,不論是為了好奇、為了了解某些人事的所以然,甚至為了某些特定的理由(我們不必列舉,但不外名利、理念、展演等等)。
歷史研究及閱讀這種活動,又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私下的,或者公開的。讀者在讀歷史作品時,可以是一種私下的活動,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滿足和啟發。但當讀者想要利用他的歷史知識去做些什麼,說些什麼,那就不一定是私下的活動,因為歷史知識常常是人們行動背後的動力,不論是私下或者公開。同樣,歷史寫作本身也許是私下的活動,但其實也是公開的活動,因為作者通常期待作品可以公開出版,供大眾閱讀。作為歷史知識的創造者,歷史作家在理想上應該要能夠遵循一條原則,即其所產生出的歷史知識,是基於歷史事實,而不是偽造出來的。也許有人認為,寫出盡量接近真實的歷史,這是歷史家的責任,因為他們寫下的東西可能會促使讀者進行某些活動,進而對社會造成影響。這是假設說,不真實的歷史寫作,是對社會文化有害的。史家寫作,就像法官判案,當然應該追溯案子發展的歷史,才能還原案情真相,使罪犯得以伏法,正義得到伸張。當然,一個史家即使是用了完全真實的歷史事實,結果仍然寫出一篇不真實的歷史敘述,這是完全可能發生的。這是因為,歷史事實雖然是客觀存在的,真正絕對客觀的歷史知識可能並不存在。所有的歷史知識都是來自史家對史料的了解和解讀,因而也就難免會有個人的偏見和疏失。何況,許多時候,寫歷史的人會為了某種目的而操弄史料,甚至故意曲解史料,以創造一種適合特定目的之歷史知識和歷史記憶。更何況,史家如何寫,不表示讀者會如何理解,或者讀者會如何利用他們讀到的歷史。
應該避免的事,是史家宣稱自己的作品已經揭露了所謂歷史的真相,描述了歷史發展的全貌。這不是說,史家不必追求歷史的真相,而是要用反省的態度承認,史家所能做到的,只是盡可能以誠實的態度去追求真相、接近真相。這誠實的態度包括承認個人可能有的文化偏見,承認所使用的材料不見得完備,了解不見得合適,並且願意接受同行的檢視。歷史寫作的功用主要不是為了娛樂讀者(雖然那也可以是一種作用),也不是為了表達高深的哲理(雖然不少史家也許私下如此希望其作品有哲學的深度),而是提供負責任的歷史敘事(儘管那不見得等於所謂的歷史真相),或者說,提供人類社會一種相對可靠的集體記憶,以供人們在充滿無數「事實」的記憶之海中摸索一條可靠的去路,並為社會的存在建構一個可靠的基礎。如果史家不認為自己有責任盡量提供接近真實的歷史,就像法官不重視追尋案情的發展,那不如去寫小說。因為,至少小說作者可以從自己所了解的人性去描述一段故事,也有可能掌握一個時代的歷史真相。不是有人說嗎?歷史作品中除了人名地名和時間之外,沒有真相,而小說中除了人名地名和時間之外,就是真相。我們不必被這種比較極端的說法所困擾,但它的確說出一些重要的現象。最可怕的,是有一類所謂的歷史家,即使明知事實為何,仍不惜扭曲事實,以書寫真實的歷史為名,為特定的立場提供偽證,以遂其私利。
總之,上面這些想法,是為了導出一個理念:歷史研究者如果能夠反省自己的工作是在什麼樣的文化脈絡及思想框架中進行的,這脈絡和框架有什麼特性,也許可以更客觀的評量個人的工作成果和思考方式的限制。這想法是否過於一廂情願?的確有可能,但看個人做什麼樣的選擇。
回顧本書的寫作,始於三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三十多年後,因為偶然的機緣重拾舊作,加以擴充,成此小書。本書既無意於做一個全面的、地毯式的描述,只希望藉著這個相當特殊的題材來挑出一段較少受注意的歷史,為那汪洋的歷史大海投入一滴墨水。至於這段故事是否會被讀者接受而造成任何的改變,則有待來日。
最後,謹以本書獻給我的家人秉真、歆笛、歆嵐,並紀念古今中外無數曾遭構陷的受害者。
導論
最近幾十年間,歷史研究發展出許多新的議題、新材料和新方法。社會和文化史有了長足的進步,學者們嘗試跳出國別史與政治史的框架,從全球的角度,帶入多重線索和跨學門的思考路徑。社會史不再是,或者不只是關切社會階層的結構和功能,而是關於宗教、文化和政治等等因素如何共同造成了社會的演進。宗教史也不只是討論宗教的範疇,如儀式、神學、教條等等,而是考量政治、經濟,或者大眾心態如何影響了宗教的發展,或者宗教與其他因素的互動關係。
在有關早期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方面,類似的趨勢也愈來愈明顯。近來有關中國宗教的研究,就有不少是從跨學科的角度出發的。本研究也希望由這種跨學科的角度出發來研究一個跨越宗教,政治,大眾心態等等因素的題目,即討論由漢到唐所謂的巫蠱之術在宮廷政治中的角色,以及此現象所反映出的諸多文化和社會問題。
對漢代歷史稍有了解者大多至少聽過漢武帝晚年發生的巫蠱之禍。在那次事件中,數千人喪命,太子自殺。由於此事件的慘烈,它成為後世史籍經常提及的例子,而巫蠱之術也成為以下數百年宮廷鬥爭的新工具,對後世宮廷政治、社會記憶,以及宗教心態均造成一定的影響。東漢學者桓譚(西元前二三—前五六)對漢武帝巫蠱之禍有以下的評論:「〔漢武帝〕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這說法認為巫蠱之禍的主因是武帝個人的迷信和消耗國力之故。但當代學者的研究顯示,巫蠱之禍不只是武帝個人的錯誤所造成的家庭悲劇,更是複雜的個人恩怨、宮廷派系之間權力鬥爭、皇位繼承、社會動盪、迷信和武帝個人的精神狀態等等因素的綜合結果。社會中流行的有關巫蠱的信仰,加上謠言在宮廷內外的流傳,更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而巫蠱遂成為所有這些因素發酵之後的藉口或者引爆點。
不過,武帝時的巫蠱之禍只是許多類似的事件中最著名的。由漢到唐,甚至到近代,史籍記載了許多發生在宮廷之間的巫蠱事件,大多牽涉到皇親國戚及政府官員,其中又以漢唐之間最為頻繁。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法律和宗教環境滋養了或鼓勵了巫蠱的信仰和行為?這些事件既然延續如此之久,是否有何模式?這些事件對於我們了解宗教和社會的發展有何意義?顯示出當時的宗教心態是什麼?同時,官方史籍的記載和私人記載、方志、醫藥文獻,以及宗教文獻如佛經道藏中的記載有何異同?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研究西歐歷史上的巫術的學者指出,有關巫術的現象必須由多重的角度出發,以包括不同的研究徑路。在中國,從政治史的角度看,記載在史書中的巫蠱事件代表的是中國宮廷政治中一種特殊的現象,因為巫蠱之術成為人們用以達成特定的政治目的、剷除異己、掠奪資源、獲得高位所使用的藉口及手段。從宗教社會史的角度來看,如果要了解為什麼巫蠱之術會被認為是一種極大的惡行,我們就必須探究當時的宗教心態和社會心理。我們必須辨識當時流行的宗教信仰,不論是佛道或民間信仰,和巫術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檢視佛道二教的理論和作為,看他們如何解釋他們的儀式行為和巫術之間的不同之處。如此就有可能建立對大眾心態的理解。從大眾心理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應對謠言的傳播和巫術的信仰之間的因果關係有所了解。從人類學的角度,我們不但應該要分析不同形式的巫術,也要檢討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中巫術的施行在理論上應該如何分析。
根據以上的理解,我們又應該提出一些關於巫術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宗教脈絡之基本問題。首先是,誰是巫者?所謂的巫蠱包括了什麼活動?什麼論述?施行巫蠱之術的動機為何?其次,是誰指控別人行使巫蠱術。那些指控別人行巫術的人真的相信有巫術嗎?或者,那些指控其實是包裹在半信半疑之中,同時夾雜了惡意和妒嫉?還有,那允許巫蠱之術被揭示或發現的機制是什麼?因為巫蠱術原本應該是在祕密之中進行的。那麼,這消息走漏或者揭露是否有某種模式?由於巫蠱事件通常會導致被控行巫蠱者的悲慘下場,我們應該知道那些被控告行使巫術的都是些什麼人,而被巫術所害的人又是些什麼身分。在事件之後,是哪些人得逞,哪些人得利?由於巫蠱之術經常牽涉到女性或者女巫,那麼巫蠱是否和施行者的性別有直接或密切的關係?我們能否由這些事件觀察到女巫和社會中女性地位的關係?又由於其實許多社會中亦有男巫存在,那麼該如何解釋?
我們還可問有關巫蠱事件的觀察者的問題:歷代作者對巫蠱的評論是如何的?是否在不同的時代有所不同,而這不同是否又可以反映當時的文化和智識環境?而且,與巫蠱術相關的法律規定是否在不同的時代也有不同?最後,各個宗教傳統是如何定義,又如何看待巫術的?這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巫術在某種意義之下是一種招引鬼神之助的活動,因而無可避免和社會上一般宗教心態有關係,且可能侵犯了宗教的權威。
再其次,我們也需要了解社會上的醫療狀態,是否當時的醫療知識可以幫忙人們了解而去除對於蠱的恐懼,或者加強了對蠱的信仰?在醫療專業人士之中,是否有對於蠱的共識?這共識又是否對社會一般人的知識環境有影響?
漢武帝時候的巫蠱事件顯示,造成巫蠱之禍的因素很複雜,包括個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集體對巫術的恐懼、臣子之間的鬥爭、派系傾軋、皇位繼承的矛盾等等。因此,應該探討各個案例的細節,將以上的問題應用到這些案例之上,看看是否可以發現某些行為模式,以幫助我們了解或想像一些資料比較缺乏的例子可能是如何發生或進行的。這樣的研究,必然是要採取跨學科的路徑,它必須要關注整個社會文化環境,才有可能了解巫蠱事件在宮廷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當然,這些應該研討的問題在本書中不見得能完全得到解答,但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正是要提出值得討論的問題,以促進我們對歷史和人類社會了解的深度。
對於熟悉歐洲近代早期獵殺女巫的歷史的學者而言,中國古代的巫蠱事件也可以提供一個跨文化比較的例子。當然,歐洲的獵巫主要是發生在基督教社會中,牽涉的主要是普通人,而有關女巫的文獻資料基本上是各城市的檔案和教會的紀錄。但學者如何去檢視資料,如何考量這些資料的意圖,以及控告及捕捉女巫的人物和機構的動機,都是有用的關於研究方法的參考。同時,不論是在歐洲或中國,巫術都被視為是異端行為,嚴重的冒犯了教會或者皇帝的權威。因而權威控有者如何看待巫術,巫術又如何被人們利用來打擊異己,是雙方共同的問題。本研究因而也會設法進行一些比較的討論,以期更深入的了解社會中信仰、政治和大眾心態之間的互動關係。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巫蠱之源起
第三章 漢代之巫蠱與宮廷政治
一、巫蠱之起
二、征和巫蠱之禍
三、巫蠱之繼續發展
第四章 六朝隋唐之巫蠱與民間信仰
第五章 人物心態與社會脈絡
一、施蠱者與被害人之身分分析
二、巫蠱事件反映之社會及宗教心態與現實
第六章 結論:中外巫術之比較考量
參考書目
索引
書摘/試閱
本研究所界定之主要討論對象,為由漢代到唐代以巫蠱之術害人之歷史記載,而並非所有關於巫術之事,或者關於巫覡之記載。作為一種黑巫術,巫蠱在現代人的概念中是邪惡的、帶有神祕性的害人之方法。但現代中文中所謂的巫蠱,其參考系統大多為西南少數民族中流行的蠱,不少學者已經有所論述。
然而在古代,巫蠱二字的意義並不完全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完全一樣。所謂巫蠱與祝詛為兩件事。巫蠱又原為二事,巫為巫術,蠱為病痛或病毒,兩者原無關係。以巫術之施行而令人中蠱毒,則為巫蠱。祝詛之術,則為以呪術之施行達到令人生病或死亡或遭禍之目的,其中不一定有蠱毒。然而巫蠱祝詛合而觀之,均為以巫術手段以達到加害他人之目的,可以黑巫術一詞統括之,在本文的討論中,將巫蠱與祝詛當作同一件事來看。因為到了漢代,實際上人們也常常認為兩者是同一回事。巫蠱祝詛之現象,為世界各文明中常見,其根源,有部分為人生理和疫病之自然因素,另一部分則為宗教中對鬼神力量之信仰,以及人因社會制約而產生的各種心理因素。
在古代中國,最早有關蠱的記載見於甲骨文中,當時是用以描述一種致病的原因。由於蠱字的構形為皿中有蟲,其基本的意義不外是某種病蟲為害,而且可能與飲食有關。不過此時所謂的蠱,應該已經是帶有某種比較神祕性、不可見的病因,因為以一條牙齒疼痛的資料來看,「有疾齒,唯蠱虐。」胡厚宣引用此條論殷人疾病時,以為卜辭中之蠱為毒物所致。就文意而言,此時的蠱字應指的是一種致病的因素,而不專指與腸胃有關的病。不過無法得知此等病痛是否為造蠱者所施放而引起的。《左傳》昭公元年記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女,陽物而晦時,涇則生內熱惑蠱之疾。」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在這段看來有些混亂的敘述中,可以注意的是,醫和所說的「疾如蠱」,是說晉侯的疾病的徵象有似蠱疾,是由於近女色所造成。這種近女色造成的疾病,不是鬼魅作祟,也不是由於飲食所造成。反過來看,這也就等於說蠱是由鬼和食物造成的疾病。「於文皿蟲為蠱」,意思應指器皿中食物腐敗生蟲稱為蠱,也就是蠱字造字的本意,是和腐敗的食物有關。「穀之飛亦為蠱」指的是穀物生蟲飛出的現象,也可稱為蠱,但已經是引申義,所以說「亦為蠱」;「女惑男」為蠱,其實是說由於近女色而產生的虛弱之疾。又說「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則此處之蠱亦為引申義。《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這裡的蠱字也是指的女色淫惑,但是此處是男子設法令女子犯淫惑之罪。至於宣公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的蠱是否如杜注所說「惑以喪志」,就不得而知了。至於「風落山為蠱」,則為另一引申義。《周易》有蠱卦:「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說文解字》段注蠱字下引:「序卦傳曰,蠱者事也。伏曼容注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看來在許慎的東漢時代,蠱字用為蠱惑之意,應該已經是一般公認的用法。但這並不違背蠱字的原意,即造成疾病的病毒。再者,醫和的說法間接指出蠱病和鬼有關係,也即是與害人的巫術有關。《侯馬盟書》中有一例,殘存詛蠱二字,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將祝詛與蠱相聯的例子。但是,此例看來可能只是咒詛者希望對方得蠱疾,不一定有放蠱毒的行為。我們可以推測,在商代,蠱作為一種病因,可能已經具有某種神祕的性質,成為人們懷疑和懼怕的對象。這種觀念,可能一直在中國西南邊境少數民族地區流傳,因而學者指出,納西族東巴圖像文字中之瘟神作容器中放二條蟲,應即蠱字在東巴文中的體現,這與商代甲骨文的造字理念是一致的。
在《周禮》中,秋官庶氏的職掌為:「掌除毒蠱。以攻說襘之,嘉草攻之。」據鄭玄注,攻說為一種祈祀,而嘉草則可能是藥草。如此,處理蠱之方式顯示人們將蠱視為一種必須用宗教和醫藥兩種方式來解決的問題。這其實與古人治療任何其他疾病一樣,因為在當時人的心中,人之所以得病,其來源本就有由於鬼神降災,以及物理生理因素兩方面。秦簡《日書》記載,如人無故得病,其解除方式常常以各種相應之儀式為之。馬王堆《五十二病方》中治病的方法,一方面施以藥劑,另一方則誦咒語,也是同樣的心理。同時,可以推測,《周禮》雖是部古代政治制度的理想建構,但它將除毒蠱的工作特別立一個官職,至少顯示當時觀念中,毒蠱是有似一種威脅公共衛生的問題,必須由政府處理。但是《周禮》中的蠱,不論是否為病名,或者為某種惡靈,都似乎尚未與祝詛之術聯在一起。
《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大約在戰國中晚期,其中多次提到服食某些東西可以不受蠱疫侵襲,譬如《中山經》中有一段:「……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類似的段落不必一一列舉。這些材料可以提供一些佐證,指出當時人概念中的蠱是可以經由服食而解決的病痛,似乎不見得必須與宗教活動發生關係。一直到秦統一之前,蠱災一詞,指的應該都是某種害人的惡靈或惡氣,但是這蠱看來並不是有人故意放來害人,而比較像是自然流行的疾病和惡靈等。例如《史記》中記載:
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注云:「磔,禳也。厲鬼為蠱,將出害人,旁磔立於四方之門。」這種在城門四隅用動物鮮血來抵禦蠱菑的方式,顯然有一種對厲鬼的相信,而「蠱菑」是厲鬼所造成的。類似的記載也可以在《禮記.月令》中見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後漢書.禮儀志》中著名的有關大儺的一段記載中,蠱也是一種可以被消滅的惡靈之屬:
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顯然這裡的概念是和周禮一致的,即蠱毒是政府必須處理的一種對公共衛生的威脅。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漢代時蠱的概念已經開始與祝詛之術聯在一起,成為巫者用來害人的工具。如此一來,巫蠱二字聯用,有了新的意義。如下文所論,由漢至唐,巫蠱一詞在史籍中不斷出現,成為漢唐宮闈政治中常見的插曲,也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之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