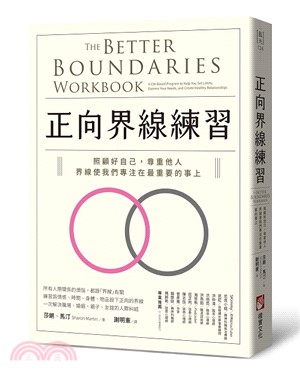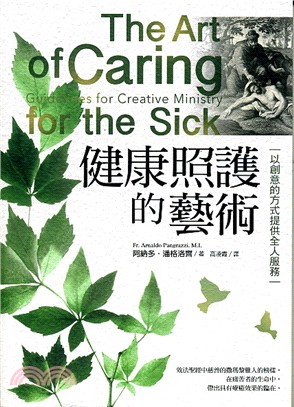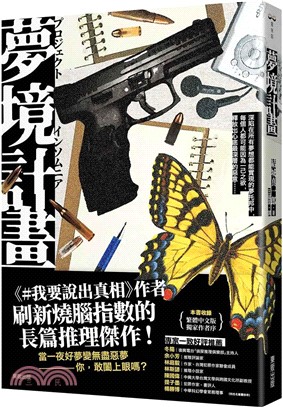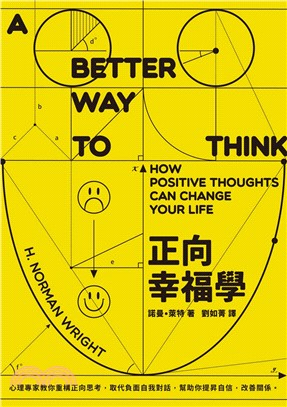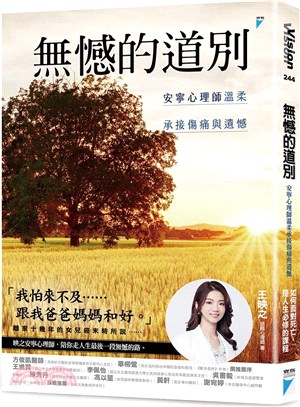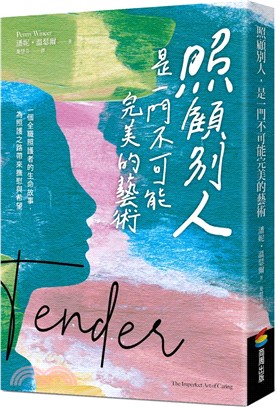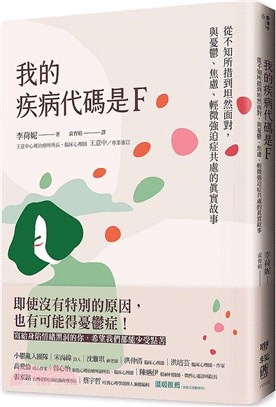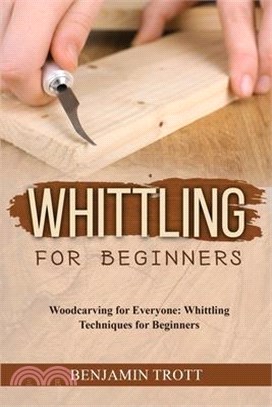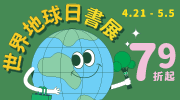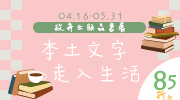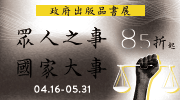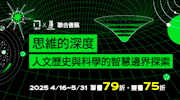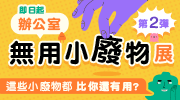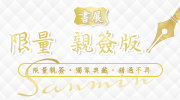論死亡與臨終(50週年經典紀念版):生死學大師的最後一堂人生課
商品資訊
系列名:綠蠹魚Read It
ISBN13:9786263612648
替代書名:On Death and Dying : What the Dying Have to Teach Doctors, Nurses, Clergy and Their Own Families
出版社:遠流
作者: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譯者:蔡孟璇
出版日:2023/09/27
裝訂/頁數:平裝/384頁
規格:21cm*14.8cm*2.1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時代雜誌〔20世紀最重要的百位思想家之一〕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 出版逾50年,生死學傳世不墜經典 }
✽ 面對死亡就是面對生命,人生在世是要學習無條件的愛
《論死亡與臨終》是20世紀晚期最重要的心理學研究資料之一。在這部1969年首度出版的經典著作裡,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醫師第一次探討了今天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悲傷五階段: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或憂鬱)與接受」。
本書能讓讀者深刻理解死亡的迫近如何影響病患,以及影響為病患提供照護的專業醫護人員、病患家屬與神職人員。伴隨著這分理解,庫伯勒─羅斯醫師更為所有人帶來了希望。
出版逾50年,《論死亡與臨終》迄今仍發揮其源遠流長的影響力,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生命末期相關議題的探討孕育出更開放的對話空間。
《論死亡與臨終》提供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的重要體驗──讓我們理解死亡,學習寬慰與療傷止痛的智慧。
✽ 專業媒體盛讚
「我今年讀到的關於生命倫理學的最佳書籍是1969年出版、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所著的《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讓我愛不釋手。」
──《美國生命倫理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能幫助我們在專業與私人生活上好好面對生命的最終章。」
──《醫療意見與評論》(Medical Opinion & Review)
✽ 本書特色
1.心理學與生命倫理學之重要研究著作。「悲傷五階段」於此書首次提出。
2.採用關懷生命的「傾聽與對話方式」,與個案探討生死議題。
3.50週年紀念版特別收錄「讀書會精選」與「進階討論指南」,協助讀者運用此書。
{ 出版逾50年,生死學傳世不墜經典 }
✽ 面對死亡就是面對生命,人生在世是要學習無條件的愛
《論死亡與臨終》是20世紀晚期最重要的心理學研究資料之一。在這部1969年首度出版的經典著作裡,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醫師第一次探討了今天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悲傷五階段: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或憂鬱)與接受」。
本書能讓讀者深刻理解死亡的迫近如何影響病患,以及影響為病患提供照護的專業醫護人員、病患家屬與神職人員。伴隨著這分理解,庫伯勒─羅斯醫師更為所有人帶來了希望。
出版逾50年,《論死亡與臨終》迄今仍發揮其源遠流長的影響力,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生命末期相關議題的探討孕育出更開放的對話空間。
《論死亡與臨終》提供了一個我們所有人都需要的重要體驗──讓我們理解死亡,學習寬慰與療傷止痛的智慧。
✽ 專業媒體盛讚
「我今年讀到的關於生命倫理學的最佳書籍是1969年出版、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所著的《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讓我愛不釋手。」
──《美國生命倫理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能幫助我們在專業與私人生活上好好面對生命的最終章。」
──《醫療意見與評論》(Medical Opinion & Review)
✽ 本書特色
1.心理學與生命倫理學之重要研究著作。「悲傷五階段」於此書首次提出。
2.採用關懷生命的「傾聽與對話方式」,與個案探討生死議題。
3.50週年紀念版特別收錄「讀書會精選」與「進階討論指南」,協助讀者運用此書。
作者簡介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醫學博士(Elisabeth Kübler-Ross, M.D. 1926-2004)
庫伯勒─羅斯醫師是現代安寧照護運動創始人之一。她的作品包括《用心去活》、《論哀傷》與《論死亡與臨終》等書。在《論死亡與臨終》書中,她首度提出悲傷五階段理論。
庫伯勒─羅斯醫師的作品全球銷售超過一千萬冊,並被翻譯成四十五種語言。《時代》雜誌將她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百位思想家之一」。
她在1977年被評選為「年度女性」,並在70年代被評選為科學界的「近十年傑出女性」。庫伯勒─羅斯資料館建立於史丹佛大學典藏部,她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大學的安寧緩和醫療計畫。
庫伯勒─羅斯醫師的堅毅和決心永遠改變了這世界面對臨終者的態度。孜孜不倦的她努力確保病患在獲得同情的同時保持尊嚴面對臨終,現已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照顧末期病人的準則。
她教導世人,面對死亡就是面對生命,人生在世是要學習無條件的愛。
庫伯勒─羅斯醫師是現代安寧照護運動創始人之一。她的作品包括《用心去活》、《論哀傷》與《論死亡與臨終》等書。在《論死亡與臨終》書中,她首度提出悲傷五階段理論。
庫伯勒─羅斯醫師的作品全球銷售超過一千萬冊,並被翻譯成四十五種語言。《時代》雜誌將她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百位思想家之一」。
她在1977年被評選為「年度女性」,並在70年代被評選為科學界的「近十年傑出女性」。庫伯勒─羅斯資料館建立於史丹佛大學典藏部,她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大學的安寧緩和醫療計畫。
庫伯勒─羅斯醫師的堅毅和決心永遠改變了這世界面對臨終者的態度。孜孜不倦的她努力確保病患在獲得同情的同時保持尊嚴面對臨終,現已成為許多西方國家照顧末期病人的準則。
她教導世人,面對死亡就是面對生命,人生在世是要學習無條件的愛。
名人/編輯推薦
【50週年紀念版──推薦序】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
艾拉.碧阿克醫師(Ira Byock, M.D.)
醫學教授.達特茅斯大學蓋塞爾醫學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at Dartmouth)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後時代,人們對疾病的態度一如整個美國社會的各個生活面向,充滿了樂觀主義與對抗的氛圍。經歷過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與韓戰的美國人,已經將無往不利、堅忍不拔的性格融入了積極而自信的美國面貌中。面對逆境時懷抱希望的態度,似乎也成為固有的美德,美式風格的一部分。
我們有絕佳的理由保持樂觀心態。物理、化學、工程等領域取得驚人的突破,以及對多數人來說最重要的,醫藥發展日新月異、突飛猛進。迄今仍致命的疾病,如肺炎、敗血症、腎衰竭與嚴重外傷等得到治癒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於是,疾病逐漸被視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感覺彷彿醫療科學就快要能阻止老化過程了(至少潛意識這麼覺得),甚至可能戰勝死亡了。
在這樣的文化裡,最優秀的醫生就是那些總是能找到某種治療方式來阻止死亡的醫生。在1950和1960年代,治療無效時,醫生鮮少會對病人承認,更經常在進一步治療其實弊大於利時,刻意不告知病人。醫師文化是「永不言死」這一立場的縮影,但醫生並非唯一一個如此假裝的人:生病的人與他們的家人,也全部不假思索地串通好,避免談及死亡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令人難過的是,醫師普遍低估了病重病患與疼痛搏鬥到最後的痛苦(經常不必要),因而疏於處理。一部分原因是當時醫生並未接受足夠的疼痛管理與處理其他症狀的訓練,此外也是因為醫生、病人及其家屬彼此心照不宣、一味維持表面陽光的虛偽態度。承認病人的疼痛加劇可能意味著承認他的病情惡化了。
那個時代的醫療文化是高度權威式的,病患的價值觀、偏好與優先考慮的事無足輕重。醫生告知病人他們所做的決定,病人只能被動接受那些決定。除了以對抗死亡的超群實力和聲望來定義最成功的醫生,同儕壓力也助長了普遍忽視病患痛苦的情況。儘管在人生最後的幾個小時裡,多數醫生都會開立足夠的嗎啡,讓病人不至於忍受劇痛而死去,但是由於擔心引起同事的側目與懷疑,他們也不敢給垂死的病人足量的藥物,好讓他們在生前最後幾個月盡可能舒服一點。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論死亡與臨終》一書,對當時的權威式體統與清教徒式極端拘謹的道德觀提出了挑戰。在那個醫護人員只用委婉說辭或拐彎抹角的耳語談論末期疾病的時代,有位醫生橫空出世,不但實際與病人討論他們的病情,更激進的是,還仔細傾聽他們的心聲。
庫伯勒─羅斯醫師與這部著作引起舉國關注,在醫療界與一般文化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單是藉由傾聽這個行為,便將生病與臨終這件事從疾病領域與醫師的管制區解放,一路直達生命經驗領域與個人的私密領地。我在大學時代,準備攻讀醫學專業的時候初次讀到《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當時,書中的訪談紀錄強烈震撼了我,這些內容清楚顯示出庫伯勒─羅斯醫師的善於傾聽,以及對病人毫無矯飾的友善態度。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促使人們改變其普遍的假設與期待,進而在短短幾年之內翻轉了臨床診療方式。庫伯勒─羅斯醫師的著作重新主張個人對生病與臨終擁有主權,重建了病人與其醫師或其他臨床工作人員的關係。突然之間,人們如何死去變得很重要。臨終病人不再被放逐到醫院走廊盡頭的邊疆病房了。《論死亡與臨終》實至名歸地成為安寧療護運動(hospice movement)的濫觴,並衍生出安寧緩和醫療這一新興專業,而它所颳起的一陣巨大改變風潮,幾乎蔓延了醫療與護理實務的每一個專業領域。舉例而言,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病人的疼痛強度已經成為除了體溫、脈搏、血壓與呼吸之外,每次都必須加以評估的「第五生命徵象」。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亦對人類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臨終之人」的經驗不再被「客觀化」,臨終的相關研究也無法再被貶低為屬於顯微解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或精神病理學的一部分。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醫師的這部開創性作品,反而為重病者的照護與其主觀經驗的探索,開拓出一個嶄新的領域。而這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對臨終與生命終期照護相關的量化研究(譯註:quantitative research,又稱定量研究)與質性研究(譯註:qualitative research,又稱質化研究、定性研究)產生興趣,研究的有效性獲得提升,從而加速了心理學、精神醫學、老年醫學、緩和醫療(palliative medicine)、臨床醫療倫理與人類學等各領域的進步。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儘管精通當時的精神病學理論,亦以此為榮,但她在理解病人經驗時,不會讓自己被佛洛伊德或榮格的概念所束縛。她所做的反而是讓受訪者的心聲與觀點來主導。她在訪談中讓受訪者以他們自己的話語解釋自己如何掙扎地活著,以及如何理解這場無可救藥的疾病。最讓庫伯勒─羅斯感興趣的心理動力學,是那些絕症患者與健康在世者之間的互動。
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庫伯勒─羅斯勾勒出她知名的「五個階段」,包括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或憂鬱)與接受,詳細描述了病重者一般會經歷的情緒狀態,以及他們用來理解這場不治之症並與之共存的調適機制。
庫伯勒─羅斯的理論普及化後成為所謂的「臨終階段」,但被批評是為臨終過程的階段套上一個公式化進程。任何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分辨,這樣的評論不但過度簡化了作者書中所述,也是不正確的解讀。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庫伯勒─羅斯清楚指出,這些情緒狀態與調適機制會以各式各樣的形態出現。她提到的訪談與故事裡,有人自然而然地經歷了最初的否認與孤立,然後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到最終接受自身處境或至少默認的這段過程,即使過程並不輕鬆。她也提到其他一些病人,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時,在否認或憤怒階段停滯不前。我們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遇見的人物與故事,在在說明了病重者與疾病帶來的不適、失能、疲憊、身體依賴,以及死亡逼近的衝擊持續搏鬥的現象不僅很普遍,而且很「正常」。我們也認識到,有些人雖然度過了否認或憤怒階段,但之後隨著病情加重,這些情緒狀態又再度出現。一個人的情感與情緒樣貌是複雜多變的,《論死亡與臨終》裡的訪談揭露出一些有時看似無法相容的狀態,例如否認與接受竟然可以共存。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對醫療保健及其相關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人民對生病與臨終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庫伯勒─羅斯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發表她的研究發現。雖然這些研究資料必能引起醫療專業讀者群的關注,她卻選擇為一般大眾而寫。或許她對「媒介即訊息」這樣的說法了然於心,這句話是另一位高瞻遠矚之士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其一九六四年的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書中所主張的觀點。(譯註:意思是人們理解一個訊息時,會受到其傳播方式的影響。)
我不知道當初庫伯勒─羅斯撰寫《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的時候,有多麼強烈的意圖要激起一場文化運動、改善臨終關懷照護,讓疾病與臨終回歸到個人生活之適當領域,但這些就是這本書實際做到的事。誠然,當時的《生活》雜誌將這本書稱為「給在世者的深刻教訓」。一點也沒錯。
人類生病經驗裡獨一無二的永恆主題,亦即知道生命終有一天會結束,讓《論死亡與臨終》這部作品與現今的讀者息息相關。作為一名醫師,我對於我們一路走了這麼遠的路感到驚訝不已,然而我們依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才能做到真正以人為本的醫療照護。這本書提醒我要傾聽,並以共同參與的夥伴身分與服務精神與那些重病患者接觸,因為他們正在經歷的這趟旅途,是沒有人會主動選擇,但所有人卻終將必須踏上的一趟旅途。
我以專業人員的身分重新閱讀《論死亡與臨終》時,身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與祖父的我,不禁再度感受到它在我個人層面上造成的巨大衝擊。
我們從《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認識的那些人,提醒著我們自己的生命終將一死,但他們也告訴我們,如何死去並非已經注定的,透過他們的選擇與他們所接受的照護品質,都可以讓它變得更好或更糟。我們看見人們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接受照護與死去,而有些方式確實對那些深愛他們的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經過了這些年,《論死亡與臨終》依然在呼籲我們採取行動,傾聽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並且發揮我們所有的知識與技能來回應──而且永遠要記得帶著一顆謙卑的心,與病人保持夥伴關係並懷抱慈悲心。
在這社會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中期,一位身形瘦小的瑞士裔美國精神科醫師大膽地為面臨生命終點的人們發聲。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為美國人豎起一面鏡子,讓它反映出他們對末期病人的態度、假設與行為,而人們並不喜歡鏡中的所見。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以《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作為媒介,將我們如何面對死亡這件事,加入了發生在環境、社會權益與醫療保健領域的文化革命議程裡。
情況從此改變了。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
艾拉.碧阿克醫師(Ira Byock, M.D.)
醫學教授.達特茅斯大學蓋塞爾醫學院(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at Dartmouth)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後時代,人們對疾病的態度一如整個美國社會的各個生活面向,充滿了樂觀主義與對抗的氛圍。經歷過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與韓戰的美國人,已經將無往不利、堅忍不拔的性格融入了積極而自信的美國面貌中。面對逆境時懷抱希望的態度,似乎也成為固有的美德,美式風格的一部分。
我們有絕佳的理由保持樂觀心態。物理、化學、工程等領域取得驚人的突破,以及對多數人來說最重要的,醫藥發展日新月異、突飛猛進。迄今仍致命的疾病,如肺炎、敗血症、腎衰竭與嚴重外傷等得到治癒已經是稀鬆平常的事。於是,疾病逐漸被視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感覺彷彿醫療科學就快要能阻止老化過程了(至少潛意識這麼覺得),甚至可能戰勝死亡了。
在這樣的文化裡,最優秀的醫生就是那些總是能找到某種治療方式來阻止死亡的醫生。在1950和1960年代,治療無效時,醫生鮮少會對病人承認,更經常在進一步治療其實弊大於利時,刻意不告知病人。醫師文化是「永不言死」這一立場的縮影,但醫生並非唯一一個如此假裝的人:生病的人與他們的家人,也全部不假思索地串通好,避免談及死亡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令人難過的是,醫師普遍低估了病重病患與疼痛搏鬥到最後的痛苦(經常不必要),因而疏於處理。一部分原因是當時醫生並未接受足夠的疼痛管理與處理其他症狀的訓練,此外也是因為醫生、病人及其家屬彼此心照不宣、一味維持表面陽光的虛偽態度。承認病人的疼痛加劇可能意味著承認他的病情惡化了。
那個時代的醫療文化是高度權威式的,病患的價值觀、偏好與優先考慮的事無足輕重。醫生告知病人他們所做的決定,病人只能被動接受那些決定。除了以對抗死亡的超群實力和聲望來定義最成功的醫生,同儕壓力也助長了普遍忽視病患痛苦的情況。儘管在人生最後的幾個小時裡,多數醫生都會開立足夠的嗎啡,讓病人不至於忍受劇痛而死去,但是由於擔心引起同事的側目與懷疑,他們也不敢給垂死的病人足量的藥物,好讓他們在生前最後幾個月盡可能舒服一點。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論死亡與臨終》一書,對當時的權威式體統與清教徒式極端拘謹的道德觀提出了挑戰。在那個醫護人員只用委婉說辭或拐彎抹角的耳語談論末期疾病的時代,有位醫生橫空出世,不但實際與病人討論他們的病情,更激進的是,還仔細傾聽他們的心聲。
庫伯勒─羅斯醫師與這部著作引起舉國關注,在醫療界與一般文化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單是藉由傾聽這個行為,便將生病與臨終這件事從疾病領域與醫師的管制區解放,一路直達生命經驗領域與個人的私密領地。我在大學時代,準備攻讀醫學專業的時候初次讀到《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當時,書中的訪談紀錄強烈震撼了我,這些內容清楚顯示出庫伯勒─羅斯醫師的善於傾聽,以及對病人毫無矯飾的友善態度。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促使人們改變其普遍的假設與期待,進而在短短幾年之內翻轉了臨床診療方式。庫伯勒─羅斯醫師的著作重新主張個人對生病與臨終擁有主權,重建了病人與其醫師或其他臨床工作人員的關係。突然之間,人們如何死去變得很重要。臨終病人不再被放逐到醫院走廊盡頭的邊疆病房了。《論死亡與臨終》實至名歸地成為安寧療護運動(hospice movement)的濫觴,並衍生出安寧緩和醫療這一新興專業,而它所颳起的一陣巨大改變風潮,幾乎蔓延了醫療與護理實務的每一個專業領域。舉例而言,到了一九九○年代晚期,病人的疼痛強度已經成為除了體溫、脈搏、血壓與呼吸之外,每次都必須加以評估的「第五生命徵象」。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亦對人類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臨終之人」的經驗不再被「客觀化」,臨終的相關研究也無法再被貶低為屬於顯微解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或精神病理學的一部分。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醫師的這部開創性作品,反而為重病者的照護與其主觀經驗的探索,開拓出一個嶄新的領域。而這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對臨終與生命終期照護相關的量化研究(譯註:quantitative research,又稱定量研究)與質性研究(譯註:qualitative research,又稱質化研究、定性研究)產生興趣,研究的有效性獲得提升,從而加速了心理學、精神醫學、老年醫學、緩和醫療(palliative medicine)、臨床醫療倫理與人類學等各領域的進步。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儘管精通當時的精神病學理論,亦以此為榮,但她在理解病人經驗時,不會讓自己被佛洛伊德或榮格的概念所束縛。她所做的反而是讓受訪者的心聲與觀點來主導。她在訪談中讓受訪者以他們自己的話語解釋自己如何掙扎地活著,以及如何理解這場無可救藥的疾病。最讓庫伯勒─羅斯感興趣的心理動力學,是那些絕症患者與健康在世者之間的互動。
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庫伯勒─羅斯勾勒出她知名的「五個階段」,包括否認與孤立、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或憂鬱)與接受,詳細描述了病重者一般會經歷的情緒狀態,以及他們用來理解這場不治之症並與之共存的調適機制。
庫伯勒─羅斯的理論普及化後成為所謂的「臨終階段」,但被批評是為臨終過程的階段套上一個公式化進程。任何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分辨,這樣的評論不但過度簡化了作者書中所述,也是不正確的解讀。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庫伯勒─羅斯清楚指出,這些情緒狀態與調適機制會以各式各樣的形態出現。她提到的訪談與故事裡,有人自然而然地經歷了最初的否認與孤立,然後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到最終接受自身處境或至少默認的這段過程,即使過程並不輕鬆。她也提到其他一些病人,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個階段時,在否認或憤怒階段停滯不前。我們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遇見的人物與故事,在在說明了病重者與疾病帶來的不適、失能、疲憊、身體依賴,以及死亡逼近的衝擊持續搏鬥的現象不僅很普遍,而且很「正常」。我們也認識到,有些人雖然度過了否認或憤怒階段,但之後隨著病情加重,這些情緒狀態又再度出現。一個人的情感與情緒樣貌是複雜多變的,《論死亡與臨終》裡的訪談揭露出一些有時看似無法相容的狀態,例如否認與接受竟然可以共存。
《論死亡與臨終》一書對醫療保健及其相關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人民對生病與臨終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庫伯勒─羅斯在《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發表她的研究發現。雖然這些研究資料必能引起醫療專業讀者群的關注,她卻選擇為一般大眾而寫。或許她對「媒介即訊息」這樣的說法了然於心,這句話是另一位高瞻遠矚之士馬歇爾.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在其一九六四年的著作《認識媒體: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書中所主張的觀點。(譯註:意思是人們理解一個訊息時,會受到其傳播方式的影響。)
我不知道當初庫伯勒─羅斯撰寫《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的時候,有多麼強烈的意圖要激起一場文化運動、改善臨終關懷照護,讓疾病與臨終回歸到個人生活之適當領域,但這些就是這本書實際做到的事。誠然,當時的《生活》雜誌將這本書稱為「給在世者的深刻教訓」。一點也沒錯。
人類生病經驗裡獨一無二的永恆主題,亦即知道生命終有一天會結束,讓《論死亡與臨終》這部作品與現今的讀者息息相關。作為一名醫師,我對於我們一路走了這麼遠的路感到驚訝不已,然而我們依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才能做到真正以人為本的醫療照護。這本書提醒我要傾聽,並以共同參與的夥伴身分與服務精神與那些重病患者接觸,因為他們正在經歷的這趟旅途,是沒有人會主動選擇,但所有人卻終將必須踏上的一趟旅途。
我以專業人員的身分重新閱讀《論死亡與臨終》時,身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與祖父的我,不禁再度感受到它在我個人層面上造成的巨大衝擊。
我們從《論死亡與臨終》一書中認識的那些人,提醒著我們自己的生命終將一死,但他們也告訴我們,如何死去並非已經注定的,透過他們的選擇與他們所接受的照護品質,都可以讓它變得更好或更糟。我們看見人們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接受照護與死去,而有些方式確實對那些深愛他們的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經過了這些年,《論死亡與臨終》依然在呼籲我們採取行動,傾聽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並且發揮我們所有的知識與技能來回應──而且永遠要記得帶著一顆謙卑的心,與病人保持夥伴關係並懷抱慈悲心。
在這社會動盪不安的二十世紀中期,一位身形瘦小的瑞士裔美國精神科醫師大膽地為面臨生命終點的人們發聲。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為美國人豎起一面鏡子,讓它反映出他們對末期病人的態度、假設與行為,而人們並不喜歡鏡中的所見。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以《論死亡與臨終》這本書作為媒介,將我們如何面對死亡這件事,加入了發生在環境、社會權益與醫療保健領域的文化革命議程裡。
情況從此改變了。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
目次
〔50週年紀念版.推薦序〕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艾拉.碧阿克醫師
〔前言〕
一場互惠的體驗,能對人類心智運作有更深入認識──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第1章 論對死亡的恐懼
第2章 面對死亡與臨終的態度
第3章 第一階段:否認與孤立
第4章 第二階段:憤怒
第5章 第三階段:討價還價
第6章 第四階段:沮喪
第7章 第五階段:接受
第8章 希望
第9章 病患的家屬
第10章 末期病患訪談實錄
第11章 死亡與臨終研討班獲得的迴響
第12章 末期病人的治療
〔附錄〕
讀書會精選──導讀《論死亡與臨終》
有尊嚴的死亡──相關公共議題討論
我們都因此而變得更好──艾拉.碧阿克醫師
〔前言〕
一場互惠的體驗,能對人類心智運作有更深入認識──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第1章 論對死亡的恐懼
第2章 面對死亡與臨終的態度
第3章 第一階段:否認與孤立
第4章 第二階段:憤怒
第5章 第三階段:討價還價
第6章 第四階段:沮喪
第7章 第五階段:接受
第8章 希望
第9章 病患的家屬
第10章 末期病患訪談實錄
第11章 死亡與臨終研討班獲得的迴響
第12章 末期病人的治療
〔附錄〕
讀書會精選──導讀《論死亡與臨終》
有尊嚴的死亡──相關公共議題討論
書摘/試閱
第1章 論對死亡的恐懼
我不祈求在遭遇危險時獲得庇護,
但求面對危險能無所畏懼。
我不祈求痛苦止息,
但求讓我擁有一顆征服痛苦的心。
我不尋求生命戰場裡的盟友,
但求自身擁有力量。
我不焦急害怕地渴望得救,
而是盼望耐心能為我贏得自由。
請應允我,不要讓我變成一個懦夫,
只在成功時沉浸於你的仁慈
而是讓我在失敗時找到你緊握住我的手。
──泰戈爾《採果集》(Fruit-Gathering)
在過去幾個世代裡,傳染病造成了人命的重大損失。嬰兒時期與童年的早夭現象很常見,每個家庭裡或多或少都有早夭的成員。醫藥在過去數十年來歷經了巨大的變化,疫苗接種的普及實際上根絕了許多疾病,至少在西歐和美國的情況是如此。化療,特別是抗生素的使用,讓感染性疾病的致死率不斷下降。更完善的兒童照護與教育也發揮效果,使兒童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過去在年輕人與中年人族群間造成高死亡率的疾病,也已經能夠克服。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從而產生了罹患高齡相關之惡性腫瘤與慢性疾病的龐大族群。
兒科醫師要處理的威脅生命的急性狀況減少了,但是身心失調和有行為問題的患者卻越來越多。內科醫師的候診室裡,有情緒問題的患者比以往都要來得多,但他們的年長患者也越來越多,他們不但努力拖著體力衰退的身體與年齡帶來的各種限制努力活下去,也必須面對寂寞和孤立帶來的痛苦折磨。這其中有多數人都是精神科醫師看不見的。他們的需求必須透過其他專業人員的誘導才能獲得滿足,例如牧師與社工等。正是為了這些人,我試圖勾勒出過去數十年來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人們心中日益懼怕死亡,情緒問題越來越多,更迫切需要理解並處理死亡與臨終的問題。
若回顧歷史並研究古老的文化與民族,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死亡對人類來說向來都是一件令人厭惡的事,或許將來也永遠會如此。從精神科醫師的觀點來看,這十分容易理解,而且我們的一個基本認識或許能充分解釋這件事,那就是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死亡對我們而言永遠不可能發生。我們的潛意識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命真的會有結束的一天,而如果我們的生命必須結束,這個結束總是被歸咎於外在他人的惡意介入。簡而言之,在我們的潛意識頭腦裡,我們只可能被殺死,自然死亡(壽終正寢)或因年邁而死亡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死亡本身就容易使人聯想到惡意行為、可怕事件、某種本質上會招來報應與懲罰的事。
記住這些根本的事實是個聰明的做法,因為這在了解我們病患一些最重要卻難以理解的溝通問題上,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必須理解的第二個事實是,在我們的潛意識頭腦裡,我們無法分辨一個願望和一個行為之間有何不同。我們都能察覺到,在我們最不合邏輯的夢境中,兩個完全相反的論述能並行不悖──這在我們夢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我們的清醒狀態下,卻難以理解且不合邏輯。如同我們的無意識頭腦無法分辨憤怒地想要殺死一個人的願望和實際去殺人的行為有何不同,年幼的孩童也無法分辨這兩者之間的不同。因為媽媽沒有滿足他的需求而憤怒地希望媽媽去死的孩子,在媽媽真正死去的時候會受到極大的創傷──即使這件事與他那個毀滅性願望在時間上並無密切關聯,但他永遠都會認為,他必須為失去母親負起部分或完全的責任。他永遠都會對自己說(但鮮少對別人說)──「是我幹的,我必須負責,我很壞,所以媽咪才會離開我。」要記得,孩子如果是因為父母的離婚、分居或遺棄而失去其中一位父母,他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死亡通常被孩子視為一件暫時的、非永久性的事,也因此和離婚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在離婚狀況下,他可能會有機會再見到其中一位父母。
許多父母都記得孩子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會把狗狗埋起來,明年春天花開的時候,牠就會醒過來。」或許也就是這同樣的動機,驅使著古埃及人供應亡者食物與物品,也讓古老的美國原住民將他們的親人和其所有物埋葬在一起。
隨著我們年紀漸長,開始明白我們的全能之神並非真的那麼全能,而且我們最強烈的願望還不足以強大到讓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之後,害怕自己間接導致親人死亡的恐懼與罪疚感也會隨之減輕。然而,恐懼只有在尚未遭受強力挑戰之前才暫時得以減輕。它所殘留的痕跡依然可以每天在醫院走廊上見到,在喪親者周遭的人身上見到。
一對夫妻很可能長年爭吵不休,但是當另一半過世時,倖存的另一半會抓著他的頭髮,大聲哀號,捶胸頓足,充滿悔恨,恐懼又痛苦,因而比以往更害怕自己的死亡,而且依然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法則──「我對他的死有責任,所以我也會遭到報應,痛苦地死去。」
或許這樣的認識有助於讓我們了解許多施行數百年之久、目的是讓眾神息怒,或在有些例子裡是讓一些人息怒的古老習俗與儀式,它們想藉此減輕預期的懲罰。我想到了古代儀式中的骨灰、破爛的喪服、面紗,以及哭喪女(譯註:類似台灣俗稱的孝女白琴)──這些都是為了要讓你同情身為哀悼者的他們,這樣的表達方式呈現出的是悲痛、哀傷與羞恥。如果有人哀痛不已,捶胸頓足、拉扯自己的頭髮、拒絕進食,這是企圖自我懲罰,以躲過或減輕自己間接導致親人死亡而預期會遭受的懲罰。
這份哀傷、羞恥與罪疚感與狂暴的憤怒情緒其實相距不遠。哀傷的過程總是包含了一些憤怒的成分。由於沒有人想要承認自己對亡者感到憤怒,因此這些情緒經常遭到偽裝或壓抑,拖長了哀悼期,或是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必須記得的是,我們不應對這樣的感受妄加評斷,認為那是不好的或可恥的,而是要去了解它們真正的意義與來源,視其為人性的一部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會再次使用小孩子作為例子,包括我們內在的小孩。一個剛剛失去母親的五歲孩子會為母親的消失責怪自己,還會因為母親遺棄他而且不再能滿足他的需求而對她生氣。於是,亡者既讓孩子深愛又渴望,同時也因這份嚴重的剝奪感,而讓他懷著同樣強度的恨意。
古希伯來人將亡者的遺體視為不潔的,不能觸碰。早期的美洲原住民也談到了惡靈,他們會往空中射箭以驅趕惡靈。許多其他文化也有處理「壞」亡者的儀式,這些都源自這種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憤怒感,只是我們不喜歡承認這一點罷了。墓碑的傳統可能源自這種想要將惡靈鎮壓在地下的意圖,哀悼者放在墳墓上的小石子,也是同樣想法所遺留的象徵。雖然我們會將軍葬禮中的鳴槍禮視為對亡者最後的致敬,但這和美洲原住民所使用的、將矛與箭射向空中的儀式具有同樣的象徵意義。
我提出這些例子是為了強調人類基本上並沒有改變。死亡依然是一個令人懼怕的恐怖事件,即使我們自認為已經在許多層面上掌握了這件事,對死亡的恐懼仍是一種普世的恐懼。
有所改變的,是我們應對並處理死亡、臨終過程以及臨終病人的方式。
我在一個科學不怎麼發達的歐洲國家長大,在那裡,現代科技才剛開始運用在醫學上,人們的生活方式幾乎和半世紀前沒什麼兩樣,我也因此有機會在短時間內研究人類進化的一部分過程。
我記得自己小時候曾經歷過一場農夫的死亡。農人從樹上摔下來,預計活不久了。他只是簡單地要求在自家辭世,而這個願望毫無疑問獲得了應允。他將每個女兒都叫進臥室,一一和她們講了幾分鐘的話,然後忍著劇痛,靜靜地處理自己的後事,分配自己擁有的財物和土地,但全部都要等到他妻子追隨他與世長辭之後才能分家。他要求孩子們分擔他在意外發生前所從事的一些工作、責任與差事,還邀請朋友前來探望他,親自向他們道別。雖然我還是家中的小孩,但他並沒有將我和我的其他姐妹排除在外,我們都能參與家族的整個準備過程,我們也都可以一同哀悼,直到他過世。他與世長辭之後,留在了自己深愛的、一手打造的家,那個自己生前生活並熱愛的住所,身旁環繞著鮮花,親朋好友和鄰居都來為他送上最後一程。現今,在那個國家,依然沒有設置虛幻的靈堂,沒有採用任何遺體保存技術,也沒有假裝亡者只是在安眠的虛偽化妝術,只有疾病造成的嚴重容貌毀損,才會用繃帶遮掩,也只有因傳染病過世的案例,才不會於下葬前將遺體放在家中。
我為何要描述這些「老派」的習俗呢?我想它們顯示了我們對死亡結局的接受,既幫助了臨終病患,也幫助了他的家人接受失去摯愛的事實。如果病人被允許在他心愛的熟悉環境中結束生命,他要做的調適會比較少。他的家人已經十分了解他,可以用一杯他最喜愛的紅酒取代鎮定劑,或為他遞上一碗家常味的熱湯,幫他開開胃,讓他能啜飲幾湯匙的分量,我想這一定都比輸入液體更愉悅吧。我不否認鎮定劑與輸液的重要性,也因自己身為鄉村醫師的經驗而完全理解它們有時是救命工具,時常難以避免,但我也知道,耐心、熟悉的人與食物這三者,能取代許多瓶的靜脈輸液,原因很簡單,這麼做能在節省人力與個別護理的情況下,滿足病患的生理需求。
孩子獲准於死亡發生期間待在家裡,參與對話與討論,甚至一同經歷恐懼,能讓他們覺得自己並非孤伶伶地體驗哀傷,也讓他們藉由分擔責任與哀悼過程而獲得安慰。這個過程能讓他們逐步做好心理準備,幫助他們將死亡視為生命的一部分,視為有助於他們成長、成熟的經驗。
這和視死亡為禁忌的社會形成極大的反差,在那樣的社會,人們認為討論死亡是件病態的事,孩童也會被排除在外,因為大人們擅自假定這對他們「太沉重」,以此作為藉口。於是他們便被送去親戚家住,而且人們常會對他們說「媽媽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旅行」這樣沒說服力的謊言,或編造出其他荒謬的故事。孩子會察覺到不對勁,如果其他親戚又對這類故事添油加醋一番,而且迴避他的問題和懷疑,拿一大堆禮物充當廉價的替代品,試圖彌補他不被允許處理的喪親之痛,那麼他對大人的不信任感將會日益加深。遲早,孩子會察覺到家庭狀況已經發生變化,而依照他們年紀與個性的不同產生程度不等的問題,包括內心難解的哀傷,並認為此一事件恐怖又神祕,甚至產生嚴重的創傷經驗,認為大人不值得信任,而他完全無法應付這樣的事。
另一個同樣不明智的行為,是告訴剛失去兄弟的小女孩,說神非常喜愛小男孩,所以才把小強尼帶走。當這名小女孩長大成為女人,她對神將永遠憤恨難消,而當她在三十年後失去自己的小兒子時,可能會罹患「精神病性憂鬱症」(psychotic depression)。
我們以為,人類的偉大解放,我們在科學與人類方面所獲得的知識,已經能夠讓我們自己與家人擁有更好的方法與工具來為這場無可避免的事件做好充分的準備。然而,容許一個人平靜安詳、保有尊嚴地在自家過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科學越進步,我們似乎就越是害怕並否認死亡這個現實。事情怎可能如此?
我們會使用委婉說辭,讓亡者看起來像是睡著了,我們將孩子送走,以保護他們不遭受家裡的焦慮與混亂所侵擾(如果患者有幸在家中離世的話),我們也不讓孩子前往醫院探視臨終的父母,而對於是否該告知病人真相,長久以來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議題──如果臨終者是由家庭醫師照料,由於他很熟悉病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情況,也清楚每個家庭成員的弱點與長處,那麼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讓我們不再冷靜面對死亡的原因有好幾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在當今的社會,臨終在許多方面都顯得更陰森可怕,換句話說,就是更孤單、更機械化、更沒人性,而且有時候,甚至也難以在技術上決定死亡時刻何時發生。
臨終過程之所以變得孤單、失去人性,是因為病人經常被帶離他熟悉的環境,匆匆忙忙被送進急診室。那些曾病重而需要休息與舒適環境的人,應該對自己被抬上擔架、忍受救護車鳴笛聲的噪音,倉促被送往醫院等待醫院大門開啟的經驗特別難以忘懷。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這種運送過程的不適與冷酷的必要,而這只是漫長折磨的開端──各種噪音、強光、注射幫浦與聲音加在一起,著實是有口難言的煎熬,即使是身體健康時都難以忍受。我們可能必須多加考慮到床單與毯子底下的病人,或許該停止這種立意良好卻只顧及效率與速度的方式,才能好好握住病人的手,對他微笑或是傾聽他的問題。我將送醫的這趟路程納入臨終的第一章,對許多人而言確實如此。我刻意以較誇大的方式讓它與在家辭世的病人形成強烈的對比──意思並非說即使住院能救他們的命,他們也不應獲救,我只是想要將焦點放在病人的體驗,以及他的需求和反應上。
當病人病入膏肓,他通常會像個無權表達任何意見的人一樣被對待,通常是另一個人在決定他是否住院、何時入院、該住哪間醫院。只要稍微多用點心就能記得,病人也是個有感覺、有願望、有想法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也有被聽見的權利。
我不祈求在遭遇危險時獲得庇護,
但求面對危險能無所畏懼。
我不祈求痛苦止息,
但求讓我擁有一顆征服痛苦的心。
我不尋求生命戰場裡的盟友,
但求自身擁有力量。
我不焦急害怕地渴望得救,
而是盼望耐心能為我贏得自由。
請應允我,不要讓我變成一個懦夫,
只在成功時沉浸於你的仁慈
而是讓我在失敗時找到你緊握住我的手。
──泰戈爾《採果集》(Fruit-Gathering)
在過去幾個世代裡,傳染病造成了人命的重大損失。嬰兒時期與童年的早夭現象很常見,每個家庭裡或多或少都有早夭的成員。醫藥在過去數十年來歷經了巨大的變化,疫苗接種的普及實際上根絕了許多疾病,至少在西歐和美國的情況是如此。化療,特別是抗生素的使用,讓感染性疾病的致死率不斷下降。更完善的兒童照護與教育也發揮效果,使兒童發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過去在年輕人與中年人族群間造成高死亡率的疾病,也已經能夠克服。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從而產生了罹患高齡相關之惡性腫瘤與慢性疾病的龐大族群。
兒科醫師要處理的威脅生命的急性狀況減少了,但是身心失調和有行為問題的患者卻越來越多。內科醫師的候診室裡,有情緒問題的患者比以往都要來得多,但他們的年長患者也越來越多,他們不但努力拖著體力衰退的身體與年齡帶來的各種限制努力活下去,也必須面對寂寞和孤立帶來的痛苦折磨。這其中有多數人都是精神科醫師看不見的。他們的需求必須透過其他專業人員的誘導才能獲得滿足,例如牧師與社工等。正是為了這些人,我試圖勾勒出過去數十年來所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人們心中日益懼怕死亡,情緒問題越來越多,更迫切需要理解並處理死亡與臨終的問題。
若回顧歷史並研究古老的文化與民族,我們會很驚訝地發現,死亡對人類來說向來都是一件令人厭惡的事,或許將來也永遠會如此。從精神科醫師的觀點來看,這十分容易理解,而且我們的一個基本認識或許能充分解釋這件事,那就是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死亡對我們而言永遠不可能發生。我們的潛意識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命真的會有結束的一天,而如果我們的生命必須結束,這個結束總是被歸咎於外在他人的惡意介入。簡而言之,在我們的潛意識頭腦裡,我們只可能被殺死,自然死亡(壽終正寢)或因年邁而死亡是難以想像的。因此,死亡本身就容易使人聯想到惡意行為、可怕事件、某種本質上會招來報應與懲罰的事。
記住這些根本的事實是個聰明的做法,因為這在了解我們病患一些最重要卻難以理解的溝通問題上,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必須理解的第二個事實是,在我們的潛意識頭腦裡,我們無法分辨一個願望和一個行為之間有何不同。我們都能察覺到,在我們最不合邏輯的夢境中,兩個完全相反的論述能並行不悖──這在我們夢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我們的清醒狀態下,卻難以理解且不合邏輯。如同我們的無意識頭腦無法分辨憤怒地想要殺死一個人的願望和實際去殺人的行為有何不同,年幼的孩童也無法分辨這兩者之間的不同。因為媽媽沒有滿足他的需求而憤怒地希望媽媽去死的孩子,在媽媽真正死去的時候會受到極大的創傷──即使這件事與他那個毀滅性願望在時間上並無密切關聯,但他永遠都會認為,他必須為失去母親負起部分或完全的責任。他永遠都會對自己說(但鮮少對別人說)──「是我幹的,我必須負責,我很壞,所以媽咪才會離開我。」要記得,孩子如果是因為父母的離婚、分居或遺棄而失去其中一位父母,他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死亡通常被孩子視為一件暫時的、非永久性的事,也因此和離婚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在離婚狀況下,他可能會有機會再見到其中一位父母。
許多父母都記得孩子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會把狗狗埋起來,明年春天花開的時候,牠就會醒過來。」或許也就是這同樣的動機,驅使著古埃及人供應亡者食物與物品,也讓古老的美國原住民將他們的親人和其所有物埋葬在一起。
隨著我們年紀漸長,開始明白我們的全能之神並非真的那麼全能,而且我們最強烈的願望還不足以強大到讓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之後,害怕自己間接導致親人死亡的恐懼與罪疚感也會隨之減輕。然而,恐懼只有在尚未遭受強力挑戰之前才暫時得以減輕。它所殘留的痕跡依然可以每天在醫院走廊上見到,在喪親者周遭的人身上見到。
一對夫妻很可能長年爭吵不休,但是當另一半過世時,倖存的另一半會抓著他的頭髮,大聲哀號,捶胸頓足,充滿悔恨,恐懼又痛苦,因而比以往更害怕自己的死亡,而且依然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法則──「我對他的死有責任,所以我也會遭到報應,痛苦地死去。」
或許這樣的認識有助於讓我們了解許多施行數百年之久、目的是讓眾神息怒,或在有些例子裡是讓一些人息怒的古老習俗與儀式,它們想藉此減輕預期的懲罰。我想到了古代儀式中的骨灰、破爛的喪服、面紗,以及哭喪女(譯註:類似台灣俗稱的孝女白琴)──這些都是為了要讓你同情身為哀悼者的他們,這樣的表達方式呈現出的是悲痛、哀傷與羞恥。如果有人哀痛不已,捶胸頓足、拉扯自己的頭髮、拒絕進食,這是企圖自我懲罰,以躲過或減輕自己間接導致親人死亡而預期會遭受的懲罰。
這份哀傷、羞恥與罪疚感與狂暴的憤怒情緒其實相距不遠。哀傷的過程總是包含了一些憤怒的成分。由於沒有人想要承認自己對亡者感到憤怒,因此這些情緒經常遭到偽裝或壓抑,拖長了哀悼期,或是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必須記得的是,我們不應對這樣的感受妄加評斷,認為那是不好的或可恥的,而是要去了解它們真正的意義與來源,視其為人性的一部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會再次使用小孩子作為例子,包括我們內在的小孩。一個剛剛失去母親的五歲孩子會為母親的消失責怪自己,還會因為母親遺棄他而且不再能滿足他的需求而對她生氣。於是,亡者既讓孩子深愛又渴望,同時也因這份嚴重的剝奪感,而讓他懷著同樣強度的恨意。
古希伯來人將亡者的遺體視為不潔的,不能觸碰。早期的美洲原住民也談到了惡靈,他們會往空中射箭以驅趕惡靈。許多其他文化也有處理「壞」亡者的儀式,這些都源自這種存在於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憤怒感,只是我們不喜歡承認這一點罷了。墓碑的傳統可能源自這種想要將惡靈鎮壓在地下的意圖,哀悼者放在墳墓上的小石子,也是同樣想法所遺留的象徵。雖然我們會將軍葬禮中的鳴槍禮視為對亡者最後的致敬,但這和美洲原住民所使用的、將矛與箭射向空中的儀式具有同樣的象徵意義。
我提出這些例子是為了強調人類基本上並沒有改變。死亡依然是一個令人懼怕的恐怖事件,即使我們自認為已經在許多層面上掌握了這件事,對死亡的恐懼仍是一種普世的恐懼。
有所改變的,是我們應對並處理死亡、臨終過程以及臨終病人的方式。
我在一個科學不怎麼發達的歐洲國家長大,在那裡,現代科技才剛開始運用在醫學上,人們的生活方式幾乎和半世紀前沒什麼兩樣,我也因此有機會在短時間內研究人類進化的一部分過程。
我記得自己小時候曾經歷過一場農夫的死亡。農人從樹上摔下來,預計活不久了。他只是簡單地要求在自家辭世,而這個願望毫無疑問獲得了應允。他將每個女兒都叫進臥室,一一和她們講了幾分鐘的話,然後忍著劇痛,靜靜地處理自己的後事,分配自己擁有的財物和土地,但全部都要等到他妻子追隨他與世長辭之後才能分家。他要求孩子們分擔他在意外發生前所從事的一些工作、責任與差事,還邀請朋友前來探望他,親自向他們道別。雖然我還是家中的小孩,但他並沒有將我和我的其他姐妹排除在外,我們都能參與家族的整個準備過程,我們也都可以一同哀悼,直到他過世。他與世長辭之後,留在了自己深愛的、一手打造的家,那個自己生前生活並熱愛的住所,身旁環繞著鮮花,親朋好友和鄰居都來為他送上最後一程。現今,在那個國家,依然沒有設置虛幻的靈堂,沒有採用任何遺體保存技術,也沒有假裝亡者只是在安眠的虛偽化妝術,只有疾病造成的嚴重容貌毀損,才會用繃帶遮掩,也只有因傳染病過世的案例,才不會於下葬前將遺體放在家中。
我為何要描述這些「老派」的習俗呢?我想它們顯示了我們對死亡結局的接受,既幫助了臨終病患,也幫助了他的家人接受失去摯愛的事實。如果病人被允許在他心愛的熟悉環境中結束生命,他要做的調適會比較少。他的家人已經十分了解他,可以用一杯他最喜愛的紅酒取代鎮定劑,或為他遞上一碗家常味的熱湯,幫他開開胃,讓他能啜飲幾湯匙的分量,我想這一定都比輸入液體更愉悅吧。我不否認鎮定劑與輸液的重要性,也因自己身為鄉村醫師的經驗而完全理解它們有時是救命工具,時常難以避免,但我也知道,耐心、熟悉的人與食物這三者,能取代許多瓶的靜脈輸液,原因很簡單,這麼做能在節省人力與個別護理的情況下,滿足病患的生理需求。
孩子獲准於死亡發生期間待在家裡,參與對話與討論,甚至一同經歷恐懼,能讓他們覺得自己並非孤伶伶地體驗哀傷,也讓他們藉由分擔責任與哀悼過程而獲得安慰。這個過程能讓他們逐步做好心理準備,幫助他們將死亡視為生命的一部分,視為有助於他們成長、成熟的經驗。
這和視死亡為禁忌的社會形成極大的反差,在那樣的社會,人們認為討論死亡是件病態的事,孩童也會被排除在外,因為大人們擅自假定這對他們「太沉重」,以此作為藉口。於是他們便被送去親戚家住,而且人們常會對他們說「媽媽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旅行」這樣沒說服力的謊言,或編造出其他荒謬的故事。孩子會察覺到不對勁,如果其他親戚又對這類故事添油加醋一番,而且迴避他的問題和懷疑,拿一大堆禮物充當廉價的替代品,試圖彌補他不被允許處理的喪親之痛,那麼他對大人的不信任感將會日益加深。遲早,孩子會察覺到家庭狀況已經發生變化,而依照他們年紀與個性的不同產生程度不等的問題,包括內心難解的哀傷,並認為此一事件恐怖又神祕,甚至產生嚴重的創傷經驗,認為大人不值得信任,而他完全無法應付這樣的事。
另一個同樣不明智的行為,是告訴剛失去兄弟的小女孩,說神非常喜愛小男孩,所以才把小強尼帶走。當這名小女孩長大成為女人,她對神將永遠憤恨難消,而當她在三十年後失去自己的小兒子時,可能會罹患「精神病性憂鬱症」(psychotic depression)。
我們以為,人類的偉大解放,我們在科學與人類方面所獲得的知識,已經能夠讓我們自己與家人擁有更好的方法與工具來為這場無可避免的事件做好充分的準備。然而,容許一個人平靜安詳、保有尊嚴地在自家過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科學越進步,我們似乎就越是害怕並否認死亡這個現實。事情怎可能如此?
我們會使用委婉說辭,讓亡者看起來像是睡著了,我們將孩子送走,以保護他們不遭受家裡的焦慮與混亂所侵擾(如果患者有幸在家中離世的話),我們也不讓孩子前往醫院探視臨終的父母,而對於是否該告知病人真相,長久以來一直是個爭議不休的議題──如果臨終者是由家庭醫師照料,由於他很熟悉病人從出生到死亡的情況,也清楚每個家庭成員的弱點與長處,那麼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讓我們不再冷靜面對死亡的原因有好幾個。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在當今的社會,臨終在許多方面都顯得更陰森可怕,換句話說,就是更孤單、更機械化、更沒人性,而且有時候,甚至也難以在技術上決定死亡時刻何時發生。
臨終過程之所以變得孤單、失去人性,是因為病人經常被帶離他熟悉的環境,匆匆忙忙被送進急診室。那些曾病重而需要休息與舒適環境的人,應該對自己被抬上擔架、忍受救護車鳴笛聲的噪音,倉促被送往醫院等待醫院大門開啟的經驗特別難以忘懷。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體會這種運送過程的不適與冷酷的必要,而這只是漫長折磨的開端──各種噪音、強光、注射幫浦與聲音加在一起,著實是有口難言的煎熬,即使是身體健康時都難以忍受。我們可能必須多加考慮到床單與毯子底下的病人,或許該停止這種立意良好卻只顧及效率與速度的方式,才能好好握住病人的手,對他微笑或是傾聽他的問題。我將送醫的這趟路程納入臨終的第一章,對許多人而言確實如此。我刻意以較誇大的方式讓它與在家辭世的病人形成強烈的對比──意思並非說即使住院能救他們的命,他們也不應獲救,我只是想要將焦點放在病人的體驗,以及他的需求和反應上。
當病人病入膏肓,他通常會像個無權表達任何意見的人一樣被對待,通常是另一個人在決定他是否住院、何時入院、該住哪間醫院。只要稍微多用點心就能記得,病人也是個有感覺、有願望、有想法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也有被聽見的權利。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