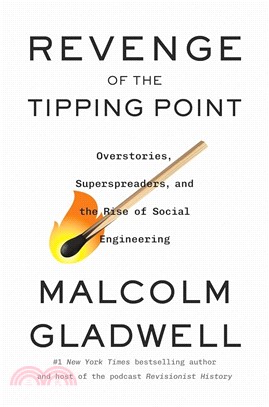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身為彭明敏親近的姪子,彭昤以頗具黑色幽默的文字,描述彭家人,以及在彭明敏逃亡後家人的遭遇與情感流動。
監視、監聽、出國被刁難……
那段在台灣成長、生活的黑暗日子中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
明敏叔逃亡之前,家屬親人雖然有一些不方便,但當局有特定箭靶,其他人只是偶爾會受到關懷。
明敏叔逃亡之後,因為當事人在境外,家屬就變成當局的箭靶,或是報復的對象。
――彭昤
作者彭昤是彭明敏教授二哥彭明輝的兒子,從小即因住居接近而與彭教授相當親近,除了親歷彭教授擔任台大教授以及之後被監視的時期之外,到美國留學後,也經常與彭教授聚會,從他的眼中,我們可以看到很不一樣的彭明敏教授,以及彭家一家人在經歷彭教授事件之後的遭遇與因應。
真情推薦
本書作者是彭明敏教授的姪子彭昤,讓外人得以一窺彭明敏教授受難前後,彭家人的遭遇、行誼跟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楊斯棓(人生路引》作者.醫師)
本書特色
從家人眼光看彭明敏的逃亡與作為。
監視、監聽、出國被刁難……
那段在台灣成長、生活的黑暗日子中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
明敏叔逃亡之前,家屬親人雖然有一些不方便,但當局有特定箭靶,其他人只是偶爾會受到關懷。
明敏叔逃亡之後,因為當事人在境外,家屬就變成當局的箭靶,或是報復的對象。
――彭昤
作者彭昤是彭明敏教授二哥彭明輝的兒子,從小即因住居接近而與彭教授相當親近,除了親歷彭教授擔任台大教授以及之後被監視的時期之外,到美國留學後,也經常與彭教授聚會,從他的眼中,我們可以看到很不一樣的彭明敏教授,以及彭家一家人在經歷彭教授事件之後的遭遇與因應。
真情推薦
本書作者是彭明敏教授的姪子彭昤,讓外人得以一窺彭明敏教授受難前後,彭家人的遭遇、行誼跟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楊斯棓(人生路引》作者.醫師)
本書特色
從家人眼光看彭明敏的逃亡與作為。
作者簡介
彭昤(意為早晨的太陽)
祖父是彭明敏教授的父親。籍貫台灣高雄,但在台北出生和成長受教育。大學時走過北中南三條橫貫公路,蘇花和台東沿海公路。一九七八年退伍後流浪美國東西南北各地方。曾參與多家化學、醫療器材和製藥公司新產品的研究發展和製造。
祖父是彭明敏教授的父親。籍貫台灣高雄,但在台北出生和成長受教育。大學時走過北中南三條橫貫公路,蘇花和台東沿海公路。一九七八年退伍後流浪美國東西南北各地方。曾參與多家化學、醫療器材和製藥公司新產品的研究發展和製造。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今天我來講一個「歸kuānn肉粽」的故事
《人生路引》作者 楊斯棓醫師
有個政治人物,對於自己擁有台大醫學系的學位,感到十分驕傲,舉國皆知。
有一次,他去拜訪彭明敏教授。話說沒幾句,他就急著想讓彭教授知道他是哪一所大學的校友。
彭教授聞「台大」,有一股強烈的親切感,畢竟一九六一年,他三十八歲時,即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是戰後台大最年輕的正教授與系主任。於是乎,彭教授娓娓道來:
「家父彭清靠一九〇七年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一九一二年畢業。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於一八九九年成立,一九一九年,改制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一九三六年之後隸屬台北帝大管理,稱『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四五年後,再改制為台大醫學院。
也就是說,家父,你學長,比你早七十四年畢業。(註:該政治人物一九八六年自台大畢業)
家父曾到東京帝大附屬泉橋慈善病院進修研習婦產科,返台後曾在高雄開設『彭產婦人科病院』,他如果當面聽到婦產科這麼一個神聖的科別被你說成:『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應該會鐵青著臉。
我兒子彭旼,也是台大醫學系畢(一九七四年畢業)。
我女兒彭曄,也是台大醫學系畢,曾任台大細胞病理科主任。
我大姊彭淑媛是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是一位婦產科醫師。她如果當面聽到婦產科這麼一個神聖的科別被你說成:『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應該是欲哭無淚。
我姊夫陳端方也是醫師,曾任省立台南醫院副院長。
他姊姊叫陳愛珠,是一位齒科醫師,嫁給詹位醫師。詹位醫師畢業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也是你學長。
詹位醫師的七子叫詹啟賢,曾任奇美醫院院長及衛生署長。
詹啟賢的女兒詹慧文是波士頓大學醫學博士,目前是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醫學中心的副教授。
而陳端方的弟弟叫陳端儀,曾任台中醫院內科主任。
還有個弟弟叫陳端堂,畢業自大阪大學醫學部,曾任省立台中醫院外科主任,也當過一任台中市長。
他們的爸爸叫陳彩龍,是日本慶應大學的醫學博士,曾任省立台中醫院院長。
陳彩龍的弟弟叫陳水潭,一九一七年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也是你學長,一九二二年畢業,曾被派任到總督府台中醫院婦科服務,他如果聽到你關於婦產科的無知笑話,可能會面無表情,欲辯無言。他曾任台中縣長,也是地方派系黑派的創始人。
我大哥彭明哲也是醫師,畢業自日本長崎醫科大學。
我二哥彭明輝讀日本慶應大學醫學系,學期中因病休學,病癒後轉唸貿易。
我三伯彭清約,也是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
我三伯的長子,我的堂兄彭明聰,是台北帝大醫學博士,還當過台大醫學院院長。
我堂兄的女婿王作人,也是台大醫科畢業,是世界知名的遺傳學泰斗。
我堂兄的長子彭福春,在美國加州任小兒科醫師。
我堂兄還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分別叫彭福佐與彭福佑。
彭福佐是台大的生化博士,台大醫學院教授退休;他的太太鍾嫈嫈亦畢業自台大醫學系,是資深家醫科主治醫師。
彭福佑是牙醫師;他的女兒是美國水牛城醫學院的臨床教學醫師。
我三伯的次子,彭明睿,也是醫師,曾在高雄市開設彭小兒科醫院。
我三伯的三子,彭明俊,也是醫師,曾任省立高雄醫院外科主任。
我三伯的女婿,李茂森,也是醫師,曾於鳳山開設杏林小兒科醫院。
我四叔彭清良也是醫師,曾與三伯在鳳山開設育仁醫院。……」
以上內容,俱是事實,但老派紳士彭教授,其實沒有跟政治人物解釋那麼多,據聞,只有提到自己的一對兒女亦是自台大醫學系畢。
政治人物想炫耀自己的學歷,卻不知眼前高人,是戰後最年輕的台大教授,其父與其子,俱是台大醫學系畢,整個家族血親、姻親畢業自台大或日本醫學院校不知凡幾,台語只能用:「歸kuānn肉粽」來形容。
該政治人物與其妻在最新一期的財產申報,有九筆土地、六筆建物。
透過本書內容,讓我了解彭家人跟那位政治人物,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醫師在大甲的土地,大部分賣掉當作赴日進修時的盤纏,沒賣掉的,後來捐贈給大甲教會。
彭明敏教授的二哥彭明輝,將名下的屏東土地,捐贈給財團法人基督教長老教會屏東中會。
攢積房產,是俗人的想望與格局。
捐出土地,是義人的慈悲與博愛。
彭明敏教授在一九九六年選總統的時候,我還沒有投票權,但是開票那天,我守在離家最近的潭子國小的開票所,手拿鯨魚旗,頭戴鯨魚帽,身穿鯨魚衣(購自彭教授競選總部),身上俱是「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的字樣,從唱票開始守到結束。那是我在那個年紀,能幫彭教授的極限。
二〇一四年,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紀念,我受彭明敏基金會之邀,擔綱第一棒演講(其他講者分別是:金恆煒、魏揚、曹長青、黃越綏),當天晚上受邀和彭教授餐敘(加州名醫張信行之妻黃美星的弟弟黃兆源夫婦、羅致政夫婦亦有參與),留下寶貴的合影。
小說家、企業家邱永漢有一本作品叫《香港》,我曾將該書與彭教授的《逃亡》一起讀,邱逃亡的目的地是香港,班機起飛後,邱寫下「肩頭的空氣的壓力,似乎也隨著飛機在空中愈上升愈輕鬆」自況,彭教授逃亡的終點是瑞典,他先飛往香港、泰國,最後換搭北歐航空飛往哥本哈根(最後飛往斯德哥爾摩機場),彭自述「當飛機飛越阿富汗上空時,從機上看地面風景是多麼美麗,感覺到我是一個自由人了,能夠回復到為人的尊嚴,開始感覺輕鬆又興奮。」
兩位前輩的命運跟感悟,竟有如此雷同處。
本書作者是彭明敏教授的姪子彭昤,讓外人得以一窺彭明敏教授受難前後,彭家人的遭遇、行誼跟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
撰稿之前,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剛被香港政府祭出一百萬港元懸賞。羅冠聰今年才二十九歲。
完稿之際,香港國安處探員搜查了羅冠聰父母及兄長的住處,並將三人帶回警署問話。
昨日台灣,今日香港。
台人若渾噩,誰知今日香港,不會是明日台灣?
「歷史繼續換咱行,新主人有新希望。追求尊嚴毋通放,新國家找新主人。」
今天我來講一個「歸kuānn肉粽」的故事
《人生路引》作者 楊斯棓醫師
有個政治人物,對於自己擁有台大醫學系的學位,感到十分驕傲,舉國皆知。
有一次,他去拜訪彭明敏教授。話說沒幾句,他就急著想讓彭教授知道他是哪一所大學的校友。
彭教授聞「台大」,有一股強烈的親切感,畢竟一九六一年,他三十八歲時,即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是戰後台大最年輕的正教授與系主任。於是乎,彭教授娓娓道來:
「家父彭清靠一九〇七年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一九一二年畢業。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於一八九九年成立,一九一九年,改制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一九三六年之後隸屬台北帝大管理,稱『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一九四五年後,再改制為台大醫學院。
也就是說,家父,你學長,比你早七十四年畢業。(註:該政治人物一九八六年自台大畢業)
家父曾到東京帝大附屬泉橋慈善病院進修研習婦產科,返台後曾在高雄開設『彭產婦人科病院』,他如果當面聽到婦產科這麼一個神聖的科別被你說成:『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應該會鐵青著臉。
我兒子彭旼,也是台大醫學系畢(一九七四年畢業)。
我女兒彭曄,也是台大醫學系畢,曾任台大細胞病理科主任。
我大姊彭淑媛是日本九州大學醫學博士,是一位婦產科醫師。她如果當面聽到婦產科這麼一個神聖的科別被你說成:『剩下一個洞、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應該是欲哭無淚。
我姊夫陳端方也是醫師,曾任省立台南醫院副院長。
他姊姊叫陳愛珠,是一位齒科醫師,嫁給詹位醫師。詹位醫師畢業自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也是你學長。
詹位醫師的七子叫詹啟賢,曾任奇美醫院院長及衛生署長。
詹啟賢的女兒詹慧文是波士頓大學醫學博士,目前是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醫學中心的副教授。
而陳端方的弟弟叫陳端儀,曾任台中醫院內科主任。
還有個弟弟叫陳端堂,畢業自大阪大學醫學部,曾任省立台中醫院外科主任,也當過一任台中市長。
他們的爸爸叫陳彩龍,是日本慶應大學的醫學博士,曾任省立台中醫院院長。
陳彩龍的弟弟叫陳水潭,一九一七年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就讀,也是你學長,一九二二年畢業,曾被派任到總督府台中醫院婦科服務,他如果聽到你關於婦產科的無知笑話,可能會面無表情,欲辯無言。他曾任台中縣長,也是地方派系黑派的創始人。
我大哥彭明哲也是醫師,畢業自日本長崎醫科大學。
我二哥彭明輝讀日本慶應大學醫學系,學期中因病休學,病癒後轉唸貿易。
我三伯彭清約,也是畢業自總督府醫學校。
我三伯的長子,我的堂兄彭明聰,是台北帝大醫學博士,還當過台大醫學院院長。
我堂兄的女婿王作人,也是台大醫科畢業,是世界知名的遺傳學泰斗。
我堂兄的長子彭福春,在美國加州任小兒科醫師。
我堂兄還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分別叫彭福佐與彭福佑。
彭福佐是台大的生化博士,台大醫學院教授退休;他的太太鍾嫈嫈亦畢業自台大醫學系,是資深家醫科主治醫師。
彭福佑是牙醫師;他的女兒是美國水牛城醫學院的臨床教學醫師。
我三伯的次子,彭明睿,也是醫師,曾在高雄市開設彭小兒科醫院。
我三伯的三子,彭明俊,也是醫師,曾任省立高雄醫院外科主任。
我三伯的女婿,李茂森,也是醫師,曾於鳳山開設杏林小兒科醫院。
我四叔彭清良也是醫師,曾與三伯在鳳山開設育仁醫院。……」
以上內容,俱是事實,但老派紳士彭教授,其實沒有跟政治人物解釋那麼多,據聞,只有提到自己的一對兒女亦是自台大醫學系畢。
政治人物想炫耀自己的學歷,卻不知眼前高人,是戰後最年輕的台大教授,其父與其子,俱是台大醫學系畢,整個家族血親、姻親畢業自台大或日本醫學院校不知凡幾,台語只能用:「歸kuānn肉粽」來形容。
該政治人物與其妻在最新一期的財產申報,有九筆土地、六筆建物。
透過本書內容,讓我了解彭家人跟那位政治人物,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醫師在大甲的土地,大部分賣掉當作赴日進修時的盤纏,沒賣掉的,後來捐贈給大甲教會。
彭明敏教授的二哥彭明輝,將名下的屏東土地,捐贈給財團法人基督教長老教會屏東中會。
攢積房產,是俗人的想望與格局。
捐出土地,是義人的慈悲與博愛。
彭明敏教授在一九九六年選總統的時候,我還沒有投票權,但是開票那天,我守在離家最近的潭子國小的開票所,手拿鯨魚旗,頭戴鯨魚帽,身穿鯨魚衣(購自彭教授競選總部),身上俱是「海洋國家,鯨神文明」的字樣,從唱票開始守到結束。那是我在那個年紀,能幫彭教授的極限。
二〇一四年,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五十週年紀念,我受彭明敏基金會之邀,擔綱第一棒演講(其他講者分別是:金恆煒、魏揚、曹長青、黃越綏),當天晚上受邀和彭教授餐敘(加州名醫張信行之妻黃美星的弟弟黃兆源夫婦、羅致政夫婦亦有參與),留下寶貴的合影。
小說家、企業家邱永漢有一本作品叫《香港》,我曾將該書與彭教授的《逃亡》一起讀,邱逃亡的目的地是香港,班機起飛後,邱寫下「肩頭的空氣的壓力,似乎也隨著飛機在空中愈上升愈輕鬆」自況,彭教授逃亡的終點是瑞典,他先飛往香港、泰國,最後換搭北歐航空飛往哥本哈根(最後飛往斯德哥爾摩機場),彭自述「當飛機飛越阿富汗上空時,從機上看地面風景是多麼美麗,感覺到我是一個自由人了,能夠回復到為人的尊嚴,開始感覺輕鬆又興奮。」
兩位前輩的命運跟感悟,竟有如此雷同處。
本書作者是彭明敏教授的姪子彭昤,讓外人得以一窺彭明敏教授受難前後,彭家人的遭遇、行誼跟不足為外人道的心酸。
撰稿之前,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剛被香港政府祭出一百萬港元懸賞。羅冠聰今年才二十九歲。
完稿之際,香港國安處探員搜查了羅冠聰父母及兄長的住處,並將三人帶回警署問話。
昨日台灣,今日香港。
台人若渾噩,誰知今日香港,不會是明日台灣?
「歷史繼續換咱行,新主人有新希望。追求尊嚴毋通放,新國家找新主人。」
序
引言
《竊聽風暴》(Lives of Others)是一部發行於二○○六年的德國電影,並在二○○七年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部電影講述了二十世紀六○到八○年代生活在東德祕密警察陰影下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故事。電影有演到如何利用造假的外國人護照逃亡,相當有意思。《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書中都提到當年想法的源頭。當然,東西柏林只有一牆之隔,聯絡也許比較簡單,但危險程度並不會差太多。
我看到《竊聽風暴》這部片時,已經是舊片了,但我還是被深深感動。電影的結局陳明了一個尖銳的對比,亦即德國和中國文化在處理過去事件的對比,特別是執政者的惡行。我想這可能是為什麼德國能在戰後快速重建登上高峰,而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反而陷入深淵的原因之一。
電影中,東德祕密警察的專業態度,和那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豬是很難堪的對比,堪比父母在一九四五年目睹戰敗離開的日本帝國軍隊和從中國來的乞丐士兵的對照。反過來看,如果這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有些專業的背景,我可能很久以前就神祕地消失在島上了。
這部電影引發我開始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在島嶼成長、生活的黑暗日子中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我以前就曾經有過類似念頭,但從來沒得到足夠的動機,當然開始會用電腦寫中文也有影響。有聽說有人在寫,但始終沒看到結果。我知道談那些日子會帶來不少痛苦,因此我很不願意或不敢去探測他人的經驗。可悲的是,我的家人在過去幾年裡失去不少集體記憶。老一代的一個一個凋零,對以前的記憶更是快速消失。其他長輩的記憶也在退化。我離開後一直想忘掉過去,一切重新開始,可以避開以前的人事就避不面對,也很少去提起那些日子,所以也不能怪老人不想去回憶不愉快或可怕的往事。
二○○九年八月我回台探望中風的父親,短短數天之中,土石流埋沒了幾個村莊。如果他能感知到這一個土石流的悲劇,也許會有很大的痛苦。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疏散到那個區域以躲避美國轟炸機,更早前他喜歡回憶住宿在三蘭村的日子和那裡的人,但對比較後來一些不愉快的事都說忘記了,也有時會說不想去想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我自己比別人先跑,也比別人跑得遠,沒資格去要別人記憶痛苦的往事。集體的記憶消失得很多很快,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生病或死亡,一大塊一大塊就不見了。
歷史可能不會重演,但若不學習歷史將遭受同樣的苦難。顯然,海島是滑回黑暗的日子,因為國民黨的執政(馬英九執政時期)正走回頭路,民進黨也只會說些好聽的話但拿不出結果,或許是無能或許是無心,或許是政客的本性。中國從來沒有猶豫攻擊日本過去的罪孽,但從來不肯透露他們對人民的任何惡行。執政者把任何證據掃入地毯下,以掩蓋其犯罪危害人民的歷史。
§
祖父母都在日本時代接受西方教會教育,父親小時候讀過一點漢文,背過《三字經》(台文),戰後父親在台大醫學院短暫就讀。外祖父在日本公學校唸兩年畢業,外祖母沒受過正式教育,母親戰後在高雄女中讀了三年,接受最多的中國教育。中文是壓迫者強迫灌入我喉嚨的語言,雖然我可以說中國話,讓人認為我是第一或第二代來自中國的移民,但寫中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問題。初中和高中的中文教師嘲笑我缺乏應有的中國家庭教學,戰和仗分不清,被罵了多次。父母親的中文跟我差不多。雖然先天不足,建中和台大也都考取。大一中文教師鼓勵我投稿,他居然說我有點才氣,他應該不知道我是思想有問題的黑五類,但他也不客氣地指出,我的字寫得實在夠差。
英語是我工作生活的語言。我能說差強人意、簡單的日常台灣話,我父母的母語。我的父親給了我一本台灣翻譯的、被稱為「紅皮聖經」的《新約》,聽說出版後不久即被執政者禁印和銷毀,但可惜我看不懂。我通常用英文起稿,用谷歌翻譯成中文後再修改。中文已經忘了很多,手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多年前第一次用台灣護照入境,護照身分證號碼不對無法驗證,海關要我寫出自己的身分歷程才讓我過關入境,過程中多次詢問辦事員字的寫法,辦事員不但取笑我,也懷疑我在台灣讀過書,更別說大學。
§
二○○九年我收到了一本明敏叔簽名的《逃亡》。這是我已經期待很長一段時間的書,從一九七八年感恩節就開始期待,那時更沒想到會在台灣出版。
當年是我讓父親被叫進初中校長辦公室,被校長貼上「思想有問題」的標籤。沒有想到明敏叔會記住四十多年前的事,並公開寫出來。一九七六年我大學畢業去當兵之前父親曾經提過一次,前後都沒人提過。
《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則是完全沒預料到的書,有一天突然看到書評,馬上去訂購。作者名字很熟但我沒見過,父母和祖母都見過他。一個外國人為正義付出很多,其他還有多位默默在背後貢獻。回台灣時,母親有一本作者送的中文版,讀了一次。
《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是當事人看到的一面,而我則是在陰影下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一點。這兩本書是一個階段的終點,但也是另一些故事的開始。逃亡發生之前,家屬親人有一些不方便,但當局有特定箭靶,其他人只偶爾會受到當局關懷。事情發生後,當事人在境外,家屬就遭殃了,變成箭靶或是報復對象,時間從明敏叔逃亡到他回台,是一段很長的日子,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我離開之前的日子。我很幸運能在一九七八年離台,讓我嘗試自由的生活,算是一大解脫,至少沒有立即的威脅。父母除了短期出國,仍繼續在台灣生活,台灣是他們的家。
§
我的命運讓我成長在特別的時間和地方,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機會。相對來說,我的生活雖有些不便,但比起真正受害者的生活,卻不值得一提。我已一點一點記錄這些經歷好幾年,卻沒敢發表,一方面是不想讓長輩再回到過去,另一方面是沒有完整的記憶,和家人談話後修正過多次,有些記憶不同。明敏叔還在的時候也不敢發表,因為不想讓他想起往事。我不知道他聽過多少,沒必要讓他多操煩,畢竟他也是有歲數的長輩。
§
雖然背景有些不一樣,但我們不是唯一受到當局關心的家庭。不過奇怪的是,多年來竟沒人出來描述過去被關心的生活。「二二八」、「白色恐怖」當事人有不少紀錄,有文章,有出書,也有影片;當事人關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理由,期滿出來日子不好過也有報告。但家人親屬的生活卻沒人去調查或報告,尤其是那些更無辜的受害人,一家少了一根支柱,一般經濟環境已經不好,加上當權不同單位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後代在那種環境如何成長。除了管區警察特別關心,職業遇到政府不必要的關心之外,幾乎沒人報告其他困難。我只能算是外圍旁觀的人,隔壁在火燒,我家也許有危險但還沒起火,不能真正瞭解他們的苦難。後來的政府有對當年的政治犯道歉,但對他們的妻子卻連提都沒提。
《竊聽風暴》(Lives of Others)是一部發行於二○○六年的德國電影,並在二○○七年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部電影講述了二十世紀六○到八○年代生活在東德祕密警察陰影下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故事。電影有演到如何利用造假的外國人護照逃亡,相當有意思。《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書中都提到當年想法的源頭。當然,東西柏林只有一牆之隔,聯絡也許比較簡單,但危險程度並不會差太多。
我看到《竊聽風暴》這部片時,已經是舊片了,但我還是被深深感動。電影的結局陳明了一個尖銳的對比,亦即德國和中國文化在處理過去事件的對比,特別是執政者的惡行。我想這可能是為什麼德國能在戰後快速重建登上高峰,而台灣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反而陷入深淵的原因之一。
電影中,東德祕密警察的專業態度,和那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豬是很難堪的對比,堪比父母在一九四五年目睹戰敗離開的日本帝國軍隊和從中國來的乞丐士兵的對照。反過來看,如果這些國民黨的暴徒流氓有些專業的背景,我可能很久以前就神祕地消失在島上了。
這部電影引發我開始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在島嶼成長、生活的黑暗日子中所看到的一些點點滴滴。我以前就曾經有過類似念頭,但從來沒得到足夠的動機,當然開始會用電腦寫中文也有影響。有聽說有人在寫,但始終沒看到結果。我知道談那些日子會帶來不少痛苦,因此我很不願意或不敢去探測他人的經驗。可悲的是,我的家人在過去幾年裡失去不少集體記憶。老一代的一個一個凋零,對以前的記憶更是快速消失。其他長輩的記憶也在退化。我離開後一直想忘掉過去,一切重新開始,可以避開以前的人事就避不面對,也很少去提起那些日子,所以也不能怪老人不想去回憶不愉快或可怕的往事。
二○○九年八月我回台探望中風的父親,短短數天之中,土石流埋沒了幾個村莊。如果他能感知到這一個土石流的悲劇,也許會有很大的痛苦。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疏散到那個區域以躲避美國轟炸機,更早前他喜歡回憶住宿在三蘭村的日子和那裡的人,但對比較後來一些不愉快的事都說忘記了,也有時會說不想去想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我自己比別人先跑,也比別人跑得遠,沒資格去要別人記憶痛苦的往事。集體的記憶消失得很多很快,而且速度越來越快,生病或死亡,一大塊一大塊就不見了。
歷史可能不會重演,但若不學習歷史將遭受同樣的苦難。顯然,海島是滑回黑暗的日子,因為國民黨的執政(馬英九執政時期)正走回頭路,民進黨也只會說些好聽的話但拿不出結果,或許是無能或許是無心,或許是政客的本性。中國從來沒有猶豫攻擊日本過去的罪孽,但從來不肯透露他們對人民的任何惡行。執政者把任何證據掃入地毯下,以掩蓋其犯罪危害人民的歷史。
§
祖父母都在日本時代接受西方教會教育,父親小時候讀過一點漢文,背過《三字經》(台文),戰後父親在台大醫學院短暫就讀。外祖父在日本公學校唸兩年畢業,外祖母沒受過正式教育,母親戰後在高雄女中讀了三年,接受最多的中國教育。中文是壓迫者強迫灌入我喉嚨的語言,雖然我可以說中國話,讓人認為我是第一或第二代來自中國的移民,但寫中文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問題。初中和高中的中文教師嘲笑我缺乏應有的中國家庭教學,戰和仗分不清,被罵了多次。父母親的中文跟我差不多。雖然先天不足,建中和台大也都考取。大一中文教師鼓勵我投稿,他居然說我有點才氣,他應該不知道我是思想有問題的黑五類,但他也不客氣地指出,我的字寫得實在夠差。
英語是我工作生活的語言。我能說差強人意、簡單的日常台灣話,我父母的母語。我的父親給了我一本台灣翻譯的、被稱為「紅皮聖經」的《新約》,聽說出版後不久即被執政者禁印和銷毀,但可惜我看不懂。我通常用英文起稿,用谷歌翻譯成中文後再修改。中文已經忘了很多,手寫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多年前第一次用台灣護照入境,護照身分證號碼不對無法驗證,海關要我寫出自己的身分歷程才讓我過關入境,過程中多次詢問辦事員字的寫法,辦事員不但取笑我,也懷疑我在台灣讀過書,更別說大學。
§
二○○九年我收到了一本明敏叔簽名的《逃亡》。這是我已經期待很長一段時間的書,從一九七八年感恩節就開始期待,那時更沒想到會在台灣出版。
當年是我讓父親被叫進初中校長辦公室,被校長貼上「思想有問題」的標籤。沒有想到明敏叔會記住四十多年前的事,並公開寫出來。一九七六年我大學畢業去當兵之前父親曾經提過一次,前後都沒人提過。
《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則是完全沒預料到的書,有一天突然看到書評,馬上去訂購。作者名字很熟但我沒見過,父母和祖母都見過他。一個外國人為正義付出很多,其他還有多位默默在背後貢獻。回台灣時,母親有一本作者送的中文版,讀了一次。
《逃亡》和《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台灣白色恐怖》是當事人看到的一面,而我則是在陰影下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一點。這兩本書是一個階段的終點,但也是另一些故事的開始。逃亡發生之前,家屬親人有一些不方便,但當局有特定箭靶,其他人只偶爾會受到當局關懷。事情發生後,當事人在境外,家屬就遭殃了,變成箭靶或是報復對象,時間從明敏叔逃亡到他回台,是一段很長的日子,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我離開之前的日子。我很幸運能在一九七八年離台,讓我嘗試自由的生活,算是一大解脫,至少沒有立即的威脅。父母除了短期出國,仍繼續在台灣生活,台灣是他們的家。
§
我的命運讓我成長在特別的時間和地方,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機會。相對來說,我的生活雖有些不便,但比起真正受害者的生活,卻不值得一提。我已一點一點記錄這些經歷好幾年,卻沒敢發表,一方面是不想讓長輩再回到過去,另一方面是沒有完整的記憶,和家人談話後修正過多次,有些記憶不同。明敏叔還在的時候也不敢發表,因為不想讓他想起往事。我不知道他聽過多少,沒必要讓他多操煩,畢竟他也是有歲數的長輩。
§
雖然背景有些不一樣,但我們不是唯一受到當局關心的家庭。不過奇怪的是,多年來竟沒人出來描述過去被關心的生活。「二二八」、「白色恐怖」當事人有不少紀錄,有文章,有出書,也有影片;當事人關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理由,期滿出來日子不好過也有報告。但家人親屬的生活卻沒人去調查或報告,尤其是那些更無辜的受害人,一家少了一根支柱,一般經濟環境已經不好,加上當權不同單位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後代在那種環境如何成長。除了管區警察特別關心,職業遇到政府不必要的關心之外,幾乎沒人報告其他困難。我只能算是外圍旁觀的人,隔壁在火燒,我家也許有危險但還沒起火,不能真正瞭解他們的苦難。後來的政府有對當年的政治犯道歉,但對他們的妻子卻連提都沒提。
目次
推薦序 今天我來講一個「歸kuānn肉粽」的故事
楊斯棓醫師
01.引言
02.彭明敏與我
03.逃亡
04.自由的滋味
05.全天候監視
06.電話監聽
07.彭和美在哪裡?
08.日本赤軍
09.李太太的兒子
10.殺人嫌疑犯
11.當兵
12.重新開始
13.回航
14.雜事
15.人物八卦
16.母親的二二八
17.家族黑暗的一面
18.家後
19.原住民血統
20.後記
21.附錄:書信
楊斯棓醫師
01.引言
02.彭明敏與我
03.逃亡
04.自由的滋味
05.全天候監視
06.電話監聽
07.彭和美在哪裡?
08.日本赤軍
09.李太太的兒子
10.殺人嫌疑犯
11.當兵
12.重新開始
13.回航
14.雜事
15.人物八卦
16.母親的二二八
17.家族黑暗的一面
18.家後
19.原住民血統
20.後記
21.附錄:書信
書摘/試閱
李太太的兒子
李太太是媽在修女會英文班認識的朋友,比媽大幾歲,同時還有台電總經理夫人、台南劉家女兒等好友。李太太個性開朗,喜歡講笑話,每次她來家裡一定是笑聲不斷。她講話有時很戲劇化,有時還會手腳並用。家裡的巴哥狗(pug)被她笑:坐沒有坐相,站沒有站相,一點也沒差。李先生的父親當過日本時代州長級官員,而他本人則是日本時代台北商業學校畢業,是一家商業銀行中高級經理。李家住在金門街汀州路口,三個兒子都很優秀。老大讀中山醫專,老二讀師大數學系,老三讀台大化學系,高中時和明敏叔的兒子彭旼在建中同學兩年,高三才分班。彭旼讀台大醫學院。
李家老大退伍後準備考牙醫執照,需要複習一些大學基礎醫學問題,和他三弟騎同一台機車去溫州街,找台大醫科剛上過基礎醫學的學生討論,想知道台大教學重點、教科書版本等,是相當合理的想法。他們進屋裡待了一陣子,機車停放在前院,看門狗記錄了機車牌照。李家兄弟離開時,看門狗沒能即時阻擋查問他們的身分、拜訪的動機,以及屋內活動細節。我不知道看門狗的布局方向,也不知道當時多少人出勤。
在那個機車還不是很普遍的時代,記憶中好像沒有其他人騎機車去過溫州街拜訪,學生大多騎自行車,私人轎車也很少,大多訪客會走到大街。一九七○年我哥哥考入台大時,系上只有兩人騎機車。
沒有人特別注意到李家公子的拜訪,同學間討論問題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我們外人根本不會知道李家兩兄弟去溫州街的事。
幾天後李太太講給我媽聽,沒人預料或想像得到,一趟同學互訪居然發展到台北縣市兩地警察調查,其他單位也許有參與調查但沒公開出面。一方面會覺得好笑,低能到難以想像,另一方面則覺得很無奈,要去面對如此無知的政府爪牙。
李太太有一天忽然接到淡水親戚的電話,警告她要小心注意,她兒子跟「極端惡劣份子」(李太太用語)有來往,警察剛大鬧一場後離開這位親戚的淡水住家,不久就會去金門街住宅繼續調查。
淡水在地管區警察帶人馬先到李先生親戚家大肆搜索調查,要知道他們和「彭氏惡徒」(李太太用語)是否有任何關係?如何認識?是哪兩人去溫州街拜訪彭氏惡徒?有何動機或是在籌劃非法活動?淡水親戚被問得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彭氏是何方惡魔?不知道是警察吃錯藥還是在講哪種笑話。溫州街或彭宅對他們完全沒意義,他們只是過平常生活的普通市民,溫州街在哪裡都不是很清楚。警察拿出機車牌照號碼為物證,指出某日某時他們的機車停在溫州街「彭氏惡徒」住宅內,機車牌照登記的是李家親戚淡水地址,「鐵證」已出,要他們把彭氏惡徒的企圖一一招供,不然就要不客氣地嚴辦。即使如此,淡水親戚也想不出溫州街有認識的人,時間也對不出名堂。淡水親戚這才了解是一場大烏龍,機車是他們家的沒錯,但實際上機車平時並沒有停放在淡水住處。
李家的淡水親戚指出,機車確實是他們的,但家裡騎車的年輕人不久前去當兵,暫時沒人騎的機車其實是借給台北的親友李家公子。他們不知道李家公子交往的朋友,更不知道機車騎到哪裡,然後告知警察李家在金門街的地址,麻煩警察去台北李家調查清楚,他們完全沒關聯,無法協助警察調查。如果有犯法,他們會把機車收回,交給警察辦案。警察轉到李家清查他們與彭氏惡徒的關係,和那天拜訪的動機,並警告他們彭氏惡徒的惡行,要他們少和彭氏惡徒來往。
淡水親戚受到很大的驚嚇,無冤無故被警察非法搜索調查。好意把機車借給親戚使用,竟然引起麻煩,真的是「好心被雷親」。不知道李太太後來如何跟淡水親戚解釋他們跟「極端惡劣份子」交往始末,也不知道淡水親戚的反應。正常人不會不了解。
李太太知道彭旼和她小兒子是高中同學,對彭旼印象很好。建中一班五、六十人,考上台大最多也不過十個左右,台大醫學系一年收七十個。也多多少少聽過明敏叔的事,更知道我媽是明敏叔的二嫂,日本時代有讀過書。但還是沒有心理準備,她沒法想像「彭氏惡徒」的惡行。事後李太太還是照常和媽有來往,直到李先生退休後,搬離台北到空氣較好的鄉間,才比較少再來往。後來李大公子如願考取了牙醫執照,老三則前往美國取得博士。
溫州街的訪客都會遭到相似的待遇,通常都是出來就被攔截,調查身分、關係、目的……等等,被攔截調查的人多少會把他們不愉快的經驗告訴我們。巷子裡沒計程車,溫州街也很少,和平東路才有車可叫,如果有訪客出現,巷口兩端都會有人看守。後來敢去溫州街的只有很熟的親友。
§
相似的事件也發生在高雄。
洪先生是堂兄堂姊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也是鹽埕教會的教友,從小就常在伯父家出入,並沒有特別注意。高中畢業後他到台北讀大學,有時會來家裡拜訪,起初是和大堂兄來住我們家,後來他和我們熟了,也會來家裡探訪,後來讀中華神學院也來找家父討論神學。
有一次他回高雄,借用朋友的機車前往伯父家探訪祖母。當時的習慣這是最起碼的禮貌。高雄五福派出所的警察不認識他,沒攔到他查問身分,也許是因為他有段時間沒去伯父家,也許是大學生看起來不一樣,也或許是出入的人太多,但記錄了機車牌照。由機車牌照查出所有人的住家地址,導致他的朋友也被警察大肆搜索調查,鬧了一陣子才找到洪先生出面收拾殘局,完全是「李太太淡水親戚」的翻版。伯父在高雄行醫多年,名聲相當好,當洪先生跟他的朋友講清楚後,他的朋友不能理解警察的愚蠢行為。祖母和伯父聽到消息後,派堂哥帶禮物去幫洪先生的朋友收驚。大白天去拜訪早年陳啟川市長和楊金虎市長都有交往的長輩,居然也會被警察調查。
§
這只是我知道得比較詳細的兩件事,其他類似的案件也不稀奇,也有聽到其他人當場被找麻煩。也許有人因此不敢再來,也許有人認為是當局正常的反應,也許有人不想讓我們有更多的負擔而沒提起。
其實那時候可能有問題的人都在監獄裡,軍事法庭想出來的罪名一定會當真,哪裡有可能讓「彭氏惡徒」在外囂張。
李太太是媽在修女會英文班認識的朋友,比媽大幾歲,同時還有台電總經理夫人、台南劉家女兒等好友。李太太個性開朗,喜歡講笑話,每次她來家裡一定是笑聲不斷。她講話有時很戲劇化,有時還會手腳並用。家裡的巴哥狗(pug)被她笑:坐沒有坐相,站沒有站相,一點也沒差。李先生的父親當過日本時代州長級官員,而他本人則是日本時代台北商業學校畢業,是一家商業銀行中高級經理。李家住在金門街汀州路口,三個兒子都很優秀。老大讀中山醫專,老二讀師大數學系,老三讀台大化學系,高中時和明敏叔的兒子彭旼在建中同學兩年,高三才分班。彭旼讀台大醫學院。
李家老大退伍後準備考牙醫執照,需要複習一些大學基礎醫學問題,和他三弟騎同一台機車去溫州街,找台大醫科剛上過基礎醫學的學生討論,想知道台大教學重點、教科書版本等,是相當合理的想法。他們進屋裡待了一陣子,機車停放在前院,看門狗記錄了機車牌照。李家兄弟離開時,看門狗沒能即時阻擋查問他們的身分、拜訪的動機,以及屋內活動細節。我不知道看門狗的布局方向,也不知道當時多少人出勤。
在那個機車還不是很普遍的時代,記憶中好像沒有其他人騎機車去過溫州街拜訪,學生大多騎自行車,私人轎車也很少,大多訪客會走到大街。一九七○年我哥哥考入台大時,系上只有兩人騎機車。
沒有人特別注意到李家公子的拜訪,同學間討論問題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我們外人根本不會知道李家兩兄弟去溫州街的事。
幾天後李太太講給我媽聽,沒人預料或想像得到,一趟同學互訪居然發展到台北縣市兩地警察調查,其他單位也許有參與調查但沒公開出面。一方面會覺得好笑,低能到難以想像,另一方面則覺得很無奈,要去面對如此無知的政府爪牙。
李太太有一天忽然接到淡水親戚的電話,警告她要小心注意,她兒子跟「極端惡劣份子」(李太太用語)有來往,警察剛大鬧一場後離開這位親戚的淡水住家,不久就會去金門街住宅繼續調查。
淡水在地管區警察帶人馬先到李先生親戚家大肆搜索調查,要知道他們和「彭氏惡徒」(李太太用語)是否有任何關係?如何認識?是哪兩人去溫州街拜訪彭氏惡徒?有何動機或是在籌劃非法活動?淡水親戚被問得一頭霧水,完全不知道彭氏是何方惡魔?不知道是警察吃錯藥還是在講哪種笑話。溫州街或彭宅對他們完全沒意義,他們只是過平常生活的普通市民,溫州街在哪裡都不是很清楚。警察拿出機車牌照號碼為物證,指出某日某時他們的機車停在溫州街「彭氏惡徒」住宅內,機車牌照登記的是李家親戚淡水地址,「鐵證」已出,要他們把彭氏惡徒的企圖一一招供,不然就要不客氣地嚴辦。即使如此,淡水親戚也想不出溫州街有認識的人,時間也對不出名堂。淡水親戚這才了解是一場大烏龍,機車是他們家的沒錯,但實際上機車平時並沒有停放在淡水住處。
李家的淡水親戚指出,機車確實是他們的,但家裡騎車的年輕人不久前去當兵,暫時沒人騎的機車其實是借給台北的親友李家公子。他們不知道李家公子交往的朋友,更不知道機車騎到哪裡,然後告知警察李家在金門街的地址,麻煩警察去台北李家調查清楚,他們完全沒關聯,無法協助警察調查。如果有犯法,他們會把機車收回,交給警察辦案。警察轉到李家清查他們與彭氏惡徒的關係,和那天拜訪的動機,並警告他們彭氏惡徒的惡行,要他們少和彭氏惡徒來往。
淡水親戚受到很大的驚嚇,無冤無故被警察非法搜索調查。好意把機車借給親戚使用,竟然引起麻煩,真的是「好心被雷親」。不知道李太太後來如何跟淡水親戚解釋他們跟「極端惡劣份子」交往始末,也不知道淡水親戚的反應。正常人不會不了解。
李太太知道彭旼和她小兒子是高中同學,對彭旼印象很好。建中一班五、六十人,考上台大最多也不過十個左右,台大醫學系一年收七十個。也多多少少聽過明敏叔的事,更知道我媽是明敏叔的二嫂,日本時代有讀過書。但還是沒有心理準備,她沒法想像「彭氏惡徒」的惡行。事後李太太還是照常和媽有來往,直到李先生退休後,搬離台北到空氣較好的鄉間,才比較少再來往。後來李大公子如願考取了牙醫執照,老三則前往美國取得博士。
溫州街的訪客都會遭到相似的待遇,通常都是出來就被攔截,調查身分、關係、目的……等等,被攔截調查的人多少會把他們不愉快的經驗告訴我們。巷子裡沒計程車,溫州街也很少,和平東路才有車可叫,如果有訪客出現,巷口兩端都會有人看守。後來敢去溫州街的只有很熟的親友。
§
相似的事件也發生在高雄。
洪先生是堂兄堂姊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也是鹽埕教會的教友,從小就常在伯父家出入,並沒有特別注意。高中畢業後他到台北讀大學,有時會來家裡拜訪,起初是和大堂兄來住我們家,後來他和我們熟了,也會來家裡探訪,後來讀中華神學院也來找家父討論神學。
有一次他回高雄,借用朋友的機車前往伯父家探訪祖母。當時的習慣這是最起碼的禮貌。高雄五福派出所的警察不認識他,沒攔到他查問身分,也許是因為他有段時間沒去伯父家,也許是大學生看起來不一樣,也或許是出入的人太多,但記錄了機車牌照。由機車牌照查出所有人的住家地址,導致他的朋友也被警察大肆搜索調查,鬧了一陣子才找到洪先生出面收拾殘局,完全是「李太太淡水親戚」的翻版。伯父在高雄行醫多年,名聲相當好,當洪先生跟他的朋友講清楚後,他的朋友不能理解警察的愚蠢行為。祖母和伯父聽到消息後,派堂哥帶禮物去幫洪先生的朋友收驚。大白天去拜訪早年陳啟川市長和楊金虎市長都有交往的長輩,居然也會被警察調查。
§
這只是我知道得比較詳細的兩件事,其他類似的案件也不稀奇,也有聽到其他人當場被找麻煩。也許有人因此不敢再來,也許有人認為是當局正常的反應,也許有人不想讓我們有更多的負擔而沒提起。
其實那時候可能有問題的人都在監獄裡,軍事法庭想出來的罪名一定會當真,哪裡有可能讓「彭氏惡徒」在外囂張。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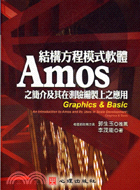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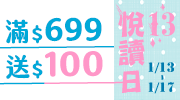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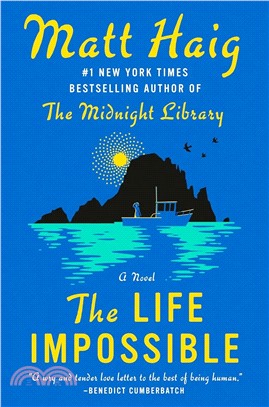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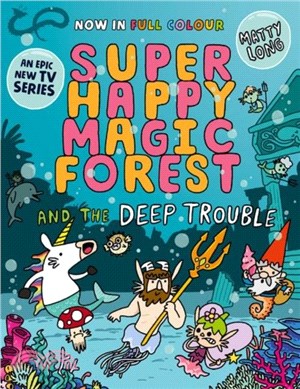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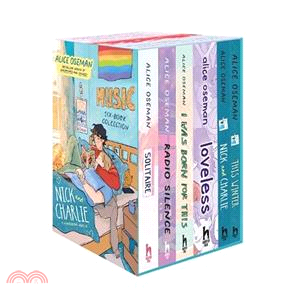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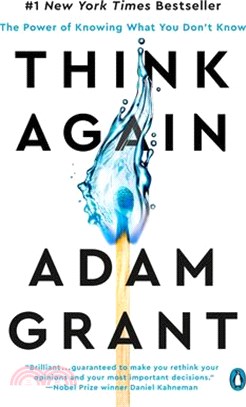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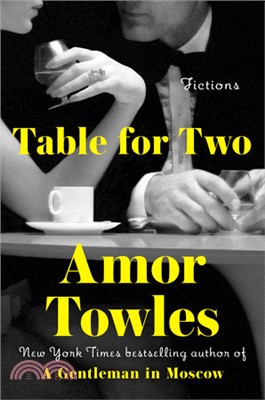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