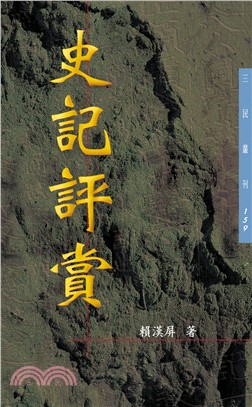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做個自立的人。
做自己的樹。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
首度針對少年所寫,啟發深刻的人生之書
《週刊朝日》連載好評如潮 單行版銷量逾三十六萬冊
紀念新版
再問一個問題,你會想成為怎樣的人?
有鋻於日本寬鬆政策造成基礎教育的崩壞
大江健三郎重新審視學校以及種種孩子所困惑的人生問題
對少年們娓娓道來的心情,成人也會動容。
年近六十、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榮耀的大江健三郎,為了將自身的經驗傳遞給年輕人,一改直搗核心的犀利筆觸,以誠摯而親切的文字,向年輕人娓娓道來他的生命故事與體悟。「為什麼孩子非得要去上學不可呢?」大江開始回顧自己的童年經驗,以及從旁觀察長子光的人生,提出他對教育溫和而深刻的看法。
十六篇以童年生活經驗為題的散文中,他認為最讓年輕人感到壓力的便是課業與未來,這是亙久不變的課題。「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人為什麼要活著?」「自己想要成為怎樣的人?」本書不僅是一本指引青少年課題的解答之書,也是擁抱青少年不安心靈的安慰手札。
打起精神來,請好好地活著。
如果我能夠留下什麼給孩子的話,
希望你們千萬要記得,善待自己心裡的那個人。
親子共讀散文。持續影響深遠的經典。
★書中收錄大江健三郎妻子親繪插畫
游珮芸教授(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專文推薦
「對孩子來說,沒有什麼不可挽回的事,這就是人類世界的原則。孩子自己必須尊重這個『原則』,這是身為孩子最大的榮耀。」――大江健三郎
各界好評
大江健三郎先生通過自己的生命故事,童年時的掙扎與思索,以及成年後實際經歷的事件和感悟,回應年輕讀者可能面臨的問題。這是大江在「自己的樹」下演繹的童年與老年的對話,也是他對年輕讀者的遺言,或者說是能夠在任何年齡讀者心中延續的新生命。――游珮芸(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
當我問起大江老師是否有意願要在報刊上連載作品時,他便拋出了一句:「如果能寫一些孩子也能了解的童話般的短文,感覺會很不錯。」然而當每周一固定去老師家取稿子時,都能看見原稿上有無數的塗改與黏貼,我深感這根本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大江老師總是帶著無比親切的笑容來迎接我,甚至鼓勵我繼續努力。如今我再次拿起這兩本書,總覺得腦子裡有一股無比寂寞的風緩緩拂上面頰。――《週刊朝日》連載擔當編輯山本朋史,週刊朝日2023年3月31日號
在日本文學中,大江健三郎所背負的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書寫是非常巨大、並且孤獨的。不僅現實社會,甚至是在文學作品中,身心障礙者都是被當作異形,或是需要隱藏起來的、伴隨著巨大悲劇的存在。然而大江健三郎卻描繪了這些群體作為「人類」的日常生活,這就像是永遠為你點起一盞照亮黑暗的燈的夥伴。――市川沙央〈破壞與共生的王之死〉,2023年第139回芥川賞得主
對我來說,大江健三郎是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史以來遭遇過的最大的巨人。他的作品,總是讓我覺得他是為了我們而寫的,作為讀者,作為後進,他寫出了我無比憧憬的、理想的、有如身在夢境般讓我淪陷的作品。――中村文則〈作為巨人的存在〉
作為大江健三郎之後的作家,我一方面被他的作品給壓倒而感到不知所措的同時,發現了自己接下來應該克服的課題。――平野啓一郎,《那個男人》作者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寫給孩子的文章,但開始閱讀之後,我發現這是一本成年人用最為誠實的語言,爽快地回答孩子們的疑問的作品。讀完之後我被其中深刻的內容給深深打動了。――日本俳句教育研究會(nhkk)
做自己的樹。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
首度針對少年所寫,啟發深刻的人生之書
《週刊朝日》連載好評如潮 單行版銷量逾三十六萬冊
紀念新版
再問一個問題,你會想成為怎樣的人?
有鋻於日本寬鬆政策造成基礎教育的崩壞
大江健三郎重新審視學校以及種種孩子所困惑的人生問題
對少年們娓娓道來的心情,成人也會動容。
年近六十、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榮耀的大江健三郎,為了將自身的經驗傳遞給年輕人,一改直搗核心的犀利筆觸,以誠摯而親切的文字,向年輕人娓娓道來他的生命故事與體悟。「為什麼孩子非得要去上學不可呢?」大江開始回顧自己的童年經驗,以及從旁觀察長子光的人生,提出他對教育溫和而深刻的看法。
十六篇以童年生活經驗為題的散文中,他認為最讓年輕人感到壓力的便是課業與未來,這是亙久不變的課題。「為什麼孩子要上學?」「人為什麼要活著?」「自己想要成為怎樣的人?」本書不僅是一本指引青少年課題的解答之書,也是擁抱青少年不安心靈的安慰手札。
打起精神來,請好好地活著。
如果我能夠留下什麼給孩子的話,
希望你們千萬要記得,善待自己心裡的那個人。
親子共讀散文。持續影響深遠的經典。
★書中收錄大江健三郎妻子親繪插畫
游珮芸教授(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專文推薦
「對孩子來說,沒有什麼不可挽回的事,這就是人類世界的原則。孩子自己必須尊重這個『原則』,這是身為孩子最大的榮耀。」――大江健三郎
各界好評
大江健三郎先生通過自己的生命故事,童年時的掙扎與思索,以及成年後實際經歷的事件和感悟,回應年輕讀者可能面臨的問題。這是大江在「自己的樹」下演繹的童年與老年的對話,也是他對年輕讀者的遺言,或者說是能夠在任何年齡讀者心中延續的新生命。――游珮芸(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
當我問起大江老師是否有意願要在報刊上連載作品時,他便拋出了一句:「如果能寫一些孩子也能了解的童話般的短文,感覺會很不錯。」然而當每周一固定去老師家取稿子時,都能看見原稿上有無數的塗改與黏貼,我深感這根本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大江老師總是帶著無比親切的笑容來迎接我,甚至鼓勵我繼續努力。如今我再次拿起這兩本書,總覺得腦子裡有一股無比寂寞的風緩緩拂上面頰。――《週刊朝日》連載擔當編輯山本朋史,週刊朝日2023年3月31日號
在日本文學中,大江健三郎所背負的有關身心障礙者的書寫是非常巨大、並且孤獨的。不僅現實社會,甚至是在文學作品中,身心障礙者都是被當作異形,或是需要隱藏起來的、伴隨著巨大悲劇的存在。然而大江健三郎卻描繪了這些群體作為「人類」的日常生活,這就像是永遠為你點起一盞照亮黑暗的燈的夥伴。――市川沙央〈破壞與共生的王之死〉,2023年第139回芥川賞得主
對我來說,大江健三郎是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史以來遭遇過的最大的巨人。他的作品,總是讓我覺得他是為了我們而寫的,作為讀者,作為後進,他寫出了我無比憧憬的、理想的、有如身在夢境般讓我淪陷的作品。――中村文則〈作為巨人的存在〉
作為大江健三郎之後的作家,我一方面被他的作品給壓倒而感到不知所措的同時,發現了自己接下來應該克服的課題。――平野啓一郎,《那個男人》作者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寫給孩子的文章,但開始閱讀之後,我發現這是一本成年人用最為誠實的語言,爽快地回答孩子們的疑問的作品。讀完之後我被其中深刻的內容給深深打動了。――日本俳句教育研究會(nhkk)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風格與傳統如川端康成等人的溫婉柔美不同,自創出一種曲折行進、氣勢洶洶的文體。
1935年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系就讀,即嗜讀卡謬、沙特等作品,初期作品受其影響甚深,以存在主義為形式,呈現社會與個人的關係。1958年,以《飼養》一書榮獲芥川賞,確立他「學生作家」的文壇地位。
1963年,大江的妻子生下一個嚴重殘障的孩子,《萬延元年的足球》便是以此為本,這本代表作榮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大獎。1970年代,他又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逐步引進小說創作中,代表作為《個人的體驗》,該書除獲第十一屆新潮文學獎,並因此作英譯而將他推向國際作家的位置。
大江的小說主題充滿爭議,他將自己歸類為「怪誕現實主義」,他擅長將最強烈的恐懼和下意識願望穿插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合常理的想像瞬間改變現實。其寫作範圍涉獵寬廣且具人本關懷的精神,無論是政治、核能危機、死亡與再生、甚至包括宇宙論,皆呈現在他的創作中。
其著作《靜靜的生活》、《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再見,我的書!》等書由時報出版。
譯者簡介
陳保朱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擔任過網路公司編輯企劃等職務,曾為《華西街的一蕊花》撰文,翻譯漫畫及雜誌文章,現為自由撰稿者及翻譯。
大江健三郎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風格與傳統如川端康成等人的溫婉柔美不同,自創出一種曲折行進、氣勢洶洶的文體。
1935年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6年入東京大學法文系就讀,即嗜讀卡謬、沙特等作品,初期作品受其影響甚深,以存在主義為形式,呈現社會與個人的關係。1958年,以《飼養》一書榮獲芥川賞,確立他「學生作家」的文壇地位。
1963年,大江的妻子生下一個嚴重殘障的孩子,《萬延元年的足球》便是以此為本,這本代表作榮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大獎。1970年代,他又將文化人類學的理念逐步引進小說創作中,代表作為《個人的體驗》,該書除獲第十一屆新潮文學獎,並因此作英譯而將他推向國際作家的位置。
大江的小說主題充滿爭議,他將自己歸類為「怪誕現實主義」,他擅長將最強烈的恐懼和下意識願望穿插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合常理的想像瞬間改變現實。其寫作範圍涉獵寬廣且具人本關懷的精神,無論是政治、核能危機、死亡與再生、甚至包括宇宙論,皆呈現在他的創作中。
其著作《靜靜的生活》、《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再見,我的書!》等書由時報出版。
譯者簡介
陳保朱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擔任過網路公司編輯企劃等職務,曾為《華西街的一蕊花》撰文,翻譯漫畫及雜誌文章,現為自由撰稿者及翻譯。
目次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人為什麼要活著?
在森林裡和海豹一起生活的孩子
想要變成怎樣的人?
抄寫
小孩子的戰鬥方式
新加坡的橡皮球
某間中學的課
我的讀書方法
人流之日
坦克羅頭的爆炸
樹上的讀書之家
對謠言的抵抗力
百年的孩子
沒有無法挽回的事情
請再等上一段時間
推薦跋 〈在「自己的樹」下,老年大江健三郎與少年的對話〉――游珮芸(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
人為什麼要活著?
在森林裡和海豹一起生活的孩子
想要變成怎樣的人?
抄寫
小孩子的戰鬥方式
新加坡的橡皮球
某間中學的課
我的讀書方法
人流之日
坦克羅頭的爆炸
樹上的讀書之家
對謠言的抵抗力
百年的孩子
沒有無法挽回的事情
請再等上一段時間
推薦跋 〈在「自己的樹」下,老年大江健三郎與少年的對話〉――游珮芸(台東大學兒文所所長)
書摘/試閱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1 到目前為止的人生當中,我曾經兩度思考過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痛苦,但是除了思考
之外別無他法。不過,就算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擁有過沉殿思考的時間,日後回想起來,就知道其實非常具有意義。 當我思考此事的時候,很幸運地,兩次都得到了好答案。我認為這是自己人生裡所得到不計其數的各式問題的答案中最好的一個。 初次遇上小孩子為什麼要上學這個問題,與其說是思索不如說是強烈質疑,那發生在我十歲那年的秋天。當年夏天,我的國家在太平洋戰爭戰敗。在這次戰爭中,日本和美、英、荷、中等聯盟國開打,核子彈第一次降落在人間都市。 因為戰敗,致使日本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那以前,我們小孩子,甚至大人,都被教育著去相信,我們的國家裡具有強大力量的天皇是個「神」。但是戰敗後,很顯然天皇也不過是個凡人而已。 戰爭的敵對國家裡,美國是我們最為恐懼,也最憎恨的敵人。然而現在,它卻是我們要從戰爭的傷害中重新站起來時最依賴的國家。 我認為這樣的變化是對的。我也很清楚,與其讓「神」來支配著現實社會,還不如施行民主,讓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更好。我漸漸感受到,我們不再有軍隊,不用因為有了敵人,就必須去殺別國的人(也可能會被殺),是個很了不起的變化。 戰爭結束的一個月後,我就不再去上學了。 直到盛夏之前,老師們原本說著天皇是「神」,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還說美國人不是人,是鬼、是野獸;突然間他們毫不在意地開始說著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錯了,現在需要反省,只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說,我們天皇也是人,而美國人則是朋友。 美國駐軍部隊乘著幾部吉普車,進入位在森林山谷間的小村莊裡――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學生們站在道路兩旁,搖著手製星條旗,大叫著Hello,夾道歡迎。那天,我離開了學校,走入森林裡。 從高處向下望著山谷,像迷你模型的吉普車沿著河旁的道路駛來,雖然瞧不清楚豆粒般大小的孩子臉上的表情,但確實聽到了Hello的叫聲,我突然流下了眼淚。
2 隔天早上開始,我一到學校就馬上從後門溜出,跑進森林裡,一個人待到傍晚。我帶著一大本植物圖鑑。把森林裡樹木的正確名稱對照著圖鑑,一一地確認並牢記在腦中。 我家從事某項和森林管理有關的工作,所以,我只要把森林裡的樹木名稱和性質都記起來,將來生活上一定派得上用場。森林裡樹木種類非常多,每一棵樹的名稱和性質都各不相同,我覺得有趣極了,幾乎沉迷於其中。到現在我還記得的樹木拉丁文學名,大多是這時候經過實地踏查、學習而來的。 我已經不打算再去學校上課了。我認為獨自在森林中,從植物圖鑑裡學好樹木的名稱和性質,就算是長大了,生活也一定不成問題。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學校裡沒有可以互相討論的老師或同學,聊聊我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樹木。我為什麼要去這樣的學校,學些和長大之後的生活似乎完全無關的東西呢? 在秋天裡一個下著大雨的日子,我仍舊繞進森林裡。雨越下越大,在林中四處形成前所未見的湍急水流,道路被土石沖毀。到了夜裡,我還是無法走回山谷裡。我發起高燒,隔日,被發現倒臥在一棵巨大的七葉樹底的洞裡,是村子裡的消防隊員們把我救了出來。 回到家中,我依舊高燒不退,從隔壁鎮上請來的醫生說――我像作夢一樣聽著――已經藥石罔效,無藥可醫了。他說完就回去了。只剩下母親,仍舊抱著希望繼續看護我。
當天深夜,我還是持續發著高燒,依舊感覺很虛弱,但是,我卻從像被熱風包圍的夢中世界裡睜開眼,腦筋清醒過來。 如今連在鄉下也很少見了,在日本過去的房子裡,大多是直接在榻榻米地板上舖好棉被就寢,而我就這樣睡著。枕邊坐著應該已經好幾日沒闔眼的母親,低頭看著我。接下來我們是以方言進行對話,但是為了讓年輕人也看得懂,所以我改成一般日語。 我也覺得自己情況不樂觀,慢慢悄聲問她。 ――媽媽,我快要死掉了嗎? ――我不認為你會死。我希望你不要死掉。 ――我聽到醫生說,這個孩子快死了,已經沒救了。他認為我會死吧!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 ――就算你真的死了,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別擔心。 ――但是,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 ――不,是一樣的!我一生下你之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所以,你們兩個孩子就會一模一樣了哦! 母親這麼回答我。 我雖然還搞不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心情平靜了下來,好好地睡了一覺。隔天早上,我就開始復原了。不過恢復得很慢,到了初冬,我才能自己去上學。
3 在教室裡上課或者是在運動場上玩棒球時――這是戰爭結束後盛行的新運動;我總會不知不覺地發著呆,一個人陷入沉思。我想著,現在在這裡的我,會不會是那發燒痛苦的孩子死掉後,媽媽再次生出來的新小孩呢?我那些舊有的回憶,是不是媽媽把那個死去的孩子所見、所聽、所讀、所做的事情,全部說給我聽,才知道的呢?而我是不是因為繼承了死去孩子所使用的語言,才可以像這樣思考、說話呢? 在教室裡或是運動場上的這些孩伴們,是不是也都經過媽媽們把那些不能長大的孩子所見、所聽、所聞、所讀過的書、做過的事重述,讓他們代替那些孩子繼續活下去呢?而這件事的證據就是我們大家都繼承了同樣的語言在說話。 而我們每個人不就是為了把這個語言變成自己的東西,所以才到學校來的嗎?我想不僅是國語、理科、算數,就連體操,也都是為了繼承死去孩子們的語言所必須學習的東西!獨自一個人跑到森林中,對照著植物圖鑑和眼前的樹木,並不能代替死去的孩子,不能和他同化,變成新的小孩。所以,我們必須到學校來,大家一起讀書、一起遊戲…… 我現在所講的事情,或許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我自己也是在很久以後才想起這個經驗,對於長大後的自己來說,那個初冬裡,好不容易養好了病,帶著平靜的喜悅再度回到學校時,才發現,一直以為已經理解清楚的事情,其實自己根本沒搞懂。 另一方面,對於現在身為小孩子、新孩子的你們,我抱著可以讓大家輕鬆理解的期望,把這從未曾書寫下的回憶細數出來。
4 另一個回憶是在我長大成人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我家裡的第一個小孩,是一個男孩,叫做光。他出生時腦部異常,頭看起來有兩個大,後面長了一個大瘤。我們請醫生盡可能地把瘤切除縫合,而不要影響到腦部本體。 光很快長大,可是到了四、五歲還是不會講話。然而他對聲音的高低、音色非常敏感,比起人類的語言,他更記得許多野鳥唱的歌曲。而且,他一聽到鳥兒唱歌,就會說出在唱片上學到的小鳥名稱。這就是光最初學會的語言。 光七歲時,比一般健康的孩子晚一年入學,並進入「特教班」就讀。那裡聚集了各式各樣身體殘障的孩子。有的孩子一直大聲尖叫,也有的孩子不能安靜片刻,動個不停,不斷撞桌子、翻倒椅子。從窗戶往裡頭窺看,光總是兩手捂著耳朵,身體僵硬著。 這時,已經是大人的我,又再次問了自己和孩童時代同樣的問題。光為什麼非去學校不可呢?他清楚野鳥的歌聲,喜歡父母教他認識小鳥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回到村子裡,住在森林高地草原上的家中,三個人一起生活呢?我可以讀著植物圖鑑,確認樹木的名稱和性質,光可以聆聽小鳥的歌聲,說出牠的名字。我太太可以幫我們兩個人畫素描,煮飯做菜。為什麼不能這樣呢? 但是,這個連身為大人的我都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光自己找到了答案。光進入「特教班」不久,就找了和自己一樣不喜歡大聲噪音的朋友。後來,這兩個小傢伙就常常一起窩在教室角落,手牽著手忍耐著。 而且,光還幫助這位運動能力比自己還弱的朋友去上廁所。自己對朋友有所幫助,這件事情對於在家中只能完全依靠母親的光而言,是非常新鮮的喜悅。之後,這兩個人就在與其他的孩子有段距離的地方,並坐在一起聽FM音樂廣播。 過了一年,光發現自己對於人類所作的音樂,比對鳥兒的歌聲更能理解。光甚至會把廣播中朋友喜歡的曲目抄寫在紙上,帶回家來,然後翻找家中的CD。就連老師也發現幾乎不說話的兩人,他們之間開始用巴哈、莫札特等字眼。
5
「特教班」到殘障學校,光都和這位朋友一起上學。在日本,高中三年結束後,就沒有智障兒可唸的學校了。畢業的這一天,老師必須對著將要畢業的光和同學解說,明日開始就不必上學,而我也以家長的身分陪同聽著。 在畢業典禮的party上,聽了好幾次明天開始不必來上學的說明後,光終於理解地說: ――真是不可思議啊! 過一會兒他的朋友也說: ――嗯,真是不可思議。 他很認真地回了話。兩個人像是嚇了一跳,說完後,浮現出平靜的微笑。 光跟著母親開始學習音樂,為了已經可以作曲的光,我以這段對話為基礎,寫下了一首詩,由光來譜曲。從這首曲子所發展出來的「畢業˙變奏曲式」曾在各演奏會上演出,很多人都聽過。 現在,對光而言,音樂是為了確認自己內心深處的豐富寶藏,並且傳遞給他人讓自己和社會有所連結的最有效語言。它雖然是萌發於家庭生活中,但是卻是在光上學之後形成。不管是國語也好,理科或算數、體操或是音樂也罷,這些語言都是為了充分瞭解自己,並且與其他人連繫。外語也是一樣。 為了學習這些東西,我想不管在任何時代,這世界上的孩子們,都應該要去上學。
(待續)
1 到目前為止的人生當中,我曾經兩度思考過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雖然痛苦,但是除了思考
之外別無他法。不過,就算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擁有過沉殿思考的時間,日後回想起來,就知道其實非常具有意義。 當我思考此事的時候,很幸運地,兩次都得到了好答案。我認為這是自己人生裡所得到不計其數的各式問題的答案中最好的一個。 初次遇上小孩子為什麼要上學這個問題,與其說是思索不如說是強烈質疑,那發生在我十歲那年的秋天。當年夏天,我的國家在太平洋戰爭戰敗。在這次戰爭中,日本和美、英、荷、中等聯盟國開打,核子彈第一次降落在人間都市。 因為戰敗,致使日本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那以前,我們小孩子,甚至大人,都被教育著去相信,我們的國家裡具有強大力量的天皇是個「神」。但是戰敗後,很顯然天皇也不過是個凡人而已。 戰爭的敵對國家裡,美國是我們最為恐懼,也最憎恨的敵人。然而現在,它卻是我們要從戰爭的傷害中重新站起來時最依賴的國家。 我認為這樣的變化是對的。我也很清楚,與其讓「神」來支配著現實社會,還不如施行民主,讓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權利更好。我漸漸感受到,我們不再有軍隊,不用因為有了敵人,就必須去殺別國的人(也可能會被殺),是個很了不起的變化。 戰爭結束的一個月後,我就不再去上學了。 直到盛夏之前,老師們原本說著天皇是「神」,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還說美國人不是人,是鬼、是野獸;突然間他們毫不在意地開始說著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錯了,現在需要反省,只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說,我們天皇也是人,而美國人則是朋友。 美國駐軍部隊乘著幾部吉普車,進入位在森林山谷間的小村莊裡――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學生們站在道路兩旁,搖著手製星條旗,大叫著Hello,夾道歡迎。那天,我離開了學校,走入森林裡。 從高處向下望著山谷,像迷你模型的吉普車沿著河旁的道路駛來,雖然瞧不清楚豆粒般大小的孩子臉上的表情,但確實聽到了Hello的叫聲,我突然流下了眼淚。
2 隔天早上開始,我一到學校就馬上從後門溜出,跑進森林裡,一個人待到傍晚。我帶著一大本植物圖鑑。把森林裡樹木的正確名稱對照著圖鑑,一一地確認並牢記在腦中。 我家從事某項和森林管理有關的工作,所以,我只要把森林裡的樹木名稱和性質都記起來,將來生活上一定派得上用場。森林裡樹木種類非常多,每一棵樹的名稱和性質都各不相同,我覺得有趣極了,幾乎沉迷於其中。到現在我還記得的樹木拉丁文學名,大多是這時候經過實地踏查、學習而來的。 我已經不打算再去學校上課了。我認為獨自在森林中,從植物圖鑑裡學好樹木的名稱和性質,就算是長大了,生活也一定不成問題。另一方面,也因為在學校裡沒有可以互相討論的老師或同學,聊聊我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樹木。我為什麼要去這樣的學校,學些和長大之後的生活似乎完全無關的東西呢? 在秋天裡一個下著大雨的日子,我仍舊繞進森林裡。雨越下越大,在林中四處形成前所未見的湍急水流,道路被土石沖毀。到了夜裡,我還是無法走回山谷裡。我發起高燒,隔日,被發現倒臥在一棵巨大的七葉樹底的洞裡,是村子裡的消防隊員們把我救了出來。 回到家中,我依舊高燒不退,從隔壁鎮上請來的醫生說――我像作夢一樣聽著――已經藥石罔效,無藥可醫了。他說完就回去了。只剩下母親,仍舊抱著希望繼續看護我。
當天深夜,我還是持續發著高燒,依舊感覺很虛弱,但是,我卻從像被熱風包圍的夢中世界裡睜開眼,腦筋清醒過來。 如今連在鄉下也很少見了,在日本過去的房子裡,大多是直接在榻榻米地板上舖好棉被就寢,而我就這樣睡著。枕邊坐著應該已經好幾日沒闔眼的母親,低頭看著我。接下來我們是以方言進行對話,但是為了讓年輕人也看得懂,所以我改成一般日語。 我也覺得自己情況不樂觀,慢慢悄聲問她。 ――媽媽,我快要死掉了嗎? ――我不認為你會死。我希望你不要死掉。 ――我聽到醫生說,這個孩子快死了,已經沒救了。他認為我會死吧!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 ――就算你真的死了,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別擔心。 ――但是,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 ――不,是一樣的!我一生下你之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所以,你們兩個孩子就會一模一樣了哦! 母親這麼回答我。 我雖然還搞不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心情平靜了下來,好好地睡了一覺。隔天早上,我就開始復原了。不過恢復得很慢,到了初冬,我才能自己去上學。
3 在教室裡上課或者是在運動場上玩棒球時――這是戰爭結束後盛行的新運動;我總會不知不覺地發著呆,一個人陷入沉思。我想著,現在在這裡的我,會不會是那發燒痛苦的孩子死掉後,媽媽再次生出來的新小孩呢?我那些舊有的回憶,是不是媽媽把那個死去的孩子所見、所聽、所讀、所做的事情,全部說給我聽,才知道的呢?而我是不是因為繼承了死去孩子所使用的語言,才可以像這樣思考、說話呢? 在教室裡或是運動場上的這些孩伴們,是不是也都經過媽媽們把那些不能長大的孩子所見、所聽、所聞、所讀過的書、做過的事重述,讓他們代替那些孩子繼續活下去呢?而這件事的證據就是我們大家都繼承了同樣的語言在說話。 而我們每個人不就是為了把這個語言變成自己的東西,所以才到學校來的嗎?我想不僅是國語、理科、算數,就連體操,也都是為了繼承死去孩子們的語言所必須學習的東西!獨自一個人跑到森林中,對照著植物圖鑑和眼前的樹木,並不能代替死去的孩子,不能和他同化,變成新的小孩。所以,我們必須到學校來,大家一起讀書、一起遊戲…… 我現在所講的事情,或許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我自己也是在很久以後才想起這個經驗,對於長大後的自己來說,那個初冬裡,好不容易養好了病,帶著平靜的喜悅再度回到學校時,才發現,一直以為已經理解清楚的事情,其實自己根本沒搞懂。 另一方面,對於現在身為小孩子、新孩子的你們,我抱著可以讓大家輕鬆理解的期望,把這從未曾書寫下的回憶細數出來。
4 另一個回憶是在我長大成人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我家裡的第一個小孩,是一個男孩,叫做光。他出生時腦部異常,頭看起來有兩個大,後面長了一個大瘤。我們請醫生盡可能地把瘤切除縫合,而不要影響到腦部本體。 光很快長大,可是到了四、五歲還是不會講話。然而他對聲音的高低、音色非常敏感,比起人類的語言,他更記得許多野鳥唱的歌曲。而且,他一聽到鳥兒唱歌,就會說出在唱片上學到的小鳥名稱。這就是光最初學會的語言。 光七歲時,比一般健康的孩子晚一年入學,並進入「特教班」就讀。那裡聚集了各式各樣身體殘障的孩子。有的孩子一直大聲尖叫,也有的孩子不能安靜片刻,動個不停,不斷撞桌子、翻倒椅子。從窗戶往裡頭窺看,光總是兩手捂著耳朵,身體僵硬著。 這時,已經是大人的我,又再次問了自己和孩童時代同樣的問題。光為什麼非去學校不可呢?他清楚野鳥的歌聲,喜歡父母教他認識小鳥的名字,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回到村子裡,住在森林高地草原上的家中,三個人一起生活呢?我可以讀著植物圖鑑,確認樹木的名稱和性質,光可以聆聽小鳥的歌聲,說出牠的名字。我太太可以幫我們兩個人畫素描,煮飯做菜。為什麼不能這樣呢? 但是,這個連身為大人的我都難以回答的問題,是光自己找到了答案。光進入「特教班」不久,就找了和自己一樣不喜歡大聲噪音的朋友。後來,這兩個小傢伙就常常一起窩在教室角落,手牽著手忍耐著。 而且,光還幫助這位運動能力比自己還弱的朋友去上廁所。自己對朋友有所幫助,這件事情對於在家中只能完全依靠母親的光而言,是非常新鮮的喜悅。之後,這兩個人就在與其他的孩子有段距離的地方,並坐在一起聽FM音樂廣播。 過了一年,光發現自己對於人類所作的音樂,比對鳥兒的歌聲更能理解。光甚至會把廣播中朋友喜歡的曲目抄寫在紙上,帶回家來,然後翻找家中的CD。就連老師也發現幾乎不說話的兩人,他們之間開始用巴哈、莫札特等字眼。
5
「特教班」到殘障學校,光都和這位朋友一起上學。在日本,高中三年結束後,就沒有智障兒可唸的學校了。畢業的這一天,老師必須對著將要畢業的光和同學解說,明日開始就不必上學,而我也以家長的身分陪同聽著。 在畢業典禮的party上,聽了好幾次明天開始不必來上學的說明後,光終於理解地說: ――真是不可思議啊! 過一會兒他的朋友也說: ――嗯,真是不可思議。 他很認真地回了話。兩個人像是嚇了一跳,說完後,浮現出平靜的微笑。 光跟著母親開始學習音樂,為了已經可以作曲的光,我以這段對話為基礎,寫下了一首詩,由光來譜曲。從這首曲子所發展出來的「畢業˙變奏曲式」曾在各演奏會上演出,很多人都聽過。 現在,對光而言,音樂是為了確認自己內心深處的豐富寶藏,並且傳遞給他人讓自己和社會有所連結的最有效語言。它雖然是萌發於家庭生活中,但是卻是在光上學之後形成。不管是國語也好,理科或算數、體操或是音樂也罷,這些語言都是為了充分瞭解自己,並且與其他人連繫。外語也是一樣。 為了學習這些東西,我想不管在任何時代,這世界上的孩子們,都應該要去上學。
(待續)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