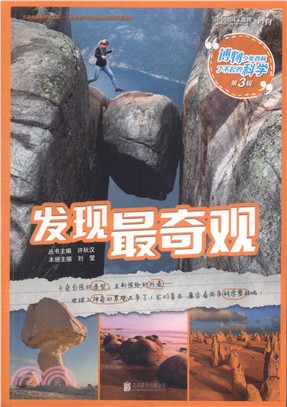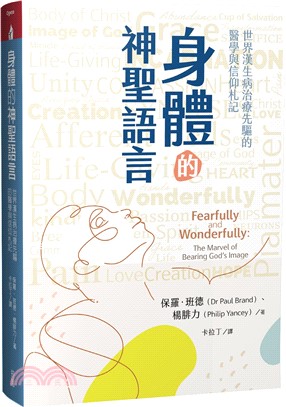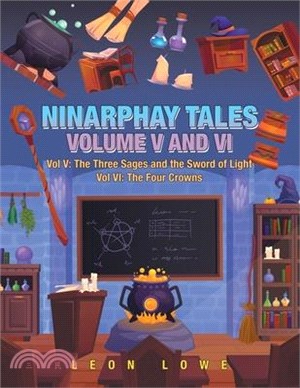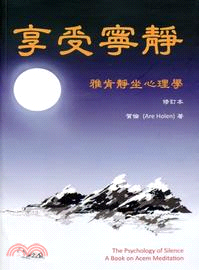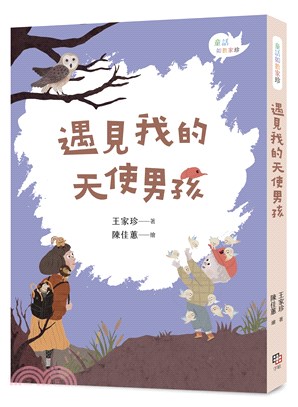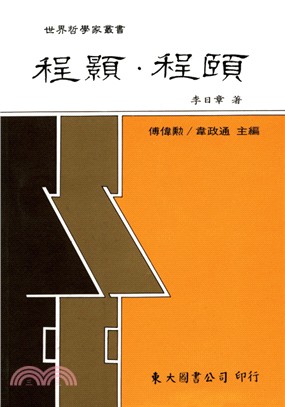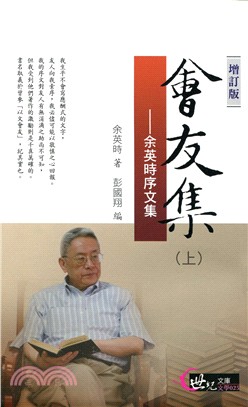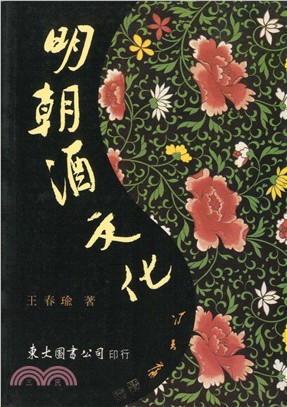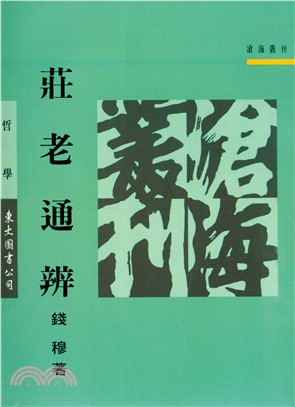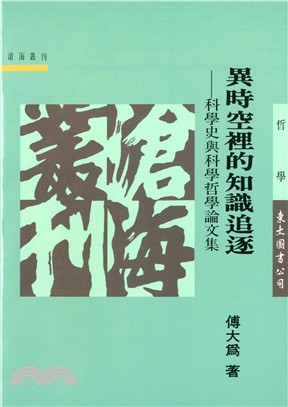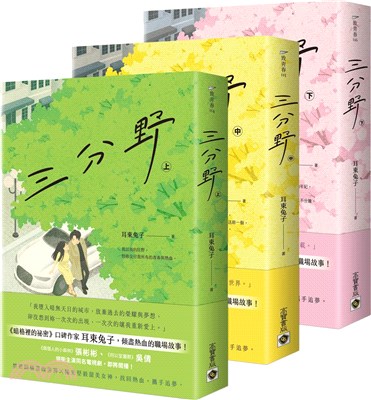意義的意志:弗蘭可意義治療法七講
商品資訊
系列名:common
ISBN13:9786267283233
替代書名:The Will to Meaning: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Logotherapy
出版社:大家
作者:弗蘭可
譯者:宋文里
出版日:2023/11/08
裝訂/頁數:精裝/240頁
規格:21.5cm*14.6cm*1.7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意義治療法的必讀經典
很可能是自佛洛伊德和阿德勒以來,最重要的思想。
――――――《美國精神病學雜誌》――――――
人的一切,都來自尋求意義的意志。
無論是阿德勒的權力意志,或佛洛伊德的享樂意志,都只是意義意志的衍生物。
從二十世紀開始,空虛與無意義成了人人都會面臨的課題。以弗蘭可醫師的話來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問題,就是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
而在存在主義精神醫學之中,意義治療法是唯一演化出一套技法的學派。藉由「反反思」與「弔詭意向」這兩種技法,弗蘭可示範了治療師如何與患者共同對抗存在空虛。在意義已變得愈發輕薄微小的今日,意義治療法的位置在何處,又該如何應用?本書詳細闡明了意義治療法與存在主義、精神醫學甚至神學領域的重疊與差異,是深入了解弗蘭可思想的必讀之作。
世人皆知,弗蘭可醫師曾待過四個納粹集中營。當他倖免生還,重回醫療崗位,不時會遇到身染不治之症的患者哭喊著問: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那樣毫無道理的無妄苦難也曾深深折磨著弗蘭可,而正是在集中營的煎熬經歷讓他開創出意義治療法。這是他走出死蔭幽谷之後所創的生命之道,其後四十年,他將一生都奉獻給意義治療,協助人們走出憂鬱、自殺意念,以及現代人特有的焦慮感與存在空虛。
本書由弗蘭可的演講所彙編而成,闡釋了意義治療法特有的體系、假設與主張,還有基礎信念。各章交織成一面關聯之網,說明了意義治療法的三大概念:意志的自由、朝向意義的意志、生命的意義。
意志的自由指的是人類意志的自由。但它絕非無條件的自由,而是指面臨任何條件時,都有採取立場的自由。人生來即是關注意義與價値的動物,但若想激發出朝向意義的意志,就要先闡明意義為何物。弗蘭可強調,意義必須設法去發現,而非由誰任意給出,並且有一定答案。換言之,每個問題總有一個答案,亦即正確的那個。在各種特定處境中,都只有一個特定意義,那便是它眞正的意義。而只要意義存在,人類就有意志朝它前行。人一生持續在追尋,也有自由著手實現的,正是生命的意義。
人類要活著,便需要意義──意義治療法的理論即奠基於此。在心理治療中,真正重要的並非技法與動力的詮釋,而是治療師與個案、醫師與患者之間作為「人」的關係,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存在會遇(existential encounter)。唯有當一個人遇上了另一個人,一個存有(being)遇上了另一個存有,會遇的意義與效果才會顯現。弗蘭可的主張與當時只強調動力論的精神分析不同,他認為人並非只會被各種驅力或本能推動,人也會被意義拉住。意義治療法不僅關注人作為存有的狀態,更強調意義本身。
此外,它增加了新的向度,將「特屬於人的現象」這個向度加入心理治療,而所謂「特屬於人的現象」,就是「自我超越的能力」,以及「自我抽離的能力」,兩者都是讓意義得以存在的關鍵因素。人本質上即有一種自我超越性與自我抽離性,前者會使人的存有往外延伸、超越自己,後者則讓人得以抽離於處境之外,乃至抽離於自身之外,也因此能賦予自己真正的態度價值,實現自己非做不可之事。
本書的核心主旨在於,人的一切,都來自尋求意義的意志。無論是阿德勒的權力意志,或佛洛伊德的享樂意志,都只是意義意志的衍生物。享樂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實現意義後所得的副作用;權力與其說是目的,實際上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人只有找不到意義時,才會轉而尋求權力與享樂。而在命運的不可改變性之下,人總是可以改變自己。人有能力型塑以及再型塑自己,對弗蘭可而言,這是人的特權,也是構成存在的要件。
我認為《意義的意志》是過去五十年心理學思想的傑出貢獻之一。
―――― 卡爾•羅傑斯 ――――
《成為一個人》作者
很可能是自佛洛伊德和阿德勒以來,最重要的思想。
――――――《美國精神病學雜誌》――――――
人的一切,都來自尋求意義的意志。
無論是阿德勒的權力意志,或佛洛伊德的享樂意志,都只是意義意志的衍生物。
從二十世紀開始,空虛與無意義成了人人都會面臨的課題。以弗蘭可醫師的話來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問題,就是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
而在存在主義精神醫學之中,意義治療法是唯一演化出一套技法的學派。藉由「反反思」與「弔詭意向」這兩種技法,弗蘭可示範了治療師如何與患者共同對抗存在空虛。在意義已變得愈發輕薄微小的今日,意義治療法的位置在何處,又該如何應用?本書詳細闡明了意義治療法與存在主義、精神醫學甚至神學領域的重疊與差異,是深入了解弗蘭可思想的必讀之作。
世人皆知,弗蘭可醫師曾待過四個納粹集中營。當他倖免生還,重回醫療崗位,不時會遇到身染不治之症的患者哭喊著問:生命的意義究竟何在?那樣毫無道理的無妄苦難也曾深深折磨著弗蘭可,而正是在集中營的煎熬經歷讓他開創出意義治療法。這是他走出死蔭幽谷之後所創的生命之道,其後四十年,他將一生都奉獻給意義治療,協助人們走出憂鬱、自殺意念,以及現代人特有的焦慮感與存在空虛。
本書由弗蘭可的演講所彙編而成,闡釋了意義治療法特有的體系、假設與主張,還有基礎信念。各章交織成一面關聯之網,說明了意義治療法的三大概念:意志的自由、朝向意義的意志、生命的意義。
意志的自由指的是人類意志的自由。但它絕非無條件的自由,而是指面臨任何條件時,都有採取立場的自由。人生來即是關注意義與價値的動物,但若想激發出朝向意義的意志,就要先闡明意義為何物。弗蘭可強調,意義必須設法去發現,而非由誰任意給出,並且有一定答案。換言之,每個問題總有一個答案,亦即正確的那個。在各種特定處境中,都只有一個特定意義,那便是它眞正的意義。而只要意義存在,人類就有意志朝它前行。人一生持續在追尋,也有自由著手實現的,正是生命的意義。
人類要活著,便需要意義──意義治療法的理論即奠基於此。在心理治療中,真正重要的並非技法與動力的詮釋,而是治療師與個案、醫師與患者之間作為「人」的關係,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存在會遇(existential encounter)。唯有當一個人遇上了另一個人,一個存有(being)遇上了另一個存有,會遇的意義與效果才會顯現。弗蘭可的主張與當時只強調動力論的精神分析不同,他認為人並非只會被各種驅力或本能推動,人也會被意義拉住。意義治療法不僅關注人作為存有的狀態,更強調意義本身。
此外,它增加了新的向度,將「特屬於人的現象」這個向度加入心理治療,而所謂「特屬於人的現象」,就是「自我超越的能力」,以及「自我抽離的能力」,兩者都是讓意義得以存在的關鍵因素。人本質上即有一種自我超越性與自我抽離性,前者會使人的存有往外延伸、超越自己,後者則讓人得以抽離於處境之外,乃至抽離於自身之外,也因此能賦予自己真正的態度價值,實現自己非做不可之事。
本書的核心主旨在於,人的一切,都來自尋求意義的意志。無論是阿德勒的權力意志,或佛洛伊德的享樂意志,都只是意義意志的衍生物。享樂與其說是目的,不如說是實現意義後所得的副作用;權力與其說是目的,實際上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人只有找不到意義時,才會轉而尋求權力與享樂。而在命運的不可改變性之下,人總是可以改變自己。人有能力型塑以及再型塑自己,對弗蘭可而言,這是人的特權,也是構成存在的要件。
我認為《意義的意志》是過去五十年心理學思想的傑出貢獻之一。
―――― 卡爾•羅傑斯 ――――
《成為一個人》作者
作者簡介
弗蘭可 (Viktor E. Frankl)
1905年出生於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取得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他曾是維也納醫學院的神經科與精神科教授,擔任維也納市立醫院門診部神經科主任長達25年。哈佛、史丹佛、達拉斯、匹茲堡等大學都曾邀他擔任客座教授,他也曾以特聘教授的身分至美國聖地牙哥與加州等地的大學任教。
二戰期間,他遭囚禁於奧徙維茲、達豪等集中營長達三年,因而一生都特別關注存在的痛苦、挫折,以及現代人特有的焦慮與空虛。他的意義治療法為心理學注入前輩諸大師所疏忽的人性關懷,開創了心理學的新里程。此後40年,他在世界各地發表了無數演講,包括台灣,並獲得歐洲、美洲、亞洲與非洲等地大學頒發的總共29個榮譽博士頭銜,以及諸多獎項,包括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普菲斯特奧斯卡獎、奧地利科學院的榮譽會員等。
1997年,弗蘭可於維也納逝世,一生留下39本著作,至今譯成48種語言。
宋文里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組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博導。專長領域為文化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精神分析、宗教研究、藝術心理學。
著有:《心理學與理心術:心靈的社會建構八講》,《鬼神・巫覡・信仰:宗教的動力心理學八講》,《文化心理學的尋語路:邁向心理學的下一頁》。
譯有:《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人類本性原論》(On Human Nature),《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觀點》(The Culture of Education),《宗教的動力心理學》(A Dynamic Psychology of Religion),《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The Suppressed Madness of Sane Men: Forty-four Years of Exploring Psychoanalysis),《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Therapy as Social Construction),以及選譯╱評註佛洛伊德作品:《重讀佛洛伊德》,《魔鬼學:從無意識到憂鬱、自戀、死本能》。
1905年出生於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取得醫學博士與哲學博士學位。他曾是維也納醫學院的神經科與精神科教授,擔任維也納市立醫院門診部神經科主任長達25年。哈佛、史丹佛、達拉斯、匹茲堡等大學都曾邀他擔任客座教授,他也曾以特聘教授的身分至美國聖地牙哥與加州等地的大學任教。
二戰期間,他遭囚禁於奧徙維茲、達豪等集中營長達三年,因而一生都特別關注存在的痛苦、挫折,以及現代人特有的焦慮與空虛。他的意義治療法為心理學注入前輩諸大師所疏忽的人性關懷,開創了心理學的新里程。此後40年,他在世界各地發表了無數演講,包括台灣,並獲得歐洲、美洲、亞洲與非洲等地大學頒發的總共29個榮譽博士頭銜,以及諸多獎項,包括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普菲斯特奧斯卡獎、奧地利科學院的榮譽會員等。
1997年,弗蘭可於維也納逝世,一生留下39本著作,至今譯成48種語言。
宋文里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心理學系諮商心理學組博士,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澳門城市大學博導。專長領域為文化心理學、人格心理學、精神分析、宗教研究、藝術心理學。
著有:《心理學與理心術:心靈的社會建構八講》,《鬼神・巫覡・信仰:宗教的動力心理學八講》,《文化心理學的尋語路:邁向心理學的下一頁》。
譯有:《成為一個人》,(On Becoming a Person),《人類本性原論》(On Human Nature),《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觀點》(The Culture of Education),《宗教的動力心理學》(A Dynamic Psychology of Religion),《正常人被鎮壓的瘋狂》(The Suppressed Madness of Sane Men: Forty-four Years of Exploring Psychoanalysis),《關係的存有:超越自我・超越社群》(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翻轉與重建:心理治療與社會建構》(Therapy as Social Construction),以及選譯╱評註佛洛伊德作品:《重讀佛洛伊德》,《魔鬼學:從無意識到憂鬱、自戀、死本能》。
序
序
本書是由一系列受邀演講稿彙輯而成。邀請者是德州達拉斯的南美以美大學(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的普金斯學院(Perkins School),時在1966年的暑修班。我被指定的講題是解釋意義治療法特有的體系。雖然有不少作者指出:相對於其他學派的存在主義精神醫療法而言,意義治療法已發展出某種確定的心理治療技法,但知道的人不多。那是迄今為止唯一在概念上能自成體系的治療法。
為了處理此一體系的基礎,本書各章就要來談談意義治療法背後的基本假定以及一些主張。各章之間形成了一個關聯網,要之,意義治療法有以下三個基本概念:(1)意志的自由;(2)朝向意義的意志;(3)生命的意義。
(1)意志的自由包含了決定論(determinism)與泛決定論(pan-determinism)相對的問題。(2)意義的意志所討論的概念乃是有別於朝向權力的意志以及朝向享樂的意志,正如在阿德勒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中所呈現的那樣。準確地說,「權力意志」一詞的鑄造者是尼采而不是阿德勒,至於「享樂意志」一詞,代表了佛洛伊德的「享樂原則」,則是我自己的說法,而非佛洛伊德本人。更且,享樂原則應該以更寬廣的平衡原則(homeostasis principle)概念來看待才對。在批評以上兩概念之同時,我們也應該更仔細詳論意義治療法的動機理論。(3)生命的意義是討論有關相對論(relativism)與主觀論(subjectivism)之間對立的問題。
在本書中討論意義治療法的應用時,也包含了三個問題面向。首先,意義治療法可運用於處理智因的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2]其次,意義治療法也運用於處理一般意義下的精神官能症;第三,意義治療法還用來處理身體因素的(somatogenic)精神官能症,或更廣泛的身心症 (somatogenic disease)。[3]我們就會看見,屬於人類的所有面向,都會反映在這套主題的關聯網之中。
在本書的〈緒論〉一章中,意義治療法會和其他治療 法學派的觀點並列,特別是與心理治療領域中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到了本書的末章所處理的,乃是意義治療法與神學的對話。
我在本書中曾儘量嘗試把意義治療法的最新發展包含進來,以便能在個體的原則上以及具體的服務上都能有詳細的材料以資說明。不過,就是這份提供整個體系全貌的意圖,使我不得不將一些在先前出版的書中已經出現過的材料囊括進來。
我所謂的「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之說,對於當前的精神醫學構成了一場挑戰。愈來愈多患者的訴苦是感覺到空虛與無意義,然而在我看來,是衍生自兩項事實。人不像動物那樣,要聽從本能說你一定要做什麼。還有,現在的人跟從前的人不一樣,不再聽從傳統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人甚至常常不知道他基本上想做什麼。反過來說,他要嘛想做別人都在做的事(從眾主義﹝conformism﹞);不然他就只能 做別人要他做的事(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我希望我能夠成功地向讀者傳達我的信念:不管傳統怎麼崩塌,生命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更有甚者,這意義實際上會維持到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而精神科醫師也有辦法向他的患者展示:生命從未停止「有意義」這回事。更明確地說,醫師無法向患者展現意義是什麼,但他很可以展示的就是有意義,而生命就是在頂著、扛著,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生命都是充滿意義的。意義治療法得來的教訓是說:甚至在生命最悲劇、最負面的面向,譬如無法避免的苦難,都可能藉由人在面對困境時所承受的態度,而將之轉變為人類的成就。意義治療法和其他的存在主義學派相對而言,就是絕對不悲觀,對它而言,最現實的乃是能夠面對人類存在處境中環環相扣的三種悲劇:痛苦、死亡與罪疚。把意義治療法叫做樂觀,堪稱公允,因為它能夠向患者展現的,正是如何把絕望轉變為勝利。
在像我們這樣的時代裡,傳統正在式微,因此精神醫學 必須視為首要任務者,就在於幫人裝備好發現意義的能力。在這個年代中,十誡對許多人而言已喪失其無條件的效度,人竟得在他一生的千萬種處境中,學會聽出隱含其中的千萬 條誡律。在這情況下,我希望讀者可聽出,意義治療法是在面對著時時刻刻的需求。
本書是由一系列受邀演講稿彙輯而成。邀請者是德州達拉斯的南美以美大學(South Methodist University)的普金斯學院(Perkins School),時在1966年的暑修班。我被指定的講題是解釋意義治療法特有的體系。雖然有不少作者指出:相對於其他學派的存在主義精神醫療法而言,意義治療法已發展出某種確定的心理治療技法,但知道的人不多。那是迄今為止唯一在概念上能自成體系的治療法。
為了處理此一體系的基礎,本書各章就要來談談意義治療法背後的基本假定以及一些主張。各章之間形成了一個關聯網,要之,意義治療法有以下三個基本概念:(1)意志的自由;(2)朝向意義的意志;(3)生命的意義。
(1)意志的自由包含了決定論(determinism)與泛決定論(pan-determinism)相對的問題。(2)意義的意志所討論的概念乃是有別於朝向權力的意志以及朝向享樂的意志,正如在阿德勒和佛洛伊德的心理學中所呈現的那樣。準確地說,「權力意志」一詞的鑄造者是尼采而不是阿德勒,至於「享樂意志」一詞,代表了佛洛伊德的「享樂原則」,則是我自己的說法,而非佛洛伊德本人。更且,享樂原則應該以更寬廣的平衡原則(homeostasis principle)概念來看待才對。在批評以上兩概念之同時,我們也應該更仔細詳論意義治療法的動機理論。(3)生命的意義是討論有關相對論(relativism)與主觀論(subjectivism)之間對立的問題。
在本書中討論意義治療法的應用時,也包含了三個問題面向。首先,意義治療法可運用於處理智因的精神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2]其次,意義治療法也運用於處理一般意義下的精神官能症;第三,意義治療法還用來處理身體因素的(somatogenic)精神官能症,或更廣泛的身心症 (somatogenic disease)。[3]我們就會看見,屬於人類的所有面向,都會反映在這套主題的關聯網之中。
在本書的〈緒論〉一章中,意義治療法會和其他治療 法學派的觀點並列,特別是與心理治療領域中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到了本書的末章所處理的,乃是意義治療法與神學的對話。
我在本書中曾儘量嘗試把意義治療法的最新發展包含進來,以便能在個體的原則上以及具體的服務上都能有詳細的材料以資說明。不過,就是這份提供整個體系全貌的意圖,使我不得不將一些在先前出版的書中已經出現過的材料囊括進來。
我所謂的「存在空虛」(existential vacuum)之說,對於當前的精神醫學構成了一場挑戰。愈來愈多患者的訴苦是感覺到空虛與無意義,然而在我看來,是衍生自兩項事實。人不像動物那樣,要聽從本能說你一定要做什麼。還有,現在的人跟從前的人不一樣,不再聽從傳統告訴你應該做什麼。人甚至常常不知道他基本上想做什麼。反過來說,他要嘛想做別人都在做的事(從眾主義﹝conformism﹞);不然他就只能 做別人要他做的事(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我希望我能夠成功地向讀者傳達我的信念:不管傳統怎麼崩塌,生命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更有甚者,這意義實際上會維持到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而精神科醫師也有辦法向他的患者展示:生命從未停止「有意義」這回事。更明確地說,醫師無法向患者展現意義是什麼,但他很可以展示的就是有意義,而生命就是在頂著、扛著,無論在什麼條件下,生命都是充滿意義的。意義治療法得來的教訓是說:甚至在生命最悲劇、最負面的面向,譬如無法避免的苦難,都可能藉由人在面對困境時所承受的態度,而將之轉變為人類的成就。意義治療法和其他的存在主義學派相對而言,就是絕對不悲觀,對它而言,最現實的乃是能夠面對人類存在處境中環環相扣的三種悲劇:痛苦、死亡與罪疚。把意義治療法叫做樂觀,堪稱公允,因為它能夠向患者展現的,正是如何把絕望轉變為勝利。
在像我們這樣的時代裡,傳統正在式微,因此精神醫學 必須視為首要任務者,就在於幫人裝備好發現意義的能力。在這個年代中,十誡對許多人而言已喪失其無條件的效度,人竟得在他一生的千萬種處境中,學會聽出隱含其中的千萬 條誡律。在這情況下,我希望讀者可聽出,意義治療法是在面對著時時刻刻的需求。
目次
序
緒論:心理治療的處境以及意義治療法的地位
Part 1 意義治療法的基礎
chapter 1 心理治療的臨床後設含意
chapter 2 自我超越之為人的現象
chapter 3 意義是什麼意思?
Part 2 意義治療法的應用
chapter 4 存在的空虛:對精神醫學的挑戰
chapter 5 意義治療的技法
chapter 6 醫療事工
chapter 7 結論:意義的面向
後話:意義治療法的去大師化作用
譯者筆記 幾則
緒論:心理治療的處境以及意義治療法的地位
Part 1 意義治療法的基礎
chapter 1 心理治療的臨床後設含意
chapter 2 自我超越之為人的現象
chapter 3 意義是什麼意思?
Part 2 意義治療法的應用
chapter 4 存在的空虛:對精神醫學的挑戰
chapter 5 意義治療的技法
chapter 6 醫療事工
chapter 7 結論:意義的面向
後話:意義治療法的去大師化作用
譯者筆記 幾則
書摘/試閱
心理治療的臨床後設含意(節錄)
心理治療有些臨床後設的含意(metaclinical implications),其主要的指涉就是關於人的概念,以及生命哲學。心理治療法當中沒有一種理論不含有人以及生命哲學。不論自覺或不自覺,心理治療都奠基於斯。就此而言,精神分析也不例外。席爾德(Paul Schilder)把精神分析稱為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而就在不久之前,普魯恩(F. Gordon Pleune)才說:「精神分析師首先最重要的,是個道德家(moralist)。」並且「會以其道德及倫理行為來影響別人。」
於是,問題絕不可能在於心理治療是否奠基於世界觀,而更應該說,在其中的世界觀究竟是對是錯。對錯是非,在此脈絡下,無論如何乃意指在此給定的哲學理論中,人類的人性是否得以保留。譬如,人類的人性品質,在那些依附著「機械模型」或「白老鼠模型」(正如奧波特所稱)的心理學家當中,是根本不管或全然忽視的。對於前者,我將其視為値得注意的事實,就是,人既然把他自己視為一種受造物,就會把自己的存在用神的意象(即造物者)來詮釋;然而一旦他開始把自己當造物者,他就會僅以他自己受造的意象來詮釋他的存在,也就只能是個機器了。
意義治療法對於人的概念乃奠基於三大支柱:意志的自由、(向於)意義的意志,以及生命的意義。其中的第一項,即意志的自由,乃是對立於當前大多數關於人的論述所採用的取向,講明白點,也就是決定論。不過,說眞的,那只是和我經常說的「泛決定論」對立而已,因為談到意志的自由時,絕對不意謂任何先決的「不可決定論」(indeterminism)。畢竟,意志的自由就是指人類意志的自由,而人類的意志就是屬於有限存在的意志。人的自由並非無條件的自由,而毋寧是當面臨任何條件時,都可以採取立場的自由。
在一次訪談過程中,哈佛的休士頓.史密斯(後來去了MIT)問我:身為一位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難道不承認人會受制於某些條件和決定性的因素嗎?我回答說,身為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我當然非常瞭解人在某種程度下不會完全不受條件所囿,無論那是生物學的、心理學的或社會學的條件。但我補充說,除了是兩個領域(即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之外,我還是四個營(就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正因如此,我也親身見證了人在多少意料不到的程度上,總是留有可以抵抗或甚至敢於抵抗最糟條件的能力。可將自己從最糟的條件中抽離,乃是人所特有的本事。不過,人這種能自任何身處的必然之境抽離出來的特殊本事,就像我們在集中營裡所見,並不是只能以英雄作風來體現,而還能透過幽默。幽默也是人所特有的一種能力。我們不必為此感到羞恥。幽默甚至可說是一種神聖的屬性。《詩篇》中有三首提到神是在「笑著」的。
幽默和英雄作風讓我們談及了人所特有的「自我抽離」(self-detachment)能力。透過這種能力,人才能夠抽離於處境之外,乃至抽離於自身之外。他能選擇對於自己的態度。以此,他眞的能夠對他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條件及決定因素採取立場。可以理解,這就是心理治療與精神醫學,也是教育與宗教的要點所在。因為,用這種眼光來看的話,一個人可以自由地為自己的性格賦形,而人就對於他所造的自己負有責任。該在乎的不是性格的特質,或驅力、本能如何的問題,而毋寧是我們對此所採的立場何在。能夠採取這種立場才使我們稱得上是人。
對於身體的、心靈的現象採取立場,表示能超越這些現象的層次,並開啟了新的向度,亦即智性的現象或靈智學的向度――用以與生物學的和心理學的向度形成對比。人的獨特現象正是座落在此向度上。
也可將此定義為精神向度。然而,正因「精神的」一詞在英語中總是跟宗教脫不了干係,我們就必須儘可能避免使用此詞。我們所知的靈智向度應是屬於人類學而非神學的向度。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意義治療法」中的「意義」(邏各斯)一詞上。除了「意義」的意思外,「邏各斯」在此也指「精神」――但是,再說一次,其中不帶有任何基本上屬於宗教的內涵。在此的「邏各斯」所指的就是人類的人性――再加上作為人的意義!
人,每當他在返身自省時,就會穿越靈智學的向度――或說,如果需要的話,在他返身自斥的時候,也會如此;每當他把自己變成一個物體(object)――或是在反對(objection)自己時;每當他表現出意識到自己時――或每當他展示出這樣的內省時。事實上,人的內省性預設了人獨有的能力,可以超越自己,用道德與倫理的條件來判斷和評估自己的行為。
當然,人可以剝奪這種屬人獨有的現象,譬如人性中的良心。他可以只用制約反應的結果來設想良心。但實際上,這樣的詮釋只在某種狀況下才會顯得充分與合適,譬如一隻狗,當牠把地毯尿濕,然後鬼鬼祟祟地鑽進沙發底下,還把尾巴夾在腿間。這隻狗實際上表現了良心嗎?我倒寧可想,牠所表現的是對於懲罰的可怕期待――這也許正是由於制約過程使然。
把良心化約為僅僅是制約過程的結果,乃是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一則顯例。我要把化約主義界定為一種偽科學的取向,其作風就是全然不顧現象中的人性,透過把這當作僅僅是副作用,更明確地說,就是化約成次於人的副現象。事實上,你就可以把化約主義界定為次人主義(sub-humanism)。要舉例的話,我拿出兩個也許最為人性的現象來說,那就是愛與良心。此兩者顯現出另一個最為驚人的人性本事,亦即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本事。人之所以超越自身,乃是用來朝向另一個人,或朝向意義。我會說,愛就是那種本事,讓他能夠眞正抓住另一個人的獨特性。良心則是另一種本事,讓他產生力量來捕捉某種情勢中眞正獨特的意義,而最終的分析就會發現,意義都有獨特性。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皆然。每一個人最終都是無可取代的,如果對於其他人不是如此,對於愛著他的人也必然如此。
正因為愛與良心的有意指涉具有獨特性,兩者都屬直覺的能力。不過,在兩者有意的指涉皆具有獨特性的這個公分母之外,它們之間仍有差異。愛所面對的獨特性是指向所愛者所具有的獨特可能性。反過來說,良心所面對的獨特性是指獨特的必然性,指向人必須碰到的獨特需求。
然而,化約主義傾向於把愛詮釋為只不過是色事的昇華,良心則只不過是根據超自我而來。我的主張是:愛實際上不可能只是色事的昇華,因為每當昇華發生時,愛始終是其預設條件。我敢說,只有當一個我能夠將愛導向一個你之程度時――只有在此刻,才能說自我也有能力整合伊底,亦即將色事整合於人格之中。
而良心不能只是超自我――其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良心在必要時可擔起責任來反對那些經由超自我而傳遞的習俗、標準、傳統與價値。因此,良心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會產生與超自我互相矛盾的功能,所以它當然不可能等同於超自我。把良心化約為超自我,以及由伊底演繹出愛,這兩者都注定是失敗的概念。
我們來問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化約主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推敲科學專業分工的效應。我們生活的時代充滿了專家,也因此付出了代價。我想把「專家」定義為見樹不見林的人:只看見一棵棵事實的樹,看不見眞理的林。舉個例來說,在思覺失調症的領域中,我們會看見生物化學所提供的排山倒海資訊。我們也會面臨多如牛毛的動力心理學假設文獻。然後還有一些文獻所關懷的是思覺失調的獨特存有模式。總之,我的看法是:任何人說他對思覺失調症擁有眞知,那麼他一定是在欺騙你,或至少是在騙自己。
個別的科學在描述眞實之時,呈現出如此乖離的圖像,如此相互差異,以致愈來愈難以達成不同圖像的融合。但不同的圖像不必然會造成缺失,反而可能在知識上有所得。用雙筒望遠鏡的觀點來看,左圖和右圖之間的差異恰恰能獲得整體的向度,也就是說,得到三維的空間,而不只是二維的平面。誠然,要能如此,有其必要的先決條件:視網膜必須能夠達成不同圖像的融合!
在視覺上能夠成立的,在認知上亦然。眞正的挑戰來自面對各門各類科學提供的諸多零星分散資料、事實及發現時,如何獲取、如何維持,以及如何儲存而能成為一個統合的人的概念。
但我們不能夠倒轉歷史的巨輪。社會沒有專家是行不通的。有太多研究是由團隊合作來完成的,而在團隊的架構中,專家無可避免。
但其中的危險眞是來自普世性的缺乏嗎?潛藏於其中、假裝的整體性,難道不是更危險嗎?所謂的危險乃是一個身為專家的人,譬如生物學領域的專家,在瞭解與解釋人時,就單單以生物學為之。同樣的情況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中亦然。就在他們宣稱達到整體性時,生物學變成生物學主義(biologism),心理學變成心理學主義(psychologism),社會學變成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換言之,也就是當科學變成意識形態之時。我想說,我們所當責難的,並非科學家的專家化,而是專家的一般化。我們應該都熟知哪一類人叫做可怕的簡化者(terrible simplificateurs)。而現在變成我們要熟知的類型,我叫它稱為可怕的普化者(terrible généralisateurs)。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無法抗拒誘惑,而必須在有限發現的基礎上一直作出過度概括宣稱的人。
我曾經碰到一句引述的話,把人界定為:「只不過是一組複雜的生物化學機制,由一個氧化系統提供動力,激發其中的各個計算機模組,以助其中貯存的大量編碼資料得以維持下來。」現在,身為一個神經學家,我贊成使用計算機模型的合理性,譬如,用來說明中樞神經系統的運作。使用這種類比法有其完全的正當性。因此,上述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效的:人是一部電腦。不過,在此同時,他仍然無限多過於電腦。那段引述錯就錯在說人「只不過」是一部電腦。
今天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談「虛無」(nothingness)時已經不再拿掉面具。今天的虛無主義是戴著面具在談人的「只不過論」。化約主義已經變成虛無主義的面具。
我們該如何來面對這檔事情?在化約主義的眼前,如何才有可能保住人的人性?分析到最終,面對著科學的多元性時,如何才有可能保住人的統一性―而這科學的多元性正是培育化約主義的溫床?
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與謝勒兩位也許比所有人都更致力於解決我們所面對的難題。哈特曼的存有論(ontology)與謝勒的哲學人類學(anthropology)都企圖讓各自的科學領域能分配到少許的效度。哈特曼區分出若干個層次,譬如身體的、心理的,再加上精神的頂峰。在此,我們再說一次,所謂「精神的」並不帶有宗教的含意,毋寧說是屬於靈智向度。哈特曼把人類存在的層次看成一個階序結構。相對於此,謝勒的哲學人類學使用了梯階的圖像而不用層次的概念,以此把人的核心設在精神軸,而把生物與心理階層放在邊緣。
哈特曼與謝勒兩位當然都有功於在存有論上作出這樣的區分:身體、心理和精神,其考量著重於質性而不只是量化的差異。不過,他們還是沒對相互間的存有論差異作出足夠的說明,也就是說,他們忽略了在另一方面還有我所謂的人類存在的整體性。或者,用阿奎納斯(Thomas Aquinas)的說法,人乃是一種「多元統合體」(unitas multiplex)。他把藝術界定為紛紜之中的統一體。因此我就把人的存在界定為縱然紛雜仍能維持的統一體!
把人設想為有身體、心理與精神的層次,就意謂能夠把人處理為身、心、靈各自分離的模組。我自己的嘗試是同時以向度人類學及存有論(dimensional anthropology and ontology)來處理存有論差異以及人類學統合的問題。這樣的取向是使用幾何學的向度概念作為質性差異的類比,而不致抹殺結構上的統一性。
我所強調的向度存有論乃是奠基於兩條法則。向度存有論的第一法則是說:一且同一的現象,由其本身投射出低於本身的諸多向度,如此一來,個體乃呈現出相互矛盾的景象。
試想想一個圓柱形的東西,譬如,一個杯子。把它的三維形體投影到只有水平垂直的二維平面,它會產生的兩個圖像,一是圓形,一是長方形。這兩個圖形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杯子是開放的容器,而相對的圓形和長方形則都是封閉的圖形。又一個矛盾!
現在,讓我們進入向度存有論的第二法則,就是說:多個不同的現象自它本身的向度中投射出較其本身低一階的向度,會顯現出曖昧的圖形。
試想像一個圓柱、一個圓錐、一顆圓球。它們在平面上的投影就是三個一模一樣的圓形。我們從投影無法推論出它們的原形。無法得知投影的來源是圓柱,是圓錐,還是圓球。
根據向度存有論的第一法則,一個現象向低階向度的投影會出現不一致的圖形,而根據第二法則,不同現象的低階向度投影則會出現同形的結果。
現在,我們要怎樣將此圖像結果運用到人類學和存有學上呢?只要把人用生物學和心理學向度來投影,我們也會得出相互矛盾的結果。因為,在一方面得出的結果就是生物學有機體,另一方面則得出了心理學機制。不過,人類的存在無論在身體面向和心理面向上是多麼矛盾互斥,但在向度人類學看來,這些向度間的矛盾對於一個整體的人來說,就毫無矛盾可言。要不然的話,難道圓形和長方形都來自同一個圓柱形的投影,這樣也算矛盾嗎?
向度存有論仍然遠遠無法解決心物二元論的問題。但它確實準準解釋了何以心物二元論的問題難以解決。在論到一個人的整體有其必然性時――不論是否有身心之別仍然都具有的整體性――這必然性卻不在生物學或心理學中,而是得在靈智學向度中尋得―正是在此,人才得以首度現出其完整的投影。
不過,跟身心二元對立問題沿著走的,還有決定論的問題,亦即自由抉擇的問題。但這問題也一樣可以沿著向度人類學的取向來解決。一個杯子的開放性在水平和垂直的二維投影中必然消失。所以嘛,人也一樣,如果在低於其本身一階的投影中出現,看起來也會成為一個封閉系統,不論這是生理學的反射系統,或是心理學的反應,還是刺激反應系統。有些動機理論,譬如至今仍依附著體內平衡的那類概念,就是把人視為封閉系統來處理。然而這種看法,就是忽視不顧人類存在必不可少的開放性,而這是謝勒、波特曼(Adolf Portmann)、蓋倫(Arnold Gehlen)等人都提出過確鑿證據的。尤其是生物學家波特曼,以及社會學家蓋倫,都曾揭示過人如何對世界開放。而我則要說,由於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要成為一個人就總是意指或導向自己之外的某人,或某事物。
所有這些,在生物學向度和心理學向度中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在向度人類學的檢視下,至少我們可瞭解這為何一定會發生。現在也看出在生物學和心理學向度中明顯的封閉性已經不再和人的人性互相矛盾了。在低階向度中的封閉性和高階向度中的開放性是完全可以相容的,不論這是在說圓柱形的杯子,還是在說人。
現在也顯得很可以理解的是,為何在低階向度中完整的研究發現(不論它是如何忽視人性),卻不必與人性發生矛盾。這說法在以下幾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中也可以說得通:華生式的行為主義,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射學,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阿德勒式的心理學。意義治療法都不會將其予以否定,而是會把它們統統收納在一個高階向度的傘蓋下――或者,如挪威心理治療師柯維浩格(Bjarne Kvilhaug)那樣,他特別指到學習理論以及行為治療法,把這些學派的發現用意義治療法的觀點予以重新詮釋與評估――這也就把它們重新人性化了。
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們所說的高階向度用來與低階向度對立,這並不意謂價値判斷。所謂「高階」向度只是說它具有較廣、較周延的包含性。這在哲學人類學裡是個很要緊的課題。其中意謂著承認人類在成為人之前,並未停止其中仍保留的獸性,好比飛機在起飛之前還得能夠在地面上運行。
心理治療有些臨床後設的含意(metaclinical implications),其主要的指涉就是關於人的概念,以及生命哲學。心理治療法當中沒有一種理論不含有人以及生命哲學。不論自覺或不自覺,心理治療都奠基於斯。就此而言,精神分析也不例外。席爾德(Paul Schilder)把精神分析稱為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而就在不久之前,普魯恩(F. Gordon Pleune)才說:「精神分析師首先最重要的,是個道德家(moralist)。」並且「會以其道德及倫理行為來影響別人。」
於是,問題絕不可能在於心理治療是否奠基於世界觀,而更應該說,在其中的世界觀究竟是對是錯。對錯是非,在此脈絡下,無論如何乃意指在此給定的哲學理論中,人類的人性是否得以保留。譬如,人類的人性品質,在那些依附著「機械模型」或「白老鼠模型」(正如奧波特所稱)的心理學家當中,是根本不管或全然忽視的。對於前者,我將其視為値得注意的事實,就是,人既然把他自己視為一種受造物,就會把自己的存在用神的意象(即造物者)來詮釋;然而一旦他開始把自己當造物者,他就會僅以他自己受造的意象來詮釋他的存在,也就只能是個機器了。
意義治療法對於人的概念乃奠基於三大支柱:意志的自由、(向於)意義的意志,以及生命的意義。其中的第一項,即意志的自由,乃是對立於當前大多數關於人的論述所採用的取向,講明白點,也就是決定論。不過,說眞的,那只是和我經常說的「泛決定論」對立而已,因為談到意志的自由時,絕對不意謂任何先決的「不可決定論」(indeterminism)。畢竟,意志的自由就是指人類意志的自由,而人類的意志就是屬於有限存在的意志。人的自由並非無條件的自由,而毋寧是當面臨任何條件時,都可以採取立場的自由。
在一次訪談過程中,哈佛的休士頓.史密斯(後來去了MIT)問我:身為一位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難道不承認人會受制於某些條件和決定性的因素嗎?我回答說,身為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我當然非常瞭解人在某種程度下不會完全不受條件所囿,無論那是生物學的、心理學的或社會學的條件。但我補充說,除了是兩個領域(即神經學與精神醫學)的教授之外,我還是四個營(就是集中營)的倖存者。正因如此,我也親身見證了人在多少意料不到的程度上,總是留有可以抵抗或甚至敢於抵抗最糟條件的能力。可將自己從最糟的條件中抽離,乃是人所特有的本事。不過,人這種能自任何身處的必然之境抽離出來的特殊本事,就像我們在集中營裡所見,並不是只能以英雄作風來體現,而還能透過幽默。幽默也是人所特有的一種能力。我們不必為此感到羞恥。幽默甚至可說是一種神聖的屬性。《詩篇》中有三首提到神是在「笑著」的。
幽默和英雄作風讓我們談及了人所特有的「自我抽離」(self-detachment)能力。透過這種能力,人才能夠抽離於處境之外,乃至抽離於自身之外。他能選擇對於自己的態度。以此,他眞的能夠對他自己的生理和心理條件及決定因素採取立場。可以理解,這就是心理治療與精神醫學,也是教育與宗教的要點所在。因為,用這種眼光來看的話,一個人可以自由地為自己的性格賦形,而人就對於他所造的自己負有責任。該在乎的不是性格的特質,或驅力、本能如何的問題,而毋寧是我們對此所採的立場何在。能夠採取這種立場才使我們稱得上是人。
對於身體的、心靈的現象採取立場,表示能超越這些現象的層次,並開啟了新的向度,亦即智性的現象或靈智學的向度――用以與生物學的和心理學的向度形成對比。人的獨特現象正是座落在此向度上。
也可將此定義為精神向度。然而,正因「精神的」一詞在英語中總是跟宗教脫不了干係,我們就必須儘可能避免使用此詞。我們所知的靈智向度應是屬於人類學而非神學的向度。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意義治療法」中的「意義」(邏各斯)一詞上。除了「意義」的意思外,「邏各斯」在此也指「精神」――但是,再說一次,其中不帶有任何基本上屬於宗教的內涵。在此的「邏各斯」所指的就是人類的人性――再加上作為人的意義!
人,每當他在返身自省時,就會穿越靈智學的向度――或說,如果需要的話,在他返身自斥的時候,也會如此;每當他把自己變成一個物體(object)――或是在反對(objection)自己時;每當他表現出意識到自己時――或每當他展示出這樣的內省時。事實上,人的內省性預設了人獨有的能力,可以超越自己,用道德與倫理的條件來判斷和評估自己的行為。
當然,人可以剝奪這種屬人獨有的現象,譬如人性中的良心。他可以只用制約反應的結果來設想良心。但實際上,這樣的詮釋只在某種狀況下才會顯得充分與合適,譬如一隻狗,當牠把地毯尿濕,然後鬼鬼祟祟地鑽進沙發底下,還把尾巴夾在腿間。這隻狗實際上表現了良心嗎?我倒寧可想,牠所表現的是對於懲罰的可怕期待――這也許正是由於制約過程使然。
把良心化約為僅僅是制約過程的結果,乃是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一則顯例。我要把化約主義界定為一種偽科學的取向,其作風就是全然不顧現象中的人性,透過把這當作僅僅是副作用,更明確地說,就是化約成次於人的副現象。事實上,你就可以把化約主義界定為次人主義(sub-humanism)。要舉例的話,我拿出兩個也許最為人性的現象來說,那就是愛與良心。此兩者顯現出另一個最為驚人的人性本事,亦即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的本事。人之所以超越自身,乃是用來朝向另一個人,或朝向意義。我會說,愛就是那種本事,讓他能夠眞正抓住另一個人的獨特性。良心則是另一種本事,讓他產生力量來捕捉某種情勢中眞正獨特的意義,而最終的分析就會發現,意義都有獨特性。每一個人和所有的人皆然。每一個人最終都是無可取代的,如果對於其他人不是如此,對於愛著他的人也必然如此。
正因為愛與良心的有意指涉具有獨特性,兩者都屬直覺的能力。不過,在兩者有意的指涉皆具有獨特性的這個公分母之外,它們之間仍有差異。愛所面對的獨特性是指向所愛者所具有的獨特可能性。反過來說,良心所面對的獨特性是指獨特的必然性,指向人必須碰到的獨特需求。
然而,化約主義傾向於把愛詮釋為只不過是色事的昇華,良心則只不過是根據超自我而來。我的主張是:愛實際上不可能只是色事的昇華,因為每當昇華發生時,愛始終是其預設條件。我敢說,只有當一個我能夠將愛導向一個你之程度時――只有在此刻,才能說自我也有能力整合伊底,亦即將色事整合於人格之中。
而良心不能只是超自我――其最簡單的理由就是:良心在必要時可擔起責任來反對那些經由超自我而傳遞的習俗、標準、傳統與價値。因此,良心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會產生與超自我互相矛盾的功能,所以它當然不可能等同於超自我。把良心化約為超自我,以及由伊底演繹出愛,這兩者都注定是失敗的概念。
我們來問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化約主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推敲科學專業分工的效應。我們生活的時代充滿了專家,也因此付出了代價。我想把「專家」定義為見樹不見林的人:只看見一棵棵事實的樹,看不見眞理的林。舉個例來說,在思覺失調症的領域中,我們會看見生物化學所提供的排山倒海資訊。我們也會面臨多如牛毛的動力心理學假設文獻。然後還有一些文獻所關懷的是思覺失調的獨特存有模式。總之,我的看法是:任何人說他對思覺失調症擁有眞知,那麼他一定是在欺騙你,或至少是在騙自己。
個別的科學在描述眞實之時,呈現出如此乖離的圖像,如此相互差異,以致愈來愈難以達成不同圖像的融合。但不同的圖像不必然會造成缺失,反而可能在知識上有所得。用雙筒望遠鏡的觀點來看,左圖和右圖之間的差異恰恰能獲得整體的向度,也就是說,得到三維的空間,而不只是二維的平面。誠然,要能如此,有其必要的先決條件:視網膜必須能夠達成不同圖像的融合!
在視覺上能夠成立的,在認知上亦然。眞正的挑戰來自面對各門各類科學提供的諸多零星分散資料、事實及發現時,如何獲取、如何維持,以及如何儲存而能成為一個統合的人的概念。
但我們不能夠倒轉歷史的巨輪。社會沒有專家是行不通的。有太多研究是由團隊合作來完成的,而在團隊的架構中,專家無可避免。
但其中的危險眞是來自普世性的缺乏嗎?潛藏於其中、假裝的整體性,難道不是更危險嗎?所謂的危險乃是一個身為專家的人,譬如生物學領域的專家,在瞭解與解釋人時,就單單以生物學為之。同樣的情況在心理學和社會學中亦然。就在他們宣稱達到整體性時,生物學變成生物學主義(biologism),心理學變成心理學主義(psychologism),社會學變成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換言之,也就是當科學變成意識形態之時。我想說,我們所當責難的,並非科學家的專家化,而是專家的一般化。我們應該都熟知哪一類人叫做可怕的簡化者(terrible simplificateurs)。而現在變成我們要熟知的類型,我叫它稱為可怕的普化者(terrible généralisateurs)。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無法抗拒誘惑,而必須在有限發現的基礎上一直作出過度概括宣稱的人。
我曾經碰到一句引述的話,把人界定為:「只不過是一組複雜的生物化學機制,由一個氧化系統提供動力,激發其中的各個計算機模組,以助其中貯存的大量編碼資料得以維持下來。」現在,身為一個神經學家,我贊成使用計算機模型的合理性,譬如,用來說明中樞神經系統的運作。使用這種類比法有其完全的正當性。因此,上述的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有效的:人是一部電腦。不過,在此同時,他仍然無限多過於電腦。那段引述錯就錯在說人「只不過」是一部電腦。
今天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談「虛無」(nothingness)時已經不再拿掉面具。今天的虛無主義是戴著面具在談人的「只不過論」。化約主義已經變成虛無主義的面具。
我們該如何來面對這檔事情?在化約主義的眼前,如何才有可能保住人的人性?分析到最終,面對著科學的多元性時,如何才有可能保住人的統一性―而這科學的多元性正是培育化約主義的溫床?
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與謝勒兩位也許比所有人都更致力於解決我們所面對的難題。哈特曼的存有論(ontology)與謝勒的哲學人類學(anthropology)都企圖讓各自的科學領域能分配到少許的效度。哈特曼區分出若干個層次,譬如身體的、心理的,再加上精神的頂峰。在此,我們再說一次,所謂「精神的」並不帶有宗教的含意,毋寧說是屬於靈智向度。哈特曼把人類存在的層次看成一個階序結構。相對於此,謝勒的哲學人類學使用了梯階的圖像而不用層次的概念,以此把人的核心設在精神軸,而把生物與心理階層放在邊緣。
哈特曼與謝勒兩位當然都有功於在存有論上作出這樣的區分:身體、心理和精神,其考量著重於質性而不只是量化的差異。不過,他們還是沒對相互間的存有論差異作出足夠的說明,也就是說,他們忽略了在另一方面還有我所謂的人類存在的整體性。或者,用阿奎納斯(Thomas Aquinas)的說法,人乃是一種「多元統合體」(unitas multiplex)。他把藝術界定為紛紜之中的統一體。因此我就把人的存在界定為縱然紛雜仍能維持的統一體!
把人設想為有身體、心理與精神的層次,就意謂能夠把人處理為身、心、靈各自分離的模組。我自己的嘗試是同時以向度人類學及存有論(dimensional anthropology and ontology)來處理存有論差異以及人類學統合的問題。這樣的取向是使用幾何學的向度概念作為質性差異的類比,而不致抹殺結構上的統一性。
我所強調的向度存有論乃是奠基於兩條法則。向度存有論的第一法則是說:一且同一的現象,由其本身投射出低於本身的諸多向度,如此一來,個體乃呈現出相互矛盾的景象。
試想想一個圓柱形的東西,譬如,一個杯子。把它的三維形體投影到只有水平垂直的二維平面,它會產生的兩個圖像,一是圓形,一是長方形。這兩個圖形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杯子是開放的容器,而相對的圓形和長方形則都是封閉的圖形。又一個矛盾!
現在,讓我們進入向度存有論的第二法則,就是說:多個不同的現象自它本身的向度中投射出較其本身低一階的向度,會顯現出曖昧的圖形。
試想像一個圓柱、一個圓錐、一顆圓球。它們在平面上的投影就是三個一模一樣的圓形。我們從投影無法推論出它們的原形。無法得知投影的來源是圓柱,是圓錐,還是圓球。
根據向度存有論的第一法則,一個現象向低階向度的投影會出現不一致的圖形,而根據第二法則,不同現象的低階向度投影則會出現同形的結果。
現在,我們要怎樣將此圖像結果運用到人類學和存有學上呢?只要把人用生物學和心理學向度來投影,我們也會得出相互矛盾的結果。因為,在一方面得出的結果就是生物學有機體,另一方面則得出了心理學機制。不過,人類的存在無論在身體面向和心理面向上是多麼矛盾互斥,但在向度人類學看來,這些向度間的矛盾對於一個整體的人來說,就毫無矛盾可言。要不然的話,難道圓形和長方形都來自同一個圓柱形的投影,這樣也算矛盾嗎?
向度存有論仍然遠遠無法解決心物二元論的問題。但它確實準準解釋了何以心物二元論的問題難以解決。在論到一個人的整體有其必然性時――不論是否有身心之別仍然都具有的整體性――這必然性卻不在生物學或心理學中,而是得在靈智學向度中尋得―正是在此,人才得以首度現出其完整的投影。
不過,跟身心二元對立問題沿著走的,還有決定論的問題,亦即自由抉擇的問題。但這問題也一樣可以沿著向度人類學的取向來解決。一個杯子的開放性在水平和垂直的二維投影中必然消失。所以嘛,人也一樣,如果在低於其本身一階的投影中出現,看起來也會成為一個封閉系統,不論這是生理學的反射系統,或是心理學的反應,還是刺激反應系統。有些動機理論,譬如至今仍依附著體內平衡的那類概念,就是把人視為封閉系統來處理。然而這種看法,就是忽視不顧人類存在必不可少的開放性,而這是謝勒、波特曼(Adolf Portmann)、蓋倫(Arnold Gehlen)等人都提出過確鑿證據的。尤其是生物學家波特曼,以及社會學家蓋倫,都曾揭示過人如何對世界開放。而我則要說,由於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要成為一個人就總是意指或導向自己之外的某人,或某事物。
所有這些,在生物學向度和心理學向度中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在向度人類學的檢視下,至少我們可瞭解這為何一定會發生。現在也看出在生物學和心理學向度中明顯的封閉性已經不再和人的人性互相矛盾了。在低階向度中的封閉性和高階向度中的開放性是完全可以相容的,不論這是在說圓柱形的杯子,還是在說人。
現在也顯得很可以理解的是,為何在低階向度中完整的研究發現(不論它是如何忽視人性),卻不必與人性發生矛盾。這說法在以下幾種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中也可以說得通:華生式的行為主義,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射學,佛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阿德勒式的心理學。意義治療法都不會將其予以否定,而是會把它們統統收納在一個高階向度的傘蓋下――或者,如挪威心理治療師柯維浩格(Bjarne Kvilhaug)那樣,他特別指到學習理論以及行為治療法,把這些學派的發現用意義治療法的觀點予以重新詮釋與評估――這也就把它們重新人性化了。
說到這裡,有必要提出一個警告。我們所說的高階向度用來與低階向度對立,這並不意謂價値判斷。所謂「高階」向度只是說它具有較廣、較周延的包含性。這在哲學人類學裡是個很要緊的課題。其中意謂著承認人類在成為人之前,並未停止其中仍保留的獸性,好比飛機在起飛之前還得能夠在地面上運行。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