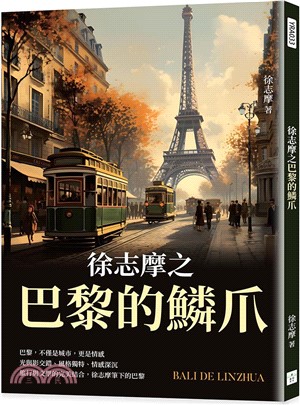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巴黎,不僅是城市,更是情感
光與影交錯、風格獨特、情感深沉
旅行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徐志摩筆下的巴黎
▎巴黎的情感與文化
〈巴黎的鱗爪〉是本書的首篇名篇,描述了徐志摩在法國首都巴黎的所見所聞。作為當代的現代詩人,徐志摩以他特有的感性筆觸,捕捉了這座城市的浪漫與歷史,同時也展現了他的世界觀和對西方文化的認知。
▎詩意的都市生活
進入書中,讀者將被帶到巴黎的各個角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韻律和情感。無論是塞納河畔,還是蒙馬特的小巷,每一個地方都流露出一種詩意的都市生活。徐志摩的筆觸細膩,他描述的巴黎不是那些經常出現在旅遊指南中的地方,而是那些只有真正懂得欣賞的人才能體會到的地方。
▎探索自我與世界
對徐志摩來說,旅行不僅僅是看到新的風景,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風景來探索自己和世界。他不僅分享了自己在巴黎的所見所聞,更多地是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他透過這座城市來思考人性、文化和藝術,使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旅遊筆記,更是一部哲學和文學的著作。
▎情感的流露與反思
在這本書中,徐志摩也分享了自己與巴黎之間的深厚情感。他描述了自己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以及與當地人的互動和交往。這些情感不僅僅是對巴黎的愛戀,更是對生活和世界的反思。透過這本書,讀者可以感受到一位詩人深入思考和感悟後的情感流露,並被其深深打動。
本書特色:本書是一部充滿詩意和哲學的作品,從自然到人文,再從情感到思考,涵蓋了多方面的主題和風格,每一篇都展現了徐志摩對於地方與自然的深厚情感。書中還涉及了多位歷史上的文學巨匠,如拜倫、羅曼羅蘭和濟慈,從中能看出他對外國詩歌的熱愛和欣賞。本書如一次充滿了情感的觀察與反思,更是一場深入的文學之旅。
光與影交錯、風格獨特、情感深沉
旅行與文學的完美結合,徐志摩筆下的巴黎
▎巴黎的情感與文化
〈巴黎的鱗爪〉是本書的首篇名篇,描述了徐志摩在法國首都巴黎的所見所聞。作為當代的現代詩人,徐志摩以他特有的感性筆觸,捕捉了這座城市的浪漫與歷史,同時也展現了他的世界觀和對西方文化的認知。
▎詩意的都市生活
進入書中,讀者將被帶到巴黎的各個角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韻律和情感。無論是塞納河畔,還是蒙馬特的小巷,每一個地方都流露出一種詩意的都市生活。徐志摩的筆觸細膩,他描述的巴黎不是那些經常出現在旅遊指南中的地方,而是那些只有真正懂得欣賞的人才能體會到的地方。
▎探索自我與世界
對徐志摩來說,旅行不僅僅是看到新的風景,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風景來探索自己和世界。他不僅分享了自己在巴黎的所見所聞,更多地是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他透過這座城市來思考人性、文化和藝術,使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旅遊筆記,更是一部哲學和文學的著作。
▎情感的流露與反思
在這本書中,徐志摩也分享了自己與巴黎之間的深厚情感。他描述了自己在巴黎的日常生活,以及與當地人的互動和交往。這些情感不僅僅是對巴黎的愛戀,更是對生活和世界的反思。透過這本書,讀者可以感受到一位詩人深入思考和感悟後的情感流露,並被其深深打動。
本書特色:本書是一部充滿詩意和哲學的作品,從自然到人文,再從情感到思考,涵蓋了多方面的主題和風格,每一篇都展現了徐志摩對於地方與自然的深厚情感。書中還涉及了多位歷史上的文學巨匠,如拜倫、羅曼羅蘭和濟慈,從中能看出他對外國詩歌的熱愛和欣賞。本書如一次充滿了情感的觀察與反思,更是一場深入的文學之旅。
作者簡介
徐志摩(西元1897~1931年),筆名南湖、雲中鶴,著名新月派現代詩人、散文家。曾赴英國留學,於倫敦劍橋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學,在校兩年深受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開始創作新詩。1923年與胡適、聞一多、梁實秋、陳源等人創建了新文學團體「新月社」。代表性作品有〈再別康橋〉、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等。
目次
巴黎的鱗爪
翡冷翠山居閒話
吸菸與文化
我所知道的康橋
拜倫
羅曼羅蘭
濟慈的夜鶯歌
天目山中筆記
鷂鷹與芙蓉雀
《生命的報酬》
翡冷翠山居閒話
吸菸與文化
我所知道的康橋
拜倫
羅曼羅蘭
濟慈的夜鶯歌
天目山中筆記
鷂鷹與芙蓉雀
《生命的報酬》
書摘/試閱
翡冷翠山居閒話
在這裡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著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絕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裡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淡香,連著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著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盡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顏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裡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裡走到朋友的家裡,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裡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鏈,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裡在沙堆裡在淺水裡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鏈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裡跳動,同在一個音波里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裡自得。
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牴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裡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著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為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裡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著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著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裡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不須應伴,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
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裡,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籟中,雲彩裡,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裡,花草的顏色與香息裡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裡我們讀得最深奧的訊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峰,雪西里與普陀山,來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己心靈上不長瘡瘢,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針。
十四年七月
天目山中筆記
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蓮花經譬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靜。廟宇在參天的大木中間藏著,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聲,竹有竹韻,鳴的禽,叫的是蟲子,閣上的大鐘,殿上的木魚,廟身的左邊右邊都安著接泉水的粗毛竹管,這就是天然的笙簫,時緩時急的參和著天空地上種種的鳴籟,靜是不靜的;但山中的聲響,不論是泥土裡的蚯蚓叫或是轎伕們深夜裡「唱寶」的異調,自有一種各別處:它來得純粹,來得清亮,來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裡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則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
夜間這些清籟搖著你入夢,清早上你也從這些清籟的懷抱中甦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樓住更是修得來的。我們的樓窗開處是一片蓊蔥的林海;林海外更有雲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接受自然的變幻;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散放你情感的變幻。自在;滿足。
今早夢迴時睜眼見滿帳的霞光。鳥雀們在讚美;我也加入一份。它們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潛深一度的沉默。
鐘樓中飛下一聲宏鐘,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盪。這一聲鐘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誇;說思流罷。耶教說阿門,印度教人說「歐姆」(Om),與這鐘聲的嗡嗡,同是從撮口外攝到闔口內包的一個無限的波動;分明是外擴,卻又是內潛;一切在它的周緣,卻又在它的中心:同時是皮又是核,是軸亦復是廓。「這偉大奧妙的」(om)使人感到動,又感到靜;從靜中見動,又從動中見靜。從安住到飛翔,又從飛翔回覆安住;從實在境界超入妙空,又從妙空化生實在:「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
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啟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象,擴大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
花開,花落,天外的流星與田畦間的飛螢,上綰雲天的青松,下臨絕海的巉巖,男女的愛,珠寶的光,火山的熔液:一嬰兒在它的搖籃中安眠。
這山上的鐘聲是晝夜不間歇的,他已經不間歇的打了十一年鐘,平均五分鐘時一次。打鐘的和尚獨自在鐘頭上住著,據說他的願心是打到他不能動彈的那天,鐘樓上供著菩薩,打鐘人在大鐘的一邊安著他的「座」,他每晚是坐著安神的,一隻手挽著鐘槌的一頭,從長期的習慣,不叫睡眠耽誤他的職司。
「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沒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竅蒙充六根,怎麼算總多了一個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師的談吐裡不少某督軍與某省長的點綴;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貪嗔的化身,無端摔破了兩個無辜的茶碗。但這打鐘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歲在五十開外,出家有二十幾年,這鐘樓,不錯,是他管的,這鐘是他打的(說著他就過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錯,是坐著安神的,但此外,可憐,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麼異樣。他拂拭著神龕,神坐,拜墊,換上香燭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乾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轉身去撞一聲鐘。他臉上看不出修行的清臒,卻沒有失眠的倦態,倒是滿滿的不時有笑容的展露;念什麼經;不就念阿彌陀佛,他竟許是不認識字的。「那一帶是什麼山,叫什麼,和尚?」「這裡是天目山,」
他說,「我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帶的,」我手點著問。「我不知道」。他回答。
山上另有一個和尚,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讀書臺的舊址,蓋有幾間屋,供著佛像,也歸廟管的,叫做茅棚,但這不比得普陀山上的真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著或是偎著修行的和尚沒一個不是鵠形鳩面,鬼似的東西。他們不開口的多,你愛布施什麼就放在他跟前的簍子或是盤子裡,他們怎麼也不睜眼,不出聲,隨你給的是金條或是鐵條。人說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沒有吃過東西,不曾挪過窩,可還是沒有死,就這冥冥的坐著。
他們大約難成佛不遠了,單看他們的臉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麼,一樣這黑刺刺,死僵僵的。「內中有幾個,」香客們說,「已經成了活佛,我們的祖母早三十年來就看見他們這樣坐著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裡的和尚,卻沒有那樣的浪漫出奇。茅棚是盡夠蔽風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鮮鮮的人,雖則他並不因此減卻他給我們的趣味。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裡來修行;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說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沉著的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著他內裡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跡;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著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裡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曾壓倒,不曾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裡豈不顫慄著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著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跌坐時意念的究竟?
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
但這也許看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絕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闌珊的收回了步伐向後退:寧可自殺。乾脆的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臘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面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上帝的愛,這知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念糊的在著;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跡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著佛教來的;印度可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盡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最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為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盡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道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十五年九月
在這裡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著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著看還不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絕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他是從繁花的山林裡吹度過來他帶來一股幽遠的淡香,連著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著你的顏面,輕繞著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閒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桀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盡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顏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那是最危險最專制不過的旅伴,你應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裡一條美麗的花蛇!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裡走到朋友的家裡,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裡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鏈,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裡在沙堆裡在淺水裡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鏈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才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裡跳動,同在一個音波里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裡自得。
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牴觸,他就捲了起來,但在澄靜的日光下,和風中,他的姿態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無阻礙的。
你一個人漫遊的時候,你就會在青草裡坐地仰臥,甚至有時打滾,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在靜僻的道上你就會不自主的狂舞,看著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種種詭異的變相,因為道旁樹木的陰影在他們紆徐的婆娑裡暗示你舞蹈的快樂;你也會得信口的歌唱,偶爾記起斷片的音調,與你自己隨口的小曲,因為樹林中的鶯燕告訴你春光是應得讚美的;更不必說你的胸襟自然會跟著曼長的山徑開拓,你的心地會看著澄藍的天空靜定,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山罅裡的泉響,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流,流,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
並且你不但不須應伴,每逢這樣的遊行,你也不必帶書。
書是理想的伴侶,但你應得帶書,是在火車上,在你住處的客室裡,不是在你獨身漫步的時候。什麼偉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優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風籟中,雲彩裡,山勢與地形的起伏裡,花草的顏色與香息裡尋得?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葛德說,在他每一頁的字句裡我們讀得最深奧的訊息。並且這書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爾帕斯與五老峰,雪西里與普陀山,來因河與揚子江;梨夢湖與西子湖,建蘭與瓊花,杭州西溪的蘆雪與威尼市夕照的紅潮,百靈與夜鶯,更不提一般黃的黃麥,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長,同在和風中波動──他們應用的符號是永遠一致的,他們的意義是永遠明顯的,只要你自己心靈上不長瘡瘢,眼不盲,耳不塞,這無形跡的最高等教育便永遠是你的名分,這不取費的最珍貴的補劑便永遠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認識了這一部書,你在這世界上寂寞時便不寂寞,窮困時不窮困,苦惱時有安慰,挫折時有鼓勵,軟弱時有督責,迷失時有南針。
十四年七月
天目山中筆記
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蓮花經譬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靜。廟宇在參天的大木中間藏著,早晚間有的是風,松有松聲,竹有竹韻,鳴的禽,叫的是蟲子,閣上的大鐘,殿上的木魚,廟身的左邊右邊都安著接泉水的粗毛竹管,這就是天然的笙簫,時緩時急的參和著天空地上種種的鳴籟,靜是不靜的;但山中的聲響,不論是泥土裡的蚯蚓叫或是轎伕們深夜裡「唱寶」的異調,自有一種各別處:它來得純粹,來得清亮,來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裡洗濯過後覺得清白些,這些山籟,雖則一樣是音響,也分明有洗淨的功能。
夜間這些清籟搖著你入夢,清早上你也從這些清籟的懷抱中甦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樓住更是修得來的。我們的樓窗開處是一片蓊蔥的林海;林海外更有雲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接受自然的變幻;從這三尺方的窗戶你散放你情感的變幻。自在;滿足。
今早夢迴時睜眼見滿帳的霞光。鳥雀們在讚美;我也加入一份。它們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潛深一度的沉默。
鐘樓中飛下一聲宏鐘,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盪。這一聲鐘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誇;說思流罷。耶教說阿門,印度教人說「歐姆」(Om),與這鐘聲的嗡嗡,同是從撮口外攝到闔口內包的一個無限的波動;分明是外擴,卻又是內潛;一切在它的周緣,卻又在它的中心:同時是皮又是核,是軸亦復是廓。「這偉大奧妙的」(om)使人感到動,又感到靜;從靜中見動,又從動中見靜。從安住到飛翔,又從飛翔回覆安住;從實在境界超入妙空,又從妙空化生實在:「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
多奇異的力量!多奧妙的啟示!包容一切衝突性的現象,擴大剎那間的視域,這單純的音響,於我是一種智靈的洗淨。
花開,花落,天外的流星與田畦間的飛螢,上綰雲天的青松,下臨絕海的巉巖,男女的愛,珠寶的光,火山的熔液:一嬰兒在它的搖籃中安眠。
這山上的鐘聲是晝夜不間歇的,他已經不間歇的打了十一年鐘,平均五分鐘時一次。打鐘的和尚獨自在鐘頭上住著,據說他的願心是打到他不能動彈的那天,鐘樓上供著菩薩,打鐘人在大鐘的一邊安著他的「座」,他每晚是坐著安神的,一隻手挽著鐘槌的一頭,從長期的習慣,不叫睡眠耽誤他的職司。
「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沒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竅蒙充六根,怎麼算總多了一個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師的談吐裡不少某督軍與某省長的點綴;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貪嗔的化身,無端摔破了兩個無辜的茶碗。但這打鐘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歲在五十開外,出家有二十幾年,這鐘樓,不錯,是他管的,這鐘是他打的(說著他就過去撞了一下),他每晚,也不錯,是坐著安神的,但此外,可憐,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麼異樣。他拂拭著神龕,神坐,拜墊,換上香燭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乾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轉身去撞一聲鐘。他臉上看不出修行的清臒,卻沒有失眠的倦態,倒是滿滿的不時有笑容的展露;念什麼經;不就念阿彌陀佛,他竟許是不認識字的。「那一帶是什麼山,叫什麼,和尚?」「這裡是天目山,」
他說,「我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帶的,」我手點著問。「我不知道」。他回答。
山上另有一個和尚,他住在更上去昭明太子讀書臺的舊址,蓋有幾間屋,供著佛像,也歸廟管的,叫做茅棚,但這不比得普陀山上的真茅棚,那看了怕人的,坐著或是偎著修行的和尚沒一個不是鵠形鳩面,鬼似的東西。他們不開口的多,你愛布施什麼就放在他跟前的簍子或是盤子裡,他們怎麼也不睜眼,不出聲,隨你給的是金條或是鐵條。人說得更奇了,有的半年沒有吃過東西,不曾挪過窩,可還是沒有死,就這冥冥的坐著。
他們大約難成佛不遠了,單看他們的臉色,就比石片泥土不差什麼,一樣這黑刺刺,死僵僵的。「內中有幾個,」香客們說,「已經成了活佛,我們的祖母早三十年來就看見他們這樣坐著的!」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裡的和尚,卻沒有那樣的浪漫出奇。茅棚是盡夠蔽風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鮮鮮的人,雖則他並不因此減卻他給我們的趣味。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裡來修行;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說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沉著的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著他內裡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跡;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著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裡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曾壓倒,不曾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裡豈不顫慄著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著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跌坐時意念的究竟?
佛於大眾中,說我當作佛,聞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將非魔作佛,惱亂我心耶。
但這也許看太奧了。我們承受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心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非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絕不肯認輸,退後,收下旗幟;並且即使承認了絕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體的取決,不來半不闌珊的收回了步伐向後退:寧可自殺。乾脆的生命的斷絕,不來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認。不錯,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亞佩臘與愛洛綺絲,但在他們是情感方面的轉變,原來對人的愛移作上帝的愛,這知感的自體與它的活動依舊不念糊的在著;在東方人,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滅,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跡的解脫。再說,這出家或出世的觀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國,是跟著佛教來的;印度可以會發生這類思想,學者們自有種種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釋,也盡有趣味的。中國何以能容留這類思想,並且在實際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最近一個朋友差一點做了小和尚)!這問題正值得研究,因為這分明不僅僅是個知識乃至意識的淺深問題,也許這情形盡有極有趣味的解釋的可能,我見聞淺,不知道我們的學者怎樣想法,我願意領教。
十五年九月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