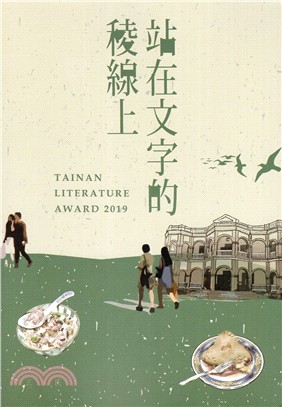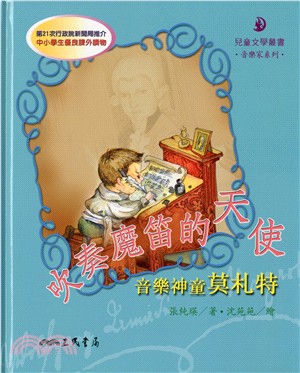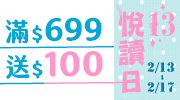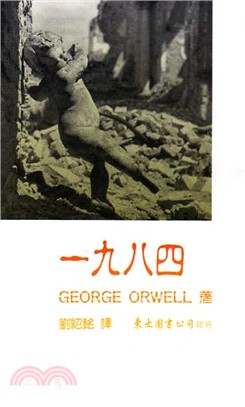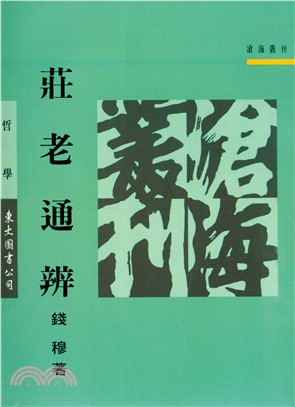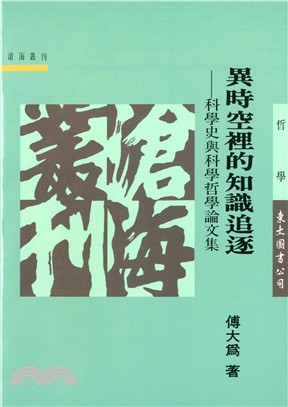永久散步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異鄉彼時,他城此刻,行走在其中的我們,
終是永久歲月裡,微不足道的標本。
李時雍第二本散文集
寫給在時間裡不願散場的人
《永久散步》集結作家李時雍一趟未曾清晰的旅程,亦是永恆探問:「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Ⅰ.燈塔街」是他在薩默維爾的浮光掠影,生活在波士頓的查爾斯河畔,彷若一名dreamer,但更多時候他以音樂/舞劇/電影安撫自己惶惶然的心,安頓那些日子裡的寂靜、困頓,總是走長長的路,看深深的暗默,在面窗的書桌上塗抹生命中一段留白,是「站在生命的中途。前頭還未顯露,而深感埡口的孤獨」。「Ⅱ.紀念碑」,則可視為時雍研究書寫《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的另一抒情對話,他走出文獻與寫作空間,實際造訪歷史現場,新城、霧社、廬山、蘭嶼,復讀島嶼上文學者前行的足跡,那些小說與影像成為門扉,當以雙腳來到,才使他「真正開始走近了事件的原點」。
本書特以不分篇章的連續編輯形式,手札日記的密語,時間的跳躍與空間的移轉,流水般形成了一個莫比烏斯環,結束的句點可能是新承接的段落,暫擱的片刻猶疑是另一次的啟程。島上捎來消息的郵局,停靠在橋中央的車站,四十四次日落的河濱……從島嶼的日初到向晚的薩默維爾;從三十歲代的《給愛麗絲》走向此刻的《永久散步》,沿途標記人從何而來?迷途的,迴旋的,顛倒的,停頓的;該向何處去?回望,是他對抗遺忘且不願散場的凝視。
「在度日之間,就讓我成為那樣一個不願散場的人吧……」——李時雍
|I.燈塔街|
遷居查爾斯河畔的這一年,
或也是一場懸浮而緩慢的告別。
讀書、寫字、發獃,
與世隔絕般地生活著他人的生活。
|II.紀念碑|
踏查虛構與文獻裡的真實場景,
所生長的島嶼,過去是什麼樣子?
未來是什麼樣子?
我補課一般,努力讀著,繼續寫著。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李時雍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侯氏家族獎學金研究員,並曾任副刊、文學雜誌、出版社主編。著有散文集《給愛麗絲》,主編《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論著《復魅:臺灣後殖民書寫的野蠻與文明》。
名人/編輯推薦
「寫作者的年輪,若析磨其中成分,是美術,音樂,電影,舞蹈,還有文學,或說許多許多的愛——那些燃燒了全部的自己,提前離席的,已成灰燼的,往往是時雍最在意的『暗中之暗』。能於暗中辨別另一種暗,必然因為,那暗,閃爍著氣質相近的毫光。」——孫梓評|作家——專文推薦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林文義|作家
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
邱貴芬|中興大學台文所終身特聘教授
侯吉諒|詩人、書畫家
施叔青|作家
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家
許悔之|詩人、有鹿文化社長
梅家玲|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兼現代中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黃春明|作家
——並肩散步推薦(按姓名筆畫排序)
序
推薦序
不願散場的人——閱讀李時雍《永久散步》
⊙孫梓評(作家)
香港朋友來台短居一季,約我去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許多次我路過它卻未能停下。看完各種押房,在小小的苔綠的放封區,想像當年許多秀異青年,莫名成為良心犯,抱持怎樣的心情在此?日落前我們走向余余劇場《百合.ゆり》,地點就在園區內禮堂。時雍替舞劇做了精采的導聆,舞蹈以家族故事為軸線,舞台上許多箱子,重複被舞者搬運堆疊撞落,箱子是很有效的道具,那麼具體,卻又抽象。
《永久散步》也讓我想到那些箱子。箱子本身表情匱乏,但能收納各種情緒。就像這些讀起來質地均勻的字,揭開之後可能藏有「燙手的心」。
輯一「燈塔街」是時雍哈佛一年的薩默維爾住處,望文生義我喜歡那街道是暗,卻有燈塔矗立指引。寫在四十歲之前的這些字,像手札,日記,或寄給親密朋友的一束信,要求敘事的人大概會迷路,然而其中一閃一閃的星芒,帶有哲學思索,是一名青年藝術家真誠的說話。我特別喜歡此輯撥亂時間線性:抵達早於出發,停留同時返回。時間在此是個地層,我們跟隨記憶,沿途拜訪左營的水兵,民雄的大學生,飛到美國度過暑假的少年……寫作者的年輪,若析磨其中成分,是美術,音樂,電影,舞蹈,還有文學,或說許多許多的愛——那些燃燒了全部的自己,提前離席的,已成灰燼的,往往是時雍最在意的「暗中之暗」。能於暗中辨別另一種暗,必然因為,那暗,閃爍著氣質相近的毫光。
書中引阿巴斯說,「我察覺人未能細看眼前景物,除非它存在框架內。」這些低溫的文字,也是時雍炭筆勾勒的景框(或者箱子)。許多話語連同事件的線條被裁切,但總有各式的人:朋友,同學,戀人,親人,甚至工作與生活中萍水相逢的誰,走進相紙,成為構圖。地球上持續的移動,形成程度不一的眷戀,就像他離開前隨手拍下一幀異國或異地的房間(那也是一個箱子)。
如同時雍,我亦篤篤寞寞察覺生命來到中途埡口,想像過可能的燦爛墜為「沒有的生活」,面對日子,惟低頭耕耘視線所及。同時明白,人生確實一趟無窮盡補課,比如,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後來便在陳列《殘骸書》得到更為立體的理解。相較於前輯較內向性的私人斷代,「紀念碑」作為輯二,彷彿由內推擴向外,置身文明與野蠻之間,當然可以與其從文學審視、梳理現代台灣四次原住民關鍵事件的論文《復魅》對讀。
「紀念碑」從學者回到作者,以均衡的抒情,寫新城,白水湖,鶯歌,和平島,蘭嶼,霧社,廬山;讀陳映真,巴代,夏曼.藍波安,鍾肇政,舞鶴,李昂,這些島國行腳,是對遺忘的喚醒(打開箱子),也是對詮釋的拮抗(衝撞箱子)。
時雍曾借小說《餘生》的句子說,思考是一場「無所為的永久散步」——不知怎的我想起一個十七歲夜晚,和同樣著迷寫作的朋友們捧著剛領到的人生第一座獎盃,在南方深夜城街,沒有盡頭往前走著,渾然不覺剛剛轉彎處是湯德章被槍決之地,再往前,來到二十年後將重新開張的林百貨。心底的柴薪熊熊燃燒,因為曾被燈塔的光拂過,散步不是為了目的,而只是讓自己在路上,持續移動著,當夜浸潤更深,哪怕置身暗中,「就讓我成為那樣一個不願散場的人吧。」
後記
未曾清晰的路
讀書時,曾念到這樣一句話:清晰的不確定。
寫作外,近年我同時的研究書寫,沿著文化人類學者詹姆斯.克里弗德對當代的旅行、移置,影響所及生命的「根源」與「路徑」等思考;他曾引用高更著名的畫作名,代為自我的問句:《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回想最後卻回覆道,只有不確定性,lucid uncertainty。
高更那幅橫長的、彷彿總結人類一生的最大規模畫作,就收藏在波士頓美術館。離開多年,我仍時常印象起那個展間,想起粗礪畫布上鋪展開的新生、成年的中途,或晦暗憂傷;而金橙色的人身,總像籠罩於豔陽的光芒。出生巴黎的藝術家餘生遠赴南太平洋的小島大溪地,愈往深處,僅為找尋一種嶄新的光色,新的顏料、繪畫主題,聽尋一種,內在愈清晰的不確定。終致在臨界著虛無面前,以一瞬揭示生命永久的勃發。
我未曾想像過會有這樣一部散文集。就像我未曾想像有這一段路。《永久散步》的文字,主要寫自二○一八至二○一九年,與二○二一到二○二三年間,並曾有各別的系列名。寫作當下,未曾浮現任何書的念頭。直到今年初,在研究室彙編另一部論著時,莫名地,想起這幾年生活過的文字,一個下午重新閱讀,竟有了它彷彿清晰的輪廓,一幕幕鋪展的影像似有回聲,我是誰?我從何處來?
此刻,我仍然懷抱著「我向何處去」的疑問?一如留在零點的薩默維爾,房間裡,暖氣時而漫起薄薄的霧,我的窗外,可見一架微鏽的舊單車斜靠欄杆。後院的樹、草坪,在雪後泛白,在春天覆蓋上金色的光。前側是家門前那條以燈塔為名的長街,如果沿著一直走,會途經古老的校園,徹夜敞亮的圖書館,地鐵站,與廣場,如果一直走,是否將又走回到清晰的查爾斯河邊。
目次
推薦序|不願散場的人⊙孫梓評(作家)
I.燈塔街
II.紀念碑
後記|未曾清晰的路
書摘/試閱
方舟
面西的塔樓,在傍晚時分像一張揚起的臉,鐘面的指針鑲著金黃色的光芒。我坐在這些日子經常待在的位置,昆西與哈佛街和麻薩諸塞大道,在帘幕微掩的窗外交會,三角的地帶,留下了一片疏疏淺淺的綠地。枯樹、鐘塔、街燈、行人,各有各的向晚的張望。
Chin,我坐在這些日子以來同張的木桌子前,寫信給你。你從西岸捎來的明信片就夾在書頁間,隨身整個星期。到了二月底這時,除去偶然的雲氣,確已令人感覺季節逐漸回暖。揮別覆雪的街道,告別眼中凝成的薄薄的霜,彷彿現跡的松鼠般,又開始出門、恢復走路的生活。
春季我旁聽著一堂王德威老師的「當代小說與歷史」,週一下午,固定至燕京那磚紅靜穆的古老建築中課室。其他時則多徘徊於圖書館間。我一直睡得不好。相較昔日臺北的朝九晚五,現在可說是一隻令自己也陌生的晝伏夜行的動物了(笑)。日裡昏沉,往往四五點才清醒起來,收拾書包,遲遲出門。
從北面進入校園,穿過草地,不用十分鐘,便能途經離家最近的燕京圖書館。哈佛有七十多座圖書館。我房間的牆上,釘有一張秋天初抵總攜著的地圖,圖上標記著分布於劍橋校區的圖書館,光點叢聚似星圖。而最大的一座懷德納,就在校園中心那片小徑分岔的大草坪前。懷德納的母親為紀念鐵達尼號船難喪生的孩子,捐贈了家中藏書,和這幢巍峨的建築。
寬闊的石階,希臘式廊柱,漫長消融於暮色,逕直走上二樓的閱讀室,室裡迴盪遼闊的寂靜,僅紙頁窸窣沙沙。擇臨窗座位,望外是教堂襯在天空中潔白的塔尖。
而此刻,我坐在另一座更常讀書的拉蒙特圖書館,另一扇窗,收容著另一座鐘塔。我更喜歡拉蒙特因唯有它是徹夜開館的。天暗前約莫五六點來到,在對街的Tatte麵包店買杯咖啡(隔壁就是哈佛書店,門前總有個在看書的流浪者),返回靠窗的位置。愈晚、念書的學生陸續前來,占滿每一張桌。我會待到凌晨,再沿著冰涼的街道,走三十分鐘路回家。
在這裡讀書、回信、寫作。在這裡讀到這樣的句子,「我孤獨 我寂寞/誰不知霧的彼面有清醒的境遇/誰不知 恨又倍加愛的濃度」而震顫,而難過。
上週五清晨,被窗外呼嘯的風雨驚醒,輾轉,卻再睡不著。終於陷入惶然不安。六點多收了東西倉促出門。
回到拉蒙特前,傘沿路翻了無數次(稍晚看到新聞才知有嚴重的風暴侵襲)。早晨的圖書館,只暈黃的光清醒。我看見幾張桌上敞開書或筆記,字跡與算式的主人,在臨旁沙發側身小睡。那天,在這些日子以來的桌前,嘗試讓自己靜下來,續續讀著陳千武的《獵女犯》。
叢林的霧,疊映著窗外的,大雨大雨一直下。擱淺的我,等待著雨水淹漫足踝,還是等待著啣枝報信的鳥,帶來遠地的消息(一如你的明信片)。Chin,有一刻,我竟感覺整座拉蒙特像潮漲中浮晃的船,微光穿透木板的間隙,直到心的底層,帶來張望,帶來絕望。
但現在,我暫且沒事了,再聊。
黑橋
暮色收復了光的一刻,延伸的柱列齊集鼓譟,如管風琴的嗡鳴,橋拱的幽暗之處像魔術師的帽袋,反覆反覆地,自深處拉出黑絲帶,一會兒,便纏縛整片黯藍的夜空。
那幾天的奧斯汀燠熱、無風。豔陽下,行走在空闊的街區,雙頰灼熱,額微汗,眼前的景物蒸騰浮晃,彷彿又回到臺灣南方的城鎮。會議次日的傍晚,我和友人自校園裡的會場悄悄抽身,前往西側鄰河的那間咖啡廳。
抵達時日光業已低斜,河面無盡的雙眼,折射著破碎的光芒,磚房、木棧的平臺、臨隔的船埠,都沐浴在一層薄薄的金黃,一艘小艇正離岸駛遠,曳出長長的漣漪。那間咖啡廳以莫札特之名。坐在窗邊,對岸不遠,丘陵側身低緩的線條竟形似八里。我喜歡一座城市被河流所環抱著,淡水的淡水河、波城的查爾斯河,科羅拉多河宛延流經奧斯汀的肚腹之間,在地圖上,像伸延的臂彎,將戀人的腰輕輕地承托。
幾個月不見,與朋友補上了彼此生活與寫作的近況,聊聊這兩天我們分別從東西岸飛來會合、參加的北美臺灣研究年會,各自讀一下書,準備隔日的報告。我們想趁稍晚夕陽不那麼熱,沿河岸走一段路,約莫日暮時分,再乘車往南邊的議會大道橋。
那座橫跨柏德女士湖的大橋,將城南的居民帶進城市的心臟,若望向道路盡頭,遠遠即能看見德州議會古老的建築,圓穹頂、寬闊的柱廊,日晝灑下時,像鹽沙雕成,夜裡巍巍然一座白色的城堡。稍早聽曾造訪的MX提起,每天,到了晝夜轉換之際,棲居於橋上的無數蝙蝠便會振翅夜行,飛行的隊伍將綿延好幾公里。
初夏之後,相較彷如永夜的冬季,日長延遲至八點二十餘分才落。來到橋下的公園,草坡上已聚集許多野餐候等的人。沿著河岸的林道步行小段,水面泊停的船艇在葉間隱現。而議會大道橋的墩柱,厚實地佇立在河中初臨的夜色,橋拱深邃如巢穴,是琴風箱的奏鳴。我和友人小口啜著氣泡飲料邊等待著。直到橋上的街燈在某刻同時電火閃爍,映照出滿橋探身,火柴般細細亮起的人影。
灰黯的雲,忽忽便自橋拱深處湧現。初始還分辨不出是夜色或其他;但習慣了幽暗的眼睛,漸次得以在色塊中,析分出點觸的顏料。一隻一隻撲翅夜行的小獸,黑色絲緞的綿長,往月升東向飛翔直至更深更深的宇宙……。
當旅程日長,許多時候,我愈感覺自己就像對倒於橋下落單的獸,與世界的白晝遠遠地隔開。有些時候我想起了你,邁叟,而愈感迷惘,為何我身處在這,在那?而這些極美的片刻,奧菲斯所曾歷的幽暗,布朗修的另一種夜,對他者來說,意謂著什麼?
隔日,會議結束之後接著晚宴,與會的學者們成群成群的,吃飯、熱烈交談未竟的話題。我獨自坐了一會兒。而後安靜地離開。
那時月光純白,自仿羅馬競技場的建築牆面,早升於透明的天空。我從校園往南,途經了白色城堡,復順著議會大道散步著。經過派拉蒙劇院。在天色漸暗時,走進酒吧密聚的街區。那幾天正值西區冠軍賽,吧檯上的電視都正轉播著火箭與勇士系列球賽,沿街喧譁。
來到河邊業近九時,夜空已將暮色盡數收回。蝙蝠離巢,黑橋寂靜。我逆著人群,從橋的這一岸,走到了對岸。再從那一岸,緩緩地,疲倦地折返。
川中島
暮色橫渡北港溪,就進入了清流。
昏朦的河堤,浮現馬賽克拼貼的壁畫,吹奏口簧琴的賽德克勇士,家屋織布的婦女,群山環伺著,一道詩歌亙古吟誦的彩虹橋。長長筆直的徑路,駛向畫中勾勒那幅部落的真實,五點過後的田野,已陷入整片暗默。
之於今日清流之名,我更習慣稱它川中島。它卻並非一座島。崇山中,被北港和眉原溪流所環圍的這片臺地,孤立竟如小小的島,也許,因此疊影著初來乍到的日殖民者心底所思念、川水匯流的長野川中島藩。而那裡和這裡,同樣有過殘酷戰爭。
小說家鍾肇政一九八○年代完成「高山組曲」,第一部即《川中島》。一九三一年春天,歷劫霧社事件後、軍警鎮壓的賽德克倖存婦孺,被安置在羅多夫、西寶兩地收容所,美其名曰「保護蕃」,實則採集中監管及懲罰。四月底的凌晨,在日方密諭或縱容下,任敵對部族闖入,戮殺餘族,甚而留下一幀陳列駐在所前馘去百零一個首級的懾人影像;日後藝術家陳界仁以此重製為視覺作品《法治圖》以省思歷史暴力和創傷。驚悸未久,五月六日,餘下不及三百族人,再被強制移徙至距離祖居地迢遙的川中島社。小說《川中島》就由零餘隊伍中的青年畢荷.瓦利斯(日文名高峯浩)故事寫起。
他是繼花岡兄弟後,被日方撫育的新生代。然而事件爆發,阻斷所有前程的幻想。鍾肇政以畢荷的目光,敘寫他在道澤駐在所小島源治庇護下倖免於難,流離川中島,後被命為警丁,靠自學復考取「現地醫」的歷程。卻屢屢夾處於殖民者與族人矛盾之間。小說末了,被安排與花岡初子成婚。
客籍出生新竹州龍潭庄的鍾肇政,曾憶述最早的霧社印象,猶髫齡時,聽聞父執輩隱微議論的新聞,唯留下恐懼:「他們的表情,語氣,似乎是興奮的,然而給予我的感受卻是恐怖的。」直到十五、六歲,隨教書小學的父親遷居大溪山裡的八結,才初次接觸到原住民婦人,以日語和他交談,同時期,也在圖書館翻讀到霧社記載的書冊。
戰後七○年代,隨寫作莫那.魯道為主角的《馬黑坡風雲》,始深入識得其後被稱為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及移住川中島的餘生者故事。小說家多次造訪舊址,亦曾拜訪改漢名為高永清的畢荷.瓦利斯(他留有一部日文所寫《霧社緋櫻之狂綻》),構想了《川中島》到描寫高砂義勇隊南洋經驗的《戰火》。將觀點移至餘生者的罪咎與認同愈複雜的困惑,更突顯所謂「賽德克精神」。小說中的主角,終於在訂定婚姻的晚宴上,對著日殖民者說出第一次婉拒的「不」。
曾經喪失祖居的根源而新立川中島社,曾經從荒蕪中拓殖的模範部落,曾經小說家為寫作踏查涉越的溪水,歷經半世紀過去,也有了老去之臉。隨著暗默寂寥的屋舍,浮現車窗前的道路,我終於踏入夢中已反覆造訪的餘生之地。
星期二的蘭嶼郵局
折返於橫貫東81線宛延的山徑,回到紅頭,沿灘頭上簇集,即舊日的森嚴地標,派出所、郵局、島上唯一座衛生所,鄉公所立於舊軍事指揮部遺址,今僅遺留一座遙望的銅像,似將被海所遺忘。
其中,小小的蘭嶼郵局,挨身坡徑上村落一幢幢屋宇隙罅間,若從環島公路騎行,不留意便會錯過。這裡承載著半世紀以來信匹帶至的好壞消息,捎來遠方的惦念,也曾換來擾動原初海洋的貨幣交流。相較於礁岸、沿公路麇集的旅宿和咖啡店遊人正喧囂,途經此地傍晚,居高的建物,兀立像閒散幕落的戲臺。
夏曼.藍波安曾寫有一篇〈星期一的蘭嶼郵局〉,敘寫這處面海背山、坐落紅頭部落進出而像是海口匯聚的舞臺。近鄰麵店、滷味攤、檳榔攤,淡水與鹹水般交往做生意的族人及漢人,小學生上下學必經之階路,常錯雜著達悟語閩南語英日語。在核廢料場矗立以南龍頭岩段海岸,漫漫數十年,驅除不離,政府撥發以「補償金」,欲換取更長久的延宕擱置。週末過後的郵局,因此聚集聽聞村廣播放送消息懞懞懂懂而至的族人們。
補償金會存入「郵局的書」即存款簿。「書」的數字,終將取代古老物物交換的漁獲、農作,定義嶄新的財富。亮潔的磁磚地板,印有排列隊伍的足印,像未來的指向。
然而相對以貨幣再交易買醉於菸酒的人,文中藉自稱「優質的神經病人」表弟安洛米恩,看向郵局內外那些「原初型的騙徒」上演的一貫戲碼:藉幫忙老人存款索取「仲介」費用,向商店賒帳,喝醉酒就吹噓著臺灣耍流氓的過去。所謂「優質」與「劣質」,區別一個人的品行,「正常人」或「神經病人」卻帶有現代主流觀點混濁著傳統的問題性。
夏曼.藍波安從小說〈安洛米恩的視界〉到《安洛米恩之死》反覆描寫這位部落人口中的「神經病人」,實則善於傳統獨自潛水、捕魚,做為迎對現代性的另類視點,並流露對安洛米恩深刻地同感、同情,在眾醉者之間,「秋分的夕陽此時顯得特別溫熱……安洛米恩清醒而逕自的下了海。」
星期一晚上,過夜臺東,搭上隔日的小飛機在午前降落蘭嶼機場,住在神話充滿的八代灣上。午後騎車,摸索著橫貫崎嶇的道路,從東清、野銀,繞行半座島返回紅頭,惦記著傍晚約定的時間。啟程前傳出的訊息,不久後回應:「非常歡迎。」「五點,約在蘭嶼郵局。」
隙罅間的綠色建物,折返找尋上坡的徑路,途經閒步的老海人,麵攤、早餐店、雜貨店,遠遠地,便看見熟悉的夏曼.藍波安,約好抵達之日碰面的他已等候在郵局之前,秋陽溫熱,向我們招招手。跟隨他身後,穿過了一級級石階,背向海,往部落深處的家屋走去。
夕陽靜靜地落海,暮色籠罩星期二的蘭嶼郵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