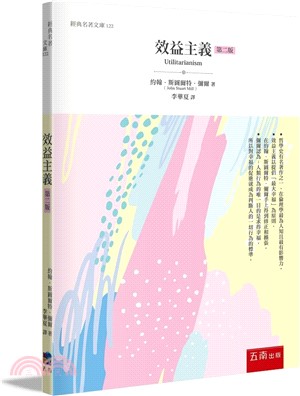效益主義
商品資訊
系列名:經典名著文庫
ISBN13:9786263667907
替代書名:Utilitarianism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
作者:約翰‧斯圖爾特‧彌爾
譯者:李華夏
出版日:2023/12/28
裝訂/頁數:平裝/112頁
規格:21cm*14.8cm*0.7cm (高/寬/厚)
重量:210克
版次:2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哲學史有名著作之一,在倫理學最為人知且最有影響力。
效益主義以提倡「最大幸福」為原則,在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手上得到修正和擴張。
彌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什麼是真正的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如何運用?
「道德基礎」的判定基準是什麼?
效用,或最大幸福原理,堅持行動當其趨於提昇幸福者是「對」,當其趨於帶來幸福反面者是「錯」,這一綱領做為道德基礎。幸福是愉悅和不再痛苦;不幸指痛苦和欠缺愉悅。愉悅和免受痛苦,是唯一值得嚮往做為目的之事物;且一切值得嚮往的事物都是可追求的,無論是因於該事物固有的愉悅,或可做為手段以提昇愉悅和規避痛苦。
有鑑於彌爾身處年代對於效益主義的誤解,而撰寫此書。這是一本影響深遠的倫理學經典,效益主義時至今日依然是倫理學領域中的主要理論之一,其帶來的意義值得後人深思。
效益主義以提倡「最大幸福」為原則,在約翰.斯圖爾特.彌爾手上得到修正和擴張。
彌爾認為:人類行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對幸福的促進就成為判斷人的一切行為的標準。
什麼是真正的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如何運用?
「道德基礎」的判定基準是什麼?
效用,或最大幸福原理,堅持行動當其趨於提昇幸福者是「對」,當其趨於帶來幸福反面者是「錯」,這一綱領做為道德基礎。幸福是愉悅和不再痛苦;不幸指痛苦和欠缺愉悅。愉悅和免受痛苦,是唯一值得嚮往做為目的之事物;且一切值得嚮往的事物都是可追求的,無論是因於該事物固有的愉悅,或可做為手段以提昇愉悅和規避痛苦。
有鑑於彌爾身處年代對於效益主義的誤解,而撰寫此書。這是一本影響深遠的倫理學經典,效益主義時至今日依然是倫理學領域中的主要理論之一,其帶來的意義值得後人深思。
作者簡介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
十九世紀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道德哲學與政治理論家,曾任國會議員,倡導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邊沁後效益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從小父親(詹姆斯.彌爾,蘇格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便以效益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來教導彌爾,事實上彌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彌爾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意無意成為效益主義學派的接班人。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哈莉耶特.泰勒.彌爾的婚姻生活。
彌爾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妻子的影響,泰勒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前衛,即使是在當今,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女性主義者也不遑多讓。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彌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彌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
著作:《邏輯體系》、《政治經濟學原理》、《論自由》、《論代議制政府》、《效益主義》、《女性的屈從地位》與《論社會主義》等等。
十九世紀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道德哲學與政治理論家,曾任國會議員,倡導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邊沁後效益主義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從小父親(詹姆斯.彌爾,蘇格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理論家、哲學家。)便以效益主義當作倫理學的基底來教導彌爾,事實上彌爾自己也與邊沁常有接觸,邊沁死後彌爾還負責整理他的著作;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意無意成為效益主義學派的接班人。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哈莉耶特.泰勒.彌爾的婚姻生活。
彌爾對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妻子的影響,泰勒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前衛,即使是在當今,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女性主義者也不遑多讓。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彌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彌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
著作:《邏輯體系》、《政治經濟學原理》、《論自由》、《論代議制政府》、《效益主義》、《女性的屈從地位》與《論社會主義》等等。
序
譯者序兼導讀
這是一本影響深遠,又是譽之所在謗亦隨之的倫理學經典,更是「述而不作」的英式代表作;因約翰.斯圖爾特.彌爾(1806-1873)在本書沒有什麼創見,但將前人不同觀念折衷整合成令人信服的功力卻是無人能比。這實得助於著者的養成教育及自我反省,其帶來的意義值得後人深思,茲分段詳述如下:
一、父雖嚴,重啟發,忌填鴨
小彌爾的養成教育全是其父親, 詹姆斯. 彌爾一手規劃。三歲學希臘文,七歲輕易讀懂柏拉圖(Pl a to)《對話錄》的前六章,八歲學拉丁文,且從此擔任其弟妹們的導師,十二歲涉獵古典哲學教條。他在自傳中不厭其煩細數其閱讀的各種書目,也承認兒時這種一等一的教育,直到成年時才完全掌握深意。因此,他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而推介他父親的方式。先說這位強勢及能幹的父親,讓他從小和同齡小孩缺少互動,更在日常生活事務中沒有自理能力(這不正是現代許多名人不食人間煙火且引以為傲的寫照嗎?),小彌爾在自傳中認真回顧以其中下等之資,在父親身教言教下所學得的,和其他同齡在正規且優質學校所學得的來比較,發現他們將青春洋溢之心智,浪費在鸚鵡學舌般細微末節上,不從事思索原由。他雖「有時」不滿他父親以超乎年齡的標準來要求他,也不得不同意「一個學生從未被要求做其做不到的事,則絕做不到其所能做的事」。(這和時下唯恐造成小孩心理陰影的教育態度有多大的落差?)我們固不能以學習成果論好壞,但一個人的思想能歷經幾世紀而不衰,與「教不嚴,師之惰」之結果,就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嘆了!
二、喜古史,年雖幼,學董狐
小彌爾十一歲曾自發性試著就羅馬政府、羅馬貴族和庶民的鬥爭、貸款利率和農地法,以他自己的意思模擬羅馬歷史,但稍長全數燒毀;卻也培養了在1818年其父《英屬印度史》付梓前,由小彌爾校對之能力;問題來了,若非老彌爾是位通才(即便如此,在數學方面還是不能解答其子的疑惑),從希臘文、拉丁文、韻文體、歷史、邏輯、科學知識、雄辯術、經濟體系等無不親自傳授(因此,還誤了《英屬印度史》的進度);老彌爾的訓練又很專業,將在演講和辯論中如何注意句子的邏輯性、何時發出驚人之語,都總結出幾條規則(惜未留下這些規則的文字紀錄),小彌爾能有此表現嗎?這種完全獨特的一對一在家教育是否值得現代「另類教學」效法,實不無疑問。父母親夠不夠博學、小孩天資夠不夠及交往圈是否皆鴻儒,在在影響小孩智力的開發和感情的培養,更別說如今社會科學的多元化及翻新率那麼高,踏入社會所面臨的嚴酷挑戰,除非家境足以達到「有閒階級」,又能致力自成一專長(如日本裕仁、明仁天皇在海洋生物學的造詣),否則糊口都有問題,對社會有何貢獻?
三、藉助詩,悟感性,輔理性
小彌爾十四歲去法國一年, 他父親臨別前特別點醒他說,與人相比是看誰能做和應做什麼,而非比別人懂多少;且一再告誡小彌爾,其之所以比同齡多出一代的智力,是有一個願付出心血的父親,因此絕不能自負不凡。隨後,小彌爾在法國除領略大自然美景,也補充了其在高等數學上的不足。回英後,因非英國國教教徒,小彌爾無法進入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只能在倫敦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旁聽法理學,接著在兩份報紙,《旅遊者》(The Traveller)及《早晨紀事》(The Morning Chronicle)撰稿;並為哲學激進派的喉舌《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寫文章;又擔任邊沁(Bentham)創辦「司法證據的理論基礎」(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的編輯,且以十七歲之齡進入英東印度公司。他參與在英國歷史學家格魯特(George Grote)家中成
立的讀書社,及倫敦辯論社(London Debating Society)的辯論,他的即興式辯才雖逐漸吸引有振奮成效和具啟發性的人士加入,卻因小彌爾在那種場合被視為早熟、「人工的人類」及智力機器,而澆息他的熱情。小彌爾原信奉蘭鐸(Landor)「少相識,少朋友,不客套」的準則,將其私人情感全獻給大眾,至此小彌爾對其為自己所設下的目的―社會的正義,感到不安;在1826至1827年間經歷「心靈危機」,所幸他從浪漫派詩人沃德沃夫(W. Wordworth)的詩作中體會到,美麗事物可產生對他人的同情及激發歡樂,和情緒文化與社會改革同等的重要(而這正是他父親最不認為有實用價值者),也發現自己不是沒有感情的人。小彌爾受浪漫派哲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歷史學家卡萊勒(Carlyle)、歌德(Goethe)的影響,將浪漫主義思想和古典哲學折衷起來。
小彌爾經過內心和憂鬱孤獨的角力,終於在詩句中找到以寬容面對爭論,修正雄心到可實踐的地步;1829年他不再參加辯論社,但帶著政治哲學不是一個提供制度的模型,而是提供原理供制度可以適應任何環境要求的辯證認知,發表了一系列「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又在《泰特雜誌》(Tait’s Magazine)和《法學家》(The Jurist)及《每月寶庫》(The Monthly Repository)推展其對人類幸福更具普世觀及厭惡門派之爭的觀點。1835年在莫理士沃夫爵士(SirMolesworth)創辦的《倫敦評論》(The London Review)任編輯,1836年和《西敏寺評論》合併成《倫敦及西敏寺評論》,除仍任編輯外,還成了所有者。1840年後陸續在《愛登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發表重要文章,旨在給英國激進派注入新精神,1859年被收錄到《考據與討論》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小彌爾也深受英國科學家及數學家牛頓爵士(Sir Issac Newton)的啟發,強調新邏輯不該僅是反對舊邏輯,主張其歸納邏輯是補充而非接替,並將此應用到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心理學和社會學,顯示小彌爾的浴火重生。
四、得真愛,倡女權,重正義
小彌爾自1 8 3 0 年和哈莉耶特. 泰勒女士相識至結婚, 情感上的滿足自不待言。其妻反對愛情, 認為愛情奴役了女性;也反對基督教,因其造成個人解放的障礙,形成社會專制;這些觀點感染了小彌爾開始關注社會主義,重新思索正義的問題。他在生活和社會的理想受其妻啟發,這也表現在小彌爾的文章上,《論自由》是最為人熟悉的;但結構上仍是小彌爾本人的。他唯一受其妻啟發的文章是「給予婦女選舉權」(Enfranchisement of Women)。其妻1858年死後,彌爾並未忘情政治,他支持美國南北戰爭的北方,用盡力氣去解釋其真正問題是解放黑奴。1 8 6 5 年他發表了「檢視威廉.漢彌頓爵士的哲學」(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和「奧古斯特.孔德及實證主義」(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彌爾反對前者這位英國直覺哲學堡壘的主張;彌爾將後者早期實證哲學教條及人道宗教區別對待,推崇實證哲學教條是柏克萊(Berkeley)及休姆(Hume)思想的自然發展,這也讓小彌爾離邊沁愈來愈遠,他認為宗教只是給人道另一個牧師階級制。同一年小彌爾不從事競選活動,卻被選為國會議員;任內促使「改革法案」通過,為了防止貪汙瀆職,強行通過數項有用的修正案、改革愛爾蘭的土地所有權、倡導婦女的代表權、減國債、改革倫敦政府,及廢除《巴黎宣言》―有關在克里米亞(Crimean)戰爭期間海上財產的運費, 更鼓吹英國為了自由可干預外國政治。後因追訴艾爾(Eyre)統治牙買加(Jamaica)期間的殘酷行徑、資助激進政治人物和自由思想家巴爾德羅(Bradlaugh)的競選經費、提出不獲認同的改革,受「溫和自由派」的抵制而不能連任。1 8 6 7 年小彌爾和戴維斯(Emily Davies)及另一位泰勒夫人創辦英國第一個「婦女參政社」,稍後發展成「婦女參政社全國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他最後的公開活動是有關發起「土地所有權改革協會」(Land Tenure ReformAssociation)。1869年小彌爾重印其父《人類心智現象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加上說明及解釋性注釋以表孝思。
五、經濟體,經三變,重分配
小彌爾做為政治經濟學家,其關注重點有三變:
1. 1844年發表《關於政治經濟體某些懸而未決問題論文集》的五篇文章中,有四篇是在解決困難度高的技術性問題:國際商業盈餘的分配、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定義,及利潤和工資的確實關係,都是以李嘉圖(D. Ricardo)為師。
2. 1848年出版《政治經濟體原理》鼓吹創立農民土地所有權是愛爾蘭壓力和失序的解方;隨後他認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同樣重要。
3. 他將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分開,他不滿那注定對勞動階級被擠壓成悲慘生存,甚至到飢餓的分配。他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但他受其妻的影響認真考量社會的基礎。他拒絕接受原設計保障原始社會和平的財產權,作為社會在不同發展階級的必要神聖地位。
小彌爾在死前數月曾公開演講,稱合作農業及由國家攔截土地不勞而獲的增量部分,是歐洲資本與勞動鬥爭的妥協方案。
六、言與行,即權宜,仍不義
小彌爾在自傳中曾說其父親對他的要求是言多於行,以致他在日常生活和操作上是遠不如其父的;這除了其父親「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外,可看出其父希望他進入「有閒階級」的期許。小彌爾曾為延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權,而在離開該公司前盡力辯護,不管是為了五斗米折腰(他承認這份薪資讓他能安於思考及寫作),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卻忽略英國剝削殖民地的道德正當性;或許他認為英國的殖民帶來印度某些產業的發展是提昇印度的福祉,至於殖民的原始動機,即使「不義」也就無所謂。正如他在本書的注中,暴君救溺水之人以求更能折磨的例子。讀者在敬佩其辯術犀利之餘,應仔細思辨其思想和儒家「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境界和其對人種歧視的幽暗。
最後,說一下「Utilitarianism」的譯名,早期譯作「功利主義」是讀通其原義,並以中國已有的思想配之;因「明其道不計其功」及「計利當計天下利」,都指行事不能僅考量自身之名和利。只可惜民間視「功利」為「勢利」,僅顧一己之私而望文生義,易遭誤解,遂取「效益主義」以顯其計算之法,但若用「效益至上主義」或更能表達求人類最大幸福的精髓。「utility」譯作「效用」和「效益」均可,但以「原理」來說,重在需要而有用,而非只算好與壞的利弊,所以採「效用原理」。「expediency」譯作「權宜」,在民間觀念上以「便宜行事」為主;但若以「春秋大義」而言,是指有條件(即特殊情況下),犧牲一己之私,為眾生除害或謀福利,而從事平常不做的行為,與「效益主義」所標榜的相符,是「可以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以權」的「權」,也是「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道德標準;用「宜」而不用「謀」,是「正其宜(誼)不謀其利」的「宜」,「宜」者,「義」也,亦符小彌爾的思路。
李華夏
完稿於二○二○年
五月廿日,小彌爾誕生之日
這是一本影響深遠,又是譽之所在謗亦隨之的倫理學經典,更是「述而不作」的英式代表作;因約翰.斯圖爾特.彌爾(1806-1873)在本書沒有什麼創見,但將前人不同觀念折衷整合成令人信服的功力卻是無人能比。這實得助於著者的養成教育及自我反省,其帶來的意義值得後人深思,茲分段詳述如下:
一、父雖嚴,重啟發,忌填鴨
小彌爾的養成教育全是其父親, 詹姆斯. 彌爾一手規劃。三歲學希臘文,七歲輕易讀懂柏拉圖(Pl a to)《對話錄》的前六章,八歲學拉丁文,且從此擔任其弟妹們的導師,十二歲涉獵古典哲學教條。他在自傳中不厭其煩細數其閱讀的各種書目,也承認兒時這種一等一的教育,直到成年時才完全掌握深意。因此,他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而推介他父親的方式。先說這位強勢及能幹的父親,讓他從小和同齡小孩缺少互動,更在日常生活事務中沒有自理能力(這不正是現代許多名人不食人間煙火且引以為傲的寫照嗎?),小彌爾在自傳中認真回顧以其中下等之資,在父親身教言教下所學得的,和其他同齡在正規且優質學校所學得的來比較,發現他們將青春洋溢之心智,浪費在鸚鵡學舌般細微末節上,不從事思索原由。他雖「有時」不滿他父親以超乎年齡的標準來要求他,也不得不同意「一個學生從未被要求做其做不到的事,則絕做不到其所能做的事」。(這和時下唯恐造成小孩心理陰影的教育態度有多大的落差?)我們固不能以學習成果論好壞,但一個人的思想能歷經幾世紀而不衰,與「教不嚴,師之惰」之結果,就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之嘆了!
二、喜古史,年雖幼,學董狐
小彌爾十一歲曾自發性試著就羅馬政府、羅馬貴族和庶民的鬥爭、貸款利率和農地法,以他自己的意思模擬羅馬歷史,但稍長全數燒毀;卻也培養了在1818年其父《英屬印度史》付梓前,由小彌爾校對之能力;問題來了,若非老彌爾是位通才(即便如此,在數學方面還是不能解答其子的疑惑),從希臘文、拉丁文、韻文體、歷史、邏輯、科學知識、雄辯術、經濟體系等無不親自傳授(因此,還誤了《英屬印度史》的進度);老彌爾的訓練又很專業,將在演講和辯論中如何注意句子的邏輯性、何時發出驚人之語,都總結出幾條規則(惜未留下這些規則的文字紀錄),小彌爾能有此表現嗎?這種完全獨特的一對一在家教育是否值得現代「另類教學」效法,實不無疑問。父母親夠不夠博學、小孩天資夠不夠及交往圈是否皆鴻儒,在在影響小孩智力的開發和感情的培養,更別說如今社會科學的多元化及翻新率那麼高,踏入社會所面臨的嚴酷挑戰,除非家境足以達到「有閒階級」,又能致力自成一專長(如日本裕仁、明仁天皇在海洋生物學的造詣),否則糊口都有問題,對社會有何貢獻?
三、藉助詩,悟感性,輔理性
小彌爾十四歲去法國一年, 他父親臨別前特別點醒他說,與人相比是看誰能做和應做什麼,而非比別人懂多少;且一再告誡小彌爾,其之所以比同齡多出一代的智力,是有一個願付出心血的父親,因此絕不能自負不凡。隨後,小彌爾在法國除領略大自然美景,也補充了其在高等數學上的不足。回英後,因非英國國教教徒,小彌爾無法進入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只能在倫敦的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旁聽法理學,接著在兩份報紙,《旅遊者》(The Traveller)及《早晨紀事》(The Morning Chronicle)撰稿;並為哲學激進派的喉舌《西敏寺評論》(Westminster Review)寫文章;又擔任邊沁(Bentham)創辦「司法證據的理論基礎」(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的編輯,且以十七歲之齡進入英東印度公司。他參與在英國歷史學家格魯特(George Grote)家中成
立的讀書社,及倫敦辯論社(London Debating Society)的辯論,他的即興式辯才雖逐漸吸引有振奮成效和具啟發性的人士加入,卻因小彌爾在那種場合被視為早熟、「人工的人類」及智力機器,而澆息他的熱情。小彌爾原信奉蘭鐸(Landor)「少相識,少朋友,不客套」的準則,將其私人情感全獻給大眾,至此小彌爾對其為自己所設下的目的―社會的正義,感到不安;在1826至1827年間經歷「心靈危機」,所幸他從浪漫派詩人沃德沃夫(W. Wordworth)的詩作中體會到,美麗事物可產生對他人的同情及激發歡樂,和情緒文化與社會改革同等的重要(而這正是他父親最不認為有實用價值者),也發現自己不是沒有感情的人。小彌爾受浪漫派哲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歷史學家卡萊勒(Carlyle)、歌德(Goethe)的影響,將浪漫主義思想和古典哲學折衷起來。
小彌爾經過內心和憂鬱孤獨的角力,終於在詩句中找到以寬容面對爭論,修正雄心到可實踐的地步;1829年他不再參加辯論社,但帶著政治哲學不是一個提供制度的模型,而是提供原理供制度可以適應任何環境要求的辯證認知,發表了一系列「時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又在《泰特雜誌》(Tait’s Magazine)和《法學家》(The Jurist)及《每月寶庫》(The Monthly Repository)推展其對人類幸福更具普世觀及厭惡門派之爭的觀點。1835年在莫理士沃夫爵士(SirMolesworth)創辦的《倫敦評論》(The London Review)任編輯,1836年和《西敏寺評論》合併成《倫敦及西敏寺評論》,除仍任編輯外,還成了所有者。1840年後陸續在《愛登堡評論》(The Edinburgh Review)發表重要文章,旨在給英國激進派注入新精神,1859年被收錄到《考據與討論》
(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小彌爾也深受英國科學家及數學家牛頓爵士(Sir Issac Newton)的啟發,強調新邏輯不該僅是反對舊邏輯,主張其歸納邏輯是補充而非接替,並將此應用到人文學科―包括歷史、心理學和社會學,顯示小彌爾的浴火重生。
四、得真愛,倡女權,重正義
小彌爾自1 8 3 0 年和哈莉耶特. 泰勒女士相識至結婚, 情感上的滿足自不待言。其妻反對愛情, 認為愛情奴役了女性;也反對基督教,因其造成個人解放的障礙,形成社會專制;這些觀點感染了小彌爾開始關注社會主義,重新思索正義的問題。他在生活和社會的理想受其妻啟發,這也表現在小彌爾的文章上,《論自由》是最為人熟悉的;但結構上仍是小彌爾本人的。他唯一受其妻啟發的文章是「給予婦女選舉權」(Enfranchisement of Women)。其妻1858年死後,彌爾並未忘情政治,他支持美國南北戰爭的北方,用盡力氣去解釋其真正問題是解放黑奴。1 8 6 5 年他發表了「檢視威廉.漢彌頓爵士的哲學」(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和「奧古斯特.孔德及實證主義」(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彌爾反對前者這位英國直覺哲學堡壘的主張;彌爾將後者早期實證哲學教條及人道宗教區別對待,推崇實證哲學教條是柏克萊(Berkeley)及休姆(Hume)思想的自然發展,這也讓小彌爾離邊沁愈來愈遠,他認為宗教只是給人道另一個牧師階級制。同一年小彌爾不從事競選活動,卻被選為國會議員;任內促使「改革法案」通過,為了防止貪汙瀆職,強行通過數項有用的修正案、改革愛爾蘭的土地所有權、倡導婦女的代表權、減國債、改革倫敦政府,及廢除《巴黎宣言》―有關在克里米亞(Crimean)戰爭期間海上財產的運費, 更鼓吹英國為了自由可干預外國政治。後因追訴艾爾(Eyre)統治牙買加(Jamaica)期間的殘酷行徑、資助激進政治人物和自由思想家巴爾德羅(Bradlaugh)的競選經費、提出不獲認同的改革,受「溫和自由派」的抵制而不能連任。1 8 6 7 年小彌爾和戴維斯(Emily Davies)及另一位泰勒夫人創辦英國第一個「婦女參政社」,稍後發展成「婦女參政社全國聯盟」(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他最後的公開活動是有關發起「土地所有權改革協會」(Land Tenure ReformAssociation)。1869年小彌爾重印其父《人類心智現象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加上說明及解釋性注釋以表孝思。
五、經濟體,經三變,重分配
小彌爾做為政治經濟學家,其關注重點有三變:
1. 1844年發表《關於政治經濟體某些懸而未決問題論文集》的五篇文章中,有四篇是在解決困難度高的技術性問題:國際商業盈餘的分配、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定義,及利潤和工資的確實關係,都是以李嘉圖(D. Ricardo)為師。
2. 1848年出版《政治經濟體原理》鼓吹創立農民土地所有權是愛爾蘭壓力和失序的解方;隨後他認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同樣重要。
3. 他將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分開,他不滿那注定對勞動階級被擠壓成悲慘生存,甚至到飢餓的分配。他沒有提出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但他受其妻的影響認真考量社會的基礎。他拒絕接受原設計保障原始社會和平的財產權,作為社會在不同發展階級的必要神聖地位。
小彌爾在死前數月曾公開演講,稱合作農業及由國家攔截土地不勞而獲的增量部分,是歐洲資本與勞動鬥爭的妥協方案。
六、言與行,即權宜,仍不義
小彌爾在自傳中曾說其父親對他的要求是言多於行,以致他在日常生活和操作上是遠不如其父的;這除了其父親「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外,可看出其父希望他進入「有閒階級」的期許。小彌爾曾為延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權,而在離開該公司前盡力辯護,不管是為了五斗米折腰(他承認這份薪資讓他能安於思考及寫作),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卻忽略英國剝削殖民地的道德正當性;或許他認為英國的殖民帶來印度某些產業的發展是提昇印度的福祉,至於殖民的原始動機,即使「不義」也就無所謂。正如他在本書的注中,暴君救溺水之人以求更能折磨的例子。讀者在敬佩其辯術犀利之餘,應仔細思辨其思想和儒家「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境界和其對人種歧視的幽暗。
最後,說一下「Utilitarianism」的譯名,早期譯作「功利主義」是讀通其原義,並以中國已有的思想配之;因「明其道不計其功」及「計利當計天下利」,都指行事不能僅考量自身之名和利。只可惜民間視「功利」為「勢利」,僅顧一己之私而望文生義,易遭誤解,遂取「效益主義」以顯其計算之法,但若用「效益至上主義」或更能表達求人類最大幸福的精髓。「utility」譯作「效用」和「效益」均可,但以「原理」來說,重在需要而有用,而非只算好與壞的利弊,所以採「效用原理」。「expediency」譯作「權宜」,在民間觀念上以「便宜行事」為主;但若以「春秋大義」而言,是指有條件(即特殊情況下),犧牲一己之私,為眾生除害或謀福利,而從事平常不做的行為,與「效益主義」所標榜的相符,是「可以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以權」的「權」,也是「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道德標準;用「宜」而不用「謀」,是「正其宜(誼)不謀其利」的「宜」,「宜」者,「義」也,亦符小彌爾的思路。
李華夏
完稿於二○二○年
五月廿日,小彌爾誕生之日
目次
第一章 緒 言
第二章 何謂效益主義
第三章 效用原理的終極拘束
第四章 效用原理能有何種證明
第五章 論正義和效用的關聯性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年表
第二章 何謂效益主義
第三章 效用原理的終極拘束
第四章 效用原理能有何種證明
第五章 論正義和效用的關聯性
約翰.斯圖爾特.彌爾年表
書摘/試閱
構成人類知識現狀的過程中,很少像界定「對」與「錯」的爭論那樣無甚進展,換句話說,對至關重要課題的思索仍原地踏步到,處於明顯的倒退狀態;或不如預期,莫此為甚。哲學從萌芽起,有關「至善」(summum bonum),或同一回事,道德的根基這個問題,一直是推理思維的主要挑戰;困擾著天縱英才的知識分子,也令他們分門別派,從此不停進行唇槍舌戰。兩千多年過去了,同樣的論爭還在繼續,哲學家依然旗幟鮮明,各有立場,不管是思想家或芸芸眾生,對此問題難有一致看法的程度,比起年輕的蘇格拉底(Socrates)就教於老邁的普羅塔哥拉斯(Protagoras)時,以效益主義的理論回擊當時在詭辯學者(Sophist)間風行的道德主張那種情況,毫不遜色(如果柏拉圖的《對話錄》是以實際對話寫就的話)。
所有學科在思索有關第一原理時,確實存在類似的混淆和不確定性,甚至在某種學科也出現類似的針鋒相對;即使被認為是所有學科中最確實的數學領域也避免不了;但,這些現象並無損於,且通常完全無損於,這些學科結論上的可信度。此一表面上的失序,合理的解釋是,一門學科的詳細教條通常不是從其所謂第一原理推演出來,也不靠其第一原理做為支持的證明。要不然,沒有哪門學科比代數學更不確定、更不足推出結論;代數學的確定性沒有一樣來自平常教給學習者的東西做為其要素,因為這些要素是由某些代數學的名師級所制定的,就像英國法律一樣充滿幻夢,也像神學那樣充滿奧祕(神蹟)。那些被一門學科最終接受為第一原理的真理,實際上是,就與該學科密切相關的基礎概念進行形上學分析(metaphisical analysis)後,所得出的最終結果;這些第一原理和學科的關係不是地基和大廈的關係,而是根和樹的關係,發揮著同樣的功能,雖從未被挖掘出,也從未曝光。但縱使在科學領域,特別真理先於普遍理論,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特殊人文學科,如道德或法律領域。所有行動皆有其某種目的,則行動的規範必須體現出,其所從屬的目的之完全特質和色彩,似乎理所當然。當我們追求某件事物時,最先需要的似乎是,就我們正要追求之事物有一清楚和正確的概念,而不是最後才去期待。由此,或可這樣想,「對」和「錯」的檢測,必須是確定什麼是「對」或「錯」的手段,不是已確定的結果。
採用天然官能(faculty),一種感覺或本能,這種流行理論來評斷「對」和「錯」,其困難並未能避免。因為,撇開道德本能的存在本身,就是頗有爭議的課題,那些相信這個理論的人常以哲學傲人,早就放棄如下的概念,在可以掌控的特殊案件,其辨別何者為「對」或「錯」一如我們其他感覺辨別當下所見或所聽。我們道德的(感官)官能,根據所有那些稱得上思想家對其的詮釋,僅提供我們道德判斷的普遍原理;它是我們理性的分支,不是我們感官官能;必須藉助道德抽象教條,不是具體道德的感知。道德直覺派和倫理學另一派,道德歸因派,差不了多少,皆堅持普遍法則的必要性。這兩派都同意一項個人行動的道德性,不是直接感知的問題,而是一種法則應用在個人案例的問題。他們也在效益主義很大程度上認可同樣的道德法則;卻在這些法則的證據,和其所由之導出權威的源頭上,有所分歧。一派認為道德的原理明顯是先驗性,除了要瞭解用語的意義外,不需得到任何人的應允。另一派的教條,「對」和「錯」與真理和虛假一樣,屬於觀察和經驗的問題。但雙方同樣接受道德性必須從原理導出;直覺派一如歸因派,強烈肯定道德科學的存在。可是他們甚少嘗試,列出先驗的原理作為學科的前提;更不曾將這些不同的原理化約成一個第一原理,或責任的共同基礎。他們或是推斷道德的日常訓誡為先驗的權威,或是鋪設成為這些準則的共同基礎,但這類通則和準則本身從未被廣泛的接受,以致沒有明顯的權威性。如要支持他們的主張,必須或是在所有道德(德性)的根基上有某種基本原理或法則,或是當有許多原理時,理應有一個確定的優先援用次序;且這個原理,或不同原理間有所衝突時,產生決定作用的規範,必須是不證自明的。
所有學科在思索有關第一原理時,確實存在類似的混淆和不確定性,甚至在某種學科也出現類似的針鋒相對;即使被認為是所有學科中最確實的數學領域也避免不了;但,這些現象並無損於,且通常完全無損於,這些學科結論上的可信度。此一表面上的失序,合理的解釋是,一門學科的詳細教條通常不是從其所謂第一原理推演出來,也不靠其第一原理做為支持的證明。要不然,沒有哪門學科比代數學更不確定、更不足推出結論;代數學的確定性沒有一樣來自平常教給學習者的東西做為其要素,因為這些要素是由某些代數學的名師級所制定的,就像英國法律一樣充滿幻夢,也像神學那樣充滿奧祕(神蹟)。那些被一門學科最終接受為第一原理的真理,實際上是,就與該學科密切相關的基礎概念進行形上學分析(metaphisical analysis)後,所得出的最終結果;這些第一原理和學科的關係不是地基和大廈的關係,而是根和樹的關係,發揮著同樣的功能,雖從未被挖掘出,也從未曝光。但縱使在科學領域,特別真理先於普遍理論,相反的情況則出現在特殊人文學科,如道德或法律領域。所有行動皆有其某種目的,則行動的規範必須體現出,其所從屬的目的之完全特質和色彩,似乎理所當然。當我們追求某件事物時,最先需要的似乎是,就我們正要追求之事物有一清楚和正確的概念,而不是最後才去期待。由此,或可這樣想,「對」和「錯」的檢測,必須是確定什麼是「對」或「錯」的手段,不是已確定的結果。
採用天然官能(faculty),一種感覺或本能,這種流行理論來評斷「對」和「錯」,其困難並未能避免。因為,撇開道德本能的存在本身,就是頗有爭議的課題,那些相信這個理論的人常以哲學傲人,早就放棄如下的概念,在可以掌控的特殊案件,其辨別何者為「對」或「錯」一如我們其他感覺辨別當下所見或所聽。我們道德的(感官)官能,根據所有那些稱得上思想家對其的詮釋,僅提供我們道德判斷的普遍原理;它是我們理性的分支,不是我們感官官能;必須藉助道德抽象教條,不是具體道德的感知。道德直覺派和倫理學另一派,道德歸因派,差不了多少,皆堅持普遍法則的必要性。這兩派都同意一項個人行動的道德性,不是直接感知的問題,而是一種法則應用在個人案例的問題。他們也在效益主義很大程度上認可同樣的道德法則;卻在這些法則的證據,和其所由之導出權威的源頭上,有所分歧。一派認為道德的原理明顯是先驗性,除了要瞭解用語的意義外,不需得到任何人的應允。另一派的教條,「對」和「錯」與真理和虛假一樣,屬於觀察和經驗的問題。但雙方同樣接受道德性必須從原理導出;直覺派一如歸因派,強烈肯定道德科學的存在。可是他們甚少嘗試,列出先驗的原理作為學科的前提;更不曾將這些不同的原理化約成一個第一原理,或責任的共同基礎。他們或是推斷道德的日常訓誡為先驗的權威,或是鋪設成為這些準則的共同基礎,但這類通則和準則本身從未被廣泛的接受,以致沒有明顯的權威性。如要支持他們的主張,必須或是在所有道德(德性)的根基上有某種基本原理或法則,或是當有許多原理時,理應有一個確定的優先援用次序;且這個原理,或不同原理間有所衝突時,產生決定作用的規範,必須是不證自明的。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