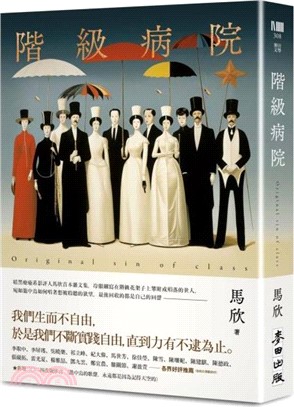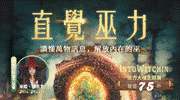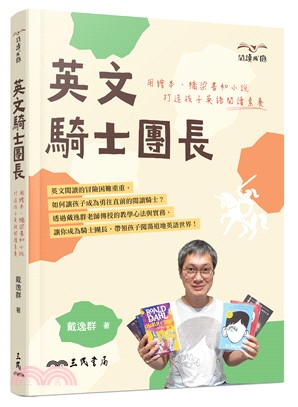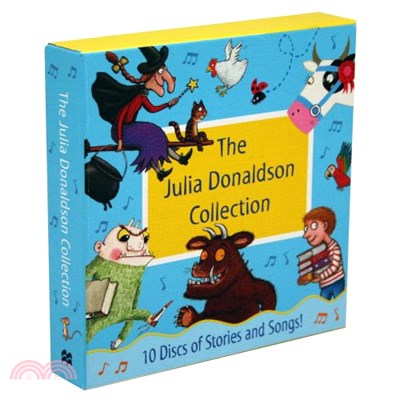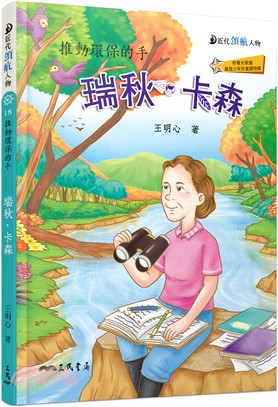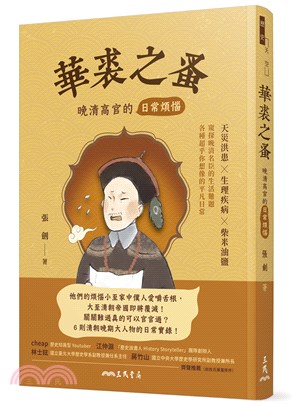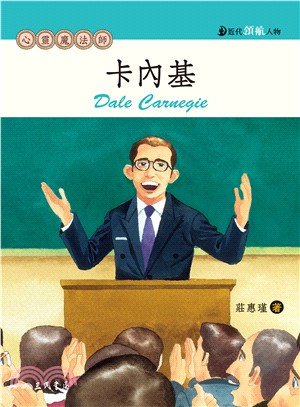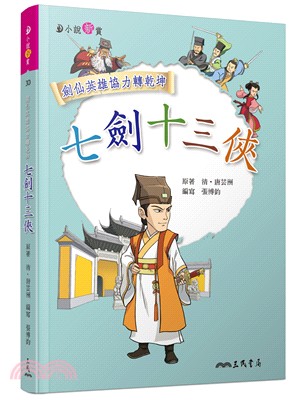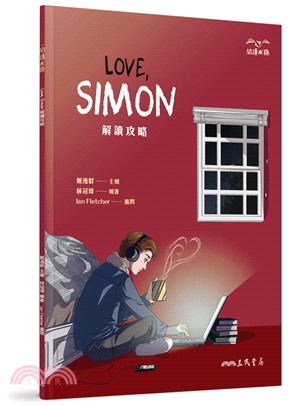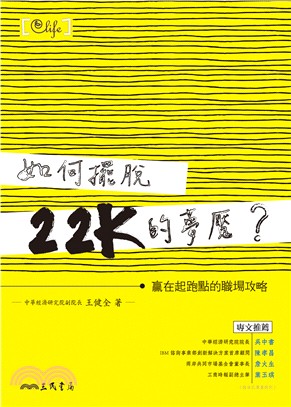階級病院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階級這框架益發堅實,甚至它已成為一個巨大城牆的存在。」
暗黑療癒系影評人馬欣首本雜文集,
細寫宛如籠中鳥的世人,
如何唱著想被聆聽的欲望,最後回收的都是自己的回聲。
李取中、李屏瑤、祁立峰、紀大偉、馬世芳、徐佳瑩、陳雪、陳珊妮、陳建騏、陳德政、張硯拓、雷光夏、楊雅喆、鄧九雲、鄭宜農、膝關節、謝盈萱──各界好評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序)
★ 新增二○二四改版自序〈籠中鳥的歌聲,永遠都是因為記得天空的〉
「《階級病院》剛問世是在二○一八年,短短五年多的時間,階級的更動就如水泥磚塊也像飛沙走石。人們跟著大趨勢啟程,但同時又想另闢密室。
金字塔上方的仍不動如山,但下方因中產階級的逐漸失勢與消失,這世界有了鴻溝之感。彷彿陡然出現了一大海峽或險峻的斷崖,兩邊的人遙遙相望,中產所依賴的或他們所熟悉的價值觀都逐漸塌陷了,掉入時間這湍急的河流之中,感受上是今非昔比,但你放眼望去,它們早就已經遠去。
九○年代以來的紅舞鞋不斷上發條魔法就鏽蝕掉了,但多巴胺仍然在整個社會散發著它加強的餘威,人們開始知道窮忙不代表能上位,只是在鍊條帶上保持著『行進』的假象,但躺平的宣告又是集體焦慮的總和。我們終於整體成為一個發條快鬆脫掉,但仍想模擬著群體樣貌的舞影者。」
——馬欣
步入被AI浸蝕,網絡社群如海妖歌吟欲望的階級病院,
人們一邊昂頭期許聚光燈青睞,
一邊將自我禁錮於嘈嘈絮語羅織的牢籠。
周旋在各式咒罵、效仿、掙扎與傷痕之間,
究竟是掙脫了階級框架,還是僅成了往復迴旋的獨舞?
當貧富看似雞犬相聞,然而咫尺天涯。人們在階級的花架子不斷上演攀附和殞落的戲碼,在充滿寓言的世界中獵奇,各色荒誕新聞映入瞳膜,自紛繁感官直入內心。身處被資本支配及這群魔狂舞的現世,「自由」成了看似唾手可得、實則遙遠的想望。
「我們生而不自由,於是我們不斷實踐自由,直到力有不逮為止。」
作為馬欣第一本深度解剖自我、洞穿社會的雜文專著,《階級病院》戳破隱埋於家族、校園、性別與社會的病態實況。回望成長以來走過的階級之路,透過頹靡妖異的破格筆觸,集結生命書寫、時論、深度書評與影評,完整俱現當代階級眾生相。
同樣一只歪掉的蝴蝶結,老師對窮女孩不耐說道「又是妳」,
換了個家境好的,卻是呵護至極,硬要調整至完美狀態。
同一輛校車駛過破落家屋與華美洋房,
女孩們一個個上車下車,小小心眼遂在車中蔓延開來……
輪到家族間的權衡角力,誰上了位咬住權勢,誰下了戲隱身離場,
她記下長輩打破男女階級往上爬,又再度被階級撂倒的身影。
而當同志情感在當代顯影,最大的拒斥來自父權社會的無法想像,種種藉口只是擦脂抹粉。
寫到從階級突圍的那些人,她深刻描繪香港風華,
記住了張國榮、梅艷芳不合時宜,卻如此絕美的凝眸身姿;
跟著椎名林檎妖魅歌吟,解開咒語、嗤咬掉文明,
讓心中爛泥滔滔湧出,原來我們皆有不振作的自由……
本書分作四輯:輯一「流冰上的童年:關於家的階級暗湧」書寫作者成長經驗、家族變遷中所經歷的階級樣貌;輯二「撕不掉的另類魔咒:身體與性別的階級戰爭」探討性別自主、同性戀情,以及女性面對自我身體與社會期待的多重困境;輯三「我們真的面對霸凌了嗎:階級下的人性之惡」深刻描繪強勢與弱勢,階級內的種種欺壓,以及人們面對自身夢想的無力;輯四「貧脊中各自妖異:試圖衝破階級的那些人」則透過張國榮、椎名林檎、是枝欲和等人物描寫,於階級藩籬之外尋找自由的可能;輯五「黑暗前的殘響:文字與影像的階級展演」透過作者觀影、閱讀經驗,分享種種生命思辨。馬欣華麗又蒼涼的筆觸,試圖鑽探階級、翻轉階級;丟下一個個你我無法迴避的永恆命題。步步為營的人生就怕自階級骨架跌落,而我們該如何生存?又如何拾回碎散的靈魂?
作者簡介
馬欣
同時是音樂迷與電影癡,其實背後動機為嗜讀人性。在娛樂線擔任採訪與編輯工作二十多年,持續觀察電影與音樂,近年轉為自由文字工作者,從事專欄文字的筆耕。曾任金曲獎流行類評審、金鐘獎評審、金馬獎評審、金音獎評審、中國時報娛樂周報十大國語流行專輯評審、海洋音樂祭評審、AMP音樂推動者大獎評審。樂評、影評與散文書寫散見於各網路、報章刊物,如:《中國時報》娛樂周報、《聯合報》、《GQ》、「博客來OKAPI」、「非常木蘭」、「書評書目」等,並曾於鏡好聽平台開設Podcast《馬欣的療癒暗房》,現主持Podcast《人間好失格》。著有影評集《反派的力量》、《當代寂寞考》、《長夜之光》;雜文集《階級病院》、《邊緣人手記》、《看似很美,其實是壞掉的》。
相關著作:《階級病院》《階級病院(限量獨家包裝版)》《階級病院(限量題字親簽珍藏版)》
名人/編輯推薦
◎ 名人推薦語:
「尼采言『當你長久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但當那深淵的黑如同白晝般的光亮,抑或那沉化作空氣般的吞吐時,身處在這世界中的我們,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在凝視著深淵?於是馬欣透過文字讓深淵來凝視你,同時提醒著我們,這句話的前半是『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
──李取中(《大誌雜誌》、《The Affairs 編集者》總編輯)
她以文字修出一頂頂娉婷樹蔭,在這個正能量高掛的當今,讀者於是動心了, 到底要繼續給明亮地曬,還是縮進一種黑暗,不再想做英雄,而能如同《四重奏》 的角色般──幸福地卑微著。
《階級病院》篇篇均為作者沒有藏招的洪荒之作,堂堂有精選輯之姿,慎重推薦給各位喜愛馬欣、喜愛觀影,以及喜愛深刻思考之人。
——吳曉樂(作家)
「我是看了馬欣影評才知道她這個作家,邊看邊想這何止影評,更像質地純粹、體貼人心的散文,如今才有幸讀到她的《階級病院》。馬欣的文字有種獨特聲腔,淡淡說出極愛極痛,熾熱轇轕的光景。就像她的『流冰』意象。冽冽冷冷、底下卻是鮮烈熱情。每個人都是一座浮島,都像一塊流冰,沒法溶解成海水,也回不去原本的冰層。魑魅搏人,世情消磨,只能這麼漂流下去。」
──祁立峰(作家)
「馬欣說話的聲音很細,臉上總掛著『外頭處處是陷阱所以要小心!』溫室花朵的表情,不像讀她文章時,字裡行間盡是豁出去的篤定。在我心目中她是輛在文字裡衝撞的跑車,零到一百之間的距離緊密到已經分不清是靜止還是疾行、是黑是白、是淡然、還是悲傷,只看到整本……一頁頁的煞車痕,情感濃度之高,觸目驚心。
從《階級病院》,看見她心中如履薄冰的世界原來不只有腳下踩著的天寒地凍,更多的是胸懷裡無限滿載的細膩情意,輻射般投向人心的能量太熱太重,釀造著時事以及專屬於自己的史詩。這杯美酒,我喝得過癮!」
──徐佳瑩(創作歌手)
「我一直是馬欣的讀者,她自在出入於各種寫作題材的功力,總是教我敬佩,而且,她是一位這麼知道節制的,把自己的ego掩藏在文脈中的書寫者。《階級病院》所收集的文章,是馬欣多年來第一次比較明確地談到自己,她在回憶的暗室裡,反覆沖洗出一個早熟少女的身影。
保守的教會女中、餐桌旁的家族角力,她像《海灘的一天》裡那個離家前的女孩,隔著一塊毛玻璃,觀察著、窺視著,也丈量著那病態的校園戰場,以及偽善的大人世界。當時站在玻璃後面張著冷靜的眼,覺得自己『不成形狀』的女孩,正是後來我們知曉的,作家馬欣的原型。」
——陳德政(作家)
「多年來閱讀馬欣的文字,總感覺她的寫字桌旁有一扇小門,裡面藏著各種幽魂與哀傷,不時會衝出來在紙上留下字跡。那是被她封印的,關於世界的真相吧!所以這一回,我真高興看到她終於打開門,直接走進去了。關於幸福的空缺,性別的面具,霸凌者的模糊臉孔,甚至體制的沉默殺人,看她直面這一切,過癮又心疼,又隱約知道:這才是讓她覺得安適的地方。雖然名之為病院,亦即是各種苦痛、異常聚集的地方,但傷口就是要通風,才能夠好好地結痂,乾燥,風化。走完這一遭,她是不是好些了呢?
至少身為讀者的我,真的覺得強壯一些些了。」
──張硯拓(影評人、釀電影主編)
「童年終於摘下了它歡愉的面具,那些當你還未意識到之前即已發生的階級傾斜。所有的孩童都必須奮力生長,或選擇性遺忘。一直到某個年紀之後,馬欣重新喚起了它們。恍然大悟之後你明白:原來在那麼幼小艱困的時光裡,如果曾擁有一本書,或僅僅是一個人的理解,那是多麽幸運,也是少數可以在幽暗中保護自己的事。謝謝馬欣。」
──雷光夏(音樂創作者)
「馬欣說過,每個人的天堂或許就是對別人的一點善意。宇宙萬物都是共生並存的,有了天堂的人肯定走過了地獄,而每個人的地獄都不一樣。我一直好奇馬欣經過什麼樣的地獄,讓她的筆鋒像手術刀。劃開皮膚,不需麻醉也不會疼痛,你立刻看清裡面潰爛壞死的組織細胞,還來不及哭喊她已幫你輕輕關上傷口,像魔術一樣。告訴你,沒關係,知道就好。請充滿善意吧。」
──鄧九雲(演員、作家)
「即使世代更迭,在各種思想上除舊佈新,『階級』確實依然存在於空氣與血液,只是後天上多了更多改變位階的可能。像馬欣這樣去抽絲剝繭世界每一角落階級之痕的人,實在是非常勇敢。畢竟,憤怒悲傷都是赤裸,而階級裡的眼光,即使邪惡了也鮮少自知。於是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或許讀者們都被迫檢視了自身也不一定。最後可能沒有誰特別清高,但如果能發現自己內心掩藏的情感比想像中不孤獨一些,那其實挺好的。」
──鄭宜農(創作歌手)
「馬欣老師的文字,像是捨生取義的烈士,像是照見啟示的先知,在你試圖放棄,準備把自己塞進妥協的舒適圈裡,她總有辦法點醒我們這些不合期待的怪胎女孩們,然後靈魂能再次被啟動、被覺醒。」
──謝盈萱(演員)
序
【新版自序】
籠中鳥的歌聲,永遠都是因為記得天空的
《階級病院》剛問世是在二○一八年,短短五年多的時間,階級的更動就如水泥磚塊也像飛沙走石。人們跟著大趨勢啟程,但同時又想另闢密室。
金字塔上方的仍不動如山,但下方因中產階級的逐漸失勢與消失,這世界有了鴻溝之感。彷彿陡然出現了一大海峽或險峻的斷崖,兩邊的人遙遙相望,中產所依賴的或他們所熟悉的價值觀都逐漸塌陷了,掉入時間這湍急的河流之中,感受上是今非昔比,但你放眼望去,它們早就已經遠去。
九○年代以來的紅舞鞋不斷上發條魔法就鏽蝕掉了,但多巴胺仍然在整個社會散發著它加強的餘威,人們開始知道窮忙不代表能上位,只是在鍊條帶上保持著「行進」的假象,但躺平的宣告又是集體焦慮的總和。我們終於整體成為一個發條快鬆脫掉,但仍想模擬著群體樣貌的舞影者。
階級這框架益發堅實,甚至它已成為一個巨大城牆的存在。中產階級雖然沒多好,但它原本投影出的是個階梯,但今日階梯被移走了一般,除非各自鑽洞擠縫,去窺視遠方富裕的城池,不然「階級」像是一大片坡地了,我們所能看到的真正富裕者,是聳立在「遙遠王國」的意象之中。
這在諾蘭執導的《黑暗騎士》裡小丑的悲憤與它的崛起就可以嗅出了未來的氣味,小丑身為影史上最知名的反派,不只是因角色寫得好也被演得好,而是他一舉一動都如舞者,跳出浮誇也跳出了決裂。不只是角色,更是告別集體瘋魔的崩潰者,以一種狂歡的姿態笑著人們活進了進步的假象與召喚(我們始終都在趕路,好像文明真有路標或帶路人),最後都被關進了以「方便」為名的金絲雀籠子之中,也如雀鳥一般,我們每日對著社群塗鴉牆啾啾叫個沒停,彷彿可以真被聆聽。
但當上千萬的籠中鳥一起啾鳴時,我們只是唱著想被聆聽的欲望,最後回收的都是自己的回聲。然而光是這樣就浪費了我們大量的人生與精神,於是我們精神上開始感到困乏,好不容易緩一緩,那些愈聚愈多的海妖仍哼唱著無完沒了的欲望之歌,你我幾乎無法認養出哪一個才是真的自己的欲望。於是水手愈來愈少,海妖再則滿滿地成為了「海的本身」。
在海上燈塔的光沒照射過來時,你幾乎以為自己是獨自在海中央,是那樣寂寞,然又是這樣的擁擠。
二十世紀的幾個崛起的傳奇巨富,創造了近乎國家統治者的格局與資源,他們已經不是八○年代製造肥皂與沙拉脫的巨商格局,而是幾乎創造了人類新的領土、養分、感官上的飽與飢等的雲端世界,那裡有人一旦無法入境或不嫻熟於新世界的規矩,在現實中的他也將岌岌可危,因為大家的眼目都跟著指尖流動,無暇看到現實中的你是如何。
這階級遊戲終於玩到影子大於個人了,世界如同投影的牆,你讓帳號安居其中,牆上人影綽綽,現實中的自己則矮小而萎縮。我們依賴著自己的夢,讓它代你發聲,如同上癮了一般,這樣以堂而皇之活在夢裡的「微型世界」,是商人統治的夢土。你我的欲望每日被餵食,藉由浮動的數字上上下下,你我的注意力始終在他方—好像冉冉上升的天燈之中。
於是我們無暇他顧了,商人或狂人政治都好,我們一起演奏與跳著狂歡的節奏,無論是咒罵他人、公審了誰,或是喜歡了誰,我們都被載到了無休的狂歡之船中,與眾人合舞時只能留神於自己的舞姿,像個他人眼神都是自己鏡子的舞者,我們成了自己的黑天鵝與白天鵝,喜歡與自厭都以分鐘來計時。
沒人公告這樣的「烏托邦」早已經來臨,也無人公告階級從我們想像的框架與掙扎的樣貌後,早已變成了一平坦的高原,年長的問年輕的人:「為何要躺平呢?」,而自己抬頭也發現前所未有的中年危機。
其實說白了,所謂貧富差距不只是指數而已,而是貧是一個系統;富是另一國度,又恍恍然回到了另一種作家雨果的語境,貧富看似雞犬相聞,然而咫尺天涯。我們回到了充滿寓言的世界,於是每天的新聞才會如此獵奇。
這樣的世界是許多經濟專家早已預言的,但在八年級以上的人仍可感覺到「精神原鄉的座標」不斷挪移,好像座標原本就立於流沙之上。在今日,或許很多人都有似夢非夢之感,每個人都拿著自己的那個夢氣球(或可以說是同溫層),行走在現世之中,好像都盡力溝通了,卻又像是跟整個世界隔水傳話。
新的時代翻篇了,我還記得三年前(疫情前)的我,那時世道的安穩雖像是已溫的洗澡水,但仍能抱著僥倖的心情。但後來所有牌桌上的遊戲規則都改了,大家被催促快啟程去新的時代,那裡有AI點亮的聖火,許諾你我更文明的未來,然往往一覺醒來,又發現網路像極當年美國大西部的拓荒年代,有著野蠻的網暴正進行著原始的狩獵,對陌生人做著週期性的「人格謀殺」,爪子仍有祖先傳承的鋒利,一人一爪地讓網路熱熱鬧鬧,也讓它相通於沉寂的暗海之中。
我們愈通天地飆升,就愈驚動了深處壓制的靈魂與哭聲。
寫到這裡,人們會覺得悲觀嗎?好像也不然,我們活在後資本寫好遊戲規則的世界裡,活得如金絲雀,這是包括漢娜鄂蘭等人預言過的事,但這時我們才真正可以去思考個人的自由是什麼?九○年代人人有機會的咒語不再,有人說多巴胺上癮的短影片讓人無法安睡,原來「自由」是在世界逐漸地石化後,自己必須思考的事,不等同於「財富自由」,而是個人如何每一步、每一天與讀這篇文的當下,你與我一起感受或想著這世界為何會走到這樣的一步,因而想通了這就是活著最大的禮物:我們生而不自由,於是我們不斷實踐自由,直到力有不逮為止。
我相信,籠中鳥的歌聲,永遠都因為牠記得天空的。
書摘/試閱
【數位盛世下的動物感傷】
「我不像你們這一代,我們連悲傷都找不到理由,怕一碰就到底了,很蒼白的悲傷。」
這個年輕創作人喝完酒後,說出了很像是日劇《只有我不在的城市裡》第一集主角被編輯退稿的台詞,「我害怕深究自己,也害怕去確認自己的一無所有。」但我看著這創作人的側臉,我是信的。沒有正當理由的悲傷,的確像霧一樣緩緩落在我看到的新世界中。
看起來極度富裕,又極度敗落的世界濃妝豔抹。每個人頻寬開最大,每個人可同時擁有三個螢幕、五光十色的人聲流動,人們開始炫耀或仿製那些情緒,在麻木之前,有點沾沾自喜的悲傷晾曬出自戀的氣味。各自表述的時代,每個人每天登台一次,在沒有人的小劇場裡。
所有的情緒在它登場前,就被預演過了,一如這幾年像被鼓勵出現的大量沒有演技的演員,我們需要他們的表情符號來演戲。
我們兩個世代情況不同,但我們都打開新世界的門,迎接我們的就是無所不在的擁抱。各種空虛的華麗,像野火燎原般燒著各種可以再生的華麗。我們踩了一地的空泛,彷彿輾過橘子與香蕉皮的聲音與氣味,有著肉色的洩憤。
我跟那位創作人說:「我們這一代像被推進一個新的舞場,不合時宜的跟著新招數比手畫腳,而你們好像原生在那裡,但那裡是個都被人工調節好的溫室。」
空虛來的時候,它會先給你滿滿的擁抱、塡滿你眼目所及之處想要的東西,直到人們開始不想要與懶得選擇時,它為你演算好一切,空虛就吃掉了這世界,
這是我們在《猜火車》年代奔跑時,隱隱不確定的遠方;也在我們還在看《鬥陣俱樂部》時,彼此揮以老拳,看著那星星點點的血,仍無法預知的一切。但我們悲傷的預感靈驗了,所有未來的「成功」,它只是很像成功,所有未來的失敗,卻都是眞的。「成功」的貼紙摳不掉,只能摳掉點黏屑,裡面可以投射出馬雲、祖克伯的頭像,在新的國度開疆闢土的西部荒野戰士,應許了新的理想國,開發了新的烏托邦,將實在世界的東西,複製在我們彈指之間。
一切以空虛為名的建設,因為滿足不了的上癮,它成為一個更精密的烏托邦, 所有讓人更便利的,都讓時間失去了實在感。人生可以讀成壓縮檔,或是被人已讀不回的擱置。
時間看似如此大把,在彈指間灰飛煙滅。未來誰說明得了人生的重量,於是它連老都不允許,老本身就不符合這世上整形過的輕快與靑春。相信自己親眼所見的人,是幸福的被催眠者,我們正以虛假空轉生命本身,科技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它改寫了人對眞假的評斷。
二○○八年《黑暗騎士》風雲一時的小丑,這魅影到二○一八年差不多已經過去了。因為溫水煮靑蛙大致上已經完成,我們失去了嘲笑能力,每一種嘲笑都帶著絕望前的哭泣。
但我們睡了,深深淺淺的,睡在被演算好的節奏裡,夢裡我們很年輕,我們比起科技的演算,該死的永遠年輕,疲倦的必須年輕。在沒有出口處,打開求生門,進入另一道前往求生門的地方,光是這樣的過程,我們的「靑春」就像熱帶氣旋不斷滯留在上空,雨要下不下的充滿水氣,我們人生面臨球賽的殘壘,「靑春」尷尬地在開機狀態,任誰都是充不飽的電池。
這讓「老」被壓縮到形同死亡的降臨,非常不慈悲地翻飛單薄起舞的人生。沒有人比得上新世界的「靑春」價値。它因炒作待價而沽,你只能追上它,與它為伍而已,人類第一次迎來一個「靑春」不朽的年代,它是絕對至高無上的商業價値。
少人提,但一定有人知道。《1984》的老大哥已來了,它不是以國度或威權統治者之姿,而是經由所有的消費行為來形塑與觀察個人,並且以消費行為來定義「成功」這個被虛擬的符號,它裡面被塞滿了各種勸敗的消費行為,同時以消費的無止盡加深失敗的存在感。
一切都在你伸手就可支付的動作中,你變得無法想像這世上金錢的累積與消失,它變成一個難以掌握的神祇。在神祇之下,成功者只是祭司,沒有榮耀這個東西,只能賺取別人的羨慕集點。
因此李滄東執導的《燃燒烈愛》雖然不是最好的作品,但裡面提到的「不要想著這裡有橘子,而是要忘記這裡沒橘子。」忘記成功價値已不存在,忘記個人的獨特性可以被取代,像日劇《火花》裡,只要抓住那幾秒的火花,那是個人追求的可貴存在,已經跟群體被設定的「價値」沒有關係。像韓劇《我的大叔》裡的大叔們,所有成功的程序都做到了,但過程中只會愈發提醒你這是空虛的本身。
忘記這裡沒有成功,只有一再重啟的「靑春」。我們迎來這空前華麗的盛世,只是這養分是來自於人類集體空前的荒涼,我們從沒像今日如此被綁成一束束,分子化的被丟置在洪流裡。
它讓我們的生活也變得空前輕盈,因為沒有價値可以衡量自己的獨特,這輕得像霧,沒有感覺,緩緩飄落,置身久了也可以開心地生活,但落後個幾步,你就可以看到霧更濃了。
跟我講話的那創作靑年衣著很潮,衣食住行都不缺,但他說的話語中並非帶著時興的自戀而產生的悲傷,而是這裡與當下都空泛的裡外,我們的輸送帶被餵得飽飽的,這樣被荒蕪了的靑春概念。
當然,我已是上一輩人的悲傷,我們這一代或許有很多烈士型的人為我們訴說。如小說《阿拉斯加之死》想逃避物質世界的主人翁、《猜火車》主角們還在有氣無力地奔跑著,如楊德昌的《一一》的少年背影、古谷實漫畫的廢柴主角。我們小時候有《四百擊》的那男孩陪我們跑到世界盡頭的海邊,我們好像有很多人可以幫我們說些什麼,甚至包括被人當成殘酷又浪漫的代表 Kurt Cobain,控訴著我們即將面對的買空賣空。
即使這樣哭笑不得,我們還是迎來了這樣的時代。
在綿延重複的時間軸上,値得一朵花盛開的時間。我們一開始就無限延長的凋零靑春,知道了這個,即使嘲笑了也是笑,値得你大力笑出聲,笑出像一個人類的回憶。靈魂逐漸遠離,往反方向奔跑的我們,迎向另一次重新啟動前的淨空模式。
【雖然可恥,但卻那麼有用——寫給那些曾被霸凌的人】
在人群中,我微微冒汗著,我們都一列一列排在樓梯口,像動物頻道裡大遷徙的牛犢即將要衝破柵欄,每人一身藍色素服,遠方有蒸便當的鹹膩味。我們照例說應該是清爽、乾淨,遠看像會散發著如同蒼翠平原的氣味吧?沒有,今日是動物的莽原,被窗口陽光曬著炙辣。
我在人群中,看起來穿得一樣,但又怕被識破的一個符號,一點點恥辱感不斷流洩出來,像是有一條粉紅色的絲巾,摸起來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緻緞面,正從我各個內心隙縫中一點點被抽出來。一團團豔粉色,像個胎衣,淌著汁,抽不斷地在我體內流洩出來,可恥感如此滑膩而確實,尤其在豔陽注視下,有種微微的嘔吐感。
身為一個被霸凌者,永遠覺得可恥的是自己。
我們那時正要去參加朝會,老師嚴厲叮囑我們的儀容,好像遠方正有戰場要我們去逐鹿,但心情因那些口號卻軟爛成一團。愈打愈不成器的軟爛在我心中發酵,朝氣是奔向自由,而非奔向層層疊疊的制度,那大概只有我這樣想。每次有校園的陽光掃入,我就像被轟炸過的草原一般,將一滴草上露蒸發殆盡地這樣想著,怎麼可能有像我這樣一點朝氣都沒有的學生啊。
我想在那裡權充成一個數字,在這三年為限的時間裡。但我的身體不聽話,我的身體無法混淆視聽。某一日,當朝會的鈴響起時,斜後方的幾個同學講起對我照例的閒語,「那麼高的個子,球打得卻很爛。」「她四肢好像不太協調,走路很奇怪。」「那頭自然捲亂成那樣,為何排在最前面?」
我的腳步突然在那一瞬間無法快速下樓,我忘記了左右腳的順序般,極端笨拙地一層層走著。無論如何冒汗,同時狠狠地斥責自己,我的下半身就是無法聽從我的意志,後面的同學都被堵住了,我遺落了我身體的存在,在一個應該朝氣蓬勃的朝會現場。
之後的一週都是如此,即使臉頰熱紅到發痛,我也無法順利下樓,只能一腳一腳的對齊,像摺疊毛巾一樣處理自己的存在。充滿恥辱感的下樓方式,那一週的每一天早晨都是迎接恥辱的來臨。我在各種整齊,需要對準的一致化場合,就會出現了各種歪扭與失控,無法成為一個號碼的深切恥辱感,是從小一開始。
之前某一篇提到因交通車的巡禮,而發現誰的家境如何,我是其中之一的顯眼。七歲前我住二樓洋房,雖然後來被迫遷離,但第一次上交通車時仍太過顯眼,兩三個同學的交頭接耳與投射過來赤裸眼神,內心就感不妙。那幾乎是喚醒我前世原來是賽倫蓋提大草原上身為一隻蹬羚的直覺,知道被在草叢裡的動物盯上了,雖看不到那動物的眼神,但那如火光的熱切,你知道狩獵的氣味正在蔓延。
從那時開始知道人還沒有披起禮教那身外套前,童年野生的各種情感原來是這般肆意流洩出來,滾滾滔滔的百無禁忌。那是如亞馬遜叢林般的破形怪狀與鮮豔叢生,是多麼吸引人,我身為一個被狩獵者,竟幾乎好奇了那在規矩下流出來的是什麼樣的腥氣。因此當它包在一個過度刻板的制服下時,我更覺得後來即將撲將出來的,是早已逮住我的惡爪,或是我自己原本厭惡的斑斑點點被刮出痕跡。
屬於受害者才有的氣味,是否被我帶進校園裡了呢?我那時曾這樣想。
我那團爛泥一樣的粉紅自尊,如大腸小腸般散亂在四周,被拉得七七八八的。如今想來是電影《發條橘子》裡的某種景貌,一切秩序下的瘋狂,被我窺見了,我這雙愛窺伺的眼啊。同學同時發現我臉上有個寶島形的胎記,在左眼下不大不小的一塊,讓我在交通車巡禮之後,有了更易被捕獲的記號。起先是三兩同學的挑釁,之後某天步下交通車時,前面的同學突然跌跤,剛好是那三位同學之一,於是我被老師誤會有推同學下車的惡意,一被公開斥責,解釋的語言再也不成句。
接下來,全班都沒人跟我說話了,在我窺伺自己將發生的一切同時,忍不住又做了一個實驗。我與之前相熟的同學講話,果然被遞了一張紙條:「我不能跟妳說話」,我在推演更多可能的同時,讓自己成為一個殘酷的觀眾,這一切就不致太難堪。
但當然難堪,被誰踩了的啪吱一聲,原來是心的顏色,鼓鼓的發脹。橘紅色、粉紅色的,那些唯一可以被允許放入井然校園裡的彩物,都流出膿汁,張牙舞爪的動物園風景,秩序下能獵捕人的訊號。
於是我有個防空洞收得緊,在那歲數是沒處可逃的。你開始有一個樓梯通往潛意識,那裡像間地下室,學習寫字寫成句,是挖地洞的逃啊,把家裡書架上可以看懂的書都拿來啃食啊,像餓死鬼一樣吃,是搭了天梯往上爬。小學三年級時,當我以為早已忘記一年級時的遭遇,我讀著沙林傑的文字,也像在戰場上歸來一樣,哭啊哭的,只管往上建、往下逃的忙。
只有書裡的那些人,讓我每日在那非洲大莽原、在亞馬遜叢林中,除了野生奔騰外,看到了有光影搖曳,有人在堡裡駐守。雖然怎麼走都還有一段距離,但總還是喊著「等我啊!」的嘶喊,逃過秩序中的至髒至亂,從此我不信整潔、不盼陽光在眾人口中的紛紛和煦。
曾像快要噎死一樣吃了《蒼蠅王》的字句,但對自認看起來一定狼狽又可恥的我,卻是有用的。後來某日,我看著那權衡著我家人與校長關係而不敢打我的老師,她做得埋怨且明顯,我聽著班上的閒言閒語,輕聲地命令老師打我吧,我還在賽倫蓋提草原上,知道草叢後的動靜,知道他們在等待總有更弱的外圍,只是再也沒有恥感。
學校這注定野蠻的地方,成為回憶後,不是曝曬就是清冷。我至今仍有一個自己在逃著,逃到那個自備的防空洞裡,打開書頁,急忙跳水一樣的逃進去,像溺水一樣哭著漂流,在那裡掏洗出泥沙中的碎鑽,是我信的人性中的一點光,帶它回到這走不穩的扶搖世界。曾自認這樣可恥的自己,懷著一點借來的清火,吃著大把如薪柴的字,我要這樣亮亮的,抵抗在晝日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