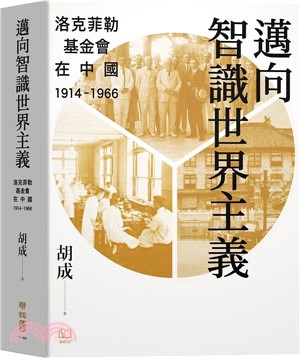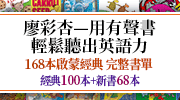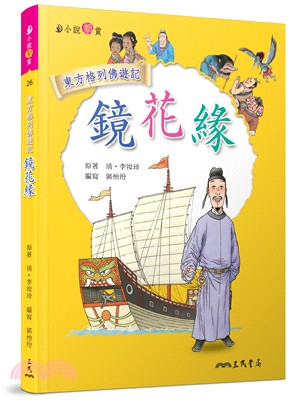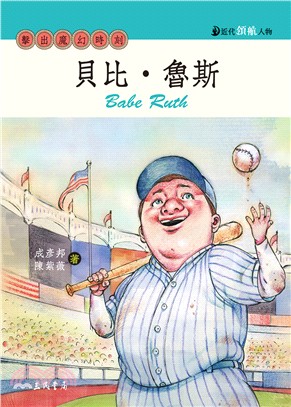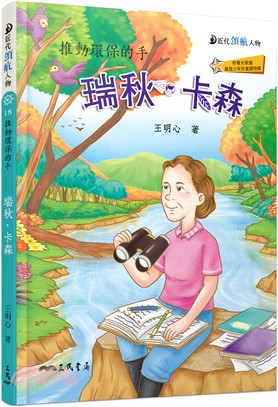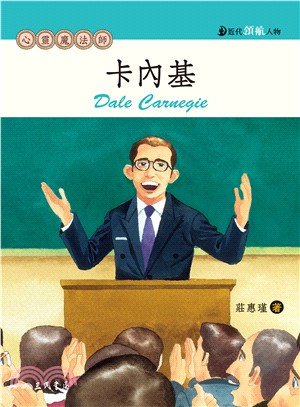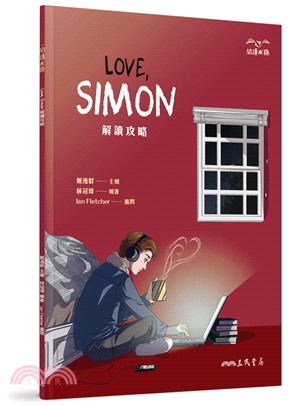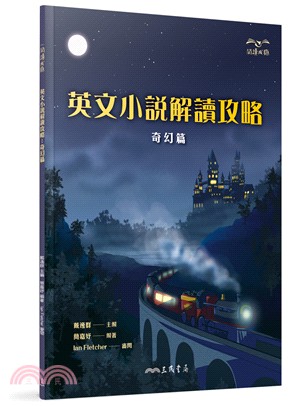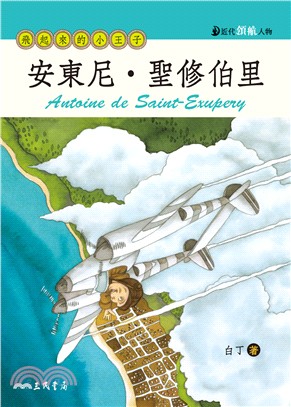商品簡介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接受美國國務院對華關係處的邀請,先後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與基金會有密切接觸,他回國後寫下了《初訪美國》一書,提出了中美兩國「能否擁有一個共同的光明」的議題。
《邁向智識世界主義》就此聚焦了洛克菲勒基金會進入中國之後所推進的慈善醫學教育事務,認為正是通過「中」、「外」參與者們的齊心協力,矢志追求和維護最高專業標準、個人尊嚴及學術自由,方能將基金會鼓吹的「在世界造福全人類」的高理想落實。正如「人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人類的攜手合作並非遙不可及,也不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好夢想。
作者簡介
南京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近二十年來關注全球史、跨國史,中美文化交往,以及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在《史林》、《近代史研究》、《漢學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新史學》等刊物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主要著作有《醫療、衛生與世界之中國:一個跨國和跨文化的歷史研究》等。
名人/編輯推薦
吳翎君
本書為迄今為止最完整的有關洛克菲勒基金會在華活動的一本學術專書。作者具悲天憫人的情懷和特殊敏銳之洞見,流暢生動的文采更使本書有別於嚴肅的學術專書;書中所言不僅是一部美國慈善機構在中國的歷史,更寫出一部近代中國人如何參與這一中美交往過程的恩惠、磨難或命運省思,隱微勾勒出「科學無國界」的共同理想。
序
自序
我們應「有一個共同的光明」
尼采於1882年撰寫《快樂的科學》時,正深戀著美麗、聰慧、高雅的俄羅斯貴族女作家莎樂美(Lou Andreas-Salomé, 1861-1937)。倆人情投意合的心靈交往,致使多年來曾讓他痛苦不堪的偏頭痛、胃痙攣得到了暫時的緩解,是其飽受挫折、充滿悲傷的人生中最感愜意的一段時光。然而,在他談及寫作之時,卻說總感到「煩惱和羞愧;但寫作於我又是必不可少的事務」。後來錢鍾書先生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提及這位偉大思想家將母雞下蛋的啼叫和詩人的歌唱相提並論,以論證「寫作都是痛苦使然」。
既然寫作絕非輕鬆愉悅,那麼寫作者為何還欲罷不能、無法放棄呢?作為一個解釋,或在於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如尼采乃為了「重估一切價值」,情感鬱勃於胸中而不得不發也。錢鍾書先生於1939年冬撰寫《談藝錄》時,也說其時戰火連天,生靈塗炭,該書「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至於史學著述,從司馬談、司馬遷的「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到較晚近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稱「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趣之行動」;都可以說但凡偉大學術著述「大抵是聖賢發憤之所作也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本書作者怎敢不時常捫心自問:「是書何以作」。畢竟從1914年至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以下簡稱基金會)在華投入了近五千萬美元,是其向全球九十六個國家或地區,即除美國之外資助最多,且也是中國百年來收到來自單一機構數額最大的慈善捐款。尤其是該會創辦了東亞設備最先進、條件最優渥,最具國際影響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以下簡稱協和);人類有史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一項跨國學術合作與交流。就以往研究來看,華文世界除資中筠先生於1996年刊發的一篇四萬餘字的長文之外,至今還沒有出版過一部由在地、或本土學者撰寫的系統性學術專著。
當然,這些年來就此專題也有若干論文發表,卻都沒有超過萬餘字,大多只能看成是對某一個人、某一件事的片斷性研究。讓人有點扼腕長嘆的,是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是一次性「客串」,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沒有人持續專注於此,抽絲剝繭,順藤摸瓜地做一些更細緻和深入的論述。這就猶如「一瞥驚鴻」,雖有「拾遺補闕」之功,卻最多只是做了一份「添磚加瓦」的工作,就事論事而多未上升至更高思想或精神層面,探尋其在世界歷史上更為長久的文化意義。畢竟,不論對於華文世界,抑或對於英文世界,乃至對於更多的人文學者來說,該研究都涉及到究竟當如何評估此類跨國學術合作—是一個陰謀、一種陷阱;或是一份情懷、一片善意?
就華文世界來看,原因或在於源遠流長的史學傳統,頗多「向內」(inside)的深入開掘;較少「向外」(outside)的廣博探索,一直不太注重在地、本土社會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及互動問題。如司馬遷撰寫的《史記》,資料主要採用漢文典籍,沒有廣泛遊歷周邊地區及毗鄰國家,雖矢志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但其關於周邊族裔的〈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等六篇相關記載,不僅比漢地中原的歷史記述省略了許多(沒有世家、本紀,以及記載天文地理等變遷的「志」等),且還沒有完全擺脫「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那種以華夏為中心的大一統理念。
與之不同,古希臘希羅多德撰寫《歷史》之時,作為商販曾向北到了黑海北岸,向南到達埃及最南端,向東至兩河流域下游一帶,向西抵達義大利半島和西西里島,對希臘周邊的族群和國家進行過細緻的考察。儘管當時希臘人普遍排外—稱外族人為「野蠻人」,但希羅多德則從不人云亦云。甚至在希臘和波斯發生爭戰之時,他雖堅定地站在希臘一邊,卻並不刻意敵視或矮化波斯人。除了如實記述波斯人的勇敢、俠義、誠實,他還稱自己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見聞,都值得欣賞和讚歎—即使在文化確較為落後的賽西亞和利比亞地區,認為也有不少令人神往的美妙傳說。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隨著邊疆危機的不斷加深,魏源等一批經世學派逐漸開始關注漠北及西北的歷史演化,華文世界的在地史、本土史,遂形成了某種「向外」的拓展意識,並有一些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問世。尤其在1906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受該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的委派,前往中亞考察的兩年多時間裡,搜尋到包括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的一批古梵文、印度文、波斯文、回鶻文、粟特文、突闕文書寫的經卷古書,再至1909年9月4日他在北京邀請包括王國維在內的一批頂級文史研究者,到六國飯店觀看自己蒐集到的文獻珍品,現場「人人都為之動容。」
概括說來,作為現代學術意義上「向外」研究的開創者,是王國維、陳垣和陳寅恪諸先生對「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探索。堪稱經典的,是王國維針對伯希和所說吐魯番地下水道受到波斯影響,認為「實則我國古代井渠之法始漢武帝用以引洛水,後之用之敦煌塞外,其發明在通西域之前,後車師等處用之,遂傳之波斯」;還有陳垣先生令人信服地論證出蒙古語的「也裡可溫」,實為「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以及陳寅恪將隋唐史演化路徑精闢地概括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如果要鑽點牛角尖的話,那個年代所謂的「塞外野蠻精悍之血」,同時也意味著蠻族鐵騎所到之處,生靈塗炭、哀鴻遍野,還有「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的血腥另一面;然終其這些大師們的一生,卻沒有一篇文字論及於此,而是更多關注了「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宏大歷史演化,也就是歷史積極和光明的那一面。這就有點像當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眼中的德意志,雖飽受法國路易十四世,以及拿破崙所發動的戰爭之蹂躪,但他在私下裡說:「我並不恨法國人,不過感謝上帝,我們趕走了他們了。對於我這個認為文化和原始風尚都很重要的人,怎麼能仇恨世界上最有素養的國家呢?我自己的許多素養也要歸功於他們呢」。
自十九世紀上半葉以來,專制的普魯士致力於德意志統一,並最終將之打造成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同時期的海涅(Harry Heine, 1797-1856)則擔心隨之興起的極端「愛國主義」,將導致憎恨外國的一切,鼓惑民眾不再想成為歐洲人,自然也不再想成為世界公民,而僅僅想做一個心胸狹窄的德國人。結果進入二十世紀之後的兩次世界大戰,德意志民族為此付出了最為慘痛的代價;以至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於1947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歌德獎(Goethe Prize)頒獎儀式上,痛定思痛地聲稱德國應與歌德為伴,方不再會窮兵黷武,民眾也才可能成為真正德國人和人類的一員。
如果要問歌德何以推崇那個時代的法國文化,關鍵在於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高度的文化教養」,即更多「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而「我們德國人還生活在昨天」。雖則,我們並不能斷定王國維、陳垣和陳寅恪諸先生關注「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是受到了歌德等人的影響;卻可以肯定沒有讀過歌德的魏源早已說過:「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諮風俗、廣鑑地球,是智士之曠識。」倘若往前追溯,更早還有孟子所說的「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的至理名言,即中國文化中似也有這樣類似開放和包容的文化胸襟。
本書正文部分談及在1943年6月—1944年7月期間,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接受美國國務院對華關係處的邀請,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後在芝加哥大學訪問,與基金會有過密切接觸。他回國後寫下了《初訪美國》的隨筆,認為「每一個認真為中國文化求出路的人,說得更狹小一點,每一個認真要在現代世界裡做人的中國人,多少會發生的一個徬徨課題,我們是維持著東方的傳統呢?還是接受一個相當陌生的西方人生態度?」當1945年8月結束了此次訪問,回到雲南後的他又寫道:「若是溝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國際誤會的話,這無疑是我們不應再事延緩的工作了。」
就在最初寫下這些文字時,費先生稱中美兩國的歷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地理環境也不同—其白天是我們的黑夜,其黑夜是我們的白天;其黑暗時代是我們的唐宋文采,其俯視宇內的雄姿是我們屈辱含辛的可憐相;並進而問道:「我們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光明?」就此後的歷史演化來看,費先生絕對算不上「親美」人士,因為在接下來的國共內戰中,他屢次擬文批評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打內戰,逮至1949年解放軍進駐北平,他又是一位積極擁護新政權的「進步」教授。只是在1957年「反右」時,不幸被人落井下石,羅織了一個罪名是「與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夫婦(美國特務)來往很密」。
1980年費先生完全恢復了名譽,赴美一個多月—參加會議、訪問和考察,此前的1979年5月他已經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過美國;故其時撰寫了題為《訪美掠影》的小冊子,對美國社會、制度和文化更沒有多少讚美之詞,談不上有什麼「親美」傾向。1990年在他八十歲生日聚會之時,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構想,雖說可能有更廣泛的意涵,但肯定也試圖回答自己當年提出那個中美「有沒有一個共同的光明」的問題。因為他接下來還說只有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相互寬容,方能「確立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促進天下大同的到來」。
職是之故,面對當下「外來╱本土」、「西方╱中國」、「全球╱在地」之間的極度緊張和對立;費先生的期盼猶如在此至暗時刻透射出來的一束光亮,或能引導我們華文世界涵詠出更多「世界公民」的胸襟和格局—說到底就是要學會理解和尊重遠方之人、陌生之人。畢竟,今天華文世界中的中國大陸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向外」的在地史、本土史仍糾纏於過去,耿耿於懷於百年來我們所遭受的種種屈辱和挫敗,勢必會帶來太多怨恨、猜忌、對抗和毀滅;倘若面對未來,稍微多一點關注近代百年來「向外」發展的開放、交流、融合及匯通,以及近三十年來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那麼就會用感恩之心、包容之心、理解之心和仁愛之心去擁抱這個世界—相信就更可能阻止未來的區域衝突或新的世界大戰之爆發。鑑於此,本書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美美與共」,怎樣「天下大同」?
緒論(節錄)
「在世界造福全人類」
第一節「點燃中國的油燈」
繼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於1931年出版《大地》(The Good Earth)之後,又一部關於中國的小說—《點燃中國的油燈》(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於1933年由美國著名的鮑勃‧斯美林(Bobbs Merrill)出版公司推出,並迅速在英美走紅。小說講述了洛克菲勒旗下的美孚石油(Standard Oil Co. Inc,以下簡稱美孚)如何在華拓展市場,並如何迅速取得成功的故事。翌年,華納大都會製片公司(Warner Bros.╱Cosmopolitan)決定著手拍攝該書的同名電影。一篇中文報導說:此片導演在中國實地考察了近半年,僱傭了多達一千餘人參與拍攝,讓人期待「片中的一切東方景物,均曾經過相當的考據,沒有一處是潦草從事的」。尤其能表明該書在英語世界暢銷,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派往英國的間諜,一度將此書作為拍發情報的密碼,關鍵詞取自發送日對應頁碼的內容。這是因為利用新近出版的流行小說,間諜們可以方便地在目標國的圖書館或書店得到副本,「使他們不必冒著風險帶一本可能會引起懷疑的書過邊境,接受檢查。」
該書作者霍巴特(Alice Tisdale Hobart, 1882-1967)出生於紐約州的洛克波特(Lockport),雖就讀過芝加哥大學,卻沒有畢業而找了份工作。1908年,她首次來到中國,探訪在杭州美國浸禮會(Baptist missionary)創辦的蕙蘭中學(Wayland Academy)任教的姐姐瑪麗(Mary Augusta Nourse, 1880-1971)後就返回美國。1914年,她結識了一位美孚在華高管,婚後來到中國,並一起去了東北,丈夫在外面做銷售,她則在家裡埋頭寫作。兩年後的1916年,她在美國著名文學和評論雜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了首篇講述東北那些每當農忙之際,就在田裡耕作;農閒之時,聚眾呼嘯山林的「馬賊」們生活之劄記,後又將之增補寫成了《滿洲日記》(Manchurian Diary),並撰寫了一部題名為《開拓古老的世界》(Pioneering Where the World is Old, 1917)的小說。在《點燃中國的油燈》出版之前,她於1926年、1928年還出版了另外兩部關於在中國生活的小說,銷路都不錯。
《點燃中國的油燈》的男主人公礦業學院畢業之後,偏逢1908年美國國內的經濟大蕭條,無法找到合適工作,不得已受聘於美孚。經過簡短培訓之後,他被派往中國東北做推銷。其時,日本在遼東半島的南滿、俄國在長春以北的北滿,大力修築鐵路;清朝政府不得不被迫在此地開放了占全國商埠五分之三的商埠,並全面開禁數以百萬計關內農民前來屯墾,東北遂也成為不僅是當時中國,也是東亞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於是就有男主人公與當地合夥人一起,每天乘坐顛簸不堪的馬車,從早到晚,由一個屯墾地到另一個屯墾地去做推銷。一天傍晚,在鄉間簡陋的客棧歇腳,他躺在十多個人擠在一堆的大坑上,強忍臭蟲叮咬,窗外北風呼嘯,忽然想到如果出售煤油時,附送一盞帶有玻璃罩、用鍍錫鐵製成燈碗的油燈,那麼屯墾人家就願意購買煤油。畢竟,東北冬季天黑的早,漫漫長夜,致使美孚很容易進入到鄉村小屋;由此想到中國其時有四億人口,如果每戶點燃一盞燈,那至少也是一個擁有上千萬盞燈的龐大市場。
由於工作出色,男主人公在幾年後被調往長江下游的一個通商口岸負責市場行銷。為了讓每戶中國家庭擁有一盞美孚油燈,他還是那樣不畏勞苦、兢兢業業,依然取得了非凡的銷售業績。當然,他知道這些成功並非完全出自於自己的努力,關鍵在於美孚和華人經理之間的良好合作關係,以及由他們發展出來那個暢通無阻的銷售網路。尤其讓他感到極有成就感的,是經銷商每天報告的銷售數字節節升高,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一天,他吩咐僕人幫助購買一盞舊式燃用花生油的油燈,作為一件古董,以便將來帶回美國讓親友們觀看。幾天後,僕人沮喪地稟告他,說找遍了全城每一個角落,也沒有看到那種油燈,如果想要購買,只能去更遠、更偏僻的鄉下尋找。這就更讓男主人公心潮澎湃,正是自己多年來的辛苦打拼,終於使整座城市沒有那種煙薰火燎的舊式豆油燈了,而是順利進入了一個便捷、高效的美孚新時代!小說就此這樣生動描述道:他坐在轉椅上,雙手放在頭後面,「那一刻,他看上去很年輕,就像當年剛剛抵達中國的那位年輕人一樣。」
男主人公的經歷是美孚在中國市場的成功縮影,其成長速度在那個時代並不多見。1870年1月,美孚石油公司總部在克利夫蘭成立,1880年就擁有了美國全國石油產量的90%。1882年,美孚派出了利比(William Herbert Libby, 1845-1917)前往東亞開拓市場。不論在日本、印度,抑或在中國,利比都是通過大力扶持當地經銷商,廣泛分發介紹美孚油燈的安全、便利性小冊子,再輔以現場展示和購買煤油後,隨即贈送油燈等多種促銷手段,短時間裡獲得了巨大的市場份額。就深入中國社會的程度來看,美孚不僅在通商口岸,且還通過手推車、小舢板而進入了內陸鄉村,銷售網絡遍及各地,無人不知,以至於美孚裝油的鍍錫鐵罐和木箱,成為各地貧苦農民家中最常見的一種裝雜物的容器。統計數據也表明在1882-1891年期間,美孚產品已經占到美國煤油出口的90%,占世界市場銷售額的70%以上,至1900-1910年的十年中,美孚售出的煤油約占中國市場的一半,1910年占有美孚在北美大陸以外售出的15%。
傳統舊式油燈多為粗瓷燈碗所制,沒有燈嘴、燈罩,點燃起來,昏暗蒙晦,且不停地冒著黑煙,甚或迸出火花。還由於夜晚沒有路燈照明,許多城市日落之後一片黑暗,外出通常持手燈內燃以蠟燭,或以油碟注落花生之油,用木棉作心點之,極不方便,故民眾「如水鳥之歸巢,晚歸家屋,至次早清晨即起,出而工作。」最初是1880年代,在上海通商口岸的鋪戶人家,大半使用洋燈,蓋「取其油既便宜,燈光明亮,懸掛一盞,滿室皆明。」 另一份上海周邊的地方性文獻,記載了舊式油燈被逐漸取代的過程,稱先使用火油燈,明亮雖遠勝舊式油燈,然煤灰飛揚,用者厭之;只是到了有玻璃罩後,使用起來光益盛而無煙,「於是上而縉紳之家,下至蓬戶甕牖,莫不樂用洋燈,而舊式之油盞燈淘汰盡矣。」到了二十世紀初,蔣夢麟回憶幼時成長的浙江餘姚鄉村,稱人們出於好奇,購買來自西洋的火柴、時鐘,生活需要則購買美孚煤油。他說因為「煤油燈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這與菜油燈的昏暗燈光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
此時美孚在各地廣泛銷售,如同英美煙草公司的香煙(British-American cigarettes)那樣,成為中國民眾大宗日用消費品,確也極大改變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習慣。1914年,時任美孚副總裁的貝米斯(William Edward Bemis, 1863-1915)在接受訪談時,談及美孚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時,稱以往在天黑較早的冬季,江浙一帶的絲綢業工場通常下午四點收工;然有了價廉物美的美孚油燈後則可勞作到深夜。《點燃中國的油燈》也有這樣的描述,男主公之所以那麼忘我地開拓市場、除追求豐厚的利潤之外,且還有將美國文化,乃至西方文明引入中國的夢想。書中的男主人公希望美孚煤油不僅為工廠女工的夜班提供了照明,且還能讓那些進入現代大學的中國男孩、女孩在美孚油燈下,愜意地閱讀來自西方的書籍,並進而領會「羅素和馬克思的詞句(riding the word of Rousseau and Marx)」。這一想法大致也來自作者姐姐先在杭州的教會學校任教,後積極參與創始金陵女子大學,試圖通過高等教育而推動中國邁入現代社會。
目次
自序:我們應有「一個共同的光明」
致謝
緒論 「在全世界造福人類」
第一節 點燃中國的油燈
第二節 「文化侵略」
第三節 富有成果的合作
第四節 「給予」與「獲取」
第一章 前往中國
第一節 「美國世紀」
第二節 最好的機會
第三節 東方教育考察團
第四節 專注於醫學教育
第五節 兩次訪華考察
第二章 重組協和
第一節 日本影響
第二節 教會醫校
第三節 英語教學
第四節 協商收購
第五節 開辦慶典
第三章 清除鉤蟲病
第一節 先期籌劃
第二節 著手行動
第三節 選定萍鄉
第四節 在地推進
第五節 啟動公共衛生教育
第四章 培養醫學精英
第一節 協和標準
第二節 優渥薪酬
第三節 校園生活
第四節 任職協和
第五節 合作平臺
第六節 理科教學
第五章 經歷革命
第一節 反帝風潮
第二節 政權更迭
第三節 中國董事
第四節 政府註冊
第五節 宗教氛圍
第六節 增加華人雇員
第六章 服務地方社會
第一節 醫院事務
第二節 診療收費
第三節 改善形象
第四節 公眾批評
第五節 訴訟糾紛
第六節 教育部巡視
第七章 鄉村重建
第一節 衛生實驗
第二節 國聯參與
第三節 關注定縣
第四節 應用科學
第五節 「中國項目」
第六節 協和的因應
第八章 支持抗戰
第一節 美日交惡
第二節 戰地救護
第三節 繼續「中國項目」
第四節 關閉協和
第五節 重開護校
第六節 接濟傑出教授
第九章 戰後恢復
第一節 人文學者
第二節 最後一筆捐贈
第三節 勉力維持
第十章 新舊協和
第一節 收歸國有
第二節 思想改造
第三節 新的體制
第四節 重提「舊協和」
結語 「我欲仁,斯仁至矣」
第一節 那段「中」「外」之間的苦澀磨合
第二節 那些參與之人的悲愴命運
第三節 那個「科學無國界」的高尚夢想
後記
中英對照表
參考文獻
索引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前往中國
第一節「美國世紀」
那個時代美國重要的出版巨頭,也被人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普通公民」的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在1941年2月17日《生活》(Life)雜誌的社論中提出了「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的理念。其時,納粹德國、義大利的鐵蹄蹂躪歐洲,日本占領了大半個中國,進而繼續染指法屬印度支那;美國社會充斥著孤立主義情緒,面對咄咄逼人的法西斯極權,大多數人幻想隔岸觀火、袖手旁觀。盧斯憂心忡忡,疾呼作為民主、自由的捍衛者美國,應當積極投入到這場世界大戰之中,幫助正在浴血奮戰的英、中等國。在盧斯看來,美國人先在1919年「巴黎和會」之後,歐洲重建過程中,拒絕了「有史以來前所未有成為世界領導者的機會」,後又因19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帶來的大蕭條,更多關注國內經濟復興,對國際事務漠不關心;他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此時的美國應「全心全意地承擔和利用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最重要國家的職責及機會,以自己認為適當目的及妥善方式,更多地影響這個世界。」
盧斯之所以能夠提出「美國世紀」的構想,與其作為在華傳教士的子女,及在中國成長的早年經歷密切相關。1897年9月,他的雙親由美國長老會派遣,乘船橫越太平洋而抵達上海,接著被派往山東登州(今蓬萊)的教會學校,講授物理學等自然科學課程。他的父親中文名字「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意為「尋求公義,畢生行在正直道路上」,相信更好的世界是要建立在各國人民互相了解,彼此服務的精神之上,故其著眼於興學與宣教並重。在華的三十一年期間裡,路思義最值得稱道的貢獻,是參與創辦了其時中國兩所重要教會大學—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正是成長在這樣一個虔誠和篤信的家庭,盧斯從小意識到一方面中國需要美國推動的現代文明,引入基督教、現代科學、民主制度及美國憲法揭櫫的各種自由理念而獲得拯救;另一方面又認為只有幫助中國步入現代世界,採用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理念,美國的國際地位方能獲得提升和被人認識到,從而成為世界公認的領導者。
作為「美國世紀」的濫觴,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就已經是一些美國人放飛夢想的地方。畢竟,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製造業取代農業而成為了美國社會獲得財富的主要源泉。1900年,美國出口總值中近三分之一是機器製造業的產品,而此時歐陸列強為保護本國市場,對於進口產品課以高稅收或高關稅,從而導致經過美西戰爭而走出孤立的美國,不得不大力開闢拉美、亞洲等不發達國家的市場。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自然受到美國政府和商人的高度關注,成為「門戶開放」意義上最大的理想市場。如《紐約時報》於1901年11月刊發一篇文章,批評了義和團事變期間列強火中取栗的野心,強調不同於旨在劃分勢力範圍,占有中國土地的歐洲列強,美國反對肢解中國,希望保持這個巨大的統一市場。文章作者建議:如果美國能讓中國相信其雄心僅在市場,在中國銷售製成品,並誠實地履行自己的貿易義務,那麼美國就能和中國站在一起,「歐洲看上去也就沒有正當的理由,指望美國對瓜分中國持寬容態度。」
如果以在華銷售最旺的美孚石油為例,似可認為美國產品那時在中國市場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原因在於中國民眾沒有那麼強的購買力。1920年代末,英國每人每年消費石油產品二百二十六公斤,法國每人每年一百六十公斤,德國每人每年五十公斤;中國每人每年則只有兩點五公斤,且其中燈油、燃料、汽油的分別占比是60%、25%、10%,瀝青或塗料油占5%,總量「僅占世界石油產量的0.5%。」原因在於中國民眾太窮,多數家庭用不起來自域外的「洋貨」。有人算過一筆帳,說用美孚煤油照明,一晝夜須銀四角,「若用國產豆油,只需洋一角。」出身於貧寒家庭,後來成為著名漢語語言學家的王力回憶道:當年他家是菜油燈和煤油燈並用,書房用煤油燈,廚房用菜油燈,至於臥室裡用什麼燈,「就看每月的經濟情形而定了」。一份對上海市郊農民購買煤油的調查表明:夏季夜短,人們「大半不用燈火。佃農中有五家,長年不用燈火,在非用不可時,以食用油一燃之耳。一百四十家中平均每家每年需六元。」
說到占領中國市場,當時幾乎所有列強都爭先恐後,無所不用其極。1850年-1890年期間,德國以鐵路建設為中心,效應擴散到了煉鐵、煤炭、機器製造以及眾多的相關產業,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英國的世界第三大工業強國。1898年,德國出兵占領山東,租借膠州灣,並於翌年成立了山東鐵路公司;並迫不及待地籌備修築青島—濟南鐵路,目的在於盡快轉移國內與鐵路相關行業的巨大產能。與其他列強相比,除美孚等極少數日用必要品之外,其他美國貨在華競爭不占優勢。一份統計表明:1911年,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所占比重,僅十分之一。同年在華的外國商人中,美國人不及百分之四。中國繁榮省分,無美國商業之者甚多:如四川一省,其面積相同於德克薩斯,人口相等於德意志,每年輸入外國商品,進口稅付一千四百萬元,貿易機會相等於日本;然美國在該省卻沒有直接商業布局。這份統計稱:此前東北棉布均從美國輸入,然1907年後市場已為日本人所奪,再至1911年的僅三年時間,日本棉布的「銷路已增至百倍矣。」
重要的是,不同於在華其他列強,以基督新教立國的美國除心心念念的中國市場之外,更在於傳播一個試圖用西方文明,或美國文化改造中國的「美國夢」。基於「自由—發展主義」的理念,美國不少重要人物堅信「其他國家可以,且應該複製美國的發展經驗和模式」。這裡或可與英國作一個比較,頗能顯現二者的不同之處。有歷史學家將1815-1914年的這段期間,稱作英國的「帝國世紀」;更能反映此時大英帝國的東方觀,是著名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關於「白人的負擔」的詩篇,即認為殖民方的白人種族,同樣受到被殖民方的其他族群之傷害。他的經典名句是「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遠不會有相遇。」然而,盧斯雖承認東方╱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觀念,卻認為兩者可以聯手而謀求共同發展。他由此呼籲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化民主國家,美國人有義務與所有人分享美國的權利法案、獨立宣言、憲法,及其優質的工業產品和生產技術,且還「必須是一種民有、民治、民享的國際主義。」
相對熱衷於市場的爭奪,傳播「美國夢」更有利於在華「美國世紀」的啟動。這裡比較「基督教青年會」(Yo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Y. M. C. A.)在英、美兩國的不同發展,我們又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該組織最初於1844年由英國商人威廉斯(George Williams, 1821-1905)創建於倫敦,宗旨是改善青年店員的精神生活。1851年一些美國年輕人來到倫敦參加世界博覽會而受影響,回國後隨即創建了美國基督教青年會。接著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二十二個城市青年會的代表在布法羅聯合成立了北美協會,並推動來自大西洋兩岸九個國家的近一百名青年會代表齊聚法國巴黎,宣告成立「基督教青年會世界協會」。與此同時,風靡北美大學校園的「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如火如荼,提出的口號是「讓這一代人的世界基督教化」。作為積極的踐行者,隨後就讀於耶魯大學的盧斯父親路思義,擔任校園刊物《舞步》(Courant)的主編,是美國大學生圈子裡鼓吹前往海外傳教的著名「三劍客」。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